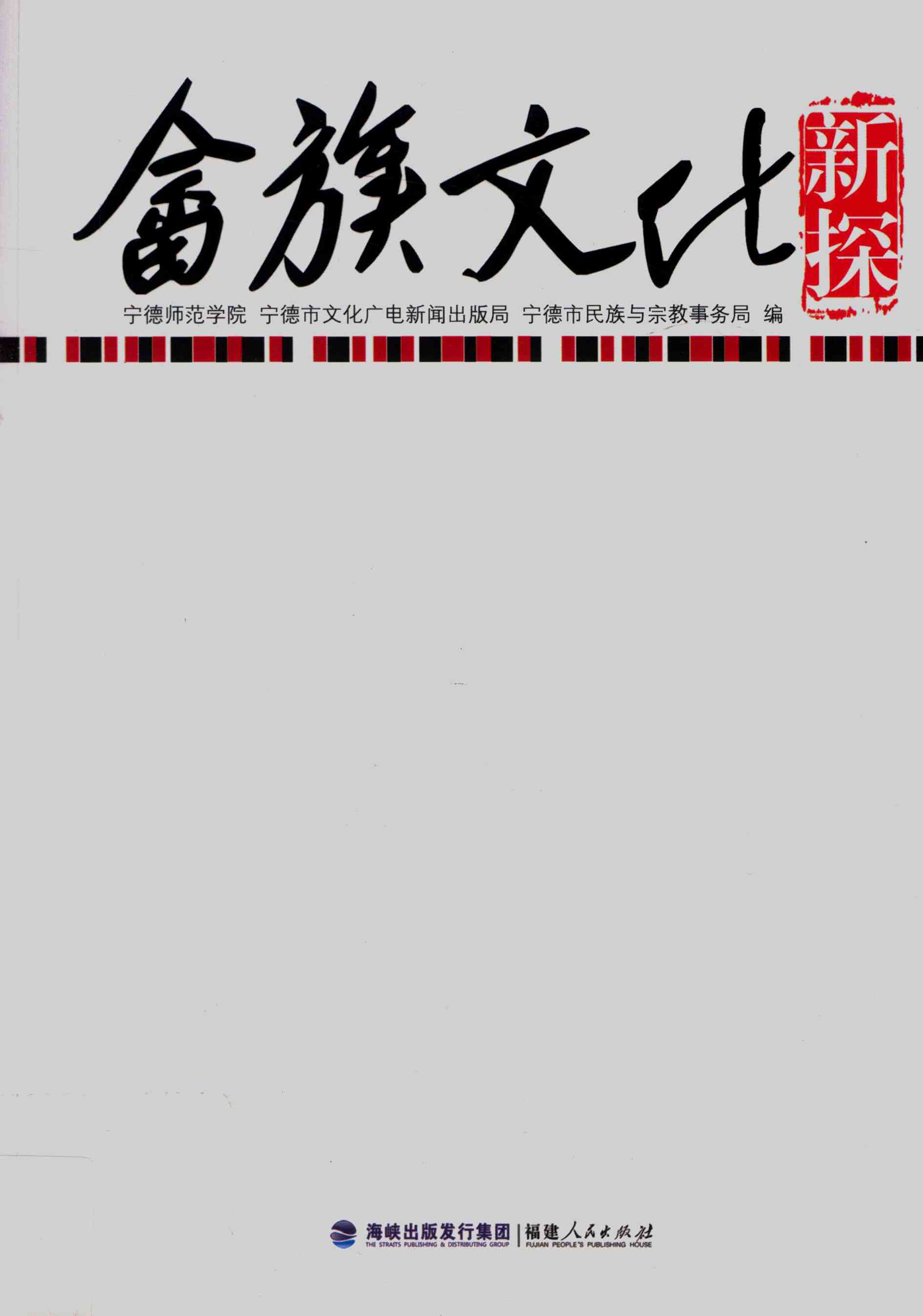内容
“滨海畲族”的形成,或者说相对弱势、落后的畲族人口竟然在相对强势、先进的汉族地区,在汉族本身人地关系已显紧张的福建沿海地区大规模集结,与其强调它的必然性,不如说这需要一种很特殊的历史机缘。这个特殊历史机缘,笔者以为主要是明嘉靖后半叶二十余年“倭寇”连续大肆侵掠和清顺治、康熙之交二三十年间从禁海迁界到复界招徕的巨大反复。
关于晚明倭患与畲民入迁闽东北滨海丘陵的关系,由于史料欠缺,此前学界不见涉及。本文也无力深究,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考察,希望能够引起注意。
检读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刊本《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货属》,发现在“菁靛”目下引有一条“旧志”的按语:
本县山场,无论城郭乡村,除附近庐舍坟墓者始为民业,高山深谷俱官山也。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俱告于官,官则随山按户,置簿收租。自辛酉(公元1561年)倭变之后,官簿无存,土豪年估其租。今考本县州籍,民山并无分抄,悉属官山,尚存官山三顷二十亩九分之税匀派于通县,而利独归于数家。种菁之户,若仿故事,召各乡菁牙、菁客,随其众寡;置簿收租,归之公家,未为不可。然
在当时,则属豪强私占。而此日,承平已久,彼此授受买山者多矣。检核旧志,至“利独归于数家”之前,文字大抵照抄万历十七年(1589年)旧志;之后,掺入新志编纂者的意思;末句则为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地权状况。闽东北的菁客中,有不少畲民。他们在官山垦植,必须向官府办理登记手续,按章交纳租税。根据这则记事,嘉靖四十年辛酉年(1561年)“倭寇”攻陷宁德县城,税收档案被毁无存,改由地方豪强粗估租额。并且渐渐地,地权关系也发生变化,彼此买卖山林的行为屡有发生。那么,一些靠种菁积攒了一些钱财的畲民便可以在滨海山林卜地居家,乃至衍为村落。
福安也曾在此前两年的农历四月被攻破县城,倭寇进城烧杀抢掠整整四天,时人称“嘉靖己未福安井邑一烬于倭”①。半年后,新授知县卢仲佃赴任,见到的仍是“荆棘满城,灰烬遍市,二百载烟火辏集之区,一旦荒墟”②的景况。而福安正是后来闽东北畲民人口最多的县份。
缪品枚统计闽东北现存蓝、雷、钟三姓族谱,有明一代入迁者有30支之多(不含宁德设区市属各县间的互迁),其中洪武1,永乐2,景泰1,天顺4,成化1,嘉靖1,隆庆1,万历7,天启2,崇祯9,具体时间不详。③那么,大倭患后迁入闽东的畲民(20支)占到明代各朝总数(29支)的69%。缪文以为明代畲族大量迁入的历史契机在于当时纺织业发展对于蓝靛染料的需求,此说不为无见。只是在总体上明代福建人口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大量菁客要从临时搭寮租山赁种,改换为纷纷“卜筑”兴村,没有一个大的人地关系变动,恐怕不能成气候。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来,倭寇频频侵扰闽东北滨海地区,本土原居民死伤逃离严重,加上前述官府地簿税册的破坏,与畲民买山定居之间应当是有内在联系的。至于这个问题所涉历史关节,尚有若干未明之处,容另文再考。
畲民入迁闽东北的更大的历史机缘,在于清初的迁界、复界政策。为了隔绝祖国大陆与台湾拥明政权的联系而实行的禁海和迁界,使人口繁盛的东南沿海三十里内外成为不见人烟的废墟,但客观上为畲族预备了一个广阔的去处,朝廷复界以后,畲民便和许多汉人一样络绎迁入。关于清初闽东的迁界、复界和畲族居住格局变化的基本情况,前引缪品枚文已经做过比较具体的描述,这里不必多说。
本文仅补充说明两点。
其一,复界后,福建畲族比较集中地迁居今日宁德市境内(包括邻境的罗源和连江),当与闽东北滨海区域的地表形态有密切关系。闽东北的地表形态与整个福建的情况,同中有异。例如,多山,溪河多独流入海,山岭纵横河道交错的结果,是把大地分划成许多“格子状”的小单位,“格子”与“格子”之间能够相互联系,但不便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整个福建大体如此,而闽东北的地形要更“细碎”些,除了古田溪与闽江可以相通,这里的河流都自成格局,交溪为福建第五大河,霍童溪为福建第七大河,全区24条较大河流的流域总面积可以占到全部土地面积的将近89%。而且陡峭的丘陵直接延伸到海中,形成全国曲折度最大的一长段海岸线。这与闽东南较多滨海小平原是很不相同的。闽东南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人口繁衍快,人地关系更紧张,汉族势力也更大。畲族在这里更难插足和立足,插上足的,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速度也更快。而闽东北滨海地带亦山亦海、山在海中的特点,可以使初迁的山地畲民更快适应环境,在海滨丘陵从事传统的生产活动。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我国东南地区这次族群居住格局大变动发生在清代,而在某种程度上,清代正是传统时代畲族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总结期,也是畲族文化的定型期,一族群在与他族群的接触和交流中澄明自身是文化史上常见的事。我很赞同蓝炯熹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所能讨论的畲族传统文化,只能是经过有清一代的发展而定型的畲族文化。当然,清代以前已经有畲民,已经有畲民文化,尤其是南宋以来关于畲民开始有越来越频繁的文献记载,可是这些记载大都很简单,印象式的勾勒多,实证性的记录少,有的陈陈相因,不能提供新的信息,我们对宋、元、明畲族文化的把握,除了个别特征(如畲军等),其余的与苗、瑶、疍、客的分别还不够清晰,这个族群的个性文化面目还比较模糊。这也使学界对畲族形成时间、源流衍化、迁徙路线、文化核心特质等的判断容易产生分歧,有些问题至今不能达成共识。若先以文献、实物、口述材料较丰富、现实生活中遗留的痕迹也较明显的清代畲族文化样态为基点,再作前溯或后察,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我们把目光收拢在清代闽东北滨海地带这个正处畲族文化重要定型期的族群集中聚居区,不难发现这里这时的畲族在经济生活、文化面相、公共治理、族群认同等方面都在渐渐发生一些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加速采借与他们混居、邻居的汉族社会的先进经验,从而不无受阻但终归是要缓慢地适应和融入与相对强势的汉族和平共处之中(族群间的交往,即使是明显有着先进、欠先进之分的族群间交往,其文化影响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当然也不会是均衡施受的,这是我们在沿用“汉化”一类词语时应当心存儆醒的)。
关于晚明倭患与畲民入迁闽东北滨海丘陵的关系,由于史料欠缺,此前学界不见涉及。本文也无力深究,只是提出一个初步的考察,希望能够引起注意。
检读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刊本《宁德县志》卷一《舆地志·物产·货属》,发现在“菁靛”目下引有一条“旧志”的按语:
本县山场,无论城郭乡村,除附近庐舍坟墓者始为民业,高山深谷俱官山也。嘉靖初年,外郡人来县境栽菁,俱告于官,官则随山按户,置簿收租。自辛酉(公元1561年)倭变之后,官簿无存,土豪年估其租。今考本县州籍,民山并无分抄,悉属官山,尚存官山三顷二十亩九分之税匀派于通县,而利独归于数家。种菁之户,若仿故事,召各乡菁牙、菁客,随其众寡;置簿收租,归之公家,未为不可。然
在当时,则属豪强私占。而此日,承平已久,彼此授受买山者多矣。检核旧志,至“利独归于数家”之前,文字大抵照抄万历十七年(1589年)旧志;之后,掺入新志编纂者的意思;末句则为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地权状况。闽东北的菁客中,有不少畲民。他们在官山垦植,必须向官府办理登记手续,按章交纳租税。根据这则记事,嘉靖四十年辛酉年(1561年)“倭寇”攻陷宁德县城,税收档案被毁无存,改由地方豪强粗估租额。并且渐渐地,地权关系也发生变化,彼此买卖山林的行为屡有发生。那么,一些靠种菁积攒了一些钱财的畲民便可以在滨海山林卜地居家,乃至衍为村落。
福安也曾在此前两年的农历四月被攻破县城,倭寇进城烧杀抢掠整整四天,时人称“嘉靖己未福安井邑一烬于倭”①。半年后,新授知县卢仲佃赴任,见到的仍是“荆棘满城,灰烬遍市,二百载烟火辏集之区,一旦荒墟”②的景况。而福安正是后来闽东北畲民人口最多的县份。
缪品枚统计闽东北现存蓝、雷、钟三姓族谱,有明一代入迁者有30支之多(不含宁德设区市属各县间的互迁),其中洪武1,永乐2,景泰1,天顺4,成化1,嘉靖1,隆庆1,万历7,天启2,崇祯9,具体时间不详。③那么,大倭患后迁入闽东的畲民(20支)占到明代各朝总数(29支)的69%。缪文以为明代畲族大量迁入的历史契机在于当时纺织业发展对于蓝靛染料的需求,此说不为无见。只是在总体上明代福建人口压力已经很大的情况下,大量菁客要从临时搭寮租山赁种,改换为纷纷“卜筑”兴村,没有一个大的人地关系变动,恐怕不能成气候。嘉靖十七年(1538年)以来,倭寇频频侵扰闽东北滨海地区,本土原居民死伤逃离严重,加上前述官府地簿税册的破坏,与畲民买山定居之间应当是有内在联系的。至于这个问题所涉历史关节,尚有若干未明之处,容另文再考。
畲民入迁闽东北的更大的历史机缘,在于清初的迁界、复界政策。为了隔绝祖国大陆与台湾拥明政权的联系而实行的禁海和迁界,使人口繁盛的东南沿海三十里内外成为不见人烟的废墟,但客观上为畲族预备了一个广阔的去处,朝廷复界以后,畲民便和许多汉人一样络绎迁入。关于清初闽东的迁界、复界和畲族居住格局变化的基本情况,前引缪品枚文已经做过比较具体的描述,这里不必多说。
本文仅补充说明两点。
其一,复界后,福建畲族比较集中地迁居今日宁德市境内(包括邻境的罗源和连江),当与闽东北滨海区域的地表形态有密切关系。闽东北的地表形态与整个福建的情况,同中有异。例如,多山,溪河多独流入海,山岭纵横河道交错的结果,是把大地分划成许多“格子状”的小单位,“格子”与“格子”之间能够相互联系,但不便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整个福建大体如此,而闽东北的地形要更“细碎”些,除了古田溪与闽江可以相通,这里的河流都自成格局,交溪为福建第五大河,霍童溪为福建第七大河,全区24条较大河流的流域总面积可以占到全部土地面积的将近89%。而且陡峭的丘陵直接延伸到海中,形成全国曲折度最大的一长段海岸线。这与闽东南较多滨海小平原是很不相同的。闽东南的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人口繁衍快,人地关系更紧张,汉族势力也更大。畲族在这里更难插足和立足,插上足的,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速度也更快。而闽东北滨海地带亦山亦海、山在海中的特点,可以使初迁的山地畲民更快适应环境,在海滨丘陵从事传统的生产活动。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是,我国东南地区这次族群居住格局大变动发生在清代,而在某种程度上,清代正是传统时代畲族接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总结期,也是畲族文化的定型期,一族群在与他族群的接触和交流中澄明自身是文化史上常见的事。我很赞同蓝炯熹的一个看法: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所能讨论的畲族传统文化,只能是经过有清一代的发展而定型的畲族文化。当然,清代以前已经有畲民,已经有畲民文化,尤其是南宋以来关于畲民开始有越来越频繁的文献记载,可是这些记载大都很简单,印象式的勾勒多,实证性的记录少,有的陈陈相因,不能提供新的信息,我们对宋、元、明畲族文化的把握,除了个别特征(如畲军等),其余的与苗、瑶、疍、客的分别还不够清晰,这个族群的个性文化面目还比较模糊。这也使学界对畲族形成时间、源流衍化、迁徙路线、文化核心特质等的判断容易产生分歧,有些问题至今不能达成共识。若先以文献、实物、口述材料较丰富、现实生活中遗留的痕迹也较明显的清代畲族文化样态为基点,再作前溯或后察,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我们把目光收拢在清代闽东北滨海地带这个正处畲族文化重要定型期的族群集中聚居区,不难发现这里这时的畲族在经济生活、文化面相、公共治理、族群认同等方面都在渐渐发生一些意义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基本趋势,是加速采借与他们混居、邻居的汉族社会的先进经验,从而不无受阻但终归是要缓慢地适应和融入与相对强势的汉族和平共处之中(族群间的交往,即使是明显有着先进、欠先进之分的族群间交往,其文化影响也不可能是单方面的,当然也不会是均衡施受的,这是我们在沿用“汉化”一类词语时应当心存儆醒的)。
相关人物
林校生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