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近现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以浙南为例
| 内容出处: | 《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及传承》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30001787 |
| 颗粒名称: | 第二章 近现代畲族服饰文化变迁——以浙南为例 |
| 分类号: | TS941.742.883 |
| 页数: | 17 |
| 页码: | 12-28 |
| 摘要: | 本章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为依据,以浙江西南部丽水地区畲族服饰为研究对象,取其近现代演变表征为经、畲族文化生活背景和历史事件为纬,梳理近现代丽水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历程将其整个历程大致分为清末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分析不同时期畲族服饰在色彩、款式、装饰等方面所体现岀的不同特色以及畲族文化生活背景対服饰发展变化的影响。 |
| 关键词: | 畲族服饰 文化变迁 近现代 |
内容
本章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为依据,以浙江西南部丽水地区畲族服饰为研究对象,取其近现代演变表征为经、畲族文化生活背景和历史事件为纬,梳理近现代丽水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历程将其整个历程大致分为清末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以来四个时期,分析不同时期畲族服饰在色彩、款式、装饰等方面所体现岀的不同特色以及畲族文化生活背景対服饰发展变化的影响。
2.1 清末时期(1840~1910)
由上章可知,19世纪中下叶丽水地区,畲族除已婚妇女头饰略具装饰意味之外,服饰风貌普遍显得粗拙简陋。男子服饰仅一件对襟长袍;女子下着及膝短裙,不穿裤子或袜子,仅赤脚。
魏兰先生(1866-1928,笔名浮云)在《畲客风俗》一书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和县畲族服饰有详尽的描述:
她们皆服青色,阔领小袖,与僧尼相似.衣不用纽扣.仅系以带子袖宽五六寸,衣长二尺八寸许。一般都围以青裙,后来也有改裙为裤的腰缚以花带,带宽二三寸,以赭色土丝织成脚穿黑色布鞋,鞋头缀红花,并有短须数茎,这种鞋仅在走亲访友做客时穿用,平时劳动穿草鞋,在家跻木屐,即木拖鞋。木屐制作简便,只选一块有一定厚度的木片,锯成如脚大小的长方形式样,钉上带子,即可穿用,在山区颇为盛行[23]。
魏兰先生所说的绣花鞋与图2-1所示的浙江博物馆藏绣花鞋恰好互为映证。从鞋的长度可证实当时的畲族妇女不缠足。
由于顺治年间“十从十不从”的易服律令,清代僧尼服沿用明朝旧制,领襟形式一般釆用交领[24],而清代服饰常用的旗袍式圆领一般从领口起沿衣襟设有一字纽一即以纽襟系扣,所以魏兰先所述“不用纽扣,仅系以带子”的畲女服应为汉式交领衣而非旗式大襟衣,长约90厘米,衣下摆约过膝。如图2-2所示景宁博物馆藏一件清代畲族新娘装与之相吻合。
由于畲民在丽水地区分布较为零散,清末各处服饰特征极有可能存在差异,魏兰先生所述仅能代表清末时存在于云和地区的一种畲族服饰风貌,不能概而论之为整个丽水地区畲族统一的着装形式。
例如,景宁畲族博物馆藏有一件搜集于景宁县外舍的畲族清代女上装。如图2-3所示,此女服为圆领右衽大襟布制上衣,衣襟处装饰简洁的柳条花边,具有典型的景宁特色。
如图2-4所示,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清代畲族钟氏祖图,从中可见三代祖先所着衣裳冠履均为典型的明代服饰。图下端有一男一女两人小像,分别位于左右两侧,女着霞帔,男着官帽马褂.均为典型清代服饰服饰。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国初,人民相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故生必时服,死虽古服不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亦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犹袭明服盖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事实上,清代时孩子小时穿前明的服式,也是常见的,老人死后,以明代服饰入殓,在一些地区也成为习惯[24]。
综上所述,清末丽水畲族服饰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服装色彩:青色为主,点缀赭色、红色。
(2)服装款式:男子着对襟长袍;女子下着及膝短裙女上装为汉式阔领小袖交领长衣与旗式右衽大襟衣两种款式并存,20世纪初开始出现改裙为裤的情况。
(3)头饰:女子盘发髻,戴竹冠,裹斑蓝花布,点缀彩色石珠(图2-5)
(4)足饰:赤足为主,偶穿红花黑布鞋,草鞋,木屐。
(5)变化变迁:时值清代部分畲民仍保持着明代汉式服饰风貌,与汉族服饰演变轨迹一致。
2.2 民国时期(1911~1949)
沈作乾在《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年)一文中写到丽水畲民服饰:“男子布衣短褐,色尚兰,质极粗厚,仅夏季穿苎而已。妇女以径寸余,长约二寸之竹筒,斜戴作菱形,裹以红布,复于头顶之前,下围以发笈岀脑后之右,约三寸,端缀红色丝条,垂于耳际……衣长过膝,色或兰或青.缘则以白色或月白色为之,间亦用红色,仅未嫁或新出阁之少妇尚之。腰围兰布带,亦有丝质者。裤甚大,无裙。富者着绣履,兰布袜。贫者或草履,或竟跣足。其他耳环、指环,皆以铜质为之.受值不过铜元几枚而已。”[25]可见到民国初年,丽水畲族青年女服有白底红花的边缘装饰,裤装已成为部分地区普遍的下装款式在其他方面,畲服基本延续了清末时的外观。勇士衡先生于1934年在浙江丽水地区所拍摄的珍贵照片呈现了当时畲族服饰的原始风貌(图2-6~图2-8,原图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9年夏天,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中国学者李化民走访浙江景宁敕木山地区,撰写了民族学上研究民国畲族服饰文化的重要著作《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简称《调查记》)。根据其记载,畲族男人穿着普通的短上衣和裤子,常穿草鞋,戴竹蔑编的斗笠,下雨时穿蓑衣,富裕的男人在过节时穿长衫。妇女们普遍穿着老式剪裁的无领上衣,领圈和袖口上镶阔边,穿宽大的过膝裙,裙子上面围一条蓝色麻布小围裙。围裙带子是用丝线和棉纱线手工制作的宽仅三厘米的彩带。妇女不裹脚,通常赤脚走路,只有在节日才穿鞋。畲族妇女头饰最明显的特色是头笄(图2-9)。男子老人梳辫子,青年人都把头发剪短,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26]
除了服饰风貌以外,《调查记》也呈现了当时畲族服饰设计制作的状况和文化背景:
首先,畲族的服饰花工艺制作、原料取材、款式设计等各方面体现出与汉族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汉族的技术和资源。如“畲族男人的衣服同周围的汉族农民完全一样”,只有富裕人家的男人在过节时才穿长衫,并且“不是由畲族妇女自己做的,而是请汉族裁缝到家里来做”;“很少见到棉布,若要使用,得向汉族商人购买”;“妇女只有在节日才穿上鞋子,这种鞋子不是她们自己做的,而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这种鞋子的式样和汉人穿的相同”;“敕木山村的畲民自己不做这种复杂的头饰,他们请景宁县城里一个银匠做”等。
其次,畲族服饰的发展进程在各方面均落后于当时的汉族,且在发展方向上表现出对汉族服饰文化的追随。这一点在男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代表着畲族服饰最高级别的礼服是汉族当时的日常服长衫:“男人的发型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中青年以及外出工作的人们,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
再次,畲民在很大程度上恪守着自身的民族服饰传统特色,尤其是畲族妇女服饰。《调査记》中多次提到“合乎传统风格”:“到处都一样,这里的妇女是保守的,她们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形式,这和汉族妇女就不一样了。妇女们相当普遍地穿着老式剪裁的上衣……”;围裙彩带上的图案是由“合乎传统风格的花样组成”;“妇女裹脚的习惯从来没有传入畲民中间”;畲族的鞋与汉族不同的是“鞋口和后根接缝处都加上了红布镶边,鞋头前面有用红线做的流苏,鞋面绣着合乎传统风格的红花”;“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有丝毫改变”。
最后,当时的政府试图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影响畲族服饰文化。《调查记》中提到民国政府禁止畲族妇女佩戴传统头饰。在景宁县,警察甚至把进城的畲族妇女的头饰扯下来,丢在地上,把它踩碎。史图博、李化民认为汉人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很强,而畲民也接受了大部分汉人的文明与文化。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被评价为一方面因减轻民族奴役和压迫而“值得称赞”,另一方面却因为某些“急于求成的官员”把“改革”定位在服装和风俗习惯上,损害了畲族的民族文化遗产。
20世纪30年代后期,民国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提岀“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但因过于脱离现实无疾而终。1937年到1938年间曾任云和县县长的沈松林先生,在《一件错事》一文中检讨了自己当年愚蠢做法,并对畲族妇女表示了歉意:“……我很惭愧,曾经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强求畲族女同胞改变发式与服装——不许她们戴头饰和穿民族服装。于是她们上街时,只好取下头上的头冠、石珠等装饰品,大体上与汉人相同。可是一出城仍旧穿戴上民族服饰,恢复原来的样子。我这种‘同化的偏见’使她们增加麻烦,回忆起来,深感惭愧和内疚,应该向畲族女同胞道歉。”[27]
浙江图书馆收藏的1947年2月7日《正报》“浙江风光”专栏中,刊登了柳意城先生《畲民生活在景宁》(1947.1.27)一文,文中记述畲民穿的是自织的麻布,女子服饰与汉人迥异。衣裳宽襟大袖,阔边绣花,长及膝盖;裤子亦绣花边,鞋子也花绿满目。“更奇特的是头部的装饰,以断竹为冠,珠绦(五色椒珠)累累,看样子很像篆文的‘并’字,这种装饰,相传为其始祖母高辛氏公主之饰云。……即在当今时代,彼等仍如原始习俗。”[28]
据《丽水文史资料》记载,作为畲族妇女最完整装束的新娘服饰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上身穿青色布衣,胸前右衣襟及领圈镶四种颜色,花样不同花边的‘通盘领’花边衣,袖口亦镶有花边;下身亦穿青色裤,裤脚绣有鼠牙式数种颜色结合的花纹。鞋的鞋面全部绣有花纹,前端束有红丝线的鞋须;袜是兰色土布靴形袜。腰束自知(织)的兰色蚕丝锦带,锦带两端有约四十公分的带须,须上有新娘本人亲自编织的精致花纹、两端带须还钉有古铜钱各八个,在走动时可听到铜钱的撞击声。戴的银器饰品有银项圈、银链、银手镯和银戒指。头部戴的是相传始祖高辛皇三公主所带凤凰冠,畲语称为‘gie’(髻)。髻的构造:丽水①是用一个小竹筒,外包本族妇女自织的特种红色丝帕;竹筒前端镶一块圆的、有花纹的特制银片;在前额顶挂有银牌三块,称‘髻牌’;头顶披有一块约一寸宽的红色绒布,由前额披向脑后;还有三串白色珍珠盘绕在外。景宁畲族妇女的髻结构更复杂,每对髻要十余两白银作原料。”[29]
可见,虽然史图博等学者认为政府“在废止这种服装以及某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方面,取得了比在社会改革上更为明显的成果”,但是通过沈松林和柳意城先生的记述可以看出,从上而下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对于畲族服饰的影响限于暂时性和表面化。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丽水地区畲族服饰特征如下:
(1)服装色彩:尚青或兰.边缘以白或月白装饰,点缀红色。
(2)服装款式:男子短衣,富者着长衫(与汉人无异);女子着无领上衣,衣长过膝,腰围布或丝带,下着阔裤或过膝裙。
(3)头饰:女子戴竹筒,裹红布,缀红丝带;男斗笠。
(4)足饰:富者着绣履、兰布袜;贫者着草履或跣足。
(5)文化变迁:其一,在工艺制作、原料取材、款式设计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落后于汉族,依赖于汉族;其二,在被汉族服饰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仍恪守传统;其三,“同化政策”、“新生活运动”等政治力量会对畲族服饰造成影响,但强硬干预的效果有限。
2.3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49~1979)
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和制度,并釆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T工作。“畲”这一民族名称在1956年正式确定,这使得畲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少数民族得到了承认和重视[29]。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也促进了汉族与畲族人民关系的进一步拉近,两民族间的经济、社会交流大大增多了。
同时,国家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增强少数民族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感除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外,邀请民族代表赴京参观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据被邀请参观1952年国庆典礼的畲族代表蓝培星回忆,“政府给每位观礼代表定做一套呢制服,包括卫生衣、卫生裤、衬衣、短裤。农民代表又额外增加一套制服,内外共四套”[29]。观礼代表的衣锦还乡,无疑也推动了现代服饰在畲族中的发展。
1953~1958年,国家民委、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合作对闽、浙、赣、粤进行大规模调查,著成《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其,中描述浙江省这一时期畲族的服饰为“妇女梳发髻,戴银冠穿花边衣,裹三角令旗式绑腿和穿高鼻绣花鞋。夏天则穿自织的粗麻布衣服。现在穿民族服装的很少,有些老年人还保留着”。[30]吕绍泉在《丽水畲族简介》中提到“妇女喜戴头冠,穿花边大襟衣衫,戴项圈、银手镯、银戒指,腰束织有花纹的丝带。从50年代后期起,年轻妇女已不喜爱这些古老的服饰,与汉族妇女穿着基本相同。而男人解放前已与汉人穿着无异,不过色彩上偏爱兰色。”[29]。
有趣的是,赴京观礼又成为弘扬民族服饰文化的契机:钟玮琪是1957年浙江省少数民族“五一”赴京观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在《毛主席的两次接见》一文中提到,观礼当天的清晨“三时左右,代表都起床了,轻手轻足地走动着又小声地谈论着,男的整整衣服,女的梳梳头发,穿起民族服装,照照镜子……”[29]在这个最隆重的场合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既说明了民族服饰在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作为最高贵的礼服的地位,也说明了当时少数民族服饰和文化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认可和支持。图2-10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蓝盛花(1953年生,景宁人)于1975年1月出席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照片,从中可见许多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大代表。而蓝盛花在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照片中手持毛主席著作,身着畲族民族服装,流露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她对自己民族身份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图2-11)。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畲族服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畲族曾经有“脱草鞋”的婚俗,源于过去畲族人民生活很苦,一年到头都穿草鞋,就是在喜庆期间送彩礼的人,也是穿着草鞋来的。所以,交罢彩礼后,主人家要请他们洗洗脚,换上布鞋,再吃点心。到了60年代,虽然还沿用脱草鞋的俗称,但草鞋早已被皮鞋、球鞋和布鞋所取代。[29]
根据2004年田野调查时当地老人的描述①,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一时期,景宁畲族女子上身着右衽大襟立领青衣,下穿阔脚裤,腰系紫红与黑色相拼的拦腰(即围裙),男子着对襟衫、大脚裤他们的服装与汉族同期服装的款式、裁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仅在拦腰、衣襟贴边等小细节处呈现出畲族自身服装的特色。春夏季一般穿着麻制上衣.衣长较短,衣摆及胯骨;冬天穿着棉制上衣,衣摆略过臀围。丝制衣服贴布边装饰有一定难度,所以一般没有花边,由于成本较高,家里比较殷实的人家才穿着,一般制成知装。畲族人民普遍生活水平不高,一般每人平均只有二件上衣。
景宁文管会馆藏20世纪50年代所制700#麻料畲女服,是2000年9月由大均村征集而来。整件衣服面料以及衬料都由麻布制成,只在滚边处用蓝色平纹棉布。裁制样板及实物照片如图2-12所示,从服装中也可以看出制衣的麻布幅宽在53厘米左右,上衣需布大约3米,整件衣服都由手工制成。
这种衣服从新中国成立后至2000年左右是景宁畲族女最普遍的日常着装,一般畲族人家都保存有类似服饰,如图2-13所示,20世纪80年代某些畲族乡村的老人家还穿这种服装。
据文管会工作人员称,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畲族人民生活比较贫困,服制因此简化。在稍富裕的家庭,人们还是尽量保持服装的民族性,衣饰稍呈秀丽,如图2-14所示,景宁文管会馆藏313#女上衣,衣襟上的贴布花边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景宁服饰装饰手法之一,这也是与其他地区畲服普遍用刺绣作为装饰手法截然不同的一点。
景宁文管会馆藏703#丝制畲族男服,如图2-15所示,同为2000年9月由大均村征集而来,与700#女服制作年代相仿。整件衣服面料以及辅料均为自织生丝布,布幅宽应在71厘米左右,估计此衣用布约2.5米。
根据当时文献记载;“解放后,完整的新娘装束已是少见中年妇女花边衣,只镶花边二至三条,衣领不镶花边,花边大都是浅兰色;老年妇女只镶一条棕黄色花边。中老年妇女头部装束如不戴髻,则把头发往后脑梳成螺旋式的发髻,中间扎红色绒线,外部套青线网罩,上部插数枝颜色不同的银簪(老年不插),这种发髻,称为‘头毛把’。目前五十岁以上的妇女,还有不少保留这种装束。戴的银手镯、银戒指、耳环等饰品,老、中、青妇女之间的式样亦有区别畲族穿的还有独特的‘骑马鞋’(木屐)和单带草鞋。”[29]
从以上资料可见,畲族传统服装在解放后衣长趋短、款式趋简;在发饰等装饰上,虽然穿戴频率减少,但款式基本不变。可见与畲族古代服饰一脉相承演变而来的近代畲服仍然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的轨迹,继续保持与汉族服装“慢半拍”的节奏。但需注意的是畲族传统服饰逐渐淡出畲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仅仅存在于特殊场合,成为一种代表民族身份、抒发民族情感的特别符号。与此同时,畲族人民的日常穿汉族常服逐步并轨,最终基本不再有差别。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畲族传统服饰特征如下:
(1)服装色彩:紫红与黑色拼色围裙,青衣,浅蓝色花边或彩色贴布花边装饰,老年女服镶棕黄色花边,男服色彩偏爱蓝色。
(2) 服装款式:男子对襟衫、大脚裤,与汉人穿着无异;女子春夏着及胯麻上衣,冬季着及臀棉上衣。
(3)头饰:梳发髻,插银簪;中年妇女则把头发梳向脑后梳成螺旋式的发髻,中间扎红色绒线,外部套青线网罩,上部插数枝颜色不同的银簪;老年妇女的发髻上不插簪。
(4) 足饰:木屐和单带草鞋;裹三角令旗式绑腿.穿高鼻绣花鞋;草鞋被皮鞋、球鞋和布鞋听取代。
(5)文化变迁:其一,畲族传统服装在新中国成立后衣长趋短、款式趋简,但在发饰等装饰上,虽然穿戴频率减少,款式基本不变一传统畲服在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的同时,逐渐淡出畲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传统服饰仅部分老人或在特殊场合穿着。其二,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以年轻妇女为代表,畲族人民的日常穿着与汉族常服逐步并轨。其三,政治上的肯定、文化上的尊重在服饰文化汉化上有积极作用。其四,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畲族服饰的发展变化产生推动作用。
2.4 改革开放以来(1980~2012)
据笔者2004年田野调査中记载,只有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才穿着前面所述右衽大襟短衫和拦腰(图2-16),但不戴头饰,因头饰一般传给了儿媳匚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畲服的制作过程通常是自种棉麻,自家织布机织造的面料,向挑货郎购得服饰辅料,请裁缝上门裁剪缝制,最后成衣染色。近三十年景宁畲族几乎没有畲民自家纺纱织布缝制衣服。虽然基本上每户畲民家里都还存有自用的织机,但现在一般都拆卸后束之高阁,只有少量人家将之摆于室内,但仅供游客参观,自己织布作衣的情况十分少见。据大张坑及东弄村里的老人说,三十多年前若家里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妇人不用务农,她们还会在家里纺纱织布。现今的畲服大多是从县城市场购买,从服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到染织制作方式截然不同。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何孝辉同浙江工业大学王真慧博士于2012年7月14日至19日到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进行了畲族文化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调査内容显示:
当今畲族妇女的服饰和头饰都是到市场上去购买,一套服饰和头饰加在一起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敕木山村我们了解到,村里仅有一二十个妇女有民族传统服饰,民族服装和头饰都是她们近几年才从县城买来的,一套服装要四五百元,头饰要看银饰重量和工艺,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都不穿着民族服装,只有到参加节目表演时或是村里来客人需要展现民族特色时,她们才会穿着民族服装、戴头饰,当问她们民族服饰美不美?为什么平常不穿着时,她们回答,民族服饰是漂亮的,但现在穿起来做事活动不方便,同时民族服饰价格普遍都比现在平常穿着的服饰要贵,如果常穿坏了也很可惜:
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服饰以价格优势在畲族日常生活中取代了农村自给自足的手工服饰制品。从表面上看,似乎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文化特征相应弱化一这一点不止在经济发展的纵向比较上显现出来,在横向贫富比较中也有体现。对比民国时期贫富家庭的穿着可见,如图2-6和图2-8,在相对穷苦的人家,即使装饰有刺绣的畲族盛装常年穿着之后残破不堪,他们仍普遍穿着“花边衫”;而在相对富裕的人家,反而日常服饰多为当时的汉族服饰。究其原因,在婚礼等民俗活动中,畲族人借助民族传统服饰彰显民族身份、传承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服饰并不需要突出其民族意义,而以实用性为主要功能。未必是穷人更恪守传统文化,而是亩于买不起其他服饰,故终身穿着结婚时置办的畲族盛装。时值当代,工业化大生产使大量廉价服饰涌入市场,迅速替代传统服饰成为了畲民以舒适、方便、价廉为首要求的日常服但是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一定带来民族文化的退后。何孝辉的调查也提及,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敕木山村出现妇女歌舞队,畲族中年妇女主动学习和传承畲族传统文化,购买民族传统服饰穿着等,这又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畲族传统文化变迁与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物质保障相比没有选择的不得已而为之,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对民族服饰的主动青睐更能反映畲民内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
对民族文化产生实质性冲击的是全球化浪潮之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一据《调查》所述,现在人们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社会生活习俗都在发生变化,村里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高、村里交通条件改善和现代传媒信息传播的影响等,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渐渐改变,年轻人不愿意学或是没有时间来学习传统文化,人们更愿意选择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以畲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服饰品彩带为例。畲家彩带不仅有围系畲家“拦腰”(围裙)的服用功能,也是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信物,更凝聚着“三公主”的动人传说,在畲族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如今在景宁,传统彩带编织工艺面临着传承危机,敕木山村和大张坑村基本没有人会编织彩带,东弄村也仅有三四十个人会编织彩带,但她们大多平时都不再编织。东弄村畲族彩带工艺传承人蓝延说,编织一条彩带最少要三四天时间,而现在一个人在外打工.一天工钱就能买上三四条机器编织的彩带。由于手工编织彩带太耗时又不经济,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再编织[31]。
在特定的时期,彩带等服饰品充当着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如今畲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不断缩减的情况下,脱离了原文化生态土壤的畲族服饰,不止其中凝聚的原料、工艺等文化特色在逐渐淘尽,其传达爱情等基于畲族传统民俗的社会功能也逐渐被抽离。
与此同时,其外观形象、审美情趣、装饰手法和民间传说等视觉图像和心理表征离析下来,演变成用来彰显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而举办的各类活动,以畲族文化节、服饰大赛为代表;另一方面是以推动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业民俗表演。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福建、浙江等畲族聚居区陆续举办了一系列畲族服饰大赛,近年在景宁举办的“三月三畲族服饰大赛”、“中华畲族服饰风格设计大赛”、“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都貝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2012年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如福建、广东、江苏、黑龙江、湖北、浙江等近10个省的服饰设计院校师生及专业设计师的1200多组参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对畲族服饰进行了解渎、重构和创新。如图2-17所示,很难说这些作品是融合了当代时尚气息的新畲服。
还是从畲族服饰激发灵感而设计出的当代时装,但这无疑是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信息或元素符号和现代服饰设计与开发相结合、通过现代艺术文化和机器工艺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在追求美、经济实用、穿着方便和现代时尚的统一。
畲服在当代的另一个舞台是由旅游业搭建的。在这里,它被作为商业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一种需要迎合市场的消费品。如图2-18所示,在民俗风情旅游的表演中,新娘不是穿传统蓝色衣裳,而是穿红色缎面旗袍,非常类似汉族新娘的装扮。畲族服饰迎合着游客们心目中的“民族”服饰形象,变得鲜艳多彩,而这个形象并不是来自于畲族传统文化,却往往是大众媒体所塑造出的一种对“民族”形象的通感。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定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符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服饰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空间。但笔者认为应注意遵循畲族服饰原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畲民的审美心理,避免损伤畲族服饰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价值。
纵观畲族服饰170年来的发展变迁,尾随主流服饰变迁轨迹的同时珍视自身文化身份,从强权之下犹守旧制、清贫之下安着华服,到在政治肯定和文化尊重中逐步涵化,最后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展出多元化格局。这一过程反映了畲族人民经济水平、文化程度、政治地位等各方面的提升,也透露岀文化全球化冲击之下保持自身文化根基的隐忧。传承畲族服饰文化的关键不是保留服饰本身,而是珍视畲族人民倾注其上的热爱和智慧。要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不能仅靠行政力量,也不能单凭经济扶持,而需要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平等的交流。
2.1 清末时期(1840~1910)
由上章可知,19世纪中下叶丽水地区,畲族除已婚妇女头饰略具装饰意味之外,服饰风貌普遍显得粗拙简陋。男子服饰仅一件对襟长袍;女子下着及膝短裙,不穿裤子或袜子,仅赤脚。
魏兰先生(1866-1928,笔名浮云)在《畲客风俗》一书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云和县畲族服饰有详尽的描述:
她们皆服青色,阔领小袖,与僧尼相似.衣不用纽扣.仅系以带子袖宽五六寸,衣长二尺八寸许。一般都围以青裙,后来也有改裙为裤的腰缚以花带,带宽二三寸,以赭色土丝织成脚穿黑色布鞋,鞋头缀红花,并有短须数茎,这种鞋仅在走亲访友做客时穿用,平时劳动穿草鞋,在家跻木屐,即木拖鞋。木屐制作简便,只选一块有一定厚度的木片,锯成如脚大小的长方形式样,钉上带子,即可穿用,在山区颇为盛行[23]。
魏兰先生所说的绣花鞋与图2-1所示的浙江博物馆藏绣花鞋恰好互为映证。从鞋的长度可证实当时的畲族妇女不缠足。
由于顺治年间“十从十不从”的易服律令,清代僧尼服沿用明朝旧制,领襟形式一般釆用交领[24],而清代服饰常用的旗袍式圆领一般从领口起沿衣襟设有一字纽一即以纽襟系扣,所以魏兰先所述“不用纽扣,仅系以带子”的畲女服应为汉式交领衣而非旗式大襟衣,长约90厘米,衣下摆约过膝。如图2-2所示景宁博物馆藏一件清代畲族新娘装与之相吻合。
由于畲民在丽水地区分布较为零散,清末各处服饰特征极有可能存在差异,魏兰先生所述仅能代表清末时存在于云和地区的一种畲族服饰风貌,不能概而论之为整个丽水地区畲族统一的着装形式。
例如,景宁畲族博物馆藏有一件搜集于景宁县外舍的畲族清代女上装。如图2-3所示,此女服为圆领右衽大襟布制上衣,衣襟处装饰简洁的柳条花边,具有典型的景宁特色。
如图2-4所示,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清代畲族钟氏祖图,从中可见三代祖先所着衣裳冠履均为典型的明代服饰。图下端有一男一女两人小像,分别位于左右两侧,女着霞帔,男着官帽马褂.均为典型清代服饰服饰。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国初,人民相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妓降优不降之说。故生必时服,死虽古服不禁;成童以上皆时服,而幼孩古服亦无禁;男子从时服,女子犹袭明服盖自顺治以至宣统,皆然也。”事实上,清代时孩子小时穿前明的服式,也是常见的,老人死后,以明代服饰入殓,在一些地区也成为习惯[24]。
综上所述,清末丽水畲族服饰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服装色彩:青色为主,点缀赭色、红色。
(2)服装款式:男子着对襟长袍;女子下着及膝短裙女上装为汉式阔领小袖交领长衣与旗式右衽大襟衣两种款式并存,20世纪初开始出现改裙为裤的情况。
(3)头饰:女子盘发髻,戴竹冠,裹斑蓝花布,点缀彩色石珠(图2-5)
(4)足饰:赤足为主,偶穿红花黑布鞋,草鞋,木屐。
(5)变化变迁:时值清代部分畲民仍保持着明代汉式服饰风貌,与汉族服饰演变轨迹一致。
2.2 民国时期(1911~1949)
沈作乾在《括苍畲民调查记》(1925年)一文中写到丽水畲民服饰:“男子布衣短褐,色尚兰,质极粗厚,仅夏季穿苎而已。妇女以径寸余,长约二寸之竹筒,斜戴作菱形,裹以红布,复于头顶之前,下围以发笈岀脑后之右,约三寸,端缀红色丝条,垂于耳际……衣长过膝,色或兰或青.缘则以白色或月白色为之,间亦用红色,仅未嫁或新出阁之少妇尚之。腰围兰布带,亦有丝质者。裤甚大,无裙。富者着绣履,兰布袜。贫者或草履,或竟跣足。其他耳环、指环,皆以铜质为之.受值不过铜元几枚而已。”[25]可见到民国初年,丽水畲族青年女服有白底红花的边缘装饰,裤装已成为部分地区普遍的下装款式在其他方面,畲服基本延续了清末时的外观。勇士衡先生于1934年在浙江丽水地区所拍摄的珍贵照片呈现了当时畲族服饰的原始风貌(图2-6~图2-8,原图存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29年夏天,德国学者史图博和中国学者李化民走访浙江景宁敕木山地区,撰写了民族学上研究民国畲族服饰文化的重要著作《浙江景宁县敕木山畲民调查记》(简称《调查记》)。根据其记载,畲族男人穿着普通的短上衣和裤子,常穿草鞋,戴竹蔑编的斗笠,下雨时穿蓑衣,富裕的男人在过节时穿长衫。妇女们普遍穿着老式剪裁的无领上衣,领圈和袖口上镶阔边,穿宽大的过膝裙,裙子上面围一条蓝色麻布小围裙。围裙带子是用丝线和棉纱线手工制作的宽仅三厘米的彩带。妇女不裹脚,通常赤脚走路,只有在节日才穿鞋。畲族妇女头饰最明显的特色是头笄(图2-9)。男子老人梳辫子,青年人都把头发剪短,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26]
除了服饰风貌以外,《调查记》也呈现了当时畲族服饰设计制作的状况和文化背景:
首先,畲族的服饰花工艺制作、原料取材、款式设计等各方面体现出与汉族的紧密联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汉族的技术和资源。如“畲族男人的衣服同周围的汉族农民完全一样”,只有富裕人家的男人在过节时才穿长衫,并且“不是由畲族妇女自己做的,而是请汉族裁缝到家里来做”;“很少见到棉布,若要使用,得向汉族商人购买”;“妇女只有在节日才穿上鞋子,这种鞋子不是她们自己做的,而是汉人为她们特制的。这种鞋子的式样和汉人穿的相同”;“敕木山村的畲民自己不做这种复杂的头饰,他们请景宁县城里一个银匠做”等。
其次,畲族服饰的发展进程在各方面均落后于当时的汉族,且在发展方向上表现出对汉族服饰文化的追随。这一点在男装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代表着畲族服饰最高级别的礼服是汉族当时的日常服长衫:“男人的发型逐渐现代化了,老人还梳着辫子,中青年以及外出工作的人们,都把头发剪短了,大多数男人把脑袋前半部剃光,而把后脑勺的头发往后梳”。
再次,畲民在很大程度上恪守着自身的民族服饰传统特色,尤其是畲族妇女服饰。《调査记》中多次提到“合乎传统风格”:“到处都一样,这里的妇女是保守的,她们至今还保持一些最初的服装形式,这和汉族妇女就不一样了。妇女们相当普遍地穿着老式剪裁的上衣……”;围裙彩带上的图案是由“合乎传统风格的花样组成”;“妇女裹脚的习惯从来没有传入畲民中间”;畲族的鞋与汉族不同的是“鞋口和后根接缝处都加上了红布镶边,鞋头前面有用红线做的流苏,鞋面绣着合乎传统风格的红花”;“头饰一定要按照自古流传下来的方式制作,畲民不能容忍有丝毫改变”。
最后,当时的政府试图以一种强硬的方式影响畲族服饰文化。《调查记》中提到民国政府禁止畲族妇女佩戴传统头饰。在景宁县,警察甚至把进城的畲族妇女的头饰扯下来,丢在地上,把它踩碎。史图博、李化民认为汉人同化外来民族的能力很强,而畲民也接受了大部分汉人的文明与文化。民国政府的民族政策被评价为一方面因减轻民族奴役和压迫而“值得称赞”,另一方面却因为某些“急于求成的官员”把“改革”定位在服装和风俗习惯上,损害了畲族的民族文化遗产。
20世纪30年代后期,民国政府提倡新生活运动,提岀“移风易俗、教民明礼知耻”的口号,但因过于脱离现实无疾而终。1937年到1938年间曾任云和县县长的沈松林先生,在《一件错事》一文中检讨了自己当年愚蠢做法,并对畲族妇女表示了歉意:“……我很惭愧,曾经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强求畲族女同胞改变发式与服装——不许她们戴头饰和穿民族服装。于是她们上街时,只好取下头上的头冠、石珠等装饰品,大体上与汉人相同。可是一出城仍旧穿戴上民族服饰,恢复原来的样子。我这种‘同化的偏见’使她们增加麻烦,回忆起来,深感惭愧和内疚,应该向畲族女同胞道歉。”[27]
浙江图书馆收藏的1947年2月7日《正报》“浙江风光”专栏中,刊登了柳意城先生《畲民生活在景宁》(1947.1.27)一文,文中记述畲民穿的是自织的麻布,女子服饰与汉人迥异。衣裳宽襟大袖,阔边绣花,长及膝盖;裤子亦绣花边,鞋子也花绿满目。“更奇特的是头部的装饰,以断竹为冠,珠绦(五色椒珠)累累,看样子很像篆文的‘并’字,这种装饰,相传为其始祖母高辛氏公主之饰云。……即在当今时代,彼等仍如原始习俗。”[28]
据《丽水文史资料》记载,作为畲族妇女最完整装束的新娘服饰在新中国成立前为:“上身穿青色布衣,胸前右衣襟及领圈镶四种颜色,花样不同花边的‘通盘领’花边衣,袖口亦镶有花边;下身亦穿青色裤,裤脚绣有鼠牙式数种颜色结合的花纹。鞋的鞋面全部绣有花纹,前端束有红丝线的鞋须;袜是兰色土布靴形袜。腰束自知(织)的兰色蚕丝锦带,锦带两端有约四十公分的带须,须上有新娘本人亲自编织的精致花纹、两端带须还钉有古铜钱各八个,在走动时可听到铜钱的撞击声。戴的银器饰品有银项圈、银链、银手镯和银戒指。头部戴的是相传始祖高辛皇三公主所带凤凰冠,畲语称为‘gie’(髻)。髻的构造:丽水①是用一个小竹筒,外包本族妇女自织的特种红色丝帕;竹筒前端镶一块圆的、有花纹的特制银片;在前额顶挂有银牌三块,称‘髻牌’;头顶披有一块约一寸宽的红色绒布,由前额披向脑后;还有三串白色珍珠盘绕在外。景宁畲族妇女的髻结构更复杂,每对髻要十余两白银作原料。”[29]
可见,虽然史图博等学者认为政府“在废止这种服装以及某些独特的风俗习惯方面,取得了比在社会改革上更为明显的成果”,但是通过沈松林和柳意城先生的记述可以看出,从上而下简单粗暴的政治手段对于畲族服饰的影响限于暂时性和表面化。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丽水地区畲族服饰特征如下:
(1)服装色彩:尚青或兰.边缘以白或月白装饰,点缀红色。
(2)服装款式:男子短衣,富者着长衫(与汉人无异);女子着无领上衣,衣长过膝,腰围布或丝带,下着阔裤或过膝裙。
(3)头饰:女子戴竹筒,裹红布,缀红丝带;男斗笠。
(4)足饰:富者着绣履、兰布袜;贫者着草履或跣足。
(5)文化变迁:其一,在工艺制作、原料取材、款式设计等各方面的发展上落后于汉族,依赖于汉族;其二,在被汉族服饰文化涵化的过程中仍恪守传统;其三,“同化政策”、“新生活运动”等政治力量会对畲族服饰造成影响,但强硬干预的效果有限。
2.3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49~1979)
新中国成立以后,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政策和制度,并釆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是1953年开始的民族识别T工作。“畲”这一民族名称在1956年正式确定,这使得畲族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的少数民族得到了承认和重视[29]。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民主改革也促进了汉族与畲族人民关系的进一步拉近,两民族间的经济、社会交流大大增多了。
同时,国家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增强少数民族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自豪感除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外,邀请民族代表赴京参观也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据被邀请参观1952年国庆典礼的畲族代表蓝培星回忆,“政府给每位观礼代表定做一套呢制服,包括卫生衣、卫生裤、衬衣、短裤。农民代表又额外增加一套制服,内外共四套”[29]。观礼代表的衣锦还乡,无疑也推动了现代服饰在畲族中的发展。
1953~1958年,国家民委、中科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合作对闽、浙、赣、粤进行大规模调查,著成《畲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其,中描述浙江省这一时期畲族的服饰为“妇女梳发髻,戴银冠穿花边衣,裹三角令旗式绑腿和穿高鼻绣花鞋。夏天则穿自织的粗麻布衣服。现在穿民族服装的很少,有些老年人还保留着”。[30]吕绍泉在《丽水畲族简介》中提到“妇女喜戴头冠,穿花边大襟衣衫,戴项圈、银手镯、银戒指,腰束织有花纹的丝带。从50年代后期起,年轻妇女已不喜爱这些古老的服饰,与汉族妇女穿着基本相同。而男人解放前已与汉人穿着无异,不过色彩上偏爱兰色。”[29]。
有趣的是,赴京观礼又成为弘扬民族服饰文化的契机:钟玮琪是1957年浙江省少数民族“五一”赴京观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在《毛主席的两次接见》一文中提到,观礼当天的清晨“三时左右,代表都起床了,轻手轻足地走动着又小声地谈论着,男的整整衣服,女的梳梳头发,穿起民族服装,照照镜子……”[29]在这个最隆重的场合穿着本民族的服饰,既说明了民族服饰在少数民族人民心目中作为最高贵的礼服的地位,也说明了当时少数民族服饰和文化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认可和支持。图2-10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蓝盛花(1953年生,景宁人)于1975年1月出席全国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照片,从中可见许多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大代表。而蓝盛花在20世纪70年代拍摄的照片中手持毛主席著作,身着畲族民族服装,流露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她对自己民族身份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图2-11)。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对畲族服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畲族曾经有“脱草鞋”的婚俗,源于过去畲族人民生活很苦,一年到头都穿草鞋,就是在喜庆期间送彩礼的人,也是穿着草鞋来的。所以,交罢彩礼后,主人家要请他们洗洗脚,换上布鞋,再吃点心。到了60年代,虽然还沿用脱草鞋的俗称,但草鞋早已被皮鞋、球鞋和布鞋所取代。[29]
根据2004年田野调查时当地老人的描述①,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这一时期,景宁畲族女子上身着右衽大襟立领青衣,下穿阔脚裤,腰系紫红与黑色相拼的拦腰(即围裙),男子着对襟衫、大脚裤他们的服装与汉族同期服装的款式、裁制方法几乎完全一样,仅在拦腰、衣襟贴边等小细节处呈现出畲族自身服装的特色。春夏季一般穿着麻制上衣.衣长较短,衣摆及胯骨;冬天穿着棉制上衣,衣摆略过臀围。丝制衣服贴布边装饰有一定难度,所以一般没有花边,由于成本较高,家里比较殷实的人家才穿着,一般制成知装。畲族人民普遍生活水平不高,一般每人平均只有二件上衣。
景宁文管会馆藏20世纪50年代所制700#麻料畲女服,是2000年9月由大均村征集而来。整件衣服面料以及衬料都由麻布制成,只在滚边处用蓝色平纹棉布。裁制样板及实物照片如图2-12所示,从服装中也可以看出制衣的麻布幅宽在53厘米左右,上衣需布大约3米,整件衣服都由手工制成。
这种衣服从新中国成立后至2000年左右是景宁畲族女最普遍的日常着装,一般畲族人家都保存有类似服饰,如图2-13所示,20世纪80年代某些畲族乡村的老人家还穿这种服装。
据文管会工作人员称,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畲族人民生活比较贫困,服制因此简化。在稍富裕的家庭,人们还是尽量保持服装的民族性,衣饰稍呈秀丽,如图2-14所示,景宁文管会馆藏313#女上衣,衣襟上的贴布花边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景宁服饰装饰手法之一,这也是与其他地区畲服普遍用刺绣作为装饰手法截然不同的一点。
景宁文管会馆藏703#丝制畲族男服,如图2-15所示,同为2000年9月由大均村征集而来,与700#女服制作年代相仿。整件衣服面料以及辅料均为自织生丝布,布幅宽应在71厘米左右,估计此衣用布约2.5米。
根据当时文献记载;“解放后,完整的新娘装束已是少见中年妇女花边衣,只镶花边二至三条,衣领不镶花边,花边大都是浅兰色;老年妇女只镶一条棕黄色花边。中老年妇女头部装束如不戴髻,则把头发往后脑梳成螺旋式的发髻,中间扎红色绒线,外部套青线网罩,上部插数枝颜色不同的银簪(老年不插),这种发髻,称为‘头毛把’。目前五十岁以上的妇女,还有不少保留这种装束。戴的银手镯、银戒指、耳环等饰品,老、中、青妇女之间的式样亦有区别畲族穿的还有独特的‘骑马鞋’(木屐)和单带草鞋。”[29]
从以上资料可见,畲族传统服装在解放后衣长趋短、款式趋简;在发饰等装饰上,虽然穿戴频率减少,但款式基本不变。可见与畲族古代服饰一脉相承演变而来的近代畲服仍然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的轨迹,继续保持与汉族服装“慢半拍”的节奏。但需注意的是畲族传统服饰逐渐淡出畲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仅仅存在于特殊场合,成为一种代表民族身份、抒发民族情感的特别符号。与此同时,畲族人民的日常穿汉族常服逐步并轨,最终基本不再有差别。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畲族传统服饰特征如下:
(1)服装色彩:紫红与黑色拼色围裙,青衣,浅蓝色花边或彩色贴布花边装饰,老年女服镶棕黄色花边,男服色彩偏爱蓝色。
(2) 服装款式:男子对襟衫、大脚裤,与汉人穿着无异;女子春夏着及胯麻上衣,冬季着及臀棉上衣。
(3)头饰:梳发髻,插银簪;中年妇女则把头发梳向脑后梳成螺旋式的发髻,中间扎红色绒线,外部套青线网罩,上部插数枝颜色不同的银簪;老年妇女的发髻上不插簪。
(4) 足饰:木屐和单带草鞋;裹三角令旗式绑腿.穿高鼻绣花鞋;草鞋被皮鞋、球鞋和布鞋听取代。
(5)文化变迁:其一,畲族传统服装在新中国成立后衣长趋短、款式趋简,但在发饰等装饰上,虽然穿戴频率减少,款式基本不变一传统畲服在趋从于主流汉族服饰的同时,逐渐淡出畲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传统服饰仅部分老人或在特殊场合穿着。其二,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以年轻妇女为代表,畲族人民的日常穿着与汉族常服逐步并轨。其三,政治上的肯定、文化上的尊重在服饰文化汉化上有积极作用。其四,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畲族服饰的发展变化产生推动作用。
2.4 改革开放以来(1980~2012)
据笔者2004年田野调査中记载,只有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才穿着前面所述右衽大襟短衫和拦腰(图2-16),但不戴头饰,因头饰一般传给了儿媳匚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畲服的制作过程通常是自种棉麻,自家织布机织造的面料,向挑货郎购得服饰辅料,请裁缝上门裁剪缝制,最后成衣染色。近三十年景宁畲族几乎没有畲民自家纺纱织布缝制衣服。虽然基本上每户畲民家里都还存有自用的织机,但现在一般都拆卸后束之高阁,只有少量人家将之摆于室内,但仅供游客参观,自己织布作衣的情况十分少见。据大张坑及东弄村里的老人说,三十多年前若家里还有劳动能力的老妇人不用务农,她们还会在家里纺纱织布。现今的畲服大多是从县城市场购买,从服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到染织制作方式截然不同。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何孝辉同浙江工业大学王真慧博士于2012年7月14日至19日到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进行了畲族文化调查(以下简称《调查》),调査内容显示:
当今畲族妇女的服饰和头饰都是到市场上去购买,一套服饰和头饰加在一起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敕木山村我们了解到,村里仅有一二十个妇女有民族传统服饰,民族服装和头饰都是她们近几年才从县城买来的,一套服装要四五百元,头饰要看银饰重量和工艺,价格在几百元到上千元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都不穿着民族服装,只有到参加节目表演时或是村里来客人需要展现民族特色时,她们才会穿着民族服装、戴头饰,当问她们民族服饰美不美?为什么平常不穿着时,她们回答,民族服饰是漂亮的,但现在穿起来做事活动不方便,同时民族服饰价格普遍都比现在平常穿着的服饰要贵,如果常穿坏了也很可惜:
经济技术的发展使工业化批量生产的服饰以价格优势在畲族日常生活中取代了农村自给自足的手工服饰制品。从表面上看,似乎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民族文化特征相应弱化一这一点不止在经济发展的纵向比较上显现出来,在横向贫富比较中也有体现。对比民国时期贫富家庭的穿着可见,如图2-6和图2-8,在相对穷苦的人家,即使装饰有刺绣的畲族盛装常年穿着之后残破不堪,他们仍普遍穿着“花边衫”;而在相对富裕的人家,反而日常服饰多为当时的汉族服饰。究其原因,在婚礼等民俗活动中,畲族人借助民族传统服饰彰显民族身份、传承民族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服饰并不需要突出其民族意义,而以实用性为主要功能。未必是穷人更恪守传统文化,而是亩于买不起其他服饰,故终身穿着结婚时置办的畲族盛装。时值当代,工业化大生产使大量廉价服饰涌入市场,迅速替代传统服饰成为了畲民以舒适、方便、价廉为首要求的日常服但是这并不表明经济的发展一定带来民族文化的退后。何孝辉的调查也提及,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在敕木山村出现妇女歌舞队,畲族中年妇女主动学习和传承畲族传统文化,购买民族传统服饰穿着等,这又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为畲族传统文化变迁与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物质保障相比没有选择的不得已而为之,可以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对民族服饰的主动青睐更能反映畲民内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自信。
对民族文化产生实质性冲击的是全球化浪潮之下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变一据《调查》所述,现在人们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社会生活习俗都在发生变化,村里年轻人受教育水平提高、村里交通条件改善和现代传媒信息传播的影响等,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在渐渐改变,年轻人不愿意学或是没有时间来学习传统文化,人们更愿意选择现代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以畲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服饰品彩带为例。畲家彩带不仅有围系畲家“拦腰”(围裙)的服用功能,也是青年男女传情达意的信物,更凝聚着“三公主”的动人传说,在畲族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如今在景宁,传统彩带编织工艺面临着传承危机,敕木山村和大张坑村基本没有人会编织彩带,东弄村也仅有三四十个人会编织彩带,但她们大多平时都不再编织。东弄村畲族彩带工艺传承人蓝延说,编织一条彩带最少要三四天时间,而现在一个人在外打工.一天工钱就能买上三四条机器编织的彩带。由于手工编织彩带太耗时又不经济,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再编织[31]。
在特定的时期,彩带等服饰品充当着畲族人民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在如今畲族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文化空间不断缩减的情况下,脱离了原文化生态土壤的畲族服饰,不止其中凝聚的原料、工艺等文化特色在逐渐淘尽,其传达爱情等基于畲族传统民俗的社会功能也逐渐被抽离。
与此同时,其外观形象、审美情趣、装饰手法和民间传说等视觉图像和心理表征离析下来,演变成用来彰显民族身份的文化符号。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为弘扬民族文化而举办的各类活动,以畲族文化节、服饰大赛为代表;另一方面是以推动经济为主要目的的旅游业民俗表演。
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福建、浙江等畲族聚居区陆续举办了一系列畲族服饰大赛,近年在景宁举办的“三月三畲族服饰大赛”、“中华畲族服饰风格设计大赛”、“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都貝有很大影响力。特别是2012年中国(浙江)畲族服饰设计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如福建、广东、江苏、黑龙江、湖北、浙江等近10个省的服饰设计院校师生及专业设计师的1200多组参赛作品。从不同的视角对畲族服饰进行了解渎、重构和创新。如图2-17所示,很难说这些作品是融合了当代时尚气息的新畲服。
还是从畲族服饰激发灵感而设计出的当代时装,但这无疑是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信息或元素符号和现代服饰设计与开发相结合、通过现代艺术文化和机器工艺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有益尝试,在追求美、经济实用、穿着方便和现代时尚的统一。
畲服在当代的另一个舞台是由旅游业搭建的。在这里,它被作为商业和娱乐产品而重新包装。文化资源被商品化了,它不再只是一种人文涵养,而成为一种需要迎合市场的消费品。如图2-18所示,在民俗风情旅游的表演中,新娘不是穿传统蓝色衣裳,而是穿红色缎面旗袍,非常类似汉族新娘的装扮。畲族服饰迎合着游客们心目中的“民族”服饰形象,变得鲜艳多彩,而这个形象并不是来自于畲族传统文化,却往往是大众媒体所塑造出的一种对“民族”形象的通感。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定意义上的“与时俱进”,符合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民族服饰文化的生存和发展争取了空间。但笔者认为应注意遵循畲族服饰原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畲民的审美心理,避免损伤畲族服饰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内在价值。
纵观畲族服饰170年来的发展变迁,尾随主流服饰变迁轨迹的同时珍视自身文化身份,从强权之下犹守旧制、清贫之下安着华服,到在政治肯定和文化尊重中逐步涵化,最后在文化全球化中发展出多元化格局。这一过程反映了畲族人民经济水平、文化程度、政治地位等各方面的提升,也透露岀文化全球化冲击之下保持自身文化根基的隐忧。传承畲族服饰文化的关键不是保留服饰本身,而是珍视畲族人民倾注其上的热爱和智慧。要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不能仅靠行政力量,也不能单凭经济扶持,而需要发自内心的尊重和平等的交流。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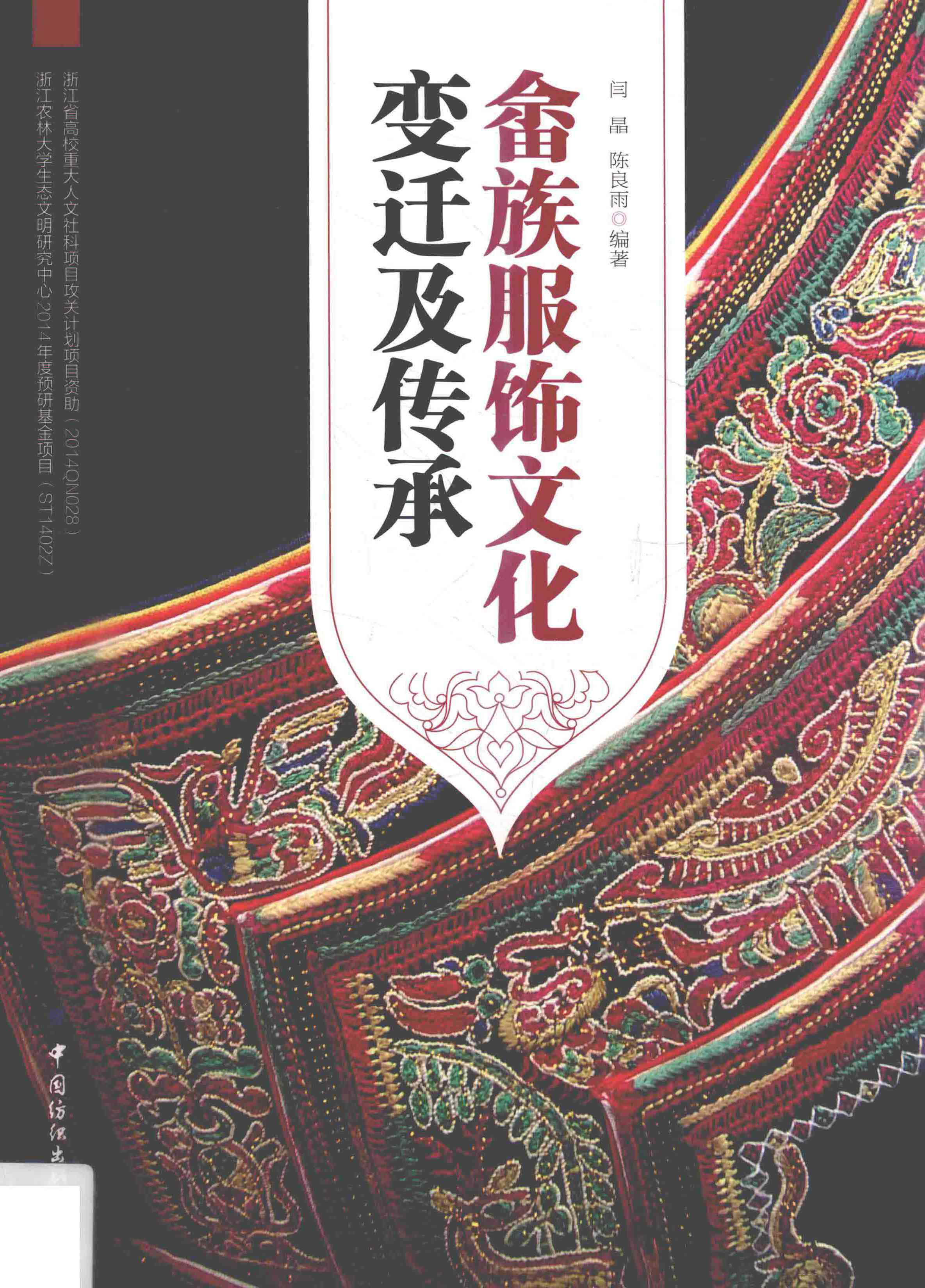
《畲族服饰文化变迁及传承》
出版者:中国纺织出版社
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以畲族服饰发展和演变的历程为经、不同时期畲族的生活文化背景为纬,梳理了从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直至20世纪的畲族服饰文化变迁轨迹。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畲族服饰在色彩、款式、装饰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不同特色以及畲族文化生活背景对服饰发展变化的影响;本书第二部分从空间的维度对浙江、福建等地区的畲族服饰现状进行田野调査并做梳理.釆取田野调查和文献考据相结合以及个别研究、比较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求对近现代畲族服饰、工艺及其文化背景有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认识。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