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安少数民族苗族概况
| 内容出处: | 《福建畲族档案资料选编(1937~1990年)》 图书 |
| 唯一号: | 130920020220000635 |
| 颗粒名称: | 福安少数民族苗族概况 |
| 分类号: | K288.3 |
| 页数: | 5 |
| 页码: | 38-4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福建省福安少数民族苗族概况等发展情况。 |
| 关键词: | 福建省 少数民族 苗族概况 |
内容
甲、发展沿革
苗族依中国目前各少数民族分布状况来看,主系多集中于云贵两广高原,他们由于长期地受到封建帝王反动统治主的压迫和剥削,纷纷被赶到荒凉贫瘠的地区去谋生,当然福安现有苗胞大概也是由这般原故而迁徙来的,但未得到可靠的根据,不过依照苗人家谱的记载,约于明末清初自广东迁移来韩(福安简称)其发展的方向可能由广东分两路向福建转移,一自沿海潮汕而泉惠、兴化、闽侯、连江而抵宁德、福安及霞浦、福鼎更向北入浙南;一自粤东北入闽西向南平、建瓯、浦城一带发展,起初可能占住平原地域,后因历代统治阶级大汉族主义的歧视排挤积极采取武力统治,经济掠夺,文化封锁,怀柔利诱,以夷制夷,挑拨离间等种种毒辣手段,造成了灾难重重,因此相率迁避穷乡山谷地方去,从劳动中求生存,在山头里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生产落后,经济不得自立,社会发展迟滞,生活极端贫困,这种发展情况,在福安现存苗族的家谱及历史传统生活状况中得到充分有力的说明。
福安苗胞主要有雷蓝钟三姓,相传当时迁来的都是雷蓝盘三系,钟姓则是雷姓女婿附庸迁来的,并不是主系,后来盘姓苗胞向北徙入浙江——现平阳泰顺浙南一带,那里的少数民族多盘姓。向东迤逦迁海外,据传也有迁日本去,致福安姓盘的苗胞,即告绝迹,现存的仅雷蓝钟三系。他们自广东迁往连江丹阳汤丘——这时可能也是住没有汉人住居的较平原地带——旋因种族歧视与迫害乃又转移迁避,雷姓最早迁来福安穆阳牛头坂,生六子,曾在该处兴盖祠宇,结果又因所开垦土地,被汉族地主阶级所掠夺,生产资料缺乏,人口激增,生活困难,又不得不向辽阔的地区去寻找开僻新环境,系于生活的需要,一子迁宁德猴党,一子入浙江温州,一子向南迁马山村旋又转移廉岭发族后乃四散分布八区一带山地,一子迁福鼎桐山,又一子迁宁德某地去,留一子住原地。钟姓与雷姓同时迁抵福安,先住韩阳坂(即今县城所属地区),后因大水灾——主要的原因或许又因大汉族的掠夺,可能也是种族压迫,致无去安居就业乃迁移大蓝村(即今之口台村后门山)。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无理迫害,钟姓苗胞历史上曾掀起过辉煌的暴动事迹,相传钟姓兄弟民族因不能忍受汉人的欺压与掠夺,由钟飞领导组织苗人3000众,进行反抗。缘因民族仇恨过深,曾残酷地屠杀过□□,致轰动一时,[畅?]谓有3000食人兵,其实是3000畲人兵之讹传,这次暴动充分证明当时反动的封建帝王对少数民族迫害欺凌的深重,也可以说明少数民族并不是府首贴耳任人宰割的羔羊。这个暴动与反抗,引起了封建反动朝廷的极大恐惧与震动,当时的封建统治主,为了麻痹苗民的反抗情绪乃实施怀柔利诱政策,采以夷制夷的手段,封钟飞为候王,缓和了民族的阶级斗争,进而展开血腥的镇压以加强统治的力量。在福安苗族历史上这次暴动是个光荣,但结果却是个耻辱。钟飞在候王的空头衔下,投降了统治阶级,实际上苗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虽经这次斗争,没得到丝毫的提高,本民族被压迫、掠夺、歧视的封建的锁链仍未摆脱掉。据云钟飞候王生九子,除二子相继迁福州及浙属处州外,一迁本县和庵村,一迁蓝田(现八区岳田乡),一迁金斗洋,其余四子仍住大蓝村。蓝姓传自广东潮州迁罗源末后始迁入福安井口(四区)村,据说蓝姓人迁福安时不只一系,可惜没有详细材料可资证实,故无法稽考。
乙、分布状况
福安苗族主要分布于白云山脉阴阳两面,北起寿宁南达赛歧廉首山区,另一部则按周宁山脉向南伸长发展遍布八六两区山地,直抵白马门与宁德接界,东南方以西圣山脉为主干,依山而住,毗连霞浦。兹按本县少数民族住域分布区乡统计分布情况如下:(一)区长潭乡和庵、桦坪、七埞、大蓝等村,洋蛟乡前洋、东头、龟武、后洋里、铁湖、岩角亭等村,步洋乡官洋岗、对面岭、岔门头、茶洋、海报岭、半山、甲藤坑、茶坑、老鼠朝江等,这个乡约占45%的苗民村数亦不少。金洋乡雷柏洋、坑里两村,许井乡除月斗上溴濑头等村外主要的井口村60多户纯系苗民,廉江乡上下天地、日宅、牛角垅、地坵、廉岭等村其中以廉岭村为全县最富庶的苗民区域,东湖乡仅梨里坑一村(以上七乡现划分为11区)。(三)区前山乡马头山、山领、鲤鱼背、里溪头、龙山峰、岐壁头、羊中坑、里坑等村,后洋乡仙领带、竹林下、山寨□□□□、蓝下蛇岭下等村。蛇岭下村约100多户全部是苗族。湖山乡所辖的南山、桐弯、石璧坑、坑山坂、湖后等5个村,其中的湖后村则苗多汉少,这一乡纯系苗民乡。余外坦洋乡的大岭村,秀龄乡的坑里,上弯洋村,社口乡的大塔仔村,沙洋乡的山头垅,马尾栏村仅是少数的苗民所住而已。(四)区下蓬乡的蓝柄、王楼、林洋湖村,中藻乡的桂垅、东山、新岭、石门里、蓝坪、普照、竹园兜村,留洋乡的许班、□尾、上洋、王莲、半岭、七埞、下南面、牛栏祭,南山村隆坪乡的蓝头、科后、后舍、上澳、大连济地壑、岭尾、葛莆洋、坑里村,黄南乡上高山、下高山、坑头里、上可坑、下可坑、溪塔、寿宁庵,咬头、虎头村,苏堤乡的墓亭村,西铭乡的亭头、外洋、𡎆村,燕桥乡的险坑、上长坑、下长坑、下山岩、长坝埞、半岭、炉里、燕科、铁长、牛三塆、洋面、北山、下坑仔、里降楼,(一部份)村(这个乡的苗族也不少),咸福乡的南山、竹洲、龙池降、屏中山村,凤梧乡(现改金梧乡居八区管)的凤洋、太阳山、半岭、小长潭、金斗洋、地坵、柯𣗬下、白墓、走马垅、老虎塆,周坑、长潭、青甲藏、石门限村,这一乡50%均系苗族。象牛乡的雷打石,卜洋头,龙井村,渡头乡的七层降,樟后,坑壑,确河洋墈,楼里,楼北山,石门头,燕窝,隆坪夫,虎岩,坪牛头村。(五)区象江乡的牛罗里,罗里坑村,赛里乡的鳌峰村的大坝、割藤塆、岭头山、村头下、牛楼村、象洋乡的外牛坑、郑里金鸟塆、龙潭面村。(六)区双留乡的坑门里两爿宫,桥洋塆(一部份)村,苏洋乡的洋上、林厚村,南塘乡的东峰院、阳梅洞、洋溪边、佬蛇岗、八斗头村,倪洋乡的南山(一部份)牛角塆,何亨村,鹤里乡的三坪、野马确、青水确、岭尾(一部份)岔栋、过洋、济篱壑、陈垅等村。(七)区岐山乡的半岭、过洋里、后洋、乌泥坑、浆后,大梨乡的吴楼,双碧乡的坑里垅、南门、鸡角城、槟〓弯、圹桥头、通湾洋、港里,湖塘乡八斗垅、半山楼、焦湾、宫兜村、樟栏乡,双贵山、北斗坑、石厝、南北斗山、上坑角里、下坑角里、塘湾兜、白石堆、本地骨村,藤江乡黄坑、田洋、林湖头村,泽聚乡田雷园、虎岩村,荷洋乡山胶岭、青山鼻、王丹坑、塘楼湾村,北坑乡的所秀栏村(一部份)大洋乡下赤、金瓜带、孔门、王必山、红下口吴山、岩下梨、仙道地村,外屿乡钟山下、大石牛、马头栏,长□(一部分)、里湾、上贵山村。(八)区溪潭乡,仙岩下、橄榄头、仙山村,凤林乡上前埔、匏头坑(一部份杂居)、岩下、占亭村,廉峰乡,□□峰,南山(杂居地)村,城山凤凰□,□□头(杂居)村,洋山乡,大丘头村,番溪乡桦林,岐山村,西岭乡,里湾,牛也坑,九部,赤林峰村,□田乡后山、七埞、蓝田,后门里下岐山村,上洪乡垅口宫(杂居)村,芹洋乡高山、川山腰村,宝西乡,林洋乡,头庄,小岭,何厝,□村,后极,如林,油西坑,北山、外瓜溪,前洋庄,岔门头,牛楼,对面楼等村。(九)区柘荣乡炳鼻峰、宜山、提刀丘,垅头,东门岭,燕岩头,招湾里彭家洋村,棠溪湖西坑,柴山,岭尾村,东岭乡青寺村,洋湖乡下犁坑(杂居地)村,潭夏乡车岭等村庄。(十)区大江乡为质,龙岩,担德岩、王坑村,凤塘乡章家山,吴明山村,炉山乡陈山峰,池头,九来峰,升中村,下邳乡,上天地,下天地,墓亭村,坂中乡狮头,香炉峰马山坑,冬花山,官岭头,西山,员里,邳里村,仙溪乡,上洋头,圭角岩下,马山,后壑,塘坝埞,梨坑,柘边,招坑里,细石峰,仁仓里村,沙塆乡破里,虎竹岩,拓柴峰,宝林洋、半山、长长里村、林洋乡里林洋、里东、圯墙肚、半山、王加厝、过洋、招兜村、白溪乡桐油湾、蛇岗、鲤鱼湾等村。(十二)区斗面乡东山、细叶山(杂居)仙人,山坪村,楼下乡虾蟆头村,松澳乡后洋、茶洋村,金溪乡八斗洋、锰尾、马头山村,港仙乡官厝里,孤楼,靠坑、葛林坪,碧后,猴头,王家山,杯路村,茜洋乡,成井,彩花桥,马头山,白梅岭,麻大坑,亭下,带龙坑,大田坪岭仔下,林家宅村等村,至现编十一区的仙岩乡的和庵,仙岭洋村,这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以上所列的村庄大约百零户以上(如仙岭洋,金斗洋等村)小的约一二户不等,他们的住地多是偏僻山谷去处,靠近汉族居地的,则多系大村落,起码则有二三十家地方,经济的条件也较充裕,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县人口约在二万左右,因散处各方,真实的户数迄难得到确实数字。
丙、经济生活情况
封建制度社会里汉人称呼苗族的男人为“畲客”,女人为“畲姆”,其称谓的来源不可考,通常谓“苗族”即“畲族”,或许以为他们外来的迁入故呼之为“客”,在名义上的确好听,没有什么歧视的口吻,其实呢,存在着十足浓厚的封建口味,这个观点究竟可靠不可靠,尚乏历史事物的稽考。苗族主要生活传统皆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以为荣,从没有人剥削人的非正确概念,但由于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造成了他们生活上的极端困难,历尽艰辛,流尽血汗,辟拓成的平原土地均为大汉族主义巧取豪夺所占有,逼使他们只好退居山区,另辟瘠瘦的梯田以营生。因为他们经济发展受阻碍,虽劳动终日仍免不了过饥寒交迫□□□□□□□□□□□□□□□□□□□□,自耕的中富农地主简直说是凤毛麟角,纵有为数也不及千分之一二,据调查解放前全县苗区以廉岭村为最富,82户中,地主仅3户,多数均是贫雇农,他们有的连地瓜饭也吃不饱,穷的连裤子也没得穿,何况穷乡僻壤的苗胞呢,稻杆当棉被是司空习惯的事,青菜马铃薯当口粮,这是可口的美味。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靠佃耕收入,所耕土地尽是山田,没有一丘田可获200斤以上的,其收入显然有限。苗民也靠副业生产收入为辅,次要经济来源是林业“担柴掮竹”多得不胜数,城镇的燃料,主要靠苗胞供应,个别的自然村亦兼习手工艺,如仙岭洋的泥匠,日宅之竹工人等。口粮纯是地瓜米,一年夹杂吃些白米饭的解放前可以说没有,青菜是自己种的,咸鱼能够吃得上“大头货”——咸黄瓜、白鲤之类很少,绝大多数吃碎鱼屑,臭虾苗之类,有的甚至连食盐也吃不上,地瓜饭臭虾苗,咸蔬菜——庵的咸芥菜、罗茯——均是他们中农以上的养料。鸡、鸭、猪、羊虽是苗族的副产品,但吃得上的百不及一,这足见苗汉两族间在经济生活上不平等的一斑。谈到土地使用权,苗汉的待遇更悬殊,二千年来苗族几乎丧失所有土地的自由使用权,迄土改前除少数大村庄外,许多小村落,一般苗胞盖房子是不准安柱石的,(相传封建统治时苗民如果盖房子安上础石汉人有权把他捣毁折卸),汉人认为安上柱石,即表示土地所有权已转移,这样,汉族地主阶级便不能随时窃占该土地。解放前,好多山区的苗民仍须向地主缴纳山租,这就是强有力的证明之一,概括说,解放前的苗胞真是“立锥无地”啊,其经济生活情况,可想而知了。
丁、政治待遇
在封建传统的压制下,苗胞根本没有政治地位可言,一切参政权利全被剥夺,苗民不准参加起码的“秀才”考试,有些经分化而变质的苗人,在满清时代至多也不过当个皇差或班头已算破天荒,了不起的一回事了,他们中除绝无仅有的偶而考中一位“武秀才”外,文秀才根本没有,这或许也是反动统治的某一朝代重文轻武政策的突出问题而已。在剥削阶级的歧视欺压下,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民族的仇恨心,汉苗不通婚就是具体的事实表现,苗胞嫁娶不准坐轿,否则经过汉族住地即遭凶殴捣毁,苗民入城买卖皆畏缩恐惧,纵受侮辱,亦忍气吞声,不与较重,汉人常常谩骂其为“臭畲客”、“臭畲姆”,嫌脏嫌臭,简直鄙视劳动,认为“天下之最贱,剃头,扛轿,吹鼓手”,最下流的生活致由苗胞去担任。满清时,还规定其家庭成份是吹鼓手、扛轿、剃头或当皇差的其子弟一律不准参加考试,基本的作用无非是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参政权利吧。汉族地主家庭常蓄养苗民妇女为婢女、佣妇,男的当长工,吃的是残羹冷饭,做的是牛马生活,长年受着汉人的虐待凌辱,茹苦含辛,眼泪只好向着肚里流,从来苗胞不敢打官司,因打官司第一要衣钱,第二要靠汉人写状纸,即使口口口口口口是现成,二千年来受尽封建社会的压迫,大汉族的侵凌,苗胞的苦水一辈子也倒不完,只要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革命胜利的今天,才能获得永久的自由与幸福。因此苗胞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确流过不少血和汗,拼死的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全国依然,福安当然不是例外,这也有其客观的因素。
戊、文化教育
苗族没有本族文字,只有语言,一般苗民均能通汉苗两种语言,近来新语汇渐多,现有语言不够表达多渗用汉语,如“人民解放军”、“毛主席”等文字则通用汉字。这可能是苗语逐渐减少的根本原因,因为经济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也剥夺了苗民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所以苗民有句“有读书子,无读书父”的谚语,最多只能于童年七八岁时,由生活较好的家长集资延聘塾师课读,一两年后就要参加劳动生产丧失读书的权利了,故苗民文化水平最高的仅能记帐,但苗民有一特长即“对诗”,苗民自幼学习唱歌,青年男女经常在山坡水涯互相“对唱诗歌”,大部份自编自唱,有的唱歌家出口成诗,即景可歌,男女结婚时常特请唱歌专家当“亲家伯”,这是苗族文化上的特点。最突出的苗胞讨亲扛轿的人,如果不能唱和诗歌,上桌不给红酒吃,故意给与红粬渗开水喝,这或许也是保持其固有文化上传统的作风吧?
己、风俗习惯
(一)婚姻:苗民最怕绝后,男女三四岁即行订婚,年19岁结婚,婚礼不管贫富,订婚时,猪脚1只,龙贴2张,红衣线2只,果子2包(红枣冰糖),送女家后即回送以糯米糍斗余,开生庚一定要二次,第一次开不到但要送开生庚的人200元(二角)笔资,女家白鲤2头;第二次才正式开到要送女家肉2斤,合婚后送日子(订婚)时间一定要在8月,礼物月饼10余斤,肉四五斤,面2斤,女方仅收肉和饼各一半,举行婚礼前一日,男家送女家猪肉40斤,油2斤,鸡雌雄各2头,鱼2头,蛋价42个,礼金72千(清时别钱)。女家赔嫁妆奁一定要三杠头,衣服足够穿3年,女结婚后3年内规定不制新衣,唯如果女方贫穷,而双方感情又融洽,则男人往往于3年内偷着为女制新衣裳。婚后2天,男人即往岳家为婿,随送岳父母猪脚1只,岳叔各送肉4斤,但岳父、岳叔每人定要备酒席一桌敬婿,岳父母却更要送婿“记路钱”2元至4元。头年节(即婚后第一年端阳节)岳家送礼很丰厚,粽4斗米,烧饼要200块,鱼2头□□□□□□□□□□□□□□□□□□“亲家伯”(会唱歌的)三人于结婚前一日由“亲家伯”领赴女方住两宵,专门对歌。第一夜对歌时,全村附近男女均集中女家和“亲家伯”对唱,女家家则准备8斗4盘为点心,人多时要吃到10余桌。第二夜点心要鸡鸭各一斗,外加菜等。第三天回家,女方亦聘请2人送女出嫁,男方来随同返去。在举行婚礼时,全村男女均集中男家吃酒,浪费极大,故男人往往订婚后无法举行婚礼。
(二)丧葬:死了人在苗民也是一种负担,人死后举行迷信佛事,村中集中百余人来死者家中吃、赌通宵彻夜。如犯“重丧”、“忌日”,死人不许收殓,甚至连续好几夜,所浪费更多了。苗民死后因经济生活问题影响,大部仅能“红圹”埋葬无法做墓。
(三)习俗:端阳节户户裹粽,粽以芦叶包裹,每条分五节,表示纪念五月五日,端午节,即生活极端困难户也得设法裹几升米,敬祖宗,旧历年家家均用糯米制糍巴或用以送礼。盖房子集体以人工帮助建筑,丧葬六亲均送粮食为主,上寿送猪脚,送者须共同吃光而后去,这都是他们取之劳动用之劳动的纯朴本质的表现。他们的服饰,男人与汉族农民无异,女人则绝不相同,女人服装规定黑衣黑裙,女子出嫁时,裙及衣裳一定要由母舅赠送,妇女头发梳理形式,出嫁前,出嫁后有区别。出嫁前,头顶平铺,已结婚的要加上“披头髻”,以示区别。嫁女妆奁,除普通钗环外,斗笠、蓑衣、锄头是免不了的物件,斗笠多系精工细制的,价值相当昂贵,男女婚后二三天就过共耕生活,夫唱妇随。“劳动”两字是其优良的传统观点。老年人虽乏劳动力,但也不会闲着白吃饭,带小孩、煮饭、烧茶水、看家、搞副产,工作还很卖力有劲,只要一口气在的话,他都会干他所能干的工作。儿童也同样地学习适合他们体力所胜任的劳动。人民政府提出劳动发家,生产致富的号召,苗胞们是有信心有把握来完成这伟大的任务。
苗胞性朴实,勤劳有毅力,团结互助观念强,阶级的仇恨心深重,意志顽强、坚定富斗争性,能刻苦耐劳,他们长期受着汉人的封建剥削歧视,对本民族间的确团结得像钢铁一样的坚固,例如汉人不能通苗语的,一到乡间查询苗人姓名住址,那就费事,尤其年关索债讨帐的更伤脑筋,从村头找到村尾,问得一身是汗,结果呢?只得到“不知道”三个字的回复。国民党反动派——蒋匪帮——统治下抓丁派饷,收捐勒诈,高租重利的层层掠夺,苗胞委实吃亏不少,如果他们没有团结力量,那里能够适应现实环境而生存呢?少数民族迫于生活,一生病连中药也吃不上,更谈不到科学的治疗(例如请西医注射吃西药等)为着克服困难多吃青草药(土草不花钱),故此青草医师多出自苗胞中。迷信比较深,动不动就请巫师驱鬼捕魔,在这种统治的迷信思想支配下,断送了不少人命。相信在共产党人民政府英明领导教育下,这不正确的习俗是有法改革的。
福安县委统战部
[福安市档案馆福安县统战54永久1]
苗族依中国目前各少数民族分布状况来看,主系多集中于云贵两广高原,他们由于长期地受到封建帝王反动统治主的压迫和剥削,纷纷被赶到荒凉贫瘠的地区去谋生,当然福安现有苗胞大概也是由这般原故而迁徙来的,但未得到可靠的根据,不过依照苗人家谱的记载,约于明末清初自广东迁移来韩(福安简称)其发展的方向可能由广东分两路向福建转移,一自沿海潮汕而泉惠、兴化、闽侯、连江而抵宁德、福安及霞浦、福鼎更向北入浙南;一自粤东北入闽西向南平、建瓯、浦城一带发展,起初可能占住平原地域,后因历代统治阶级大汉族主义的歧视排挤积极采取武力统治,经济掠夺,文化封锁,怀柔利诱,以夷制夷,挑拨离间等种种毒辣手段,造成了灾难重重,因此相率迁避穷乡山谷地方去,从劳动中求生存,在山头里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因而生产落后,经济不得自立,社会发展迟滞,生活极端贫困,这种发展情况,在福安现存苗族的家谱及历史传统生活状况中得到充分有力的说明。
福安苗胞主要有雷蓝钟三姓,相传当时迁来的都是雷蓝盘三系,钟姓则是雷姓女婿附庸迁来的,并不是主系,后来盘姓苗胞向北徙入浙江——现平阳泰顺浙南一带,那里的少数民族多盘姓。向东迤逦迁海外,据传也有迁日本去,致福安姓盘的苗胞,即告绝迹,现存的仅雷蓝钟三系。他们自广东迁往连江丹阳汤丘——这时可能也是住没有汉人住居的较平原地带——旋因种族歧视与迫害乃又转移迁避,雷姓最早迁来福安穆阳牛头坂,生六子,曾在该处兴盖祠宇,结果又因所开垦土地,被汉族地主阶级所掠夺,生产资料缺乏,人口激增,生活困难,又不得不向辽阔的地区去寻找开僻新环境,系于生活的需要,一子迁宁德猴党,一子入浙江温州,一子向南迁马山村旋又转移廉岭发族后乃四散分布八区一带山地,一子迁福鼎桐山,又一子迁宁德某地去,留一子住原地。钟姓与雷姓同时迁抵福安,先住韩阳坂(即今县城所属地区),后因大水灾——主要的原因或许又因大汉族的掠夺,可能也是种族压迫,致无去安居就业乃迁移大蓝村(即今之口台村后门山)。为了反抗统治者的无理迫害,钟姓苗胞历史上曾掀起过辉煌的暴动事迹,相传钟姓兄弟民族因不能忍受汉人的欺压与掠夺,由钟飞领导组织苗人3000众,进行反抗。缘因民族仇恨过深,曾残酷地屠杀过□□,致轰动一时,[畅?]谓有3000食人兵,其实是3000畲人兵之讹传,这次暴动充分证明当时反动的封建帝王对少数民族迫害欺凌的深重,也可以说明少数民族并不是府首贴耳任人宰割的羔羊。这个暴动与反抗,引起了封建反动朝廷的极大恐惧与震动,当时的封建统治主,为了麻痹苗民的反抗情绪乃实施怀柔利诱政策,采以夷制夷的手段,封钟飞为候王,缓和了民族的阶级斗争,进而展开血腥的镇压以加强统治的力量。在福安苗族历史上这次暴动是个光荣,但结果却是个耻辱。钟飞在候王的空头衔下,投降了统治阶级,实际上苗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虽经这次斗争,没得到丝毫的提高,本民族被压迫、掠夺、歧视的封建的锁链仍未摆脱掉。据云钟飞候王生九子,除二子相继迁福州及浙属处州外,一迁本县和庵村,一迁蓝田(现八区岳田乡),一迁金斗洋,其余四子仍住大蓝村。蓝姓传自广东潮州迁罗源末后始迁入福安井口(四区)村,据说蓝姓人迁福安时不只一系,可惜没有详细材料可资证实,故无法稽考。
乙、分布状况
福安苗族主要分布于白云山脉阴阳两面,北起寿宁南达赛歧廉首山区,另一部则按周宁山脉向南伸长发展遍布八六两区山地,直抵白马门与宁德接界,东南方以西圣山脉为主干,依山而住,毗连霞浦。兹按本县少数民族住域分布区乡统计分布情况如下:(一)区长潭乡和庵、桦坪、七埞、大蓝等村,洋蛟乡前洋、东头、龟武、后洋里、铁湖、岩角亭等村,步洋乡官洋岗、对面岭、岔门头、茶洋、海报岭、半山、甲藤坑、茶坑、老鼠朝江等,这个乡约占45%的苗民村数亦不少。金洋乡雷柏洋、坑里两村,许井乡除月斗上溴濑头等村外主要的井口村60多户纯系苗民,廉江乡上下天地、日宅、牛角垅、地坵、廉岭等村其中以廉岭村为全县最富庶的苗民区域,东湖乡仅梨里坑一村(以上七乡现划分为11区)。(三)区前山乡马头山、山领、鲤鱼背、里溪头、龙山峰、岐壁头、羊中坑、里坑等村,后洋乡仙领带、竹林下、山寨□□□□、蓝下蛇岭下等村。蛇岭下村约100多户全部是苗族。湖山乡所辖的南山、桐弯、石璧坑、坑山坂、湖后等5个村,其中的湖后村则苗多汉少,这一乡纯系苗民乡。余外坦洋乡的大岭村,秀龄乡的坑里,上弯洋村,社口乡的大塔仔村,沙洋乡的山头垅,马尾栏村仅是少数的苗民所住而已。(四)区下蓬乡的蓝柄、王楼、林洋湖村,中藻乡的桂垅、东山、新岭、石门里、蓝坪、普照、竹园兜村,留洋乡的许班、□尾、上洋、王莲、半岭、七埞、下南面、牛栏祭,南山村隆坪乡的蓝头、科后、后舍、上澳、大连济地壑、岭尾、葛莆洋、坑里村,黄南乡上高山、下高山、坑头里、上可坑、下可坑、溪塔、寿宁庵,咬头、虎头村,苏堤乡的墓亭村,西铭乡的亭头、外洋、𡎆村,燕桥乡的险坑、上长坑、下长坑、下山岩、长坝埞、半岭、炉里、燕科、铁长、牛三塆、洋面、北山、下坑仔、里降楼,(一部份)村(这个乡的苗族也不少),咸福乡的南山、竹洲、龙池降、屏中山村,凤梧乡(现改金梧乡居八区管)的凤洋、太阳山、半岭、小长潭、金斗洋、地坵、柯𣗬下、白墓、走马垅、老虎塆,周坑、长潭、青甲藏、石门限村,这一乡50%均系苗族。象牛乡的雷打石,卜洋头,龙井村,渡头乡的七层降,樟后,坑壑,确河洋墈,楼里,楼北山,石门头,燕窝,隆坪夫,虎岩,坪牛头村。(五)区象江乡的牛罗里,罗里坑村,赛里乡的鳌峰村的大坝、割藤塆、岭头山、村头下、牛楼村、象洋乡的外牛坑、郑里金鸟塆、龙潭面村。(六)区双留乡的坑门里两爿宫,桥洋塆(一部份)村,苏洋乡的洋上、林厚村,南塘乡的东峰院、阳梅洞、洋溪边、佬蛇岗、八斗头村,倪洋乡的南山(一部份)牛角塆,何亨村,鹤里乡的三坪、野马确、青水确、岭尾(一部份)岔栋、过洋、济篱壑、陈垅等村。(七)区岐山乡的半岭、过洋里、后洋、乌泥坑、浆后,大梨乡的吴楼,双碧乡的坑里垅、南门、鸡角城、槟〓弯、圹桥头、通湾洋、港里,湖塘乡八斗垅、半山楼、焦湾、宫兜村、樟栏乡,双贵山、北斗坑、石厝、南北斗山、上坑角里、下坑角里、塘湾兜、白石堆、本地骨村,藤江乡黄坑、田洋、林湖头村,泽聚乡田雷园、虎岩村,荷洋乡山胶岭、青山鼻、王丹坑、塘楼湾村,北坑乡的所秀栏村(一部份)大洋乡下赤、金瓜带、孔门、王必山、红下口吴山、岩下梨、仙道地村,外屿乡钟山下、大石牛、马头栏,长□(一部分)、里湾、上贵山村。(八)区溪潭乡,仙岩下、橄榄头、仙山村,凤林乡上前埔、匏头坑(一部份杂居)、岩下、占亭村,廉峰乡,□□峰,南山(杂居地)村,城山凤凰□,□□头(杂居)村,洋山乡,大丘头村,番溪乡桦林,岐山村,西岭乡,里湾,牛也坑,九部,赤林峰村,□田乡后山、七埞、蓝田,后门里下岐山村,上洪乡垅口宫(杂居)村,芹洋乡高山、川山腰村,宝西乡,林洋乡,头庄,小岭,何厝,□村,后极,如林,油西坑,北山、外瓜溪,前洋庄,岔门头,牛楼,对面楼等村。(九)区柘荣乡炳鼻峰、宜山、提刀丘,垅头,东门岭,燕岩头,招湾里彭家洋村,棠溪湖西坑,柴山,岭尾村,东岭乡青寺村,洋湖乡下犁坑(杂居地)村,潭夏乡车岭等村庄。(十)区大江乡为质,龙岩,担德岩、王坑村,凤塘乡章家山,吴明山村,炉山乡陈山峰,池头,九来峰,升中村,下邳乡,上天地,下天地,墓亭村,坂中乡狮头,香炉峰马山坑,冬花山,官岭头,西山,员里,邳里村,仙溪乡,上洋头,圭角岩下,马山,后壑,塘坝埞,梨坑,柘边,招坑里,细石峰,仁仓里村,沙塆乡破里,虎竹岩,拓柴峰,宝林洋、半山、长长里村、林洋乡里林洋、里东、圯墙肚、半山、王加厝、过洋、招兜村、白溪乡桐油湾、蛇岗、鲤鱼湾等村。(十二)区斗面乡东山、细叶山(杂居)仙人,山坪村,楼下乡虾蟆头村,松澳乡后洋、茶洋村,金溪乡八斗洋、锰尾、马头山村,港仙乡官厝里,孤楼,靠坑、葛林坪,碧后,猴头,王家山,杯路村,茜洋乡,成井,彩花桥,马头山,白梅岭,麻大坑,亭下,带龙坑,大田坪岭仔下,林家宅村等村,至现编十一区的仙岩乡的和庵,仙岭洋村,这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以上所列的村庄大约百零户以上(如仙岭洋,金斗洋等村)小的约一二户不等,他们的住地多是偏僻山谷去处,靠近汉族居地的,则多系大村落,起码则有二三十家地方,经济的条件也较充裕,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县人口约在二万左右,因散处各方,真实的户数迄难得到确实数字。
丙、经济生活情况
封建制度社会里汉人称呼苗族的男人为“畲客”,女人为“畲姆”,其称谓的来源不可考,通常谓“苗族”即“畲族”,或许以为他们外来的迁入故呼之为“客”,在名义上的确好听,没有什么歧视的口吻,其实呢,存在着十足浓厚的封建口味,这个观点究竟可靠不可靠,尚乏历史事物的稽考。苗族主要生活传统皆靠劳动生产,自食其力以为荣,从没有人剥削人的非正确概念,但由于传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造成了他们生活上的极端困难,历尽艰辛,流尽血汗,辟拓成的平原土地均为大汉族主义巧取豪夺所占有,逼使他们只好退居山区,另辟瘠瘦的梯田以营生。因为他们经济发展受阻碍,虽劳动终日仍免不了过饥寒交迫□□□□□□□□□□□□□□□□□□□□,自耕的中富农地主简直说是凤毛麟角,纵有为数也不及千分之一二,据调查解放前全县苗区以廉岭村为最富,82户中,地主仅3户,多数均是贫雇农,他们有的连地瓜饭也吃不饱,穷的连裤子也没得穿,何况穷乡僻壤的苗胞呢,稻杆当棉被是司空习惯的事,青菜马铃薯当口粮,这是可口的美味。他们生活的主要来源,靠佃耕收入,所耕土地尽是山田,没有一丘田可获200斤以上的,其收入显然有限。苗民也靠副业生产收入为辅,次要经济来源是林业“担柴掮竹”多得不胜数,城镇的燃料,主要靠苗胞供应,个别的自然村亦兼习手工艺,如仙岭洋的泥匠,日宅之竹工人等。口粮纯是地瓜米,一年夹杂吃些白米饭的解放前可以说没有,青菜是自己种的,咸鱼能够吃得上“大头货”——咸黄瓜、白鲤之类很少,绝大多数吃碎鱼屑,臭虾苗之类,有的甚至连食盐也吃不上,地瓜饭臭虾苗,咸蔬菜——庵的咸芥菜、罗茯——均是他们中农以上的养料。鸡、鸭、猪、羊虽是苗族的副产品,但吃得上的百不及一,这足见苗汉两族间在经济生活上不平等的一斑。谈到土地使用权,苗汉的待遇更悬殊,二千年来苗族几乎丧失所有土地的自由使用权,迄土改前除少数大村庄外,许多小村落,一般苗胞盖房子是不准安柱石的,(相传封建统治时苗民如果盖房子安上础石汉人有权把他捣毁折卸),汉人认为安上柱石,即表示土地所有权已转移,这样,汉族地主阶级便不能随时窃占该土地。解放前,好多山区的苗民仍须向地主缴纳山租,这就是强有力的证明之一,概括说,解放前的苗胞真是“立锥无地”啊,其经济生活情况,可想而知了。
丁、政治待遇
在封建传统的压制下,苗胞根本没有政治地位可言,一切参政权利全被剥夺,苗民不准参加起码的“秀才”考试,有些经分化而变质的苗人,在满清时代至多也不过当个皇差或班头已算破天荒,了不起的一回事了,他们中除绝无仅有的偶而考中一位“武秀才”外,文秀才根本没有,这或许也是反动统治的某一朝代重文轻武政策的突出问题而已。在剥削阶级的歧视欺压下,造成了严重的阶级民族的仇恨心,汉苗不通婚就是具体的事实表现,苗胞嫁娶不准坐轿,否则经过汉族住地即遭凶殴捣毁,苗民入城买卖皆畏缩恐惧,纵受侮辱,亦忍气吞声,不与较重,汉人常常谩骂其为“臭畲客”、“臭畲姆”,嫌脏嫌臭,简直鄙视劳动,认为“天下之最贱,剃头,扛轿,吹鼓手”,最下流的生活致由苗胞去担任。满清时,还规定其家庭成份是吹鼓手、扛轿、剃头或当皇差的其子弟一律不准参加考试,基本的作用无非是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参政权利吧。汉族地主家庭常蓄养苗民妇女为婢女、佣妇,男的当长工,吃的是残羹冷饭,做的是牛马生活,长年受着汉人的虐待凌辱,茹苦含辛,眼泪只好向着肚里流,从来苗胞不敢打官司,因打官司第一要衣钱,第二要靠汉人写状纸,即使口口口口口口是现成,二千年来受尽封建社会的压迫,大汉族的侵凌,苗胞的苦水一辈子也倒不完,只要团结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革命胜利的今天,才能获得永久的自由与幸福。因此苗胞在土地革命时期的确流过不少血和汗,拼死的进行民族解放斗争,全国依然,福安当然不是例外,这也有其客观的因素。
戊、文化教育
苗族没有本族文字,只有语言,一般苗民均能通汉苗两种语言,近来新语汇渐多,现有语言不够表达多渗用汉语,如“人民解放军”、“毛主席”等文字则通用汉字。这可能是苗语逐渐减少的根本原因,因为经济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也剥夺了苗民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所以苗民有句“有读书子,无读书父”的谚语,最多只能于童年七八岁时,由生活较好的家长集资延聘塾师课读,一两年后就要参加劳动生产丧失读书的权利了,故苗民文化水平最高的仅能记帐,但苗民有一特长即“对诗”,苗民自幼学习唱歌,青年男女经常在山坡水涯互相“对唱诗歌”,大部份自编自唱,有的唱歌家出口成诗,即景可歌,男女结婚时常特请唱歌专家当“亲家伯”,这是苗族文化上的特点。最突出的苗胞讨亲扛轿的人,如果不能唱和诗歌,上桌不给红酒吃,故意给与红粬渗开水喝,这或许也是保持其固有文化上传统的作风吧?
己、风俗习惯
(一)婚姻:苗民最怕绝后,男女三四岁即行订婚,年19岁结婚,婚礼不管贫富,订婚时,猪脚1只,龙贴2张,红衣线2只,果子2包(红枣冰糖),送女家后即回送以糯米糍斗余,开生庚一定要二次,第一次开不到但要送开生庚的人200元(二角)笔资,女家白鲤2头;第二次才正式开到要送女家肉2斤,合婚后送日子(订婚)时间一定要在8月,礼物月饼10余斤,肉四五斤,面2斤,女方仅收肉和饼各一半,举行婚礼前一日,男家送女家猪肉40斤,油2斤,鸡雌雄各2头,鱼2头,蛋价42个,礼金72千(清时别钱)。女家赔嫁妆奁一定要三杠头,衣服足够穿3年,女结婚后3年内规定不制新衣,唯如果女方贫穷,而双方感情又融洽,则男人往往于3年内偷着为女制新衣裳。婚后2天,男人即往岳家为婿,随送岳父母猪脚1只,岳叔各送肉4斤,但岳父、岳叔每人定要备酒席一桌敬婿,岳父母却更要送婿“记路钱”2元至4元。头年节(即婚后第一年端阳节)岳家送礼很丰厚,粽4斗米,烧饼要200块,鱼2头□□□□□□□□□□□□□□□□□□“亲家伯”(会唱歌的)三人于结婚前一日由“亲家伯”领赴女方住两宵,专门对歌。第一夜对歌时,全村附近男女均集中女家和“亲家伯”对唱,女家家则准备8斗4盘为点心,人多时要吃到10余桌。第二夜点心要鸡鸭各一斗,外加菜等。第三天回家,女方亦聘请2人送女出嫁,男方来随同返去。在举行婚礼时,全村男女均集中男家吃酒,浪费极大,故男人往往订婚后无法举行婚礼。
(二)丧葬:死了人在苗民也是一种负担,人死后举行迷信佛事,村中集中百余人来死者家中吃、赌通宵彻夜。如犯“重丧”、“忌日”,死人不许收殓,甚至连续好几夜,所浪费更多了。苗民死后因经济生活问题影响,大部仅能“红圹”埋葬无法做墓。
(三)习俗:端阳节户户裹粽,粽以芦叶包裹,每条分五节,表示纪念五月五日,端午节,即生活极端困难户也得设法裹几升米,敬祖宗,旧历年家家均用糯米制糍巴或用以送礼。盖房子集体以人工帮助建筑,丧葬六亲均送粮食为主,上寿送猪脚,送者须共同吃光而后去,这都是他们取之劳动用之劳动的纯朴本质的表现。他们的服饰,男人与汉族农民无异,女人则绝不相同,女人服装规定黑衣黑裙,女子出嫁时,裙及衣裳一定要由母舅赠送,妇女头发梳理形式,出嫁前,出嫁后有区别。出嫁前,头顶平铺,已结婚的要加上“披头髻”,以示区别。嫁女妆奁,除普通钗环外,斗笠、蓑衣、锄头是免不了的物件,斗笠多系精工细制的,价值相当昂贵,男女婚后二三天就过共耕生活,夫唱妇随。“劳动”两字是其优良的传统观点。老年人虽乏劳动力,但也不会闲着白吃饭,带小孩、煮饭、烧茶水、看家、搞副产,工作还很卖力有劲,只要一口气在的话,他都会干他所能干的工作。儿童也同样地学习适合他们体力所胜任的劳动。人民政府提出劳动发家,生产致富的号召,苗胞们是有信心有把握来完成这伟大的任务。
苗胞性朴实,勤劳有毅力,团结互助观念强,阶级的仇恨心深重,意志顽强、坚定富斗争性,能刻苦耐劳,他们长期受着汉人的封建剥削歧视,对本民族间的确团结得像钢铁一样的坚固,例如汉人不能通苗语的,一到乡间查询苗人姓名住址,那就费事,尤其年关索债讨帐的更伤脑筋,从村头找到村尾,问得一身是汗,结果呢?只得到“不知道”三个字的回复。国民党反动派——蒋匪帮——统治下抓丁派饷,收捐勒诈,高租重利的层层掠夺,苗胞委实吃亏不少,如果他们没有团结力量,那里能够适应现实环境而生存呢?少数民族迫于生活,一生病连中药也吃不上,更谈不到科学的治疗(例如请西医注射吃西药等)为着克服困难多吃青草药(土草不花钱),故此青草医师多出自苗胞中。迷信比较深,动不动就请巫师驱鬼捕魔,在这种统治的迷信思想支配下,断送了不少人命。相信在共产党人民政府英明领导教育下,这不正确的习俗是有法改革的。
福安县委统战部
[福安市档案馆福安县统战54永久1]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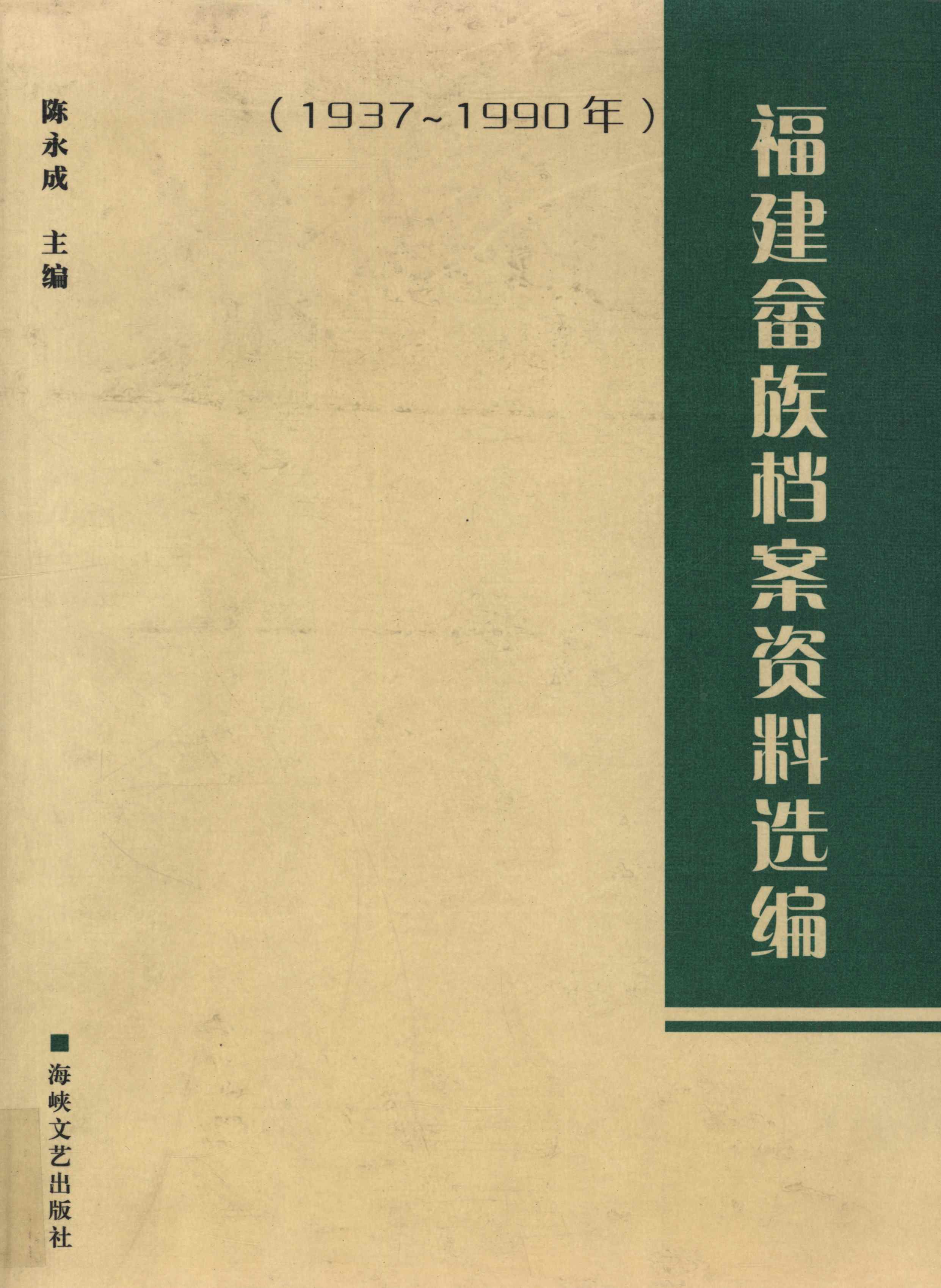
相关地名
福建省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