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对中国港台新儒家对朱子判定的检查
| 内容出处: | 《朱子涵养工夫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574 |
| 颗粒名称: | 六 对中国港台新儒家对朱子判定的检查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7 |
| 页码: | 469-47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牟宗三认为朱子的道德形态是他律,因为朱子将心与理的关系理解为心具理,而心是气之灵,故理不在心外,心外无理。但朱子心与理的结构义中,本心的主宰地位已经确立,本心能具理并自觉践行道德规范。此外,朱子的涵养工夫是成德的根本工夫,而不是被致知吞没的涵养。虽然朱子也强调下学而上达、博文而约礼等成德路径,但这些路径都是以持敬涵养为前提的。因此,牟宗三对朱子的道德形态的判断是有误的。 |
| 关键词: | 南平市 朱子思想 落实 架构 |
内容
(一)对“朱子的心为认知义”的检查
牟宗三对朱子心与理的关系的判定决定了其对朱子道德形态的判断,他认为朱子的心与理的关系是“心具众理”而不是“心即理”,心为“气心”,理外具于心,所以涵养工夫只能涵养不动之“性体”,而不是涵养本心,本心没有自发、自生的力量,故涵养工夫无法成为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朱子确实有以“气之灵”释心,其目的在于为“心能知觉”寻找形质上的根据,因为心为气之灵,所以心为灵明知觉,此气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朱子认为心有形体,理无形体,心又是形体中的灵的部分,所以能为无形之理提供着落处。所以,“气之灵”之气为“形器义”,而不是具有善恶的“气质义”。以此为基础,牟宗三认为在朱子心与理的关系中心只有认知的功能,从功能义上认识朱子的心与理的关系,符合朱子以气言心的说法,但朱子“心之能”的前提在于“理具于心”的结构,如果只从认知义上言心,直接从心之用开始认识朱子心与理的关系,显然缺失了心与理关系的结构义这一前提。牟宗三将朱子的“心具众理”诠释为心认知地具理,将“心具众理”从存有层面的“本具”曲解为工夫层面的“认知地具”,显然与朱子思想本义不符。①
所以,从工夫层面上看,穷理的前提是“心具众理”,穷理需要以持敬涵养为前提,由此说明了朱子的道德形态并非他律。在朱子这里,心不能免除气禀的影响,虽然每个人都“心具众理”,但必须要去做穷理致知的工夫,道德知识的学习是成德必须经历的路径,所以朱子提出下学而上达、博文而约礼、知至而意诚、致知而力行,都是对成德路径的证明,但是都没有动摇涵养工夫为成德根本的地位。穷理是穷“本具之理”,穷理始终都在持敬的关照下进行。下学到上达中有“豁然贯通”的时候,其中有本心力量的呈现,是道德天赋能力的展现,而不全部依靠习惯和经验的积累。对此陈来认为朱子“心具众理”是存有层面的心与理的关系,理潜存于心,“人所先天固有的不是一切知识,而是某些道德的良知(及生理本能)……虽然每个人心具众理,但这些理并未全部反映为人的良知,或者说人的良知并没有把心中所具的众理全部反映出来。……为了使人认识到心中本具众理,并达到心与理的彻底自觉,必须经过格物穷理的认识过程。……只是这些原则是常常是潜在的,在经过格物穷理之后才能成为人的现实意识的真正原则”①。所以,“心具众理”是本具和内具、自具的结合,说明了心的能动和自觉的能力,也说明朱子的涵养和穷理主要依靠自觉、自律的工夫完成。此外,陈来也指出了陆学的“心即理”这个命题本身不是朱子所反对的,朱子反对的是二人对工夫路径和方法的认识。陈来说:“心即理并不是主张人的一切意识活动无条件地合于理义要求。陆学所谓心即是理,在直接意义上是指本心即理。此外亦指人发明本心之后意识活动自然合理。陆学的这个思想朱熹并非不了解。”②
(二)对“朱子涵养工夫为小学工夫”的检查
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是通过对外在的规范的遵守而养成好的习惯,如此涵养工夫就是外在的、经验的道德实践,而不是自觉、自律的道德实践,由此判朱子为道德他律。首先,朱子涵养本原的地位在《知言疑义》中就已提出,在《仁说》中确立,《仁说》中朱子将仁解释为仁体、性体,涵养本原是涵养性之全体,但此性之全体本具于心,所以朱子的涵养工夫是涵养性,也是涵养本心,并且本心的主宰地位在《仁说》之后随着“心具众理”“心主性情”等命题的提出就已经确立本心的主宰地位。中年时期所确立的持敬的工夫是操存涵养、整顿身心,中晚年时期朱子还以求放心解释持敬,晚年以“精神专一”解释持敬,无论持敬为哪一种解释,心的主宰地位是前提,而本心的操习并不只是对外在规范的遵守而养成的习惯,本心居积极主动的地位。其次,从克己与复礼的关系上看,朱子晚年时期重视以复礼作为克己的规矩准绳,认为克己要落实在复礼上完成,体现出朱子对外在规范的重视。但是,从工夫的过程来说须通过克己来完成复礼,所以内心的自觉和道德主体的地位是首先确立的,这也是克己复礼没有超出主敬地位的原因。朱子将持敬作为自得于心的工夫,如果自得于心则也不必做克己工夫,朱子还提出持敬是克己的立脚处,说明主敬的地位没有改变,朱子的涵养并不主要依靠克己复礼完成,说明了通过外部规范的制约不是首选的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自律是成德工夫的第一义。
最后,从涵养与其他工夫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涵养工夫是成德的根本工夫,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牟先生认为朱子的涵养是被致知吞没的涵养,是在“道问学”中的“尊德性”,即“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而完成的,如此“尊德性”就成为经验的、外在的“尊德性”。经前文分析可知,“下学而上达”说明了朱子对成德次序的认识,“尊德性”必须有“道问学”的工夫,但并不是说“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完成的,这是对朱子的误解。朱子晚年并没有改变涵养为致知的根本工夫的地位,持敬是穷理的前提。朱子晚年也并没有以致知言诚意,而是提出知至后的诚意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工夫意义和工夫内容,省察和慎独都是完成意诚的工夫。致知是诚意的主要工夫,但知至不等于意诚,诚意有自己的工夫,所以诚意并不是如牟宗三所说的外在的诚、认知地诚,诚意是通过省察和慎独等自觉的道德实践完成的。由此可见,朱子的涵养工夫也不是经验的、外在的,有学者提出:“朱子探讨道德发生的问题虽然仍遵循孟子的性善论,认为道德有其先验的存在性与超越的内在性,一切道德的观念或行为是以人类至善天性作为根源依据的,而且再次绝对至善的根源为大前提下,每个人对于道德的认知或判断,终究是以个人的自觉自律为依据。”①虽然朱子认为道德认知在成德中有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作用,道德的养成和完善主要是通过自律来完成和实现的。
(三)对“朱子知行不一”的检查
中年时期朱子确立了基本的知先行重的知行观,至晚年时发展成为对成德路径的全面论述。首先,朱子同时从两个方面对致知和践履的关系做出阐释:一方面,致知是大学工夫的下手处,但是要补涵养于未发一段的工夫,说明了持敬是穷理、致知之本,穷理没有超出持敬涵养的道德义,说明知的目的最终是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另一方面朱子提出致知而后力行说明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大学》的工夫规模体现了知先行后的入德次序。朱子以知至而后意诚说明了知先行后,以真知必能行说明了知行合一的意诚的境界,最终以意诚为行之始,将成德的标准落到行上说,说明了朱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
其次,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看,朱子晚年提出“无时不涵养省察”“未发已发都要省察”的观点,说明朱子注重省察对涵养工夫的补充,省察是完成诚意和慎独阶段的重要工夫,这也说明朱子晚年重视对自觉的道德实践的落实。
最后,朱子的涵养工夫并不只是精神意识上的活动,虽然朱子晚年将持敬诠释为“精神专一”,但并没有取消持敬为整顿身心的解释,涵养本身就是身心合一的道德实践。朱子涵养工夫的特点是以持敬贯彻所有工夫始终,强调平日涵养无间断、事中涵养等观点其实都体现了朱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从具体的涵养工夫来说,朱子中晚年开始重视诚与敬的分辨,提出不能以敬代诚,将诚落在诚意工夫上解释,诚意主要是为了解决知行不一的自欺的问题,可以看出朱子晚年重视道德实践的落实。朱子中晚年开始对主静保持警惕的态度,以持敬限制静坐,提出无事时且静坐、不能专于静坐的观点,说明了朱子重视“事中涵养”而非“静中涵养”,这也说明朱子重行而非重知。朱子晚年对立志工夫也有进一步重视,这是基于在志与意的分析中发现志具备意所没有的特点和功能,所以需要拈出立志工夫来补充居敬,朱子的目的也是解决道德实践动力不足的问题。可见,朱子对涵养工夫的修正和完善真正是其知行合一思想的体现。
(四)对“以朱子成德路径判朱子为他律”的检查
对于朱子晚年不仅从知行关系还从《格物补传》中的积累至贯通、《大学》中的知至而后诚意、《论语》中的博文约礼、《孟子》中的博学而反约来贯通《论语》中下学而上达的思想,从“四书”工夫思想贯通的角度对朱子晚年的成德路径做了阐发,可见朱子晚年对成德艰难的认识,鼓励人做工夫要勇猛精进。同时朱子批评陆学上达而下学,也批评了陈淳“先见天理源头”,二者都是不够重视穷理的体现。对于朱子晚年对成德路径的集中阐发,牟宗三提出这是朱子注重工夫的深度和广度的表现,他说:“安卿病处,依朱子所见,单在只吃馒头尖,广度深度工夫俱不作,只想凭空理会那源头处,空守著那个荡漾如水银的天理而不放,故朱子反覆告诫之也。并非不可说源头处,亦非定不许‘先见天理源头’也。即是朱子晚年甚至历来不喜‘先见天理源头’之见,重在平说平磨,亦只怕人两脚踏空,先只空见个‘天理源头’有何益?故其虽遮拨之,然一至正面叮咛反覆,却只重在深度广度平磨将去。此其重点知在工夫之踏实与充实,并非客观义理上定不许‘先见天理源头’也。此见前训潘时举言为学两进路便可知。”①在此牟宗三指出朱子晚年不喜“先见天理本原”并不是对持敬涵养的否定,而是肯定朱子晚年重视工夫的深度和广度,广度上重视涵养与致知的平衡,怕门人两脚踏空,只守个天理本原。深度上强调格物穷理致知等下学工夫的积累,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并且,朱子重视下学工夫是强调工夫的踏实与充实,牟先生以深度和广度的“平磨”来说明朱子晚年对下学工夫的重视。牟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朱子也说“见天理源头”,但是与象山不同,同时他做出了优劣判定,他说:“并非一说‘先见天理源头’便是象山学也。在朱子之义理系统中亦可说‘先见天理源头’(先理会太极大本),然在此系统中不如在五峰、象山学中先识本心仁体为切要,故朱子得以重视平磨以遮拨之也。”①牟宗三认为朱子也言“先见天理源头”,即先理会大本所在,也就是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也就是涵养本原,但是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本原没有在五峰和象山言“先识仁体本心”这么重要,所以朱子重视穷理致知作为下学工夫的积累。
由此可以看出,牟宗三认为工夫的“平磨”即通过穷理致知的下学工夫的积累至上达不是最优的道德修养方法,是通过练习、模仿达到的道德的规范,所以是他律的、外在的。相比之下五峰、象山的先识本心仁体是最优的方法,因为本心主宰、本心自觉,道德形态也是自律的。牟先生依此创造出朱子是横贯系统和象山是纵贯系统来说明象山的道德形态是自律,朱子的道德形态是他律,最终以象山为优,朱子为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作为成德的路径的说明,意诚之前的穷理、致知、省察、慎独、“克己复礼”等下学工夫的积累过程需要练习、模仿和外在规范的学习,但是下学至上达存在积累至贯通的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贯通的阶段并不是完全依靠练习和模仿实现的,朱子指出其中有融会贯通觉悟处,二程言其中有类推的方法,还有其他不可言说的体验处,这都说明朱子的成德路径不是通过他律实现的。并且需要指出的是朱子以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在致知之前,持敬涵养的根本地位已经确立了其成德的主要方法不是依靠他律而是依靠自觉本心为善的前提。最后,作为穷理、致知、省察、克己复礼等下学工夫本身,也不是属于依靠练习、模仿完成的工夫,穷理是穷心中本具之理,致知是致本心之虚灵明觉,省察是解决自欺的行为,是对不知不觉的私意的检查,也是慎独的工夫,是需要通过本心的主宰,通过本心的自我认识和行动的自我约束来实现,所以可知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作为成德的基本路径,并不影响朱子的涵养工夫是自律自觉的工夫。
牟宗三对朱子心与理的关系的判定决定了其对朱子道德形态的判断,他认为朱子的心与理的关系是“心具众理”而不是“心即理”,心为“气心”,理外具于心,所以涵养工夫只能涵养不动之“性体”,而不是涵养本心,本心没有自发、自生的力量,故涵养工夫无法成为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朱子确实有以“气之灵”释心,其目的在于为“心能知觉”寻找形质上的根据,因为心为气之灵,所以心为灵明知觉,此气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朱子认为心有形体,理无形体,心又是形体中的灵的部分,所以能为无形之理提供着落处。所以,“气之灵”之气为“形器义”,而不是具有善恶的“气质义”。以此为基础,牟宗三认为在朱子心与理的关系中心只有认知的功能,从功能义上认识朱子的心与理的关系,符合朱子以气言心的说法,但朱子“心之能”的前提在于“理具于心”的结构,如果只从认知义上言心,直接从心之用开始认识朱子心与理的关系,显然缺失了心与理关系的结构义这一前提。牟宗三将朱子的“心具众理”诠释为心认知地具理,将“心具众理”从存有层面的“本具”曲解为工夫层面的“认知地具”,显然与朱子思想本义不符。①
所以,从工夫层面上看,穷理的前提是“心具众理”,穷理需要以持敬涵养为前提,由此说明了朱子的道德形态并非他律。在朱子这里,心不能免除气禀的影响,虽然每个人都“心具众理”,但必须要去做穷理致知的工夫,道德知识的学习是成德必须经历的路径,所以朱子提出下学而上达、博文而约礼、知至而意诚、致知而力行,都是对成德路径的证明,但是都没有动摇涵养工夫为成德根本的地位。穷理是穷“本具之理”,穷理始终都在持敬的关照下进行。下学到上达中有“豁然贯通”的时候,其中有本心力量的呈现,是道德天赋能力的展现,而不全部依靠习惯和经验的积累。对此陈来认为朱子“心具众理”是存有层面的心与理的关系,理潜存于心,“人所先天固有的不是一切知识,而是某些道德的良知(及生理本能)……虽然每个人心具众理,但这些理并未全部反映为人的良知,或者说人的良知并没有把心中所具的众理全部反映出来。……为了使人认识到心中本具众理,并达到心与理的彻底自觉,必须经过格物穷理的认识过程。……只是这些原则是常常是潜在的,在经过格物穷理之后才能成为人的现实意识的真正原则”①。所以,“心具众理”是本具和内具、自具的结合,说明了心的能动和自觉的能力,也说明朱子的涵养和穷理主要依靠自觉、自律的工夫完成。此外,陈来也指出了陆学的“心即理”这个命题本身不是朱子所反对的,朱子反对的是二人对工夫路径和方法的认识。陈来说:“心即理并不是主张人的一切意识活动无条件地合于理义要求。陆学所谓心即是理,在直接意义上是指本心即理。此外亦指人发明本心之后意识活动自然合理。陆学的这个思想朱熹并非不了解。”②
(二)对“朱子涵养工夫为小学工夫”的检查
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是通过对外在的规范的遵守而养成好的习惯,如此涵养工夫就是外在的、经验的道德实践,而不是自觉、自律的道德实践,由此判朱子为道德他律。首先,朱子涵养本原的地位在《知言疑义》中就已提出,在《仁说》中确立,《仁说》中朱子将仁解释为仁体、性体,涵养本原是涵养性之全体,但此性之全体本具于心,所以朱子的涵养工夫是涵养性,也是涵养本心,并且本心的主宰地位在《仁说》之后随着“心具众理”“心主性情”等命题的提出就已经确立本心的主宰地位。中年时期所确立的持敬的工夫是操存涵养、整顿身心,中晚年时期朱子还以求放心解释持敬,晚年以“精神专一”解释持敬,无论持敬为哪一种解释,心的主宰地位是前提,而本心的操习并不只是对外在规范的遵守而养成的习惯,本心居积极主动的地位。其次,从克己与复礼的关系上看,朱子晚年时期重视以复礼作为克己的规矩准绳,认为克己要落实在复礼上完成,体现出朱子对外在规范的重视。但是,从工夫的过程来说须通过克己来完成复礼,所以内心的自觉和道德主体的地位是首先确立的,这也是克己复礼没有超出主敬地位的原因。朱子将持敬作为自得于心的工夫,如果自得于心则也不必做克己工夫,朱子还提出持敬是克己的立脚处,说明主敬的地位没有改变,朱子的涵养并不主要依靠克己复礼完成,说明了通过外部规范的制约不是首选的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自律是成德工夫的第一义。
最后,从涵养与其他工夫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涵养工夫是成德的根本工夫,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牟先生认为朱子的涵养是被致知吞没的涵养,是在“道问学”中的“尊德性”,即“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而完成的,如此“尊德性”就成为经验的、外在的“尊德性”。经前文分析可知,“下学而上达”说明了朱子对成德次序的认识,“尊德性”必须有“道问学”的工夫,但并不是说“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完成的,这是对朱子的误解。朱子晚年并没有改变涵养为致知的根本工夫的地位,持敬是穷理的前提。朱子晚年也并没有以致知言诚意,而是提出知至后的诚意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工夫意义和工夫内容,省察和慎独都是完成意诚的工夫。致知是诚意的主要工夫,但知至不等于意诚,诚意有自己的工夫,所以诚意并不是如牟宗三所说的外在的诚、认知地诚,诚意是通过省察和慎独等自觉的道德实践完成的。由此可见,朱子的涵养工夫也不是经验的、外在的,有学者提出:“朱子探讨道德发生的问题虽然仍遵循孟子的性善论,认为道德有其先验的存在性与超越的内在性,一切道德的观念或行为是以人类至善天性作为根源依据的,而且再次绝对至善的根源为大前提下,每个人对于道德的认知或判断,终究是以个人的自觉自律为依据。”①虽然朱子认为道德认知在成德中有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作用,道德的养成和完善主要是通过自律来完成和实现的。
(三)对“朱子知行不一”的检查
中年时期朱子确立了基本的知先行重的知行观,至晚年时发展成为对成德路径的全面论述。首先,朱子同时从两个方面对致知和践履的关系做出阐释:一方面,致知是大学工夫的下手处,但是要补涵养于未发一段的工夫,说明了持敬是穷理、致知之本,穷理没有超出持敬涵养的道德义,说明知的目的最终是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另一方面朱子提出致知而后力行说明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大学》的工夫规模体现了知先行后的入德次序。朱子以知至而后意诚说明了知先行后,以真知必能行说明了知行合一的意诚的境界,最终以意诚为行之始,将成德的标准落到行上说,说明了朱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
其次,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看,朱子晚年提出“无时不涵养省察”“未发已发都要省察”的观点,说明朱子注重省察对涵养工夫的补充,省察是完成诚意和慎独阶段的重要工夫,这也说明朱子晚年重视对自觉的道德实践的落实。
最后,朱子的涵养工夫并不只是精神意识上的活动,虽然朱子晚年将持敬诠释为“精神专一”,但并没有取消持敬为整顿身心的解释,涵养本身就是身心合一的道德实践。朱子涵养工夫的特点是以持敬贯彻所有工夫始终,强调平日涵养无间断、事中涵养等观点其实都体现了朱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从具体的涵养工夫来说,朱子中晚年开始重视诚与敬的分辨,提出不能以敬代诚,将诚落在诚意工夫上解释,诚意主要是为了解决知行不一的自欺的问题,可以看出朱子晚年重视道德实践的落实。朱子中晚年开始对主静保持警惕的态度,以持敬限制静坐,提出无事时且静坐、不能专于静坐的观点,说明了朱子重视“事中涵养”而非“静中涵养”,这也说明朱子重行而非重知。朱子晚年对立志工夫也有进一步重视,这是基于在志与意的分析中发现志具备意所没有的特点和功能,所以需要拈出立志工夫来补充居敬,朱子的目的也是解决道德实践动力不足的问题。可见,朱子对涵养工夫的修正和完善真正是其知行合一思想的体现。
(四)对“以朱子成德路径判朱子为他律”的检查
对于朱子晚年不仅从知行关系还从《格物补传》中的积累至贯通、《大学》中的知至而后诚意、《论语》中的博文约礼、《孟子》中的博学而反约来贯通《论语》中下学而上达的思想,从“四书”工夫思想贯通的角度对朱子晚年的成德路径做了阐发,可见朱子晚年对成德艰难的认识,鼓励人做工夫要勇猛精进。同时朱子批评陆学上达而下学,也批评了陈淳“先见天理源头”,二者都是不够重视穷理的体现。对于朱子晚年对成德路径的集中阐发,牟宗三提出这是朱子注重工夫的深度和广度的表现,他说:“安卿病处,依朱子所见,单在只吃馒头尖,广度深度工夫俱不作,只想凭空理会那源头处,空守著那个荡漾如水银的天理而不放,故朱子反覆告诫之也。并非不可说源头处,亦非定不许‘先见天理源头’也。即是朱子晚年甚至历来不喜‘先见天理源头’之见,重在平说平磨,亦只怕人两脚踏空,先只空见个‘天理源头’有何益?故其虽遮拨之,然一至正面叮咛反覆,却只重在深度广度平磨将去。此其重点知在工夫之踏实与充实,并非客观义理上定不许‘先见天理源头’也。此见前训潘时举言为学两进路便可知。”①在此牟宗三指出朱子晚年不喜“先见天理本原”并不是对持敬涵养的否定,而是肯定朱子晚年重视工夫的深度和广度,广度上重视涵养与致知的平衡,怕门人两脚踏空,只守个天理本原。深度上强调格物穷理致知等下学工夫的积累,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并且,朱子重视下学工夫是强调工夫的踏实与充实,牟先生以深度和广度的“平磨”来说明朱子晚年对下学工夫的重视。牟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朱子也说“见天理源头”,但是与象山不同,同时他做出了优劣判定,他说:“并非一说‘先见天理源头’便是象山学也。在朱子之义理系统中亦可说‘先见天理源头’(先理会太极大本),然在此系统中不如在五峰、象山学中先识本心仁体为切要,故朱子得以重视平磨以遮拨之也。”①牟宗三认为朱子也言“先见天理源头”,即先理会大本所在,也就是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也就是涵养本原,但是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本原没有在五峰和象山言“先识仁体本心”这么重要,所以朱子重视穷理致知作为下学工夫的积累。
由此可以看出,牟宗三认为工夫的“平磨”即通过穷理致知的下学工夫的积累至上达不是最优的道德修养方法,是通过练习、模仿达到的道德的规范,所以是他律的、外在的。相比之下五峰、象山的先识本心仁体是最优的方法,因为本心主宰、本心自觉,道德形态也是自律的。牟先生依此创造出朱子是横贯系统和象山是纵贯系统来说明象山的道德形态是自律,朱子的道德形态是他律,最终以象山为优,朱子为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作为成德的路径的说明,意诚之前的穷理、致知、省察、慎独、“克己复礼”等下学工夫的积累过程需要练习、模仿和外在规范的学习,但是下学至上达存在积累至贯通的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贯通的阶段并不是完全依靠练习和模仿实现的,朱子指出其中有融会贯通觉悟处,二程言其中有类推的方法,还有其他不可言说的体验处,这都说明朱子的成德路径不是通过他律实现的。并且需要指出的是朱子以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在致知之前,持敬涵养的根本地位已经确立了其成德的主要方法不是依靠他律而是依靠自觉本心为善的前提。最后,作为穷理、致知、省察、克己复礼等下学工夫本身,也不是属于依靠练习、模仿完成的工夫,穷理是穷心中本具之理,致知是致本心之虚灵明觉,省察是解决自欺的行为,是对不知不觉的私意的检查,也是慎独的工夫,是需要通过本心的主宰,通过本心的自我认识和行动的自我约束来实现,所以可知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作为成德的基本路径,并不影响朱子的涵养工夫是自律自觉的工夫。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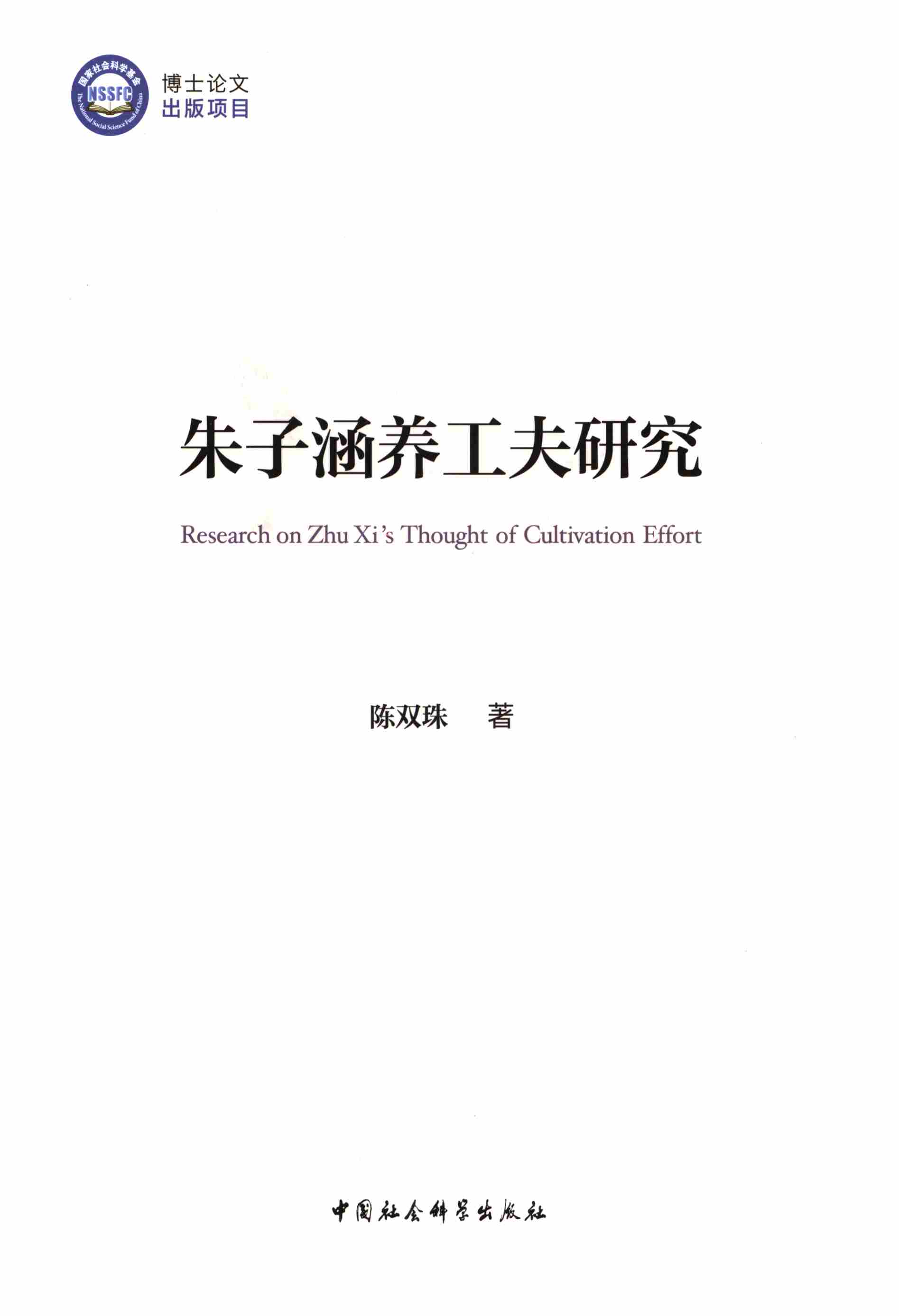
《朱子涵养工夫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以朱子涵养工夫为研究对象,将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分为中年、中晚年、晚年三个阶段,梳理出朱子涵养工夫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和发展历程。全书围绕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涵养工夫内在的关系以及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三个角度对朱子涵养工夫进行了考察;从脉络发展的视野厘清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和思想地位;从学术史论辩的视野探寻朱子涵养工夫的特点;从工夫论的确立到完善的动态考察探求朱子涵养工夫思想背后的心性论的建构和完善的过程;从而对朱子的修身涵养理论进行了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研究,也对学术史上关于朱子涵养工夫的诸多判定和争议进行了检查。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