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 内容出处: | 《朱子涵养工夫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558 |
| 颗粒名称: | 结论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27 |
| 页码: | 449-475 |
| 摘要: | 本文主要描述了朱熹的涵养工夫思想及其心性论的建立和完善过程。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确立了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并逐渐建立了心性论的基本架构。此后,他进一步在心性之辨中确立了性善论的地位,论证了涵养工夫的重要和克己复礼工夫的必要。在晚年时期,朱子对心性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并对涵养工夫做出了修正和补充,强调了格物穷理、致知省察等下学工夫的必要性。 |
| 关键词: | 南平市 朱子思想 落实 架构 |
内容
一 涵养工夫与心性论的建立和完善
朱子涵养工夫的确立是经由对“中和旧说”的反思,最后在“中和新说”中完成的。1168年朱子39岁在《已发未发说》中初步对已发未发的做了界定。次年,在对《已发未发说》修改的基础上,朱子又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对未发已发的阐述进一步明晰,由此朱子以未发已发分辨性情的思路基本形成,在未发和未发之中的区别中说明了未发之中的重要,从而为未发前涵养工夫的落实提供了心性论的基础。朱子对心性论的建构首先从未发已发的区分中开始主要是基于对辩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所以将涵养工夫落实于未发之前是“新说”时期朱子的主要任务,对此陈来也指出:“己丑之悟的重点还是在确立未发时心的涵养工夫。”①1169年朱子在《答张钦夫》中进一步明确未发已发的思想,提出“心贯性情”的说法,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和心、性、情三分的基本心性架构,标志朱子“中和新说”理论的正式确立,也为涵养贯通未发已发、彻上彻下、存养先于察识等工夫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心性论基础。学界对“己丑之悟”有很高的评价,陈来说:“己丑之悟才从根本上确立了朱熹的学术面貌。”①究其原因,即因为朱子在“己丑之悟”中完成了心性论的基本建构的同时工夫论的基本架构也确立起来。
在“新说”的基础上,朱子于1171年作《尽心说》《胡子知言疑义》,次年在与胡伯逢、胡广仲等湖湘学者的通信中提出性具于心、心具理、心主性情等观点,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对胡宏的心性观点做进一步辨析。朱子在性情之辨中确立了性善论的地位,论证了涵养工夫的重要和克己复礼工夫的必要,又以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对恶的产生进行了说明,提出尽心须假存养的观点,为涵养与致知关系的确立提供了心性论上的基础,又进一步向湖湘学者阐明涵养的地位重于察识。1172年至1174年朱子围绕《仁说》与张栻、胡伯逢展开讨论,进一步对心、性、情做出分辨,以“仁性爱情”确立了仁体、心体的地位,为克己复礼工夫的地位提供了心性论上的证明,将克己复礼工夫纳入涵养的范围之内。此后在《观心说》中朱子再一次明确一心为主宰的地位,也说明了操存是操存一心而不是以心观心,标志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结束。由此可见朱子于46岁前已完成心性论的基本建构,也标志朱子思想体系和学术规模的基本确立。②此后,朱子在《集注》中对“心具众理”命题做了完整阐释,确立了心与理关系的基本命题,由此说明了心具众理与穷理的关系。朱子又以尽心和存心的关系说明涵养与穷理的关系,以尽心为知至,以知至为贯通的阶段,诚意没有独立的工夫内容。在《集注》时期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考虑到气禀对性、才的影响,开始注重穷理工夫,是《仁说》中心性论进一步完善的体现。在此阶段,朱子体现出“四书”互证的方法,为“四书”工夫的贯通做了准备,代表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
50岁后朱子提出要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提出涵养本原、求放心是第一义等观点,说明朱子的工夫思想从《论语》贯通至《孟子》。中晚时期朱子延续“中和新说”确立的涵养须用敬、涵养无间断、敬为彻上彻下等基本观点,说明“中和新说”后朱子保持涵养工夫的基本观点。朱子晚年对中年时期所提出的“心主性情”“心具众理”等命题做进一步阐释,对“心如谷种”“心具众理”“心统性情”等心性论命题做一步诠释,对心、性、情、意、志、欲、才等心性概念做了进一步辨析,代表晚年对心性论的进一步完善。朱子晚年进一步重视意、志、欲的作用,为落实诚意、立志、克己复礼的工夫做了心性论上的说明。朱子晚年重视气禀对心性结构的影响,围绕生之谓性、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气强理弱等命题进一步深化对中年时期的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的关系的认识,提出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堕在气质后形成的,气质之性不改变天命之性,可见朱子晚年并没有改变中年时期所确立的性善论的基础,故对涵养本原、持敬为本、一心为主宰等基本涵养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朱子晚年注意到气禀对人成德的影响,认识到成德的艰难和修养工夫的重要,所以比较注重强调格物穷理、致知省察等下学工夫的必要性,注重省察对涵养的帮助,批评识心、先见天理本原等不下学只要上达的工夫思想,在持敬为本的基础上落实了克己复礼、诚意、立志等工夫对持敬的补充,体现了朱子知先行后、积累至贯通、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也说明朱子晚年工夫思想随着心性论的进一步完善而更加严密。
二 涵养工夫的确立、修正与完善的过程
“中和新说”时期朱子提出涵养须用敬、涵养要贯彻动静、涵养无间断、敬为彻上彻下等观点确立了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但是牟宗三因此认为:“朱子中和新说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定论”①,以“新说”为定论实在言之过早,“中和新说”时期朱子对涵养工夫的建构并不完整,这一时期更多的是确立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以持敬为重,认为涵养本原可以变化气质,“中和新说”后朱子在《仁说》《尽心说》《集注》等阶段将克己复礼纳入涵养工夫的范畴,后提出尽心须假存养,落实了存养与穷理的关系。50岁后朱子虽然不再致力于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但从朱子在50岁后对涵养工夫的论说中可知其“道理只争丝发之间”的精神。《集注》后提出持敬即求放心、求放心与克己为一事,体现《集注》后对“四书”工夫的贯通,但是朱子强调就切实处做工夫,说明朱子工夫思想以《论语》为宗。朱子晚年后仍坚持涵养本原的观点,重视气禀的影响,以此说明了涵养工夫的重要性,但对持敬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和新说”时朱子以主一、直内解释持敬,但在晚年后朱子偏向从“精神专一”上解释敬的工夫,体现出朱子对持敬理解的重大变化。另外,对于其他涵养工夫的解释以及涵养工夫之间的关系,朱子在中年后至晚年仍不断进行修正、补充与完善,在主敬涵养的基础上,以静坐、诚意、克己复礼、立志作为持敬的重要补充,说明朱子晚年涵养工夫严密的特点。
(一)持敬与主静
“中和新说”时期朱子以动静区分未发已发,强调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提出持敬以静为本的主静涵养的观点,45岁后朱子开始认识到与陆学的区别,中晚年后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成为朱陆之辩的核心,基于对陆学轻视穷理工夫的批评,朱子50岁后慎言主静,将静限制为工夫后的境界,强调不能离敬言静,又以持敬消解静坐。朱子认为儒释静坐工夫的区别在于有没有以持敬为主,朱子批评子静不读书、不求义理、静坐澄心,本质上是告子的义外说。晚年后朱子仍然坚持不以主静言敬的立场,避免从工夫上言静的工夫,以静为工夫后的境界,否定以静求静的工夫思想,并提出“主一兼动静而言”,取消了言主静的意义。朱子晚年后肯定静坐工夫对于收敛身心的意义,但将静坐限定于无事的状态,将静坐限制于持敬的统摄,实际上消解了静坐的意义,说明了朱子主敬涵养的基本立场。
(二)持敬与克己
朱子45岁时与湖湘学派的论辩已经基本完成,朱子开始反思自己在与湖湘学派论辩的过程中因强调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而将持敬抬得过高。随着《仁说》中确立了仁体的地位,克己复礼工夫受到重视,敬与克己的关系就成为朱子关注的重要问题,成为朱子对涵养工夫之间关系的第一次检查。《仁说》前朱子主要遵从伊川的“敬则无己可克”的观点,提出“持敬则无须克己”“克己就是持敬”,直接以持敬作为为仁的工夫。《仁说》后朱子认识到克己复礼是为仁的重要工夫,将克己与持敬并举,并提出“克己在持敬之上”,认为克己复礼是孔门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提高了克己复礼的地位,但是朱子同时提出克己复礼是颜回的方法,对资质要求很高,建议以持敬为涵养的主要工夫,工夫比较平实容易,说明了中年时期持敬仍是第一义的工夫。朱子提出“克己持敬并举”是反思伊川“敬则无己可克”的开始。中晚年时期,朱子避免多言“克己在持敬之上”,提出“敬是立脚处”“敬与克己须俱到”的观点,一方面仍以敬解释克己工夫,因为持敬工夫平实,克己工夫对资质要求太高,认为伊川“敬则无己可克”虽然省事,但此事甚大、甚难,体现出朱子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另一方面,朱子对持敬与克己工夫内容做了区分,提出二者须俱到,说明了朱子在保持主敬涵养的立场上,为克己工夫提供了独立的工夫意义。
进入晚年后,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做了修正,改变了中年时期以“克己复理”诠释“克己复礼”的观点,提出不能以“复理”诠释复礼,将工夫重点落在复礼上完成。朱子提出克己复礼在克己与复礼上都要做工夫,但不是两件事,克己的内容是复礼,礼是克己与复礼的规矩准绳,克己在复礼上完成。朱子晚年一方面以克己复礼作为下学的工夫,将为仁作为上达的工夫,只有先克己复礼才能实现为仁,这是朱子晚年对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的强调,朱子由此批判象山言克己过于直接,教人“当下便是”,也批评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是将工夫说得太快;另一方面朱子将克己工夫落实到复礼上完成,是警惕大程门人直接以“复理”解释复礼,如此则克己没有复礼作为规范,克己工夫被悬空。朱子同时依此批判佛老言克己以后不言复礼,将克己工夫沦为空寂,这是朱子晚年将克己工夫规范化的理性伦理的体现,也是朱子晚年言工夫的精密之处。基于朱子晚年对克己复礼的诠释发生了变化,朱子对敬与克己复礼关系的理解也有进一步修正,朱子继续对伊川“敬则无己可克”做反省,认为此事甚大、甚难,认为伊川将敬的工夫说得太高,强调“敬则无己可克”是工夫后的境界。朱子认为克己在持敬之上,克己是较快、较高的工夫,持敬为较缓、较平实的工夫,以乾坤二道比喻克己与持敬,认为二者各有优劣,要逐项做工夫。钱穆认为朱子言克己与持敬和致知并立为三,其看到了朱子晚年对克己复礼的重视,但是克己没有取代主敬涵养的地位,克己在涵养工夫的范围内,是对主敬的重要补充。
对于持敬与克己复礼的关系,钱穆认为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出现三次变化,他说:“伊川又言:敬则无己可克。朱子先亦引其说,稍后则谓敬之外亦须兼用克己工夫,更后乃谓克己工夫尚在主敬工夫之上。关于此,朱子思想显有三变。”①钱穆认为朱子单独提出克己工夫是在主敬涵养之后,改变了朱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两大工夫架构,变成持敬、克己与致知三足鼎立的工夫架构。从持敬与克己的关系上看,可以说持敬与克己是并立的两个工夫,但如果将克己与持敬、致知并立为三,则改变了朱子主敬涵养的立场,所以对钱穆这个判断是需要慎重对待的。综合朱子从中年时期开始至晚年对持敬与克己工夫关系的梳理可知,朱子持敬与克己工夫的关系不仅只有三变,朱子中年至中晚年时期主要认为“敬则无己可克”,以持敬解释克己,克己工夫没有下落处,但《仁说》之后也同时将克己与持敬并举,即钱穆所说的持敬之外兼用克己。至晚年时朱子确实有很多克己在持敬之上的论述,说明朱子晚年对克己工夫的重视,但朱子同时提出二者相资相成,是互相配合、内外参合的关系,并且朱子至去世前强调克己与持敬要逐项做工夫,二者各有优劣,这都说明朱子最终没有将克己置于主敬之上,也说明克己复礼没有取代主敬涵养的地位,而与持敬和致知并列为三,在涵养工夫的内部可以说克己与持敬并立,但是克己复礼没有推翻朱子涵养须用敬的基本立场,这也是朱子晚年持敬与克己的最终关系,也说明了朱子晚年工夫思想平稳和严密的特点。
(三)敬与诚
中年时期,朱子确定以“真实无妄”解释诚的工夫,常常合说诚敬,以诚敬为涵养,但重点落在敬上,诚只是形容持敬工夫的程度,没有单独的工夫意义。《集注》后朱子将“四书”中的诚的工夫贯通,将诚的工夫落到意上考察,以诚意释诚的工夫,贯通了《中庸》《孟子》中的诚与《大学》中的诚意,诚开始有了独立的工夫内容。《集注》后朱子提出诚是实、敬是畏,二者内涵不同,所以不能以敬代诚,“敬可为诚之之一事,不可专以敬为诚之之道”,由此与明道所言“诚敬一事”分道扬镳。朱子同时提出不能以诚代敬,否则持敬不能为主,工夫支离。可见诚已超出敬的限制,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工夫位置,所以朱子提出持敬与诚意要同时做工夫,诚意成为持敬的重要补充,但没有动摇主敬涵养的地位。朱子晚年同时存在合说诚敬与分说诚敬的情况,朱子仍合说诚敬为专一的工夫,但对二者进行了更为清晰的区分,以持敬为专一,以诚为一,修正了“诚在敬之上”的说法,以工夫内容区分二者,认为诚敬不分先后,应该逐项做工夫,提出二程言“诚然后敬”是从工夫境界上说,对诚敬关系的处理平稳了许多。从朱子晚年对诚敬关系的处理可以反映出朱子晚年对工夫的认识是从做工夫和工夫的境界两个层面来说的,从做工夫上说应逐项做工夫,而所谓工夫的上下、工夫的贯通则是做工夫后的境界。并且朱子在诚敬关系上与象山存在分歧,象山言“存诚”,反对持敬。
(四)持敬与立志
朱子对立志工夫的重视始于《集注》,在《集注》中朱子开始对志的概念和作用做了诠释,朱子以“心之所之”解释志,说明了志对成德的方向和动力的作用,又以“志于道”作为志的内容,提出了儒家对道德主体的责任和使命,但立志工夫还没有被单独拈出。《集注》后朱子继续注意立志工夫,提出读书人就是要立下圣人之志,认为学者不能坚持的首要原因是没有立下志向,这是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为成德路径的基础上,教人勇猛精进,坚持做工夫的体现。同时朱子分析了立志与持敬的关系,提出“信得及”为成德第一义,证明涵养本原仍是第一节的工夫,而将立志作为第二节工夫。在持敬与立志的关系上,朱子提出立志就是本心的坚守,对持守助力作用,但是提出立志要以明理为前提,在立志的基础上做工夫要勇猛精进,不能空言立志,认为象山立志太高,而不教人穷理,与象山的立志思想进行区分,也开始注意到胡宏言立志于持敬的关系。晚年时期在对心、性、情、志等进一步分辨析的基础上,朱子进一步重视立志工夫,不能只在读书上立志,提出“一切之事皆要立志”,立志是格物、致知工夫的前提,强调成德工夫要勇猛精进。并且,朱子提出立志与气禀的影响无关,强调无论气禀如何都要以尧舜为志,勇猛精进是成德的唯一途径。对持敬与立志的关系,朱子在强调立志是为学、为事之本的基础上提出要居敬以立其志,说明以持敬为主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朱子采纳五峰的观点提出敬与立志各有精粗、大细的不同,二者互为表里,内外参合,要逐项做工夫,但是同时对五峰的观点进行了检查,认为五峰过分强调居敬与立志,忽视了其中格物工夫的作用。朱子强调致知是广大的工夫,需要通过积累与贯通才能达到,强调成德的艰难以及工夫不能过于急迫,体现出对涵养与致知基本工夫架构的坚持。
综上分析可知,朱子对涵养工夫的建构和完善贯穿其一生的思想路程,并不是在“中和新说”时期就完成的,“中和新说”后持敬与克己复礼、诚意、立志、静坐等工夫的关系也不断补充和修正,最后形成以持敬为主,克己复礼、诚意、立志、静坐为补充的广大的涵养工夫系统,这也说明朱子晚年主敬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涵养作为成德第一位的工夫也没有改变。朱子从广度上补充了立志工夫,从深度上补充了诚和克己复礼两个工夫,又提升了省察、诚意的地位,强调隐微处做工夫的重要。这都是基于朱子晚年认识到成德的艰难,也与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相互印证。朱子对涵养工夫的修正和补充是朱子思想不断完善的体现,也是朱子工夫思想严密性的体现。
三 涵养工夫的地位
(一)涵养与省察
朱子46岁前对涵养工夫地位的认识主要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进行考察,“旧说”时期朱子以心为已发,认为在已发之际的察识可以体验未发前的大本。“新说”后朱子以心贯通未发已发,涵养工夫落实于未发之前,提出涵养先于察识、涵养重于察识的观点,与张栻为代表的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做出区分,体现出“中和新说”时期对未发前涵养工夫的重视。同时,基于持敬贯通动静、彻上彻下的认识,朱子提出未发前为敬之体,即未发之中,已发后敬又行于省察之中,是随事而发,强调持敬与省察不是两节工夫。45岁后由于不再与湖湘学派论辩,同时开始认识到与陆学的分歧,涵养与省察不再是定位涵养工夫地位的唯一关系。朱子在《集注》中将慎独从戒惧中分离出来,慎独需要通过省察来完成,又以戒惧与慎独的关系说明了涵养与省察的关系,是朱子开始重视慎独、诚意的表现。《集注》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不再是定位涵养工夫地位的重点,朱子不再集中强调涵养先于察识、涵养重于察识的地位,朱子提出持敬为主,省察到私意应以持敬为主,先落实持敬工夫,因为持敬是立脚处,是成德的根据。同时提出省察对持敬无间断有辅助作用,二者互相配合,强调省察对涵养的意义。《集注》后朱子延续以戒惧和慎独来说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但进一步对此前的修正做了说明,对胡季随将戒慎和慎独混为涵养提出辨析,强调慎独工夫的独立性,说明了朱子中晚年时期对省察的重视。朱子晚年在对心、性、情的分疏更加细密的基础上对意的作用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再加上对气禀的重视,朱子晚年对诚意、省察工夫有进一步的重视。朱子将尽心的境界从知至推后至诚意,继续将诚的工夫落到诚意上说,以意诚为成德的标准,以省察为知至后诚意工夫完成的关键,成为决定能否成德的最终工夫,这都体现出朱子晚年对诚意工夫的重视。在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朱子改变了“中和新说”时期确立的“涵养先于察识”“涵养为本,省察为助”的主次关系,进一步修正了中晚年时期的“无时不涵养,无事不省察”的说法,提出涵养省察无分先后,未发要涵养省察,已发也要涵养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强调省察对慎独的作用,强调慎独对持敬无间断的意义,同时对陆子静言“涵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的说法提出批评,以平日涵养省察作为对涵养与省察无分先后的定说。
(二)涵养与致知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已拈出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作为为学的基本工夫架构。在“中和新说”时期,涵养与致知不是朱子考察涵养工夫地位的核心内容,但是都是为了落实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强调持敬是为学与成德的根本工夫,是为了补今人小学阶段欠缺的涵养工夫。①朱子提出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强调持敬贯彻穷理终始,提出持敬以诚意正心即孟子的求放心,《大学》中的每一个工夫的完成都不能离开持敬为前提,由此确定了持敬与大学工夫的关系。同时,朱子提出居敬穷理互发的观点,强调居敬与穷理二者不能偏废。在此阶段,朱子与湖湘学派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也出现分歧,朱子批评胡广仲先致知后持敬的工夫思想,谨防工夫陷入支离。在此阶段朱子以专一解释主一,认为支离就是不专一,也说明朱子中年时期已将持敬解释为专一,但不是主要观点。朱子从45岁开始注意到与象山在涵养与致知关系上的区分,开始指出陆学的不足在于脱略文字、直趋本根,认为陆学的成德路径与《中庸》中的知先行后的路径不符合,批评陆学不重穷理,认为陆学是禅学。由此奠定了鹅湖之会中二人的无法言合的基调,鹅湖之辩的核心内容即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所引申出的成德路径的分歧。鹅湖之辩以后,涵养和致知的关系成为朱子言涵养工夫地位的核心问题,朱子首先提出持敬与求放心为成德的根本工夫,保证涵养为本的立场。鹅湖之辩后,朱子于49岁开始朱陆之辩持续至象山去世,朱子批评陆学不重穷理的立场都没有停止,但是朱陆之辩的过程中朱子体现出从褒贬相间,期待陆学转变至最后严厉的批评,将陆学判为乱道误人的态度变化的过程。55岁后基于浙学的问题的发现,朱子对浙中吕氏门人提出读书要以持守为本,否则会落入功利之学。中晚年后朱子对支离的问题比较重视,一方面基于对浙中学者支离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基于陆学对朱子支离的批评,朱子同时做了反省,并在晚年后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看出,朱子中晚年论证涵养与格物的关系从两个面向展开,一方面对峙陆学,向陆学及门人强调涵养不离穷理,否则沦为虚空;另一方面对峙浙学,强调读书要以涵养为本,否则会陷入支离。可见朱子言涵养与格致的关系,是双管齐下、攻守兼备的,朱子对其中一方的强调只是基于与其对话的对象不同,由此可知朱子涵养与致知关系的整体性,朱子并未落入“道问学”一边。学者葛兆光便提出:“由于后来与陆九渊等的辩论,感觉上朱熹的立场似乎逐渐偏向‘道问学’的知识主义方面,其实,应当注意,这恰是由于激烈论辩中,各自的立场不能不过度凸显而导致的印象。”①
朱子晚年提出修养工夫三四分在外、六七分在内,这说明朱子晚年仍然坚持持敬为本、穷理为助的基本立场,强调持敬与穷理不能偏废一方。在持敬为本的立场上,朱子继续批评浙学支离,还提出支离之病比陆学不重穷理更为严重。朱子晚年与象山的论辩绝笔,但朱子没有停止对陆学的批评,并且对陆学的批评更为严厉,首先对方宾王等人言“识心”之误;其次对项平父等人从气禀角度说明穷理之必要。朱子批评象山将“识心”理解为禅学的空言“识心”,提出“识心”本是识心中本具之理,即致知,所以“识心”要通过穷理工夫长期的积累。同时,朱子从气禀与穷理的关系证明穷理工夫的必要,提出持敬和求放心都不在事外,穷理是敬在事中的工夫,二者不为两节。朱子又对象山去世后陆学后人崇尚江西气象做了严厉批评并表示对道统的担忧,将陆学定为禅学,可见朱子晚年言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注重强调穷理的必要性,说明了朱子对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的坚持,最后朱子回到对陈淳、廖子晦等人言“先见天理源头”的检查上,强调工夫进路无非下学至上达。
在成德路径上,朱子晚年不仅从致知与力行的关系,还以《格物补传》中积累至贯通、《大学》中致知与诚意、《论语》中博文与约礼、《孟子》中博学与反约等一系列关系来说明成德路径的下学而上达,提出持敬、格物致知、省察等工夫都是下学工夫的内容,朱子强调要区分做工夫与工夫的境界,强调做工夫上要逐项做工夫,而贯通是做工夫后的境界,不是工夫的下手处,工夫虽然都贯通在心上做,但在心上做的工夫又各有节目、次第,不可笼统而论。所以朱子从工夫进路上与陆学也做了区分,体现出对二程的基本工夫架构的继承,但朱子强化了这两大工夫在工夫论中的地位,说明了朱子工夫思想以理性主义的修养方法为主导。对此陈来亦提出:“朱熹认为陆学的修养方法实质上只是基于一种类似禅宗顿悟的神秘体验,通过静坐澄心,以求在沉静的心理状态中获得一种突发的特别的体验,这种体验的实在性朱熹并不否认……但是他所否定的不是这种体验的实在性而是它对于道德提高的可靠性。朱熹指出,如果以为一旦获得某种体验之后,便以为从此本心发明,一切行动思虑都是本心发见,这正是陆门弟子狂妄颠倒的真正根由。朱熹对陆学夸大主体的伦理本能及以静坐反观修养方法的批评,应当承认比较近乎道德生活的实际情况。”①
四 朱子涵养工夫的思想特色
(一)与湖湘学派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主要集中与湖湘学派在心性论和工夫上的论辩,至朱子45岁时结束。朱子以心统性情作为心性论基础,以心贯通未发已发,强调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的重要性,湖湘学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涵养落实在已发后,朱子认为湖湘学派缺少了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没有涵养心之全体,只是涵养心之一端,显得急迫。在《仁说》阶段,朱子与南轩辨析性情关系,批评南轩“以万物一体为仁”“以公言仁”,批评胡广仲“以知觉训仁”,认为都是不辨心性、性情和已发未发的表现。在工夫次序上,湖湘学派主张先察识后涵养,认为察识重于涵养,朱子则强调涵养工夫要落实于未发之前,所以涵养要先于察识、重于察识的基本观点。基于与湖湘学派的论辩,未发前涵养工夫、涵养和察识的关系成为朱子46岁前关注的核心问题。以45岁时的《观心说》为标志,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基本完成,也标志朱子心性论和基本工夫架构的确立。此后朱子开始对二程及门人做内部的检查,并转向对陆学的注意。正是因为朱子46岁前确立的涵养工夫和48岁时确立以《大学》为工夫规模,朱子在中晚年以后的涵养工夫思想才有了同时对辩陆学和浙学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并且,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实际上给湖湘学者思想的转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湖湘学派部分学者已经接受了朱子涵养要在未发之前的观点。朱子晚年后基于对诚意工夫的重视,省察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朱子提出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的观点,可以说是朱子晚年对湖湘学派重视省察的观点的重新采纳。另外,受到胡宏的启发,朱子晚年提出“居敬以持其志”的观点是对主敬涵养的重要补充,但朱子也对五峰言立志居敬的观点做了检查,朱子提出五峰重视立志与居敬,忽视其间一大段的格物穷理工夫,将工夫都说成向内而没有向外,所以工夫格局不够广大,气象显得急迫。
(二)与二程及门人
从心性论上看,朱子在《仁说》阶段批评龟山“万物一体为仁”,又批评谢上蔡“以知觉训仁”,说明朱子对性情之辨的强调,体现出对程颢门人心学倾向的警惕。对此陈来认为:“批评以万物一体为仁使人脱离了人的本性及其现实表现,而使仁学失去其内在意义。朱子又批评谢上蔡‘知觉言仁’可能导致认欲为理而忽略了仁学的规范意义。这两点可以说都是针对大程子以下的心学传统而言。”①朱子晚年对上蔡“以知觉为仁”的问题重新进行了讨论主要针对陆学而发,朱子发现陆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以知觉为仁,则工夫会落入禅学。对于未发已发的思想,朱子晚年多次强调不能固守程门以未发为“耳无闻、目无见”,认为应当从子思、孟子的观点中去体会未发已发,遵从《中庸》主旨,并且朱子晚年还指出伊川言“凡言心者,皆指已发”是不恰当的,说明了朱子晚年对程门心性思想的检查。朱子最终改变中年时期以应事接物作为未发已发的标准,以《遗书》中“才思即是已发”作为未发已发的标准,也说明了朱子对二程思想理解的成熟与深化。
从工夫上看,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确立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以持敬为成德工夫的第一义,认为持敬可以对治气质和私欲,体现出对伊川“敬则无己可克”的遵从,《仁说》之后朱子对伊川的观点做出检查,立场上遵从“敬则无己可克”的思想,但同时提出克己复礼的工夫作为持敬工夫的必要补充,到中晚时期提出“克己在持敬之上”,体现出对克己复礼思想的进一步重视,但本质上仍是以敬言克己,晚年后朱子才有了突破。朱子晚年提出“克己在持敬之上”是工夫后的境界,持敬与克己两个工夫都各有优点,持敬平实,克己复礼快速,二者要逐项做工夫,最后比较平稳地处理了持敬和克己的关系,体现出晚年工夫思想的严密,说明朱子对伊川“敬则无己可克”的修正。朱子晚年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中体现出对心学倾向的警惕,朱子晚年强调不以“复理”解释复礼,即反对二程和大程门人以“复理”解释复礼,因为说复礼则克己工夫有落脚的地方,所以朱子提出克己的内容是复礼,克己要在复礼上完成,如果只说“复理”,则克己工夫悬空。朱子批评谢上蔡以我视、听、言、动的克己工夫没有以礼作为规矩准绳,批评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将工夫说得太快。朱子又批判佛老克己以后不言复礼,从而将克己工夫沦为空寂,最后引申到对陆学的批评,体现了朱子重视外在的伦理规范准则和理性主义精神。除此之外,朱子与二程在持敬与诚的关系上的理解也有不同,朱子中年时期提出“敬可为诚之之一事,不可专以敬为诚之之道”,也是对明道所言“诚敬一事”的说法进行补充和说明,中晚年时期将诚的工夫落到诚意上说,诚的工夫有了实际的工夫对象和独立的工夫地位,晚年时期提出诚与敬要逐项做工夫,说明朱子晚年对诚的工夫更加重视,体现了朱子对二程工夫思想的修正以及晚年工夫思想的严密。
(三)与象山及陆学门人
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是朱陆论辩的主题,朱子45岁时始言陆学不足,在46岁鹅湖之辩与陆学公开分歧,49岁开始集中批评陆学,至陆象山去世后十多年时间也没有停止与陆学的论辩。朱陆之辩中朱子的态度出现了一个变化的过程,55岁前朱子对陆学的批评还是比较客气委婉的,并且褒贬相间,期待陆学能转向,与陆学反复商讨,希望二人都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不要偏废一边。从55岁开始对陆学展开严厉批判,直言陆学“高”“大”“颠”“狂”“异”,对象山的批评不留情面;57岁时朱子见两家已经陷入竞辩之端于是提出调停;58岁后对陆学全面否定,直指陆学乱道误人;至63岁象山去世后,朱子仍没有停止对陆学不重穷理的批评,朱子批评陆学言识心之弊,不知以穷理的积累去实现“识心”,从气禀与穷理的角度证明穷理的必要,批评陆学不知气禀之杂,对江西气象贻害后学的情况十分担心。直至朱子晚年判陆学为禅,体现出与45岁时批评象山“有禅的意思”一以贯之,但程度有加深。由此可见,从朱陆之辩的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朱陆学问始终不相契,所以可知历史上对朱子做出“朱陆晚同”或者“朱陆早同”的判断不符合朱陆之辩的学术史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朱陆二人在涵养工夫上的分歧还体现在二人采用了不同的涵养工夫方法。朱子涵养工夫的主要方法是涵养须用敬,主敬涵养是朱子言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而象山反对持敬工夫,认为持敬是二程杜撰的,缺乏圣贤之学的依据。陆学认为涵养即孟子的求放心,发明本心,二者在学术脉络上体现为以孔门为宗和以孟子为宗的分歧。除此之外,朱子与象山在对主静、诚、立志、克己复礼等工夫的理解上也存在分歧,体现出朱陆涵养工夫内在系统的不一致性。在对主静的理解上,朱子反对以主静持敬,反对以静求静的工夫思想,批评佛家以静坐为坐禅,其实也在批评陆学。在对“克己复礼”的理解中,朱子晚年以礼为“克己复礼”的规矩准绳,强调克己的内容是复礼,克己在复礼上完成,反对只言克己不言复礼,认为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是将克己说得太高,反对禅学只言克己,复礼工夫都落空,可以看出朱子也是依此批评陆学的。在对诚理解上,朱子合说诚敬,以诚敬为涵养,并区分出诚与敬的工夫内容的不同,认为持敬与诚意要逐处做工夫。但是象山反对合说诚敬,主要是反对持敬,朱子以实解释诚,象山以诚为诚体,将诚的工夫理解为存诚。在对立志的理解上,朱子言持敬与立志是相互配合、表里粗细的关系,批评象山以圣人为志,立论很高,但轻视下学阶段的工夫,最后结果导致空有议论。如此说明,朱陆不仅在对涵养与穷理关系的理解上不相契,对涵养工夫本身的理解,以及涵养工夫建构及地位也可以说无法契合。需要指出的是,朱陆涵养工夫终不能相契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心性论的不同,朱子晚年十分重视气禀对心、性的影响,并注意到陆学不知气禀之杂,判陆学与告子的义外说无异,最终落入禅学。朱子认为禅学是心理为二,儒学是心理为一,但是陆学虽言心与理一,却没有体察到气禀和私欲对人心的影响,与禅学的问题一样。正是基于对气禀和私欲的影响的重视,朱子晚年更加认识到成德的艰难,强调下学阶段工夫的积累最后上达至贯通的境界,体现出朱陆在成德路径上的区别。朱子与陆学分歧不在于某一工夫上的理解不同,而是由心性论的不同以至于成德工夫路径上的分道扬镳,由此可知,历史上为了证明陆学、心学与朱学不相异而提出的朱陆晚年为同的观点不符合朱子本身的学术立场。
(四)与浙中吕氏及门人
朱子与浙中学者的学术交流很早就已开始,在吕祖谦去世前,朱子为了对峙陆学有意与吕祖谦达成一致战线,故朱子言陆学之失大多是在与吕祖谦、吕子约等浙中学者的论学中阐发的。吕祖谦去世后,陈亮入狱,朱子开始注意到浙学欠缺涵养工夫导致支离、功利的问题。朱子从55岁开始在对峙陆学的同时对峙浙学,与吕氏门人的对话主要围绕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展开。朱子认为吕氏门人穷理不以持敬涵养为本导致支离和事功,强调要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建议浙中学者读书要先读书“四书”等圣贤之书,立下为学主旨。对于浙学欠缺持敬工夫的情况,朱子晚年的批评更加严厉,并且朱子认为在陆学不重穷理和浙中学者不重涵养之间,不重持敬涵养的问题更加严重。朱子对浙学的批评从55岁后持续至朱子晚年,这个过程也是朱子论辩陆学及门人的过程,说明了朱子在阐述涵养与致知的工夫关系上同时对峙陆学和浙学的完整立场,没有偏向一方。
五 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检查
由“绪论”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理解以及朱陆异同的理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经全文分析可知,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包括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中以朱子晚年涵养工夫弥合朱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阳明曾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提出:“知其晚岁故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①阳明否定《集注》《或问》和《语类》判定朱子晚年思想的有效性,认为《集注》《或问》是朱子48岁时所作的,而《语类》是门人附会己见,故而特地摘录《文集》中属于“朱子晚年”的书信为据。阳明全书共摘录朱子34封书信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1195年吕子约回复朱子的一封书信,结合陈来先生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此34封书信做考证归纳可知:《朱子晚年定论》中朱子48岁之前的书信有8篇,48—59岁的书信有18篇,60岁以后的书信仅5篇。如此可见,阳明所引书信约四分之一是在朱子48岁前,属于阳明所认为的朱子中年未定时期。从本书对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来看,《朱子晚年定论》中真正属于朱子晚年思想阶段的才5篇。从内容上看,阳明对朱子书信的摘录有断章取义之嫌,由此可知《朱子晚年定论》的依据有偏失,有失客观,这与此前学界对《朱子晚年定论》的客观性判定相符合。陈荣捷后来总结前人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主要有四点:“一为其误以中年之书为晚年所缮;二为其以《集注》《或问》为中年未定之说;三为其断章取义,只取其厌烦就约之语与己见符合者;四为其误解‘定本’,且改为‘旧本’。”①陈来也认为:“王阳明之《晚年定论》不顾材料为证,徒据臆想,以‘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即使《晚年定论》所收皆朱子60岁后书,也不能证明阳明之说,盖朱学本身包含有尊德性的内容,且在朱子晚年书信中取三十通此类者并非难事,然亦不济事也。后李绂即如此。然而,批评《晚年定论》的《通辨》其考证也并非精详可称,材料也远不充分。”②虽然亦有学者为阳明辩护,认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虽然史料有问题,但义理没有问题,如刘述先便说:“从考据的观点看,阳明编纂《朱子晚年定论》可谓一无是处。”③他提出:“阳明的‘定论’不是以时间为标准,是以义理为标准。”④刘述先为阳明之误开脱,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阳明摘录朱子书信的内容,皆是朱子言涵养、求放心、持敬、存心重要的部分,想要证明朱子晚年的转向。但经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言涵养为本,强调求放心的重要依然是延续“中和新说”以来的基本立场,涵养为本、求放心思想并不是至晚年才提出的,反而是在“新说”时就已经提出的基本观点,作为朱子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涵养为本的立场从“新说”后至晚年都没有改变,并不是阳明所说的“晚岁大悟中年之非”之旨。朱子并没有因言涵养而轻穷理或者省察,并且朱子对陆学不重穷理的批评从朱子中晚年延续至晚年。从工夫路径上说,朱子晚年后特别强调成德的“下学而上达”的路径,这都是朱子重“道问学”的体现,朱子言涵养与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总是强调不能偏废一方。
对于《朱子晚年定论》中对朱子静坐的判定,阳明引朱子37岁、40岁、55岁、57岁时的四封书信中言静坐与静的内容,并对朱子做了肯定。从时间上看,根据本书对朱子晚年阶段的划分,四封书信都不属于朱子晚年的观点。即便是王门心学后人李绂对朱子所划分的晚年(51岁后),也只有两篇属于朱子晚年,即便四篇都属于朱子晚年,其中论说也不能作为朱子晚年言静坐工夫的定论。这是因为静坐工夫不是朱子晚年时期才提出的,朱子晚年时仍没有完全否定静坐工夫的意义,所以不能说朱子改变中年之说而为晚年定论。更重要的是,阳明没有认识到静坐工夫在朱子涵养工夫中的地位以及脉络的变化,朱子晚年虽然肯定静坐工夫,肯定其有助于涵养本原,但朱子却以敬消解静坐,“敬之外别无静的工夫”是朱子晚年对静的工夫的最终判断,静坐工夫本身在朱子工夫思想里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对此阳明竟毫无察觉。由此可知,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所以无法成为定论,关键在于没有对朱子涵养工夫做全面的考察,没有将涵养工夫放在朱子工夫系统中去观察,而只关注朱子言涵养本身,这是为学方法上的缺失,故无法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地位有全面的判定,更无法对朱陆涵养的异同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六 对中国港台新儒家对朱子判定的检查
(一)对“朱子的心为认知义”的检查
牟宗三对朱子心与理的关系的判定决定了其对朱子道德形态的判断,他认为朱子的心与理的关系是“心具众理”而不是“心即理”,心为“气心”,理外具于心,所以涵养工夫只能涵养不动之“性体”,而不是涵养本心,本心没有自发、自生的力量,故涵养工夫无法成为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朱子确实有以“气之灵”释心,其目的在于为“心能知觉”寻找形质上的根据,因为心为气之灵,所以心为灵明知觉,此气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朱子认为心有形体,理无形体,心又是形体中的灵的部分,所以能为无形之理提供着落处。所以,“气之灵”之气为“形器义”,而不是具有善恶的“气质义”。以此为基础,牟宗三认为在朱子心与理的关系中心只有认知的功能,从功能义上认识朱子的心与理的关系,符合朱子以气言心的说法,但朱子“心之能”的前提在于“理具于心”的结构,如果只从认知义上言心,直接从心之用开始认识朱子心与理的关系,显然缺失了心与理关系的结构义这一前提。牟宗三将朱子的“心具众理”诠释为心认知地具理,将“心具众理”从存有层面的“本具”曲解为工夫层面的“认知地具”,显然与朱子思想本义不符。①
所以,从工夫层面上看,穷理的前提是“心具众理”,穷理需要以持敬涵养为前提,由此说明了朱子的道德形态并非他律。在朱子这里,心不能免除气禀的影响,虽然每个人都“心具众理”,但必须要去做穷理致知的工夫,道德知识的学习是成德必须经历的路径,所以朱子提出下学而上达、博文而约礼、知至而意诚、致知而力行,都是对成德路径的证明,但是都没有动摇涵养工夫为成德根本的地位。穷理是穷“本具之理”,穷理始终都在持敬的关照下进行。下学到上达中有“豁然贯通”的时候,其中有本心力量的呈现,是道德天赋能力的展现,而不全部依靠习惯和经验的积累。对此陈来认为朱子“心具众理”是存有层面的心与理的关系,理潜存于心,“人所先天固有的不是一切知识,而是某些道德的良知(及生理本能)……虽然每个人心具众理,但这些理并未全部反映为人的良知,或者说人的良知并没有把心中所具的众理全部反映出来。……为了使人认识到心中本具众理,并达到心与理的彻底自觉,必须经过格物穷理的认识过程。……只是这些原则是常常是潜在的,在经过格物穷理之后才能成为人的现实意识的真正原则”①。所以,“心具众理”是本具和内具、自具的结合,说明了心的能动和自觉的能力,也说明朱子的涵养和穷理主要依靠自觉、自律的工夫完成。此外,陈来也指出了陆学的“心即理”这个命题本身不是朱子所反对的,朱子反对的是二人对工夫路径和方法的认识。陈来说:“心即理并不是主张人的一切意识活动无条件地合于理义要求。陆学所谓心即是理,在直接意义上是指本心即理。此外亦指人发明本心之后意识活动自然合理。陆学的这个思想朱熹并非不了解。”②
(二)对“朱子涵养工夫为小学工夫”的检查
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是通过对外在的规范的遵守而养成好的习惯,如此涵养工夫就是外在的、经验的道德实践,而不是自觉、自律的道德实践,由此判朱子为道德他律。首先,朱子涵养本原的地位在《知言疑义》中就已提出,在《仁说》中确立,《仁说》中朱子将仁解释为仁体、性体,涵养本原是涵养性之全体,但此性之全体本具于心,所以朱子的涵养工夫是涵养性,也是涵养本心,并且本心的主宰地位在《仁说》之后随着“心具众理”“心主性情”等命题的提出就已经确立本心的主宰地位。中年时期所确立的持敬的工夫是操存涵养、整顿身心,中晚年时期朱子还以求放心解释持敬,晚年以“精神专一”解释持敬,无论持敬为哪一种解释,心的主宰地位是前提,而本心的操习并不只是对外在规范的遵守而养成的习惯,本心居积极主动的地位。其次,从克己与复礼的关系上看,朱子晚年时期重视以复礼作为克己的规矩准绳,认为克己要落实在复礼上完成,体现出朱子对外在规范的重视。但是,从工夫的过程来说须通过克己来完成复礼,所以内心的自觉和道德主体的地位是首先确立的,这也是克己复礼没有超出主敬地位的原因。朱子将持敬作为自得于心的工夫,如果自得于心则也不必做克己工夫,朱子还提出持敬是克己的立脚处,说明主敬的地位没有改变,朱子的涵养并不主要依靠克己复礼完成,说明了通过外部规范的制约不是首选的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自律是成德工夫的第一义。
最后,从涵养与其他工夫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涵养工夫是成德的根本工夫,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牟先生认为朱子的涵养是被致知吞没的涵养,是在“道问学”中的“尊德性”,即“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而完成的,如此“尊德性”就成为经验的、外在的“尊德性”。经前文分析可知,“下学而上达”说明了朱子对成德次序的认识,“尊德性”必须有“道问学”的工夫,但并不是说“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完成的,这是对朱子的误解。朱子晚年并没有改变涵养为致知的根本工夫的地位,持敬是穷理的前提。朱子晚年也并没有以致知言诚意,而是提出知至后的诚意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工夫意义和工夫内容,省察和慎独都是完成意诚的工夫。致知是诚意的主要工夫,但知至不等于意诚,诚意有自己的工夫,所以诚意并不是如牟宗三所说的外在的诚、认知地诚,诚意是通过省察和慎独等自觉的道德实践完成的。由此可见,朱子的涵养工夫也不是经验的、外在的,有学者提出:“朱子探讨道德发生的问题虽然仍遵循孟子的性善论,认为道德有其先验的存在性与超越的内在性,一切道德的观念或行为是以人类至善天性作为根源依据的,而且再次绝对至善的根源为大前提下,每个人对于道德的认知或判断,终究是以个人的自觉自律为依据。”①虽然朱子认为道德认知在成德中有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作用,道德的养成和完善主要是通过自律来完成和实现的。
(三)对“朱子知行不一”的检查
中年时期朱子确立了基本的知先行重的知行观,至晚年时发展成为对成德路径的全面论述。首先,朱子同时从两个方面对致知和践履的关系做出阐释:一方面,致知是大学工夫的下手处,但是要补涵养于未发一段的工夫,说明了持敬是穷理、致知之本,穷理没有超出持敬涵养的道德义,说明知的目的最终是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另一方面朱子提出致知而后力行说明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大学》的工夫规模体现了知先行后的入德次序。朱子以知至而后意诚说明了知先行后,以真知必能行说明了知行合一的意诚的境界,最终以意诚为行之始,将成德的标准落到行上说,说明了朱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
其次,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看,朱子晚年提出“无时不涵养省察”“未发已发都要省察”的观点,说明朱子注重省察对涵养工夫的补充,省察是完成诚意和慎独阶段的重要工夫,这也说明朱子晚年重视对自觉的道德实践的落实。
最后,朱子的涵养工夫并不只是精神意识上的活动,虽然朱子晚年将持敬诠释为“精神专一”,但并没有取消持敬为整顿身心的解释,涵养本身就是身心合一的道德实践。朱子涵养工夫的特点是以持敬贯彻所有工夫始终,强调平日涵养无间断、事中涵养等观点其实都体现了朱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从具体的涵养工夫来说,朱子中晚年开始重视诚与敬的分辨,提出不能以敬代诚,将诚落在诚意工夫上解释,诚意主要是为了解决知行不一的自欺的问题,可以看出朱子晚年重视道德实践的落实。朱子中晚年开始对主静保持警惕的态度,以持敬限制静坐,提出无事时且静坐、不能专于静坐的观点,说明了朱子重视“事中涵养”而非“静中涵养”,这也说明朱子重行而非重知。朱子晚年对立志工夫也有进一步重视,这是基于在志与意的分析中发现志具备意所没有的特点和功能,所以需要拈出立志工夫来补充居敬,朱子的目的也是解决道德实践动力不足的问题。可见,朱子对涵养工夫的修正和完善真正是其知行合一思想的体现。
(四)对“以朱子成德路径判朱子为他律”的检查
对于朱子晚年不仅从知行关系还从《格物补传》中的积累至贯通、《大学》中的知至而后诚意、《论语》中的博文约礼、《孟子》中的博学而反约来贯通《论语》中下学而上达的思想,从“四书”工夫思想贯通的角度对朱子晚年的成德路径做了阐发,可见朱子晚年对成德艰难的认识,鼓励人做工夫要勇猛精进。同时朱子批评陆学上达而下学,也批评了陈淳“先见天理源头”,二者都是不够重视穷理的体现。对于朱子晚年对成德路径的集中阐发,牟宗三提出这是朱子注重工夫的深度和广度的表现,他说:“安卿病处,依朱子所见,单在只吃馒头尖,广度深度工夫俱不作,只想凭空理会那源头处,空守著那个荡漾如水银的天理而不放,故朱子反覆告诫之也。并非不可说源头处,亦非定不许‘先见天理源头’也。即是朱子晚年甚至历来不喜‘先见天理源头’之见,重在平说平磨,亦只怕人两脚踏空,先只空见个‘天理源头’有何益?故其虽遮拨之,然一至正面叮咛反覆,却只重在深度广度平磨将去。此其重点知在工夫之踏实与充实,并非客观义理上定不许‘先见天理源头’也。此见前训潘时举言为学两进路便可知。”①在此牟宗三指出朱子晚年不喜“先见天理本原”并不是对持敬涵养的否定,而是肯定朱子晚年重视工夫的深度和广度,广度上重视涵养与致知的平衡,怕门人两脚踏空,只守个天理本原。深度上强调格物穷理致知等下学工夫的积累,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并且,朱子重视下学工夫是强调工夫的踏实与充实,牟先生以深度和广度的“平磨”来说明朱子晚年对下学工夫的重视。牟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朱子也说“见天理源头”,但是与象山不同,同时他做出了优劣判定,他说:“并非一说‘先见天理源头’便是象山学也。在朱子之义理系统中亦可说‘先见天理源头’(先理会太极大本),然在此系统中不如在五峰、象山学中先识本心仁体为切要,故朱子得以重视平磨以遮拨之也。”①牟宗三认为朱子也言“先见天理源头”,即先理会大本所在,也就是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也就是涵养本原,但是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本原没有在五峰和象山言“先识仁体本心”这么重要,所以朱子重视穷理致知作为下学工夫的积累。
由此可以看出,牟宗三认为工夫的“平磨”即通过穷理致知的下学工夫的积累至上达不是最优的道德修养方法,是通过练习、模仿达到的道德的规范,所以是他律的、外在的。相比之下五峰、象山的先识本心仁体是最优的方法,因为本心主宰、本心自觉,道德形态也是自律的。牟先生依此创造出朱子是横贯系统和象山是纵贯系统来说明象山的道德形态是自律,朱子的道德形态是他律,最终以象山为优,朱子为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作为成德的路径的说明,意诚之前的穷理、致知、省察、慎独、“克己复礼”等下学工夫的积累过程需要练习、模仿和外在规范的学习,但是下学至上达存在积累至贯通的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贯通的阶段并不是完全依靠练习和模仿实现的,朱子指出其中有融会贯通觉悟处,二程言其中有类推的方法,还有其他不可言说的体验处,这都说明朱子的成德路径不是通过他律实现的。并且需要指出的是朱子以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在致知之前,持敬涵养的根本地位已经确立了其成德的主要方法不是依靠他律而是依靠自觉本心为善的前提。最后,作为穷理、致知、省察、克己复礼等下学工夫本身,也不是属于依靠练习、模仿完成的工夫,穷理是穷心中本具之理,致知是致本心之虚灵明觉,省察是解决自欺的行为,是对不知不觉的私意的检查,也是慎独的工夫,是需要通过本心的主宰,通过本心的自我认识和行动的自我约束来实现,所以可知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作为成德的基本路径,并不影响朱子的涵养工夫是自律自觉的工夫。
朱子涵养工夫的确立是经由对“中和旧说”的反思,最后在“中和新说”中完成的。1168年朱子39岁在《已发未发说》中初步对已发未发的做了界定。次年,在对《已发未发说》修改的基础上,朱子又作《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对未发已发的阐述进一步明晰,由此朱子以未发已发分辨性情的思路基本形成,在未发和未发之中的区别中说明了未发之中的重要,从而为未发前涵养工夫的落实提供了心性论的基础。朱子对心性论的建构首先从未发已发的区分中开始主要是基于对辩湖湘学派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进路,所以将涵养工夫落实于未发之前是“新说”时期朱子的主要任务,对此陈来也指出:“己丑之悟的重点还是在确立未发时心的涵养工夫。”①1169年朱子在《答张钦夫》中进一步明确未发已发的思想,提出“心贯性情”的说法,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和心、性、情三分的基本心性架构,标志朱子“中和新说”理论的正式确立,也为涵养贯通未发已发、彻上彻下、存养先于察识等工夫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心性论基础。学界对“己丑之悟”有很高的评价,陈来说:“己丑之悟才从根本上确立了朱熹的学术面貌。”①究其原因,即因为朱子在“己丑之悟”中完成了心性论的基本建构的同时工夫论的基本架构也确立起来。
在“新说”的基础上,朱子于1171年作《尽心说》《胡子知言疑义》,次年在与胡伯逢、胡广仲等湖湘学者的通信中提出性具于心、心具理、心主性情等观点,确立了心的主宰地位,对胡宏的心性观点做进一步辨析。朱子在性情之辨中确立了性善论的地位,论证了涵养工夫的重要和克己复礼工夫的必要,又以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对恶的产生进行了说明,提出尽心须假存养的观点,为涵养与致知关系的确立提供了心性论上的基础,又进一步向湖湘学者阐明涵养的地位重于察识。1172年至1174年朱子围绕《仁说》与张栻、胡伯逢展开讨论,进一步对心、性、情做出分辨,以“仁性爱情”确立了仁体、心体的地位,为克己复礼工夫的地位提供了心性论上的证明,将克己复礼工夫纳入涵养的范围之内。此后在《观心说》中朱子再一次明确一心为主宰的地位,也说明了操存是操存一心而不是以心观心,标志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结束。由此可见朱子于46岁前已完成心性论的基本建构,也标志朱子思想体系和学术规模的基本确立。②此后,朱子在《集注》中对“心具众理”命题做了完整阐释,确立了心与理关系的基本命题,由此说明了心具众理与穷理的关系。朱子又以尽心和存心的关系说明涵养与穷理的关系,以尽心为知至,以知至为贯通的阶段,诚意没有独立的工夫内容。在《集注》时期提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考虑到气禀对性、才的影响,开始注重穷理工夫,是《仁说》中心性论进一步完善的体现。在此阶段,朱子体现出“四书”互证的方法,为“四书”工夫的贯通做了准备,代表朱子思想体系的成熟。
50岁后朱子提出要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提出涵养本原、求放心是第一义等观点,说明朱子的工夫思想从《论语》贯通至《孟子》。中晚时期朱子延续“中和新说”确立的涵养须用敬、涵养无间断、敬为彻上彻下等基本观点,说明“中和新说”后朱子保持涵养工夫的基本观点。朱子晚年对中年时期所提出的“心主性情”“心具众理”等命题做进一步阐释,对“心如谷种”“心具众理”“心统性情”等心性论命题做一步诠释,对心、性、情、意、志、欲、才等心性概念做了进一步辨析,代表晚年对心性论的进一步完善。朱子晚年进一步重视意、志、欲的作用,为落实诚意、立志、克己复礼的工夫做了心性论上的说明。朱子晚年重视气禀对心性结构的影响,围绕生之谓性、本然之性、气质之性、气强理弱等命题进一步深化对中年时期的天命之性和气禀之性的关系的认识,提出气质之性是天命之性堕在气质后形成的,气质之性不改变天命之性,可见朱子晚年并没有改变中年时期所确立的性善论的基础,故对涵养本原、持敬为本、一心为主宰等基本涵养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朱子晚年注意到气禀对人成德的影响,认识到成德的艰难和修养工夫的重要,所以比较注重强调格物穷理、致知省察等下学工夫的必要性,注重省察对涵养的帮助,批评识心、先见天理本原等不下学只要上达的工夫思想,在持敬为本的基础上落实了克己复礼、诚意、立志等工夫对持敬的补充,体现了朱子知先行后、积累至贯通、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也说明朱子晚年工夫思想随着心性论的进一步完善而更加严密。
二 涵养工夫的确立、修正与完善的过程
“中和新说”时期朱子提出涵养须用敬、涵养要贯彻动静、涵养无间断、敬为彻上彻下等观点确立了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但是牟宗三因此认为:“朱子中和新说后,持守、居敬、主静工夫定论”①,以“新说”为定论实在言之过早,“中和新说”时期朱子对涵养工夫的建构并不完整,这一时期更多的是确立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以持敬为重,认为涵养本原可以变化气质,“中和新说”后朱子在《仁说》《尽心说》《集注》等阶段将克己复礼纳入涵养工夫的范畴,后提出尽心须假存养,落实了存养与穷理的关系。50岁后朱子虽然不再致力于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但从朱子在50岁后对涵养工夫的论说中可知其“道理只争丝发之间”的精神。《集注》后提出持敬即求放心、求放心与克己为一事,体现《集注》后对“四书”工夫的贯通,但是朱子强调就切实处做工夫,说明朱子工夫思想以《论语》为宗。朱子晚年后仍坚持涵养本原的观点,重视气禀的影响,以此说明了涵养工夫的重要性,但对持敬的理解发生了变化,“中和新说”时朱子以主一、直内解释持敬,但在晚年后朱子偏向从“精神专一”上解释敬的工夫,体现出朱子对持敬理解的重大变化。另外,对于其他涵养工夫的解释以及涵养工夫之间的关系,朱子在中年后至晚年仍不断进行修正、补充与完善,在主敬涵养的基础上,以静坐、诚意、克己复礼、立志作为持敬的重要补充,说明朱子晚年涵养工夫严密的特点。
(一)持敬与主静
“中和新说”时期朱子以动静区分未发已发,强调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提出持敬以静为本的主静涵养的观点,45岁后朱子开始认识到与陆学的区别,中晚年后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成为朱陆之辩的核心,基于对陆学轻视穷理工夫的批评,朱子50岁后慎言主静,将静限制为工夫后的境界,强调不能离敬言静,又以持敬消解静坐。朱子认为儒释静坐工夫的区别在于有没有以持敬为主,朱子批评子静不读书、不求义理、静坐澄心,本质上是告子的义外说。晚年后朱子仍然坚持不以主静言敬的立场,避免从工夫上言静的工夫,以静为工夫后的境界,否定以静求静的工夫思想,并提出“主一兼动静而言”,取消了言主静的意义。朱子晚年后肯定静坐工夫对于收敛身心的意义,但将静坐限定于无事的状态,将静坐限制于持敬的统摄,实际上消解了静坐的意义,说明了朱子主敬涵养的基本立场。
(二)持敬与克己
朱子45岁时与湖湘学派的论辩已经基本完成,朱子开始反思自己在与湖湘学派论辩的过程中因强调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而将持敬抬得过高。随着《仁说》中确立了仁体的地位,克己复礼工夫受到重视,敬与克己的关系就成为朱子关注的重要问题,成为朱子对涵养工夫之间关系的第一次检查。《仁说》前朱子主要遵从伊川的“敬则无己可克”的观点,提出“持敬则无须克己”“克己就是持敬”,直接以持敬作为为仁的工夫。《仁说》后朱子认识到克己复礼是为仁的重要工夫,将克己与持敬并举,并提出“克己在持敬之上”,认为克己复礼是孔门传授心法切要之言,提高了克己复礼的地位,但是朱子同时提出克己复礼是颜回的方法,对资质要求很高,建议以持敬为涵养的主要工夫,工夫比较平实容易,说明了中年时期持敬仍是第一义的工夫。朱子提出“克己持敬并举”是反思伊川“敬则无己可克”的开始。中晚年时期,朱子避免多言“克己在持敬之上”,提出“敬是立脚处”“敬与克己须俱到”的观点,一方面仍以敬解释克己工夫,因为持敬工夫平实,克己工夫对资质要求太高,认为伊川“敬则无己可克”虽然省事,但此事甚大、甚难,体现出朱子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另一方面,朱子对持敬与克己工夫内容做了区分,提出二者须俱到,说明了朱子在保持主敬涵养的立场上,为克己工夫提供了独立的工夫意义。
进入晚年后,朱子对克己复礼的诠释做了修正,改变了中年时期以“克己复理”诠释“克己复礼”的观点,提出不能以“复理”诠释复礼,将工夫重点落在复礼上完成。朱子提出克己复礼在克己与复礼上都要做工夫,但不是两件事,克己的内容是复礼,礼是克己与复礼的规矩准绳,克己在复礼上完成。朱子晚年一方面以克己复礼作为下学的工夫,将为仁作为上达的工夫,只有先克己复礼才能实现为仁,这是朱子晚年对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的强调,朱子由此批判象山言克己过于直接,教人“当下便是”,也批评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是将工夫说得太快;另一方面朱子将克己工夫落实到复礼上完成,是警惕大程门人直接以“复理”解释复礼,如此则克己没有复礼作为规范,克己工夫被悬空。朱子同时依此批判佛老言克己以后不言复礼,将克己工夫沦为空寂,这是朱子晚年将克己工夫规范化的理性伦理的体现,也是朱子晚年言工夫的精密之处。基于朱子晚年对克己复礼的诠释发生了变化,朱子对敬与克己复礼关系的理解也有进一步修正,朱子继续对伊川“敬则无己可克”做反省,认为此事甚大、甚难,认为伊川将敬的工夫说得太高,强调“敬则无己可克”是工夫后的境界。朱子认为克己在持敬之上,克己是较快、较高的工夫,持敬为较缓、较平实的工夫,以乾坤二道比喻克己与持敬,认为二者各有优劣,要逐项做工夫。钱穆认为朱子言克己与持敬和致知并立为三,其看到了朱子晚年对克己复礼的重视,但是克己没有取代主敬涵养的地位,克己在涵养工夫的范围内,是对主敬的重要补充。
对于持敬与克己复礼的关系,钱穆认为持敬与克己的关系出现三次变化,他说:“伊川又言:敬则无己可克。朱子先亦引其说,稍后则谓敬之外亦须兼用克己工夫,更后乃谓克己工夫尚在主敬工夫之上。关于此,朱子思想显有三变。”①钱穆认为朱子单独提出克己工夫是在主敬涵养之后,改变了朱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两大工夫架构,变成持敬、克己与致知三足鼎立的工夫架构。从持敬与克己的关系上看,可以说持敬与克己是并立的两个工夫,但如果将克己与持敬、致知并立为三,则改变了朱子主敬涵养的立场,所以对钱穆这个判断是需要慎重对待的。综合朱子从中年时期开始至晚年对持敬与克己工夫关系的梳理可知,朱子持敬与克己工夫的关系不仅只有三变,朱子中年至中晚年时期主要认为“敬则无己可克”,以持敬解释克己,克己工夫没有下落处,但《仁说》之后也同时将克己与持敬并举,即钱穆所说的持敬之外兼用克己。至晚年时朱子确实有很多克己在持敬之上的论述,说明朱子晚年对克己工夫的重视,但朱子同时提出二者相资相成,是互相配合、内外参合的关系,并且朱子至去世前强调克己与持敬要逐项做工夫,二者各有优劣,这都说明朱子最终没有将克己置于主敬之上,也说明克己复礼没有取代主敬涵养的地位,而与持敬和致知并列为三,在涵养工夫的内部可以说克己与持敬并立,但是克己复礼没有推翻朱子涵养须用敬的基本立场,这也是朱子晚年持敬与克己的最终关系,也说明了朱子晚年工夫思想平稳和严密的特点。
(三)敬与诚
中年时期,朱子确定以“真实无妄”解释诚的工夫,常常合说诚敬,以诚敬为涵养,但重点落在敬上,诚只是形容持敬工夫的程度,没有单独的工夫意义。《集注》后朱子将“四书”中的诚的工夫贯通,将诚的工夫落到意上考察,以诚意释诚的工夫,贯通了《中庸》《孟子》中的诚与《大学》中的诚意,诚开始有了独立的工夫内容。《集注》后朱子提出诚是实、敬是畏,二者内涵不同,所以不能以敬代诚,“敬可为诚之之一事,不可专以敬为诚之之道”,由此与明道所言“诚敬一事”分道扬镳。朱子同时提出不能以诚代敬,否则持敬不能为主,工夫支离。可见诚已超出敬的限制,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工夫位置,所以朱子提出持敬与诚意要同时做工夫,诚意成为持敬的重要补充,但没有动摇主敬涵养的地位。朱子晚年同时存在合说诚敬与分说诚敬的情况,朱子仍合说诚敬为专一的工夫,但对二者进行了更为清晰的区分,以持敬为专一,以诚为一,修正了“诚在敬之上”的说法,以工夫内容区分二者,认为诚敬不分先后,应该逐项做工夫,提出二程言“诚然后敬”是从工夫境界上说,对诚敬关系的处理平稳了许多。从朱子晚年对诚敬关系的处理可以反映出朱子晚年对工夫的认识是从做工夫和工夫的境界两个层面来说的,从做工夫上说应逐项做工夫,而所谓工夫的上下、工夫的贯通则是做工夫后的境界。并且朱子在诚敬关系上与象山存在分歧,象山言“存诚”,反对持敬。
(四)持敬与立志
朱子对立志工夫的重视始于《集注》,在《集注》中朱子开始对志的概念和作用做了诠释,朱子以“心之所之”解释志,说明了志对成德的方向和动力的作用,又以“志于道”作为志的内容,提出了儒家对道德主体的责任和使命,但立志工夫还没有被单独拈出。《集注》后朱子继续注意立志工夫,提出读书人就是要立下圣人之志,认为学者不能坚持的首要原因是没有立下志向,这是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为成德路径的基础上,教人勇猛精进,坚持做工夫的体现。同时朱子分析了立志与持敬的关系,提出“信得及”为成德第一义,证明涵养本原仍是第一节的工夫,而将立志作为第二节工夫。在持敬与立志的关系上,朱子提出立志就是本心的坚守,对持守助力作用,但是提出立志要以明理为前提,在立志的基础上做工夫要勇猛精进,不能空言立志,认为象山立志太高,而不教人穷理,与象山的立志思想进行区分,也开始注意到胡宏言立志于持敬的关系。晚年时期在对心、性、情、志等进一步分辨析的基础上,朱子进一步重视立志工夫,不能只在读书上立志,提出“一切之事皆要立志”,立志是格物、致知工夫的前提,强调成德工夫要勇猛精进。并且,朱子提出立志与气禀的影响无关,强调无论气禀如何都要以尧舜为志,勇猛精进是成德的唯一途径。对持敬与立志的关系,朱子在强调立志是为学、为事之本的基础上提出要居敬以立其志,说明以持敬为主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朱子采纳五峰的观点提出敬与立志各有精粗、大细的不同,二者互为表里,内外参合,要逐项做工夫,但是同时对五峰的观点进行了检查,认为五峰过分强调居敬与立志,忽视了其中格物工夫的作用。朱子强调致知是广大的工夫,需要通过积累与贯通才能达到,强调成德的艰难以及工夫不能过于急迫,体现出对涵养与致知基本工夫架构的坚持。
综上分析可知,朱子对涵养工夫的建构和完善贯穿其一生的思想路程,并不是在“中和新说”时期就完成的,“中和新说”后持敬与克己复礼、诚意、立志、静坐等工夫的关系也不断补充和修正,最后形成以持敬为主,克己复礼、诚意、立志、静坐为补充的广大的涵养工夫系统,这也说明朱子晚年主敬的地位并没有改变,涵养作为成德第一位的工夫也没有改变。朱子从广度上补充了立志工夫,从深度上补充了诚和克己复礼两个工夫,又提升了省察、诚意的地位,强调隐微处做工夫的重要。这都是基于朱子晚年认识到成德的艰难,也与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相互印证。朱子对涵养工夫的修正和补充是朱子思想不断完善的体现,也是朱子工夫思想严密性的体现。
三 涵养工夫的地位
(一)涵养与省察
朱子46岁前对涵养工夫地位的认识主要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进行考察,“旧说”时期朱子以心为已发,认为在已发之际的察识可以体验未发前的大本。“新说”后朱子以心贯通未发已发,涵养工夫落实于未发之前,提出涵养先于察识、涵养重于察识的观点,与张栻为代表的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做出区分,体现出“中和新说”时期对未发前涵养工夫的重视。同时,基于持敬贯通动静、彻上彻下的认识,朱子提出未发前为敬之体,即未发之中,已发后敬又行于省察之中,是随事而发,强调持敬与省察不是两节工夫。45岁后由于不再与湖湘学派论辩,同时开始认识到与陆学的分歧,涵养与省察不再是定位涵养工夫地位的唯一关系。朱子在《集注》中将慎独从戒惧中分离出来,慎独需要通过省察来完成,又以戒惧与慎独的关系说明了涵养与省察的关系,是朱子开始重视慎独、诚意的表现。《集注》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不再是定位涵养工夫地位的重点,朱子不再集中强调涵养先于察识、涵养重于察识的地位,朱子提出持敬为主,省察到私意应以持敬为主,先落实持敬工夫,因为持敬是立脚处,是成德的根据。同时提出省察对持敬无间断有辅助作用,二者互相配合,强调省察对涵养的意义。《集注》后朱子延续以戒惧和慎独来说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但进一步对此前的修正做了说明,对胡季随将戒慎和慎独混为涵养提出辨析,强调慎独工夫的独立性,说明了朱子中晚年时期对省察的重视。朱子晚年在对心、性、情的分疏更加细密的基础上对意的作用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再加上对气禀的重视,朱子晚年对诚意、省察工夫有进一步的重视。朱子将尽心的境界从知至推后至诚意,继续将诚的工夫落到诚意上说,以意诚为成德的标准,以省察为知至后诚意工夫完成的关键,成为决定能否成德的最终工夫,这都体现出朱子晚年对诚意工夫的重视。在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朱子改变了“中和新说”时期确立的“涵养先于察识”“涵养为本,省察为助”的主次关系,进一步修正了中晚年时期的“无时不涵养,无事不省察”的说法,提出涵养省察无分先后,未发要涵养省察,已发也要涵养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强调省察对慎独的作用,强调慎独对持敬无间断的意义,同时对陆子静言“涵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的说法提出批评,以平日涵养省察作为对涵养与省察无分先后的定说。
(二)涵养与致知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已拈出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作为为学的基本工夫架构。在“中和新说”时期,涵养与致知不是朱子考察涵养工夫地位的核心内容,但是都是为了落实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强调持敬是为学与成德的根本工夫,是为了补今人小学阶段欠缺的涵养工夫。①朱子提出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强调持敬贯彻穷理终始,提出持敬以诚意正心即孟子的求放心,《大学》中的每一个工夫的完成都不能离开持敬为前提,由此确定了持敬与大学工夫的关系。同时,朱子提出居敬穷理互发的观点,强调居敬与穷理二者不能偏废。在此阶段,朱子与湖湘学派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也出现分歧,朱子批评胡广仲先致知后持敬的工夫思想,谨防工夫陷入支离。在此阶段朱子以专一解释主一,认为支离就是不专一,也说明朱子中年时期已将持敬解释为专一,但不是主要观点。朱子从45岁开始注意到与象山在涵养与致知关系上的区分,开始指出陆学的不足在于脱略文字、直趋本根,认为陆学的成德路径与《中庸》中的知先行后的路径不符合,批评陆学不重穷理,认为陆学是禅学。由此奠定了鹅湖之会中二人的无法言合的基调,鹅湖之辩的核心内容即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所引申出的成德路径的分歧。鹅湖之辩以后,涵养和致知的关系成为朱子言涵养工夫地位的核心问题,朱子首先提出持敬与求放心为成德的根本工夫,保证涵养为本的立场。鹅湖之辩后,朱子于49岁开始朱陆之辩持续至象山去世,朱子批评陆学不重穷理的立场都没有停止,但是朱陆之辩的过程中朱子体现出从褒贬相间,期待陆学转变至最后严厉的批评,将陆学判为乱道误人的态度变化的过程。55岁后基于浙学的问题的发现,朱子对浙中吕氏门人提出读书要以持守为本,否则会落入功利之学。中晚年后朱子对支离的问题比较重视,一方面基于对浙中学者支离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基于陆学对朱子支离的批评,朱子同时做了反省,并在晚年后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由此看出,朱子中晚年论证涵养与格物的关系从两个面向展开,一方面对峙陆学,向陆学及门人强调涵养不离穷理,否则沦为虚空;另一方面对峙浙学,强调读书要以涵养为本,否则会陷入支离。可见朱子言涵养与格致的关系,是双管齐下、攻守兼备的,朱子对其中一方的强调只是基于与其对话的对象不同,由此可知朱子涵养与致知关系的整体性,朱子并未落入“道问学”一边。学者葛兆光便提出:“由于后来与陆九渊等的辩论,感觉上朱熹的立场似乎逐渐偏向‘道问学’的知识主义方面,其实,应当注意,这恰是由于激烈论辩中,各自的立场不能不过度凸显而导致的印象。”①
朱子晚年提出修养工夫三四分在外、六七分在内,这说明朱子晚年仍然坚持持敬为本、穷理为助的基本立场,强调持敬与穷理不能偏废一方。在持敬为本的立场上,朱子继续批评浙学支离,还提出支离之病比陆学不重穷理更为严重。朱子晚年与象山的论辩绝笔,但朱子没有停止对陆学的批评,并且对陆学的批评更为严厉,首先对方宾王等人言“识心”之误;其次对项平父等人从气禀角度说明穷理之必要。朱子批评象山将“识心”理解为禅学的空言“识心”,提出“识心”本是识心中本具之理,即致知,所以“识心”要通过穷理工夫长期的积累。同时,朱子从气禀与穷理的关系证明穷理工夫的必要,提出持敬和求放心都不在事外,穷理是敬在事中的工夫,二者不为两节。朱子又对象山去世后陆学后人崇尚江西气象做了严厉批评并表示对道统的担忧,将陆学定为禅学,可见朱子晚年言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注重强调穷理的必要性,说明了朱子对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的坚持,最后朱子回到对陈淳、廖子晦等人言“先见天理源头”的检查上,强调工夫进路无非下学至上达。
在成德路径上,朱子晚年不仅从致知与力行的关系,还以《格物补传》中积累至贯通、《大学》中致知与诚意、《论语》中博文与约礼、《孟子》中博学与反约等一系列关系来说明成德路径的下学而上达,提出持敬、格物致知、省察等工夫都是下学工夫的内容,朱子强调要区分做工夫与工夫的境界,强调做工夫上要逐项做工夫,而贯通是做工夫后的境界,不是工夫的下手处,工夫虽然都贯通在心上做,但在心上做的工夫又各有节目、次第,不可笼统而论。所以朱子从工夫进路上与陆学也做了区分,体现出对二程的基本工夫架构的继承,但朱子强化了这两大工夫在工夫论中的地位,说明了朱子工夫思想以理性主义的修养方法为主导。对此陈来亦提出:“朱熹认为陆学的修养方法实质上只是基于一种类似禅宗顿悟的神秘体验,通过静坐澄心,以求在沉静的心理状态中获得一种突发的特别的体验,这种体验的实在性朱熹并不否认……但是他所否定的不是这种体验的实在性而是它对于道德提高的可靠性。朱熹指出,如果以为一旦获得某种体验之后,便以为从此本心发明,一切行动思虑都是本心发见,这正是陆门弟子狂妄颠倒的真正根由。朱熹对陆学夸大主体的伦理本能及以静坐反观修养方法的批评,应当承认比较近乎道德生活的实际情况。”①
四 朱子涵养工夫的思想特色
(一)与湖湘学派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主要集中与湖湘学派在心性论和工夫上的论辩,至朱子45岁时结束。朱子以心统性情作为心性论基础,以心贯通未发已发,强调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的重要性,湖湘学派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涵养落实在已发后,朱子认为湖湘学派缺少了未发前涵养一段工夫,没有涵养心之全体,只是涵养心之一端,显得急迫。在《仁说》阶段,朱子与南轩辨析性情关系,批评南轩“以万物一体为仁”“以公言仁”,批评胡广仲“以知觉训仁”,认为都是不辨心性、性情和已发未发的表现。在工夫次序上,湖湘学派主张先察识后涵养,认为察识重于涵养,朱子则强调涵养工夫要落实于未发之前,所以涵养要先于察识、重于察识的基本观点。基于与湖湘学派的论辩,未发前涵养工夫、涵养和察识的关系成为朱子46岁前关注的核心问题。以45岁时的《观心说》为标志,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基本完成,也标志朱子心性论和基本工夫架构的确立。此后朱子开始对二程及门人做内部的检查,并转向对陆学的注意。正是因为朱子46岁前确立的涵养工夫和48岁时确立以《大学》为工夫规模,朱子在中晚年以后的涵养工夫思想才有了同时对辩陆学和浙学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并且,朱子与湖湘学派的论辩实际上给湖湘学者思想的转变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湖湘学派部分学者已经接受了朱子涵养要在未发之前的观点。朱子晚年后基于对诚意工夫的重视,省察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朱子提出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的观点,可以说是朱子晚年对湖湘学派重视省察的观点的重新采纳。另外,受到胡宏的启发,朱子晚年提出“居敬以持其志”的观点是对主敬涵养的重要补充,但朱子也对五峰言立志居敬的观点做了检查,朱子提出五峰重视立志与居敬,忽视其间一大段的格物穷理工夫,将工夫都说成向内而没有向外,所以工夫格局不够广大,气象显得急迫。
(二)与二程及门人
从心性论上看,朱子在《仁说》阶段批评龟山“万物一体为仁”,又批评谢上蔡“以知觉训仁”,说明朱子对性情之辨的强调,体现出对程颢门人心学倾向的警惕。对此陈来认为:“批评以万物一体为仁使人脱离了人的本性及其现实表现,而使仁学失去其内在意义。朱子又批评谢上蔡‘知觉言仁’可能导致认欲为理而忽略了仁学的规范意义。这两点可以说都是针对大程子以下的心学传统而言。”①朱子晚年对上蔡“以知觉为仁”的问题重新进行了讨论主要针对陆学而发,朱子发现陆学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以知觉为仁,则工夫会落入禅学。对于未发已发的思想,朱子晚年多次强调不能固守程门以未发为“耳无闻、目无见”,认为应当从子思、孟子的观点中去体会未发已发,遵从《中庸》主旨,并且朱子晚年还指出伊川言“凡言心者,皆指已发”是不恰当的,说明了朱子晚年对程门心性思想的检查。朱子最终改变中年时期以应事接物作为未发已发的标准,以《遗书》中“才思即是已发”作为未发已发的标准,也说明了朱子对二程思想理解的成熟与深化。
从工夫上看,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确立未发前涵养工夫的地位,以持敬为成德工夫的第一义,认为持敬可以对治气质和私欲,体现出对伊川“敬则无己可克”的遵从,《仁说》之后朱子对伊川的观点做出检查,立场上遵从“敬则无己可克”的思想,但同时提出克己复礼的工夫作为持敬工夫的必要补充,到中晚时期提出“克己在持敬之上”,体现出对克己复礼思想的进一步重视,但本质上仍是以敬言克己,晚年后朱子才有了突破。朱子晚年提出“克己在持敬之上”是工夫后的境界,持敬与克己两个工夫都各有优点,持敬平实,克己复礼快速,二者要逐项做工夫,最后比较平稳地处理了持敬和克己的关系,体现出晚年工夫思想的严密,说明朱子对伊川“敬则无己可克”的修正。朱子晚年对克己复礼的诠释中体现出对心学倾向的警惕,朱子晚年强调不以“复理”解释复礼,即反对二程和大程门人以“复理”解释复礼,因为说复礼则克己工夫有落脚的地方,所以朱子提出克己的内容是复礼,克己要在复礼上完成,如果只说“复理”,则克己工夫悬空。朱子批评谢上蔡以我视、听、言、动的克己工夫没有以礼作为规矩准绳,批评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将工夫说得太快。朱子又批判佛老克己以后不言复礼,从而将克己工夫沦为空寂,最后引申到对陆学的批评,体现了朱子重视外在的伦理规范准则和理性主义精神。除此之外,朱子与二程在持敬与诚的关系上的理解也有不同,朱子中年时期提出“敬可为诚之之一事,不可专以敬为诚之之道”,也是对明道所言“诚敬一事”的说法进行补充和说明,中晚年时期将诚的工夫落到诚意上说,诚的工夫有了实际的工夫对象和独立的工夫地位,晚年时期提出诚与敬要逐项做工夫,说明朱子晚年对诚的工夫更加重视,体现了朱子对二程工夫思想的修正以及晚年工夫思想的严密。
(三)与象山及陆学门人
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是朱陆论辩的主题,朱子45岁时始言陆学不足,在46岁鹅湖之辩与陆学公开分歧,49岁开始集中批评陆学,至陆象山去世后十多年时间也没有停止与陆学的论辩。朱陆之辩中朱子的态度出现了一个变化的过程,55岁前朱子对陆学的批评还是比较客气委婉的,并且褒贬相间,期待陆学能转向,与陆学反复商讨,希望二人都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上不要偏废一边。从55岁开始对陆学展开严厉批判,直言陆学“高”“大”“颠”“狂”“异”,对象山的批评不留情面;57岁时朱子见两家已经陷入竞辩之端于是提出调停;58岁后对陆学全面否定,直指陆学乱道误人;至63岁象山去世后,朱子仍没有停止对陆学不重穷理的批评,朱子批评陆学言识心之弊,不知以穷理的积累去实现“识心”,从气禀与穷理的角度证明穷理的必要,批评陆学不知气禀之杂,对江西气象贻害后学的情况十分担心。直至朱子晚年判陆学为禅,体现出与45岁时批评象山“有禅的意思”一以贯之,但程度有加深。由此可见,从朱陆之辩的学术史的梳理可以看出朱陆学问始终不相契,所以可知历史上对朱子做出“朱陆晚同”或者“朱陆早同”的判断不符合朱陆之辩的学术史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朱陆二人在涵养工夫上的分歧还体现在二人采用了不同的涵养工夫方法。朱子涵养工夫的主要方法是涵养须用敬,主敬涵养是朱子言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而象山反对持敬工夫,认为持敬是二程杜撰的,缺乏圣贤之学的依据。陆学认为涵养即孟子的求放心,发明本心,二者在学术脉络上体现为以孔门为宗和以孟子为宗的分歧。除此之外,朱子与象山在对主静、诚、立志、克己复礼等工夫的理解上也存在分歧,体现出朱陆涵养工夫内在系统的不一致性。在对主静的理解上,朱子反对以主静持敬,反对以静求静的工夫思想,批评佛家以静坐为坐禅,其实也在批评陆学。在对“克己复礼”的理解中,朱子晚年以礼为“克己复礼”的规矩准绳,强调克己的内容是复礼,克己在复礼上完成,反对只言克己不言复礼,认为明道言“克己自能复礼”是将克己说得太高,反对禅学只言克己,复礼工夫都落空,可以看出朱子也是依此批评陆学的。在对诚理解上,朱子合说诚敬,以诚敬为涵养,并区分出诚与敬的工夫内容的不同,认为持敬与诚意要逐处做工夫。但是象山反对合说诚敬,主要是反对持敬,朱子以实解释诚,象山以诚为诚体,将诚的工夫理解为存诚。在对立志的理解上,朱子言持敬与立志是相互配合、表里粗细的关系,批评象山以圣人为志,立论很高,但轻视下学阶段的工夫,最后结果导致空有议论。如此说明,朱陆不仅在对涵养与穷理关系的理解上不相契,对涵养工夫本身的理解,以及涵养工夫建构及地位也可以说无法契合。需要指出的是,朱陆涵养工夫终不能相契的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心性论的不同,朱子晚年十分重视气禀对心、性的影响,并注意到陆学不知气禀之杂,判陆学与告子的义外说无异,最终落入禅学。朱子认为禅学是心理为二,儒学是心理为一,但是陆学虽言心与理一,却没有体察到气禀和私欲对人心的影响,与禅学的问题一样。正是基于对气禀和私欲的影响的重视,朱子晚年更加认识到成德的艰难,强调下学阶段工夫的积累最后上达至贯通的境界,体现出朱陆在成德路径上的区别。朱子与陆学分歧不在于某一工夫上的理解不同,而是由心性论的不同以至于成德工夫路径上的分道扬镳,由此可知,历史上为了证明陆学、心学与朱学不相异而提出的朱陆晚年为同的观点不符合朱子本身的学术立场。
(四)与浙中吕氏及门人
朱子与浙中学者的学术交流很早就已开始,在吕祖谦去世前,朱子为了对峙陆学有意与吕祖谦达成一致战线,故朱子言陆学之失大多是在与吕祖谦、吕子约等浙中学者的论学中阐发的。吕祖谦去世后,陈亮入狱,朱子开始注意到浙学欠缺涵养工夫导致支离、功利的问题。朱子从55岁开始在对峙陆学的同时对峙浙学,与吕氏门人的对话主要围绕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展开。朱子认为吕氏门人穷理不以持敬涵养为本导致支离和事功,强调要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建议浙中学者读书要先读书“四书”等圣贤之书,立下为学主旨。对于浙学欠缺持敬工夫的情况,朱子晚年的批评更加严厉,并且朱子认为在陆学不重穷理和浙中学者不重涵养之间,不重持敬涵养的问题更加严重。朱子对浙学的批评从55岁后持续至朱子晚年,这个过程也是朱子论辩陆学及门人的过程,说明了朱子在阐述涵养与致知的工夫关系上同时对峙陆学和浙学的完整立场,没有偏向一方。
五 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检查
由“绪论”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对朱子涵养工夫的理解以及朱陆异同的理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经全文分析可知,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包括李绂的《朱子晚年全论》中以朱子晚年涵养工夫弥合朱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阳明曾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提出:“知其晚岁故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①阳明否定《集注》《或问》和《语类》判定朱子晚年思想的有效性,认为《集注》《或问》是朱子48岁时所作的,而《语类》是门人附会己见,故而特地摘录《文集》中属于“朱子晚年”的书信为据。阳明全书共摘录朱子34封书信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1195年吕子约回复朱子的一封书信,结合陈来先生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对此34封书信做考证归纳可知:《朱子晚年定论》中朱子48岁之前的书信有8篇,48—59岁的书信有18篇,60岁以后的书信仅5篇。如此可见,阳明所引书信约四分之一是在朱子48岁前,属于阳明所认为的朱子中年未定时期。从本书对朱子思想阶段的划分来看,《朱子晚年定论》中真正属于朱子晚年思想阶段的才5篇。从内容上看,阳明对朱子书信的摘录有断章取义之嫌,由此可知《朱子晚年定论》的依据有偏失,有失客观,这与此前学界对《朱子晚年定论》的客观性判定相符合。陈荣捷后来总结前人对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的批评主要有四点:“一为其误以中年之书为晚年所缮;二为其以《集注》《或问》为中年未定之说;三为其断章取义,只取其厌烦就约之语与己见符合者;四为其误解‘定本’,且改为‘旧本’。”①陈来也认为:“王阳明之《晚年定论》不顾材料为证,徒据臆想,以‘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即使《晚年定论》所收皆朱子60岁后书,也不能证明阳明之说,盖朱学本身包含有尊德性的内容,且在朱子晚年书信中取三十通此类者并非难事,然亦不济事也。后李绂即如此。然而,批评《晚年定论》的《通辨》其考证也并非精详可称,材料也远不充分。”②虽然亦有学者为阳明辩护,认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虽然史料有问题,但义理没有问题,如刘述先便说:“从考据的观点看,阳明编纂《朱子晚年定论》可谓一无是处。”③他提出:“阳明的‘定论’不是以时间为标准,是以义理为标准。”④刘述先为阳明之误开脱,但是必须承认的是,阳明摘录朱子书信的内容,皆是朱子言涵养、求放心、持敬、存心重要的部分,想要证明朱子晚年的转向。但经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言涵养为本,强调求放心的重要依然是延续“中和新说”以来的基本立场,涵养为本、求放心思想并不是至晚年才提出的,反而是在“新说”时就已经提出的基本观点,作为朱子涵养工夫的基本立场,涵养为本的立场从“新说”后至晚年都没有改变,并不是阳明所说的“晚岁大悟中年之非”之旨。朱子并没有因言涵养而轻穷理或者省察,并且朱子对陆学不重穷理的批评从朱子中晚年延续至晚年。从工夫路径上说,朱子晚年后特别强调成德的“下学而上达”的路径,这都是朱子重“道问学”的体现,朱子言涵养与致知、“尊德性”与“道问学”,总是强调不能偏废一方。
对于《朱子晚年定论》中对朱子静坐的判定,阳明引朱子37岁、40岁、55岁、57岁时的四封书信中言静坐与静的内容,并对朱子做了肯定。从时间上看,根据本书对朱子晚年阶段的划分,四封书信都不属于朱子晚年的观点。即便是王门心学后人李绂对朱子所划分的晚年(51岁后),也只有两篇属于朱子晚年,即便四篇都属于朱子晚年,其中论说也不能作为朱子晚年言静坐工夫的定论。这是因为静坐工夫不是朱子晚年时期才提出的,朱子晚年时仍没有完全否定静坐工夫的意义,所以不能说朱子改变中年之说而为晚年定论。更重要的是,阳明没有认识到静坐工夫在朱子涵养工夫中的地位以及脉络的变化,朱子晚年虽然肯定静坐工夫,肯定其有助于涵养本原,但朱子却以敬消解静坐,“敬之外别无静的工夫”是朱子晚年对静的工夫的最终判断,静坐工夫本身在朱子工夫思想里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对此阳明竟毫无察觉。由此可知,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所以无法成为定论,关键在于没有对朱子涵养工夫做全面的考察,没有将涵养工夫放在朱子工夫系统中去观察,而只关注朱子言涵养本身,这是为学方法上的缺失,故无法对朱子涵养工夫的地位有全面的判定,更无法对朱陆涵养的异同有客观全面的认识。
六 对中国港台新儒家对朱子判定的检查
(一)对“朱子的心为认知义”的检查
牟宗三对朱子心与理的关系的判定决定了其对朱子道德形态的判断,他认为朱子的心与理的关系是“心具众理”而不是“心即理”,心为“气心”,理外具于心,所以涵养工夫只能涵养不动之“性体”,而不是涵养本心,本心没有自发、自生的力量,故涵养工夫无法成为自觉的、自律的道德实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朱子确实有以“气之灵”释心,其目的在于为“心能知觉”寻找形质上的根据,因为心为气之灵,所以心为灵明知觉,此气不具有道德上的意义。朱子认为心有形体,理无形体,心又是形体中的灵的部分,所以能为无形之理提供着落处。所以,“气之灵”之气为“形器义”,而不是具有善恶的“气质义”。以此为基础,牟宗三认为在朱子心与理的关系中心只有认知的功能,从功能义上认识朱子的心与理的关系,符合朱子以气言心的说法,但朱子“心之能”的前提在于“理具于心”的结构,如果只从认知义上言心,直接从心之用开始认识朱子心与理的关系,显然缺失了心与理关系的结构义这一前提。牟宗三将朱子的“心具众理”诠释为心认知地具理,将“心具众理”从存有层面的“本具”曲解为工夫层面的“认知地具”,显然与朱子思想本义不符。①
所以,从工夫层面上看,穷理的前提是“心具众理”,穷理需要以持敬涵养为前提,由此说明了朱子的道德形态并非他律。在朱子这里,心不能免除气禀的影响,虽然每个人都“心具众理”,但必须要去做穷理致知的工夫,道德知识的学习是成德必须经历的路径,所以朱子提出下学而上达、博文而约礼、知至而意诚、致知而力行,都是对成德路径的证明,但是都没有动摇涵养工夫为成德根本的地位。穷理是穷“本具之理”,穷理始终都在持敬的关照下进行。下学到上达中有“豁然贯通”的时候,其中有本心力量的呈现,是道德天赋能力的展现,而不全部依靠习惯和经验的积累。对此陈来认为朱子“心具众理”是存有层面的心与理的关系,理潜存于心,“人所先天固有的不是一切知识,而是某些道德的良知(及生理本能)……虽然每个人心具众理,但这些理并未全部反映为人的良知,或者说人的良知并没有把心中所具的众理全部反映出来。……为了使人认识到心中本具众理,并达到心与理的彻底自觉,必须经过格物穷理的认识过程。……只是这些原则是常常是潜在的,在经过格物穷理之后才能成为人的现实意识的真正原则”①。所以,“心具众理”是本具和内具、自具的结合,说明了心的能动和自觉的能力,也说明朱子的涵养和穷理主要依靠自觉、自律的工夫完成。此外,陈来也指出了陆学的“心即理”这个命题本身不是朱子所反对的,朱子反对的是二人对工夫路径和方法的认识。陈来说:“心即理并不是主张人的一切意识活动无条件地合于理义要求。陆学所谓心即是理,在直接意义上是指本心即理。此外亦指人发明本心之后意识活动自然合理。陆学的这个思想朱熹并非不了解。”②
(二)对“朱子涵养工夫为小学工夫”的检查
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是通过对外在的规范的遵守而养成好的习惯,如此涵养工夫就是外在的、经验的道德实践,而不是自觉、自律的道德实践,由此判朱子为道德他律。首先,朱子涵养本原的地位在《知言疑义》中就已提出,在《仁说》中确立,《仁说》中朱子将仁解释为仁体、性体,涵养本原是涵养性之全体,但此性之全体本具于心,所以朱子的涵养工夫是涵养性,也是涵养本心,并且本心的主宰地位在《仁说》之后随着“心具众理”“心主性情”等命题的提出就已经确立本心的主宰地位。中年时期所确立的持敬的工夫是操存涵养、整顿身心,中晚年时期朱子还以求放心解释持敬,晚年以“精神专一”解释持敬,无论持敬为哪一种解释,心的主宰地位是前提,而本心的操习并不只是对外在规范的遵守而养成的习惯,本心居积极主动的地位。其次,从克己与复礼的关系上看,朱子晚年时期重视以复礼作为克己的规矩准绳,认为克己要落实在复礼上完成,体现出朱子对外在规范的重视。但是,从工夫的过程来说须通过克己来完成复礼,所以内心的自觉和道德主体的地位是首先确立的,这也是克己复礼没有超出主敬地位的原因。朱子将持敬作为自得于心的工夫,如果自得于心则也不必做克己工夫,朱子还提出持敬是克己的立脚处,说明主敬的地位没有改变,朱子的涵养并不主要依靠克己复礼完成,说明了通过外部规范的制约不是首选的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自律是成德工夫的第一义。
最后,从涵养与其他工夫关系中也可以看出涵养工夫是成德的根本工夫,在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中,牟先生认为朱子的涵养是被致知吞没的涵养,是在“道问学”中的“尊德性”,即“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而完成的,如此“尊德性”就成为经验的、外在的“尊德性”。经前文分析可知,“下学而上达”说明了朱子对成德次序的认识,“尊德性”必须有“道问学”的工夫,但并不是说“尊德性”是通过“道问学”完成的,这是对朱子的误解。朱子晚年并没有改变涵养为致知的根本工夫的地位,持敬是穷理的前提。朱子晚年也并没有以致知言诚意,而是提出知至后的诚意具有自己的独立的工夫意义和工夫内容,省察和慎独都是完成意诚的工夫。致知是诚意的主要工夫,但知至不等于意诚,诚意有自己的工夫,所以诚意并不是如牟宗三所说的外在的诚、认知地诚,诚意是通过省察和慎独等自觉的道德实践完成的。由此可见,朱子的涵养工夫也不是经验的、外在的,有学者提出:“朱子探讨道德发生的问题虽然仍遵循孟子的性善论,认为道德有其先验的存在性与超越的内在性,一切道德的观念或行为是以人类至善天性作为根源依据的,而且再次绝对至善的根源为大前提下,每个人对于道德的认知或判断,终究是以个人的自觉自律为依据。”①虽然朱子认为道德认知在成德中有重要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作用,道德的养成和完善主要是通过自律来完成和实现的。
(三)对“朱子知行不一”的检查
中年时期朱子确立了基本的知先行重的知行观,至晚年时发展成为对成德路径的全面论述。首先,朱子同时从两个方面对致知和践履的关系做出阐释:一方面,致知是大学工夫的下手处,但是要补涵养于未发一段的工夫,说明了持敬是穷理、致知之本,穷理没有超出持敬涵养的道德义,说明知的目的最终是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另一方面朱子提出致知而后力行说明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大学》的工夫规模体现了知先行后的入德次序。朱子以知至而后意诚说明了知先行后,以真知必能行说明了知行合一的意诚的境界,最终以意诚为行之始,将成德的标准落到行上说,说明了朱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
其次,从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看,朱子晚年提出“无时不涵养省察”“未发已发都要省察”的观点,说明朱子注重省察对涵养工夫的补充,省察是完成诚意和慎独阶段的重要工夫,这也说明朱子晚年重视对自觉的道德实践的落实。
最后,朱子的涵养工夫并不只是精神意识上的活动,虽然朱子晚年将持敬诠释为“精神专一”,但并没有取消持敬为整顿身心的解释,涵养本身就是身心合一的道德实践。朱子涵养工夫的特点是以持敬贯彻所有工夫始终,强调平日涵养无间断、事中涵养等观点其实都体现了朱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从具体的涵养工夫来说,朱子中晚年开始重视诚与敬的分辨,提出不能以敬代诚,将诚落在诚意工夫上解释,诚意主要是为了解决知行不一的自欺的问题,可以看出朱子晚年重视道德实践的落实。朱子中晚年开始对主静保持警惕的态度,以持敬限制静坐,提出无事时且静坐、不能专于静坐的观点,说明了朱子重视“事中涵养”而非“静中涵养”,这也说明朱子重行而非重知。朱子晚年对立志工夫也有进一步重视,这是基于在志与意的分析中发现志具备意所没有的特点和功能,所以需要拈出立志工夫来补充居敬,朱子的目的也是解决道德实践动力不足的问题。可见,朱子对涵养工夫的修正和完善真正是其知行合一思想的体现。
(四)对“以朱子成德路径判朱子为他律”的检查
对于朱子晚年不仅从知行关系还从《格物补传》中的积累至贯通、《大学》中的知至而后诚意、《论语》中的博文约礼、《孟子》中的博学而反约来贯通《论语》中下学而上达的思想,从“四书”工夫思想贯通的角度对朱子晚年的成德路径做了阐发,可见朱子晚年对成德艰难的认识,鼓励人做工夫要勇猛精进。同时朱子批评陆学上达而下学,也批评了陈淳“先见天理源头”,二者都是不够重视穷理的体现。对于朱子晚年对成德路径的集中阐发,牟宗三提出这是朱子注重工夫的深度和广度的表现,他说:“安卿病处,依朱子所见,单在只吃馒头尖,广度深度工夫俱不作,只想凭空理会那源头处,空守著那个荡漾如水银的天理而不放,故朱子反覆告诫之也。并非不可说源头处,亦非定不许‘先见天理源头’也。即是朱子晚年甚至历来不喜‘先见天理源头’之见,重在平说平磨,亦只怕人两脚踏空,先只空见个‘天理源头’有何益?故其虽遮拨之,然一至正面叮咛反覆,却只重在深度广度平磨将去。此其重点知在工夫之踏实与充实,并非客观义理上定不许‘先见天理源头’也。此见前训潘时举言为学两进路便可知。”①在此牟宗三指出朱子晚年不喜“先见天理本原”并不是对持敬涵养的否定,而是肯定朱子晚年重视工夫的深度和广度,广度上重视涵养与致知的平衡,怕门人两脚踏空,只守个天理本原。深度上强调格物穷理致知等下学工夫的积累,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并且,朱子重视下学工夫是强调工夫的踏实与充实,牟先生以深度和广度的“平磨”来说明朱子晚年对下学工夫的重视。牟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朱子也说“见天理源头”,但是与象山不同,同时他做出了优劣判定,他说:“并非一说‘先见天理源头’便是象山学也。在朱子之义理系统中亦可说‘先见天理源头’(先理会太极大本),然在此系统中不如在五峰、象山学中先识本心仁体为切要,故朱子得以重视平磨以遮拨之也。”①牟宗三认为朱子也言“先见天理源头”,即先理会大本所在,也就是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也就是涵养本原,但是牟宗三认为朱子的涵养本原没有在五峰和象山言“先识仁体本心”这么重要,所以朱子重视穷理致知作为下学工夫的积累。
由此可以看出,牟宗三认为工夫的“平磨”即通过穷理致知的下学工夫的积累至上达不是最优的道德修养方法,是通过练习、模仿达到的道德的规范,所以是他律的、外在的。相比之下五峰、象山的先识本心仁体是最优的方法,因为本心主宰、本心自觉,道德形态也是自律的。牟先生依此创造出朱子是横贯系统和象山是纵贯系统来说明象山的道德形态是自律,朱子的道德形态是他律,最终以象山为优,朱子为劣。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作为成德的路径的说明,意诚之前的穷理、致知、省察、慎独、“克己复礼”等下学工夫的积累过程需要练习、模仿和外在规范的学习,但是下学至上达存在积累至贯通的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贯通的阶段并不是完全依靠练习和模仿实现的,朱子指出其中有融会贯通觉悟处,二程言其中有类推的方法,还有其他不可言说的体验处,这都说明朱子的成德路径不是通过他律实现的。并且需要指出的是朱子以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在致知之前,持敬涵养的根本地位已经确立了其成德的主要方法不是依靠他律而是依靠自觉本心为善的前提。最后,作为穷理、致知、省察、克己复礼等下学工夫本身,也不是属于依靠练习、模仿完成的工夫,穷理是穷心中本具之理,致知是致本心之虚灵明觉,省察是解决自欺的行为,是对不知不觉的私意的检查,也是慎独的工夫,是需要通过本心的主宰,通过本心的自我认识和行动的自我约束来实现,所以可知朱子以“下学而上达”作为成德的基本路径,并不影响朱子的涵养工夫是自律自觉的工夫。
附注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81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73页。
②钱穆提出:“朱子46岁鹅湖初会时,朱子之思想体系与其学术规模已大体确立。”见钱穆《朱子新学案》三,第390页。陈来也提出:“从40岁到46岁与陆九渊鹅湖相会,朱熹哲学的基本思想在这几年全部建立起来。”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2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198页。
①钱穆:《朱子学提纲》,第112页。
①杨儒宾曾指出:“‘主敬’与‘穷理’并不是平行的关系,‘主敬’更具有时间上的优先性。”见钟彩钧主编《朱子学的开展·学术篇》,台北市: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版,第236页。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415—416页。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190页。
①(明)王阳明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册,第140页。
①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第356页。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45页。
③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576页。
④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578页。
①具体阐述参见陈双珠《“后具”抑或“本具”?——关于“心具众理”命题之再诠释》,《儒教文化研究》(第31辑),首尔: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19年版。
①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334—337页。
②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415页。
①周天令:《朱子道德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501页。
①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下),第501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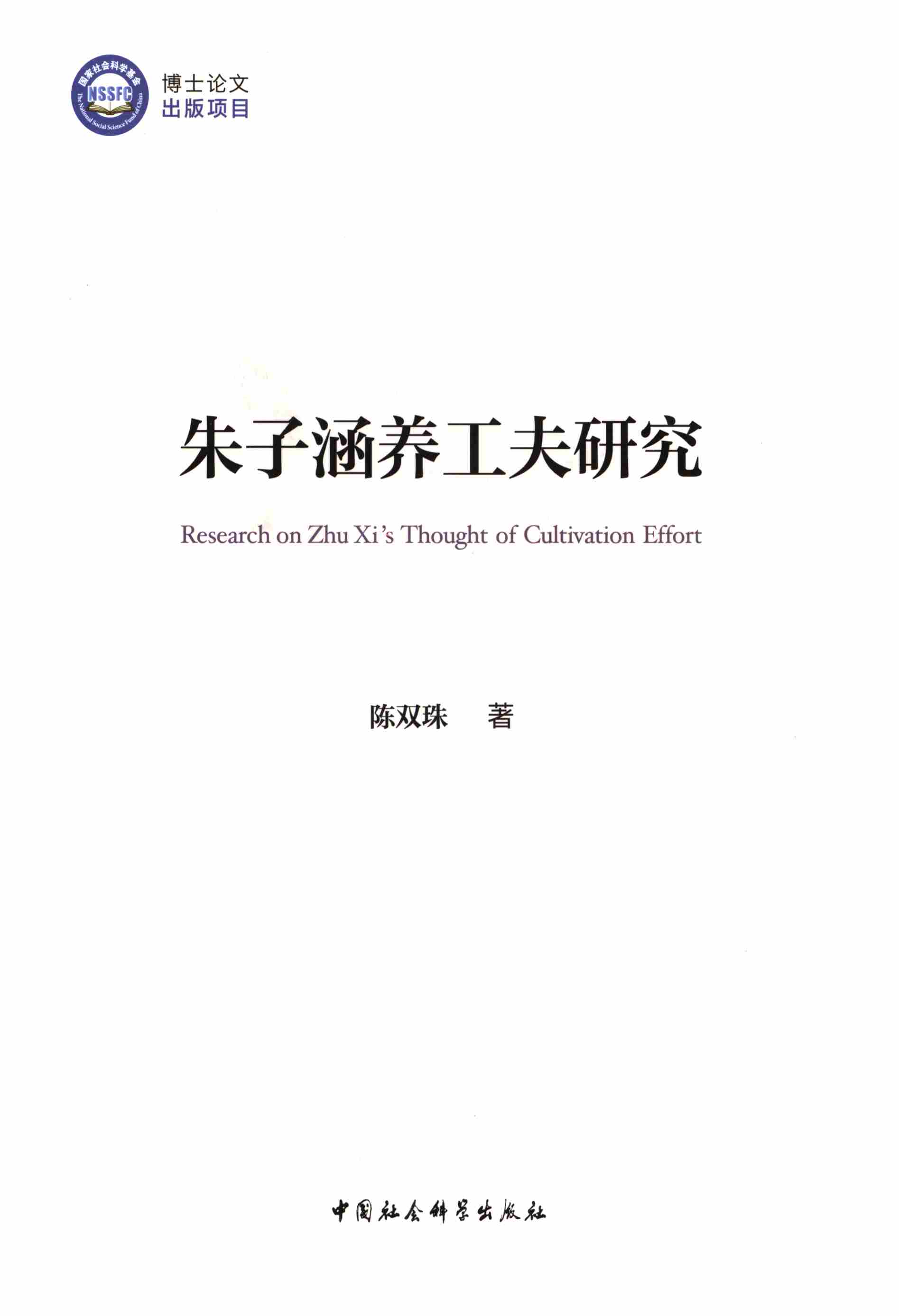
《朱子涵养工夫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以朱子涵养工夫为研究对象,将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分为中年、中晚年、晚年三个阶段,梳理出朱子涵养工夫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和发展历程。全书围绕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涵养工夫内在的关系以及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三个角度对朱子涵养工夫进行了考察;从脉络发展的视野厘清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和思想地位;从学术史论辩的视野探寻朱子涵养工夫的特点;从工夫论的确立到完善的动态考察探求朱子涵养工夫思想背后的心性论的建构和完善的过程;从而对朱子的修身涵养理论进行了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研究,也对学术史上关于朱子涵养工夫的诸多判定和争议进行了检查。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