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涵养工夫的地位
| 内容出处: | 《朱子涵养工夫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532 |
| 颗粒名称: | 第四节 涵养工夫的地位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1 |
| 页码: | 388-44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在晚年时期对涵养工夫的地位进行了讨论,主要围绕涵养与致知、涵养与省察的关系展开。其中,涵养与致知的关系是重点,朱子同时对话陆学与浙学,最后回到对门人的检查,体现了他对自身工夫思想的反思。在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朱子晚年也做出重大调整,更加重视省察工夫。此外,朱子在之前对知行关系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成德的次序,以《大学》为工夫规模,最终认识成德路径。 |
| 关键词: | 南平市 朱子思想 落实 架构 |
内容
朱子在晚年时期对涵养工夫的地位的讨论主要还是围绕涵养与致知、涵养与省察的关系展开的,其中涵养与致知的关系仍然是朱子晚年讨论的重点,对此朱子仍是同时对话陆学与浙学,最后回到了对自己门人的检查,体现出朱子晚年对自身工夫思想的反思。在涵养与省察的关系上,朱子晚年也做出重大调整,体现出对省察工夫的进一步重视。更重要的是,在之前对知行关系的基本认识的基础上,朱子晚年对成德的次序集中进行讨论,体现出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也体现了朱子对成德路径的最终认识。
一 涵养与致知
(一)持敬涵养为本
1.持敬为本,穷理为助
朱子在中年时期确立了以持敬涵养为成德的根本工夫,晚年后朱子仍然保持持敬存养、持敬为穷理之本、持敬即求放心、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的基本观点。朱子说:“敬则心存,心存,则理具于此而得失可验,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①61岁时又说:“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②同年又说:“学者堕在语言,心实无得,固为大病。……近因病后,不敢极力读书,闲中却觉有进步处,大抵孟子所论‘求其放心’是要诀尔。”③进入晚年后,由于年老多病,朱子越发认识到涵养是成德的关键。62岁时又说:“所谓‘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穷理’,此说甚当。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岂是此事之外更无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无可下手处。此本既立,即自然寻得路径进进不已耳。”④在此朱子指出了涵养是成德的根本工夫,是其他修养工夫的前提。65岁时朱子又说:“先立根本、后立趋向,即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后,然后自能寻向上去’,亦此意也。”⑤持敬涵养是立根本的工夫,必须先落实,立下根本之后再进一步穷理致知,所以说“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同年朱子又说:“主一无适者亦必有所谓格物穷理者以先后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养必以敬,而进学则在致知。’此两言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其一而可行可飞者也。世衰道微,异说蜂起,其间盖有全出于异端而犹不失于为己者,其他则皆饰私反理而不足谓之学矣。”①在此朱子仍以主一无适言持敬涵养,体现出朱子晚年仍遵从二程涵养与致知两大工夫路径,涵养与致知作为成德的两大基本方法,二者不能偏废一方。朱子晚年特别强调持敬与穷理不可偏废一方,偏重任何一方都是错的。他说:“见人之敏者,太去理会外事,则教之使去父慈、子孝处理会,曰:‘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若是人专只去里面理会,则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时,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②朱子认为程子教人,因人而异,如果太理会外面事,则要注意以持敬为本,不能泛然观理,如果只专从里面理会,则要注意穷理的必要,持敬穷理应当一起理会,但是在持敬涵养上必须用六七分力气,在格物穷理上可用三四分力气,可见朱子的成德工夫主要依靠涵养而不是穷理,穷理是对涵养的辅助,他说:“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③由此可见,朱子晚年持敬为本的地位没有改变,涵养依然是成德工夫的第一义。
2.批浙学支离
朱子在55岁后开始批评浙中吕氏门人欠缺持守工夫,不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最后流为事功之学,并同时检查自身与浙中学者的支离问题,进入晚年后,朱子继续指出浙中学者欠缺涵养本原的工夫,批评吕氏门人支离。
然觉得今世为学不过两种,一则径趋简约,脱略过高;一则专务外驰,支离繁碎。其过高者固为有害,然犹为近本;其外驰者诡谲狼狈,更不可言。吾侪幸稍平正,然亦觉欠却涵养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义,盖多得之,已略注其间矣。小差处不难见,但却欲贤者更于本原处加功也。①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当今为学的问题总结起来可以为两种,一种是做工夫路径过于简约,脱略文字,喜欢高论;一种是专务外驰,不重涵养,如此则工夫支离繁碎。明显,前者指陆学,后者针对浙中吕氏门人而发。朱子认为陆学立论过高固然有害,但是贴近根本,而工夫向外求索则诡辩奇怪,更不值得说。可以看出,朱子认为相比陆学,浙学的问题更严重,可见朱子坚持以涵养工夫作为成德的根本,其地位不能动摇。同时,朱子提出自己的工夫架构稍稍平正一些,但还是觉得自己涵养本原的工夫有所欠缺,应该进行反思,同时也建议吴伯丰在涵养本原的工夫上加倍努力。62岁时陆子静还未去世,当时朱子对陆学及门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但是与浙学相比,朱子认为浙学欠缺涵养的问题比陆学更严重,如此可见朱子批评浙学的程度,但朱子并没有用很严厉的语气或者很重的话语批评浙学。朱子62岁时,郑可学对朱子说不能去见陆子静,担心受其影响学会参禅,对此朱子说:“此人言极有理。吾友不去见,亦是。然更有一说:须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则自不走往他。若自家无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见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羡。若是自家自无住处,忽见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虽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①可见,朱子认为陆子静之学固然不可取,但是修身立命必须以涵养工夫为本才能有归处,而浙中吕氏的问题比陆子静不立文字更严重。吕祖俭对朱子说:“今所虑者,非在于堕释氏之见,乃在于日用之间主敬守义工夫自不接续而已。若于此能自力,则敬义夹持,此心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②朱子回应:“此正如明道所说扶醉人语,不溺于虚无空寂,即沦于纷扰支离矣。”③可见朱子言空虚针对陆学,言支离针对吕学。68岁时,朱子又致信万正淳批评吕祖俭不知以涵养为本。
子约之病,乃宾主不明,非界分不明也。不知论集义所生则义为主、论配义与道则气为主,一向都欲以义为主,故失之。若如其言,则孟子数语之中,两句已相复矣,天下岂有如此絮底圣贤耶!子约见得道理大段支离,又且固执己见,不能虚心择善,所论不同处极多,不但此一义也。④
朱子认为吕祖俭的问题不是不辨义利,而是宾主不明,不以涵养为本。吕祖俭不知言集义所生是以义为主,不知言配义以道时是以气为主,一直以义为主,所以有了偏失之处。朱子认为如果按吕祖俭都以义为主,则孟子言集义所生和配义与道就重复了,圣贤不可能如此烦琐。朱子认为吕子约理解圣贤的道理大段支离,又固执己见,不虚心采纳别人的说法,所以不只与朱子在这点上不同,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朱子认为吕祖俭质朴老实,但看道理不分明,表示惋惜。次年朱子又致信吕祖俭,建议他同时做致知与涵养的工夫,如此才能解决支离的问题。
窃意贤者用力于此,不为不久,其切问近思之意不为不笃,而比观所讲与累书自叙说处,觉得瞻前顾后,头绪太多,所以胸次为此等丛杂壅塞缠绕,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学后生闻一言且守一言,解一义且守一义,虽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离纷扰,狼狈道途,日暮程遥,无所归宿也。①
朱子指出吕子约做读书工夫过于瞻前顾后,头绪太多,所以显得过于烦琐缠绕,不够明白直接,反而不如闻一言守一言,解一义且守一义,也就是致知与涵养并进,互相配合,如此虽然不能马上有很大的成效,也可以避免工夫支离纷扰及工夫路径过于曲折缠绕。
(二)涵养与致知并进
1.涵养为本与致知为先
朱子同时有先致知后涵养和涵养为致知之本的说法,二者看似矛盾,朱子晚年做了解释,涵养工夫为先是从大纲上说,《语类》载:“问致知涵养先后。曰:‘须先致知而后涵养。’”问:“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纲说。要穷理,须是着意。不着意,如何会理会得分晓。”②在此,朱子提出涵养在致知之先是从大纲上说,是总论,相当于指导思想。在做工夫上,要从致知入手。《语类》又载:“王德辅问:‘须是先知,然后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点与曾子,便是两个样子:曾点便是理会得底,而行有不掩;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处。”①对于王德辅提问是否先知然后才能行,朱子则回答不能因为不明理就不持守,朱子要说明不能因为知没有完成就不做行的工夫,强调持守工夫要先落实。如果只做穷理不去持守,则会出现“知而不行”的情况,如果能像曾子一样先持守,则能在持守中渐渐明理,最终是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在此,朱子说明了持守为先、持敬以穷理的原理。持敬为先与致知作为大学工夫的入手处不矛盾,朱子说:“‘致知’一章,此是大学最初下手处。若理会得透彻,后面便容易。”②大学工夫的规模体现了成德的次序,致知作为大学工夫的入手处,说明了成德的次序从致知开始。
夫庄敬持养,此心既存,亦可谓之无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穷,则于应事接物之际不能处其当,则未免于纷扰,而敬亦不得行焉。虽与流放而不知者异,然苟不合正理,则亦未免为妄与邪心也。故致知所以为《大学》之首,与其用力之次第,则先生所作《大学传》所引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数条是也,但庄敬持养又其本耳。③
朱子认为庄敬持养后本心既存,理论上可以说没有邪心存在,但是如果知有未至、理有未穷,则在具体的应事接物中不能妥当,本心也难免受到纷扰,如此敬也不能再发生作用。在此,朱子说明了穷理、致知工夫对持敬的影响。朱子认为这虽然与放失本心而不自知的情况不同,但心在事事物物中不能合于理,则难免成为邪妄之心,这就是致知之所以成为大学工夫之首的原因,但是同时庄敬持养又是根本的工夫。在此,朱子说明了致知作为大学工夫的入手处与持敬涵养为根本工夫不是矛盾的,涵养与致知在做工夫上是同时进行的。
任道弟问:“或问,涵养又在致知之先?”曰:“涵养是合下在先。古人从小以敬涵养,父兄渐渐教之读书,识义理。今若说待涵养了方去理会致知,也无期限。须是两下用工,也着涵养,也着致知。伊川多说敬,敬则此心不放,事事皆从此做去。”贺孙。《广录》云:“或问存养、致知先后。”曰:“程先生谓:‘存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盖古人才生下儿子,便有存养他底道理。父兄渐渐教他读书,识义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学者先须存养。然存养便当去穷理。若说道,俟我存养得,却去穷理,则无期矣。”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解释所谓涵养在致知之先是从总体而言的,古人从小就以敬完成了涵养工夫,如此再去读书求义,所以古人的涵养工夫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至大学阶段时就可以直接做致知工夫。因为今人都缺了小学阶段的持敬涵养,所以必须先落实存养工夫,但是存养和穷理要一起做,如果涵养好了再去穷理,则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涵养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穷理,所以涵养和穷理是必须同时做的,持敬本心的同时,事事都从持敬做去。
2.居敬穷理互发是境界
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更加注意强调涵养和致知不可偏废一方,涵养与致知如鸟之双翼要两下用功,可以看出朱子比较重视涵养与致知对彼此的相互作用。朱子说:“(涵养与致知)二者偏废不得。致知须用涵养,涵养必用致知。”①61岁时又说:“学者若不穷理,又见不得道理。然去穷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这里。”②涵养与致知二者不可偏废一方,二者互相配合,偏废任何一方,另一方的工夫都不能完成。他又说:“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③又说:“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才见成两处,便不得。”④如此可见,朱子提出不能穷理也不能持守,涵养中自有穷理,穷理是穷所涵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而涵养是养所穷之理,二者是互相包含的,两不相离,不能将二者分为两处做工夫。63岁时,朱子直接提出持敬穷理不能分为两节工夫,他说:“然‘敬’即学之本,而穷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两截看也。”⑤持敬是为学的前提,穷理是为学的内容,二者不可分作两节工夫,朱子又以下雨与蒸汽的循环做比喻来说明涵养与穷理的互相发明。
人之为学,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后,到处湿润,其气易得蒸郁。才略晴,被日头略照,又蒸得雨来。前日亢旱时,只缘久无雨下,四面干枯;纵有些少,都滋润不得,故更不能蒸郁得成。人之于义理,若见得后,又有涵养底工夫,日日在这里面,便意思自好,理义也容易得见,正如雨蒸郁得成后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者,日间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养工夫。设或理会得些小道理,也滋润他不得,少间私欲起来,又间断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①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做学问就像下雨一样,下雨后到处湿润,水汽容易蒸发,等天晴被太阳照一照,水蒸气化为雨落下来,但如果一直干旱无雨,空气干枯,下一点雨也无法滋润,更谈不上蒸得水汽。就像人对于义理,如果见得义理后,又做涵养工夫,义理便能日日记在心里,义理也容易理解,就像下雨后水汽蒸发得雨。如果不做涵养工夫,或许能理会一些小道理,对涵养帮助不大,私欲很快就会起来影响本心,使涵养工夫出现间断,就像干旱很久了空气里没有水汽蒸出雨是一样的道理。在此朱子说明了涵养与穷理相互发明、互相促进,偏失一方就会影响另一方。65岁后,朱子直接提出居敬穷理互发的观点,他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②在此,朱子以左脚和右脚互相配合行走来比喻居敬与穷理互相促进的关系,能持敬则穷理的工夫更细密,能穷理则持敬的工夫更进一步,就像两只脚走路,一只脚走,另一只脚停,但都在完成走路这件事。朱子也说明了持敬是向内收敛,穷理是向外致知,二者的方向不同,所以两足同时走路是不行的。朱子最后提出居敬穷理互发是境界,比较严密地说明了二者的关系,他说:“初做工夫时,欲做此一事,又碍彼一事,便没理会处。只如居敬、穷理两事便相碍。居敬是个收敛执持底道理,穷理是个推寻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时,则自不相碍矣。”①朱子提出居敬和穷理刚开始做工夫的时候其实是互相妨碍的,但如果两个工夫都做到纯熟,则不会互相妨碍,而是互相配合。
(三)批陆:不重穷理
1.言“识心”之弊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就已经讨论了“识心”的说法,当时朱子并没有直接否定“识心”的说法,并且从儒家的立场对“识心”做了解释,以区别禅学“识心”的说法。
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书》所谓“天叙”“天秩”“天命”“天讨”,《孟子》所谓“物皆然,心为甚”者,皆谓此也。若不于此先致其知,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如此,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且如释氏擎拳竖拂、运水般柴之说,岂不见此心?岂不识此心?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正为不见天理而专认此心以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耳。前辈有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盖谓此也。②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儒家做工夫最关键以穷理为先,一物有一物之理,必须先明白一物有一物之理,然后心之所发才能各有自己的准则,孟子所说“物皆然,心为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此,朱子提出必须先明白一物有一物之理,心才能够依据准则而发,说明了大学工夫的次序。朱子又提出如果不在心上先致心之知,使其见到心所以为心的道理,否则格物致知过于广泛而没有准则,则其心之所存所发,无法自然合理。在此,朱子以致心之知来解释“识心”,以“识心”为格物致知的前提,实际上以涵养本原解释“识心”。朱子认为佛家也说要见此心、识此心,但是佛家的“识心”、见心的工夫不是尧舜之道,因为不见心中之理,而专认心为主宰,不知心为主宰的原因,如此心则不能免于私欲的影响。由此,朱子说明了儒家和佛家言“识心”的区别,朱子认为儒家的心是本心具理,所以穷理工夫之前的“识心”是识心中之理,为穷理提供是非准则,而“识心”的目的是认识到此心为主宰,保证此心为主宰。佛教的“识心”则是只以心为主宰,而不明白心为主宰的依据在于心中本具之理,所以空言“识心”。可以看出,朱子当时并没有否定“识心”的说法,“识心”能认识到心中万理具备而有成德的标准和可能,所以在朱子53岁时没有反对项平父所说“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已发时常常记得”①,可见朱子此处以“识心”为未发前涵养工夫。进入晚年后,朱子改变了“识心”为未发前涵养工夫的说法,以致知解释“识心”,提出“识心”必须经过穷理的积累。
如邵子又谓“心者性之郛郭”,乃为近之。但其语意未免太粗,须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无病耳。所谓“识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说是也。然亦须知所谓识心,非徒欲识此心之精灵知觉也,乃欲识此心之义理精微耳。欲识其义理之精微,则固当以穷尽天下之理为期,但至于久熟而贯通焉,则不待一一穷之,而天下之理固已无一毫之不尽矣。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今先立定限,以为不必尽穷于事事物物之间而直欲侥幸于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卤灭裂而终不能有所发明也。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邵雍所言“心者性之郛郭”比较贴近地说明了心性关系,但语意未免太笼统,不够细致,因为只说明了心承载性,但没有体现心性关系的核心在于心是身之主宰的原因,在于性是心的道理。在心性关系的基础上,朱子肯定“识心”与致知最为贴近,朱子又强调要知道“识心”并不是认识此心之知觉的功能,而是要认识心中精微的义理,而想要认识心中精微的义理,就必须以穷尽天下之理为目标,在久久熟练后达到贯通的境界。贯通之后则不用一一去穷理,天下之理都能穷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是学者通过努力做工夫穷理纯熟后融会贯通的缘故。如此可见朱子以致知解释“识心”,“识心”要通过穷理的积累达到贯通的境界。这说明朱子提出“识心”之说本来没有错,但是却被后人曲解误用了。朱子认为“识心”之弊在于专是务虚而又高论狂妄,所以朱子晚年言“识心”之弊主要针对陆学而发。
近来学者多说“万理具于心,苟识得心,则于天下之事无不得其当”,而指致知之说为非,其意大率谓求理于事物,则是外物。谊窃谓知者心之所觉,吾之所固有,盖太极无所不该,而天下未尝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汩于物欲,乱于气习,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开其蔽以复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者,岂皆穷之于外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所以处之者,欲穷其当,则固在我矣。……必也如程子所谓“觉悟贯通,于天下万物之理无一毫之不尽,则义精而用妙”,始可以言尽心知性矣。不知或者识心之说,岂一超直入者乎?……恐不可专以庄敬持养、此心既存为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纷扰、敬不得行然后为有妄之邪心也。所论近世识心之弊,则深中其失。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推此以穷天下之理。今之所谓识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礼益卑,今人则论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见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近来学者喜欢说万理具于心,只要识心则天下之事都能得到妥当的处理,由此而认为没有必要做穷理致知的工夫,其中大概意思是穷理是从外物中求理,是心外的工夫。对此,朱子提出知是心之所觉,知觉是本心所固有的,该遍天地万物,所以天下没有心外之物,也没有心外之理,只是因为物欲的遮蔽、习气的扰乱才使知觉被遮蔽而不光明,而持敬、穷理的工夫都是去蔽恢复本心之知觉的工夫。程子说一物有一物之理,必须穷尽其理,但是穷理并不是穷心外之理。朱子以程子言觉悟贯通后才可以言尽心知性为据,提出不经过穷理直言“识心”,工夫太过“一超直入”。在此基础上,朱子进一步提出工夫不能专以持敬涵养,如不务穷理最终难免成为邪妄之心,这是专言“识心”造成的弊病。朱子提出古人对存心的重视是将存心推至穷理工夫,而今人说“识心”则是将理存于心外,古人知得越多越谦虚,但现在的人喜欢高谈阔论又十分狂妄,可以看出朱子在此所批评的是陆学。心固不可不识,然静而有以存之,动而有以察之,则其体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识心者,则异于是。盖其静也初无持养之功,其动也又无体验之实,但于流行发见之处认得顷刻间正当底意思,便以为本心之妙不过如是……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过,此用便息,岂有只据此顷刻间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无不各得其当之理耶?所以为其学者,于其功夫到处亦或小有效验,然亦不离此处,而其轻肆狂妄、不顾义理之弊,已有不可胜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语人,徒增竞辨之端也。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再次对方宾王提出心固然不能不识,“识心”就是静时存养、动时察识,如此则心之体用昭然明白。在此,朱子又以存养和省察为“识心”工夫。朱子提出近世言“识心”则不是如此理解的,在静时没有持敬存养,动时又不实际去省察,而只是在流行发见之端认得道理,便以此为心之神妙的全部内容,而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而未言及心之全体。朱子认为“识心”之端,不是“识心”工夫。朱子认为只是根据流动发生之端的省察就能在使心在已发后事事物物皆合于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学者因为工夫小有成效就轻肆狂妄,不顾义理上的弊病,坚持以此为“识心”工夫,这是需要注意的。朱子对此很谨慎,他告诉方宾王不要将这话告诉别人,否则只会增加竞辩的事端。此时朱子与象山还没有结束论辩,与陆学门人关系紧张,所以告诉方宾王这个说法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不想徒增竞辩的争端,这显然是针对陆学门人而言的,可知朱子以上批评针对陆学而发。
2.不知气禀之杂
朱子认为是否承认气禀对心的影响是儒释的区别,也是朱陆之分,朱子认为禅学与陆学都没有体察到气禀和私欲对人心的影响,所以不重穷理,朱子说:“虽说心与理一,而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亦是见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学》所以贵格物也。”①可见,朱子认为陆学虽言心与理为一,但是没有注意到气禀与物欲对心的影响,不知气禀之杂是陆学不重穷理的根源。
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向在铅山得他书云,看见佛之所以与儒异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义。某答他云,公亦只见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说儒者绝断得许多利欲,便是千了百当,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这气禀不好,今才任意发出,许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气有不好底夹杂在里,一齐羇将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性。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孟子不说到气一截,所以说万千与告子几个,然终不得他分晓。告子以后,如荀扬之徒,皆是把气做性说了。”②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陆子静的学问有很多问题,但根源在于没有注意到气禀之杂,所以把许多粗的、恶的气与心之妙理混淆。朱子认为陆子静只说儒者要断绝利欲,不让利欲任意发出,但是却不知道因为刚开始的气禀不好才任意发出不好的利欲。在此,朱子以气禀说明了人发出不好的利与欲的原因,气禀最终导致人不能诚意,也就是不能自觉地达到完善的境界,所以要通过长久的磨炼才能去除气禀的影响。而陆子静只说从胸中流出的是自然天理,不知有不好的气夹杂在天理中,没有意识到因为气禀的影响造成了不同的人成德的努力程度和完成程度的不同。言自然天理是对本心的过分自信。所以朱子批评陆子静看书,不作明理,所以采纳的是粗糙的观点,门人弟子也是如此,无兄无父,只说我胸中流出的是天理,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有气禀之性的存在。所以二程才说论性不论气是对性认识的不完备,孟子即缺失论气的一截,所以与告子论辩,没有最终的分晓。告子后,荀子、扬雄之徒都把气说成性了,以气为性,则动摇了天命之性。在此,朱子强调要重视气禀对性的影响,如果不重视气禀的影响则论性不完备,也无法重视穷理工夫,但如果把气当成性,即如告子以生为性,则论性不够明白。朱子晚年改变了“新说”时期所认为的持敬可以完全解决气禀和私欲的问题,而强调以穷理对治气禀,以气禀的影响说明了穷理工夫的必要。
大抵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然圣贤教人,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未尝教人只守此心者,盖为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之禀不能无偏,若不讲明体察,极精极密,往往随其所偏堕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为此说者,观其言语动作,略无毫发近似圣贤气象,正坐此耳)。是以圣贤教人,虽以恭敬持守为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验今,体会推寻,内外参合。盖必如此,然后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间万事、一切言语,无不洞然了其白黑。……若如来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穷理,故此心虽似明白,然却不能应事,此固已失之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从大抵上说每个人之心都万理具备,如果能存得此心,便是圣贤,其他就没有什么工夫了。然而圣贤教人之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从来没有教人只做持守工夫,就是因为此心虽然本具万理,但却因气禀的影响难免有偏,如果不讲明体察,做更加精密的工夫,则此心就会随其所偏流入私欲中而不自知。所以圣贤教人做工夫,虽然以持守为先,而在持守之中又必须即事即物做穷理工夫,如此内外工夫相配合。朱子认为必须如此,才能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如果如项平父所说只做持守本心的工夫,一点不去穷理,则此心看起来似乎明白,但却不能应事,其实已失本心了。认识到气禀对成德的影响,朱子晚年更加注重持敬与穷理二者缺一不可,强调内外工夫互相配合,改变了中年时期认为持敬能变化气质的观点,这也是朱子与陆学工夫分歧的原因所在。
问:“季通说‘尽心’,谓‘圣人此心才见得尽,则所行无有不尽’。故程子曰:‘圣人无俟于力行。'”……又曰:“尽心如明镜,无些子蔽翳。只看镜子若有些少照不见处,便是本身有些尘污。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鹘突窒碍,便只是自家见不尽。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今人多是气质偏了,又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尽知,圣贤所以贵于穷理。”又曰:“万理虽具于吾心,还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个心在这里,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许多道理。少间遇事做得一边,又不知那一边;见得东,遗却西。少间只成私意,皆不能尽道理。尽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无有不合道理。”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尽心的境界就像明镜一样,没有一点点遮蔽,如果镜子上有少许遮蔽,便是本心还有未光明处,说明朱子以尽心为成德的标准。朱子认为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大多是因为气质偏了,又被物欲遮蔽,所以本心昏昧而不能尽知,这是圣贤之所以重视穷理的原因。朱子又说万理虽本具于心,但还要教人去知此本具之理,才是得理于心。现在人有心却不让自己去穷理知理,所以最终心都发为私意,不能尽心中之理,如果能尽此心中之理,则心洞然光明,事事物物都合于理。在此,朱子以不能穷理则不能尽心的角度说明了不能只守此具理之心,应该要使心知所具之理而使心事事物物都合于理才是尽心,在此朱子将尽心诠释为成德的境界,而穷理是达到尽心必须做的工夫。63岁时朱子又致信项平父说明穷理须以涵养为本,所以穷理不在心外。
所论义袭,犹未离乎旧见。……如孟子答公孙丑问“气”一节,专以“浩然之气”为主。其曰“是集义所生者”,言此气是积累行义之功而自生于内也;其曰“非义袭而取之也”,言此气非是所行之义潜往掩袭而取之于外也;其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于义,而此气不生也,是岂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义为外……然告子之病,盖不知心之慊处即是义之所安,其不慊处即是不合于义,故直以义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见得此意而识义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不慊与不慊,亦有必待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者。……来喻敬义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学之本,而穷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两截看也。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项平父的“义袭”仍然没有改变旧见,孟子言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如此说明所养之气是自己生于心内之气,孟子言“非义袭而取之”即说明此气不是取之于外,而“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则说明如果心不合于义,则此气不生。朱子又说告子不知气生于内而以义在心外,告子的问题在于不知道诚意必须通过讲学省察才能达到,所以敬是为学之本,但穷理却是敬在事中的工夫,二者不能分为两节。在此,朱子提出正因为涵养是前提,格致为心内的工夫。1194年,朱子在《经筵讲义》中又说:“然而尚幸有可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于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励,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从今日从事于敬以求放心,则犹可以涵养本原而致其精明以为穷理之本。”①朱子认为要兼取孟子求放心和二程持敬,而求放心是通过“事中持敬”来实现的,如此则可以涵养本原使本心达到精一、光明的程度,依此成为穷理的根本。
朱子于1200年又言求放心不在讲学应事之外,朱子说:“若论功夫,则只择善固执、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如说‘求其放心’,亦只是说日用之间收敛整齐,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几其中许多合做底道理渐次分明,可以体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后别分一心出外以应事接物也。”②可见,朱子认为所谓的涵养工夫就是在事中对善的坚守、对仁义中正的践行,而没有别的一段涵养本原的工夫,求放心只是在日用之间收敛整齐,不使心向外走作,对道理的体察也不是一心来藏道理,又分出一心应接事物,体察与应接都是涵养此心,对此王懋竑认为此是朱子言涵养的“定论”:“廖书在庚申正二月间,此真所谓晚年定论者。”③
3.江西气象遗害
1189年后朱子与象山绝笔,但是朱子对象山和陆学的批评并没有停止,相反在象山去世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朱子都没有停止对象山和陆学的批评,一方面是朱子对象山直接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陆学门人的批评,因为陆学在当时影响很大,极大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朱子最终上升到对儒家道统的担忧。
许行父谓:“陆子静只要顿悟,更无工夫。”曰:“如此说不得。不曾见他病处,说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风便骂将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见他不是,须子细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穷理。既知他不是处,须知是处在那里;他既错了,自家合当如何,方始有进。子静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说得他!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稊稗’,恐反为子静之笑也。”①
由引文可知,许行父提出陆子静只要顿悟,没有其他工夫,朱子马上提醒许行父不能这样说。朱子认为许行父对陆子静的批评没有抓到要害,不能从根本上驳倒他。现在的人批评陆子静大多也是跟风,没有找到陆子静的根本错误。朱子指出陆子静问题的根源在于不穷理,但朱子也认可陆子静重视以涵养为本,指出现在的人不如象山用功,没有资格去批评他。朱子言“五谷不熟,不如稊稗”是指浙中学者欠缺涵养工夫,其问题比象山不重穷理更严重。在此,朱子肯定了象山的涵养工夫,否定他人对象山顿悟的批评,说明朱子在此还没有从工夫路径上批评象山。1189年朱子致信邵叔义说:“子静书来,殊无义理,每为闭匿,不敢广以示人,不谓渠乃自暴扬如此。……吾人所学,却且要自家识见分明,持守正当,深当以此等气象举止为戒耳。”②朱子直言陆子静“殊无义理”,认为其言论封闭藏匿,不敢广示他人,提出为学主旨是要先自己见识分明,持守正当,即持敬和明理不偏废一方,并劝告别人以子静的气象、举止为戒。同年,朱子还致信赵子钦提出在与陆子静的交流中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子静后来得书,愈甚于前。大抵其学于心地工夫不为无所见,但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穷理细密功夫,卒并与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觉,而高谈大论,以为天理尽在是也,则其所谓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①朱子认为陆子静的问题比以前更严重,其问题并不在于不重涵养,而是将涵养架得过高而不做更为细密的穷理工夫,如此所涵养的本心也会失去,最后导致人欲横流而不自知,他所说的心上的工夫也不能安在。在此,朱子批评象山不重穷理而导致工夫高悬,语气很重。次年朱子又致信姜叔权、汪长孺,以‘江西气象’批评二人。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学问气象?顷见其徒自说见处,言语意气、次第节拍正是如此,更无少异。恐是用心过当,致得如此张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异事,甚不便也。长孺所见亦然。但贤者天资慈祥,故于恻隐上发,彼资禀粗厉,故别生一种病痛,大抵其不稳帖而轻肆动荡,则不相远也。正恐须且尽底放下,令胸中平实,无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当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批评姜叔权说其学问全与江西气象相似,认为他与陆学门人自说见处,言语意气、次第节拍都一样。朱子又说汪长孺也是如此,圣人天资慈祥,所以能发于恻隐,但枉长孺天资和禀赋都粗劣,所以没有发出恻隐,不仅不稳妥还轻肆动荡,朱子建议他们放下这种高谈阔论的习惯,令心中平实。同年朱子又致信汪长孺说:“别纸所论,殊不可晓。既云‘识得八病,遂见天理流行昭著,无丝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气盈矜暴之失,复生大疑,郁结数日,首尾全不相应?似是意气全未安帖,用心过当,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气象。……此须放下,只且虚心平意玩味圣贤言语,不要希求奇特,庶几可救。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后观书,此又转见诡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详审,不可容易也。”①朱子认为汪长孺受到象山影响,全似江西气象,批评他不重视读书穷理的工夫,气象诡怪多端。朱子建议姜、汪二人先把高论放下,令心中平实,虚心体会圣贤言语,不要在奇怪臆想的言论上求道理。1193年,象山已去世一年,朱子对子静的批评仍然很重,认为象山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
大抵近年风俗浮浅,士大夫之贤者不过守文墨、按故事,说得几句好话而已。如狄梁公、寇莱公、杜、范、富、韩诸公规模事业,固未尝有讲之者,下至王介甫做处,亦模索不着。……子静旅榇经由,闻甚周旋之,此殊可伤。见其平日大拍头、胡叫唤,岂谓遽至此哉?然其说颇行于江湖间,损贤者之志而益愚者之过,不知此祸又何时而已耳。许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②
朱子认为近年风气日益浮浅,士大夫中的贤人不过也是只守文字,流于空谈,受到江西气象的影响很大。朱子提出见陆子静平日拍大头、胡叫唤,说明陆学的弊病不是一日两日突然就如此的。然而陆子静的学说颇为流行,不仅损害贤者的志向也加重了愚蠢之人的过错,不知陆学的祸害什么时候能停止,许行父似乎已经受到江西陆学的毒害。由此可见,在象山去世之后,朱子仍旧没有停止对象山的批评,甚至提出江西陆学是影响当时学术风气的祸害,可见朱子对陆学批评的程度。1195年,朱子又致信廖子晦提出吴伯起也受到陆学风气的影响。
此间有吴伯起者,不曾讲学,后闻陆子静门人说话,自谓有所解悟,便能不顾利害。及其作令,才被对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尝笑之,以为何至如此,若对移作指使,即逐日执杖子去知府厅前唱喏;若对移做押录,即逐日抱文案去知县案前呈覆。更做耆长壮丁,亦不妨与它去做,况主簿乎?吴不能用,竟至愤郁成疾而死,当时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许多下情,所失愈多。虽其临机失于断决,亦是平日欠了持论也。①由引文可见,朱子说吴伯起不做讲学求义的工夫,后来听了陆子静门人说话,就认为自己有很多领悟,便不顾利害,高谈阔论以至于被罢免官职,都是因为他平日不持守。朱子认为如果他能够应事接物,即使被罢免主簿,也不妨碍做别的,最后因为不被重用竟然愤郁成疾而死。朱子认为如果他当时能放下高论,在平日中多做持守工夫,可能不会到忧愤至死的地步。1196年,朱子致信孙敬甫言陆学对近年学术风气的影响,朱子依然批评陆学高谈阔论、不重穷理明义,认为陆学应事接物的能力太差。要之持敬致知实交相发,而敬常为主,所居既广,则所向坦然,无非大路,圣贤事业,虽未易以一言尽,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如陆氏之学则在近年一种浮浅颇僻议论中,固自卓然,非其俦匹,其徒传习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间者,但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讳。当时若只如晁文元、陈忠肃诸人分明招认,着实受用亦自有得力处,不必如此隐讳遮藏,改名换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诚之域也。然在吾辈须当知其如此,而勿为所惑,若于吾学果有所见,则彼之言钉钉胶粘一切假合处,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来矣,切勿与辨以起其纷拏。①
在此,朱子提出持敬与致知要互相发明,如果以持敬为主,则居敬穷理肯定是朝着成德的方向,不会与圣贤之道相差太远。朱子提出陆学近年表现出肤浅偏僻、自视甚高的问题,而且其门人当中也有能修身齐家治理政事的人才,但因为陆学的为学宗旨本来是从禅学中来,无法掩盖。在此指出了陆学造成不好的学术风气的根源原因在于宗旨来自禅学。朱子举晁文元、陈忠肃等人都曾坦白承认受到禅学的启发为例,提出既然如此则不必遮掩隐藏,想要欺骗别人但不能自欺,自欺则陷入不诚的境地。朱子在此提醒孙敬甫不要被陆学迷惑,如果能对朱学有领会,则陆子静的附会、虚假的言论自然能分辨,并告诫敬甫不要与陆门论辩而引起纷争。如此可见,朱子晚年很注意不和陆学门人直接辩论,但没有中断对陆学的批评。朱子在此指出陆学的为学宗旨来自禅学是江西气象的根本原因,说明朱子对陆学的批判是很重的,实质上是将陆学判入了禅学,对陆学的批评已经超出了儒家的范围。
4.判陆学为禅
综合前文分析可知,朱子对禅学的批评有针对大程门人而发的时候,但大多时候针对陆学而发,朱子批评陆学为禅不是因为陆学在世界观、人生观与佛学相似,更多的是从为学方法和工夫形式上看,朱子的标准在于有没有重视穷理。对此朱子说:“此是求其放心乃为学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须更做穷理功夫,方见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两事,随感即应,自然中节,方是儒者事业,不然却亦与释子坐禅摄念无异矣。”①可以看出,朱子认为求放心是根本,但在此基础上必须做穷理工夫,涵养与穷理不是两件事,应该合起来做,如果只言涵养不言穷理与佛家的坐禅无异。涵养与格致的关系是朱陆之辩的核心内容,朱子45岁第一次指出陆学不重穷理,认为陆子静全是禅学②,50岁后朱陆围绕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展开集中论辩,至60岁时与象山绝笔,朱子两次批评陆学为禅,52岁时说陆子静有“禅底意思”③,56岁时又说陆子静有“禅底意思”④。
朱子进入晚年后仍以不重穷理作为批评陆学的基本立场,朱子批评陆学为禅不仅贯穿了朱陆之辩的过程,直至象山去世后朱子晚年的十年时间,指陆学为禅是朱子批评陆学的一条主线。朱子65岁说:“盖谓其本是禅学,却以吾儒说话摭掩。”⑤又说:“陆子静之学,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看是甚文字,不过假借以说其胸中所见者耳。据其所见,本不须圣人文字得。他却须要以圣人文字说者,此正如贩盐者,上面须得数片鲞鱼遮盖,方过得关津,不被人捉了耳。”⑥
66岁时说:“圣贤教人有定本,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也。其人资质刚柔敏钝,不可一概论,其教则不易。禅家教更无定,今日说有定,明日又说无定,陆子静似之。圣贤之教无内外本末上下,今子静却要理会内,不管外面,却无此理。硬要转圣贤之说为他说,宁若尔说,且作尔说,不可诬罔圣贤亦如此。”①67岁时说:“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讳。”②68岁时又说:“只是禅。初间犹自以吾儒之说盖覆,如今一向说得炽,不复遮护了。”③由此可见,朱子判陆子静为禅是一以贯之的,朱子从中年45岁后至去世的二十五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改变批陆学为禅的观点。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判子静为禅并没有从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上做系统的批评,只是从心性论中的心与理的关系、为学方法以及工夫形式上批评陆学为禅,不仅延续中年时期的“脱略文字,直趋本根”的工夫形式,还批评象山不重穷理,认为其为学宗旨来自禅学,实际上对象山的批评已经超出了儒家内部的范围。
二 涵养与省察
(一)省察是诚意之助
省察是指内心的反省和检查,中年时期认为省察“察人欲之将萌”,晚年时期将省察主要落实到私意和自欺的检查,说明了省察对诚意工夫完成的作用。由于朱子晚年特别注意气禀的影响,朱子认识到私意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所以省察的地位得到重视。
彦忠问:“居常苦私意纷搅,虽即觉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洁静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静‘有头’之说,却是使得。惟其此心无主宰,故为私意所胜。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见破了这私意只是从外面入。纵饶有所发动,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劳,自家这里亦容他不得。此事须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后方省察,殊不济事。”①
由引文可见,彦忠提出自己常常苦于私意纷扰,虽然自己也努力抑制,但成效不好,对此朱子回答说只是因为本心没有居于主宰地位,所以被私意所胜,最需要做的就是常常省察,使良心常在,私意就不会从外面进入而影响本心。如果私意稍有发动,本心为主宰,自然会将私意克除。朱子强调平日省察的重要性,如果等私意影响本心后再去省察,也没什么用。在此,朱子认为省察是平日工夫,是在私意影响本心之前对私意的省察,省察的地位上升到和涵养一样,成为平日工夫。朱子说:“且于日用处省察,善便存放这里,恶便去而不为,便是自家切己处。”②对于省察如何成为诚意的工夫,朱子分析是先省察到善与恶,然后再去存善去恶,这说明了诚意工夫包含两个阶段,一是省察到意之善恶,二是为善去恶,朱子说:“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诚其意。”③可见,省察对诚意的帮助是通过致知的环节完成的,省察不能完成诚意,但如果没有省察则诚意的工夫不能完成。朱子说:“只是说心之所发,要常常省察,莫教他自欺耳。人心下自是有两般,所以要谨。谨时便知得是自慊,是自欺,而不至于自欺。若是不谨,则自慊也不知,自欺也不知。”④在诚意工夫完成的次序上,要先省察以解决自欺的问题,因为谨慎省察才能发现内心是自欺还是自慊,如果不省察,则内心是自慊还是自欺无法知晓,可见省察对诚意的作用。
基于朱子晚年对私意问题的认识,朱子认为诚意是很难完成的工夫,所以进一步强调省察的作用,他说:“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见是别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计较利害,犹只是因利害上起,这个病犹是轻。惟是未计较利害时,已自有私意,这个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这个躯壳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谓流注想者是也。所谓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觉,流射做那里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①在此,朱子提出本心如果只是计较利害,问题则比较轻,但在还未计较利害时就已经有私意,这个问题最严重。朱子提出人有了躯壳之后便自私了,说明了自私来源于形气之私,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就像佛家所说的“流注想者”,说明私意的影响就像水流,是不知不觉影响本心的,私意萌发的端倪十分微小,很难发现,需要直接做省察工夫。因为朱子认识到人受到气禀的影响而私意不可避免产生,并且私意对本心的影响有不知不觉的特点,所以更体现出省察工夫的重要,如果不做省察工夫,无法发现自欺。所以要达到自慊而无一毫自欺的境界必须通过省察,朱子说:“盖到物格、知至后,已是意诚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御寇,寇虽已尽剪除了,犹恐林谷草莽间有小小隐伏者,或能间出为害,更当搜过始得。”②朱子提出省察是在知至之后单独属于诚意阶段的工夫,知至之后已经完成了诚意的八九分的工夫,只是从上面省察,将剩下的私意检查出来,知至后的扫尾工作是更为细致的工作,也是诚意完成的关键。
(二)无时不涵养省察
从朱子晚年的文献来看,朱子60岁后的书信很少涉及对涵养与省察的关系的讨论,主要是因为涵养与省察的关系是朱子中年时期与湖湘学派论辩的核心,朱子45岁作《观心说》标志朱子与张栻论辩结束,由此朱子的心性论基本确立,工夫的基本架构基本形成,所以涵养与省察的关系在此后不是考察涵养工夫地位的核心问题。中年时期,湖湘学派主张先察识后涵养,朱子主张涵养于未发之前,强调涵养先于察识的地位,这是基于朱子对未发前涵养工夫的重视。中晚年时期朱子提出无时不涵养、无事不省察,强调涵养是平日无间断的工夫,而省察是针对私欲萌发而做的检查工夫,并且中晚年时期朱子已开始注重阐述省察对涵养的意义。晚年后基于对私意问题的重视,朱子认识到省察是诚意完成的关键工夫,省察的地位得到提升。朱子晚年对湖湘学派言涵养与省察的关系再一次进行讨论,对涵养与省察关系的表述出现了重大变化。
莹以所论湖南问答呈先生。先生曰:“已发未发,不必大泥。只是既涵养,又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若戒惧不睹不闻,便是通贯动静,只此便是工夫。至于慎独,又是或恐私意有萌处,又加紧切。若谓已发了更不须省察,则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发后省察。今湖南诸说,却是未发时安排如何涵养,已发时旋安排如何省察。”①
必大录云:“存养省察,是通贯乎已发未发功夫。未发时固要存养,已发时亦要存养。未发时固要省察,已发时亦要省察。只是要无时不做功夫。若谓已发后不当省察,不成便都不照管他。胡季随谓譬如射者失傅弦上始欲求中,则其不中也必矣。”②
由第一段引文可见,朱子强调不要太过拘泥于未发已发之分,应该既涵养又省察,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涵养与省察片刻不能间断,将戒慎恐惧通贯动静。至于慎独,则是在私意萌发前更加紧急关键。如果认为已发了就不用省察则不可以,如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已发后的省察。在此朱子其实已经表明了无论未发已发都要省察,以此批评湖湘学派是未发时安排涵养,已发时安排省察,如此涵养与省察则出现间断。第二段朱子认为存养省察贯通未发已发,未发时要存养也要省察,已发时要存养也要省察,无时不做涵养省察的工夫,这与第一段表达的意思一致。朱子取消了中年时先涵养后察识的说法,强调应该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朱子还批评了湖湘学派将涵养和省察安排为未发已发的两段工夫,未发时安排如何涵养,是求中;已发时安排如何省察,则私意已发,再救偏失则来不及。所以未发前就要涵养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则可以保证涵养省察工夫没有间断。由此可见,朱子晚年时期不再对涵养与省察做未发已发工夫的区分,取消了涵养与省察的先后。此后朱子又说:“今人非无恻隐、羞恶、是非、辞逊发见处,只是不省察了。若于日用间试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趱出来,就此便操存涵养将去,便是下手处。”①朱子提出今人之所以发不出善端只是因为没有省察,应该在日用间省察此四端,就此操存涵养,可见朱子认为对于四端是先省察再操存涵养。同年,朱子对陆子静言涵养与省察的关系做出批评。
陆子静云:“涵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陈正己力排其说。曰:“子静之说无定常,要云今日之说自如此,明日之说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见人说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谓须是涵养;若有人向他说涵养,他又言须是省察以胜之。自渠好为诃佛骂祖之说,致令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①
对于陆子静认为“涵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的说法,朱子提出象山说法不定,经常有变。朱子认为陆子静是故意与人抬杠,看到别人重视省察,便故意反着说必须涵养,若有人向他说涵养,他又会说省察比涵养更重要。在此,朱子认为象山与朱子的论辩已经是意气之争,认为陆子静喜欢诃佛骂祖之说,最终导致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可见,朱陆论辩绝笔之后,朱子其实已经不在意象山说什么了。此后,朱子更加重视省察对成德的作用,提出要时时省察,如果时时省察则道统不会间断,特别在慎独的时候人容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所以省察也是慎独的关键。朱子说:“‘子在川上’一段注:‘此道体之本然也,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才不省察,便间断,此所以‘其要只在慎独’。人多于独处间断。”②朱子提出在道体之本然的时候,就要时时做省察工夫,这样道体发用才不会间断。不省察,道体就会间断,其中最关键的是慎独,人在独自的场景,很难做到道德的自觉,所以要达到慎独的境界,必须做省察的工夫。所以朱子肯定门人以慎独强调省察的作用,门人说:“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后行不得,二是役于欲后行不得。人须是下穷理工夫,使无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无一私之或作。然此两段工夫皆归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慎独。'”③朱子回答:“固是。若不慎独,便去隐微处间断了。能慎独,然后无间断。”④朱子也认为如果不慎独,工夫便在隐微处间断;如果能慎独,持敬则不会间断,这是慎独对持敬的意义。
同时,朱子也说明了涵养对省察的意义,68岁时朱子说:“心存时少,亡时多。存养得熟后,临事省察不费力。”①朱子认为涵养工夫做好了,省察也可以减少很多力气,这是从工夫的完成上说,并不是从做工夫上言二者先后。同年,朱子还以动静区分涵养与省察。朱子说:“存养是静工夫。静时是中,以其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也。省察是动工夫。动时是和。才有思为,便是动。发而中节无所乖戾,乃和也。其静时,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乃复所谓‘见天地之心’,静中之动也。其动时,发皆中节,止于其则,乃艮之‘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动中之静也。穷理读书,皆是动中工夫。”②在此朱子以动静区分省察和存养,并且提出才思就是发动,符合朱子晚年以思作为未发已发区分的标准,说明将省察从事的范围扩大到思的范围,只要思虑发动就要做省察工夫,也符合朱子无时不涵养省察的观点,所以很多时候朱子将涵养与省察并说。68岁时,朱子引“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说:“若说三者工夫,则在平日操存省察耳。”③69岁后又说:“方其静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应接也,此理亦随处发见。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养久之,则是理愈明,虽欲忘之而不可得矣。”④朱子晚年将涵养与省察并说,不言涵养与省察的先后,将涵养与省察并列为平日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是朱子晚年对涵养与省察关系的定说。
三全球成德路径
(一)致知而力行
朱子在中年时期已经确立了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等基本知行观,中晚年时期提出义理不明不能践履,以致知为先力行为重的基本立场。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也以持守与穷理的关系来说明知行关系,说明朱子以道德践履为涵养工夫,如此主敬作为涵养的主要工夫容易被理解为践履,对此朱子在进入晚年前对二者做出了明确的区分。朱子说:“但主敬方是小学存养之事,未可便谓笃行,须修身齐家以下乃可谓之笃行耳。”①朱子以主敬涵养为小学阶段的存养工夫,补今人小学工夫之缺,但是朱子强调主敬不是笃行,修身以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才可以说是笃行,可见朱子最常以持敬与穷理的关系说明涵养与穷理的关系,但不等于知行关系。知行关系体现了涵养践履与穷理的关系,也体现了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以及朱子对《大学》工夫次序的遵循。
朱子晚年延续中年时期对知行关系的基本立场,强调致知为大学工夫的入手处,他说:“‘致知’一章,此是大学最初下手处。若理会得透彻,后面便容易。故程子此处说得节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资质耳。虽若不同,其实一也。”②朱子提出大学工夫最初的下手处,致知是大学工夫的开始,因为每个人的资质不同,其中致知工夫节目最多,虽然其中节目不同,但境界都是到知至。其中节目其实是指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的过程,其中体现了成德的积累至贯通的过程,成德的速度因人而异。对于大学工夫次序的区分,朱子还做了特别的说明:“但《大学》次序,亦谓学之本末终始无非己事,但须实进得一等,方有立脚处,做得后段功夫,真有效验尔,非谓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后段而听其自尔也。”③在此,朱子说明了对大学工夫次序进行区分的意义在于说明大学工夫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都是自己的事,所以必须实实在在地做好每一步的工夫才有做后面工夫的基础,后面的工夫才能真正有效果,并不是说前面的工夫没有完成,后面的工夫就不管不做了。在此,朱子说明《大学》的工夫次序是指工夫完成的先后,而不是前面的工夫没有完成,后面的工夫不能做,朱子其实说明了工夫可以同时做,但工夫的效果和完成的程度受到前面工夫完成程度的影响,《大学》的工夫次序实际上说明的是入德的次序和成德的路径。68岁时朱子提出做学问只有两个路径,致知和力行,也说明了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以及成德的路径要以知为起点。
所喻前论未契,今且当以涵养本原、勉强实履为事,此又错了也。此是见识大不分明,须痛下功夫钻研勘教透彻了,方是了当。自此以后,方有下手涵养践履处。……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须是先依次第十分着力,节次见效了,向后又看甚处欠阙,即便于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见人说着自家见处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养本原、勉强实履,此如小儿迷藏之戏,你东边来,我即西边去闪,你西边来,我又东边去避,如此出没,何时是了邪!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吕祖俭只以涵养本原和道德践履作为修养方法是不够的,如果义理不明就应该做穷理工夫使义理透彻,如此才有涵养和践履下手的地方,在此朱子说明了知先行后的成德路径。朱子认为吕祖俭欠缺了义理上的工夫却不从义理上探究,而是去别处闲坐,嘴上说是涵养与践履,却是未知先行。朱子认为做学问只有致知和力行两个路径,人必须依照次第做工夫,等前面的工夫有效果再向后看哪里有欠缺的地方,从欠缺的地方做工夫。在此,朱子说明了从工夫的完成上说是先致知后力行,致知完成后再检查行的完成,哪里欠缺就在哪里做工夫,不能逃避问题,逃避是无法成德的。除此之外,朱子晚年从《格物补传》中的积累至贯通、《大学》中的致知与诚意、《论语》中的博文与约礼、下学与上达等多个维度来说明成德的路径,体现了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兼对“四书”工夫思想的贯通。
(二)积累至贯通
积累至贯通是朱子言成德次序的经典命题,朱子以积累至贯通来说明大学工夫中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正心这一段工夫节目中境界的变化,朱子最早于1164年《吕氏大学解》中提出这个问题,吕大临说:“以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与尧舜同者也。理既穷,则知自至,与尧舜同者忽然自见,默而识之。”①对此,朱子提出:“愚谓致知格物,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则所致之知固有浅深,岂遽以为与尧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见之也哉?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②当时朱子遵从延平主旨,反对吕大临认为致知可以与尧舜同而忽然自见,认为格物致知要从具体的一事一物的工夫积累至贯通的境界。中年时期朱子作《格物补传》说:“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而不明矣。”③朱子认为通过格物工夫的积累能自然而然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此时以知至为贯通。陈来认为这种贯通是伦理学方面的“从特殊的具体规范上升到普遍的道德原理的意义”①。朱子进入晚年后仍然以格物穷理作为积累的过程,61岁时朱子批评方宾王和姜叔权等人言“识心”之误,强调“识心”需要通过穷理的积累才能达到。
然亦须知所谓识心,非徒欲识此心之精灵知觉也,乃欲识此心之义理精微耳。欲识其义理之精微,则固当以穷尽天下之理为期,但至于久熟而贯通焉,则不待一一穷之,而天下之理固已无一毫之不尽矣。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今先立定限,以为不必尽穷于事事物物之间而直欲侥幸于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卤灭裂而终不能有所发明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所谓“识心”并不是只去认识心之精明知觉,而是要认识此心之义理精微之处。要识得义理之精微,就应当以穷尽天下之理为目标,工夫纯熟后自然能达到贯通的境界。到了贯通的境界,则不用每件事物上都去穷理,天下之理都能被穷尽,所谓举一反三、闻一知十都是学者工夫达到一定深度、熟练的程度,然后才能融会贯通。朱子强调如果认为不必穷理就能达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效果是不可能的,朱子在此实际上是以致知解释“识心”,强调要通过穷理的积累才能到达知至的境界。62岁时朱子对方宾王说:“圣人生知,固不待多学而识,学者非由多学,则固无以识其全也。故必格物穷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诸约。及夫积累既久,豁然贯通,则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矣。”①朱子提出学者多是学而知之,必须通过格物穷理以达到博学,通过主敬和力行达到约礼,强调博学和约礼都需要通过长久的工夫积累才能豁然贯通。在此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博学前的积累,以主敬和力行为约礼的积累,如此可见格物穷理与主敬力行都是积累的过程。此后,朱子又进一步明确持敬存养其实没有很多积累的工夫,格物穷理需要更多积累的过程,他说:“敬之与否只在当人一念操舍之间,而格物致知莫先于读书讲学之为事,至于读书又必循序致一,积累渐进而后可以有功也。”②所以朱子言积累至贯通大多是从格物穷理、读书明义上来说的,也就是说贯通的境界主要是通过穷理而不是持守来实现的。
朱子65岁时又以延平的“洒然冰释”来说明穷理对于贯通的作用,延平说:“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冻解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③延平认为如果工夫没有做到“洒然冰释处”,纵然有持守工夫也没有用。对此胡季随说:“窃恐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处’,必于理皆透彻而所知极其精妙,方能尔也。学者既未能尔,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厌饫,以俟其自得。”④胡季随认为所谓的“洒然冰释”就是穷理至知至的境界,如果学者不能穷理以致知,则只能暂且持守以等待自得。对此朱子补充提出“洒然冰释”是意诚的境界,同时强调只通过持守的积累是无法达到贯通的境界的。
此一条,尝以示诸朋友,有辅汉卿者下语云:“‘洒然冰解冻释’,是功夫到后,疑情剥落,知无不至处。知至则意诚,而自无私欲之萌,不但无形显之过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遏捺,苟免显然尤悔,则隐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岂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则横放四出矣。今曰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说甚善。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须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旦牵强着力做得。今湖南学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厌饫,而俟其自得”,未为不是,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答者乃云“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强欲做此模样,殊不知通透洒落如何令得?才有一毫令之之心,则终身只是作意助长,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①
由引文可见,辅广认为延平“洒然冰解冻释”是做工夫达到知至、意诚的境界,如此则私欲不会萌发。但如果只用持守工夫想要遏制私意是十分吃力的。辅广提出有的学者认为“洒然冰释”是令自己胸中通透洒落不符合延平本意。对此,朱子认为辅广说得极好,朱子提出大抵上说“洒然冻释”是工夫后见识分明、涵养纯熟的境界,必须从真实的工夫中积累而来,而不是勉强在遏制私欲上用力。所以胡季随说“只得且持守”恐怕错了,因为欠缺了穷理这一节工夫。“胸中洒落”并不是为了回到本心原来的样子而勉强去模仿,只要有一点勉强的意思就是私意在内,就是自欺,永远不能到达洒然的境界。由此说明朱子也认为持守无法完全解决私欲和私意的问题,也就是说持守工夫积累再多也无法到达贯通的境界。可以看出,朱子晚年对成德路径的理解与“中和新说”时期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中年时期朱子认为“敬则无己可克”,如果涵养工夫做好了是不会有私欲和私意问题的产生的,但是朱子晚年认识到私欲和私意的产生受到气禀的影响,自欺的问题没有这么容易解决,所以朱子晚年将工夫贯通后的境界由知至推后至意诚,以意诚为心与理的贯通,王懋竑说:“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犹修书不辍,夜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且曰:‘为学之要,惟在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久之,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至极而已矣。’”①格物、穷理、致知、省察作为完成诚意的工夫都属于积累的阶段,至于具体如何从格物穷理的积累到达贯通的境界,朱子遵从程子的解释,以“推”作为贯通的方法。
然而尚赖程氏之言,有可以补其亡者。如曰:“……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又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余矣。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②
二程认为格物不是只有一个方法,读书讲义、论古今是非、应事接物皆是穷理工夫的内容,但是如果能长期坚持格物穷理的工夫,通过久久的练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达到贯通的境界。穷理并不是说一定要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也不是说只穷得一理后就能贯通,但如果对自己身上以至于万物之理理会得多了,自然会有贯通领悟的时候。格物并不是穷尽天下之物之理,但如果从一件事物上穷尽事物之理,在其他事物上则可以类推。比如要孝顺则应当寻求之所以孝顺的道理,如果一件事情上无法穷理,先暂且在别的事物上领悟。或者先从容易处开始,或者先从难处开始,因每个人资质的浅深而定。穷理的方法有很多,只要领悟一个道理,就可以依此类推旁通。这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万理同出一原,所以通过类推的方法就可以达到贯通的境界。朱子67岁时还提出涵养本原和心理贯通都需要积累的过程,他说:“所喻涵养本原之功,诚易间断,然才觉得间断,便是相续处。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积累将去,久之自然接续打成一片耳。讲学功夫亦是如此,莫论事之大小、理之浅深,但到目前,即与理会到底,久之自然浃洽贯通也。”①在此,朱子提出涵养本原也需要积累的过程,因为持敬容易间断,但如果发现了间断,就是接续起来的地方,所以需要常常提撕省察、渐渐积累,最后自然涵养无间断。讲学工夫也是如此,无论事情大小,道理深浅,只要通过长久的积累,最后都能达到心与理的贯通。可见,持敬、格物、穷理、致知,包括省察等意诚前的工夫都属于成德工夫的积累。
(三)知至而后意诚
1.先致知后诚意
先致知后诚意是《大学》的工夫次第,朱子对《大学》的诠释遵从了《大学》中知至而后意诚的成德次序,在知行关系上体现为知先行后的成德路径,与象山以诚为先、以知为行的观点不同。后世“朱陆晚同说”为了合同朱陆,提出朱子晚年因为重视省察和诚意,改变了知先行后的立场终与陆学为同。比如李绂判定朱子为“先行后知”,“省察先于致知”。①李绂所引的“朱子晚年”的材料并非皆是其划定的55岁后,如其中朱子《答任伯起》②的时间为1182年,此时朱子53岁。抛开李绂史料的真实性不言,朱子晚年确实对诚意和省察有一定修正,但是并没有改变《集注》阶段已经确立知至而后意诚的成德次序。但是,朱子改变了《集注》中以知至为贯通的境界,而将贯通的境界提推至意诚,如此知至之后诚意工夫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工夫内容,朱子又以省察和慎独工夫落实了诚意阶段的工夫。1190年朱子致信汪长孺说:“《大学》‘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旧说不同。若如旧说,则物格之后更无下功夫处,向后许多经传皆为剩语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来说得之。”③在此,朱子提出若如《章句》旧解则物格之后就没有下工夫的地方了,因为旧注中以物格知至为“事事物物皆合于理”,认为物格知至之后意就自然诚了,如此则造成物格之后不须做工夫,诚意工夫就没有下落处。所以62岁时朱子重新解释了“知至而后意诚”:“知则知其是非。到意诚时,则无不是,无有非,无一毫错,此已是七八分人。然又不是今日知至,意乱发不妨,待明日方诚。如言孔子‘七十而从心’,不成未七十心皆不可从!只是说次第如此。”①在此,朱子提出知至则知是知非,到意诚时无非无错,知至已完成诚意的七八分的工作,还有两三分是独属于诚意阶段的工夫。但是并不是说知至后才可以做诚意工夫,只是说从工夫完成上看是知至而后意诚,致知和诚意可以同时做工夫。朱子63岁后又提出知至之后意还有未诚之处来落实诚意的工夫。
或问:“知至以后,善恶既判,何由意有未诚处?”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后事。‘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一念才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无放心底圣贤,然一念之微,所当深谨,才说知至后不用诚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厘间不可不子细理会。才说太快,便失却此项工夫也。”②
对于知至以后还有意未诚的问题,朱子提出以克己工夫来解决。克己是知至以后的工夫,一念能克则成圣,一念放下心便不正。自古圣贤都没有放其心,但是在一念的微小处,是应当谨慎的地方,所以才说知至之后不用诚意的工夫是不够的。朱子又以人心道心相差毫厘却不可不仔细理会来说明在细微之处做诚意工夫的重要,因为诚意工夫是在微小处做工夫,所以朱子认为如果工夫做得太快,就会失去诚意工夫的意义。对于知至之后的“毋自欺”,朱子解释:“物既格,知既至,到这里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许多一齐扫了。若如此,却不消说下面许多。看下面许多,节节有工夫。”③可见,朱子认为克己、毋自欺都是知至以后诚意的工夫,而“毋自欺”是通过慎独和省察完成的。
门人曾光祖问:“物格、知至,则意无不诚,而又有慎独之说。莫是当诚意时,自当更用工夫否?”①朱子回答:“这是先穷得理,先知得到了,更须于细微处用工夫。若不真知得到,都恁地鹘鹘突突,虽十目视,十手指,众所共知之处,亦自七颠八倒了,更如何地慎独!”②在此,朱子提出慎独工夫是在知至之后的细微处做工夫,是真知以后的工夫,慎独完成的是致知所不能完成的部分工作,朱子说:“‘知至而后意诚’,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曰慎独。”③慎独是知至以后意诚的工夫,朱子又说:“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慎独者,诚意之助也。致知,则意已诚七八分了,只是犹恐隐微独处尚有些子未诚实处,故其要在慎独。”④在此朱子说明了致知完成了诚意的大部分任务,是诚意工夫的根本,所以知至在意诚之先,慎独是完成诚意两三分的工作,慎独是诚意的辅助工夫。朱子在《集注》时期已经以省察作为慎独和诚意的工夫方法,所以朱子又说知至后的诚意工夫需要通过省察完成,他说:“然‘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盖到物格、知至后,已是意诚七八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御寇,寇虽已尽剪除了,犹恐林谷草莽间有小小隐伏者,或能间出为害,更当搜过始得。”⑤由此可知,知至之后的诚意工夫包括了省察和慎独,慎独也需要通过省察来完成。
朱子又以致知和诚意来说明知行关系,致知为知,诚意是道德行动的开始,65岁时朱子说:“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①由此致知和诚意关系也说明了朱子知先行后的成德路径,因为诚意是自觉的道德实践的开始,所以诚意的地位就凸显出来。朱子强调诚意的完成很艰难,这与朱子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的观点相互印证。
《大学》之道,莫切于致知,莫难于诚意。意有未诚,必当随事即物求其所以当然之理。然观天下之事,其几甚微,善恶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杂乎芒芴之间者,静而察之者精,则动而行之者善。圣贤之学必以践履为言者,亦曰“见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后意无不诚,盖若泛论“知至”如诸家所谓极尽而无余,则遂与上文所谓“致知”者为无别。况必待尽知万物之理而后别求诚意之功,则此意何时而可诚耶?……窃尝体之于心,事物之来,必精察乎善恶之两端,如是而为善,则确守而不违,如是而为恶,则深绝而勿近(先生勿去此并上二句),亦庶几不苟于致知,而所知者非复泛然无切于事理,不苟于诚意,而好善恶恶直欲无一毫自欺之意。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大学》中最早开始的工夫是致知,而最难完成的是诚意。如果意有不诚的地方,一定要在事事物物中寻求所当然之理,即必须通过致知来诚意,致知是诚意的大段工夫。朱子又说天下之事,也有几微之处,在几微之处,善恶邪正、是非得失都是相糅相杂的,所以静时省察到其中的善是精,动时发为行的可以称为善,所以圣贤之学一定要以践履为标准。朱子提出如今周舜弼教人必说知至后意无不诚,但是如果泛论知至为知之极尽无余,则与致知没有分别。况且如果要等尽知万物之理后再做诚意工夫,则“意”什么时候能诚呢?在此,朱子提出致知就是为了诚意,诚意并不是在致知之外别做工夫。当事物来时,必须省察其善恶两端,如果为善则实守其善;如果为恶则去其恶。如此从致知上看则所知者皆合于事理,从诚意上看则好善恶恶而无一毫自欺之意。
朱子以毋自欺、慎独作为诚意的工夫,诚意是《大学》中最难完成的工夫,意诚也是最高的境界,所以朱子将诚意作为善恶评判的标准,朱子说:“‘格物是梦觉关。诚意是善恶关。过得此二关,上面工夫却一节易如一节了。到得平天下处,尚有些工夫。只为天下阔,须着如此点检。’又曰:‘诚意是转关处。’又曰:‘诚意是人鬼关!’”①朱子以意诚作为成德的标准,是修身工夫做高的境界。基于朱子对诚意工夫的重视,朱子去世前仍然对诚意的解释有许多讨论,《语类》中载了四段沈僩与朱子关于诚意的修改的讨论,一是问:“‘诚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旧注好。”②二是敬子问:“‘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某意欲改作‘外为善,而中实容其不善之杂’,如何?”③三是沈僩载:“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伤杂耳。某之言某,却即说得那个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说得是,盖知其为不善之杂,而又盖庇以为之,此方是自欺。谓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盖庇了,吓人说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谓如人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个不满处,他却不说是他有不满处,却遮盖了,硬说我做得是,这便是自欺。却将那虚假之善,来盖覆这真实之恶。某之说却说高了,移了这位次了,所以人难晓。大率人难晓处,不是道理有错处时,便是语言有病;不是语言有病时,便是移了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说时,便与那“小人闲居为不善”处,都说得贴了。’”①四是:“次日,又曰:‘夜来说得也未尽。夜来归去又思看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段,便是连那“毋自欺”也说。言人之毋自欺时,便要“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样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恶恶不“如恶恶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谓如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时,便当斩根去之,真个是“如恶恶臭”,始得。如“小人闲居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说。“闲居为不善”,便是恶恶不“如恶恶臭”;“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义都贴实平易,坦然无许多屈曲。某旧说忒说阔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样人如旧说者,欲节去之又可惜。但终非本文之意耳。’”②朱子甚至在易箦的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王懋竑说:“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犹修书不辍,夜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且曰:‘为学之要,惟在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久之,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至极而已矣。’”③如此可见,朱子最终以意诚为心与理贯通的境界,成为自觉的道德行动的开始。
2.以尽心为意诚
基于朱子晚年对心、性、情等概念都做了更为细致的剖析,特别是在对情的剖析中注意到心、知、意三者的关系,朱子注意到私意对本心的影响,再加上朱子晚年对气禀对心性结构影响的认识,朱子认识到没有一丝一毫私意的意诚的境界只靠致知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朱子改变了《格物补转》中以知至为贯通处的说法,知至并不代表诚意的完成,知至后还有诚意阶段的工夫。与此相应,朱子晚年后改变了《集注》中以《孟子》的尽心为《大学》的知至的观点,以尽心为意诚。
某前以孟子“尽心”为如大学“知至”,今思之,恐当作“意诚”说。盖孟子当时特地说个“尽心”,煞须用功。所谓尽心者,言心之所存,更无一毫不尽,好善便“如好好色”,恶恶便“如恶恶臭”,彻底如此,没些虚伪不实。童云:“如所谓尽心力为之之‘尽’否。”曰:“然。”①
由上文可见,朱子61岁时检讨自己以前将尽心解为知至有所不妥,同时提出应当以尽心为意诚,朱子认为孟子提出“尽心知性”之说是煞费苦心的,这里涉及朱子对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的关系的认识。朱子在《知言疑义》阶段已经提出“尽心须假存养”的观点,认为尽心须以存养为前提,穷理是穷本具之理,尽心是尽其所存之心。在此,朱子认为尽心的境界是尽到没有一丝一毫不尽的地步,好善与恶恶就如好好色和恶恶臭一样,真实不伪,其实就是意诚的境界。因为诚意是行动的开始,尽心也要从行动上理解,而不是从致知上理解,所以对于弟子提出尽心是不是尽心力而为之的问题,朱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可见尽心从工夫上说就是诚意,从境界上说就是意诚,也就是知行合一。由前分析可知,朱子将尽心理解为意诚的原因在于晚年重视私意和气禀的影响,知至时还不能尽心之体用,到意诚时才是心理合一、知行合一,才是真正尽心之体用。
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今人多是气质偏了,又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尽知,圣贤所以贵于穷理。又曰:“理虽具于吾心,还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个心在这里,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许多道理。少间遇事做得一边,又不知那一边;见得东,遗却西。少间只成私意,皆不能尽道理。尽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无有不合道理。”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本心本来虚灵明觉,万理具于心中,所以从理论上说人人应当知晓万理,但是大多数人都受到气禀的影响,再加上物欲的遮蔽,导致本心昏聩而不能尽知本具之理,正因为如此,圣贤才要重视穷理工夫。所以虽然万理已具于心,但不等于人人已知万理,要通过穷理才能真正知理,得理于心。虽然每个人都有具理之本心,如果不穷理以致知,难免受到私意影响而不能达到知至。朱子在此指出尽心就是要通过穷理和去除私意,也就是通过诚意阶段的工夫来使事事物物都合于理,最终实现尽心之体用。如此可见,要达到尽心的境界,在穷理工夫的基础上还有诚意工夫,也就是说知至不能作为尽心的完成,意诚才是尽心的完成。
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改变了以尽心为知至的观点,以尽心为意诚,如此尽心的工夫除了穷理致知的工夫之外,还要做诚意阶段的工夫,但是牟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朱子晚年对尽心说法的修正,仍然认为朱子的尽心是知至,最终将朱子的尽心思想判定为“认知地尽”,他说:“无论以‘知至’说尽心,或以‘诚意’说尽心,皆非孟子‘尽心’之义。……以‘知至’说尽心,是认知地尽……以诚意说尽心,是实行地尽。但此使行地尽却是依所知之理尽心力而为之,心成虚字,是他律道理,非孟子‘尽心’之义。”①牟宗三认为朱子以知至说尽心是“认知地尽”,又以诚意说尽心是“实行地尽”,但“实行地尽”是依据所知之理而尽心力而为之,是他律道德,此心不是孟子所言本心,所以无论是以知至说尽心还是以诚意说尽心都不是孟子言尽心的本意。牟宗三的结论是朱子以知的工夫涵盖行的工夫,使行的工夫成为他律道德。但是,朱子晚年以尽心为意诚的原因即在于认识到致知以后诚意阶段工夫的必要性,致知阶段的工夫不能涵盖诚意阶段的工夫,诚意有独属于诚意阶段的工夫,即省察与慎独。省察与慎独的完成在知至之后,但从做工夫上说慎独与省察并不以穷理致知为前提,而是以持敬涵养为前提,只要确立了涵养为本的工夫,慎独与省察作为诚意阶段的工夫是自觉自律而非他律。牟宗三在此认为朱子以实行言尽心,实行是依据所知之理而尽心力而为之,从而混淆了朱子言知先行后是从工夫的完成上说的,而非从工夫的下手处说,也就是说意诚的完成一定要在知至之后,但是致知的同时也要做诚意阶段的工夫,所以诚意工夫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不以穷理致知为前提,可见认知地尽、他律道德是牟宗三对朱子的误判。朱子说:“论其理,则心为粗而性天为妙;论其功夫,则尽为重而知为轻。故云‘所谓尽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时事,但以表里虚实反复相明,非有功夫渐次也’。”②如此可见尽心的完成在知性之后,穷理工夫在尽心之先,并不能说明朱子有重知的他律道德的倾向,相反,朱子将尽心的完成推至诚意阶段说明了尽心比知性更为重要,而诚意阶段的慎独和省察工夫的独立性也说明了尽心之心并不是虚说,心仍然要发挥主宰作用,尽心、诚意并没有因为穷理的限制而成为认知地尽、外在的诚的他律道德。总而言之,朱子晚年将尽心作为意诚的境界恰恰说明了朱子对道德行动的重视,说明了朱子知先行重、知行合一的知行观。
(四)博学而反约
由前文分析可知,致知而力行、积累至贯通、知至而后意诚这三组关系体现出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但是朱子又从《论语》中博文与约礼的关系、致知与克己复礼的关系、《孟子》中博学与反约的关系来说明成德的路径,体现出对“四书”工夫思想的贯通,也说明了以“四书”中的思想做相互印证是朱子工夫思想的特色。朱子说:“侯氏谓博文是‘致知、格物’,约礼是‘克己复礼’,极分晓。而程子却作两样说,便是某有时晓他老先生说话不得。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这却是知要。盖天下之理,都理会透,到无可理会处,便约。盖博而详,所以方能说到要约处。约与要同。”①侯氏是指二程表弟也是二程门人侯仲良,侯仲良以博文为致知格物,约礼为克己复礼,朱子认为侯氏将博文约礼区分得很明白,反而认为二程有时候说得不够准确。这也说明朱子晚年将克己复礼理解为践履,从朱子晚年将克己落实到复礼上说可以看出来。朱子又以《孟子》言博学明理是为了反其约来说明知不是目的,行才是目的,博学就是明理,到贯通处就是自我的约束就是克己复礼。博学和反约与致知和力行、致知和诚意一样都是并行不悖的两个工夫,不能偏废一方,朱子又说:“务反求者,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堕于一偏。此皆学者之大病也!”②朱子强调不能只务反约而认为泛观博览为外,也不能只务泛观博览,而以内省工夫为狭隘,博览与反约二者不能偏废,知行并重,知与行要互相配合。
朱子此后又论及博学和反约的次序,他说:“知读《论》《孟》不废,其善。且先将正文熟读,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诸先生说有发明处者,博观而审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于己者,皆当玩味,未可便恐路径支离而谓所有不必讲也。”①从工夫完成的先后来看应该是先博文后反约,不能因为担心工夫路径的支离而偏废一方,知行两个工夫要同时并进。同年,朱子明确了博学和反约就是知行关系,他说:“圣人生知,固不待多学而识,学者非由多学,则固无以识其全也。故必格物穷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诸约。”②朱子区分了圣人生而知之与学者学而知之,认为大多学者成德的途径无非多学习,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博学,又通过主敬力行达到反之约。主敬属于力行,而不是笃行,这是要注意的。由此可知,朱子的工夫规模可以归纳为知行两途,为学不过知行两件事,他说:“学者以玩索、践履为先。”③又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知得,守得。”④甚至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⑤朱子甚至提出圣人教人只是博文约礼两个工夫,他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圣门教人,只此两事,须是互相发明。约礼底工夫深,则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则约礼底工夫愈密。”⑥以上都说明博学与反约、博文与约礼、理会与践行、玩索与践履都是朱子表达知行关系的不同说法。朱子认为从做工夫上看,二者互相配合、互相发明,行是对知的持守;从工夫完成的先后上看,则是知先行后、行比知重。所以,朱子强调知行要逐项做工夫,不能以工夫完成的境界处作为做工夫处,朱子说:“不要说总会。如‘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说总会处?”①朱子认为做工夫和工夫的境界需要区分,从做工夫上说二者分别做工夫,知有知的工夫,行有行的工夫,朱子说:“如颜子‘克己复礼’,亦须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成只守个克己复礼,将下面许多都除了!”②工夫的完成要以道德行动作为标准,但做工夫不能从境界处、总会处、贯通处入手,以致知作为成德工夫的开始是朱子晚年对成德路径的强调。
(五)下学而上达
“下学而上达”并不是朱子晚年时才提出的观点,1174年朱子说:“圣门之学,下学而上达,至于穷神知化,亦不过德盛仁熟而自至耳。”③在此,朱子以《论语》中孔子所言“下学而上达”作为当时对成德路径的认识,以《系辞下》中“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作为修养工夫之后的仁的最高的境界。“下学而上达”说明了成德工夫的基础是下学,通过下学的积累而贯通至上达的境界,这与朱子之前所言的工夫路径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1.批陆“上达而下学”
朱子晚年言“下学而上达”主要针对陆学而发,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注重气禀对人成德的影响,认识到成德的艰难,所以更加重视穷理、致知、省察等下学工夫的积累,鼓励人做工夫勇猛精进,强调以孔子下学而上达为成德路径。由于陆学不言气禀对本心的影响,以尊德性为先,注重发明本心,工夫不从致知入手,而从涵养践履入手,认为知必能行,行就是知,与朱子知先行后、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恰恰相反,所以朱子批评象山将成德说得太快。
问:“陆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上做去。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须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虽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也须是‘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方得。……大抵今之为学者有二病,一种只当下便是底,一种便是如公平日所习底。却是这中间一条路,不曾有人行得。”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门人认为陆象山以为成德“当下便是”,将成德说得太快,朱子认为孔孟圣贤没有教人这样做工夫,圣贤都是教人从平实的地方做工夫,克己复礼是必须先克尽己私才能归仁。孟子虽然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必须“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才能成为尧舜。在此朱子其实批评象山只教人立志却不教人穷理,导致议论太高。朱子指出当下为学有两种弊病,一种只说“当下便是”,一种便是从平日中积累练习,中间有一条路即“下学而上达”。对于陆子静的“当下便是”,朱子做了详细的剖析。
或问:“陆象山大要说当下便是,与圣人不同处是那里?”曰:“圣人有这般说话否?圣人不曾恁地说。圣人只说‘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今截断‘克己复礼’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圣人当年领三千来人,积年累岁,是理会甚么?何故不说道,才见得,便教他归去自理会便了?子静如今也有许多人来从学,亦自长久相聚,还理会个甚么?何故不教他自归去理会?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须是做得尧许多工夫,方到得尧;须是做得舜许多工夫,方到得舜。”①
由引文可见,对于门人提出象山言“当下便是”与圣人做工夫的不同之处,朱子则强调圣人没有提出过“当下便是”的说法,圣人只教人克己复礼,现在陆子静却截断克己复礼,认为当下就可以为仁,即不知孔子当年带领三千弟子积年累岁地理会道理,并没有让弟子见得本心就叫他自己回去理会。朱子指出子静也是有许多人来从学的,也与学生长久相聚,为何不叫学生自己回去理会。朱子认为孟子所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必须得做尧舜的许多工夫,才能到达尧舜的境界。
他是会说得动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会使得人都恁地发颠发狂。某也会恁地说,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坏了人。他之说,却是使人先见得这一个物事了,方下来做工夫,却是上达而下学,与圣人“下学上达”都不相似。然他才见了,便发颠狂,岂肯下来做?若有这个直截道理,圣人那里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②
朱子认为陆子静之论立论很高,说得很好听,使别人听了很高兴,甚至会使人发癫发狂。朱子说这种使人高兴的话他也会说,只是不敢,怕误导了别人。陆子静的工夫路径就是使人先见境界才下手做工夫,这种路径是先上达后下学,与圣人“下学而上达”都不一样。朱子又指出“上达而下学”的弊端在于人先见了上达便癫狂自大,不肯再去做下学的工夫。如果真的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可以成德,那圣人怎么还需要教人从下学一步步做工夫到上达。可见,朱子晚年辟“先见天理源头”不仅针对陈淳、廖子晦而发,更是针对陆学而发。
朱子认为立高论而欠缺下学的工夫既是禅学也是陆学的问题,他说:“敬子诸人却甚进,此亦无他,只是渠肯听人说话,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闲说耳。大率江西人尚气,不肯随人后,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烦如此逐些理会,须要立个高论笼罩将去。”①69岁后朱子批评陆子静误人,《语类》载:“因言读书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穷得一句,便得这一句道理。读书须是晓得文义了,便思量圣贤意指是如何?要将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问为学,曰:‘公们都被陆子静误,教莫要读书,误公一生!……今教公之法:只讨圣贤之书,逐日逐段,分明理会。且降伏其心,逊志以求之,理会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会得一段,便一段义明;积累久之,渐渐晓得。’”②朱子认为陆子静自己不重下学工夫,又教人不要读书,误导后学,对学术风气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朱子强调读书、穷理工夫,皆是从一句话、一件事中做起,工夫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贯通,无论是下学还是上达都需要逐项理会,积累久久才能达到贯通的境界。由上分析可知,朱子强调“下学而上达”与朱子强调以致知作为工夫的入手处相对应,朱子注重格物、穷理等下学工夫的积累终与陆学的成德路径相区别。
2.辟“先见天理源头”
朱子晚年时期因陈淳喜言“先见天理本原”,所以特别向陈淳阐明“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对门人偏向主敬涵养进行纠偏。当陈淳提出下学是不是大段工夫时,朱子说:“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不要理会下学,只理会上达,即都无事可做,恐孤单枯燥。”①朱子指出要多说下学的工夫,少说上达的工夫,因为没有下学就不可能有上达,朱子说:“然尝以熹所闻圣贤之学,则见其心之所有不离乎日用寻常之近小,而其远者大者自不待于他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而无所归宿也,故曰‘下学而上达’。”②朱子指出下学工夫是离日用寻常最近的地方,做工夫应先从近的地方做起,如果先从上达处做,则过于空疏放浪。同时朱子也指出不能只做下学的工夫,否则气象狭隘,但如果只理会上达,则都是高深的道理,无事可做,则孤单枯燥。所以下学与上达都要做工夫,久了自然能从下学贯通到上达,但是如果只想着贯通处,不做下学的工夫则无法成德,朱子说:“譬如耕田,须是下了种子,便去耘锄灌溉,然后到那熟处。而今只想象那熟处,却不曾下得种子,如何会熟?”③可见,朱子认为应该从下学工夫开始做起,没有下学就不可能上达,对于下学的工夫内容,朱子也有详细的讨论。
胡叔器因问:“下学莫只是就切近处求否?”曰:“也不须恁地拣,事到面前,便与他理会。且如读书:读第一章,便与他理会第一章;读第二章,便与他理会第二章。今日撞着这事,便与他理会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会那事。万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拣大底要底理会,其它都不管。程先生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此皆不是。”①
前文分析可见,朱子提出要从日用处先做工夫,即先做下学工夫,门人胡安之因此提出下学是否只是就近处求,朱子则回答说不是有意拣近处做工夫,而是由具体的事决定,遇到什么事,就在什么事上理会,就像读书,读第一章,便理会第一章,读第二章便理会第二章,万事只是一理,不能只挑大的要紧的事去理会,其他事都不管。朱子又引二程言穷理不一定要穷尽天下之理,也不是穷得一理就停止,但是积累很多后,自然有贯通领悟的地方。二程又说从自己身上以至于万事万物之理理会得多了自然豁然有觉悟的地方。可以看出,穷理就是下学的积累,贯通是上达,朱子晚年以意诚为心与理的贯通处。朱子又提出现在有人专务博文却要去穷尽天下之理,专务约礼又说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这都是不对的,因为颠倒了下学和上达的工夫次序。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子反对先从上达做工夫与反对先从贯通处做工夫、反对先见天理源头是一致的,这也是朱子晚年将居敬穷理互发、知行互发限定在工夫的境界义的原因。朱子强调做工夫要从下学做起,与朱子晚年重视穷理、致知、省察的工夫也是一以贯之的。
曾子父子之学自相反,一是从下做到,一是从上见得。子贡亦做得七八分工夫,圣人也要唤醒他,唤不上。圣人不是不说这道理,也不是便说这道理,只是说之有时,教人有序。子晦之说无头。如吾友所说从原头来,又却要先见个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处。子晦疑得也是,只说不出。吾友合下来说话,便有此病;是先见“有所立卓尔”,然后“博文约礼”也。……下学上达,自有次第。于下学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学中,如致知时,亦有理会那上达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这事上,理会个合做底是如何?少间,又就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见得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见得这事道理原头处。逐事都如此理会,便件件知得个原头处。”①
曾子父子的工夫路径是相反的,曾点是先见上达,曾子是先从下学开始做,子贡是下学做了七八分,孔子要启发他,但没有成功,这说明圣人教人成德的方法有很多,因人因时而异。但廖子晦的说法没有根据,如果说从源头来,又要在源头前面先见个天理才去做工夫,这就是问题所在,就等于说先见“所立卓尔”的境界,然后再去博文约礼,二者都是上达处,不是做工夫处。朱子提出下学上达中自然有工夫次第,下学中,致知就是在事上理会理以及理之所以然,再去思考如何合于理、为什么能合于理,如此最后见到道理的源头,如果逐事都如此理会,则件件事情都能知道道理的源头处,所以道理的源头处是从格物、穷理、致知上逐渐完成的,由此也说明了下学和上达的关系。朱子晚年反对廖子晦“先见天理源头”,也反对陈淳“只吃馒头尖处”,1199年,朱子与陈淳相别十年后会面坐论。朱子见陈淳言主敬涵养则件件天理流行可见也有“先见天理源头”的问题,故与陈淳做了详细的讨论。
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淳曰:“数年来见得日用间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无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闪避。……而其所以为此理之大处,却只在人伦;而身上工夫切要处,却只在主敬。敬则此心常惺惺,大纲卓然不昧,天理无时而不流行……”先生曰:“恁地泛说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劳心落在无涯可测之处。”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问陈淳相别十年是否有什么重要的修养方法和问题可以讨论,陈淳认为自己数年大事小事都见得分明,每件事情都能做到天理流行,使事合于理。朱子认为天理最重要的地方在人伦日用中,所以自身最关键的工夫在于主敬。陈淳进一步提出主敬则此心常惺惺,大纲卓然不昧,天理无时不流行。对此,朱子表示这样泛说也容易,朱子思考了很久又指出陈淳偏向主敬恐怕会将心落在无涯可测之处,即恐怕会落入佛老虚无之说。所以当陈淳接着又问孔子“与点”②一段如何理解时,朱子就直接指出陈淳这样的理解是只吃馒头尖尖,提醒陈淳要重视下学的工夫。
因问:“向来所呈与点说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爱人说此话。《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做工夫处。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圣贤说事亲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长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处。通贯浃洽,自然见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说‘与点’,正如吃馒头,只撮个尖处,不吃下面馅子,许多滋味都不见。……昨廖子晦亦说‘与点’及鬼神,反复问难,转见支离没合杀了。圣贤教人,无非下学工夫。”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对陈淳提出自己不喜欢别人过于关注孔子表扬曾点这段话,朱子认为孔子教人都是从做工夫处教人,不能因为夫子有一次赞同曾点的志向便将人伦日用近处的工夫都省去。圣贤说事亲、事君、事长、言、行都是做工夫的地方,如果只说“与点”即只是立志,就像吃馒头只吃馒头尖处不吃下面的馅,所以下面许多滋味都不知道。朱子认为廖子晦也说“与点”,与陈淳都是一样的问题。由此可见,朱子去世的前一年仍在讨论成德的工夫路径,一方面基于对陆学上达而下学的批评,一方面基于对门人先见天理源头的检查,二者的问题都在于不重视下学工夫,没有遵循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朱子最后提出“圣贤教人,无非下学工夫”,这句话是说得很重的,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在上达处做工夫的意义,上达是通过下学积累到一定程度所达到的境界,所以不是做工夫处。
一 涵养与致知
(一)持敬涵养为本
1.持敬为本,穷理为助
朱子在中年时期确立了以持敬涵养为成德的根本工夫,晚年后朱子仍然保持持敬存养、持敬为穷理之本、持敬即求放心、持敬贯彻大学工夫始终的基本观点。朱子说:“敬则心存,心存,则理具于此而得失可验,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①61岁时又说:“穷理以虚心静虑为本。”②同年又说:“学者堕在语言,心实无得,固为大病。……近因病后,不敢极力读书,闲中却觉有进步处,大抵孟子所论‘求其放心’是要诀尔。”③进入晚年后,由于年老多病,朱子越发认识到涵养是成德的关键。62岁时又说:“所谓‘守得定,方可以致知穷理’,此说甚当。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岂是此事之外更无他事?只是此本不立,即无可下手处。此本既立,即自然寻得路径进进不已耳。”④在此朱子指出了涵养是成德的根本工夫,是其他修养工夫的前提。65岁时朱子又说:“先立根本、后立趋向,即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后,然后自能寻向上去’,亦此意也。”⑤持敬涵养是立根本的工夫,必须先落实,立下根本之后再进一步穷理致知,所以说“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同年朱子又说:“主一无适者亦必有所谓格物穷理者以先后之也,故程夫子之言曰:‘涵养必以敬,而进学则在致知。’此两言者如车两轮,如鸟两翼,未有废其一而可行可飞者也。世衰道微,异说蜂起,其间盖有全出于异端而犹不失于为己者,其他则皆饰私反理而不足谓之学矣。”①在此朱子仍以主一无适言持敬涵养,体现出朱子晚年仍遵从二程涵养与致知两大工夫路径,涵养与致知作为成德的两大基本方法,二者不能偏废一方。朱子晚年特别强调持敬与穷理不可偏废一方,偏重任何一方都是错的。他说:“见人之敏者,太去理会外事,则教之使去父慈、子孝处理会,曰:‘若不务此,而徒欲泛然以观万物之理,则吾恐其如大军之游骑,出太远而无所归。’若是人专只去里面理会,则教之以‘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要之,内事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但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若是工夫中半时,已自不可。况在外工夫多,在内工夫少耶!此尤不可也。”②朱子认为程子教人,因人而异,如果太理会外面事,则要注意以持敬为本,不能泛然观理,如果只专从里面理会,则要注意穷理的必要,持敬穷理应当一起理会,但是在持敬涵养上必须用六七分力气,在格物穷理上可用三四分力气,可见朱子的成德工夫主要依靠涵养而不是穷理,穷理是对涵养的辅助,他说:“持敬是穷理之本;穷得理明,又是养心之助。”③由此可见,朱子晚年持敬为本的地位没有改变,涵养依然是成德工夫的第一义。
2.批浙学支离
朱子在55岁后开始批评浙中吕氏门人欠缺持守工夫,不在本原处辨天理人欲,最后流为事功之学,并同时检查自身与浙中学者的支离问题,进入晚年后,朱子继续指出浙中学者欠缺涵养本原的工夫,批评吕氏门人支离。
然觉得今世为学不过两种,一则径趋简约,脱略过高;一则专务外驰,支离繁碎。其过高者固为有害,然犹为近本;其外驰者诡谲狼狈,更不可言。吾侪幸稍平正,然亦觉欠却涵养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所寄疑义,盖多得之,已略注其间矣。小差处不难见,但却欲贤者更于本原处加功也。①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当今为学的问题总结起来可以为两种,一种是做工夫路径过于简约,脱略文字,喜欢高论;一种是专务外驰,不重涵养,如此则工夫支离繁碎。明显,前者指陆学,后者针对浙中吕氏门人而发。朱子认为陆学立论过高固然有害,但是贴近根本,而工夫向外求索则诡辩奇怪,更不值得说。可以看出,朱子认为相比陆学,浙学的问题更严重,可见朱子坚持以涵养工夫作为成德的根本,其地位不能动摇。同时,朱子提出自己的工夫架构稍稍平正一些,但还是觉得自己涵养本原的工夫有所欠缺,应该进行反思,同时也建议吴伯丰在涵养本原的工夫上加倍努力。62岁时陆子静还未去世,当时朱子对陆学及门人的批评是十分严厉的,但是与浙学相比,朱子认为浙学欠缺涵养的问题比陆学更严重,如此可见朱子批评浙学的程度,但朱子并没有用很严厉的语气或者很重的话语批评浙学。朱子62岁时,郑可学对朱子说不能去见陆子静,担心受其影响学会参禅,对此朱子说:“此人言极有理。吾友不去见,亦是。然更有一说:须修身立命,自有道理,则自不走往他。若自家无所守,安知一旦立脚得牢!正如人有屋可居,见他人有屋宇,必不起健羡。若是自家自无住处,忽见人有屋欲借自家,自家虽欲不入,安得不入?切宜自作工夫!”①可见,朱子认为陆子静之学固然不可取,但是修身立命必须以涵养工夫为本才能有归处,而浙中吕氏的问题比陆子静不立文字更严重。吕祖俭对朱子说:“今所虑者,非在于堕释氏之见,乃在于日用之间主敬守义工夫自不接续而已。若于此能自力,则敬义夹持,此心少放,自不到得生病痛也。”②朱子回应:“此正如明道所说扶醉人语,不溺于虚无空寂,即沦于纷扰支离矣。”③可见朱子言空虚针对陆学,言支离针对吕学。68岁时,朱子又致信万正淳批评吕祖俭不知以涵养为本。
子约之病,乃宾主不明,非界分不明也。不知论集义所生则义为主、论配义与道则气为主,一向都欲以义为主,故失之。若如其言,则孟子数语之中,两句已相复矣,天下岂有如此絮底圣贤耶!子约见得道理大段支离,又且固执己见,不能虚心择善,所论不同处极多,不但此一义也。④
朱子认为吕祖俭的问题不是不辨义利,而是宾主不明,不以涵养为本。吕祖俭不知言集义所生是以义为主,不知言配义以道时是以气为主,一直以义为主,所以有了偏失之处。朱子认为如果按吕祖俭都以义为主,则孟子言集义所生和配义与道就重复了,圣贤不可能如此烦琐。朱子认为吕子约理解圣贤的道理大段支离,又固执己见,不虚心采纳别人的说法,所以不只与朱子在这点上不同,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同。朱子认为吕祖俭质朴老实,但看道理不分明,表示惋惜。次年朱子又致信吕祖俭,建议他同时做致知与涵养的工夫,如此才能解决支离的问题。
窃意贤者用力于此,不为不久,其切问近思之意不为不笃,而比观所讲与累书自叙说处,觉得瞻前顾后,头绪太多,所以胸次为此等丛杂壅塞缠绕,不能得明快直截,反不得如新学后生闻一言且守一言,解一义且守一义,虽未能便有所得,亦且免得如此支离纷扰,狼狈道途,日暮程遥,无所归宿也。①
朱子指出吕子约做读书工夫过于瞻前顾后,头绪太多,所以显得过于烦琐缠绕,不够明白直接,反而不如闻一言守一言,解一义且守一义,也就是致知与涵养并进,互相配合,如此虽然不能马上有很大的成效,也可以避免工夫支离纷扰及工夫路径过于曲折缠绕。
(二)涵养与致知并进
1.涵养为本与致知为先
朱子同时有先致知后涵养和涵养为致知之本的说法,二者看似矛盾,朱子晚年做了解释,涵养工夫为先是从大纲上说,《语类》载:“问致知涵养先后。曰:‘须先致知而后涵养。’”问:“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纲说。要穷理,须是着意。不着意,如何会理会得分晓。”②在此,朱子提出涵养在致知之先是从大纲上说,是总论,相当于指导思想。在做工夫上,要从致知入手。《语类》又载:“王德辅问:‘须是先知,然后行?’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曾点与曾子,便是两个样子:曾点便是理会得底,而行有不掩;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处。”①对于王德辅提问是否先知然后才能行,朱子则回答不能因为不明理就不持守,朱子要说明不能因为知没有完成就不做行的工夫,强调持守工夫要先落实。如果只做穷理不去持守,则会出现“知而不行”的情况,如果能像曾子一样先持守,则能在持守中渐渐明理,最终是能达到知行合一的。在此,朱子说明了持守为先、持敬以穷理的原理。持敬为先与致知作为大学工夫的入手处不矛盾,朱子说:“‘致知’一章,此是大学最初下手处。若理会得透彻,后面便容易。”②大学工夫的规模体现了成德的次序,致知作为大学工夫的入手处,说明了成德的次序从致知开始。
夫庄敬持养,此心既存,亦可谓之无邪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穷,则于应事接物之际不能处其当,则未免于纷扰,而敬亦不得行焉。虽与流放而不知者异,然苟不合正理,则亦未免为妄与邪心也。故致知所以为《大学》之首,与其用力之次第,则先生所作《大学传》所引程子、游氏、胡氏之言数条是也,但庄敬持养又其本耳。③
朱子认为庄敬持养后本心既存,理论上可以说没有邪心存在,但是如果知有未至、理有未穷,则在具体的应事接物中不能妥当,本心也难免受到纷扰,如此敬也不能再发生作用。在此,朱子说明了穷理、致知工夫对持敬的影响。朱子认为这虽然与放失本心而不自知的情况不同,但心在事事物物中不能合于理,则难免成为邪妄之心,这就是致知之所以成为大学工夫之首的原因,但是同时庄敬持养又是根本的工夫。在此,朱子说明了致知作为大学工夫的入手处与持敬涵养为根本工夫不是矛盾的,涵养与致知在做工夫上是同时进行的。
任道弟问:“或问,涵养又在致知之先?”曰:“涵养是合下在先。古人从小以敬涵养,父兄渐渐教之读书,识义理。今若说待涵养了方去理会致知,也无期限。须是两下用工,也着涵养,也着致知。伊川多说敬,敬则此心不放,事事皆从此做去。”贺孙。《广录》云:“或问存养、致知先后。”曰:“程先生谓:‘存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盖古人才生下儿子,便有存养他底道理。父兄渐渐教他读书,识义理。今人先欠了此一段,故学者先须存养。然存养便当去穷理。若说道,俟我存养得,却去穷理,则无期矣。”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解释所谓涵养在致知之先是从总体而言的,古人从小就以敬完成了涵养工夫,如此再去读书求义,所以古人的涵养工夫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完成了,至大学阶段时就可以直接做致知工夫。因为今人都缺了小学阶段的持敬涵养,所以必须先落实存养工夫,但是存养和穷理要一起做,如果涵养好了再去穷理,则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涵养好,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穷理,所以涵养和穷理是必须同时做的,持敬本心的同时,事事都从持敬做去。
2.居敬穷理互发是境界
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更加注意强调涵养和致知不可偏废一方,涵养与致知如鸟之双翼要两下用功,可以看出朱子比较重视涵养与致知对彼此的相互作用。朱子说:“(涵养与致知)二者偏废不得。致知须用涵养,涵养必用致知。”①61岁时又说:“学者若不穷理,又见不得道理。然去穷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这里。”②涵养与致知二者不可偏废一方,二者互相配合,偏废任何一方,另一方的工夫都不能完成。他又说:“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③又说:“涵养中自有穷理工夫,穷其所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养其所穷之理,两项都不相离。才见成两处,便不得。”④如此可见,朱子提出不能穷理也不能持守,涵养中自有穷理,穷理是穷所涵养之理,穷理中自有涵养工夫,而涵养是养所穷之理,二者是互相包含的,两不相离,不能将二者分为两处做工夫。63岁时,朱子直接提出持敬穷理不能分为两节工夫,他说:“然‘敬’即学之本,而穷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两截看也。”⑤持敬是为学的前提,穷理是为学的内容,二者不可分作两节工夫,朱子又以下雨与蒸汽的循环做比喻来说明涵养与穷理的互相发明。
人之为学,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后,到处湿润,其气易得蒸郁。才略晴,被日头略照,又蒸得雨来。前日亢旱时,只缘久无雨下,四面干枯;纵有些少,都滋润不得,故更不能蒸郁得成。人之于义理,若见得后,又有涵养底工夫,日日在这里面,便意思自好,理义也容易得见,正如雨蒸郁得成后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者,日间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养工夫。设或理会得些小道理,也滋润他不得,少间私欲起来,又间断去,正如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①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做学问就像下雨一样,下雨后到处湿润,水汽容易蒸发,等天晴被太阳照一照,水蒸气化为雨落下来,但如果一直干旱无雨,空气干枯,下一点雨也无法滋润,更谈不上蒸得水汽。就像人对于义理,如果见得义理后,又做涵养工夫,义理便能日日记在心里,义理也容易理解,就像下雨后水汽蒸发得雨。如果不做涵养工夫,或许能理会一些小道理,对涵养帮助不大,私欲很快就会起来影响本心,使涵养工夫出现间断,就像干旱很久了空气里没有水汽蒸出雨是一样的道理。在此朱子说明了涵养与穷理相互发明、互相促进,偏失一方就会影响另一方。65岁后,朱子直接提出居敬穷理互发的观点,他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②在此,朱子以左脚和右脚互相配合行走来比喻居敬与穷理互相促进的关系,能持敬则穷理的工夫更细密,能穷理则持敬的工夫更进一步,就像两只脚走路,一只脚走,另一只脚停,但都在完成走路这件事。朱子也说明了持敬是向内收敛,穷理是向外致知,二者的方向不同,所以两足同时走路是不行的。朱子最后提出居敬穷理互发是境界,比较严密地说明了二者的关系,他说:“初做工夫时,欲做此一事,又碍彼一事,便没理会处。只如居敬、穷理两事便相碍。居敬是个收敛执持底道理,穷理是个推寻究竟底道理。只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时,则自不相碍矣。”①朱子提出居敬和穷理刚开始做工夫的时候其实是互相妨碍的,但如果两个工夫都做到纯熟,则不会互相妨碍,而是互相配合。
(三)批陆:不重穷理
1.言“识心”之弊
朱子在“中和新说”时期就已经讨论了“识心”的说法,当时朱子并没有直接否定“识心”的说法,并且从儒家的立场对“识心”做了解释,以区别禅学“识心”的说法。
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书》所谓“天叙”“天秩”“天命”“天讨”,《孟子》所谓“物皆然,心为甚”者,皆谓此也。若不于此先致其知,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如此,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且如释氏擎拳竖拂、运水般柴之说,岂不见此心?岂不识此心?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正为不见天理而专认此心以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耳。前辈有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盖谓此也。②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儒家做工夫最关键以穷理为先,一物有一物之理,必须先明白一物有一物之理,然后心之所发才能各有自己的准则,孟子所说“物皆然,心为甚”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此,朱子提出必须先明白一物有一物之理,心才能够依据准则而发,说明了大学工夫的次序。朱子又提出如果不在心上先致心之知,使其见到心所以为心的道理,否则格物致知过于广泛而没有准则,则其心之所存所发,无法自然合理。在此,朱子以致心之知来解释“识心”,以“识心”为格物致知的前提,实际上以涵养本原解释“识心”。朱子认为佛家也说要见此心、识此心,但是佛家的“识心”、见心的工夫不是尧舜之道,因为不见心中之理,而专认心为主宰,不知心为主宰的原因,如此心则不能免于私欲的影响。由此,朱子说明了儒家和佛家言“识心”的区别,朱子认为儒家的心是本心具理,所以穷理工夫之前的“识心”是识心中之理,为穷理提供是非准则,而“识心”的目的是认识到此心为主宰,保证此心为主宰。佛教的“识心”则是只以心为主宰,而不明白心为主宰的依据在于心中本具之理,所以空言“识心”。可以看出,朱子当时并没有否定“识心”的说法,“识心”能认识到心中万理具备而有成德的标准和可能,所以在朱子53岁时没有反对项平父所说“此心元是圣贤,只要于未发时常常识得,已发时常常记得”①,可见朱子此处以“识心”为未发前涵养工夫。进入晚年后,朱子改变了“识心”为未发前涵养工夫的说法,以致知解释“识心”,提出“识心”必须经过穷理的积累。
如邵子又谓“心者性之郛郭”,乃为近之。但其语意未免太粗,须知心是身之主宰而性是心之道理,乃无病耳。所谓“识察此心,乃致知之切近者”,此说是也。然亦须知所谓识心,非徒欲识此心之精灵知觉也,乃欲识此心之义理精微耳。欲识其义理之精微,则固当以穷尽天下之理为期,但至于久熟而贯通焉,则不待一一穷之,而天下之理固已无一毫之不尽矣。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今先立定限,以为不必尽穷于事事物物之间而直欲侥幸于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卤灭裂而终不能有所发明也。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邵雍所言“心者性之郛郭”比较贴近地说明了心性关系,但语意未免太笼统,不够细致,因为只说明了心承载性,但没有体现心性关系的核心在于心是身之主宰的原因,在于性是心的道理。在心性关系的基础上,朱子肯定“识心”与致知最为贴近,朱子又强调要知道“识心”并不是认识此心之知觉的功能,而是要认识心中精微的义理,而想要认识心中精微的义理,就必须以穷尽天下之理为目标,在久久熟练后达到贯通的境界。贯通之后则不用一一去穷理,天下之理都能穷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是学者通过努力做工夫穷理纯熟后融会贯通的缘故。如此可见朱子以致知解释“识心”,“识心”要通过穷理的积累达到贯通的境界。这说明朱子提出“识心”之说本来没有错,但是却被后人曲解误用了。朱子认为“识心”之弊在于专是务虚而又高论狂妄,所以朱子晚年言“识心”之弊主要针对陆学而发。
近来学者多说“万理具于心,苟识得心,则于天下之事无不得其当”,而指致知之说为非,其意大率谓求理于事物,则是外物。谊窃谓知者心之所觉,吾之所固有,盖太极无所不该,而天下未尝有心外之物也。惟其汩于物欲,乱于气习,故其知乃始蔽而不明。而敬以持之、思以通之者,亦曰开其蔽以复其本心之知耳。程子曰“凡一物有一理,须是穷致其理”者,岂皆穷之于外哉?“在物为理,处物为义”,所以处之者,欲穷其当,则固在我矣。……必也如程子所谓“觉悟贯通,于天下万物之理无一毫之不尽,则义精而用妙”,始可以言尽心知性矣。不知或者识心之说,岂一超直入者乎?……恐不可专以庄敬持养、此心既存为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纷扰、敬不得行然后为有妄之邪心也。所论近世识心之弊,则深中其失。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推此以穷天下之理。今之所谓识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礼益卑,今人则论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见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近来学者喜欢说万理具于心,只要识心则天下之事都能得到妥当的处理,由此而认为没有必要做穷理致知的工夫,其中大概意思是穷理是从外物中求理,是心外的工夫。对此,朱子提出知是心之所觉,知觉是本心所固有的,该遍天地万物,所以天下没有心外之物,也没有心外之理,只是因为物欲的遮蔽、习气的扰乱才使知觉被遮蔽而不光明,而持敬、穷理的工夫都是去蔽恢复本心之知觉的工夫。程子说一物有一物之理,必须穷尽其理,但是穷理并不是穷心外之理。朱子以程子言觉悟贯通后才可以言尽心知性为据,提出不经过穷理直言“识心”,工夫太过“一超直入”。在此基础上,朱子进一步提出工夫不能专以持敬涵养,如不务穷理最终难免成为邪妄之心,这是专言“识心”造成的弊病。朱子提出古人对存心的重视是将存心推至穷理工夫,而今人说“识心”则是将理存于心外,古人知得越多越谦虚,但现在的人喜欢高谈阔论又十分狂妄,可以看出朱子在此所批评的是陆学。心固不可不识,然静而有以存之,动而有以察之,则其体用亦昭然矣。近世之言识心者,则异于是。盖其静也初无持养之功,其动也又无体验之实,但于流行发见之处认得顷刻间正当底意思,便以为本心之妙不过如是……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耳,此事一过,此用便息,岂有只据此顷刻间意思便能使天下事事物物无不各得其当之理耶?所以为其学者,于其功夫到处亦或小有效验,然亦不离此处,而其轻肆狂妄、不顾义理之弊,已有不可胜言者。此真不可以不戒。然亦切勿以此语人,徒增竞辨之端也。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再次对方宾王提出心固然不能不识,“识心”就是静时存养、动时察识,如此则心之体用昭然明白。在此,朱子又以存养和省察为“识心”工夫。朱子提出近世言“识心”则不是如此理解的,在静时没有持敬存养,动时又不实际去省察,而只是在流行发见之端认得道理,便以此为心之神妙的全部内容,而不知此只是心之用,而未言及心之全体。朱子认为“识心”之端,不是“识心”工夫。朱子认为只是根据流动发生之端的省察就能在使心在已发后事事物物皆合于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些学者因为工夫小有成效就轻肆狂妄,不顾义理上的弊病,坚持以此为“识心”工夫,这是需要注意的。朱子对此很谨慎,他告诉方宾王不要将这话告诉别人,否则只会增加竞辩的事端。此时朱子与象山还没有结束论辩,与陆学门人关系紧张,所以告诉方宾王这个说法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不想徒增竞辩的争端,这显然是针对陆学门人而言的,可知朱子以上批评针对陆学而发。
2.不知气禀之杂
朱子认为是否承认气禀对心的影响是儒释的区别,也是朱陆之分,朱子认为禅学与陆学都没有体察到气禀和私欲对人心的影响,所以不重穷理,朱子说:“虽说心与理一,而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亦是见得不真,故有此病。此《大学》所以贵格物也。”①可见,朱子认为陆学虽言心与理为一,但是没有注意到气禀与物欲对心的影响,不知气禀之杂是陆学不重穷理的根源。
陆子静之学,看他千般万般病,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杂,把许多粗恶底气都把做心之妙理,合当恁地自然做将去。向在铅山得他书云,看见佛之所以与儒异者,止是他底全是利,吾儒止是全在义。某答他云,公亦只见得第二着。看他意,只说儒者绝断得许多利欲,便是千了百当,一向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初自受得这气禀不好,今才任意发出,许多不好底,也只都做好商量了。只道这是胸中流出,自然天理;不知气有不好底夹杂在里,一齐羇将去,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静书,只见他许多粗暴底意思可畏。其徒都是这样,才说得几句,便无大无小,无父无兄,只我胸中流出底是天理,全不着得些工夫。看来这错处,只在不知有气禀之性。又曰:“‘论性不论气,不备。’孟子不说到气一截,所以说万千与告子几个,然终不得他分晓。告子以后,如荀扬之徒,皆是把气做性说了。”②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陆子静的学问有很多问题,但根源在于没有注意到气禀之杂,所以把许多粗的、恶的气与心之妙理混淆。朱子认为陆子静只说儒者要断绝利欲,不让利欲任意发出,但是却不知道因为刚开始的气禀不好才任意发出不好的利欲。在此,朱子以气禀说明了人发出不好的利与欲的原因,气禀最终导致人不能诚意,也就是不能自觉地达到完善的境界,所以要通过长久的磨炼才能去除气禀的影响。而陆子静只说从胸中流出的是自然天理,不知有不好的气夹杂在天理中,没有意识到因为气禀的影响造成了不同的人成德的努力程度和完成程度的不同。言自然天理是对本心的过分自信。所以朱子批评陆子静看书,不作明理,所以采纳的是粗糙的观点,门人弟子也是如此,无兄无父,只说我胸中流出的是天理,这种错误观点的根本原因在于不知有气禀之性的存在。所以二程才说论性不论气是对性认识的不完备,孟子即缺失论气的一截,所以与告子论辩,没有最终的分晓。告子后,荀子、扬雄之徒都把气说成性了,以气为性,则动摇了天命之性。在此,朱子强调要重视气禀对性的影响,如果不重视气禀的影响则论性不完备,也无法重视穷理工夫,但如果把气当成性,即如告子以生为性,则论性不够明白。朱子晚年改变了“新说”时期所认为的持敬可以完全解决气禀和私欲的问题,而强调以穷理对治气禀,以气禀的影响说明了穷理工夫的必要。
大抵人之一心,万理具备,若能存得,便是圣贤,更有何事?然圣贤教人,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未尝教人只守此心者,盖为此心此理虽本完具,却为气质之禀不能无偏,若不讲明体察,极精极密,往往随其所偏堕于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为此说者,观其言语动作,略无毫发近似圣贤气象,正坐此耳)。是以圣贤教人,虽以恭敬持守为先,而于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验今,体会推寻,内外参合。盖必如此,然后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于世间万事、一切言语,无不洞然了其白黑。……若如来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穷理,故此心虽似明白,然却不能应事,此固已失之矣。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从大抵上说每个人之心都万理具备,如果能存得此心,便是圣贤,其他就没有什么工夫了。然而圣贤教人之所以有许多门路节次,而从来没有教人只做持守工夫,就是因为此心虽然本具万理,但却因气禀的影响难免有偏,如果不讲明体察,做更加精密的工夫,则此心就会随其所偏流入私欲中而不自知。所以圣贤教人做工夫,虽然以持守为先,而在持守之中又必须即事即物做穷理工夫,如此内外工夫相配合。朱子认为必须如此,才能见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如果如项平父所说只做持守本心的工夫,一点不去穷理,则此心看起来似乎明白,但却不能应事,其实已失本心了。认识到气禀对成德的影响,朱子晚年更加注重持敬与穷理二者缺一不可,强调内外工夫互相配合,改变了中年时期认为持敬能变化气质的观点,这也是朱子与陆学工夫分歧的原因所在。
问:“季通说‘尽心’,谓‘圣人此心才见得尽,则所行无有不尽’。故程子曰:‘圣人无俟于力行。'”……又曰:“尽心如明镜,无些子蔽翳。只看镜子若有些少照不见处,便是本身有些尘污。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鹘突窒碍,便只是自家见不尽。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今人多是气质偏了,又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尽知,圣贤所以贵于穷理。”又曰:“万理虽具于吾心,还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个心在这里,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许多道理。少间遇事做得一边,又不知那一边;见得东,遗却西。少间只成私意,皆不能尽道理。尽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无有不合道理。”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尽心的境界就像明镜一样,没有一点点遮蔽,如果镜子上有少许遮蔽,便是本心还有未光明处,说明朱子以尽心为成德的标准。朱子认为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大多是因为气质偏了,又被物欲遮蔽,所以本心昏昧而不能尽知,这是圣贤之所以重视穷理的原因。朱子又说万理虽本具于心,但还要教人去知此本具之理,才是得理于心。现在人有心却不让自己去穷理知理,所以最终心都发为私意,不能尽心中之理,如果能尽此心中之理,则心洞然光明,事事物物都合于理。在此,朱子以不能穷理则不能尽心的角度说明了不能只守此具理之心,应该要使心知所具之理而使心事事物物都合于理才是尽心,在此朱子将尽心诠释为成德的境界,而穷理是达到尽心必须做的工夫。63岁时朱子又致信项平父说明穷理须以涵养为本,所以穷理不在心外。
所论义袭,犹未离乎旧见。……如孟子答公孙丑问“气”一节,专以“浩然之气”为主。其曰“是集义所生者”,言此气是积累行义之功而自生于内也;其曰“非义袭而取之也”,言此气非是所行之义潜往掩袭而取之于外也;其曰“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者,言心有不慊,即是不合于义,而此气不生也,是岂可得而掩取哉!告子乃不知此,而以义为外……然告子之病,盖不知心之慊处即是义之所安,其不慊处即是不合于义,故直以义为外而不求。今人因孟子之言,却有见得此意而识义之在内者,然又不知心之不慊与不慊,亦有必待讲学省察而后能察其精微者。……来喻敬义二字功夫不同,固是如此。然敬即学之本,而穷理乃其事,亦不可全作两截看也。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项平父的“义袭”仍然没有改变旧见,孟子言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如此说明所养之气是自己生于心内之气,孟子言“非义袭而取之”即说明此气不是取之于外,而“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则说明如果心不合于义,则此气不生。朱子又说告子不知气生于内而以义在心外,告子的问题在于不知道诚意必须通过讲学省察才能达到,所以敬是为学之本,但穷理却是敬在事中的工夫,二者不能分为两节。在此,朱子提出正因为涵养是前提,格致为心内的工夫。1194年,朱子在《经筵讲义》中又说:“然而尚幸有可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于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励,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从今日从事于敬以求放心,则犹可以涵养本原而致其精明以为穷理之本。”①朱子认为要兼取孟子求放心和二程持敬,而求放心是通过“事中持敬”来实现的,如此则可以涵养本原使本心达到精一、光明的程度,依此成为穷理的根本。
朱子于1200年又言求放心不在讲学应事之外,朱子说:“若论功夫,则只择善固执、中正仁义,便是理会此事处,非是别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讲学应事之外也。如说‘求其放心’,亦只是说日用之间收敛整齐,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几其中许多合做底道理渐次分明,可以体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后别分一心出外以应事接物也。”②可见,朱子认为所谓的涵养工夫就是在事中对善的坚守、对仁义中正的践行,而没有别的一段涵养本原的工夫,求放心只是在日用之间收敛整齐,不使心向外走作,对道理的体察也不是一心来藏道理,又分出一心应接事物,体察与应接都是涵养此心,对此王懋竑认为此是朱子言涵养的“定论”:“廖书在庚申正二月间,此真所谓晚年定论者。”③
3.江西气象遗害
1189年后朱子与象山绝笔,但是朱子对象山和陆学的批评并没有停止,相反在象山去世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朱子都没有停止对象山和陆学的批评,一方面是朱子对象山直接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陆学门人的批评,因为陆学在当时影响很大,极大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朱子最终上升到对儒家道统的担忧。
许行父谓:“陆子静只要顿悟,更无工夫。”曰:“如此说不得。不曾见他病处,说他不倒。大抵今人多是望风便骂将去,都不曾根究到底。见他不是,须子细推原怎生不是,始得,此便是穷理。既知他不是处,须知是处在那里;他既错了,自家合当如何,方始有进。子静固有病,而今人却不曾似他用功,如何便说得他!所谓‘五谷不熟,不如稊稗’,恐反为子静之笑也。”①
由引文可知,许行父提出陆子静只要顿悟,没有其他工夫,朱子马上提醒许行父不能这样说。朱子认为许行父对陆子静的批评没有抓到要害,不能从根本上驳倒他。现在的人批评陆子静大多也是跟风,没有找到陆子静的根本错误。朱子指出陆子静问题的根源在于不穷理,但朱子也认可陆子静重视以涵养为本,指出现在的人不如象山用功,没有资格去批评他。朱子言“五谷不熟,不如稊稗”是指浙中学者欠缺涵养工夫,其问题比象山不重穷理更严重。在此,朱子肯定了象山的涵养工夫,否定他人对象山顿悟的批评,说明朱子在此还没有从工夫路径上批评象山。1189年朱子致信邵叔义说:“子静书来,殊无义理,每为闭匿,不敢广以示人,不谓渠乃自暴扬如此。……吾人所学,却且要自家识见分明,持守正当,深当以此等气象举止为戒耳。”②朱子直言陆子静“殊无义理”,认为其言论封闭藏匿,不敢广示他人,提出为学主旨是要先自己见识分明,持守正当,即持敬和明理不偏废一方,并劝告别人以子静的气象、举止为戒。同年,朱子还致信赵子钦提出在与陆子静的交流中发现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说:“子静后来得书,愈甚于前。大抵其学于心地工夫不为无所见,但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穷理细密功夫,卒并与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横流,不自知觉,而高谈大论,以为天理尽在是也,则其所谓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①朱子认为陆子静的问题比以前更严重,其问题并不在于不重涵养,而是将涵养架得过高而不做更为细密的穷理工夫,如此所涵养的本心也会失去,最后导致人欲横流而不自知,他所说的心上的工夫也不能安在。在此,朱子批评象山不重穷理而导致工夫高悬,语气很重。次年朱子又致信姜叔权、汪长孺,以‘江西气象’批评二人。
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学问气象?顷见其徒自说见处,言语意气、次第节拍正是如此,更无少异。恐是用心过当,致得如此张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异事,甚不便也。长孺所见亦然。但贤者天资慈祥,故于恻隐上发,彼资禀粗厉,故别生一种病痛,大抵其不稳帖而轻肆动荡,则不相远也。正恐须且尽底放下,令胸中平实,无此等奇特意想,方是正当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批评姜叔权说其学问全与江西气象相似,认为他与陆学门人自说见处,言语意气、次第节拍都一样。朱子又说汪长孺也是如此,圣人天资慈祥,所以能发于恻隐,但枉长孺天资和禀赋都粗劣,所以没有发出恻隐,不仅不稳妥还轻肆动荡,朱子建议他们放下这种高谈阔论的习惯,令心中平实。同年朱子又致信汪长孺说:“别纸所论,殊不可晓。既云‘识得八病,遂见天理流行昭著,无丝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气盈矜暴之失,复生大疑,郁结数日,首尾全不相应?似是意气全未安帖,用心过当,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气象。……此须放下,只且虚心平意玩味圣贤言语,不要希求奇特,庶几可救。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后观书,此又转见诡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详审,不可容易也。”①朱子认为汪长孺受到象山影响,全似江西气象,批评他不重视读书穷理的工夫,气象诡怪多端。朱子建议姜、汪二人先把高论放下,令心中平实,虚心体会圣贤言语,不要在奇怪臆想的言论上求道理。1193年,象山已去世一年,朱子对子静的批评仍然很重,认为象山影响了当时的学术风气。
大抵近年风俗浮浅,士大夫之贤者不过守文墨、按故事,说得几句好话而已。如狄梁公、寇莱公、杜、范、富、韩诸公规模事业,固未尝有讲之者,下至王介甫做处,亦模索不着。……子静旅榇经由,闻甚周旋之,此殊可伤。见其平日大拍头、胡叫唤,岂谓遽至此哉?然其说颇行于江湖间,损贤者之志而益愚者之过,不知此祸又何时而已耳。许教似亦小中毒也。如何如何。②
朱子认为近年风气日益浮浅,士大夫中的贤人不过也是只守文字,流于空谈,受到江西气象的影响很大。朱子提出见陆子静平日拍大头、胡叫唤,说明陆学的弊病不是一日两日突然就如此的。然而陆子静的学说颇为流行,不仅损害贤者的志向也加重了愚蠢之人的过错,不知陆学的祸害什么时候能停止,许行父似乎已经受到江西陆学的毒害。由此可见,在象山去世之后,朱子仍旧没有停止对象山的批评,甚至提出江西陆学是影响当时学术风气的祸害,可见朱子对陆学批评的程度。1195年,朱子又致信廖子晦提出吴伯起也受到陆学风气的影响。
此间有吴伯起者,不曾讲学,后闻陆子静门人说话,自谓有所解悟,便能不顾利害。及其作令,才被对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而百方求免。熹尝笑之,以为何至如此,若对移作指使,即逐日执杖子去知府厅前唱喏;若对移做押录,即逐日抱文案去知县案前呈覆。更做耆长壮丁,亦不妨与它去做,况主簿乎?吴不能用,竟至愤郁成疾而死,当时若放得下,却未必死,今不免死,而枉陪了许多下情,所失愈多。虽其临机失于断决,亦是平日欠了持论也。①由引文可见,朱子说吴伯起不做讲学求义的工夫,后来听了陆子静门人说话,就认为自己有很多领悟,便不顾利害,高谈阔论以至于被罢免官职,都是因为他平日不持守。朱子认为如果他能够应事接物,即使被罢免主簿,也不妨碍做别的,最后因为不被重用竟然愤郁成疾而死。朱子认为如果他当时能放下高论,在平日中多做持守工夫,可能不会到忧愤至死的地步。1196年,朱子致信孙敬甫言陆学对近年学术风气的影响,朱子依然批评陆学高谈阔论、不重穷理明义,认为陆学应事接物的能力太差。要之持敬致知实交相发,而敬常为主,所居既广,则所向坦然,无非大路,圣贤事业,虽未易以一言尽,然其大概似恐不出此也。……如陆氏之学则在近年一种浮浅颇僻议论中,固自卓然,非其俦匹,其徒传习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间者,但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讳。当时若只如晁文元、陈忠肃诸人分明招认,着实受用亦自有得力处,不必如此隐讳遮藏,改名换姓,欲以欺人而人不可欺,徒以自欺而自陷于不诚之域也。然在吾辈须当知其如此,而勿为所惑,若于吾学果有所见,则彼之言钉钉胶粘一切假合处,自然解拆破散收拾不来矣,切勿与辨以起其纷拏。①
在此,朱子提出持敬与致知要互相发明,如果以持敬为主,则居敬穷理肯定是朝着成德的方向,不会与圣贤之道相差太远。朱子提出陆学近年表现出肤浅偏僻、自视甚高的问题,而且其门人当中也有能修身齐家治理政事的人才,但因为陆学的为学宗旨本来是从禅学中来,无法掩盖。在此指出了陆学造成不好的学术风气的根源原因在于宗旨来自禅学。朱子举晁文元、陈忠肃等人都曾坦白承认受到禅学的启发为例,提出既然如此则不必遮掩隐藏,想要欺骗别人但不能自欺,自欺则陷入不诚的境地。朱子在此提醒孙敬甫不要被陆学迷惑,如果能对朱学有领会,则陆子静的附会、虚假的言论自然能分辨,并告诫敬甫不要与陆门论辩而引起纷争。如此可见,朱子晚年很注意不和陆学门人直接辩论,但没有中断对陆学的批评。朱子在此指出陆学的为学宗旨来自禅学是江西气象的根本原因,说明朱子对陆学的批判是很重的,实质上是将陆学判入了禅学,对陆学的批评已经超出了儒家的范围。
4.判陆学为禅
综合前文分析可知,朱子对禅学的批评有针对大程门人而发的时候,但大多时候针对陆学而发,朱子批评陆学为禅不是因为陆学在世界观、人生观与佛学相似,更多的是从为学方法和工夫形式上看,朱子的标准在于有没有重视穷理。对此朱子说:“此是求其放心乃为学根本田地,既能如此向上须更做穷理功夫,方见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两事,随感即应,自然中节,方是儒者事业,不然却亦与释子坐禅摄念无异矣。”①可以看出,朱子认为求放心是根本,但在此基础上必须做穷理工夫,涵养与穷理不是两件事,应该合起来做,如果只言涵养不言穷理与佛家的坐禅无异。涵养与格致的关系是朱陆之辩的核心内容,朱子45岁第一次指出陆学不重穷理,认为陆子静全是禅学②,50岁后朱陆围绕涵养与致知的关系展开集中论辩,至60岁时与象山绝笔,朱子两次批评陆学为禅,52岁时说陆子静有“禅底意思”③,56岁时又说陆子静有“禅底意思”④。
朱子进入晚年后仍以不重穷理作为批评陆学的基本立场,朱子批评陆学为禅不仅贯穿了朱陆之辩的过程,直至象山去世后朱子晚年的十年时间,指陆学为禅是朱子批评陆学的一条主线。朱子65岁说:“盖谓其本是禅学,却以吾儒说话摭掩。”⑤又说:“陆子静之学,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看是甚文字,不过假借以说其胸中所见者耳。据其所见,本不须圣人文字得。他却须要以圣人文字说者,此正如贩盐者,上面须得数片鲞鱼遮盖,方过得关津,不被人捉了耳。”⑥
66岁时说:“圣贤教人有定本,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是也。其人资质刚柔敏钝,不可一概论,其教则不易。禅家教更无定,今日说有定,明日又说无定,陆子静似之。圣贤之教无内外本末上下,今子静却要理会内,不管外面,却无此理。硬要转圣贤之说为他说,宁若尔说,且作尔说,不可诬罔圣贤亦如此。”①67岁时说:“其宗旨本自禅学中来,不可掩讳。”②68岁时又说:“只是禅。初间犹自以吾儒之说盖覆,如今一向说得炽,不复遮护了。”③由此可见,朱子判陆子静为禅是一以贯之的,朱子从中年45岁后至去世的二十五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改变批陆学为禅的观点。需要注意的是,朱子判子静为禅并没有从系统的世界观、人生观上做系统的批评,只是从心性论中的心与理的关系、为学方法以及工夫形式上批评陆学为禅,不仅延续中年时期的“脱略文字,直趋本根”的工夫形式,还批评象山不重穷理,认为其为学宗旨来自禅学,实际上对象山的批评已经超出了儒家内部的范围。
二 涵养与省察
(一)省察是诚意之助
省察是指内心的反省和检查,中年时期认为省察“察人欲之将萌”,晚年时期将省察主要落实到私意和自欺的检查,说明了省察对诚意工夫完成的作用。由于朱子晚年特别注意气禀的影响,朱子认识到私意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所以省察的地位得到重视。
彦忠问:“居常苦私意纷搅,虽即觉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洁静不起。”先生笑曰:“此正子静‘有头’之说,却是使得。惟其此心无主宰,故为私意所胜。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见破了这私意只是从外面入。纵饶有所发动,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劳,自家这里亦容他不得。此事须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后方省察,殊不济事。”①
由引文可见,彦忠提出自己常常苦于私意纷扰,虽然自己也努力抑制,但成效不好,对此朱子回答说只是因为本心没有居于主宰地位,所以被私意所胜,最需要做的就是常常省察,使良心常在,私意就不会从外面进入而影响本心。如果私意稍有发动,本心为主宰,自然会将私意克除。朱子强调平日省察的重要性,如果等私意影响本心后再去省察,也没什么用。在此,朱子认为省察是平日工夫,是在私意影响本心之前对私意的省察,省察的地位上升到和涵养一样,成为平日工夫。朱子说:“且于日用处省察,善便存放这里,恶便去而不为,便是自家切己处。”②对于省察如何成为诚意的工夫,朱子分析是先省察到善与恶,然后再去存善去恶,这说明了诚意工夫包含两个阶段,一是省察到意之善恶,二是为善去恶,朱子说:“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诚其意。”③可见,省察对诚意的帮助是通过致知的环节完成的,省察不能完成诚意,但如果没有省察则诚意的工夫不能完成。朱子说:“只是说心之所发,要常常省察,莫教他自欺耳。人心下自是有两般,所以要谨。谨时便知得是自慊,是自欺,而不至于自欺。若是不谨,则自慊也不知,自欺也不知。”④在诚意工夫完成的次序上,要先省察以解决自欺的问题,因为谨慎省察才能发现内心是自欺还是自慊,如果不省察,则内心是自慊还是自欺无法知晓,可见省察对诚意的作用。
基于朱子晚年对私意问题的认识,朱子认为诚意是很难完成的工夫,所以进一步强调省察的作用,他说:“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见是别人事,便自不如己事切了。若是计较利害,犹只是因利害上起,这个病犹是轻。惟是未计较利害时,已自有私意,这个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这个躯壳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谓流注想者是也。所谓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觉,流射做那里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①在此,朱子提出本心如果只是计较利害,问题则比较轻,但在还未计较利害时就已经有私意,这个问题最严重。朱子提出人有了躯壳之后便自私了,说明了自私来源于形气之私,是无法避免的问题,就像佛家所说的“流注想者”,说明私意的影响就像水流,是不知不觉影响本心的,私意萌发的端倪十分微小,很难发现,需要直接做省察工夫。因为朱子认识到人受到气禀的影响而私意不可避免产生,并且私意对本心的影响有不知不觉的特点,所以更体现出省察工夫的重要,如果不做省察工夫,无法发现自欺。所以要达到自慊而无一毫自欺的境界必须通过省察,朱子说:“盖到物格、知至后,已是意诚八九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御寇,寇虽已尽剪除了,犹恐林谷草莽间有小小隐伏者,或能间出为害,更当搜过始得。”②朱子提出省察是在知至之后单独属于诚意阶段的工夫,知至之后已经完成了诚意的八九分的工夫,只是从上面省察,将剩下的私意检查出来,知至后的扫尾工作是更为细致的工作,也是诚意完成的关键。
(二)无时不涵养省察
从朱子晚年的文献来看,朱子60岁后的书信很少涉及对涵养与省察的关系的讨论,主要是因为涵养与省察的关系是朱子中年时期与湖湘学派论辩的核心,朱子45岁作《观心说》标志朱子与张栻论辩结束,由此朱子的心性论基本确立,工夫的基本架构基本形成,所以涵养与省察的关系在此后不是考察涵养工夫地位的核心问题。中年时期,湖湘学派主张先察识后涵养,朱子主张涵养于未发之前,强调涵养先于察识的地位,这是基于朱子对未发前涵养工夫的重视。中晚年时期朱子提出无时不涵养、无事不省察,强调涵养是平日无间断的工夫,而省察是针对私欲萌发而做的检查工夫,并且中晚年时期朱子已开始注重阐述省察对涵养的意义。晚年后基于对私意问题的重视,朱子认识到省察是诚意完成的关键工夫,省察的地位得到提升。朱子晚年对湖湘学派言涵养与省察的关系再一次进行讨论,对涵养与省察关系的表述出现了重大变化。
莹以所论湖南问答呈先生。先生曰:“已发未发,不必大泥。只是既涵养,又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若戒惧不睹不闻,便是通贯动静,只此便是工夫。至于慎独,又是或恐私意有萌处,又加紧切。若谓已发了更不须省察,则亦不可。如曾子三省,亦是已发后省察。今湖南诸说,却是未发时安排如何涵养,已发时旋安排如何省察。”①
必大录云:“存养省察,是通贯乎已发未发功夫。未发时固要存养,已发时亦要存养。未发时固要省察,已发时亦要省察。只是要无时不做功夫。若谓已发后不当省察,不成便都不照管他。胡季随谓譬如射者失傅弦上始欲求中,则其不中也必矣。”②
由第一段引文可见,朱子强调不要太过拘泥于未发已发之分,应该既涵养又省察,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涵养与省察片刻不能间断,将戒慎恐惧通贯动静。至于慎独,则是在私意萌发前更加紧急关键。如果认为已发了就不用省察则不可以,如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就是已发后的省察。在此朱子其实已经表明了无论未发已发都要省察,以此批评湖湘学派是未发时安排涵养,已发时安排省察,如此涵养与省察则出现间断。第二段朱子认为存养省察贯通未发已发,未发时要存养也要省察,已发时要存养也要省察,无时不做涵养省察的工夫,这与第一段表达的意思一致。朱子取消了中年时先涵养后察识的说法,强调应该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朱子还批评了湖湘学派将涵养和省察安排为未发已发的两段工夫,未发时安排如何涵养,是求中;已发时安排如何省察,则私意已发,再救偏失则来不及。所以未发前就要涵养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则可以保证涵养省察工夫没有间断。由此可见,朱子晚年时期不再对涵养与省察做未发已发工夫的区分,取消了涵养与省察的先后。此后朱子又说:“今人非无恻隐、羞恶、是非、辞逊发见处,只是不省察了。若于日用间试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趱出来,就此便操存涵养将去,便是下手处。”①朱子提出今人之所以发不出善端只是因为没有省察,应该在日用间省察此四端,就此操存涵养,可见朱子认为对于四端是先省察再操存涵养。同年,朱子对陆子静言涵养与省察的关系做出批评。
陆子静云:“涵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陈正己力排其说。曰:“子静之说无定常,要云今日之说自如此,明日之说自不如此。大抵他只要拗:才见人说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谓须是涵养;若有人向他说涵养,他又言须是省察以胜之。自渠好为诃佛骂祖之说,致令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①
对于陆子静认为“涵养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的说法,朱子提出象山说法不定,经常有变。朱子认为陆子静是故意与人抬杠,看到别人重视省察,便故意反着说必须涵养,若有人向他说涵养,他又会说省察比涵养更重要。在此,朱子认为象山与朱子的论辩已经是意气之争,认为陆子静喜欢诃佛骂祖之说,最终导致其门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可见,朱陆论辩绝笔之后,朱子其实已经不在意象山说什么了。此后,朱子更加重视省察对成德的作用,提出要时时省察,如果时时省察则道统不会间断,特别在慎独的时候人容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所以省察也是慎独的关键。朱子说:“‘子在川上’一段注:‘此道体之本然也,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才不省察,便间断,此所以‘其要只在慎独’。人多于独处间断。”②朱子提出在道体之本然的时候,就要时时做省察工夫,这样道体发用才不会间断。不省察,道体就会间断,其中最关键的是慎独,人在独自的场景,很难做到道德的自觉,所以要达到慎独的境界,必须做省察的工夫。所以朱子肯定门人以慎独强调省察的作用,门人说:“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后行不得,二是役于欲后行不得。人须是下穷理工夫,使无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无一私之或作。然此两段工夫皆归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慎独。'”③朱子回答:“固是。若不慎独,便去隐微处间断了。能慎独,然后无间断。”④朱子也认为如果不慎独,工夫便在隐微处间断;如果能慎独,持敬则不会间断,这是慎独对持敬的意义。
同时,朱子也说明了涵养对省察的意义,68岁时朱子说:“心存时少,亡时多。存养得熟后,临事省察不费力。”①朱子认为涵养工夫做好了,省察也可以减少很多力气,这是从工夫的完成上说,并不是从做工夫上言二者先后。同年,朱子还以动静区分涵养与省察。朱子说:“存养是静工夫。静时是中,以其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也。省察是动工夫。动时是和。才有思为,便是动。发而中节无所乖戾,乃和也。其静时,思虑未萌,知觉不昧,乃复所谓‘见天地之心’,静中之动也。其动时,发皆中节,止于其则,乃艮之‘不获其身,不见其人’,动中之静也。穷理读书,皆是动中工夫。”②在此朱子以动静区分省察和存养,并且提出才思就是发动,符合朱子晚年以思作为未发已发区分的标准,说明将省察从事的范围扩大到思的范围,只要思虑发动就要做省察工夫,也符合朱子无时不涵养省察的观点,所以很多时候朱子将涵养与省察并说。68岁时,朱子引“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说:“若说三者工夫,则在平日操存省察耳。”③69岁后又说:“方其静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应接也,此理亦随处发见。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养久之,则是理愈明,虽欲忘之而不可得矣。”④朱子晚年将涵养与省察并说,不言涵养与省察的先后,将涵养与省察并列为平日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是朱子晚年对涵养与省察关系的定说。
三全球成德路径
(一)致知而力行
朱子在中年时期已经确立了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等基本知行观,中晚年时期提出义理不明不能践履,以致知为先力行为重的基本立场。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也以持守与穷理的关系来说明知行关系,说明朱子以道德践履为涵养工夫,如此主敬作为涵养的主要工夫容易被理解为践履,对此朱子在进入晚年前对二者做出了明确的区分。朱子说:“但主敬方是小学存养之事,未可便谓笃行,须修身齐家以下乃可谓之笃行耳。”①朱子以主敬涵养为小学阶段的存养工夫,补今人小学工夫之缺,但是朱子强调主敬不是笃行,修身以后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才可以说是笃行,可见朱子最常以持敬与穷理的关系说明涵养与穷理的关系,但不等于知行关系。知行关系体现了涵养践履与穷理的关系,也体现了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以及朱子对《大学》工夫次序的遵循。
朱子晚年延续中年时期对知行关系的基本立场,强调致知为大学工夫的入手处,他说:“‘致知’一章,此是大学最初下手处。若理会得透彻,后面便容易。故程子此处说得节目最多,皆是因人之资质耳。虽若不同,其实一也。”②朱子提出大学工夫最初的下手处,致知是大学工夫的开始,因为每个人的资质不同,其中致知工夫节目最多,虽然其中节目不同,但境界都是到知至。其中节目其实是指从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的过程,其中体现了成德的积累至贯通的过程,成德的速度因人而异。对于大学工夫次序的区分,朱子还做了特别的说明:“但《大学》次序,亦谓学之本末终始无非己事,但须实进得一等,方有立脚处,做得后段功夫,真有效验尔,非谓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后段而听其自尔也。”③在此,朱子说明了对大学工夫次序进行区分的意义在于说明大学工夫从格物致知到平天下都是自己的事,所以必须实实在在地做好每一步的工夫才有做后面工夫的基础,后面的工夫才能真正有效果,并不是说前面的工夫没有完成,后面的工夫就不管不做了。在此,朱子说明《大学》的工夫次序是指工夫完成的先后,而不是前面的工夫没有完成,后面的工夫不能做,朱子其实说明了工夫可以同时做,但工夫的效果和完成的程度受到前面工夫完成程度的影响,《大学》的工夫次序实际上说明的是入德的次序和成德的路径。68岁时朱子提出做学问只有两个路径,致知和力行,也说明了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以及成德的路径要以知为起点。
所喻前论未契,今且当以涵养本原、勉强实履为事,此又错了也。此是见识大不分明,须痛下功夫钻研勘教透彻了,方是了当。自此以后,方有下手涵养践履处。……大抵学问只有两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须是先依次第十分着力,节次见效了,向后又看甚处欠阙,即便于此更加功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见人说着自家见处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养本原、勉强实履,此如小儿迷藏之戏,你东边来,我即西边去闪,你西边来,我又东边去避,如此出没,何时是了邪!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吕祖俭只以涵养本原和道德践履作为修养方法是不够的,如果义理不明就应该做穷理工夫使义理透彻,如此才有涵养和践履下手的地方,在此朱子说明了知先行后的成德路径。朱子认为吕祖俭欠缺了义理上的工夫却不从义理上探究,而是去别处闲坐,嘴上说是涵养与践履,却是未知先行。朱子认为做学问只有致知和力行两个路径,人必须依照次第做工夫,等前面的工夫有效果再向后看哪里有欠缺的地方,从欠缺的地方做工夫。在此,朱子说明了从工夫的完成上说是先致知后力行,致知完成后再检查行的完成,哪里欠缺就在哪里做工夫,不能逃避问题,逃避是无法成德的。除此之外,朱子晚年从《格物补传》中的积累至贯通、《大学》中的致知与诚意、《论语》中的博文与约礼、下学与上达等多个维度来说明成德的路径,体现了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兼对“四书”工夫思想的贯通。
(二)积累至贯通
积累至贯通是朱子言成德次序的经典命题,朱子以积累至贯通来说明大学工夫中格物致知以至于诚意正心这一段工夫节目中境界的变化,朱子最早于1164年《吕氏大学解》中提出这个问题,吕大临说:“以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与尧舜同者也。理既穷,则知自至,与尧舜同者忽然自见,默而识之。”①对此,朱子提出:“愚谓致知格物,大学之端,始学之事也。一物格,则一知至,其功有渐,积久贯通,然后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诚心正矣。然则所致之知固有浅深,岂遽以为与尧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见之也哉?此殆释氏‘一闻千悟’‘一超直入’之虚谈,非圣门明善诚身之实务也。”②当时朱子遵从延平主旨,反对吕大临认为致知可以与尧舜同而忽然自见,认为格物致知要从具体的一事一物的工夫积累至贯通的境界。中年时期朱子作《格物补传》说:“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而不明矣。”③朱子认为通过格物工夫的积累能自然而然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此时以知至为贯通。陈来认为这种贯通是伦理学方面的“从特殊的具体规范上升到普遍的道德原理的意义”①。朱子进入晚年后仍然以格物穷理作为积累的过程,61岁时朱子批评方宾王和姜叔权等人言“识心”之误,强调“识心”需要通过穷理的积累才能达到。
然亦须知所谓识心,非徒欲识此心之精灵知觉也,乃欲识此心之义理精微耳。欲识其义理之精微,则固当以穷尽天下之理为期,但至于久熟而贯通焉,则不待一一穷之,而天下之理固已无一毫之不尽矣。举一而三反,闻一而知十,乃学者用功之深、穷理之熟,然后能融会贯通,以至于此。今先立定限,以为不必尽穷于事事物物之间而直欲侥幸于三反知十之效,吾恐其莽卤灭裂而终不能有所发明也。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认为所谓“识心”并不是只去认识心之精明知觉,而是要认识此心之义理精微之处。要识得义理之精微,就应当以穷尽天下之理为目标,工夫纯熟后自然能达到贯通的境界。到了贯通的境界,则不用每件事物上都去穷理,天下之理都能被穷尽,所谓举一反三、闻一知十都是学者工夫达到一定深度、熟练的程度,然后才能融会贯通。朱子强调如果认为不必穷理就能达到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效果是不可能的,朱子在此实际上是以致知解释“识心”,强调要通过穷理的积累才能到达知至的境界。62岁时朱子对方宾王说:“圣人生知,固不待多学而识,学者非由多学,则固无以识其全也。故必格物穷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诸约。及夫积累既久,豁然贯通,则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矣。”①朱子提出学者多是学而知之,必须通过格物穷理以达到博学,通过主敬和力行达到约礼,强调博学和约礼都需要通过长久的工夫积累才能豁然贯通。在此朱子以格物穷理为博学前的积累,以主敬和力行为约礼的积累,如此可见格物穷理与主敬力行都是积累的过程。此后,朱子又进一步明确持敬存养其实没有很多积累的工夫,格物穷理需要更多积累的过程,他说:“敬之与否只在当人一念操舍之间,而格物致知莫先于读书讲学之为事,至于读书又必循序致一,积累渐进而后可以有功也。”②所以朱子言积累至贯通大多是从格物穷理、读书明义上来说的,也就是说贯通的境界主要是通过穷理而不是持守来实现的。
朱子65岁时又以延平的“洒然冰释”来说明穷理对于贯通的作用,延平说:“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冻解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③延平认为如果工夫没有做到“洒然冰释处”,纵然有持守工夫也没有用。对此胡季随说:“窃恐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处’,必于理皆透彻而所知极其精妙,方能尔也。学者既未能尔,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厌饫,以俟其自得。”④胡季随认为所谓的“洒然冰释”就是穷理至知至的境界,如果学者不能穷理以致知,则只能暂且持守以等待自得。对此朱子补充提出“洒然冰释”是意诚的境界,同时强调只通过持守的积累是无法达到贯通的境界的。
此一条,尝以示诸朋友,有辅汉卿者下语云:“‘洒然冰解冻释’,是功夫到后,疑情剥落,知无不至处。知至则意诚,而自无私欲之萌,不但无形显之过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着力遏捺,苟免显然尤悔,则隐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岂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则横放四出矣。今曰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说甚善。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须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旦牵强着力做得。今湖南学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厌饫,而俟其自得”,未为不是,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答者乃云“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强欲做此模样,殊不知通透洒落如何令得?才有一毫令之之心,则终身只是作意助长,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①
由引文可见,辅广认为延平“洒然冰解冻释”是做工夫达到知至、意诚的境界,如此则私欲不会萌发。但如果只用持守工夫想要遏制私意是十分吃力的。辅广提出有的学者认为“洒然冰释”是令自己胸中通透洒落不符合延平本意。对此,朱子认为辅广说得极好,朱子提出大抵上说“洒然冻释”是工夫后见识分明、涵养纯熟的境界,必须从真实的工夫中积累而来,而不是勉强在遏制私欲上用力。所以胡季随说“只得且持守”恐怕错了,因为欠缺了穷理这一节工夫。“胸中洒落”并不是为了回到本心原来的样子而勉强去模仿,只要有一点勉强的意思就是私意在内,就是自欺,永远不能到达洒然的境界。由此说明朱子也认为持守无法完全解决私欲和私意的问题,也就是说持守工夫积累再多也无法到达贯通的境界。可以看出,朱子晚年对成德路径的理解与“中和新说”时期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中年时期朱子认为“敬则无己可克”,如果涵养工夫做好了是不会有私欲和私意问题的产生的,但是朱子晚年认识到私欲和私意的产生受到气禀的影响,自欺的问题没有这么容易解决,所以朱子晚年将工夫贯通后的境界由知至推后至意诚,以意诚为心与理的贯通,王懋竑说:“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犹修书不辍,夜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且曰:‘为学之要,惟在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久之,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至极而已矣。’”①格物、穷理、致知、省察作为完成诚意的工夫都属于积累的阶段,至于具体如何从格物穷理的积累到达贯通的境界,朱子遵从程子的解释,以“推”作为贯通的方法。
然而尚赖程氏之言,有可以补其亡者。如曰:“……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读书讲明道义,或论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否,皆穷理也。但能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贯通处。”又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格物非欲尽穷天下之物,但于一事上穷尽,其他可以类推。至于言孝,则当求其所以为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穷不得,且别穷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难者,各随人浅深。譬如千蹊万径,皆可以适国,但得一道而入,则可以推类而通其余矣。盖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无不通也。”②
二程认为格物不是只有一个方法,读书讲义、论古今是非、应事接物皆是穷理工夫的内容,但是如果能长期坚持格物穷理的工夫,通过久久的练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达到贯通的境界。穷理并不是说一定要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也不是说只穷得一理后就能贯通,但如果对自己身上以至于万物之理理会得多了,自然会有贯通领悟的时候。格物并不是穷尽天下之物之理,但如果从一件事物上穷尽事物之理,在其他事物上则可以类推。比如要孝顺则应当寻求之所以孝顺的道理,如果一件事情上无法穷理,先暂且在别的事物上领悟。或者先从容易处开始,或者先从难处开始,因每个人资质的浅深而定。穷理的方法有很多,只要领悟一个道理,就可以依此类推旁通。这是因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道理,但万理同出一原,所以通过类推的方法就可以达到贯通的境界。朱子67岁时还提出涵养本原和心理贯通都需要积累的过程,他说:“所喻涵养本原之功,诚易间断,然才觉得间断,便是相续处。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积累将去,久之自然接续打成一片耳。讲学功夫亦是如此,莫论事之大小、理之浅深,但到目前,即与理会到底,久之自然浃洽贯通也。”①在此,朱子提出涵养本原也需要积累的过程,因为持敬容易间断,但如果发现了间断,就是接续起来的地方,所以需要常常提撕省察、渐渐积累,最后自然涵养无间断。讲学工夫也是如此,无论事情大小,道理深浅,只要通过长久的积累,最后都能达到心与理的贯通。可见,持敬、格物、穷理、致知,包括省察等意诚前的工夫都属于成德工夫的积累。
(三)知至而后意诚
1.先致知后诚意
先致知后诚意是《大学》的工夫次第,朱子对《大学》的诠释遵从了《大学》中知至而后意诚的成德次序,在知行关系上体现为知先行后的成德路径,与象山以诚为先、以知为行的观点不同。后世“朱陆晚同说”为了合同朱陆,提出朱子晚年因为重视省察和诚意,改变了知先行后的立场终与陆学为同。比如李绂判定朱子为“先行后知”,“省察先于致知”。①李绂所引的“朱子晚年”的材料并非皆是其划定的55岁后,如其中朱子《答任伯起》②的时间为1182年,此时朱子53岁。抛开李绂史料的真实性不言,朱子晚年确实对诚意和省察有一定修正,但是并没有改变《集注》阶段已经确立知至而后意诚的成德次序。但是,朱子改变了《集注》中以知至为贯通的境界,而将贯通的境界提推至意诚,如此知至之后诚意工夫就有了自己独立的工夫内容,朱子又以省察和慎独工夫落实了诚意阶段的工夫。1190年朱子致信汪长孺说:“《大学》‘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二句,《章句》注解新旧说不同。若如旧说,则物格之后更无下功夫处,向后许多经传皆为剩语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来说得之。”③在此,朱子提出若如《章句》旧解则物格之后就没有下工夫的地方了,因为旧注中以物格知至为“事事物物皆合于理”,认为物格知至之后意就自然诚了,如此则造成物格之后不须做工夫,诚意工夫就没有下落处。所以62岁时朱子重新解释了“知至而后意诚”:“知则知其是非。到意诚时,则无不是,无有非,无一毫错,此已是七八分人。然又不是今日知至,意乱发不妨,待明日方诚。如言孔子‘七十而从心’,不成未七十心皆不可从!只是说次第如此。”①在此,朱子提出知至则知是知非,到意诚时无非无错,知至已完成诚意的七八分的工作,还有两三分是独属于诚意阶段的工夫。但是并不是说知至后才可以做诚意工夫,只是说从工夫完成上看是知至而后意诚,致知和诚意可以同时做工夫。朱子63岁后又提出知至之后意还有未诚之处来落实诚意的工夫。
或问:“知至以后,善恶既判,何由意有未诚处?”曰:“克己之功,乃是知至以后事。‘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一念才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无放心底圣贤,然一念之微,所当深谨,才说知至后不用诚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厘间不可不子细理会。才说太快,便失却此项工夫也。”②
对于知至以后还有意未诚的问题,朱子提出以克己工夫来解决。克己是知至以后的工夫,一念能克则成圣,一念放下心便不正。自古圣贤都没有放其心,但是在一念的微小处,是应当谨慎的地方,所以才说知至之后不用诚意的工夫是不够的。朱子又以人心道心相差毫厘却不可不仔细理会来说明在细微之处做诚意工夫的重要,因为诚意工夫是在微小处做工夫,所以朱子认为如果工夫做得太快,就会失去诚意工夫的意义。对于知至之后的“毋自欺”,朱子解释:“物既格,知既至,到这里方可着手下工夫。不是物格、知至了,下面许多一齐扫了。若如此,却不消说下面许多。看下面许多,节节有工夫。”③可见,朱子认为克己、毋自欺都是知至以后诚意的工夫,而“毋自欺”是通过慎独和省察完成的。
门人曾光祖问:“物格、知至,则意无不诚,而又有慎独之说。莫是当诚意时,自当更用工夫否?”①朱子回答:“这是先穷得理,先知得到了,更须于细微处用工夫。若不真知得到,都恁地鹘鹘突突,虽十目视,十手指,众所共知之处,亦自七颠八倒了,更如何地慎独!”②在此,朱子提出慎独工夫是在知至之后的细微处做工夫,是真知以后的工夫,慎独完成的是致知所不能完成的部分工作,朱子说:“‘知至而后意诚’,已有八分。恐有照管不到,故曰慎独。”③慎独是知至以后意诚的工夫,朱子又说:“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慎独者,诚意之助也。致知,则意已诚七八分了,只是犹恐隐微独处尚有些子未诚实处,故其要在慎独。”④在此朱子说明了致知完成了诚意的大部分任务,是诚意工夫的根本,所以知至在意诚之先,慎独是完成诚意两三分的工作,慎独是诚意的辅助工夫。朱子在《集注》时期已经以省察作为慎独和诚意的工夫方法,所以朱子又说知至后的诚意工夫需要通过省察完成,他说:“然‘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知若未至,何由得如此?盖到物格、知至后,已是意诚七八分了。只是更就上面省察,如用兵御寇,寇虽已尽剪除了,犹恐林谷草莽间有小小隐伏者,或能间出为害,更当搜过始得。”⑤由此可知,知至之后的诚意工夫包括了省察和慎独,慎独也需要通过省察来完成。
朱子又以致知和诚意来说明知行关系,致知为知,诚意是道德行动的开始,65岁时朱子说:“格物者,知之始也;诚意者,行之始也。”①由此致知和诚意关系也说明了朱子知先行后的成德路径,因为诚意是自觉的道德实践的开始,所以诚意的地位就凸显出来。朱子强调诚意的完成很艰难,这与朱子知易行难、知先行重的观点相互印证。
《大学》之道,莫切于致知,莫难于诚意。意有未诚,必当随事即物求其所以当然之理。然观天下之事,其几甚微,善恶邪正、是非得失未有不相揉杂乎芒芴之间者,静而察之者精,则动而行之者善。圣贤之学必以践履为言者,亦曰“见诸行事”,皆平日之所素定者耳。今先生之教必曰知之者切而后意无不诚,盖若泛论“知至”如诸家所谓极尽而无余,则遂与上文所谓“致知”者为无别。况必待尽知万物之理而后别求诚意之功,则此意何时而可诚耶?……窃尝体之于心,事物之来,必精察乎善恶之两端,如是而为善,则确守而不违,如是而为恶,则深绝而勿近(先生勿去此并上二句),亦庶几不苟于致知,而所知者非复泛然无切于事理,不苟于诚意,而好善恶恶直欲无一毫自欺之意。②
由引文可见,朱子提出《大学》中最早开始的工夫是致知,而最难完成的是诚意。如果意有不诚的地方,一定要在事事物物中寻求所当然之理,即必须通过致知来诚意,致知是诚意的大段工夫。朱子又说天下之事,也有几微之处,在几微之处,善恶邪正、是非得失都是相糅相杂的,所以静时省察到其中的善是精,动时发为行的可以称为善,所以圣贤之学一定要以践履为标准。朱子提出如今周舜弼教人必说知至后意无不诚,但是如果泛论知至为知之极尽无余,则与致知没有分别。况且如果要等尽知万物之理后再做诚意工夫,则“意”什么时候能诚呢?在此,朱子提出致知就是为了诚意,诚意并不是在致知之外别做工夫。当事物来时,必须省察其善恶两端,如果为善则实守其善;如果为恶则去其恶。如此从致知上看则所知者皆合于事理,从诚意上看则好善恶恶而无一毫自欺之意。
朱子以毋自欺、慎独作为诚意的工夫,诚意是《大学》中最难完成的工夫,意诚也是最高的境界,所以朱子将诚意作为善恶评判的标准,朱子说:“‘格物是梦觉关。诚意是善恶关。过得此二关,上面工夫却一节易如一节了。到得平天下处,尚有些工夫。只为天下阔,须着如此点检。’又曰:‘诚意是转关处。’又曰:‘诚意是人鬼关!’”①朱子以意诚作为成德的标准,是修身工夫做高的境界。基于朱子对诚意工夫的重视,朱子去世前仍然对诚意的解释有许多讨论,《语类》中载了四段沈僩与朱子关于诚意的修改的讨论,一是问:“‘诚意’章‘自欺’注,今改本恐不如旧注好。”②二是敬子问:“‘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注云:‘外为善,而中实未能免于不善之杂。’某意欲改作‘外为善,而中实容其不善之杂’,如何?”③三是沈僩载:“次早,又曰:‘昨夜思量,敬子之言自是,但伤杂耳。某之言某,却即说得那个自欺之根。自欺却是敬子“容”字之意。“容”字却说得是,盖知其为不善之杂,而又盖庇以为之,此方是自欺。谓如人有一石米,却只有九斗,欠了一斗,此欠者便是自欺之根,自家却自盖庇了,吓人说是一石,此便是自欺。谓如人为善,他心下也自知有个不满处,他却不说是他有不满处,却遮盖了,硬说我做得是,这便是自欺。却将那虚假之善,来盖覆这真实之恶。某之说却说高了,移了这位次了,所以人难晓。大率人难晓处,不是道理有错处时,便是语言有病;不是语言有病时,便是移了这步位了。今若只恁地说时,便与那“小人闲居为不善”处,都说得贴了。’”①四是:“次日,又曰:‘夜来说得也未尽。夜来归去又思看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段,便是连那“毋自欺”也说。言人之毋自欺时,便要“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样方得。若好善不“如好好色”,恶恶不“如恶恶臭”,此便是自欺。毋自欺者,谓如为善,若有些子不善而自欺时,便当斩根去之,真个是“如恶恶臭”,始得。如“小人闲居为不善”底一段,便是自欺底,只是反说。“闲居为不善”,便是恶恶不“如恶恶臭”;“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着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若只如此看,此一篇文义都贴实平易,坦然无许多屈曲。某旧说忒说阔了、高了、深了。然又自有一样人如旧说者,欲节去之又可惜。但终非本文之意耳。’”②朱子甚至在易箦的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王懋竑说:“三月初先生病已甚,犹修书不辍,夜为诸生讲论,多至夜分。且曰:‘为学之要,惟在事事审求其是,决去其非,积累久之,心与理一,自然所发皆无私曲。圣人应万事,天地生万物,至极而已矣。’”③如此可见,朱子最终以意诚为心与理贯通的境界,成为自觉的道德行动的开始。
2.以尽心为意诚
基于朱子晚年对心、性、情等概念都做了更为细致的剖析,特别是在对情的剖析中注意到心、知、意三者的关系,朱子注意到私意对本心的影响,再加上朱子晚年对气禀对心性结构影响的认识,朱子认识到没有一丝一毫私意的意诚的境界只靠致知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朱子改变了《格物补转》中以知至为贯通处的说法,知至并不代表诚意的完成,知至后还有诚意阶段的工夫。与此相应,朱子晚年后改变了《集注》中以《孟子》的尽心为《大学》的知至的观点,以尽心为意诚。
某前以孟子“尽心”为如大学“知至”,今思之,恐当作“意诚”说。盖孟子当时特地说个“尽心”,煞须用功。所谓尽心者,言心之所存,更无一毫不尽,好善便“如好好色”,恶恶便“如恶恶臭”,彻底如此,没些虚伪不实。童云:“如所谓尽心力为之之‘尽’否。”曰:“然。”①
由上文可见,朱子61岁时检讨自己以前将尽心解为知至有所不妥,同时提出应当以尽心为意诚,朱子认为孟子提出“尽心知性”之说是煞费苦心的,这里涉及朱子对尽心知性与存心养性的关系的认识。朱子在《知言疑义》阶段已经提出“尽心须假存养”的观点,认为尽心须以存养为前提,穷理是穷本具之理,尽心是尽其所存之心。在此,朱子认为尽心的境界是尽到没有一丝一毫不尽的地步,好善与恶恶就如好好色和恶恶臭一样,真实不伪,其实就是意诚的境界。因为诚意是行动的开始,尽心也要从行动上理解,而不是从致知上理解,所以对于弟子提出尽心是不是尽心力而为之的问题,朱子的回答是肯定的。可见尽心从工夫上说就是诚意,从境界上说就是意诚,也就是知行合一。由前分析可知,朱子将尽心理解为意诚的原因在于晚年重视私意和气禀的影响,知至时还不能尽心之体用,到意诚时才是心理合一、知行合一,才是真正尽心之体用。
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今人多是气质偏了,又为物欲所蔽,故昏而不能尽知,圣贤所以贵于穷理。又曰:“理虽具于吾心,还使教他知,始得。今人有个心在这里,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许多道理。少间遇事做得一边,又不知那一边;见得东,遗却西。少间只成私意,皆不能尽道理。尽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物物无有不合道理。”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认为本心本来虚灵明觉,万理具于心中,所以从理论上说人人应当知晓万理,但是大多数人都受到气禀的影响,再加上物欲的遮蔽,导致本心昏聩而不能尽知本具之理,正因为如此,圣贤才要重视穷理工夫。所以虽然万理已具于心,但不等于人人已知万理,要通过穷理才能真正知理,得理于心。虽然每个人都有具理之本心,如果不穷理以致知,难免受到私意影响而不能达到知至。朱子在此指出尽心就是要通过穷理和去除私意,也就是通过诚意阶段的工夫来使事事物物都合于理,最终实现尽心之体用。如此可见,要达到尽心的境界,在穷理工夫的基础上还有诚意工夫,也就是说知至不能作为尽心的完成,意诚才是尽心的完成。
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改变了以尽心为知至的观点,以尽心为意诚,如此尽心的工夫除了穷理致知的工夫之外,还要做诚意阶段的工夫,但是牟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朱子晚年对尽心说法的修正,仍然认为朱子的尽心是知至,最终将朱子的尽心思想判定为“认知地尽”,他说:“无论以‘知至’说尽心,或以‘诚意’说尽心,皆非孟子‘尽心’之义。……以‘知至’说尽心,是认知地尽……以诚意说尽心,是实行地尽。但此使行地尽却是依所知之理尽心力而为之,心成虚字,是他律道理,非孟子‘尽心’之义。”①牟宗三认为朱子以知至说尽心是“认知地尽”,又以诚意说尽心是“实行地尽”,但“实行地尽”是依据所知之理而尽心力而为之,是他律道德,此心不是孟子所言本心,所以无论是以知至说尽心还是以诚意说尽心都不是孟子言尽心的本意。牟宗三的结论是朱子以知的工夫涵盖行的工夫,使行的工夫成为他律道德。但是,朱子晚年以尽心为意诚的原因即在于认识到致知以后诚意阶段工夫的必要性,致知阶段的工夫不能涵盖诚意阶段的工夫,诚意有独属于诚意阶段的工夫,即省察与慎独。省察与慎独的完成在知至之后,但从做工夫上说慎独与省察并不以穷理致知为前提,而是以持敬涵养为前提,只要确立了涵养为本的工夫,慎独与省察作为诚意阶段的工夫是自觉自律而非他律。牟宗三在此认为朱子以实行言尽心,实行是依据所知之理而尽心力而为之,从而混淆了朱子言知先行后是从工夫的完成上说的,而非从工夫的下手处说,也就是说意诚的完成一定要在知至之后,但是致知的同时也要做诚意阶段的工夫,所以诚意工夫有自己的独立性,并不以穷理致知为前提,可见认知地尽、他律道德是牟宗三对朱子的误判。朱子说:“论其理,则心为粗而性天为妙;论其功夫,则尽为重而知为轻。故云‘所谓尽其心者,即是知性而知天者也。三者只是一时事,但以表里虚实反复相明,非有功夫渐次也’。”②如此可见尽心的完成在知性之后,穷理工夫在尽心之先,并不能说明朱子有重知的他律道德的倾向,相反,朱子将尽心的完成推至诚意阶段说明了尽心比知性更为重要,而诚意阶段的慎独和省察工夫的独立性也说明了尽心之心并不是虚说,心仍然要发挥主宰作用,尽心、诚意并没有因为穷理的限制而成为认知地尽、外在的诚的他律道德。总而言之,朱子晚年将尽心作为意诚的境界恰恰说明了朱子对道德行动的重视,说明了朱子知先行重、知行合一的知行观。
(四)博学而反约
由前文分析可知,致知而力行、积累至贯通、知至而后意诚这三组关系体现出朱子以《大学》为工夫规模,但是朱子又从《论语》中博文与约礼的关系、致知与克己复礼的关系、《孟子》中博学与反约的关系来说明成德的路径,体现出对“四书”工夫思想的贯通,也说明了以“四书”中的思想做相互印证是朱子工夫思想的特色。朱子说:“侯氏谓博文是‘致知、格物’,约礼是‘克己复礼’,极分晓。而程子却作两样说,便是某有时晓他老先生说话不得。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这却是知要。盖天下之理,都理会透,到无可理会处,便约。盖博而详,所以方能说到要约处。约与要同。”①侯氏是指二程表弟也是二程门人侯仲良,侯仲良以博文为致知格物,约礼为克己复礼,朱子认为侯氏将博文约礼区分得很明白,反而认为二程有时候说得不够准确。这也说明朱子晚年将克己复礼理解为践履,从朱子晚年将克己落实到复礼上说可以看出来。朱子又以《孟子》言博学明理是为了反其约来说明知不是目的,行才是目的,博学就是明理,到贯通处就是自我的约束就是克己复礼。博学和反约与致知和力行、致知和诚意一样都是并行不悖的两个工夫,不能偏废一方,朱子又说:“务反求者,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堕于一偏。此皆学者之大病也!”②朱子强调不能只务反约而认为泛观博览为外,也不能只务泛观博览,而以内省工夫为狭隘,博览与反约二者不能偏废,知行并重,知与行要互相配合。
朱子此后又论及博学和反约的次序,他说:“知读《论》《孟》不废,其善。且先将正文熟读,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诸先生说有发明处者,博观而审取之,凡一言一句有益于己者,皆当玩味,未可便恐路径支离而谓所有不必讲也。”①从工夫完成的先后来看应该是先博文后反约,不能因为担心工夫路径的支离而偏废一方,知行两个工夫要同时并进。同年,朱子明确了博学和反约就是知行关系,他说:“圣人生知,固不待多学而识,学者非由多学,则固无以识其全也。故必格物穷理以致其博,主敬力行以反诸约。”②朱子区分了圣人生而知之与学者学而知之,认为大多学者成德的途径无非多学习,通过格物穷理达到博学,又通过主敬力行达到反之约。主敬属于力行,而不是笃行,这是要注意的。由此可知,朱子的工夫规模可以归纳为知行两途,为学不过知行两件事,他说:“学者以玩索、践履为先。”③又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知得,守得。”④甚至说:“只有两件事:理会,践行。”⑤朱子甚至提出圣人教人只是博文约礼两个工夫,他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圣门教人,只此两事,须是互相发明。约礼底工夫深,则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则约礼底工夫愈密。”⑥以上都说明博学与反约、博文与约礼、理会与践行、玩索与践履都是朱子表达知行关系的不同说法。朱子认为从做工夫上看,二者互相配合、互相发明,行是对知的持守;从工夫完成的先后上看,则是知先行后、行比知重。所以,朱子强调知行要逐项做工夫,不能以工夫完成的境界处作为做工夫处,朱子说:“不要说总会。如‘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文便是要一一去用工,何曾说总会处?”①朱子认为做工夫和工夫的境界需要区分,从做工夫上说二者分别做工夫,知有知的工夫,行有行的工夫,朱子说:“如颜子‘克己复礼’,亦须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成只守个克己复礼,将下面许多都除了!”②工夫的完成要以道德行动作为标准,但做工夫不能从境界处、总会处、贯通处入手,以致知作为成德工夫的开始是朱子晚年对成德路径的强调。
(五)下学而上达
“下学而上达”并不是朱子晚年时才提出的观点,1174年朱子说:“圣门之学,下学而上达,至于穷神知化,亦不过德盛仁熟而自至耳。”③在此,朱子以《论语》中孔子所言“下学而上达”作为当时对成德路径的认识,以《系辞下》中“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作为修养工夫之后的仁的最高的境界。“下学而上达”说明了成德工夫的基础是下学,通过下学的积累而贯通至上达的境界,这与朱子之前所言的工夫路径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1.批陆“上达而下学”
朱子晚年言“下学而上达”主要针对陆学而发,由前文分析可知,朱子晚年注重气禀对人成德的影响,认识到成德的艰难,所以更加重视穷理、致知、省察等下学工夫的积累,鼓励人做工夫勇猛精进,强调以孔子下学而上达为成德路径。由于陆学不言气禀对本心的影响,以尊德性为先,注重发明本心,工夫不从致知入手,而从涵养践履入手,认为知必能行,行就是知,与朱子知先行后、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恰恰相反,所以朱子批评象山将成德说得太快。
问:“陆象山道,当下便是。”曰:“看圣贤教人,曾有此等语无?圣人教人,皆从平实地上做去。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须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孟子虽云‘人皆可以为尧舜’,也须是‘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方得。……大抵今之为学者有二病,一种只当下便是底,一种便是如公平日所习底。却是这中间一条路,不曾有人行得。”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门人认为陆象山以为成德“当下便是”,将成德说得太快,朱子认为孔孟圣贤没有教人这样做工夫,圣贤都是教人从平实的地方做工夫,克己复礼是必须先克尽己私才能归仁。孟子虽然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必须“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才能成为尧舜。在此朱子其实批评象山只教人立志却不教人穷理,导致议论太高。朱子指出当下为学有两种弊病,一种只说“当下便是”,一种便是从平日中积累练习,中间有一条路即“下学而上达”。对于陆子静的“当下便是”,朱子做了详细的剖析。
或问:“陆象山大要说当下便是,与圣人不同处是那里?”曰:“圣人有这般说话否?圣人不曾恁地说。圣人只说‘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今截断‘克己复礼’一段,便道只恁地便了。不知圣人当年领三千来人,积年累岁,是理会甚么?何故不说道,才见得,便教他归去自理会便了?子静如今也有许多人来从学,亦自长久相聚,还理会个甚么?何故不教他自归去理会?只消恁地便了?且如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似易。须是做得尧许多工夫,方到得尧;须是做得舜许多工夫,方到得舜。”①
由引文可见,对于门人提出象山言“当下便是”与圣人做工夫的不同之处,朱子则强调圣人没有提出过“当下便是”的说法,圣人只教人克己复礼,现在陆子静却截断克己复礼,认为当下就可以为仁,即不知孔子当年带领三千弟子积年累岁地理会道理,并没有让弟子见得本心就叫他自己回去理会。朱子指出子静也是有许多人来从学的,也与学生长久相聚,为何不叫学生自己回去理会。朱子认为孟子所言“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看起来很容易,但是必须得做尧舜的许多工夫,才能到达尧舜的境界。
他是会说得动人,使人都恁地快活,便会使得人都恁地发颠发狂。某也会恁地说,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坏了人。他之说,却是使人先见得这一个物事了,方下来做工夫,却是上达而下学,与圣人“下学上达”都不相似。然他才见了,便发颠狂,岂肯下来做?若有这个直截道理,圣人那里教人恁地步步做上去?②
朱子认为陆子静之论立论很高,说得很好听,使别人听了很高兴,甚至会使人发癫发狂。朱子说这种使人高兴的话他也会说,只是不敢,怕误导了别人。陆子静的工夫路径就是使人先见境界才下手做工夫,这种路径是先上达后下学,与圣人“下学而上达”都不一样。朱子又指出“上达而下学”的弊端在于人先见了上达便癫狂自大,不肯再去做下学的工夫。如果真的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方法可以成德,那圣人怎么还需要教人从下学一步步做工夫到上达。可见,朱子晚年辟“先见天理源头”不仅针对陈淳、廖子晦而发,更是针对陆学而发。
朱子认为立高论而欠缺下学的工夫既是禅学也是陆学的问题,他说:“敬子诸人却甚进,此亦无他,只是渠肯听人说话,依本分,循次序,平心看文字,不敢如此走作闲说耳。大率江西人尚气,不肯随人后,凡事要自我出,自由自在,故不耐烦如此逐些理会,须要立个高论笼罩将去。”①69岁后朱子批评陆子静误人,《语类》载:“因言读书之法,曰:‘一句有一句道理,穷得一句,便得这一句道理。读书须是晓得文义了,便思量圣贤意指是如何?要将作何用?’因坐中有江西士人问为学,曰:‘公们都被陆子静误,教莫要读书,误公一生!……今教公之法:只讨圣贤之书,逐日逐段,分明理会。且降伏其心,逊志以求之,理会得一句,便一句理明;理会得一段,便一段义明;积累久之,渐渐晓得。’”②朱子认为陆子静自己不重下学工夫,又教人不要读书,误导后学,对学术风气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朱子强调读书、穷理工夫,皆是从一句话、一件事中做起,工夫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实现贯通,无论是下学还是上达都需要逐项理会,积累久久才能达到贯通的境界。由上分析可知,朱子强调“下学而上达”与朱子强调以致知作为工夫的入手处相对应,朱子注重格物、穷理等下学工夫的积累终与陆学的成德路径相区别。
2.辟“先见天理源头”
朱子晚年时期因陈淳喜言“先见天理本原”,所以特别向陈淳阐明“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对门人偏向主敬涵养进行纠偏。当陈淳提出下学是不是大段工夫时,朱子说:“圣贤教人,多说下学事,少说上达事。说下学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会下学,又局促了。须事事理会过,将来也要知个贯通处。不要理会下学,只理会上达,即都无事可做,恐孤单枯燥。”①朱子指出要多说下学的工夫,少说上达的工夫,因为没有下学就不可能有上达,朱子说:“然尝以熹所闻圣贤之学,则见其心之所有不离乎日用寻常之近小,而其远者大者自不待于他求,初不若是其荒忽放浪而无所归宿也,故曰‘下学而上达’。”②朱子指出下学工夫是离日用寻常最近的地方,做工夫应先从近的地方做起,如果先从上达处做,则过于空疏放浪。同时朱子也指出不能只做下学的工夫,否则气象狭隘,但如果只理会上达,则都是高深的道理,无事可做,则孤单枯燥。所以下学与上达都要做工夫,久了自然能从下学贯通到上达,但是如果只想着贯通处,不做下学的工夫则无法成德,朱子说:“譬如耕田,须是下了种子,便去耘锄灌溉,然后到那熟处。而今只想象那熟处,却不曾下得种子,如何会熟?”③可见,朱子认为应该从下学工夫开始做起,没有下学就不可能上达,对于下学的工夫内容,朱子也有详细的讨论。
胡叔器因问:“下学莫只是就切近处求否?”曰:“也不须恁地拣,事到面前,便与他理会。且如读书:读第一章,便与他理会第一章;读第二章,便与他理会第二章。今日撞着这事,便与他理会这事;明日撞着那事,便理会那事。万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拣大底要底理会,其它都不管。程先生曰:‘穷理者,非谓必尽穷天下之理,又非谓止穷得一理便到。但积累多后,自当脱然有悟处。’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万物之理,理会得多,自当豁然有个觉处。’今人务博者,却要尽穷天下之理;务约者又谓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此皆不是。”①
前文分析可见,朱子提出要从日用处先做工夫,即先做下学工夫,门人胡安之因此提出下学是否只是就近处求,朱子则回答说不是有意拣近处做工夫,而是由具体的事决定,遇到什么事,就在什么事上理会,就像读书,读第一章,便理会第一章,读第二章便理会第二章,万事只是一理,不能只挑大的要紧的事去理会,其他事都不管。朱子又引二程言穷理不一定要穷尽天下之理,也不是穷得一理就停止,但是积累很多后,自然有贯通领悟的地方。二程又说从自己身上以至于万事万物之理理会得多了自然豁然有觉悟的地方。可以看出,穷理就是下学的积累,贯通是上达,朱子晚年以意诚为心与理的贯通处。朱子又提出现在有人专务博文却要去穷尽天下之理,专务约礼又说反身而诚则天下之物无不在我,这都是不对的,因为颠倒了下学和上达的工夫次序。由此也可以看出,朱子反对先从上达做工夫与反对先从贯通处做工夫、反对先见天理源头是一致的,这也是朱子晚年将居敬穷理互发、知行互发限定在工夫的境界义的原因。朱子强调做工夫要从下学做起,与朱子晚年重视穷理、致知、省察的工夫也是一以贯之的。
曾子父子之学自相反,一是从下做到,一是从上见得。子贡亦做得七八分工夫,圣人也要唤醒他,唤不上。圣人不是不说这道理,也不是便说这道理,只是说之有时,教人有序。子晦之说无头。如吾友所说从原头来,又却要先见个天理在前面,方去做,此正是病处。子晦疑得也是,只说不出。吾友合下来说话,便有此病;是先见“有所立卓尔”,然后“博文约礼”也。……下学上达,自有次第。于下学中又有次第:致知又有多少次第,力行又有多少次第。淳曰:“下学中,如致知时,亦有理会那上达底意思否?”曰:“非也。致知,今且就这事上,理会个合做底是如何?少间,又就这事上思量合做底,因甚是恁地?便见得这事道理合恁地。又思量因甚道理合恁地?便见得这事道理原头处。逐事都如此理会,便件件知得个原头处。”①
曾子父子的工夫路径是相反的,曾点是先见上达,曾子是先从下学开始做,子贡是下学做了七八分,孔子要启发他,但没有成功,这说明圣人教人成德的方法有很多,因人因时而异。但廖子晦的说法没有根据,如果说从源头来,又要在源头前面先见个天理才去做工夫,这就是问题所在,就等于说先见“所立卓尔”的境界,然后再去博文约礼,二者都是上达处,不是做工夫处。朱子提出下学上达中自然有工夫次第,下学中,致知就是在事上理会理以及理之所以然,再去思考如何合于理、为什么能合于理,如此最后见到道理的源头,如果逐事都如此理会,则件件事情都能知道道理的源头处,所以道理的源头处是从格物、穷理、致知上逐渐完成的,由此也说明了下学和上达的关系。朱子晚年反对廖子晦“先见天理源头”,也反对陈淳“只吃馒头尖处”,1199年,朱子与陈淳相别十年后会面坐论。朱子见陈淳言主敬涵养则件件天理流行可见也有“先见天理源头”的问题,故与陈淳做了详细的讨论。
先生曰:“尧卿安卿且坐。相别十年,有甚大头项工夫,大头项疑难,可商量处?”淳曰:“数年来见得日用间大事小事分明,件件都是天理流行,无一事不是合做底,更不容挨推闪避。……而其所以为此理之大处,却只在人伦;而身上工夫切要处,却只在主敬。敬则此心常惺惺,大纲卓然不昧,天理无时而不流行……”先生曰:“恁地泛说也容易。”久之,曰:“只恐劳心落在无涯可测之处。”①
由引文可见,朱子问陈淳相别十年是否有什么重要的修养方法和问题可以讨论,陈淳认为自己数年大事小事都见得分明,每件事情都能做到天理流行,使事合于理。朱子认为天理最重要的地方在人伦日用中,所以自身最关键的工夫在于主敬。陈淳进一步提出主敬则此心常惺惺,大纲卓然不昧,天理无时不流行。对此,朱子表示这样泛说也容易,朱子思考了很久又指出陈淳偏向主敬恐怕会将心落在无涯可测之处,即恐怕会落入佛老虚无之说。所以当陈淳接着又问孔子“与点”②一段如何理解时,朱子就直接指出陈淳这样的理解是只吃馒头尖尖,提醒陈淳要重视下学的工夫。
因问:“向来所呈与点说一段如何?”曰:“某平生便是不爱人说此话。《论语》一部自‘学而时习之’至‘尧曰’,都是做工夫处。不成只说了‘与点’,便将许多都掉了。圣贤说事亲便要如此,事君便要如此,事长便要如此,言便要如此,行便要如此,都是好用工夫处。通贯浃洽,自然见得在面前。若都掉了,只管说‘与点’,正如吃馒头,只撮个尖处,不吃下面馅子,许多滋味都不见。……昨廖子晦亦说‘与点’及鬼神,反复问难,转见支离没合杀了。圣贤教人,无非下学工夫。”①
由引文可知,朱子对陈淳提出自己不喜欢别人过于关注孔子表扬曾点这段话,朱子认为孔子教人都是从做工夫处教人,不能因为夫子有一次赞同曾点的志向便将人伦日用近处的工夫都省去。圣贤说事亲、事君、事长、言、行都是做工夫的地方,如果只说“与点”即只是立志,就像吃馒头只吃馒头尖处不吃下面的馅,所以下面许多滋味都不知道。朱子认为廖子晦也说“与点”,与陈淳都是一样的问题。由此可见,朱子去世的前一年仍在讨论成德的工夫路径,一方面基于对陆学上达而下学的批评,一方面基于对门人先见天理源头的检查,二者的问题都在于不重视下学工夫,没有遵循下学而上达的成德路径。朱子最后提出“圣贤教人,无非下学工夫”,这句话是说得很重的,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在上达处做工夫的意义,上达是通过下学积累到一定程度所达到的境界,所以不是做工夫处。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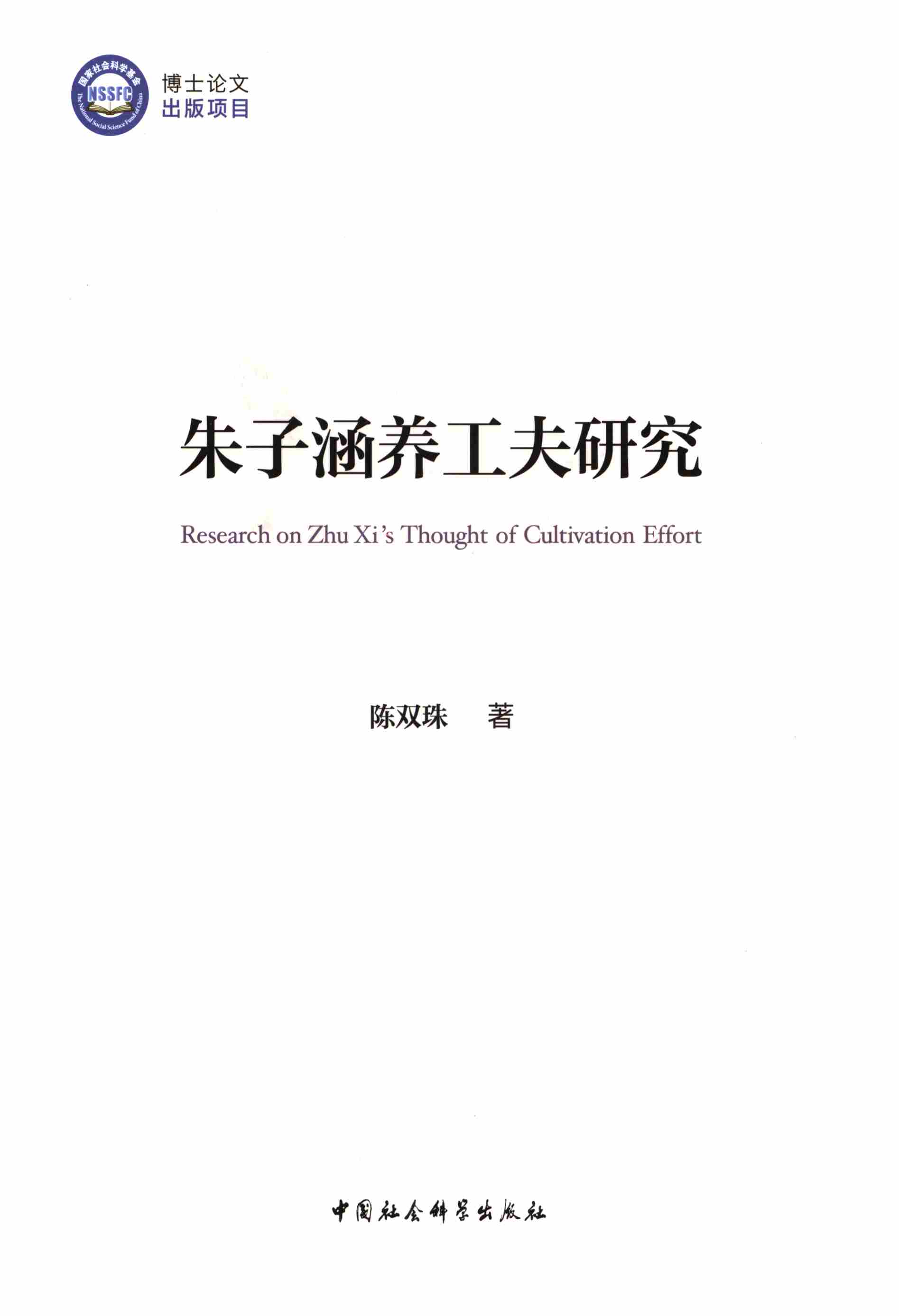
《朱子涵养工夫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以朱子涵养工夫为研究对象,将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分为中年、中晚年、晚年三个阶段,梳理出朱子涵养工夫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和发展历程。全书围绕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涵养工夫内在的关系以及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三个角度对朱子涵养工夫进行了考察;从脉络发展的视野厘清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和思想地位;从学术史论辩的视野探寻朱子涵养工夫的特点;从工夫论的确立到完善的动态考察探求朱子涵养工夫思想背后的心性论的建构和完善的过程;从而对朱子的修身涵养理论进行了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研究,也对学术史上关于朱子涵养工夫的诸多判定和争议进行了检查。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