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一)合说与分说
朱子中年时期以敬代诚,合说诚敬,以诚为形容敬的虚词,所以诚没有独立的工夫意义。朱子进入晚年后仍有继续合说诚敬的情况,如朱子说:“用诚敬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③但是,朱子晚年后开始注意在合说诚敬的同时也区分二者的不同,61岁后曾有人问:“‘祭如在’,人子固是尽诚意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④朱子答:“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这里尽其诚敬,祖宗之气便在这里,只是一个根苗来。如树已枯朽,边傍新根,即接续这正气来。”①在此,朱子悄然将“尽诚以祭”的说法改为“尽诚敬”,祭祀只有诚是不够的,持敬不可缺少,祭祀还是以敬为主。64岁时朱子又说:“‘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自谓当祭之时,或有故而使人摄之,礼虽不废,然不得自尽其诚敬,终是不满于心也。……盖神明不可见,惟是此心尽其诚敬,专一在于所祭之神,便见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②朱子认为祭祀的时候礼不能废,最关键的是心做到十分的诚敬,诚敬就是专一,可见诚敬的重点还是在敬上。但是合说诚敬比单说一个“敬”字更好,这说明诚还是有独立的意义的。
用之问:“舜‘孳孳为善’。‘未接物时,只主于敬,便是为善。’以此观之,圣人之道不是默然无言。圣人之心‘纯亦不已’,虽无事时,也常有个主宰在这里。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这便如夜来说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须常存个诚敬做主,学问方有所归着。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顿处。不然,却似无家舍人,虽有千万之宝,亦无安顿处。”③
对于门人以主敬来说明未发前涵养工夫的重要,朱子则提出要存诚敬之心作为主宰,学问才有归处,才有着落处。诚敬之心如果能存得就像人有屋舍,有安顿之处。在此,朱子言诚敬涵养,也是以诚形容持敬的程度。63岁后朱子还说:“斯须之间,人谁不能,未知他果有诚敬之心否。”①正因为朱子常将诚敬合说,会使人产生诚敬是一个工夫的误解,有人便问:“专一可以至诚敬否?”②朱子却回答:“诚与敬不同。”③持敬是专一,诚不是专一,诚就是一,所以朱子认为诚与敬不同,不能以专一作为诚与敬的方法。如此说明当朱子合说诚敬,诚也有自己单独的意义,合说是因为诚敬都为涵养工夫,诚是对主敬涵养的补充,分说是因为二者有自己独立的工夫意义。合说诚敬是朱子的工夫特色,相比之下,陆子静则反对合说诚敬。象山认为诚与敬是不同的工夫,故不能合说,并且象山肯定诚但否定敬,他说:“且如‘存诚’‘持敬’二语自不同,岂可合说?‘存诚’字于古有考,‘持敬’字乃后来杜撰。《易》曰:‘闲邪存其诚。’《孟子》曰:‘存其心’,某旧亦尝以‘存’名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某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夫天所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④象山认为存诚与持敬是两个不同的工夫,其以《易经》言存诚为依据,以诚为“心之本体”与良心等同,《易经》的“存诚”就是《孟子》的存心,孟子言“反身而诚”,只要存诚就能自然明理,因为理本在心内,所以存诚就是存得此心为主宰。由此可见,象山认同诚的工夫,认为诚在《易经》《孟子》等经典中有依据,而持敬却没有,象山认为持敬是二程后来的杜撰,在经典中没有出处,所以象山否定持敬作为涵养的主要工夫,也反对合说诚敬,由此体现出二者是遵从孔子还是孟子的学术脉络的差异。
(二)二者逐处理会
由前文分析可知,象山反对朱子合说诚敬,将诚解为存诚,如此诚不是工夫而是诚体或者心体,诚本身不能成为工夫,要通过存才能成为工夫。朱子与象山不同,朱子中年时期已将诚解为实,诚是动词不是名词,晚年依然延续中年时期的理解。朱子说:“‘反身而诚’,见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亏欠了他底。”①又说:“‘反身而诚’,孟子之意主于‘诚’字,言反身而实有此理也。为父而实有慈,为子而实有孝,岂不快活。若反身不诚,是无此理。既无此理,但有恐惧而已,岂得乐哉!”②朱子认为诚就是将本心所具之理真实展现,并以此诠释孟子反身而诚的思想。对于诚与敬的区别,朱子中晚年时期已经提出诚与敬的区别是实与畏,晚年时期仍是依此作为区分诚敬,朱子说:“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诚是不欺妄底意思。”③持敬是不放纵,诚是不欺妄。此外,朱子晚年还讨论了诚与敬工夫的先后次序,基于二程所说:“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须敬而后能诚。”④宋容之认为“诚必在敬之先”,二程对诚敬的先后分两个情况来说,如果诚的工夫做好就可以完成持敬,但如果诚的工夫没有完成,须以持敬来帮助诚的完成。在此,二程似乎偏重于诚在持敬之先,宋容之才会有如此理解,但是朱子是反对的,他说:“如‘好乐苟善,不害于正’之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说、‘敬必以诚为先’之说,亦互有得失,但终是本领未正,未容轻议,便使一一剖析将去,亦恐未必有益。”⑤朱子认为宋容之的观点太绝对,如果一一剖析则站不住脚,可惜朱子彼时并没有做进一步讨论。65岁时,朱子重新解释了诚敬先后的问题。
胡:学者问曰:“《遗书》曰:‘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须敬而后能诚。’学者如何便能诚?恐不若专主于敬而后能诚也。”大时答曰:“诚者天之道也,而实然之理亦可以言诚。敬道之成,则圣人矣,而整齐严肃亦可以言敬。此两事者,皆学者所当用力也。”
朱: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诚是真实无妄之名,意思不同。诚而后能敬者,意诚而后心正也;敬而后能诚者,意虽未诚,而能常若有畏,则当不敢自欺而进于诚矣。此程子之意也。问者略见此意而不能达之于言,答者却答不着。①
对于《遗书》中所言诚与敬的关系,有人对胡季随提出人不能直接完成诚的工夫,应该要先主于敬然后才能诚,对此胡季随回答说诚虽然是天之道,但实然之理也可以言诚,敬是此天之道的完成,是圣人的境界,但是整齐严肃也可以言敬。胡季随的意思是当以诚为天之道,敬为天之道完成时,诚在敬先。当以诚为实然之理,敬为整顿身心时,则敬在诚先。胡季随其实区分了诚与敬从工夫的境界和做工夫上说的两个含义,从境界上说诚在敬先,从做工夫上说,敬在诚先。朱子对胡季随的回答不够满意,他认为胡季随“答者却答不着”,没回答到点子上。朱子认为应该从工夫的内容上区分二者,敬是畏,诚是真实无妄,二者意思不同。二程“诚然后能敬”是说“意诚然后心正”,这是从工夫境界上而言的。而“敬而后能诚”是说还没有到意诚的程度时,常常用敬的工夫使其有畏的状态,如此则不敢自欺,能对诚意工夫有一进步的帮助作用。朱子以诚的工夫的完成为意诚,以敬的工夫的完成为心正,所以二程说诚然后能敬,但是从做工夫上看,持敬对诚意有帮助作用,所以在诚意之前就应该落实持敬工夫。在此朱子将诚落到意上说,与象山的诚体相区别,诚落到意上说之后,诚的工夫更为平实,也延续了中晚年时期的观点。由此也可以注意到,无论从做工夫还是从工夫的境界上说,诚意的地位没有超出持敬,体现出朱子主敬涵养的立场。在对诚与敬工夫相区别的基础上,朱子提出不要太过于纠结诚与敬的先后次序,最重要的是理解如何做工夫,然后逐项落实。
因问:“‘诚敬’二字如何看?”广云:“先敬,然后诚。”曰:“且莫理会先后。敬是如何?诚是如何?”广曰:“敬是把作工夫,诚则到自然处。”曰:“敬也有把捉时,也有自然时;诚也有勉为诚时,亦有自然诚时。且说此二字义,敬只是个收敛畏惧,不纵放;诚只是个朴直悫实,不欺诳。初时须着如此不纵放,不欺诳;到得工夫到时,则自然不纵放,不欺诳矣。”①
朱子问辅广如何理解“诚敬”二字,辅广认为诚的完成在敬之后,朱子则提出不要理会二者的先后次序,重点在二者如何做工夫。辅广认为敬是“把捉”,有勉强之意,诚则是到自然不勉强的境界,可见辅广认为诚的境界高于敬。朱子则提出敬也有勉强的时候,也可达到自然不勉强的境界。诚的工夫也有勉强为诚的时候,也有自然为诚的时候,不能只以境界为区分标准。二者只要从工夫的含义上进行区分,敬只是收敛畏惧的意思,持敬是不放纵身心;诚是朴直真实的意思,诚就是不欺妄。刚开始做工夫的时候二者都是勉强的过程,但工夫做到一定境界就自然不放纵,自然不欺妄了,敬与诚都要经过勉力的过程才能达到不勉的境界。朱子在此其实强调了二者从工夫的完成上看其实没有高下之分,所以不需要区分先后,只要二者都勉力做工夫。
“苏季明尝患思虑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诚之本也。须是事事能专一时,便好。不拘思虑与应事,皆要专一。’而今学问,只是要一个专一……”或问:“专一可以至诚敬否?”曰:“诚与敬不同:诚是实理,是人前辈后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诚。若只做得两三分,说道今且谩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诚。敬是戒慎恐惧意。”①
朱子认为苏季明有“思虑不定”的问题,伊川认为的思虑不定是不能诚的根本原因。如果事事都能做到专一,则思虑就能定。学问求理也只要专一就不会有思虑不定的问题。在此伊川想要表达持敬对诚意的作用。但是,当有人依此提出专一是否可以达到诚敬时,朱子则回答诚与敬二者的工夫是不同的。诚就是实实在在遵循理,人前人后都如此,做一件事做到十分,不到十分都不是诚。持敬就是戒慎恐惧的意思,没有程度的要求,说明在做工夫的要求上,诚的要求比敬高,诚意的工夫比较难。所以朱子后来又说:“‘谨’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诚。程子曰:‘主一之谓敬,一者之谓诚。’敬尚是着力。”②朱子认为谨的要求不如敬,敬的要求则不如诚。敬是主一,而诚则是一,敬是往一的方向努力,而诚就是要做到一,但其中要经历从勉强到不勉强的过程,朱子说:“‘反身而诚’,则恕从这里流出,不用勉强。未到恁田地,须是勉强。此因林伯松问‘强恕’说。”①朱子以强恕说明诚的过程是敬贯通了勉励而行最终到达不勉而行的境界。
以此为基础,也就可以理解朱子言主敬行恕的意思,恕其实是诚的工夫。朱子说:“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在学者也知得此理是备于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诚’。若勉强行恕,拗转这道理来,便是恕。所谓勉强者,犹未能恕,必待勉强而后能也。所谓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尽了,这道理便真实备于我,无欠阙。”②朱子认为要达到反身而诚的过程需要勉强行恕,行恕需要勉力而行,而恕是行恕后的结果,是勉强而行的结果,就去去除私意,使道理真实备于我,在此朱子将恕、诚意和反身而诚等同。正因为诚与敬工夫内容上的区别,所以朱子提出诚敬须逐处做工夫,二者不要混在一起说,朱子说:“须逐处理会。诚若是有不欺意处,只做不欺意会;敬若是有谨畏意处,只做谨畏意会。中庸说诚,作中庸看;孟子说诚处,作孟子看。将来自相发明耳。”③如果有自欺的地方就做诚意工夫,有不敬畏的情况就做持敬工夫,《中庸》与《孟子》的诚各自做工夫,等到达一定境界,自然能够相互发明、相互补充。
朱子中年时期以敬代诚,合说诚敬,以诚为形容敬的虚词,所以诚没有独立的工夫意义。朱子进入晚年后仍有继续合说诚敬的情况,如朱子说:“用诚敬涵养为格物致知之本。”③但是,朱子晚年后开始注意在合说诚敬的同时也区分二者的不同,61岁后曾有人问:“‘祭如在’,人子固是尽诚意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④朱子答:“上蔡言:‘自家精神,即祖考精神。’这里尽其诚敬,祖宗之气便在这里,只是一个根苗来。如树已枯朽,边傍新根,即接续这正气来。”①在此,朱子悄然将“尽诚以祭”的说法改为“尽诚敬”,祭祀只有诚是不够的,持敬不可缺少,祭祀还是以敬为主。64岁时朱子又说:“‘吾不与祭,如不祭’,孔子自谓当祭之时,或有故而使人摄之,礼虽不废,然不得自尽其诚敬,终是不满于心也。……盖神明不可见,惟是此心尽其诚敬,专一在于所祭之神,便见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②朱子认为祭祀的时候礼不能废,最关键的是心做到十分的诚敬,诚敬就是专一,可见诚敬的重点还是在敬上。但是合说诚敬比单说一个“敬”字更好,这说明诚还是有独立的意义的。
用之问:“舜‘孳孳为善’。‘未接物时,只主于敬,便是为善。’以此观之,圣人之道不是默然无言。圣人之心‘纯亦不已’,虽无事时,也常有个主宰在这里。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槁木死灰。”曰:“这便如夜来说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须常存个诚敬做主,学问方有所归着。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顿处。不然,却似无家舍人,虽有千万之宝,亦无安顿处。”③
对于门人以主敬来说明未发前涵养工夫的重要,朱子则提出要存诚敬之心作为主宰,学问才有归处,才有着落处。诚敬之心如果能存得就像人有屋舍,有安顿之处。在此,朱子言诚敬涵养,也是以诚形容持敬的程度。63岁后朱子还说:“斯须之间,人谁不能,未知他果有诚敬之心否。”①正因为朱子常将诚敬合说,会使人产生诚敬是一个工夫的误解,有人便问:“专一可以至诚敬否?”②朱子却回答:“诚与敬不同。”③持敬是专一,诚不是专一,诚就是一,所以朱子认为诚与敬不同,不能以专一作为诚与敬的方法。如此说明当朱子合说诚敬,诚也有自己单独的意义,合说是因为诚敬都为涵养工夫,诚是对主敬涵养的补充,分说是因为二者有自己独立的工夫意义。合说诚敬是朱子的工夫特色,相比之下,陆子静则反对合说诚敬。象山认为诚与敬是不同的工夫,故不能合说,并且象山肯定诚但否定敬,他说:“且如‘存诚’‘持敬’二语自不同,岂可合说?‘存诚’字于古有考,‘持敬’字乃后来杜撰。《易》曰:‘闲邪存其诚。’《孟子》曰:‘存其心’,某旧亦尝以‘存’名斋。《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某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夫天所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④象山认为存诚与持敬是两个不同的工夫,其以《易经》言存诚为依据,以诚为“心之本体”与良心等同,《易经》的“存诚”就是《孟子》的存心,孟子言“反身而诚”,只要存诚就能自然明理,因为理本在心内,所以存诚就是存得此心为主宰。由此可见,象山认同诚的工夫,认为诚在《易经》《孟子》等经典中有依据,而持敬却没有,象山认为持敬是二程后来的杜撰,在经典中没有出处,所以象山否定持敬作为涵养的主要工夫,也反对合说诚敬,由此体现出二者是遵从孔子还是孟子的学术脉络的差异。
(二)二者逐处理会
由前文分析可知,象山反对朱子合说诚敬,将诚解为存诚,如此诚不是工夫而是诚体或者心体,诚本身不能成为工夫,要通过存才能成为工夫。朱子与象山不同,朱子中年时期已将诚解为实,诚是动词不是名词,晚年依然延续中年时期的理解。朱子说:“‘反身而诚’,见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亏欠了他底。”①又说:“‘反身而诚’,孟子之意主于‘诚’字,言反身而实有此理也。为父而实有慈,为子而实有孝,岂不快活。若反身不诚,是无此理。既无此理,但有恐惧而已,岂得乐哉!”②朱子认为诚就是将本心所具之理真实展现,并以此诠释孟子反身而诚的思想。对于诚与敬的区别,朱子中晚年时期已经提出诚与敬的区别是实与畏,晚年时期仍是依此作为区分诚敬,朱子说:“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诚是不欺妄底意思。”③持敬是不放纵,诚是不欺妄。此外,朱子晚年还讨论了诚与敬工夫的先后次序,基于二程所说:“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须敬而后能诚。”④宋容之认为“诚必在敬之先”,二程对诚敬的先后分两个情况来说,如果诚的工夫做好就可以完成持敬,但如果诚的工夫没有完成,须以持敬来帮助诚的完成。在此,二程似乎偏重于诚在持敬之先,宋容之才会有如此理解,但是朱子是反对的,他说:“如‘好乐苟善,不害于正’之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说、‘敬必以诚为先’之说,亦互有得失,但终是本领未正,未容轻议,便使一一剖析将去,亦恐未必有益。”⑤朱子认为宋容之的观点太绝对,如果一一剖析则站不住脚,可惜朱子彼时并没有做进一步讨论。65岁时,朱子重新解释了诚敬先后的问题。
胡:学者问曰:“《遗书》曰:‘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须敬而后能诚。’学者如何便能诚?恐不若专主于敬而后能诚也。”大时答曰:“诚者天之道也,而实然之理亦可以言诚。敬道之成,则圣人矣,而整齐严肃亦可以言敬。此两事者,皆学者所当用力也。”
朱: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诚是真实无妄之名,意思不同。诚而后能敬者,意诚而后心正也;敬而后能诚者,意虽未诚,而能常若有畏,则当不敢自欺而进于诚矣。此程子之意也。问者略见此意而不能达之于言,答者却答不着。①
对于《遗书》中所言诚与敬的关系,有人对胡季随提出人不能直接完成诚的工夫,应该要先主于敬然后才能诚,对此胡季随回答说诚虽然是天之道,但实然之理也可以言诚,敬是此天之道的完成,是圣人的境界,但是整齐严肃也可以言敬。胡季随的意思是当以诚为天之道,敬为天之道完成时,诚在敬先。当以诚为实然之理,敬为整顿身心时,则敬在诚先。胡季随其实区分了诚与敬从工夫的境界和做工夫上说的两个含义,从境界上说诚在敬先,从做工夫上说,敬在诚先。朱子对胡季随的回答不够满意,他认为胡季随“答者却答不着”,没回答到点子上。朱子认为应该从工夫的内容上区分二者,敬是畏,诚是真实无妄,二者意思不同。二程“诚然后能敬”是说“意诚然后心正”,这是从工夫境界上而言的。而“敬而后能诚”是说还没有到意诚的程度时,常常用敬的工夫使其有畏的状态,如此则不敢自欺,能对诚意工夫有一进步的帮助作用。朱子以诚的工夫的完成为意诚,以敬的工夫的完成为心正,所以二程说诚然后能敬,但是从做工夫上看,持敬对诚意有帮助作用,所以在诚意之前就应该落实持敬工夫。在此朱子将诚落到意上说,与象山的诚体相区别,诚落到意上说之后,诚的工夫更为平实,也延续了中晚年时期的观点。由此也可以注意到,无论从做工夫还是从工夫的境界上说,诚意的地位没有超出持敬,体现出朱子主敬涵养的立场。在对诚与敬工夫相区别的基础上,朱子提出不要太过于纠结诚与敬的先后次序,最重要的是理解如何做工夫,然后逐项落实。
因问:“‘诚敬’二字如何看?”广云:“先敬,然后诚。”曰:“且莫理会先后。敬是如何?诚是如何?”广曰:“敬是把作工夫,诚则到自然处。”曰:“敬也有把捉时,也有自然时;诚也有勉为诚时,亦有自然诚时。且说此二字义,敬只是个收敛畏惧,不纵放;诚只是个朴直悫实,不欺诳。初时须着如此不纵放,不欺诳;到得工夫到时,则自然不纵放,不欺诳矣。”①
朱子问辅广如何理解“诚敬”二字,辅广认为诚的完成在敬之后,朱子则提出不要理会二者的先后次序,重点在二者如何做工夫。辅广认为敬是“把捉”,有勉强之意,诚则是到自然不勉强的境界,可见辅广认为诚的境界高于敬。朱子则提出敬也有勉强的时候,也可达到自然不勉强的境界。诚的工夫也有勉强为诚的时候,也有自然为诚的时候,不能只以境界为区分标准。二者只要从工夫的含义上进行区分,敬只是收敛畏惧的意思,持敬是不放纵身心;诚是朴直真实的意思,诚就是不欺妄。刚开始做工夫的时候二者都是勉强的过程,但工夫做到一定境界就自然不放纵,自然不欺妄了,敬与诚都要经过勉力的过程才能达到不勉的境界。朱子在此其实强调了二者从工夫的完成上看其实没有高下之分,所以不需要区分先后,只要二者都勉力做工夫。
“苏季明尝患思虑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诚之本也。须是事事能专一时,便好。不拘思虑与应事,皆要专一。’而今学问,只是要一个专一……”或问:“专一可以至诚敬否?”曰:“诚与敬不同:诚是实理,是人前辈后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诚。若只做得两三分,说道今且谩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诚。敬是戒慎恐惧意。”①
朱子认为苏季明有“思虑不定”的问题,伊川认为的思虑不定是不能诚的根本原因。如果事事都能做到专一,则思虑就能定。学问求理也只要专一就不会有思虑不定的问题。在此伊川想要表达持敬对诚意的作用。但是,当有人依此提出专一是否可以达到诚敬时,朱子则回答诚与敬二者的工夫是不同的。诚就是实实在在遵循理,人前人后都如此,做一件事做到十分,不到十分都不是诚。持敬就是戒慎恐惧的意思,没有程度的要求,说明在做工夫的要求上,诚的要求比敬高,诚意的工夫比较难。所以朱子后来又说:“‘谨’字未如敬,敬又未如诚。程子曰:‘主一之谓敬,一者之谓诚。’敬尚是着力。”②朱子认为谨的要求不如敬,敬的要求则不如诚。敬是主一,而诚则是一,敬是往一的方向努力,而诚就是要做到一,但其中要经历从勉强到不勉强的过程,朱子说:“‘反身而诚’,则恕从这里流出,不用勉强。未到恁田地,须是勉强。此因林伯松问‘强恕’说。”①朱子以强恕说明诚的过程是敬贯通了勉励而行最终到达不勉而行的境界。
以此为基础,也就可以理解朱子言主敬行恕的意思,恕其实是诚的工夫。朱子说:“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在学者也知得此理是备于我,只是未能‘反身而诚’。若勉强行恕,拗转这道理来,便是恕。所谓勉强者,犹未能恕,必待勉强而后能也。所谓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尽了,这道理便真实备于我,无欠阙。”②朱子认为要达到反身而诚的过程需要勉强行恕,行恕需要勉力而行,而恕是行恕后的结果,是勉强而行的结果,就去去除私意,使道理真实备于我,在此朱子将恕、诚意和反身而诚等同。正因为诚与敬工夫内容上的区别,所以朱子提出诚敬须逐处做工夫,二者不要混在一起说,朱子说:“须逐处理会。诚若是有不欺意处,只做不欺意会;敬若是有谨畏意处,只做谨畏意会。中庸说诚,作中庸看;孟子说诚处,作孟子看。将来自相发明耳。”③如果有自欺的地方就做诚意工夫,有不敬畏的情况就做持敬工夫,《中庸》与《孟子》的诚各自做工夫,等到达一定境界,自然能够相互发明、相互补充。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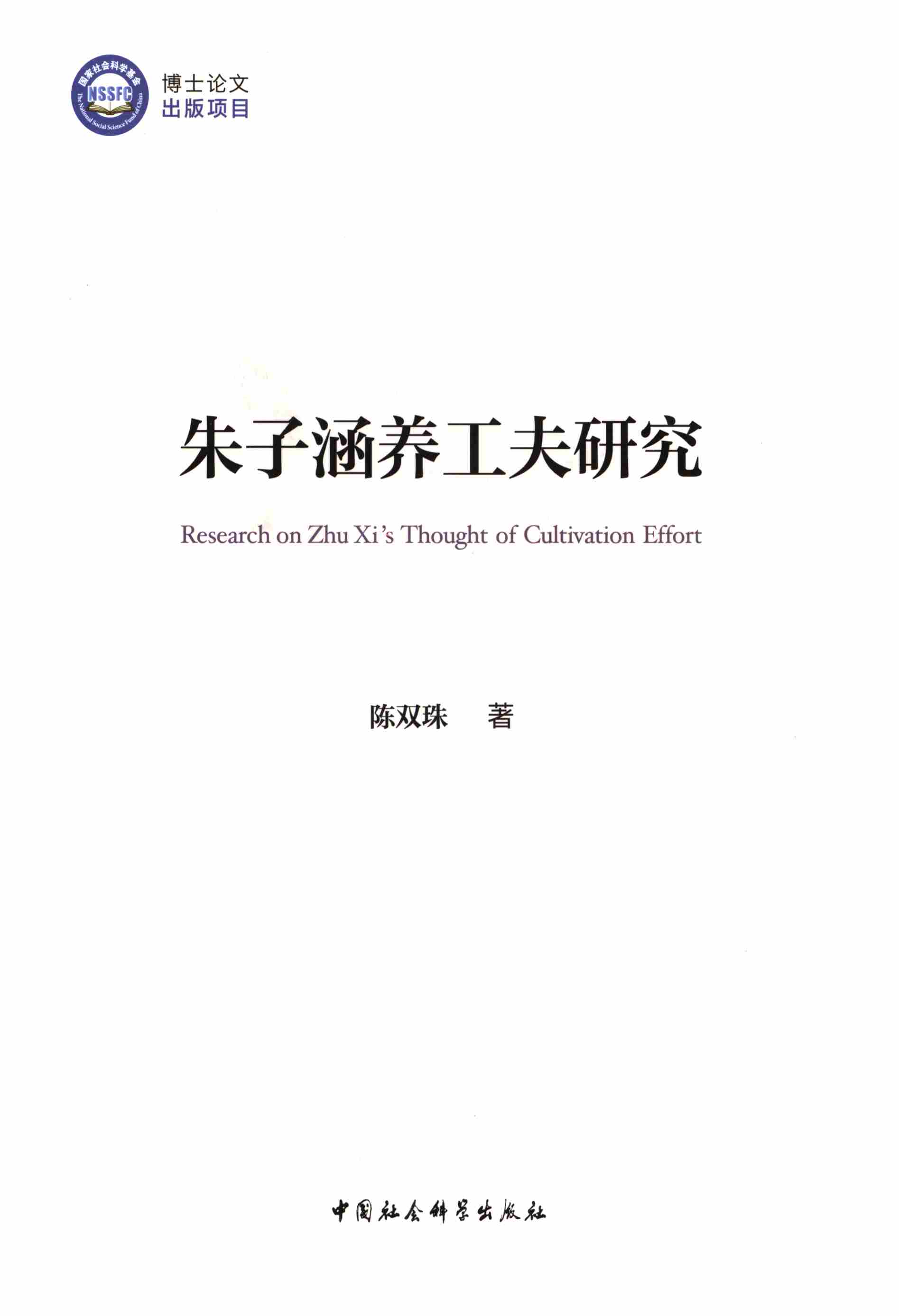
《朱子涵养工夫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以朱子涵养工夫为研究对象,将朱子涵养工夫的发展分为中年、中晚年、晚年三个阶段,梳理出朱子涵养工夫思想发展的大体脉络和发展历程。全书围绕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涵养工夫内在的关系以及涵养工夫在朱子工夫论中的地位三个角度对朱子涵养工夫进行了考察;从脉络发展的视野厘清朱子涵养工夫的内容和思想地位;从学术史论辩的视野探寻朱子涵养工夫的特点;从工夫论的确立到完善的动态考察探求朱子涵养工夫思想背后的心性论的建构和完善的过程;从而对朱子的修身涵养理论进行了整体性、系统性、动态性的研究,也对学术史上关于朱子涵养工夫的诸多判定和争议进行了检查。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