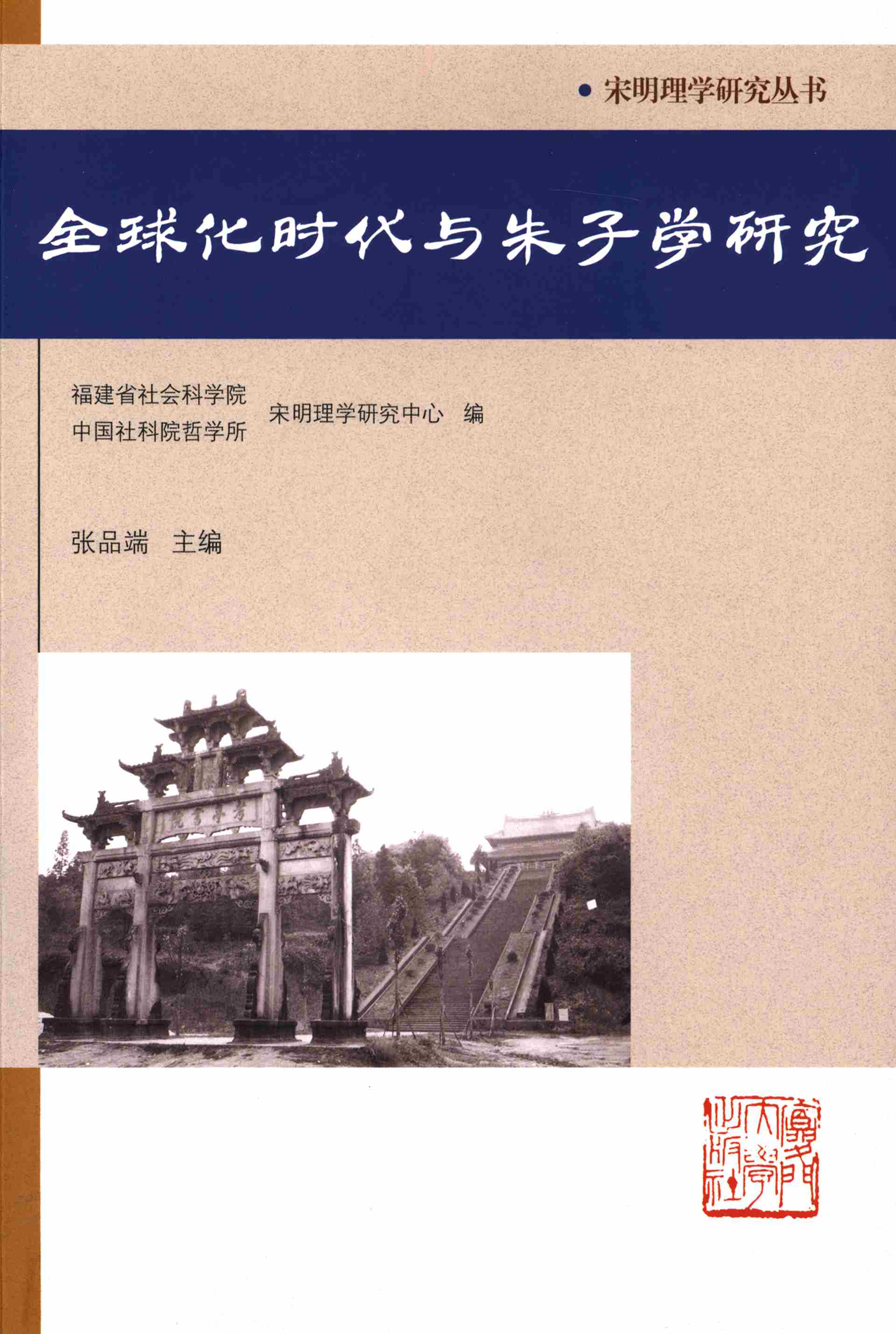三、“国法”顺应“天理”
| 内容出处: | 《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8204 |
| 颗粒名称: | 三、“国法”顺应“天理”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5 |
| 页码: | 114-11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宋明理学强调“国法”必须顺应“天理”,法有定制,依法审判。立法应保持稳定性和一贯性,司法应追求客观实在,依法审判已成为常态。执法者不能受制于人情而违法,要保障法的公正性和司法的正义性。 |
| 关键词: | 宋明理学 国法 法律思想 |
内容
“国法”顺应“天理”,就是说国法的创建、修改以及适用都必须符合“理”之“势”,要适应天理发展的趋向与需要。一方面只要是合理的就必然能够成势,“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而另一方面,顺势就必然能够达到合理,“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③,“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也”④,不可逆理而为:“顺逆者理也,理所制者道也。可否者事也,事以成者势也。以其顺成其可,以其逆成其否,理成势者也。循其可则顺,用其否则逆,势成理者也。”⑤应当因势顺理,达到天下平的最高境界。而宋明理学的“势”是时势、形势、趋势,需要仔细研究、估计时势和审视权变,顺势而为。对于国法而言,宋明理学主张既要注重法律的规定性,又要视义理而为权的灵活性,坚持“法有定制”、依法审判、“随时制宜”的理性原则,这也是宋明理学义理化法律思想的又一表现。
一是法有定制:明儒丘浚主张“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不仅“能施行于一时”,且应“为法于百世”①。他主张立法应该保持“经常”:“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②丘浚论述:
人之有罪者,或犯于有司,则当随其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罚焉;或轻或重,必当其情,不可掩蔽也。否则,非明矣。雷之威岁岁有常,虩虩之声震惊百里,如国家有律令之制,违其式而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轻或重,皆定制,不可变渝也。否则,非敕矣。夫法有定制,而人之犯也不常。则随其所犯而施之以责罚,必明必允,使吾所罚者,与其一定之法,无或出入,无相背戾,常整饬而严谨焉。用狱如此,无不利者矣。③
强调了重视“立法稳定”问题。对于朱熹,也认为不能轻易地改变原有立法,指出“圣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者,兼当时人习惯,亦不以为异也”④。旧法的确是不再适合时宜也应当是“小变其法”,旧法对于现实并“无大利害”就“不必议更张”,“兴其滞补其弊”。而对于那些一时难以把握,于时并不有害的旧法则更是不能轻易地变法,而应当“谨守常法”。吕坤曾上疏曰:“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轻其重,太祖既定为律,列圣又增为例。如轻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则例不得为一定之法。”⑤这反映了宋明理学立法谨慎态度和保持立法的稳定性与一贯性。因此,在传统法律条款的制定实践中,宋元明清的基本法律保持相当的稳定性,立法者尽可能将犯罪情节、刑罚上做出准确的描述与精确规定,以减少司法官员自由裁量的空间。
二是依法审判。宋明理学为追求息讼理想目标,实现更为广义的利益平衡,也必然要求做到“合理”“合情”与“合法”,由此才能够避免民众对司法行为正当性的质疑,服判息讼。宋明理学法律义理化要求在以“义理之所当否”为辨别是非的根本准则同时,也将追求法律事实的客观实在作为重要内容,更为重视“案件的事理情节”与依律例断案,使之成为司法的重要依据。由人伦理性向科学理性、知识理性并举转变。因此,在宋以后,司法技术层面的“案情、实情”,追求“法律情节”合理性是司法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求其理所安”“夺于公证”:“以众说互相法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别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证,而无以误。”①而依法审判已经成为常态,曲法被视为逆理。故而张晋藩先生说:“从现存的司法档案中可以看出,依律例断案是清代民事案件审理的最基本形式。”②在诉讼过程中,不能与律例相背,“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③。肯定了依法审判的意义。
同时,“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饬法明伦,而法有轻重”④,因而需要“酌之理,参之分”予以处置。这就必将涉及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具体运用。“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皆执一之论,未尽于义也。义既未安,则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为公器也。不得于义,则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则不得为义”。充分肯定了“法者天下之公器”,要求“惟善持法”,承认了法的公正性。在此,程颐又阐释法与义关系,提出义的实现前提在于法为公器,而且“法王于义,义当而谓之屈法,不知法者也”⑤。强调了法的公正性,保障了义理的实现,同时不能够因为强求于义理而“屈法、不知法”,亵渎法的公正性。为追求天理,实现司法的公正性,理学家也要求执法者不能受制于人情而违法。程颐指出:“自古立法制事,牵于人情,率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防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⑥这就是说,如果因为“害于近戚,防于贵家”就会牵于人情,势必导致“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丧失法公正性,也就无法保障司法正义。不一味随意顺从不当人情这一理念为宋之士大夫普遍所接受,朱熹也指出:“处乡曲,固要人情周尽,但要分别是非,不要一面随顺,失了自家。”⑦
真德秀反对“殉人情”,“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骨瓦)公法,以殉人情”①。显然,理学家主张在法律运用中要“准情酌理”,于法外推情察理”,而又不“与律例十分相背”。司法者据实情判决无疑能体现天理的正义性,而司法者审判过程中遵循“情理”以合理规避律例,同样也是谋求实现利益平衡。这种利益平衡衡量的标准就是“天理、人情”,所以国法没有成为天理、人情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国法是利益平衡的具体体现。
三是随时制宜。“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矣”②,宋明理学之法律强调因势顺理、顺事制法、随时制宜的原则。定罪量刑,应随时势的变化与社会状况的不同而更改,以求因事而立的,“上古世淳而人朴,顺事而为治耳。至尧始为治道,因事制法,著见功迹,而可为典常也。不惟随时,亦其忧患后世而有作也”③、“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焉,则何义之有”④?这里说明二程认为对待以往制定的法律,要根据义理与具体情况进行修改,不能守成不变,“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二程认为: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处亦不见说,独答颜回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于四代中举这一个法式,其详细虽不可见,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后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⑤
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二程虽然说过孔子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但即使是三王之法,也要“损益文质,随时之宜”,只有随时顺事所制定的法律才能够符合时代要求。朱熹继承并发扬了二程思想,认为“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①。强调祖宗之法也是“随时”,“若经世一事,向使先生见用,其将如何?曰:亦是只是随时。”②先人立法之初本身就存在弊端,“虽是圣人法,岂有无弊者”、“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③。同时由于后人“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甚至认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④。故而对于不适时宜、有弊立法就必须“变而通之”,“圣人姑为一代之法,到不可用法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⑤、“使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礼,必裁酌从今之宜而为之也”,力求做到“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变”⑥。
王夫之从律法应因“势”顺“理”出发,提出“趋时更新”,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王夫之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⑦古代的制度法令只能适应于古代社会,而今天的治国方法也不一定能适应于后世。“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举凡一兴一废,一繁一简,因乎时而不可执也”⑧,王夫之认为律令的制定和变更必须因时因地而异。法律不因时而变,就会固守古制,墨守成法。
一是法有定制:明儒丘浚主张“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不仅“能施行于一时”,且应“为法于百世”①。他主张立法应该保持“经常”:“盖经常,则有所持循而无变易之烦。……以此立法,则民熟于耳目,而吏不能以为奸。”②丘浚论述:
人之有罪者,或犯于有司,则当随其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罚焉;或轻或重,必当其情,不可掩蔽也。否则,非明矣。雷之威岁岁有常,虩虩之声震惊百里,如国家有律令之制,违其式而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轻或重,皆定制,不可变渝也。否则,非敕矣。夫法有定制,而人之犯也不常。则随其所犯而施之以责罚,必明必允,使吾所罚者,与其一定之法,无或出入,无相背戾,常整饬而严谨焉。用狱如此,无不利者矣。③
强调了重视“立法稳定”问题。对于朱熹,也认为不能轻易地改变原有立法,指出“圣人立法,一定而不可易者,兼当时人习惯,亦不以为异也”④。旧法的确是不再适合时宜也应当是“小变其法”,旧法对于现实并“无大利害”就“不必议更张”,“兴其滞补其弊”。而对于那些一时难以把握,于时并不有害的旧法则更是不能轻易地变法,而应当“谨守常法”。吕坤曾上疏曰:“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轻其重,太祖既定为律,列圣又增为例。如轻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则例不得为一定之法。”⑤这反映了宋明理学立法谨慎态度和保持立法的稳定性与一贯性。因此,在传统法律条款的制定实践中,宋元明清的基本法律保持相当的稳定性,立法者尽可能将犯罪情节、刑罚上做出准确的描述与精确规定,以减少司法官员自由裁量的空间。
二是依法审判。宋明理学为追求息讼理想目标,实现更为广义的利益平衡,也必然要求做到“合理”“合情”与“合法”,由此才能够避免民众对司法行为正当性的质疑,服判息讼。宋明理学法律义理化要求在以“义理之所当否”为辨别是非的根本准则同时,也将追求法律事实的客观实在作为重要内容,更为重视“案件的事理情节”与依律例断案,使之成为司法的重要依据。由人伦理性向科学理性、知识理性并举转变。因此,在宋以后,司法技术层面的“案情、实情”,追求“法律情节”合理性是司法的重要内容,强调了“求其理所安”“夺于公证”:“以众说互相法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别似是而非者,亦将夺于公证,而无以误。”①而依法审判已经成为常态,曲法被视为逆理。故而张晋藩先生说:“从现存的司法档案中可以看出,依律例断案是清代民事案件审理的最基本形式。”②在诉讼过程中,不能与律例相背,“自理词讼,原不必事事照例。但本案情节,应用何律何例,必须考究明白,再就本地风俗,准情酌理而变通之,庶不与律例十分相背”③。肯定了依法审判的意义。
同时,“原情定罪,而罪有等差;饬法明伦,而法有轻重”④,因而需要“酌之理,参之分”予以处置。这就必将涉及天理、国法与人情的具体运用。“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皆执一之论,未尽于义也。义既未安,则非明也。有所不行,不害为公器也。不得于义,则非恩之正。害恩之正,则不得为义”。充分肯定了“法者天下之公器”,要求“惟善持法”,承认了法的公正性。在此,程颐又阐释法与义关系,提出义的实现前提在于法为公器,而且“法王于义,义当而谓之屈法,不知法者也”⑤。强调了法的公正性,保障了义理的实现,同时不能够因为强求于义理而“屈法、不知法”,亵渎法的公正性。为追求天理,实现司法的公正性,理学家也要求执法者不能受制于人情而违法。程颐指出:“自古立法制事,牵于人情,率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则害于近戚;限田产,则防于贵家。如此之类,既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则是牵于朋比也。”⑥这就是说,如果因为“害于近戚,防于贵家”就会牵于人情,势必导致“不能断以大公而必行”,丧失法公正性,也就无法保障司法正义。不一味随意顺从不当人情这一理念为宋之士大夫普遍所接受,朱熹也指出:“处乡曲,固要人情周尽,但要分别是非,不要一面随顺,失了自家。”⑦
真德秀反对“殉人情”,“公事在官,是非有理,轻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骨瓦)公法,以殉人情”①。显然,理学家主张在法律运用中要“准情酌理”,于法外推情察理”,而又不“与律例十分相背”。司法者据实情判决无疑能体现天理的正义性,而司法者审判过程中遵循“情理”以合理规避律例,同样也是谋求实现利益平衡。这种利益平衡衡量的标准就是“天理、人情”,所以国法没有成为天理、人情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国法是利益平衡的具体体现。
三是随时制宜。“时异而势异,势异而理亦异矣”②,宋明理学之法律强调因势顺理、顺事制法、随时制宜的原则。定罪量刑,应随时势的变化与社会状况的不同而更改,以求因事而立的,“上古世淳而人朴,顺事而为治耳。至尧始为治道,因事制法,著见功迹,而可为典常也。不惟随时,亦其忧患后世而有作也”③、“居今之时,不安今之法令,非义也。若论为治,不为则已,如复为之,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若须更改而后焉,则何义之有”④?这里说明二程认为对待以往制定的法律,要根据义理与具体情况进行修改,不能守成不变,“须于今之法度内处得其当,方为合义”。二程认为:
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损益文质,随时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处亦不见说,独答颜回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是于四代中举这一个法式,其详细虽不可见,而孔子但示其大法,使后人就上修之。二千年来,亦无一人识者。⑤
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二程虽然说过孔子之法“乃通万世不易之法”,但即使是三王之法,也要“损益文质,随时之宜”,只有随时顺事所制定的法律才能够符合时代要求。朱熹继承并发扬了二程思想,认为“祖宗之所以为法,盖亦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便。而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以遗子孙而欲其万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则变而通之,是乃后人之责”①。强调祖宗之法也是“随时”,“若经世一事,向使先生见用,其将如何?曰:亦是只是随时。”②先人立法之初本身就存在弊端,“虽是圣人法,岂有无弊者”、“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③。同时由于后人“未必皆其竭心思法圣智”,“行之既久而不能无弊”,甚至认为“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④。故而对于不适时宜、有弊立法就必须“变而通之”,“圣人姑为一代之法,到不可用法处,圣人须别有通变之道”⑤、“使圣贤者作,必不尽如古礼,必裁酌从今之宜而为之也”,力求做到“因事制宜,以趋一时之变”⑥。
王夫之从律法应因“势”顺“理”出发,提出“趋时更新”,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王夫之说:“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⑦古代的制度法令只能适应于古代社会,而今天的治国方法也不一定能适应于后世。“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举凡一兴一废,一繁一简,因乎时而不可执也”⑧,王夫之认为律令的制定和变更必须因时因地而异。法律不因时而变,就会固守古制,墨守成法。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