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途径
| 内容出处: |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560 |
| 颗粒名称: | 二、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途径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4 |
| 页码: | 284-287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清代台湾传播朱子学的途径。其中,一批笃信孔孟程朱、道德文章为时人所称道的名宦醇儒入台主政,成为传播程朱理学及大陆文化的先驱。他们通过兴办书院学校、培养儒学人才,以及兴建朱子祠堂、崇奉理学先贤等方式,推动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同时,官方还引进理学典籍,灌输朱子思想,并制定奖励政策,引导原住民儿童攻读经书。这些措施有助于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促进中华文化的统一。 |
| 关键词: | 朱子学 儒家文化 朱熹 |
内容
(一)儒学官员主政,推动理学传播
清初治台官吏,多为笃信孔孟程朱、道德文章为时人所称道的名宦醇儒。他们抵台后,大都重教兴文,关心民瘼,成为传播程朱理学及大陆文化的先驱。其中不遗余力推动儒学教育的官员首推陈瑸,他先后任台湾知县和台厦道兼理学政。此公“清操绝俗,慈惠利民,暇即引诸生考课,以立品敦伦为先”;②同时还“捐俸修郡邑文庙及朱子祠”。首任知府蒋毓英,任内“进父老子弟,教以孝弟之义,振兴文教,捐俸创立义学,延师课督”。③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台湾府的靳治扬,“捐资修文庙”,“尤雅意作人,番童有未知礼义者,立社学延师教之”。雍正十一年(1733年)巡察台湾兼理学政的林天木“动辄以宋名儒为范”,“取士以品行为先”。④这一大批杰出的儒学名臣的入台主政,在宝岛播撒朱子学与大陆文明的种子,一向受到岛内外人士的赞赏。台湾大学陈昭英博士认为:“所谓台湾儒学,只能说是闽学在台的一个支脉,或指儒学在台湾的存在、发展。”“就闽台的渊源而言,许多执教于台湾的官学、书院的教师,甚至学有专精的行政首长本身即来自福建,自然而然将闽学传入台湾。”⑤
事实确实如此,除行政长官外,台湾各级文教官员大多从福建选调。据统计,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60年中,台湾历任府学教授17名,训导4名;凤山、诸罗、台湾三县儒学教谕50名,训导17名,全部是福建儒士。他们中不少是闽学群儒后裔,对传播与弘扬朱子学分外勤勉。如长乐林谦光、陈志友、晋江黄赐英等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分别调任台湾府儒学教授、诸罗县儒学教谕和凤山县儒学教谕。建阳袁弘仁,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首任台湾府学训导。他们均“好学不倦,文辞苍蔚,风士多宗之”。①他们可谓在台湾传授弘扬朱子学的中坚。
(二)兴办书院学校,培养儒学人才
从郑经时代起,台湾就已开始兴学重教。至清代更蔚然成风。台湾县与凤山、诸罗、彰化诸县都先后于康熙和雍正年间建起了儒学。与此同时,为满足各种不同层次人士的要求,福建盛行的书院,也迅速在台湾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台湾知府卫台揆首建崇文书院;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分巡道梁文煊建海东书院;雍正年间,中社书院、正音书院、南社书院先后建成;乾隆时,又建起了白沙、凤阁、龙门、南湖、文石等书院;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台湾各地的书院已达45所。②此外,官办或私立的社学、义学、私塾也大量涌现。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仅诸罗一县就建了8所社学。乾隆年间,澎湖通判胡建伟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在他的倡导下“澎岛十三澳内,每社皆有蒙塾,书声相闻……虽贫民亦送其子弟入塾”。③
由于明清两代的科举取士都以《四书》《五经》为本,故各级各类学校、书院自然都以儒家经典、尤其是朱子校注编定的《四书》《五经》和朱子的其他著作为教科书。这样,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就制度化了。
(三)兴建朱子祠堂,崇奉理学先贤
随着大陆教育制度、教育模式在台湾的逐步推广,朱熹及其师友弟子也随之受到台湾各地官府和士民的景仰。不少儒学及书院都先后建起了朱子祠。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台厦道周昌、首任知府蒋毓英将郑氏府邸旧址改建为台湾府儒学,改额曰“先师庙”,其建筑群中包括大成殿、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等;内设孔子神位及十哲、先贤先儒姓氏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陈瑸捐俸又于学宫左侧建朱子祠,这是在台湾建立的第一座朱子祠。未建专祠者,也大多在孔庙设立牌位,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蔡元定、黄榦、陈淳、蔡清、真德秀等一大批闽学先贤,都成为台湾士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四)引进理学典籍,灌输朱子思想
为了使程朱理学思想深入人心,清初台湾官方规定学校的主要课程为《性理大全》《四书》《诗集传》《古文辞》《资治通鉴纲目》《十三经》及《二十二史》等。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台厦道陈瑸在《新建朱文公祠碑记》中说:“矧自孔孟而后,正学失传,斯道不绝如线,得文公剖晰发明于经史及百氏之书,始旷然如日中天,凡学者口之所诵,心之所维,当无有不寤寐依之,羹墙见之者,何有于世相后、地相去之拘拘乎?”①他期望生徒对朱子的著述“信之深、思之至。切己精察,实力供行,勿稍游移坠落流俗边去”。②为了引导“土番”研习朱子典籍,官府还制定了赠予读书番童每人一册《四书》等奖励政策。这种政策,有助于调动各地原住民儿童攻读经书的积极性。雍正十二年(1734年),当地官员在对南北路各番社社学巡察中发现,不少“番童”均能“背诵《四书》及《毛诗》”,“亦知文理”,甚至“有背诵《易经》无讹者”。③
台湾各类学校设立之初,书籍短缺,难以满足学校、书院教学和士人学习之需。于是,一些赴台官员特意从大陆筹集典籍,运往台湾。如道光六年(1826年),福建巡抚孙文准赴台巡视时,特意从颇负盛名的福州鳌峰书院藏书中,拨出一批理学要籍,随船入台,赠给台湾仰山书院,其中有《朱子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学的》《读朱随笔》《二程文集》《二程语录》《重编杨龟山集》《重编罗豫章集》《李延平集》《张南轩文集》《黄勉斋集》《真西山文集》《伊洛渊源录》《道南源委》《濂洛关闽书》《文文山集》《谢叠山集》《重编熊勿轩集》等,总共45种166部。从而既解决了部分教学急需,又扩大了朱子学在台湾的影响,使朱子思想迅速在台湾生根开花,成为全岛共尊的社会思想。
清初治台官吏,多为笃信孔孟程朱、道德文章为时人所称道的名宦醇儒。他们抵台后,大都重教兴文,关心民瘼,成为传播程朱理学及大陆文化的先驱。其中不遗余力推动儒学教育的官员首推陈瑸,他先后任台湾知县和台厦道兼理学政。此公“清操绝俗,慈惠利民,暇即引诸生考课,以立品敦伦为先”;②同时还“捐俸修郡邑文庙及朱子祠”。首任知府蒋毓英,任内“进父老子弟,教以孝弟之义,振兴文教,捐俸创立义学,延师课督”。③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知台湾府的靳治扬,“捐资修文庙”,“尤雅意作人,番童有未知礼义者,立社学延师教之”。雍正十一年(1733年)巡察台湾兼理学政的林天木“动辄以宋名儒为范”,“取士以品行为先”。④这一大批杰出的儒学名臣的入台主政,在宝岛播撒朱子学与大陆文明的种子,一向受到岛内外人士的赞赏。台湾大学陈昭英博士认为:“所谓台湾儒学,只能说是闽学在台的一个支脉,或指儒学在台湾的存在、发展。”“就闽台的渊源而言,许多执教于台湾的官学、书院的教师,甚至学有专精的行政首长本身即来自福建,自然而然将闽学传入台湾。”⑤
事实确实如此,除行政长官外,台湾各级文教官员大多从福建选调。据统计,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的60年中,台湾历任府学教授17名,训导4名;凤山、诸罗、台湾三县儒学教谕50名,训导17名,全部是福建儒士。他们中不少是闽学群儒后裔,对传播与弘扬朱子学分外勤勉。如长乐林谦光、陈志友、晋江黄赐英等人,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分别调任台湾府儒学教授、诸罗县儒学教谕和凤山县儒学教谕。建阳袁弘仁,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首任台湾府学训导。他们均“好学不倦,文辞苍蔚,风士多宗之”。①他们可谓在台湾传授弘扬朱子学的中坚。
(二)兴办书院学校,培养儒学人才
从郑经时代起,台湾就已开始兴学重教。至清代更蔚然成风。台湾县与凤山、诸罗、彰化诸县都先后于康熙和雍正年间建起了儒学。与此同时,为满足各种不同层次人士的要求,福建盛行的书院,也迅速在台湾发展起来。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台湾知府卫台揆首建崇文书院;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分巡道梁文煊建海东书院;雍正年间,中社书院、正音书院、南社书院先后建成;乾隆时,又建起了白沙、凤阁、龙门、南湖、文石等书院;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台湾各地的书院已达45所。②此外,官办或私立的社学、义学、私塾也大量涌现。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仅诸罗一县就建了8所社学。乾隆年间,澎湖通判胡建伟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在他的倡导下“澎岛十三澳内,每社皆有蒙塾,书声相闻……虽贫民亦送其子弟入塾”。③
由于明清两代的科举取士都以《四书》《五经》为本,故各级各类学校、书院自然都以儒家经典、尤其是朱子校注编定的《四书》《五经》和朱子的其他著作为教科书。这样,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就制度化了。
(三)兴建朱子祠堂,崇奉理学先贤
随着大陆教育制度、教育模式在台湾的逐步推广,朱熹及其师友弟子也随之受到台湾各地官府和士民的景仰。不少儒学及书院都先后建起了朱子祠。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台厦道周昌、首任知府蒋毓英将郑氏府邸旧址改建为台湾府儒学,改额曰“先师庙”,其建筑群中包括大成殿、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明伦堂等;内设孔子神位及十哲、先贤先儒姓氏牌。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陈瑸捐俸又于学宫左侧建朱子祠,这是在台湾建立的第一座朱子祠。未建专祠者,也大多在孔庙设立牌位,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蔡元定、黄榦、陈淳、蔡清、真德秀等一大批闽学先贤,都成为台湾士人顶礼膜拜的对象。
(四)引进理学典籍,灌输朱子思想
为了使程朱理学思想深入人心,清初台湾官方规定学校的主要课程为《性理大全》《四书》《诗集传》《古文辞》《资治通鉴纲目》《十三经》及《二十二史》等。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台厦道陈瑸在《新建朱文公祠碑记》中说:“矧自孔孟而后,正学失传,斯道不绝如线,得文公剖晰发明于经史及百氏之书,始旷然如日中天,凡学者口之所诵,心之所维,当无有不寤寐依之,羹墙见之者,何有于世相后、地相去之拘拘乎?”①他期望生徒对朱子的著述“信之深、思之至。切己精察,实力供行,勿稍游移坠落流俗边去”。②为了引导“土番”研习朱子典籍,官府还制定了赠予读书番童每人一册《四书》等奖励政策。这种政策,有助于调动各地原住民儿童攻读经书的积极性。雍正十二年(1734年),当地官员在对南北路各番社社学巡察中发现,不少“番童”均能“背诵《四书》及《毛诗》”,“亦知文理”,甚至“有背诵《易经》无讹者”。③
台湾各类学校设立之初,书籍短缺,难以满足学校、书院教学和士人学习之需。于是,一些赴台官员特意从大陆筹集典籍,运往台湾。如道光六年(1826年),福建巡抚孙文准赴台巡视时,特意从颇负盛名的福州鳌峰书院藏书中,拨出一批理学要籍,随船入台,赠给台湾仰山书院,其中有《朱子文集》《朱子语类》《朱子学的》《读朱随笔》《二程文集》《二程语录》《重编杨龟山集》《重编罗豫章集》《李延平集》《张南轩文集》《黄勉斋集》《真西山文集》《伊洛渊源录》《道南源委》《濂洛关闽书》《文文山集》《谢叠山集》《重编熊勿轩集》等,总共45种166部。从而既解决了部分教学急需,又扩大了朱子学在台湾的影响,使朱子思想迅速在台湾生根开花,成为全岛共尊的社会思想。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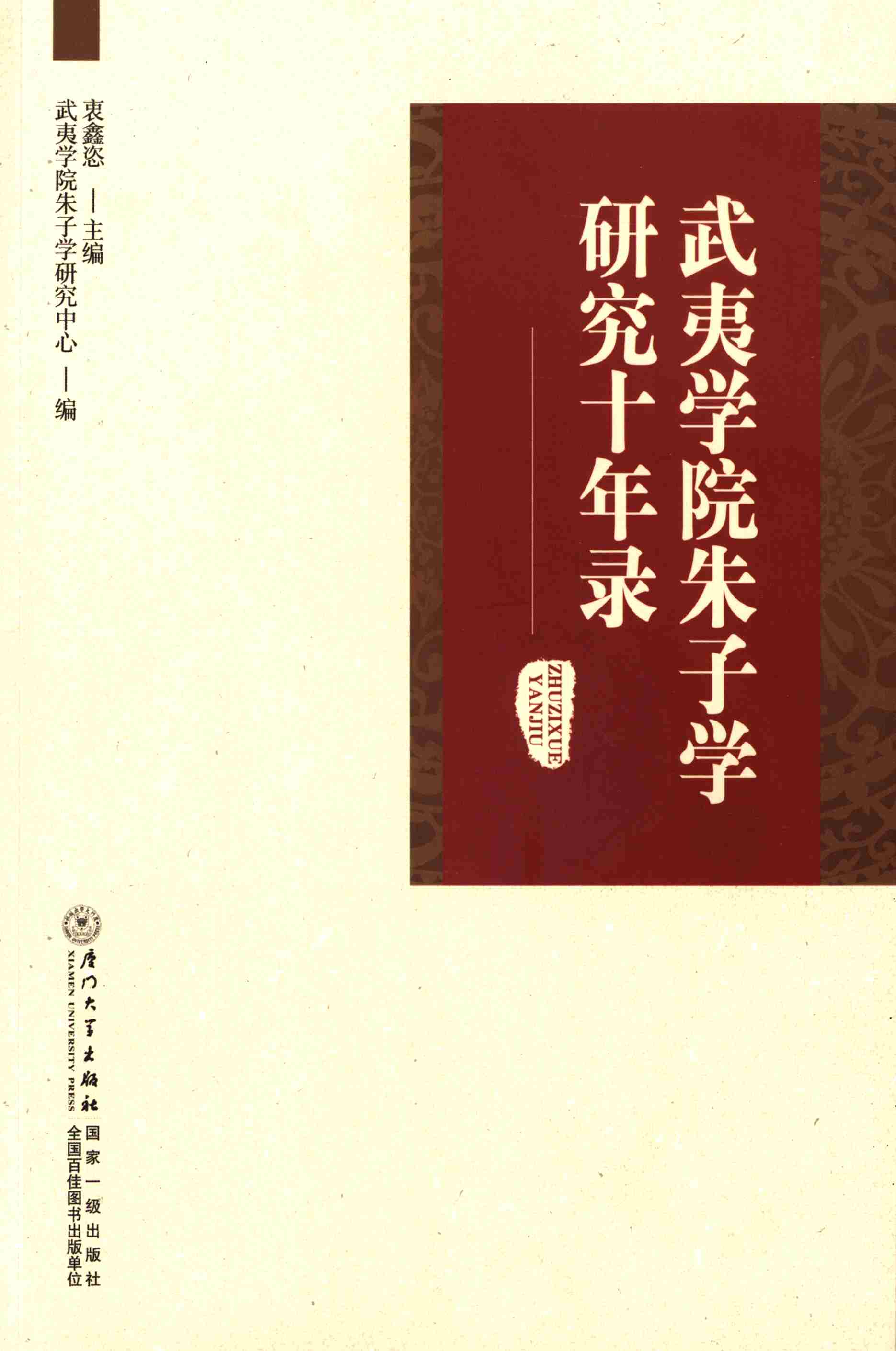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十年录》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精选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2008-2018年公开发表的朱子学研究论文37篇,按文章内容分成了朱子与理学、朱子与社会、朱子与教育、朱子与当代、朱子与东亚、朱子与闽台等几组。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