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农业与荒政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405 |
| 颗粒名称: | (六)农业与荒政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8 |
| 页码: | 583-590 |
| 摘要: | 本文主要介绍朱熹在农业生产和救荒方面的主要思想和做法。朱熹非常关注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提倡劝农,通过撰写《劝农文》和实施经界法等方式鼓励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他重视农时、施肥、插秧、除草等农事活动的时间和方法,并重视土壤肥力的培养和改良。朱熹还强调多种经营,广泛种植经济作物,改善农民生活和缓解粮食紧张问题。他还主张修建水利工程,建立社仓救济贫民,简化救荒流程,鼓励富户赈粜并保证其利益,对不愿赈粜者加以惩罚。朱熹的农业思想和救灾措施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 关键词: | 清初 朱子学 农业 |
内容
在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是关乎国家治乱、政权稳固、社会发展与民众生活的头等大事,亦是实行道德教化的物质基础。而“劝农”则构成了州县地方官员日常工作中的一项基本职责。朱熹长期生活在农村,十分关注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状况,又曾历任多处地方官,自然对农业生产的内容与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他说:“契勘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是以国家务农重谷,使凡州县守倅皆以劝农为职,每岁二月,载酒出郊,延见父老,喻以课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盖欲吾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以共趋于富庶仁寿之域,德至渥也。”②
为了鼓励农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朱熹亲自撰写了不少《劝农文》,从中不难看出朱熹对于农业生产的基本内容与技术方法的了解和重视。譬如,朱熹对农时十分重视,每逢春播时节都要事先提醒农民及时播种,否则便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他曾写道:“今来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农时节,不可迟缓。仰诸父老教训子弟,递相劝率,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无致因循,自取饥饿。”③此外,朱熹对于施肥、插秧、除草、收获等农事活动的时间亦有明确的交代。如谓:“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禾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仔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①
由于朱熹任职之处土地多较贫瘠,故其特别重视土壤肥力的培养和改良。一方面,朱熹主张通过深耕和反复犁耙的办法,增强土壤的保水性,使生土变为熟土。譬如他说:“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杷,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②另一方面,朱熹也很强调肥料的使用,要求农民“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其造粪壤,亦须秋冬无事之时,预先划取土面草根,㬠曝烧灰,旋用大粪拌和,入种子在内,然后撒种”③。
朱熹虽然强调种植水稻是南方农业生产的基础,但他同时也提倡农民广泛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以改善生活,缓解粮食紧张。故曰:“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④朱熹还认识到,不同的农作物往往适合于不同地区的土壤,所以可以利用不同的土壤条件,因地制宜地种植不同作物,以尽量开发地力,增加收成。“山原陆地,可种粟麦麻豆去处,亦须趁时竭力耕种,务尽地力。庶几青黄未交之际,有以接续饮食,不至饥饿。”⑤对于一些当地不曾种植,却又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作物,朱熹亦试图通过改善种植条件与种植方法的方式加以引进。譬如他说:“蚕桑之务,亦是本业。而本州从来不宜桑拓,盖缘民间种不得法。今仰人户常于冬月多往外路买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深开窠窟,多用粪壤,试行栽种。待其稍长,即与削去细碎拳曲枝条,数年之后,必见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种吉贝麻苧,亦可供备衣着,免被寒冻。”①
针对当时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土地抛荒现象,朱熹认为主要是由于官府侵扰与野兽践踏造成。因此,为了鼓励垦荒,朱熹一方面希望朝廷实行经界法,以革除产去税存、租税不均的弊端;另一方面劝谕民众捕杀野兽,如规定凡猎杀大象者,即赏钱三十贯,并约束官府不得追取野兽的牙齿蹄角。同时,凡是愿意开垦荒田之人,只要到官府陈请,待官府勘察核实后,便可将荒田作为自己的永久产业,并免除三年租税。
此外,朱熹还很重视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陂塘水利,农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叶力兴修,取令多蓄水泉,准备将来灌溉。如事干众,即时闻官,纠率人功,借贷钱本,日下修筑,不管误事。”②又说:“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如有怠惰,不趁时工作之人,仰众列状申县,乞行惩戒。如有工力浩瀚去处,私下难以纠集,即仰经县自陈,官为修筑。如县司不为措置,即仰经军投陈,切待别作行遣。”③基于灌溉对农作物生长的决定性意义,而单纯依靠自然的水源条件往往又难以满足需要,故朱熹亦将水利视为农事之本。为了确保灌溉用水的需要,朱熹要求有用水需求的农户相互合作,协力修建水利工程。若工程较大,花费较多,民间无法负担,则须及时报告官府,由官府召集人手,借贷资金,进行修筑。对于那些本应参与水利修建,却消极怠工、延误工期的人,亦须列状申报,由官府加以惩戒。
尽管当时人们已经开始采用兴修水利等一些人工的方法来改良自然条件,辅助农业生产,但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严重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若是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难免造成灾荒,从而极大地威胁社会稳定和民众的生存。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荒政的研究、讨论和实施。就宋朝来看,由于灾荒频发,为了预防由灾荒引发的粮食短缺,政府先后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备的粮食仓储制度。
宋代的仓种名目繁多,其中影响较大、分布较广的主要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广惠仓等由朝廷直接下诏建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管理的全国性仓种。这些仓种在设立之初,都曾在备灾救荒、救济孤贫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为因素的破坏和客观情况的改变,原先的制度多已不同程度地发生异化,无法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于名存实亡。对此,朱熹即云:“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①朱熹在知南康军与漳州期间,发现南康的常平仓本应储粮五六万石,漳州的常平仓亦有六七万石,其实“尽是浮埃空壳”;在浙东为官时,又发现当地的常平仓与省仓相连,结果每当官吏检点省仓时,便挂省仓牌子,检点常平仓时,又挂常平仓牌子,其实“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②为了补救这一问题,南宋之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仓种,其中自然以朱熹创立的社仓最为知名,影响亦最大。
乾道四年(1168)春夏之交,福建建宁府崇安县遭遇饥荒,官府拨给常平米六百石,委托朱熹与当地耆老刘如愚共同负责崇安县开耀乡的赈灾事宜。饥荒顺利度过之后,民众于当年冬天将所贷之米归还。次年夏天,朱熹考虑到“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③,于是建议官府每年都将粮食借贷给民众,“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①,并且规定每石米收取20%的利息,如遇歉收,则减免一半利息,遇到大的饥荒,则免除全部利息。若有不愿参加借贷的,亦不勉强。后来,因考虑到粮食分别贮藏于民众家中,不便监管与出纳,故建立社仓以储之。事实证明,朱熹设计的这一社仓制度十分合理,并且成效卓著。在开耀乡设立社仓的十四年后,“其支息米造成仓敖三间收贮,已将元米陆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已申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系臣(指朱熹)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掌管,遇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以此之故,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②。
淳熙八年(1181),朱熹奏事延和殿时,即以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所行社仓之法上奏,并请求孝宗将其推行各地。朱熹建议,诸路、州、军“有愿依此置立社仓者,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与本乡出等人户,主执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与本县官同共出纳。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数,即送原米还官,却将息米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息米及数,亦当拨还。如有乡土风俗不同者,更许随宜立约,申官遵守,实为久远之利。其不愿置立去处,官司不得抑勒,则亦不至骚扰”③。为了方便社仓在各地的建立与推广,朱熹还详细撰写了一份建宁府社仓见行事目④,以供皇帝和其他官员参考。而孝宗亦很快同意了朱熹的请求,下诏颁行社仓之法于四方,社仓遂在各地普遍地建立起来。
由于社仓属于民办,形式比较灵活,因而在推广过程中,不同地区往往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进行一些调整,逐渐扩大了社仓的来源与用途。不少社仓除了用于赈贷外,还广泛用于赈粜,甚至衍生出慈幼、居养贫病、周济行旅等功能,而其底本亦不仅仅局限于官府的借贷。如刘宰说:“今社仓落落布天下,皆本于文公。……其本或出于官,或出于家,或出于众,其事已不同;或及于一乡,或及于一邑,或粜而不贷,或贷而不粜,吾邑贷于乡,粜于市,其事亦各异。”①而邵武军光泽县则考虑到“市里之间民无盖藏,每及春夏之交,则常籴贵而食艰也。又病夫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则无所于归,而或死于道路也”,故建立社仓,“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则捐价而粜,以平市价;冬则增价而籴,以备来岁。又买民田若干亩,籍僧田、民田当没入者若干亩,岁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仓,以助民之举子者如帅司法。既又附仓列屋四楹,以待道涂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栖托食饮,而无暴露迫逐之苦”。②这一做法亦得到朱熹的肯定,被誉为“条画精明,综理纤密”③。
关于救荒,朱熹还强调“救荒之务,检放为先。行之及早,则民知有所恃赖,未便逃移;放之稍宽,则民间留得禾米,未便阙乏”④。因此,他批评当时“州郡多是吝惜财计,不以爱民为念,故所差官承望风指,已是不敢从实检定分数。及至申到帐状,州郡又加裁减,不肯依数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检踏后时,致有无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迟缓之罪,而检官反谓人户违法,不为检定。其有检定申到者,州郡亦不为蠲放,就中下户所放不多,尤被其害”⑤。为了避免检放工作骚扰贫民,朱熹主张简化手续,对最贫困的那部分农户实行免检全放的优待政策。当时,一般将农户按田赋多少分为五等,朱熹建议朝廷“自今水旱约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并免检踏具帐,先与全户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户依此施行。其州县差官后时,致得旱损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损田即与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远,比并邻至分数检放,庶几贫民永远利便”①。
面对灾荒,朱熹除了请求朝廷救济粮食、蠲免赋税之外,还积极利用市场手段,招邀外地米商,并鼓励当地富户捐献。譬如,朱熹在浙东救荒时,发现广东米价较低,且海路运抵浙东较近,旋即派人赴福建、广东两路沿海发榜招邀米商,承诺严格约束本地税务,“不得妄收力胜杂物税钱,到日只依市价出粜,更不裁减。如有不售者,官为依价收籴”②,从而保证了外地米商的合理利益,免除其后顾之忧。此外,朱熹还希望朝廷将今年粜过米钱及兑那诸色窠名支拨充作收籴本钱,以便及时支付,又建议朝廷对愿意前来赈粜的米商量立赏格,“仍先降空名付身数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贩到米斛之人,即与书填给付。盖缘客人粜货了毕,便欲归回元处,不能等候”③,如此处理方可不失信于人,方便日后再次招邀。
灾荒发生之时,朱熹既告诫当地富户必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免致流移,防止将来田土抛荒,公私受弊,又希望其除了接济佃户之外,能够将剩余粮食原价、足量地售予有需要的贫民,“则不惟贫民下户获免流移饥饿之患,而上户之所保全,亦自不为不多”④。对于赈粜粮食多的富户,朱熹承诺官府将施行保明,申奏推赏。若富户依规借贷出去的粮食日后无法全额收回,官府将负责为其追讨。但是,如有故意违抗命令、不肯赈粜之人,亦允许民众到县衙陈诉,由官府核实追究。为了维护富户献米赈粜的意愿与积极性,朱熹还敦促朝廷尽快兑现对合乎要求的应募献米者的奖赏,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推赏的标准。譬如,富户经过去年的捐献,想必今年的储粮已经不多,若坚持依照旧的标准进行推赏,恐怕几乎没有符合推赏标准的人可以捐献。因此,朱熹建议将今年的推赏标准临时降低一半,“庶几应募者众,得济饥民”,并且严格推赏的程序与责任,“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状式,及令逐处官司承受应募理赏词状文帖,并要当日行遣。如将来依式奏到省部,却称文字不圆,及诸处故违程限者,官员重加降责,人吏并行决配,庶几富者乐输,贫者得食,实为两便”。①
为了鼓励农民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朱熹亲自撰写了不少《劝农文》,从中不难看出朱熹对于农业生产的基本内容与技术方法的了解和重视。譬如,朱熹对农时十分重视,每逢春播时节都要事先提醒农民及时播种,否则便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和收成。他曾写道:“今来春气已中,土膏脉起,正是耕农时节,不可迟缓。仰诸父老教训子弟,递相劝率,浸种下秧,深耕浅种。趋时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无致因循,自取饥饿。”③此外,朱熹对于施肥、插秧、除草、收获等农事活动的时间亦有明确的交代。如谓:“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秧苗既长,便须及时趁早栽插,莫令迟缓,过却时节”,“禾苗既长,秆草亦生。须是放干田水,仔细辨认,逐一拔出,踏在泥里,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属,亦须节次芟削,取令净尽,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①
由于朱熹任职之处土地多较贫瘠,故其特别重视土壤肥力的培养和改良。一方面,朱熹主张通过深耕和反复犁耙的办法,增强土壤的保水性,使生土变为熟土。譬如他说:“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至正月以后,更多著遍数,节次犁杷,然后布种。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种禾易长,盛水难干。”②另一方面,朱熹也很强调肥料的使用,要求农民“耕田之后,春间须是拣选肥好田段,多用粪壤拌和种子,种出秧苗。其造粪壤,亦须秋冬无事之时,预先划取土面草根,㬠曝烧灰,旋用大粪拌和,入种子在内,然后撒种”③。
朱熹虽然强调种植水稻是南方农业生产的基础,但他同时也提倡农民广泛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以改善生活,缓解粮食紧张。故曰:“种田固是本业,然粟豆麻麦、菜蔬茄芋之属,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种植,青黄未交得以接济,不为无补。今仰人户更以余力广行栽种。”④朱熹还认识到,不同的农作物往往适合于不同地区的土壤,所以可以利用不同的土壤条件,因地制宜地种植不同作物,以尽量开发地力,增加收成。“山原陆地,可种粟麦麻豆去处,亦须趁时竭力耕种,务尽地力。庶几青黄未交之际,有以接续饮食,不至饥饿。”⑤对于一些当地不曾种植,却又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作物,朱熹亦试图通过改善种植条件与种植方法的方式加以引进。譬如他说:“蚕桑之务,亦是本业。而本州从来不宜桑拓,盖缘民间种不得法。今仰人户常于冬月多往外路买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间,深开窠窟,多用粪壤,试行栽种。待其稍长,即与削去细碎拳曲枝条,数年之后,必见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种吉贝麻苧,亦可供备衣着,免被寒冻。”①
针对当时出现的较为严重的土地抛荒现象,朱熹认为主要是由于官府侵扰与野兽践踏造成。因此,为了鼓励垦荒,朱熹一方面希望朝廷实行经界法,以革除产去税存、租税不均的弊端;另一方面劝谕民众捕杀野兽,如规定凡猎杀大象者,即赏钱三十贯,并约束官府不得追取野兽的牙齿蹄角。同时,凡是愿意开垦荒田之人,只要到官府陈请,待官府勘察核实后,便可将荒田作为自己的永久产业,并免除三年租税。
此外,朱熹还很重视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他说:“陂塘水利,农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叶力兴修,取令多蓄水泉,准备将来灌溉。如事干众,即时闻官,纠率人功,借贷钱本,日下修筑,不管误事。”②又说:“陂塘之利,农事之本,尤当协力兴修。如有怠惰,不趁时工作之人,仰众列状申县,乞行惩戒。如有工力浩瀚去处,私下难以纠集,即仰经县自陈,官为修筑。如县司不为措置,即仰经军投陈,切待别作行遣。”③基于灌溉对农作物生长的决定性意义,而单纯依靠自然的水源条件往往又难以满足需要,故朱熹亦将水利视为农事之本。为了确保灌溉用水的需要,朱熹要求有用水需求的农户相互合作,协力修建水利工程。若工程较大,花费较多,民间无法负担,则须及时报告官府,由官府召集人手,借贷资金,进行修筑。对于那些本应参与水利修建,却消极怠工、延误工期的人,亦须列状申报,由官府加以惩戒。
尽管当时人们已经开始采用兴修水利等一些人工的方法来改良自然条件,辅助农业生产,但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农业生产基本上还是处于靠天吃饭的状态,严重依赖于自然气候条件。若是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难免造成灾荒,从而极大地威胁社会稳定和民众的生存。因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对荒政的研究、讨论和实施。就宋朝来看,由于灾荒频发,为了预防由灾荒引发的粮食短缺,政府先后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备的粮食仓储制度。
宋代的仓种名目繁多,其中影响较大、分布较广的主要有常平仓、义仓、惠民仓、广惠仓等由朝廷直接下诏建立,隶属于中央政府管理的全国性仓种。这些仓种在设立之初,都曾在备灾救荒、救济孤贫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人为因素的破坏和客观情况的改变,原先的制度多已不同程度地发生异化,无法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于名存实亡。对此,朱熹即云:“常平义仓,尚有古法之遗意,然皆藏于州县,所恩不过市井惰游辈,至于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濒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往往全其封鐍,递相付授,至或累数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获已,然后发之,则已化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①朱熹在知南康军与漳州期间,发现南康的常平仓本应储粮五六万石,漳州的常平仓亦有六七万石,其实“尽是浮埃空壳”;在浙东为官时,又发现当地的常平仓与省仓相连,结果每当官吏检点省仓时,便挂省仓牌子,检点常平仓时,又挂常平仓牌子,其实“只是一个仓,互相遮瞒”。②为了补救这一问题,南宋之后,各地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仓种,其中自然以朱熹创立的社仓最为知名,影响亦最大。
乾道四年(1168)春夏之交,福建建宁府崇安县遭遇饥荒,官府拨给常平米六百石,委托朱熹与当地耆老刘如愚共同负责崇安县开耀乡的赈灾事宜。饥荒顺利度过之后,民众于当年冬天将所贷之米归还。次年夏天,朱熹考虑到“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③,于是建议官府每年都将粮食借贷给民众,“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①,并且规定每石米收取20%的利息,如遇歉收,则减免一半利息,遇到大的饥荒,则免除全部利息。若有不愿参加借贷的,亦不勉强。后来,因考虑到粮食分别贮藏于民众家中,不便监管与出纳,故建立社仓以储之。事实证明,朱熹设计的这一社仓制度十分合理,并且成效卓著。在开耀乡设立社仓的十四年后,“其支息米造成仓敖三间收贮,已将元米陆百石纳还本府。其见管三千一百石,并是累年人户纳到息米,已申本府照会,将来依前敛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系臣(指朱熹)与本乡土居官及士人数人同共掌管,遇敛散时,即申府差县官一员监视出纳。以此之故,一乡四五十里之间,虽遇凶年,人不阙食”②。
淳熙八年(1181),朱熹奏事延和殿时,即以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所行社仓之法上奏,并请求孝宗将其推行各地。朱熹建议,诸路、州、军“有愿依此置立社仓者,州县量支常平米斛,责与本乡出等人户,主执敛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乡土居或寄居官员士人有行义者,与本县官同共出纳。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数,即送原米还官,却将息米敛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愿出米作本者亦从其便,息米及数,亦当拨还。如有乡土风俗不同者,更许随宜立约,申官遵守,实为久远之利。其不愿置立去处,官司不得抑勒,则亦不至骚扰”③。为了方便社仓在各地的建立与推广,朱熹还详细撰写了一份建宁府社仓见行事目④,以供皇帝和其他官员参考。而孝宗亦很快同意了朱熹的请求,下诏颁行社仓之法于四方,社仓遂在各地普遍地建立起来。
由于社仓属于民办,形式比较灵活,因而在推广过程中,不同地区往往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进行一些调整,逐渐扩大了社仓的来源与用途。不少社仓除了用于赈贷外,还广泛用于赈粜,甚至衍生出慈幼、居养贫病、周济行旅等功能,而其底本亦不仅仅局限于官府的借贷。如刘宰说:“今社仓落落布天下,皆本于文公。……其本或出于官,或出于家,或出于众,其事已不同;或及于一乡,或及于一邑,或粜而不贷,或贷而不粜,吾邑贷于乡,粜于市,其事亦各异。”①而邵武军光泽县则考虑到“市里之间民无盖藏,每及春夏之交,则常籴贵而食艰也。又病夫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而至或弃杀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则无所于归,而或死于道路也”,故建立社仓,“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则捐价而粜,以平市价;冬则增价而籴,以备来岁。又买民田若干亩,籍僧田、民田当没入者若干亩,岁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仓,以助民之举子者如帅司法。既又附仓列屋四楹,以待道涂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栖托食饮,而无暴露迫逐之苦”。②这一做法亦得到朱熹的肯定,被誉为“条画精明,综理纤密”③。
关于救荒,朱熹还强调“救荒之务,检放为先。行之及早,则民知有所恃赖,未便逃移;放之稍宽,则民间留得禾米,未便阙乏”④。因此,他批评当时“州郡多是吝惜财计,不以爱民为念,故所差官承望风指,已是不敢从实检定分数。及至申到帐状,州郡又加裁减,不肯依数分明除放。又早田收割日久,检踏后时,致有无根查者,乃是州郡差官迟缓之罪,而检官反谓人户违法,不为检定。其有检定申到者,州郡亦不为蠲放,就中下户所放不多,尤被其害”⑤。为了避免检放工作骚扰贫民,朱熹主张简化手续,对最贫困的那部分农户实行免检全放的优待政策。当时,一般将农户按田赋多少分为五等,朱熹建议朝廷“自今水旱约及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并免检踏具帐,先与全户蠲放。如及五分以上,即并第四等户依此施行。其州县差官后时,致得旱损田苗不存根查,亦乞立法坐罪。其所损田即与相度地形高低、水源近远,比并邻至分数检放,庶几贫民永远利便”①。
面对灾荒,朱熹除了请求朝廷救济粮食、蠲免赋税之外,还积极利用市场手段,招邀外地米商,并鼓励当地富户捐献。譬如,朱熹在浙东救荒时,发现广东米价较低,且海路运抵浙东较近,旋即派人赴福建、广东两路沿海发榜招邀米商,承诺严格约束本地税务,“不得妄收力胜杂物税钱,到日只依市价出粜,更不裁减。如有不售者,官为依价收籴”②,从而保证了外地米商的合理利益,免除其后顾之忧。此外,朱熹还希望朝廷将今年粜过米钱及兑那诸色窠名支拨充作收籴本钱,以便及时支付,又建议朝廷对愿意前来赈粜的米商量立赏格,“仍先降空名付身数十道付本司,俟有上件贩到米斛之人,即与书填给付。盖缘客人粜货了毕,便欲归回元处,不能等候”③,如此处理方可不失信于人,方便日后再次招邀。
灾荒发生之时,朱熹既告诫当地富户必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务令足食,免致流移,防止将来田土抛荒,公私受弊,又希望其除了接济佃户之外,能够将剩余粮食原价、足量地售予有需要的贫民,“则不惟贫民下户获免流移饥饿之患,而上户之所保全,亦自不为不多”④。对于赈粜粮食多的富户,朱熹承诺官府将施行保明,申奏推赏。若富户依规借贷出去的粮食日后无法全额收回,官府将负责为其追讨。但是,如有故意违抗命令、不肯赈粜之人,亦允许民众到县衙陈诉,由官府核实追究。为了维护富户献米赈粜的意愿与积极性,朱熹还敦促朝廷尽快兑现对合乎要求的应募献米者的奖赏,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推赏的标准。譬如,富户经过去年的捐献,想必今年的储粮已经不多,若坚持依照旧的标准进行推赏,恐怕几乎没有符合推赏标准的人可以捐献。因此,朱熹建议将今年的推赏标准临时降低一半,“庶几应募者众,得济饥民”,并且严格推赏的程序与责任,“仍勒所司立定保明状式,及令逐处官司承受应募理赏词状文帖,并要当日行遣。如将来依式奏到省部,却称文字不圆,及诸处故违程限者,官员重加降责,人吏并行决配,庶几富者乐输,贫者得食,实为两便”。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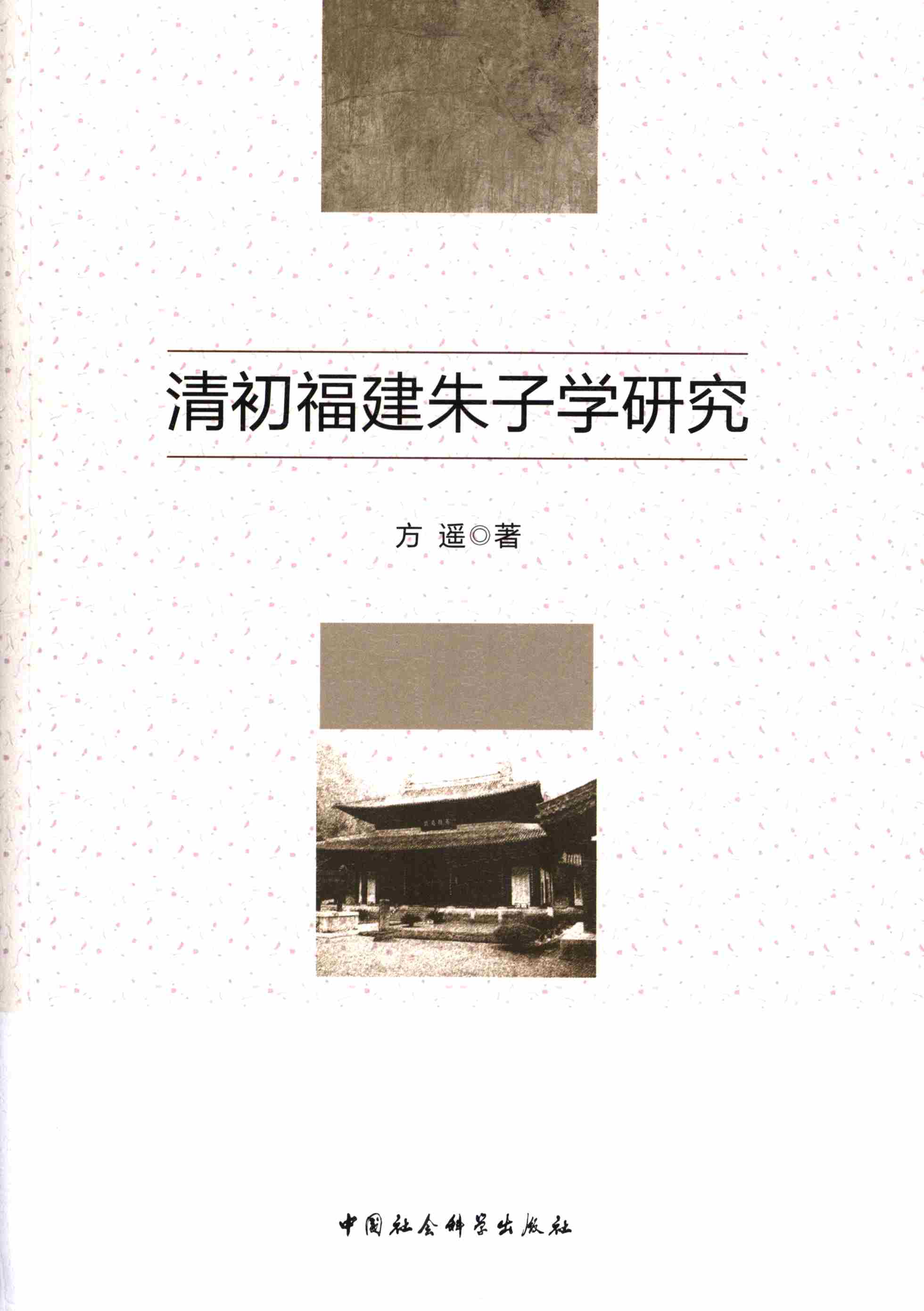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