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李光地的《春秋》学研究
| 内容出处: |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388 |
| 颗粒名称: | 五 李光地的《春秋》学研究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30 |
| 页码: | 452-481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熹与李光地对待《春秋》的态度和评价有所不同。朱熹主张将《春秋》视为史书,重视其中的史实和大义,强调其作为经学典籍的地位。而李光地则认为《春秋》与鲁国旧史紧密相关,尽管他也重视其中的史实,但更多地将其视为行事之实的典范和样板。尽管在对待《春秋》的重视程度上有所不同,但两位学者都认为《春秋》是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义理和道德准则。 |
| 关键词: | 李光地 史书 《春秋》 |
内容
《春秋》一书,朱熹主要以史书视之,主张“只如看史样看”④。虽然朱熹亦曾说过“《春秋》之书,亦经世之大法也”⑤,“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⑥之类的话,但他其实对《春秋》并不十分重视,反而屡言“《春秋》难看,此生不敢问”⑦,“《春秋》难看,平生所以不敢说着”⑧,“《春秋》无理会处,不须枉费心力”①,“学《春秋》者多凿说”②,“某所以都不敢信诸家解,除非是得孔子还魂亲说出,不知如何”③,可见《春秋》学在朱熹的经学体系中并不占有核心的位置。而李光地在对待《春秋》的态度上却与朱熹大为不同,不仅极力称赞,反复讨论,而且提出“《春秋》义法大抵一出于《周易》”④,认为其中包含了性命之义理与万世之准则,从而将其与《周易》并列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学典籍。故曰:
《春秋》字字皆经称量,又义精仁熟,恰当事理,字面上下增减,变不变,称名辨物,俱是化工。⑤
别的经书,都是据理而谈,待人以事实之。此经(指《春秋》)却是现在日用间事,立朝理家,往来酬酢,大经大法,微文小节,经权常变,一举一动,一名一号,无不本之天理,合乎人情。直是人生要紧切务,斯须不可离者。⑥
《易》也者,达乎天德而周于民用;《春秋》也者,穷乎人事而临以天则。故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显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⑦
《易》《春秋》,在五经中最奇,其中条分缕析,又皆是自然之理,日用眼前之事,所以为妙。《易》虚而实,空空洞洞,无所指定,而天下事事物物,形象变态,无一不备。《春秋》实而虚,有名有事,各不相假,然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万世,皆于是取则。人情物理,皆禀律令。幽隐微暧,神明鉴诸,信造化之精髓,性命之模范也。①
虽然在对待《春秋》的重视程度上与朱熹有所不同,但在对《春秋》性质的判断上,李光地仍基本遵从朱熹之说,以《春秋》为史书。譬如他说:
史书惟《春秋》当法。年下书时,时下书月,月下书日。有以两日赴者,则书两日;有灾眚经几日者,则书某月;有无关轻重者,则不书日。②
凡会外大夫不书“公”,非讳也,存内外君臣之体,盖史法也。③
在李光地看来,《春秋》不仅符合一般史书的体例与特征,而且史法严谨,足以作为后世史书的典范与样板。即便将它与其他公认的优秀史书相比,亦无出其右者。如“《左传》隐公在,公子翚便称隐公;《史记》武帝在,便称武帝,极有名史尚如此。试看字字着落,一毫不差,一毫不假借,除《春秋》更无有二”④。因此,若不熟读《春秋》,不要说大经大法不可知,就连作史的几项基本要素“年月、称谓、序次、体裁,不知《春秋》,下笔便错”⑤。李光地还举韩愈《平淮西碑》所记唐宪宗平定淮西藩镇之事为例,认为韩愈之所以在文中记征伐之事极为简略,似今日发兵,明日即捷,是因为“淮、蔡内地,聚天下之力,四年而后克之,作文者尚铺张扬厉,岂不辱国?此等处直学《书经》不书年月体,一跳便跳过许多年、许多事去,其义则出自《春秋》”①。
既然以《春秋》为史书,那么就牵涉到《春秋》的成书问题。李光地认为其并非出于孔子的私人撰述,而是依据鲁国旧史略加删削而成,只有删减,并无增加,且删削之处极少。他说:
古史书事,月日而已,无以时者,惟鲁之旧史名《春秋》。意者,鲁史记事以时欤?②
古书于字句间不能无错,惟六经无错处。《春秋》于本文错者仍之,却无奈他何。孔子于子阳曰:“吾知之,此公子阳生也。”子贡云:“既知之,何不改之?”子曰:“如不知何?”……《春秋》未经笔削,想亦是如此。③又说:
夫子当初,止因鲁史之旧,当时赴告有便书,无便不书,夫子岂得增减?只是定义例而已。④
《春秋》因旧史,从讣告,有所损而不能益也。……夫子参稽国史,以及七十二邦之闻,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辞也。⑤
如楚文、沃武,入春秋已强大,而不见于经者,告命未通也。虽同盟同会之人,其事不告,则亦不书,旧史所无故也。⑥
李光地认为,《春秋》乃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鲁史亦名《春秋》,且鲁史与《春秋》皆以时记事,二者之间拥有许多共同点。同样,由于《春秋》是据鲁史而作,故其中有意保留了原文的一些错误。如《春秋》载:昭公“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据《公羊传》,孔子明知此“伯于阳”为“公子阳生”之误,但为了保存鲁史原貌并未加以修改。若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春秋》未经笔削”。李光地还采《左传》之说①,指出孔子据鲁史修《春秋》的一大原则是“赴告有便书,无便不书”,故所书皆实有其事,而未书则由于旧史未载。他进而利用这一原则对《春秋》经文中的不少疑难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例如,庄公十二年,南宫万弑宋闵公,后反叛被镇压,遂出奔陈国,最后陈国在宋国的要求下将南宫万送回宋国。但《春秋》仅书“宋万出奔陈”,而未书“陈人杀万”。对此,李光地解释道:“愚谓闵弑、万奔,书,宋来告也。杀万、葬闵,不书,宋不告,鲁不会也。”②又如,僖公二年,晋国假道虞国进攻虢国,灭了下阳;僖公五年,晋国再次假道虞国进攻虢国,不仅灭了虢国,还在回师途中顺道灭了虞国,抓住了虞公。但《春秋》仅书“灭下阳”“执虞公”,而未书“灭虢”“灭虞”。对此,李光地解释道:“‘灭夏阳’,‘执虞公’,晋人必将有辞以告于诸侯,故得而书之也。灭虢、灭虞,晋人讳其事而不告,故不得而书之也。”③又如,春秋时楚国多次救援郑国,但《春秋》往往未书“救郑”。对此,李光地解释道:“或救而不及则不书,或诸侯恶而削其籍则亦不书也。当是时,楚、郑方与中国为敌,其兴师伐救之事,不讣可知,但凭列国诸侯在会者之记载耳。”④总之,在李光地看来,《春秋》未书其事的原因多是由于未赴告鲁国。
孔子曾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⑤孟子亦云:“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①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在于以褒贬设素王之法,行天子之事。对于这种解释,李光地并不认同。他说:
凡说夫子竟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是非褒贬,怎生峻厉,都是膜外话。夫子不过是该称君,该称臣,还你个本分便是。所以说“必也正名”。当时礼法荡尽,冠履倒置,圣人不别作一书,即用现成鲁史,为之笔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不过不肯一毫苟且假借而已。②
“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谓欲借二百四十年君臣之行事以寓义理,则是非善恶深切而著明。后之说者,以为圣人行事之实也。夫褒贬亦空言也,而何行事之实之有?③
岂知夫子垂世立教,不寓之他书,而必修《春秋》。盖他书为空言,《春秋》则有二百四十余年之行事,因而著其是非褒贬,则比之空言者,尤为深切著明。不是说夫子实行王者之事也,书仍旧是空言,但书中有许多行事在耳。④
至“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说作圣人托南面之权,为见之行事,非也。谓他书托之空言,不若《春秋》皆是列国实事,有可考证,功罪易见,义理易明耳。⑤
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盖谓《春秋》本诸侯之史,其时列邦僭乱,名分混淆,而史体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则一裁以武、成班爵之旧,其行事则一律以周公制礼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犹曰“天子之史”云尔。说者不察,而以为夫子行南面之权,则近于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盖谓凡著书者,言理则虚,征事则实,故虽言理义以垂训,不如借二百余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见于此尔。说者以为《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只是据实直书而已,君便称君,臣便称臣,通过“正名”的方式使得君臣父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以此重建被严重毁坏的社会秩序和礼乐制度。因此,孔子所说的“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只是希望借助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列国实事以寓义理,使后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是非善恶,并有所鉴戒,既非托南面之权,更无所谓行事之实。而孟子所说的“《春秋》,天子之事也”,也只是说当时礼崩乐坏,名分混淆,史体乖舛,故孔子欲以周初的礼法制度为标准,来为天子修史,以拨乱反正,而非代王者立法。根据李光地的理解,“天子之事”即“天子之史”。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与周王室关系最为亲近,亦保存了最多的西周礼法制度。而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其内容必然与“天子之事”密切相关。故曰:“事是桓、文,王降而霸;史是《春秋》,周礼在鲁。俱隐隐与王迹事相关,乃义之所由起也。”②
关于研究《春秋》的方法,朱熹主张通过书中记载的史实来明其大义,使后人知晓是非善恶与治乱兴衰之道,并引为鉴戒,因而反对在一字一词上求圣人褒贬之意,或妄立所谓的“凡例”,以免陷于穿凿附会的解说。故曰: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①
当时史书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见。及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说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其字,有甚微词奥义,使人晓不得,足以褒贬荣辱人来?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在目,观之者知所惩劝,故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犯耳。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②
在这一问题上,李光地的观点与朱熹有同亦有异。由于李光地主张《春秋》是孔子据鲁史而作,且“有所损而不能益”,自然也不能同意传统的“一字褒贬”说。他说:
《诗》不必篇篇皆美刺,《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贬。《诗》贞淫并著,而其教归于正人心。《春秋》善恶并书,而其教主于存天理。③
《易》不蔽于卜筮,而蔽于占候;《春秋》不蔽于书法,而蔽于义例。非谓卜筮之非占,而书法之无义也。以为候之流于拘,而例之失于凿也。自汉以来病之。问其说,曰:“《易》者变动不居,其可以星日气候推乎?《春秋》者因物付物,其可以文法律例求乎?”④
论人止就其事迹,不必钩深索隐,钩棘得之,未必不差。如用刑,宁失出,毋失入也。孔子论人,以及《春秋》书法,皆是如此。《春秋》如今日档案则例一般,凡大事须查案定拟。韩文公云:“《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但得王法不泯便好,何用又推深一层?如今觉得《春秋》千变万化,都是平平常常情理。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只是直书其事,使天理自彰,是非善恶自现而已,并非言言皆寓褒贬。若是执着于每字每事中求其褒贬,则将蔽于义例,而失于穿凿附会。譬如,文公三年,楚国围攻江国,晋国派遣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文公四年,晋侯讨伐秦国,后楚国灭亡江国。但《春秋》却先书“楚人灭江”,后书“晋侯伐秦”。对此,后世学者多以褒贬之义加以解释。李光地并不赞同,提出:“书‘晋侯伐秦’于‘楚人灭江’之下,见其重于修怨,轻于救患,无攘却之善也。救江则遣处父,伐秦则身亲之,侯伯之职安在哉?于秦、晋往复之间,非褒贬所系也。”②又如,宣公八年,鲁大夫仲遂死于齐国的垂地。由于仲遂曾杀文公太子,故不少学者认为《春秋》称“仲遂”而不称“公子遂”亦是出于褒贬之义。对此,李光地说道:“仲遂之卒,不称公子,以为蒙前文,固也。然实于其殁也名而绝之,如翚于隐之例耳。其或卒,或不卒,不可以为褒贬。”③他又引《春秋》“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为据,认为“《春秋》书‘犹绎’,而《檀弓》有‘卿卒不绎’之言,则仲遂之功罪姑无论矣。所谓‘书王法而不诛其人身’者,此类也”④,可见《春秋》并无贬斥仲遂之意。又如,襄公二十九年,吴王派公子季札出使鲁国,《春秋》书:“吴子使札来聘。”一些学者认为,《春秋》称季札为“札”是对他让国之德的褒扬。对此,李光地亦不赞同,指出:“子札褒贬之说棼如。愚谓《春秋》于札无褒贬焉耳。褒贬者必于事,于来聘而褒贬其生平,远矣。札在国,必曰王子札也。其称于我,亦必其王子札也。”⑤
同时,李光地还认为,《春秋》的书法严谨主要体现在大经大法上,即对待大事极为严格,王法森然,一毫不肯假借,必明其是非邪正,但对于一般的人与事则较为宽大忠厚,都是平平常常情理,只要“有一丝合于善,便奖许之恐后,其仁爱至矣”①,并不钩深索隐、诛其人身,因而自然反对所谓的“诛心”之说:
《史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说者谓《春秋》由事迹上推见人之心曲,所谓“诛心”,其实非也。“见”字读现,与上“显”字同。《易》言造化幽微之故,以至于人事;《春秋》则由事迹之显著,而至于精微。句法少一“以”字,不与上对耳。见,即所谓“见之行事”也。②
司马迁言:“《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见”即“显”也。天道隐,人事显,盖言《易》本天道以该人事,《春秋》推人事以合天道,故其下即云:“《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说者又似以推见至隐为推究隐情之义,故谭经往往有锻炼文致者,皆由于此也。③
需要注意的是,李光地只是说“《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贬”,批评“例之失于凿”而已,并没有说《春秋》“书法之无义也”。相反,由于李光地认定《春秋》从大经大法到微文小节中都蕴含了天理之常、性命之理与万世之法,并寄托了孔子“推见至隐”的深刻用意,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否认其中存在孔子特殊的书法与义例。譬如他说:
朱子说,《春秋》据事直书为多,未必尽有褒贬。或不以为然。不知朱子不是说全无褒贬,谓未必如今人说一字不放空,都有褒贬耳。④
《春秋》最是难看,无一点文采,不过几个字眼,颠倒用得的确,便使万世之大经大法,灿然具备。微而显,显而微,一归义理之精,无非自然之则。①
一部《春秋》,不过几个字换来换去,数之可了。这几个字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参互错综,遂千变万化。曲曲折折,精义入神,不可思议,又至稳至当,极合人情。即以此尽天下之事,类万物之情,通性命之理。②
近看《春秋》,见得一片天理人情,只苦来日有限,未能卒业。其中义例纷然,变化错出,思之皆有妙义。③
《论语》有十数章,便是《春秋》义例。如《八佾》“雍彻”,“陈恒司败”,“崔子、子文”,“冉子退朝”,“正名”,“为卫君”之类,不独大义朗然,即词语轻重婉直之间,都是义例。如“臧文仲窃位”举其大,“微生高不直”举其小皆是。④
④同上书、第262页
由此可见,李光地反对的只是穿凿附会、过度夸大的“一字褒贬”说,而未否认《春秋》中存在各种书法、义例。相反,李光地还对这些书法、义例极为重视,赞叹有加,认为其皆出于孔子的有意安排,千变万化,精义入神,至当不易,可与《论语》等经典相互发明,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篇幅来发明、探讨《春秋》中的书法、义例。
(1)关于称谓之例,李光地说道:
如乱臣贼子,初则削其籍,称其名,后乃称其爵,或称其国,或称某国人,或称盗。盖初则疾恶之至,绝之非其臣子也。既而并存其爵,若曰此为其某官,为其世子,而至为此事也。史官如董狐、南史者甚少,焉能皆死其官?使弑君之贼,皆如赵盾、崔杼之不能逃其罪,史官既不能死其职,则弑君之贼必秉国钧,安肯以己行弑讣于诸侯?势必另举一人以实之。如魏高贵乡公之事,司马昭问陈泰曰:“今日之事,何以处我?”陈泰曰:“惟杀贾充,稍可以谢天下。”昭问其次,曰:“泰言有进于此者,不知其次。”论首恶则昭也,乃诛行刺之成济而归狱焉。朱子灼知确见,故书曰:“魏司马昭弑其主髦。”假使考之不确,既不能无所证据,而以大恶加人,若书其归狱之人,却令首谋者漏网,后世将竟不知其为某某也。夫子于此等,则书曰某国,罪其大臣也;曰某国人,则与谋者多也;曰盗,宦官宫妾之类不足齿数也。不书其名,一以见阙疑之意,一以使后之人不知所主名而推求之,则其人亦不能以归狱于他人而卸其罪。此等义例,信非圣人不能创。①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必削属籍,而不以爵氏通。……其后或姓氏之,或世子、公子之。不削属籍,则弑君者犹夫人,无以正其弑之罪也。不姓氏之,世子、公子之,则安知其非微者、盗者,而为邦之臣子乎?是无以著其弑之实也。凡具其实者之谓案,正其罪者之谓断。先案而后断者,史体也;先断而后案者,经义也。②
然则有称国以弑,称国人以弑者,岂不得其主名与?曰:“苟不得其主名,则从盗杀蔡侯申之例矣,殆非也。”……曰:“《春秋》因旧史,从讣告,有所损而不能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有董狐、南史之谅,其赴于友邦,实者几何?夫不以实赴者,则必有所诿其罪矣,大都微者当之也。夫子参稽国史,以及七十二邦之闻,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辞也。故欲正其所诛,则赴异而事专;欲从其所诿,则实乖而网漏。今有杀人之狱,而断之者知其为豪杰魁横而无输辞也。与其移辜以弊狱,孰若悬案以征凶?故书曰某国弑其君,执政任事必有当之者,则乱臣贼子死有余惧。书王法而不诛其人身,意盖如此也。”①
凡称国、称人以弑者,其国以弑赴而有所诿者也。故夫子不从其所诿,明元凶之有在,慑奸恶于无形也。若其国不以弑赴,则旧史阙焉,夫子无从加焉,楚公子围之类是也。②
李光地指出,《春秋》对于乱臣贼子初削其籍,称其名,而后又称其爵、其国,或称某国人、盗。初削其籍是因为要正其罪状,表示此人已不再是国君之臣子。后书其官爵,则是为了存其罪证,表示其身为某官或世子、公子,却仍犯下此等恶事,其罪更甚。由于弑君者在当权之后会利用权力诿罪于卑微之人,而史官未必都能做到秉笔直书,故读者通过史书往往只知最后归罪之人,遂使真正的元凶逃脱谴责。因此,为了避免因考证不确、证据不足而无端将大恶强加于无辜之人,或仅书归狱之人,却令背后的主谋者漏网,孔子对于弑君之事的记录十分谨慎,书某国表示罪其执政大臣,书某国人表示同谋者多,书盗则表示宦官、宫妾之类不足齿数。而他之所以不直书其名,一是为了阙疑,因旧史无载;二是为了引导后人进一步推求其罪魁祸首,不让元凶有机会逃脱惩罚。
其二曰:
春秋初,诸侯兄弟多字,蔡叔、蔡季、纪季、许叔之类是也。其后,率称公子,例已见前也。叙伯叔者,著亲亲之恩;系属籍者,寓上下之等。春秋之初,国命未移,故亲亲之词厚。其后也,世卿逾恣,故上下之语严。奉君命则曰兄弟而名之,对上之称也;杀若奔则曰兄弟而名之,存亲之实也。叔肸称公弟于其卒,无列也;季友字于其归,非对上之称,且贤之也。无列何以不称公子?则以为于时之公子未有不贵者也。③
李光地提出,春秋初,诸侯的兄弟多称字,以示亲亲之恩,后礼法逐渐崩坏,若奉君命而列于朝廷则称名,以严上下之等;被杀或出奔亦称名,以存亲戚之实。例如,闵公元年,鲁闵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季友回到鲁国,《春秋》书:“季子来归。”季友字“季”,李光地认为,《春秋》称其字主要是因为春秋初诸侯兄弟有称字的惯例。“‘季子来归’,以为旌其贤,亦可通。然诸侯兄弟,有称字之例。”①又如,宣公十七年,鲁宣公之弟叔肸去世,《春秋》书:“公弟叔肸卒。”李光地认为“叔”是叔肸之字,《春秋》称其字是因为叔肸未列于朝廷。“肸无列于朝,则‘叔’非氏也。‘叔’非氏,则是《春秋》字之也。”②
其三曰:
卒称其本爵,葬从其僭号。却有两说:一世情,一道理。世情者,其国来讣,称其僭号,我因其讣而记之于我史册中,则我为政。我为政,则何必依其僭,直云某爵而已。至葬,则我往其国而会其葬,以彼为主,吾非天王,安得入其国,对其臣子而贬其君父?殊无宾主之礼。《公羊》所谓“卒从正,葬从主人”也。以道理言,先正其罪,后纪其实。不书本爵,何以见其实?不著僭号,何以见其僭?前之义例已明,而后随其常称,两相印证,所谓“微而显”也。此竟是《春秋》一通例。……如吴、楚先书国,后书爵,亦是此例。先儒以为进之,非也。惟吴、楚之丧,止于其来讣时书其本爵而已,至葬,虽鲁君或在,亦不书。盖葬虽从主人,而断不可书曰某王,故宁阙之。③
《春秋》列侯皆僭爵,故鲁亦侯也,而称公。然而经因之者,本国也。其余则卒也,以其班秩秩之;及其葬也,以其僭号称之。不以秩秩,则无以正其僭之非也;不以号称,则无以存其僭之实也。凡《春秋》书法,多如此者。①
崩薨与卒,皆有常称,礼也。五等之君,谥从其爵,制也。经之所书,夺其薨之常称于卒,而仍其公之僭谥于葬者何?曰:彼来赴,礼在彼也。彼有干于礼,吾从而卒之。我往会,礼在我也。礼无不敬,故仍而公之。何以知彼之有干于礼也?曰:其来赴者,若侯、若伯、若子,必皆曰我公薨也。若吴、楚,必曰我王崩也。干礼莫大焉,故存其始封之爵,又从而卒之也。往葬而贬其称焉,非邦交之礼,且无以著其僭号之罪,故仍其所僭之谥,从而公之。何以不书吴、楚?曰:王者所辟也。其王子削曰公子,可也;其王削曰某公,犹不可也。是故《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不著其葬号之谓也。②
李光地指出,《春秋》书诸侯之卒时称其本爵,书其葬时则从其僭号,并试图从世情与道理两方面对这一义例加以解释。从世情来看,诸侯去世后,其国必以其僭号来讣告。若将其记载于本国史册中,则以我为主,故不必依其僭号,只是直书其本爵即可。若往其国而会其葬,则以彼为主,不应对其臣子而贬其君父,故据宾主之礼而书其僭号。从道理来看,诸侯卒时书其本爵是为了表示其僭越之罪过,葬时书其僭号则是为了保存其僭越之实证。反过来说,若不书本爵,则无以反衬其僭越之非;不书僭号,则无以显示其僭越之罪。如对吴、楚两国先书国,后书爵,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因吴、楚等国僭越太甚,故其国君葬时亦不书其为王,宁可阙如。
其四曰:
自君杀之者,君杀也。国杀者,君臣共之也。人杀者,国乱而见杀,或众讨而杀之也。众讨而杀之者,必去其官与属。国乱见杀,则不去其官与属。①
李光地认为,《春秋》中凡是书大夫为某君杀,则是为国君所杀;书大夫为某国杀,则是为其国君臣共同杀死;书大夫为某国人杀,或是因其国动乱而被杀,或是因众人讨伐而被杀。其中,若因众人讨伐而被杀,则削去其官职与属籍;若是因国家动乱而被杀,则保留其官职与属籍。
关于杀大夫行为的合法性,李光地说道:
专杀大夫,非制也,无罪而杀,尤非义也。盖杀大夫之罪,不著名者为上,著名者次之,称人杀者又次之。削大夫者,杀者几无罪矣。②
在他看来,擅杀大夫是非法的,无罪而杀尤其不义。《春秋》记杀大夫之事,若不书姓名,则表示杀人者罪行最重;若书姓名,则杀人者罪行较轻;若称某国人杀,则罪行更轻;若削去被杀者官职,则表示杀人者几乎无罪。
其五曰:
人北杏之会,则曷为于鄄焉爵?人北杏之会,则义见矣,于其始乎见义也。虽然,会盟则爵之,搂伐则犹人之也。搂伐之事大,盖三王之罪人也。③
自桓霸后,征伐皆人之。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无道之世也。虽然,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赐。义既明矣,功则可进而进之也。桓之功于中国,自救邢始也。称师,别于人也,谓其能以众正矣。①
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据此,李光地认为,《春秋》记诸侯会盟、征伐之事,不称爵而称人,是对其违背礼法、道义的批评。相较之下,因为会盟之罪较轻,故《春秋》仅在记载北杏之会,即由齐桓公主持的诸侯第一次会盟时削爵称人以明其义,此后会盟仍称诸侯爵位。而征伐之罪较重,故《春秋》自齐桓公称霸后,于诸侯征伐多称人。但是,由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有尊王攘夷之功,使诸夏之民免于披发左衽,故《春秋》于齐国征伐之事或称师,有别于人,以示其功劳。
其六曰:
古之侯伯,有存亡继绝,急病分灾,尊王室,安诸夏之义,修而行之,是天下之公利也。《春秋》书诸侯事,如内辞者四:城楚丘、戍虎牢、伐陈、归粟于蔡是也。楚丘不城,卫入于狄矣。虎牢不戍,郑入于楚矣。戍陈、粟蔡,皆公举也,故以公辞也。齐桓存三亡国,独楚丘公其辞,何也?同则举重,救卫为重也。②
《左传》云:“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③李光地据此指出,古之诸侯有存亡继绝、急病分灾、尊王攘夷的责任和义务,若其行为符合这一要求,则代表天下公义,无须区分内外,故《春秋》记载其事便不书诸侯国名而为内辞。如僖公二年,齐桓公率诸侯在楚邱筑城,帮助卫国抵御狄的入侵,《春秋》书“城楚邱”;襄公五年,诸侯戍守陈国,助其抵御楚国入侵,《春秋》书“戍陈”;襄公十年,诸侯戍守虎牢,抵御楚军,《春秋》书“戍郑虎牢”;定公五年,蔡国被楚国围困,国内饥乏,诸侯将粮食送到蔡国,助其度过饥荒,《春秋》书“归粟于蔡”。至于齐桓公曾三次保存亡国,而《春秋》为何仅在“城楚邱”一事上使用内辞,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同样性质的事情只需举其重者以明义,而救援卫国的意义更为重要。
此外,关于《春秋》中其他“以名字、爵氏为褒贬”的义例与变例,李光地还总结归纳道:“《春秋》者,正名之书。秩序命讨,于名乎寓之。诸侯不生名,失地名,灭同姓名。然或失地而不名者,国灭而奔,哀之也。或灭同姓而不名者,贬爵为人,足以见志也。国灭而奔,则不名以哀之。而有不哀之者,徐子章羽也,僭王者也。国灭而受执,则名以责之。而有不责之者,虞公、夔子,人其灭同姓者于上,则存灭者之爵,甚灭之者之罪也。其奔也不名,其复也名,卫侯郑、衎也。其奔可恕,其复可罪也。大夫不名,必事可贤焉者,高子、季子也。三恪之国,则因事以存其官,宋司马、司城也。非此族也,则以姓名通。其不称姓氏者,非有大恶,则君未赐氏焉尔。”①
(2)关于记时之例,李光地认为应先记年,后书时,然后书月,最后书日。所谓“年下书时,时下书月,月下书日”②。若一季中并无值得记载的史事,则必书春夏春秋之时及其开始的第一个月份。所谓“四时无事,则书首月”③,“四时者,纪事之纲,故经虽其时无事,必书首月者,备天道也”④。这一义例只有碰到极为特殊的情况才可能发生改变。
如桓公四年、七年,《春秋》未书秋冬,李光地认为这并非阙文,而是孔子有意删削。因为秋冬象征刑罚,而罪恶莫大于弑君。对于鲁桓公弑君篡位的罪行,不但无人加以讨伐,周天子反而遣人来聘,谷伯绥、邓侯吾离亦远涉来朝,其行为皆有悖天道,使乱臣贼子无所畏惧。是故孔子削去当年秋冬之文,“乃恭行天讨之志,非阙文也”①1。
昭公十年,《春秋》未书冬。李光地认为这是孔子对鲁昭公当年娶吴孟子的批评。因为冬季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判而后阴阳交,所以冬季又象征夫妇之别。而鲁昭公娶吴孟子的行为扰乱、破坏了同姓不通婚的周礼,故孔子要“削冬见志”。
定公十四年,《春秋》亦未书冬。李光地认为这表达了孔子对自己当年不得已离开鲁国,治国安邦之志无法实现的伤感。“天之功,至冬而成。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将向于成而去,王道之不就,天道之不终也。是故不书冬者伤之。”②
又如隐公元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公元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孙于齐。”照理说,既然已书“春王正月”,春季中就不应该再记载其他史事。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特书首月者,其一时无事者也。若其时之他月有事,则不特书首月矣。惟隐、庄之元年,他月有事,而特书首月,则以虽不行即位之礼,而元年不可以无正也。③
《春秋》存首月者,一时无事者也。隐、庄三月有事而存首月,为元年虽不即位,而有朝庙告正之礼。④
换言之,隐公与庄公元年虽不行即位之礼,但有朝庙告正之礼,故不可不书正月。
庄公二十二年,《春秋》书:“夏五月。”照理说,夏季无事,应书“夏四月”,而非“夏五月”。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庄之二十二年夏无事,不书首月而书五月,何也?曰:“是庄公在丧纳币之岁也。周之夏四月,夏之春二月也,《周官》以是月会男女。《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言其礼之宜豫,则是月者,婚姻之月也。居丧纳币,则婚姻之礼废。比事属辞以见意,其义不亦深乎?”①
四时无事,则书首月。今以五月首时,何也?昏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娶仇人之女,当丧而图婚,亲纳币以固之,观社以尸之,丹楹刻桷以饰之,大夫宗妇觌用币以侈之,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周礼》仲春会男女,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姻之时也。昏姻之礼不正,义系月,故去月。②
李光地指出,根据《周礼》的规定,婚姻之事应在周历四月或夏历二月举行,而鲁庄公不仅娶仇人之女,而且在居丧期间的冬季亲赴齐国纳币,严重破坏了礼制。由于“昏礼”之义系于月,所以《春秋》不书“夏四月”,而书“夏五月”。
其二曰:
《春秋》以日月为义例,信乎?曰:“此亦史法之旧云尔。事之大且要者,则谨而日之。私家记录犹然,况国乘乎?是故郊祀宗庙则日,崩薨卒葬则日,天灾地变物异则日,以至会不日而盟则日,侵伐不日而战灭则日,此其大凡也。有应日而不日者矣,未有不应日而日者也。应日而不日者,旧史失之也,略之也,以是为特笔之褒贬则否。”③
《春秋》书事,月而不日,时而不月者,多矣,惟所谨者,则日之。灾异日,祭祀日,盟日,战日,入国灭国日,崩薨卒葬日。故有此数事而不日者,未有他事而日者。其有此数事而不日者何?曰:“史失之也。”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记时的另一项原则是对于祭祀宗庙、崩薨卒葬、灾异、结盟、战灭等重大史事要慎重记载具体日期。而且只有应书日而不书日的变例,没有不应书日而书日的情况。至于应书日而不书日,主要是因为旧史记载的简略与阙失,而非出于孔子的特笔褒贬。关于“会不日而盟则日,侵伐不日而战灭则日”的原因,李光地解释道:“月而不日,常事耳,则众纷纷而凿为之说。……‘会’之见书于《春秋》,于‘盟’略,故或时而不月,或月而不日,亦犹侵伐之于战灭也。”②也就是说,相较于“盟”与“战灭”,“会”与“侵伐”在春秋时更常发生,所以《春秋》在记载此类史事时往往不书日或月。
定公三年,鲁定公派遣大夫仲孙何忌与邾国国君结盟,《春秋》书:“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结盟大事理应书日,而此次结盟《春秋》仅书时,而未书月与日,李光地认为并非由于记载阙失,或许是孔子为了批评定公派遣大夫与对方国君结盟,身份并不对等,有怠慢对方之嫌,故有意不书月与日。“凡盟必日之,拔之盟,不日而且不月,又夫子当时之事,非遗失也。无亦非鲁以大夫盟邾君,故去月日以见慢欤?厥后句绎则如常书。”③
定公四年,鲁定公与诸侯在皋鼬结盟,《春秋》书:“五月,公及诸侯盟于皋鼬。”此次结盟亦未书日,李光地认为同样不是由于记载阙失,而是为了突显当时诸侯众志涣散,怠慢、忽视礼乐之事的状况。“皋鼬之盟不日,亦当时事,非遗失也。著众志已涣散,怠于礼而略于事矣。”①
僖公十六年正月,有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又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国都,《春秋》书:“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显然,“陨石于宋”与“六鹢退飞”都属于所谓的“物异”,而《春秋》却前者书日,后者不书日。对此,李光地说道:“六鹢书‘是月’,不止嫌与陨石同日而已,如止嫌同日,何不更著其日乎?或者‘六鹢退飞’不止一日也。”②在他看来,“六鹢退飞”之所以书月不书日,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与“陨石于宋”发生于同一天,而是由于其出现不止一日,所以符合《春秋》记时的另一条义例:“有灾眚经几日者,则书某月。”③
其三曰:
凡书时而不月以纪事者,盖旧史略焉,则未知其曷月与、日与,徒可得为此时而已。后代史书,年而不知其时,时而不知其日月者,盖多附于年时之终。若附于年时之终,则嫌其为卒时卒月之事也。今书无月有时之事于前,有月之事于后,则事之先后不出乎此时之中,而不正名其为首月也。先儒以为下有次月,则此必首月者,误矣。④
李光地认为,《春秋》纪事凡是仅书时而不书月者,多是因为史料缺乏,因而不知其发生的具体日月,只知大致时节。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便将其事系于该时开头,而将其他知道确切月份之事书于后。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清楚地表示此事发生的时节,不像后世史书将其附于年时之末那样容易产生误解,而并不意味着此事一定发生在其时首月。
其四曰:
凡《春秋》书事系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则非复蒙此日,而蒙上之时月也。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中记载具体日期之事,若其后紧跟着的事件并未书日,并不意味着两件事同日发生,而表示两件事同一月份或同一时节发生。故桓公十二年冬,《春秋》两书“丙戌”之日,“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李光地认为这正是因为“此两事适同日”,为了避免误会,“故特两书日以别之”。②
其五曰:
日食,书日书朔,朔日食也;书日不书朔,朔后食也;书朔不书日,朔前食也;不书日不书朔,阴雨食也。阴雨食,则国都不见而他处见之,非灵台所睹测,则未知其为正朔与?朔之前后与?是以阙之也。③
李光地指出,《春秋》在记载日食这一天象时,同时书日书朔表示朔日日食,书日而不书朔表示朔后日食,书朔而不书日表示朔前日食,不书日亦不书朔表示阴雨天日食。阴雨天日食之所以不书日亦不书朔,是由于国都的灵台观测不到,无法得知当日为朔日,抑或朔之前后,故阙而不书。
(3)关于避讳之例,李光地说道:
国恶则讳,臣子之礼也。夫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盖以其不变是非之实,但隐之而已,则直道行乎其间,无伤乎天下万世之公义也。昭公谓吴女为孟子,自讳之也。故《春秋》因之,曰“孟子卒”,不称“夫人”,不称“薨”,为君讳也。他日答司败以“知礼”,而又引为己过者以此。①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曰“知礼”,为尊者讳也。及司败指出娶同姓,辄自引过,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娶同姓为非礼,固昭然不没,而臣子之分亦得。此便是《春秋》义例。②
李光地指出,“讳国恶”是《春秋》书法的一条原则,体现了臣子之礼。孔L子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因此,鲁国的史官亦为国君所做的不合礼法、有损国家形象的恶事、丑事加以避讳。由于避讳只是对某事进行回避,不直书其事,并未伪造、歪曲事实,所以被认为没有损害天下万世之公义。譬如,鲁昭公娶同姓吴女为妻,讳称“孟子”。哀公十二年,吴孟子去世,《春秋》书:“孟子卒。”既不称“夫人”,亦不称“薨”,正是为鲁昭公避讳的缘故。类似地,据《论语》记载,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回答知礼,这亦是为昭公避讳。而当陈司败指出昭公娶同姓之女的行为不合礼法时,孔子立刻承认错误,引为己过,而未否认、歪曲事实,体现了“直在其中”的原则。
其二曰:
国之败辱亦讳,臣子之礼也。虽然,败辱而旋复者则不讳。是故乾时之败不讳,以其旋胜也。讙、阐之取不讳,以其旋归也。③
人取我国之土地不书,讳之也。至济西则书,后卒归也。不书则后归无因,既归则不必讳矣。战败不书,讳之也。至乾时之败则书,长勺即胜也。④
李光地指出,《春秋》对于鲁国在诸侯战争中战败、失地等耻辱亦多加以避讳。若是战败后旋胜,或失地后收复,则不必避讳。譬如,庄公九年,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乾时发生战争,鲁国战败。第二年,鲁庄公即在长勺击败齐国军队。故《春秋》书:“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并未避讳。又如,宣公元年,齐国占取了鲁国济水以西的田地。宣公十年,齐国又将济西之地归还给鲁国。故《春秋》书:“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并未避讳。哀公八年,齐国占取了鲁国的讙地与阐地,当年即归还鲁国。故《春秋》书:“夏,齐人取讙及阐”,亦未避讳。
关于战争方面的避讳,李光地又提出“周讳战,不讳败”的义例。他说:
鲁讳败,不讳战,败之辱大于战也;周讳战,不讳败,战之辱大于败也。①
鲁讳败,不讳战;周讳战,不讳败,莫敢与王战者也。战而胜,犹耻也。战之耻甚于败,故讳战,不讳败。②.
李光地指出,《春秋》在记录周天子参加的战争时,避讳书战,而不避讳书败。因为按照礼法的规定,诸侯是不应该与天子发生战争的。若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发生战争,即便周天子获胜,亦是一种极大的耻辱,且战争本身的耻辱超过战败的耻辱,所以周讳战,不讳败。
其三曰:
公及诸侯之大夫盟,诸侯之大夫来盟,皆不书公,亦讳也,非其班也。以此类之,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不著其所与盟者,亦为诸侯讳尔。谓嘉屈完之慕义,美桓公之用礼,盖取孟氏所谓“彼善于此”者,君子则于是乎见蛮荆大邦之抗,管子功烈之卑也。③
高子来盟,楚屈完来盟,旧说未是。圣人妙尽人情,都是内本国而外他国,内中国而外四裔之意。大凡鲁君与诸国之大夫盟,皆不书公,惟书及某盟而已,不肯以我君与诸大夫等也。鲁有难而齐轻之,故使高子来。桓公率众诸侯以临江、汉,倾天下之力,兴问罪之师,而楚子不亲出,仅遣屈完来,皆可耻者。故不著其君使之来,若彼国无君而其臣擅来者,非吾之辱也。独成公于楚师之临,孟献子、季文子不敢出,公自出与公子婴齐盟。书公者,所以著季、孟主忧、主辱之罪。①
李光地指出,鲁国国君与他国大夫会盟,或他国大夫来鲁国会盟,《春秋》皆不书“公”,以示避讳。这是因为二者的身份地位并不对等,如此会盟有悖于礼法。不单是鲁国国君,有时其他诸侯遇到类似情况,《春秋》亦为其避讳,以示“内本国而外他国,内中国而外四裔之意”。同时,他国国君派大夫前来与我国国君会盟,对我国来说亦是一种耻辱,故《春秋》于此往往不书“使”。因为书“使”意味着这些大臣的出访得到了天子或国君的正式命令,而不书“使”则表示他国无君而其臣擅来,因而不是我国的耻辱。譬如,闵公二年,齐桓公派大夫高傒来鲁国会盟,《春秋》书:“冬,齐高子来盟”,既不书“公”,亦未书“使”。又如,僖公四年,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的军队侵伐蔡国,胜利后又进攻楚国,楚成王派大夫屈完来召陵的诸侯军中会盟。《春秋》书:“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同样不书“公”,亦不书“使”。唯有成公二年,楚国进攻鲁国,鲁成公亲自到蜀地与楚国公子婴齐会盟,《春秋》书:“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楚国进攻鲁国时,鲁国大夫孟献子、季文子不敢挺身而出,致使鲁成公不得不亲自出面与公子婴齐会盟,所以《春秋》据实直书“公”,以示孟献子与季文子辱及君父之罪。
其四曰:
内于外诸侯不言朝,尊内也,聘无不可言者。内大夫于他邦亦不言聘,何也?曰:“鲁于大国,有比年而聘,有年而屡聘,而于天子略矣。故书‘聘’则恶显,书‘如’则词微。以聘行乎,以事行乎,悉以‘如’书之。”①
李光地认为,《春秋》于鲁国大夫奉命访问他国之事书“如”而不书“聘”亦是为了避讳。因为鲁国极少朝见周天子,却对其他大国聘问频繁,显然有悖礼法。在这种情况下,若直书“聘”则突显了鲁国国君的罪恶,若与因他事赴外国一般书“如”,则较为隐晦,可遮掩其罪。
最后,李光地指出,《春秋》中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书法与义例,但并不意味着每次碰到相同的情况都必然会使用同样的书法或义例。因为孔子既要借助各种书法、义例来突显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是非善恶,使读者知所鉴戒,又必须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如实地记录、保存史实,所以《春秋》往往首先以一个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作为典型,来表明一定的“义”,然后对于其他同类的人物或事件则按照常规或现状直书,而不使用特殊的笔法。而这亦成为《春秋》中的一条基本义例,所谓“义既明则存其实,盖一经之通例也”②。故曰:
《春秋》义明则从实。如弑君者之绝其属也,义既明矣,则公子之,世子之。五等之讣也,从周室之班,义既明矣,于其葬也,则公之,夫非先谨而后纵也。不明其义于先,是逆僭终无惩也;不存其实于后,是逆僭之迹不著。故前为断,而后为案也。③
隐无正者,二年以后无正月也;桓无王者,十八年之中,十四年不书王也。正者,诸侯所禀于王;王者,正诸侯者也。下不禀则无正,上不正则无王。桓弑其君,王不讨焉,而生死恩逮,是之谓不正而无王;隐终其位,王命四至,而朝聘奔会无一者,是之谓不禀而无正。然则他君异于此欤?曰:一经之始,于二君见义焉耳。《春秋》书法,见义者,义明则止,其余以常书。①在此,为了更详细地说明“义既明则存其实”这一通例,李光地列举了《春秋》中的一些具体表现与事例。譬如,对于弑君者,《春秋》先削其官爵,绝其为君之臣属,以明其义,而后又书其官爵,以存其弑君之实证。又如,对于去世的诸侯,《春秋》先书其本爵,以明其义,而后又从其僭号,以存其僭越之实证。同样,《春秋》记载隐公一朝的历史,元年之后便不书“正月”,记载桓公一朝的历史,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书“王”,这是对于隐公终身未朝聘于周天子,以及桓公弑君,而王不加讨,反而恩命累加的谴责与批判。可是这样的问题并非只发生在隐公与桓公二人身上,但除了隐公与桓公外,《春秋》并未在记载鲁国其他朝代历史的时候使用同样的书法。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隐、桓二公是《春秋》一书里最初的两位国君,故将其作为典型,以申明《春秋》大义。义明则止,故其余部分皆照常书写。而这也再次印证了李光地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诸经多将首二篇包括全书之义。……《春秋》隐、桓二公,亦尽一部《春秋》道理。隐无王,桓无天。无王者,隐公终身未尝朝聘于周,直似非其臣子者然。无天者,桓公弑君,王不加讨,又从而恩命稠叠焉。惟此二义,一部《春秋》,岂复外此。”②
类似地,隐公元年,周天子派遣宰咺到鲁国馈赠惠公与仲子的助葬物品,《春秋》书:“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冒。”桓公八年,周天子派遣家父到鲁国来聘问,《春秋》书:“天王使家父来聘。”庄公元年,周天子派遣荣叔到鲁国赏赐、追命桓公,《春秋》书:“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文公五年,周天子派遣荣叔到鲁国馈赠助葬物品,后鲁国为庄公夫人成风举行葬礼,周天子又派遣召伯到鲁国参加葬礼,《春秋》书:“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会葬。”李光地指出,隐公元年“赗仲子”与文公五年“会成风”两事类似,桓公八年“聘桓公”与庄公元年“锡桓公命”两事亦类似,但“皆名冢宰于前,王不称天于后”,这并非两事在性质或“义”上有什么不同,而是《春秋》“事同则举重,义明则以常书之法也”。①
综上可见,李光地虽不否认《春秋》中寓有孔子的褒贬之意,但他显然更注重从内外之别、君臣之义等礼法制度与伦理规范的角度来看待、归纳、发明和阐释《春秋》中的各种书法与义例。概括起来,其与朱熹所理解的“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春秋》大义内容大体一致,既体现了李光地的朱子学立场,亦从侧面反映出李光地与朱熹在《春秋》义例问题上的异中之同。至于发明《春秋》义例的具体方法,李光地则特别强调“属辞比事”的重要性。关于属辞比事,李光地解释道:“《春秋》之教,所谓‘比事’者,以同类之事相例也;所谓‘属辞’者,考其上下文以见意也。”②换言之,比事就是将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属辞就是通过考察上下文来理解经意。李光地指出,属辞比事“此最要紧。岂止《春秋》,凡经书皆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不是相比,则道理不能见得确实。况比事属词,《春秋》之教乎?圣人文章,随处不同。褒与贬不同矣,贬之中亦自不同。有贬至十分者,有九分几厘者”③。在他看来,《春秋》中的义例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书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圣人的微言大义有时就蕴含于极其微小的文字差别中,若不通过属辞比事的方法,就不可能准确、完整地把握《春秋》书法与圣贤义理。李光地之所以如此重视《春秋》的书法、义例,一方面固然是受到清初传统经典与经学研究复兴的影响,另一方面恐怕亦是由于清初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不安,故希望通过对《春秋》书法、义例中蕴含的君臣之义与礼法制度的关注、阐发与提倡来实现其稳定、重塑清初政治、社会、伦理秩序的目的,推动国家由乱而治。
《春秋》字字皆经称量,又义精仁熟,恰当事理,字面上下增减,变不变,称名辨物,俱是化工。⑤
别的经书,都是据理而谈,待人以事实之。此经(指《春秋》)却是现在日用间事,立朝理家,往来酬酢,大经大法,微文小节,经权常变,一举一动,一名一号,无不本之天理,合乎人情。直是人生要紧切务,斯须不可离者。⑥
《易》也者,达乎天德而周于民用;《春秋》也者,穷乎人事而临以天则。故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显至隐。《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⑦
《易》《春秋》,在五经中最奇,其中条分缕析,又皆是自然之理,日用眼前之事,所以为妙。《易》虚而实,空空洞洞,无所指定,而天下事事物物,形象变态,无一不备。《春秋》实而虚,有名有事,各不相假,然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万世,皆于是取则。人情物理,皆禀律令。幽隐微暧,神明鉴诸,信造化之精髓,性命之模范也。①
虽然在对待《春秋》的重视程度上与朱熹有所不同,但在对《春秋》性质的判断上,李光地仍基本遵从朱熹之说,以《春秋》为史书。譬如他说:
史书惟《春秋》当法。年下书时,时下书月,月下书日。有以两日赴者,则书两日;有灾眚经几日者,则书某月;有无关轻重者,则不书日。②
凡会外大夫不书“公”,非讳也,存内外君臣之体,盖史法也。③
在李光地看来,《春秋》不仅符合一般史书的体例与特征,而且史法严谨,足以作为后世史书的典范与样板。即便将它与其他公认的优秀史书相比,亦无出其右者。如“《左传》隐公在,公子翚便称隐公;《史记》武帝在,便称武帝,极有名史尚如此。试看字字着落,一毫不差,一毫不假借,除《春秋》更无有二”④。因此,若不熟读《春秋》,不要说大经大法不可知,就连作史的几项基本要素“年月、称谓、序次、体裁,不知《春秋》,下笔便错”⑤。李光地还举韩愈《平淮西碑》所记唐宪宗平定淮西藩镇之事为例,认为韩愈之所以在文中记征伐之事极为简略,似今日发兵,明日即捷,是因为“淮、蔡内地,聚天下之力,四年而后克之,作文者尚铺张扬厉,岂不辱国?此等处直学《书经》不书年月体,一跳便跳过许多年、许多事去,其义则出自《春秋》”①。
既然以《春秋》为史书,那么就牵涉到《春秋》的成书问题。李光地认为其并非出于孔子的私人撰述,而是依据鲁国旧史略加删削而成,只有删减,并无增加,且删削之处极少。他说:
古史书事,月日而已,无以时者,惟鲁之旧史名《春秋》。意者,鲁史记事以时欤?②
古书于字句间不能无错,惟六经无错处。《春秋》于本文错者仍之,却无奈他何。孔子于子阳曰:“吾知之,此公子阳生也。”子贡云:“既知之,何不改之?”子曰:“如不知何?”……《春秋》未经笔削,想亦是如此。③又说:
夫子当初,止因鲁史之旧,当时赴告有便书,无便不书,夫子岂得增减?只是定义例而已。④
《春秋》因旧史,从讣告,有所损而不能益也。……夫子参稽国史,以及七十二邦之闻,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辞也。⑤
如楚文、沃武,入春秋已强大,而不见于经者,告命未通也。虽同盟同会之人,其事不告,则亦不书,旧史所无故也。⑥
李光地认为,《春秋》乃孔子因鲁史旧文而作,鲁史亦名《春秋》,且鲁史与《春秋》皆以时记事,二者之间拥有许多共同点。同样,由于《春秋》是据鲁史而作,故其中有意保留了原文的一些错误。如《春秋》载:昭公“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据《公羊传》,孔子明知此“伯于阳”为“公子阳生”之误,但为了保存鲁史原貌并未加以修改。若从这一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春秋》未经笔削”。李光地还采《左传》之说①,指出孔子据鲁史修《春秋》的一大原则是“赴告有便书,无便不书”,故所书皆实有其事,而未书则由于旧史未载。他进而利用这一原则对《春秋》经文中的不少疑难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例如,庄公十二年,南宫万弑宋闵公,后反叛被镇压,遂出奔陈国,最后陈国在宋国的要求下将南宫万送回宋国。但《春秋》仅书“宋万出奔陈”,而未书“陈人杀万”。对此,李光地解释道:“愚谓闵弑、万奔,书,宋来告也。杀万、葬闵,不书,宋不告,鲁不会也。”②又如,僖公二年,晋国假道虞国进攻虢国,灭了下阳;僖公五年,晋国再次假道虞国进攻虢国,不仅灭了虢国,还在回师途中顺道灭了虞国,抓住了虞公。但《春秋》仅书“灭下阳”“执虞公”,而未书“灭虢”“灭虞”。对此,李光地解释道:“‘灭夏阳’,‘执虞公’,晋人必将有辞以告于诸侯,故得而书之也。灭虢、灭虞,晋人讳其事而不告,故不得而书之也。”③又如,春秋时楚国多次救援郑国,但《春秋》往往未书“救郑”。对此,李光地解释道:“或救而不及则不书,或诸侯恶而削其籍则亦不书也。当是时,楚、郑方与中国为敌,其兴师伐救之事,不讣可知,但凭列国诸侯在会者之记载耳。”④总之,在李光地看来,《春秋》未书其事的原因多是由于未赴告鲁国。
孔子曾说:“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⑤孟子亦云:“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①据此,一些学者认为孔子作《春秋》的用意在于以褒贬设素王之法,行天子之事。对于这种解释,李光地并不认同。他说:
凡说夫子竟操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是非褒贬,怎生峻厉,都是膜外话。夫子不过是该称君,该称臣,还你个本分便是。所以说“必也正名”。当时礼法荡尽,冠履倒置,圣人不别作一书,即用现成鲁史,为之笔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不过不肯一毫苟且假借而已。②
“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谓欲借二百四十年君臣之行事以寓义理,则是非善恶深切而著明。后之说者,以为圣人行事之实也。夫褒贬亦空言也,而何行事之实之有?③
岂知夫子垂世立教,不寓之他书,而必修《春秋》。盖他书为空言,《春秋》则有二百四十余年之行事,因而著其是非褒贬,则比之空言者,尤为深切著明。不是说夫子实行王者之事也,书仍旧是空言,但书中有许多行事在耳。④
至“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皆说作圣人托南面之权,为见之行事,非也。谓他书托之空言,不若《春秋》皆是列国实事,有可考证,功罪易见,义理易明耳。⑤
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盖谓《春秋》本诸侯之史,其时列邦僭乱,名分混淆,而史体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则一裁以武、成班爵之旧,其行事则一律以周公制礼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犹曰“天子之史”云尔。说者不察,而以为夫子行南面之权,则近于夸矣。又董仲舒述夫子之言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盖谓凡著书者,言理则虚,征事则实,故虽言理义以垂训,不如借二百余年行事,使是非得失皆著见于此尔。说者以为《春秋》是夫子之行事,非空言比,亦似非本意。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只是据实直书而已,君便称君,臣便称臣,通过“正名”的方式使得君臣父子各止其所,各得其安,以此重建被严重毁坏的社会秩序和礼乐制度。因此,孔子所说的“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只是希望借助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列国实事以寓义理,使后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是非善恶,并有所鉴戒,既非托南面之权,更无所谓行事之实。而孟子所说的“《春秋》,天子之事也”,也只是说当时礼崩乐坏,名分混淆,史体乖舛,故孔子欲以周初的礼法制度为标准,来为天子修史,以拨乱反正,而非代王者立法。根据李光地的理解,“天子之事”即“天子之史”。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与周王室关系最为亲近,亦保存了最多的西周礼法制度。而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其内容必然与“天子之事”密切相关。故曰:“事是桓、文,王降而霸;史是《春秋》,周礼在鲁。俱隐隐与王迹事相关,乃义之所由起也。”②
关于研究《春秋》的方法,朱熹主张通过书中记载的史实来明其大义,使后人知晓是非善恶与治乱兴衰之道,并引为鉴戒,因而反对在一字一词上求圣人褒贬之意,或妄立所谓的“凡例”,以免陷于穿凿附会的解说。故曰:
《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想孔子当时只是要备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写在这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①
当时史书掌于史官,想人不得见。及孔子取而笔削之,而其义大明。孔子亦何尝有意说用某字,使人知劝;用某字,使人知惧;用其字,有甚微词奥义,使人晓不得,足以褒贬荣辱人来?不过如今之史书直书其事,善者恶者了然在目,观之者知所惩劝,故乱臣贼子有所畏惧而不犯耳。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②
在这一问题上,李光地的观点与朱熹有同亦有异。由于李光地主张《春秋》是孔子据鲁史而作,且“有所损而不能益”,自然也不能同意传统的“一字褒贬”说。他说:
《诗》不必篇篇皆美刺,《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贬。《诗》贞淫并著,而其教归于正人心。《春秋》善恶并书,而其教主于存天理。③
《易》不蔽于卜筮,而蔽于占候;《春秋》不蔽于书法,而蔽于义例。非谓卜筮之非占,而书法之无义也。以为候之流于拘,而例之失于凿也。自汉以来病之。问其说,曰:“《易》者变动不居,其可以星日气候推乎?《春秋》者因物付物,其可以文法律例求乎?”④
论人止就其事迹,不必钩深索隐,钩棘得之,未必不差。如用刑,宁失出,毋失入也。孔子论人,以及《春秋》书法,皆是如此。《春秋》如今日档案则例一般,凡大事须查案定拟。韩文公云:“《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但得王法不泯便好,何用又推深一层?如今觉得《春秋》千变万化,都是平平常常情理。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只是直书其事,使天理自彰,是非善恶自现而已,并非言言皆寓褒贬。若是执着于每字每事中求其褒贬,则将蔽于义例,而失于穿凿附会。譬如,文公三年,楚国围攻江国,晋国派遣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文公四年,晋侯讨伐秦国,后楚国灭亡江国。但《春秋》却先书“楚人灭江”,后书“晋侯伐秦”。对此,后世学者多以褒贬之义加以解释。李光地并不赞同,提出:“书‘晋侯伐秦’于‘楚人灭江’之下,见其重于修怨,轻于救患,无攘却之善也。救江则遣处父,伐秦则身亲之,侯伯之职安在哉?于秦、晋往复之间,非褒贬所系也。”②又如,宣公八年,鲁大夫仲遂死于齐国的垂地。由于仲遂曾杀文公太子,故不少学者认为《春秋》称“仲遂”而不称“公子遂”亦是出于褒贬之义。对此,李光地说道:“仲遂之卒,不称公子,以为蒙前文,固也。然实于其殁也名而绝之,如翚于隐之例耳。其或卒,或不卒,不可以为褒贬。”③他又引《春秋》“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为据,认为“《春秋》书‘犹绎’,而《檀弓》有‘卿卒不绎’之言,则仲遂之功罪姑无论矣。所谓‘书王法而不诛其人身’者,此类也”④,可见《春秋》并无贬斥仲遂之意。又如,襄公二十九年,吴王派公子季札出使鲁国,《春秋》书:“吴子使札来聘。”一些学者认为,《春秋》称季札为“札”是对他让国之德的褒扬。对此,李光地亦不赞同,指出:“子札褒贬之说棼如。愚谓《春秋》于札无褒贬焉耳。褒贬者必于事,于来聘而褒贬其生平,远矣。札在国,必曰王子札也。其称于我,亦必其王子札也。”⑤
同时,李光地还认为,《春秋》的书法严谨主要体现在大经大法上,即对待大事极为严格,王法森然,一毫不肯假借,必明其是非邪正,但对于一般的人与事则较为宽大忠厚,都是平平常常情理,只要“有一丝合于善,便奖许之恐后,其仁爱至矣”①,并不钩深索隐、诛其人身,因而自然反对所谓的“诛心”之说:
《史记》:“《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说者谓《春秋》由事迹上推见人之心曲,所谓“诛心”,其实非也。“见”字读现,与上“显”字同。《易》言造化幽微之故,以至于人事;《春秋》则由事迹之显著,而至于精微。句法少一“以”字,不与上对耳。见,即所谓“见之行事”也。②
司马迁言:“《易》本隐以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见”即“显”也。天道隐,人事显,盖言《易》本天道以该人事,《春秋》推人事以合天道,故其下即云:“《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说者又似以推见至隐为推究隐情之义,故谭经往往有锻炼文致者,皆由于此也。③
需要注意的是,李光地只是说“《春秋》不必言言皆褒贬”,批评“例之失于凿”而已,并没有说《春秋》“书法之无义也”。相反,由于李光地认定《春秋》从大经大法到微文小节中都蕴含了天理之常、性命之理与万世之法,并寄托了孔子“推见至隐”的深刻用意,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否认其中存在孔子特殊的书法与义例。譬如他说:
朱子说,《春秋》据事直书为多,未必尽有褒贬。或不以为然。不知朱子不是说全无褒贬,谓未必如今人说一字不放空,都有褒贬耳。④
《春秋》最是难看,无一点文采,不过几个字眼,颠倒用得的确,便使万世之大经大法,灿然具备。微而显,显而微,一归义理之精,无非自然之则。①
一部《春秋》,不过几个字换来换去,数之可了。这几个字忽如此用,忽不如此用;忽用,忽不用。参互错综,遂千变万化。曲曲折折,精义入神,不可思议,又至稳至当,极合人情。即以此尽天下之事,类万物之情,通性命之理。②
近看《春秋》,见得一片天理人情,只苦来日有限,未能卒业。其中义例纷然,变化错出,思之皆有妙义。③
《论语》有十数章,便是《春秋》义例。如《八佾》“雍彻”,“陈恒司败”,“崔子、子文”,“冉子退朝”,“正名”,“为卫君”之类,不独大义朗然,即词语轻重婉直之间,都是义例。如“臧文仲窃位”举其大,“微生高不直”举其小皆是。④
④同上书、第262页
由此可见,李光地反对的只是穿凿附会、过度夸大的“一字褒贬”说,而未否认《春秋》中存在各种书法、义例。相反,李光地还对这些书法、义例极为重视,赞叹有加,认为其皆出于孔子的有意安排,千变万化,精义入神,至当不易,可与《论语》等经典相互发明,故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篇幅来发明、探讨《春秋》中的书法、义例。
(1)关于称谓之例,李光地说道:
如乱臣贼子,初则削其籍,称其名,后乃称其爵,或称其国,或称某国人,或称盗。盖初则疾恶之至,绝之非其臣子也。既而并存其爵,若曰此为其某官,为其世子,而至为此事也。史官如董狐、南史者甚少,焉能皆死其官?使弑君之贼,皆如赵盾、崔杼之不能逃其罪,史官既不能死其职,则弑君之贼必秉国钧,安肯以己行弑讣于诸侯?势必另举一人以实之。如魏高贵乡公之事,司马昭问陈泰曰:“今日之事,何以处我?”陈泰曰:“惟杀贾充,稍可以谢天下。”昭问其次,曰:“泰言有进于此者,不知其次。”论首恶则昭也,乃诛行刺之成济而归狱焉。朱子灼知确见,故书曰:“魏司马昭弑其主髦。”假使考之不确,既不能无所证据,而以大恶加人,若书其归狱之人,却令首谋者漏网,后世将竟不知其为某某也。夫子于此等,则书曰某国,罪其大臣也;曰某国人,则与谋者多也;曰盗,宦官宫妾之类不足齿数也。不书其名,一以见阙疑之意,一以使后之人不知所主名而推求之,则其人亦不能以归狱于他人而卸其罪。此等义例,信非圣人不能创。①
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必削属籍,而不以爵氏通。……其后或姓氏之,或世子、公子之。不削属籍,则弑君者犹夫人,无以正其弑之罪也。不姓氏之,世子、公子之,则安知其非微者、盗者,而为邦之臣子乎?是无以著其弑之实也。凡具其实者之谓案,正其罪者之谓断。先案而后断者,史体也;先断而后案者,经义也。②
然则有称国以弑,称国人以弑者,岂不得其主名与?曰:“苟不得其主名,则从盗杀蔡侯申之例矣,殆非也。”……曰:“《春秋》因旧史,从讣告,有所损而不能益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不有董狐、南史之谅,其赴于友邦,实者几何?夫不以实赴者,则必有所诿其罪矣,大都微者当之也。夫子参稽国史,以及七十二邦之闻,得其故矣,而不敢造其辞也。故欲正其所诛,则赴异而事专;欲从其所诿,则实乖而网漏。今有杀人之狱,而断之者知其为豪杰魁横而无输辞也。与其移辜以弊狱,孰若悬案以征凶?故书曰某国弑其君,执政任事必有当之者,则乱臣贼子死有余惧。书王法而不诛其人身,意盖如此也。”①
凡称国、称人以弑者,其国以弑赴而有所诿者也。故夫子不从其所诿,明元凶之有在,慑奸恶于无形也。若其国不以弑赴,则旧史阙焉,夫子无从加焉,楚公子围之类是也。②
李光地指出,《春秋》对于乱臣贼子初削其籍,称其名,而后又称其爵、其国,或称某国人、盗。初削其籍是因为要正其罪状,表示此人已不再是国君之臣子。后书其官爵,则是为了存其罪证,表示其身为某官或世子、公子,却仍犯下此等恶事,其罪更甚。由于弑君者在当权之后会利用权力诿罪于卑微之人,而史官未必都能做到秉笔直书,故读者通过史书往往只知最后归罪之人,遂使真正的元凶逃脱谴责。因此,为了避免因考证不确、证据不足而无端将大恶强加于无辜之人,或仅书归狱之人,却令背后的主谋者漏网,孔子对于弑君之事的记录十分谨慎,书某国表示罪其执政大臣,书某国人表示同谋者多,书盗则表示宦官、宫妾之类不足齿数。而他之所以不直书其名,一是为了阙疑,因旧史无载;二是为了引导后人进一步推求其罪魁祸首,不让元凶有机会逃脱惩罚。
其二曰:
春秋初,诸侯兄弟多字,蔡叔、蔡季、纪季、许叔之类是也。其后,率称公子,例已见前也。叙伯叔者,著亲亲之恩;系属籍者,寓上下之等。春秋之初,国命未移,故亲亲之词厚。其后也,世卿逾恣,故上下之语严。奉君命则曰兄弟而名之,对上之称也;杀若奔则曰兄弟而名之,存亲之实也。叔肸称公弟于其卒,无列也;季友字于其归,非对上之称,且贤之也。无列何以不称公子?则以为于时之公子未有不贵者也。③
李光地提出,春秋初,诸侯的兄弟多称字,以示亲亲之恩,后礼法逐渐崩坏,若奉君命而列于朝廷则称名,以严上下之等;被杀或出奔亦称名,以存亲戚之实。例如,闵公元年,鲁闵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季友回到鲁国,《春秋》书:“季子来归。”季友字“季”,李光地认为,《春秋》称其字主要是因为春秋初诸侯兄弟有称字的惯例。“‘季子来归’,以为旌其贤,亦可通。然诸侯兄弟,有称字之例。”①又如,宣公十七年,鲁宣公之弟叔肸去世,《春秋》书:“公弟叔肸卒。”李光地认为“叔”是叔肸之字,《春秋》称其字是因为叔肸未列于朝廷。“肸无列于朝,则‘叔’非氏也。‘叔’非氏,则是《春秋》字之也。”②
其三曰:
卒称其本爵,葬从其僭号。却有两说:一世情,一道理。世情者,其国来讣,称其僭号,我因其讣而记之于我史册中,则我为政。我为政,则何必依其僭,直云某爵而已。至葬,则我往其国而会其葬,以彼为主,吾非天王,安得入其国,对其臣子而贬其君父?殊无宾主之礼。《公羊》所谓“卒从正,葬从主人”也。以道理言,先正其罪,后纪其实。不书本爵,何以见其实?不著僭号,何以见其僭?前之义例已明,而后随其常称,两相印证,所谓“微而显”也。此竟是《春秋》一通例。……如吴、楚先书国,后书爵,亦是此例。先儒以为进之,非也。惟吴、楚之丧,止于其来讣时书其本爵而已,至葬,虽鲁君或在,亦不书。盖葬虽从主人,而断不可书曰某王,故宁阙之。③
《春秋》列侯皆僭爵,故鲁亦侯也,而称公。然而经因之者,本国也。其余则卒也,以其班秩秩之;及其葬也,以其僭号称之。不以秩秩,则无以正其僭之非也;不以号称,则无以存其僭之实也。凡《春秋》书法,多如此者。①
崩薨与卒,皆有常称,礼也。五等之君,谥从其爵,制也。经之所书,夺其薨之常称于卒,而仍其公之僭谥于葬者何?曰:彼来赴,礼在彼也。彼有干于礼,吾从而卒之。我往会,礼在我也。礼无不敬,故仍而公之。何以知彼之有干于礼也?曰:其来赴者,若侯、若伯、若子,必皆曰我公薨也。若吴、楚,必曰我王崩也。干礼莫大焉,故存其始封之爵,又从而卒之也。往葬而贬其称焉,非邦交之礼,且无以著其僭号之罪,故仍其所僭之谥,从而公之。何以不书吴、楚?曰:王者所辟也。其王子削曰公子,可也;其王削曰某公,犹不可也。是故《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不著其葬号之谓也。②
李光地指出,《春秋》书诸侯之卒时称其本爵,书其葬时则从其僭号,并试图从世情与道理两方面对这一义例加以解释。从世情来看,诸侯去世后,其国必以其僭号来讣告。若将其记载于本国史册中,则以我为主,故不必依其僭号,只是直书其本爵即可。若往其国而会其葬,则以彼为主,不应对其臣子而贬其君父,故据宾主之礼而书其僭号。从道理来看,诸侯卒时书其本爵是为了表示其僭越之罪过,葬时书其僭号则是为了保存其僭越之实证。反过来说,若不书本爵,则无以反衬其僭越之非;不书僭号,则无以显示其僭越之罪。如对吴、楚两国先书国,后书爵,也是同样的道理。但因吴、楚等国僭越太甚,故其国君葬时亦不书其为王,宁可阙如。
其四曰:
自君杀之者,君杀也。国杀者,君臣共之也。人杀者,国乱而见杀,或众讨而杀之也。众讨而杀之者,必去其官与属。国乱见杀,则不去其官与属。①
李光地认为,《春秋》中凡是书大夫为某君杀,则是为国君所杀;书大夫为某国杀,则是为其国君臣共同杀死;书大夫为某国人杀,或是因其国动乱而被杀,或是因众人讨伐而被杀。其中,若因众人讨伐而被杀,则削去其官职与属籍;若是因国家动乱而被杀,则保留其官职与属籍。
关于杀大夫行为的合法性,李光地说道:
专杀大夫,非制也,无罪而杀,尤非义也。盖杀大夫之罪,不著名者为上,著名者次之,称人杀者又次之。削大夫者,杀者几无罪矣。②
在他看来,擅杀大夫是非法的,无罪而杀尤其不义。《春秋》记杀大夫之事,若不书姓名,则表示杀人者罪行最重;若书姓名,则杀人者罪行较轻;若称某国人杀,则罪行更轻;若削去被杀者官职,则表示杀人者几乎无罪。
其五曰:
人北杏之会,则曷为于鄄焉爵?人北杏之会,则义见矣,于其始乎见义也。虽然,会盟则爵之,搂伐则犹人之也。搂伐之事大,盖三王之罪人也。③
自桓霸后,征伐皆人之。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无道之世也。虽然,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赐。义既明矣,功则可进而进之也。桓之功于中国,自救邢始也。称师,别于人也,谓其能以众正矣。①
孔子曾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据此,李光地认为,《春秋》记诸侯会盟、征伐之事,不称爵而称人,是对其违背礼法、道义的批评。相较之下,因为会盟之罪较轻,故《春秋》仅在记载北杏之会,即由齐桓公主持的诸侯第一次会盟时削爵称人以明其义,此后会盟仍称诸侯爵位。而征伐之罪较重,故《春秋》自齐桓公称霸后,于诸侯征伐多称人。但是,由于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有尊王攘夷之功,使诸夏之民免于披发左衽,故《春秋》于齐国征伐之事或称师,有别于人,以示其功劳。
其六曰:
古之侯伯,有存亡继绝,急病分灾,尊王室,安诸夏之义,修而行之,是天下之公利也。《春秋》书诸侯事,如内辞者四:城楚丘、戍虎牢、伐陈、归粟于蔡是也。楚丘不城,卫入于狄矣。虎牢不戍,郑入于楚矣。戍陈、粟蔡,皆公举也,故以公辞也。齐桓存三亡国,独楚丘公其辞,何也?同则举重,救卫为重也。②
《左传》云:“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③李光地据此指出,古之诸侯有存亡继绝、急病分灾、尊王攘夷的责任和义务,若其行为符合这一要求,则代表天下公义,无须区分内外,故《春秋》记载其事便不书诸侯国名而为内辞。如僖公二年,齐桓公率诸侯在楚邱筑城,帮助卫国抵御狄的入侵,《春秋》书“城楚邱”;襄公五年,诸侯戍守陈国,助其抵御楚国入侵,《春秋》书“戍陈”;襄公十年,诸侯戍守虎牢,抵御楚军,《春秋》书“戍郑虎牢”;定公五年,蔡国被楚国围困,国内饥乏,诸侯将粮食送到蔡国,助其度过饥荒,《春秋》书“归粟于蔡”。至于齐桓公曾三次保存亡国,而《春秋》为何仅在“城楚邱”一事上使用内辞,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同样性质的事情只需举其重者以明义,而救援卫国的意义更为重要。
此外,关于《春秋》中其他“以名字、爵氏为褒贬”的义例与变例,李光地还总结归纳道:“《春秋》者,正名之书。秩序命讨,于名乎寓之。诸侯不生名,失地名,灭同姓名。然或失地而不名者,国灭而奔,哀之也。或灭同姓而不名者,贬爵为人,足以见志也。国灭而奔,则不名以哀之。而有不哀之者,徐子章羽也,僭王者也。国灭而受执,则名以责之。而有不责之者,虞公、夔子,人其灭同姓者于上,则存灭者之爵,甚灭之者之罪也。其奔也不名,其复也名,卫侯郑、衎也。其奔可恕,其复可罪也。大夫不名,必事可贤焉者,高子、季子也。三恪之国,则因事以存其官,宋司马、司城也。非此族也,则以姓名通。其不称姓氏者,非有大恶,则君未赐氏焉尔。”①
(2)关于记时之例,李光地认为应先记年,后书时,然后书月,最后书日。所谓“年下书时,时下书月,月下书日”②。若一季中并无值得记载的史事,则必书春夏春秋之时及其开始的第一个月份。所谓“四时无事,则书首月”③,“四时者,纪事之纲,故经虽其时无事,必书首月者,备天道也”④。这一义例只有碰到极为特殊的情况才可能发生改变。
如桓公四年、七年,《春秋》未书秋冬,李光地认为这并非阙文,而是孔子有意删削。因为秋冬象征刑罚,而罪恶莫大于弑君。对于鲁桓公弑君篡位的罪行,不但无人加以讨伐,周天子反而遣人来聘,谷伯绥、邓侯吾离亦远涉来朝,其行为皆有悖天道,使乱臣贼子无所畏惧。是故孔子削去当年秋冬之文,“乃恭行天讨之志,非阙文也”①1。
昭公十年,《春秋》未书冬。李光地认为这是孔子对鲁昭公当年娶吴孟子的批评。因为冬季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判而后阴阳交,所以冬季又象征夫妇之别。而鲁昭公娶吴孟子的行为扰乱、破坏了同姓不通婚的周礼,故孔子要“削冬见志”。
定公十四年,《春秋》亦未书冬。李光地认为这表达了孔子对自己当年不得已离开鲁国,治国安邦之志无法实现的伤感。“天之功,至冬而成。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将向于成而去,王道之不就,天道之不终也。是故不书冬者伤之。”②
又如隐公元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公元年,《春秋》书:“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孙于齐。”照理说,既然已书“春王正月”,春季中就不应该再记载其他史事。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特书首月者,其一时无事者也。若其时之他月有事,则不特书首月矣。惟隐、庄之元年,他月有事,而特书首月,则以虽不行即位之礼,而元年不可以无正也。③
《春秋》存首月者,一时无事者也。隐、庄三月有事而存首月,为元年虽不即位,而有朝庙告正之礼。④
换言之,隐公与庄公元年虽不行即位之礼,但有朝庙告正之礼,故不可不书正月。
庄公二十二年,《春秋》书:“夏五月。”照理说,夏季无事,应书“夏四月”,而非“夏五月”。对此,李光地解释道:
庄之二十二年夏无事,不书首月而书五月,何也?曰:“是庄公在丧纳币之岁也。周之夏四月,夏之春二月也,《周官》以是月会男女。《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言其礼之宜豫,则是月者,婚姻之月也。居丧纳币,则婚姻之礼废。比事属辞以见意,其义不亦深乎?”①
四时无事,则书首月。今以五月首时,何也?昏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娶仇人之女,当丧而图婚,亲纳币以固之,观社以尸之,丹楹刻桷以饰之,大夫宗妇觌用币以侈之,礼之失未有甚于庄公者也。《周礼》仲春会男女,周之四月,夏之二月,昏姻之时也。昏姻之礼不正,义系月,故去月。②
李光地指出,根据《周礼》的规定,婚姻之事应在周历四月或夏历二月举行,而鲁庄公不仅娶仇人之女,而且在居丧期间的冬季亲赴齐国纳币,严重破坏了礼制。由于“昏礼”之义系于月,所以《春秋》不书“夏四月”,而书“夏五月”。
其二曰:
《春秋》以日月为义例,信乎?曰:“此亦史法之旧云尔。事之大且要者,则谨而日之。私家记录犹然,况国乘乎?是故郊祀宗庙则日,崩薨卒葬则日,天灾地变物异则日,以至会不日而盟则日,侵伐不日而战灭则日,此其大凡也。有应日而不日者矣,未有不应日而日者也。应日而不日者,旧史失之也,略之也,以是为特笔之褒贬则否。”③
《春秋》书事,月而不日,时而不月者,多矣,惟所谨者,则日之。灾异日,祭祀日,盟日,战日,入国灭国日,崩薨卒葬日。故有此数事而不日者,未有他事而日者。其有此数事而不日者何?曰:“史失之也。”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记时的另一项原则是对于祭祀宗庙、崩薨卒葬、灾异、结盟、战灭等重大史事要慎重记载具体日期。而且只有应书日而不书日的变例,没有不应书日而书日的情况。至于应书日而不书日,主要是因为旧史记载的简略与阙失,而非出于孔子的特笔褒贬。关于“会不日而盟则日,侵伐不日而战灭则日”的原因,李光地解释道:“月而不日,常事耳,则众纷纷而凿为之说。……‘会’之见书于《春秋》,于‘盟’略,故或时而不月,或月而不日,亦犹侵伐之于战灭也。”②也就是说,相较于“盟”与“战灭”,“会”与“侵伐”在春秋时更常发生,所以《春秋》在记载此类史事时往往不书日或月。
定公三年,鲁定公派遣大夫仲孙何忌与邾国国君结盟,《春秋》书:“冬,仲孙何忌及邾子盟于拔。”结盟大事理应书日,而此次结盟《春秋》仅书时,而未书月与日,李光地认为并非由于记载阙失,或许是孔子为了批评定公派遣大夫与对方国君结盟,身份并不对等,有怠慢对方之嫌,故有意不书月与日。“凡盟必日之,拔之盟,不日而且不月,又夫子当时之事,非遗失也。无亦非鲁以大夫盟邾君,故去月日以见慢欤?厥后句绎则如常书。”③
定公四年,鲁定公与诸侯在皋鼬结盟,《春秋》书:“五月,公及诸侯盟于皋鼬。”此次结盟亦未书日,李光地认为同样不是由于记载阙失,而是为了突显当时诸侯众志涣散,怠慢、忽视礼乐之事的状况。“皋鼬之盟不日,亦当时事,非遗失也。著众志已涣散,怠于礼而略于事矣。”①
僖公十六年正月,有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又有六只水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国都,《春秋》书:“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显然,“陨石于宋”与“六鹢退飞”都属于所谓的“物异”,而《春秋》却前者书日,后者不书日。对此,李光地说道:“六鹢书‘是月’,不止嫌与陨石同日而已,如止嫌同日,何不更著其日乎?或者‘六鹢退飞’不止一日也。”②在他看来,“六鹢退飞”之所以书月不书日,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与“陨石于宋”发生于同一天,而是由于其出现不止一日,所以符合《春秋》记时的另一条义例:“有灾眚经几日者,则书某月。”③
其三曰:
凡书时而不月以纪事者,盖旧史略焉,则未知其曷月与、日与,徒可得为此时而已。后代史书,年而不知其时,时而不知其日月者,盖多附于年时之终。若附于年时之终,则嫌其为卒时卒月之事也。今书无月有时之事于前,有月之事于后,则事之先后不出乎此时之中,而不正名其为首月也。先儒以为下有次月,则此必首月者,误矣。④
李光地认为,《春秋》纪事凡是仅书时而不书月者,多是因为史料缺乏,因而不知其发生的具体日月,只知大致时节。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便将其事系于该时开头,而将其他知道确切月份之事书于后。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清楚地表示此事发生的时节,不像后世史书将其附于年时之末那样容易产生误解,而并不意味着此事一定发生在其时首月。
其四曰:
凡《春秋》书事系日矣,其下有不月日而事者,则非复蒙此日,而蒙上之时月也。①
李光地指出,《春秋》中记载具体日期之事,若其后紧跟着的事件并未书日,并不意味着两件事同日发生,而表示两件事同一月份或同一时节发生。故桓公十二年冬,《春秋》两书“丙戌”之日,“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李光地认为这正是因为“此两事适同日”,为了避免误会,“故特两书日以别之”。②
其五曰:
日食,书日书朔,朔日食也;书日不书朔,朔后食也;书朔不书日,朔前食也;不书日不书朔,阴雨食也。阴雨食,则国都不见而他处见之,非灵台所睹测,则未知其为正朔与?朔之前后与?是以阙之也。③
李光地指出,《春秋》在记载日食这一天象时,同时书日书朔表示朔日日食,书日而不书朔表示朔后日食,书朔而不书日表示朔前日食,不书日亦不书朔表示阴雨天日食。阴雨天日食之所以不书日亦不书朔,是由于国都的灵台观测不到,无法得知当日为朔日,抑或朔之前后,故阙而不书。
(3)关于避讳之例,李光地说道:
国恶则讳,臣子之礼也。夫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盖以其不变是非之实,但隐之而已,则直道行乎其间,无伤乎天下万世之公义也。昭公谓吴女为孟子,自讳之也。故《春秋》因之,曰“孟子卒”,不称“夫人”,不称“薨”,为君讳也。他日答司败以“知礼”,而又引为己过者以此。①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曰“知礼”,为尊者讳也。及司败指出娶同姓,辄自引过,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娶同姓为非礼,固昭然不没,而臣子之分亦得。此便是《春秋》义例。②
李光地指出,“讳国恶”是《春秋》书法的一条原则,体现了臣子之礼。孔L子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因此,鲁国的史官亦为国君所做的不合礼法、有损国家形象的恶事、丑事加以避讳。由于避讳只是对某事进行回避,不直书其事,并未伪造、歪曲事实,所以被认为没有损害天下万世之公义。譬如,鲁昭公娶同姓吴女为妻,讳称“孟子”。哀公十二年,吴孟子去世,《春秋》书:“孟子卒。”既不称“夫人”,亦不称“薨”,正是为鲁昭公避讳的缘故。类似地,据《论语》记载,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孔子回答知礼,这亦是为昭公避讳。而当陈司败指出昭公娶同姓之女的行为不合礼法时,孔子立刻承认错误,引为己过,而未否认、歪曲事实,体现了“直在其中”的原则。
其二曰:
国之败辱亦讳,臣子之礼也。虽然,败辱而旋复者则不讳。是故乾时之败不讳,以其旋胜也。讙、阐之取不讳,以其旋归也。③
人取我国之土地不书,讳之也。至济西则书,后卒归也。不书则后归无因,既归则不必讳矣。战败不书,讳之也。至乾时之败则书,长勺即胜也。④
李光地指出,《春秋》对于鲁国在诸侯战争中战败、失地等耻辱亦多加以避讳。若是战败后旋胜,或失地后收复,则不必避讳。譬如,庄公九年,鲁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乾时发生战争,鲁国战败。第二年,鲁庄公即在长勺击败齐国军队。故《春秋》书:“八月庚申,及齐师战于乾时,我师败绩”,并未避讳。又如,宣公元年,齐国占取了鲁国济水以西的田地。宣公十年,齐国又将济西之地归还给鲁国。故《春秋》书:“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并未避讳。哀公八年,齐国占取了鲁国的讙地与阐地,当年即归还鲁国。故《春秋》书:“夏,齐人取讙及阐”,亦未避讳。
关于战争方面的避讳,李光地又提出“周讳战,不讳败”的义例。他说:
鲁讳败,不讳战,败之辱大于战也;周讳战,不讳败,战之辱大于败也。①
鲁讳败,不讳战;周讳战,不讳败,莫敢与王战者也。战而胜,犹耻也。战之耻甚于败,故讳战,不讳败。②.
李光地指出,《春秋》在记录周天子参加的战争时,避讳书战,而不避讳书败。因为按照礼法的规定,诸侯是不应该与天子发生战争的。若周天子与诸侯之间发生战争,即便周天子获胜,亦是一种极大的耻辱,且战争本身的耻辱超过战败的耻辱,所以周讳战,不讳败。
其三曰:
公及诸侯之大夫盟,诸侯之大夫来盟,皆不书公,亦讳也,非其班也。以此类之,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不著其所与盟者,亦为诸侯讳尔。谓嘉屈完之慕义,美桓公之用礼,盖取孟氏所谓“彼善于此”者,君子则于是乎见蛮荆大邦之抗,管子功烈之卑也。③
高子来盟,楚屈完来盟,旧说未是。圣人妙尽人情,都是内本国而外他国,内中国而外四裔之意。大凡鲁君与诸国之大夫盟,皆不书公,惟书及某盟而已,不肯以我君与诸大夫等也。鲁有难而齐轻之,故使高子来。桓公率众诸侯以临江、汉,倾天下之力,兴问罪之师,而楚子不亲出,仅遣屈完来,皆可耻者。故不著其君使之来,若彼国无君而其臣擅来者,非吾之辱也。独成公于楚师之临,孟献子、季文子不敢出,公自出与公子婴齐盟。书公者,所以著季、孟主忧、主辱之罪。①
李光地指出,鲁国国君与他国大夫会盟,或他国大夫来鲁国会盟,《春秋》皆不书“公”,以示避讳。这是因为二者的身份地位并不对等,如此会盟有悖于礼法。不单是鲁国国君,有时其他诸侯遇到类似情况,《春秋》亦为其避讳,以示“内本国而外他国,内中国而外四裔之意”。同时,他国国君派大夫前来与我国国君会盟,对我国来说亦是一种耻辱,故《春秋》于此往往不书“使”。因为书“使”意味着这些大臣的出访得到了天子或国君的正式命令,而不书“使”则表示他国无君而其臣擅来,因而不是我国的耻辱。譬如,闵公二年,齐桓公派大夫高傒来鲁国会盟,《春秋》书:“冬,齐高子来盟”,既不书“公”,亦未书“使”。又如,僖公四年,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的军队侵伐蔡国,胜利后又进攻楚国,楚成王派大夫屈完来召陵的诸侯军中会盟。《春秋》书:“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同样不书“公”,亦不书“使”。唯有成公二年,楚国进攻鲁国,鲁成公亲自到蜀地与楚国公子婴齐会盟,《春秋》书:“十有一月,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楚国进攻鲁国时,鲁国大夫孟献子、季文子不敢挺身而出,致使鲁成公不得不亲自出面与公子婴齐会盟,所以《春秋》据实直书“公”,以示孟献子与季文子辱及君父之罪。
其四曰:
内于外诸侯不言朝,尊内也,聘无不可言者。内大夫于他邦亦不言聘,何也?曰:“鲁于大国,有比年而聘,有年而屡聘,而于天子略矣。故书‘聘’则恶显,书‘如’则词微。以聘行乎,以事行乎,悉以‘如’书之。”①
李光地认为,《春秋》于鲁国大夫奉命访问他国之事书“如”而不书“聘”亦是为了避讳。因为鲁国极少朝见周天子,却对其他大国聘问频繁,显然有悖礼法。在这种情况下,若直书“聘”则突显了鲁国国君的罪恶,若与因他事赴外国一般书“如”,则较为隐晦,可遮掩其罪。
最后,李光地指出,《春秋》中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书法与义例,但并不意味着每次碰到相同的情况都必然会使用同样的书法或义例。因为孔子既要借助各种书法、义例来突显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是非善恶,使读者知所鉴戒,又必须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如实地记录、保存史实,所以《春秋》往往首先以一个或若干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作为典型,来表明一定的“义”,然后对于其他同类的人物或事件则按照常规或现状直书,而不使用特殊的笔法。而这亦成为《春秋》中的一条基本义例,所谓“义既明则存其实,盖一经之通例也”②。故曰:
《春秋》义明则从实。如弑君者之绝其属也,义既明矣,则公子之,世子之。五等之讣也,从周室之班,义既明矣,于其葬也,则公之,夫非先谨而后纵也。不明其义于先,是逆僭终无惩也;不存其实于后,是逆僭之迹不著。故前为断,而后为案也。③
隐无正者,二年以后无正月也;桓无王者,十八年之中,十四年不书王也。正者,诸侯所禀于王;王者,正诸侯者也。下不禀则无正,上不正则无王。桓弑其君,王不讨焉,而生死恩逮,是之谓不正而无王;隐终其位,王命四至,而朝聘奔会无一者,是之谓不禀而无正。然则他君异于此欤?曰:一经之始,于二君见义焉耳。《春秋》书法,见义者,义明则止,其余以常书。①在此,为了更详细地说明“义既明则存其实”这一通例,李光地列举了《春秋》中的一些具体表现与事例。譬如,对于弑君者,《春秋》先削其官爵,绝其为君之臣属,以明其义,而后又书其官爵,以存其弑君之实证。又如,对于去世的诸侯,《春秋》先书其本爵,以明其义,而后又从其僭号,以存其僭越之实证。同样,《春秋》记载隐公一朝的历史,元年之后便不书“正月”,记载桓公一朝的历史,十八年中有十四年不书“王”,这是对于隐公终身未朝聘于周天子,以及桓公弑君,而王不加讨,反而恩命累加的谴责与批判。可是这样的问题并非只发生在隐公与桓公二人身上,但除了隐公与桓公外,《春秋》并未在记载鲁国其他朝代历史的时候使用同样的书法。李光地认为,这是因为隐、桓二公是《春秋》一书里最初的两位国君,故将其作为典型,以申明《春秋》大义。义明则止,故其余部分皆照常书写。而这也再次印证了李光地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诸经多将首二篇包括全书之义。……《春秋》隐、桓二公,亦尽一部《春秋》道理。隐无王,桓无天。无王者,隐公终身未尝朝聘于周,直似非其臣子者然。无天者,桓公弑君,王不加讨,又从而恩命稠叠焉。惟此二义,一部《春秋》,岂复外此。”②
类似地,隐公元年,周天子派遣宰咺到鲁国馈赠惠公与仲子的助葬物品,《春秋》书:“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冒。”桓公八年,周天子派遣家父到鲁国来聘问,《春秋》书:“天王使家父来聘。”庄公元年,周天子派遣荣叔到鲁国赏赐、追命桓公,《春秋》书:“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文公五年,周天子派遣荣叔到鲁国馈赠助葬物品,后鲁国为庄公夫人成风举行葬礼,周天子又派遣召伯到鲁国参加葬礼,《春秋》书:“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王使召伯来会葬。”李光地指出,隐公元年“赗仲子”与文公五年“会成风”两事类似,桓公八年“聘桓公”与庄公元年“锡桓公命”两事亦类似,但“皆名冢宰于前,王不称天于后”,这并非两事在性质或“义”上有什么不同,而是《春秋》“事同则举重,义明则以常书之法也”。①
综上可见,李光地虽不否认《春秋》中寓有孔子的褒贬之意,但他显然更注重从内外之别、君臣之义等礼法制度与伦理规范的角度来看待、归纳、发明和阐释《春秋》中的各种书法与义例。概括起来,其与朱熹所理解的“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春秋》大义内容大体一致,既体现了李光地的朱子学立场,亦从侧面反映出李光地与朱熹在《春秋》义例问题上的异中之同。至于发明《春秋》义例的具体方法,李光地则特别强调“属辞比事”的重要性。关于属辞比事,李光地解释道:“《春秋》之教,所谓‘比事’者,以同类之事相例也;所谓‘属辞’者,考其上下文以见意也。”②换言之,比事就是将同类事物进行比较,属辞就是通过考察上下文来理解经意。李光地指出,属辞比事“此最要紧。岂止《春秋》,凡经书皆然。同中之异,异中之同,不是相比,则道理不能见得确实。况比事属词,《春秋》之教乎?圣人文章,随处不同。褒与贬不同矣,贬之中亦自不同。有贬至十分者,有九分几厘者”③。在他看来,《春秋》中的义例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书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圣人的微言大义有时就蕴含于极其微小的文字差别中,若不通过属辞比事的方法,就不可能准确、完整地把握《春秋》书法与圣贤义理。李光地之所以如此重视《春秋》的书法、义例,一方面固然是受到清初传统经典与经学研究复兴的影响,另一方面恐怕亦是由于清初政局与社会的动荡不安,故希望通过对《春秋》书法、义例中蕴含的君臣之义与礼法制度的关注、阐发与提倡来实现其稳定、重塑清初政治、社会、伦理秩序的目的,推动国家由乱而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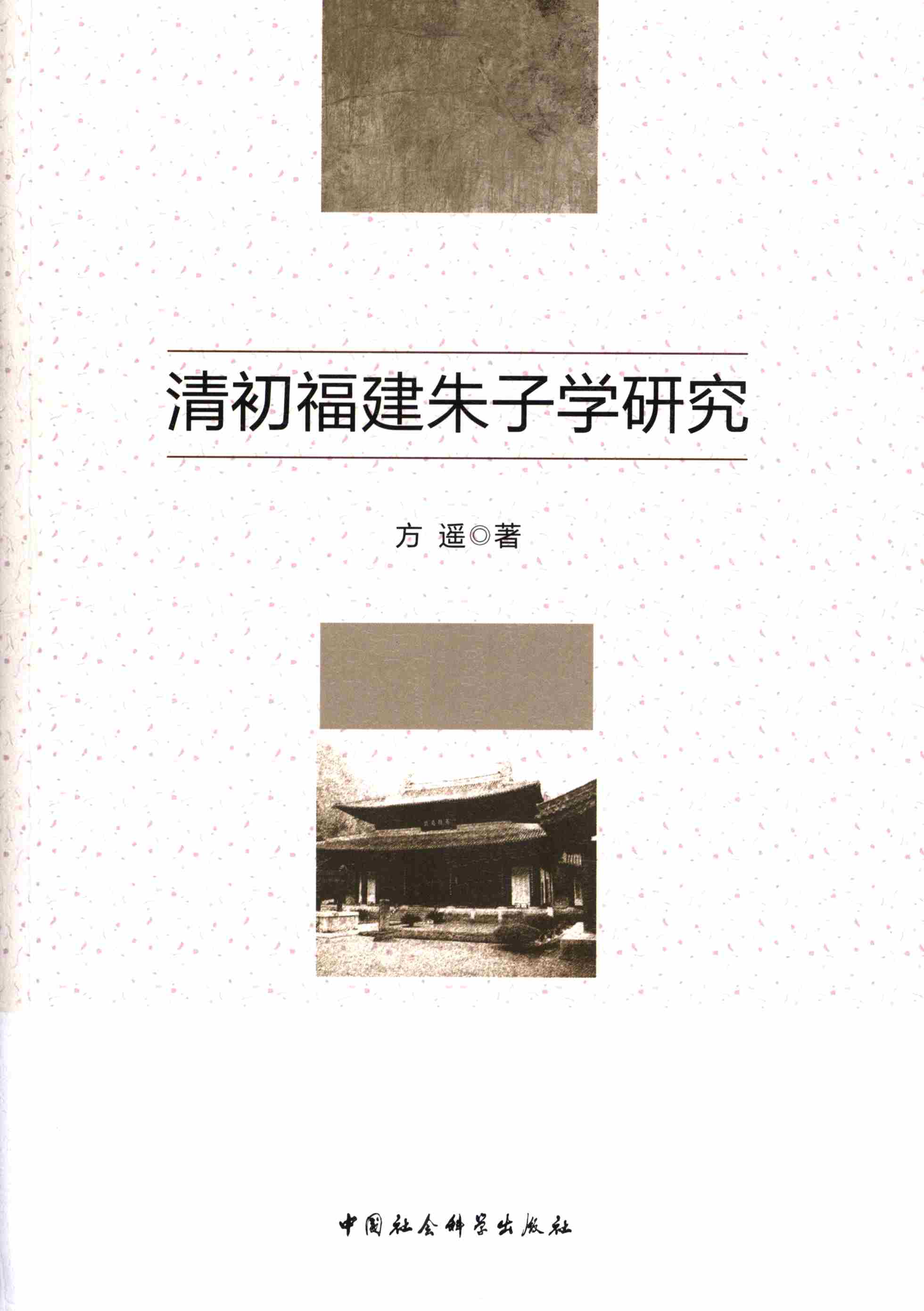
《清初福建朱子学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视角,将清初福建朱子学与王学、经学、实学等清初学术思想界中具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或思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注重探讨清初福建朱子学者的义理思想,也对其义理思想之外的其他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理论及实践活动予以关注,在回顾、发掘朱熹本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把握了清初福建朱子学的思想特点、时代特征与整体面貌,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初朱子学在时代学术思潮变迁中发挥的作用。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