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问学”“尊德性”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80 |
| 颗粒名称: | 一、“道问学”“尊德性”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6 |
| 页码: | 122-126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朱熹和戴震两位学者在学术思想上的差异和传承关系。朱熹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对后世影响深远。戴震作为清代学者,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
| 关键词: | 朱熹 戴震 宋学 |
内容
朱熹是继孔子之后对传统中国社会后期影响至为深远的圣贤人物,位列孔庙十二哲之次,成为中国学统和道统系列中的重要代表。同时在民间社会层面上,朱子通过著述和讲学乃至门生弟子的代代传承,渐次形成一个能够延续思想学说的重要流派,以《朱子小学》和《家礼》等理学教义,躬行践履于族规民约和世道人心之中,对基层社会尤其是明清徽州地区的风土民情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至清代,随着汉宋学术之争的显著化,程朱之学遭到了江浙皖地区学者如陈确、毛奇龄等人的猛烈攻击。其中,朱熹乡邦的“新安理学”地区,也同时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尤以黄生、姚际恒和戴震最为突出。因戴震与朱熹同出于徽州,既有乡邦之谊,且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最高峰,所以两者之间学术思想的差异,以及后生对乡贤的严词评判,定会受到今世学者更多地关注与评价。评议之辞既关乎学理上的是非之争,也兼有情分上的好恶之偏。遗憾的是,人们只乐观其间之“异”,而容易忽略其间之“同”,也就遮蔽了戴氏继承和发展朱熹治学方法及学术思想的内在承续性。
朱熹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同时在经学、小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也做出过重要贡献,惜其一生被理学盛名所掩,论者大多注目其性命道体之说,而没其躬行实践的格物朴实之学。事实上,他治学领域广博,天文地理、河渠农桑、草木鸟兽、律吕术数,无不触类旁通,源流毕贯,不仅能通古训经典之义,达孔孟周程之道,甚至还能够根据高山上的螺蚌化石,考证出海陆变迁和地壳演化的科技知识和道理,可见其“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治学目的。自谓:“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可见朱子首先是第一流的学问家,其次才是理学家。他读书善据古籍以补正讹脱,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如其《古文尚书》辨伪、《诗序》发疑,皆究其微旨,通其大例,本证旁证,奄若合符;而《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系列训诂集释之作,则稽览群籍,是正讹舛,捃摭稽核,至为精博。朱子曾自述学问大概曰:“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陆)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朱)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又曰:“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可见其学即有义理之思,又兼训诂之学,故章学诚称之为:“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章氏《朱陆》及《书朱陆篇后》两文,曾将朱子学术与戴震的传承,探赜索隐,条分缕析,影响很大。胡适也因其言对乡贤朱子的考证之学颇有赞词,认为清代三百年的学者,尤其是乾嘉汉学之“皖派”学者,实际上是继承了朱熹治学的方法,东原学术乃朱子学之后继也。其后,傅斯年与钱穆也称:“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衍之宋学。”“徽学渊源实本紫阳而不可诬。”此等中肯独到之语,说明了民国期间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学术实际上是扩大而延伸了的宋明理学,清儒也为探求圣贤义理而终生孜孜矻矻,虽时代有别,取径不同,却可谓殊途同归。
朱子与戴震所追求的同是孔孟之道,所取路径也大略相同:东原“以词通道”“实事求是”,便是朱子“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之法,朱子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读书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学者之不可不知也。”此乃正为戴氏“以词通道”路径的直接来源。东原以乡贤为榜样,秉承朱子之学,一生专意于学问,治学主张由“格物”到“穷理”,即“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空所依傍”标示其治学的显著态度,即对前贤时彦,皆以正心诚意待之,“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不作偏激之言。常云:“仆以为考古宜心平,凡论一事,勿以人之见蔽我,勿以我之见自蔽。”他以汉学继理学,而以求“道”为根本。常云:“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其“非与后儒竞立说”的原则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也不依傍昔儒以附骥尾,君子务在闻道也。如此不偏宋、不佞汉的观点,被胡适和梁启超等赞誉为最能表现科学研究的特点,体现近代思想解放之精神。
有学者认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出版,决定其反对程朱理学的根本基调,表明了朱熹与戴震之间是对立关系。仅从文字表面上看起来似有道理,但章太炎深刻地指出:“清宪帝亦利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睢……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䀌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章氏所言应是戴氏本意所在,他深知在文字狱的时代,个人著作的面世务必用语隐讳,知所避忌;从学理层面上说,“借古讽今”应该是通过批判程朱理学以达到针砭现实目的最为恰切的处理手段。戴震的真实话语表达,可以从他寄给段玉裁书信中的自然用语窥见一斑,知其心曲。曰:“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以个人书信与正规著作相比较,是最能真实表露作者内心意图的文字实录,此中“今人”绝对不会是指程朱,定是那些“理”字不离于口、害人不轻手的在位者和当权派;而《疏证》中的“理”字在书信中都被替换成“意见”二字,其中深意,不言自明。因此,与其说《孟子字义疏证》的内容是批判程朱理学,毋宁说是借批判理学之名而抨击强权势利者的“以理杀人”。戴震对于程朱学术与理学末流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疏证》一书乃是借用“洛闽之言”作为靶子,来抨击朝廷以“理”学为幌子残害民众,即“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的事实。胡适曾言:章学诚常骂戴氏,但他实在是戴学的第一知己。我们由此也可以说,戴东原痛斥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但他实在是程朱的第一知己。
其次,《疏证》一书在写作形式上也深受《朱子语类》的问答辩驳式影响,更是模仿了朱熹弟子陈淳《北溪字义》的词典释义方法,将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和范畴以字义训诂的形式构建起来。陈氏书列出命、性、心、情、仁义礼智信、道、理、诚、经权等26门,荟萃宋五子之说,而以朱子说为折中;戴氏书以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为目,列为44条,认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因此,陈、戴两书之间的传承关系也昭然若揭。这些问题早在东原去世之当时,洪榜即明确指出《疏证》“非言性命之旨也,训诂而已矣,度数而已矣”,即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只是责难程朱之书,而应理解为戴氏为了剔除附着在程朱理学上的异端成分,通过文字考证和经典诠释的手段为程朱做辩护和澄清。洪氏云:“戴氏《与彭进士书》,非难程朱也,正陆王之失耳;非正陆王也,辟老释之邪说耳;非辟老释也,辟夫后之学者实为老释而阳为儒书;援周孔之言,入老释之教;以老释之似,乱周孔之真,而皆附于程朱之学。”“戴氏之书,非故为异同,非缘隙嚷嘲,非欲夺彼与此,昭昭甚明矣。”洪榜一生服膺东原,为戴氏学说而上下游说,论定戴震的“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故江藩作《汉学师承记》特为表彰洪氏,全载此文以为援引,致使后世不至于泯灭戴学“义理”层面的功劳。梁启超指出:洪氏“这几句话批评得对极了,试拿毛西河攻击程朱的书,陆稼书攻击陆王的书,和东原各书相对照,便可以见出东原的态度确是‘学者的’了”。“东原并没有攻击别派的行为,不过将这派那派研究出他们的真相,理清楚他们的系统,叫他们彼此不相蒙混,这种工作,无论对于某种学问,在批评家或历史家是最必要的。我们认东原为最忠实于这种工作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正人心之要”的《疏证》一书,用“以词通道”的方法探明“治乱之源”,悟得“圣人之道”,正是秉承了朱子由“道问学”而至“尊德性”的路径而来,也正印证了冯友兰所言:“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
至清代,随着汉宋学术之争的显著化,程朱之学遭到了江浙皖地区学者如陈确、毛奇龄等人的猛烈攻击。其中,朱熹乡邦的“新安理学”地区,也同时出现了异样的声音,尤以黄生、姚际恒和戴震最为突出。因戴震与朱熹同出于徽州,既有乡邦之谊,且为各自时代的学术最高峰,所以两者之间学术思想的差异,以及后生对乡贤的严词评判,定会受到今世学者更多地关注与评价。评议之辞既关乎学理上的是非之争,也兼有情分上的好恶之偏。遗憾的是,人们只乐观其间之“异”,而容易忽略其间之“同”,也就遮蔽了戴氏继承和发展朱熹治学方法及学术思想的内在承续性。
朱熹不仅是一位划时代的理学家,同时在经学、小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也做出过重要贡献,惜其一生被理学盛名所掩,论者大多注目其性命道体之说,而没其躬行实践的格物朴实之学。事实上,他治学领域广博,天文地理、河渠农桑、草木鸟兽、律吕术数,无不触类旁通,源流毕贯,不仅能通古训经典之义,达孔孟周程之道,甚至还能够根据高山上的螺蚌化石,考证出海陆变迁和地壳演化的科技知识和道理,可见其“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治学目的。自谓:“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也。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笃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属也。”可见朱子首先是第一流的学问家,其次才是理学家。他读书善据古籍以补正讹脱,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如其《古文尚书》辨伪、《诗序》发疑,皆究其微旨,通其大例,本证旁证,奄若合符;而《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系列训诂集释之作,则稽览群籍,是正讹舛,捃摭稽核,至为精博。朱子曾自述学问大概曰:“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陆)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朱)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上多了。”又曰:“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可见其学即有义理之思,又兼训诂之学,故章学诚称之为:“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章氏《朱陆》及《书朱陆篇后》两文,曾将朱子学术与戴震的传承,探赜索隐,条分缕析,影响很大。胡适也因其言对乡贤朱子的考证之学颇有赞词,认为清代三百年的学者,尤其是乾嘉汉学之“皖派”学者,实际上是继承了朱熹治学的方法,东原学术乃朱子学之后继也。其后,傅斯年与钱穆也称:“自今日观之,清代所谓宋学,实是明代之官学;而所谓汉学,大体上直是自紫阳至深宁一脉相衍之宋学。”“徽学渊源实本紫阳而不可诬。”此等中肯独到之语,说明了民国期间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学术实际上是扩大而延伸了的宋明理学,清儒也为探求圣贤义理而终生孜孜矻矻,虽时代有别,取径不同,却可谓殊途同归。
朱子与戴震所追求的同是孔孟之道,所取路径也大略相同:东原“以词通道”“实事求是”,便是朱子“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之法,朱子云:“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读书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学者之不可不知也。”此乃正为戴氏“以词通道”路径的直接来源。东原以乡贤为榜样,秉承朱子之学,一生专意于学问,治学主张由“格物”到“穷理”,即“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空所依傍”标示其治学的显著态度,即对前贤时彦,皆以正心诚意待之,“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不作偏激之言。常云:“仆以为考古宜心平,凡论一事,勿以人之见蔽我,勿以我之见自蔽。”他以汉学继理学,而以求“道”为根本。常云:“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其“非与后儒竞立说”的原则是: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也不依傍昔儒以附骥尾,君子务在闻道也。如此不偏宋、不佞汉的观点,被胡适和梁启超等赞誉为最能表现科学研究的特点,体现近代思想解放之精神。
有学者认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一书的出版,决定其反对程朱理学的根本基调,表明了朱熹与戴震之间是对立关系。仅从文字表面上看起来似有道理,但章太炎深刻地指出:“清宪帝亦利洛闽,刑爵无常,益以恣睢……戴震生雍正末,见其诏令谪人不以法律,顾摭取洛闽儒言以相稽,觇司隐微,罪及燕语。九服非不宽也,而迾之以丛棘,令士民摇手触禁,其䀌伤深。震自幼为贾贩,转运千里,复具知民生隐曲,而上无一言之惠,故发愤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专务平恕,为臣民诉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章氏所言应是戴氏本意所在,他深知在文字狱的时代,个人著作的面世务必用语隐讳,知所避忌;从学理层面上说,“借古讽今”应该是通过批判程朱理学以达到针砭现实目的最为恰切的处理手段。戴震的真实话语表达,可以从他寄给段玉裁书信中的自然用语窥见一斑,知其心曲。曰:“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以个人书信与正规著作相比较,是最能真实表露作者内心意图的文字实录,此中“今人”绝对不会是指程朱,定是那些“理”字不离于口、害人不轻手的在位者和当权派;而《疏证》中的“理”字在书信中都被替换成“意见”二字,其中深意,不言自明。因此,与其说《孟子字义疏证》的内容是批判程朱理学,毋宁说是借批判理学之名而抨击强权势利者的“以理杀人”。戴震对于程朱学术与理学末流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疏证》一书乃是借用“洛闽之言”作为靶子,来抨击朝廷以“理”学为幌子残害民众,即“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的事实。胡适曾言:章学诚常骂戴氏,但他实在是戴学的第一知己。我们由此也可以说,戴东原痛斥程朱理学“以理杀人”,但他实在是程朱的第一知己。
其次,《疏证》一书在写作形式上也深受《朱子语类》的问答辩驳式影响,更是模仿了朱熹弟子陈淳《北溪字义》的词典释义方法,将理学思想体系中的几个重要概念和范畴以字义训诂的形式构建起来。陈氏书列出命、性、心、情、仁义礼智信、道、理、诚、经权等26门,荟萃宋五子之说,而以朱子说为折中;戴氏书以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为目,列为44条,认为“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因此,陈、戴两书之间的传承关系也昭然若揭。这些问题早在东原去世之当时,洪榜即明确指出《疏证》“非言性命之旨也,训诂而已矣,度数而已矣”,即不能简单地认为仅仅只是责难程朱之书,而应理解为戴氏为了剔除附着在程朱理学上的异端成分,通过文字考证和经典诠释的手段为程朱做辩护和澄清。洪氏云:“戴氏《与彭进士书》,非难程朱也,正陆王之失耳;非正陆王也,辟老释之邪说耳;非辟老释也,辟夫后之学者实为老释而阳为儒书;援周孔之言,入老释之教;以老释之似,乱周孔之真,而皆附于程朱之学。”“戴氏之书,非故为异同,非缘隙嚷嘲,非欲夺彼与此,昭昭甚明矣。”洪榜一生服膺东原,为戴氏学说而上下游说,论定戴震的“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故江藩作《汉学师承记》特为表彰洪氏,全载此文以为援引,致使后世不至于泯灭戴学“义理”层面的功劳。梁启超指出:洪氏“这几句话批评得对极了,试拿毛西河攻击程朱的书,陆稼书攻击陆王的书,和东原各书相对照,便可以见出东原的态度确是‘学者的’了”。“东原并没有攻击别派的行为,不过将这派那派研究出他们的真相,理清楚他们的系统,叫他们彼此不相蒙混,这种工作,无论对于某种学问,在批评家或历史家是最必要的。我们认东原为最忠实于这种工作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部“正人心之要”的《疏证》一书,用“以词通道”的方法探明“治乱之源”,悟得“圣人之道”,正是秉承了朱子由“道问学”而至“尊德性”的路径而来,也正印证了冯友兰所言:“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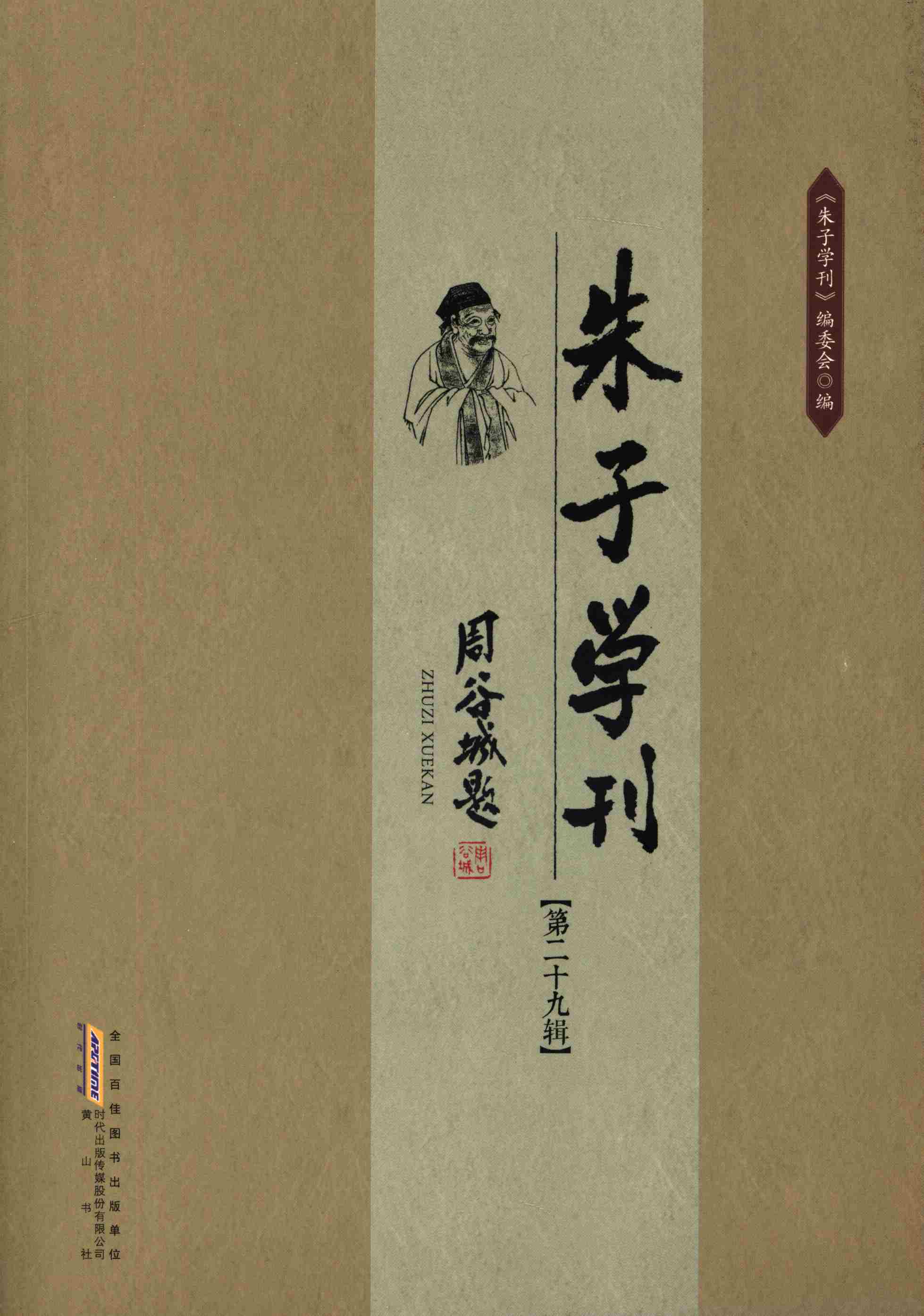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徐道彬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