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纠偏与发展:《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的直接原因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55 |
| 颗粒名称: | 三、纠偏与发展:《仪礼经传通解》编撰的直接原因 |
| 分类号: | B244.7-55 |
| 页数: | 6 |
| 页码: | 056-061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朱熹在编撰《通解》时所面临的学术思想与历史环境问题。朱熹在讲学中强调《仪礼》的重要性,并对王安石废除《仪礼》的科举制度提出批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司马光执政时期《仪礼》仍未受到重视。尽管朱熹极力主张礼学的重要性,但南宋时期重视义理之学的社会思潮已经形成洪流,导致礼学衰落。 |
| 关键词: | 编撰缘由 下学上达 切问近思 |
内容
前文已言下学上达与切问近思的研究方式是朱子编撰《通解》的内在动力和学术根源,但是学术思想落实到具体行为仍需要有历史因素的推波助澜。朱子编撰《通解》一书的行动便是朱子在学术思想基础上受历史环境影响而产生纠偏历史思潮的具体结果。
《通解》的编撰是处于王安石科举改革后的时代,正如朱子所言:
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
朱子在讲学时亦念念不忘责备王安石废除《仪礼》之学,他说:“‘《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曰:‘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究。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诚然朱子所言的废《仪礼》而独存《礼记》的科举制度为《仪礼》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但是把《仪礼》传播不广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科举政策则有失公平,因为王安石执政期间不过从熙宁元年到熙宁九年,而司马光执政时期更是全部废除王安石执政期间的政治措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司马光执政的元祐四年的选举制度与王安石期间已经有了明显差异,但是《仪礼》依旧流传不广。《宋史·选举志》载: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
此文献所载内容发生的时间为元祐四年,宋神宗、王安石均已经离世,而此次科举考试正是在司马光全面主持朝局的情况下实行的政策,《仪礼》在诸经当中处于中经的地位,仍旧比《礼记》低一等。与熙宁时期完全相反的各项政策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有更多的科举政策,如:“(元祐)六年,诏复通礼科。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而这在宋哲宗亲政之后的绍圣四年,其举措不但没有废除礼学在经学中的地位,反而加强其经学地位,并于科举中大力扶持,《宋史·选举志一》载:
四年,诏礼部,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藉,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期半及他经。继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罢之。
这是哲宗在绍圣四年所进行的选举改革,我们于此“二《礼》”,实难确证其为哪二《礼》,但是据宋哲宗亲政后以恢复神宗时期的政策为主基调而言,此“二《礼》”当指宋神宗时期保留的《周礼》与《礼记》二经。至于历史真实情况,因材料不足,暂时付之阙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还是以继承宋神宗改革意志的宋哲宗,他们都十分重视礼学,尤其是宋哲宗更是把礼经的科举录取名额占到总的录取名额的一半之多。虽然统治者大力提倡礼学,但事与愿违,无论是《礼记》《周礼》、通礼科均与《仪礼》一样被置于冷门的经学地位,朱子曾直言此种情况:
祖宗时有开宝通礼科,学究试默义,须是念得礼熟,是得礼官用此等人为之。介甫一切罢去,尽令做大义。故今之礼官,不问是甚人皆可做。某尝谓,朝廷须留此等专科,如史科亦尝有。
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认为此处是朱子专门针对王安石废罢《仪礼》后对南宋礼学产生的重要影响,明显为《朱子语类》所惑。前文已言,在宋神宗、王安石均已过世之后,司马光在元祐四年恢复了《仪礼》的经学地位,而《宋史》明言元祐六年恢复被王安石废罢的通礼一科。由此可见,朱子把宋代的礼学思潮发展方向归咎为王安石一人,明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朱子对礼学的学术思潮的概括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即当时学术思潮是“尽令做大义”,而礼学人才凋零的情况甚至达到主管礼仪官员都对礼学十分陌生,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的士人了。
虽然朱子极力把礼学的衰落归因于王安石,但是重视义理之学的社会思潮已经形成洪流,其本人也难以避免。我们以《朱子年谱》为检索对象,发现朱子本人的礼学作品只有早年的《祭仪》《家礼》,直到晚年庆元党禁时期才带领众多弟子着手编撰《通解》。其在礼学上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与其在四书学所作的工作,不可同日而语。检索《朱子语类》中涉及四书学的内容与礼学内容的卷数与篇幅便可证实上述内容了。如果以上还只是旁证,那么朱子生平对礼学的熟悉程度则可以直接证实朱子在礼学方面所花时间与精力的有限程度了。
绍熙五年(1194)秋,光宗内禅,宁宗即位,召朱熹赴行在。冬十月,朱熹奏乞讨论嫡孙承重之服。朱熹《乞讨论丧服劄子》一文有明确的阐述,但缺少明确的经文依据,朱熹此次上书以失败告终,后来在郑玄注找到文献依据。“这件事使朱熹深受震动,义理要想说服人,在国家礼制层面上的讨论还必须寻找经典依据”。虽然三礼之学规模庞大,且朱子时代三礼的注、疏本尚未合刊,对朱子研读三礼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正如前文所言,朱子治学是下学上达、切问近思的途径,其没有透彻研究礼学经典注疏,直接证实了朱子在礼学文献方面所花时间与精力不足的问题。假如朱子在研读礼学文献方面所花时间和精力足够多,当不会出现礼学文献不熟的问题。不论是朱子所花时间、精力还是注重礼学的义理的研讨,都显示了朱子对礼学文献的疏忽的情况。这绝非我们对朱子学术的吹毛求疵,因为朱子在平时讲学中不只一次强调学古礼,当求其内在的义理,并加以合符实际的应用。《朱子语类》载:
杨通老问《礼书》。曰:“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各各有义理。然又须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见得度数文为之末,如此岂能识得深意?如将一碗干硬底饭来吃,有甚滋味?若白地将自家所见揣摸他本来意思不如此,也不济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会这个,下稍溺於器数,一齐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尽晓其意,且要识得大纲。”
此条为叶贺孙辛亥(1191)以后所闻。除此之外,叶贺孙于同卷中尚录有多条相似内容的语录,当为可信。朱子在此主要强调学者要从礼书中看出古人的意思,而不是“度数文为之末”,换言之,朱子追求的是理解礼书的内在礼义,而非限于礼仪方面,更非“溺于器数”,事实上,朱子与宋代其他注重《礼记》的学者并没有根本区别,都是注重其内在学理。仅是朱子治学方法比其他宋儒更为严谨的强调学习者需要在学习礼书内在义理过程中,把握具体礼仪“大纲”,至于何为大纲则由行礼者根据自身工夫而定夺,可见朱子偏向于礼学的义理方面,则可确定了。至于具体礼仪内容,朱子则持可以损减的观点。《朱子语类》载:
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
朱子所举例子为衣服观履不必如古,但是何者为大纲,何者为细节,而对礼学内容的减杀的标准为什么?朱子都未曾系统论述,亦与当时重视《礼记》的学者无本质的差别。
朱子生平著作等身,难以面面俱到,亦属正常。但是在四书学中,我们难以看到上述如此大的失误,亦显示出朱子对四书学重视程度远非礼学可比。甚至到了晚年,朱子对礼学典籍的整理难度或者重视程度仍旧缺少清晰的认识。他说:
古人自幼入小学,便教以礼;及长,自然在规矩之中。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礼,也易学。今人乍见,往往以为难。某尝要取《三礼》编成一书,事多蹉过。若有朋友,只两年工夫可成。
此条为邵浩丙午(1186)所闻录。朱子此时尚未充分认识礼书修撰的难度,这便导致《通解》一书最终只能以未完稿而嘱托于后学,其原因虽有多种,但是最为重要的当属朱子本人的学术兴趣更倾向于注重义理之学。
通过以上的略显烦琐的考论证实了:从北宋开始,学者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义理的研究方面,朱子亦是随时代大潮而发展。但是正是前文所言朱子本人的治学的方法论特质,才逐步把朱子的学术关注点引入到《通解》的编撰方面。朱子是宋学的典型代表,具有宋学的各种特征,但是其在深入学习宋学的基础上,通过归因于王安石罢废《仪礼》之学及自身的深刻反思纠正了宋代学者注重《礼记》之学,而罢废《仪礼》学的学术思潮,重新重视《仪礼》学,并以《仪礼》为主体内容,采编源自各种典籍的礼学资料,补充《仪礼》所缺之资料,重新构建礼仪与礼义并重的礼学资料体系,虽有逆时代学术思潮而动且有未完成编撰工作之遗憾,但是纠正宋学的弊端,发展宋学的优秀成果的目的却呈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推动《通解》的编撰工作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而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通解》是朱子在下学上达、切问近思的学术思想指导下,逐渐克服宋学空疏的弊端,实现由宋代理学走向传统经学之路,并在纠正宋代礼学弊端,发展宋代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编撰《通解》,开创了后世编撰礼书的新典范。
《通解》的编撰是处于王安石科举改革后的时代,正如朱子所言:
熙宁以来,王安石变乱旧制,废罢《仪礼》,而独存《礼记》之科,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其失已甚。
朱子在讲学时亦念念不忘责备王安石废除《仪礼》之学,他说:“‘《礼》非全书,而《礼记》尤杂。今合取《仪礼》为正,然后取《礼记》诸书之说,以类相从,更取诸儒剖击之说各附其下,庶便搜阅。’又曰:‘前此《三礼》同为一经,故有《三礼》学究。王介甫废了《仪礼》,取《礼记》,某以此知其无识。’”诚然朱子所言的废《仪礼》而独存《礼记》的科举制度为《仪礼》被遗忘的重要原因,但是把《仪礼》传播不广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科举政策则有失公平,因为王安石执政期间不过从熙宁元年到熙宁九年,而司马光执政时期更是全部废除王安石执政期间的政治措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司马光执政的元祐四年的选举制度与王安石期间已经有了明显差异,但是《仪礼》依旧流传不广。《宋史·选举志》载:
四年,乃立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内听习一经。初试本经义二道,《语》《孟》义各一道,次试赋及律诗各一首,次论一首,末试子、史、时务策二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易》《公羊》《穀梁》《仪礼》为中经,《左氏春秋》得兼《公羊》《穀梁》《书》《周礼》得兼《仪礼》或《易》,《礼记》《诗》并兼《书》,愿习二大经者听,不得偏占两中经。
此文献所载内容发生的时间为元祐四年,宋神宗、王安石均已经离世,而此次科举考试正是在司马光全面主持朝局的情况下实行的政策,《仪礼》在诸经当中处于中经的地位,仍旧比《礼记》低一等。与熙宁时期完全相反的各项政策并不仅仅局限于此,而是有更多的科举政策,如:“(元祐)六年,诏复通礼科。初,开宝中,改乡贡《开元礼》为《通礼》,熙宁尝罢,至是始复。”而这在宋哲宗亲政之后的绍圣四年,其举措不但没有废除礼学在经学中的地位,反而加强其经学地位,并于科举中大力扶持,《宋史·选举志一》载:
四年,诏礼部,凡内外试题悉集以为藉,遇试,颁付考官,以防复出。罢《春秋》科,凡试,优取二《礼》,两经许占全额之半,而以期半及他经。继而复立《春秋》博士,崇宁罢之。
这是哲宗在绍圣四年所进行的选举改革,我们于此“二《礼》”,实难确证其为哪二《礼》,但是据宋哲宗亲政后以恢复神宗时期的政策为主基调而言,此“二《礼》”当指宋神宗时期保留的《周礼》与《礼记》二经。至于历史真实情况,因材料不足,暂时付之阙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还是以继承宋神宗改革意志的宋哲宗,他们都十分重视礼学,尤其是宋哲宗更是把礼经的科举录取名额占到总的录取名额的一半之多。虽然统治者大力提倡礼学,但事与愿违,无论是《礼记》《周礼》、通礼科均与《仪礼》一样被置于冷门的经学地位,朱子曾直言此种情况:
祖宗时有开宝通礼科,学究试默义,须是念得礼熟,是得礼官用此等人为之。介甫一切罢去,尽令做大义。故今之礼官,不问是甚人皆可做。某尝谓,朝廷须留此等专科,如史科亦尝有。
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认为此处是朱子专门针对王安石废罢《仪礼》后对南宋礼学产生的重要影响,明显为《朱子语类》所惑。前文已言,在宋神宗、王安石均已过世之后,司马光在元祐四年恢复了《仪礼》的经学地位,而《宋史》明言元祐六年恢复被王安石废罢的通礼一科。由此可见,朱子把宋代的礼学思潮发展方向归咎为王安石一人,明显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朱子对礼学的学术思潮的概括则基本符合历史事实,即当时学术思潮是“尽令做大义”,而礼学人才凋零的情况甚至达到主管礼仪官员都对礼学十分陌生,更不用说其他普通的士人了。
虽然朱子极力把礼学的衰落归因于王安石,但是重视义理之学的社会思潮已经形成洪流,其本人也难以避免。我们以《朱子年谱》为检索对象,发现朱子本人的礼学作品只有早年的《祭仪》《家礼》,直到晚年庆元党禁时期才带领众多弟子着手编撰《通解》。其在礼学上花费的精力和时间与其在四书学所作的工作,不可同日而语。检索《朱子语类》中涉及四书学的内容与礼学内容的卷数与篇幅便可证实上述内容了。如果以上还只是旁证,那么朱子生平对礼学的熟悉程度则可以直接证实朱子在礼学方面所花时间与精力的有限程度了。
绍熙五年(1194)秋,光宗内禅,宁宗即位,召朱熹赴行在。冬十月,朱熹奏乞讨论嫡孙承重之服。朱熹《乞讨论丧服劄子》一文有明确的阐述,但缺少明确的经文依据,朱熹此次上书以失败告终,后来在郑玄注找到文献依据。“这件事使朱熹深受震动,义理要想说服人,在国家礼制层面上的讨论还必须寻找经典依据”。虽然三礼之学规模庞大,且朱子时代三礼的注、疏本尚未合刊,对朱子研读三礼增加了很大的难度,但正如前文所言,朱子治学是下学上达、切问近思的途径,其没有透彻研究礼学经典注疏,直接证实了朱子在礼学文献方面所花时间与精力不足的问题。假如朱子在研读礼学文献方面所花时间和精力足够多,当不会出现礼学文献不熟的问题。不论是朱子所花时间、精力还是注重礼学的义理的研讨,都显示了朱子对礼学文献的疏忽的情况。这绝非我们对朱子学术的吹毛求疵,因为朱子在平时讲学中不只一次强调学古礼,当求其内在的义理,并加以合符实际的应用。《朱子语类》载:
杨通老问《礼书》。曰:“看礼书见古人极有精密处,事无微细,各各有义理。然又须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见得度数文为之末,如此岂能识得深意?如将一碗干硬底饭来吃,有甚滋味?若白地将自家所见揣摸他本来意思不如此,也不济事。兼自家工夫未到,只去理会这个,下稍溺於器数,一齐都昏倒了。如今度得未可尽晓其意,且要识得大纲。”
此条为叶贺孙辛亥(1191)以后所闻。除此之外,叶贺孙于同卷中尚录有多条相似内容的语录,当为可信。朱子在此主要强调学者要从礼书中看出古人的意思,而不是“度数文为之末”,换言之,朱子追求的是理解礼书的内在礼义,而非限于礼仪方面,更非“溺于器数”,事实上,朱子与宋代其他注重《礼记》的学者并没有根本区别,都是注重其内在学理。仅是朱子治学方法比其他宋儒更为严谨的强调学习者需要在学习礼书内在义理过程中,把握具体礼仪“大纲”,至于何为大纲则由行礼者根据自身工夫而定夺,可见朱子偏向于礼学的义理方面,则可确定了。至于具体礼仪内容,朱子则持可以损减的观点。《朱子语类》载:
今所集《礼书》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后人自去减杀,求其可行者而已。
朱子所举例子为衣服观履不必如古,但是何者为大纲,何者为细节,而对礼学内容的减杀的标准为什么?朱子都未曾系统论述,亦与当时重视《礼记》的学者无本质的差别。
朱子生平著作等身,难以面面俱到,亦属正常。但是在四书学中,我们难以看到上述如此大的失误,亦显示出朱子对四书学重视程度远非礼学可比。甚至到了晚年,朱子对礼学典籍的整理难度或者重视程度仍旧缺少清晰的认识。他说:
古人自幼入小学,便教以礼;及长,自然在规矩之中。横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礼,也易学。今人乍见,往往以为难。某尝要取《三礼》编成一书,事多蹉过。若有朋友,只两年工夫可成。
此条为邵浩丙午(1186)所闻录。朱子此时尚未充分认识礼书修撰的难度,这便导致《通解》一书最终只能以未完稿而嘱托于后学,其原因虽有多种,但是最为重要的当属朱子本人的学术兴趣更倾向于注重义理之学。
通过以上的略显烦琐的考论证实了:从北宋开始,学者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义理的研究方面,朱子亦是随时代大潮而发展。但是正是前文所言朱子本人的治学的方法论特质,才逐步把朱子的学术关注点引入到《通解》的编撰方面。朱子是宋学的典型代表,具有宋学的各种特征,但是其在深入学习宋学的基础上,通过归因于王安石罢废《仪礼》之学及自身的深刻反思纠正了宋代学者注重《礼记》之学,而罢废《仪礼》学的学术思潮,重新重视《仪礼》学,并以《仪礼》为主体内容,采编源自各种典籍的礼学资料,补充《仪礼》所缺之资料,重新构建礼仪与礼义并重的礼学资料体系,虽有逆时代学术思潮而动且有未完成编撰工作之遗憾,但是纠正宋学的弊端,发展宋学的优秀成果的目的却呈现得淋漓尽致,从而推动《通解》的编撰工作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而顺利进行。
综上所述,《通解》是朱子在下学上达、切问近思的学术思想指导下,逐渐克服宋学空疏的弊端,实现由宋代理学走向传统经学之路,并在纠正宋代礼学弊端,发展宋代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编撰《通解》,开创了后世编撰礼书的新典范。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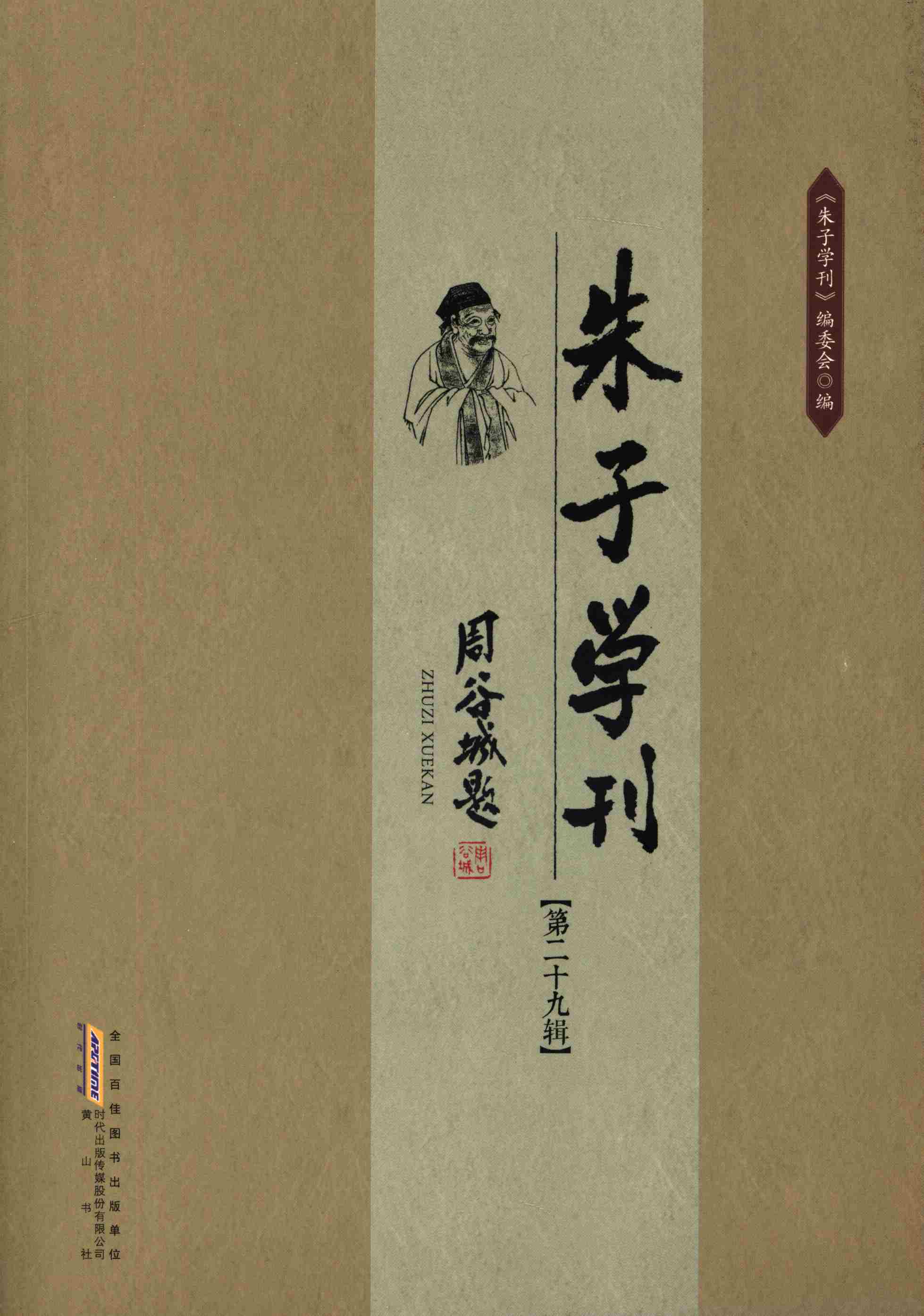
《朱子学刊·第二十九辑》
出版者:黄山书社
本书收录了《朱子哲学体系建构的方法学》《朱熹婚丧礼制的推行》《朱熹理学的传播路径及其对徽州日常生活的影响》《戴震与朱熹关系平议》《陈北溪论“命”》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王志阳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