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韩国儒学研究的概念史清理
| 内容出处: |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200 |
| 颗粒名称: | 一 韩国儒学研究的概念史清理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8 |
| 页码: | 885-89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韩国儒学研究需要汉学和哲学的基本功,同时面临多重文本的交错和论争的挑战。现存的“主理派/主气派”解释框架在学界引发了讨论,需要重新审视与修正。韩国儒学的核心概念包括“主理”、“主气”、“理发”、“气发”,它们具有多义性,需要进行概念史的清理。 |
| 关键词: | 韩国儒学 主理派 主气派 |
内容
韩国儒学研究不易,儒者文本积累数百年,义理辨析入微;研究者不仅要有汉学(sinology)的基本功,更需要哲学(philosophy)的敏锐度与思辨力,否则难以进入韩国儒学的精神世界,也难以掌握韩国儒学的精髓。依笔者管见,韩国儒学研究所凭借的“文本”(text),就有其独特性。因为,研究者首先面对的就是多重文本的交错①,如果研究者无法对此多重文本的来源与义理脉络有清楚的掌握,便可能如堕五里雾中,摸不着头绪,而越说越糊涂。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儒学的思想内容多以“论争”(debate)方式进行,参与的儒者众多,各有不同的学派或政治立场,动辄往复辩论多回,甚至论辩数百年而不息。如何在对立的论争中,以严谨的逻辑与论证,分辨双方思路与论点的不同,又能彼此联结与统合,这需要哲学的概念分析与思辨训练。仅以朝鲜性理学的论争为例,表面上起因于朱熹诸多文本的不一致,但实际上涉及诸儒者对朱熹思想的理解与诠释。一旦涉及论争,双方便以朱熹思想为坐标,展开两方面的攻防:一是朱熹文本的根据,一是朱熹思想的内在逻辑性。就此而言,韩国儒学研究,既需要尊重且掌握多重文本的解读(不能绕过文本,凭空立说),也需要辨析诸哲学概念与论题的异同,以思考普遍哲学问题。换言之,就韩国儒学研究而言,精读文本与哲学分析,脉络化(contextualization)与去脉络化(de-contextualization)②,缺一不可。
不可否认,自从日本学者高桥亨于1929年发表《李朝儒學史に於ける主理派主氣派の發達》后,"主理派/主气派”的解释框架(framework),影响韩国儒学研究甚大。①但随着韩国学界对于韩国儒学研究的累积与深入,20世纪90年代左右,开始出现批判的声音,如李东熙、崔英辰、韩亨祚、赵南浩等学者,皆认为高桥亨之说有待商榷。近年来,高桥亨的解释框架也再度在韩国学界引发讨论,2005年与201I年,韩国学界皆出版高桥亨的专辑②,2012年9月台湾大学也举办“东亚视域中的韩国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③,聚焦于高桥亨的解释框架,进行客观的学术批判,并寻求新的解释框架。
笔者认为,高桥亨以“主理派/主气派”的框架来解释朝鲜儒学,相较于以往以“人物”“学派”为主的朝鲜儒学研究,在方法论的自觉上,有其创新之功。尤其,他以汉文学科的学术训练,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扎下深厚的基础,这是其优点,也是今日韩国儒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功。然而,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不等于汉学研究,除基本功外,还须具备哲学性的思维才能入其堂奥,彰显韩国儒学思想的深度。高桥亨的问题就在于他缺乏哲学的思辨与敏锐度。简言之,高桥亨以朝鲜儒学重要的“主理”“主气”概念为理论判准,将朝鲜儒学分为“主理派/主气派”。问题是,朝鲜儒者的“主理”“主气”概念,不等同于高桥亨所杜撰的“主理派”“主气派”(韩国儒学文本从未岀现此概念)。④前者是朝鲜儒学本有的重要概念,具有理论简别的意义,且有多义性(polysemy)5后者是高桥亨在概念不清之下所虚构的分派,在义理简别与描述功能上,都不能精准地掌握朝鲜儒学。但因高桥亨“主理派/主气派”分类以“主理/主气”概念为根据,致使韩国学者检讨高桥亨之说时,将“主理派/主气派”等同“主理/主气”,产生不少混淆。
严格地说,朝鲜性理学的发展,有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之别,而没有“主理派”与“主气派”的区分。当然,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的激烈对立,岭南学派的李葛庵(名玄逸,1627—1704)与畿湖学派的宋尤庵(名时烈,1607—1689)都是关键性人物。李栗谷(名珥,1536—1584)或畿湖学派并未自称为“主气派”,岭南学派柳稷(号百拙庵,1602—1662)曾批评栗谷的理气说是主气论,且是异端。如此一来,“主理”为正学,“主气”为异端,就带有价值评判,“主气”乃带有负面评价。不过,在朝鲜性理学尊重性理的共识下,不论岭南学派或畿湖学派,都无法接受“主气派”的标签。更重要的是,若仔细检视高桥亨“主理派/主气派”解释框架的“论据”(reasons forjustification),就可以发现,高桥亨因为无法掌握朱熹的哲学思想,遂无法理解“四七论争”的哲学思辨性,且又泯除朝鲜儒者“主理”“主气”的多义性,致使其解释框架无法使诸多重要核心概念有清楚的定位,也无法简别不同儒学系统的根本差异,毫无理论效力可言,反而混淆并曲解了朝鲜儒学史。因此,高桥亨的解释框架该是寿终正寝的时候了。①
虽然韩国儒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高桥亨解释框架的限制,但笔者认为在提出新的解释框架前,仍有必要内在于韩国儒学的脉络,对于诸多具有多义性的重要概念进行概念史的清理,以呈现韩国儒学细致、复杂、丰富的思想内核,进而汲取思想资源,回应当代的问题,或普遍哲学问题的提问。一般而言,韩国儒学的研究者,在解读多重文本时,不难发现,诸儒者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如心、性、理、气、理发、气发、主理、主气、道心、人心、四端、七情等,在诸儒者的理论建构与工夫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含义与联结,其意义结构也有差异。这种概念的多义性也显示哲学思考向度与焦点的不同,故韩国儒学概念史的逐步清理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笔者以“主理”与“主气”、“理发”与“气发”为例,做简要的分析。
就韩国儒学的发展而言,“主理”“主气”此对概念,从李退溪开始直至韩末,虽是固有的传统术语,但此对概念在诸多朝鲜儒者的文本中,各自有不同的含义,有其多义性。如退溪将“主理”“主气”与“理发”“气发”相对应,其含义着重在“性发为情”的根源处,故“理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主理”(四端主于理而气随之),“气发”(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主气”(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①然而,栗谷反对退溪的“理气互发”,认为仅就“气发”(气发理乘)的方向发展,才有所谓“主理”、“主气”可言,故“气发”包含“主理”与“主气”。②又如韩末崔惠冈(名汉绮,1804—1877),也使用“主理”“主气”此对概念,但其含义乃在指涉“性理学”(主理)与其自身的“气学”(主气)。③故若无视于“主理”“主气”概念的多义性,将无法简别诸儒思想的异同,而流于一偏之见。例如,即使我们采取退溪“主理”“主气”相互对立的含义,但“主气”并不意味着否定理的实在性,“主理”也不意味着否定气的活动性。又如,虽然栗谷的“气发”包含“主理”“主气”,但仍然重视“理无为”的根源性。不论退溪或栗谷,皆以体现人性之善,性理之价值为归趣。即使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皆不背离此种性理的思想主旋律。
另就“理发”“气发”来说,这两个概念也是韩国儒学的核心概念,对于退溪与栗谷思想的理解,最为关键。然而,“理发”“气发”之“发”,也有多义性,须视诸儒者使用的文本脉络与义理系统而定。举例而言,退溪、奇高峰(名大升,1527—1572)、栗谷等儒者在讨论理气、心性问题时,他们主要所使用的词汇是“发”或“发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沿用古汉语的用法,将“发见”等同“发现”,含义相同,意味着理、气①或心②、性、情③的显现、呈现。即使有些儒者使用“发现”,其含义也同于“发见”。不过,在退溪与高峰论辩“理发”“气发”时,双方皆用“发用”一词。④而栗谷在辩驳退溪“理气互发”时,也常使用“发用”一词。⑤再者,“发动”一词,本来出现于朱熹之文,而栗谷在说明“气发”时,也使用此一词汇。⑥因此,就古代汉语(或朝鲜儒者的用法)而言,“理发”“气发”之“发”,可以意味着“发见”(同“发现”)、“发用”、“发动”诸义。后两者与动力(活动性、能动性)有关,而“发见”就有歧义,既可以指(理、气)的主动显现(呈现),也可以指(理、气)的被动显现(呈现)。此在解读“气发”之“发”时,“发见”(发现)、“发用”、“发动”相联结,明显地指出“气”的主动显现,具有活动性、能动性,较无疑义。但涉及“理发”之“发”时,仅就“发见”而言,就有两种解读与理解。一是“理”主动显现,具有活动性、能动性;一是“理”无活动性、能动性,必须借由“气”才能显现,在这个意义下,“理”是被动显现。如此一来,就涉及退溪的“理发”:“理”是否能活动?
不过,令当今学者混淆的是,现代汉语中,保留且使用“发现”,而无“发见”,其含义并非古代汉语的显现、呈现之义。但在韩语与日语中,虽保留“发见”(〓〓,はつけん)与“发现”(發顯、〓〓,はつげん)两词汇,但其用法与含义,已经与古代汉语不同了,两个词汇的含义有别。若用英文来表达,现代韩语的“发见”,意指discover,find;“发现”(發顯),意指present,reveal,manifest。对比之下,现代汉语的“发现”与现代韩语的“发见”含义相近,而不同于现代韩语的“发现”。因此,在现代汉语与韩语学者,虽以同一词汇“发现”来理解退溪的“理发”时,其含义却不同。另就“发用”一词来说,古今汉语的含义相近,意指generate。
职是之故,在中国,就使用古今汉语的台湾学者而言,退溪的“理气互发”或栗谷的“气发理乘”时,两者之“发”(理发、气发),都有活动义、能动性、主宰性,故多以“发用”理解之,少用“发见”(显现、呈现)之义。因此,根据朱熹“气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①之思路,台湾学界研究韩国儒学的学者多有共识:即朱熹之“理”作为“存在之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merely being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②,是万物存在的存有论根据;而真正化生万物(能凝聚生物)的是“气”,气有活动义、能动性。在此理解下,栗谷的“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气发理乘一途说)等论述,相当准确地诠释朱熹理气论,故栗谷是朱熹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另一方面,退溪就四端七情之讨论所揭示的“理气互发”(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显示“理发”之“理”能“发用”,具有活动义、能动性、主宰性。若再参照退溪的“理动”“理到”诸说,就发现退溪的见解超越朱熹的理气论,有所发明,是朱熹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者。
然而,在韩国学界,学者对退溪“理发”之“发”的解读,多从古代“发见”(现代韩语“发现”“发显”)来理解,意味着“理”之显现、呈现(理自身显现或理在气上显现)。据此,退溪之“理发”不涉及“理能否活动”之问题。①退溪与朱熹一样,在论及四端七情时,都聚焦于情之根源(所从来)问题,而不是理之活动。在这个意义下,退溪之理发、气发,只是揭示四端与七情在价值论上各有不同来源,其立场与观点与朱熹相同,退溪才是朱熹的继承者。相对地,栗谷错解朱熹与退溪对于四端七情的讨论,迳从存有论的角度来质问,可说偏离朱熹、退溪的论题了。另一种解读是,退溪之“理发”虽也从“理之发见”来理解,但着重在理自身的显现,而理之所以能显现,乃因其自身能活动、能发用,故退溪之“理发”,意味着“理能活动”。②借此彰显四端作为道德主体的纯粹性、超越性、能动性,此乃退溪对朱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有关“理发”“气发”的多义性,不仅显现在前述的不同理解上,朝鲜时代儒者的解析更为细密。如退溪学派的李寒洲(名震相,1818—4816)以“横说”来诠释退溪的“理气互发”说(理之所发、气之所发),又以“竖说”来阐释四端七情都是“理发一途”。③而栗谷学派的田艮斋(名愚,1841-1922)认为“气发理乘一途说”才是四端七情的本旨,以此为逻辑前提,从情之根源上说,四七都可说是“理发”;从以情之作用者为中心看,四七都可说是“气发”。④由此可见,面对五百余年的韩国儒学思想之积淀,当今研究者有必要内在于韩国儒学的脉络,逐步进行概念史的清理工作。
不可否认,自从日本学者高桥亨于1929年发表《李朝儒學史に於ける主理派主氣派の發達》后,"主理派/主气派”的解释框架(framework),影响韩国儒学研究甚大。①但随着韩国学界对于韩国儒学研究的累积与深入,20世纪90年代左右,开始出现批判的声音,如李东熙、崔英辰、韩亨祚、赵南浩等学者,皆认为高桥亨之说有待商榷。近年来,高桥亨的解释框架也再度在韩国学界引发讨论,2005年与201I年,韩国学界皆出版高桥亨的专辑②,2012年9月台湾大学也举办“东亚视域中的韩国儒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③,聚焦于高桥亨的解释框架,进行客观的学术批判,并寻求新的解释框架。
笔者认为,高桥亨以“主理派/主气派”的框架来解释朝鲜儒学,相较于以往以“人物”“学派”为主的朝鲜儒学研究,在方法论的自觉上,有其创新之功。尤其,他以汉文学科的学术训练,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考证上,扎下深厚的基础,这是其优点,也是今日韩国儒学研究者所应具备的基本功。然而,韩国儒学思想研究不等于汉学研究,除基本功外,还须具备哲学性的思维才能入其堂奥,彰显韩国儒学思想的深度。高桥亨的问题就在于他缺乏哲学的思辨与敏锐度。简言之,高桥亨以朝鲜儒学重要的“主理”“主气”概念为理论判准,将朝鲜儒学分为“主理派/主气派”。问题是,朝鲜儒者的“主理”“主气”概念,不等同于高桥亨所杜撰的“主理派”“主气派”(韩国儒学文本从未岀现此概念)。④前者是朝鲜儒学本有的重要概念,具有理论简别的意义,且有多义性(polysemy)5后者是高桥亨在概念不清之下所虚构的分派,在义理简别与描述功能上,都不能精准地掌握朝鲜儒学。但因高桥亨“主理派/主气派”分类以“主理/主气”概念为根据,致使韩国学者检讨高桥亨之说时,将“主理派/主气派”等同“主理/主气”,产生不少混淆。
严格地说,朝鲜性理学的发展,有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之别,而没有“主理派”与“主气派”的区分。当然,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的激烈对立,岭南学派的李葛庵(名玄逸,1627—1704)与畿湖学派的宋尤庵(名时烈,1607—1689)都是关键性人物。李栗谷(名珥,1536—1584)或畿湖学派并未自称为“主气派”,岭南学派柳稷(号百拙庵,1602—1662)曾批评栗谷的理气说是主气论,且是异端。如此一来,“主理”为正学,“主气”为异端,就带有价值评判,“主气”乃带有负面评价。不过,在朝鲜性理学尊重性理的共识下,不论岭南学派或畿湖学派,都无法接受“主气派”的标签。更重要的是,若仔细检视高桥亨“主理派/主气派”解释框架的“论据”(reasons forjustification),就可以发现,高桥亨因为无法掌握朱熹的哲学思想,遂无法理解“四七论争”的哲学思辨性,且又泯除朝鲜儒者“主理”“主气”的多义性,致使其解释框架无法使诸多重要核心概念有清楚的定位,也无法简别不同儒学系统的根本差异,毫无理论效力可言,反而混淆并曲解了朝鲜儒学史。因此,高桥亨的解释框架该是寿终正寝的时候了。①
虽然韩国儒学研究者已经意识到高桥亨解释框架的限制,但笔者认为在提出新的解释框架前,仍有必要内在于韩国儒学的脉络,对于诸多具有多义性的重要概念进行概念史的清理,以呈现韩国儒学细致、复杂、丰富的思想内核,进而汲取思想资源,回应当代的问题,或普遍哲学问题的提问。一般而言,韩国儒学的研究者,在解读多重文本时,不难发现,诸儒者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如心、性、理、气、理发、气发、主理、主气、道心、人心、四端、七情等,在诸儒者的理论建构与工夫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含义与联结,其意义结构也有差异。这种概念的多义性也显示哲学思考向度与焦点的不同,故韩国儒学概念史的逐步清理有其必要性与重要性。笔者以“主理”与“主气”、“理发”与“气发”为例,做简要的分析。
就韩国儒学的发展而言,“主理”“主气”此对概念,从李退溪开始直至韩末,虽是固有的传统术语,但此对概念在诸多朝鲜儒者的文本中,各自有不同的含义,有其多义性。如退溪将“主理”“主气”与“理发”“气发”相对应,其含义着重在“性发为情”的根源处,故“理发”(四端理发而气随之)=“主理”(四端主于理而气随之),“气发”(七情气发而理乘之)=“主气”(七情主于气而理乘之)。①然而,栗谷反对退溪的“理气互发”,认为仅就“气发”(气发理乘)的方向发展,才有所谓“主理”、“主气”可言,故“气发”包含“主理”与“主气”。②又如韩末崔惠冈(名汉绮,1804—1877),也使用“主理”“主气”此对概念,但其含义乃在指涉“性理学”(主理)与其自身的“气学”(主气)。③故若无视于“主理”“主气”概念的多义性,将无法简别诸儒思想的异同,而流于一偏之见。例如,即使我们采取退溪“主理”“主气”相互对立的含义,但“主气”并不意味着否定理的实在性,“主理”也不意味着否定气的活动性。又如,虽然栗谷的“气发”包含“主理”“主气”,但仍然重视“理无为”的根源性。不论退溪或栗谷,皆以体现人性之善,性理之价值为归趣。即使岭南学派与畿湖学派,皆不背离此种性理的思想主旋律。
另就“理发”“气发”来说,这两个概念也是韩国儒学的核心概念,对于退溪与栗谷思想的理解,最为关键。然而,“理发”“气发”之“发”,也有多义性,须视诸儒者使用的文本脉络与义理系统而定。举例而言,退溪、奇高峰(名大升,1527—1572)、栗谷等儒者在讨论理气、心性问题时,他们主要所使用的词汇是“发”或“发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沿用古汉语的用法,将“发见”等同“发现”,含义相同,意味着理、气①或心②、性、情③的显现、呈现。即使有些儒者使用“发现”,其含义也同于“发见”。不过,在退溪与高峰论辩“理发”“气发”时,双方皆用“发用”一词。④而栗谷在辩驳退溪“理气互发”时,也常使用“发用”一词。⑤再者,“发动”一词,本来出现于朱熹之文,而栗谷在说明“气发”时,也使用此一词汇。⑥因此,就古代汉语(或朝鲜儒者的用法)而言,“理发”“气发”之“发”,可以意味着“发见”(同“发现”)、“发用”、“发动”诸义。后两者与动力(活动性、能动性)有关,而“发见”就有歧义,既可以指(理、气)的主动显现(呈现),也可以指(理、气)的被动显现(呈现)。此在解读“气发”之“发”时,“发见”(发现)、“发用”、“发动”相联结,明显地指出“气”的主动显现,具有活动性、能动性,较无疑义。但涉及“理发”之“发”时,仅就“发见”而言,就有两种解读与理解。一是“理”主动显现,具有活动性、能动性;一是“理”无活动性、能动性,必须借由“气”才能显现,在这个意义下,“理”是被动显现。如此一来,就涉及退溪的“理发”:“理”是否能活动?
不过,令当今学者混淆的是,现代汉语中,保留且使用“发现”,而无“发见”,其含义并非古代汉语的显现、呈现之义。但在韩语与日语中,虽保留“发见”(〓〓,はつけん)与“发现”(發顯、〓〓,はつげん)两词汇,但其用法与含义,已经与古代汉语不同了,两个词汇的含义有别。若用英文来表达,现代韩语的“发见”,意指discover,find;“发现”(發顯),意指present,reveal,manifest。对比之下,现代汉语的“发现”与现代韩语的“发见”含义相近,而不同于现代韩语的“发现”。因此,在现代汉语与韩语学者,虽以同一词汇“发现”来理解退溪的“理发”时,其含义却不同。另就“发用”一词来说,古今汉语的含义相近,意指generate。
职是之故,在中国,就使用古今汉语的台湾学者而言,退溪的“理气互发”或栗谷的“气发理乘”时,两者之“发”(理发、气发),都有活动义、能动性、主宰性,故多以“发用”理解之,少用“发见”(显现、呈现)之义。因此,根据朱熹“气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①之思路,台湾学界研究韩国儒学的学者多有共识:即朱熹之“理”作为“存在之理”,是“只存有而不活动”(merely being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②,是万物存在的存有论根据;而真正化生万物(能凝聚生物)的是“气”,气有活动义、能动性。在此理解下,栗谷的“发之者,气也。所以发者,理也。非气则不能发,非理则无所发”、“理无为而气有为,故气发而理乘”(气发理乘一途说)等论述,相当准确地诠释朱熹理气论,故栗谷是朱熹思想的忠实继承者。另一方面,退溪就四端七情之讨论所揭示的“理气互发”(四端之情,理发而气随之……七者之情,气发而理乘之),则显示“理发”之“理”能“发用”,具有活动义、能动性、主宰性。若再参照退溪的“理动”“理到”诸说,就发现退溪的见解超越朱熹的理气论,有所发明,是朱熹思想的创造性转化者。
然而,在韩国学界,学者对退溪“理发”之“发”的解读,多从古代“发见”(现代韩语“发现”“发显”)来理解,意味着“理”之显现、呈现(理自身显现或理在气上显现)。据此,退溪之“理发”不涉及“理能否活动”之问题。①退溪与朱熹一样,在论及四端七情时,都聚焦于情之根源(所从来)问题,而不是理之活动。在这个意义下,退溪之理发、气发,只是揭示四端与七情在价值论上各有不同来源,其立场与观点与朱熹相同,退溪才是朱熹的继承者。相对地,栗谷错解朱熹与退溪对于四端七情的讨论,迳从存有论的角度来质问,可说偏离朱熹、退溪的论题了。另一种解读是,退溪之“理发”虽也从“理之发见”来理解,但着重在理自身的显现,而理之所以能显现,乃因其自身能活动、能发用,故退溪之“理发”,意味着“理能活动”。②借此彰显四端作为道德主体的纯粹性、超越性、能动性,此乃退溪对朱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事实上,有关“理发”“气发”的多义性,不仅显现在前述的不同理解上,朝鲜时代儒者的解析更为细密。如退溪学派的李寒洲(名震相,1818—4816)以“横说”来诠释退溪的“理气互发”说(理之所发、气之所发),又以“竖说”来阐释四端七情都是“理发一途”。③而栗谷学派的田艮斋(名愚,1841-1922)认为“气发理乘一途说”才是四端七情的本旨,以此为逻辑前提,从情之根源上说,四七都可说是“理发”;从以情之作用者为中心看,四七都可说是“气发”。④由此可见,面对五百余年的韩国儒学思想之积淀,当今研究者有必要内在于韩国儒学的脉络,逐步进行概念史的清理工作。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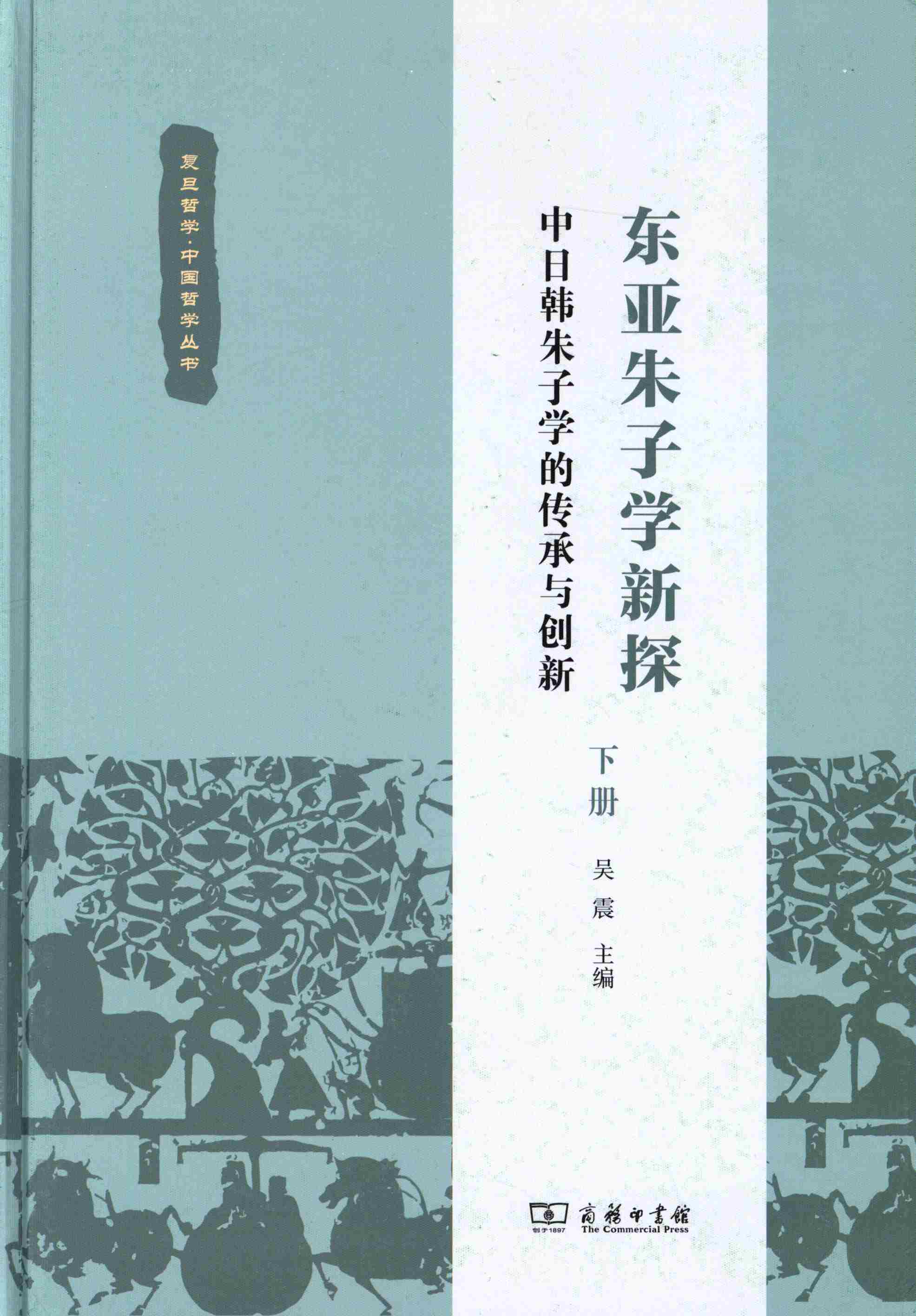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下册》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结项成果,并于今年被认定为是成果。近九十万字,吴震教授主编,由海内外中国哲学领域的一线学者组成的性团队合作分篇撰写,代表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的成果。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