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蔡书之疑
| 内容出处: |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137 |
| 颗粒名称: | (三)蔡书之疑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7 |
| 页码: | 671-677 |
| 摘要: | 本文针对《圣学十图》中的“蔡书之内容”以及南塘和钱穆对其的观点进行考察分析。其中包括对《答蔡季通》第2书中的问题的讨论,特别是关于人心与道心的探讨。南塘认为《答蔡季通》第2书存在问题,其立论不足以成为根据;钱穆则概括了朱熹在该书中的错误观点。最后,通过对朱熹的其他著作和相关语录的对比,揭示了《答蔡季通》第2书中的语言问题所在。 |
| 关键词: | 韩国儒学 朱子学 蔡书之疑 |
内容
由于该信所引起的争议很大,为了论证的便利,首先展现其文本内容便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1.蔡书之内容
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以其主理而无形,故公而无不善;以其主气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发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盖自其根本而已然,非为气之所为有过不及而后流于人欲也。然但谓之人心,则固未以为悉皆邪恶;但谓之危,则固未以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于理而主于形,则其流为邪恶以致凶咎,亦不难矣。此其所以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无恶、有安而无顷、有准的而可凭据也。故必其致精一于此两者之间,使公而无不善者常为一身万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与焉,则凡所云为不待择于过不及之间而自然无不中矣。(原小注:凡物剖判之初,且当论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后,方可论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审其善不善也。“允执厥中”,则无过不及而自得其中矣,非精一以求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尝直以形气之发尽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纯粹之时,如来喻之所疑也。但此所谓清明纯粹者,既属乎形气之偶然,则亦但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耳,不可便认以为道心,而欲据之以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虽言夜气,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义之心,非直以此为夜气为主也。虽言养气,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义,非直就此其中择其无过不及者而养之也。来喻主张“气”字太过,故于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别中气过不及处,亦觉有差。但既无与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①关于该信的写作年代,颇有争议。②本文认定其写作时间在己酉(1189)三月十八日与秋九月之间。该信内容丰富,首次出现了后世东亚儒学中的常用表述“主理”以及“主气”两词,也指出了道心之必善而无恶的性质。③与此同时,朱熹试图从本源上对人心道心做根本区分,他认为道心主理人心主气,故而前者(道心)必善。但是,朱熹对人心的说法出现了相互冲突之处,故而就出现了他后来所承认的“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至于该书所存在的问题,后文会予以详细检讨。
2.南塘对《答蔡季通》第2书的看法
在《朱子言论同异考》中,南塘提到了自己读到该信时的心路历程:
《答蔡季通》论人心道心书,骤看似以人心为气发道心为理发,故后来为理气互发之论者,尤以此书为左契。然细考之,则实不然。其论人心曰主于形而有质,曰私而或不善。盖皆指耳目口体而言也。何者谓之形?而耳目口体之形可谓之形,而心上发出之气不可谓之形也。谓之私则耳目口体之形可谓之私,而心上发出之气不可谓之私也。盖以仁义礼智之理,与耳目口体之形对言,而曰此公而无不善,故其发皆天理。彼私而或不善,故其发皆人欲云云。此所谓析言之也,非以心中所具之理气析言之,而谓人心从气而发而道心从理而发也。下文所谓清明纯粹,不隔乎理者,亦指耳目口体之形气而言也。耳目口体之气,或有时而清明纯粹,则视自然明,听自然聪,四体自然收束不惰,此所谓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者也。饮食男女本乎天理,则人心之发亦莫非性命之所行。而但为发于吾身之私者,故易隔乎理而不得其正耳。幸而耳目口体之气,亦有清明纯粹之时,则虽其发于私者,亦自能得其正而天理不为所隔矣。先生之指,只如此而已。若是指心之发处,则清明纯粹者,既皆属乎人心,而不可认以为道心矣。彼道心之发又是何气也?大抵情之原于性而发于心者,无论四七人道只是一般。而其所以有此人心者,由其有耳目口体之形,固谓之发于耳目口体之气。或有清明纯粹之时,则其视听食息之欲,亦皆自然得其正,故谓之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也。其以此为心之发处,主理主气之证者,盖皆误认也。余旧看此书,亦不解其指,遂妄疑其初年未定之论,而《庸序》之述,亦或有前后本也。偶与季明言,如此方觉其前见之粗谬,而涣然无疑于先生之指矣。
《答蔡季通》论人心道心之说,旧尝疑其有二歧之嫌。然其书乃在《中庸序》文既述之后,则又似晚年所论。强为之解,而终涉龃龉,未见其有浃洽之意。则又疑《庸序》之述亦有前后之异,而此书终不得为定论矣。后见先生《答郑子上书》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也,人心也。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据此则先生果自以答蔡书为未是矣。子上又问曰:“窃寻《中庸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乃所以发明此意。今如所说,却是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云云。”先生又答曰:“《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据此则《中庸序》果亦有前后本之不同矣!若非子上之屡有问辩,答蔡书几为千古之疑案矣。……
又按:答蔡书虽不得为定论,然其指亦非直以人心为发于气,道心为发于理也。但其立语未莹易使人错看耳。①
根据南塘的夫子自道,该信曾经令他非常头疼。韩国儒学中的一部分人以该书为佐证,要么认为朱熹是主张理气互发说的,要么利用该书为退溪的理气互发说辩护。②南塘最初也认为朱熹在该信中主张理气互发,不过由于其反理气互发说的立场,他则怀疑该信“有二歧之嫌”。但该信明显又是撰写于《中庸章句序》之后,故而就不应该和该序所代表的朱熹的道心人心思想晚年定论相矛盾。但是该信又确实和《中庸章句序》有明显冲突之处。于是南塘就试图强行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南塘后来改变了思路,怀疑《中庸章句序》的内容有过明显调整,而该信和调整前的内容是一致的,故而也不是定论。后来,南塘的怀疑在朱熹《答郑子上》第11书中得到了部分证实,《中庸章句序》的内容确实有修正。而在朱熹《答郑子上》第10书中,朱熹亲口承认,“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既然该信连朱熹都认为有问题,不应该成为立论的根据,那么在南塘看来韩国儒学中主张该信支持理气互发说的观点,就是站不住脚的。南塘之前还用心反驳对该信的理气互发说式的利用,其结论是“皆误认也”。即便是这样,南塘还是在论蔡书的最后下了一个按语,再次确证了两点:第一,朱熹的答蔡书不是定论。第二,该书话语有问题。虽然该书并不明确主张人心气发道心理发,但是容易使得人们误会它主张这个观点。内在于韩国儒学的脉络,应该说,南塘的相关观点是有力的。但是,在我看来,南塘囿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对“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是针对《答蔡季通》第2书中的哪些话的解读,值得进一步深思。
3.钱穆对《答蔡季通》第2书的看法
史学家钱穆对该信也很感兴趣,他是结合郑子上的相关材料来解读《答蔡季通》第2书中存在的“语却未莹”问题的。先看有关郑子上的一条语录:“因郑子上书来问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可学窃寻《中庸序》,以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盖觉于理谓性命,觉于欲谓形气云云。可学近观《中庸序》所谓‘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来专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于形气,如何去得!然人于性命之理不明,而专为形气所使,则流于人欲矣。如其达性命之理,则虽人心之用,而无非道心……可学以为必有道心,而后可以用人心,而于人心之中,又当识道心。若专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则固流入于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则是判性命为二物,而所谓道心者,空虚无有,将流于释老之学,而非《虞书》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①这条语录是余大雅在去世之前所记录,时间是1189年的夏秋之间。结合《语类》与《文集》的材料,可以认定该条语录中所说的“因郑子上书”指的就是《答郑子上》第10书,而“先生曰”的内容应该也在《答郑子上》第10书中。由于郑子上的反复追问,朱熹终于说道:“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②
问题在于,“语却未莹”之处何在?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钱穆提到了一条语录:“季通以书问《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气。先生曰:‘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气亦皆有善。不知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船无柁,纵之行,有时入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乃形气,则乃理也。’〔可学〕”③看来,这条语录应该是朱熹、蔡季通和郑子上三人密切联系频繁探讨人心道心问题的时候。根据《朱子语录姓氏》,钱穆认为该条语录乃郑可学辛亥(1 191)所录。蔡季通在给朱熹的书信中强调形气亦皆有善的观点,从而一定程度上为来自形气的人心辩护。而朱熹对蔡氏的相关观点的回应应该就一方面体现在《答蔡季通》第2书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本条语录中。后来,朱熹认识到自己的《答蔡季通》第2书“语有未莹,不足据以为说”。钱穆的解释是:“其答季通,谓‘人心道心之别,自其根本而已然’,此殆所谓下语未莹也。《语类》此条,亦似把道心与形气划分两边说之,不见其间相沟通处。殆因季通来书主张气字太过,故答语亦不觉主张理一边太过了,未从正面把两边相通合一处提出,故有‘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之云也。”①
应该说,钱说有一定道理,其说可以和《答郑子上》第11书中的句子相互对应。“‘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可学蒙喻此语,极有开发。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书,语未莹,不足据以为说。’可学窃寻《中庸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乃所以发明此意。今如所云,却是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可学窃疑向所闻此心之灵一段所见差谬,先生欲觉其愚迷,故直于本原处指示,使不走作,非谓形气无预而皆出于心。愚意以为觉于理,则一本于性命而为道心;觉于欲,则涉于形气而为人心。如此所见,如何?”②确实,季通强调形气也可以有善,或许是一种主张善由气导的思想。而在朱熹看来,形气之有善,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理(或道心)。不过,钱穆先生对“下语未莹”处的判断却没有击中要害。
在我看来,《答蔡季通》第2书之所以被朱熹认为是“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人心道心乃出于形气还是本于性命,而是以天理人欲来谈道心人心,这才是要害所在。在该书中,朱熹“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的话语,是明显的严重错误。该书在《中庸章句序》之后,不应该出现私而或不善的人心乃人欲之所做的话语。在宋明理学中,人欲一词指的是人的私欲,是不好的恶的东西。而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对人心的规定是可善可恶,或者说是兼善恶的,故而不能说是人欲。人心是人欲的观点是朱熹的旧观点,他后来在《中庸章句序》里放弃了此观点。故而,“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的语言才是“语却未莹”的根本所在。当然了,后面的话语也有问题。“人心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盖自其根本而已然,非为气之所为有过不及而后流于人欲也。”这句话也暗示人心流于人欲乃自根本而已然,同样无法和人心人欲说拉开距离。朱熹在《戊申封事》(1188)以及《中庸章句序》之后,就抛弃了以天理人欲来谈道心人心的传统思路。但《答蔡季通》第2书明显在那两份文本之后,故而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于是,在仅仅一日之隔的给郑子上的书信,朱熹就以“觉于理”来规定道心,以“觉于欲”来规定人心。“理”是天理,而“欲”则是欲望而不是人欲。这么表述,就没有问题了。而郑子上理论修为有限,竟然没有看破此点。而朱熹也没有明说。高明如南塘,也未能识破此点,反而附和朱熹的错误说法,也说什么“彼私而或不善,故其发皆人欲云云”,还以《答郑子上》中的相关话语为最终定论,岂不可惜!
1.蔡书之内容
人之有生,性与气合而已。然即其已合而析言之,则性主于理而无形,气主于形而有质。以其主理而无形,故公而无不善;以其主气而有质,故私而或不善。以其公而善也,故其发皆天理之所行;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盖自其根本而已然,非为气之所为有过不及而后流于人欲也。然但谓之人心,则固未以为悉皆邪恶;但谓之危,则固未以为便致凶咎。但既不主于理而主于形,则其流为邪恶以致凶咎,亦不难矣。此其所以为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无恶、有安而无顷、有准的而可凭据也。故必其致精一于此两者之间,使公而无不善者常为一身万事之主,而私而或不善者不得与焉,则凡所云为不待择于过不及之间而自然无不中矣。(原小注:凡物剖判之初,且当论其善不善;二者既分之后,方可论其中不中。“惟精惟一”,所以审其善不善也。“允执厥中”,则无过不及而自得其中矣,非精一以求中矣。)此舜戒禹之本意,而序文述之,固未尝直以形气之发尽为不善,而不容其有清明纯粹之时,如来喻之所疑也。但此所谓清明纯粹者,既属乎形气之偶然,则亦但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耳,不可便认以为道心,而欲据之以为精一之地也。如孟子虽言夜气,而其所欲存者乃在乎仁义之心,非直以此为夜气为主也。虽言养气,而其所用力乃在乎集义,非直就此其中择其无过不及者而养之也。来喻主张“气”字太过,故于此有不察。其他如分别中气过不及处,亦觉有差。但既无与乎道心之微,故有所不暇辨耳。①关于该信的写作年代,颇有争议。②本文认定其写作时间在己酉(1189)三月十八日与秋九月之间。该信内容丰富,首次出现了后世东亚儒学中的常用表述“主理”以及“主气”两词,也指出了道心之必善而无恶的性质。③与此同时,朱熹试图从本源上对人心道心做根本区分,他认为道心主理人心主气,故而前者(道心)必善。但是,朱熹对人心的说法出现了相互冲突之处,故而就出现了他后来所承认的“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至于该书所存在的问题,后文会予以详细检讨。
2.南塘对《答蔡季通》第2书的看法
在《朱子言论同异考》中,南塘提到了自己读到该信时的心路历程:
《答蔡季通》论人心道心书,骤看似以人心为气发道心为理发,故后来为理气互发之论者,尤以此书为左契。然细考之,则实不然。其论人心曰主于形而有质,曰私而或不善。盖皆指耳目口体而言也。何者谓之形?而耳目口体之形可谓之形,而心上发出之气不可谓之形也。谓之私则耳目口体之形可谓之私,而心上发出之气不可谓之私也。盖以仁义礼智之理,与耳目口体之形对言,而曰此公而无不善,故其发皆天理。彼私而或不善,故其发皆人欲云云。此所谓析言之也,非以心中所具之理气析言之,而谓人心从气而发而道心从理而发也。下文所谓清明纯粹,不隔乎理者,亦指耳目口体之形气而言也。耳目口体之气,或有时而清明纯粹,则视自然明,听自然聪,四体自然收束不惰,此所谓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者也。饮食男女本乎天理,则人心之发亦莫非性命之所行。而但为发于吾身之私者,故易隔乎理而不得其正耳。幸而耳目口体之气,亦有清明纯粹之时,则虽其发于私者,亦自能得其正而天理不为所隔矣。先生之指,只如此而已。若是指心之发处,则清明纯粹者,既皆属乎人心,而不可认以为道心矣。彼道心之发又是何气也?大抵情之原于性而发于心者,无论四七人道只是一般。而其所以有此人心者,由其有耳目口体之形,固谓之发于耳目口体之气。或有清明纯粹之时,则其视听食息之欲,亦皆自然得其正,故谓之不隔乎理,而助其发挥也。其以此为心之发处,主理主气之证者,盖皆误认也。余旧看此书,亦不解其指,遂妄疑其初年未定之论,而《庸序》之述,亦或有前后本也。偶与季明言,如此方觉其前见之粗谬,而涣然无疑于先生之指矣。
《答蔡季通》论人心道心之说,旧尝疑其有二歧之嫌。然其书乃在《中庸序》文既述之后,则又似晚年所论。强为之解,而终涉龃龉,未见其有浃洽之意。则又疑《庸序》之述亦有前后之异,而此书终不得为定论矣。后见先生《答郑子上书》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也,人心也。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据此则先生果自以答蔡书为未是矣。子上又问曰:“窃寻《中庸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乃所以发明此意。今如所说,却是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云云。”先生又答曰:“《中庸序》后亦改定,别纸录去。”据此则《中庸序》果亦有前后本之不同矣!若非子上之屡有问辩,答蔡书几为千古之疑案矣。……
又按:答蔡书虽不得为定论,然其指亦非直以人心为发于气,道心为发于理也。但其立语未莹易使人错看耳。①
根据南塘的夫子自道,该信曾经令他非常头疼。韩国儒学中的一部分人以该书为佐证,要么认为朱熹是主张理气互发说的,要么利用该书为退溪的理气互发说辩护。②南塘最初也认为朱熹在该信中主张理气互发,不过由于其反理气互发说的立场,他则怀疑该信“有二歧之嫌”。但该信明显又是撰写于《中庸章句序》之后,故而就不应该和该序所代表的朱熹的道心人心思想晚年定论相矛盾。但是该信又确实和《中庸章句序》有明显冲突之处。于是南塘就试图强行调和二者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尝试是不成功的。南塘后来改变了思路,怀疑《中庸章句序》的内容有过明显调整,而该信和调整前的内容是一致的,故而也不是定论。后来,南塘的怀疑在朱熹《答郑子上》第11书中得到了部分证实,《中庸章句序》的内容确实有修正。而在朱熹《答郑子上》第10书中,朱熹亲口承认,“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既然该信连朱熹都认为有问题,不应该成为立论的根据,那么在南塘看来韩国儒学中主张该信支持理气互发说的观点,就是站不住脚的。南塘之前还用心反驳对该信的理气互发说式的利用,其结论是“皆误认也”。即便是这样,南塘还是在论蔡书的最后下了一个按语,再次确证了两点:第一,朱熹的答蔡书不是定论。第二,该书话语有问题。虽然该书并不明确主张人心气发道心理发,但是容易使得人们误会它主张这个观点。内在于韩国儒学的脉络,应该说,南塘的相关观点是有力的。但是,在我看来,南塘囿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对“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是针对《答蔡季通》第2书中的哪些话的解读,值得进一步深思。
3.钱穆对《答蔡季通》第2书的看法
史学家钱穆对该信也很感兴趣,他是结合郑子上的相关材料来解读《答蔡季通》第2书中存在的“语却未莹”问题的。先看有关郑子上的一条语录:“因郑子上书来问人心、道心,先生曰:‘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可学窃寻《中庸序》,以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盖觉于理谓性命,觉于欲谓形气云云。可学近观《中庸序》所谓‘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又知前日之失。向来专以人可以有道心,而不可以有人心,今方知其不然。人心出于形气,如何去得!然人于性命之理不明,而专为形气所使,则流于人欲矣。如其达性命之理,则虽人心之用,而无非道心……可学以为必有道心,而后可以用人心,而于人心之中,又当识道心。若专用人心而不知道心,则固流入于放僻邪侈之域;若只守道心,而欲屏去人心,则是判性命为二物,而所谓道心者,空虚无有,将流于释老之学,而非《虞书》之所指者。未知然否?〔大雅〕”①这条语录是余大雅在去世之前所记录,时间是1189年的夏秋之间。结合《语类》与《文集》的材料,可以认定该条语录中所说的“因郑子上书”指的就是《答郑子上》第10书,而“先生曰”的内容应该也在《答郑子上》第10书中。由于郑子上的反复追问,朱熹终于说道:“昨答季通书,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②
问题在于,“语却未莹”之处何在?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钱穆提到了一条语录:“季通以书问《中庸序》所云人心形气。先生曰:‘形气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季通云形气亦皆有善。不知形气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则形气善;不由道心,一付于形气,则为恶。形气犹船也,道心犹柁也。船无柁,纵之行,有时入于波涛,有时入于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运之,则虽入波涛无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物乃形气,则乃理也。’〔可学〕”③看来,这条语录应该是朱熹、蔡季通和郑子上三人密切联系频繁探讨人心道心问题的时候。根据《朱子语录姓氏》,钱穆认为该条语录乃郑可学辛亥(1 191)所录。蔡季通在给朱熹的书信中强调形气亦皆有善的观点,从而一定程度上为来自形气的人心辩护。而朱熹对蔡氏的相关观点的回应应该就一方面体现在《答蔡季通》第2书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本条语录中。后来,朱熹认识到自己的《答蔡季通》第2书“语有未莹,不足据以为说”。钱穆的解释是:“其答季通,谓‘人心道心之别,自其根本而已然’,此殆所谓下语未莹也。《语类》此条,亦似把道心与形气划分两边说之,不见其间相沟通处。殆因季通来书主张气字太过,故答语亦不觉主张理一边太过了,未从正面把两边相通合一处提出,故有‘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之云也。”①
应该说,钱说有一定道理,其说可以和《答郑子上》第11书中的句子相互对应。“‘此心之灵,其觉于理者,道心也;其觉于欲者,人心也。’可学蒙喻此语,极有开发。但先生又云:‘向答季通书,语未莹,不足据以为说。’可学窃寻《中庸序》云:‘人心出于形气,道心本于性命。’而答季通书,乃所以发明此意。今如所云,却是一本性命说而不及形气。可学窃疑向所闻此心之灵一段所见差谬,先生欲觉其愚迷,故直于本原处指示,使不走作,非谓形气无预而皆出于心。愚意以为觉于理,则一本于性命而为道心;觉于欲,则涉于形气而为人心。如此所见,如何?”②确实,季通强调形气也可以有善,或许是一种主张善由气导的思想。而在朱熹看来,形气之有善,不是来自自身,而是来自理(或道心)。不过,钱穆先生对“下语未莹”处的判断却没有击中要害。
在我看来,《答蔡季通》第2书之所以被朱熹认为是“语却未莹,不足据以为说”,根本原因并不在于人心道心乃出于形气还是本于性命,而是以天理人欲来谈道心人心,这才是要害所在。在该书中,朱熹“以其私而或不善也,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的话语,是明显的严重错误。该书在《中庸章句序》之后,不应该出现私而或不善的人心乃人欲之所做的话语。在宋明理学中,人欲一词指的是人的私欲,是不好的恶的东西。而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对人心的规定是可善可恶,或者说是兼善恶的,故而不能说是人欲。人心是人欲的观点是朱熹的旧观点,他后来在《中庸章句序》里放弃了此观点。故而,“故其发皆人欲之所作”的语言才是“语却未莹”的根本所在。当然了,后面的话语也有问题。“人心此舜之戒禹所以有人心、道心之别,盖自其根本而已然,非为气之所为有过不及而后流于人欲也。”这句话也暗示人心流于人欲乃自根本而已然,同样无法和人心人欲说拉开距离。朱熹在《戊申封事》(1188)以及《中庸章句序》之后,就抛弃了以天理人欲来谈道心人心的传统思路。但《答蔡季通》第2书明显在那两份文本之后,故而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于是,在仅仅一日之隔的给郑子上的书信,朱熹就以“觉于理”来规定道心,以“觉于欲”来规定人心。“理”是天理,而“欲”则是欲望而不是人欲。这么表述,就没有问题了。而郑子上理论修为有限,竟然没有看破此点。而朱熹也没有明说。高明如南塘,也未能识破此点,反而附和朱熹的错误说法,也说什么“彼私而或不善,故其发皆人欲云云”,还以《答郑子上》中的相关话语为最终定论,岂不可惜!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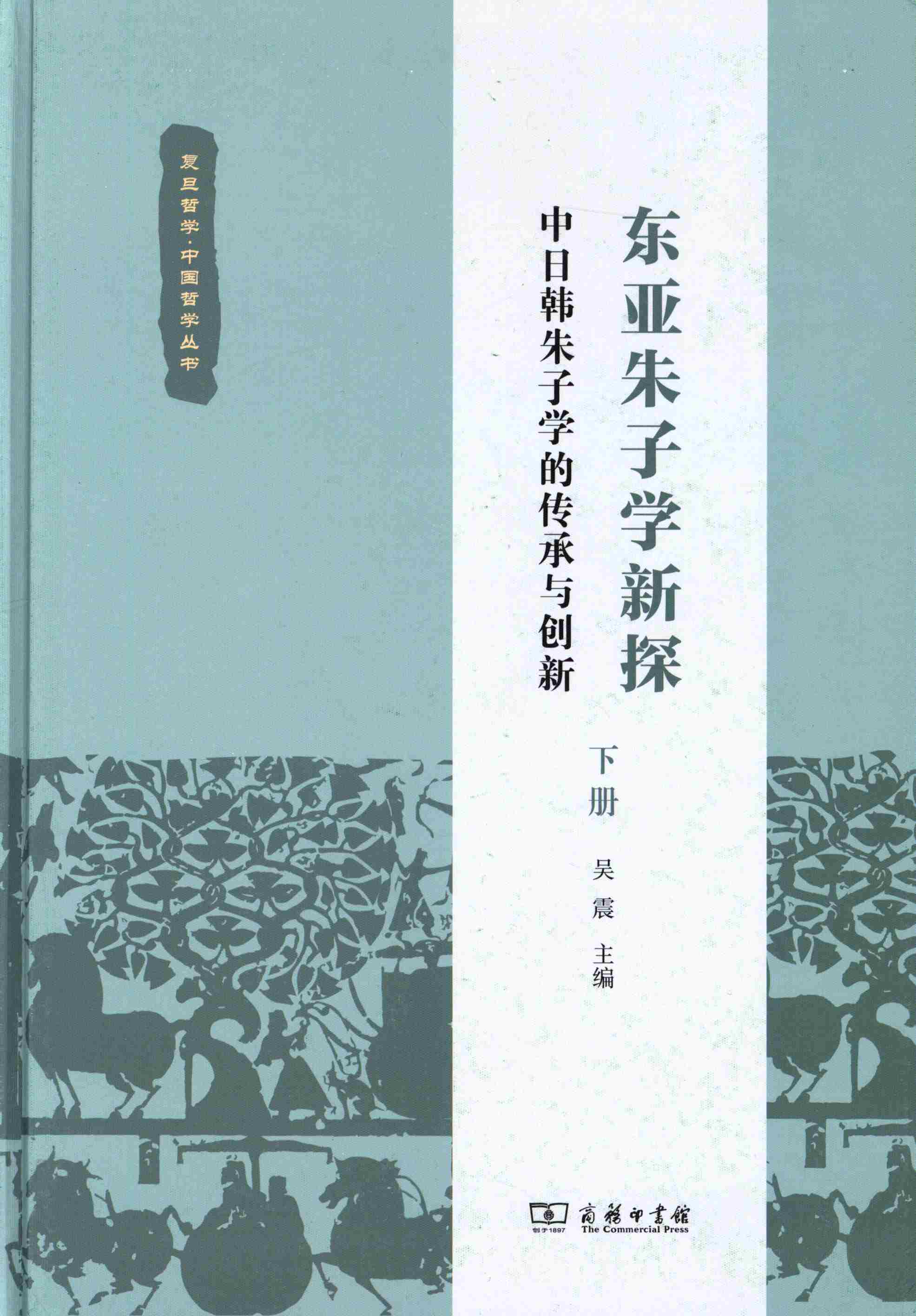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下册》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结项成果,并于今年被认定为是成果。近九十万字,吴震教授主编,由海内外中国哲学领域的一线学者组成的性团队合作分篇撰写,代表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的成果。
阅读
相关人物
谢晓东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