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三宅尚斋以及崎门学的“智藏”论
| 内容出处: |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049 |
| 颗粒名称: | 二 三宅尚斋以及崎门学的“智藏”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2 |
| 页码: | 483-494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日本江户时代崎门学派朱子学者三宅尚斋所著《智藏说》的特点和背景。这本书收集了许多关于“智藏”的论述,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的。其中楠本版和生田版是最完整的版本,将《智藏说》与附录合并构成独立的著作。《智藏说》主要收录了《礼记》和《中庸》的注释,以及山崎闇斋、佐藤直方和浅见絅斋等学者对“智藏”观点的见解。尚斋认为朱熹《玉山讲义》中的核心思想就在于“智藏”,因此编写了《智藏说》来补充《玉山讲义附录》的内容。本文分析了《智藏说》的来源和结构,并指出要深入理解崎门学者对于“智藏”观的看法,需要参考附录中的其他文献。 |
| 关键词: | 日本 朱子学 智藏说 |
内容
闇斋三大高弟(崎门三杰①)之一的三宅尚斋特别编写了《智藏说》《智藏论笔札》,收集许多中、日两方有关“智藏”的论述。佐藤直方、浅见絅斋对“智藏”的见解也收录在这两篇文章中。这两本书没有正式出版,以抄本的形式流传。据笔者的调查,三宅尚斋《智藏说》有三种抄本,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收藏其中两种版本。一是生田格抄写的版本(以下称为生田版),一是楠本硕水抄写的版本(以下称为楠本版)。另外名古屋蓬左文库所藏的中村政永编:《道学资讲》中也收入一种版本(以下称为《道学资讲》版)。《道学资讲》版《智藏说》最后附录久米订斋《读智藏说笔记》。楠本版与生田版,结构、内容皆完全一致,在三宅尚斋的《智藏说》后面,作为“智藏说附录”,除了久米订斋《读智藏说笔记》之外,还附上三宅尚斋《智藏论笔札》、若林强斋《玉山讲义师说》、幸田子善《玉山讲义笔记》、宇井默斋《读思录》。楠本版与生田版都将《智藏说》与附录各篇合并,构成《智藏说》这一独立的著作。可说是目前能够搜集到的资料中最完整的崎门“智藏”说相关文献。因此,本文根据楠本版《智藏说》来分析、探讨崎门学者的“智藏”观。
《智藏说》乃是享保十四年(1729),尚斋六十八岁时的著作。但这部著作并非开展尚斋自己的见解,而是主要收录《礼记》的《月令》《乐记》《礼运》诸篇、《礼记·中庸》的郑注、《易·系辞上》、《程氏遗书》、《正蒙》、《朱子语类》、《朱子文集》中的“智藏”相关文献,最后附录山崎闇斋、佐藤直方以及浅见絅斋针对“智藏”的见解。尚斋在跋文中说:
智藏之说,其由来久矣。至朱子详发其微意,《玉山讲义附录》,栉比其说,无复遗蕴焉。盖识智藏之意思者,而后可语祭祀卜筮之妙矣。……今编次《附录》之不载者一、二以为讲求之资云。①
由此可以确认,尚斋也认为朱熹《玉山讲义》的核心思想就在“智藏”,他为了补充保科正之编的《玉山讲义附录》的内容,而编纂这部《智藏说》。可以说《智藏说》这本也是立足于“述而不作”这一崎门学派的学术立场来撰写的。因此本书大部分由中国古籍的引文构成,从其引文中很难窥知尚斋以及崎门学者自己具体的“智藏”观。若要了解崎门学者自己的观点,势必要参考书中最后面出现的山崎闇斋、佐藤直方、浅见絅斋三者的“智藏”相关见解。但在《智藏说》中,尚斋摘录的崎门学者见解,只有四条短文而已,因此,若要深入理解崎门“智藏”论的意涵,我们除了《智藏说》之外,必须参考附录中的三宅尚斋《智藏论笔札》、久米订斋《读智藏说笔记》、若林强斋《玉山讲义师说》、幸田子善《玉山讲义笔记》等文献。
三宅尚斋在《智藏说》中摘录闇斋《土津灵神碑》的以下文句:
智藏而无迹。识此而后,可以语道体,可以论鬼神。②
在此,闇斋认为了解“智藏而无迹”这件事,才能体会“道体”以及“鬼神”的问题。崎门学者将“智藏”理解为与“道体”密切有关的概念,这一点由以下的数据也可以证明。①
夫智藏而无迹者,道体之妙也。②
知藏ハ道體仁義禮智ノコト,孟子鑿知筋ノ一處二云コトニ非ルナリ。③(中译:知藏是道体仁义礼智之事,非孟子凿知一条之处所谓之事。)
道體至極真實無妄,真味八藏ノ一字,コレアツテ天地造化ノ止ムコトナク,人倫日用ノ道ノ絶ヱルコトモナイ。④(中译:道体至极真实无妄,真味是藏之一字,有此而天地造化无止,人伦日用之道亦无绝也。)
知藏而无迹,谓之有则无迹之可见,谓之无则有理之不泯。所谓人心太极之至灵,无极而太极。⑤
如此,崎门学者将“智藏”理解为“道体”或“无极而太极”的境界。虽然看不到任何作用、现象(迹),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虚空的。若从形而上的“理”这一角度来说,确确实实有存在物,这就是“智藏”的境界。宇井默斋在《读思录》中将“冬藏”的位相认定为“寂然未发之体”:
天道则春夏秋冬无端无始,似不可分未发已发、体用、动静实然。冬藏乃天心之未发而元亨利贞之性所以立也。盖春生夏长秋收,皆有化育之可见。而冬藏则无迹之可见,岂非寂然未发之体乎。人心之未发亦犹此也。恻隐羞恶辞让皆有可为之事,而是非之心则分别其为是为非,而已无迹之可见矣。故在天道则冬藏无迹,乃元亨利贞之所以立也。在人心则分别为是为非而收敛无迹,乃仁义礼智之所以立也。天人一物、内外一理,
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①
在此我们看到在天道的“元亨利贞”中,以“冬藏无迹”的“贞”之位相为其他“元亨利”三者的根源、基础,同样在人道的“仁义礼智”中,以“收敛无迹”的“智”之位相为其他三德“仁义礼”的根源、基础这种思维逻辑。在朱熹思想中,“仁义礼智”这四德都是形而上的“性”,也就是“理”,都属于未发层次的概念。但崎门学者明显地将未发之“性”(理)的世界分为两层:有具体现象(“迹”)②的“仁义礼”之层次与没有具体现象(“迹”)的“智”之层次,而将后者视为前者所以成立的根本基础。笔者认为崎门学者在“仁义礼智”四德之中,特别将“智”抽离出来,将它视为“道体”或“太极”的理由也在这里(请参考附录的图一)。
但“收敛无迹”的“智”为什么能够成为“仁义礼”三德的根源、基础呢?既然“智”是无任何作用的“寂然未发”之存有,如何关系到“仁义礼”三德呢?我们可以参考《智藏说》所摘录的浅见絅斋之以下见解:
浅见先生曰:知是理之活者耳。知是理之体段。又曰:以物冲击物,徐徐时物不发动,急切则物飞跃突出,亦可以见贞下之元矣。朱子以静中有物为太极(说见《语类》九十六)。亦是智藏。故余尝谓:明德是知也。具众理应万事,非知而何也。舜之大知亦是道理之光耀者,即是太极。③
如此,絅斋将“知”(智)定义为“理之活者”“理之体段”。这一定义在佐藤直方的见解中也可以看到。三宅尚斋在《智藏论笔札》中引用佐藤直方的见解如下说:
理ノイキタモノカ知ソ。理ノナリカ职卜云コトヲヨク合点セヨ。物理ノッマリタコトテナケレハ涙ハ出ヌゾ。シキミヲ打ハナスニ、ソロソロウチテハハナレヌ。八ヅマヌユへナリ。ツントウテハヒョントハナレルソ。玉録知藏ノ処へ太極也卜云等語ヲ引テアルハ細ナルコト也。故二予日明德八知也卜。具衆理應萬事卜云モノ八知テナウテ何ソヤ。兎角理ノ生タモノ、理ノナリカ知シャト云コトヲ合点セヨ。孺子ノ井二入ホトアワレナト云ノ理ノツマリタコトハナイソ。故二井二入卜其偲恻隐スルソ。長者力井二入分八サホトニナイソ。コフトヒビクモノ八理ノ生?モノソ。ヒヒクト應ス。ヒヒクト云処力知ソ。ヒヒク卜應スルト云へハ、モフナリカナニトナクトモック。是カクレテ、ナリノナニモノト云二、知ホトナモノハナイソ。聖賢ノ知ハ、キラリトシテアルホト二、本来ノ知ナリ、藏ソ。小人ノハクモリテヲル。故二少ノコトテモモダック。ソレハソレ知蔵二非ス。舜ノ大智ノ如キハ理ノキラリト照テァリテ太極ソ。知八理ノ生タモノト云ヲ、カへスカへス合点セョ。石佛ニハヒヒカヌモノソ。①(中译:理之活者是为知。须体会理之体段是为智。若物理不充塞溢满胸壑,则泪不流。诚如以木击木,徐徐击之则不发动,不弹之故也,急切击之则(其木)飞跃突出。《玉录》知藏之处引“太极也”等语是细心留意也。故予曰:“明德是知也。”所谓“具众理应万事”无非是知。总之,须体会理之活者、理之体段,即是知此事。恻隐之理充塞满溢莫若孺子入井之事,故孺子入井,恻隐之心立生;若年长者入井,恻隐之心未必深刻若此,之所以响应如此,即理之活者。有所响应就有所回应,响应之处乃是知。……圣贤之知辉耀如此,亦是本来之知故也,藏也。小人之知隐晦不明,故有所磨磨蹭蹭,彼非知藏。如舜之大智,理辉耀照映,此即太极。知者即理之活者,须再三体会之,若是石佛即无响应。)
在此,直方再三强调“智”的意思就是“理ノイキタモノ”、“理ノナリ”。“イキタモノ”就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存在”的意思,“ナリ”可以翻译为“形状、样子、状态”。因此,直方的“智”义(“理ノイキタモノ”“理ノナリ”)其实是将綱斋的“智”义(“理之活者”“理之体段”)用和文表示而已,两者的意思完全一样。由此可知,在崎门学派,“理之活者”“理之体段”这两者就是“智”的核心定义,受到相当大的重视。“智”乃是“理之体段”,也就是“理”的本来面目,最根源原始的状态。关于这一定义,我们还可以理解,但“理之活者”这一定义,看字面无法马上了解其具体意义。“理之活者”到底表示什么呢?因为这段引文是使用古日文(江户时代的口语体),又是抄本手写的关系,有些字无法判别,也有意义、脉络不够清楚的地方,但笔者认为直方想要表达的整体意思大概是如下:
人类有时候会感动流泪,那是因为人类内在之“理”以“ツマリタ”状态,亦即紧张充实的状态存在待命,而面对各种情况,其“理”会回应的缘故。在看到婴儿快掉入水井时,马上出现“アハレ(可怜)”这种恻隐之情,也是因为存在着紧张充实的“理”的关系。如此,“理”具有按照外界的刺激,自然“ヒビク”(响应)的功能。因为“理”会响应,所以我们会产生各种情感,感动流泪。“理”会响应,因此“理”并不是死理,而是活生生充满生命力而起作用(“应ス”)的存有。也可以说,这种活生生的响应功能本身就是“理”的真相。“智”就是从这一角度来形容“理”的概念。因此“智”オ是“理”的本来形态,亦即“理之体段”。直方将这种“理”活化着,若碰到它就会敏锐地响应的状态用“キラリ”(闪耀)一词来形容。直方认为“石佛”面对任何情况,受到任何刺激都不会响应,是因为石佛的“理”并没有活化,不是活生生闪耀的,也就是没有“智”的缘故。
浅见綱斋也与直方相同,从“响应”(“ヒビク”)这一角度来说明“知”(智)。
事物ノ黒白是非善悪即固ヨリ吾心ニアリ。故事物ノ白黒ノナリカキラリト吾心二照テ、ドフ云コトナシニアルハ即知ゾ。ドフトナリトモ、ヲコツケ八知二ナリカ出来テ本二非ス。本来ノ知八譬ハ此家ニ夕タミ六帖敷ソナレハ六帖敷卜云カ、ナントナシ二心二キラリト照テアリ。此カ理卜知覚卜更二ハナレヌト云モノソ。知藏ノ極ノ吟味ノッマリノ、コレニナルコトソ。扔此カ貞下ノ元卜云コトニ引付テ、ズント面白テ、ズントスマシタコトソ。人心二事事物物ノキラトアルコトデ、サワルトヒビクモノカアルソ。知力明德卜云モココゾ。サテ知力四ノ者ノアタマト云モココゾ。仁卜云モ此サワルトヒビクモノカナクテハ出来ヌ筈ソ。或問曰、然八仁カアタマト云ハ如何ゾ。籾ッマル所ハトウデモ仁ナルカ。曰、ソノヨウニ引合テ云ハムツチャトシタコトソ。知力四者ヲ兼ヌルトモ、仁カ四者ヲ兼ヌルトモ云ルルソ。ッメテ云へ八畢竟一ッニナルソ。①(中译:事物之黑白、是非、善恶即固在吾心,故事物之白黑真相,辉耀映照于吾心,自然显现,此即是知。……本来之知,譬如此家有六张草甸,就云有六张草甸,自然而然辉耀映照于心,此即所谓理与知觉不相离,再三吟味知藏之极之目的,正在达此境地。再者[若将此]与贞下之元相互关联,则是极有趣、极清楚之事。人心中有事事物物闪耀者,乃稍一触碰即会响应者,之所以云知是明德亦在于此。再者,之所以云知是四者之首亦在于此。即使是仁,若无此稍一碰触,即会响应者,则无法成立。或问曰:然则何以云以仁为首?莫非仁方オ是充塞溢满胸壑者。曰:如此强合二者,牽强为说,甚是勉强。可说知兼四者,亦可说仁兼四者,若追根究底,毕竟为一。)
如此,綱斋也承认人心中有相应于外界的刺激而闪耀地响应的存在,将它视为“知”(智)。綱斋认为因为有会响应的“智”,所以才能产生“仁”,或者也可以说因为有“智”,所以“仁”才能产生意义、作用。据直方、綱斋的思维逻辑,“智”意味着“理”所具有的作为“本体”产生“作用”的形而上性能量本身,因此,不仅“仁”而已,一切万物之“理”以“智”为基础才能产生各种作用、各种意义。若没有“智”,一切之“理”就变成“死理”,丧失其具体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仁、义、礼、智四者中都存在着“智”,“智”贯彻、贯通四德。对崎门学者而言,朱熹思想中,除了“仁”兼四德之外,也有“智”兼四德之观点的理由就在这里。
因为有“智”(会响应、感应的形而上层次的能量),所以“仁义礼”能够作为“本体”确立,实际生起具体作用。因此,如上指出,宇井默斋说“收敛无迹”之“智”的存在オ是“仁义礼智之所以立”的基础。
“智”的功能只在心内分别是非,并没有展现具体现象,亦即“收敛无迹”,但对崎门学者而言,“收敛无迹”并不是消极的状态,而是包含着所有作用、现象之潜力的最充实状态。由于还没有作为具体现象发泄自己,因此它是极度充满能量的充实状态。于是,幸田子善在《玉山讲义笔记》中如下说道:
蓋冬者藏也、地中二引込コミ、梨柿熟シテシマフテ、天地ノハタラキハナニモナク、隱居シテ何モ蟄ハナイガソノ藏ル処、来年ノヲヲゴトヲスル、ソコ二以テヲル。又冬ヲシマウ、シカレバ冬二ハ二役ヲ以テヲルコト也。来年ノイロイロノ細工、コノ中二出来テヲルコトナリ。智有藏之義、易ノ顕仁藏用カラ出タコト也。コフ云コトユへ、人ノ智八ソトニ出ルカワルイ。浅ヒ智力、、ソトニ出ル。深ヒ智八ソトニ出ヌコト也。ソレユへ舜ノ智デモリコフ立テハセヌ。人ノ智ヲトラレルコト、大智八内へ内ヘシヅムト朱子ノ語アリ。智八ソコニアリテ物ヲ分ツバカリジャ。ソレハワルイ、ソレハヨイト、ソトへ出ルト義二ナルコト也。ソレユへ朱子ノ智ハ太極ジャト云ハレタモソレデ、ハタラタモノノ内ニハイリテヲルガ智ジャ。然ルニ朱子ノ説二モアリテ、老子ノ智ガココニ近ヒ。弯ハ用ユレハワルイト見テ、身分ハタラカズ、人ヲッカフテ無為卜シタ。①(中译:盖冬者藏也,缩隐于地中,梨柿熟而完尽,天地之活动运化殆尽,隐居蛰伏而不出。然其所藏处,具隔年之大用。又冬为藏,故此冬有两用也。来年之诸般运用,已然备于此中。智有藏之义,系源自《易》之“显诸仁,藏诸用”也。是故,人智显于外者不佳,浅智现于外,深智不出外也,故舜之智亦未现其聪明。论及人之智,朱子亦言及“大智深沉向内”。智者,仅在分别事物何者不好、何者为好等等而已。分辨之智出于外,则为义也。故朱子曰“智乃太极”,其理亦在于此,存于发用之中者是为智。然诚如朱子亦言:“老子之智近于此。”“智”以为发用是为不善,故其自身不发用,然却使人发其用,以维持其无为之境界。)
如此,幸田子善在没有向外展现具体作用这一点看出“智”的积极意义。对幸田而言,“智”虽然自己没有具体的作用,不会展现具体现象,但它具有使其他“理”生起“作用”、展现具体“现象”(“自分ハタラカズ、人ヲッカフ”)的功能、特色。其实正因为自己没有具体作用,所以オ成为使“万理”生起“作用”的基础,若其具有某种具体的作用、现象,那意味着它的功能、发展方向将受到某一个限定,无法成为“万理”的普遍性基础、根源。根据幸田的思维脉络,朱熹将“收敛无迹”的“智”定义为“太极”的理由也在这里。诚如众所皆知的,朱熹思想中的“太极”就是“无极”,未受到任何限定的未发层次最根源的“理”,亦即“万理”的起点、根源,笔者认为崎门学者所理解的“智藏”就等于这种“无极而太极”的位相。附带而言,“太极”就是“道”的根源、本体,亦即“道体”,因此,如前面所说,崎门学者将“智”理解为“道体”。
另外,笔者认为以上所介绍的崎门学者之“智”理解或“智藏”观中,将“仁义礼智”(或者“元亨利贞”)四者的循环从本体能量或形而上生命力的流露与收敛这一角度来理解。“智”(贞)相当于冬天的位相,虽然看不到任何现象、作用,但其中充满展现各种现象的本体能量、潜カ,只是还没发现而已。到了“仁”(元),亦即春天的位相,其本体能量开始向外展现而现象化、作用化,到了“礼”(亨),亦即夏天的位相,其现象化的程度达到最高点,接下来又开始向内收敛,形而下的现象、作用渐渐缩小,“义”(利),亦即秋天的位相就是代表这种收敛之德,经过“义”的位相,这一收敛越来越加速,到了“智”的位相,其现象、作用完全消失,回到原来的“寂然无迹”之“智藏”状态。这一循环,若从形而下的现象、作用的角度来看,“智”之位相指数是零,接下来渐渐增加,到了“礼”之位相成为最高的一百,但接着渐渐减少,到了“智”,其指数又成为零。不过,外在的“现象、作用”原来是内在的“本体”本身展现出来的,因此,形而下的“现象、作用”之增加等于形而上的“本体”能量本身的减少,所以若从形而上的“本体”能量这一角度来看,同样的四德循环呈现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作为四德之起点的“智”之位相的指数才是一百,接着渐渐减少,而到了“礼”的位相变成零,过了“礼”之后,渐渐增加,到了“智”又恢复成原来的指数一百。因此,若以形而上的“本体”世界为标准,可以说“智”的位相才是最完整、最充实、最有活力的状态(请参考附录的图二)。幕末的崎门派学者楠本端山将“智藏”的“无迹”“至寂”之境界用“活泼泼地”一词来形容的理由也在这里:
知藏之无迹,冬收之至寂,无声无臭之全体,活泼泼地。①
根据崎门学者的逻辑,我们在“至寂”“无迹”的“智藏”之位相中可以看到尚未受到限定的、尚未发散现象化的“理”之最原始、完整姿态,亦即“理”之原貌。对崎门学者而言,体会“智藏”等于了解“理”本身。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明白了崎门学者再三强调体会“智藏”才能真正了解“道体”“太极”的深层理由。
最后附带而言,在上列的“智藏”相关文献中,崎门学者有时说“智藏”,有时说“知藏”,看似将“智”与“知”没有严格加以区别。这可能在日语手抄本上,有时无意识地把“智”简略写成“知”的关系。严格而言,“智”与“知”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用说,“智藏”才是正确的说法。那么“智”与“知”的差别在哪里?崎门学者如何理解“智”与“知”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三宅尚斋如下说明:
知,为智之用,非矣。知者心之神明,妙众理。是兼体用而言。便是智之兼气质而言者也。故知有深浅,有广狭也(原注:虚灵知觉之知,与大学致知之知同)。妙众理,静时知照而藏,动时与理运用。犹藏诸冬而发诸冬也。①
如此尚斋明确将“知”定义为“智”(理、本体)加气质的概念;换言之,将“智”从体用合并的角度来说明的概念。尚斋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根据朱熹的“知”义。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将“知”解释为“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的存在。②自不待言地,“妙众理”涉及“本体”,“宰万物”则表示其“作用”。尚斋根据朱熹的这一“知”诠释,认为“知”会“兼体用”③,进而认为“知”等于作为“人之神明”的“心”。尚斋如下说明:
心,虚灵知觉,人之神明,具众理,应万事者也。知,心之神明,妙众理,裁万事者也。言心,知觉在其中。分而言之,则心,人之神明,虚而照者也。知,心之神明,活底者也。故心,人之神,知,又心之神。知神一,
故曰:神发知。④
万物备于我。而知则运用其理,以应万物者。我心未即物时,只是一
理浑然,无声臭。⑤
人不只内具众理,还有运用其理而反应万事万物的功能,尚斋认为这种功能就是“心”,亦即“知”。根据尚斋的思维脉络,因为有“知”这一功能,所以仁、义、礼等“理”实际产生作用,可以避免变成丧失感应能力的“死理”。人所内具的理能够活泼泼地感应的原因就在“知”,此“知”的本体根据就是“智”。在这个意义上,“知”表示“理”之生命能量本身的展现,亦即“活底者”的面貌。而其生命能量的形而上根据就是“智”。崎门学者将“智”定义为“理之活者”的原因也在这里。
《智藏说》乃是享保十四年(1729),尚斋六十八岁时的著作。但这部著作并非开展尚斋自己的见解,而是主要收录《礼记》的《月令》《乐记》《礼运》诸篇、《礼记·中庸》的郑注、《易·系辞上》、《程氏遗书》、《正蒙》、《朱子语类》、《朱子文集》中的“智藏”相关文献,最后附录山崎闇斋、佐藤直方以及浅见絅斋针对“智藏”的见解。尚斋在跋文中说:
智藏之说,其由来久矣。至朱子详发其微意,《玉山讲义附录》,栉比其说,无复遗蕴焉。盖识智藏之意思者,而后可语祭祀卜筮之妙矣。……今编次《附录》之不载者一、二以为讲求之资云。①
由此可以确认,尚斋也认为朱熹《玉山讲义》的核心思想就在“智藏”,他为了补充保科正之编的《玉山讲义附录》的内容,而编纂这部《智藏说》。可以说《智藏说》这本也是立足于“述而不作”这一崎门学派的学术立场来撰写的。因此本书大部分由中国古籍的引文构成,从其引文中很难窥知尚斋以及崎门学者自己具体的“智藏”观。若要了解崎门学者自己的观点,势必要参考书中最后面出现的山崎闇斋、佐藤直方、浅见絅斋三者的“智藏”相关见解。但在《智藏说》中,尚斋摘录的崎门学者见解,只有四条短文而已,因此,若要深入理解崎门“智藏”论的意涵,我们除了《智藏说》之外,必须参考附录中的三宅尚斋《智藏论笔札》、久米订斋《读智藏说笔记》、若林强斋《玉山讲义师说》、幸田子善《玉山讲义笔记》等文献。
三宅尚斋在《智藏说》中摘录闇斋《土津灵神碑》的以下文句:
智藏而无迹。识此而后,可以语道体,可以论鬼神。②
在此,闇斋认为了解“智藏而无迹”这件事,才能体会“道体”以及“鬼神”的问题。崎门学者将“智藏”理解为与“道体”密切有关的概念,这一点由以下的数据也可以证明。①
夫智藏而无迹者,道体之妙也。②
知藏ハ道體仁義禮智ノコト,孟子鑿知筋ノ一處二云コトニ非ルナリ。③(中译:知藏是道体仁义礼智之事,非孟子凿知一条之处所谓之事。)
道體至極真實無妄,真味八藏ノ一字,コレアツテ天地造化ノ止ムコトナク,人倫日用ノ道ノ絶ヱルコトモナイ。④(中译:道体至极真实无妄,真味是藏之一字,有此而天地造化无止,人伦日用之道亦无绝也。)
知藏而无迹,谓之有则无迹之可见,谓之无则有理之不泯。所谓人心太极之至灵,无极而太极。⑤
如此,崎门学者将“智藏”理解为“道体”或“无极而太极”的境界。虽然看不到任何作用、现象(迹),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虚空的。若从形而上的“理”这一角度来说,确确实实有存在物,这就是“智藏”的境界。宇井默斋在《读思录》中将“冬藏”的位相认定为“寂然未发之体”:
天道则春夏秋冬无端无始,似不可分未发已发、体用、动静实然。冬藏乃天心之未发而元亨利贞之性所以立也。盖春生夏长秋收,皆有化育之可见。而冬藏则无迹之可见,岂非寂然未发之体乎。人心之未发亦犹此也。恻隐羞恶辞让皆有可为之事,而是非之心则分别其为是为非,而已无迹之可见矣。故在天道则冬藏无迹,乃元亨利贞之所以立也。在人心则分别为是为非而收敛无迹,乃仁义礼智之所以立也。天人一物、内外一理,
知道者默而观之可也。①
在此我们看到在天道的“元亨利贞”中,以“冬藏无迹”的“贞”之位相为其他“元亨利”三者的根源、基础,同样在人道的“仁义礼智”中,以“收敛无迹”的“智”之位相为其他三德“仁义礼”的根源、基础这种思维逻辑。在朱熹思想中,“仁义礼智”这四德都是形而上的“性”,也就是“理”,都属于未发层次的概念。但崎门学者明显地将未发之“性”(理)的世界分为两层:有具体现象(“迹”)②的“仁义礼”之层次与没有具体现象(“迹”)的“智”之层次,而将后者视为前者所以成立的根本基础。笔者认为崎门学者在“仁义礼智”四德之中,特别将“智”抽离出来,将它视为“道体”或“太极”的理由也在这里(请参考附录的图一)。
但“收敛无迹”的“智”为什么能够成为“仁义礼”三德的根源、基础呢?既然“智”是无任何作用的“寂然未发”之存有,如何关系到“仁义礼”三德呢?我们可以参考《智藏说》所摘录的浅见絅斋之以下见解:
浅见先生曰:知是理之活者耳。知是理之体段。又曰:以物冲击物,徐徐时物不发动,急切则物飞跃突出,亦可以见贞下之元矣。朱子以静中有物为太极(说见《语类》九十六)。亦是智藏。故余尝谓:明德是知也。具众理应万事,非知而何也。舜之大知亦是道理之光耀者,即是太极。③
如此,絅斋将“知”(智)定义为“理之活者”“理之体段”。这一定义在佐藤直方的见解中也可以看到。三宅尚斋在《智藏论笔札》中引用佐藤直方的见解如下说:
理ノイキタモノカ知ソ。理ノナリカ职卜云コトヲヨク合点セヨ。物理ノッマリタコトテナケレハ涙ハ出ヌゾ。シキミヲ打ハナスニ、ソロソロウチテハハナレヌ。八ヅマヌユへナリ。ツントウテハヒョントハナレルソ。玉録知藏ノ処へ太極也卜云等語ヲ引テアルハ細ナルコト也。故二予日明德八知也卜。具衆理應萬事卜云モノ八知テナウテ何ソヤ。兎角理ノ生タモノ、理ノナリカ知シャト云コトヲ合点セヨ。孺子ノ井二入ホトアワレナト云ノ理ノツマリタコトハナイソ。故二井二入卜其偲恻隐スルソ。長者力井二入分八サホトニナイソ。コフトヒビクモノ八理ノ生?モノソ。ヒヒクト應ス。ヒヒクト云処力知ソ。ヒヒク卜應スルト云へハ、モフナリカナニトナクトモック。是カクレテ、ナリノナニモノト云二、知ホトナモノハナイソ。聖賢ノ知ハ、キラリトシテアルホト二、本来ノ知ナリ、藏ソ。小人ノハクモリテヲル。故二少ノコトテモモダック。ソレハソレ知蔵二非ス。舜ノ大智ノ如キハ理ノキラリト照テァリテ太極ソ。知八理ノ生タモノト云ヲ、カへスカへス合点セョ。石佛ニハヒヒカヌモノソ。①(中译:理之活者是为知。须体会理之体段是为智。若物理不充塞溢满胸壑,则泪不流。诚如以木击木,徐徐击之则不发动,不弹之故也,急切击之则(其木)飞跃突出。《玉录》知藏之处引“太极也”等语是细心留意也。故予曰:“明德是知也。”所谓“具众理应万事”无非是知。总之,须体会理之活者、理之体段,即是知此事。恻隐之理充塞满溢莫若孺子入井之事,故孺子入井,恻隐之心立生;若年长者入井,恻隐之心未必深刻若此,之所以响应如此,即理之活者。有所响应就有所回应,响应之处乃是知。……圣贤之知辉耀如此,亦是本来之知故也,藏也。小人之知隐晦不明,故有所磨磨蹭蹭,彼非知藏。如舜之大智,理辉耀照映,此即太极。知者即理之活者,须再三体会之,若是石佛即无响应。)
在此,直方再三强调“智”的意思就是“理ノイキタモノ”、“理ノナリ”。“イキタモノ”就是“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存在”的意思,“ナリ”可以翻译为“形状、样子、状态”。因此,直方的“智”义(“理ノイキタモノ”“理ノナリ”)其实是将綱斋的“智”义(“理之活者”“理之体段”)用和文表示而已,两者的意思完全一样。由此可知,在崎门学派,“理之活者”“理之体段”这两者就是“智”的核心定义,受到相当大的重视。“智”乃是“理之体段”,也就是“理”的本来面目,最根源原始的状态。关于这一定义,我们还可以理解,但“理之活者”这一定义,看字面无法马上了解其具体意义。“理之活者”到底表示什么呢?因为这段引文是使用古日文(江户时代的口语体),又是抄本手写的关系,有些字无法判别,也有意义、脉络不够清楚的地方,但笔者认为直方想要表达的整体意思大概是如下:
人类有时候会感动流泪,那是因为人类内在之“理”以“ツマリタ”状态,亦即紧张充实的状态存在待命,而面对各种情况,其“理”会回应的缘故。在看到婴儿快掉入水井时,马上出现“アハレ(可怜)”这种恻隐之情,也是因为存在着紧张充实的“理”的关系。如此,“理”具有按照外界的刺激,自然“ヒビク”(响应)的功能。因为“理”会响应,所以我们会产生各种情感,感动流泪。“理”会响应,因此“理”并不是死理,而是活生生充满生命力而起作用(“应ス”)的存有。也可以说,这种活生生的响应功能本身就是“理”的真相。“智”就是从这一角度来形容“理”的概念。因此“智”オ是“理”的本来形态,亦即“理之体段”。直方将这种“理”活化着,若碰到它就会敏锐地响应的状态用“キラリ”(闪耀)一词来形容。直方认为“石佛”面对任何情况,受到任何刺激都不会响应,是因为石佛的“理”并没有活化,不是活生生闪耀的,也就是没有“智”的缘故。
浅见綱斋也与直方相同,从“响应”(“ヒビク”)这一角度来说明“知”(智)。
事物ノ黒白是非善悪即固ヨリ吾心ニアリ。故事物ノ白黒ノナリカキラリト吾心二照テ、ドフ云コトナシニアルハ即知ゾ。ドフトナリトモ、ヲコツケ八知二ナリカ出来テ本二非ス。本来ノ知八譬ハ此家ニ夕タミ六帖敷ソナレハ六帖敷卜云カ、ナントナシ二心二キラリト照テアリ。此カ理卜知覚卜更二ハナレヌト云モノソ。知藏ノ極ノ吟味ノッマリノ、コレニナルコトソ。扔此カ貞下ノ元卜云コトニ引付テ、ズント面白テ、ズントスマシタコトソ。人心二事事物物ノキラトアルコトデ、サワルトヒビクモノカアルソ。知力明德卜云モココゾ。サテ知力四ノ者ノアタマト云モココゾ。仁卜云モ此サワルトヒビクモノカナクテハ出来ヌ筈ソ。或問曰、然八仁カアタマト云ハ如何ゾ。籾ッマル所ハトウデモ仁ナルカ。曰、ソノヨウニ引合テ云ハムツチャトシタコトソ。知力四者ヲ兼ヌルトモ、仁カ四者ヲ兼ヌルトモ云ルルソ。ッメテ云へ八畢竟一ッニナルソ。①(中译:事物之黑白、是非、善恶即固在吾心,故事物之白黑真相,辉耀映照于吾心,自然显现,此即是知。……本来之知,譬如此家有六张草甸,就云有六张草甸,自然而然辉耀映照于心,此即所谓理与知觉不相离,再三吟味知藏之极之目的,正在达此境地。再者[若将此]与贞下之元相互关联,则是极有趣、极清楚之事。人心中有事事物物闪耀者,乃稍一触碰即会响应者,之所以云知是明德亦在于此。再者,之所以云知是四者之首亦在于此。即使是仁,若无此稍一碰触,即会响应者,则无法成立。或问曰:然则何以云以仁为首?莫非仁方オ是充塞溢满胸壑者。曰:如此强合二者,牽强为说,甚是勉强。可说知兼四者,亦可说仁兼四者,若追根究底,毕竟为一。)
如此,綱斋也承认人心中有相应于外界的刺激而闪耀地响应的存在,将它视为“知”(智)。綱斋认为因为有会响应的“智”,所以才能产生“仁”,或者也可以说因为有“智”,所以“仁”才能产生意义、作用。据直方、綱斋的思维逻辑,“智”意味着“理”所具有的作为“本体”产生“作用”的形而上性能量本身,因此,不仅“仁”而已,一切万物之“理”以“智”为基础才能产生各种作用、各种意义。若没有“智”,一切之“理”就变成“死理”,丧失其具体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仁、义、礼、智四者中都存在着“智”,“智”贯彻、贯通四德。对崎门学者而言,朱熹思想中,除了“仁”兼四德之外,也有“智”兼四德之观点的理由就在这里。
因为有“智”(会响应、感应的形而上层次的能量),所以“仁义礼”能够作为“本体”确立,实际生起具体作用。因此,如上指出,宇井默斋说“收敛无迹”之“智”的存在オ是“仁义礼智之所以立”的基础。
“智”的功能只在心内分别是非,并没有展现具体现象,亦即“收敛无迹”,但对崎门学者而言,“收敛无迹”并不是消极的状态,而是包含着所有作用、现象之潜力的最充实状态。由于还没有作为具体现象发泄自己,因此它是极度充满能量的充实状态。于是,幸田子善在《玉山讲义笔记》中如下说道:
蓋冬者藏也、地中二引込コミ、梨柿熟シテシマフテ、天地ノハタラキハナニモナク、隱居シテ何モ蟄ハナイガソノ藏ル処、来年ノヲヲゴトヲスル、ソコ二以テヲル。又冬ヲシマウ、シカレバ冬二ハ二役ヲ以テヲルコト也。来年ノイロイロノ細工、コノ中二出来テヲルコトナリ。智有藏之義、易ノ顕仁藏用カラ出タコト也。コフ云コトユへ、人ノ智八ソトニ出ルカワルイ。浅ヒ智力、、ソトニ出ル。深ヒ智八ソトニ出ヌコト也。ソレユへ舜ノ智デモリコフ立テハセヌ。人ノ智ヲトラレルコト、大智八内へ内ヘシヅムト朱子ノ語アリ。智八ソコニアリテ物ヲ分ツバカリジャ。ソレハワルイ、ソレハヨイト、ソトへ出ルト義二ナルコト也。ソレユへ朱子ノ智ハ太極ジャト云ハレタモソレデ、ハタラタモノノ内ニハイリテヲルガ智ジャ。然ルニ朱子ノ説二モアリテ、老子ノ智ガココニ近ヒ。弯ハ用ユレハワルイト見テ、身分ハタラカズ、人ヲッカフテ無為卜シタ。①(中译:盖冬者藏也,缩隐于地中,梨柿熟而完尽,天地之活动运化殆尽,隐居蛰伏而不出。然其所藏处,具隔年之大用。又冬为藏,故此冬有两用也。来年之诸般运用,已然备于此中。智有藏之义,系源自《易》之“显诸仁,藏诸用”也。是故,人智显于外者不佳,浅智现于外,深智不出外也,故舜之智亦未现其聪明。论及人之智,朱子亦言及“大智深沉向内”。智者,仅在分别事物何者不好、何者为好等等而已。分辨之智出于外,则为义也。故朱子曰“智乃太极”,其理亦在于此,存于发用之中者是为智。然诚如朱子亦言:“老子之智近于此。”“智”以为发用是为不善,故其自身不发用,然却使人发其用,以维持其无为之境界。)
如此,幸田子善在没有向外展现具体作用这一点看出“智”的积极意义。对幸田而言,“智”虽然自己没有具体的作用,不会展现具体现象,但它具有使其他“理”生起“作用”、展现具体“现象”(“自分ハタラカズ、人ヲッカフ”)的功能、特色。其实正因为自己没有具体作用,所以オ成为使“万理”生起“作用”的基础,若其具有某种具体的作用、现象,那意味着它的功能、发展方向将受到某一个限定,无法成为“万理”的普遍性基础、根源。根据幸田的思维脉络,朱熹将“收敛无迹”的“智”定义为“太极”的理由也在这里。诚如众所皆知的,朱熹思想中的“太极”就是“无极”,未受到任何限定的未发层次最根源的“理”,亦即“万理”的起点、根源,笔者认为崎门学者所理解的“智藏”就等于这种“无极而太极”的位相。附带而言,“太极”就是“道”的根源、本体,亦即“道体”,因此,如前面所说,崎门学者将“智”理解为“道体”。
另外,笔者认为以上所介绍的崎门学者之“智”理解或“智藏”观中,将“仁义礼智”(或者“元亨利贞”)四者的循环从本体能量或形而上生命力的流露与收敛这一角度来理解。“智”(贞)相当于冬天的位相,虽然看不到任何现象、作用,但其中充满展现各种现象的本体能量、潜カ,只是还没发现而已。到了“仁”(元),亦即春天的位相,其本体能量开始向外展现而现象化、作用化,到了“礼”(亨),亦即夏天的位相,其现象化的程度达到最高点,接下来又开始向内收敛,形而下的现象、作用渐渐缩小,“义”(利),亦即秋天的位相就是代表这种收敛之德,经过“义”的位相,这一收敛越来越加速,到了“智”的位相,其现象、作用完全消失,回到原来的“寂然无迹”之“智藏”状态。这一循环,若从形而下的现象、作用的角度来看,“智”之位相指数是零,接下来渐渐增加,到了“礼”之位相成为最高的一百,但接着渐渐减少,到了“智”,其指数又成为零。不过,外在的“现象、作用”原来是内在的“本体”本身展现出来的,因此,形而下的“现象、作用”之增加等于形而上的“本体”能量本身的减少,所以若从形而上的“本体”能量这一角度来看,同样的四德循环呈现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作为四德之起点的“智”之位相的指数才是一百,接着渐渐减少,而到了“礼”的位相变成零,过了“礼”之后,渐渐增加,到了“智”又恢复成原来的指数一百。因此,若以形而上的“本体”世界为标准,可以说“智”的位相才是最完整、最充实、最有活力的状态(请参考附录的图二)。幕末的崎门派学者楠本端山将“智藏”的“无迹”“至寂”之境界用“活泼泼地”一词来形容的理由也在这里:
知藏之无迹,冬收之至寂,无声无臭之全体,活泼泼地。①
根据崎门学者的逻辑,我们在“至寂”“无迹”的“智藏”之位相中可以看到尚未受到限定的、尚未发散现象化的“理”之最原始、完整姿态,亦即“理”之原貌。对崎门学者而言,体会“智藏”等于了解“理”本身。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明白了崎门学者再三强调体会“智藏”才能真正了解“道体”“太极”的深层理由。
最后附带而言,在上列的“智藏”相关文献中,崎门学者有时说“智藏”,有时说“知藏”,看似将“智”与“知”没有严格加以区别。这可能在日语手抄本上,有时无意识地把“智”简略写成“知”的关系。严格而言,“智”与“知”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用说,“智藏”才是正确的说法。那么“智”与“知”的差别在哪里?崎门学者如何理解“智”与“知”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三宅尚斋如下说明:
知,为智之用,非矣。知者心之神明,妙众理。是兼体用而言。便是智之兼气质而言者也。故知有深浅,有广狭也(原注:虚灵知觉之知,与大学致知之知同)。妙众理,静时知照而藏,动时与理运用。犹藏诸冬而发诸冬也。①
如此尚斋明确将“知”定义为“智”(理、本体)加气质的概念;换言之,将“智”从体用合并的角度来说明的概念。尚斋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根据朱熹的“知”义。
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将“知”解释为“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的存在。②自不待言地,“妙众理”涉及“本体”,“宰万物”则表示其“作用”。尚斋根据朱熹的这一“知”诠释,认为“知”会“兼体用”③,进而认为“知”等于作为“人之神明”的“心”。尚斋如下说明:
心,虚灵知觉,人之神明,具众理,应万事者也。知,心之神明,妙众理,裁万事者也。言心,知觉在其中。分而言之,则心,人之神明,虚而照者也。知,心之神明,活底者也。故心,人之神,知,又心之神。知神一,
故曰:神发知。④
万物备于我。而知则运用其理,以应万物者。我心未即物时,只是一
理浑然,无声臭。⑤
人不只内具众理,还有运用其理而反应万事万物的功能,尚斋认为这种功能就是“心”,亦即“知”。根据尚斋的思维脉络,因为有“知”这一功能,所以仁、义、礼等“理”实际产生作用,可以避免变成丧失感应能力的“死理”。人所内具的理能够活泼泼地感应的原因就在“知”,此“知”的本体根据就是“智”。在这个意义上,“知”表示“理”之生命能量本身的展现,亦即“活底者”的面貌。而其生命能量的形而上根据就是“智”。崎门学者将“智”定义为“理之活者”的原因也在这里。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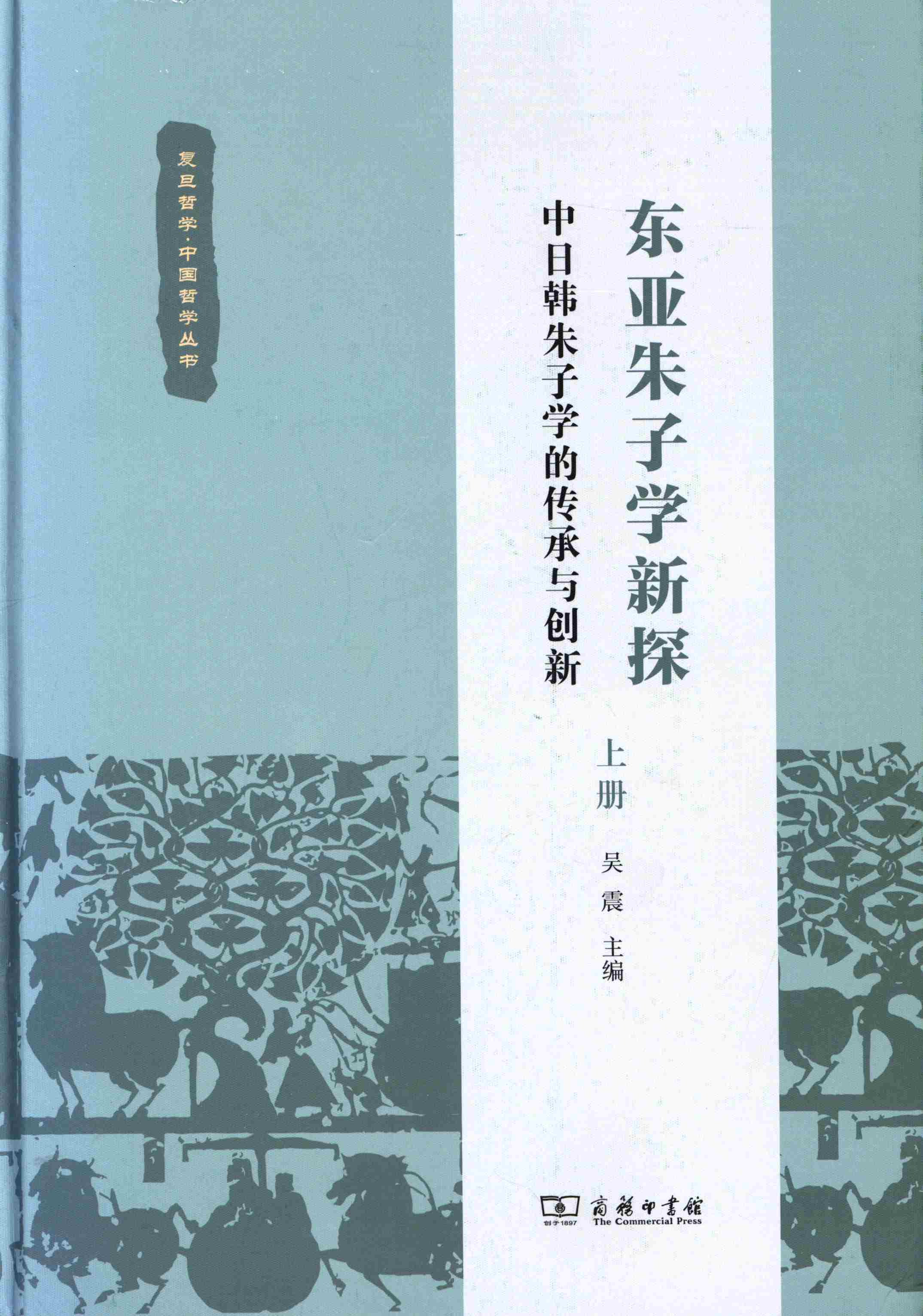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这部《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结项成果,并于今年被认定为是成果。全书共由四篇三十七章组成,近九十万字,吴震教授主编,由海内外中国哲学领域的一线学者组成的性团队合作分篇撰写,代表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的成果。本书的四篇结构是:一、“东亚儒学与中国朱子学”;二、“日本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三、“韩国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比较研究与回顾综述”;后是两篇“附录”,分别是“近十年来日本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近十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本书进一步拓展了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广度,可以认为,通过本书的出版,“东亚朱子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有充分理由得以成立(如同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东亚儒学”或“东亚哲学”已渐形成一般),进而,本书的出版也得以重新展现了中国哲学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