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汉语会汉语
| 内容出处: |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7027 |
| 颗粒名称: | (二)以汉语会汉语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5 |
| 页码: | 407-41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日本学者荻生徂徕的古文辞学方法和对经典解释学的看法。他认为,掌握中文需要直接学习汉语,而不是依赖日本传统的训读法。他总结了一套“学问之法”,主张直接阅读汉籍,并认为这是最上乘的学习方法。此外,他还强调了“以古言征古义”的经典解释学方法,主张通过把握圣人之道来理解经典。他的读书法在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一种风气。 |
| 关键词: | 徂徕学派 日本 辞学方法 |
内容
不用说,对徂徕而言,中文是一门外语,故阅读中国典籍首先须通过语言关,然而根据他阅读中国古书的一个经验之谈,他的古汉语完全是无师自通的,表明他似乎有非同寻常的语言天赋:
记予侍先大夫,七八岁时,先大夫命予录其日间行事,或朝府,或客来,说何事,作何事,及风雨阴晴,家人琐细事,皆录,每夜临卧,必口授笔受,予十一二时,既能自读书,未尝受句读,盖由此故。……少小耳目
所熟,故随读便解,不烦讲说耳。④
盖谓徂徕七八岁时就能写字,十一二岁时,在从未受过“句读”训练的情况下,便能自己“读书”且“随读便解”,无须旁人指点,也不依赖他人“讲说”。此处“句读”特指日本的一种阅读汉籍的训读法,又称“和训”——即依日语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语序,将汉语的语序颠倒过来读,徂徕贬称其为“和训回环之读”①,这是当时日本人阅读汉籍的一种主要手法。然而徂徕却完全不受此拘限便能自由地阅读汉籍,据其自述,这是得益于“少小”时,其父对他的“口授笔受”。对于徂徕这番自述,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质疑,因为通过自学而掌握一门外语并非绝对不可能。但是徂徕根据他的经验,归结出直接“以汉语会汉语”的读书法(徂徕称之为“学问之法”),与他在经典解释学上主张“以古言征古义”的方法配套,这就值得关注。
徂徕晚年在《译文筌蹄题言十则》中,就如何做学问总结出一套方法论原则,他指出他特别厌恶“讲说”——即指听人讲解汉书,以为“讲说”有“十害”而无一利,由此“十害”还将引发“百弊”,其病根在于“贵耳贱目,废读务听”,为断绝此类弊害,所以徂徕竭力主张直接读书,他引以为自豪的“最上乘”的学习方法是:
故予尝为蒙生定学问之法,先为崎阳之学②,教以俗语,诵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子史集四部书,势
如破竹,是最上乘也。③
这是说从学中文发音开始,而且是中文口语的发音,杜绝使用“和训回环”的方法,如果掌握了读音,便可成为“中华人”,然后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积少成多,最后就能达到读汉书“势如破竹”的上乘境地。只是由于在语言学上看,“中国语又简而文,此方语又冗而俚”,以日本的“冗而俚”之语言去对应中国的“简而文”的语言终究存在局限,“故译语之力终有所不及者存矣,译以为筌,为是故也”。①可见,“译”只是一种“筌”,按照“得鱼忘筌”之说,“筌”最终是要忘却的,因此“译”只是理解中国语言的一种方便法门,重要的是通过直接把握中国的古文辞学才能掌握圣人之道。
除了“最上乘”法之外,徂徕为身处穷乡僻壤而无缘接触“崎阳之学”者又设定了“第二等法”,具体内容,此不繁引。有趣的是,徂徕对此“第二等法”也寄予很高期望,一开始允许诸生借用和训来读四书五经及小学、孝经、文选之类书籍,然后令读《史记》《汉书》“各二三遍”,而后“便禁其一有和训者不得经目,授以温公《资治通鉴》类无和训者,读之一遍,何书不可读,然后始得为中华诸生”,原来,即便按照“第二等法”读书,最终也能成为“中华诸生”。在此过程中,重要的是必须记住“读书欲远离和训,此则真正读书法”②。如果说“最上乘”读书法的适应对象是以业儒为志向的年轻学子,那么从研究的角度看,将他们培养成“中华诸生”似乎还可理解,然而对于那些边缘地区的“寒乡”出身的人来说,也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则日本读书人岂非全部成了“中华人”?其实,徂徕之意无非是说,在读书能力上培养成如同“中华诸生”一般的超强技能,由此就能直捣中华典籍的巢穴,以中华人一样的语言能力同中华人进行对话——主要是经典对话。
表面看来,徂徕提倡的这套以摈除“和训”而主张“直读”汉籍为特色的“学问之法”有点高深莫测,然而在当时特别是在其创立的“蘐园学社”中影响却非常广泛,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风气:评品文章概以是否有“倭气”为标准,学问素养的高深概以能否“通唐音”为准则。例如徂徕曾批评仁斋“未免倭训读字”③,又如徂徕门下有位并不擅长中国古文辞的弟子平野金华(1688—1732)的一部汉语著作《金华稿删》便遭人非议,理由是其中“有倭字,有倭句,有倭气,用古每谬,自运多妄”④。另据雨森芳洲(1668—1755)《橘窗茶话》的记载,他年轻时听说朱舜水弟子今井弘济(1652—1689)“深通唐音”,心慕不已,便向弘济弟子打听弘济“读书专用唐音耶?”得到的回答是“固用唐音,训读亦不废”,于是,雨森评品道:“此乃学唐人中之杰然者也。”①再如徂徕大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亦力主直读法而反对用“倭语”读“中夏之书”,他在《倭读要领》一书中重申了徂徕的读书法,指出:“且先生(引者按,指徂徕)能华语,尤恶侏离之读,亦与纯(引者按,即春台)素心合。盖知倭读之难而为害之大耳。……夫倭语不可以读中夏之书,审矣。”②该书分上下两卷,其中有些专论文章如“日本无文字说”“中国文字始行于此方说”“颠倒读害文义说”等引人注意,他从文字学等角度进一步强调徂徕学语言方法论——以汉语读汉书的重要性。
只是徂徕所谓的以汉语读汉书或以汉语会汉语,其实是初学入门“第一关”,至多成就个“不会文章的华人耳”③,所以高级目标是要懂得“古文辞学”。他之所以主张以汉语会汉语,因为在他看来,中文与日文之词往往“意同而语异”,若以和训方法读中文,则只能通其大意而不能得其语言韵味,重要的是,“语以代异”——即语言随着时代不同而有变化,而语言本身又有“气格、风调、色泽、神理”,所以如果不懂语言,就无法掌握“古今雅俗”的语言韵味,阅读《诗经》尤其如此,“得意而不得语者之不能尽夫《诗》也”,由于《诗经》表现的是人情,所以不能尽夫《诗》的结果就是“得意而不得语者之不能尽夫情也”④,意谓就不能真正掌握中国古人的“情”。
徂徕主张以汉语会汉语的另一重要理由是,语言翻译总有局限,他认为中文与日文“体质本殊,由何吻合”,亦即中日两国语言不同,故翻译也无法实现意义上的“吻合”,如果运用“和训回环之读”的方法,虽能了解大意,但实际上却颇为“牵强”,都不免“隔靴搔痒”,“故学者先务唯要其就华人言语,识其本来面目,而其本来面目,华人所不识也,岂非身在庐山中故乎?”⑤可见,徂徕相当自信,他相信汉语的本来面目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忘了,因为他们都“身在庐山”的缘故,而日本人倒是有可能更了解汉语的庐山真面目,此说值得回味。只是徂徕并未对何谓“本来面目”有具体阐述,然而不难推测,其意概指西汉以前的古文辞,这在当时宋代中国已经失传。总之,以汉语读汉书只是一种初级的但又是必要的语言训练,重要的是以古文辞学为标准来把握中国古言,由此才能更上一层楼,实现“以古言征古义”。
记予侍先大夫,七八岁时,先大夫命予录其日间行事,或朝府,或客来,说何事,作何事,及风雨阴晴,家人琐细事,皆录,每夜临卧,必口授笔受,予十一二时,既能自读书,未尝受句读,盖由此故。……少小耳目
所熟,故随读便解,不烦讲说耳。④
盖谓徂徕七八岁时就能写字,十一二岁时,在从未受过“句读”训练的情况下,便能自己“读书”且“随读便解”,无须旁人指点,也不依赖他人“讲说”。此处“句读”特指日本的一种阅读汉籍的训读法,又称“和训”——即依日语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语序,将汉语的语序颠倒过来读,徂徕贬称其为“和训回环之读”①,这是当时日本人阅读汉籍的一种主要手法。然而徂徕却完全不受此拘限便能自由地阅读汉籍,据其自述,这是得益于“少小”时,其父对他的“口授笔受”。对于徂徕这番自述,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质疑,因为通过自学而掌握一门外语并非绝对不可能。但是徂徕根据他的经验,归结出直接“以汉语会汉语”的读书法(徂徕称之为“学问之法”),与他在经典解释学上主张“以古言征古义”的方法配套,这就值得关注。
徂徕晚年在《译文筌蹄题言十则》中,就如何做学问总结出一套方法论原则,他指出他特别厌恶“讲说”——即指听人讲解汉书,以为“讲说”有“十害”而无一利,由此“十害”还将引发“百弊”,其病根在于“贵耳贱目,废读务听”,为断绝此类弊害,所以徂徕竭力主张直接读书,他引以为自豪的“最上乘”的学习方法是:
故予尝为蒙生定学问之法,先为崎阳之学②,教以俗语,诵以华音,译以此方俚语,绝不作和训回环之读,始以零细者二字三字为句,后使读成书者,崎阳之学既成,乃始得为中华人,而后稍稍读经子史集四部书,势
如破竹,是最上乘也。③
这是说从学中文发音开始,而且是中文口语的发音,杜绝使用“和训回环”的方法,如果掌握了读音,便可成为“中华人”,然后读“经史子集”四部书,积少成多,最后就能达到读汉书“势如破竹”的上乘境地。只是由于在语言学上看,“中国语又简而文,此方语又冗而俚”,以日本的“冗而俚”之语言去对应中国的“简而文”的语言终究存在局限,“故译语之力终有所不及者存矣,译以为筌,为是故也”。①可见,“译”只是一种“筌”,按照“得鱼忘筌”之说,“筌”最终是要忘却的,因此“译”只是理解中国语言的一种方便法门,重要的是通过直接把握中国的古文辞学才能掌握圣人之道。
除了“最上乘”法之外,徂徕为身处穷乡僻壤而无缘接触“崎阳之学”者又设定了“第二等法”,具体内容,此不繁引。有趣的是,徂徕对此“第二等法”也寄予很高期望,一开始允许诸生借用和训来读四书五经及小学、孝经、文选之类书籍,然后令读《史记》《汉书》“各二三遍”,而后“便禁其一有和训者不得经目,授以温公《资治通鉴》类无和训者,读之一遍,何书不可读,然后始得为中华诸生”,原来,即便按照“第二等法”读书,最终也能成为“中华诸生”。在此过程中,重要的是必须记住“读书欲远离和训,此则真正读书法”②。如果说“最上乘”读书法的适应对象是以业儒为志向的年轻学子,那么从研究的角度看,将他们培养成“中华诸生”似乎还可理解,然而对于那些边缘地区的“寒乡”出身的人来说,也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则日本读书人岂非全部成了“中华人”?其实,徂徕之意无非是说,在读书能力上培养成如同“中华诸生”一般的超强技能,由此就能直捣中华典籍的巢穴,以中华人一样的语言能力同中华人进行对话——主要是经典对话。
表面看来,徂徕提倡的这套以摈除“和训”而主张“直读”汉籍为特色的“学问之法”有点高深莫测,然而在当时特别是在其创立的“蘐园学社”中影响却非常广泛,以至于形成了一种风气:评品文章概以是否有“倭气”为标准,学问素养的高深概以能否“通唐音”为准则。例如徂徕曾批评仁斋“未免倭训读字”③,又如徂徕门下有位并不擅长中国古文辞的弟子平野金华(1688—1732)的一部汉语著作《金华稿删》便遭人非议,理由是其中“有倭字,有倭句,有倭气,用古每谬,自运多妄”④。另据雨森芳洲(1668—1755)《橘窗茶话》的记载,他年轻时听说朱舜水弟子今井弘济(1652—1689)“深通唐音”,心慕不已,便向弘济弟子打听弘济“读书专用唐音耶?”得到的回答是“固用唐音,训读亦不废”,于是,雨森评品道:“此乃学唐人中之杰然者也。”①再如徂徕大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亦力主直读法而反对用“倭语”读“中夏之书”,他在《倭读要领》一书中重申了徂徕的读书法,指出:“且先生(引者按,指徂徕)能华语,尤恶侏离之读,亦与纯(引者按,即春台)素心合。盖知倭读之难而为害之大耳。……夫倭语不可以读中夏之书,审矣。”②该书分上下两卷,其中有些专论文章如“日本无文字说”“中国文字始行于此方说”“颠倒读害文义说”等引人注意,他从文字学等角度进一步强调徂徕学语言方法论——以汉语读汉书的重要性。
只是徂徕所谓的以汉语读汉书或以汉语会汉语,其实是初学入门“第一关”,至多成就个“不会文章的华人耳”③,所以高级目标是要懂得“古文辞学”。他之所以主张以汉语会汉语,因为在他看来,中文与日文之词往往“意同而语异”,若以和训方法读中文,则只能通其大意而不能得其语言韵味,重要的是,“语以代异”——即语言随着时代不同而有变化,而语言本身又有“气格、风调、色泽、神理”,所以如果不懂语言,就无法掌握“古今雅俗”的语言韵味,阅读《诗经》尤其如此,“得意而不得语者之不能尽夫《诗》也”,由于《诗经》表现的是人情,所以不能尽夫《诗》的结果就是“得意而不得语者之不能尽夫情也”④,意谓就不能真正掌握中国古人的“情”。
徂徕主张以汉语会汉语的另一重要理由是,语言翻译总有局限,他认为中文与日文“体质本殊,由何吻合”,亦即中日两国语言不同,故翻译也无法实现意义上的“吻合”,如果运用“和训回环之读”的方法,虽能了解大意,但实际上却颇为“牵强”,都不免“隔靴搔痒”,“故学者先务唯要其就华人言语,识其本来面目,而其本来面目,华人所不识也,岂非身在庐山中故乎?”⑤可见,徂徕相当自信,他相信汉语的本来面目就连中国人自己也忘了,因为他们都“身在庐山”的缘故,而日本人倒是有可能更了解汉语的庐山真面目,此说值得回味。只是徂徕并未对何谓“本来面目”有具体阐述,然而不难推测,其意概指西汉以前的古文辞,这在当时宋代中国已经失传。总之,以汉语读汉书只是一种初级的但又是必要的语言训练,重要的是以古文辞学为标准来把握中国古言,由此才能更上一层楼,实现“以古言征古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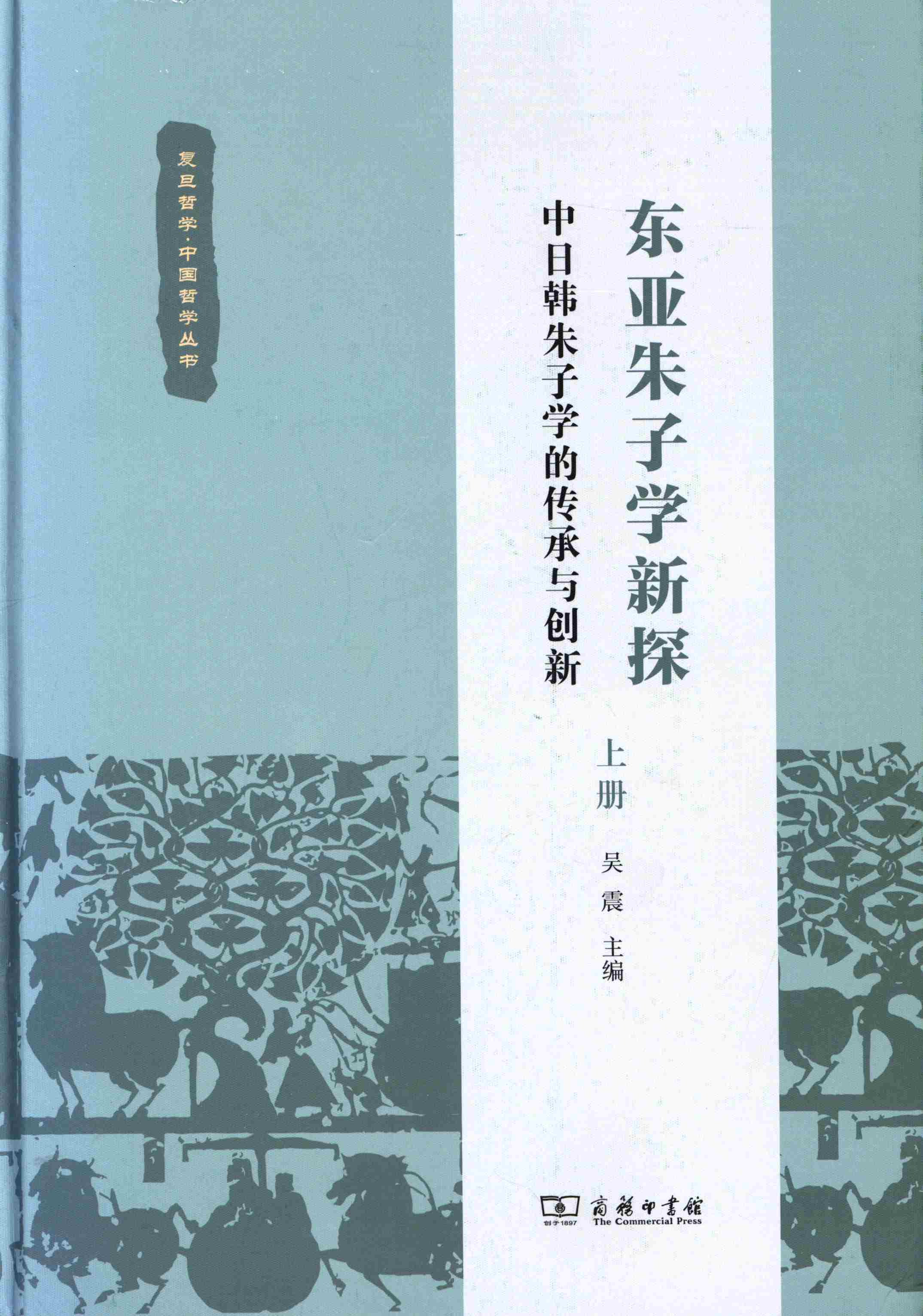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这部《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结项成果,并于今年被认定为是成果。全书共由四篇三十七章组成,近九十万字,吴震教授主编,由海内外中国哲学领域的一线学者组成的性团队合作分篇撰写,代表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的成果。本书的四篇结构是:一、“东亚儒学与中国朱子学”;二、“日本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三、“韩国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比较研究与回顾综述”;后是两篇“附录”,分别是“近十年来日本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近十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本书进一步拓展了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广度,可以认为,通过本书的出版,“东亚朱子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有充分理由得以成立(如同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东亚儒学”或“东亚哲学”已渐形成一般),进而,本书的出版也得以重新展现了中国哲学等。
阅读
相关人物
吴震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