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综述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1》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6786 |
| 颗粒名称: | 2021年度韩国学者对朱子学及韩国儒学的研究综述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7 |
| 页码: | 134-140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2021年韩国学者在朱子学研究领域的哲学研究成果,包括有关朱子晚年说与退溪的问题意识的论文、中和新说与朱熹哲学核心本领的研究、朱子哲学中义概念的社会伦理学含义的研究等。此外,也涉及到朱子哲学与王阳明哲学的美德伦理与美德认识论的比较研究以及朱子学与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
| 关键词: | 韩国学者 朱子学 韩国儒学 |
内容
2021年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大致分为“哲学研究”“教育学研究”“经学、诠释学研究”,其中有“比较研究”或者“部分研究”。
1.哲学研究
有关“哲学研究”的论文有:《理学与心学的间隔何以解决:朱子的晚年说与退溪的问题意识》(金炯瓒,《退溪学报》Vol.150,2021);《中和新说与朱熹哲学的核心本领》(黄甲渊,《泛韩哲学》Vol.102,2021);《朱子哲学中“义”概念的社会伦理学的含义》(洪性敏,《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朱熹的“中底未发”与“不中底未发”及其工夫的有无》(李宗雨,《栗谷学研究》Vol.45,2021);《朱熹有无“未发工夫”之论与湖洛论辩》(李宗雨,《温知论丛》Vol.67,2021);《朱子道德哲学中“气强理弱”的意义小考》(金慧洙,《阳明学》Vol.62,2021);《朱熹对李翱<灭情论》的批判之妥当性再考》(洪麟,《儒学研究》Vol.55,2021);《洞察:豁然贯通的现代诠释》(JeongHwan-hui,《东洋古典研究》Vol.84,2021);《中国佛教初期批判的论点与变化:<难神灭论>与<朱子语类>的<释氏>篇为主》(ParkGyeong-mi,《韩国佛教史研究》Vol.0No.19,2021);《朱子“一物”与“二物”概念的实践道德的涵义及其概念展开样态研究》(KimBaeg-nyeong,《儒学研究》Vol.57,2021);《朱子读书论中的切己工夫及其医疗的思考》(JungByung-seok,《哲学论丛》Vol.103,2021);《宋代新儒学的仁论与理一分殊概念》(LeeKang-hee,《东洋哲学》Vol.56No.1,2021);《儒家鬼神论的思维结构与朱熹鬼神论的解读》(JoHyeon-ung,《儒学研究》Vol.57,2021)。
韩国学者朱子哲学研究也有比较研究的方式。比如,《朱熹与王阳明的美德伦理与美德认识论:是非之心与良知为主》(LeeChan,《儒学研究》Vol.57,2021);《朱陆经典观比较研究》(朱光镐,《哲学研究》Vol.159,2021);《黄道周的朱陆观研究2》(LimHong-tai,《栗谷学研究》Vol.46,2021);《儒学的和平思想:孔子、孟子、朱子的“仁”概念为主》(AnYoon-kyoung,《人与和平》Vol.2No.1,2021);《朱子与甑山的相生理论比较》(AnYoon-kyoung,《大顺思想论丛》Vol.38,2021);《知讷与朱熹的伦理思想比较分析》(金钟龙,《佛教研究》Vol.54,2021);《朱熹的“理”“气”、栗谷的“理”“气”、基督教的“灵”“肉”谈论》(LeeYong-tae,《韩中言语文化研究》Vol.ONo.62,2021);《阴阳与五行的相关性:对周敦颐、朱熹理论的几何学分析》(Kim Hak-yong,《退溪学报》Vol.150,2021)。
哲学研究中部分涉及到朱子哲学的成果有《<为学之方图>与<圣学辑要>的<修己>篇的“敬”工夫之间的连贯性小考:静坐的意义为主》(Koh Yoon-suk,《儒教思想研究》Vol.86No.7,2021);《艮斋田愚的未发论与静坐观》(李承焕,《东洋哲学》Vol.55,2021);《李滉未发论的形成背景与天理体认的方法》(Kim Seung-young,《栗谷学研究》Vol.44,2021);《南塘对<太极图说>的理气论解释体系》(崔英辰、赵甜甜,《哲学》Vol.146,2021);《南塘韩元震的阳明学批判论研究》(裴帝晟,《阳明学》Vol.62,2021);《从修已治人的观点分析艮斋田愚的“絜矩之道”注释分析》(李天承,《韩国哲学论集》Vol.71,2021);《栗谷修养论中“诚意”的道德实践强化的特点》(Lee Young-kyung,《儒教思想研究》Vol.85,2021);《“理气之妙”的“妙”字解读:对栗谷理气论的过程原子论分析》(JeongKang-gil,《栗谷学研究》Vol.45,2021);《艮斋田愚的新正统主义性理学》(宣炳三,《人文科学研究》Vol.44,2021);《韩国洛学对“理弱气强”的认识方式》(LeeWon-jun,《栗谷学研究》Vol.44,2021);《茶山丁若镛的<大学>解释中“恕”的含义》(Kim Young-woo,《退溪学论丛》Vol.38,2021);《艮斋田愚的心统性情论及其哲学含义》(郑宗模,《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16世纪后半期朝鲜学界对阳明学的批判理论与有关文庙制度改正的议论》(Jeong Du-young,《历史与实学》Vol.76,2021);《“心即理”说与对其回应的栗谷“心是气”论:知觉说与格物说为主》(Chae Hee Doh,《栗谷学研究》Vol.33,2021);《朝鲜时代东儒传统的形成及其涵义》(Oh Se-jin,《儒学研究》Vol.56No.1,2021);《儒学的“未发”与圆佛教的“精神”概念比较:朱子与鼎山为主》(Park Sung-ho,《韩国宗教》Vol.49,2021);《退溪的人心道心说:<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图>的修改为主》(Jeong,Do-hee,《退溪学论集》Vol.29,2021);《朝鲜儒学中“直”思想的传承关系及其内在的问题研究》(Kim Chang-gyung,《儒学研究》Vol.57No.1,2021);《从发展史的视野看李珥的“理”概念》(李俸珪,《泰东古典研究》Vol.47,2021)。
金炯瓒教授的论文通过分析王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的内容,提出其中包含“理学”与“心学”,两者之间的矛盾没有达到恰当的解决。金教授指出,《朱子晚年定论》收录朱子从37岁到69岁的书信,当然不能代表朱子的晚年观点,但是如果把书中的朱子书信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从中可以了解朱子学问观点的演变过程。《朱子晚年定论》收录鹅湖之集稍后的朱子书信反复强调尊德性的内省涵养,警惕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方法。金教授把道问学的方法称为“理学”,尊德性的工夫称为“心学”,特别提出朱子57岁视力出问题是朱子更加重视“心学”的一个重要契机:“熹衰病,今岁幸不至剧,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闲坐,却得收拾放心,觉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金教授又把小学工夫和“心学”联系起来,指出朱子在《大学章句》中特别阐发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而在《大学章句序》中却非常重视小学工夫,这意味着朱子当时把小学的尊德性工夫当成道问学工夫的基础,也即是说“心学”是“理学”的根柢。金教授说,世界的普遍原理为人的道德本性,具备于每个人的心中,但是要呈现道德本性,关键都在其人本身,所以在朱子的工夫论中,比起探求客观原理的“理学”工夫,修养身心的“心学”工夫是更重要的。虽然如此,朱子的工夫论,仍然强调格物致知,其原因是朱子认为如果没有“理学”的内容,“心学”不免危殆不安。在此观点的基础之上,金教授主张朱子的晚年追求建立的是合“理学”与“心学”为一的工夫论体系。金教授的这篇论文虽然没有独创的观点,但是比较清楚地说明朱子学体系中“理学”与“心学”的共存情况。
一部分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深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牟宗三先生是20世纪出现的新朱子。黄甲渊教授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关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论文,几年前把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翻译成韩语。《中和新说与朱熹哲学的核心本领》这一文重述了他多年以来的一贯观点,而且把自己的体悟一言以蔽之:朱子哲学的核心本领是“本体的静态性”,也即是人人都熟悉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朱子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黄教授强调,朱子哲学的“性”与“心”的平行关系的两个概念:心是能(主),性是所(客),心是主宰性理的呈现和视听言动的所有活动,性是心的标准或者原理。工夫的主体与对象都是心,至于性,不存在工夫。黄教授认为,朱子哲学中的“性理”是静态的原理(实体),故性理不能通过自身的“振动(自觉)”实现道德价值,而心作为知觉与实践的主体,没有至善与原理的意思。黄教授还认为,对于朱子来说,理是静态的本体,所以朱子的居敬与格物致知的工夫论是合乎朱子本来的整个理论框架的。论文中,大胆提出一个没有资料支撑的假说:朱子哲学的思维模式跟朱子当时的时代精神有关系:朱子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危机重重,所以朱子不能支持道德意志的自由立法,而维护现有的社会规范。黄教授是全北大学艮斋学研究所的所长,而艮斋是朝鲜末期的一位学者,主张“性师心弟”论,其内容是性是最尊严的而没有活动力量,而心是有善有恶的而有主宰力量,所以“心”作为实践的主体要尊奉“性”的命令而行事。牟宗三先生所了解的朱子哲学,与艮斋的“性师心弟”论,有不少的共同点,可以说黄教授的朱子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一贯性。艮斋认为,“性”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易的真理,他激烈批判“性”既存有又活动的观点,而牟宗三却认为“理”是既存有又活动的,严重批判“理”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观点。对100年前的艮斋来说,牟宗三先生和黄教授的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都是他的论敌经常主张的老观点而已。可是对现代研究者来说,艮斋的“性师心弟”论才是很陌生的,牟宗三先生的观点人人都很熟悉。“理”到底是能活动的存在,还是只存有的本体而已?这个问题也是朱子学研究者值得注意研究的主题。
李宗雨教授的两篇论文集中讨论朱子哲学中的“未发”是“中”还是“不中”的问题和未发时需不需要工夫的问题。李教授简单分析朱子哲学的“未发”概念,指出朱子在《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是“性”,“性”是“中”,是天下之大本,但是有时候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有“不中”的情况,前后的说明不完全一致。这里的“中”既然属于“性”,那么这个“中”的性应该是本然之性,而其“不中”的性则属于气质之性。未发是性,性有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所以未发有中与不中的不同情况。若说本然之性,则圣人和众人的未发都是“中”,而若说气质之性,则圣人的未发是中,众人的未发是不中。对于本然之性,未发时不需要涵养的工夫,因为本然之性是无时不在;而对于气质之性,未发时需要戒慎恐惧的工夫。朝鲜时期的理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退溪、栗谷以后朝鲜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学者是尤庵(宋时烈),尤庵的嫡传是遂庵(权尚夏),他有“江门八学士”,其中的崔徵厚和韩弘祚提出“未发之前,只有本然之性,而不可谓有气质之性;及其发也,方有气质之性。道心即本然之性所发也,人心即本性之由于耳目口鼻而发,所谓气质之性也”。意思是,未发时只有本然之性,不存在气质之性。江门八学士中的巍岩(李柬)支持这个观点:“性有二名,何也?以其单指兼指之有异也。何谓单指?大本达道,天命之本然,是所谓本然之性也。无论动静而专言其理,故曰单指也。何谓兼指?气有清浊粹驳,而理有中不中,是所谓气质之性也,无论善恶而并论其气,故曰兼指也。然则所谓未发,正是气不用事时也。所谓清浊粹驳者,无情意无造作,澹然纯一善而已。此处正好单指其本然之理也。何必兼指其不用事之气乎?”巍岩认为,未发时是气不用事之时,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单指本然之理,不需要兼指不用事的气,也即是说不用说气质之性。表面上看,崔徵厚和韩弘祚主张未发时不存在气质之性,而巍岩则主张未发时不用提到气质之性,有微妙的不同,但大体的看法是一致的。对此,另一江门八学士南塘(韩元震)进行批判,“今以情为气质之性,则是本然之性在前,气质之性在后,相为体用始终,而地头阶级截然矣。岂非二性乎?”南塘的意思是,如果气质之性不在未发时,而在已发时,则属于情。本然之性是性,而气质之性是情,则等于说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情。遂庵也同意南塘的观点。朝鲜时期的首都汉阳(今为首尔)位于汉江的北边,这个汉江也称为“洛水”,所以汉阳地区成立的一个学派称为“洛论”,而韩国忠清道也叫湖西,所以这个地区成立的一个学派称为“湖论”。三渊(金昌翕)等洛论学者大体赞同崔徵厚、韩弘祚、巍岩的观点,与南塘等大部分湖论学者进行论辩。等于说,洛论一般主张未发时不存在“不中”,都是“中”的状态,而湖论一般主张未发时也存在不中的情况。至于工夫论,洛论和湖论都主张未发时需要工夫,但其工夫的目的有所不同:洛论的目标是涵养本然之性,而湖论的目标是变化气质。金教授特地介绍,李显益主张未发时不需要工夫,也不能着工夫。李显益说:“且朱子之以涵养于未发,省察于已发言者,则是宽言之未发;‘未发时自着不得工夫’云者,则是窄言之未发。何尝有妨碍乎?虽然,窄言之未发,是为未发之真境,而此则以地头着工为言终不可。”李显益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心之未发已发问题。他区分广义上的未发和狭义上的未发,广义上的未发包括平时的大部分时间,而狭义上的未发是无所偏倚的状态。所以广义上的未发当然需要戒慎恐惧的工夫,而狭义上的未发根本不需要工夫,也不能着工夫。金教授不太考虑“性”的未发、已发和“心”的未发、已发之间的区别,笼统讨论“中”和“不中”的问题,但是论文中介绍的资料,对了解朝鲜时期“未发”论辩中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教育学研究
韩国的朱子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教育学研究较为丰富,2021年有一篇教育学的朱子学研究博士论文《朱子“学”研究》(Han Ji-yoon,高丽大学校教育大学院,2021)和硕士论文《朱子读书法之道德教育上的含义》(朴智惠,韩国教员大学校大学院,2021),期刊论文有《朱子“仁”概念的教育学意义》(Jeon Sun-suk,《教育哲学研究》Vol.43No.2,2021);《朱熹读书法中作为读解方法的“缝罅”概念小考》(Cheon Won-seok,《读书研究》Vol.61No.9,2021);《伦理与思想》《实现知行一致的学问方法》(Han Ji-yoon,《教育哲学》Vol.81No.1);《朱子认识能力理论的教育学诠释》(Han Ji-yoon,《孔子学》Vol.45,2021)。其中,Han Ji-yoon的博士论文研究朱子“学”概念的渊源、核心内容、实践方法等,其以教育学的角度集中分析道德目的的体会及其对实践的影响。
韩国的朱子学研究中“教育学研究”经常与“比较研究”结合在一起。2021年这方面的研究有《杜威与朱熹的教育目的比较:<学校与社会>与<小学>为主》(Kim Su-youn、申昌镐,《人格教育》Vol.15No.2,2021);《人性教育的视野分析气质与性格:Chloninger,C.R.与朱熹的观点为主》(Lee Wha-sik,《学习者中心教科教育研究》Vol.21,2021);《基于人生观的道德教育比较研究:朱子与卢梭为主》(HanJi-yoon,《初等道德教育》Vol.0No.74,2021);《为改善<伦理与思想>教材“儒家伦理”部分叙述的分析与提议:朱子、阳明、退溪、栗谷的伦理思想为主》(Kang Bo-seung,《伦理教育研究》Vol.61,2021);《近代以前小学教育的结构与文字学习教材的国语教育史的意义》(Heo Jae-young,《韩末研究》 Vol.59,2021);《<小学>的韩国式变更》(Bak Soon-nam,《韩国文学论丛》Vol.87No.1,2021);《<小学>的道德教育理论与教学相长的含义》(KwonYoon-Jung,《初等道德教育》Vol.0No.74,2021)。
朝鲜时期的学者一般很重视朱子的《小学》书,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所以现代的不少研究者关注《小学》在当代道德教育上的意义,也有些教授、教师和书院的山长等进行《小学》教育活动。申昌镐教授等的《杜威与朱熹的教育目的比较:<学校与社会>与<小学>为主》一文对朱子与杜威的道德目的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人工智能和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时代,韩国社会该追求的教育方向。按照杜威的教育思想,教育是教师—学习—环境的交互作用,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者所具有的潜在能力的开发,其方法是学习者通过对环境的经验,进行对个人知识的反省,不断重构主体的知识体系,而学校应该提供学习者能成长为社会成员的经验环境,所以学校应该跟社会联系在一起,既是学习者社会训练的机构,也是实际生活的空间。按照朱子的教育思想,小学要教学生自己训练洒扫、应对、进退的生活礼节,实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家庭、社会道德规范,以追求恢复自己的道德本性,通过与人为善,与他人共同体现共同体的公共之善。申教授等指出杜威的教育目的是个人的认知、心理的变化发展,所以没有提出具体的教育方向,而朱子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恢复本性、成为圣人,其教育方向清楚明白。申教授等认为,人类的教育与人工智能的开发有所不同,人类的教育应该考虑人格的完成、本性的恢复,而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多多少少不重视学校的教育空间,可能导致学校的危机、教育的危机。申教授等主张今后的教育应该参考朱子、杜威的教育思想,重新建立起加强实用性、社会性功能的学校。申教授等的论文虽然没有新意,但是对朱子和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的话语:学校是人类完成个人人格,成为社会成员的教育空间。从中可见,韩国的教育研究者非常重视朱子《小学》的教育思想。
3.经学、诠释学研究
经学方面的单独或者比较的研究有《朱熹阙文说的意思与作用:<论语>的“色斯举矣”句为主》(朴英姬,《中国语文学志》Vol.77,2021);《<论语集注>的文献学读解:<学而>篇注释分析》(柳浚弼,《大东文化研究》Vol.113,2021);《中国儒学史中的“絜矩”含义演变小考:郑玄与朱熹为主》(朴素铉,《中国文学》Vol.107No.1,2021);《从<大学>解释的差异看其含义:朱熹、王守仁、尹鑴的见解为主》(Choi Jeong-mook,《东西哲学研究》Vol.99,2021);《朱熹与李滉的修辞学的<论语>诠释》(You Min-jung,《退溪学报》Vol.149,2021);《峿堂对朱子(大学章句序)的修辞学读法》(Shin Jae-sik,《退溪学论丛》Vol.37,2021);《二程<诗经>学的朝鲜时代接受样态:朝鲜时代<诗经>学中程子学与朱子学的拮抗》(金秀炅,《泰东古典研究》Vol.46,2021)。
除此以外,部分涉及朱子学的有硕士论文《正祖的<大学>解释研究》(李诗然,庆尚大学校大学院硕士论文,2021)与期刊论文《退溪李滉<启蒙传疑>收录的<周易参同契>的意义研究》(Seo Geun-sik,《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朝鲜知性史中“王道”与“霸道”话语》(Kim Hong-baek,《古典文学研究》Vol.60,2021);《道学文论中“载道”与周敦颐“文辞”的意思与地位再考》(李定桓,《退溪学报》Vol.150,2021);《权近<周易浅见录>中的象数学方法论》(ImJae-kyu,《泰东古典研究》Vol.46No.1,2021);《李焕模的<书传记疑>中的多维性诠释》(Lee Eun-ho,《泰东古典研究》Vol.46No.1,2021);《朝鲜后期<聚星图>制作及其意义》(Kang Shin-Ae,《美术史学研究》Vol.309,2021);《星湖李瀷与白云沈大允的<国风>说比较研究:朱熹所定的淫诗为对象》(Hong Yoon-bin,《古典与解释》Vol.33,2021);《中国灾异观的成立与变化》(Lee Suk-hyun,《人文社会科学研究》Vol.22,2021);《李睟光与郑经世的道文论》(Oh Se-hyun,《韩国汉文学研究》Vol.83,2021);《星湖李瀷的冠婚礼仪节研究》(Doh Min-jae,《温知论丛》Vol.67,2021)。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系)
1.哲学研究
有关“哲学研究”的论文有:《理学与心学的间隔何以解决:朱子的晚年说与退溪的问题意识》(金炯瓒,《退溪学报》Vol.150,2021);《中和新说与朱熹哲学的核心本领》(黄甲渊,《泛韩哲学》Vol.102,2021);《朱子哲学中“义”概念的社会伦理学的含义》(洪性敏,《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朱熹的“中底未发”与“不中底未发”及其工夫的有无》(李宗雨,《栗谷学研究》Vol.45,2021);《朱熹有无“未发工夫”之论与湖洛论辩》(李宗雨,《温知论丛》Vol.67,2021);《朱子道德哲学中“气强理弱”的意义小考》(金慧洙,《阳明学》Vol.62,2021);《朱熹对李翱<灭情论》的批判之妥当性再考》(洪麟,《儒学研究》Vol.55,2021);《洞察:豁然贯通的现代诠释》(JeongHwan-hui,《东洋古典研究》Vol.84,2021);《中国佛教初期批判的论点与变化:<难神灭论>与<朱子语类>的<释氏>篇为主》(ParkGyeong-mi,《韩国佛教史研究》Vol.0No.19,2021);《朱子“一物”与“二物”概念的实践道德的涵义及其概念展开样态研究》(KimBaeg-nyeong,《儒学研究》Vol.57,2021);《朱子读书论中的切己工夫及其医疗的思考》(JungByung-seok,《哲学论丛》Vol.103,2021);《宋代新儒学的仁论与理一分殊概念》(LeeKang-hee,《东洋哲学》Vol.56No.1,2021);《儒家鬼神论的思维结构与朱熹鬼神论的解读》(JoHyeon-ung,《儒学研究》Vol.57,2021)。
韩国学者朱子哲学研究也有比较研究的方式。比如,《朱熹与王阳明的美德伦理与美德认识论:是非之心与良知为主》(LeeChan,《儒学研究》Vol.57,2021);《朱陆经典观比较研究》(朱光镐,《哲学研究》Vol.159,2021);《黄道周的朱陆观研究2》(LimHong-tai,《栗谷学研究》Vol.46,2021);《儒学的和平思想:孔子、孟子、朱子的“仁”概念为主》(AnYoon-kyoung,《人与和平》Vol.2No.1,2021);《朱子与甑山的相生理论比较》(AnYoon-kyoung,《大顺思想论丛》Vol.38,2021);《知讷与朱熹的伦理思想比较分析》(金钟龙,《佛教研究》Vol.54,2021);《朱熹的“理”“气”、栗谷的“理”“气”、基督教的“灵”“肉”谈论》(LeeYong-tae,《韩中言语文化研究》Vol.ONo.62,2021);《阴阳与五行的相关性:对周敦颐、朱熹理论的几何学分析》(Kim Hak-yong,《退溪学报》Vol.150,2021)。
哲学研究中部分涉及到朱子哲学的成果有《<为学之方图>与<圣学辑要>的<修己>篇的“敬”工夫之间的连贯性小考:静坐的意义为主》(Koh Yoon-suk,《儒教思想研究》Vol.86No.7,2021);《艮斋田愚的未发论与静坐观》(李承焕,《东洋哲学》Vol.55,2021);《李滉未发论的形成背景与天理体认的方法》(Kim Seung-young,《栗谷学研究》Vol.44,2021);《南塘对<太极图说>的理气论解释体系》(崔英辰、赵甜甜,《哲学》Vol.146,2021);《南塘韩元震的阳明学批判论研究》(裴帝晟,《阳明学》Vol.62,2021);《从修已治人的观点分析艮斋田愚的“絜矩之道”注释分析》(李天承,《韩国哲学论集》Vol.71,2021);《栗谷修养论中“诚意”的道德实践强化的特点》(Lee Young-kyung,《儒教思想研究》Vol.85,2021);《“理气之妙”的“妙”字解读:对栗谷理气论的过程原子论分析》(JeongKang-gil,《栗谷学研究》Vol.45,2021);《艮斋田愚的新正统主义性理学》(宣炳三,《人文科学研究》Vol.44,2021);《韩国洛学对“理弱气强”的认识方式》(LeeWon-jun,《栗谷学研究》Vol.44,2021);《茶山丁若镛的<大学>解释中“恕”的含义》(Kim Young-woo,《退溪学论丛》Vol.38,2021);《艮斋田愚的心统性情论及其哲学含义》(郑宗模,《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16世纪后半期朝鲜学界对阳明学的批判理论与有关文庙制度改正的议论》(Jeong Du-young,《历史与实学》Vol.76,2021);《“心即理”说与对其回应的栗谷“心是气”论:知觉说与格物说为主》(Chae Hee Doh,《栗谷学研究》Vol.33,2021);《朝鲜时代东儒传统的形成及其涵义》(Oh Se-jin,《儒学研究》Vol.56No.1,2021);《儒学的“未发”与圆佛教的“精神”概念比较:朱子与鼎山为主》(Park Sung-ho,《韩国宗教》Vol.49,2021);《退溪的人心道心说:<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图>的修改为主》(Jeong,Do-hee,《退溪学论集》Vol.29,2021);《朝鲜儒学中“直”思想的传承关系及其内在的问题研究》(Kim Chang-gyung,《儒学研究》Vol.57No.1,2021);《从发展史的视野看李珥的“理”概念》(李俸珪,《泰东古典研究》Vol.47,2021)。
金炯瓒教授的论文通过分析王阳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论》的内容,提出其中包含“理学”与“心学”,两者之间的矛盾没有达到恰当的解决。金教授指出,《朱子晚年定论》收录朱子从37岁到69岁的书信,当然不能代表朱子的晚年观点,但是如果把书中的朱子书信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排列,从中可以了解朱子学问观点的演变过程。《朱子晚年定论》收录鹅湖之集稍后的朱子书信反复强调尊德性的内省涵养,警惕倾向于道问学的工夫方法。金教授把道问学的方法称为“理学”,尊德性的工夫称为“心学”,特别提出朱子57岁视力出问题是朱子更加重视“心学”的一个重要契机:“熹衰病,今岁幸不至剧,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瞑目闲坐,却得收拾放心,觉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金教授又把小学工夫和“心学”联系起来,指出朱子在《大学章句》中特别阐发格物致知的重要性,而在《大学章句序》中却非常重视小学工夫,这意味着朱子当时把小学的尊德性工夫当成道问学工夫的基础,也即是说“心学”是“理学”的根柢。金教授说,世界的普遍原理为人的道德本性,具备于每个人的心中,但是要呈现道德本性,关键都在其人本身,所以在朱子的工夫论中,比起探求客观原理的“理学”工夫,修养身心的“心学”工夫是更重要的。虽然如此,朱子的工夫论,仍然强调格物致知,其原因是朱子认为如果没有“理学”的内容,“心学”不免危殆不安。在此观点的基础之上,金教授主张朱子的晚年追求建立的是合“理学”与“心学”为一的工夫论体系。金教授的这篇论文虽然没有独创的观点,但是比较清楚地说明朱子学体系中“理学”与“心学”的共存情况。
一部分韩国学者的朱子学研究深受牟宗三先生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牟宗三先生是20世纪出现的新朱子。黄甲渊教授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关朱子学与阳明学的论文,几年前把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翻译成韩语。《中和新说与朱熹哲学的核心本领》这一文重述了他多年以来的一贯观点,而且把自己的体悟一言以蔽之:朱子哲学的核心本领是“本体的静态性”,也即是人人都熟悉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朱子的‘理’只存有而不活动”。黄教授强调,朱子哲学的“性”与“心”的平行关系的两个概念:心是能(主),性是所(客),心是主宰性理的呈现和视听言动的所有活动,性是心的标准或者原理。工夫的主体与对象都是心,至于性,不存在工夫。黄教授认为,朱子哲学中的“性理”是静态的原理(实体),故性理不能通过自身的“振动(自觉)”实现道德价值,而心作为知觉与实践的主体,没有至善与原理的意思。黄教授还认为,对于朱子来说,理是静态的本体,所以朱子的居敬与格物致知的工夫论是合乎朱子本来的整个理论框架的。论文中,大胆提出一个没有资料支撑的假说:朱子哲学的思维模式跟朱子当时的时代精神有关系:朱子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危机重重,所以朱子不能支持道德意志的自由立法,而维护现有的社会规范。黄教授是全北大学艮斋学研究所的所长,而艮斋是朝鲜末期的一位学者,主张“性师心弟”论,其内容是性是最尊严的而没有活动力量,而心是有善有恶的而有主宰力量,所以“心”作为实践的主体要尊奉“性”的命令而行事。牟宗三先生所了解的朱子哲学,与艮斋的“性师心弟”论,有不少的共同点,可以说黄教授的朱子哲学研究也有一定的一贯性。艮斋认为,“性”是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可易的真理,他激烈批判“性”既存有又活动的观点,而牟宗三却认为“理”是既存有又活动的,严重批判“理”只存有而不活动的观点。对100年前的艮斋来说,牟宗三先生和黄教授的这个理论没有什么新鲜的内容,都是他的论敌经常主张的老观点而已。可是对现代研究者来说,艮斋的“性师心弟”论才是很陌生的,牟宗三先生的观点人人都很熟悉。“理”到底是能活动的存在,还是只存有的本体而已?这个问题也是朱子学研究者值得注意研究的主题。
李宗雨教授的两篇论文集中讨论朱子哲学中的“未发”是“中”还是“不中”的问题和未发时需不需要工夫的问题。李教授简单分析朱子哲学的“未发”概念,指出朱子在《中庸章句》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是“性”,“性”是“中”,是天下之大本,但是有时候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有“不中”的情况,前后的说明不完全一致。这里的“中”既然属于“性”,那么这个“中”的性应该是本然之性,而其“不中”的性则属于气质之性。未发是性,性有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所以未发有中与不中的不同情况。若说本然之性,则圣人和众人的未发都是“中”,而若说气质之性,则圣人的未发是中,众人的未发是不中。对于本然之性,未发时不需要涵养的工夫,因为本然之性是无时不在;而对于气质之性,未发时需要戒慎恐惧的工夫。朝鲜时期的理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退溪、栗谷以后朝鲜时期影响力最大的学者是尤庵(宋时烈),尤庵的嫡传是遂庵(权尚夏),他有“江门八学士”,其中的崔徵厚和韩弘祚提出“未发之前,只有本然之性,而不可谓有气质之性;及其发也,方有气质之性。道心即本然之性所发也,人心即本性之由于耳目口鼻而发,所谓气质之性也”。意思是,未发时只有本然之性,不存在气质之性。江门八学士中的巍岩(李柬)支持这个观点:“性有二名,何也?以其单指兼指之有异也。何谓单指?大本达道,天命之本然,是所谓本然之性也。无论动静而专言其理,故曰单指也。何谓兼指?气有清浊粹驳,而理有中不中,是所谓气质之性也,无论善恶而并论其气,故曰兼指也。然则所谓未发,正是气不用事时也。所谓清浊粹驳者,无情意无造作,澹然纯一善而已。此处正好单指其本然之理也。何必兼指其不用事之气乎?”巍岩认为,未发时是气不用事之时,所以这个时候只需要单指本然之理,不需要兼指不用事的气,也即是说不用说气质之性。表面上看,崔徵厚和韩弘祚主张未发时不存在气质之性,而巍岩则主张未发时不用提到气质之性,有微妙的不同,但大体的看法是一致的。对此,另一江门八学士南塘(韩元震)进行批判,“今以情为气质之性,则是本然之性在前,气质之性在后,相为体用始终,而地头阶级截然矣。岂非二性乎?”南塘的意思是,如果气质之性不在未发时,而在已发时,则属于情。本然之性是性,而气质之性是情,则等于说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情。遂庵也同意南塘的观点。朝鲜时期的首都汉阳(今为首尔)位于汉江的北边,这个汉江也称为“洛水”,所以汉阳地区成立的一个学派称为“洛论”,而韩国忠清道也叫湖西,所以这个地区成立的一个学派称为“湖论”。三渊(金昌翕)等洛论学者大体赞同崔徵厚、韩弘祚、巍岩的观点,与南塘等大部分湖论学者进行论辩。等于说,洛论一般主张未发时不存在“不中”,都是“中”的状态,而湖论一般主张未发时也存在不中的情况。至于工夫论,洛论和湖论都主张未发时需要工夫,但其工夫的目的有所不同:洛论的目标是涵养本然之性,而湖论的目标是变化气质。金教授特地介绍,李显益主张未发时不需要工夫,也不能着工夫。李显益说:“且朱子之以涵养于未发,省察于已发言者,则是宽言之未发;‘未发时自着不得工夫’云者,则是窄言之未发。何尝有妨碍乎?虽然,窄言之未发,是为未发之真境,而此则以地头着工为言终不可。”李显益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心之未发已发问题。他区分广义上的未发和狭义上的未发,广义上的未发包括平时的大部分时间,而狭义上的未发是无所偏倚的状态。所以广义上的未发当然需要戒慎恐惧的工夫,而狭义上的未发根本不需要工夫,也不能着工夫。金教授不太考虑“性”的未发、已发和“心”的未发、已发之间的区别,笼统讨论“中”和“不中”的问题,但是论文中介绍的资料,对了解朝鲜时期“未发”论辩中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2.教育学研究
韩国的朱子学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教育学研究较为丰富,2021年有一篇教育学的朱子学研究博士论文《朱子“学”研究》(Han Ji-yoon,高丽大学校教育大学院,2021)和硕士论文《朱子读书法之道德教育上的含义》(朴智惠,韩国教员大学校大学院,2021),期刊论文有《朱子“仁”概念的教育学意义》(Jeon Sun-suk,《教育哲学研究》Vol.43No.2,2021);《朱熹读书法中作为读解方法的“缝罅”概念小考》(Cheon Won-seok,《读书研究》Vol.61No.9,2021);《伦理与思想》《实现知行一致的学问方法》(Han Ji-yoon,《教育哲学》Vol.81No.1);《朱子认识能力理论的教育学诠释》(Han Ji-yoon,《孔子学》Vol.45,2021)。其中,Han Ji-yoon的博士论文研究朱子“学”概念的渊源、核心内容、实践方法等,其以教育学的角度集中分析道德目的的体会及其对实践的影响。
韩国的朱子学研究中“教育学研究”经常与“比较研究”结合在一起。2021年这方面的研究有《杜威与朱熹的教育目的比较:<学校与社会>与<小学>为主》(Kim Su-youn、申昌镐,《人格教育》Vol.15No.2,2021);《人性教育的视野分析气质与性格:Chloninger,C.R.与朱熹的观点为主》(Lee Wha-sik,《学习者中心教科教育研究》Vol.21,2021);《基于人生观的道德教育比较研究:朱子与卢梭为主》(HanJi-yoon,《初等道德教育》Vol.0No.74,2021);《为改善<伦理与思想>教材“儒家伦理”部分叙述的分析与提议:朱子、阳明、退溪、栗谷的伦理思想为主》(Kang Bo-seung,《伦理教育研究》Vol.61,2021);《近代以前小学教育的结构与文字学习教材的国语教育史的意义》(Heo Jae-young,《韩末研究》 Vol.59,2021);《<小学>的韩国式变更》(Bak Soon-nam,《韩国文学论丛》Vol.87No.1,2021);《<小学>的道德教育理论与教学相长的含义》(KwonYoon-Jung,《初等道德教育》Vol.0No.74,2021)。
朝鲜时期的学者一般很重视朱子的《小学》书,对后世的影响特别大,所以现代的不少研究者关注《小学》在当代道德教育上的意义,也有些教授、教师和书院的山长等进行《小学》教育活动。申昌镐教授等的《杜威与朱熹的教育目的比较:<学校与社会>与<小学>为主》一文对朱子与杜威的道德目的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人工智能和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时代,韩国社会该追求的教育方向。按照杜威的教育思想,教育是教师—学习—环境的交互作用,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者所具有的潜在能力的开发,其方法是学习者通过对环境的经验,进行对个人知识的反省,不断重构主体的知识体系,而学校应该提供学习者能成长为社会成员的经验环境,所以学校应该跟社会联系在一起,既是学习者社会训练的机构,也是实际生活的空间。按照朱子的教育思想,小学要教学生自己训练洒扫、应对、进退的生活礼节,实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家庭、社会道德规范,以追求恢复自己的道德本性,通过与人为善,与他人共同体现共同体的公共之善。申教授等指出杜威的教育目的是个人的认知、心理的变化发展,所以没有提出具体的教育方向,而朱子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恢复本性、成为圣人,其教育方向清楚明白。申教授等认为,人类的教育与人工智能的开发有所不同,人类的教育应该考虑人格的完成、本性的恢复,而疫情全球大流行时期多多少少不重视学校的教育空间,可能导致学校的危机、教育的危机。申教授等主张今后的教育应该参考朱子、杜威的教育思想,重新建立起加强实用性、社会性功能的学校。申教授等的论文虽然没有新意,但是对朱子和杜威的教育思想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的话语:学校是人类完成个人人格,成为社会成员的教育空间。从中可见,韩国的教育研究者非常重视朱子《小学》的教育思想。
3.经学、诠释学研究
经学方面的单独或者比较的研究有《朱熹阙文说的意思与作用:<论语>的“色斯举矣”句为主》(朴英姬,《中国语文学志》Vol.77,2021);《<论语集注>的文献学读解:<学而>篇注释分析》(柳浚弼,《大东文化研究》Vol.113,2021);《中国儒学史中的“絜矩”含义演变小考:郑玄与朱熹为主》(朴素铉,《中国文学》Vol.107No.1,2021);《从<大学>解释的差异看其含义:朱熹、王守仁、尹鑴的见解为主》(Choi Jeong-mook,《东西哲学研究》Vol.99,2021);《朱熹与李滉的修辞学的<论语>诠释》(You Min-jung,《退溪学报》Vol.149,2021);《峿堂对朱子(大学章句序)的修辞学读法》(Shin Jae-sik,《退溪学论丛》Vol.37,2021);《二程<诗经>学的朝鲜时代接受样态:朝鲜时代<诗经>学中程子学与朱子学的拮抗》(金秀炅,《泰东古典研究》Vol.46,2021)。
除此以外,部分涉及朱子学的有硕士论文《正祖的<大学>解释研究》(李诗然,庆尚大学校大学院硕士论文,2021)与期刊论文《退溪李滉<启蒙传疑>收录的<周易参同契>的意义研究》(Seo Geun-sik,《东洋哲学研究》Vol.105,2021);《朝鲜知性史中“王道”与“霸道”话语》(Kim Hong-baek,《古典文学研究》Vol.60,2021);《道学文论中“载道”与周敦颐“文辞”的意思与地位再考》(李定桓,《退溪学报》Vol.150,2021);《权近<周易浅见录>中的象数学方法论》(ImJae-kyu,《泰东古典研究》Vol.46No.1,2021);《李焕模的<书传记疑>中的多维性诠释》(Lee Eun-ho,《泰东古典研究》Vol.46No.1,2021);《朝鲜后期<聚星图>制作及其意义》(Kang Shin-Ae,《美术史学研究》Vol.309,2021);《星湖李瀷与白云沈大允的<国风>说比较研究:朱熹所定的淫诗为对象》(Hong Yoon-bin,《古典与解释》Vol.33,2021);《中国灾异观的成立与变化》(Lee Suk-hyun,《人文社会科学研究》Vol.22,2021);《李睟光与郑经世的道文论》(Oh Se-hyun,《韩国汉文学研究》Vol.83,2021);《星湖李瀷的冠婚礼仪节研究》(Doh Min-jae,《温知论丛》Vol.67,2021)。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哲学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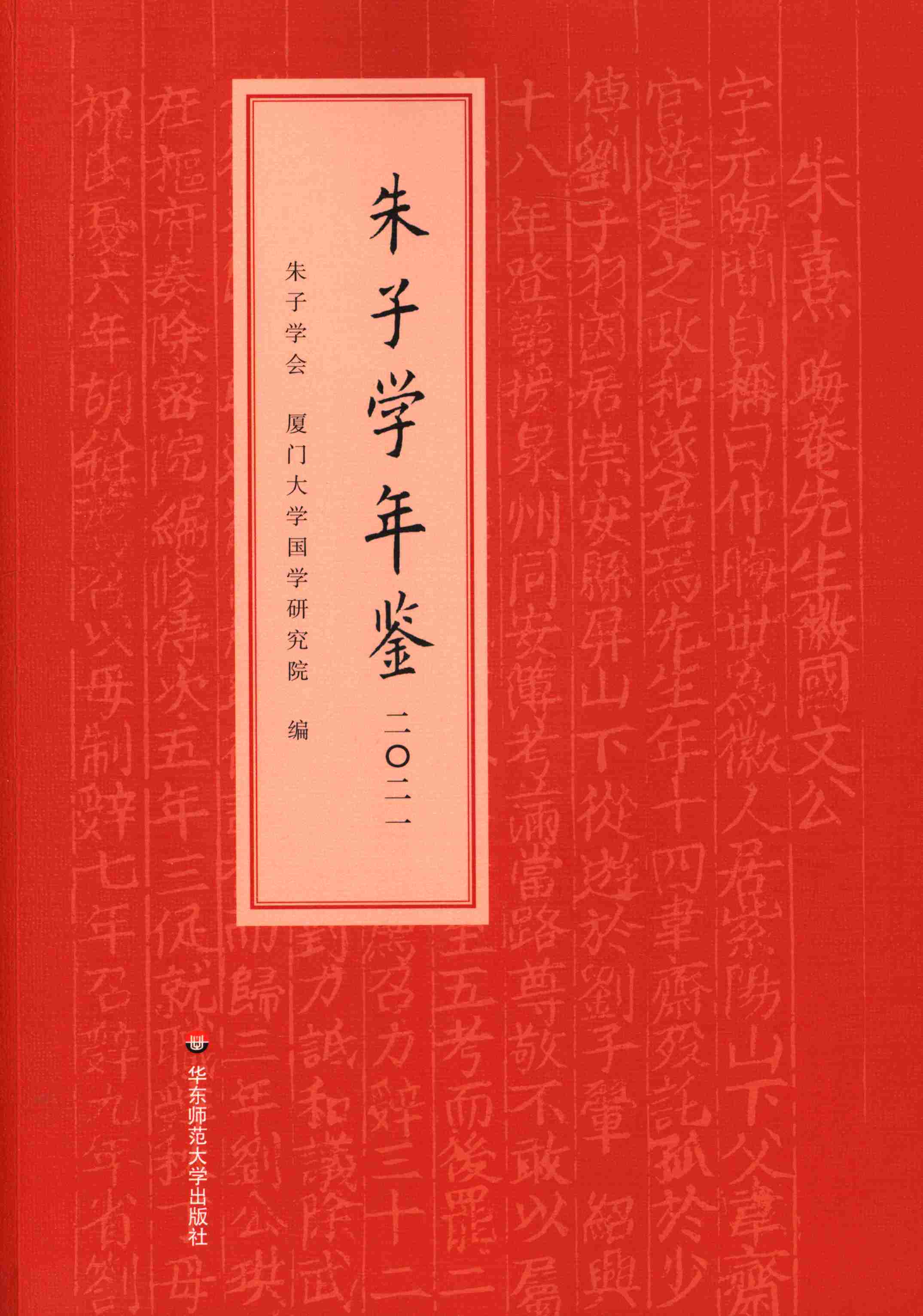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1》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共9部分: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学界概况、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收录《融突和合论——中国哲学元理》《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2021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简介》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