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熹对乡饮酒礼的改定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与朱子后学》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6696 |
| 颗粒名称: | 二、朱熹对乡饮酒礼的改定 |
| 分类号: | K892.9 |
| 页数: | 15 |
| 页码: | 24-38 |
| 摘要: | 本文详细描述了中国古代的乡饮酒礼,从《仪礼·乡饮酒礼》等文献中还原了这一传统礼仪的全过程。其中包括谋宾、邀宾、迎宾、献酒、作乐、旅酬、饮无算爵、行无算乐、送宾等环节。同时,文章分析了乡饮酒礼的主要功能,包括尊贤和养老两个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兴盛,乡饮酒礼发展出两种形式,一是鹿鸣宴,为贡举之人饯行,二是正齿位之礼,为地方上父老百姓劝善行礼、言及孝子养亲的乡饮酒礼仪式。 |
| 关键词: | 乡饮酒礼 古代 朱熹时代 |
内容
当时人已经意识到,宋代流行的鹿鸣宴,与上古乡饮酒礼之间存在巨大差异:
然古礼有宾、主、僎、介,与今之礼不同。器以尊俎,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与今之仪不同。今制,州、军贡士之月,以礼饮酒,且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人行、上舍生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序宾、养老之意也。是月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③
这种批评,实际上是用养老的正齿位礼,来批评州一级贡士鹿鸣宴。所幸当时的明州(今宁波)地区,还保留了唐代古礼的遗风(“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存”),即乡里养老之礼。于是政和议礼局讨论新礼时,便自然而然对之大加参酌借鉴,包括饮酒祭降、作乐器用之类。实际上,明州地区民间的乡饮酒礼,是一种岁末会拜之习。“以岁之元日或冬至,太守率乡之士大夫,释菜于先圣先师,而后会拜堂上,长幼有序,登降有仪,摈介有数,仿古乡饮酒礼。”①这实际上类似于唐代的“正齿位”之礼,不过加进了一些新的元素。南宋士人四处呼吁恢复乡饮酒礼,使其重回到上古乡饮酒礼尊老的本质,明州的乡饮酒礼遗俗自然成了一种文化范本。绍兴七年(1137),在四明地区“耆老会”的鼓动下,明州郡太守仇悆在当地学校中推行乡饮酒礼,后来又用官田106亩作为此后举行乡饮酒礼的开支基础。②这种经验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
绍兴十三年(1143),比部郎中林保上奏,请求制定乡饮酒礼仪制,朝廷“颁乡饮酒仪于郡国”③,即向全国颁布此礼。同时,朝廷还把是否参加过乡饮酒礼作为参与科举考试的必要前提条件:“非尝与乡饮酒者,毋得应举。”④这就是所谓“乡饮酒举士法”。四年后,即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下诏,州县每三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⑤于是乡饮酒礼便在各州郡开始推行。但是,这个制度推行十多年后,“士人不以为便”,于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四月,朝廷采纳了抚州通判陈泳的奏请,规定不再把乡饮酒礼作为举人考试的必要条件(“虽不与乡饮酒者许应举”⑥),下诏“罢乡饮酒举士法”⑦。其政策是,“乡饮酒听人自为之,公家不得预”⑧。此后,公家不再组织地方乡饮酒礼,各地自行组织。这当然导致了民间乡饮酒礼的衰落。
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是国子祭酒高闶制定的⑨,他制定时参照了明州地区的乡饮酒礼样本。这个礼式曾被朝廷“镂版颁行”,见于今本《宋会要辑稿》之“礼部”四十六。其内容较长,无法赘引,兹列其程序如下:
(1)设主、宾、僎、介、三宾、设郡僚之位;(2)释菜于先圣先师;(3)肃宾;(4)序宾;(5)主献;(6)宾酬;(7)主人酬介;(8)介酬众宾;(9)沃洗;(10)拜送;(11)约束九事。①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此礼式共有十二节:
其仪有肃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凡十二节。又有约束凡(九)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②《玉海》也有类似记载:
绍兴十三年四月六日,礼部言:“比部郎林保奏,‘修定乡饮酒矩范仪制,请遍下郡国’。今取明州已行仪制与林保所具规式参酌修具,镂版颁行。”奏可。其礼有主、宾、僎、介、三宾,有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及约束九事。③
这几处记载,大同小异。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乡饮酒礼仪式与唐代以来的鹿鸣宴显然不同。王美华根据《宋会要辑稿》,将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仪式与唐代《开元礼》进行了比较,总结出绍兴十三年所颁乡饮酒礼的若干特点:
第一,明确行之于州及县。第二,设立了主(州以郡守、县以县令为主)、宾(择乡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为宾)、僎(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介(以次长)、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其主、宾、僎、介的位置与古礼相同。开元礼无“僎”,绍兴仪制则有“僎”,显然绍兴乡饮酒礼的复古倾向更为明显。第三,“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制不见明确规定于古礼与唐《开元礼》。第四,仪制中“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诸节,比唐《开元礼》简略。……第五,“司正扬觯致辞”的寓意,充分显示了绍兴乡饮酒礼明显的尊德尚齿、劝导忠孝节义、和睦乡里的主旨。综合来说,绍兴乡饮酒礼的内容明显是唐贞观尊德尚齿的乡饮酒仪制而来的,行于州县两级的以尊德尚齿为目的的礼仪形式。①
不过,高闶草具的这个乡饮酒礼仪式颁布后,却遭到天下儒生的一致批评,《宋史》记载:“僎、介之位,皆与古制不合,诸儒莫解其指意。”②当时群儒的批评,可以从两种相反的角度来理解:其一,时人认为,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仪式的复古程度不够,或不够准确;其二,时人已经习惯了科举贡士的鹿鸣宴式的乡饮酒礼,认为这种礼仪形式不合古制。
绍兴十三年,朱熹14岁。但半个世纪之后,即庆元年间(1195—1200),博学的朱熹对高闶草具的这套礼式进行了改革:“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③
朱熹对高闶草具的绍兴十三年礼式的批评,部分地见于《朱子语类》:
乡饮酒礼:堂上主客列两边,主入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对。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试时,众士人拜知举。知举受拜了,却在堂上令众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举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礼犹有存者。近年问人则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间此礼又失了。
明州行乡饮酒礼,其仪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仪礼》,只将《礼记·乡饮酒义》做这文字。似乎编入国史实录,果然是贻笑千古者也!《仪礼》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谓迎宾;拜至,谓至阶;拜送,谓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礼中四节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两拜,客去又拜两拜,谓之“拜既”,岂非大可笑!礼,既饮,“左执爵,祭脯醢”。所以左执爵者,谓欲用右手取脯醢,从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荐脯醢”,自教一人在边进脯醢。右手自无用,却将左手只管把了爵,将右顺便手却缩了!是可笑否?
绍兴初,为乡饮酒礼,朝廷行下一仪制,极乖陋。此时乃高抑崇为礼官。看他为慎终丧礼,是煞看许多文字,如《仪礼》一齐都考得仔细。如何定乡饮酒礼乃如此疏缪?更不识着《仪礼》,只把《礼记·乡饮酒义》铺排教人行。且试举一项,如《乡饮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谢宾至堂,是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宾拜洗,是为“拜洗”。主人取爵实之,献宾,宾西阶上拜,是为“拜受”。若“拜送”,乃是宾进受爵,主人阼阶上拜,如今云“送酒”,是为“拜送爵”。宾复西阶上位,方有“拜告旨”“拜既爵”,及酢主人之礼。他乃将“拜送”,作送之门外再拜为拜送;门外两拜了,又两拜,为“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仔细。“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礼。
“抑崇”是高闶的字,《宋史》有传。他曾做过礼部员外郎、礼部侍郎②,与朱熹所说“高抑崇为礼官”相合。朱熹对高闶制定的丧礼制度,评价并不低(“考得仔细”),但对他制定的乡饮酒礼则斥为“可笑”“疏缪”“不仔细”。
从上引材料看来,朱熹批评绍兴十三年乡饮酒礼,主要集中在仪式方面。他认为,宋人的拜礼,由拜与答拜转变为“交拜”,由同向北面拜转变为对拜,是古礼之失。①他批评高闶所定仪式中,不懂“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等仪节。在高氏的礼仪版本中,甚至把主人感谢宾饮尽自己所献之酒的“拜送”,误解为送客至门外。
查《宋会要辑稿》,在“主献”环节,确有如下仪节:
主人跪,左执觯饮宾,宾拜,一拜。跪受饮釂,主人答拜。拜先兴,执事者右荐脯醢,宾受讫,兴。②
可以与《仪礼·乡饮酒礼》原文进行对照:
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宾西阶上拜,主人少退。宾进受爵以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爵,宾少退。荐脯醢。宾升席自西方,乃设折俎。主人阼阶东疑立,宾坐,左执爵,祭脯醢,奠爵于荐西,兴,右手取肺,却左手执本,坐,弗缭,右绝末以祭,尚左手,哜之。兴,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
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主人献宾之后,有司进献脯醢,然后宾左手执酒爵、右手祭脯醢(这是“祭先”的环节,即把脯醢抓一点在豆间,表示不忘造物先祖)。朱熹批评的是,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仪式中,高闶没有读懂《仪礼》中的“祭先”环节,只剩下了执事者进荐脯醢这一动作,变成了宾径直享用脯醢。朱熹的批评并非刻意挑剔和顽固复古,“左执爵,祭用右手”是古礼中的定式,纯粹是出于左右两手的使用方便。高闶礼仪中的“执事者右荐脯醢”与宾的“左执爵,祭脯醢”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另外,绍兴礼式中,把乡饮酒礼完成之后送宾出门外的仪式,称为“拜送”,这也引起朱熹的嘲笑。“拜送”又称“拜送爵”,是指行礼过程中,当宾客饮下主人所献之酒时,主人在阼阶对他所行的拜礼。不仅如此,绍兴礼式在“拜送”环节,还有“拜既拜诉”四字①。“拜既”又称“拜既爵”,指主人对宾客饮酒并“告旨”(称颂主人酒美)的回拜,如果放在整个送宾的环节,更是不类。这些错误均相当严重,难怪朱熹要予以严厉批评了。②
那么,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是什么面貌呢?《宋史·礼志》对其具体仪式有详细记载:
其主,则州以守、县以令,位于东南;宾,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介以次长,位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司正,以众所推服者;相及赞,以士之熟于礼仪者。
其日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介与众宾既入,主人序宾祭酒,再拜,诣罍洗洗觯,至酒尊所酌实觯,授执事者,至宾席前跪以献宾,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主以下各就席坐讫。酒再行,次沃洗,赞者请司正扬觯致辞,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③
此段300余字的记载,相当概括,肯定不是朱熹版本的全文,但可见其梗概。如果把《开元礼》中的乡饮酒礼、绍兴十三年高闶草具的乡饮酒礼、朱熹庆元年间改定的乡饮酒礼这三者进行比较,会发现诸多富于历史意味的现象。以下在上引王美华文的基础上,再加发覆。
第一,朱熹定礼,重新确定了宾、主、介、僎的身份和秩序,尤其是僎的身份和秩序。据《仪礼》和《礼记》,乡饮酒礼中受到礼遇的宾和介是“处士贤者”,即地方上未仕的长者、贤者,类似于后代的乡绅,郑玄注:“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而与之饮酒,是亦将献之,以礼礼宾之也。”主人,是“诸侯之乡大夫”,即地方长官。僎(古文经作遵或全,也有作驺、驯等),是本乡在外地任职的官员,他们若此时在本乡参加乡饮酒礼,要么是前来观礼,要么是辅助主人(乡大夫)完成仪式。因为不是所有的乡里都有人在外任职,也不是所有在外任职的官员都会回来参加故乡的乡饮酒礼,所以“僎”(遵者)的到来具有不确定性。在《仪礼·乡饮酒礼》的布席环节,并没有为他们安布座席;如果他们半途加入时,必须等整个仪式中某两个节目的衔接处,才能让他们进入(以免打扰整个仪式的进行)。一旦他们参加乡饮酒礼,则安布在阼阶之东北,主人在阼阶上,宾在西北,介在西南,这样形成所谓四方布席的格局:
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礼记·乡饮酒义》)
僎(遵者)的位置,说明了他们身份的特殊,他们与乡大夫同为在朝之官,与乡饮酒礼要招待的对象——德高年长的地方耆宿不同,所以坐在东边,即主人的一方;但他们的地位、德行、年齿有可能高于主人,于是将其席安在东方靠北一点。
正因为僎(遵者)是个不固定的参礼者,所以宋代以前,都没有为之常设席位。《开元礼》的《乡饮酒礼》和《正齿位》二篇中,都没有僎(遵者)的身影。北宋初年的《开宝礼》已佚,无从了解当时的国家典制。但是,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议礼局专门上呈了一道札子,其中己提到僎(遵者):
惟今州郡贡士之日设鹿鸣宴,正古者宾兴贤能,行乡饮酒之遗礼也。窃详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则与今之礼不同。其器以笾、豆、尊、俎,则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于东南,僎坐于东北,则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则与今之仪不同。①
这道奏折所批评的对象,是当时正在流行的鹿鸣宴。而议礼局的礼官们向往并试图恢复的乡饮酒礼,则有僎(遵者)的席位(“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这道奏折后来获准执行,也就是说,政和修礼使得僎(遵者)成为与宾、主、介并举的一个常设席位。而后来南宋绍兴十三年礼式中,僎(遵者)更成为一个常设席位。朱熹的庆元定礼,进一步明确了僎(遵者)的身份和地位:“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②僎(遵者)的身份逐渐法定化,反映出宋代官僚体制的变化(详下)。
第二,朱熹定礼,进一步确定了乡饮酒礼中“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式。这一仪式既不见于《仪礼》,也不见于唐代的《开元礼》,但它有着悠久的传统。《礼记·文王世子》谓:“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孔疏:
云“先圣,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为先圣,近周公处祭周公,近孔子处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辞,立学为重,故及先圣,常奠为轻,故唯祭先师,此经始立学,故奠先圣先师。①
祭先圣先师,有两种情况:一是初立学宫之时;二是平常的春、秋二仲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据正史记载,东汉时“郡国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祠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曹魏正始年间,“齐王每讲经遍,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弗躬亲”②。
北齐和隋朝已有乡饮酒礼祭先圣先师之礼,《隋书》卷九《礼仪志四》:
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③
到唐代,国家正式将释奠先圣先师列为国家祀典,与天神、地祇、人鬼共享祭祀④。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祭孔,成为成例。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下令州县学校皆建孔子庙,于是孔庙遍及全国各地。然而,唐代并没把祭孔纳入乡饮酒礼之中。
科举考试以儒家经义取士,进一步促进了士人对孔儒的崇祀。到宋代,先圣先师与进士发榜和闻喜宴联系起来,发榜唱名之后,“既谢恩,诣国学谒先圣先师,进士过堂阁下告名”⑤。绍兴乡饮酒礼仪式规定,在行礼的当天一大早,主人便要去拜祭先圣先师:“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⑥也就是说,对先圣先师行释菜礼之后,才开始肃宾和其他仪节。向先圣先师行释菜礼,虽是上古以来的学校礼仪,但从《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的演变过程来看,它与乡饮酒礼并无直接联系,只是南宋才将二者联系起来,这大概是采用明州经验的结果,因为明州地区的乡饮酒礼保存有此种仪式。
朱熹的庆元礼式,对“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程序只字未改,完全加以继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有《行乡饮酒礼告先圣文》一篇:
昨朝廷举行乡饮酒之礼,而县之有司奉行不谨,容节谬乱,仪矩阙疏,甚不足以称明天子举遗兴礼之意。今者宾兴有日,熹谨与诸生考协礼文,推阐圣制,周旋揖逊,一如旧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礼,谨修虔告。①
这篇告文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但从祭文内容可知,朱熹不满意县里举行乡饮酒礼的疏漏谬乱,故而与弟子们一起重新演练了一番乡饮酒礼。他“一如旧章”地习礼之前,首先用舍菜之礼祭祀先圣孔子。他对于向孔圣行祭的神位、时间、仪式和祭器等特别注意,专有《释奠申礼部检状》加以考订说明②。
朱熹对绍兴礼式中崇祀先圣先师仪式的继承,是他尊孔崇儒、祖述道统的必然结果。道学家特别重视尧舜禹三代、文王、周公、孔、思、孟的学脉传灯,这种“判教”也是他们被目为“道学”中人的一大标志③。正如尤褒所说:“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④乡饮酒礼的根本是教化乡里、引导人心,朱熹定礼,首先祭祀先圣先师,自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三,对照《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可知朱熹的礼式沿续了绍兴礼式从简从俗的思路,其仪节已大为减省。现将上古、唐代、宋代几个时期的乡饮酒礼仪式,用表格展列如下:
由上表可知,时代越晚,乡饮酒礼的仪式越趋简化。
1.《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戒宾环节,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不再设此①。
2.《仪礼》和《开元礼》中,主人与宾行的“一献之礼”,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只有主人献宾、宾回酢主人,省略了主人再酬宾这一环节;主人与介行礼,《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介回酢主人的环节,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则省略之。
3.在酬众宾环节,《仪礼》和《开元礼》中对三宾(长、次、又次)都是主人亲自分别酬酒;对堂下众宾的酬酒,《仪礼》由介完成,《开元礼》则由主人亲自完成(“每一人升,受爵”,即一一分别酬之)。而到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则大为减省,对三宾和堂下众宾的酬酒,均由介一人来完成,主人不再参与。
4.在旅酬环节,《仪礼》和《开元礼》都有“无算爵,无算乐”,而绍兴礼式虽然也说到“修爵无算”,但限定为“酒三行”,并特别注明:“每酒一行,主人揖宾及介,介揖众宾,并礼生唱之。”也就是说,主、宾、介、众宾依顺序献酒,饮三个循环。而到了朱熹礼式中,更简化为“酒再行”,即只饮两个循环。
5.《仪礼》和《开元礼》中均有歌笙作乐环节,而绍兴仪式和朱熹礼式中未有明载。《宋史·乐志》记载有《淳化乡饮酒》三十三章,包括《鹿鸣》六章、《南陔》二章、《嘉鱼》八章、《崇丘》二章、《关雎》十章、《鹊巢》六章。①这些都只是袭用了《诗经·小雅》中的篇名,其具体歌词并非《诗经》原句,当是宋人创作,以用于科举贡士的鹿鸣宴。政和议礼时,奏议称“其有古乐处,令用古乐”②。然而,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均没有提到用乐的仪节。朱熹本人十分清楚,《鹿鸣》三诗是“上下通用之乐”,“乡饮酒亦用”③。无奈他身处的南宋时代,古乐散失殆尽:“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④可能正由于此,他制礼时将“作乐”一项付之阙如。至于当时民间基层社会举行乡饮酒礼时是否用乐,还有待考证。
第四,在删繁就简的同时,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却另外增加了一个“沃洗”仪节。它被安排在旅酬的“酒三行”(朱熹的“酒再行”)之后。朱熹礼式在《宋史·礼志》中只有“沃洗”这样一个名目,其细节不得而知,但绍兴礼式却载之甚详:
沃洗:卒饮,赞者诣主人席前唱曰:“请主人沃洗。”相者捧觯,请主人酌酒。相者捧觯诣洗所,跪,直洗者亦跪受,立饮讫。各就位扬觯。赞者诣席前唱曰:“主人以下皆执笏。”次引司正出位,赞者曰:“请司正扬觯。”次引司正取主人觯诣洗觯,至席前跪而扬觯讫。赞者请司正致词。司正乃言曰:“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仰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今兹举行乡饮,非专为饮食而已,凡我长幼,各相劝勉,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胥训告,胥教诲,毋或愆堕,以忝所生。”赞者曰:“修爵讫。”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①
这一段仪节,不见于《仪礼》,在《开元礼》的《乡饮酒》中也无有所见。但从《开元礼》的《正齿位》中则可以发现它的前缘:
司正适篚,跪取觯,兴,进,立于楹间,北面,乃扬觯而言曰:“朝廷率由旧章,敦行礼教,凡我长幼,各相劝勖,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无或僭惰,以忝所生。”宾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觯,再拜,跪取觯饮,卒爵,兴。宾、主以下皆坐,司正适篚,跪,奠觯,兴,降复位。无算爵。②
不难发现,南宋乡饮酒礼的“沃洗”环节,是由唐代正齿位的“司正扬觯而言”演变而来。它设在乡饮酒礼的末尾,通过司正的一番话,来宣示举行乡饮酒礼的目的,并劝勉参加的乡党们要敦行礼教,孝忠家国。
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发展了唐人在乡饮酒礼末尾的这番宣教仪节。
“司正”之职,在上古礼制中一般由主人之相(身份很低)担任,在饮酒、耦射等环节中“正宾主之礼”,即进行礼制监察。在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旅酬阶段,他“当监旅酬”(郑玄注)。由这种“正气凛然”的身份角色来进行宣示礼教,非常自然。与唐代《开元礼》稍有不同的是,宋礼司正的开场词是“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这与上古乐教的“道古”环节可以对应。《礼记·乐记》说,凡是正音雅乐演奏之后,都有一个“道古”的环节:“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宋人之所以要重拾并强调这个“道古”仪节,多多少少与它的内涵有关——“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正是南宋理学家们念兹在兹的根本追求,也正是理学家们通过仪式来教化乡里的一个重要抓手。
然古礼有宾、主、僎、介,与今之礼不同。器以尊俎,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东南,僎坐东北,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与今之仪不同。今制,州、军贡士之月,以礼饮酒,且以知州、军事为主人。学事司所在,以提举学事为主人。其次本州官人行、上舍生当贡者与州之群老,为众宾,亦古者序宾、养老之意也。是月也,会凡学之士及武士习射,亦古者习射于序之意也。③
这种批评,实际上是用养老的正齿位礼,来批评州一级贡士鹿鸣宴。所幸当时的明州(今宁波)地区,还保留了唐代古礼的遗风(“唐贞观所颁礼,惟明州独存”),即乡里养老之礼。于是政和议礼局讨论新礼时,便自然而然对之大加参酌借鉴,包括饮酒祭降、作乐器用之类。实际上,明州地区民间的乡饮酒礼,是一种岁末会拜之习。“以岁之元日或冬至,太守率乡之士大夫,释菜于先圣先师,而后会拜堂上,长幼有序,登降有仪,摈介有数,仿古乡饮酒礼。”①这实际上类似于唐代的“正齿位”之礼,不过加进了一些新的元素。南宋士人四处呼吁恢复乡饮酒礼,使其重回到上古乡饮酒礼尊老的本质,明州的乡饮酒礼遗俗自然成了一种文化范本。绍兴七年(1137),在四明地区“耆老会”的鼓动下,明州郡太守仇悆在当地学校中推行乡饮酒礼,后来又用官田106亩作为此后举行乡饮酒礼的开支基础。②这种经验在全国起到示范效应。
绍兴十三年(1143),比部郎中林保上奏,请求制定乡饮酒礼仪制,朝廷“颁乡饮酒仪于郡国”③,即向全国颁布此礼。同时,朝廷还把是否参加过乡饮酒礼作为参与科举考试的必要前提条件:“非尝与乡饮酒者,毋得应举。”④这就是所谓“乡饮酒举士法”。四年后,即绍兴十七年(1147),朝廷下诏,州县每三年举行一次乡饮酒礼,⑤于是乡饮酒礼便在各州郡开始推行。但是,这个制度推行十多年后,“士人不以为便”,于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四月,朝廷采纳了抚州通判陈泳的奏请,规定不再把乡饮酒礼作为举人考试的必要条件(“虽不与乡饮酒者许应举”⑥),下诏“罢乡饮酒举士法”⑦。其政策是,“乡饮酒听人自为之,公家不得预”⑧。此后,公家不再组织地方乡饮酒礼,各地自行组织。这当然导致了民间乡饮酒礼的衰落。
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是国子祭酒高闶制定的⑨,他制定时参照了明州地区的乡饮酒礼样本。这个礼式曾被朝廷“镂版颁行”,见于今本《宋会要辑稿》之“礼部”四十六。其内容较长,无法赘引,兹列其程序如下:
(1)设主、宾、僎、介、三宾、设郡僚之位;(2)释菜于先圣先师;(3)肃宾;(4)序宾;(5)主献;(6)宾酬;(7)主人酬介;(8)介酬众宾;(9)沃洗;(10)拜送;(11)约束九事。①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此礼式共有十二节:
其仪有肃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凡十二节。又有约束凡(九)事。主人以守令,其酒食器用,乡大夫士之有力者共为之。②《玉海》也有类似记载:
绍兴十三年四月六日,礼部言:“比部郎林保奏,‘修定乡饮酒矩范仪制,请遍下郡国’。今取明州已行仪制与林保所具规式参酌修具,镂版颁行。”奏可。其礼有主、宾、僎、介、三宾,有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沃洗、扬觯、拜送、拜既,及约束九事。③
这几处记载,大同小异。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乡饮酒礼仪式与唐代以来的鹿鸣宴显然不同。王美华根据《宋会要辑稿》,将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仪式与唐代《开元礼》进行了比较,总结出绍兴十三年所颁乡饮酒礼的若干特点:
第一,明确行之于州及县。第二,设立了主(州以郡守、县以县令为主)、宾(择乡里寄居年德高及致仕者为宾)、僎(州以通判、县以丞或簿)、介(以次长)、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其主、宾、僎、介的位置与古礼相同。开元礼无“僎”,绍兴仪制则有“僎”,显然绍兴乡饮酒礼的复古倾向更为明显。第三,“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制不见明确规定于古礼与唐《开元礼》。第四,仪制中“肃宾、序宾、祭酒、主献、宾酬、主人酬介、介酬众宾、修爵无算”诸节,比唐《开元礼》简略。……第五,“司正扬觯致辞”的寓意,充分显示了绍兴乡饮酒礼明显的尊德尚齿、劝导忠孝节义、和睦乡里的主旨。综合来说,绍兴乡饮酒礼的内容明显是唐贞观尊德尚齿的乡饮酒仪制而来的,行于州县两级的以尊德尚齿为目的的礼仪形式。①
不过,高闶草具的这个乡饮酒礼仪式颁布后,却遭到天下儒生的一致批评,《宋史》记载:“僎、介之位,皆与古制不合,诸儒莫解其指意。”②当时群儒的批评,可以从两种相反的角度来理解:其一,时人认为,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礼仪式的复古程度不够,或不够准确;其二,时人已经习惯了科举贡士的鹿鸣宴式的乡饮酒礼,认为这种礼仪形式不合古制。
绍兴十三年,朱熹14岁。但半个世纪之后,即庆元年间(1195—1200),博学的朱熹对高闶草具的这套礼式进行了改革:“庆元中,朱熹以《仪礼》改定,知学者皆尊用之,主、宾、僎、介之位,始有定说。”③
朱熹对高闶草具的绍兴十三年礼式的批评,部分地见于《朱子语类》:
乡饮酒礼:堂上主客列两边,主入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对。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试时,众士人拜知举。知举受拜了,却在堂上令众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举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礼犹有存者。近年问人则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间此礼又失了。
明州行乡饮酒礼,其仪乃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仪礼》,只将《礼记·乡饮酒义》做这文字。似乎编入国史实录,果然是贻笑千古者也!《仪礼》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谓迎宾;拜至,谓至阶;拜送,谓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礼中四节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两拜,客去又拜两拜,谓之“拜既”,岂非大可笑!礼,既饮,“左执爵,祭脯醢”。所以左执爵者,谓欲用右手取脯醢,从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荐脯醢”,自教一人在边进脯醢。右手自无用,却将左手只管把了爵,将右顺便手却缩了!是可笑否?
绍兴初,为乡饮酒礼,朝廷行下一仪制,极乖陋。此时乃高抑崇为礼官。看他为慎终丧礼,是煞看许多文字,如《仪礼》一齐都考得仔细。如何定乡饮酒礼乃如此疏缪?更不识着《仪礼》,只把《礼记·乡饮酒义》铺排教人行。且试举一项,如《乡饮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宾升,主人阼阶上当楣北面再拜,谢宾至堂,是为“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宾拜洗,是为“拜洗”。主人取爵实之,献宾,宾西阶上拜,是为“拜受”。若“拜送”,乃是宾进受爵,主人阼阶上拜,如今云“送酒”,是为“拜送爵”。宾复西阶上位,方有“拜告旨”“拜既爵”,及酢主人之礼。他乃将“拜送”,作送之门外再拜为拜送;门外两拜了,又两拜,为“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仔细。“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礼。
“抑崇”是高闶的字,《宋史》有传。他曾做过礼部员外郎、礼部侍郎②,与朱熹所说“高抑崇为礼官”相合。朱熹对高闶制定的丧礼制度,评价并不低(“考得仔细”),但对他制定的乡饮酒礼则斥为“可笑”“疏缪”“不仔细”。
从上引材料看来,朱熹批评绍兴十三年乡饮酒礼,主要集中在仪式方面。他认为,宋人的拜礼,由拜与答拜转变为“交拜”,由同向北面拜转变为对拜,是古礼之失。①他批评高闶所定仪式中,不懂“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等仪节。在高氏的礼仪版本中,甚至把主人感谢宾饮尽自己所献之酒的“拜送”,误解为送客至门外。
查《宋会要辑稿》,在“主献”环节,确有如下仪节:
主人跪,左执觯饮宾,宾拜,一拜。跪受饮釂,主人答拜。拜先兴,执事者右荐脯醢,宾受讫,兴。②
可以与《仪礼·乡饮酒礼》原文进行对照:
主人坐取爵,实之宾之席前,西北面献宾。宾西阶上拜,主人少退。宾进受爵以复位。主人阼阶上拜送爵,宾少退。荐脯醢。宾升席自西方,乃设折俎。主人阼阶东疑立,宾坐,左执爵,祭脯醢,奠爵于荐西,兴,右手取肺,却左手执本,坐,弗缭,右绝末以祭,尚左手,哜之。兴,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兴,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执爵,兴。主人阼阶上答拜。
按照《仪礼·乡饮酒礼》,主人献宾之后,有司进献脯醢,然后宾左手执酒爵、右手祭脯醢(这是“祭先”的环节,即把脯醢抓一点在豆间,表示不忘造物先祖)。朱熹批评的是,绍兴十三年的乡饮酒仪式中,高闶没有读懂《仪礼》中的“祭先”环节,只剩下了执事者进荐脯醢这一动作,变成了宾径直享用脯醢。朱熹的批评并非刻意挑剔和顽固复古,“左执爵,祭用右手”是古礼中的定式,纯粹是出于左右两手的使用方便。高闶礼仪中的“执事者右荐脯醢”与宾的“左执爵,祭脯醢”完全不是同一回事。
另外,绍兴礼式中,把乡饮酒礼完成之后送宾出门外的仪式,称为“拜送”,这也引起朱熹的嘲笑。“拜送”又称“拜送爵”,是指行礼过程中,当宾客饮下主人所献之酒时,主人在阼阶对他所行的拜礼。不仅如此,绍兴礼式在“拜送”环节,还有“拜既拜诉”四字①。“拜既”又称“拜既爵”,指主人对宾客饮酒并“告旨”(称颂主人酒美)的回拜,如果放在整个送宾的环节,更是不类。这些错误均相当严重,难怪朱熹要予以严厉批评了。②
那么,朱熹改定的乡饮酒礼是什么面貌呢?《宋史·礼志》对其具体仪式有详细记载:
其主,则州以守、县以令,位于东南;宾,以里居年高及致仕者,位于西北;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介以次长,位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司正,以众所推服者;相及赞,以士之熟于礼仪者。
其日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介与众宾既入,主人序宾祭酒,再拜,诣罍洗洗觯,至酒尊所酌实觯,授执事者,至宾席前跪以献宾,宾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众宾,宾主以下各就席坐讫。酒再行,次沃洗,赞者请司正扬觯致辞,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主人兴,复至阼阶楣下,僎从。宾、介复至西阶下立,三宾至西阶立,并南向。主人拜,宾、介以下再拜。宾、介与众宾先自西趋出,主人少立,自东出。宾以下立于庠门外之右,东乡;主人立于门外之左,西乡,僎从。主人再拜,宾介以下皆再拜,退。③
此段300余字的记载,相当概括,肯定不是朱熹版本的全文,但可见其梗概。如果把《开元礼》中的乡饮酒礼、绍兴十三年高闶草具的乡饮酒礼、朱熹庆元年间改定的乡饮酒礼这三者进行比较,会发现诸多富于历史意味的现象。以下在上引王美华文的基础上,再加发覆。
第一,朱熹定礼,重新确定了宾、主、介、僎的身份和秩序,尤其是僎的身份和秩序。据《仪礼》和《礼记》,乡饮酒礼中受到礼遇的宾和介是“处士贤者”,即地方上未仕的长者、贤者,类似于后代的乡绅,郑玄注:“贤者为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众宾,而与之饮酒,是亦将献之,以礼礼宾之也。”主人,是“诸侯之乡大夫”,即地方长官。僎(古文经作遵或全,也有作驺、驯等),是本乡在外地任职的官员,他们若此时在本乡参加乡饮酒礼,要么是前来观礼,要么是辅助主人(乡大夫)完成仪式。因为不是所有的乡里都有人在外任职,也不是所有在外任职的官员都会回来参加故乡的乡饮酒礼,所以“僎”(遵者)的到来具有不确定性。在《仪礼·乡饮酒礼》的布席环节,并没有为他们安布座席;如果他们半途加入时,必须等整个仪式中某两个节目的衔接处,才能让他们进入(以免打扰整个仪式的进行)。一旦他们参加乡饮酒礼,则安布在阼阶之东北,主人在阼阶上,宾在西北,介在西南,这样形成所谓四方布席的格局:
宾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阴阳也,三宾象三光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接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接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僎于东北,以辅主人也。(《礼记·乡饮酒义》)
僎(遵者)的位置,说明了他们身份的特殊,他们与乡大夫同为在朝之官,与乡饮酒礼要招待的对象——德高年长的地方耆宿不同,所以坐在东边,即主人的一方;但他们的地位、德行、年齿有可能高于主人,于是将其席安在东方靠北一点。
正因为僎(遵者)是个不固定的参礼者,所以宋代以前,都没有为之常设席位。《开元礼》的《乡饮酒礼》和《正齿位》二篇中,都没有僎(遵者)的身影。北宋初年的《开宝礼》已佚,无从了解当时的国家典制。但是,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议礼局专门上呈了一道札子,其中己提到僎(遵者):
惟今州郡贡士之日设鹿鸣宴,正古者宾兴贤能,行乡饮酒之遗礼也。窃详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则与今之礼不同。其器以笾、豆、尊、俎,则与今之器不同。宾坐于西北,介坐于西南,主人坐于东南,僎坐于东北,则与今之位不同。主人献宾,宾酢主人,主人酬宾;次主人献介,介酢主人;次主人献众宾。则与今之仪不同。①
这道奏折所批评的对象,是当时正在流行的鹿鸣宴。而议礼局的礼官们向往并试图恢复的乡饮酒礼,则有僎(遵者)的席位(“古者乡饮酒仪立宾、主、僎、介”)。这道奏折后来获准执行,也就是说,政和修礼使得僎(遵者)成为与宾、主、介并举的一个常设席位。而后来南宋绍兴十三年礼式中,僎(遵者)更成为一个常设席位。朱熹的庆元定礼,进一步明确了僎(遵者)的身份和地位:“僎,则州以倅、县以丞或簿,位东北。”②僎(遵者)的身份逐渐法定化,反映出宋代官僚体制的变化(详下)。
第二,朱熹定礼,进一步确定了乡饮酒礼中“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仪式。这一仪式既不见于《仪礼》,也不见于唐代的《开元礼》,但它有着悠久的传统。《礼记·文王世子》谓:“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孔疏:
云“先圣,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为先圣,近周公处祭周公,近孔子处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辞,立学为重,故及先圣,常奠为轻,故唯祭先师,此经始立学,故奠先圣先师。①
祭先圣先师,有两种情况:一是初立学宫之时;二是平常的春、秋二仲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据正史记载,东汉时“郡国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祠先圣先师周公、孔子,牲以太牢”;曹魏正始年间,“齐王每讲经遍,辄使太常释奠先圣先师于辟雍,弗躬亲”②。
北齐和隋朝已有乡饮酒礼祭先圣先师之礼,《隋书》卷九《礼仪志四》:
后齐制,新立学,必释奠礼先圣先师,每岁春秋二仲,常行其礼。……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年别一行乡饮酒礼。州郡学则以春秋仲月释奠。州郡县亦每年于学一行乡饮酒礼。③
到唐代,国家正式将释奠先圣先师列为国家祀典,与天神、地祇、人鬼共享祭祀④。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即二月和八月的第一个丁日祭孔,成为成例。贞观四年(630),唐太宗下令州县学校皆建孔子庙,于是孔庙遍及全国各地。然而,唐代并没把祭孔纳入乡饮酒礼之中。
科举考试以儒家经义取士,进一步促进了士人对孔儒的崇祀。到宋代,先圣先师与进士发榜和闻喜宴联系起来,发榜唱名之后,“既谢恩,诣国学谒先圣先师,进士过堂阁下告名”⑤。绍兴乡饮酒礼仪式规定,在行礼的当天一大早,主人便要去拜祭先圣先师:“质明,主人率宾以下,先释菜于先圣先师,退各就次,以俟肃宾。”⑥也就是说,对先圣先师行释菜礼之后,才开始肃宾和其他仪节。向先圣先师行释菜礼,虽是上古以来的学校礼仪,但从《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的演变过程来看,它与乡饮酒礼并无直接联系,只是南宋才将二者联系起来,这大概是采用明州经验的结果,因为明州地区的乡饮酒礼保存有此种仪式。
朱熹的庆元礼式,对“释菜于先圣先师”这一程序只字未改,完全加以继承。《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有《行乡饮酒礼告先圣文》一篇:
昨朝廷举行乡饮酒之礼,而县之有司奉行不谨,容节谬乱,仪矩阙疏,甚不足以称明天子举遗兴礼之意。今者宾兴有日,熹谨与诸生考协礼文,推阐圣制,周旋揖逊,一如旧章。即事之初,敢以舍菜之礼,谨修虔告。①
这篇告文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但从祭文内容可知,朱熹不满意县里举行乡饮酒礼的疏漏谬乱,故而与弟子们一起重新演练了一番乡饮酒礼。他“一如旧章”地习礼之前,首先用舍菜之礼祭祀先圣孔子。他对于向孔圣行祭的神位、时间、仪式和祭器等特别注意,专有《释奠申礼部检状》加以考订说明②。
朱熹对绍兴礼式中崇祀先圣先师仪式的继承,是他尊孔崇儒、祖述道统的必然结果。道学家特别重视尧舜禹三代、文王、周公、孔、思、孟的学脉传灯,这种“判教”也是他们被目为“道学”中人的一大标志③。正如尤褒所说:“夫道学者,尧、舜所以帝,禹、汤、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设教。”④乡饮酒礼的根本是教化乡里、引导人心,朱熹定礼,首先祭祀先圣先师,自然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第三,对照《仪礼·乡饮酒礼》《礼记·乡饮酒义》和《开元礼》,可知朱熹的礼式沿续了绍兴礼式从简从俗的思路,其仪节已大为减省。现将上古、唐代、宋代几个时期的乡饮酒礼仪式,用表格展列如下:
由上表可知,时代越晚,乡饮酒礼的仪式越趋简化。
1.《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戒宾环节,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不再设此①。
2.《仪礼》和《开元礼》中,主人与宾行的“一献之礼”,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只有主人献宾、宾回酢主人,省略了主人再酬宾这一环节;主人与介行礼,《仪礼》和《开元礼》中,都有介回酢主人的环节,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则省略之。
3.在酬众宾环节,《仪礼》和《开元礼》中对三宾(长、次、又次)都是主人亲自分别酬酒;对堂下众宾的酬酒,《仪礼》由介完成,《开元礼》则由主人亲自完成(“每一人升,受爵”,即一一分别酬之)。而到了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则大为减省,对三宾和堂下众宾的酬酒,均由介一人来完成,主人不再参与。
4.在旅酬环节,《仪礼》和《开元礼》都有“无算爵,无算乐”,而绍兴礼式虽然也说到“修爵无算”,但限定为“酒三行”,并特别注明:“每酒一行,主人揖宾及介,介揖众宾,并礼生唱之。”也就是说,主、宾、介、众宾依顺序献酒,饮三个循环。而到了朱熹礼式中,更简化为“酒再行”,即只饮两个循环。
5.《仪礼》和《开元礼》中均有歌笙作乐环节,而绍兴仪式和朱熹礼式中未有明载。《宋史·乐志》记载有《淳化乡饮酒》三十三章,包括《鹿鸣》六章、《南陔》二章、《嘉鱼》八章、《崇丘》二章、《关雎》十章、《鹊巢》六章。①这些都只是袭用了《诗经·小雅》中的篇名,其具体歌词并非《诗经》原句,当是宋人创作,以用于科举贡士的鹿鸣宴。政和议礼时,奏议称“其有古乐处,令用古乐”②。然而,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中,均没有提到用乐的仪节。朱熹本人十分清楚,《鹿鸣》三诗是“上下通用之乐”,“乡饮酒亦用”③。无奈他身处的南宋时代,古乐散失殆尽:“今之礼,尚有见于威仪辞逊之际;若乐,则全是失了!”④可能正由于此,他制礼时将“作乐”一项付之阙如。至于当时民间基层社会举行乡饮酒礼时是否用乐,还有待考证。
第四,在删繁就简的同时,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却另外增加了一个“沃洗”仪节。它被安排在旅酬的“酒三行”(朱熹的“酒再行”)之后。朱熹礼式在《宋史·礼志》中只有“沃洗”这样一个名目,其细节不得而知,但绍兴礼式却载之甚详:
沃洗:卒饮,赞者诣主人席前唱曰:“请主人沃洗。”相者捧觯,请主人酌酒。相者捧觯诣洗所,跪,直洗者亦跪受,立饮讫。各就位扬觯。赞者诣席前唱曰:“主人以下皆执笏。”次引司正出位,赞者曰:“请司正扬觯。”次引司正取主人觯诣洗觯,至席前跪而扬觯讫。赞者请司正致词。司正乃言曰:“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仰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今兹举行乡饮,非专为饮食而已,凡我长幼,各相劝勉,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胥训告,胥教诲,毋或愆堕,以忝所生。”赞者曰:“修爵讫。”司正复位,主人以下复坐。①
这一段仪节,不见于《仪礼》,在《开元礼》的《乡饮酒》中也无有所见。但从《开元礼》的《正齿位》中则可以发现它的前缘:
司正适篚,跪取觯,兴,进,立于楹间,北面,乃扬觯而言曰:“朝廷率由旧章,敦行礼教,凡我长幼,各相劝勖,忠于国,孝于亲,内穆于闺门,外比于乡党,无或僭惰,以忝所生。”宾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觯,再拜,跪取觯饮,卒爵,兴。宾、主以下皆坐,司正适篚,跪,奠觯,兴,降复位。无算爵。②
不难发现,南宋乡饮酒礼的“沃洗”环节,是由唐代正齿位的“司正扬觯而言”演变而来。它设在乡饮酒礼的末尾,通过司正的一番话,来宣示举行乡饮酒礼的目的,并劝勉参加的乡党们要敦行礼教,孝忠家国。
绍兴礼式和朱熹礼式发展了唐人在乡饮酒礼末尾的这番宣教仪节。
“司正”之职,在上古礼制中一般由主人之相(身份很低)担任,在饮酒、耦射等环节中“正宾主之礼”,即进行礼制监察。在乡饮酒礼和乡射礼的旅酬阶段,他“当监旅酬”(郑玄注)。由这种“正气凛然”的身份角色来进行宣示礼教,非常自然。与唐代《开元礼》稍有不同的是,宋礼司正的开场词是“古者于旅也语,于是道古”,这与上古乐教的“道古”环节可以对应。《礼记·乐记》说,凡是正音雅乐演奏之后,都有一个“道古”的环节:“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宋人之所以要重拾并强调这个“道古”仪节,多多少少与它的内涵有关——“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正是南宋理学家们念兹在兹的根本追求,也正是理学家们通过仪式来教化乡里的一个重要抓手。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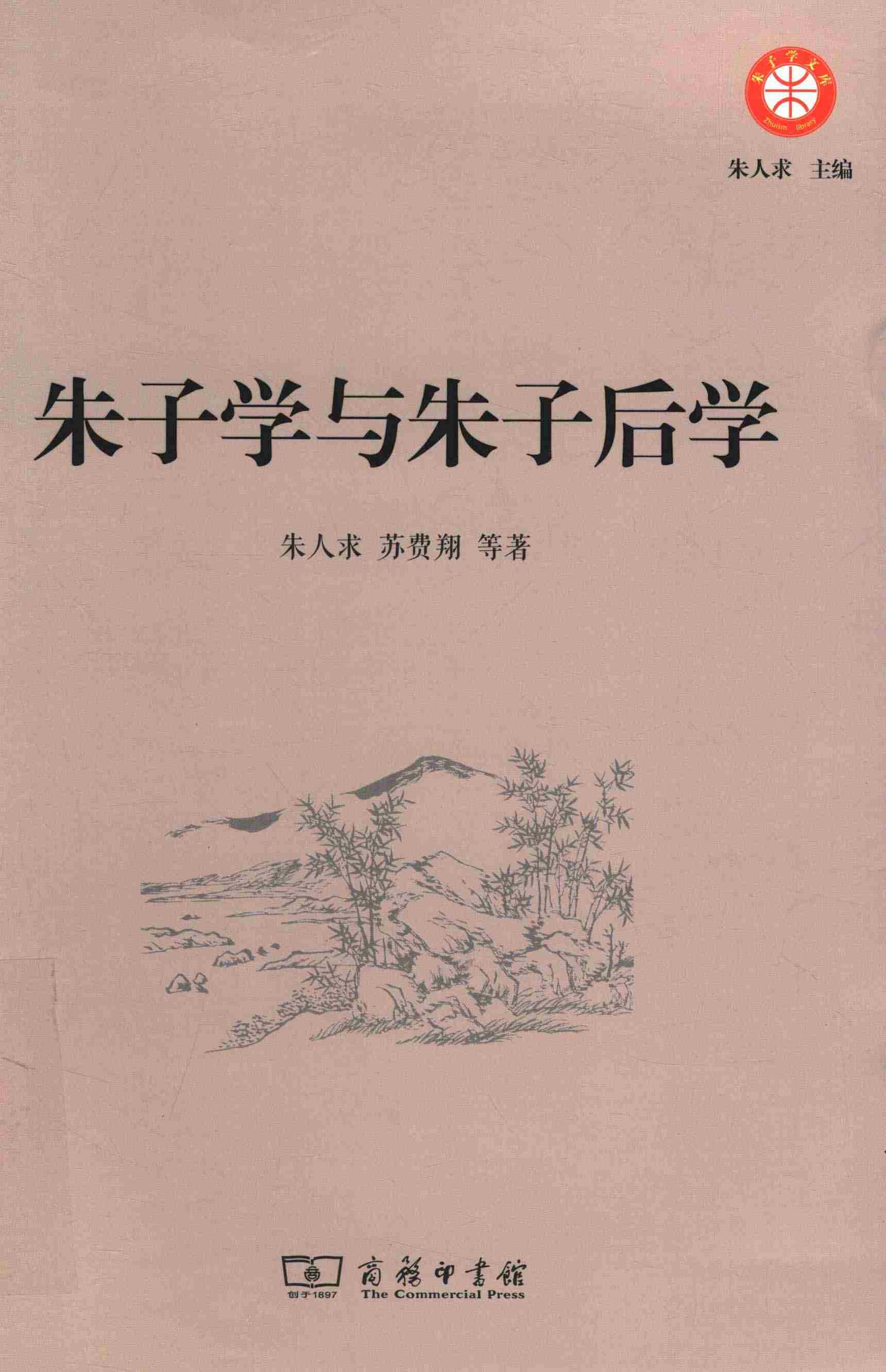
《朱子学与朱子后学》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收录了来自美国、德国、法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知名朱子学者近作14篇,内容涉及朱子的道统论、礼学、气论、诗论、格物致知论、人心道心、家国天下等问题,时间上从南宋跨越到现代,空间上从中国走向东亚世界,以点带面,简单勾勒了朱子思想的多元面向,介绍了朱子学的思想理念、政治实践及其当代价值。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