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日本的场合——其二:朱舜水与安东省庵、德川光圀等
| 内容出处: | 《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028 |
| 颗粒名称: | 四 日本的场合——其二:朱舜水与安东省庵、德川光圀等 |
| 分类号: | K892.27 |
| 页数: | 13 |
| 页码: | 303-31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舜水在长崎为德川光圀制作深衣时,他坦言深衣制作不易,需要文献考证和复原各种装饰。小宅处斋询问了野服制作的问题,朱舜水回答说野服在历代都有变化。 |
| 关键词: | 南平市 礼文备具 家礼 |
内容
接下来应注意的事例是朱舜水的场合,因为他于万治二年(1659)亡命长崎之后,曾尝试制作深衣。邀请他制作的先是安东省庵,然后是德川光圀。
(一)安东省庵
安东省庵(1622—1701)为柳川藩的儒者,松永尺五的门人,因师事朱舜水并援助其在长崎的生活而闻名。
省庵向朱舜水请教了各种问题,服装是其所关心的事情之一。例如,他们有如下的问答:
问:老师所服,是大明礼服否?
答:巾、道袍,大明谓之亵衣,不敢施于公廷之上。下者非上命不敢服此见上人,上人亦不敢衣此见秀才,惟燕居为可耳。今来日本,乃以此为礼衣,实非也。(《答安东守约问八条》,《朱舜水集》上册《问答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374)
据此,朱舜水没有身着深衣、幅巾,所穿的是道袍,他称之为“亵衣”。道袍是平时的服装,这一点已如上述。另外,他虽然戴有头巾,但不是幅巾,而是包玉巾。由其他资料可以确认,朱舜水平时身着道袍(道服)和包玉巾,43其姿态由目前存于水户德川家的朱舜水坐像可以窥见(<图13>)。
省庵由对服饰的关心,进而向朱舜水请求制作深衣:
日本儒者能整顿得冠婚葬祭四大节,亦是一事。
问:将以深衣为日本之礼服,如何?
答:颇好,但图中有差处,不佞不解,亦无余银,令裁工制来一看。(《朱舜水寄安东省庵笔语》44)
这是说,省庵为了整理冠婚葬祭的仪礼,而问“以深衣为日本之礼服,如何?”,这是很大胆的说法。对此,朱舜水回答道,深衣的制作方法不太清楚,而且深衣图前后有矛盾,因此先让裁工试做一下。
但是,制作深衣并非易事。省庵向朱舜水这样说道:
凶服之制,素所愿也。制之则深衣幅巾,非力所及,不若凶服唯衰而已。制深衣幅巾也,敬计合吉凶服,出银二十两余,则方决为之。去年借银多矣,无可通移者。(安东守约《上朱先生二十二首》第16,《朱舜水集》上册,页754)
在这里,省庵改变了方针,由于凶服(丧服)比深衣、幅巾是更为简易的服装,所以想首先制作“衰衣”(斩衰、齐衰)。而且,如果这些吉服、凶服都要做成,制作费用需要共计银二十余两的巨款,这毕竟无法筹备。另一方面,朱舜水在给省庵的信中则说:
制深衣裁工,为虏官所获,囚禁狱中未来,来则急急为之,无问其费矣。潦草则所费不甚相远,而不可以为式,亦不可也。历访他工无知者,今好此者多,但未有能之者耳。(《与安东守约书二十五首》第18,《朱舜水集》上册,页166)也就是说,可依托的裁工不知何故被逮捕了,导致深衣制作受挫。虽然让其他裁工做了尝试,但是却没有能够正经地按照礼式正确制作深衣的有技术的人。朱舜水进而说道:
明朝衰衣之制……今所做者无此,失其制矣。……惟深衣幅巾,能为之者,百中之一二耳。必竢前工到,方可为之,须少宽半年。梁冠不佞亦能为,当备料制奉。(《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第13,《朱舜水集》上册,页182)在这里,朱舜水说,制作儒教所说的衰衣也并不容易,至于深衣、幅巾,由于没有适当的裁工,希望再等半年。所谓“俟前工到”,大致是指等到上述被逮捕的裁工回来以后的意思。
由此可见,深衣制作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若是粗略地制作,那么另当别论,如果要按照礼式来制作,那么有以下各种因素对制作造成了妨碍:第一、朱舜水未见过深衣,第二、必须按照《家礼》及其他各种文献来正确地再现,第三、需要一定的费用,第四、有技术的裁工几乎没有,第五、好不容易找到的裁工却发生了被逮捕的意外事件,等等。最终的结果似乎是朱舜水未能为省庵制成深衣。
(二)德川光圀
宽文五年(1665)六月,朱舜水为了服务于德川光圀而从长崎来到江户。这一次,他为了光圀而开始着手深衣的制作。
如上所述,在前一年的宽文四年(1664),德川光圀圀的使者小宅处斋曾为了招聘朱舜水而访问长崎,当时两人有过一场笔谈。并不太受人注意的是,两人最初的问答正是围绕深衣的问题:
问:本邦近代儒风日盛,师及门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风。然所制者,皆以《礼记》及《朱子家礼》、罗氏《鹤林玉露》等考之。异域殊俗,虽以义兴之,而广狭长短不便人体。想尺度之品、制法之义,别有所传乎?赐教示。
答:……仆匏系长崎,如坐井观天……至若深衣之制,亦只学圣之粗迹耳。《玉藻》文深义远,诚为难解。《家礼》徒成聚讼,未有定规。服深衣,必冠缁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带,系带有绦,垂与裳齐,屦顺裳色,絇繶纯纂(綦)。贵国衣服有制,恐未敢轻易改易也。(《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朱舜水集》上册《问答四》第1条)
在这里,小宅处斋就深衣及野服的制作进行了询问,朱舜水的回答与其对安东省庵的回答一样,坦陈制作不易。并说除了有必要作文献上的考证以外,还必须对缁冠、幅巾、大带、绦、屦甚至絇、繶、纯、綦等等装饰全部复原。45
处斋又就野服问道:
问:野服法,朱文公初制之,然世无服之者。迄罗大经时,其服已绝,才在赵季仁处见之。先生在南京见其服否?但历代有异乎?
答:晦翁先生言“得见祖宗旧制”,则非初制矣。但明朝冠裳之制,大备于古,自有法服,故不用先代之物,而其制遂不可见耳。(《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朱舜水集》上册《问答四》第55条)
关于朱熹所作的野服,上面已经提到,处斋是以此为前提而进行的提问,朱舜水则说,明代另有所规定的服装,关于野服,未能亲眼见过。
如此看来,朱舜水对于制作深衣及野服是有点消极的,然而到了江户以后,这次受到了光圀的直接催促。正如“今水户上公欲做深衣”46所说,结果,在宽文六年(1666),朱舜水决定让居住在长崎的福建人陈二娘这位女性来制作。在寄给长崎町年寄的高木作右卫门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仆抵东武(按,即江户)以来,所见诸公必以深衣相访。朔日,上公特问深衣可有唐人能作否。仆云:“现有闽人陈二娘云能制此衣,言之颇似明晓,且云能制冠履,然行役不能细问,未知其所制果能合式否?”。今,上公欲令此人制深衣一套前来审看之。仆奉托台台,惟冀台台面谕何仁右卫门(按,即上述长崎唐通事〔译者按,“唐通事”即汉语翻译官〕何毓楚)唤取此人到府(按,即町年寄的官署),做一套寄来为感。其细数另具于后,诸事俱毫梶川弥三郎书中,不备不宣。
一 深衣一领(用上好袒兰木绵做,缘用上好黑花布单)
一 缁布冠一顶(笄一枚)
一 幅巾一顶
一 大带一条(用白绢为之,辟缘也镶也用绢)
一 黑履一双
一 系带绦一条(或长崎为之,或东武为之亦可)
以上六件令二娘制(《朱舜水寄高木作右卫门》47)
这是说,朱舜水根据光圀(上公)的意向,通过长崎的友人,让人制作深衣。不用说,这里所列举的六件与《家礼》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指示必须依照《家礼》做一套深衣,以准备一套朱子学风格的儒服。
此外,朱舜水到了江户以后不久,便撰述了一篇《深衣议》的文章。48文章很长,其要点是:一、深衣有大带、绦、缁布冠、幅巾、履、履的装饰以及有关尺寸颜色的严密规定,因此若要全部复原成一套,是相当烦琐的;二、自己并没有穿过深衣;三、虽然制作不得不依赖于专门的制工,但他们没有知识而难以达到精纯,等等。这与上述对小宅处斋的回答几乎完全一样。
然而,尽管朱舜水做了不少的努力,最终似乎也没有能够完成深衣。取而代之制成的却是野服和道服。
关于野服和道服的制作,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载:
甲寅,二年。先是上公使先生制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之类也。49
亦即延宝二年(1674),到江户九年后,朱舜水让人制作完成了野服、道服及其他服饰,这里不可忽视的是,没有列举出深衣。关于这一点,还值得注意的是,元禄七年(1694),光圀圀向前关白(译者按,“关白”为日本古代替天皇行使职权的官职名)的鹰司房辅赠送道服之际所说的一番话(译者按,原文为古代日语):
只今世间通用之道服,不知古来谁人所制。大致所见,其全据直裰,取用于裙、褊、袗。而直裰仅为僧服,即在官之士或隐居隐逸之身,不出家而着用,虽少有疑议,亦自然可有之欤。要之,依古服为宜。若制之,则深衣为吉凶贵贱通用之正服,然全依深衣制之,则相见于异形,可略改深衣而新制矣。50
也就是说,光圀虽承认深衣乃是“吉凶贵贱通用之正服”,但是看上去却像是“异形”,他顾虑到这一点,所以让人制道服而代之。
(三)野服和道服的制作
然而,在野服及道服的制作过程中,有水户儒者人见懋斋(野传)和人见竹洞(野节)参与其间。其实,懋斋曾经尝试过野服的制作,在朱舜水的遗著《朱氏谈绮》51卷上所收《野服正制》的开头,有如下记载:
野服正制题辞
子朱子晚年着野服见客,尝称吕原明之言,从赵季仁之制,事载于《文公年谱》、罗氏《玉露》。然《年谱》略而未尽,《玉露》虽寝备,而其言简矣。余患其制难详,因是揭《玉露》本文附注于其下,未详者并按深衣道服之制,搜辑当时巨儒之定论,亦窃附管见,以为成式,绘图于后,便观览也。凡几易不措,方得脱稿,于是就正于弘文学士林先生损益疏冗,庶俾考古者有所折衷云。宽文甲辰三月既望,懋斋野传书。
题后数年,会明征士舜水先生来本朝,游事我君。余陶炙久矣,恳求改削之。先生指点无隐,完补罅漏。于是始惬素愿,深以为幸。丁未之夏,野传书于武州不忍池上寓舍。
据此,懋斋曾在宽文四年(1664)这一年,便已就《朱子年谱》及《鹤林玉露》对野服进行了考证,在对《鹤林玉露》的记述加注作图的同时,请求林鹅峰(弘文学士林先生)加以损益。此后,朱舜水来到江户,于是请其订正,至宽文七年(1667)脱稿。围绕野服,与朱舜水的往来问答,现存有朱舜水寄给懋斋的书信,由这些书信来看,朱舜水不仅对其记述内容,而且就野服的实际制作也进行了指导,并校订了《野服图说》。52
接着,朱舜水与人见竹洞就道服及其他事项进行了讨论。例如朱舜水在信中写道:
披风、道服奉览。道服镶边,彼时无石青细,故窄狭不堪。今欲为之,须大尺阔三寸五分净,惟后据不妨稍狭。(《与野节(野竹洞)书三十五首》第3)53
由此看来,朱舜水将“披风”和“道服”的实物送给了竹洞。披风即指覆盖双肩的大衣。54对此,竹洞的回函大致是以下这封信:
前日所许借之道服,制工晚成,还璧延及今日,多罪多罪。晦翁先生尝制野服着之。后罗鹤林所谓其制似道服,仆欲见道服久矣。今遇翁之来于江城,并得野服之制。国俗服制混淆,无儒服之制。以此道服为国儒之所服,则仆所愿也。其礼改之则道即在兹乎。奈何,伏请鉴察。(《人见竹洞寄朱舜水书》)55
这里竹洞所说“以此道服为国儒之所服,则仆所愿也”,是值得关注的说法,与上述安东省庵的场合相同,充分显示其对中国的仪礼及服饰的钦佩之情。56
经由上述考证而制成的野服及道服的制法被收录在《朱氏谈绮》的《野服正制》中。关于《野服正制》的内容,其目录如下所示,其中未见载深衣:
野服图说
《鹤林玉露》野服说·注解
裁衣法
裁裳法
野服前图
野服后图
裳制
大带制
道服着用之图
道服图说
道服前图
道服后图
外襟式
内襟式
道服制
包玉巾 纱帽唐巾
披风图
披风前图
披风后图
尺式
其中,关于野服和道服的图,见<图14>和<图15>。57
由上可见,对儒教文化怀有憧憬之情的德川光圀及水户儒者曾向朱舜水请求制作深衣,但并未实现,实际上所制作的仅仅是,在儒服中也相当简便的野服和道服。
(一)安东省庵
安东省庵(1622—1701)为柳川藩的儒者,松永尺五的门人,因师事朱舜水并援助其在长崎的生活而闻名。
省庵向朱舜水请教了各种问题,服装是其所关心的事情之一。例如,他们有如下的问答:
问:老师所服,是大明礼服否?
答:巾、道袍,大明谓之亵衣,不敢施于公廷之上。下者非上命不敢服此见上人,上人亦不敢衣此见秀才,惟燕居为可耳。今来日本,乃以此为礼衣,实非也。(《答安东守约问八条》,《朱舜水集》上册《问答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374)
据此,朱舜水没有身着深衣、幅巾,所穿的是道袍,他称之为“亵衣”。道袍是平时的服装,这一点已如上述。另外,他虽然戴有头巾,但不是幅巾,而是包玉巾。由其他资料可以确认,朱舜水平时身着道袍(道服)和包玉巾,43其姿态由目前存于水户德川家的朱舜水坐像可以窥见(<图13>)。
省庵由对服饰的关心,进而向朱舜水请求制作深衣:
日本儒者能整顿得冠婚葬祭四大节,亦是一事。
问:将以深衣为日本之礼服,如何?
答:颇好,但图中有差处,不佞不解,亦无余银,令裁工制来一看。(《朱舜水寄安东省庵笔语》44)
这是说,省庵为了整理冠婚葬祭的仪礼,而问“以深衣为日本之礼服,如何?”,这是很大胆的说法。对此,朱舜水回答道,深衣的制作方法不太清楚,而且深衣图前后有矛盾,因此先让裁工试做一下。
但是,制作深衣并非易事。省庵向朱舜水这样说道:
凶服之制,素所愿也。制之则深衣幅巾,非力所及,不若凶服唯衰而已。制深衣幅巾也,敬计合吉凶服,出银二十两余,则方决为之。去年借银多矣,无可通移者。(安东守约《上朱先生二十二首》第16,《朱舜水集》上册,页754)
在这里,省庵改变了方针,由于凶服(丧服)比深衣、幅巾是更为简易的服装,所以想首先制作“衰衣”(斩衰、齐衰)。而且,如果这些吉服、凶服都要做成,制作费用需要共计银二十余两的巨款,这毕竟无法筹备。另一方面,朱舜水在给省庵的信中则说:
制深衣裁工,为虏官所获,囚禁狱中未来,来则急急为之,无问其费矣。潦草则所费不甚相远,而不可以为式,亦不可也。历访他工无知者,今好此者多,但未有能之者耳。(《与安东守约书二十五首》第18,《朱舜水集》上册,页166)也就是说,可依托的裁工不知何故被逮捕了,导致深衣制作受挫。虽然让其他裁工做了尝试,但是却没有能够正经地按照礼式正确制作深衣的有技术的人。朱舜水进而说道:
明朝衰衣之制……今所做者无此,失其制矣。……惟深衣幅巾,能为之者,百中之一二耳。必竢前工到,方可为之,须少宽半年。梁冠不佞亦能为,当备料制奉。(《答安东守约书三十首》第13,《朱舜水集》上册,页182)在这里,朱舜水说,制作儒教所说的衰衣也并不容易,至于深衣、幅巾,由于没有适当的裁工,希望再等半年。所谓“俟前工到”,大致是指等到上述被逮捕的裁工回来以后的意思。
由此可见,深衣制作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困难。若是粗略地制作,那么另当别论,如果要按照礼式来制作,那么有以下各种因素对制作造成了妨碍:第一、朱舜水未见过深衣,第二、必须按照《家礼》及其他各种文献来正确地再现,第三、需要一定的费用,第四、有技术的裁工几乎没有,第五、好不容易找到的裁工却发生了被逮捕的意外事件,等等。最终的结果似乎是朱舜水未能为省庵制成深衣。
(二)德川光圀
宽文五年(1665)六月,朱舜水为了服务于德川光圀而从长崎来到江户。这一次,他为了光圀而开始着手深衣的制作。
如上所述,在前一年的宽文四年(1664),德川光圀圀的使者小宅处斋曾为了招聘朱舜水而访问长崎,当时两人有过一场笔谈。并不太受人注意的是,两人最初的问答正是围绕深衣的问题:
问:本邦近代儒风日盛,师及门生往往服深衣、野服等,堂堂有洙泗之风。然所制者,皆以《礼记》及《朱子家礼》、罗氏《鹤林玉露》等考之。异域殊俗,虽以义兴之,而广狭长短不便人体。想尺度之品、制法之义,别有所传乎?赐教示。
答:……仆匏系长崎,如坐井观天……至若深衣之制,亦只学圣之粗迹耳。《玉藻》文深义远,诚为难解。《家礼》徒成聚讼,未有定规。服深衣,必冠缁布,上冒幅巾,腰束大带,系带有绦,垂与裳齐,屦顺裳色,絇繶纯纂(綦)。贵国衣服有制,恐未敢轻易改易也。(《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朱舜水集》上册《问答四》第1条)
在这里,小宅处斋就深衣及野服的制作进行了询问,朱舜水的回答与其对安东省庵的回答一样,坦陈制作不易。并说除了有必要作文献上的考证以外,还必须对缁冠、幅巾、大带、绦、屦甚至絇、繶、纯、綦等等装饰全部复原。45
处斋又就野服问道:
问:野服法,朱文公初制之,然世无服之者。迄罗大经时,其服已绝,才在赵季仁处见之。先生在南京见其服否?但历代有异乎?
答:晦翁先生言“得见祖宗旧制”,则非初制矣。但明朝冠裳之制,大备于古,自有法服,故不用先代之物,而其制遂不可见耳。(《答小宅生顺问六十一条》,《朱舜水集》上册《问答四》第55条)
关于朱熹所作的野服,上面已经提到,处斋是以此为前提而进行的提问,朱舜水则说,明代另有所规定的服装,关于野服,未能亲眼见过。
如此看来,朱舜水对于制作深衣及野服是有点消极的,然而到了江户以后,这次受到了光圀的直接催促。正如“今水户上公欲做深衣”46所说,结果,在宽文六年(1666),朱舜水决定让居住在长崎的福建人陈二娘这位女性来制作。在寄给长崎町年寄的高木作右卫门的书信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仆抵东武(按,即江户)以来,所见诸公必以深衣相访。朔日,上公特问深衣可有唐人能作否。仆云:“现有闽人陈二娘云能制此衣,言之颇似明晓,且云能制冠履,然行役不能细问,未知其所制果能合式否?”。今,上公欲令此人制深衣一套前来审看之。仆奉托台台,惟冀台台面谕何仁右卫门(按,即上述长崎唐通事〔译者按,“唐通事”即汉语翻译官〕何毓楚)唤取此人到府(按,即町年寄的官署),做一套寄来为感。其细数另具于后,诸事俱毫梶川弥三郎书中,不备不宣。
一 深衣一领(用上好袒兰木绵做,缘用上好黑花布单)
一 缁布冠一顶(笄一枚)
一 幅巾一顶
一 大带一条(用白绢为之,辟缘也镶也用绢)
一 黑履一双
一 系带绦一条(或长崎为之,或东武为之亦可)
以上六件令二娘制(《朱舜水寄高木作右卫门》47)
这是说,朱舜水根据光圀(上公)的意向,通过长崎的友人,让人制作深衣。不用说,这里所列举的六件与《家礼》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指示必须依照《家礼》做一套深衣,以准备一套朱子学风格的儒服。
此外,朱舜水到了江户以后不久,便撰述了一篇《深衣议》的文章。48文章很长,其要点是:一、深衣有大带、绦、缁布冠、幅巾、履、履的装饰以及有关尺寸颜色的严密规定,因此若要全部复原成一套,是相当烦琐的;二、自己并没有穿过深衣;三、虽然制作不得不依赖于专门的制工,但他们没有知识而难以达到精纯,等等。这与上述对小宅处斋的回答几乎完全一样。
然而,尽管朱舜水做了不少的努力,最终似乎也没有能够完成深衣。取而代之制成的却是野服和道服。
关于野服和道服的制作,今井弘济、安积觉《舜水先生行实》载:
甲寅,二年。先是上公使先生制明室衣冠,至是而成。朝服、角带、野服、道服、明道巾、纱帽、幞头之类也。49
亦即延宝二年(1674),到江户九年后,朱舜水让人制作完成了野服、道服及其他服饰,这里不可忽视的是,没有列举出深衣。关于这一点,还值得注意的是,元禄七年(1694),光圀圀向前关白(译者按,“关白”为日本古代替天皇行使职权的官职名)的鹰司房辅赠送道服之际所说的一番话(译者按,原文为古代日语):
只今世间通用之道服,不知古来谁人所制。大致所见,其全据直裰,取用于裙、褊、袗。而直裰仅为僧服,即在官之士或隐居隐逸之身,不出家而着用,虽少有疑议,亦自然可有之欤。要之,依古服为宜。若制之,则深衣为吉凶贵贱通用之正服,然全依深衣制之,则相见于异形,可略改深衣而新制矣。50
也就是说,光圀虽承认深衣乃是“吉凶贵贱通用之正服”,但是看上去却像是“异形”,他顾虑到这一点,所以让人制道服而代之。
(三)野服和道服的制作
然而,在野服及道服的制作过程中,有水户儒者人见懋斋(野传)和人见竹洞(野节)参与其间。其实,懋斋曾经尝试过野服的制作,在朱舜水的遗著《朱氏谈绮》51卷上所收《野服正制》的开头,有如下记载:
野服正制题辞
子朱子晚年着野服见客,尝称吕原明之言,从赵季仁之制,事载于《文公年谱》、罗氏《玉露》。然《年谱》略而未尽,《玉露》虽寝备,而其言简矣。余患其制难详,因是揭《玉露》本文附注于其下,未详者并按深衣道服之制,搜辑当时巨儒之定论,亦窃附管见,以为成式,绘图于后,便观览也。凡几易不措,方得脱稿,于是就正于弘文学士林先生损益疏冗,庶俾考古者有所折衷云。宽文甲辰三月既望,懋斋野传书。
题后数年,会明征士舜水先生来本朝,游事我君。余陶炙久矣,恳求改削之。先生指点无隐,完补罅漏。于是始惬素愿,深以为幸。丁未之夏,野传书于武州不忍池上寓舍。
据此,懋斋曾在宽文四年(1664)这一年,便已就《朱子年谱》及《鹤林玉露》对野服进行了考证,在对《鹤林玉露》的记述加注作图的同时,请求林鹅峰(弘文学士林先生)加以损益。此后,朱舜水来到江户,于是请其订正,至宽文七年(1667)脱稿。围绕野服,与朱舜水的往来问答,现存有朱舜水寄给懋斋的书信,由这些书信来看,朱舜水不仅对其记述内容,而且就野服的实际制作也进行了指导,并校订了《野服图说》。52
接着,朱舜水与人见竹洞就道服及其他事项进行了讨论。例如朱舜水在信中写道:
披风、道服奉览。道服镶边,彼时无石青细,故窄狭不堪。今欲为之,须大尺阔三寸五分净,惟后据不妨稍狭。(《与野节(野竹洞)书三十五首》第3)53
由此看来,朱舜水将“披风”和“道服”的实物送给了竹洞。披风即指覆盖双肩的大衣。54对此,竹洞的回函大致是以下这封信:
前日所许借之道服,制工晚成,还璧延及今日,多罪多罪。晦翁先生尝制野服着之。后罗鹤林所谓其制似道服,仆欲见道服久矣。今遇翁之来于江城,并得野服之制。国俗服制混淆,无儒服之制。以此道服为国儒之所服,则仆所愿也。其礼改之则道即在兹乎。奈何,伏请鉴察。(《人见竹洞寄朱舜水书》)55
这里竹洞所说“以此道服为国儒之所服,则仆所愿也”,是值得关注的说法,与上述安东省庵的场合相同,充分显示其对中国的仪礼及服饰的钦佩之情。56
经由上述考证而制成的野服及道服的制法被收录在《朱氏谈绮》的《野服正制》中。关于《野服正制》的内容,其目录如下所示,其中未见载深衣:
野服图说
《鹤林玉露》野服说·注解
裁衣法
裁裳法
野服前图
野服后图
裳制
大带制
道服着用之图
道服图说
道服前图
道服后图
外襟式
内襟式
道服制
包玉巾 纱帽唐巾
披风图
披风前图
披风后图
尺式
其中,关于野服和道服的图,见<图14>和<图15>。57
由上可见,对儒教文化怀有憧憬之情的德川光圀及水户儒者曾向朱舜水请求制作深衣,但并未实现,实际上所制作的仅仅是,在儒服中也相当简便的野服和道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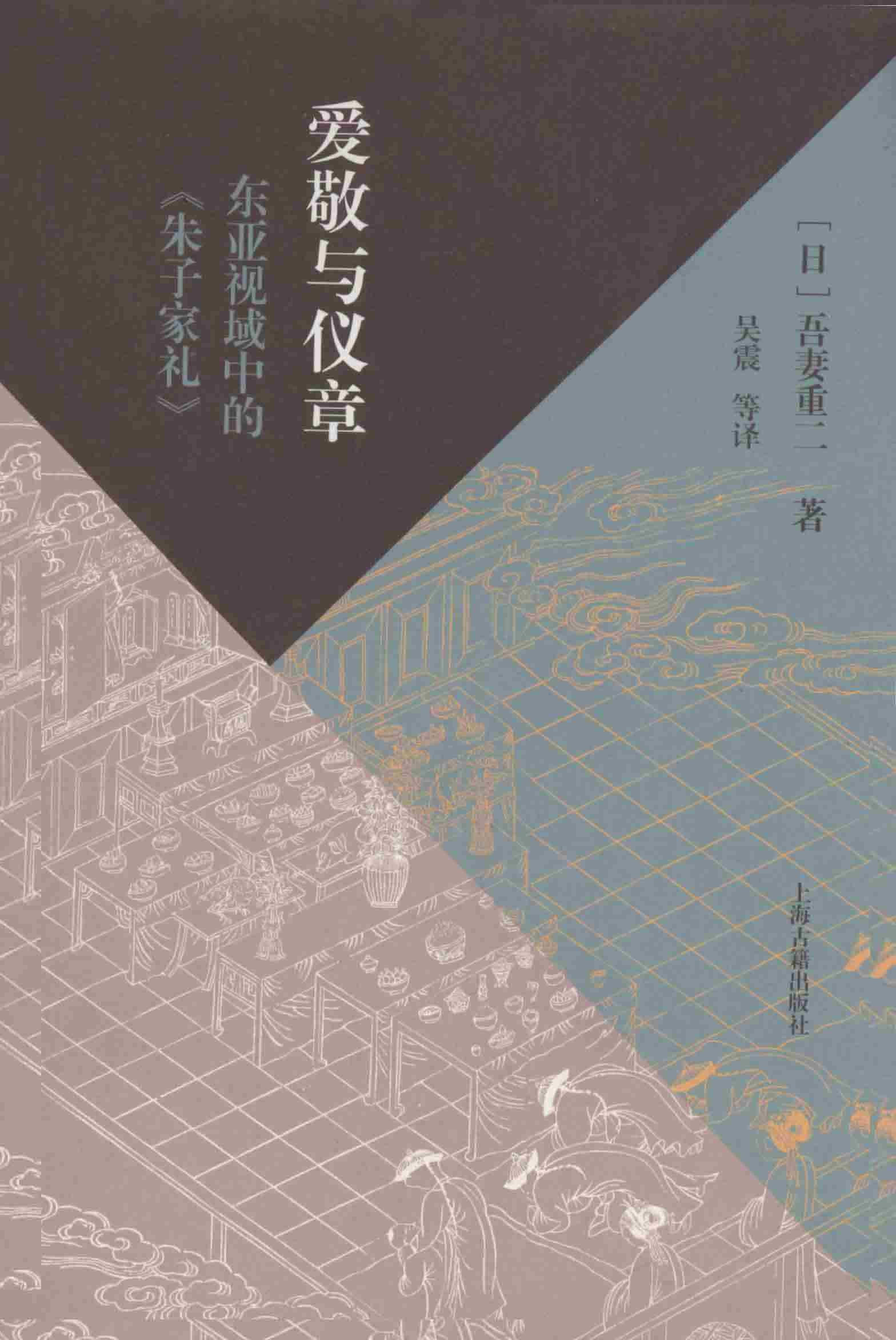
《爱敬与仪章:东亚视域中的《朱子家礼》》
出版者: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为朱子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影响后世达七百年,深刻塑造了中华礼仪文明。本书为日本朱子学、礼学专家吾妻重二教授《家礼》学研究成果的汇集。全书分三编:文献足征、礼文备具、礼书承传,共十三章,广涉《家礼》版本、木主、深衣、日本《家礼》接受史等议题,融文献学、历史学、哲学于一炉,全面深入地揭示《家礼》在东亚的“漫游史”。
阅读
相关人物
朱舜水
相关人物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