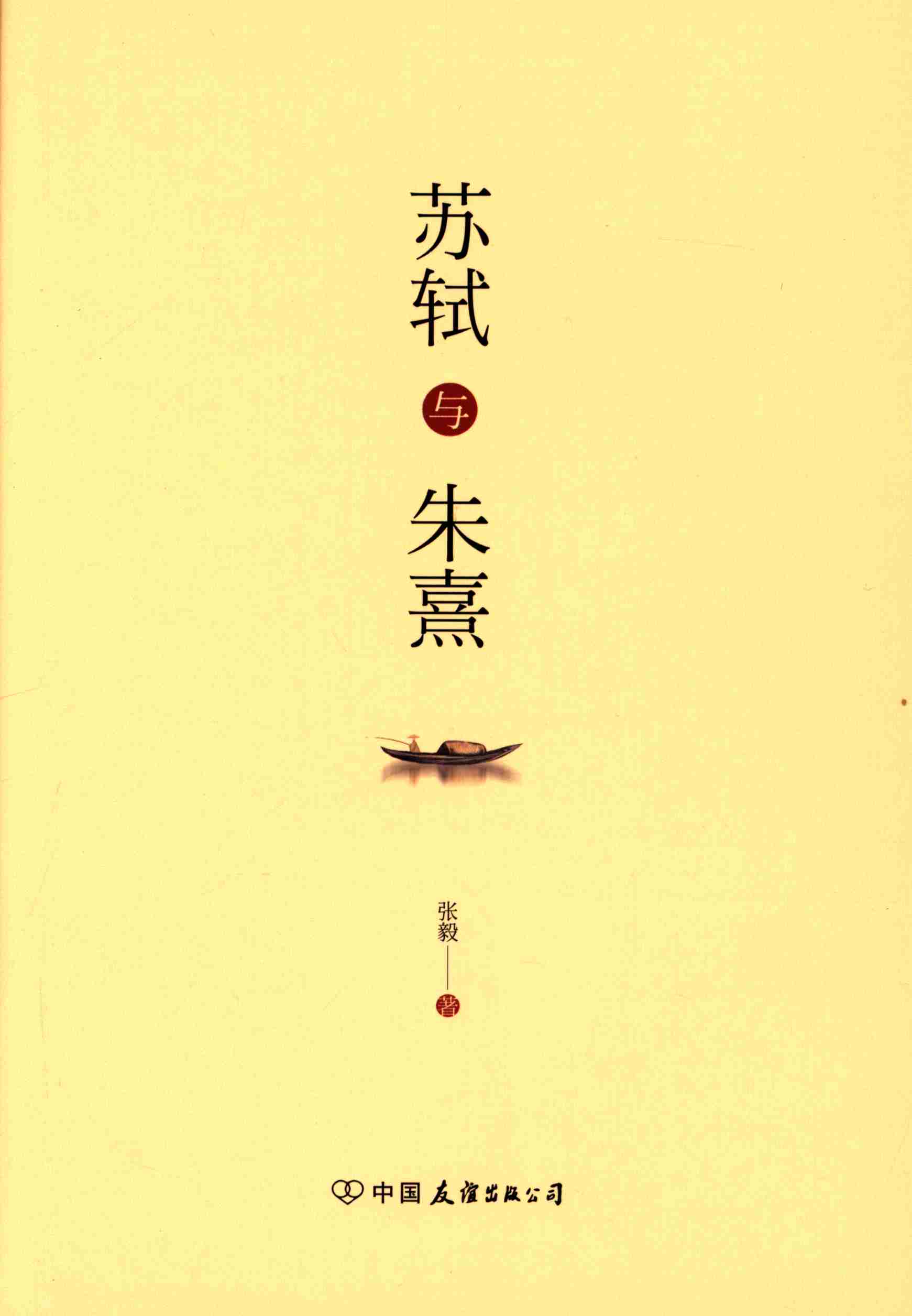是非谁人评说
| 内容出处: | 《苏轼与朱熹》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4261 |
| 颗粒名称: | 是非谁人评说 |
| 分类号: | K825.6 |
| 页数: | 10 |
| 页码: | 241-25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中国古代的灵魂不死之说可能涉及宗教迷信,但在讨论人类精神活动和文化发展时,确实存在某些历史文化人物的思想和学说,宛如不朽的灵魂一样流传下来,影响着世代的人们。诗人和作家的作品通过广泛传播在人们心中永生。苏轼的诗歌代表了东坡体和山谷体诗,被视为宋诗的代表之一。苏轼的诗词被赞誉为开辟了古文运动的新天地,他的散文被认为是“唐宋八大家”中最高的作品之一。他的随笔小品因其独特的神韵受到人们的喜爱,并为后世作家所效仿。苏轼的词被视为宋代一代文学的代表,他以诗入词,革新了词体和词风。此外,苏轼的书法和绘画也是他的才华所在,他将诗、书、画三者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文人画的倡导者。总而言之,苏轼作为一个全才,在诗歌、散文、词、书法和绘画等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
| 关键词: | 诗人 优秀 作品 |
内容
中国古代有灵魂不死之说,如果是指个人的魂魄可以离开肉体而存在,那是一种宗教迷信。倘若就人类的精神活动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确有某些历史文化人物的思想和学说像不朽的灵魂薪火相传,映照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田,供人们借鉴评说。
诗人和作家是以优秀作品的广为传诵而活在人们心里,因其作品的不朽而得到永生。所以谈到苏轼时,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东坡体诗与黄庭坚的山谷体诗,被人们看作宋诗的代表,并称为“苏、黄”,是中国古典诗歌自唐诗的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高峰。从宋代就开始了的唐、宋诗之争中,对苏、黄诗的评价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宗宋诗者认为诗道自杜甫之后,苏、黄诗复出而振之,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尽兼众体而自成一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出奇无穷,清新神逸。而主唐诗者则指责苏、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文人之诗而非诗人之诗,诗道至此,可谓一厄。无论褒与贬,都承认苏、黄诗有自己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魅力,能继唐诗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说:“只知诗到苏、黄尽。”在中国现代新诗没有产生以前,学诗者和作诗者,不入于唐则流于宋,始终未能跳出李、杜、苏、黄的藩篱。
就文而言,苏轼的散文被公认为“唐宋八大家”中文学性和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他出入三教,才高识广,以奔放的才情和平易畅达的文风开辟了散文创作的新天地,无论言理、记事、表情写意,均能挥洒自如,各臻其极,代表了宋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长期以来,-直是人们学习作文的榜样。特别是他独具神韵的随笔小品,为明清以至现代主张抒写性灵的作家所效法,苏东坡的文名家喻户晓。人们一般认为苏轼的文比诗好,而词又比文好。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词在当时作为一种配乐的音乐文学,形成了富有音乐感的长短参差的句法,本身就有一种曲折委婉的节律,能将诗人内心的生命体验和情绪颤动真切地表现出来。苏轼在用词来反映自己特有的生命情调和精神风貌时,注入了一种清旷浩逸之气,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词被人们认为是宋代的一代之文学。苏轼的以诗入词,全面地革新了词体和词风,指出向上一路,如刘熙载《艺概》所言:“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此外,苏轼的书法也卓然成家,借笔墨写胸中逸气,线条流动代表生命运动的时间节律,表达心情、人格和意境。他将诗、书、画三者融为一体,是中国文人画的倡导者。尽管苏轼绘画的真迹已失传,但他说的“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却是文人画的精髓所在,表明画也有传情写意的功能,可以寓空间画面于流动的诗意挥写之中,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及墨色的浓淡,超以象外而融入诗心,直接表达文人高雅脱俗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形成了中国文人画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的艺术特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苏轼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杰出的文艺全才。但苏轼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
还在宋代,秦观在《答傅彬老简》里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秦观是苏轼的得意门生和知己,他所说的“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指苏轼的生命精神和处世态度而言,如坦荡真率的个性,潇洒自如的气度,随缘放旷的文心,超世而入世、入世而超世的襟怀等。这些才是苏轼文化人格的根本所在,他的诗、词、文和书画等,不过是这一根本的外在表现形式。
后世喜爱苏轼作品的人,往往能“披文而入情”,用心灵去体会苏轼性命自得的灵魂奥秘及人生意义。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在他所作的《次苏子瞻先后事》里,通过对正史未载的苏轼的生活史和佚事趣闻的描述,展示诗人颦笑于无心之际的神情和潇洒之趣。现代因提倡小品文和“幽默”而闻名于世的林语堂,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任。他把苏轼作为中国文化或东方文明的代表,称苏轼的著作是“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在他精心撰写的《苏东坡传》里,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心灵像天真的小孩,可却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其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他活得很快慰,欣赏自己生命的每一时刻,因为生命毕竟是永恒的美好的。所以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也有的人仅从政治态度和哲学思想的角度来评论苏轼,甚至根据某种现实政治的需要把他划归儒家保守阵营,说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想在评法批儒的运动中把他批倒批臭。真是蚍蜉撼树,甚可笑。
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则从另一个角度评价苏轼的意义,他在《美的历程》里认为:苏轼是地主阶级士大夫进取与退隐双重矛盾心理的人格化身,他在诗文中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不仅是对政治社会的退隐,更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企求解脱和舍弃,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所以对当时封建社会秩序是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作用的。这些评说尽管角度不同,但都深入到了苏轼生命精神的某一方面,是很精辟的。
从本质上说,苏轼是诗人,是文学家,不能用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标准去衡量他。诗人重感性经验,以审美活动为生命的最高形式,故苏轼把超出经验世界之外的人生价值的思考,放在有限的生存世界加以体验,他的生命就是诗。人生的痛苦和生命的短暂,使他产生如梦幻般的虚无之感,懂得生活中存在的荒谬和现实对人性的压抑,要在审美体验中重新建构自得适意的人生经验,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生活,将平凡的生活作诗意的扩展,以驱除内心的悲凉和空漠,以寻求解脱。他在把生活艺术化的想象中,肯定生命的感觉存在、本能冲动和丰富情感,以超然的态度享受自我生命的全部激情,自己吟诗作文安慰自己,使生命体验成为文学语言,成为精美的艺术品。
这种生命体验方式和表现方式本身就是对生活的肯定,尽管不同时期的人所感受和接触的生活不同,但欢乐也好,忧伤也好,都是生命的馈赠。生活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生命体验的方式却是一样的,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生与死、痛苦与逍遥、失意与自得、充实与虚无等问题的纠缠时,都会与苏轼有相似的生命体验和感受,都能在读他的作品时产生共鸣。所以我们才会把一个民族的诗人当作这个民族心灵和精神的体现者来看待,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蕴含着一个民族对生活最深的体会和文化心理。苏轼的意义,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把握。
谈到朱熹,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苏轼的文学作品,即使初通文墨之人,也能凭自己的生命体验,立刻感受到里面的天生好语言,故能广泛地传播于人口,历久弥新。而朱熹的思想,他的理学著作,若不是专门的研究者,如今恐怕很少有人能耐心地加以理会了。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历代统治者的提倡,朱熹理学的影响早已不限于读书人,他所讲的做人标准和人生价值观念,已成为某种民族集体潜意识,积沉在中国人心里,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之间,都可以察觉到它的存在。
最早对朱熹及其思想加以褒扬的是他的学生,黄榦在《朱子行状》里称朱熹“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他认为朱熹是儒家道统的传人,为世人树立起了做人的标准,是人们的精神导师或教主,与孔子一样,可称为万世师表。但真正把朱熹抬高到与孔圣人并列的地位,用他的理学思想来对全国人民施行教化的,还是宋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君王,他们已经从本质上认清了程朱理学对于中国社会的真正意义。因为要维护封建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必须要有一种思想上的大一统,而朱熹的理学思想,以其精密、庞大和系统,是堪此重任的。
理学是讲道理之学,道理不同于自然科学所讲的真理,不必经受客观事实的充分验证,只要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行。做人的道理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共同承认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之上的伦理,这正是新儒家学说所要强调的。以《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为中心展开的程朱理学,若加以大力推广,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和社会意识,就不仅可以为王权专制提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保证,也可以为一切士人和官吏指明成圣成贤的修身方法,还可以将儒家传统文化的纲常伦理准则和德行优先于知识的价值观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所有中国人的思想里。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朱熹理学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期,一些守旧的读书人还在那里赞叹朱熹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时,具有反封建意识的思想家戴震,在其《孟子字义疏证》中,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他又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道出了程、朱把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伦理说成“天理”后,人们“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的惨祸烈毒。理学给年轻的幼者和地位低下的卑贱者,造成了极为沉重的精神负担和人性压抑的痛苦。
理学对维护封建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极为有利的。它不仅能使卑贱者甘于贫贱,年轻人安分守己,也可以造就出一批注重气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的仁人志士,他们能对国家和君王尽忠尽职,九死一生而不悔。所以“五四”时期的革命青年,在以科学和民主反抗封建专制者及其余孽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程朱理学进行猛烈的批判。反理学,一直是“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思想主题之一,形成了一种革命的传统,反传统的传统。
当然,如果不考虑程朱理学在封建专制社会政治中的实际作用,忘掉历史上曾有过的以理杀人的残忍,仅从理论上来看待朱熹的思想学说的话,未尝没有迷人之处。朱熹所讲的克己复礼功夫,大公无私的“道心”,用理性主宰支配感情,在内心保持对道德律令的敬畏等,确实能使想从事道德履践的人树立伦理主体的庄重严肃,消除唯利是图、人欲横流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道德沦丧。
发端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新儒家,鉴于西方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和血腥污秽,认为西方人只追求物欲而道德式微,战乱屡起,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文化的发展应当是多元的,西方资本主义虽有科学技术发达造成的高度的物质文明,但要讲精神文明,则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中华本土的儒家传统文化自处于优越的地位。他们主张继承传统,对儒家文化作同情的理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感慨科学并非万能,公道仍在人心,希望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去吸收外来文化。其弟子张君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在于它全力注重于人生问题的探讨,而人生观起于自觉,非科学所能为力。
梁漱溟把文化归之于人生和人心,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断言:只有复兴宋明理学倡导的“孔颜乐处”的人生态度,才可以真正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才会有结果。冯友兰称自己的哲学为“新理学”,他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学术之源,接着往下讲,认为可以对朱熹的思想进行纯理论的抽象继承,用来调节新的人际关系,使人具有以“贡献”为目的的道德境界。牟宗三则标榜新儒家“德行优先于知识”的原则,认为“德行”二字是包括品德在内的“生死智慧”,实际上是讲如何处世做人的,可以提高人的教养而具有一种清明的理性。
稍后一些的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多对宋明理学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负面影响有清醒的认识,主张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有的认为儒家维护封建专制的“外王”之道虽不可取,但通过弘扬新儒家的“内圣”之学,是可以开展出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的。还有的则主张应当把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加以区别,认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早在清末民初就已经破产了,但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本身仍有其源头活水,在现代的“国学”研究中仍发挥着作用。反对儒家的意识形态,不等于要把儒学也反对掉,如此才能正确了解“五四”反传统、反儒家的历史意义云云。
以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宋明理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现代新儒家的出现,绝非空穴来风,亦非学者书斋里的玄想,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延续性的表现。传统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很难反掉的,或者说,能完全反掉的传统,并非真正的传统。如今一般人在生活中常说的做人要讲“良心”,否则“天理难容”,说自己“问心无愧”,又说“好人一生平安”等,其实就是理学所倡导的处世做人的传统思想的通俗表达,只不过大家习惯成自然,没有自觉到而已。
如何使传统观念适应经济、政治现代化的需要,一直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想要解决而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像鲁迅等一批革命的文学家,对封建社会的吃人礼教进行批判,对程朱理学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与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眷恋宋明理学所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无疑是一鲜明的对照。如果考虑到现代新儒家多以学者或哲人的面貌出现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中,也存在着过去中国士人里那种文人与儒者的差别。大概这也是一种传统吧!言中国文化,无论古今,只注意哲人的抽象理论,以不变之理应万变,而忽略文学家充满感性生命力的精神创造,无疑是极不全面的。因为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对生命存在的深入体验,才是文化创造和发展的源头活水。
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
俱往矣!
诗人和作家是以优秀作品的广为传诵而活在人们心里,因其作品的不朽而得到永生。所以谈到苏轼时,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作品。他的东坡体诗与黄庭坚的山谷体诗,被人们看作宋诗的代表,并称为“苏、黄”,是中国古典诗歌自唐诗的李白、杜甫之后的又一高峰。从宋代就开始了的唐、宋诗之争中,对苏、黄诗的评价一直是个热门话题。宗宋诗者认为诗道自杜甫之后,苏、黄诗复出而振之,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尽兼众体而自成一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出奇无穷,清新神逸。而主唐诗者则指责苏、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是文人之诗而非诗人之诗,诗道至此,可谓一厄。无论褒与贬,都承认苏、黄诗有自己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魅力,能继唐诗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说:“只知诗到苏、黄尽。”在中国现代新诗没有产生以前,学诗者和作诗者,不入于唐则流于宋,始终未能跳出李、杜、苏、黄的藩篱。
就文而言,苏轼的散文被公认为“唐宋八大家”中文学性和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他出入三教,才高识广,以奔放的才情和平易畅达的文风开辟了散文创作的新天地,无论言理、记事、表情写意,均能挥洒自如,各臻其极,代表了宋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长期以来,-直是人们学习作文的榜样。特别是他独具神韵的随笔小品,为明清以至现代主张抒写性灵的作家所效法,苏东坡的文名家喻户晓。人们一般认为苏轼的文比诗好,而词又比文好。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里说:“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词在当时作为一种配乐的音乐文学,形成了富有音乐感的长短参差的句法,本身就有一种曲折委婉的节律,能将诗人内心的生命体验和情绪颤动真切地表现出来。苏轼在用词来反映自己特有的生命情调和精神风貌时,注入了一种清旷浩逸之气,有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象。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词被人们认为是宋代的一代之文学。苏轼的以诗入词,全面地革新了词体和词风,指出向上一路,如刘熙载《艺概》所言:“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此外,苏轼的书法也卓然成家,借笔墨写胸中逸气,线条流动代表生命运动的时间节律,表达心情、人格和意境。他将诗、书、画三者融为一体,是中国文人画的倡导者。尽管苏轼绘画的真迹已失传,但他说的“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却是文人画的精髓所在,表明画也有传情写意的功能,可以寓空间画面于流动的诗意挥写之中,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及墨色的浓淡,超以象外而融入诗心,直接表达文人高雅脱俗的生命体验和感受,形成了中国文人画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的艺术特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苏轼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杰出的文艺全才。但苏轼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
还在宋代,秦观在《答傅彬老简》里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秦观是苏轼的得意门生和知己,他所说的“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指苏轼的生命精神和处世态度而言,如坦荡真率的个性,潇洒自如的气度,随缘放旷的文心,超世而入世、入世而超世的襟怀等。这些才是苏轼文化人格的根本所在,他的诗、词、文和书画等,不过是这一根本的外在表现形式。
后世喜爱苏轼作品的人,往往能“披文而入情”,用心灵去体会苏轼性命自得的灵魂奥秘及人生意义。明代公安三袁之一的袁中道,在他所作的《次苏子瞻先后事》里,通过对正史未载的苏轼的生活史和佚事趣闻的描述,展示诗人颦笑于无心之际的神情和潇洒之趣。现代因提倡小品文和“幽默”而闻名于世的林语堂,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自任。他把苏轼作为中国文化或东方文明的代表,称苏轼的著作是“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在他精心撰写的《苏东坡传》里,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心灵像天真的小孩,可却比中国其他诗人更具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其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他活得很快慰,欣赏自己生命的每一时刻,因为生命毕竟是永恒的美好的。所以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
也有的人仅从政治态度和哲学思想的角度来评论苏轼,甚至根据某种现实政治的需要把他划归儒家保守阵营,说他反对王安石变法,想在评法批儒的运动中把他批倒批臭。真是蚍蜉撼树,甚可笑。
当代美学家李泽厚则从另一个角度评价苏轼的意义,他在《美的历程》里认为:苏轼是地主阶级士大夫进取与退隐双重矛盾心理的人格化身,他在诗文中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不仅是对政治社会的退隐,更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企求解脱和舍弃,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所以对当时封建社会秩序是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作用的。这些评说尽管角度不同,但都深入到了苏轼生命精神的某一方面,是很精辟的。
从本质上说,苏轼是诗人,是文学家,不能用政治家和哲学家的标准去衡量他。诗人重感性经验,以审美活动为生命的最高形式,故苏轼把超出经验世界之外的人生价值的思考,放在有限的生存世界加以体验,他的生命就是诗。人生的痛苦和生命的短暂,使他产生如梦幻般的虚无之感,懂得生活中存在的荒谬和现实对人性的压抑,要在审美体验中重新建构自得适意的人生经验,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生活,将平凡的生活作诗意的扩展,以驱除内心的悲凉和空漠,以寻求解脱。他在把生活艺术化的想象中,肯定生命的感觉存在、本能冲动和丰富情感,以超然的态度享受自我生命的全部激情,自己吟诗作文安慰自己,使生命体验成为文学语言,成为精美的艺术品。
这种生命体验方式和表现方式本身就是对生活的肯定,尽管不同时期的人所感受和接触的生活不同,但欢乐也好,忧伤也好,都是生命的馈赠。生活的具体内容千差万别,生命体验的方式却是一样的,当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生与死、痛苦与逍遥、失意与自得、充实与虚无等问题的纠缠时,都会与苏轼有相似的生命体验和感受,都能在读他的作品时产生共鸣。所以我们才会把一个民族的诗人当作这个民族心灵和精神的体现者来看待,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蕴含着一个民族对生活最深的体会和文化心理。苏轼的意义,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把握。
谈到朱熹,问题就比较复杂了。苏轼的文学作品,即使初通文墨之人,也能凭自己的生命体验,立刻感受到里面的天生好语言,故能广泛地传播于人口,历久弥新。而朱熹的思想,他的理学著作,若不是专门的研究者,如今恐怕很少有人能耐心地加以理会了。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历代统治者的提倡,朱熹理学的影响早已不限于读书人,他所讲的做人标准和人生价值观念,已成为某种民族集体潜意识,积沉在中国人心里,我们在有意或无意之间,都可以察觉到它的存在。
最早对朱熹及其思想加以褒扬的是他的学生,黄榦在《朱子行状》里称朱熹“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他认为朱熹是儒家道统的传人,为世人树立起了做人的标准,是人们的精神导师或教主,与孔子一样,可称为万世师表。但真正把朱熹抬高到与孔圣人并列的地位,用他的理学思想来对全国人民施行教化的,还是宋代以后的历代统治者。尤其是明清两代的君王,他们已经从本质上认清了程朱理学对于中国社会的真正意义。因为要维护封建大一统的国家政治,必须要有一种思想上的大一统,而朱熹的理学思想,以其精密、庞大和系统,是堪此重任的。
理学是讲道理之学,道理不同于自然科学所讲的真理,不必经受客观事实的充分验证,只要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就行。做人的道理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共同承认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之上的伦理,这正是新儒家学说所要强调的。以《大学》所讲的“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为中心展开的程朱理学,若加以大力推广,成为一种习惯势力和社会意识,就不仅可以为王权专制提供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保证,也可以为一切士人和官吏指明成圣成贤的修身方法,还可以将儒家传统文化的纲常伦理准则和德行优先于知识的价值观贯彻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所有中国人的思想里。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朱熹理学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思想。正因为如此,当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期,一些守旧的读书人还在那里赞叹朱熹学说“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时,具有反封建意识的思想家戴震,在其《孟子字义疏证》中,对程朱理学进行了抨击。他认为:“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他又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道出了程、朱把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伦理说成“天理”后,人们“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的惨祸烈毒。理学给年轻的幼者和地位低下的卑贱者,造成了极为沉重的精神负担和人性压抑的痛苦。
理学对维护封建专制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极为有利的。它不仅能使卑贱者甘于贫贱,年轻人安分守己,也可以造就出一批注重气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的仁人志士,他们能对国家和君王尽忠尽职,九死一生而不悔。所以“五四”时期的革命青年,在以科学和民主反抗封建专制者及其余孽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程朱理学进行猛烈的批判。反理学,一直是“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的基本思想主题之一,形成了一种革命的传统,反传统的传统。
当然,如果不考虑程朱理学在封建专制社会政治中的实际作用,忘掉历史上曾有过的以理杀人的残忍,仅从理论上来看待朱熹的思想学说的话,未尝没有迷人之处。朱熹所讲的克己复礼功夫,大公无私的“道心”,用理性主宰支配感情,在内心保持对道德律令的敬畏等,确实能使想从事道德履践的人树立伦理主体的庄重严肃,消除唯利是图、人欲横流给社会带来的动荡和道德沦丧。
发端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现代新儒家,鉴于西方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和血腥污秽,认为西方人只追求物欲而道德式微,战乱屡起,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文化的发展应当是多元的,西方资本主义虽有科学技术发达造成的高度的物质文明,但要讲精神文明,则包括程朱理学在内的中华本土的儒家传统文化自处于优越的地位。他们主张继承传统,对儒家文化作同情的理解。如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感慨科学并非万能,公道仍在人心,希望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去吸收外来文化。其弟子张君劢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在于它全力注重于人生问题的探讨,而人生观起于自觉,非科学所能为力。
梁漱溟把文化归之于人生和人心,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断言:只有复兴宋明理学倡导的“孔颜乐处”的人生态度,才可以真正吸收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才会有结果。冯友兰称自己的哲学为“新理学”,他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学术之源,接着往下讲,认为可以对朱熹的思想进行纯理论的抽象继承,用来调节新的人际关系,使人具有以“贡献”为目的的道德境界。牟宗三则标榜新儒家“德行优先于知识”的原则,认为“德行”二字是包括品德在内的“生死智慧”,实际上是讲如何处世做人的,可以提高人的教养而具有一种清明的理性。
稍后一些的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多对宋明理学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负面影响有清醒的认识,主张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有的认为儒家维护封建专制的“外王”之道虽不可取,但通过弘扬新儒家的“内圣”之学,是可以开展出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的。还有的则主张应当把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加以区别,认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作为一种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早在清末民初就已经破产了,但儒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本身仍有其源头活水,在现代的“国学”研究中仍发挥着作用。反对儒家的意识形态,不等于要把儒学也反对掉,如此才能正确了解“五四”反传统、反儒家的历史意义云云。
以包括朱熹思想在内的宋明理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现代新儒家的出现,绝非空穴来风,亦非学者书斋里的玄想,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延续性的表现。传统是一种习惯势力,是很难反掉的,或者说,能完全反掉的传统,并非真正的传统。如今一般人在生活中常说的做人要讲“良心”,否则“天理难容”,说自己“问心无愧”,又说“好人一生平安”等,其实就是理学所倡导的处世做人的传统思想的通俗表达,只不过大家习惯成自然,没有自觉到而已。
如何使传统观念适应经济、政治现代化的需要,一直是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想要解决而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像鲁迅等一批革命的文学家,对封建社会的吃人礼教进行批判,对程朱理学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老调子已经唱完”。这与梁漱溟等现代新儒家眷恋宋明理学所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无疑是一鲜明的对照。如果考虑到现代新儒家多以学者或哲人的面貌出现的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中,也存在着过去中国士人里那种文人与儒者的差别。大概这也是一种传统吧!言中国文化,无论古今,只注意哲人的抽象理论,以不变之理应万变,而忽略文学家充满感性生命力的精神创造,无疑是极不全面的。因为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对生命存在的深入体验,才是文化创造和发展的源头活水。
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
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