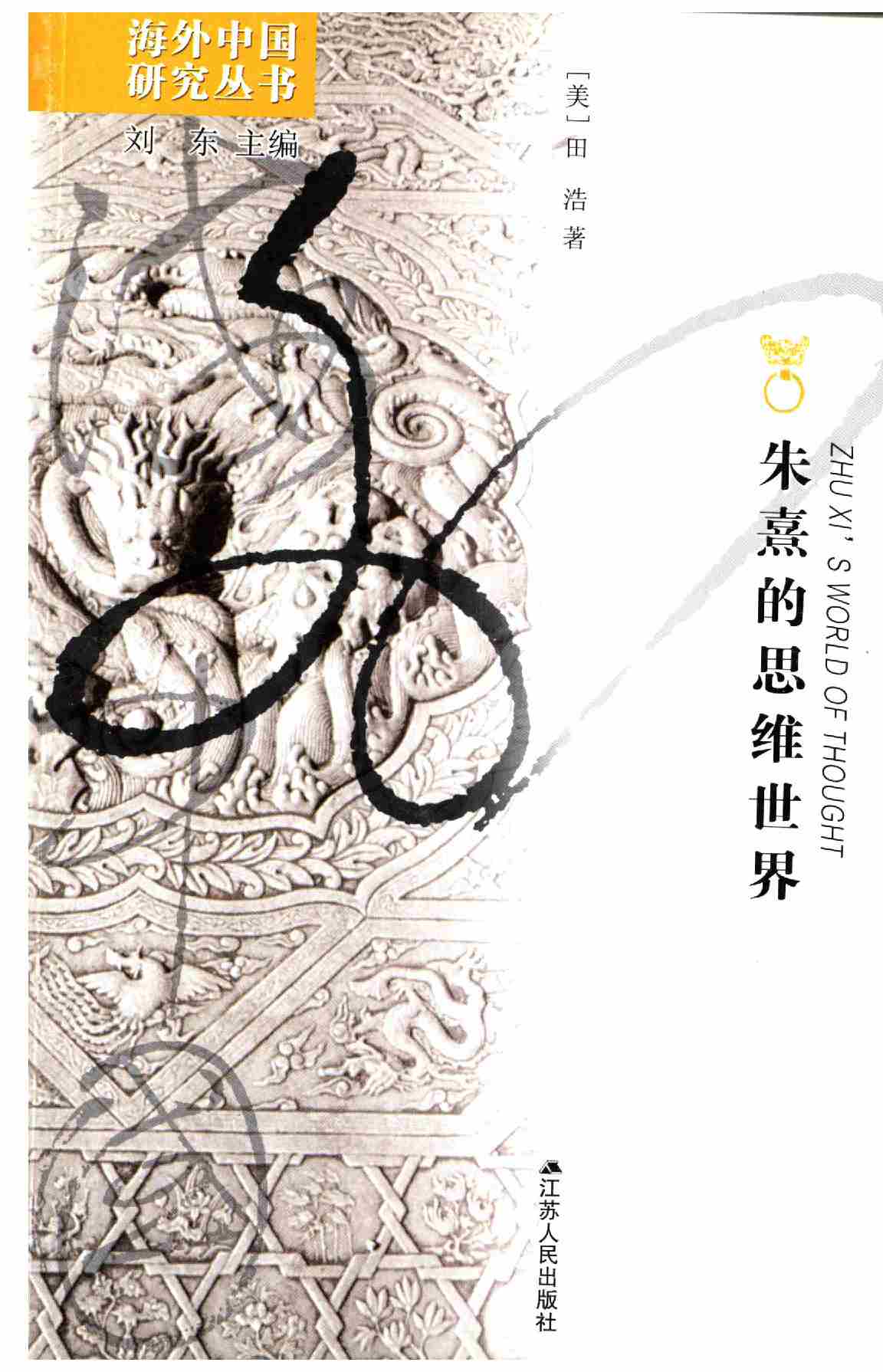第二部 第二时期(1163—1181)
内容
金人在1161年南下入侵,宋朝的政治文化随着双方的紧张情势与军事行动而变化。高宗在1162年夏天宣布退位,孝宗继位(1162—1189年在位)。孝宗依照惯例广征举国学者官员建言,道学人士也响应呼吁提出种种建议,要求改革朝政、对金人抗战。1164年孝宗与金人签订停战和约后,这种兴奋的心情愿望随之消退。新约不像以前的和约那样不平等,道学人士还是为失去收复北方的机会而感到万分失望。然而,这时道学人士与朝廷执政人物的关系,比前一时期改善许多,道学传统与程学的后人都没有遭受猛烈抨击,而且他们更愿意出仕。
比较第一与第二时期进士的来源,或许能显示政府与道学间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详细具体的量化当然不容易,我想选择在12世纪90年代被“庆元党案”列为“伪学”(道学)的人士,以及攻击道学的人士加以说明。这份所谓的“伪学”名单虽然是由攻击迫害道学的人士所罗列的,它还颇有几分道理,因为名单上的人在学术和政治方面的联系,远超过他们在官场上互相举荐与援引的关系。攻击道学的人士的联系没有如此密切,但是都曾上书批评道学,或做过攻击道学的事情。这批人只是因为反对道学而被列入名单,所以很难判断他们究竟属于哪个士大夫团体。目前所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详细比较名单上的道学人士与反对道学人士,以及他们所属的团体人数;就名单的性质而言,被列入的道学人士显然比较多。近代学者素来认为这些人攻击道学的动机无非是出于个人好恶、嫉妒,甚至有盲目的反智倾向;不过我觉得这犹待商榷,他们或许别有反对的理由。就目前不完整的资料来看,两个名单没有显示年龄、地位、官阶或地理分布的重大差异,而且两派在上述特征上的分布面都很广,很难根据这些特征讨论两个团体的不同。59名道学人士被列入“伪学”的名单,攻击道学的名单上则有35名。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些资料,可以考查到他们哪年得到的进士学位。59名道学人士中有36人的进士学位可考,而35名反道学的人士中有21人可考。①
现有数据虽然有以上的限制,有些数字仍然能显示部分的趋势。“伪学”名单中的五位(相当于总数的14%)道学人士,在第一个时期(1127—1162年)得到学位。这五个人当中有两个最为突出,即朱熹和周必大(1126—1204年),不过他们当时都还很年轻,朱熹只有18岁,周必大是26岁,与道学尚未有密切的关系。在36个获得进士学位的道学人士中,有86%的人在第二个时期(1163—1181年)中举。在21个反对道学的人士中,有43%的人在第一时期考中进士,57%的人在第二个时期获得学位。从1172年开始的十年,吕祖谦和尤袤(1127—1194年)担任科举主考官,情形显得更为突出。在分等考卷时,吕祖谦因父丧必须回金华,但其友尤袤按照他们的愿望,完成试事。这一年中举的道学人士比任何一年都要多,而只有一位后来的道学人士在当年通过进士考试。在“伪学”名单上,19%的人在1172年获得进士。吕祖谦的努力以及意识型态的偏好不仅表现在统计数字上,在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朝廷明文禁止考场徇私,并设下种种防范措施使考官无法认出考生的试卷,但吕祖谦还是认出陆九渊的考卷,虽然以前他只读过几篇陆九渊的短文,至于认出同乡友人陈傅良(1137—1203年)的考卷就更不在话下。吕祖谦当时的地位和声望非常崇高,敢公开说他认出陆九渊的考卷,而且1172年中举人数的数字没有包括陆九渊这么著名的案例,因为他比较早去世,没有赶上编制“伪学”名单的时间。总而言之,在1172年到1182年的十年间,上述的道学人士中有44%的人获得进士学位,而21位反道学的人士中只有一人获得进士学位,仅占5%。与第一个时期相比,第二个时期道学人士获得进士学位的人数和比例都大幅增加,攻击道学的宿儒则相形减少。
由于当时的气氛对道学日益有利,赵彦中(1169年进士)在1180年上书,对科举注重讨论人性、天理以及二程之学的影响表示不满。①赵彦中参加1169年的考试,通过科举的道学人士和反道学人士人数相当,但1169年是两派中举人数相当的最后一年。赵彦中这类人不仅不满某次考试不公,而且意识到考生与考官形成特殊的关系,会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长期合作,所以考试与政治派系有直接的关系。
1161年金人的入侵激发南宋人士对儒家价值观的进一步认同,使他们更热心教育年轻人以振兴价值观。高宗时期抗金失利,孝宗时期的相对成功显然增加士人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危机以及后来的和平给文士以捍卫传统更坚强的信心,利用和平的环境发展传统。政治环境相对缓和,知识分子可以花更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与辩论。
1162年高宗退位,孝宗继任,其实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张九成、胡宏和胡寅已经去世,李侗(李延平,1093—1163年)不久也谢世。到1163年,南宋头十年出生的第一代学人开始成熟,并成为这时期儒学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朱熹、陆九龄(1132—1180年)、张栻和吕祖谦。除朱熹外,这些知名的学者都在1180年或1181年前后相继过世,更年轻的学者虽然在1181年前已经开始活跃,但朱熹、张适与吕祖谦仍然主导这段时期的道学,被称作“东南三贤”。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大致相同,而且1163年南宋最有希望收复北方的时候,三位学者都在京师临安,颇有几分象征的意义。他们在平日交往和书信往返中,建立日益深厚的友谊,这些思想交流促从朱熹的思想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与前一个时期有显著不同。朱熹的生平思想已有非常详尽的研究,所以这里只简单谈论他的生平大略。朱熹的童年是在高宗时代的混乱和动荡中渡过的,其父朱松(1097—1143年)因反对和金政策被贬谪到福建。朱熹出生后不久,朱松的县尉的职务也被革除。朱松是杨时的学生,他培养朱熹对二程之学与司马光历史著作的兴趣。他过世前将儿子的教育委托给邻近三位研究程学的学者,胡宏的大侄子胡宪(1082—1162年)是其中一位。胡宪并没有把胡氏家学对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强烈敌意带进对朱熹的教育中,他对张九成所表达的一些佛教思想抱持很宽容的态度。另一位老师刘子翚(1101—1147年)的文章只保存在《诸儒鸣道集》中。朱熹这时非常喜爱大慧宗杲的禅宗学说,并且师事大慧的弟子道谦,可能是由于他的学习环境使然,而亲师的亡故也促使他寻求精神的慰藉,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他的少年时代相继去世,负责教育他的三位先生中的两位也很快过世。这些不幸的变故不仅使他更迷恋佛学与道家思想,而且让他感受生者的强烈使命感。朱熹经历了这些人事的重大变化,且没有一位固定而且影响深远的老师,所以比其他儒生更能独立思考。
朱熹的命运在1148年考取进士后开始变化。虽然位在五甲,名列九十,但他比大多数中第的人要年轻一半以上,所以很早就可以不必再为科举考试浪费许多时间,并得以迅速进入仕途。1153年他被任命为福建同安县主簿,并且在任达四年之久。在职期间他改进地方税收、整顿治安、提高教育水平以及制定礼仪规范。这个职务使他了解官场的实务,随后他被授予“岳庙督查”的闲职,有几年悠闲读书和思考的时间。
朱熹的思想到12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发生变化。从1153年开始,他数次拜访李侗。李侗是杨时的学生,朱熹的父亲曾极力赞扬他是二程学术的传人。朱熹最初在探讨程学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道家和佛教,李侗批评他研究这些异教,要他把精力集中在程学的研究上。宋代佛教在福建地区的影响很大,所以当地许多学人喜欢综合儒佛的学说教义,朱熹少年时期的三个老师就是如此;另外有些人则热衷建立儒学的正统权威,例如李侗、胡宏和朱震等人。朱熹在1159年编辑第一部著述《上蔡语录》,删去许多谢良佐批评老师二程助长佛学的言辞。其实在二程的第一代学生中,谢良佐可能是最倾向佛学的人,但是《上蔡语录》显示朱熹向程学迈进一步,逐渐接受李侗完全认同程学的观点。
到12世纪60年代,朱熹与李侗一样敌视佛道二教。他1166年撰写“杂学辨”,抨击融合儒学与佛道学说的学风,批评苏轼对《易经》、苏辙对《老子》、张九成对《中庸》以及吕本中对《大学》的注解。友人何镐(叔京,1128—1175年)为他写题跋,明确说明他的用意。朱熹认为苏氏兄弟、张九成及吕本中将儒家经典与老子、庄子、佛祖的思想混为一谈,后来的学人因为这些文人享有盛名而接受他们的看法,异端邪说因此日渐发展猖狂。何镐在跋文里说朱熹“大惧吾道之不明也,弗顾流俗之讥议,尝即其书,破其疵缪,针其膏肓,使读者晓然知异端为非,而圣言之为正也。”①
朱熹摘要引用张九成对《中庸》的注解后,指出张九成的观点与经典或二程的看法不同,并且批评张九成强调内在发展,却迷失方向,甚至走上异端的路子,不重视思考和经典诠释。而且朱熹认为张九成把仁解释成知觉,以及他对本心的主观理解,都是禅宗顿悟思想的反映。朱熹认为张九成不过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禅僧,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说张九成受到禅宗不少的影响,那倒是不假。朱熹的“杂学辨”显示他已经与年轻时代的儒佛合一的思想告别,并开始清理那些他所认为的儒家内部异说。
朱熹在1163年所完成的《论语要义》以及在第二个时期的其他著作,都显示他的发展方向日渐成熟。到1163年前,他虽然收录很多以前和当代学人对《论语》的注解,但已经奉二程的《论语》注解为圭臬。1168年编辑《二程遗书》完成时,他指出程氏兄弟复兴了古代圣人的绝学。1172年他在《论孟精义》中进一步用二程门人的著作解释二程的经典解释。1177年他完成《论孟集注或问》,书中驳斥许多程学门人的观点,同年完成的另一部著述《周易本义》,更显示他的独立与成熟;他不像程颐将《周易》解释成关于理的哲学著作,而强调它的占卜本义。朱熹在编选或诠释各家学说的过程中,显示他从道学的学徒走向道学权威的自信与成熟。
要从朱熹所在的背景中了解朱熹,就得探索其他儒家学者的思想以及他们与朱熹的交往。在1163到1181年这段时期,如果我们将张栻、吕祖谦与朱熹放到当时的历史地位上来考查,就不会像以往的研究那样过于集中在朱熹的身上。从秦桧的高压政策下解脱出来以后,道学学者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他们的思想,自由地吸引更多的学生。吕祖谦努力保护这个群体,使它不受外来压力的影响,他的领导地位——与以前和以后时期相比——鼓励各种观点的交流以及道学群体的相对多元化。
即使有这种相对的多元化倾向,紧张依然存在。由于12世纪60年代政治环境的变化,因为元祐遗事而引起的政治争执日益消退,思想的因素和学术渊源在划分集团时有日益重要的影响。张栻、朱熹以及吕祖谦都试图使道学更纯正,而为摆脱杂学的影响,尤其是佛教的影响,他们培植出更强烈的独特道学群体意识。政治压力的相对宽松,不仅提供道学群体发展的环境,而且也使道学人士开始专注界定这个传统内的成员与学说内容。
第二章 张栻
张栻或许是12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道学家,朱熹赞扬他说:“敬夫道学之懿,为世醇儒。”①张栻的父亲张浚在朝廷里享有盛名,张栻自己则天资聪颖,在老师胡宏去世后,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张栻以胡氏家学为基础,使湖湘学派的哲学完全发展成熟,但是1180年张栻去世后,湖湘学派也随之衰落。不过在12世纪70年代,张栻在教学方面的影响已经不如吕祖谦,而理论研究也不如朱熹。张栻被官修的《宋史》列入道学传,并受到现代东亚学者的注意,但仍被欧美学者忽视。②
张栻在1163年应诏入京,为父亲张浚的复出作准备时,初次见到朱熹。张浚的主战计划虽然在高宗时期没有成功,但是在重新考虑对金作战时,他又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张栻从幼年起就曾跟随父亲离开四川老家,转赴各地任职,因此继承乃父“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的壮志。①在紧张军事局势下,张栻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张浚不幸在1164年去世,张栻不得不暂时去职守孝。
张栻以直言著称,孝宗曾经抱怨“伏节死义之臣”难得,张栻答道:“〔忠臣〕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②孝宗曾问他“天”的问题,张栻回答说,天与苍天的意义不同,天指上帝,亦即最高“主宰”的古老代称。因为上帝与君主最为接近,孝宗应该使他的想法与上帝一致,否则“上帝震怒”③。由于宋朝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张栻激励孝宗放弃和谈,努力自强以收复北方失土。孝宗曾问他可否乘金人连年灾荒的机会北伐,张栻指出宋朝自身的弱点,认为关键不在于宋金双方物资的暂时状况,而在于宋朝有没有改善朝政的运作,以及加强战备的长远计划;没有赢得民心是不可能收复中原的,而赢得民心的方法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④。
这种传统儒家重视民生的思想也表现在张栻的政绩中。在北方沦陷的危机之际,张栻合于儒家理想的表现出类拔萃,朱熹因此称赞说:“小大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无几人;而其承家之孝,许国之忠,判决之明,计虑之审,又未有如公者。”⑤张栻除在京师担任侍讲,并在吏部和中书省任职外,也曾在地方任职十多年,管理地方广达四州。他每次上任都频频察访百姓疾苦,并且进行改革和救济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传统传记虽然通常会提到称誉政绩的客套话,但他的确是个好地方官。⑥他也极重视地方学校和教育,为达到复兴教育和启发人民的目的,他为各种学校、书院写作至少54篇题记。他的题记赋予教育事业维护儒家道德的特殊使命,他说:“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然则有国者之于学,其可一日而忽哉。”①
张栻认为在当时不友善的文化环境下,必须特别强调儒家的道德教育。那些追求佛、道异端的人虽然不好,但他们其实只是反映出违背道德的时代风气而已。有些学者文士认为儒学不切实际,逐利之心甚至使一些讲经的老成学者也常追求私人目的,专攻理论的儒家学者则更糟糕:
近世一种学者之弊,渺茫臆度,更无讲学之功。其意见只则类异端“一超径诣”之说,又出异端之下,非惟自误,亦且误人,不可不察也。②
总而言之,他叹息懂得儒学真义并且能够履行实践的人太少,所以必须将“吾儒”和各种异端之学的追随者区分开。③他在给朱熹、吕祖谦的信中经常提到当代精神的堕落腐化。不论这些看法有多夸张,它仍然激起保卫儒家传统和教育社会的热情。
张栻从幼年起的教育就围绕着二程的思想体系展开。他从小接受父亲庭训,张浚曾经追随二程的学生,也曾从游于与二程敌对的四川苏氏兄弟的传人,此外,他还与继承王安石传统的改革派交往,所以他并不能完全赞成道学家对传统的一切宣言。张浚自己的思想背景虽然复杂,并且和四川老家关系密切,他仍然让张栻学习胡氏的二程之学,而不选择苏氏兄弟的学说。④张浚弃官以后似乎更加认同他的道学朋友,思想的隔阂也比以前少。张栻起初只能以通信和读书的方式向胡宏学习,在1161年初次面见胡宏时,竟然感极而泣。胡宏看出这位青年的诚恳和潜力,开始向他讲授“仁”的道理。张栻回来后仔细思索,并给胡宏写一封论仁的信,胡宏读信后叹道:“圣门有人,幸甚幸甚!”①
张栻后来写作一篇论仁的长文,题名为“希颜录”。在《论语·雍也》中,孔子称赞爱徒颜回好学,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希颜录”收集几世纪以来儒家学者对颜回仁德的评语,并把颜回当成功夫修养的模范。胡宏告诫张栻说,这么重要的文章不容稍有错误,而且考虑几百年来不同的观点时,必须在众多的历史材料中“于未精当中求精当”。胡宏称赞张栻的考据功力,并且说:“先贤之言,去取大是难事。”②胡宏其实是在鼓励张栻以自己的判断取择传统。胡宏在他们第二次会面后不久就去世,张栻得到他的著作认真研读。
张栻的“希颜录”在他思想发展过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将“希颜录”当做衡量个人修养进境的标准,朱熹说:
〔张栻〕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观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远矣,而犹未敢自以为足,则又取友四方,益务求其学之所未至。盖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复不置者十有余年。③
张栻加入道学群体后,思想日益成熟,“希颜录”完成14年后,在1173年出版,张栻为此撰写一篇跋文。④
张栻在1173年还撰写《祭巳论语解》和《孟子说》,用流畅的古文论述《论语》和《孟子》的要旨。他比同时的道学人士少使用宋代的哲学词汇,他以胡宏为程颐的《易传》所作的注释为基础,强调《易经》的经世和政治道德的指导意义,而《经世纪年》则反映丰富的实务经验,《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则表现出胡氏家学传统中以历史服务道德的精神,他称赞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为“儒将”,是弃利求义的典范。①
张栻著作的流传有些问题。他讨论仁的长文和他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都曾与朋友(尤其是朱熹)往复讨论而修改多次。1173年所完成的几部著作是他思想的分水岭,显示他自认对传统的看法已趋成熟。朱熹在1184年编辑张栻的遗稿,完成《南轩集》并为它写序,删除了“希颜录”等早期的文章。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朱熹删除“希颜录”等论仁的文章及张栻给他的部分信件后,如何使我们研究张栻的思想以及朱、张两人的交流时备受限制。朱熹自己说“希颜录”对张栻每天的修养功夫十分重要,却决定删除这篇文章,确实令人感到惊讶惋惜。经过朱熹的编辑,加上张栻在1173年以前不断修改自己文章,我们很难根据现有的材料研究张栻思想的进化和发展。现存的材料表现出他与朱熹观点明显相似的特色,但是他们的思想其实并不如此一致,在1173年以前尤其显然。②对研究12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张栻所领导的湖湘学派,这些问题无疑是重大的障碍,也使后人难以再现道学原有的多样特性。
张栻不断研究“仁”的意义,使他沉浸在儒家的文献里。在《论语》的“颜渊”篇中,孔子说:“克己复礼”;在“八佾”篇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孟子以仁为“仁义礼智”的四德之一;二程则以仁为四德的总和,而且仁与万物为一体;张栻则在“仁说”中阐述仁之体用的关系。由于“仁说”明确表达张栻所认为的儒家基本价值,我们把这篇完成于1172年或1173年的文章几乎全部抄录于此:
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理,则智也。是四者,虽未形见,而其理固根于此,则体实具于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谓爱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发见于情,则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而所谓恻隐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为不仁,甚至于为忮为忍,岂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即克,则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爱之理无所蔽,则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其用亦无不周矣。故指爱以名仁,则迷其体。〔程子所谓“爱是情,仁是性”《二程遗书》卷十八谓此。〕而爱之理,则仁也。指公以为仁,则失其真。〔程子所谓“仁道难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为仁”《二程遗书》卷三谓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静而仁义礼智之礼具,动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达。其名义位置,固不容相夺伦,然而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恭让有节,是礼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知觉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见其兼能而贯通者矣。是以孟子于仁,统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犹在《易》乾坤四德,而统言“乾元”“坤元”也。然则学者其可不求仁为要,而为仁其可不以克己为道乎?①
张栻虽然在这里没有区分二程的思想,其实这篇文章中“程子”的话全部是程颐所讲的。“公”的含意很复杂,包括公德心、公正不偏袒等许多意思。张栻的著作中,“公”是就克己、克除私欲的层面而言,所以比较具有公正、不偏袒的意思;但是就以他对公事的责任心来说,“公”自然也包括“公德心”的意思。我们在谈陈亮时会讨论到,在某些宋儒的心目中,所谓“公”更具有“公益”的意义。
张栻在“仁说”中采用程颐“仁”为“爱之理”的说法,反对韩愈(768—824年)认为“仁”就是“爱”的说法。仁是“爱之理”、“性之德”,不是“情”。张栻以此区别为基础,援引二程的观点,认为爱是情感,仁却是人的本性。张栻将仁视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也是受到二程认为“仁”是生命的种子与万物的基础的影响。“仁说”以孟子所主张的仁即是人心的学说为基础,与程颢一样坚信“识仁”最重要。我们会在第三章中讨论张栻与朱熹的理论,它们虽然都建立在孟子与二程学说的基础上,但双方对“仁说”仍有不同意见。
张栻对仁一再精思独解,使他渐渐偏离老师胡宏性无善恶的理论;如果仁与人性不可分割,那么性怎么可能不是善的呢?张栻比胡宏更强调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他在《孟子说》中写道:“夫善者,性也。”①并且遵从孟子的说法,认为性善是因为性具有四德之端:
孟子所以道性善者,盖性难言也。其渊源纯粹可得而名言者,善而已。所谓善者,盖以其仁义礼知之所存,由是而发,无人欲之私乱之,则无非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矣。②
孟子认为“四端”是本然的善性,而从“四端”发展出来的“四德”则是本性的表现,所以孟子认为“四端”比“四德”更为基本。张栻却把次序颠倒过来,认为“四德”是性,“四端”是心:
仁、义、礼、知具于性,而其端绪之著见,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故原其未发,则仁之体立而义、礼、知即是而存焉。循其既发,则恻隐之心形,而其羞恶、辞让、是非亦由是而著焉。③
张栻用“未发”和“已发”区分四德和四端,并根据胡宏的性是静态时的体、心是性动态时的用,提出性是静的、未发的,心是动的、已发的;可见他对四德四端的看法与孟子不同,因为他接受胡宏区分心性的理论。张栻一定知道自己与孟子有些微差异,但他或许觉得更能巩固孟子学说的基础。儒家在面临佛教挑战它的道德、伦理权威时,需要一个比孟子学说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宋代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也在破坏传统家庭、社会关系,可能也促使张栻比孟子更强调传统家庭、社会关系所依赖的“四德”;他认为这些传统关系极其重要: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而又有君臣之义、朋友之信也。是五者天所命而非人之所能为。(①张栻坚信儒家的基本家庭社会伦常是人民生活和国家的生存的根本。人性论既然一直是支撑保卫儒家伦理的重要传统据点,所以他努力巩固人性论的基础,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栻以“四德”就是“天命之性”,进一步提供性善的根据。《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张栻据此推论性源于天命。所以人与生俱来的“天命之性”是至善无恶的。②张栻把性说成是“天命”之性,强调性是绝对至善,又认为人应该顺着人性的“本然”去体会性善。张栻把善比喻作顺从,说善是“循其性之本然而发见者也。有以乱之而非顺之,谓之则为不善矣。”③并以《孟子·告子上》中以水喻性的话来论证他的观点。孟子说:“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存之,可使在山。”外在的干扰消失后,水就会顺着自然之势往下流。张栻把这道理运用于人性论,推理说:“故夫无所为而然者,性情之正,乃所谓善也。若有以使之则为不善。”④许多儒家学者素来对为追求短暂成效而“有以使之”的行为抱怀疑态度,张栻认为“无所为而然”就是义、理,“有以使之”就是私利与人欲,更加强这种倾向。
张栻借用二程“气禀”的概念解释恶的起源问题。程颢曾经评论告子“生之谓性”的话(见《孟子·告子上》):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性也。①张栻以此作基础,解释为什么会有不善:
盖有是身,则形得以拘之,气得以汩之,欲得以诱之,而情始乱。情乱则失其性之正,是以为不善也。而岂性之罪哉?②
张栻既然认为恶是从气禀来,那么程颢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的“性”只是指气禀而言。
张栻又借用《礼记》进一步解释性的善恶。《礼记》说人生而静,而且有“性之欲”和“人之欲”的分别。张栻以胡宏主张的性静但“不能不动”的观点为基础,指出“性之欲”就是性对外物的反应,这种反应无穷无尽时,人的好恶没有节制,行为也容易变成不善,但不善并不是“性之理”,而是“一己之私”所造成的。张栻进一步说明这个区别:“譬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于因其流激,汩于泥沙,则其浊也,岂其性哉?”③
恶既然是从气禀来的,就可以用人性原有的善来克服。张栻主张回归本原以变化气禀,是从张载的“变化气质”的理论发展来的。张栻运用“气质之性”的观念解释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区分“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三种人,坚持这些区别只是就学问的起点而言:“困而学虽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则一者,以夫人性本善故耳。”①生而知之者的知识,别人以“困而学之”也能得到。从根本上说,下愚者和圣人有同样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的本性都是至善的,所以都能够以修养获得进步,甚至成为尧舜般的圣人,这种理论或许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宋代的经济、城市和教育的发展使社会阶层流动到达空前的地步。不过张栻变化气质的理论主要是就道德伦理而发的:“人所禀之质虽有不同,然无有善恶之类一定而不可变者,盖均是人也。”②张栻虽然认为人都可以改变气质,但他的理论却也为善恶绝对区分提供基础。
张栻的绝对性善论影响他对义、利的区分。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虽然已经开始区分“义”、“利”,二程进一步将它们决然对立。张栻以二程的理论为基础,把义利之分说成儒学修养的第一步功夫,而且认为义利之分就是天理、人欲之分;在这方面他取法程颐而非胡宏:“夫善者,天理之公孳孳为善者,存乎此而不舍也。至于利则一己之利而已,盖其处心积虑惟以便利于己也。”③要人认真研究重义君子和趋利小人之间的区别。
张栻用是否“有所为而然”来区分义利,使义利之辨更加决绝。他认为不应该为实现自己欲望而采取“有所为而然”的行动:
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自未尝省察者言之,终日之间鲜不为利矣。非特名位货殖而后为利也。斯须之顷,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则一而已。④“无所为而然”指性被思虑困扰并付诸行动前的状态,就是义和天理;“为利”指性被成心和欲望干扰且行动后的状态。张栻认为趋利并不只限于传统儒家经常批评的对名位和财富的追求,将“利”的范围扩大;在张栻的定义下,禁止趋利的戒律延伸到生活的各种领域,并且适用于社会各阶层。
张栻认为不“有所为而然”就是遵循道、守“道”不移,循“道”的人可富也可贫,应该“安于命”,不做有违于“道”的事:
惟君子则审其在己,不为欲恶所迁,故枉道而可得富贵,己则守其义而不处;在己者正矣,不幸而得贫贱,己则安于命而不去。此其所以无入而不自得也。①
循道和灭欲都需要修身自律。有人会说只要遵从自己的良知就已经足够,因为良心感到羞耻的事就是“私欲”,心里不觉得压抑负担的事就是礼。张栻认为这种说法太主观:“苟工夫未到,而但认己意为则,且将以私为非私,而谓非礼为礼,不亦误乎?”②必须做格物的修养功夫,以加强对“理”的认识,方能避免这种主观的偏见。不过“格物”也可能被误解为主观直觉的功夫修养,大慧宗呆就鼓励他的儒家朋友做这种纯粹内向的“格物”功夫。张栻想要反击禅宗的影响:
理不遗乎物,至极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则纯乎我”,是欲格去乎物,而己独立,此非异端之见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说,是反镜而索照也。③
如果“格物”完全依赖于“格物”的人,会造成物我的隔离,形成不正常的作用关系,有如用镜子的背面照自己一样。
张栻试图兼顾内外,同时讲究外在的“格物”和内在的“居敬”,希望能够维持两者的平衡。他讲解《大学》说:“自诚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无非格物致知事也。”①有时候又把“格物”和“居敬”的次序倒过来说:“格物有道,其惟为敬乎”。②张栻解释程颐主张的“居敬”:“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程子〕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③学者必须懂得“一”的意义,才知道功夫从何处着手。张栻虽然很重视“格物”,其实“格物”时,“敬”的态度也非常重要;他或许认为“敬”比“格物”重要,至少他在谈论“敬”时更富有活力:“居敬则专而不杂,序而不乱,常而不迫,其所行自简也。”④“简”意指人心不受欲望诱惑,行为就不会被外物干扰。“简”也和他所反对的“有所为而然”有关,张栻在“主一箴”中进一步解释“一”:
曷为其敬?妙在主一。曷为其一?惟以无适。居无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须造次,是保是积。既久而精,乃会于极。勉哉勿倦,圣贤可则。⑤
换句话说,张栻继承了湖湘学派养心、正心的修身传统。
张栻谈论仁、性、修身时常说到“理”,是否也专注于“理”的玄想思辨呢?他在《孟子说》中说理在物先:“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⑥有时也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解释万物的生成:“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⑦又把宋代哲学词汇和传统的“天”与“天命”的概念结合起来讲存在的基础:
天命之全体,流行无间,贯乎古今,通乎万物者也。众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尝有间断。圣人尽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立则俱立,达则俱达。盖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为大,而命之理所以为微。若释氏之见,则以为万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极本然之全体,而反为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谓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识道心者也。①
张栻的目的显然是在批驳佛教信徒,因为他们破坏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他认为佛教徒被一己私利蒙蔽,所以只能了解人心,而无法懂得道或心中的道德原理。
张栻这里的理论一如在讲修养时强调心的作用与地位。他认为心和性的本体就是天:“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②心是主宰内在之性和外在事物的无限力量:“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③朱熹主张“心统性情”,但是心必须遵从理的规范,虽然也讲心是主宰,能够实现理,但不肯让心控制理本身。就此而言,朱熹赋予的心的主宰功能没有张栻所主张的那么广大绝对,因为湖湘学派很明确地将心看做理的主宰。这种程度的差异根源于胡宏的思想,而张栻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
张栻虽然也对“理”做抽象的哲学讨论,但他和胡宏都比较喜欢讨论道德修养和文化价值的问题。他一方面有将心、性、天、理等同起来的倾向,所以不像朱熹将这些概念做细致的区分;在另外一方面,他注重心的修养,也对儒家的功夫修养传统有很大的贡献。这两个方面虽然优劣互现,其实相辅相成。张栻反对空谈心性,因为湖湘学派的精神修养一向重视自我反省和日常功夫,他批评当时的儒生学者不能领略周敦颐和二程“穷理居敬”的实践精义。④连黄宗羲(1610—1695年)也说:“第南轩早知持养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养,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却平日一段涵养工夫,至晚年而后悟也。”①
张栻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他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天理。在日用中发现天理是二程的中心思想之一,但程颐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教训常常被道学人士忽视。朱熹称赞张栻用天理、人欲的概念做义利之分,能够“扩前圣之所未发”。②
张栻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发扬胡宏的湖湘学派思想。张栻不但继承胡宏对于历史、经世实践、心性关系的思想,而且使湖湘学派更牢固地扎根于孟子和二程学术的传统中。张栻也追随胡宏,继承程颢对心、性和仁问题的看法,所以陆九渊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③张栻一生多次返回长沙岳麓书院讲学,由于他是知名的学者和官员,许多学生前往听讲。追随他学术的后学也不少,不过他死后却没有人能够真正继承衣钵。
湖湘学派为什么会衰落呢?传统的解释是湖湘学派的思想和教学都被朱熹的成就超越掩盖,但似乎还有其他的因素。宋代的湖南比浙江和福建落后许多,所以胡宏和张栻是在文化和经济较不发达的地方努力耕耘,客观条件与吕祖谦所在的浙江和朱熹所在的福建有不少差距。这种客观条件的差异限制了湖湘学派与其他派别的竞争能力。以吕祖谦为例,他的书院地处文化中心地带,又能吸引京城的士人,就拥有许多优势;岳麓书院缺乏这种优势,在张栻身后很快就衰落下来,一直等到1193年朱熹在湖南担任地方官时,才重新恢复旧观。④张栻1180年去世后,岳麓书院如此迅速衰落,似乎暗示它可能在1180年以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岳麓书院迅速变成朱熹学术的一个中心,张栻的弟子似乎有难以为继的问题。
湖湘学派衰落的部分原因也在于张栻的思想成分复杂。他的思想涉及层面广大,比南宋的第一代道学家宽广;他把实践置于理论之上,又强调心的修养与格物穷理。他思想里实践、修心、格物等几条线索在12世纪最后的20年里,都各自发展成独立的道学流派。张栻去世后,学生门人转到其他师门派别下,而这些派别将张栻留下的几条线索发展得更系统、更谨密。湖湘学派或许由于特别重视佛教的挑战,不像朱熹那么热衷区分儒家内部的派别。例如,胡宏的儿子胡大时是张栻的高徒,张栻去世后,他先后追随道学的三个主要流派。由于下一代道学家将张栻思想中的主要线索都做更深的发展,后人很少想要特别研究张栻,应该也是湖湘学派没落的原因。朱熹思想的发展也是使湖湘学派衰落的原因,因为12世纪70年代中期,朱熹的理论成就已使张栻黯然失色。下一章将要讨论朱熹与张栻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砥砺切磋的各种问题。
第三章 朱熹与张栻
南宋道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朱熹的道学思想发展主要表现在他与张栻间气氛和谐的学术讨论中。朱熹认为张栻做人明快,与学者讨论问题时,能够迅速了解各种观念,并且将它们形诸文字。朱熹也宣称自己需要勤奋治学,而张栻却能闻道“甚早甚易”。朱熹比张栻年长三岁,但承认“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①朱熹的学派声势大盛以后,学者一般都强调朱熹的学说如何创新与深刻,而忽略张栻的贡献;其实他们的交往使双方都获益匪浅。朱熹与张栻广泛讨论诸般哲学问题,探讨名词概念,一般而言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他们也曾就各自的《论语》、《孟子》注解中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交换看法。②在这里我并不准备探讨他们之间所有的意见分歧,而集中讨论对道学同道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
一、功夫修养与“中和”问题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功夫修养以及心的观念,当时有两个不同的理解传统。功夫修养包含内心修为的过程,朱熹对这过程的理解是从一个传统出发,向另外一个传统发展,然后进行理论的综合,而这项综合的工作是他成为道学理论大家历程中最重要的发展分水岭。不过,朱熹理论的全面发展是渐进与累积的过程,并非突然激烈的决裂变化。近代学者已经充分研究过朱熹与张栻对于“中”、“和”与心、性关系的讨论,①我在此只简单介绍,而较详细讨论朱、张二人关系对朱熹思想演变造成影响的部分。
“中和”问题是起源于《中庸》的第一章: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按照《中庸》的说法,“中和”是人与天地合一的关键,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周敦颐、邵雍注重主静,说心是“太极”与万物的根源,周敦颐更进一步将“静”与“一”看做是“无欲”的状态;张载则区别“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程颢提倡灭除私欲以存定人性;程颐则更加强调“主敬”的专一修养功夫。北宋道学家比更早期的儒家学者对心性问题有更明确的概念,所以更注重功夫修为以达到性或心的“中”的境界,最终的目的则在于得“道”,与天地万物合一。但他们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例如,程颐认为在情未发前,应该认真存养,而情已发后,应该加以省察。
如何经由功夫修养而达到与天地万物合一?12世纪上半叶的道学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流派主张:一派在福建,另一派在湖南。在福建方面,以程颐的学生杨时、罗从彦(1072—1135年)为代表,他们把默坐澄心当做体验本心和定性的方法,认为静坐沉思可以排除各种私欲,而获得澄清的心境。罗从彦将这套方法传授给李侗,李侗又将它传授给朱熹。李侗教导朱熹不仅要在静坐中获得澄清的心境,而且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功夫修养。但是朱熹当时认为,李侗对动静修养的教导是两个不同的学说。李侗认为这种心的澄净状态是日常行为修养功夫的基础,朱熹却对这两种直观的学说可能推衍出的矛盾颇感不安。问题的关键在于:活动的心怎样才能意识到它在行动前的寂静状态?朱熹思考李侗的观点达八年之久,在1166年得到初步的结论,认为如果了解内心的直观合一的境界不可能轻易实现,李侗的学说基本上还是站得住脚的。朱熹以前受张栻的湖南传统启发,对李侗的教导产生疑虑,现在思考出解决的方法,大概想要以此说服张栻,所以在1167年到湖南拜访,并停留两个月之久。
湖湘学派代表二程对于心的理论的另外一支主要发展流派。张栻以程颐所谓的“情”指心的已发状态、胡宏主张的心是性的作用的观点为基础,极力强调心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体验,认为唯有在行为活动中体验“静”,才能够获得心的“中”。张栻不主张静坐沉思,而认为应该利用心的潜能去体认四端,即可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把握天理,所以功夫修为应该先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天理开始,然后再来持养天理;张栻的方法观点比李侗更倾向行动。
从1167年朱熹在湖南逗留的两个月时间里,以及他在次年所写的四封信来看,他放弃李侗的观点,转而接受湖湘学派的主张。朱熹根据湖湘学派的看法,认为性是体,心为用;情未发前为性,情已发后为心。
但是朱熹不久又开始质疑湖湘学派的学说。学生问他为什么放弃李侗的观点,朱熹回答时显得颇为不安,并且承认由于仅强调从日常行为中领悟天理,不按照李侗所提出的方法致力于获致心的澄静状态,他有一种道德力量低落的感觉。从理论上来说,张栻主张的动中求静的方法只解决片面的问题:既然动、静在“太极”里总是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够在静中求动呢?难道不能在心活动以前就持养心的本体吗?这些问题使他越过师友,直接向二程的著作求教。
朱熹在1169年给湖南友人的书信中说,他研读程颐的著作后,已经找到答案,解决动静中和问题的困惑,而且先前建立在湖南学说上的观点缺乏坚实的基础。他引用程颐的著作,解答这些段落与他们以前都注意到的段落间的矛盾,而这些引起注意的段落都见于他一年前编辑成的《程氏遗书》。朱熹现在相信,湖南的朋友认为情已发后是心,是因为他们只接受程颐早期的看法,其实程颐已经修正自己的看法,指出心兼具静而未发的“体”以及已发贯穿万物的“用”两面。
若能够做到程颐讲的“主敬”,心就能动静适宜,进而理解存养天理,所以程颐提出的“主敬”与“致知”是最好的功夫修养方法:“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①朱熹根据这种看法,对中和问题得出一套完整的见解,进一步认为在省察和存养之前,不需要等待情的已发。情即使处在未发前的寂静状态,心一直是悠悠然的存在。但静只是心所处的一种状态,这种可以体会的心境虽然也是功夫修养的目的,但它并不是性。朱熹得到这见解后,就能够兼顾湖南与福建两种功夫修养的传统。朱熹在1172年左右写作“中和旧说序”,进一步考查自己思想的演进,从李侗的影响、张栻的冲击,然后到自己的功夫修养观,朱熹从此认为自己的思想已经成熟,以后未对这问题作重大的立场改变。不过,朱熹晚年只提到存养的功夫,所以可说他所谓兼顾动静的修养方法,与湖湘学派所强调的要素似乎渐行渐远。①
朱熹对这问题的思索演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里要讨论其中的三点意义。第一,他将道学家既有的理论加以综合,成为一套新的系统。他接受程颐主敬的观点后,就超越周敦颐的“无欲”、“主静”的学说以及程颢的“定性”的观点。程颢除努力追寻内在之性的寂静状态外,还强调要如实地应对外在事物;因此,程颢的理论较周敦颐的观点显得更为积极。朱熹要将湖湘学派在日用行为中寻求理的方法与福建学派静坐体验天理的方法融为一体,所以特别强调读书的重要。朱熹以前的福建道学家较重视以冥思直观的方法了解心,所以对研读书本知识较缺乏兴趣。根据朱熹的新见解,心的功夫修养较倾向读书以及对万物的经验观察。当然,他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而是从道德哲学家的角度来强调经验观察的;②所以朱熹比早期福建的道学家,更强调学术研究和多事述作的倾向。
其次,朱熹在历经放弃老师的观点以及再修正的过程中渐趋成熟,显然经过一段内心挣扎的痛苦,到达自由超越的重要阶段。他批判老师李侗及挚友张栻的观点,而痛苦扬弃它们后,得以直接把握程颐的学说,必然感到无限解脱与欣慰。他在摸索的过程中,自信他的二程研究足以纠正一般对二程学术的解释。朱熹处理动静中和问题时表现得很成熟,所以他对自己的权威更有自信;从此以后,他评析与重建儒家传统的工作更显著进步。
第三,张栻在朱熹的思想演变过程中,担任重要的催化剂。张栻所秉持的湖南修养功夫传统促使朱熹对自己的福建传统产生怀疑,张栻的动中求静的学说也是朱熹静中求动观点的重要转折环节,所以张栻帮助朱熹进一步解决两种道学传统间在修养功夫与中和问题上的对立,甚至可以说湖南道学家以“性为体,心为用”的说法,促使朱熹特别努力使用“体用”的概念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
前面一章讨论张栻很注重程颐格物与主敬的学说时,我们推测张栻与朱熹讨论心的中和问题时,张栻很可能首先提出这些讨论主题。他们在1163年、1164年及1167年几次会面谈论的内容,几乎没有文献数据可资参考,而且朱熹未将张栻早期的部分信件文章编进张栻的文集,而尚存的材料又往往很难准确判断完成的年代,所以很难判定究竟谁给对方的影响比较大。不过从1172年朱熹所写的“中和旧说序”,我们知道张栻立刻同意朱熹的最后主张,唯有一点仍然不能同意朱熹,张栻依旧认为持养前,必须要在日用生活中体验天理。①双方的共识如此容易达成,似乎表示朱熹也接受张栻强调主敬、格物的观点。张栻即使率先提到这些观点,或者促使朱熹思考这些问题,也不能因此贬抑朱熹理论综合的成就与哲学地位。不过,朱熹及日后的学者何以忽视或低估他与同代人的思想交流,由此大概可看出部分端倪。
在朱熹从1170年到1172年的交往友人中,吕祖谦一再提醒朱熹修养本心的功夫需要兼重动静。吕祖谦指出朱熹对胡宏《知言》中一段话的批评并不公平,认为朱熹的批评是从在静中持养的角度出发,而胡宏那段话是谈论日用生活的验察;吕祖谦并且指出这两种修养方法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朱熹批评胡宏没有追求本心时,的确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胡宏曾特别引用孟子对齐宣王谈论本心的看法作为例证,孟子建议齐宣王把不忍杀牛的感情推广到百姓(《孟子·梁惠王上》)。吕祖谦非常能够把握两种修养方法的要点,显示他已经完全接受这个观点,或者他在朱熹综合理论前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从后面我们对吕祖谦个人与思想的讨论来看,他很可能很早就注意到两种修养方法并重的理论。无论如何,朱熹的态度并没有吕祖谦那么持平,他回答说:“二者诚不可偏废,然圣门之教,详于持养而略于体察,与此章之义正相反。”①朱熹认为理解与省察天理是向外的,所以必须在持养天理之后。
二、《胡子知言》的讨论
第二个重要的讨论集中在胡宏《知言》的内容。朱熹在对本心的中和状态形成新观点的过程中,开始不满胡宏的《知言》。约从1170年开始,他要求张栻、吕祖谦一起批判《知言》。根据朱熹的说法,到1172年时三个人同意哪些段落有问题,②朱熹把这些意见记录下来,编成“胡子知言疑义”,张栻也表示基本同意这记录的观点。③
朱熹对《胡子知言》的讨论,显示当时的道学家对前人的著作进行一系列的修正。朱熹引用胡宏的一段话,表示他宁可采取张载的语言来描述心的功用,张栻对这两种表达方式都不太满意,而提出自己的说法。朱熹称赞张栻的说法有独到之处,但是他马上补充说:“凡言删改者,亦且是私窃讲贯议论,以为当如此耳,未可遽涂其本编也。”④朱熹在讨论开始的时候,显然无意改动胡宏的原文,可是他终究着手修改《知言》。
在另外一处文字中,张栻反对朱熹删改胡宏的原作,加进自己的用语,从而改变胡宏的本意。张栻提醒朱熹,应该尊重保存前代学人的思想;不过在另外两处文字中,张栻又表示一段“当删去”,另一段“不必存”。①唯有吕祖谦提的三段话始终维护胡宏,反对修改原作。朱熹在最后一次讨论中,直言不讳主张修改胡宏的原文:“此段诚不必存,……今欲存此以下,而颇改其语。”②为自己的删改行为辩护。
朱熹对胡宏的批评终究取得上风,他反对的段落在今本的《胡子知言》六卷中除四库本之外都不再出现。③到底是朱熹还是张栻删改胡宏的原作?答案虽然很难断定,但删改的主张来自朱熹则全无疑义。唯有朱熹一人记载讨论过程中三方的意见,张栻与吕祖谦的意见并不在他们的文集里。“胡子知言疑义”最重要的意义是显示道学领袖在琢磨近期道学家的著作,重建自己的传统。
朱熹对胡宏的著作提出八点疑问,后代学者把这八点归纳成三个主题。④第一,朱熹反对胡宏性无善恶的观点。第二,朱熹认为胡宏把心看做性之已发,而仁就是心,所以胡宏是从“用”而不是从“体”的角度讨论心与仁的问题。第三,胡宏认为,只有省察心活动的最初阶段,才能够把握心、持养心;朱熹认为这是错误的想法。前面已经处理过修养功夫的问题,后面要谈关于仁的争论,所以这里先讨论性和心的问题。
胡宏说性为天下之大本,但是心能够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朱熹反对这种“心以成性”的观点。朱熹引用程颐对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的解释,指出程颐是指心中的天理(即是性),而胡宏却是针对心的功用而言。胡宏认为性与心为一体两面,一体两用,互相关联。朱熹为否定这种关系,引用张载的“心统性情”的观点。⑤
另外一段讨论与此类似。朱熹引用胡宏的话:“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朱熹上溯这个错误的观点到程门学生谢良佐,并且再次引用张载对情的看法,以修正胡宏的学说:“性不能不动,动则情矣;心主性情。”张栻与朱熹的修正看法不同,表示要回到程颐而不是张载的论点,并且引用程颐的话:“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但是朱熹这次反对程颐的说法,认为所谓“有形”的意义不明;①朱熹显然不是简单借用程颐的权威就足以被说服的。
不论是胡宏的“心以成性”,或是朱熹的“心统性情”,两人都看重心的地位,认为心具有超越的性质,并且都区分无所不在的“天地之心”和依赖个人生命而存在的“一己之心”。胡宏回答学生问题时,曾经表示心超越生死,而学生对他的回答颇为困惑,朱熹于是抓住这把柄,批评他的观点包含佛教生死轮回的观点,应该提到“理一分殊”的看法。换句话说,心中的天理是超越的,而心的本身并非超越的;②而对朱熹而言,心中之理就是性。
胡宏相信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且同行而异情。胡宏虽然要人在道德修为中区别天理、人欲,但是朱熹指责他对本性问题的观点。朱熹指出,人虽然不能知道天理的起源是什么,但是人生而具有天理,所以天理是先天的。只有受到形体的限制、习惯的熏陶或者受到情感困扰时,才会产生人欲;所以人欲不是天生的。如果认为两者都是天生的,如何能区别它们呢?朱熹认为胡宏不能认识本体是纯净不受人欲污染的,却妄想在天理中发现人欲,又在人欲中发现天理。③
胡宏还说观察人对别人与事物的好恶,可以理解天理、人欲的区别,好恶是人的本性,因此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朱熹指责胡宏的观点是“性外有道”,而且使得天理、人欲没有先后主从的区别,会违背《诗经·烝民》的意旨: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①《孟子·万章上》引用这段话来说明本性先天就包含德性,朱熹进一步扩充它的范围,以区别人欲与天命法则,因为天命的法则与天理、人性完全相同。
朱熹虽然承认好恶是本性固有的,但他坚持好恶不是性的本身,而称它为“物”,并引经据典支持这种分别。《诗经·烝民》说:“有物有则”,这分别也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谓的“形色,天性也”。朱熹总结说:“今欲语性,乃举物而遗则,恐未得为无害也。”②朱熹将好恶当做“物”,似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可以把好恶当做“情”,就能够与他整个哲学体系更相应一致;亦即把“情”当做性的“用”,就足以与性的本身区分。但朱熹舍此不为,却引用经典的权威批评胡宏的论述。总而言之,朱熹所希望的是把性与天理视为一事,不像胡宏认为性并无善恶的分别。
性如果真的像胡宏主张的无善恶分别,问题是:善从何处而来?朱熹明白胡宏一直坚守着儒家行善的目标,对他所谓“人之为道,至大也,至善也”一语也推崇有加,但朱熹立刻补充说,本性如果没有善恶的区别,儒家的善行就失去根据。③
朱熹继续讨论胡宏对儒家善行的看法。胡宏指出圣人也有情、欲、忧、怨,与众人的区别仅在于行为合于节度:
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为正,挟非而行则为邪。正者为善,邪者为恶。而世儒乃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
朱熹认为胡宏的推理有误:
然不知所中之节,圣人所自为耶?将性有之耶?谓圣人所自为,则必无是理,谓性所固有,则性之本善也明矣。①
朱熹极力强调唯有肯定行为中节就是内在的善性,联系圣人与合于节度的行为才有意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张栻如何放弃胡宏“性无善恶”的主张,所以他立刻同意胡宏这项观念是错误的。
然而,张栻仍然坚持程颢的观点,认为善是性,但恶也不能说不是性。张栻引用程颢以水喻性的比喻,将善比喻成水本然的澄清状态,将恶形容为污水。善与内在的本性一致,而恶起源于物欲的困扰,所以学问的目的就是清除本性所受的污染,恢复最初的澄净本源。朱熹在这里只略带一笔说,程颢所谓恶也是性,只是专指气质之性而言。②
然而,程颢这段话一直困扰朱熹,值得进一步讨论。陈荣捷先生承认朱熹讨论程颢的著作时,以谈论这段话最多。因为程颢将清水比喻善性,陈先生觉得这种比喻很贴切,所以他的讨论就此打住,把难题简单搁在一边。③钱穆先生(1895—1990年)显然更了解这段文字如何困扰朱熹,他指出朱熹在《朱子语类》里,不断抱怨程颢的这项观点令人费解,竟然达30多次,并且认为程颢对性的看法不完整。朱熹坚持程颢的“性即理”,称它是孔子以来无人了解的至理名言,其实也隐约批评程颢一番。钱穆先生列举二程兄弟对本性问题的看法,显示程颢的观点的确与程颐颇有不同。④程颢认为性有善恶,而胡宏进一步说性无善恶。
朱熹和胡宏的另一个歧异在于他们对事物的本体的了解。二程谈论本体时,往往关心万物已经存在的状态,不是事物尚未生成前的本体阶段,例如,他们喜欢张载的“西铭”,而不喜欢《正蒙》,因为前者谈论具体实在事物的本体,而后者较为抽象。程颐晚年比较能够接受张载,而朱熹以程颐所讲的“性即理”学说为中心线索,把张载、周敦颐和二程兄弟的哲学融合成一个体系。胡宏较接近二程的立论倾向,只讨论已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本体;吕祖谦认为《知言》的价值胜过《正蒙》,很可能也是反映二程的这种思想倾向。但是朱熹坚持将本体解释成万物生成具体实物前的抽象第一原理。①
朱熹与胡宏所讨论的本体,其实在完全不同的层次。胡宏是从万物已经生成为具体实物的前提下,谈论天理人欲同为一体,而且心为性的作用。朱熹则根据自己的形而上哲学立场,分析胡宏学说的隐含意义。如果胡宏的性无善恶论指涉事物未发的寂静状态,朱熹才可接受他的理论。事物一旦有动静分别,立刻有善恶之分,而且合乎节度者才是善。朱熹认定胡宏的立场必须要谈论两种善性,甚至于两种本性:一为原初的本然之性,其二是通过情感作用的活动而呈现的性。②朱熹虽然谈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但是他没有将两者当成两种性,而且认为设定两种实在的性,根本是不能成立的理论。朱熹自认驳倒胡宏的观点,虽然胡宏没有像朱熹那样说两种本性。
朱熹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主张行为中可得见的善行,就是来自本性中的善性。朱熹根据这个思路,在1171年写信给胡宏的侄子胡实(1136—1173年)说:
盖谓天命为不囿于物可也,以为不囿于善,则不知天之所以为天矣。谓恶不可以言性可也,以为善不足以言性,则不知善之所自来矣。《知言》中此等议论与其他好处自相矛盾者极多,却与告子、杨子、释氏、苏氏之言几无以异。昨来所以不免致疑者,正为如此。①
善的本体就是最根本的原理,所以一旦认识终极的本体,就可以了解天如何成为天,以及善的根源。
朱熹是从形而上的思辨哲学出发,辩护最基本的原理,所以严厉批判胡宏的人性论观点。朱熹在1171年写信给胡宏的儿子,承认胡宏的本意是要极力推崇性的地位,但是称扬性超越善恶之分别,其实在无意间贬抑性的地位。性若非绝对的至善,而与人欲有相同的本体,它不可能是纯粹的。朱熹告诫他的学生说,胡宏的诠释无异说性是“空物”,与苏氏兄弟和佛教的异端很相似。②
三、“仁说”
朱熹与张栻讨论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仁”。他们的讨论早在1163年初次见面时大概已经开始,并持续达十余年。朱熹虽然在1167年拜访张栻的两个月间也曾经涉及这个问题,但在“中和”问题解决前,“仁”的问题还没有成为中心议题。朱熹写了一篇谈“仁”的文章,并且在1172年和1173年间与张栻、吕祖谦通信交换对“仁”的看法。朱熹到1173年时的观点大概与张栻已经变成一致,他与吕祖谦磋商后,将“仁说”做最后的修订。
朱熹论仁是以“天地之心”为根据。《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且卦辞用“元、亨、利、贞”形容天地的大德。程颐、程颢受《周易》以天地生成万物的看法影响,认为生成万物的“大德”就是天地之心: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①朱熹发挥说:
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或详之。盖夫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②朱熹然后以体用关系的角度阐述仁,认为天地、人心都有体用两面,而且由体用的关系,天地的本体在“元”起时就涵盖其中,人心中的所有德性也可以用“仁”统摄;他说:
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③
朱熹还引经据典说明人应该怎样作为,才能将仁体实践于日常生活中。
朱熹随后意图修正他所谓的早期道学家的错误,并且解决他与程颐间的一项明显差异。程颐认为“爱”不是“仁”,朱熹则指出仁是“爱之理”,并不是“爱”的本身;所以程颐的原意虽然没有讲得很明白,两人的观点其实没有矛盾。
“爱之理”与“心之德”合起来马上成为儒家对仁的标准诠释,能够涵盖体用关系,比以前任何“仁”的定义都要清晰。张载在著名的“西铭”中明确论及仁的本体,并隐约谈到仁的作用。程颐不仅澄清张载的观点,而且建立“爱为情、仁为性”的学说。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颐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①谢良佐以“知”说明仁,杨时以“公”解释仁。这里“公”是指公正无私,意指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如果天地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无所不爱。张栻则从“知”和“公”的角度说仁。朱熹在程颐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点,但是他更强调“爱”的因素,把儒家传统中几个重要的概念融合起来,写成一篇面面俱到的文章。
中国与日本的学者素来很注意朱熹的“仁说”以及他与张栻的信函,并且大都强调朱熹的理论综合很有创见,并肯定张栻最后接受朱熹的观点。例如,佐藤仁先生即说:“这篇文章透露出张南轩的湖南学识招架不住而且全倒向朱子的观点。”②刘述先先生还感慨在现存的张栻著作里“几无〔胡〕五峰学之痕迹,也看不出他本人的思想的特色何在,其学也无传人,大概因此附于朱子,遂完全为朱子学所压盖下去。”③我要考查这些说法,而且想平衡学者一贯侧重朱熹的倾向,所以较注意张栻的思想,以及他如何使朱熹的综合理论更加丰富。
张栻从1161年撰写“希颜录”开始,就一直努力研究仁的概念,而且数易其稿,直到1173年才能定稿。这篇文章完稿时,他也在修订“仁说”(原文见第二章),张栻“仁说”的修订稿无论语气、内容都与朱熹的“仁说”极其相似,所以从朱熹的学生陈淳(1159—1223年)开始,有的学者就误以为它出自朱熹的手笔。①但《朱文公文集》的编者说:“浙本误以〔张〕南轩先生“仁说”为朱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仁说”又注‘此篇疑是“仁说”序,姑附此’十字,今悉删正之。”②
由于这两篇文章非常相似,有些学者急于证明朱熹的“仁说”比较早,所以是原创的观念,这种说法的证据其实很有问题,基本的材料来自朱熹给吕祖谦的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在1173年初写的“答吕伯恭第十六书”,信中提到张栻说自己对“仁说”已经没有疑问,③陈荣捷先生就以此说朱熹的文章已经是“定稿”。④可是朱熹在当年秋末冬初所写的“答吕伯恭第二十三书”中,又说接到张栻的“仁说”。⑤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答吕伯恭第二十四书”中开门见山说:““仁说”近再改定。”⑥朱熹这里使用“再”字,显示他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朱熹在1173年年底以前,还在继续修改“仁说”。第二封信是“答吕伯恭第二十四书”,朱熹在信中提到张栻在1173年底曾送达书信与“言仁录”,朱熹评论此文“稍胜前本”,而且说“仁说”曾经根据他们交换的意见修改。⑦可是这封信提到的“仁说”虽然是张栻的作品,但它只是张栻最后的定本。总而言之,将这些信件放在一起考查,显示张栻即使说对“仁说”已经没有疑问后,双方的文章仍然在变化改进。
由于双方一直修改论仁的文章,而且张栻论仁的重要著作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委实很难证明朱熹的“仁说”比较早完成。朱熹把张栻去世后遗留下来的文稿编辑成文集时,没有把“言仁录”、“希颜录”以及张栻写给朱熹的论仁的部分信件收进去。张栻从1161年以后,一直在写作讨论仁的问题,所以他们讨论仁的问题时,张栻的文章一定是重要的焦点和催化剂,尤其是在1167年拜访张栻的时候,因为朱熹还要等几年才开始写他自己的“仁说”。我们虽然无法比较张栻早期论仁的文章与朱熹的“仁说”的措辞用语,但从现存的文章与信件判断,张栻对朱熹发展出的论仁的综合学说似乎颇有贡献。
朱熹给张栻的信中批评早期儒者的观点偏颇不周全:二程以前的儒生把“仁”化约成“爱之情”,因此看不出仁的重要;程颐严格区别“仁为性”、“爱为情”后,仁的重要性才再次获得肯定。然而,程颐的学生过于强调仁为性,反而忽略爱,比将仁视为爱的早期儒者更加不如。程颐的学生由于没有抓住仁的根本,不但个人修养没有成就,而且只能一味凭空玄想臆测仁的原理。他们由于这种无知,成为孔子所批评的“好仁不好学”的人(《论语·阳货》)。朱熹如此严厉指责道学传统中人,生动地显示他在12世纪70年代初,已经自信具有定义道学传统的权威地位。
朱熹在1171年进一步宣称,要纠正从二程学生而来的流行错误,需要为“仁”确立更清楚的概念。他在“答张敬夫第十六书”里说:
熹窃尝谓若实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进,但不学以明之则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为助,则自无此蔽矣。若且欲晓得仁之名义,则又不若且将爱字推求,若见得仁之所以爱而爱之所以不能尽仁,则仁之名义意思了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于恍惚有无之间也。①简而言之,人必须对仁的意义和内容有更精确的理解,方能够谈到功夫修养,而儒学的讨论才得以回归正确的途径。
朱熹和张栻在通信讨论仁的问题时,产生许多极有意义的争论,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天地之心”的问题上。朱熹在他的“仁说”里借用程颐的话:“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出自程颐的《易经》注解。张栻不同意这个说法,而支持程颐的另外一句话:“天地生物之心”①,张栻认为这两句话有根本的差别。张栻和胡宏都认为心是一种奇妙的超越力量,能够包含天下、约制万物。“天地生物之心”反映出他们的主张:心是活动不息的观念。张栻根据自己的理解,指出“天地生物之心”不受它所生的事物限制;朱熹所提出的“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的看法,则使心一定要受到限制。
朱熹答复张栻说,程颐这两句话其实意义完全相同。朱熹虽然即刻在“仁说图”中引用张栻喜爱的“天地生物之心”一语,但仍然指出这两种说法都认为天地之心就是生成万物的作用。他在1172年给另外一个朋友的信中,猛烈抨击湖湘学派的观点:
大抵近年学者不肯以爱言仁,故见先生君子“程颐”以一阳生物论天地之心,则必欿然不满于其意。复于言外生说,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心者,实不外此。外此而言,则必溺于虚、沦于静而体用本末不相管矣。②
朱熹警告说,湖湘学派把心视为具有超越功能的观点,会导致佛、道所讲的虚空与寂静。然而,比较一下朱熹当时的记录与12世纪7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胡家的成员与张栻都比朱熹更专心于政务,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持养此心,所以朱熹的批评是有些夸张。
朱熹和张栻虽然对“天地之心”无法获得共同的见解,但他们都同意“天地之心”与“人心”是相连的。朱熹提出:“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为人之心。”①双方对这句话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朱熹的重点是在温暖柔和的同情心,人们因这种同情心而可以爱人、惠及他人。张栻则顺着二程所提示的另外一条思路,强调要经由无所不包的“仁”,与万物犹如一体般互相联系。朱熹承认“仁”的普遍性能使“爱”惠及万物,但他很注意程颐曾提出的警告:普遍而没有区别的爱有流于“兼爱”的危险,视人如己可能会导致自我否定的结果,甚至荒谬到投身喂虎。同情心则较为实际可行,而且同情或爱其他的事物只是仁的效果作用,而不是仁的本体。②有些在伦理学上强调“爱”以及“与人一体”的人,都不了解只有爱是不足的,因为爱不能告诉我们应该为人做什么。朱熹虽然如此夸大嘲弄张栻的立场,其实张栻没有掉进虚无的相对主义或滥情无度的危险里。儒家学者把爱与义、孝等特定的道德行为相连,而这些道德提供行为纲常的规范。
朱、张双方的文章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处:他们都用“爱之理”描述仁的本体。由于朱熹删除张栻论仁的一大部分论述,我们无从知道“爱之理”是否来自张栻的“希颜录”和“言仁录”,也不能否定是朱熹首先使用这句话的传统看法。可是张栻马上在“仁说”和“癸巳论语解”中使用这句话,强调万物一体,要将爱推及万物,所以张栻将“爱之理”解释成公正无私、与人一体;但朱熹否认这句话有“万物一体”的含意。朱熹认为万物既然都具有此理,不必等待与万物合为一体以成就“爱之理”。公正无私虽然与仁很接近,但朱熹重申程颐的观点,认为“公”不足以代表仁的本体。从湖湘学派的立场来看,朱熹限制心与仁的本体;但从朱熹优越的形而上观点来看,湖湘学派强调仁有公正无私和无欲的特性,其实限制了仁。朱熹虽然在“仁说”里没有使用“公”一词,而且极少提到去除私欲的问题,但他使用“克己”一词,显然对达到公正无私和控制私欲的境界,也有浓厚的兴趣。然而朱熹与张栻通信论难时,极力划分这些特征与仁的区别,而且努力将仁与理完全等同。①朱熹所谓的“爱之理”没有强调爱包含世界的普遍意义,而特别指出它包括儒家一切的基本德目及相关的价值,而且这些道德价值是基本的先验法则,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事物为基础。朱熹认为仁是基本的先验原则,因为它就是性,而非情或心。
朱熹也反对湖湘学派将仁与心的知觉视为一事。张栻与其他的湖南学者继承谢良佐、程颢的观点,认为仁就是心初发的积极作用,而且是功夫修养的基础。张栻在一封讨论仁的信中再次肯定这个说法,似乎显示“中和”的讨论并没有如一般所说的使他放弃湖湘学派的传统。张栻所说的“觉”指感受到别人痛苦而产生的同情心,《孟子·公孙丑上》特别注意一种不忍见到他人受苦而能自发反应的心,就犹如拯救即将坠入井中的孺子的不忍之心。“觉”是发自内在心性的道德情感,“觉”也意指心的认知状态,用以探讨湖湘学派与朱熹的争论很适切。朱熹以“觉”的这层意义为重点,解释张栻和湖湘学派的观点。朱熹认为广义的仁包含其他儒家德目,湖湘学派却因为仁包含智,而错把智当成仁。仁人当然有知有觉,但仁不能被化约成知觉。②朱熹为强调仁是性、是理,而不是心,而把仁称为“心之德”。
朱熹认为把知觉当做仁,其实是以心来求心。他在讨论中和问题时指出,体验心所发的最初情感,不但需要有主动观察体验的心,还要有被动接受体察的心。他不太能理解胡宏、张栻和其他程颢后学其实是在谈论心的直观反省,并不是以一心求他心。朱熹也批评湖湘学派对孔子所谓“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的诠释。程颐曾经解释这段话说:反省别人的过错,可以知道别人是否有仁;湖南学者将这段话当做功夫修养的戒律。朱熹虽然称赞他们关怀自我修养的态度,但认为这种解释需要心不断犯错、观错,并且知道“仁”正在观察这些错误。朱熹指责这种方法会导致不必要的精神压力。①但是朱熹早先指责湖湘学派万物一体的观点会造成功夫修为的松懈,所以他这里的尖锐批评似乎有些混淆不清。
张栻回答学生问题时,颇能显示他接受朱熹批评的程度。张栻回复朱熹谈论“知觉为仁”的信函已然失传,所以这些师生问答的记录显得弥足珍贵。学生问张栻如何看待朱熹对谢良佐的评价,他回答说同意仁不能被化约成知觉,但也指出朱熹的批评稍嫌过分,并且补充说,心之所知唯有仁。另外一个学生引用朱熹“以心求心”的批评,请教张栻是否因此要明确修改他对孔子“观过斯知仁矣”的诠释,并请张栻澄清从反省失节的行为以知仁的论点,而且追问省察割股救父等极端的事如何能够教人以仁?②
张栻回答说,他仔细研究程颐的学说,而改正自己接近佛教的错误倾向,然后承认接受朱熹分别“厚”与“仁”的说法,但仍然认为反省过错很有益处。他也承认读书学习很重要,但坚持直接体验仁的一贯湖湘学派观点:
须是仔细玩味,方见圣人当时立言意思也。过于厚者,谓之仁则不可,然心之不远者可知。比夫过于薄,甚至于为忮为忍者,其相去不亦远乎?请用此意体认,用见仁之所以为仁之义,不至渺茫恍惚矣。①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评论这段话时,赞赏张栻把观过知仁与日常生活中的修养功夫相连,“如工夫有间断,知间断便是续,故观过斯知仁”。黄宗羲认为朱熹未能适切欣赏张栻的入手功夫:“若观过知仁,消融气质,正下手之法。”程颢类似的“识仁”说法,毕竟不仅只是“知仁”而已。②
有些20世纪的学者对张栻和朱熹论仁问题的评论,可与黄宗羲的看法相提并论。批评朱熹最激烈的莫过于牟宗三先生(1909—1995年),他认为朱熹曲解张栻对心以及仁的本体的看法。牟先生把张栻放进由孟子到程颢、胡宏的一支儒家传统,代表论心的主流观点,强调内在自发的道德情感,而且认为仁的本体不受任何限制。牟先生把朱熹归入程颐的系统,并追溯这支系统的脉络到荀子,尤其因为他们去除心内在的道德主动性,把心降低到仅具有认知的作用。朱熹不把心、性、情统整为一体,而以过度知性的分析方法严格区分它们的意义。牟先生认为,朱熹降低知觉领悟的地位,认为知觉领悟是被动的,所以人需要依靠“格”外在的事物,以了解心中内在的理。牟先生并且批评张栻不能适切捍卫自己的主流传统,不能了解朱熹援用程子权威时,其实是以程颐的观点误解程颢的观点。③
钱穆先生对牟宗三先生的看法提供了大概是最好的答复。钱先生指出,朱熹为反对佛教心理皆空的主张,必须将心与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所以他将仁视为生成的力量与天地之心。为建立这种联系的基础,朱熹说:
万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圣人之心。天地之生万物,一个物里面便有一个天地之心。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①
这种联系建立后,朱熹便可以宣称:“仁者心便是理”。②朱熹讨论功夫修养的目的,在于成就天地之仁时说:“学者克己复礼上做工夫,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③钱先生认为,在这些段落中,理、仁、心同为一体,④证明朱熹对心有更为广泛的看法,较牟先生所宣称的更接近孟子的主张。然而朱熹同时坚持了解心与仁的区别,以及一己之心与天地之心的道德差距,由于极为关注这些区别差距,他强烈反对湖湘学派的观点。
张栻与朱熹讨论仁的过程中,也的确获得一些共同的看法,并修改自己的“仁说”。朱熹在一封信中批评张栻不以体用关系了解性情,也没有提到“心统性情”的看法。今本的张栻“仁说”包括这些语句,显然张栻采纳朱熹这些建议,也接受“爱之理”必须先于“万物一体”的观点。张栻曾经在稿本中提到,天地之间无不是体之仁。朱熹认为如此则仁体就变成具体的实物,而且使万物与心中的仁的界限变得模糊。其实张栻从来没有将仁与心视作具体的实物,他的目的只是要指出仁无所不包。朱熹虽然明显误解张栻的观点,但张栻还是把这段话从“仁说”的定本中删除。⑤
我们若比较朱熹“仁说”的定本与他和张栻的书信,不难发现朱熹也曾因为张栻反对,而稍微修改自己的文章。⑥“仁说”定稿后,朱熹在“仁说图”中提到“公”的概念两次,也更明确谈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仁;这些改变都反映张栻关怀的课题。佐藤仁先生认为,朱熹得以发展出仁的概念,张栻的贡献远比这些细微末节更全面:“朱子和张南轩关于仁性的论辩,给朱子思想中的仁提供了最后的一笔。此外,这些论辩使朱子扫除了从南轩那边而来的湖湘学派加诸他的早期影响。”①
双方的差别当然依旧存在。朱熹比较注重理论,张栻倾向实践。张栻强调克己以及去除无知和私欲,朱熹则在克己与学问间寻求平衡。张栻对朱熹的妥协也有限,他在“仁说”中并没有放弃谢良佐的仁为知觉的观念,然而他表达“仁者知觉不昧”观点的方式,并没有与朱熹直接对抗的味道。他虽然同意不能将仁化约为“公”,但他没有完全放弃这观念,而且他的“仁说”定本中说:“公者,人之所能仁也。”②最重要的是,张栻的“仁说”并没有采用朱熹仁为“心之德”的说法。现代学者曾经讨论张栻为什么既不采纳,也没有提出疑问。他或许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其他的差异中,③或者根本没有异议,因为他们都师承二程的传统,而二程曾用种子来比喻仁、万物生成之理。④
“心之德”一词其实原来是张栻的用语,朱熹使用这句术语约12年后,承认它是张栻的用语,证据来自朱熹本人。朱熹承认这事实时,张栻已经去世五年,他没有必要承认贡献应该归功于张栻。朱熹当时编撰张栻文集,显然曾经重新审阅双方通信论学的内容与顺序。他在1185年写信给吕祖俭(吕祖谦之弟,1196年去世),描述张栻对他的“仁说”的反应:“欲改‘性之德,爱之本’六字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①朱熹显然承认张栻针对“性之德”而提出“心之德”的观念。根据这段材料的背景,“心之德”很符合湖湘学派对心的看法。我们无从究知“心之德”是否来自“希颜录”和“言仁录”,因为朱熹在编《南轩集》时,并没有收入这两篇重要的文章。
朱熹在这封信中又回忆说,他当时反对“心之德”的说法,因为它意义过于模糊,可以任人随意解释:“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着题,更需细意玩索,庶几可见耳。”②可是他却在自己的“仁说”定本里使用“心之德”,并以“爱之理”平衡这观点。朱熹显然认为,从湖湘学派所坚持的心的观点理解“心之德”,可能造成许多损害,以“爱之理”平衡后,就可以完全排除可能的损害。朱熹在1185年承认自己借用同时代人的学术观点,是相当罕见的事例,所以后来的学者很容易忽视它所呈现的朱熹思想发展过程。
张栻虽然没有向朱熹全面投降,但朱熹也的确赢得令人心服口服。张栻一旦接受朱熹的主张,承认湖湘学派思想来自谢良佐,就无法在程颢的哲学中寻求自己的学术渊源,所以追随朱熹向程颐寻求权威,使他在朱熹制定的规则下与朱熹展开论战。现代考证学者批评张栻没有清楚区分出二程思想的差异,而朱熹运用程颐来补充,甚至改变程颢的观点,都显示12世纪道学复杂多变的趋势。
整体而言,朱熹强调理论建构,张栻偏重实践,比较喜欢讨论文化价值以及实际的政策问题,但被迫讨论基本原理层次的问题。朱熹有时蓄意忽视张栻和胡宏的原意,而极力推衍他们理论的含意。例如,胡宏和张栻从体用的角度谈论具体的实物,朱熹却曲解他们在谈基本原理的本体。由于讨论层次的差异,朱熹赢得的一些协议,表面的意义甚于实际。朱熹与张栻的讨论,也证明朱熹比同时代的道学人士喜欢谈形而上的思辨哲学。
朱熹界定厘清许多观念名词,赋予它们重要的意义,而建立一套前所未有的综合儒学体系。在这过程中,他从与张栻的讨论里受益匪浅。后代的儒家学者承认张栻对朱熹的理论发展有贡献,但又常被两种看法遮掩而不彰。一派学者要证明朱熹理论的正统地位,并确立自己的理论权威;另外一派学者则指责张栻捍卫程颢和胡宏的传统不力,使他们自己的传统衰落。为重现12世纪儒家思想的发展动力,我特别强调张栻的贡献,而这种重建的工作由于材料的不完整而变得更加复杂。
朱熹编辑张栻的文集时,删除一些重要的材料,还改动《胡子知言》;我们重视历史材料的原貌,无法不对朱熹的做法不满。朱熹决定不要保留这些材料时,其实是在努力减低道学传统的多样特性,留下较为同质而确定的学术遗产。他的目的不是要客观整合文献,也不是否认朋友的贡献,他最关心的问题是道统的传承。朱熹的做法适切保证他所界定的道统得到传承,遗憾的是,朱熹删改张栻的文集后,他们求道的过程及思想世界都更难以如实地重建。在道学发展的第三时期,朱熹1184年编辑《南轩集》以前,整个思想气氛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要先谈一谈12世纪70年代的道学领袖吕祖谦。
第四章 吕祖谦
吕祖谦虽然不被《宋史》列入“道学列传”,并且鲜为现代学者所论及,但从12世纪60年代末期到1181年他去世的十几年里,他其实是道学最重要的领袖。①吕祖谦比12世纪其他道学领袖在政治上更得意,而学问也广为时人推崇,但吕祖谦身后受到的批评却引发一个根本的问题:他到底是位主张多元化、不受教条拘束的思想家,抑或是摇摆不定、缺乏决断的人?
吕祖谦出身望族,富有才华。吕氏家族从汉代被封在东莱后,产生不少政府官员,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到北宋达到最高峰。吕祖谦的先人吕蒙正(946—1011年)、吕夷简(978—1043年)和吕公著在北宋四朝分别官拜宰相,其他许多家族成员也甚获皇帝重臣的信任。吕祖谦的曾伯祖吕好问在女真人征服北方后,辅佐高宗在南方建立政权,功业彪炳显赫;在十一、十二两世纪,吕氏家人辅佐宋室的功绩无人能及。吕氏家族的学术表现也是出类拔萃,上下七代人中有17人被列入《宋元学案》,其中三人甚至各有专章论述,另外一人与范镇(1008—1089年)并列;其中最重要的是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等三人。
吕祖谦将吕氏家学传统和道学流派结合,发展出12世纪道学的一支主要流派。全祖望(1705—1775年)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说: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
全祖望这段话虽然是在18世纪回顾历史时所说的,但他认为吕祖谦是12世纪后半叶道学的一位主要领袖,见解十分正确。全祖望区分这三派学术时,不幸忽略张栻的地位;现代学者牟宗三先生把张栻放进他的划分系统里,却转而忽视吕祖谦。其实吕祖谦和张栻都不容忽视,而且除朱、陆、张、吕四派外,许多其他南宋道学家也颇值得研究。倘若一定要坚持简单的三派区分方法,全祖望的分法问题比较少,因为在12世纪后半叶,吕祖谦的影响力比张栻大得多。无论如何,全祖望准确指出吕祖谦学派的特点是能够兼容并蓄,而形成这种特色的主要原因是吕家从北方带来很多中原文献。
吕祖谦以家学和藏书为基础,在金华创建一所书院。他在金华附近的明招山任教一段时间后,于1170年把教学的中心移到城东的丽泽书院,与弟弟吕祖俭一起主持教务。当时的丽泽书院可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在南康附近)和张栻的岳麓书院(在长沙附近)媲美,丽泽书院的学者继承吕学的传统,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时代,使吕祖谦的史学和经世之学成为后世金华学派的基础。①学者几百年来把金华学派归在浙东史学和经世之学的范围里,除婺州金华外,此派的大本营还包括浙南的温州和浙北的明州(今宁波)。把这三处的主要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甚为恰当,因为吕祖谦的思想对这三个地区的学者都有影响,而且这些学者在当时已经有共同的归属感。
吕祖谦在金华讲学期间,学生从各方登门受教,吕祖谦也认为士子应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他对“道”和文化传统具有更根本的责任感,并且试图影响学生,使他们也能关心文化、道德和哲学的问题。吕祖谦对心、性的看法接近孟子,属于当时道学的主流见解,但是他不像一些道学家花许多时间研究这些哲学问题的细节。他与朱熹、张栻等同道最大的不同处,在于他更注意全国的政治问题,重视历史研究和经世之学,而这正是吕祖谦与其他浙东儒者的共同点,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也远比一般的宋代儒者(尤其是道学家)活泼。
过去几世纪的学者讨论吕家学术传统时,侧重四个主要的特点,而它们大多源于朱熹对吕家学术的评论。②朱熹认为吕氏学术的特色:第一,“不名一师,不私一说”。这个传统是吕希哲在11世纪中叶有意识开创的。吕希哲曾追随欧阳修(1007—1072年)的弟子焦千之,又曾问学于胡瑗(993—1057年)和孙复(992—1057年),使他的学术奠基在北宋第一代复兴儒学的学者的学说上;他又曾从学于王安石等第二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学者;道学的兴起也引起他注意,而与邵雍、二程过从甚密。朱熹的《伊川先生年谱》据《吕氏童蒙训》说:“吕希哲原明与先生〔程颐〕邻斋,首以师礼事焉,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③可见朱熹十分了解吕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对道学的兴起有很重要的帮助。吕希哲的孙子吕本中继承“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家风,先后追随过刘安世(1048—1125年)、杨时、陈瓘(1057—1122年)、尹焞、王(1082—1153年)等名儒,这些儒家学者和二程都有交往,其实他们代表的是12世纪初期范围视野较为宽广的道学。例如,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弟子,他的语录只保存在张九成弟子所编的《诸儒鸣道集》里。张九成和吕家的关系也很深厚,他与吕本中亦师亦友,写给吕本中的信充满感情,目前都收录在《横浦文集》和《横浦日新》里。①
吕本中的弟子林之奇(1112—1176年)把多样化的传统传给吕祖谦。林氏是吕祖谦青年时代最主要的老师,对吕祖谦的历史观——尤其是他对《书经》的看法——影响重大。吕祖谦年轻时也透过其他老师与广义的道学建立联系,他曾短暂地追随胡宪,从杨时与张九成的弟子汪应辰(1119—1176年)处得益尤多。胡宪的学术则结合二程的学说(尤其是他们的《易经》学说)和胡家的史学与经学。②胡宪是胡宏的堂弟,也是朱熹的父亲朱松托孤时指定的三个老师之一,所以朱熹与吕祖谦有一个道学传统中的共同老师。吕祖谦还和道学的另一个分支有关系,他们是在温州永嘉的程颐传人,可上溯到郑伯熊(1128—1181年),甚至周行己(1091年进士),周行己曾经带领八个永嘉同乡北上向程颐求学。③
朱熹承认吕祖谦学问广博,但批评他不能专注研究学问的根本;似乎用程颢既能广博又能“守约”的标准衡量吕祖谦。《朱子语类》记载朱熹弟子吴昌寿批评:“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朱熹甚表认可同意。④朱熹并将批评引申到整个吕氏家族的学问,他在“与林择之第十一封信”中说:“吕公家传深有警悟之处,前辈涵养深厚乃如此。但其论学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则博而杂矣。”①
第二,吕家“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学术风格使他们比较能够包容佛教。宋儒大多受过佛教的影响,但吕家比一般宋儒更能认清这事实,而且能够坦率承认佛教的影响。吕希哲晚年研习佛学,与僧侣交游,认为儒释两家教义有许多相近之处,所以主张调和两家学说。吕本中继承调和论的立场倾向,尤其喜好禅宗。吕祖谦在这方面的态度与先人不同,不但没有鼓吹佛教,而且还批评佛教。然而,还是有人认为他曾受禅宗顿悟学说的影响,因为他在“易说”中说过:“知此理,则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终身之蒙蔽,可以一语通;滔天之罪恶,可以一念消。”②但这句话是他在讲解《易经》睽卦时所说的,从上下文的脉络可以看出原意似与佛学无关(在第五章我们会再讨论吕祖谦的易学)。不过,朱熹仍然“有疑于伯恭词气之间,恐其未免有阴主释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发之于口耳。此非小病。”③
朱熹既然没有具体指出吕祖谦的思想和文章中有哪些地方“有阴主释氏之意,但……不发之于口耳”,我们也许不应太强调吕家传统中佛学的成分对他的影响。其实朱熹也曾经批评吕祖谦与张栻不读佛经:“〔张〕钦夫、〔吕〕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④道学虽然深受佛道两教影响,许多道学中人却对佛道深怀敌意,甚至把它们斥为异端。
吕家继承唐代大家族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这种风格在宋代显得十分突出。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吕家因为受到佛道两家相对主义倾向的影响,而“喜和不喜争,喜融通不喜矫激”①。吕家当然不是有兼容并蓄胸怀的唯一宋代政治家族,但这些家族多半不是道学中人。吕祖谦虽然不如先人深受佛教影响,他还是比较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他的包容倾向还有一个重要基础:他认为闻道十分困难,“善未易明,理未易察”②。又说:“义理无穷,才智有限。”③承认难以明确了解“道”;而且为人秉性谦和,所以特别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不轻易排斥异己。他说:“人各有偏处”,所以应“就自己偏处,寻源流下工夫”④。这种个性使他擅长在儒家学者间扮演调停折中的角色,不过他也不免受到当时道学界狭隘学风的影响;他只追求儒家学者间的和谐共识,尤其是道学家间的和谐共识。
第三,吕家不论接受多少佛家影响,涉猎各种不同的理论,其家学终究还是以《四书》为中心,而《四书》是道学界公认的儒家主要思想文献。吕本中虽然又加入《孝经》,但仍然认为《四书》比传统的《五经》重要。他说:
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⑤
所以《四书》和《孝经》比起其他经书更属儒学的根本,儒学的基础稳固后,才能运用其他各家的理论。吕氏所关怀的《四书》问题和其他道学家相同,包括:“存心养性”、“穷理”、“尽心”、“正心”、“诚意”等主题。例如,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⑥。道学当时甚至还未兴起。吕氏一直很注重孟子的修身方法,这点也和其他道学家一样。
第四,吕氏重视功夫修养的情形,从他们的治家格言“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出自《周易·大畜卦》)即可见一斑。吕公著早年就依此治学,而且把它变成家学的精华,吕家的成员虽然转益多师,他们最珍贵的还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家学传统。这个格言很能反映吕氏“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作风,因此能够在历代产生出许多杰出人物,并且发扬它的教训,收集大量图书,建立当时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全祖望说:“中原文献之传,犹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①这些藏书不但培养丰富的文学修养,对他们的史学研究也很有帮助。
二程在广博的吕学中占有很特殊的地位。吕希哲曾从游于程颐,吕希哲的子孙又追随过杨时等二程最亲近的弟子。吕祖谦把杨时的《中庸》注解当做研习此书的标准,认为个人教育应该以二程和杨时的文章语录为中心。吕本中也把张载的学问纳入吕氏的家学,所以1345年编成的《宋史》虽然未把吕祖谦列在“道学列传”内,却仍说吕祖谦的思想是张载和二程哲学结合的产物,②当然二程和张载的哲学并不是吕祖谦综合思想中的唯一成分。
吕祖谦的家世和教育都很优越,所以他在科举和仕途上都很得意,发展比其他南宋主要道学家顺利。他在1163年考中进士,不久又获得博学宏词科的殊荣;宋朝300年历史中,只有34人曾登上博学宏词科。报考博学宏词科需要熟读大量典籍,范围涉及文学、历史以及历代制度,吕祖谦能荣登此科显示他一直究心学问研究,以及他对效忠皇帝有十分的热诚。吕祖谦登上博学宏词科后立刻踏上仕途,担任的职位多半是史官,但是他的双亲分别在1166年和1172年去世,他两次离职回乡守制。张栻等人在此期间经常造访,使吕祖谦与士大夫的关系得以维持不坠,所以他守丧期满后旋即被朝廷重新启用。
吕祖谦在1169年被任命为太学博士,随后出任位处京城南郊的严州州学。吕祖谦把金华书院的学规引进州学,当时张栻是严州的地方官,两人住得很近,可以每天相聚。1170年吕祖谦写作两篇有名的奏议,劝孝宗选用贤能,远离小人,矢志收复北方河山。不久,孝宗擢升他和尤袤为礼部考官,因此成为1172年进士会试的主考。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次考试的结果显示政治气氛转向,对道学群体非常有利。由于著名史学家李焘(1115—1184年)的推荐,吕祖谦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又兼任国史编修官以及实录院检讨官,主持徽宗(1100—1126年在位)实录的编纂。吕氏家人担任过几次类似的工作,吕夷简编修过太祖(960—976年在位)到真宗三朝的国史,吕公著则主编英宗(1063—1067年在位)和神宗(1067—1085年在位)实录,可见吕家编修实录的经验比时人丰富。由于徽宗实录会涉及北方沦陷的问题,所以这项工作在政治上很敏感。1177年实录完成,吕祖谦在呈献时,劝皇帝汲取经验教训,进行改革。孝宗再次提拔他,请他负责收集编纂北宋时期的杰出奏议、序跋和札记。他在这部汇集北宋政治智慧和文学典范的著作里,收录大量苏轼、王安石和欧阳修的文章,但也包含其他北宋人的作品。吕祖谦发扬一贯兼容并蓄的精神,不以人废言,只论文章的优劣,不管作者的政治和哲学立场。这部书完成后孝宗御赐《皇朝文鉴》的书名,并赏吕祖谦三百两银子,再度擢升他的官阶。
吕祖谦40岁的时候已经深受皇帝的敬重与信任,并和周必大等政府要员关系友好密切。吕祖谦的人缘良好,多少与他家人世代在朝任官有关。宋朝南迁后,吕家仍维持北方望族的习惯,与外地的名门大族联姻通婚。吕祖谦先娶韩元吉(1118—1187年)之女,后来又和芮烨(1114—1172年)的女儿结婚,韩、芮两姓不是金华同乡,但都是名门显宦。吕祖谦一直很密切注意朝廷的政局变化,不像朱熹不屑参政,但疾病使他的政治潜力未能完全发挥;他在1178年患病,次年辞去所有的官职,两年后就去世。
吕祖谦的一生都被病痛所困扰。父母于1166年和1172年去世,他两度返乡守孝三年。三个妻子都在生产后去世,子女中只有一男一女存活下来。从1157年他初次结婚,到1179年第三任妻子过世为止,总共只过了八年的婚姻生活,所以在第一次结婚后的3/4时间里,他是个孤独的鳏夫。吕祖谦从幼年起就病魔缠身,从症状来看似乎是年轻时得肺结核,40多岁时又中风。他抱怨右半身体虚弱疲惫、动作不灵,有时连饮食都无法自理,只能写很短的信。他在一封信中说:“药物日进三、四服,未尝废炙艾,医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则盖燥涸,以此犹未绝也。”①从他祖先和宋代士人的一般寿命来看,他应该还可以再活十几或二十几年,但是体弱多病以及守孝和丧妻的伤痛,都促使他在中壮之年就去世。
吕祖谦早年病中的反省却改变他的性格。他幼年时期脾气很坏,疾病又火上添油,甚至遇到不喜欢吃的东西就要摔盘子,但病痛没有妨碍他认真读书,朱熹说吕祖谦在病中也是书不离手。②《宋史》说吕祖谦“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③性格从此变成非常宽厚。吕祖谦家庭教育加强了他对政治和文化危机的社会责任感,他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三个年头里,一直在金华专心教学研究,学生再度云集门下。这种门庭若市的盛况有诸多原因:吕祖谦具有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且中过博学宏词科,此外还曾担任过太学博士,又主持过1172年的进士考试。他奉旨编修的书也受到广泛的好评,而且金华的书院离首都临安很近,从临安坐船逆流而上,最多四天就可以抵达金华。
吕祖谦的讲学有独到之处。他强调学生应该发掘新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墨守成规,他说:
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①
他也劝朱熹多教导学生在日用生活中作修养功夫,教学则应注意方向和顺序,他说:
致知、力行,本交相发,工夫初不可偏。学者若有实心,则讲贯玩索,固为进德之要。其间亦有一等后生,推求言句工夫常多,点检日用工夫常少。虽便略见仿佛,然终非实有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训诱之际,愿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语上”、“不可以语上”之别。……非谓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为缓,但示之者,当循循有序耳。②
吕祖谦留意到若要寻求知识与实践的平衡,学生应该自己思考。
吕祖谦教过多少学生呢?1180年左右,丽泽书院有近300学生。③陈荣捷(1901—1994年)先生向来重视朱熹的成就,却也完全接受这个说法。④这300个学生外,还应该加上1180年以外的丽泽书院学生,1167年、1168年和1173年三年在明招山任教时的学生,以及严州官学的学生,总数至少上千人。即使只计算1180当年的300个学生,他也无疑是12世纪70年代最受欢迎的老师,与张栻在12世纪60年代所受的欢迎程度相当。
吕祖谦的学生人数和朱熹的学生人数相比呢?以现在的眼光回顾,朱熹是南宋时代最著名的老师,例如,陈荣捷先生在《朱子门人》中列出的467人中,①只有五人是在1167—1179年间列入门下。朱熹在南康重建白鹿洞书院后,又有35位年代可考的学生投入门下,另外9个本地学生从游的年代不明,即使把这9名学生都包括进去,朱熹在这15年内似乎只有49个学生,而吕祖谦在1180年一年里就有近300的学生。朱熹1181年所收的49个学生约占他学生总数的10%左右,这些数字虽然不完整,仍然明白显示朱熹的学生大部分是在1182年到1200年之间投入门下,亦即吕祖谦去世后的19年间所招收的。
吕祖谦在父丧不久后就再广收学生门徒,因此几个友人对他略有微词,但是没有人怀疑他的哀伤及孝思。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
〔吕祖谦〕尝与汪端明书曰:“刘子澄传道尊意,是时以四方士子业已会聚,难于遽已,今岁悉谢遣归。”祖望谨案:此即〔陆〕象山谓“伯恭在哀绖中,而户外屡恒满”者也。〔张〕南轩亦尝问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议其非者。”观此条,则〔吕〕先生因〔汪〕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过者。②
吕祖谦虽然把学生“悉谢遣归”,张栻仍认为他对这些学生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吕〕伯恭真不易得,向来聚徒颇众,今岁已谢遣。然渠犹谓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谓来者既为学业之故,先怀利心,恐难纳之于义。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断有所未足。③
有些学生当然只是为准备科举而入门进修,但必定也有被吕祖谦广博的学识和道德修养吸引来的学生。
吕祖谦有几部主要著作是根据讲稿编成的。他的《书经》讲词被学生编成《东莱书说》,他在太学时根据“为诸生课试之作”而编成《东莱博议》,尤其著名。①《东莱博议》虽然是学生用来准备科考的范文,但就像吕祖谦曾对张栻说的,里面的文章也教导学生道德原则和历史教训。吕祖谦对追求“道”的一心投入很能表现道学群体的共同特点,他明白宣言:“坚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力,乃区区所望。”②许多儒家学者偏离儒家正道的时候,这种对道投入奉献的热诚尤其重要,吕祖谦向朱熹说:
论学之难,高者其病堕于玄虚,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异端,平者浸失其传,犹为惇训,故勤行义。轻重不同,然要皆是偏。③
再三强调当日学者治学方法褊狭的弊病。
吕祖谦认为当时不友善的气氛四处弥漫,有些登门求教的学生也感染这种态度,使儒学之道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从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实者,所宜深察。往时固有得前辈言语声欬以借口,而行则不掩焉。媢嫉者往往指摘此辈,以姗侮吾道,绍兴之初是也。虽有教无类,然今日此道单微,排毁者举目皆是,恐须谨严也。④
吕祖谦尤其担心自称道学弟子的人行为不轨,提供敌人攻讦的口实。现有的材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们知道陈公辅曾经向道学示好,批评“王安石学行之误”,可是他后来态度一变,在1136年上书高宗,嘲笑道学“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幅巾大袖,高视阔步”⑤。吕祖谦的忧虑与其他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教派(fundamentalistsects)颇为类似,而他明确表现这种忧虑。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是最宽厚开明的道学领袖,而且政治地位最为稳固,甚至敢公开宣扬他在评阅进士试卷时,认出陆九渊的文章。
吕祖谦虽然有时表现出很深沉的忧虑,但对扭转恶劣的环境更表乐观。他鼓励学生潘景宪(叔度,1134—1190年)加强责任感:
大抵讲论治道,不当言主意难移,当思臣道未尽。不当思邪说难胜,当思正道未明。盖工夫到此,必有应,原不在外也。①
吕祖谦认为士大夫应该负起实际行动的责任,不应该只是坐论空谈、抱怨世道人心不古:“士大夫喜言风俗不好。风俗是谁做来?身便是风俗,不自去做,如何得会好?”②他还批评秦汉以后的士大夫:“外风俗而论政事。”③吕祖谦认为讲学是解决当时各种问题的关键:
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熏蒸上腾,亦有转移之理。④
吕祖谦的政治学术生涯显示,他希望从朝廷开始,由上而下影响世道风俗,在社会上培养正直奉献的儒者,从而改造社会、政治,使它们符合道的理想。吕祖谦对教导士子应试的态度比张栻、朱熹积极,认为科举的成功可以使他们从政治中心改造影响社会。这种对体制内改革的信心,无疑深受出身仕宦家庭的背景影响。
吕祖谦为教导学生进入体制内工作,在金华书院的课程里对政府各种制度进行详尽的分析,这套教材流传使用150年后,才被后代门人编成《历代制度详说》出版。吕祖谦叙述评论历代制度,讨论的题目包括:学校、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马政、考绩、宗室和祀事。吕祖谦不但分析各种制度在历史上的优缺点,而且讨论它们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情况,他的判断多基于现实条件而非空泛的理论。例如,他认为当时百姓有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所以张载、胡宏等学者要想在全国实行井田制度,只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①
吕祖谦在其他著作中讨论到法治的问题。许多儒家士大夫重德治而轻视法治,吕祖谦却很肯定法律的功用。②他认为一般人反对用法,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申韩之法,其实法律的本质与申韩之法不同:“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韩深刻之书,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会看得仁义之气,蔼然在其中,但续降者有时务快,多过法耳。”③法律应该建立在人情物理和仁义的基础上,而不是系于人主的好恶。法律的“仁义之气”不是抽象的理论,应该是实在的东西,有时必须用严刑峻法吓阻不法,才能达到仁的目的。法律如果太宽松,违法犯禁的人会增加,结果受法律制裁的人反而比较多。这些观点虽然都是从政府的立场出发,但他也主张公私应该并重:
世俗多谓公私不两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则公私两全;否则公私两失。……庶或公不败事,私不伤义,便是忠厚底气象。④
有人也许会怀疑吕祖谦强调法治和主张公私并顾,只是反映岀权贵大家的背景观点。当然对吕氏这种家族而言,主张忠君和善待私家既是理想,也有实际利益的成分。假如硬要说他注重法制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许多统治阶级成员比较不注重法制和私人利益,又做何解释呢?吕祖谦和一般儒家学者都认为道德是治国的根本,但注重法制和私家利益是他的一大特点,而其他的浙东儒者也持相似的看法,陈傅良和陈亮的立场更鲜明,尤其是陈亮的例子,更能明确说明浙东学派如何寻求公(社会或国家利益)和私(或家庭利益)之间的平衡。
吕祖谦与其他浙东学者经常批评当时的风气太重文轻武,吕祖谦却编辑宋代最重要的文选之一《宋文鉴》,而且也是当时的文学大家,所以他反对重文轻武,并不是要以重武轻文的政策取而代之。浙东学者经常批评宋太祖把武官地位降到文官之下,并把兵权从武官手里转到文官手里。吕祖谦和他的浙东友人认为文武应该均衡合一。他引证古史说:
自古文武只一道。尧舜三代之时,公卿大夫在内则理政事,在外则掌征伐。孔子之时,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自当夹谷之会。西汉尤知此理,大臣韩安国之徒,亦出守边。东汉流品始分,刘巴轻张飞矣。①
东汉以后文学日兴,而文武之途渐分,历史提供许多徒重虚文而导致祸害的教训。吕祖谦又在《东莱博议·魏懿公好鹤》中用魏懿公(公元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鹤的典故,讽喻许多近世的士大夫与魏懿公的鹤没有什么区别:
永嘉之季,清言者满朝。一觞一咏,傲睨万物。旷怀雅量,独立风尘之表。神峰隽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乱,屠之不啻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鹤也。普通之际,朝谈释而暮言老,环坐听讲,迭问更难,国殆成俗。一旦侯景逼台城,士大夫习于骄惰,至不能跨马,束手就
①《宋元学案》,卷51,页1661。按:诸葛亮曾为此责备刘巴;参见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39,页982,注3。
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鹤也。①
吕祖谦的祖先来自北方,他虽然多病,但可能学过骑马,所以讽刺不会骑马的南方文人。玩马球的风气在宋代衰落,士大夫子弟只爱在院里街中安然踢球,可以想见骑术退步的情形。②吕祖谦承认这些士大夫并非全无可取之处:“是数国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词藻,望其威仪,接其议论,挹其风度,可嘉可仰,可慕可亲。”然而“卒然临之以患难,则异于懿公之鹤者几希”③。
从历史中寻找实际教训也是吕祖谦和其他浙东学者的重大相似处。他认为读史时应该厘清时代背景,设身处地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教训:
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④
又说:
看史须看一半便揜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⑤
吕祖谦认为吸收道德教训是读史的目的之一,但他更注重从历史中获得实际事功的借鉴,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限于道德的教训,还认为读史应要注重变化发展,不能只求博闻强记。他说:
陈莹中尝谓《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然虽是药山,又须是会采。若不能采,不过博闻强记而已。壶丘子问于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对曰:“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变。”此可取以为史之法。①
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变化,他说:“此事极,则须有人变之,无人变,则其势自变。”②齐桓公(公元前684—前642年在位)就是不懂局势的变化而招致祸害。他标榜“尊王攘夷”,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人,在葵丘之会达到成就高峰后,却变得傲慢堕落,种下霸业衰落的种子。吕祖谦认为齐桓公历史的教训在于:
〔齐桓公〕抑不知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也。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驱骏马而驰峻阪,中间岂有驻足之地乎?③吕祖谦指出齐桓公由盛而衰的模式,并可见于汉人与胡人互动的历史。
吕祖谦认为,学者在寻找历史的发展变化模式时,也应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性。权力结构不同,治国的方法也不同;例如在读《左传》时,学者应该把春秋时代划分成三个时期:五霸兴起前、五霸时期和五霸衰落后的时期。吕祖谦用权力结构划分历史,并不表示他认为统治阶级是决定历史的最终力量,他依然遵循孔子、孟子的传统,认为国家的兴亡最终取决于人民。
吕祖谦着眼于权力结构来为历史分期断限,并以此讨论过去的种种制度是否适用于宋代的现实状况。例如张载、胡宏等人主张恢复井田,吕祖谦则认为宋代距离井田制度的时代已将近两千年,历史条件改变太多,不可能恢复这种古代制度。与其固执古人的制度,不如改变旧制以完成古人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国家太平。④他一再强调唯有了解历史背景,才能善用历史知识。
由于史书质量的参差不齐,有的泛泛阅览即可,有的则须一字一句小心谨读。几部最重要的史书更应该以读经的态度来读:“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者,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真不可一字草草。”①《后汉书》以后的史书品质大半不高,可以在上面少花些时间。吕祖谦也用史学家的眼光看待儒家经典,开清代浙东史家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先河:“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②又说:“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接。”③这三段话里提到《左传》两次,可见《左传》在他的史学里占有中心地位。
吕祖谦认为《左传》是非常重要的史书,所以把它当成一部独立的著作,而不把它视为《春秋》的注解。他如此重视《左传》,但没有因此对《春秋》减低兴趣;《春秋》是宋代学者最重视的经典之一,产生至少240部相关的著作,数量超过其他任何经学著作。吕祖谦继承北宋孙复等学者的立场,强调《春秋》“尊王攘夷”的大义。④吕祖谦对《左传》的看法比较独到,除写过《东莱博议》外,另有《春秋左氏传说》和《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等两部与《左传》有关的著作。吕祖谦注意《左传》的细节,从中得出很多重要的结论。例如,他计算周朝将领的名字,证明周朝王室的军队确实越来越少,所以吕祖谦认为《左传》延续六经,继续记载古代的事物制度。
吕祖谦为延续《左传》的记录,开始撰写《大事记》,并在注释里评论各种事物和讨论史学得失。《大事记》大量取材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年)的《史记》,写作的方法也很受《史记》纪传体例的影响。他不但用《史记》和其他早期的材料纠正《资治通鉴》的细节,而且写了两部批评《通鉴》的专著,可惜这两部书都未能保存至今。①吕祖谦打算用《大事记》取代《通鉴》,但只写到公元前90年,就不得不因病搁笔,留下一千多年的空白。不过他完成了《十七史详解》,可以用它为基础完成《大事记》。从《大事记》的结构及一些论述可以看出吕祖谦史学的一些特点,例如,他不像朱熹死抱着正统问题不放。吕祖谦在写《三国史详解》时,以曹操(155—220年)为正统,替魏国写纪,蜀汉的刘备(161—223年)和诸葛亮等人只有传。②这种务实的历史写作方式比较接近司马光,与朱熹的距离比较远。吕祖谦之后的浙东学者也倾向司马迁那种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但他们没有为吕祖谦继续完成《大事记》。
比较注意哲学问题是吕祖谦与同时的浙东学者不同的地方。浙东儒者一般较鲜论及性、命、心等题目,这些题目却是吕祖谦思想的重要部分。对于心的问题,吕祖谦注重孟子所讲的“本心”,追随孟子教人先寻回本心,因为它是一切学问和道德实践的基础。吕祖谦在孟子的“本心”的概念上,加上道学的“理”的概念:“凡人未尝无良知良能也。若能知所以养之,则此理自存,至于生生不穷矣。”③人若能存养此天理,则不需再向外寻求:“本不在外,自求而已”,所以“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④。反躬自省非常重要,因为外在的世界是人内心世界的反映:“近日思得内外相应,不差毫发。外有龃龉,即内有窒碍。只有‘反己’两字,更无别法也。”⑤吕祖谦对自省有强烈的信心,但告诫世人不要仰赖顿悟:“致知与求见不同。人能朝思于斯,夕于斯,一旦豁然有见,却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须是下集义工夫,涵养体察,平稳妥帖,释然心解,乃是。”⑥吕祖谦虽然在此似乎很重视内向的反省与直观的方法,但在他的思想体系里,格物的地位更加重要。这点明确显示在他对名物制度和历史研究的专心一致上;朱熹批评吕本中深染大慧禅的色彩,但很难如此批评吕祖谦。
吕祖谦也遵循孟子的观点主张性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中正仁义之体,而万物之一源也。中则无不正矣。”①他借用张载和二程的气禀论解释恶的存在:“性本善,但气质有偏,固才与性,亦流而偏耳。”②吕祖谦以此为基础,认为功夫修养的关键在于存养本心,使本心不被不正当的欲望干扰:“此心常操而存,则心宽体胖,怡愉安泰。福本自内有,若一欲败度纵败礼,则祸自外来。”③(按:“纵”疑当在“一”字前。)在存心和去除欲望方面,吕祖谦的功夫修养观与张栻和朱熹很相近,不过他不像张、朱那样深入讨论修养功夫各个阶段的细节。但我们在讨论“胡子知言疑义”时已经说过,在吕、张、朱三位学者中,吕祖谦最坚持功夫的涵养与体验要维持平衡,④日后朱熹却最以此著称。
吕祖谦与其他道学家认为仁是四德及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他在讲解《孟子》时曾经说:
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尽了。更说礼字,又可以知其等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与礼,更有甚事。⑤
礼在吕祖谦思想中有关键性的地位,认为礼不但是理,而且也是养心的必须之具。⑥他注重礼,而且认为仁与礼具有互相联系的关系,但仁仍无疑比礼更为根本:
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习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则礼乐虽未尝废于天下,而我无是理,则与礼乐判然二物耳。①
吕祖谦继承家族一贯注重忠孝的传统,但是他把忠孝及其他道德行为都归于仁的范围,而且是从仁而来:“孝、弟,所以为仁也。体爱亲敬长之心,存主而扩充之,仁其可知矣。”②显示他既与张栻都认为仁就是心,也与朱熹一样认为仁就是理。吕祖谦有些论点更能显示与张栻、朱熹的共通处,但他更接近朱熹。吕祖谦与张栻都认为仁就是孟子所说的“本心”:“仁是人之本心,浑然一体。”③而且仁的特点包括“公”和“一”:
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见至明。而此心不变,譬如镜之照物,惟其无私,而物之妍丑,自不能逃。虽千百遍照之,其妍丑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恶人,亦如是而已。④
他写信给朱熹时,又曾经以朱熹使用的比喻讲解仁与爱的关系:
盖爱者,仁之发;仁者,爱之理。体用未尝相离,而亦未尝相侵。所私窃虑者,此本讲论形容之语,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缘指出分明,学者便有容易领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原殆(始)不可不谨也。⑤
吕祖谦认为求仁的关键是“居敬”和“存诚”,一般湖南道学家所讲的“敬”近于“恭敬”,而吕祖谦所讲的“敬”则较近“严肃认真”的意思,他尤其注重专“一”和“诚”:
敬之一字,乃学者入道之门。敬也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大学》曰:“君之无所不用其极”,盖非特一事当然也,凡事皆若是而后可。①有人问:“诚、敬两字有异否?”他回答说:“只是一般。所谓存诚,存便是敬。”②所以吕祖谦对功夫修养问题的看法与程颐和朱熹见解一样,三位学者都强调“敬”。总而言之,他努力追求书本学问、治国与功夫修养三者间的均衡。
吕祖谦的学问广博,使他有时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他的许多看法和不同的儒家学者相近,而这些学者的学术各自发展,在日后变得互相矛盾。某些现代学者把吕祖谦说成没有高深理论成就的史学家,其实是不公平的论断。他的家学风格和个人性格都倾向于在异中求同,以寻求儒学同道的和谐统一。如果现代学者能像研究朱熹那样仔细研究吕祖谦的著作,我们或许能更清楚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和结构。现代学者尚未对吕祖谦做恰如其分的研究,或多或少也与他广博的学识和庞大的著作有关,使他比同时代的学者更难以为人了解。
吕祖谦比朱熹和张栻年轻,而且考上进士的年代也比较晚,但是从12世纪60年代晚期起,他就是道学的主要领袖,而且地位一直维持到1181年去世为止。吕祖谦的道德学问及政治社会地位吸引大量的学生,对道学的成长贡献良多。政府为科举阅卷能够公平,订定许多誊抄卷子和糊名的规则,防止主考认出考生的卷子。吕祖谦对个人文风极为敏感,能在担任主考时录取许多道学家,数目之多超过整个宋朝其他任何一次进士考试。政府和社会评论素来严厉制裁偏颇的主考,吕祖谦却敢公开说他认出陆九渊的考卷,而且没有因此受到制裁,1172年的进士考试证明他在政府和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朱熹在与张栻的交往论学中,到1173年已经渐渐取得支配的地位,但他从来不能够支配吕祖谦的思想。朱熹在道学同道中的影响力超越吕祖谦,是吕氏去世后的事情,假如多活20年的是吕祖谦而不是朱熹,吕祖谦的思想对宋代文化界和宋以后文化史的影响或许会大不相同,至少宋代的政治气氛必然会有所不同,因为吕祖谦比其他道学家更受朝廷官员尊敬。即使两人都活到1200年,朱熹的理论和行为也会甚受吕祖谦影响,因为从1163年起到吕祖谦1181年去世为止,两人一直相互影响甚巨。
第五章 朱熹与吕祖谦
朱熹和吕祖谦曾就社会、政治、教育和哲学等问题交换过许多意见,若能适切考查这些意见交流,对了解双方的互相影响应该颇有帮助。朱熹和吕祖谦的关系显示吕祖谦在1168年到1181年期间是道学最重要的领袖,朱熹在这时期对吕祖谦的温和态度,与日后对亡友的尖锐批评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态度的转变以及他与吕氏的朋友关系,显示了朱熹在吕祖谦去世前后与整个儒家群体的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吕祖谦大概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朱熹在1156年任职于同安县时,曾经因公事前往吕祖谦父亲任官的福州,得以认识吕祖谦,两人开始书信往来。在12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两人的书信往返激增。朱熹在1181年接到吕祖谦最后一封信不久后,获悉挚友去世的消息。他们的友谊维持得很久,比朱熹与张栻的关系还要长八年,这或许与吕祖谦的家在金华有关。金华距离京城临安很近,又在临安前往福建的路上,所以两人相处的机会自然比较多。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件尚存104封,比写给其他人的都多。吕祖谦写给朱熹的信则有67封流传下来,也比给其他人的信函多一倍有余。①双方信函交往频繁外,亲近的关系也可以从所讨论的事情中可见一斑,不但涉及政治学术的问题,也谈到许多家庭事务,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朱熹的长子朱塾(1153—1191年)的事。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说:“此儿懒惰之甚,在家读书,绝不成伦理。”①这个儿子虽然有些恶习,但朱熹担心自己由于父子关系而爱深责切,对孩子管教过严,因此采纳孟子“易子而教”的建议,委托吕祖谦负责儿子的教育和道德修养。1173年朱塾21岁的时候,朱熹把他送到吕祖谦那里,并且严格要求他在那里不许常常喝酒。吕祖谦安排他住在亲近的学生潘景宪(1137—1193年)家,规定他不能单独离家,每天都要和潘景宪一起面见吕祖谦,聆听教训。三四年后,吕祖谦促成朱、潘两家联姻。
朱塾迎娶潘景宪的长女(生于1161年),不久后吕祖谦把独女华年(生于1159年)嫁给潘景宪的近亲潘景良,所以吕祖谦和朱家都与婺州的大族潘家结为姻亲。朱塾在1180年回到朱家,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仍然失败落第。后来朱熹利用官荫的权利,使朱塾挂上朝廷礼官的头衔,但是这个儿子仍然不成大器,在官场上终无建树,1191年在婺州的岳家去世。朱熹把儿子交给吕祖谦管教,不只因为吕祖谦的社会名望和政治地位崇高,朱熹也信任他的学术水平和个人修养,希望能够改变儿子的脾气和行为。吕祖谦不但负责教育朱熹的长子,并且替他安排婚姻,的确帮了朱熹大忙。
吕祖谦也充当朱熹与许多儒生学者间的桥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陆九渊。吕祖谦在1172年提拔陆九渊通过进士考试后,就一直照顾他,并且为调解朱陆双方的思想分歧,在1175年春邀请他们到他家来会面,朱熹因故不能前来,吕祖谦就专程赶去看望。他从金华出发,行程约250公里,赶到朱熹在福建崇安的家,随后俩人一起去朱熹的寒泉精舍,在那里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完成《近思录》的初稿。他们又一起翻越武夷山,到达江西名胜鹅湖寺,会见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吕祖谦希望陆氏兄弟和朱熹能够建立友好的关系,居中协调他们对读书和功夫修养的看法。在从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鹅湖之会是朱陆学派分道扬镳的分水岭。吕祖谦的性格和居中协调的努力犹能暂时缓减道学内部的紧张关系。第九章会再谈到吕祖谦在鹅湖之会后的六年里,一直引导陆九渊兄弟,使他们比较能接受他与朱熹的共同观点。
一、社会政治问题
南宋的国家大事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对付占据北方的金人,吕祖谦一家和朱熹的父亲及其他道学人士一样,也直言不讳批评秦桧与他的和议政策。吕家家人甚至曾亲身参与朝廷变迁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尤其吕好问曾短暂做过兵部尚书,并陪同皇帝前往金营投降。金人将吕好问送回开封,命令他协助张邦昌的傀儡政权,但他竟然说服当权者扶立宋皇室唯一没有被俘的皇子。宋高宗在南方再建政权,曾经对吕好问说:“宗庙获全,卿之力也。”①随后任命吕好问为尚书右丞。然而吕好问曾经在北方傀儡政权任职,招致许多批评,因此随即转任不太重要的职位;吕好问的儿子吕本中也与秦桧不和而去职。吕本中虽然反对秦桧的和金政策,主张收复北方,但终究是个务实的人,认为金人的军事力量强大,所以建议高宗不要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应该巩固国力,保卫南方。②吕祖谦承袭吕本中的观点,主张要先改革朝政、加强国力,准备充足后才能发动攻势。他采取主和、主战两派间的温和中间路线,③可与张栻后来的成熟看法相提并论。
朱熹年轻时坚决主战,在12世纪60年代上书提倡军事反攻,严厉谴责所有的议和派人士;但中年以后,体认金人的军力强大,态度开始冷静下来,类似吕祖谦的务实观点,逐渐取代主战的立场。他虽然终生不忘收复失土,但晚年对主战派的抨击比对主和派的攻击还要强烈,而且开始体认到至少需要10—30年的准备,才能收复北方。朱熹在思想成熟后,更强调防守和自强的立场:
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①他60多岁的时候,可能变得比吕祖谦更重防守和谨慎,但吕祖谦的立场显然曾影响朱熹。
当时内政的主要问题是减轻农民的负担。1167年福建崇安县县令请求刘如愚(1142年进士)与朱熹支援赈灾,朱熹从邻近的建阳县调请救灾物资,他的朋友魏掞之(1116—1173年)早在12世纪50年代初期已在当地建立良好的社仓制度。州知府王淮(1127—1187年)在1168年建议刘如愚和朱熹保留百姓偿还的贷款,以供紧急不时之需。刘如愚与朱熹根据魏掞之的先例,建议设立社仓,获得州府拨给赞助费用。崇安的社仓在1171年建立完成,由刘如愚的亲戚负责掌管,但后代人把社仓主要归功于朱熹。②
政府的义仓主要是在灾荒时,以直接发放实物或稳定市价的办法帮助农民,但由于官僚作风作梗,官方义仓的效率很低,涵盖范围也只限于城镇附近,且常由村吏或佛教僧侣负责分发赈灾物资。朱熹反对佛教僧侣参与,努力动员儒生参加这类社会活动,相信参与社仓可以培养同道的认同感以及对仁的体认。朱熹进行这项工作时,正是宋代民间社会意识日益增长抬头的时候,例如,婺州的乡村已经自组互助制度,而有的组织成为社仓的基础。①
朱熹的社仓遭到某些人批评指责,认为他仿效王安石“青苗法”的借贷办法,连张栻也不免有此疑虑,吕祖谦则挺身为朱熹辩护。朱熹和王安石都使用政府的资金作基金,要求借款人偿还贷款、支付利息。②朱熹在1185年所写的“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中,反对别人将他与王安石的办法相提并论,指出他出借谷物,而不是出借现金,实施的方式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不是以县为单位,并且由当地士人管理,目的是稳定农民经济,不是增加政府的收入。朱熹再三提到吕祖谦巡视崇安后,称赞社仓能师法古人的美意,是受古人启发,与王安石的失败实验不同。吕祖谦并表示要在金华建立社仓,而朱熹这篇文章就是为潘景宪主持的金华社仓的成立启用而写作的,赞扬潘景宪实现老师的夙愿。③先前吕祖谦曾安排朱熹的儿子朱塾住在潘景宪家,并让他迎娶潘景宪的长女。朱熹在1182年办理赈灾事务时,也获得与吕祖谦有关系的婺州士人帮助。
孝宗皇帝虽然赞扬朱熹的社仓制度,并且要将它推行到全国各地,但由于反对者阻止政府的支持,最后成立的社仓很少。除朱熹家乡的社仓外,金华社仓可能持续得最久。不过到13世纪中叶,地方胥吏开始接管金华的社仓,只在荒年发放谷物,并且要求以现金偿还借贷的谷物,朱熹希望由儒家君子长年监督救济照顾农民的设想,从此变成地方官僚系统赈灾的另外一个工具。①朱熹倡导的社仓只短暂按照计划发挥作用,但已体现他政治理想的实践。魏掞之的社仓建立时间更早,刘如愚在“朱熹社仓”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及吕祖谦的襄助,使社仓传播到金华,都显示后人所谓的“朱子社仓”并不是朱熹一人的功劳,而是道学人士合作应付需要而进行的社会福利事业。从朱熹担任地方官时写的“劝立社仓榜”等文,以及他支持吕大钧(1030—1081年)的乡约,可以看出他非常关注建立地方社群组织,②乡约成为鼓励乡民行善的地方社会组织。
二、书院与教育
朱熹与吕祖谦关心许多地方小区建设的事务,但最关注文人知识分子群体的建立,而书院、精舍是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组织。吕祖谦在1166年母亲去世后,选择明招山母亲的墓地附近建立一座精舍,并且在当地教导后学。朱熹的母亲于1169年9月去世,他次年也在母亲墓地不远处建立寒泉精舍。吕祖谦返家后,以当时无比丰富的家庭藏书为基础,在金华城内成立丽泽书院;由于他的声望以及校址方便,当时有300多学生同时在此就学。
朱熹1179年在江西南康任职时,也营建一座书院。他写信给吕祖谦讨论兴建的计划,并要求吕祖谦为书院撰写铭文。朱熹表示任职期间,每四五天就要到官学一次。官方开办学校是为让学生准备应试科举,朱熹却很遗憾县内三所学校都是为准备科举而设置的。他在官学中讲解经典中的道德原理,并且明确地对官学的教学内容发表意见。①太学官员杨大发(1175年进士)大概对朱熹干涉学校很不满,向吕祖谦抱怨。吕祖谦得知朱、杨双方紧张关系后,写信给朱熹,提醒他不要干涉学校教师的做法。
朱熹在回信中为他在官学的行为辩解:
学中向来略为说《大学》,近已终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论语》,诸生说未到处略为发明,兼亦未尝辄升讲座、侵官渎告,如来教所虑也。②朱熹对外人的批评表示不满,声称自己只是想仿效汉代的文翁,做一点补益的工作。文翁的教化功德备受赞扬,后人认为他将孔孟之道传给四川百姓,例如杜甫(712—770年)曾说过:“文翁儒化成。”③朱熹表示南康地区佛教和道教寺院为数极多,所以他的行动尤其有必要。
朱熹又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以振兴儒家传统。④这座书院坐落在距南康城十几里的一个山谷,在十、十一两世纪盛极一时,宋太宗(976—997年在位)甚至曾经赐给书院一套儒家典籍。11世纪朝廷下令所有州和部分县建立官学,以培养科举人才。固然并非所有州县都能建立官学,但兴建的风气在11世纪中期达到高潮,12世纪初的头25年时间里,又再现一次高峰。北宋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官学,私学因此没落萧条,朱熹在1179年甚至得请樵夫帮忙,才找到白鹿洞书院的旧址。他上书朝廷要求资助重建这座书院,因为它象征儒家教育与文人价值,否则就只有任异教在山中林立。
这座书院获得朝廷同意后不到六个月就完成修建,并在1180年3月开放讲学,恰好是朱熹到任南康的第十二个月;努力一年就获得授权重建。白鹿洞书院除获得私人和朝廷的资助,地方政府也拨给田地作为学田,地方文人和皇室也捐赠书籍。它的重建与12世纪60年代岳麓书院的修复有相似之处,只是岳麓书院的重建被渲染得更多。孝宗时期(1162—1189年)重建或兴建很多书院,而宋代的私人书院总数至少有375个。①
以朝廷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而言,朱熹应该满意进展,事实却不然。他经常抱怨一些官员阻止计划,有人推测这位不知名的官员是杨大发,因为他不满朱熹干涉官学。不过杨大发是朱熹指派监督工程的两人之一,朱熹和他也有诗文往来,吕祖谦介入调解,必然缓和两人的紧张关系。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中至少有五封提到杨大发,还数度赞扬杨大发建庙纪念周敦颐以及六位当地的杰出人士。②建庙是朱熹计划中的重要的部分,希望以此增强当地百姓的儒家道德观念,并使地方儒生学士更能团结。如果杨大发阻挠计划,朱熹应该会在文章中否定杨大发,不会数度称赞他。杨大发虽然在15年后反对道学,但是白鹿洞的共事早已时过境迁,不应该根据后来紧张的环境衡量早期的关系。
一位美国汉学家的研究指出,朱熹有些言语显示,“别人抨击他重建书院的方式以及教学方法,使朱熹深感愤怒”①。可以使我们更了解朱熹的性格。或许因为他在此以前只担任过一项职务,而且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因此对书院的拖延和问题感到不耐烦,尤其政府的官学只在书院十来里外的地方,位置更加方便,他实在需要寻找理由使用政府资源,说服地方文人捐助修建一座新的书院。所以,朱熹在给朝廷的文书中,一再强调书院重要的历史及象征意义,却很少提及书院教学的活动;给朋友的书信则直率表达他对教育的使命感。道学人士普遍担心科举对士人文化的影响,但白鹿洞书院也花费近1/3的时间准备科举。除了朱熹自己的述说,并没有其他证据显示有人反对重建这座书院,所以朱熹的抱怨大概可以反映出他行事不老练,或者误解现实政策,与吕祖谦和张栻在政府任职的情况相比较,他这方面的不足更为明显。
朱熹强调建立制度,并且获得政府的资助,所以白鹿洞书院的地位比当时其他书院更为稳固。私人的努力与资金不足以建设书院,因此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成为朝廷和道学人士在13世纪关系改善以后合作的范例。朱熹为书院制定的行为规范为日后书院的发展开创先例,与官学的繁文缛节相较,朱熹希望造成学生承担更多责任的气氛。他把一篇训词贴在大门门楣上,要求学生学习古人的行为准则:
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②
朱熹希望学生能够修养道德,他警告说如果不然,就得接受官学里的规定。他的学生程端蒙在1187年制定一些细则,以补充朱熹的学规,不过朱熹觉得细则只能用于层次比较低的学生,①而白鹿洞书院的学生已经受过官学或私塾的纪律培养,是层次很高的学者。
朱熹陈述的规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结,并且成为这座书院的“学规”。这些规则都很简明扼要,除一条规则外其他都取自经典。首先规定最根本的基础,人际最基本的五伦关系,取自《孟子·滕文公上》,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具有这些品德的人才可以开始学习。其次,关于学习的次序,取自《中庸》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第三,关于功夫修养的关键,取自《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以及《易经》损益二卦象传:“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第四,引用董仲舒(公元前176—前104年)的话:“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世态度的准则。第五,谈到与人相处之道,引用《论语·卫灵公》上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孟子·离娄上》中的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②所以从第三段到第五段都是解释学习的要点,因为“学”主要是对道德原理的自我修养。
朱熹的学规不仅要有别于官学的繁琐规定,也要在佛教戒律外树立新的途径。朱熹不喜欢佛教,但他和其他儒生学士大都很欣赏禅宗的戒律。此外,朱熹的学规谈到互相鼓励道德修养,和吕大钧的乡约有相似之处。
朱熹更直接的灵感应该是吕祖谦的书院学规。吕祖谦在1167年写下他的书院规范,并在1170年前修改两次,所以这些条文比朱熹的学规早将近12年。强调在儒家生活规范中体认道德修养,是这两种学规最基本的相似处。吕祖谦在1168年立下学生需要遵守的基本常规:“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他除将这些重要的儒家道德列作人际关系的准则外,还阐释入书院学习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①如果书院学生违反上述条文,同学会加以劝诫,如果不能起作用,同学就要开会讨论他犯的过错。如果仍然不改过向善,书院就要将他除名。吕祖谦的规则与12年后的朱熹学规一样,都希望能够引导学生自我修养,鼓励学生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似乎都简单地将道德行为与学问视为一事,因此有人或许会认为他们将学问化约成道德伦理的领域,朱熹学规的倾向尤其明显。他们表面似乎将道德修养当做学问的主要内容,但不应该简单地认为他们的学问最终的目的仅是实践道德行为,这解释过于简单,会贬低他们更广泛的课程以及实践的目的。整体观察他们的思想和文章,显示他们对学问和儒家传统的看法其实包含其他的内容。
吕祖谦与朱熹后期的学规不同,他特别详细规定学生的行为细节。有些条文规定学生间相处,要根据年龄大小称呼对方,不能谄媚或贬抑别人,也要遵守预习和讨论的规定。例如,学生得记录课堂上或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当做小组讨论的依据,还必须在笔记上签字显示哪些问题已经讨论过。
吕祖谦认为,使学生具有群体意识十分重要,可以使学生“勿狎非类”。所谓“非类”的意思并不太清楚,但是吕祖谦似乎努力减少学生遭受来自团体外的影响。吕祖谦虽然比较开明,可是排外倾向如此明显,显示道学同道有与别的团体划清界限的普遍倾向。他们与书院外的乡绅来往十分谨慎,尽量避免联系与冲突。例如,吕祖谦规定学生不许向官员送礼或关说,告诫学生要讲地方政府和官吏的好处,不可议论他们的是非。学生与其他社会人物接触时,不能与酗酒、赌博、打架或阅读不正经书籍的人交往,而且必须与家庭保持密切的联系。吕祖谦严格要求学生和父母同住,遵守正确的丧葬礼节,避免为钱财与宗族争执。其他方面还包括在课堂上要严肃认真,学习必须勤奋。学生在一年内不能有100天以上的时间不在书院,每年至少要拜访以往的师长一次。如果在路上遇到老师,要行特殊的礼节表示敬意。①这些规定的目的是维系书院的团结。
朱熹的学规比较注重基本原则,而吕祖谦的学规则比较强调行为规范;朱熹强调理论,吕祖谦侧重实践。如果指责朱熹的学规缺乏实践的意义,倒也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他强调遵守孝道。然而,他们所强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确实有明显的区别,朱熹的规范简约,且多取自经典;吕祖谦的学规详细周到,起头是总论,继以个别条文。朱熹的条文更为精致、系统,从道德修养的最基本的德目开始,结尾以三段话阐释学问的要务。两人目的都是组织学生,以研习经典及基本人伦关系的方式,学习儒家学说的真理;所以绾合儒家的团体是他们共同的主要目的之一。朱熹简练的学规名声日起,其他书院也相继采用,这份学规与吕祖谦早年学规的相似之处,再次显示吕祖谦在朱熹的贡献中发挥过作用。
吕祖谦应朱熹的要求而写作“白鹿洞书院记”,文中说重建书院的目的众所周知,朱熹对这份题记做大量评注,并将最后定稿刻在书院石碑上。他们提到重建书院的三个目的是要面对三项挑战:佛、道二教的竞争、改进教育制度以及弘扬儒学。吕祖谦讲他们都批评王安石新法中教育制度的弊病,反对学校太注重科举文章的习作,而倾向程颢的做法,以书院培养学生,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和道德教育。根据吕祖谦的想法,这座书院会精研二程和张载的学说。②
三、重建道学传统
朱熹在1173年编辑《伊洛渊源录》时,更进一步强调二程以及他们最亲密的友人、学生是一支鲜明的儒学传统。这本书没有全面讨论11世纪复兴儒学的学者,只褒扬强调“道”的人。朱熹追随程颐的说法,认为致力于道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儒者,研究文学和经学的学者则不然,所以他略过11世纪中叶对儒学复兴持比较宽广观念的学者,以传记和师承谱系追溯他所认为的道学流派渊源,指出这些先贤的贡献是延续道统,绍述古代圣人。朱熹在开头几章集中讨论开创道学的主要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他虽然用“伊洛”当做书名,而且二程素来被视为道学传统的源泉,但这里强调周敦颐的开山功劳,的确饶富意义。
邓广铭(1907—1998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周敦颐其实没有学生,在北宋时期也没有被视作重要的思想家,南宋的道学家才将他变成道学传统中重要的人物,朱熹尤其如此。朱熹夸大周敦颐的地位,甚至引起道学内部不同的意见。汪应辰两次写信给朱熹,表示怀疑二程是周敦颐学生的说法,推测二程顶多年轻时曾经受周敦颐影响,但《伊洛渊源录》却断定周敦颐和二程有明确的师生关系。朱熹答复汪应辰,只简单解释他的说法来自吕大临(1044—1093年)记录在《二程语录》里的一条。朱熹承认汪应辰的质疑有道理,但没有修改《伊洛渊源录》的说法,仅引用吕大临的话为证据。邓广铭先生指出,朱熹避开汪应辰的合理的挑战,却以有问题的材料改写道学的历史。①
朱熹虽然是把周敦颐扶上道学宗师位子的主要人物,其实有些道学家已经为此奠立基础。本书在第一部已经提到,朱震早在1134年就说二程的学识甚受周敦颐的影响,湖湘学派也一直同时强调周敦颐和二程,胡宏和张栻都认为二程延袭周敦颐的一些思想。张栻除曾引用周敦颐的思想,至少写过六篇文章赞扬周敦颐。①陆九渊虽然不承认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见第九章),但也相信周敦颐曾经教导二程。汪应辰反对周敦颐与二程有师生关系的说法,其实不是涉及二程地位的唯一敏感问题,例如,杨时就不承认二程曾经追随过张载,而且贬抑张载:“横渠之学,其源出自程氏。”②吕祖谦一意结合张载与二程的思想,但对周敦颐并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从朱熹回答吕祖谦关于《伊洛渊源录》的问题来看,朱熹将周敦颐当做早期道学关键人物,吕祖谦并无异议。③吕氏一家对周敦颐遗留的学说也没有敌意,吕希哲、吕本中虽然曾经判断二程曾向周敦颐学习,但认为他们后来超越周敦颐。④因此,强调二程地位的学者不必然贬低周敦颐的地位。总而言之,我们不宜夸大道学人士反对周敦颐的情形。
朱熹也强调二程的贡献比较大。朱熹虽然引用程颐的“明道先生行状”为依据,表示二程的确曾经追随周敦颐,但更侧重二程的贡献。根据程颐这篇行状的说法,程颢得到周敦颐直接传授,但没有寻得学问的根本,所以自己苦心钻研近十年之久;程颐认为周敦颐的学问还不足以指导程颢这般天赋异禀的人。程颢回顾《六经》后,才获得思想的突破,发现古代圣人的道理。程颐形容他的兄长:
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①
程颐显然认为程颢超越周敦颐,朱熹也含蓄接受这个说法,后来更明确赞扬二程复兴儒家之道。朱熹作《中庸章注》序时,指出二程与道的传承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说而得其心也。②
这段文字与程颐的“明道先生行状”和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似乎互有抵触,因为朱熹在书中指出周敦颐重新发现道,并将道传给二程;这项表面的矛盾显示:现代的研究可能太高估朱熹对周敦颐的推崇。③
朱熹在1193年所写的“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提供另一个角度,可以观察朱熹如何评价周敦颐和二程。朱熹虽然强调周敦颐的独特角色,但认为二程的贡献更大:“〔周〕先生之学实得孔、孟不传之绪,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④周敦颐因为传道而受赞扬,但朱熹将发扬道的功劳归于二程。
就《伊洛渊源录》的篇幅而言,北宋五子的轻重排列依次是: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最后才是周敦颐。朱熹也很重视二程的其他同道,尤其是胡宏及吕祖谦的先人吕希哲、胡安国;这两个例子都显示朱熹给二程的篇幅比周敦颐多。
朱熹编辑《伊洛渊源录》赞美书中的人物,有力发扬一支研究道的独特儒学传统。全书近五章半的篇幅是谈论二程的主要学生,而其他20个较不重要的学生只在一章中简单带过。朱熹用巧妙的方式以二程为中心建立传统,并且用“伊洛”标榜二程的学派,结合四位儒学宗师与34位门徒,展现11世纪后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几代道学发展。朱熹在1173年对道学范围的界定比晚年的见解宽广,但是比起同时代的学者已经狭隘许多,《诸儒鸣道集》就是很好的例子。
朱熹重新界定道学的范围,其实隐然要回应及取代《诸儒鸣道集》的看法。这部书是由张九成的学生在12世纪60年代编辑的,选取的人物顺序与朱熹不甚相同: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然后才是二程;所以司马光传道的地位仅次于周敦颐,而且司马光和张载被列在周敦颐和二程中间。周敦颐的地位在此不成问题,显示南宋初期不少道学人士认为周敦颐属于道学的一员,而且拥有特殊的地位;所以朱熹将周敦颐包括在内,并不算拓宽道学的传统。《诸儒鸣道集》虽然包括邵雍,但并未将他置于“北宋五子”的崇高地位,也没包括胡宏,但这部最早的道学选集还是显示道学初期较广阔的背景,因为它不集中于二程,而且较少谈论抽象的哲学问题。这本书还包括其他儒家学者,最有名的要属张九成,但朱熹将他排除在外,认为他受到佛教的影响太深。《诸儒鸣道集》反映道学初期视野广阔的另一证据:保存一些别处不见的著作。例如,刘安世的《元城语录》、江公望(北宋末期)的《性说》、刘子翚(1101—1147年)的《圣传论》以及潘植(12世纪初)的《忘荃集》最完整版本。①潘植和刘子翚对佛教很有好感;江公望说有些儒生为性下定义时,不够重视人情的作用;潘植反对将道与物理分离。张九成不喜欢抽象的哲学,也明显表现在寓道于实践的思想,而《诸儒鸣道集》处处显示这种倾向。例如,它收入周敦颐的《通书》,而“太极图说”就未在书中出现。总而言之,这部选集呈现的道学,上溯几代到二程以及元祐党人中的同道,尤其是司马光和刘安世,包括日后选集所删去的人物,描述的范围比流传的朱熹版本要宽广 许多。
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被元代的《宋史》编者当做撰写“道学列传”和“儒林列传”的基本资料;18世纪《四库全书》的编者回顾说,以道学来划分儒家学者,始于朱熹1173年完成的《伊洛渊源录》。①朱熹以前虽然就 有人界定道学的范围,但《伊洛渊源录》是重建或重新定义这支学术传统 的重要一步。
朱熹和吕祖谦为弘扬道学,合作编辑一部哲学的入门选集《近思录》。吕祖谦在1175年拜访朱熹时,共同完成大部分的编辑工作,随后一直联络讨论某些章节,直到1178年オ定稿。《近思录》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不同,只包括北宋四子:周敦颐、二程与张载,传承的顺序依旧是从周敦颐到二程,再到张载,邵雍被排除在外。朱熹在别的著作里引用邵雍的宇宙论和自然观,但认为邵雍不应该包括在道学的主流里,因为他有宿命论的思想,而且不够重视个人修养和道德。②全书最强调二程,其次是张载。全书总共622条,二程占80%的篇幅,张载占18%,周敦颐占的比例不到2%,而取自“太极图说”的只有一条。③从《近思录》的编排数目以及《伊洛渊源录》的篇目,可看出周敦颐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 因此,对朱子哲学的传统认识恐怕得修正,应该更注意张载,而不是周敦颐,虽然强调张载可能要归因于吕祖谦。
自从南宋末以来,朱熹的后学将他当做《近思录》的唯一作者,但钱穆与陈荣捷等现代学者注意到吕祖谦的协助与贡献。①吕祖谦的观点影响这本书的内容,由于他的坚持,朱熹保留一条论法制的条文,又删除几处抨击科举的文字。吕祖谦在一些特别的段落使朱熹放弃原来的目标。朱熹重视抽象的哲学,但却是吕祖谦劝他将讨论抽象哲学的“道体”当做全书的第一卷。吕祖谦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删除程颢的“仁论”,而收录程颐的《易传》许多言论。朱熹质疑程颐注解《易经》的方法,原本希望《近思录》不要引用任何段落,但结果全书有106处文字出自程颐的《易传》,竟然占总篇幅的17%,仅次于朱熹编辑的《二程遗书》。朱熹在多年后解释说,他对吕祖谦让步是因为吕祖谦建议的段落很能解释日用生活中的功夫修养。②可是朱熹为什么不满程颐的《易传》呢?
四、哲学的问题
宋代解释《易经》主要有两个派别,程颐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以道德伦理的角度解释《易经》,而不是从象数占卜的角度看待它。程颐追随王弼(226—249年),将“大传”附会在每一个六十四卦经文后,但把重点放在“大传”,而不在卦爻经文,也不用邵雍、周敦颐偏重卦爻象数的方法,而将“大传”的道德原理应用到功夫修养。③朱熹的方法又与程颐不同,不采取王弼以来将“大传”附会于每一个六十四卦经文的本子,而采用吕祖谦编辑的《东莱吕氏古易》,并曾为该文撰写跋文。吕祖谦以司马 光的学生晁说之(1059-1129年)的说法为基础,致力恢复上古经文的原貌,将“大传”与六十四卦分开。朱熹借用吕祖谦的易经古文,特别注意卦象(包括卦辞和爻辞),而不是程颐所使用的后出传文。朱熹认为孔子撰写“十翼”(大传)的传统说法可信,但孔子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延袭伏羲发明八卦的原意。朱熹将他采信的上古经文与“大传”的哲学诠释分开,力图改正程颐对《易经》作过度的哲学诠释。程颐很少讨论卦象结构,而谈论卦辞跟爻辞的暗示的内在普遍原理。朱熹的做法与程颐相反,他借用邵雍和周敦颐的象数见解,从讨论卦爻的结构位置开始,强调有关的卦象神谕。朱熹认为程颐只强调传文中所提示的特定普遍原 理,而忽视卦象神谕在不同情况下的意义。①
朱熹相信《易经》的本意只是占卜之书,不像其他经典具有强烈的道德教育意义。朱熹没有取消《易经》的占卜功能,其实是鼓励同时的文人把它当做功夫修养的工具。他在1176年给吕祖谦的一封信中说:
故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凶吉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②
卦爻所提示的具体行为指示,取决于占卜当时的情况背景,唯有圣人能知道如何在任何情况正确行动,因为他们了解万物几微的力量,能够因势利导。除少数的圣人外,每个人都有时需要占卜的指示,以探究自然的道理,成就人事、解决疑难。如果能够正确使用《易经》占卜预测未来,内心必然诚敬无私,了解人、天、地为一体。不过占卜不必用于道德原则十分清楚的情况,唯有极尽人事之后,才用占卜解决疑难、指示行动。朱熹在1195年就用占卜决定是否上书反对压制道学,当时他的学生畏惧朝廷的迫害,希望劝止朱熹上书,卜筮呈现不要上书的卦象后,朱熹采纳建议,焚毁上书。①
吕祖谦对占卜的看法与朱熹不同。《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中对士人谈到占卜,认为占卜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的形象是人心的表露:
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龟即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变,乃吾心之变。……妄者见其妄,僭者见其僭,妖者见其妖,皆心之所自发见耳。②
朱熹虽然要士人自己占卜,但不支持以占卜为生的人,吕祖谦则进一步谈到巫妖,生动表达他对占卜的态度。吕祖谦与程颐都反对占卜,即使他未追随程颐采用王弼的《易经》版本。上述引文也明确表达他的看法,认为占卜只能告诉我们内心已经认识的事物。
吕祖谦在别的著作中更清楚指出:心决定占卜的结果。《增修东莱书说》中说:
未占之先,自断于心,而后命于元龟。我志既先定矣,以次而谋之人,谋之鬼,谋之卜筮。圣人占卜,非泛然无主于中,委占卜以为定论矣。①
吕祖谦是位历史学家,经典提到占卜的时候,他必须承认古人“谋之幽明”,但认为古人问卜,不过是为对事物的看法多求个观点而已。吕祖谦认为圣人占卜,但圣人不看重占卜。他也不鼓励士人将占卜当做自我修养的手段,认为占卜不足多论,因为占卜的结果已经先在心中决定了。
吕祖谦进一步澄清心与天地奥妙的关系,认为古代圣人之心是“天心”。前面也提到,张九成与胡宏用“天心”形容古圣人之心,相信人的德性与“天心”相连,吕祖谦的用法与他们很相近。“天心”只在经典中的《尚书》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汉代的古文派经学家加进去的伪经,但吕祖谦讲授《尚书》时,至少引用“天心”十次以上,形容上古商周时代开国君主和大臣的心意。②这两代的圣王据说与德合一,可以上接天心,下得民心。他们得到天心,承受天命治理国家。天心无私,所以这些圣王之心也是纯然无私的。
吕祖谦谈到更早的圣人时,认为天心与圣人之心合一是普遍的原理:“圣人之心,即天之心。圣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舜禅让君位给禹时,天的“历数”已经在禹。圣人之心就是天心,因为“此心、此理,盖纯乎天也”③。
吕祖谦认为“天命之谓性”(《中庸》)外,天也赋予人之心,所以有人问心、性应该如何区别,他回答:“心犹帝,性犹天。本然者谓之性,主宰者谓之心。”④暗示不只圣人的心与天合一,心与天的联系也是普遍的;吕祖谦说:“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①进一步区别天心与视任何人事为外物的心,②并根据同样的想法,将心与道的相等关系普遍化:“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③因为道就是理,所以又回到吕祖谦天理合一的看法。
吕祖谦视理和天为一,又将理与天命相连:“命者,正理也。禀于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谓命也。”④人不可能逃避天的规范,夏代的君主不再推行德政,不遵从天的规范,天“遂降之以灾”,所以“天理感应之速反复手间耳”,而且“非汤放桀,乃天也。以此深见,伐夏非汤之本意,实迫于天命之不得已耳”⑤。所以吕祖谦结合两种观念:新的哲学意义的“理”,以及古代经典里会惩罚不道德君主的“天”。理或道德提供天与人之间的联系:“一理流通,天与圣人本无间。”⑥就此而言,天经由天理治理人民,但这说法与吕祖谦一向主张的“命由心定”的说法有明显的差异,矛盾只有在先预设心终究与天及理合一的情况下才可能消解,但也仅能解决部分的矛盾。一旦追问伦理学的难题时,这个矛盾差别就更明显:为什么人会丧失道德,无法认识心与天理是一体的呢?
吕祖谦引用《尚书·大禹谟》中舜的十六字传心诀,讨论这项伦理学难题的关键。这段话成为道学论心的重点,原文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吕祖谦解释说:
人心,私心也,私则胶胶扰扰,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难见也。此乃心之定体,一则不杂,精则不差,此又下工夫处。既有他定体,又知所用工,然后能允执其中也。⑦
根据吕祖谦的解释,这段话既主张孟子的性善说,也肯定必须每日律己修养才能达到善的境界。人有道心仍然不足以为善,因为成为善人还需要认真严肃的修养。
吕祖谦为确定弥补这伦理学的问题,转向《易经》寻求解释。他在解释“复”卦时,将自我修养与孟子的心性本善的理论结合:
夫复自大言之,则天地阴阳消长,有必复之理;自小言之,则人之一心善端发现,虽穷凶极恶之人,此善端亦未尝不复。才复,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体之爻观之。初九,一阳潜伏于五阴之下,虽五阴积累在上,而一阳即动,便觉五阴已自有消散披靡气象。人有千过万恶,丛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复,则虽有千过万恶,亦便觉有消散披靡气象。……学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复,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发处,亦人心固有之理。……人虽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终不可泯没,便是天行无闲之理。①
天刚健不息的运行以及他对“复”卦的解释,不但加强吕祖谦对孟子性善理论的信念,也使他对个人能够实现自我道德转化更有信心。吕祖谦的分析虽然与程颐对《易经》的哲学诠释比较接近,但他和朱熹都分析卦爻的结构变化,并将得到的教训运用到自我向善转化的努力中。
吕祖谦和朱熹对《易经》看法的相似处,从朱熹对“复”卦的评注中显示得很清楚。《周易本义》中指出,人可以从“复”卦中看到天地之心的运作:
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②
朱熹接着引用邵雍的诗,谈论天心在冬至时,处于寂然不动的状态,似乎全然不存在,一旦又受阳气催动,便能再化生万物。朱熹在此引用程颐和邵雍的诗文讨论爻辞,显然他一方面批评早先道学的易学传统,但也从中吸收不少解释;而且他与吕祖谦都从观察天与四季往复运行的过程,肯定人的本然善心能够回归自身,提供改邪归正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为确定善性,心安理得地引用邵雍谈论“天心”的诗。朱熹与吕祖谦都认为“天心”就是“君子之心”,朱熹说:“盖君子心大则是天心,心小则文王之翼翼,皆为好也。”①并引用荀子的话:“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②朱熹谈论天是有意识的主宰时,所谓“天”一直遵循道及理;总而言之,天就是理。理虽然是朱熹理论体系的中心观念,但理本身不直接控制万物的运行,由于需要一股制约的力量,他在几处视天为主宰,至少说过一次“天心”就是理的主宰,因为“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摄是理者,即其心也。”③朱熹在这些段落里谈到圣人尽其心,所以能够知天、知性、与万物合为一体时,圣人之心与“天心”合而为一。学者在讨论朱熹对人可以向善的信念根据时,大多提及人性与天地之性为一体。④不过,将天心与圣人之心或君子之心结合起来,无疑又给朱熹提供另外的根据。
以心而论,朱熹以两个观念表达人可以为善的信念。第一,《易经》的复卦显示,人心与天地之心合一,因为人也具有使万物生长的仁德。其次,朱熹以帝舜的十六字传心诀为基础,发展“人心”与“道心”区别的主要理论,提出道德修养的要务。由于人心很不稳定,而道心是绝对的至善,所以必须将"人心”转化为与天理合一的"道心”;①胡宏对道心的解释更明白而简练:"道心与天无二”,且说"仁,天也。”②
"道心”与"天心”的相似之处显示,两者都是用以确认人可以为善的隐喻。人的意识可以使自我作自私的抉择,而导致自利与罪恶的行为。朱熹否定自私的思虑算计是"天心”,因为天心一直与道一致;同样的道理,君子扩充心,其心就能与天合一、与道一致;换句话说,就成为天心。道心就是人具有的本心,若能够存养此本然的心,它就会引导人走上道德的路径;所以"天心”、"道心”都是与道德合一,自私的思虑则与天心、道心背道而驰。朱熹虽然从来没有清楚说明"道心”与"天心”其实是相同的概念,但两者的相似之处足以明确将它们联结在一起。朱熹未明确指出其间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天心”有时指圣王之心,甚至当朝皇帝之心,以当时的背景,要将"天心”普遍化成为心处于至善的观念模式,比普通化"道心”困难;然而,这两个形容心自然与道德规范一致的概念,仍然为自我修为能够克服私欲,达到与正道和谐的信念,提供额外的支持。传统的儒家学者认为宇宙的自然规律内涵道德的意义,所以朱熹将人心与天及道联结,加强人具有努力向善的潜能的信心基础。
朱熹和吕祖谦都要在儒家学者间建立一个致力于道的群体,他们的个人风格不同,也影响道学内部以及道学与外人的关系;吕祖谦逝世后的时期,这点显示得更明白。
吕祖谦来自当时最有名望的士大夫家族,不仅提倡拥护家礼及传统,而且维护私人家族的利益。南宋的望族一般与当地其他望族联姻, 所以也专注地方的事务;但有些新近移民的家族的做法有异,仍然流行与外地的家族联姻。①吕祖谦的情况与北宋的联姻模式比较一致,他第一任妻子是韩元吉的女儿,韩家是开封的望族,北方沦陷后移居福建。这位妻子在婚后七年去世,吕祖谦又娶她的妹妹为妻。他再度成为鳏夫后,迎娶著名的太学博士芮烨的女儿,而芮烨来自湖州。吕祖谦的女儿嫁入金华当地的望族,但这似乎是安排朱熹的儿子与同一家族联姻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显示他对朱熹格外宽厚与亲近。许多北方大族逃离女真人征服的北方后,无法保持既有的地位与传统,但吕家在这方面非常成功,至少到吕祖谦这代依然如此。
吕祖谦与北宋时代的先人都比较注重全国的政治,比较不特别关心地方的事务。他具有丰富的历史制度知识,并且明了当代的政治现实,因此朝廷讨论政治制度时,他是各方尊敬的权威。浙东其他的学者与陈亮一样,只注重全国与家族内的事务,吕祖谦则没有忽视中间层次的小区组织。例如,他为朱熹的社仓计划辩护,而且计划在金华建立类似的社仓;此外他通过在朝任官的朋友,协助朱熹建立他的第一座社仓与书院。
吕祖谦比较注重全国的事务,朱熹则活跃于中层的小区组织。朱熹在国家控制地方的权力削弱,而地方家族势力抬头的局势下,提倡一系列的组织加强中层的小区意识与团结。朱熹在社区组织的礼仪规范下,特别注重乡约、先贤祠、书院及社仓。他的社区制度的构想大多来自别人,但能将不同的办法融合,以达到整合儒学群体的目的。吕祖谦与朱熹都致力于加强道学家的意识和凝聚力,他们的重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关心三个层次的事务,而且努力合作,互相支持,以强化国力及道学。
吕祖谦对朱熹的理论和实践有明显的影响。以书院而论,吕祖谦比朱熹早几年建立精舍与书院,而且吕祖谦是一名非常成功的老师,也必然引起朱熹注意,而吕祖谦为学生制定的学规是12年后朱熹学规的蓝本。白鹿洞书院筹建的过程中,吕祖谦经常提供建议,朱熹并且将吕祖谦为书院重建完成而写的题记刻在书院石碑上。他们讨论胡宏的《知言》时,吕祖谦提醒朱熹要兼重精神修养的两种方法,而朱熹后来以此著称于世。朱熹与张栻处理“仁说”问题时,经常写信给吕祖谦讨论这个题目。在经学研究方面,朱熹以哲学诠释《易经》的基本文献框架是吕祖谦重编的《易经》,吕祖谦对《诗经》经文与“毛诗序”的看法,成为朱熹诠释该书的重要根据。《近思录》的内容及编排也证明吕祖谦介入颇深,这项合作计划如何进行,清楚记录在他们的书信与朱熹对学生的谈话里,但大部分日后的学者忽略、甚至贬抑吕祖谦对这部书的贡献。朱熹或许要为后学门人的偏见负担部分责任;吕祖谦去世后,朱熹总是避免强调故人的贡献,本书后面还会讨论,他批判浙东的功利学派,也连带影响他对吕祖谦的评价。
吕祖谦在各种讨论中,证明他能够讨论三个层次的问题。他虽然劝朱熹在《近思录》第一卷讨论“道体”,但大体而言,他不像朱熹那么注意抽象的思辨哲学。朱熹与吕祖谦讨论的思辨哲学问题,的确不如他与张栻讨论的多。吕祖谦理论色彩虽然不如朱熹强烈,但现代学者也不应继续忽视他著作中的理论成分。他们讨论《易经》时使用的“天心”一词,可以提供另一观点考查他们如何追求修养的确立,而他们对于心与修养的看法也显示他们对占卜的看法。吕祖谦的体系强调心,甚于注重理;朱熹的体系则较以理为中心。吕祖谦调解学说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平衡太过强调心或理的观念,而由于他企图达到两者的和谐与平衡,他的思想具有兼容并蓄的色彩;这种印象使现代学者不能认真严肃地研究他的著作。
一般也认为吕祖谦对朱熹研究的中心议题如心、性、理所言甚少,他的专长是历史研究,而朱熹的特长是经典。朱熹和吕祖谦的学术重点的确不同,但这种比较的结论容易忽视吕祖谦对道德、哲学及经学的见解;其实他对这些领域的学术和教育都有贡献。
若将吕祖谦学术的重点置于实际问题与历史研究,他真正的重点容易被误解。吕祖谦的社会活动、学术研究与历史著作虽然很著名,但仍然秉持如下信念:
静多于动,践履多于发用,涵养多于讲说,读经多于读史。工夫如此,然后能可久可大。①
这段话显示吕祖谦的基本重点与朱熹相似。吕祖谦的历史著作充满心、性、理的讨论,包含许多经典记载的圣人言行,而且他对三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也是用以加强道德修养,这些都颇值得注意。对吕祖谦而言,经典与历史著作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因为经典都是上古时代的历史材料,《诗经》、《尚书》与《春秋》尤其如此。
现代学者比较朱熹和吕祖谦时,大多隐然接受朱熹的判断。朱熹同意学生的评语:“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他也说:“伯恭之弊尽在于巧。”②从他们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可以厘清朱熹所谓的“巧”。第一,朱熹说《尚书》很难解读,吕祖谦回答说没有事情不能解释清楚,但几年后吕祖谦承认朱熹对《尚书》的几处疑问是正确的。他们对这部经典的解释仍然不同,朱熹抱怨吕祖谦有时勉强解释《尚书》中无法解释的部分。其次,朱熹虽然欣赏吕祖谦对《诗经》一些解释,也赞同他将经文与序分开处理,但觉得他的解释有时太过取巧。第三,朱熹承认《左传》包含经典未触及的道理,但质疑何必花费许多时间追寻《左传》包括的琐碎细微的道理。他也承认吕祖谦对《左传》的解释极博学详细,但又批评他有时望文生义。第四,朱熹极力抨击苏洵、苏轼和苏辙以佛、道二教的学说污染儒学,吕祖谦却认为他们的偏差不应招致如此强烈的抨击;朱熹因此写信给张栻,抱怨吕祖谦一番:
渠又为留意科举文学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坏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苏学为非,左遮右拦,阳挤阴助,此尤使人不满意。①
张栻回答说,吕祖谦虽然“于苏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来见渠亦非助苏氏,但习熟元祐间一等长厚之论,未肯诵言排之耳。”②
朱熹和张栻虽然大张旗鼓声讨苏轼,吕祖谦仍然很尊敬苏轼的作品。南宋一般的道学家对苏轼与古文的兴趣降低,吕祖谦却例外。他继承家学的传统,甚至推崇江西诗人。③他只在受人请托或应酬时,才会写作纯文学的作品,但也的确写过许多各种文体的文章。他评论文章的范例时,常教人学习欧阳修和苏轼的作品,《宋文鉴》就是力求文与理的统一。当代学者刘昭仁先生曾经指出,吕祖谦不赞成将学术分成追随程颐的“道”的学说与推崇苏轼文学的两派。④吕祖谦调和苏轼与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反映他要加强儒学的团结,并且全面保存儒学的传统。
朱熹虽然从吕祖谦的调和受益良多,但有时严厉批评吕祖谦调和分歧、寻求妥协的倾向;他曾经说:
伯恭讲论甚好,但每事要鹘囵说作一块,又生怕人说异端俗学之非,护苏氏尤力。以为争较是非,不如敛藏持养。⑤
吕祖谦方面则认为朱熹过于强硬,不够宽容和厚道。⑥
朱熹也承认他们的性情不同,他赞扬吕祖谦:“天资温厚,故其论平恕委屈之意多。”而自己的性格是“质失之暴悍,故凡所论皆有奋发直前之气”。而这缺点比吕祖谦退让的性格更糟糕,“熹之发足以自挠而伤物”①。
朱熹和吕祖谦的性格虽然不同,但他对吕祖谦的感情和尊重是真诚的。吕祖谦去世时,朱熹表达最深沉的情感。吕祖谦去世的消息到达后,他在家中洒酒设奠,并且送去祭文。他的“祭吕伯恭著作文”大部分是赞扬吕祖谦温和谦恭、不轻易批评别人、文采出众、兼采百家风格,入朝出仕,树立道德的榜样。
最重要的是,朱熹谈到吕祖谦的去世对道学的意义。朱熹赞扬吕祖谦的道学,并且感叹“吾道”的衰落,以及吕祖谦去世对“吾党”的影响。吕祖谦虽然以前用过“吾党”的字眼,但朱熹也使用这词指称道学,则颇令人意外。在12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使用这字眼,显示道学同道已经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团结而且独特的团体。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表示反对结党以后,”党”一直有极端反面的政治及道德的含意。北宋的政治家一般对它有比较好的看法,不过即使欧阳修写“朋党论”为君子结党辩护,仍然没有去除它的负面意涵。②反对道学的人士已经警告朝廷这个团体像党派般运作,朱熹在“祭吕伯恭著作文”开头几句话意味深长:
呜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张〕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斯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则病将孰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号天而恸哭耶?③
朱熹在这篇祭文里清楚指出,张栻和吕祖谦是他所属团体的领袖,而且他们以道的学说贡献儒家的文化。朱熹在此大胆提出道学的政治、社会、文化的主张。由于祭文的体裁,朱熹将自己置于亡友之下,但含蓄表示要实现道学团体的目标。
朱熹反问“道学将谁使之振?”表示他会努力接过亡友领导道学的责任。张栻与吕祖谦去世后,朱熹宣称今后无人能够提醒纠正他的错误,既然已经没有人足以匡正他的错误,他又自谦说“若我之愚”,似乎暗示身边的人都不如自己。
朱熹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呢?吕祖谦提醒朱熹有“伤急不容耐处”,朱熹在1175年也承认有这种倾向。①张栻在一封信中,以元晦称呼朱熹,提出惊人的告诫:
又虑元晦学行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见他人不是,觉已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辩论之劲,排辟之严。纵有所疑,不敢以请。深恐谀言多而拂论少,万一有于所偏处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②
既然朱熹在吕祖谦的祭文中明确表示他要挺身负起领导道学的责任,并且说没有人可以纠正他的错误,道学下一阶段的发展使张栻的批评不幸言中。张栻与吕祖谦去世后,朱熹在没有如此亲密的同侪友人的环境下,继续发展道学的哲学理论以及组织道学的同道。朱熹在随后思想气氛比较冲突对立的年代里,对吕祖谦的态度比对故人生前还要严厉。
比较第一与第二时期进士的来源,或许能显示政府与道学间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详细具体的量化当然不容易,我想选择在12世纪90年代被“庆元党案”列为“伪学”(道学)的人士,以及攻击道学的人士加以说明。这份所谓的“伪学”名单虽然是由攻击迫害道学的人士所罗列的,它还颇有几分道理,因为名单上的人在学术和政治方面的联系,远超过他们在官场上互相举荐与援引的关系。攻击道学的人士的联系没有如此密切,但是都曾上书批评道学,或做过攻击道学的事情。这批人只是因为反对道学而被列入名单,所以很难判断他们究竟属于哪个士大夫团体。目前所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详细比较名单上的道学人士与反对道学人士,以及他们所属的团体人数;就名单的性质而言,被列入的道学人士显然比较多。近代学者素来认为这些人攻击道学的动机无非是出于个人好恶、嫉妒,甚至有盲目的反智倾向;不过我觉得这犹待商榷,他们或许别有反对的理由。就目前不完整的资料来看,两个名单没有显示年龄、地位、官阶或地理分布的重大差异,而且两派在上述特征上的分布面都很广,很难根据这些特征讨论两个团体的不同。59名道学人士被列入“伪学”的名单,攻击道学的名单上则有35名。根据我们现有的一些资料,可以考查到他们哪年得到的进士学位。59名道学人士中有36人的进士学位可考,而35名反道学的人士中有21人可考。①
现有数据虽然有以上的限制,有些数字仍然能显示部分的趋势。“伪学”名单中的五位(相当于总数的14%)道学人士,在第一个时期(1127—1162年)得到学位。这五个人当中有两个最为突出,即朱熹和周必大(1126—1204年),不过他们当时都还很年轻,朱熹只有18岁,周必大是26岁,与道学尚未有密切的关系。在36个获得进士学位的道学人士中,有86%的人在第二个时期(1163—1181年)中举。在21个反对道学的人士中,有43%的人在第一时期考中进士,57%的人在第二个时期获得学位。从1172年开始的十年,吕祖谦和尤袤(1127—1194年)担任科举主考官,情形显得更为突出。在分等考卷时,吕祖谦因父丧必须回金华,但其友尤袤按照他们的愿望,完成试事。这一年中举的道学人士比任何一年都要多,而只有一位后来的道学人士在当年通过进士考试。在“伪学”名单上,19%的人在1172年获得进士。吕祖谦的努力以及意识型态的偏好不仅表现在统计数字上,在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朝廷明文禁止考场徇私,并设下种种防范措施使考官无法认出考生的试卷,但吕祖谦还是认出陆九渊的考卷,虽然以前他只读过几篇陆九渊的短文,至于认出同乡友人陈傅良(1137—1203年)的考卷就更不在话下。吕祖谦当时的地位和声望非常崇高,敢公开说他认出陆九渊的考卷,而且1172年中举人数的数字没有包括陆九渊这么著名的案例,因为他比较早去世,没有赶上编制“伪学”名单的时间。总而言之,在1172年到1182年的十年间,上述的道学人士中有44%的人获得进士学位,而21位反道学的人士中只有一人获得进士学位,仅占5%。与第一个时期相比,第二个时期道学人士获得进士学位的人数和比例都大幅增加,攻击道学的宿儒则相形减少。
由于当时的气氛对道学日益有利,赵彦中(1169年进士)在1180年上书,对科举注重讨论人性、天理以及二程之学的影响表示不满。①赵彦中参加1169年的考试,通过科举的道学人士和反道学人士人数相当,但1169年是两派中举人数相当的最后一年。赵彦中这类人不仅不满某次考试不公,而且意识到考生与考官形成特殊的关系,会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长期合作,所以考试与政治派系有直接的关系。
1161年金人的入侵激发南宋人士对儒家价值观的进一步认同,使他们更热心教育年轻人以振兴价值观。高宗时期抗金失利,孝宗时期的相对成功显然增加士人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危机以及后来的和平给文士以捍卫传统更坚强的信心,利用和平的环境发展传统。政治环境相对缓和,知识分子可以花更多的精力从事学术研究与辩论。
1162年高宗退位,孝宗继任,其实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张九成、胡宏和胡寅已经去世,李侗(李延平,1093—1163年)不久也谢世。到1163年,南宋头十年出生的第一代学人开始成熟,并成为这时期儒学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最有名的是朱熹、陆九龄(1132—1180年)、张栻和吕祖谦。除朱熹外,这些知名的学者都在1180年或1181年前后相继过世,更年轻的学者虽然在1181年前已经开始活跃,但朱熹、张适与吕祖谦仍然主导这段时期的道学,被称作“东南三贤”。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大致相同,而且1163年南宋最有希望收复北方的时候,三位学者都在京师临安,颇有几分象征的意义。他们在平日交往和书信往返中,建立日益深厚的友谊,这些思想交流促从朱熹的思想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与前一个时期有显著不同。朱熹的生平思想已有非常详尽的研究,所以这里只简单谈论他的生平大略。朱熹的童年是在高宗时代的混乱和动荡中渡过的,其父朱松(1097—1143年)因反对和金政策被贬谪到福建。朱熹出生后不久,朱松的县尉的职务也被革除。朱松是杨时的学生,他培养朱熹对二程之学与司马光历史著作的兴趣。他过世前将儿子的教育委托给邻近三位研究程学的学者,胡宏的大侄子胡宪(1082—1162年)是其中一位。胡宪并没有把胡氏家学对佛教和道家思想的强烈敌意带进对朱熹的教育中,他对张九成所表达的一些佛教思想抱持很宽容的态度。另一位老师刘子翚(1101—1147年)的文章只保存在《诸儒鸣道集》中。朱熹这时非常喜爱大慧宗杲的禅宗学说,并且师事大慧的弟子道谦,可能是由于他的学习环境使然,而亲师的亡故也促使他寻求精神的慰藉,他的父亲和两个兄弟在他的少年时代相继去世,负责教育他的三位先生中的两位也很快过世。这些不幸的变故不仅使他更迷恋佛学与道家思想,而且让他感受生者的强烈使命感。朱熹经历了这些人事的重大变化,且没有一位固定而且影响深远的老师,所以比其他儒生更能独立思考。
朱熹的命运在1148年考取进士后开始变化。虽然位在五甲,名列九十,但他比大多数中第的人要年轻一半以上,所以很早就可以不必再为科举考试浪费许多时间,并得以迅速进入仕途。1153年他被任命为福建同安县主簿,并且在任达四年之久。在职期间他改进地方税收、整顿治安、提高教育水平以及制定礼仪规范。这个职务使他了解官场的实务,随后他被授予“岳庙督查”的闲职,有几年悠闲读书和思考的时间。
朱熹的思想到12世纪50年代末开始发生变化。从1153年开始,他数次拜访李侗。李侗是杨时的学生,朱熹的父亲曾极力赞扬他是二程学术的传人。朱熹最初在探讨程学时,还兴致勃勃地谈论道家和佛教,李侗批评他研究这些异教,要他把精力集中在程学的研究上。宋代佛教在福建地区的影响很大,所以当地许多学人喜欢综合儒佛的学说教义,朱熹少年时期的三个老师就是如此;另外有些人则热衷建立儒学的正统权威,例如李侗、胡宏和朱震等人。朱熹在1159年编辑第一部著述《上蔡语录》,删去许多谢良佐批评老师二程助长佛学的言辞。其实在二程的第一代学生中,谢良佐可能是最倾向佛学的人,但是《上蔡语录》显示朱熹向程学迈进一步,逐渐接受李侗完全认同程学的观点。
到12世纪60年代,朱熹与李侗一样敌视佛道二教。他1166年撰写“杂学辨”,抨击融合儒学与佛道学说的学风,批评苏轼对《易经》、苏辙对《老子》、张九成对《中庸》以及吕本中对《大学》的注解。友人何镐(叔京,1128—1175年)为他写题跋,明确说明他的用意。朱熹认为苏氏兄弟、张九成及吕本中将儒家经典与老子、庄子、佛祖的思想混为一谈,后来的学人因为这些文人享有盛名而接受他们的看法,异端邪说因此日渐发展猖狂。何镐在跋文里说朱熹“大惧吾道之不明也,弗顾流俗之讥议,尝即其书,破其疵缪,针其膏肓,使读者晓然知异端为非,而圣言之为正也。”①
朱熹摘要引用张九成对《中庸》的注解后,指出张九成的观点与经典或二程的看法不同,并且批评张九成强调内在发展,却迷失方向,甚至走上异端的路子,不重视思考和经典诠释。而且朱熹认为张九成把仁解释成知觉,以及他对本心的主观理解,都是禅宗顿悟思想的反映。朱熹认为张九成不过是披着儒家外衣的禅僧,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不过说张九成受到禅宗不少的影响,那倒是不假。朱熹的“杂学辨”显示他已经与年轻时代的儒佛合一的思想告别,并开始清理那些他所认为的儒家内部异说。
朱熹在1163年所完成的《论语要义》以及在第二个时期的其他著作,都显示他的发展方向日渐成熟。到1163年前,他虽然收录很多以前和当代学人对《论语》的注解,但已经奉二程的《论语》注解为圭臬。1168年编辑《二程遗书》完成时,他指出程氏兄弟复兴了古代圣人的绝学。1172年他在《论孟精义》中进一步用二程门人的著作解释二程的经典解释。1177年他完成《论孟集注或问》,书中驳斥许多程学门人的观点,同年完成的另一部著述《周易本义》,更显示他的独立与成熟;他不像程颐将《周易》解释成关于理的哲学著作,而强调它的占卜本义。朱熹在编选或诠释各家学说的过程中,显示他从道学的学徒走向道学权威的自信与成熟。
要从朱熹所在的背景中了解朱熹,就得探索其他儒家学者的思想以及他们与朱熹的交往。在1163到1181年这段时期,如果我们将张栻、吕祖谦与朱熹放到当时的历史地位上来考查,就不会像以往的研究那样过于集中在朱熹的身上。从秦桧的高压政策下解脱出来以后,道学学者有更多的时间发展他们的思想,自由地吸引更多的学生。吕祖谦努力保护这个群体,使它不受外来压力的影响,他的领导地位——与以前和以后时期相比——鼓励各种观点的交流以及道学群体的相对多元化。
即使有这种相对的多元化倾向,紧张依然存在。由于12世纪60年代政治环境的变化,因为元祐遗事而引起的政治争执日益消退,思想的因素和学术渊源在划分集团时有日益重要的影响。张栻、朱熹以及吕祖谦都试图使道学更纯正,而为摆脱杂学的影响,尤其是佛教的影响,他们培植出更强烈的独特道学群体意识。政治压力的相对宽松,不仅提供道学群体发展的环境,而且也使道学人士开始专注界定这个传统内的成员与学说内容。
第二章 张栻
张栻或许是12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道学家,朱熹赞扬他说:“敬夫道学之懿,为世醇儒。”①张栻的父亲张浚在朝廷里享有盛名,张栻自己则天资聪颖,在老师胡宏去世后,成为湖湘学派的领袖。张栻以胡氏家学为基础,使湖湘学派的哲学完全发展成熟,但是1180年张栻去世后,湖湘学派也随之衰落。不过在12世纪70年代,张栻在教学方面的影响已经不如吕祖谦,而理论研究也不如朱熹。张栻被官修的《宋史》列入道学传,并受到现代东亚学者的注意,但仍被欧美学者忽视。②
张栻在1163年应诏入京,为父亲张浚的复出作准备时,初次见到朱熹。张浚的主战计划虽然在高宗时期没有成功,但是在重新考虑对金作战时,他又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张栻从幼年起就曾跟随父亲离开四川老家,转赴各地任职,因此继承乃父“慨然以奋伐仇虏,克复神州为己任”的壮志。①在紧张军事局势下,张栻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张浚不幸在1164年去世,张栻不得不暂时去职守孝。
张栻以直言著称,孝宗曾经抱怨“伏节死义之臣”难得,张栻答道:“〔忠臣〕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若平时不能犯颜敢谏,他日何望其伏节死义?”②孝宗曾问他“天”的问题,张栻回答说,天与苍天的意义不同,天指上帝,亦即最高“主宰”的古老代称。因为上帝与君主最为接近,孝宗应该使他的想法与上帝一致,否则“上帝震怒”③。由于宋朝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张栻激励孝宗放弃和谈,努力自强以收复北方失土。孝宗曾问他可否乘金人连年灾荒的机会北伐,张栻指出宋朝自身的弱点,认为关键不在于宋金双方物资的暂时状况,而在于宋朝有没有改善朝政的运作,以及加强战备的长远计划;没有赢得民心是不可能收复中原的,而赢得民心的方法在于“不尽其力,不伤其财”④。
这种传统儒家重视民生的思想也表现在张栻的政绩中。在北方沦陷的危机之际,张栻合于儒家理想的表现出类拔萃,朱熹因此称赞说:“小大之臣奋不顾身以任其责者盖无几人;而其承家之孝,许国之忠,判决之明,计虑之审,又未有如公者。”⑤张栻除在京师担任侍讲,并在吏部和中书省任职外,也曾在地方任职十多年,管理地方广达四州。他每次上任都频频察访百姓疾苦,并且进行改革和救济以减轻百姓的负担;传统传记虽然通常会提到称誉政绩的客套话,但他的确是个好地方官。⑥他也极重视地方学校和教育,为达到复兴教育和启发人民的目的,他为各种学校、书院写作至少54篇题记。他的题记赋予教育事业维护儒家道德的特殊使命,他说:“人伦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废,废则国随之。然则有国者之于学,其可一日而忽哉。”①
张栻认为在当时不友善的文化环境下,必须特别强调儒家的道德教育。那些追求佛、道异端的人虽然不好,但他们其实只是反映出违背道德的时代风气而已。有些学者文士认为儒学不切实际,逐利之心甚至使一些讲经的老成学者也常追求私人目的,专攻理论的儒家学者则更糟糕:
近世一种学者之弊,渺茫臆度,更无讲学之功。其意见只则类异端“一超径诣”之说,又出异端之下,非惟自误,亦且误人,不可不察也。②
总而言之,他叹息懂得儒学真义并且能够履行实践的人太少,所以必须将“吾儒”和各种异端之学的追随者区分开。③他在给朱熹、吕祖谦的信中经常提到当代精神的堕落腐化。不论这些看法有多夸张,它仍然激起保卫儒家传统和教育社会的热情。
张栻从幼年起的教育就围绕着二程的思想体系展开。他从小接受父亲庭训,张浚曾经追随二程的学生,也曾从游于与二程敌对的四川苏氏兄弟的传人,此外,他还与继承王安石传统的改革派交往,所以他并不能完全赞成道学家对传统的一切宣言。张浚自己的思想背景虽然复杂,并且和四川老家关系密切,他仍然让张栻学习胡氏的二程之学,而不选择苏氏兄弟的学说。④张浚弃官以后似乎更加认同他的道学朋友,思想的隔阂也比以前少。张栻起初只能以通信和读书的方式向胡宏学习,在1161年初次面见胡宏时,竟然感极而泣。胡宏看出这位青年的诚恳和潜力,开始向他讲授“仁”的道理。张栻回来后仔细思索,并给胡宏写一封论仁的信,胡宏读信后叹道:“圣门有人,幸甚幸甚!”①
张栻后来写作一篇论仁的长文,题名为“希颜录”。在《论语·雍也》中,孔子称赞爱徒颜回好学,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希颜录”收集几世纪以来儒家学者对颜回仁德的评语,并把颜回当成功夫修养的模范。胡宏告诫张栻说,这么重要的文章不容稍有错误,而且考虑几百年来不同的观点时,必须在众多的历史材料中“于未精当中求精当”。胡宏称赞张栻的考据功力,并且说:“先贤之言,去取大是难事。”②胡宏其实是在鼓励张栻以自己的判断取择传统。胡宏在他们第二次会面后不久就去世,张栻得到他的著作认真研读。
张栻的“希颜录”在他思想发展过程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将“希颜录”当做衡量个人修养进境的标准,朱熹说:
〔张栻〕作“希颜录”一篇,蚤夜观省以自警策,所造既深远矣,而犹未敢自以为足,则又取友四方,益务求其学之所未至。盖玩索讲评践行体验反复不置者十有余年。③
张栻加入道学群体后,思想日益成熟,“希颜录”完成14年后,在1173年出版,张栻为此撰写一篇跋文。④
张栻在1173年还撰写《祭巳论语解》和《孟子说》,用流畅的古文论述《论语》和《孟子》的要旨。他比同时的道学人士少使用宋代的哲学词汇,他以胡宏为程颐的《易传》所作的注释为基础,强调《易经》的经世和政治道德的指导意义,而《经世纪年》则反映丰富的实务经验,《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则表现出胡氏家学传统中以历史服务道德的精神,他称赞三国时代的诸葛亮为“儒将”,是弃利求义的典范。①
张栻著作的流传有些问题。他讨论仁的长文和他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都曾与朋友(尤其是朱熹)往复讨论而修改多次。1173年所完成的几部著作是他思想的分水岭,显示他自认对传统的看法已趋成熟。朱熹在1184年编辑张栻的遗稿,完成《南轩集》并为它写序,删除了“希颜录”等早期的文章。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朱熹删除“希颜录”等论仁的文章及张栻给他的部分信件后,如何使我们研究张栻的思想以及朱、张两人的交流时备受限制。朱熹自己说“希颜录”对张栻每天的修养功夫十分重要,却决定删除这篇文章,确实令人感到惊讶惋惜。经过朱熹的编辑,加上张栻在1173年以前不断修改自己文章,我们很难根据现有的材料研究张栻思想的进化和发展。现存的材料表现出他与朱熹观点明显相似的特色,但是他们的思想其实并不如此一致,在1173年以前尤其显然。②对研究12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间张栻所领导的湖湘学派,这些问题无疑是重大的障碍,也使后人难以再现道学原有的多样特性。
张栻不断研究“仁”的意义,使他沉浸在儒家的文献里。在《论语》的“颜渊”篇中,孔子说:“克己复礼”;在“八佾”篇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孟子以仁为“仁义礼智”的四德之一;二程则以仁为四德的总和,而且仁与万物为一体;张栻则在“仁说”中阐述仁之体用的关系。由于“仁说”明确表达张栻所认为的儒家基本价值,我们把这篇完成于1172年或1173年的文章几乎全部抄录于此:
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理,则智也。是四者,虽未形见,而其理固根于此,则体实具于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谓爱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发见于情,则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而所谓恻隐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为不仁,甚至于为忮为忍,岂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即克,则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爱之理无所蔽,则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其用亦无不周矣。故指爱以名仁,则迷其体。〔程子所谓“爱是情,仁是性”《二程遗书》卷十八谓此。〕而爱之理,则仁也。指公以为仁,则失其真。〔程子所谓“仁道难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为仁”《二程遗书》卷三谓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静而仁义礼智之礼具,动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达。其名义位置,固不容相夺伦,然而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恭让有节,是礼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知觉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见其兼能而贯通者矣。是以孟子于仁,统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犹在《易》乾坤四德,而统言“乾元”“坤元”也。然则学者其可不求仁为要,而为仁其可不以克己为道乎?①
张栻虽然在这里没有区分二程的思想,其实这篇文章中“程子”的话全部是程颐所讲的。“公”的含意很复杂,包括公德心、公正不偏袒等许多意思。张栻的著作中,“公”是就克己、克除私欲的层面而言,所以比较具有公正、不偏袒的意思;但是就以他对公事的责任心来说,“公”自然也包括“公德心”的意思。我们在谈陈亮时会讨论到,在某些宋儒的心目中,所谓“公”更具有“公益”的意义。
张栻在“仁说”中采用程颐“仁”为“爱之理”的说法,反对韩愈(768—824年)认为“仁”就是“爱”的说法。仁是“爱之理”、“性之德”,不是“情”。张栻以此区别为基础,援引二程的观点,认为爱是情感,仁却是人的本性。张栻将仁视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力量,也是受到二程认为“仁”是生命的种子与万物的基础的影响。“仁说”以孟子所主张的仁即是人心的学说为基础,与程颢一样坚信“识仁”最重要。我们会在第三章中讨论张栻与朱熹的理论,它们虽然都建立在孟子与二程学说的基础上,但双方对“仁说”仍有不同意见。
张栻对仁一再精思独解,使他渐渐偏离老师胡宏性无善恶的理论;如果仁与人性不可分割,那么性怎么可能不是善的呢?张栻比胡宏更强调孟子人性本善的观点,他在《孟子说》中写道:“夫善者,性也。”①并且遵从孟子的说法,认为性善是因为性具有四德之端:
孟子所以道性善者,盖性难言也。其渊源纯粹可得而名言者,善而已。所谓善者,盖以其仁义礼知之所存,由是而发,无人欲之私乱之,则无非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矣。②
孟子认为“四端”是本然的善性,而从“四端”发展出来的“四德”则是本性的表现,所以孟子认为“四端”比“四德”更为基本。张栻却把次序颠倒过来,认为“四德”是性,“四端”是心:
仁、义、礼、知具于性,而其端绪之著见,则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故原其未发,则仁之体立而义、礼、知即是而存焉。循其既发,则恻隐之心形,而其羞恶、辞让、是非亦由是而著焉。③
张栻用“未发”和“已发”区分四德和四端,并根据胡宏的性是静态时的体、心是性动态时的用,提出性是静的、未发的,心是动的、已发的;可见他对四德四端的看法与孟子不同,因为他接受胡宏区分心性的理论。张栻一定知道自己与孟子有些微差异,但他或许觉得更能巩固孟子学说的基础。儒家在面临佛教挑战它的道德、伦理权威时,需要一个比孟子学说更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宋代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也在破坏传统家庭、社会关系,可能也促使张栻比孟子更强调传统家庭、社会关系所依赖的“四德”;他认为这些传统关系极其重要:
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为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夫妇之别,而又有君臣之义、朋友之信也。是五者天所命而非人之所能为。(①张栻坚信儒家的基本家庭社会伦常是人民生活和国家的生存的根本。人性论既然一直是支撑保卫儒家伦理的重要传统据点,所以他努力巩固人性论的基础,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栻以“四德”就是“天命之性”,进一步提供性善的根据。《中庸》说:“天命之谓性。”张栻据此推论性源于天命。所以人与生俱来的“天命之性”是至善无恶的。②张栻把性说成是“天命”之性,强调性是绝对至善,又认为人应该顺着人性的“本然”去体会性善。张栻把善比喻作顺从,说善是“循其性之本然而发见者也。有以乱之而非顺之,谓之则为不善矣。”③并以《孟子·告子上》中以水喻性的话来论证他的观点。孟子说:“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存之,可使在山。”外在的干扰消失后,水就会顺着自然之势往下流。张栻把这道理运用于人性论,推理说:“故夫无所为而然者,性情之正,乃所谓善也。若有以使之则为不善。”④许多儒家学者素来对为追求短暂成效而“有以使之”的行为抱怀疑态度,张栻认为“无所为而然”就是义、理,“有以使之”就是私利与人欲,更加强这种倾向。
张栻借用二程“气禀”的概念解释恶的起源问题。程颢曾经评论告子“生之谓性”的话(见《孟子·告子上》):
“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性也。①张栻以此作基础,解释为什么会有不善:
盖有是身,则形得以拘之,气得以汩之,欲得以诱之,而情始乱。情乱则失其性之正,是以为不善也。而岂性之罪哉?②
张栻既然认为恶是从气禀来,那么程颢所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的“性”只是指气禀而言。
张栻又借用《礼记》进一步解释性的善恶。《礼记》说人生而静,而且有“性之欲”和“人之欲”的分别。张栻以胡宏主张的性静但“不能不动”的观点为基础,指出“性之欲”就是性对外物的反应,这种反应无穷无尽时,人的好恶没有节制,行为也容易变成不善,但不善并不是“性之理”,而是“一己之私”所造成的。张栻进一步说明这个区别:“譬诸水,泓然而澄者,其本然也;其水不能不流也,流亦其性也;至于因其流激,汩于泥沙,则其浊也,岂其性哉?”③
恶既然是从气禀来的,就可以用人性原有的善来克服。张栻主张回归本原以变化气禀,是从张载的“变化气质”的理论发展来的。张栻运用“气质之性”的观念解释孔子在《论语·季氏》中区分“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三种人,坚持这些区别只是就学问的起点而言:“困而学虽在二者之下,然其至则一者,以夫人性本善故耳。”①生而知之者的知识,别人以“困而学之”也能得到。从根本上说,下愚者和圣人有同样的基础,也就是说他们的本性都是至善的,所以都能够以修养获得进步,甚至成为尧舜般的圣人,这种理论或许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宋代的经济、城市和教育的发展使社会阶层流动到达空前的地步。不过张栻变化气质的理论主要是就道德伦理而发的:“人所禀之质虽有不同,然无有善恶之类一定而不可变者,盖均是人也。”②张栻虽然认为人都可以改变气质,但他的理论却也为善恶绝对区分提供基础。
张栻的绝对性善论影响他对义、利的区分。孟子和其他早期儒家虽然已经开始区分“义”、“利”,二程进一步将它们决然对立。张栻以二程的理论为基础,把义利之分说成儒学修养的第一步功夫,而且认为义利之分就是天理、人欲之分;在这方面他取法程颐而非胡宏:“夫善者,天理之公孳孳为善者,存乎此而不舍也。至于利则一己之利而已,盖其处心积虑惟以便利于己也。”③要人认真研究重义君子和趋利小人之间的区别。
张栻用是否“有所为而然”来区分义利,使义利之辨更加决绝。他认为不应该为实现自己欲望而采取“有所为而然”的行动:
盖圣学无所为而然也。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义利之分也。自未尝省察者言之,终日之间鲜不为利矣。非特名位货殖而后为利也。斯须之顷,意之所向,一涉于有所为,虽有浅深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则一而已。④“无所为而然”指性被思虑困扰并付诸行动前的状态,就是义和天理;“为利”指性被成心和欲望干扰且行动后的状态。张栻认为趋利并不只限于传统儒家经常批评的对名位和财富的追求,将“利”的范围扩大;在张栻的定义下,禁止趋利的戒律延伸到生活的各种领域,并且适用于社会各阶层。
张栻认为不“有所为而然”就是遵循道、守“道”不移,循“道”的人可富也可贫,应该“安于命”,不做有违于“道”的事:
惟君子则审其在己,不为欲恶所迁,故枉道而可得富贵,己则守其义而不处;在己者正矣,不幸而得贫贱,己则安于命而不去。此其所以无入而不自得也。①
循道和灭欲都需要修身自律。有人会说只要遵从自己的良知就已经足够,因为良心感到羞耻的事就是“私欲”,心里不觉得压抑负担的事就是礼。张栻认为这种说法太主观:“苟工夫未到,而但认己意为则,且将以私为非私,而谓非礼为礼,不亦误乎?”②必须做格物的修养功夫,以加强对“理”的认识,方能避免这种主观的偏见。不过“格物”也可能被误解为主观直觉的功夫修养,大慧宗呆就鼓励他的儒家朋友做这种纯粹内向的“格物”功夫。张栻想要反击禅宗的影响:
理不遗乎物,至极其理,所以致其知也。今乃云“物格则纯乎我”,是欲格去乎物,而己独立,此非异端之见而何!且物果可格乎?如其说,是反镜而索照也。③
如果“格物”完全依赖于“格物”的人,会造成物我的隔离,形成不正常的作用关系,有如用镜子的背面照自己一样。
张栻试图兼顾内外,同时讲究外在的“格物”和内在的“居敬”,希望能够维持两者的平衡。他讲解《大学》说:“自诚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无非格物致知事也。”①有时候又把“格物”和“居敬”的次序倒过来说:“格物有道,其惟为敬乎”。②张栻解释程颐主张的“居敬”:“致知所以明是心也。敬者所以持是心而勿失也。故〔程子〕曰:‘主一之谓敬。’又曰:‘无适之谓一。’”③学者必须懂得“一”的意义,才知道功夫从何处着手。张栻虽然很重视“格物”,其实“格物”时,“敬”的态度也非常重要;他或许认为“敬”比“格物”重要,至少他在谈论“敬”时更富有活力:“居敬则专而不杂,序而不乱,常而不迫,其所行自简也。”④“简”意指人心不受欲望诱惑,行为就不会被外物干扰。“简”也和他所反对的“有所为而然”有关,张栻在“主一箴”中进一步解释“一”:
曷为其敬?妙在主一。曷为其一?惟以无适。居无越思,事靡它及。涵泳于中,匪忘匪亟。斯须造次,是保是积。既久而精,乃会于极。勉哉勿倦,圣贤可则。⑤
换句话说,张栻继承了湖湘学派养心、正心的修身传统。
张栻谈论仁、性、修身时常说到“理”,是否也专注于“理”的玄想思辨呢?他在《孟子说》中说理在物先:“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⑥有时也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解释万物的生成:“太极动而二气形,二气形而万物化生,人与物俱本乎此者也。”⑦又把宋代哲学词汇和传统的“天”与“天命”的概念结合起来讲存在的基础:
天命之全体,流行无间,贯乎古今,通乎万物者也。众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尝有间断。圣人尽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立则俱立,达则俱达。盖公天下之理,非有我之得私,此仁之道所以为大,而命之理所以为微。若释氏之见,则以为万化皆吾心所造,皆自吾心生者,是昧夫太极本然之全体,而反为自利自私,天命不流通也。故其所谓心者,是亦人心而已,而非识道心者也。①
张栻的目的显然是在批驳佛教信徒,因为他们破坏儒家伦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他认为佛教徒被一己私利蒙蔽,所以只能了解人心,而无法懂得道或心中的道德原理。
张栻这里的理论一如在讲修养时强调心的作用与地位。他认为心和性的本体就是天:“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②心是主宰内在之性和外在事物的无限力量:“心也者,贯万事、统万理,而为万物之主宰者也。”③朱熹主张“心统性情”,但是心必须遵从理的规范,虽然也讲心是主宰,能够实现理,但不肯让心控制理本身。就此而言,朱熹赋予的心的主宰功能没有张栻所主张的那么广大绝对,因为湖湘学派很明确地将心看做理的主宰。这种程度的差异根源于胡宏的思想,而张栻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传统。
张栻虽然也对“理”做抽象的哲学讨论,但他和胡宏都比较喜欢讨论道德修养和文化价值的问题。他一方面有将心、性、天、理等同起来的倾向,所以不像朱熹将这些概念做细致的区分;在另外一方面,他注重心的修养,也对儒家的功夫修养传统有很大的贡献。这两个方面虽然优劣互现,其实相辅相成。张栻反对空谈心性,因为湖湘学派的精神修养一向重视自我反省和日常功夫,他批评当时的儒生学者不能领略周敦颐和二程“穷理居敬”的实践精义。④连黄宗羲(1610—1695年)也说:“第南轩早知持养是本,省察所以成其持养,故力省而功倍。朱子缺却平日一段涵养工夫,至晚年而后悟也。”①
张栻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他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天理。在日用中发现天理是二程的中心思想之一,但程颐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教训常常被道学人士忽视。朱熹称赞张栻用天理、人欲的概念做义利之分,能够“扩前圣之所未发”。②
张栻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发扬胡宏的湖湘学派思想。张栻不但继承胡宏对于历史、经世实践、心性关系的思想,而且使湖湘学派更牢固地扎根于孟子和二程学术的传统中。张栻也追随胡宏,继承程颢对心、性和仁问题的看法,所以陆九渊说:“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③张栻一生多次返回长沙岳麓书院讲学,由于他是知名的学者和官员,许多学生前往听讲。追随他学术的后学也不少,不过他死后却没有人能够真正继承衣钵。
湖湘学派为什么会衰落呢?传统的解释是湖湘学派的思想和教学都被朱熹的成就超越掩盖,但似乎还有其他的因素。宋代的湖南比浙江和福建落后许多,所以胡宏和张栻是在文化和经济较不发达的地方努力耕耘,客观条件与吕祖谦所在的浙江和朱熹所在的福建有不少差距。这种客观条件的差异限制了湖湘学派与其他派别的竞争能力。以吕祖谦为例,他的书院地处文化中心地带,又能吸引京城的士人,就拥有许多优势;岳麓书院缺乏这种优势,在张栻身后很快就衰落下来,一直等到1193年朱熹在湖南担任地方官时,才重新恢复旧观。④张栻1180年去世后,岳麓书院如此迅速衰落,似乎暗示它可能在1180年以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岳麓书院迅速变成朱熹学术的一个中心,张栻的弟子似乎有难以为继的问题。
湖湘学派衰落的部分原因也在于张栻的思想成分复杂。他的思想涉及层面广大,比南宋的第一代道学家宽广;他把实践置于理论之上,又强调心的修养与格物穷理。他思想里实践、修心、格物等几条线索在12世纪最后的20年里,都各自发展成独立的道学流派。张栻去世后,学生门人转到其他师门派别下,而这些派别将张栻留下的几条线索发展得更系统、更谨密。湖湘学派或许由于特别重视佛教的挑战,不像朱熹那么热衷区分儒家内部的派别。例如,胡宏的儿子胡大时是张栻的高徒,张栻去世后,他先后追随道学的三个主要流派。由于下一代道学家将张栻思想中的主要线索都做更深的发展,后人很少想要特别研究张栻,应该也是湖湘学派没落的原因。朱熹思想的发展也是使湖湘学派衰落的原因,因为12世纪70年代中期,朱熹的理论成就已使张栻黯然失色。下一章将要讨论朱熹与张栻的关系,以及他们互相砥砺切磋的各种问题。
第三章 朱熹与张栻
南宋道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朱熹的道学思想发展主要表现在他与张栻间气氛和谐的学术讨论中。朱熹认为张栻做人明快,与学者讨论问题时,能够迅速了解各种观念,并且将它们形诸文字。朱熹也宣称自己需要勤奋治学,而张栻却能闻道“甚早甚易”。朱熹比张栻年长三岁,但承认“敬夫见识,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①朱熹的学派声势大盛以后,学者一般都强调朱熹的学说如何创新与深刻,而忽略张栻的贡献;其实他们的交往使双方都获益匪浅。朱熹与张栻广泛讨论诸般哲学问题,探讨名词概念,一般而言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他们也曾就各自的《论语》、《孟子》注解中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交换看法。②在这里我并不准备探讨他们之间所有的意见分歧,而集中讨论对道学同道非常重要的三个问题。
一、功夫修养与“中和”问题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涉及功夫修养以及心的观念,当时有两个不同的理解传统。功夫修养包含内心修为的过程,朱熹对这过程的理解是从一个传统出发,向另外一个传统发展,然后进行理论的综合,而这项综合的工作是他成为道学理论大家历程中最重要的发展分水岭。不过,朱熹理论的全面发展是渐进与累积的过程,并非突然激烈的决裂变化。近代学者已经充分研究过朱熹与张栻对于“中”、“和”与心、性关系的讨论,①我在此只简单介绍,而较详细讨论朱、张二人关系对朱熹思想演变造成影响的部分。
“中和”问题是起源于《中庸》的第一章: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按照《中庸》的说法,“中和”是人与天地合一的关键,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周敦颐、邵雍注重主静,说心是“太极”与万物的根源,周敦颐更进一步将“静”与“一”看做是“无欲”的状态;张载则区别“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程颢提倡灭除私欲以存定人性;程颐则更加强调“主敬”的专一修养功夫。北宋道学家比更早期的儒家学者对心性问题有更明确的概念,所以更注重功夫修为以达到性或心的“中”的境界,最终的目的则在于得“道”,与天地万物合一。但他们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例如,程颐认为在情未发前,应该认真存养,而情已发后,应该加以省察。
如何经由功夫修养而达到与天地万物合一?12世纪上半叶的道学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流派主张:一派在福建,另一派在湖南。在福建方面,以程颐的学生杨时、罗从彦(1072—1135年)为代表,他们把默坐澄心当做体验本心和定性的方法,认为静坐沉思可以排除各种私欲,而获得澄清的心境。罗从彦将这套方法传授给李侗,李侗又将它传授给朱熹。李侗教导朱熹不仅要在静坐中获得澄清的心境,而且要在日常生活中做功夫修养。但是朱熹当时认为,李侗对动静修养的教导是两个不同的学说。李侗认为这种心的澄净状态是日常行为修养功夫的基础,朱熹却对这两种直观的学说可能推衍出的矛盾颇感不安。问题的关键在于:活动的心怎样才能意识到它在行动前的寂静状态?朱熹思考李侗的观点达八年之久,在1166年得到初步的结论,认为如果了解内心的直观合一的境界不可能轻易实现,李侗的学说基本上还是站得住脚的。朱熹以前受张栻的湖南传统启发,对李侗的教导产生疑虑,现在思考出解决的方法,大概想要以此说服张栻,所以在1167年到湖南拜访,并停留两个月之久。
湖湘学派代表二程对于心的理论的另外一支主要发展流派。张栻以程颐所谓的“情”指心的已发状态、胡宏主张的心是性的作用的观点为基础,极力强调心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体验,认为唯有在行为活动中体验“静”,才能够获得心的“中”。张栻不主张静坐沉思,而认为应该利用心的潜能去体认四端,即可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把握天理,所以功夫修为应该先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天理开始,然后再来持养天理;张栻的方法观点比李侗更倾向行动。
从1167年朱熹在湖南逗留的两个月时间里,以及他在次年所写的四封信来看,他放弃李侗的观点,转而接受湖湘学派的主张。朱熹根据湖湘学派的看法,认为性是体,心为用;情未发前为性,情已发后为心。
但是朱熹不久又开始质疑湖湘学派的学说。学生问他为什么放弃李侗的观点,朱熹回答时显得颇为不安,并且承认由于仅强调从日常行为中领悟天理,不按照李侗所提出的方法致力于获致心的澄静状态,他有一种道德力量低落的感觉。从理论上来说,张栻主张的动中求静的方法只解决片面的问题:既然动、静在“太极”里总是处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够在静中求动呢?难道不能在心活动以前就持养心的本体吗?这些问题使他越过师友,直接向二程的著作求教。
朱熹在1169年给湖南友人的书信中说,他研读程颐的著作后,已经找到答案,解决动静中和问题的困惑,而且先前建立在湖南学说上的观点缺乏坚实的基础。他引用程颐的著作,解答这些段落与他们以前都注意到的段落间的矛盾,而这些引起注意的段落都见于他一年前编辑成的《程氏遗书》。朱熹现在相信,湖南的朋友认为情已发后是心,是因为他们只接受程颐早期的看法,其实程颐已经修正自己的看法,指出心兼具静而未发的“体”以及已发贯穿万物的“用”两面。
若能够做到程颐讲的“主敬”,心就能动静适宜,进而理解存养天理,所以程颐提出的“主敬”与“致知”是最好的功夫修养方法:“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①朱熹根据这种看法,对中和问题得出一套完整的见解,进一步认为在省察和存养之前,不需要等待情的已发。情即使处在未发前的寂静状态,心一直是悠悠然的存在。但静只是心所处的一种状态,这种可以体会的心境虽然也是功夫修养的目的,但它并不是性。朱熹得到这见解后,就能够兼顾湖南与福建两种功夫修养的传统。朱熹在1172年左右写作“中和旧说序”,进一步考查自己思想的演进,从李侗的影响、张栻的冲击,然后到自己的功夫修养观,朱熹从此认为自己的思想已经成熟,以后未对这问题作重大的立场改变。不过,朱熹晚年只提到存养的功夫,所以可说他所谓兼顾动静的修养方法,与湖湘学派所强调的要素似乎渐行渐远。①
朱熹对这问题的思索演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里要讨论其中的三点意义。第一,他将道学家既有的理论加以综合,成为一套新的系统。他接受程颐主敬的观点后,就超越周敦颐的“无欲”、“主静”的学说以及程颢的“定性”的观点。程颢除努力追寻内在之性的寂静状态外,还强调要如实地应对外在事物;因此,程颢的理论较周敦颐的观点显得更为积极。朱熹要将湖湘学派在日用行为中寻求理的方法与福建学派静坐体验天理的方法融为一体,所以特别强调读书的重要。朱熹以前的福建道学家较重视以冥思直观的方法了解心,所以对研读书本知识较缺乏兴趣。根据朱熹的新见解,心的功夫修养较倾向读书以及对万物的经验观察。当然,他不是从科学的角度,而是从道德哲学家的角度来强调经验观察的;②所以朱熹比早期福建的道学家,更强调学术研究和多事述作的倾向。
其次,朱熹在历经放弃老师的观点以及再修正的过程中渐趋成熟,显然经过一段内心挣扎的痛苦,到达自由超越的重要阶段。他批判老师李侗及挚友张栻的观点,而痛苦扬弃它们后,得以直接把握程颐的学说,必然感到无限解脱与欣慰。他在摸索的过程中,自信他的二程研究足以纠正一般对二程学术的解释。朱熹处理动静中和问题时表现得很成熟,所以他对自己的权威更有自信;从此以后,他评析与重建儒家传统的工作更显著进步。
第三,张栻在朱熹的思想演变过程中,担任重要的催化剂。张栻所秉持的湖南修养功夫传统促使朱熹对自己的福建传统产生怀疑,张栻的动中求静的学说也是朱熹静中求动观点的重要转折环节,所以张栻帮助朱熹进一步解决两种道学传统间在修养功夫与中和问题上的对立,甚至可以说湖南道学家以“性为体,心为用”的说法,促使朱熹特别努力使用“体用”的概念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
前面一章讨论张栻很注重程颐格物与主敬的学说时,我们推测张栻与朱熹讨论心的中和问题时,张栻很可能首先提出这些讨论主题。他们在1163年、1164年及1167年几次会面谈论的内容,几乎没有文献数据可资参考,而且朱熹未将张栻早期的部分信件文章编进张栻的文集,而尚存的材料又往往很难准确判断完成的年代,所以很难判定究竟谁给对方的影响比较大。不过从1172年朱熹所写的“中和旧说序”,我们知道张栻立刻同意朱熹的最后主张,唯有一点仍然不能同意朱熹,张栻依旧认为持养前,必须要在日用生活中体验天理。①双方的共识如此容易达成,似乎表示朱熹也接受张栻强调主敬、格物的观点。张栻即使率先提到这些观点,或者促使朱熹思考这些问题,也不能因此贬抑朱熹理论综合的成就与哲学地位。不过,朱熹及日后的学者何以忽视或低估他与同代人的思想交流,由此大概可看出部分端倪。
在朱熹从1170年到1172年的交往友人中,吕祖谦一再提醒朱熹修养本心的功夫需要兼重动静。吕祖谦指出朱熹对胡宏《知言》中一段话的批评并不公平,认为朱熹的批评是从在静中持养的角度出发,而胡宏那段话是谈论日用生活的验察;吕祖谦并且指出这两种修养方法都很重要,缺一不可。朱熹批评胡宏没有追求本心时,的确有些言过其实,因为胡宏曾特别引用孟子对齐宣王谈论本心的看法作为例证,孟子建议齐宣王把不忍杀牛的感情推广到百姓(《孟子·梁惠王上》)。吕祖谦非常能够把握两种修养方法的要点,显示他已经完全接受这个观点,或者他在朱熹综合理论前已经朝这个方向发展了。从后面我们对吕祖谦个人与思想的讨论来看,他很可能很早就注意到两种修养方法并重的理论。无论如何,朱熹的态度并没有吕祖谦那么持平,他回答说:“二者诚不可偏废,然圣门之教,详于持养而略于体察,与此章之义正相反。”①朱熹认为理解与省察天理是向外的,所以必须在持养天理之后。
二、《胡子知言》的讨论
第二个重要的讨论集中在胡宏《知言》的内容。朱熹在对本心的中和状态形成新观点的过程中,开始不满胡宏的《知言》。约从1170年开始,他要求张栻、吕祖谦一起批判《知言》。根据朱熹的说法,到1172年时三个人同意哪些段落有问题,②朱熹把这些意见记录下来,编成“胡子知言疑义”,张栻也表示基本同意这记录的观点。③
朱熹对《胡子知言》的讨论,显示当时的道学家对前人的著作进行一系列的修正。朱熹引用胡宏的一段话,表示他宁可采取张载的语言来描述心的功用,张栻对这两种表达方式都不太满意,而提出自己的说法。朱熹称赞张栻的说法有独到之处,但是他马上补充说:“凡言删改者,亦且是私窃讲贯议论,以为当如此耳,未可遽涂其本编也。”④朱熹在讨论开始的时候,显然无意改动胡宏的原文,可是他终究着手修改《知言》。
在另外一处文字中,张栻反对朱熹删改胡宏的原作,加进自己的用语,从而改变胡宏的本意。张栻提醒朱熹,应该尊重保存前代学人的思想;不过在另外两处文字中,张栻又表示一段“当删去”,另一段“不必存”。①唯有吕祖谦提的三段话始终维护胡宏,反对修改原作。朱熹在最后一次讨论中,直言不讳主张修改胡宏的原文:“此段诚不必存,……今欲存此以下,而颇改其语。”②为自己的删改行为辩护。
朱熹对胡宏的批评终究取得上风,他反对的段落在今本的《胡子知言》六卷中除四库本之外都不再出现。③到底是朱熹还是张栻删改胡宏的原作?答案虽然很难断定,但删改的主张来自朱熹则全无疑义。唯有朱熹一人记载讨论过程中三方的意见,张栻与吕祖谦的意见并不在他们的文集里。“胡子知言疑义”最重要的意义是显示道学领袖在琢磨近期道学家的著作,重建自己的传统。
朱熹对胡宏的著作提出八点疑问,后代学者把这八点归纳成三个主题。④第一,朱熹反对胡宏性无善恶的观点。第二,朱熹认为胡宏把心看做性之已发,而仁就是心,所以胡宏是从“用”而不是从“体”的角度讨论心与仁的问题。第三,胡宏认为,只有省察心活动的最初阶段,才能够把握心、持养心;朱熹认为这是错误的想法。前面已经处理过修养功夫的问题,后面要谈关于仁的争论,所以这里先讨论性和心的问题。
胡宏说性为天下之大本,但是心能够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朱熹反对这种“心以成性”的观点。朱熹引用程颐对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的解释,指出程颐是指心中的天理(即是性),而胡宏却是针对心的功用而言。胡宏认为性与心为一体两面,一体两用,互相关联。朱熹为否定这种关系,引用张载的“心统性情”的观点。⑤
另外一段讨论与此类似。朱熹引用胡宏的话:“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朱熹上溯这个错误的观点到程门学生谢良佐,并且再次引用张载对情的看法,以修正胡宏的学说:“性不能不动,动则情矣;心主性情。”张栻与朱熹的修正看法不同,表示要回到程颐而不是张载的论点,并且引用程颐的话:“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但是朱熹这次反对程颐的说法,认为所谓“有形”的意义不明;①朱熹显然不是简单借用程颐的权威就足以被说服的。
不论是胡宏的“心以成性”,或是朱熹的“心统性情”,两人都看重心的地位,认为心具有超越的性质,并且都区分无所不在的“天地之心”和依赖个人生命而存在的“一己之心”。胡宏回答学生问题时,曾经表示心超越生死,而学生对他的回答颇为困惑,朱熹于是抓住这把柄,批评他的观点包含佛教生死轮回的观点,应该提到“理一分殊”的看法。换句话说,心中的天理是超越的,而心的本身并非超越的;②而对朱熹而言,心中之理就是性。
胡宏相信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且同行而异情。胡宏虽然要人在道德修为中区别天理、人欲,但是朱熹指责他对本性问题的观点。朱熹指出,人虽然不能知道天理的起源是什么,但是人生而具有天理,所以天理是先天的。只有受到形体的限制、习惯的熏陶或者受到情感困扰时,才会产生人欲;所以人欲不是天生的。如果认为两者都是天生的,如何能区别它们呢?朱熹认为胡宏不能认识本体是纯净不受人欲污染的,却妄想在天理中发现人欲,又在人欲中发现天理。③
胡宏还说观察人对别人与事物的好恶,可以理解天理、人欲的区别,好恶是人的本性,因此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朱熹指责胡宏的观点是“性外有道”,而且使得天理、人欲没有先后主从的区别,会违背《诗经·烝民》的意旨: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①《孟子·万章上》引用这段话来说明本性先天就包含德性,朱熹进一步扩充它的范围,以区别人欲与天命法则,因为天命的法则与天理、人性完全相同。
朱熹虽然承认好恶是本性固有的,但他坚持好恶不是性的本身,而称它为“物”,并引经据典支持这种分别。《诗经·烝民》说:“有物有则”,这分别也就是《孟子·尽心上》所谓的“形色,天性也”。朱熹总结说:“今欲语性,乃举物而遗则,恐未得为无害也。”②朱熹将好恶当做“物”,似乎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可以把好恶当做“情”,就能够与他整个哲学体系更相应一致;亦即把“情”当做性的“用”,就足以与性的本身区分。但朱熹舍此不为,却引用经典的权威批评胡宏的论述。总而言之,朱熹所希望的是把性与天理视为一事,不像胡宏认为性并无善恶的分别。
性如果真的像胡宏主张的无善恶分别,问题是:善从何处而来?朱熹明白胡宏一直坚守着儒家行善的目标,对他所谓“人之为道,至大也,至善也”一语也推崇有加,但朱熹立刻补充说,本性如果没有善恶的区别,儒家的善行就失去根据。③
朱熹继续讨论胡宏对儒家善行的看法。胡宏指出圣人也有情、欲、忧、怨,与众人的区别仅在于行为合于节度:
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为正,挟非而行则为邪。正者为善,邪者为恶。而世儒乃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
朱熹认为胡宏的推理有误:
然不知所中之节,圣人所自为耶?将性有之耶?谓圣人所自为,则必无是理,谓性所固有,则性之本善也明矣。①
朱熹极力强调唯有肯定行为中节就是内在的善性,联系圣人与合于节度的行为才有意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张栻如何放弃胡宏“性无善恶”的主张,所以他立刻同意胡宏这项观念是错误的。
然而,张栻仍然坚持程颢的观点,认为善是性,但恶也不能说不是性。张栻引用程颢以水喻性的比喻,将善比喻成水本然的澄清状态,将恶形容为污水。善与内在的本性一致,而恶起源于物欲的困扰,所以学问的目的就是清除本性所受的污染,恢复最初的澄净本源。朱熹在这里只略带一笔说,程颢所谓恶也是性,只是专指气质之性而言。②
然而,程颢这段话一直困扰朱熹,值得进一步讨论。陈荣捷先生承认朱熹讨论程颢的著作时,以谈论这段话最多。因为程颢将清水比喻善性,陈先生觉得这种比喻很贴切,所以他的讨论就此打住,把难题简单搁在一边。③钱穆先生(1895—1990年)显然更了解这段文字如何困扰朱熹,他指出朱熹在《朱子语类》里,不断抱怨程颢的这项观点令人费解,竟然达30多次,并且认为程颢对性的看法不完整。朱熹坚持程颢的“性即理”,称它是孔子以来无人了解的至理名言,其实也隐约批评程颢一番。钱穆先生列举二程兄弟对本性问题的看法,显示程颢的观点的确与程颐颇有不同。④程颢认为性有善恶,而胡宏进一步说性无善恶。
朱熹和胡宏的另一个歧异在于他们对事物的本体的了解。二程谈论本体时,往往关心万物已经存在的状态,不是事物尚未生成前的本体阶段,例如,他们喜欢张载的“西铭”,而不喜欢《正蒙》,因为前者谈论具体实在事物的本体,而后者较为抽象。程颐晚年比较能够接受张载,而朱熹以程颐所讲的“性即理”学说为中心线索,把张载、周敦颐和二程兄弟的哲学融合成一个体系。胡宏较接近二程的立论倾向,只讨论已存在的具体事物的本体;吕祖谦认为《知言》的价值胜过《正蒙》,很可能也是反映二程的这种思想倾向。但是朱熹坚持将本体解释成万物生成具体实物前的抽象第一原理。①
朱熹与胡宏所讨论的本体,其实在完全不同的层次。胡宏是从万物已经生成为具体实物的前提下,谈论天理人欲同为一体,而且心为性的作用。朱熹则根据自己的形而上哲学立场,分析胡宏学说的隐含意义。如果胡宏的性无善恶论指涉事物未发的寂静状态,朱熹才可接受他的理论。事物一旦有动静分别,立刻有善恶之分,而且合乎节度者才是善。朱熹认定胡宏的立场必须要谈论两种善性,甚至于两种本性:一为原初的本然之性,其二是通过情感作用的活动而呈现的性。②朱熹虽然谈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但是他没有将两者当成两种性,而且认为设定两种实在的性,根本是不能成立的理论。朱熹自认驳倒胡宏的观点,虽然胡宏没有像朱熹那样说两种本性。
朱熹认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是主张行为中可得见的善行,就是来自本性中的善性。朱熹根据这个思路,在1171年写信给胡宏的侄子胡实(1136—1173年)说:
盖谓天命为不囿于物可也,以为不囿于善,则不知天之所以为天矣。谓恶不可以言性可也,以为善不足以言性,则不知善之所自来矣。《知言》中此等议论与其他好处自相矛盾者极多,却与告子、杨子、释氏、苏氏之言几无以异。昨来所以不免致疑者,正为如此。①
善的本体就是最根本的原理,所以一旦认识终极的本体,就可以了解天如何成为天,以及善的根源。
朱熹是从形而上的思辨哲学出发,辩护最基本的原理,所以严厉批判胡宏的人性论观点。朱熹在1171年写信给胡宏的儿子,承认胡宏的本意是要极力推崇性的地位,但是称扬性超越善恶之分别,其实在无意间贬抑性的地位。性若非绝对的至善,而与人欲有相同的本体,它不可能是纯粹的。朱熹告诫他的学生说,胡宏的诠释无异说性是“空物”,与苏氏兄弟和佛教的异端很相似。②
三、“仁说”
朱熹与张栻讨论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仁”。他们的讨论早在1163年初次见面时大概已经开始,并持续达十余年。朱熹虽然在1167年拜访张栻的两个月间也曾经涉及这个问题,但在“中和”问题解决前,“仁”的问题还没有成为中心议题。朱熹写了一篇谈“仁”的文章,并且在1172年和1173年间与张栻、吕祖谦通信交换对“仁”的看法。朱熹到1173年时的观点大概与张栻已经变成一致,他与吕祖谦磋商后,将“仁说”做最后的修订。
朱熹论仁是以“天地之心”为根据。《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且卦辞用“元、亨、利、贞”形容天地的大德。程颐、程颢受《周易》以天地生成万物的看法影响,认为生成万物的“大德”就是天地之心: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①朱熹发挥说:
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或详之。盖夫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②朱熹然后以体用关系的角度阐述仁,认为天地、人心都有体用两面,而且由体用的关系,天地的本体在“元”起时就涵盖其中,人心中的所有德性也可以用“仁”统摄;他说:
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复礼为仁”,言能克去己私,复乎天理,则此心之体无不在,而此心之用无不行也。③
朱熹还引经据典说明人应该怎样作为,才能将仁体实践于日常生活中。
朱熹随后意图修正他所谓的早期道学家的错误,并且解决他与程颐间的一项明显差异。程颐认为“爱”不是“仁”,朱熹则指出仁是“爱之理”,并不是“爱”的本身;所以程颐的原意虽然没有讲得很明白,两人的观点其实没有矛盾。
“爱之理”与“心之德”合起来马上成为儒家对仁的标准诠释,能够涵盖体用关系,比以前任何“仁”的定义都要清晰。张载在著名的“西铭”中明确论及仁的本体,并隐约谈到仁的作用。程颐不仅澄清张载的观点,而且建立“爱为情、仁为性”的学说。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颐说:“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①谢良佐以“知”说明仁,杨时以“公”解释仁。这里“公”是指公正无私,意指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如果天地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无所不爱。张栻则从“知”和“公”的角度说仁。朱熹在程颐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点,但是他更强调“爱”的因素,把儒家传统中几个重要的概念融合起来,写成一篇面面俱到的文章。
中国与日本的学者素来很注意朱熹的“仁说”以及他与张栻的信函,并且大都强调朱熹的理论综合很有创见,并肯定张栻最后接受朱熹的观点。例如,佐藤仁先生即说:“这篇文章透露出张南轩的湖南学识招架不住而且全倒向朱子的观点。”②刘述先先生还感慨在现存的张栻著作里“几无〔胡〕五峰学之痕迹,也看不出他本人的思想的特色何在,其学也无传人,大概因此附于朱子,遂完全为朱子学所压盖下去。”③我要考查这些说法,而且想平衡学者一贯侧重朱熹的倾向,所以较注意张栻的思想,以及他如何使朱熹的综合理论更加丰富。
张栻从1161年撰写“希颜录”开始,就一直努力研究仁的概念,而且数易其稿,直到1173年才能定稿。这篇文章完稿时,他也在修订“仁说”(原文见第二章),张栻“仁说”的修订稿无论语气、内容都与朱熹的“仁说”极其相似,所以从朱熹的学生陈淳(1159—1223年)开始,有的学者就误以为它出自朱熹的手笔。①但《朱文公文集》的编者说:“浙本误以〔张〕南轩先生“仁说”为朱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仁说”又注‘此篇疑是“仁说”序,姑附此’十字,今悉删正之。”②
由于这两篇文章非常相似,有些学者急于证明朱熹的“仁说”比较早,所以是原创的观念,这种说法的证据其实很有问题,基本的材料来自朱熹给吕祖谦的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在1173年初写的“答吕伯恭第十六书”,信中提到张栻说自己对“仁说”已经没有疑问,③陈荣捷先生就以此说朱熹的文章已经是“定稿”。④可是朱熹在当年秋末冬初所写的“答吕伯恭第二十三书”中,又说接到张栻的“仁说”。⑤更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在“答吕伯恭第二十四书”中开门见山说:““仁说”近再改定。”⑥朱熹这里使用“再”字,显示他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朱熹在1173年年底以前,还在继续修改“仁说”。第二封信是“答吕伯恭第二十四书”,朱熹在信中提到张栻在1173年底曾送达书信与“言仁录”,朱熹评论此文“稍胜前本”,而且说“仁说”曾经根据他们交换的意见修改。⑦可是这封信提到的“仁说”虽然是张栻的作品,但它只是张栻最后的定本。总而言之,将这些信件放在一起考查,显示张栻即使说对“仁说”已经没有疑问后,双方的文章仍然在变化改进。
由于双方一直修改论仁的文章,而且张栻论仁的重要著作今天已经不复存在,委实很难证明朱熹的“仁说”比较早完成。朱熹把张栻去世后遗留下来的文稿编辑成文集时,没有把“言仁录”、“希颜录”以及张栻写给朱熹的论仁的部分信件收进去。张栻从1161年以后,一直在写作讨论仁的问题,所以他们讨论仁的问题时,张栻的文章一定是重要的焦点和催化剂,尤其是在1167年拜访张栻的时候,因为朱熹还要等几年才开始写他自己的“仁说”。我们虽然无法比较张栻早期论仁的文章与朱熹的“仁说”的措辞用语,但从现存的文章与信件判断,张栻对朱熹发展出的论仁的综合学说似乎颇有贡献。
朱熹给张栻的信中批评早期儒者的观点偏颇不周全:二程以前的儒生把“仁”化约成“爱之情”,因此看不出仁的重要;程颐严格区别“仁为性”、“爱为情”后,仁的重要性才再次获得肯定。然而,程颐的学生过于强调仁为性,反而忽略爱,比将仁视为爱的早期儒者更加不如。程颐的学生由于没有抓住仁的根本,不但个人修养没有成就,而且只能一味凭空玄想臆测仁的原理。他们由于这种无知,成为孔子所批评的“好仁不好学”的人(《论语·阳货》)。朱熹如此严厉指责道学传统中人,生动地显示他在12世纪70年代初,已经自信具有定义道学传统的权威地位。
朱熹在1171年进一步宣称,要纠正从二程学生而来的流行错误,需要为“仁”确立更清楚的概念。他在“答张敬夫第十六书”里说:
熹窃尝谓若实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进,但不学以明之则有擿埴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为助,则自无此蔽矣。若且欲晓得仁之名义,则又不若且将爱字推求,若见得仁之所以爱而爱之所以不能尽仁,则仁之名义意思了然在目矣,初不必求之于恍惚有无之间也。①简而言之,人必须对仁的意义和内容有更精确的理解,方能够谈到功夫修养,而儒学的讨论才得以回归正确的途径。
朱熹和张栻在通信讨论仁的问题时,产生许多极有意义的争论,其中一个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天地之心”的问题上。朱熹在他的“仁说”里借用程颐的话:“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出自程颐的《易经》注解。张栻不同意这个说法,而支持程颐的另外一句话:“天地生物之心”①,张栻认为这两句话有根本的差别。张栻和胡宏都认为心是一种奇妙的超越力量,能够包含天下、约制万物。“天地生物之心”反映出他们的主张:心是活动不息的观念。张栻根据自己的理解,指出“天地生物之心”不受它所生的事物限制;朱熹所提出的“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的看法,则使心一定要受到限制。
朱熹答复张栻说,程颐这两句话其实意义完全相同。朱熹虽然即刻在“仁说图”中引用张栻喜爱的“天地生物之心”一语,但仍然指出这两种说法都认为天地之心就是生成万物的作用。他在1172年给另外一个朋友的信中,猛烈抨击湖湘学派的观点:
大抵近年学者不肯以爱言仁,故见先生君子“程颐”以一阳生物论天地之心,则必欿然不满于其意。复于言外生说,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心者,实不外此。外此而言,则必溺于虚、沦于静而体用本末不相管矣。②
朱熹警告说,湖湘学派把心视为具有超越功能的观点,会导致佛、道所讲的虚空与寂静。然而,比较一下朱熹当时的记录与12世纪70年代初的实际情况,不难发现胡家的成员与张栻都比朱熹更专心于政务,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持养此心,所以朱熹的批评是有些夸张。
朱熹和张栻虽然对“天地之心”无法获得共同的见解,但他们都同意“天地之心”与“人心”是相连的。朱熹提出:“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为人之心。”①双方对这句话的理解却大相径庭。朱熹的重点是在温暖柔和的同情心,人们因这种同情心而可以爱人、惠及他人。张栻则顺着二程所提示的另外一条思路,强调要经由无所不包的“仁”,与万物犹如一体般互相联系。朱熹承认“仁”的普遍性能使“爱”惠及万物,但他很注意程颐曾提出的警告:普遍而没有区别的爱有流于“兼爱”的危险,视人如己可能会导致自我否定的结果,甚至荒谬到投身喂虎。同情心则较为实际可行,而且同情或爱其他的事物只是仁的效果作用,而不是仁的本体。②有些在伦理学上强调“爱”以及“与人一体”的人,都不了解只有爱是不足的,因为爱不能告诉我们应该为人做什么。朱熹虽然如此夸大嘲弄张栻的立场,其实张栻没有掉进虚无的相对主义或滥情无度的危险里。儒家学者把爱与义、孝等特定的道德行为相连,而这些道德提供行为纲常的规范。
朱、张双方的文章还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处:他们都用“爱之理”描述仁的本体。由于朱熹删除张栻论仁的一大部分论述,我们无从知道“爱之理”是否来自张栻的“希颜录”和“言仁录”,也不能否定是朱熹首先使用这句话的传统看法。可是张栻马上在“仁说”和“癸巳论语解”中使用这句话,强调万物一体,要将爱推及万物,所以张栻将“爱之理”解释成公正无私、与人一体;但朱熹否认这句话有“万物一体”的含意。朱熹认为万物既然都具有此理,不必等待与万物合为一体以成就“爱之理”。公正无私虽然与仁很接近,但朱熹重申程颐的观点,认为“公”不足以代表仁的本体。从湖湘学派的立场来看,朱熹限制心与仁的本体;但从朱熹优越的形而上观点来看,湖湘学派强调仁有公正无私和无欲的特性,其实限制了仁。朱熹虽然在“仁说”里没有使用“公”一词,而且极少提到去除私欲的问题,但他使用“克己”一词,显然对达到公正无私和控制私欲的境界,也有浓厚的兴趣。然而朱熹与张栻通信论难时,极力划分这些特征与仁的区别,而且努力将仁与理完全等同。①朱熹所谓的“爱之理”没有强调爱包含世界的普遍意义,而特别指出它包括儒家一切的基本德目及相关的价值,而且这些道德价值是基本的先验法则,不需要依靠任何其他事物为基础。朱熹认为仁是基本的先验原则,因为它就是性,而非情或心。
朱熹也反对湖湘学派将仁与心的知觉视为一事。张栻与其他的湖南学者继承谢良佐、程颢的观点,认为仁就是心初发的积极作用,而且是功夫修养的基础。张栻在一封讨论仁的信中再次肯定这个说法,似乎显示“中和”的讨论并没有如一般所说的使他放弃湖湘学派的传统。张栻所说的“觉”指感受到别人痛苦而产生的同情心,《孟子·公孙丑上》特别注意一种不忍见到他人受苦而能自发反应的心,就犹如拯救即将坠入井中的孺子的不忍之心。“觉”是发自内在心性的道德情感,“觉”也意指心的认知状态,用以探讨湖湘学派与朱熹的争论很适切。朱熹以“觉”的这层意义为重点,解释张栻和湖湘学派的观点。朱熹认为广义的仁包含其他儒家德目,湖湘学派却因为仁包含智,而错把智当成仁。仁人当然有知有觉,但仁不能被化约成知觉。②朱熹为强调仁是性、是理,而不是心,而把仁称为“心之德”。
朱熹认为把知觉当做仁,其实是以心来求心。他在讨论中和问题时指出,体验心所发的最初情感,不但需要有主动观察体验的心,还要有被动接受体察的心。他不太能理解胡宏、张栻和其他程颢后学其实是在谈论心的直观反省,并不是以一心求他心。朱熹也批评湖湘学派对孔子所谓“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的诠释。程颐曾经解释这段话说:反省别人的过错,可以知道别人是否有仁;湖南学者将这段话当做功夫修养的戒律。朱熹虽然称赞他们关怀自我修养的态度,但认为这种解释需要心不断犯错、观错,并且知道“仁”正在观察这些错误。朱熹指责这种方法会导致不必要的精神压力。①但是朱熹早先指责湖湘学派万物一体的观点会造成功夫修为的松懈,所以他这里的尖锐批评似乎有些混淆不清。
张栻回答学生问题时,颇能显示他接受朱熹批评的程度。张栻回复朱熹谈论“知觉为仁”的信函已然失传,所以这些师生问答的记录显得弥足珍贵。学生问张栻如何看待朱熹对谢良佐的评价,他回答说同意仁不能被化约成知觉,但也指出朱熹的批评稍嫌过分,并且补充说,心之所知唯有仁。另外一个学生引用朱熹“以心求心”的批评,请教张栻是否因此要明确修改他对孔子“观过斯知仁矣”的诠释,并请张栻澄清从反省失节的行为以知仁的论点,而且追问省察割股救父等极端的事如何能够教人以仁?②
张栻回答说,他仔细研究程颐的学说,而改正自己接近佛教的错误倾向,然后承认接受朱熹分别“厚”与“仁”的说法,但仍然认为反省过错很有益处。他也承认读书学习很重要,但坚持直接体验仁的一贯湖湘学派观点:
须是仔细玩味,方见圣人当时立言意思也。过于厚者,谓之仁则不可,然心之不远者可知。比夫过于薄,甚至于为忮为忍者,其相去不亦远乎?请用此意体认,用见仁之所以为仁之义,不至渺茫恍惚矣。①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评论这段话时,赞赏张栻把观过知仁与日常生活中的修养功夫相连,“如工夫有间断,知间断便是续,故观过斯知仁”。黄宗羲认为朱熹未能适切欣赏张栻的入手功夫:“若观过知仁,消融气质,正下手之法。”程颢类似的“识仁”说法,毕竟不仅只是“知仁”而已。②
有些20世纪的学者对张栻和朱熹论仁问题的评论,可与黄宗羲的看法相提并论。批评朱熹最激烈的莫过于牟宗三先生(1909—1995年),他认为朱熹曲解张栻对心以及仁的本体的看法。牟先生把张栻放进由孟子到程颢、胡宏的一支儒家传统,代表论心的主流观点,强调内在自发的道德情感,而且认为仁的本体不受任何限制。牟先生把朱熹归入程颐的系统,并追溯这支系统的脉络到荀子,尤其因为他们去除心内在的道德主动性,把心降低到仅具有认知的作用。朱熹不把心、性、情统整为一体,而以过度知性的分析方法严格区分它们的意义。牟先生认为,朱熹降低知觉领悟的地位,认为知觉领悟是被动的,所以人需要依靠“格”外在的事物,以了解心中内在的理。牟先生并且批评张栻不能适切捍卫自己的主流传统,不能了解朱熹援用程子权威时,其实是以程颐的观点误解程颢的观点。③
钱穆先生对牟宗三先生的看法提供了大概是最好的答复。钱先生指出,朱熹为反对佛教心理皆空的主张,必须将心与理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所以他将仁视为生成的力量与天地之心。为建立这种联系的基础,朱熹说:
万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圣人之心。天地之生万物,一个物里面便有一个天地之心。圣人于天下,一个人里面便有一个圣人之心。①
这种联系建立后,朱熹便可以宣称:“仁者心便是理”。②朱熹讨论功夫修养的目的,在于成就天地之仁时说:“学者克己复礼上做工夫,到私欲尽后,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③钱先生认为,在这些段落中,理、仁、心同为一体,④证明朱熹对心有更为广泛的看法,较牟先生所宣称的更接近孟子的主张。然而朱熹同时坚持了解心与仁的区别,以及一己之心与天地之心的道德差距,由于极为关注这些区别差距,他强烈反对湖湘学派的观点。
张栻与朱熹讨论仁的过程中,也的确获得一些共同的看法,并修改自己的“仁说”。朱熹在一封信中批评张栻不以体用关系了解性情,也没有提到“心统性情”的看法。今本的张栻“仁说”包括这些语句,显然张栻采纳朱熹这些建议,也接受“爱之理”必须先于“万物一体”的观点。张栻曾经在稿本中提到,天地之间无不是体之仁。朱熹认为如此则仁体就变成具体的实物,而且使万物与心中的仁的界限变得模糊。其实张栻从来没有将仁与心视作具体的实物,他的目的只是要指出仁无所不包。朱熹虽然明显误解张栻的观点,但张栻还是把这段话从“仁说”的定本中删除。⑤
我们若比较朱熹“仁说”的定本与他和张栻的书信,不难发现朱熹也曾因为张栻反对,而稍微修改自己的文章。⑥“仁说”定稿后,朱熹在“仁说图”中提到“公”的概念两次,也更明确谈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仁;这些改变都反映张栻关怀的课题。佐藤仁先生认为,朱熹得以发展出仁的概念,张栻的贡献远比这些细微末节更全面:“朱子和张南轩关于仁性的论辩,给朱子思想中的仁提供了最后的一笔。此外,这些论辩使朱子扫除了从南轩那边而来的湖湘学派加诸他的早期影响。”①
双方的差别当然依旧存在。朱熹比较注重理论,张栻倾向实践。张栻强调克己以及去除无知和私欲,朱熹则在克己与学问间寻求平衡。张栻对朱熹的妥协也有限,他在“仁说”中并没有放弃谢良佐的仁为知觉的观念,然而他表达“仁者知觉不昧”观点的方式,并没有与朱熹直接对抗的味道。他虽然同意不能将仁化约为“公”,但他没有完全放弃这观念,而且他的“仁说”定本中说:“公者,人之所能仁也。”②最重要的是,张栻的“仁说”并没有采用朱熹仁为“心之德”的说法。现代学者曾经讨论张栻为什么既不采纳,也没有提出疑问。他或许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其他的差异中,③或者根本没有异议,因为他们都师承二程的传统,而二程曾用种子来比喻仁、万物生成之理。④
“心之德”一词其实原来是张栻的用语,朱熹使用这句术语约12年后,承认它是张栻的用语,证据来自朱熹本人。朱熹承认这事实时,张栻已经去世五年,他没有必要承认贡献应该归功于张栻。朱熹当时编撰张栻文集,显然曾经重新审阅双方通信论学的内容与顺序。他在1185年写信给吕祖俭(吕祖谦之弟,1196年去世),描述张栻对他的“仁说”的反应:“欲改‘性之德,爱之本’六字为‘心之德,善之本,而天地万物皆吾体也。’”①朱熹显然承认张栻针对“性之德”而提出“心之德”的观念。根据这段材料的背景,“心之德”很符合湖湘学派对心的看法。我们无从究知“心之德”是否来自“希颜录”和“言仁录”,因为朱熹在编《南轩集》时,并没有收入这两篇重要的文章。
朱熹在这封信中又回忆说,他当时反对“心之德”的说法,因为它意义过于模糊,可以任人随意解释:“但心之德可以通用其他,则尤不着题,更需细意玩索,庶几可见耳。”②可是他却在自己的“仁说”定本里使用“心之德”,并以“爱之理”平衡这观点。朱熹显然认为,从湖湘学派所坚持的心的观点理解“心之德”,可能造成许多损害,以“爱之理”平衡后,就可以完全排除可能的损害。朱熹在1185年承认自己借用同时代人的学术观点,是相当罕见的事例,所以后来的学者很容易忽视它所呈现的朱熹思想发展过程。
张栻虽然没有向朱熹全面投降,但朱熹也的确赢得令人心服口服。张栻一旦接受朱熹的主张,承认湖湘学派思想来自谢良佐,就无法在程颢的哲学中寻求自己的学术渊源,所以追随朱熹向程颐寻求权威,使他在朱熹制定的规则下与朱熹展开论战。现代考证学者批评张栻没有清楚区分出二程思想的差异,而朱熹运用程颐来补充,甚至改变程颢的观点,都显示12世纪道学复杂多变的趋势。
整体而言,朱熹强调理论建构,张栻偏重实践,比较喜欢讨论文化价值以及实际的政策问题,但被迫讨论基本原理层次的问题。朱熹有时蓄意忽视张栻和胡宏的原意,而极力推衍他们理论的含意。例如,胡宏和张栻从体用的角度谈论具体的实物,朱熹却曲解他们在谈基本原理的本体。由于讨论层次的差异,朱熹赢得的一些协议,表面的意义甚于实际。朱熹与张栻的讨论,也证明朱熹比同时代的道学人士喜欢谈形而上的思辨哲学。
朱熹界定厘清许多观念名词,赋予它们重要的意义,而建立一套前所未有的综合儒学体系。在这过程中,他从与张栻的讨论里受益匪浅。后代的儒家学者承认张栻对朱熹的理论发展有贡献,但又常被两种看法遮掩而不彰。一派学者要证明朱熹理论的正统地位,并确立自己的理论权威;另外一派学者则指责张栻捍卫程颢和胡宏的传统不力,使他们自己的传统衰落。为重现12世纪儒家思想的发展动力,我特别强调张栻的贡献,而这种重建的工作由于材料的不完整而变得更加复杂。
朱熹编辑张栻的文集时,删除一些重要的材料,还改动《胡子知言》;我们重视历史材料的原貌,无法不对朱熹的做法不满。朱熹决定不要保留这些材料时,其实是在努力减低道学传统的多样特性,留下较为同质而确定的学术遗产。他的目的不是要客观整合文献,也不是否认朋友的贡献,他最关心的问题是道统的传承。朱熹的做法适切保证他所界定的道统得到传承,遗憾的是,朱熹删改张栻的文集后,他们求道的过程及思想世界都更难以如实地重建。在道学发展的第三时期,朱熹1184年编辑《南轩集》以前,整个思想气氛已经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要先谈一谈12世纪70年代的道学领袖吕祖谦。
第四章 吕祖谦
吕祖谦虽然不被《宋史》列入“道学列传”,并且鲜为现代学者所论及,但从12世纪60年代末期到1181年他去世的十几年里,他其实是道学最重要的领袖。①吕祖谦比12世纪其他道学领袖在政治上更得意,而学问也广为时人推崇,但吕祖谦身后受到的批评却引发一个根本的问题:他到底是位主张多元化、不受教条拘束的思想家,抑或是摇摆不定、缺乏决断的人?
吕祖谦出身望族,富有才华。吕氏家族从汉代被封在东莱后,产生不少政府官员,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到北宋达到最高峰。吕祖谦的先人吕蒙正(946—1011年)、吕夷简(978—1043年)和吕公著在北宋四朝分别官拜宰相,其他许多家族成员也甚获皇帝重臣的信任。吕祖谦的曾伯祖吕好问在女真人征服北方后,辅佐高宗在南方建立政权,功业彪炳显赫;在十一、十二两世纪,吕氏家人辅佐宋室的功绩无人能及。吕氏家族的学术表现也是出类拔萃,上下七代人中有17人被列入《宋元学案》,其中三人甚至各有专章论述,另外一人与范镇(1008—1089年)并列;其中最重要的是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等三人。
吕祖谦将吕氏家学传统和道学流派结合,发展出12世纪道学的一支主要流派。全祖望(1705—1775年)在“同谷三先生书院记”中说:
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其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径路虽别,要其归宿于圣人,则一也。①
全祖望这段话虽然是在18世纪回顾历史时所说的,但他认为吕祖谦是12世纪后半叶道学的一位主要领袖,见解十分正确。全祖望区分这三派学术时,不幸忽略张栻的地位;现代学者牟宗三先生把张栻放进他的划分系统里,却转而忽视吕祖谦。其实吕祖谦和张栻都不容忽视,而且除朱、陆、张、吕四派外,许多其他南宋道学家也颇值得研究。倘若一定要坚持简单的三派区分方法,全祖望的分法问题比较少,因为在12世纪后半叶,吕祖谦的影响力比张栻大得多。无论如何,全祖望准确指出吕祖谦学派的特点是能够兼容并蓄,而形成这种特色的主要原因是吕家从北方带来很多中原文献。
吕祖谦以家学和藏书为基础,在金华创建一所书院。他在金华附近的明招山任教一段时间后,于1170年把教学的中心移到城东的丽泽书院,与弟弟吕祖俭一起主持教务。当时的丽泽书院可与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在南康附近)和张栻的岳麓书院(在长沙附近)媲美,丽泽书院的学者继承吕学的传统,并一直延续到元、明时代,使吕祖谦的史学和经世之学成为后世金华学派的基础。①学者几百年来把金华学派归在浙东史学和经世之学的范围里,除婺州金华外,此派的大本营还包括浙南的温州和浙北的明州(今宁波)。把这三处的主要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甚为恰当,因为吕祖谦的思想对这三个地区的学者都有影响,而且这些学者在当时已经有共同的归属感。
吕祖谦在金华讲学期间,学生从各方登门受教,吕祖谦也认为士子应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但他对“道”和文化传统具有更根本的责任感,并且试图影响学生,使他们也能关心文化、道德和哲学的问题。吕祖谦对心、性的看法接近孟子,属于当时道学的主流见解,但是他不像一些道学家花许多时间研究这些哲学问题的细节。他与朱熹、张栻等同道最大的不同处,在于他更注意全国的政治问题,重视历史研究和经世之学,而这正是吕祖谦与其他浙东儒者的共同点,他们对历史的看法也远比一般的宋代儒者(尤其是道学家)活泼。
过去几世纪的学者讨论吕家学术传统时,侧重四个主要的特点,而它们大多源于朱熹对吕家学术的评论。②朱熹认为吕氏学术的特色:第一,“不名一师,不私一说”。这个传统是吕希哲在11世纪中叶有意识开创的。吕希哲曾追随欧阳修(1007—1072年)的弟子焦千之,又曾问学于胡瑗(993—1057年)和孙复(992—1057年),使他的学术奠基在北宋第一代复兴儒学的学者的学说上;他又曾从学于王安石等第二代儒学复兴运动的学者;道学的兴起也引起他注意,而与邵雍、二程过从甚密。朱熹的《伊川先生年谱》据《吕氏童蒙训》说:“吕希哲原明与先生〔程颐〕邻斋,首以师礼事焉,既而四方之士,从游者日众。”③可见朱熹十分了解吕家的社会政治地位对道学的兴起有很重要的帮助。吕希哲的孙子吕本中继承“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家风,先后追随过刘安世(1048—1125年)、杨时、陈瓘(1057—1122年)、尹焞、王(1082—1153年)等名儒,这些儒家学者和二程都有交往,其实他们代表的是12世纪初期范围视野较为宽广的道学。例如,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弟子,他的语录只保存在张九成弟子所编的《诸儒鸣道集》里。张九成和吕家的关系也很深厚,他与吕本中亦师亦友,写给吕本中的信充满感情,目前都收录在《横浦文集》和《横浦日新》里。①
吕本中的弟子林之奇(1112—1176年)把多样化的传统传给吕祖谦。林氏是吕祖谦青年时代最主要的老师,对吕祖谦的历史观——尤其是他对《书经》的看法——影响重大。吕祖谦年轻时也透过其他老师与广义的道学建立联系,他曾短暂地追随胡宪,从杨时与张九成的弟子汪应辰(1119—1176年)处得益尤多。胡宪的学术则结合二程的学说(尤其是他们的《易经》学说)和胡家的史学与经学。②胡宪是胡宏的堂弟,也是朱熹的父亲朱松托孤时指定的三个老师之一,所以朱熹与吕祖谦有一个道学传统中的共同老师。吕祖谦还和道学的另一个分支有关系,他们是在温州永嘉的程颐传人,可上溯到郑伯熊(1128—1181年),甚至周行己(1091年进士),周行己曾经带领八个永嘉同乡北上向程颐求学。③
朱熹承认吕祖谦学问广博,但批评他不能专注研究学问的根本;似乎用程颢既能广博又能“守约”的标准衡量吕祖谦。《朱子语类》记载朱熹弟子吴昌寿批评:“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朱熹甚表认可同意。④朱熹并将批评引申到整个吕氏家族的学问,他在“与林择之第十一封信”中说:“吕公家传深有警悟之处,前辈涵养深厚乃如此。但其论学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则博而杂矣。”①
第二,吕家“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学术风格使他们比较能够包容佛教。宋儒大多受过佛教的影响,但吕家比一般宋儒更能认清这事实,而且能够坦率承认佛教的影响。吕希哲晚年研习佛学,与僧侣交游,认为儒释两家教义有许多相近之处,所以主张调和两家学说。吕本中继承调和论的立场倾向,尤其喜好禅宗。吕祖谦在这方面的态度与先人不同,不但没有鼓吹佛教,而且还批评佛教。然而,还是有人认为他曾受禅宗顿悟学说的影响,因为他在“易说”中说过:“知此理,则知百年之嫌隙,可以一日解;终身之蒙蔽,可以一语通;滔天之罪恶,可以一念消。”②但这句话是他在讲解《易经》睽卦时所说的,从上下文的脉络可以看出原意似与佛学无关(在第五章我们会再讨论吕祖谦的易学)。不过,朱熹仍然“有疑于伯恭词气之间,恐其未免有阴主释氏之意,但其德性深厚能不发之于口耳。此非小病。”③
朱熹既然没有具体指出吕祖谦的思想和文章中有哪些地方“有阴主释氏之意,但……不发之于口耳”,我们也许不应太强调吕家传统中佛学的成分对他的影响。其实朱熹也曾经批评吕祖谦与张栻不读佛经:“〔张〕钦夫、〔吕〕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④道学虽然深受佛道两教影响,许多道学中人却对佛道深怀敌意,甚至把它们斥为异端。
吕家继承唐代大家族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这种风格在宋代显得十分突出。诚如钱穆先生所说,吕家因为受到佛道两家相对主义倾向的影响,而“喜和不喜争,喜融通不喜矫激”①。吕家当然不是有兼容并蓄胸怀的唯一宋代政治家族,但这些家族多半不是道学中人。吕祖谦虽然不如先人深受佛教影响,他还是比较能容忍不同的意见。他的包容倾向还有一个重要基础:他认为闻道十分困难,“善未易明,理未易察”②。又说:“义理无穷,才智有限。”③承认难以明确了解“道”;而且为人秉性谦和,所以特别愿意倾听别人的意见,不轻易排斥异己。他说:“人各有偏处”,所以应“就自己偏处,寻源流下工夫”④。这种个性使他擅长在儒家学者间扮演调停折中的角色,不过他也不免受到当时道学界狭隘学风的影响;他只追求儒家学者间的和谐共识,尤其是道学家间的和谐共识。
第三,吕家不论接受多少佛家影响,涉猎各种不同的理论,其家学终究还是以《四书》为中心,而《四书》是道学界公认的儒家主要思想文献。吕本中虽然又加入《孝经》,但仍然认为《四书》比传统的《五经》重要。他说:
学问当以《孝经》、《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为本。熟味详究,然后通求之《诗》、《书》、《易》、《春秋》,必有得也。既自做主张,则诸子百家长处,皆为吾用。⑤
所以《四书》和《孝经》比起其他经书更属儒学的根本,儒学的基础稳固后,才能运用其他各家的理论。吕氏所关怀的《四书》问题和其他道学家相同,包括:“存心养性”、“穷理”、“尽心”、“正心”、“诚意”等主题。例如,吕公著“自少讲学,即以治心养性为本”⑥。道学当时甚至还未兴起。吕氏一直很注重孟子的修身方法,这点也和其他道学家一样。
第四,吕氏重视功夫修养的情形,从他们的治家格言“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出自《周易·大畜卦》)即可见一斑。吕公著早年就依此治学,而且把它变成家学的精华,吕家的成员虽然转益多师,他们最珍贵的还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家学传统。这个格言很能反映吕氏“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作风,因此能够在历代产生出许多杰出人物,并且发扬它的教训,收集大量图书,建立当时最丰富的私人藏书。全祖望说:“中原文献之传,犹归吕氏,其余大儒非及也。”①这些藏书不但培养丰富的文学修养,对他们的史学研究也很有帮助。
二程在广博的吕学中占有很特殊的地位。吕希哲曾从游于程颐,吕希哲的子孙又追随过杨时等二程最亲近的弟子。吕祖谦把杨时的《中庸》注解当做研习此书的标准,认为个人教育应该以二程和杨时的文章语录为中心。吕本中也把张载的学问纳入吕氏的家学,所以1345年编成的《宋史》虽然未把吕祖谦列在“道学列传”内,却仍说吕祖谦的思想是张载和二程哲学结合的产物,②当然二程和张载的哲学并不是吕祖谦综合思想中的唯一成分。
吕祖谦的家世和教育都很优越,所以他在科举和仕途上都很得意,发展比其他南宋主要道学家顺利。他在1163年考中进士,不久又获得博学宏词科的殊荣;宋朝300年历史中,只有34人曾登上博学宏词科。报考博学宏词科需要熟读大量典籍,范围涉及文学、历史以及历代制度,吕祖谦能荣登此科显示他一直究心学问研究,以及他对效忠皇帝有十分的热诚。吕祖谦登上博学宏词科后立刻踏上仕途,担任的职位多半是史官,但是他的双亲分别在1166年和1172年去世,他两次离职回乡守制。张栻等人在此期间经常造访,使吕祖谦与士大夫的关系得以维持不坠,所以他守丧期满后旋即被朝廷重新启用。
吕祖谦在1169年被任命为太学博士,随后出任位处京城南郊的严州州学。吕祖谦把金华书院的学规引进州学,当时张栻是严州的地方官,两人住得很近,可以每天相聚。1170年吕祖谦写作两篇有名的奏议,劝孝宗选用贤能,远离小人,矢志收复北方河山。不久,孝宗擢升他和尤袤为礼部考官,因此成为1172年进士会试的主考。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次考试的结果显示政治气氛转向,对道学群体非常有利。由于著名史学家李焘(1115—1184年)的推荐,吕祖谦被任命为太学博士,又兼任国史编修官以及实录院检讨官,主持徽宗(1100—1126年在位)实录的编纂。吕氏家人担任过几次类似的工作,吕夷简编修过太祖(960—976年在位)到真宗三朝的国史,吕公著则主编英宗(1063—1067年在位)和神宗(1067—1085年在位)实录,可见吕家编修实录的经验比时人丰富。由于徽宗实录会涉及北方沦陷的问题,所以这项工作在政治上很敏感。1177年实录完成,吕祖谦在呈献时,劝皇帝汲取经验教训,进行改革。孝宗再次提拔他,请他负责收集编纂北宋时期的杰出奏议、序跋和札记。他在这部汇集北宋政治智慧和文学典范的著作里,收录大量苏轼、王安石和欧阳修的文章,但也包含其他北宋人的作品。吕祖谦发扬一贯兼容并蓄的精神,不以人废言,只论文章的优劣,不管作者的政治和哲学立场。这部书完成后孝宗御赐《皇朝文鉴》的书名,并赏吕祖谦三百两银子,再度擢升他的官阶。
吕祖谦40岁的时候已经深受皇帝的敬重与信任,并和周必大等政府要员关系友好密切。吕祖谦的人缘良好,多少与他家人世代在朝任官有关。宋朝南迁后,吕家仍维持北方望族的习惯,与外地的名门大族联姻通婚。吕祖谦先娶韩元吉(1118—1187年)之女,后来又和芮烨(1114—1172年)的女儿结婚,韩、芮两姓不是金华同乡,但都是名门显宦。吕祖谦一直很密切注意朝廷的政局变化,不像朱熹不屑参政,但疾病使他的政治潜力未能完全发挥;他在1178年患病,次年辞去所有的官职,两年后就去世。
吕祖谦的一生都被病痛所困扰。父母于1166年和1172年去世,他两度返乡守孝三年。三个妻子都在生产后去世,子女中只有一男一女存活下来。从1157年他初次结婚,到1179年第三任妻子过世为止,总共只过了八年的婚姻生活,所以在第一次结婚后的3/4时间里,他是个孤独的鳏夫。吕祖谦从幼年起就病魔缠身,从症状来看似乎是年轻时得肺结核,40多岁时又中风。他抱怨右半身体虚弱疲惫、动作不灵,有时连饮食都无法自理,只能写很短的信。他在一封信中说:“药物日进三、四服,未尝废炙艾,医者或云血本少,用火则盖燥涸,以此犹未绝也。”①从他祖先和宋代士人的一般寿命来看,他应该还可以再活十几或二十几年,但是体弱多病以及守孝和丧妻的伤痛,都促使他在中壮之年就去世。
吕祖谦早年病中的反省却改变他的性格。他幼年时期脾气很坏,疾病又火上添油,甚至遇到不喜欢吃的东西就要摔盘子,但病痛没有妨碍他认真读书,朱熹说吕祖谦在病中也是书不离手。②《宋史》说吕祖谦“少卞急,一日,诵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③性格从此变成非常宽厚。吕祖谦家庭教育加强了他对政治和文化危机的社会责任感,他在有生之年的最后三个年头里,一直在金华专心教学研究,学生再度云集门下。这种门庭若市的盛况有诸多原因:吕祖谦具有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并且中过博学宏词科,此外还曾担任过太学博士,又主持过1172年的进士考试。他奉旨编修的书也受到广泛的好评,而且金华的书院离首都临安很近,从临安坐船逆流而上,最多四天就可以抵达金华。
吕祖谦的讲学有独到之处。他强调学生应该发掘新的观点,而不是一味墨守成规,他说:
今之为学,自初至长,多随所习熟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后有功。①
他也劝朱熹多教导学生在日用生活中作修养功夫,教学则应注意方向和顺序,他说:
致知、力行,本交相发,工夫初不可偏。学者若有实心,则讲贯玩索,固为进德之要。其间亦有一等后生,推求言句工夫常多,点检日用工夫常少。虽便略见仿佛,然终非实有诸己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训诱之际,愿常存此意。夫子教人亦有“可以语上”、“不可以语上”之别。……非谓使之但力行,而以致知为缓,但示之者,当循循有序耳。②
吕祖谦留意到若要寻求知识与实践的平衡,学生应该自己思考。
吕祖谦教过多少学生呢?1180年左右,丽泽书院有近300学生。③陈荣捷(1901—1994年)先生向来重视朱熹的成就,却也完全接受这个说法。④这300个学生外,还应该加上1180年以外的丽泽书院学生,1167年、1168年和1173年三年在明招山任教时的学生,以及严州官学的学生,总数至少上千人。即使只计算1180当年的300个学生,他也无疑是12世纪70年代最受欢迎的老师,与张栻在12世纪60年代所受的欢迎程度相当。
吕祖谦的学生人数和朱熹的学生人数相比呢?以现在的眼光回顾,朱熹是南宋时代最著名的老师,例如,陈荣捷先生在《朱子门人》中列出的467人中,①只有五人是在1167—1179年间列入门下。朱熹在南康重建白鹿洞书院后,又有35位年代可考的学生投入门下,另外9个本地学生从游的年代不明,即使把这9名学生都包括进去,朱熹在这15年内似乎只有49个学生,而吕祖谦在1180年一年里就有近300的学生。朱熹1181年所收的49个学生约占他学生总数的10%左右,这些数字虽然不完整,仍然明白显示朱熹的学生大部分是在1182年到1200年之间投入门下,亦即吕祖谦去世后的19年间所招收的。
吕祖谦在父丧不久后就再广收学生门徒,因此几个友人对他略有微词,但是没有人怀疑他的哀伤及孝思。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说:
〔吕祖谦〕尝与汪端明书曰:“刘子澄传道尊意,是时以四方士子业已会聚,难于遽已,今岁悉谢遣归。”祖望谨案:此即〔陆〕象山谓“伯恭在哀绖中,而户外屡恒满”者也。〔张〕南轩亦尝问朱子曰:“伯恭聚徒,世多议其非者。”观此条,则〔吕〕先生因〔汪〕玉山之言而止,亦善改过者。②
吕祖谦虽然把学生“悉谢遣归”,张栻仍认为他对这些学生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吕〕伯恭真不易得,向来聚徒颇众,今岁已谢遣。然渠犹谓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谓来者既为学业之故,先怀利心,恐难纳之于义。大抵渠凡事似于果断有所未足。③
有些学生当然只是为准备科举而入门进修,但必定也有被吕祖谦广博的学识和道德修养吸引来的学生。
吕祖谦有几部主要著作是根据讲稿编成的。他的《书经》讲词被学生编成《东莱书说》,他在太学时根据“为诸生课试之作”而编成《东莱博议》,尤其著名。①《东莱博议》虽然是学生用来准备科考的范文,但就像吕祖谦曾对张栻说的,里面的文章也教导学生道德原则和历史教训。吕祖谦对追求“道”的一心投入很能表现道学群体的共同特点,他明白宣言:“坚任道之志,而致察理之力,乃区区所望。”②许多儒家学者偏离儒家正道的时候,这种对道投入奉献的热诚尤其重要,吕祖谦向朱熹说:
论学之难,高者其病堕于玄虚,平者其末流于章句。二者之失,高者便入于异端,平者浸失其传,犹为惇训,故勤行义。轻重不同,然要皆是偏。③
再三强调当日学者治学方法褊狭的弊病。
吕祖谦认为当时不友善的气氛四处弥漫,有些登门求教的学生也感染这种态度,使儒学之道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从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实者,所宜深察。往时固有得前辈言语声欬以借口,而行则不掩焉。媢嫉者往往指摘此辈,以姗侮吾道,绍兴之初是也。虽有教无类,然今日此道单微,排毁者举目皆是,恐须谨严也。④
吕祖谦尤其担心自称道学弟子的人行为不轨,提供敌人攻讦的口实。现有的材料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我们知道陈公辅曾经向道学示好,批评“王安石学行之误”,可是他后来态度一变,在1136年上书高宗,嘲笑道学“狂言怪语,淫说鄙论……幅巾大袖,高视阔步”⑤。吕祖谦的忧虑与其他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教派(fundamentalistsects)颇为类似,而他明确表现这种忧虑。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是最宽厚开明的道学领袖,而且政治地位最为稳固,甚至敢公开宣扬他在评阅进士试卷时,认出陆九渊的文章。
吕祖谦虽然有时表现出很深沉的忧虑,但对扭转恶劣的环境更表乐观。他鼓励学生潘景宪(叔度,1134—1190年)加强责任感:
大抵讲论治道,不当言主意难移,当思臣道未尽。不当思邪说难胜,当思正道未明。盖工夫到此,必有应,原不在外也。①
吕祖谦认为士大夫应该负起实际行动的责任,不应该只是坐论空谈、抱怨世道人心不古:“士大夫喜言风俗不好。风俗是谁做来?身便是风俗,不自去做,如何得会好?”②他还批评秦汉以后的士大夫:“外风俗而论政事。”③吕祖谦认为讲学是解决当时各种问题的关键:
尝思时事所以艰难,风俗所以浇薄,推其病源,皆由讲学不明之故。若使讲学者多,其达也,自上而下,为势固易;虽不幸皆穷,然善类既多,气焰必大,熏蒸上腾,亦有转移之理。④
吕祖谦的政治学术生涯显示,他希望从朝廷开始,由上而下影响世道风俗,在社会上培养正直奉献的儒者,从而改造社会、政治,使它们符合道的理想。吕祖谦对教导士子应试的态度比张栻、朱熹积极,认为科举的成功可以使他们从政治中心改造影响社会。这种对体制内改革的信心,无疑深受出身仕宦家庭的背景影响。
吕祖谦为教导学生进入体制内工作,在金华书院的课程里对政府各种制度进行详尽的分析,这套教材流传使用150年后,才被后代门人编成《历代制度详说》出版。吕祖谦叙述评论历代制度,讨论的题目包括:学校、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荒政、田制、屯田、兵制、马政、考绩、宗室和祀事。吕祖谦不但分析各种制度在历史上的优缺点,而且讨论它们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情况,他的判断多基于现实条件而非空泛的理论。例如,他认为当时百姓有自由买卖土地的权利,所以张载、胡宏等学者要想在全国实行井田制度,只不过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①
吕祖谦在其他著作中讨论到法治的问题。许多儒家士大夫重德治而轻视法治,吕祖谦却很肯定法律的功用。②他认为一般人反对用法,因为他们心里想的是申韩之法,其实法律的本质与申韩之法不同:“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韩深刻之书,此殊未然。人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会看得仁义之气,蔼然在其中,但续降者有时务快,多过法耳。”③法律应该建立在人情物理和仁义的基础上,而不是系于人主的好恶。法律的“仁义之气”不是抽象的理论,应该是实在的东西,有时必须用严刑峻法吓阻不法,才能达到仁的目的。法律如果太宽松,违法犯禁的人会增加,结果受法律制裁的人反而比较多。这些观点虽然都是从政府的立场出发,但他也主张公私应该并重:
世俗多谓公私不两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则公私两全;否则公私两失。……庶或公不败事,私不伤义,便是忠厚底气象。④
有人也许会怀疑吕祖谦强调法治和主张公私并顾,只是反映岀权贵大家的背景观点。当然对吕氏这种家族而言,主张忠君和善待私家既是理想,也有实际利益的成分。假如硬要说他注重法制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许多统治阶级成员比较不注重法制和私人利益,又做何解释呢?吕祖谦和一般儒家学者都认为道德是治国的根本,但注重法制和私家利益是他的一大特点,而其他的浙东儒者也持相似的看法,陈傅良和陈亮的立场更鲜明,尤其是陈亮的例子,更能明确说明浙东学派如何寻求公(社会或国家利益)和私(或家庭利益)之间的平衡。
吕祖谦与其他浙东学者经常批评当时的风气太重文轻武,吕祖谦却编辑宋代最重要的文选之一《宋文鉴》,而且也是当时的文学大家,所以他反对重文轻武,并不是要以重武轻文的政策取而代之。浙东学者经常批评宋太祖把武官地位降到文官之下,并把兵权从武官手里转到文官手里。吕祖谦和他的浙东友人认为文武应该均衡合一。他引证古史说:
自古文武只一道。尧舜三代之时,公卿大夫在内则理政事,在外则掌征伐。孔子之时,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劫舍,孔子亦自当夹谷之会。西汉尤知此理,大臣韩安国之徒,亦出守边。东汉流品始分,刘巴轻张飞矣。①
东汉以后文学日兴,而文武之途渐分,历史提供许多徒重虚文而导致祸害的教训。吕祖谦又在《东莱博议·魏懿公好鹤》中用魏懿公(公元前668—前660年在位)好鹤的典故,讽喻许多近世的士大夫与魏懿公的鹤没有什么区别:
永嘉之季,清言者满朝。一觞一咏,傲睨万物。旷怀雅量,独立风尘之表。神峰隽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乱,屠之不啻机上肉,是亦懿公之鹤也。普通之际,朝谈释而暮言老,环坐听讲,迭问更难,国殆成俗。一旦侯景逼台城,士大夫习于骄惰,至不能跨马,束手就
①《宋元学案》,卷51,页1661。按:诸葛亮曾为此责备刘巴;参见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39,页982,注3。
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鹤也。①
吕祖谦的祖先来自北方,他虽然多病,但可能学过骑马,所以讽刺不会骑马的南方文人。玩马球的风气在宋代衰落,士大夫子弟只爱在院里街中安然踢球,可以想见骑术退步的情形。②吕祖谦承认这些士大夫并非全无可取之处:“是数国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词藻,望其威仪,接其议论,挹其风度,可嘉可仰,可慕可亲。”然而“卒然临之以患难,则异于懿公之鹤者几希”③。
从历史中寻找实际教训也是吕祖谦和其他浙东学者的重大相似处。他认为读史时应该厘清时代背景,设身处地从前人的经验中汲取教训:
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④
又说:
看史须看一半便揜卷,料其后成败如何。其大要有六:择善、警戒、阃范、治体、议论、处事。⑤
吕祖谦认为吸收道德教训是读史的目的之一,但他更注重从历史中获得实际事功的借鉴,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并不限于道德的教训,还认为读史应要注重变化发展,不能只求博闻强记。他说:
陈莹中尝谓《通鉴》如药山,随取随得。然虽是药山,又须是会采。若不能采,不过博闻强记而已。壶丘子问于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对曰:“人之所游,观其所见;我之所游,观其所变。”此可取以为史之法。①
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变化,他说:“此事极,则须有人变之,无人变,则其势自变。”②齐桓公(公元前684—前642年在位)就是不懂局势的变化而招致祸害。他标榜“尊王攘夷”,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人,在葵丘之会达到成就高峰后,却变得傲慢堕落,种下霸业衰落的种子。吕祖谦认为齐桓公历史的教训在于:
〔齐桓公〕抑不知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强而止于强,必不能保其强也。霸而止于霸,必不能保其霸也。驱骏马而驰峻阪,中间岂有驻足之地乎?③吕祖谦指出齐桓公由盛而衰的模式,并可见于汉人与胡人互动的历史。
吕祖谦认为,学者在寻找历史的发展变化模式时,也应该了解每个时代的特性。权力结构不同,治国的方法也不同;例如在读《左传》时,学者应该把春秋时代划分成三个时期:五霸兴起前、五霸时期和五霸衰落后的时期。吕祖谦用权力结构划分历史,并不表示他认为统治阶级是决定历史的最终力量,他依然遵循孔子、孟子的传统,认为国家的兴亡最终取决于人民。
吕祖谦着眼于权力结构来为历史分期断限,并以此讨论过去的种种制度是否适用于宋代的现实状况。例如张载、胡宏等人主张恢复井田,吕祖谦则认为宋代距离井田制度的时代已将近两千年,历史条件改变太多,不可能恢复这种古代制度。与其固执古人的制度,不如改变旧制以完成古人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国家太平。④他一再强调唯有了解历史背景,才能善用历史知识。
由于史书质量的参差不齐,有的泛泛阅览即可,有的则须一字一句小心谨读。几部最重要的史书更应该以读经的态度来读:“学者观史各有详略,如《左传》、《史记》、《前汉》三者,皆当精熟细看,反复考究,真不可一字草草。”①《后汉书》以后的史书品质大半不高,可以在上面少花些时间。吕祖谦也用史学家的眼光看待儒家经典,开清代浙东史家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先河:“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②又说:“观史先自《书》始,然后次及《左氏》、《通鉴》,欲其体统源流相接。”③这三段话里提到《左传》两次,可见《左传》在他的史学里占有中心地位。
吕祖谦认为《左传》是非常重要的史书,所以把它当成一部独立的著作,而不把它视为《春秋》的注解。他如此重视《左传》,但没有因此对《春秋》减低兴趣;《春秋》是宋代学者最重视的经典之一,产生至少240部相关的著作,数量超过其他任何经学著作。吕祖谦继承北宋孙复等学者的立场,强调《春秋》“尊王攘夷”的大义。④吕祖谦对《左传》的看法比较独到,除写过《东莱博议》外,另有《春秋左氏传说》和《东莱吕太史春秋左传类编》等两部与《左传》有关的著作。吕祖谦注意《左传》的细节,从中得出很多重要的结论。例如,他计算周朝将领的名字,证明周朝王室的军队确实越来越少,所以吕祖谦认为《左传》延续六经,继续记载古代的事物制度。
吕祖谦为延续《左传》的记录,开始撰写《大事记》,并在注释里评论各种事物和讨论史学得失。《大事记》大量取材司马迁(公元前145—前90年)的《史记》,写作的方法也很受《史记》纪传体例的影响。他不但用《史记》和其他早期的材料纠正《资治通鉴》的细节,而且写了两部批评《通鉴》的专著,可惜这两部书都未能保存至今。①吕祖谦打算用《大事记》取代《通鉴》,但只写到公元前90年,就不得不因病搁笔,留下一千多年的空白。不过他完成了《十七史详解》,可以用它为基础完成《大事记》。从《大事记》的结构及一些论述可以看出吕祖谦史学的一些特点,例如,他不像朱熹死抱着正统问题不放。吕祖谦在写《三国史详解》时,以曹操(155—220年)为正统,替魏国写纪,蜀汉的刘备(161—223年)和诸葛亮等人只有传。②这种务实的历史写作方式比较接近司马光,与朱熹的距离比较远。吕祖谦之后的浙东学者也倾向司马迁那种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但他们没有为吕祖谦继续完成《大事记》。
比较注意哲学问题是吕祖谦与同时的浙东学者不同的地方。浙东儒者一般较鲜论及性、命、心等题目,这些题目却是吕祖谦思想的重要部分。对于心的问题,吕祖谦注重孟子所讲的“本心”,追随孟子教人先寻回本心,因为它是一切学问和道德实践的基础。吕祖谦在孟子的“本心”的概念上,加上道学的“理”的概念:“凡人未尝无良知良能也。若能知所以养之,则此理自存,至于生生不穷矣。”③人若能存养此天理,则不需再向外寻求:“本不在外,自求而已”,所以“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④。反躬自省非常重要,因为外在的世界是人内心世界的反映:“近日思得内外相应,不差毫发。外有龃龉,即内有窒碍。只有‘反己’两字,更无别法也。”⑤吕祖谦对自省有强烈的信心,但告诫世人不要仰赖顿悟:“致知与求见不同。人能朝思于斯,夕于斯,一旦豁然有见,却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须是下集义工夫,涵养体察,平稳妥帖,释然心解,乃是。”⑥吕祖谦虽然在此似乎很重视内向的反省与直观的方法,但在他的思想体系里,格物的地位更加重要。这点明确显示在他对名物制度和历史研究的专心一致上;朱熹批评吕本中深染大慧禅的色彩,但很难如此批评吕祖谦。
吕祖谦也遵循孟子的观点主张性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中正仁义之体,而万物之一源也。中则无不正矣。”①他借用张载和二程的气禀论解释恶的存在:“性本善,但气质有偏,固才与性,亦流而偏耳。”②吕祖谦以此为基础,认为功夫修养的关键在于存养本心,使本心不被不正当的欲望干扰:“此心常操而存,则心宽体胖,怡愉安泰。福本自内有,若一欲败度纵败礼,则祸自外来。”③(按:“纵”疑当在“一”字前。)在存心和去除欲望方面,吕祖谦的功夫修养观与张栻和朱熹很相近,不过他不像张、朱那样深入讨论修养功夫各个阶段的细节。但我们在讨论“胡子知言疑义”时已经说过,在吕、张、朱三位学者中,吕祖谦最坚持功夫的涵养与体验要维持平衡,④日后朱熹却最以此著称。
吕祖谦与其他道学家认为仁是四德及一切道德行为的基础,他在讲解《孟子》时曾经说:
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尽了。更说礼字,又可以知其等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与礼,更有甚事。⑤
礼在吕祖谦思想中有关键性的地位,认为礼不但是理,而且也是养心的必须之具。⑥他注重礼,而且认为仁与礼具有互相联系的关系,但仁仍无疑比礼更为根本:
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是理,在我习矣而著,行矣而察,否则礼乐虽未尝废于天下,而我无是理,则与礼乐判然二物耳。①
吕祖谦继承家族一贯注重忠孝的传统,但是他把忠孝及其他道德行为都归于仁的范围,而且是从仁而来:“孝、弟,所以为仁也。体爱亲敬长之心,存主而扩充之,仁其可知矣。”②显示他既与张栻都认为仁就是心,也与朱熹一样认为仁就是理。吕祖谦有些论点更能显示与张栻、朱熹的共通处,但他更接近朱熹。吕祖谦与张栻都认为仁就是孟子所说的“本心”:“仁是人之本心,浑然一体。”③而且仁的特点包括“公”和“一”:
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见至明。而此心不变,譬如镜之照物,惟其无私,而物之妍丑,自不能逃。虽千百遍照之,其妍丑固自若也。惟仁者能好恶人,亦如是而已。④
他写信给朱熹时,又曾经以朱熹使用的比喻讲解仁与爱的关系:
盖爱者,仁之发;仁者,爱之理。体用未尝相离,而亦未尝相侵。所私窃虑者,此本讲论形容之语,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缘指出分明,学者便有容易领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原殆(始)不可不谨也。⑤
吕祖谦认为求仁的关键是“居敬”和“存诚”,一般湖南道学家所讲的“敬”近于“恭敬”,而吕祖谦所讲的“敬”则较近“严肃认真”的意思,他尤其注重专“一”和“诚”:
敬之一字,乃学者入道之门。敬也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大学》曰:“君之无所不用其极”,盖非特一事当然也,凡事皆若是而后可。①有人问:“诚、敬两字有异否?”他回答说:“只是一般。所谓存诚,存便是敬。”②所以吕祖谦对功夫修养问题的看法与程颐和朱熹见解一样,三位学者都强调“敬”。总而言之,他努力追求书本学问、治国与功夫修养三者间的均衡。
吕祖谦的学问广博,使他有时似乎自相矛盾,因为他的许多看法和不同的儒家学者相近,而这些学者的学术各自发展,在日后变得互相矛盾。某些现代学者把吕祖谦说成没有高深理论成就的史学家,其实是不公平的论断。他的家学风格和个人性格都倾向于在异中求同,以寻求儒学同道的和谐统一。如果现代学者能像研究朱熹那样仔细研究吕祖谦的著作,我们或许能更清楚把握他的思想脉络和结构。现代学者尚未对吕祖谦做恰如其分的研究,或多或少也与他广博的学识和庞大的著作有关,使他比同时代的学者更难以为人了解。
吕祖谦比朱熹和张栻年轻,而且考上进士的年代也比较晚,但是从12世纪60年代晚期起,他就是道学的主要领袖,而且地位一直维持到1181年去世为止。吕祖谦的道德学问及政治社会地位吸引大量的学生,对道学的成长贡献良多。政府为科举阅卷能够公平,订定许多誊抄卷子和糊名的规则,防止主考认出考生的卷子。吕祖谦对个人文风极为敏感,能在担任主考时录取许多道学家,数目之多超过整个宋朝其他任何一次进士考试。政府和社会评论素来严厉制裁偏颇的主考,吕祖谦却敢公开说他认出陆九渊的考卷,而且没有因此受到制裁,1172年的进士考试证明他在政府和社会上的特殊地位。朱熹在与张栻的交往论学中,到1173年已经渐渐取得支配的地位,但他从来不能够支配吕祖谦的思想。朱熹在道学同道中的影响力超越吕祖谦,是吕氏去世后的事情,假如多活20年的是吕祖谦而不是朱熹,吕祖谦的思想对宋代文化界和宋以后文化史的影响或许会大不相同,至少宋代的政治气氛必然会有所不同,因为吕祖谦比其他道学家更受朝廷官员尊敬。即使两人都活到1200年,朱熹的理论和行为也会甚受吕祖谦影响,因为从1163年起到吕祖谦1181年去世为止,两人一直相互影响甚巨。
第五章 朱熹与吕祖谦
朱熹和吕祖谦曾就社会、政治、教育和哲学等问题交换过许多意见,若能适切考查这些意见交流,对了解双方的互相影响应该颇有帮助。朱熹和吕祖谦的关系显示吕祖谦在1168年到1181年期间是道学最重要的领袖,朱熹在这时期对吕祖谦的温和态度,与日后对亡友的尖锐批评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态度的转变以及他与吕氏的朋友关系,显示了朱熹在吕祖谦去世前后与整个儒家群体的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吕祖谦大概是朱熹最亲近的朋友。朱熹在1156年任职于同安县时,曾经因公事前往吕祖谦父亲任官的福州,得以认识吕祖谦,两人开始书信往来。在12世纪60年代末,尤其是70年代,两人的书信往返激增。朱熹在1181年接到吕祖谦最后一封信不久后,获悉挚友去世的消息。他们的友谊维持得很久,比朱熹与张栻的关系还要长八年,这或许与吕祖谦的家在金华有关。金华距离京城临安很近,又在临安前往福建的路上,所以两人相处的机会自然比较多。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件尚存104封,比写给其他人的都多。吕祖谦写给朱熹的信则有67封流传下来,也比给其他人的信函多一倍有余。①双方信函交往频繁外,亲近的关系也可以从所讨论的事情中可见一斑,不但涉及政治学术的问题,也谈到许多家庭事务,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朱熹的长子朱塾(1153—1191年)的事。朱熹给吕祖谦的信中说:“此儿懒惰之甚,在家读书,绝不成伦理。”①这个儿子虽然有些恶习,但朱熹担心自己由于父子关系而爱深责切,对孩子管教过严,因此采纳孟子“易子而教”的建议,委托吕祖谦负责儿子的教育和道德修养。1173年朱塾21岁的时候,朱熹把他送到吕祖谦那里,并且严格要求他在那里不许常常喝酒。吕祖谦安排他住在亲近的学生潘景宪(1137—1193年)家,规定他不能单独离家,每天都要和潘景宪一起面见吕祖谦,聆听教训。三四年后,吕祖谦促成朱、潘两家联姻。
朱塾迎娶潘景宪的长女(生于1161年),不久后吕祖谦把独女华年(生于1159年)嫁给潘景宪的近亲潘景良,所以吕祖谦和朱家都与婺州的大族潘家结为姻亲。朱塾在1180年回到朱家,第三次参加科举考试,仍然失败落第。后来朱熹利用官荫的权利,使朱塾挂上朝廷礼官的头衔,但是这个儿子仍然不成大器,在官场上终无建树,1191年在婺州的岳家去世。朱熹把儿子交给吕祖谦管教,不只因为吕祖谦的社会名望和政治地位崇高,朱熹也信任他的学术水平和个人修养,希望能够改变儿子的脾气和行为。吕祖谦不但负责教育朱熹的长子,并且替他安排婚姻,的确帮了朱熹大忙。
吕祖谦也充当朱熹与许多儒生学者间的桥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陆九渊。吕祖谦在1172年提拔陆九渊通过进士考试后,就一直照顾他,并且为调解朱陆双方的思想分歧,在1175年春邀请他们到他家来会面,朱熹因故不能前来,吕祖谦就专程赶去看望。他从金华出发,行程约250公里,赶到朱熹在福建崇安的家,随后俩人一起去朱熹的寒泉精舍,在那里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完成《近思录》的初稿。他们又一起翻越武夷山,到达江西名胜鹅湖寺,会见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吕祖谦希望陆氏兄弟和朱熹能够建立友好的关系,居中协调他们对读书和功夫修养的看法。在从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鹅湖之会是朱陆学派分道扬镳的分水岭。吕祖谦的性格和居中协调的努力犹能暂时缓减道学内部的紧张关系。第九章会再谈到吕祖谦在鹅湖之会后的六年里,一直引导陆九渊兄弟,使他们比较能接受他与朱熹的共同观点。
一、社会政治问题
南宋的国家大事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对付占据北方的金人,吕祖谦一家和朱熹的父亲及其他道学人士一样,也直言不讳批评秦桧与他的和议政策。吕家家人甚至曾亲身参与朝廷变迁中一些最重要的事件,尤其吕好问曾短暂做过兵部尚书,并陪同皇帝前往金营投降。金人将吕好问送回开封,命令他协助张邦昌的傀儡政权,但他竟然说服当权者扶立宋皇室唯一没有被俘的皇子。宋高宗在南方再建政权,曾经对吕好问说:“宗庙获全,卿之力也。”①随后任命吕好问为尚书右丞。然而吕好问曾经在北方傀儡政权任职,招致许多批评,因此随即转任不太重要的职位;吕好问的儿子吕本中也与秦桧不和而去职。吕本中虽然反对秦桧的和金政策,主张收复北方,但终究是个务实的人,认为金人的军事力量强大,所以建议高宗不要贸然采取军事行动,应该巩固国力,保卫南方。②吕祖谦承袭吕本中的观点,主张要先改革朝政、加强国力,准备充足后才能发动攻势。他采取主和、主战两派间的温和中间路线,③可与张栻后来的成熟看法相提并论。
朱熹年轻时坚决主战,在12世纪60年代上书提倡军事反攻,严厉谴责所有的议和派人士;但中年以后,体认金人的军力强大,态度开始冷静下来,类似吕祖谦的务实观点,逐渐取代主战的立场。他虽然终生不忘收复失土,但晚年对主战派的抨击比对主和派的攻击还要强烈,而且开始体认到至少需要10—30年的准备,才能收复北方。朱熹在思想成熟后,更强调防守和自强的立场:
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①他60多岁的时候,可能变得比吕祖谦更重防守和谨慎,但吕祖谦的立场显然曾影响朱熹。
当时内政的主要问题是减轻农民的负担。1167年福建崇安县县令请求刘如愚(1142年进士)与朱熹支援赈灾,朱熹从邻近的建阳县调请救灾物资,他的朋友魏掞之(1116—1173年)早在12世纪50年代初期已在当地建立良好的社仓制度。州知府王淮(1127—1187年)在1168年建议刘如愚和朱熹保留百姓偿还的贷款,以供紧急不时之需。刘如愚与朱熹根据魏掞之的先例,建议设立社仓,获得州府拨给赞助费用。崇安的社仓在1171年建立完成,由刘如愚的亲戚负责掌管,但后代人把社仓主要归功于朱熹。②
政府的义仓主要是在灾荒时,以直接发放实物或稳定市价的办法帮助农民,但由于官僚作风作梗,官方义仓的效率很低,涵盖范围也只限于城镇附近,且常由村吏或佛教僧侣负责分发赈灾物资。朱熹反对佛教僧侣参与,努力动员儒生参加这类社会活动,相信参与社仓可以培养同道的认同感以及对仁的体认。朱熹进行这项工作时,正是宋代民间社会意识日益增长抬头的时候,例如,婺州的乡村已经自组互助制度,而有的组织成为社仓的基础。①
朱熹的社仓遭到某些人批评指责,认为他仿效王安石“青苗法”的借贷办法,连张栻也不免有此疑虑,吕祖谦则挺身为朱熹辩护。朱熹和王安石都使用政府的资金作基金,要求借款人偿还贷款、支付利息。②朱熹在1185年所写的“婺州金华县社仓记”中,反对别人将他与王安石的办法相提并论,指出他出借谷物,而不是出借现金,实施的方式是以乡镇为基本单位,不是以县为单位,并且由当地士人管理,目的是稳定农民经济,不是增加政府的收入。朱熹再三提到吕祖谦巡视崇安后,称赞社仓能师法古人的美意,是受古人启发,与王安石的失败实验不同。吕祖谦并表示要在金华建立社仓,而朱熹这篇文章就是为潘景宪主持的金华社仓的成立启用而写作的,赞扬潘景宪实现老师的夙愿。③先前吕祖谦曾安排朱熹的儿子朱塾住在潘景宪家,并让他迎娶潘景宪的长女。朱熹在1182年办理赈灾事务时,也获得与吕祖谦有关系的婺州士人帮助。
孝宗皇帝虽然赞扬朱熹的社仓制度,并且要将它推行到全国各地,但由于反对者阻止政府的支持,最后成立的社仓很少。除朱熹家乡的社仓外,金华社仓可能持续得最久。不过到13世纪中叶,地方胥吏开始接管金华的社仓,只在荒年发放谷物,并且要求以现金偿还借贷的谷物,朱熹希望由儒家君子长年监督救济照顾农民的设想,从此变成地方官僚系统赈灾的另外一个工具。①朱熹倡导的社仓只短暂按照计划发挥作用,但已体现他政治理想的实践。魏掞之的社仓建立时间更早,刘如愚在“朱熹社仓”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及吕祖谦的襄助,使社仓传播到金华,都显示后人所谓的“朱子社仓”并不是朱熹一人的功劳,而是道学人士合作应付需要而进行的社会福利事业。从朱熹担任地方官时写的“劝立社仓榜”等文,以及他支持吕大钧(1030—1081年)的乡约,可以看出他非常关注建立地方社群组织,②乡约成为鼓励乡民行善的地方社会组织。
二、书院与教育
朱熹与吕祖谦关心许多地方小区建设的事务,但最关注文人知识分子群体的建立,而书院、精舍是实现这一目标最重要的组织。吕祖谦在1166年母亲去世后,选择明招山母亲的墓地附近建立一座精舍,并且在当地教导后学。朱熹的母亲于1169年9月去世,他次年也在母亲墓地不远处建立寒泉精舍。吕祖谦返家后,以当时无比丰富的家庭藏书为基础,在金华城内成立丽泽书院;由于他的声望以及校址方便,当时有300多学生同时在此就学。
朱熹1179年在江西南康任职时,也营建一座书院。他写信给吕祖谦讨论兴建的计划,并要求吕祖谦为书院撰写铭文。朱熹表示任职期间,每四五天就要到官学一次。官方开办学校是为让学生准备应试科举,朱熹却很遗憾县内三所学校都是为准备科举而设置的。他在官学中讲解经典中的道德原理,并且明确地对官学的教学内容发表意见。①太学官员杨大发(1175年进士)大概对朱熹干涉学校很不满,向吕祖谦抱怨。吕祖谦得知朱、杨双方紧张关系后,写信给朱熹,提醒他不要干涉学校教师的做法。
朱熹在回信中为他在官学的行为辩解:
学中向来略为说《大学》,近已终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论语》,诸生说未到处略为发明,兼亦未尝辄升讲座、侵官渎告,如来教所虑也。②朱熹对外人的批评表示不满,声称自己只是想仿效汉代的文翁,做一点补益的工作。文翁的教化功德备受赞扬,后人认为他将孔孟之道传给四川百姓,例如杜甫(712—770年)曾说过:“文翁儒化成。”③朱熹表示南康地区佛教和道教寺院为数极多,所以他的行动尤其有必要。
朱熹又在庐山重建白鹿洞书院以振兴儒家传统。④这座书院坐落在距南康城十几里的一个山谷,在十、十一两世纪盛极一时,宋太宗(976—997年在位)甚至曾经赐给书院一套儒家典籍。11世纪朝廷下令所有州和部分县建立官学,以培养科举人才。固然并非所有州县都能建立官学,但兴建的风气在11世纪中期达到高潮,12世纪初的头25年时间里,又再现一次高峰。北宋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官学,私学因此没落萧条,朱熹在1179年甚至得请樵夫帮忙,才找到白鹿洞书院的旧址。他上书朝廷要求资助重建这座书院,因为它象征儒家教育与文人价值,否则就只有任异教在山中林立。
这座书院获得朝廷同意后不到六个月就完成修建,并在1180年3月开放讲学,恰好是朱熹到任南康的第十二个月;努力一年就获得授权重建。白鹿洞书院除获得私人和朝廷的资助,地方政府也拨给田地作为学田,地方文人和皇室也捐赠书籍。它的重建与12世纪60年代岳麓书院的修复有相似之处,只是岳麓书院的重建被渲染得更多。孝宗时期(1162—1189年)重建或兴建很多书院,而宋代的私人书院总数至少有375个。①
以朝廷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而言,朱熹应该满意进展,事实却不然。他经常抱怨一些官员阻止计划,有人推测这位不知名的官员是杨大发,因为他不满朱熹干涉官学。不过杨大发是朱熹指派监督工程的两人之一,朱熹和他也有诗文往来,吕祖谦介入调解,必然缓和两人的紧张关系。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中至少有五封提到杨大发,还数度赞扬杨大发建庙纪念周敦颐以及六位当地的杰出人士。②建庙是朱熹计划中的重要的部分,希望以此增强当地百姓的儒家道德观念,并使地方儒生学士更能团结。如果杨大发阻挠计划,朱熹应该会在文章中否定杨大发,不会数度称赞他。杨大发虽然在15年后反对道学,但是白鹿洞的共事早已时过境迁,不应该根据后来紧张的环境衡量早期的关系。
一位美国汉学家的研究指出,朱熹有些言语显示,“别人抨击他重建书院的方式以及教学方法,使朱熹深感愤怒”①。可以使我们更了解朱熹的性格。或许因为他在此以前只担任过一项职务,而且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因此对书院的拖延和问题感到不耐烦,尤其政府的官学只在书院十来里外的地方,位置更加方便,他实在需要寻找理由使用政府资源,说服地方文人捐助修建一座新的书院。所以,朱熹在给朝廷的文书中,一再强调书院重要的历史及象征意义,却很少提及书院教学的活动;给朋友的书信则直率表达他对教育的使命感。道学人士普遍担心科举对士人文化的影响,但白鹿洞书院也花费近1/3的时间准备科举。除了朱熹自己的述说,并没有其他证据显示有人反对重建这座书院,所以朱熹的抱怨大概可以反映出他行事不老练,或者误解现实政策,与吕祖谦和张栻在政府任职的情况相比较,他这方面的不足更为明显。
朱熹强调建立制度,并且获得政府的资助,所以白鹿洞书院的地位比当时其他书院更为稳固。私人的努力与资金不足以建设书院,因此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成为朝廷和道学人士在13世纪关系改善以后合作的范例。朱熹为书院制定的行为规范为日后书院的发展开创先例,与官学的繁文缛节相较,朱熹希望造成学生承担更多责任的气氛。他把一篇训词贴在大门门楣上,要求学生学习古人的行为准则:
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则夫思虑云为之际。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必有严于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诸君其亦念之哉!②
朱熹希望学生能够修养道德,他警告说如果不然,就得接受官学里的规定。他的学生程端蒙在1187年制定一些细则,以补充朱熹的学规,不过朱熹觉得细则只能用于层次比较低的学生,①而白鹿洞书院的学生已经受过官学或私塾的纪律培养,是层次很高的学者。
朱熹陈述的规则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总结,并且成为这座书院的“学规”。这些规则都很简明扼要,除一条规则外其他都取自经典。首先规定最根本的基础,人际最基本的五伦关系,取自《孟子·滕文公上》,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具有这些品德的人才可以开始学习。其次,关于学习的次序,取自《中庸》第二十章:“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第三,关于功夫修养的关键,取自《论语·卫灵公》:“言忠信,行笃敬。”以及《易经》损益二卦象传:“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第四,引用董仲舒(公元前176—前104年)的话:“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为处世态度的准则。第五,谈到与人相处之道,引用《论语·卫灵公》上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孟子·离娄上》中的话:“行有不得,反求诸己。”②所以从第三段到第五段都是解释学习的要点,因为“学”主要是对道德原理的自我修养。
朱熹的学规不仅要有别于官学的繁琐规定,也要在佛教戒律外树立新的途径。朱熹不喜欢佛教,但他和其他儒生学士大都很欣赏禅宗的戒律。此外,朱熹的学规谈到互相鼓励道德修养,和吕大钧的乡约有相似之处。
朱熹更直接的灵感应该是吕祖谦的书院学规。吕祖谦在1167年写下他的书院规范,并在1170年前修改两次,所以这些条文比朱熹的学规早将近12年。强调在儒家生活规范中体认道德修养,是这两种学规最基本的相似处。吕祖谦在1168年立下学生需要遵守的基本常规:“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他除将这些重要的儒家道德列作人际关系的准则外,还阐释入书院学习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①如果书院学生违反上述条文,同学会加以劝诫,如果不能起作用,同学就要开会讨论他犯的过错。如果仍然不改过向善,书院就要将他除名。吕祖谦的规则与12年后的朱熹学规一样,都希望能够引导学生自我修养,鼓励学生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似乎都简单地将道德行为与学问视为一事,因此有人或许会认为他们将学问化约成道德伦理的领域,朱熹学规的倾向尤其明显。他们表面似乎将道德修养当做学问的主要内容,但不应该简单地认为他们的学问最终的目的仅是实践道德行为,这解释过于简单,会贬低他们更广泛的课程以及实践的目的。整体观察他们的思想和文章,显示他们对学问和儒家传统的看法其实包含其他的内容。
吕祖谦与朱熹后期的学规不同,他特别详细规定学生的行为细节。有些条文规定学生间相处,要根据年龄大小称呼对方,不能谄媚或贬抑别人,也要遵守预习和讨论的规定。例如,学生得记录课堂上或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当做小组讨论的依据,还必须在笔记上签字显示哪些问题已经讨论过。
吕祖谦认为,使学生具有群体意识十分重要,可以使学生“勿狎非类”。所谓“非类”的意思并不太清楚,但是吕祖谦似乎努力减少学生遭受来自团体外的影响。吕祖谦虽然比较开明,可是排外倾向如此明显,显示道学同道有与别的团体划清界限的普遍倾向。他们与书院外的乡绅来往十分谨慎,尽量避免联系与冲突。例如,吕祖谦规定学生不许向官员送礼或关说,告诫学生要讲地方政府和官吏的好处,不可议论他们的是非。学生与其他社会人物接触时,不能与酗酒、赌博、打架或阅读不正经书籍的人交往,而且必须与家庭保持密切的联系。吕祖谦严格要求学生和父母同住,遵守正确的丧葬礼节,避免为钱财与宗族争执。其他方面还包括在课堂上要严肃认真,学习必须勤奋。学生在一年内不能有100天以上的时间不在书院,每年至少要拜访以往的师长一次。如果在路上遇到老师,要行特殊的礼节表示敬意。①这些规定的目的是维系书院的团结。
朱熹的学规比较注重基本原则,而吕祖谦的学规则比较强调行为规范;朱熹强调理论,吕祖谦侧重实践。如果指责朱熹的学规缺乏实践的意义,倒也有些言过其实,因为他强调遵守孝道。然而,他们所强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确实有明显的区别,朱熹的规范简约,且多取自经典;吕祖谦的学规详细周到,起头是总论,继以个别条文。朱熹的条文更为精致、系统,从道德修养的最基本的德目开始,结尾以三段话阐释学问的要务。两人目的都是组织学生,以研习经典及基本人伦关系的方式,学习儒家学说的真理;所以绾合儒家的团体是他们共同的主要目的之一。朱熹简练的学规名声日起,其他书院也相继采用,这份学规与吕祖谦早年学规的相似之处,再次显示吕祖谦在朱熹的贡献中发挥过作用。
吕祖谦应朱熹的要求而写作“白鹿洞书院记”,文中说重建书院的目的众所周知,朱熹对这份题记做大量评注,并将最后定稿刻在书院石碑上。他们提到重建书院的三个目的是要面对三项挑战:佛、道二教的竞争、改进教育制度以及弘扬儒学。吕祖谦讲他们都批评王安石新法中教育制度的弊病,反对学校太注重科举文章的习作,而倾向程颢的做法,以书院培养学生,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和道德教育。根据吕祖谦的想法,这座书院会精研二程和张载的学说。②
三、重建道学传统
朱熹在1173年编辑《伊洛渊源录》时,更进一步强调二程以及他们最亲密的友人、学生是一支鲜明的儒学传统。这本书没有全面讨论11世纪复兴儒学的学者,只褒扬强调“道”的人。朱熹追随程颐的说法,认为致力于道的学者才是真正的儒者,研究文学和经学的学者则不然,所以他略过11世纪中叶对儒学复兴持比较宽广观念的学者,以传记和师承谱系追溯他所认为的道学流派渊源,指出这些先贤的贡献是延续道统,绍述古代圣人。朱熹在开头几章集中讨论开创道学的主要人物: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和张载。他虽然用“伊洛”当做书名,而且二程素来被视为道学传统的源泉,但这里强调周敦颐的开山功劳,的确饶富意义。
邓广铭(1907—1998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周敦颐其实没有学生,在北宋时期也没有被视作重要的思想家,南宋的道学家才将他变成道学传统中重要的人物,朱熹尤其如此。朱熹夸大周敦颐的地位,甚至引起道学内部不同的意见。汪应辰两次写信给朱熹,表示怀疑二程是周敦颐学生的说法,推测二程顶多年轻时曾经受周敦颐影响,但《伊洛渊源录》却断定周敦颐和二程有明确的师生关系。朱熹答复汪应辰,只简单解释他的说法来自吕大临(1044—1093年)记录在《二程语录》里的一条。朱熹承认汪应辰的质疑有道理,但没有修改《伊洛渊源录》的说法,仅引用吕大临的话为证据。邓广铭先生指出,朱熹避开汪应辰的合理的挑战,却以有问题的材料改写道学的历史。①
朱熹虽然是把周敦颐扶上道学宗师位子的主要人物,其实有些道学家已经为此奠立基础。本书在第一部已经提到,朱震早在1134年就说二程的学识甚受周敦颐的影响,湖湘学派也一直同时强调周敦颐和二程,胡宏和张栻都认为二程延袭周敦颐的一些思想。张栻除曾引用周敦颐的思想,至少写过六篇文章赞扬周敦颐。①陆九渊虽然不承认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见第九章),但也相信周敦颐曾经教导二程。汪应辰反对周敦颐与二程有师生关系的说法,其实不是涉及二程地位的唯一敏感问题,例如,杨时就不承认二程曾经追随过张载,而且贬抑张载:“横渠之学,其源出自程氏。”②吕祖谦一意结合张载与二程的思想,但对周敦颐并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从朱熹回答吕祖谦关于《伊洛渊源录》的问题来看,朱熹将周敦颐当做早期道学关键人物,吕祖谦并无异议。③吕氏一家对周敦颐遗留的学说也没有敌意,吕希哲、吕本中虽然曾经判断二程曾向周敦颐学习,但认为他们后来超越周敦颐。④因此,强调二程地位的学者不必然贬低周敦颐的地位。总而言之,我们不宜夸大道学人士反对周敦颐的情形。
朱熹也强调二程的贡献比较大。朱熹虽然引用程颐的“明道先生行状”为依据,表示二程的确曾经追随周敦颐,但更侧重二程的贡献。根据程颐这篇行状的说法,程颢得到周敦颐直接传授,但没有寻得学问的根本,所以自己苦心钻研近十年之久;程颐认为周敦颐的学问还不足以指导程颢这般天赋异禀的人。程颢回顾《六经》后,才获得思想的突破,发现古代圣人的道理。程颐形容他的兄长:
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①
程颐显然认为程颢超越周敦颐,朱熹也含蓄接受这个说法,后来更明确赞扬二程复兴儒家之道。朱熹作《中庸章注》序时,指出二程与道的传承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盖子思之功于是为大,而微程夫子,则亦莫能因其说而得其心也。②
这段文字与程颐的“明道先生行状”和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似乎互有抵触,因为朱熹在书中指出周敦颐重新发现道,并将道传给二程;这项表面的矛盾显示:现代的研究可能太高估朱熹对周敦颐的推崇。③
朱熹在1193年所写的“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提供另一个角度,可以观察朱熹如何评价周敦颐和二程。朱熹虽然强调周敦颐的独特角色,但认为二程的贡献更大:“〔周〕先生之学实得孔、孟不传之绪,以授河南二程先生而道以大明。”④周敦颐因为传道而受赞扬,但朱熹将发扬道的功劳归于二程。
就《伊洛渊源录》的篇幅而言,北宋五子的轻重排列依次是:程颢、程颐、张载、邵雍,最后才是周敦颐。朱熹也很重视二程的其他同道,尤其是胡宏及吕祖谦的先人吕希哲、胡安国;这两个例子都显示朱熹给二程的篇幅比周敦颐多。
朱熹编辑《伊洛渊源录》赞美书中的人物,有力发扬一支研究道的独特儒学传统。全书近五章半的篇幅是谈论二程的主要学生,而其他20个较不重要的学生只在一章中简单带过。朱熹用巧妙的方式以二程为中心建立传统,并且用“伊洛”标榜二程的学派,结合四位儒学宗师与34位门徒,展现11世纪后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几代道学发展。朱熹在1173年对道学范围的界定比晚年的见解宽广,但是比起同时代的学者已经狭隘许多,《诸儒鸣道集》就是很好的例子。
朱熹重新界定道学的范围,其实隐然要回应及取代《诸儒鸣道集》的看法。这部书是由张九成的学生在12世纪60年代编辑的,选取的人物顺序与朱熹不甚相同:周敦颐、司马光、张载,然后才是二程;所以司马光传道的地位仅次于周敦颐,而且司马光和张载被列在周敦颐和二程中间。周敦颐的地位在此不成问题,显示南宋初期不少道学人士认为周敦颐属于道学的一员,而且拥有特殊的地位;所以朱熹将周敦颐包括在内,并不算拓宽道学的传统。《诸儒鸣道集》虽然包括邵雍,但并未将他置于“北宋五子”的崇高地位,也没包括胡宏,但这部最早的道学选集还是显示道学初期较广阔的背景,因为它不集中于二程,而且较少谈论抽象的哲学问题。这本书还包括其他儒家学者,最有名的要属张九成,但朱熹将他排除在外,认为他受到佛教的影响太深。《诸儒鸣道集》反映道学初期视野广阔的另一证据:保存一些别处不见的著作。例如,刘安世的《元城语录》、江公望(北宋末期)的《性说》、刘子翚(1101—1147年)的《圣传论》以及潘植(12世纪初)的《忘荃集》最完整版本。①潘植和刘子翚对佛教很有好感;江公望说有些儒生为性下定义时,不够重视人情的作用;潘植反对将道与物理分离。张九成不喜欢抽象的哲学,也明显表现在寓道于实践的思想,而《诸儒鸣道集》处处显示这种倾向。例如,它收入周敦颐的《通书》,而“太极图说”就未在书中出现。总而言之,这部选集呈现的道学,上溯几代到二程以及元祐党人中的同道,尤其是司马光和刘安世,包括日后选集所删去的人物,描述的范围比流传的朱熹版本要宽广 许多。
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被元代的《宋史》编者当做撰写“道学列传”和“儒林列传”的基本资料;18世纪《四库全书》的编者回顾说,以道学来划分儒家学者,始于朱熹1173年完成的《伊洛渊源录》。①朱熹以前虽然就 有人界定道学的范围,但《伊洛渊源录》是重建或重新定义这支学术传统 的重要一步。
朱熹和吕祖谦为弘扬道学,合作编辑一部哲学的入门选集《近思录》。吕祖谦在1175年拜访朱熹时,共同完成大部分的编辑工作,随后一直联络讨论某些章节,直到1178年オ定稿。《近思录》与朱熹的《伊洛渊源录》不同,只包括北宋四子:周敦颐、二程与张载,传承的顺序依旧是从周敦颐到二程,再到张载,邵雍被排除在外。朱熹在别的著作里引用邵雍的宇宙论和自然观,但认为邵雍不应该包括在道学的主流里,因为他有宿命论的思想,而且不够重视个人修养和道德。②全书最强调二程,其次是张载。全书总共622条,二程占80%的篇幅,张载占18%,周敦颐占的比例不到2%,而取自“太极图说”的只有一条。③从《近思录》的编排数目以及《伊洛渊源录》的篇目,可看出周敦颐在朱熹心目中的地位。 因此,对朱子哲学的传统认识恐怕得修正,应该更注意张载,而不是周敦颐,虽然强调张载可能要归因于吕祖谦。
自从南宋末以来,朱熹的后学将他当做《近思录》的唯一作者,但钱穆与陈荣捷等现代学者注意到吕祖谦的协助与贡献。①吕祖谦的观点影响这本书的内容,由于他的坚持,朱熹保留一条论法制的条文,又删除几处抨击科举的文字。吕祖谦在一些特别的段落使朱熹放弃原来的目标。朱熹重视抽象的哲学,但却是吕祖谦劝他将讨论抽象哲学的“道体”当做全书的第一卷。吕祖谦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删除程颢的“仁论”,而收录程颐的《易传》许多言论。朱熹质疑程颐注解《易经》的方法,原本希望《近思录》不要引用任何段落,但结果全书有106处文字出自程颐的《易传》,竟然占总篇幅的17%,仅次于朱熹编辑的《二程遗书》。朱熹在多年后解释说,他对吕祖谦让步是因为吕祖谦建议的段落很能解释日用生活中的功夫修养。②可是朱熹为什么不满程颐的《易传》呢?
四、哲学的问题
宋代解释《易经》主要有两个派别,程颐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以道德伦理的角度解释《易经》,而不是从象数占卜的角度看待它。程颐追随王弼(226—249年),将“大传”附会在每一个六十四卦经文后,但把重点放在“大传”,而不在卦爻经文,也不用邵雍、周敦颐偏重卦爻象数的方法,而将“大传”的道德原理应用到功夫修养。③朱熹的方法又与程颐不同,不采取王弼以来将“大传”附会于每一个六十四卦经文的本子,而采用吕祖谦编辑的《东莱吕氏古易》,并曾为该文撰写跋文。吕祖谦以司马 光的学生晁说之(1059-1129年)的说法为基础,致力恢复上古经文的原貌,将“大传”与六十四卦分开。朱熹借用吕祖谦的易经古文,特别注意卦象(包括卦辞和爻辞),而不是程颐所使用的后出传文。朱熹认为孔子撰写“十翼”(大传)的传统说法可信,但孔子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不延袭伏羲发明八卦的原意。朱熹将他采信的上古经文与“大传”的哲学诠释分开,力图改正程颐对《易经》作过度的哲学诠释。程颐很少讨论卦象结构,而谈论卦辞跟爻辞的暗示的内在普遍原理。朱熹的做法与程颐相反,他借用邵雍和周敦颐的象数见解,从讨论卦爻的结构位置开始,强调有关的卦象神谕。朱熹认为程颐只强调传文中所提示的特定普遍原 理,而忽视卦象神谕在不同情况下的意义。①
朱熹相信《易经》的本意只是占卜之书,不像其他经典具有强烈的道德教育意义。朱熹没有取消《易经》的占卜功能,其实是鼓励同时的文人把它当做功夫修养的工具。他在1176年给吕祖谦的一封信中说:
故今欲凡读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虚心以求其词义之所指,以为凶吉可否之决,然后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后推之于事,使上自王公、下至庶民所以修身治国,皆有可用。②
卦爻所提示的具体行为指示,取决于占卜当时的情况背景,唯有圣人能知道如何在任何情况正确行动,因为他们了解万物几微的力量,能够因势利导。除少数的圣人外,每个人都有时需要占卜的指示,以探究自然的道理,成就人事、解决疑难。如果能够正确使用《易经》占卜预测未来,内心必然诚敬无私,了解人、天、地为一体。不过占卜不必用于道德原则十分清楚的情况,唯有极尽人事之后,才用占卜解决疑难、指示行动。朱熹在1195年就用占卜决定是否上书反对压制道学,当时他的学生畏惧朝廷的迫害,希望劝止朱熹上书,卜筮呈现不要上书的卦象后,朱熹采纳建议,焚毁上书。①
吕祖谦对占卜的看法与朱熹不同。《东莱先生左氏博议》中对士人谈到占卜,认为占卜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的形象是人心的表露:
未灼之前,三兆已具。未揲之前,三易已彰。龟即灼矣,蓍既揲矣。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是易之变,乃吾心之变。……妄者见其妄,僭者见其僭,妖者见其妖,皆心之所自发见耳。②
朱熹虽然要士人自己占卜,但不支持以占卜为生的人,吕祖谦则进一步谈到巫妖,生动表达他对占卜的态度。吕祖谦与程颐都反对占卜,即使他未追随程颐采用王弼的《易经》版本。上述引文也明确表达他的看法,认为占卜只能告诉我们内心已经认识的事物。
吕祖谦在别的著作中更清楚指出:心决定占卜的结果。《增修东莱书说》中说:
未占之先,自断于心,而后命于元龟。我志既先定矣,以次而谋之人,谋之鬼,谋之卜筮。圣人占卜,非泛然无主于中,委占卜以为定论矣。①
吕祖谦是位历史学家,经典提到占卜的时候,他必须承认古人“谋之幽明”,但认为古人问卜,不过是为对事物的看法多求个观点而已。吕祖谦认为圣人占卜,但圣人不看重占卜。他也不鼓励士人将占卜当做自我修养的手段,认为占卜不足多论,因为占卜的结果已经先在心中决定了。
吕祖谦进一步澄清心与天地奥妙的关系,认为古代圣人之心是“天心”。前面也提到,张九成与胡宏用“天心”形容古圣人之心,相信人的德性与“天心”相连,吕祖谦的用法与他们很相近。“天心”只在经典中的《尚书》出现过一次,而且还是汉代的古文派经学家加进去的伪经,但吕祖谦讲授《尚书》时,至少引用“天心”十次以上,形容上古商周时代开国君主和大臣的心意。②这两代的圣王据说与德合一,可以上接天心,下得民心。他们得到天心,承受天命治理国家。天心无私,所以这些圣王之心也是纯然无私的。
吕祖谦谈到更早的圣人时,认为天心与圣人之心合一是普遍的原理:“圣人之心,即天之心。圣人之所推,即天所命也。”舜禅让君位给禹时,天的“历数”已经在禹。圣人之心就是天心,因为“此心、此理,盖纯乎天也”③。
吕祖谦认为“天命之谓性”(《中庸》)外,天也赋予人之心,所以有人问心、性应该如何区别,他回答:“心犹帝,性犹天。本然者谓之性,主宰者谓之心。”④暗示不只圣人的心与天合一,心与天的联系也是普遍的;吕祖谦说:“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①进一步区别天心与视任何人事为外物的心,②并根据同样的想法,将心与道的相等关系普遍化:“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③因为道就是理,所以又回到吕祖谦天理合一的看法。
吕祖谦视理和天为一,又将理与天命相连:“命者,正理也。禀于天而正理不可易者,所谓命也。”④人不可能逃避天的规范,夏代的君主不再推行德政,不遵从天的规范,天“遂降之以灾”,所以“天理感应之速反复手间耳”,而且“非汤放桀,乃天也。以此深见,伐夏非汤之本意,实迫于天命之不得已耳”⑤。所以吕祖谦结合两种观念:新的哲学意义的“理”,以及古代经典里会惩罚不道德君主的“天”。理或道德提供天与人之间的联系:“一理流通,天与圣人本无间。”⑥就此而言,天经由天理治理人民,但这说法与吕祖谦一向主张的“命由心定”的说法有明显的差异,矛盾只有在先预设心终究与天及理合一的情况下才可能消解,但也仅能解决部分的矛盾。一旦追问伦理学的难题时,这个矛盾差别就更明显:为什么人会丧失道德,无法认识心与天理是一体的呢?
吕祖谦引用《尚书·大禹谟》中舜的十六字传心诀,讨论这项伦理学难题的关键。这段话成为道学论心的重点,原文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吕祖谦解释说:
人心,私心也,私则胶胶扰扰,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难见也。此乃心之定体,一则不杂,精则不差,此又下工夫处。既有他定体,又知所用工,然后能允执其中也。⑦
根据吕祖谦的解释,这段话既主张孟子的性善说,也肯定必须每日律己修养才能达到善的境界。人有道心仍然不足以为善,因为成为善人还需要认真严肃的修养。
吕祖谦为确定弥补这伦理学的问题,转向《易经》寻求解释。他在解释“复”卦时,将自我修养与孟子的心性本善的理论结合:
夫复自大言之,则天地阴阳消长,有必复之理;自小言之,则人之一心善端发现,虽穷凶极恶之人,此善端亦未尝不复。才复,便有亨通之理。且以卦体之爻观之。初九,一阳潜伏于五阴之下,虽五阴积累在上,而一阳即动,便觉五阴已自有消散披靡气象。人有千过万恶,丛萃一身,人之善心一复,则虽有千过万恶,亦便觉有消散披靡气象。……学者最要就天行上看,天道之有复,乃天行自然之道理,人之善心发处,亦人心固有之理。……人虽以私意障蔽,然秉彝终不可泯没,便是天行无闲之理。①
天刚健不息的运行以及他对“复”卦的解释,不但加强吕祖谦对孟子性善理论的信念,也使他对个人能够实现自我道德转化更有信心。吕祖谦的分析虽然与程颐对《易经》的哲学诠释比较接近,但他和朱熹都分析卦爻的结构变化,并将得到的教训运用到自我向善转化的努力中。
吕祖谦和朱熹对《易经》看法的相似处,从朱熹对“复”卦的评注中显示得很清楚。《周易本义》中指出,人可以从“复”卦中看到天地之心的运作:
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程子论之详矣。②
朱熹接着引用邵雍的诗,谈论天心在冬至时,处于寂然不动的状态,似乎全然不存在,一旦又受阳气催动,便能再化生万物。朱熹在此引用程颐和邵雍的诗文讨论爻辞,显然他一方面批评早先道学的易学传统,但也从中吸收不少解释;而且他与吕祖谦都从观察天与四季往复运行的过程,肯定人的本然善心能够回归自身,提供改邪归正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为确定善性,心安理得地引用邵雍谈论“天心”的诗。朱熹与吕祖谦都认为“天心”就是“君子之心”,朱熹说:“盖君子心大则是天心,心小则文王之翼翼,皆为好也。”①并引用荀子的话:“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②朱熹谈论天是有意识的主宰时,所谓“天”一直遵循道及理;总而言之,天就是理。理虽然是朱熹理论体系的中心观念,但理本身不直接控制万物的运行,由于需要一股制约的力量,他在几处视天为主宰,至少说过一次“天心”就是理的主宰,因为“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摄是理者,即其心也。”③朱熹在这些段落里谈到圣人尽其心,所以能够知天、知性、与万物合为一体时,圣人之心与“天心”合而为一。学者在讨论朱熹对人可以向善的信念根据时,大多提及人性与天地之性为一体。④不过,将天心与圣人之心或君子之心结合起来,无疑又给朱熹提供另外的根据。
以心而论,朱熹以两个观念表达人可以为善的信念。第一,《易经》的复卦显示,人心与天地之心合一,因为人也具有使万物生长的仁德。其次,朱熹以帝舜的十六字传心诀为基础,发展“人心”与“道心”区别的主要理论,提出道德修养的要务。由于人心很不稳定,而道心是绝对的至善,所以必须将"人心”转化为与天理合一的"道心”;①胡宏对道心的解释更明白而简练:"道心与天无二”,且说"仁,天也。”②
"道心”与"天心”的相似之处显示,两者都是用以确认人可以为善的隐喻。人的意识可以使自我作自私的抉择,而导致自利与罪恶的行为。朱熹否定自私的思虑算计是"天心”,因为天心一直与道一致;同样的道理,君子扩充心,其心就能与天合一、与道一致;换句话说,就成为天心。道心就是人具有的本心,若能够存养此本然的心,它就会引导人走上道德的路径;所以"天心”、"道心”都是与道德合一,自私的思虑则与天心、道心背道而驰。朱熹虽然从来没有清楚说明"道心”与"天心”其实是相同的概念,但两者的相似之处足以明确将它们联结在一起。朱熹未明确指出其间的联系,可能是因为"天心”有时指圣王之心,甚至当朝皇帝之心,以当时的背景,要将"天心”普遍化成为心处于至善的观念模式,比普通化"道心”困难;然而,这两个形容心自然与道德规范一致的概念,仍然为自我修为能够克服私欲,达到与正道和谐的信念,提供额外的支持。传统的儒家学者认为宇宙的自然规律内涵道德的意义,所以朱熹将人心与天及道联结,加强人具有努力向善的潜能的信心基础。
朱熹和吕祖谦都要在儒家学者间建立一个致力于道的群体,他们的个人风格不同,也影响道学内部以及道学与外人的关系;吕祖谦逝世后的时期,这点显示得更明白。
吕祖谦来自当时最有名望的士大夫家族,不仅提倡拥护家礼及传统,而且维护私人家族的利益。南宋的望族一般与当地其他望族联姻, 所以也专注地方的事务;但有些新近移民的家族的做法有异,仍然流行与外地的家族联姻。①吕祖谦的情况与北宋的联姻模式比较一致,他第一任妻子是韩元吉的女儿,韩家是开封的望族,北方沦陷后移居福建。这位妻子在婚后七年去世,吕祖谦又娶她的妹妹为妻。他再度成为鳏夫后,迎娶著名的太学博士芮烨的女儿,而芮烨来自湖州。吕祖谦的女儿嫁入金华当地的望族,但这似乎是安排朱熹的儿子与同一家族联姻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显示他对朱熹格外宽厚与亲近。许多北方大族逃离女真人征服的北方后,无法保持既有的地位与传统,但吕家在这方面非常成功,至少到吕祖谦这代依然如此。
吕祖谦与北宋时代的先人都比较注重全国的政治,比较不特别关心地方的事务。他具有丰富的历史制度知识,并且明了当代的政治现实,因此朝廷讨论政治制度时,他是各方尊敬的权威。浙东其他的学者与陈亮一样,只注重全国与家族内的事务,吕祖谦则没有忽视中间层次的小区组织。例如,他为朱熹的社仓计划辩护,而且计划在金华建立类似的社仓;此外他通过在朝任官的朋友,协助朱熹建立他的第一座社仓与书院。
吕祖谦比较注重全国的事务,朱熹则活跃于中层的小区组织。朱熹在国家控制地方的权力削弱,而地方家族势力抬头的局势下,提倡一系列的组织加强中层的小区意识与团结。朱熹在社区组织的礼仪规范下,特别注重乡约、先贤祠、书院及社仓。他的社区制度的构想大多来自别人,但能将不同的办法融合,以达到整合儒学群体的目的。吕祖谦与朱熹都致力于加强道学家的意识和凝聚力,他们的重点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关心三个层次的事务,而且努力合作,互相支持,以强化国力及道学。
吕祖谦对朱熹的理论和实践有明显的影响。以书院而论,吕祖谦比朱熹早几年建立精舍与书院,而且吕祖谦是一名非常成功的老师,也必然引起朱熹注意,而吕祖谦为学生制定的学规是12年后朱熹学规的蓝本。白鹿洞书院筹建的过程中,吕祖谦经常提供建议,朱熹并且将吕祖谦为书院重建完成而写的题记刻在书院石碑上。他们讨论胡宏的《知言》时,吕祖谦提醒朱熹要兼重精神修养的两种方法,而朱熹后来以此著称于世。朱熹与张栻处理“仁说”问题时,经常写信给吕祖谦讨论这个题目。在经学研究方面,朱熹以哲学诠释《易经》的基本文献框架是吕祖谦重编的《易经》,吕祖谦对《诗经》经文与“毛诗序”的看法,成为朱熹诠释该书的重要根据。《近思录》的内容及编排也证明吕祖谦介入颇深,这项合作计划如何进行,清楚记录在他们的书信与朱熹对学生的谈话里,但大部分日后的学者忽略、甚至贬抑吕祖谦对这部书的贡献。朱熹或许要为后学门人的偏见负担部分责任;吕祖谦去世后,朱熹总是避免强调故人的贡献,本书后面还会讨论,他批判浙东的功利学派,也连带影响他对吕祖谦的评价。
吕祖谦在各种讨论中,证明他能够讨论三个层次的问题。他虽然劝朱熹在《近思录》第一卷讨论“道体”,但大体而言,他不像朱熹那么注意抽象的思辨哲学。朱熹与吕祖谦讨论的思辨哲学问题,的确不如他与张栻讨论的多。吕祖谦理论色彩虽然不如朱熹强烈,但现代学者也不应继续忽视他著作中的理论成分。他们讨论《易经》时使用的“天心”一词,可以提供另一观点考查他们如何追求修养的确立,而他们对于心与修养的看法也显示他们对占卜的看法。吕祖谦的体系强调心,甚于注重理;朱熹的体系则较以理为中心。吕祖谦调解学说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平衡太过强调心或理的观念,而由于他企图达到两者的和谐与平衡,他的思想具有兼容并蓄的色彩;这种印象使现代学者不能认真严肃地研究他的著作。
一般也认为吕祖谦对朱熹研究的中心议题如心、性、理所言甚少,他的专长是历史研究,而朱熹的特长是经典。朱熹和吕祖谦的学术重点的确不同,但这种比较的结论容易忽视吕祖谦对道德、哲学及经学的见解;其实他对这些领域的学术和教育都有贡献。
若将吕祖谦学术的重点置于实际问题与历史研究,他真正的重点容易被误解。吕祖谦的社会活动、学术研究与历史著作虽然很著名,但仍然秉持如下信念:
静多于动,践履多于发用,涵养多于讲说,读经多于读史。工夫如此,然后能可久可大。①
这段话显示吕祖谦的基本重点与朱熹相似。吕祖谦的历史著作充满心、性、理的讨论,包含许多经典记载的圣人言行,而且他对三代以后的历史研究也是用以加强道德修养,这些都颇值得注意。对吕祖谦而言,经典与历史著作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因为经典都是上古时代的历史材料,《诗经》、《尚书》与《春秋》尤其如此。
现代学者比较朱熹和吕祖谦时,大多隐然接受朱熹的判断。朱熹同意学生的评语:“东莱博学多识则有之矣,守约恐未也。”他也说:“伯恭之弊尽在于巧。”②从他们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可以厘清朱熹所谓的“巧”。第一,朱熹说《尚书》很难解读,吕祖谦回答说没有事情不能解释清楚,但几年后吕祖谦承认朱熹对《尚书》的几处疑问是正确的。他们对这部经典的解释仍然不同,朱熹抱怨吕祖谦有时勉强解释《尚书》中无法解释的部分。其次,朱熹虽然欣赏吕祖谦对《诗经》一些解释,也赞同他将经文与序分开处理,但觉得他的解释有时太过取巧。第三,朱熹承认《左传》包含经典未触及的道理,但质疑何必花费许多时间追寻《左传》包括的琐碎细微的道理。他也承认吕祖谦对《左传》的解释极博学详细,但又批评他有时望文生义。第四,朱熹极力抨击苏洵、苏轼和苏辙以佛、道二教的学说污染儒学,吕祖谦却认为他们的偏差不应招致如此强烈的抨击;朱熹因此写信给张栻,抱怨吕祖谦一番:
渠又为留意科举文学之久,出入苏氏父子波澜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坏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苏学为非,左遮右拦,阳挤阴助,此尤使人不满意。①
张栻回答说,吕祖谦虽然“于苏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来见渠亦非助苏氏,但习熟元祐间一等长厚之论,未肯诵言排之耳。”②
朱熹和张栻虽然大张旗鼓声讨苏轼,吕祖谦仍然很尊敬苏轼的作品。南宋一般的道学家对苏轼与古文的兴趣降低,吕祖谦却例外。他继承家学的传统,甚至推崇江西诗人。③他只在受人请托或应酬时,才会写作纯文学的作品,但也的确写过许多各种文体的文章。他评论文章的范例时,常教人学习欧阳修和苏轼的作品,《宋文鉴》就是力求文与理的统一。当代学者刘昭仁先生曾经指出,吕祖谦不赞成将学术分成追随程颐的“道”的学说与推崇苏轼文学的两派。④吕祖谦调和苏轼与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反映他要加强儒学的团结,并且全面保存儒学的传统。
朱熹虽然从吕祖谦的调和受益良多,但有时严厉批评吕祖谦调和分歧、寻求妥协的倾向;他曾经说:
伯恭讲论甚好,但每事要鹘囵说作一块,又生怕人说异端俗学之非,护苏氏尤力。以为争较是非,不如敛藏持养。⑤
吕祖谦方面则认为朱熹过于强硬,不够宽容和厚道。⑥
朱熹也承认他们的性情不同,他赞扬吕祖谦:“天资温厚,故其论平恕委屈之意多。”而自己的性格是“质失之暴悍,故凡所论皆有奋发直前之气”。而这缺点比吕祖谦退让的性格更糟糕,“熹之发足以自挠而伤物”①。
朱熹和吕祖谦的性格虽然不同,但他对吕祖谦的感情和尊重是真诚的。吕祖谦去世时,朱熹表达最深沉的情感。吕祖谦去世的消息到达后,他在家中洒酒设奠,并且送去祭文。他的“祭吕伯恭著作文”大部分是赞扬吕祖谦温和谦恭、不轻易批评别人、文采出众、兼采百家风格,入朝出仕,树立道德的榜样。
最重要的是,朱熹谈到吕祖谦的去世对道学的意义。朱熹赞扬吕祖谦的道学,并且感叹“吾道”的衰落,以及吕祖谦去世对“吾党”的影响。吕祖谦虽然以前用过“吾党”的字眼,但朱熹也使用这词指称道学,则颇令人意外。在12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使用这字眼,显示道学同道已经意识到自己成为一个团结而且独特的团体。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表示反对结党以后,”党”一直有极端反面的政治及道德的含意。北宋的政治家一般对它有比较好的看法,不过即使欧阳修写“朋党论”为君子结党辩护,仍然没有去除它的负面意涵。②反对道学的人士已经警告朝廷这个团体像党派般运作,朱熹在“祭吕伯恭著作文”开头几句话意味深长:
呜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岁已夺吾〔张〕敬夫,今者伯恭胡为又至于不淑耶?道学将谁使之振?君德将谁使之复?后生将谁使之诲?斯民将谁使之福耶?经说将谁使之继?事记将谁使之续耶?若我之愚,则病将孰为之箴,而过将谁为之督耶?然则伯恭之亡,曷为而不使我失声而惊呼,号天而恸哭耶?③
朱熹在这篇祭文里清楚指出,张栻和吕祖谦是他所属团体的领袖,而且他们以道的学说贡献儒家的文化。朱熹在此大胆提出道学的政治、社会、文化的主张。由于祭文的体裁,朱熹将自己置于亡友之下,但含蓄表示要实现道学团体的目标。
朱熹反问“道学将谁使之振?”表示他会努力接过亡友领导道学的责任。张栻与吕祖谦去世后,朱熹宣称今后无人能够提醒纠正他的错误,既然已经没有人足以匡正他的错误,他又自谦说“若我之愚”,似乎暗示身边的人都不如自己。
朱熹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呢?吕祖谦提醒朱熹有“伤急不容耐处”,朱熹在1175年也承认有这种倾向。①张栻在一封信中,以元晦称呼朱熹,提出惊人的告诫:
又虑元晦学行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见他人不是,觉已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辩论之劲,排辟之严。纵有所疑,不敢以请。深恐谀言多而拂论少,万一有于所偏处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②
既然朱熹在吕祖谦的祭文中明确表示他要挺身负起领导道学的责任,并且说没有人可以纠正他的错误,道学下一阶段的发展使张栻的批评不幸言中。张栻与吕祖谦去世后,朱熹在没有如此亲密的同侪友人的环境下,继续发展道学的哲学理论以及组织道学的同道。朱熹在随后思想气氛比较冲突对立的年代里,对吕祖谦的态度比对故人生前还要严厉。
附注
①关于“庆元党案”,参看《宋元学案》,卷97,页3197—3200;关于道学人士获得学位的时间以及背景,见ConradSchirokauer(谢康伦),“Neo-ConfuciansunderAttack:TheCondemnationofWei-hsueh,”inJohnW.Haeger,ed.,CrisisandProsperityinSungChina,(Tucson:Uni-versityofArizonaPress,1975),pp.167—168,184—192.我根据昌彼德、王德毅主编的《宋人全集资料索引》(台北:鼎文书局,1974—1976年),册4,页3536,并且加上赵彦逾(1160年进士)。
进学术的发展,也加速道学同道与道学传统的形成。
①毕沅:《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147,页3936。关于1178年的另外一份上书,见卷146,页3896。
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2,页16上—46上,特别是页46上。又见市来津由彦:“朱子の‘杂学辨’とその周边”,收入宋代史研究会编:《宋代の社会と宗教》(东京:汲古书院,1985年),页3—49;Chung Tsai-chun(钟彩钧),The Development ofthe Concepts ofHeaven and ofMan in the Philosophy ofChuHsi(Taipei: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Academia Sinica,1993),pp.72—87.
①《朱文公文集》,卷81,页2下。
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高畑常信先生写的关于张栻的几篇文章,参其《张南轩集人名索引·付论文》(名古屋:采华书林,1976年)。又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页375—381,522—550;胡昭曦:“谯定、张栻与朱熹的学术关系”,《中国哲学》,第16辑(1993年),页240—262;朱汉民:“张栻和岳麓书院”,收入朱瑞熙编,《朱熹教育和中国文化》(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页272—280。
①朱熹的祭文见《朱文公文集》,卷89,页1上—10上,特别是页2上。又参《宋史》,卷429,页12770—12775;高畑常信:“张南轩年谱”,收入其《张南轩集人名索引·付论文》,页65—89。
②《宋史》,卷429,页12774。
③《宋元学案》,卷50,页1633。
④《宋史》,卷429,页12771—12774,重点在页12771。
⑤《朱文公文集》,卷89,页4下。
⑥高畑常信:“张南轩の静江府におけゐ治政”,收入其《张南轩集人名索引·付论文》,页90—109。
①《南轩集》,卷9,页3上。
②《南轩集》,卷26,页2下。又见《宋元学案》,卷50,页1625和1627的引文。
③《宋元学案》,卷50,页1613,1618,1626—1631。
④关于张栻对苏轼的看法,见《南轩集》,卷35,页2上—3上。
①胡宏:《五峰集》,卷2,页65下;《胡宏集》,页132。朱熹:《朱文公文集》,卷89,页1下。
②《五峰集》,卷2,页67下;卷2,页68下。《胡宏集》,页133,134。
③《朱文公文集》,卷89,页1下—2上。
④《南轩集》,卷33,页8下—9下;又见卷25,页7上下。
①见朱熹在《南轩集》中的序文。张栻对诸葛亮的论述见《南轩集》,卷10,页5上—7上;卷36,页10上下,及张栻的《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百部丛书集成本)。又参见刘子健:“从儒将的概念说到历史上对南宋初张浚的评论”,收入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国史释论》(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年),页481—490。②高畑常信:“张南轩の思想变迁”,收入其《张南轩集人名索引·附论文》,页1—25;“张南轩集の版本”,收入其《张南轩集人名索引·附论文》,页26—65。
①《南轩集》,卷18,页1上—2上。《易经》中的乾卦其实使用“乾”、“坤”这样的名词,与“天”、“地”等词相近。陈荣捷在《朱子新探索》页375—376中指出张栻引用二程或经典的引文。又见《南轩集》,卷25,页13上下。
①张栻:《孟子说》(四库全书本),卷6,页12下;又见其《癸巳论语解》(百部丛书集成本),卷9页1下。
②《孟子说》,卷3,页1下。
③《孟子说》,卷2,页27下—28上。
①《南轩集》,卷14,页2上下。
②《孟子说》,卷3,页1下以及卷6,页3上。
③《孟子说》,卷6,页12下。
④《孟子说》,卷6,页4上。
①程颢、程颐:《二程集》,册1,页10。
②《孟子说》,卷6,页3下。
③《宋元学案》,卷50,页1623。
①《癸巳论语解》,卷8,页21下。
②《癸巳论语解》,卷8,页14上。
③《孟子说》,卷7,页25上。
④《南轩集》,卷14,页5下—6上。
①《癸巳论语解》,卷2,页13下。
②《宋元学案》,卷50,页1618。
③《宋元学案》,卷50,页1618。
①《宋元学案》,卷50,页1624。
②《宋元学案》,卷50,页1613。
③《南轩集》,卷12,页2下;见《二程集》,册1,页143。
④《癸巳论语解》,卷3,页11下。
⑤《南轩集》,卷36,页9上下。
⑥《孟子说》,卷6,页30上。
⑦《南轩集》,卷11,页7上。
①《宋元学案》,卷50,页1619—1620。
②《孟子说》,卷7,页1上。
③《南轩集》,卷12,页2下。
④《癸巳论语解》,序,页1下。
①《宋元学案》,卷50,页1635。
②《朱文公文集》,卷89,页9下;见《宋明理学史》,上册,页337—338关于张栻的三个贡献。
③《陆九渊集》,卷34,页413。
④参见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1986年)。
①引文见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0,页1635。类似说法又见《宋史》,卷427,页12710;卷429,页12775;《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03,页4140;(中华书局本),卷103,页2605;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25—529。
②《朱文公文集》,卷31,页10上,17上—20下.21上—37上。有关讨论又见钱穆:《朱子新学案》,册4,页510—530;高畑常信:“张南轩の《论语解》に与えた朱子の影响”,收入其《张南轩集人名索引·附论文》,页110—123;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30—537。
①例如钱穆:《朱子新学案》,册1,页105—112;册2,页123—182。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北:中华文化出版社事业委员会,1953年),页103—109。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册3,页71—228。王懋竑:《朱子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66年),卷1上,页23—27;卷1下,页35—42。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37—543;陈来:《朱熹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91—188,(也有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页434—440。蔡仁厚:《宋明理学》(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册1,页76—106。友枝龙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东京:春秋社,1969年),页38—102。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页71—138。申美子:《朱子诗中的思想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束景南:《朱子大传》(泉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页233—267。Chung Tsai-chun(钟彩钧),The DevelopmentoftheConcepts ofHeavenand ofMan,pp.89—130.
①《二程集》,册1,页188;《朱文公文集》,卷64,页28上—29下。
①钱穆:《朱子新探索》,册3,页219—223。
②YungSikKim(金永植),“ChuHsi(1130—1200)onCalendarSpecialistsandTheirKnowl-edge:AScholarsAttitudeTowardTechnicalScientificKnowledgeinTraditionalChina,”T’oungPao78,1—3(1992),pp.94—115;与其“ProblemsintheStudyoftheHistoryofChineseScience,”Minerva20(1982),pp.83—104;陈正夫、何植靖:“朱熹理学与自然科学”,《中国哲学》,第9辑(1983年),页240—256。
①《朱文公文集》,卷75,页22下—23上。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43。
①《朱文公文集》,卷73,页46下,“胡子知言疑义”。
②钱穆:《朱子新探索》,册3,页200。
③《南轩集》,卷21,页9下。
④《朱文公文集》,卷73,页40下,“胡子知言疑义”。
①《朱文公文集》,卷73,页44下,45上,47上,“胡子知言疑义”。
②《朱文公文集》,卷73,页47上,“胡子知言疑义”。
③吴仁湖先生在标点本《胡宏集》的序言提到这发现,见序页3。陈荣捷在《朱子新探索》中提到张栻和吕祖谦的一些话,已不在两人的文集中,见页544的注165。
④《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01,页4104;(中华书局本),卷101,页2582。后代学者例如《宋元学案》,卷42,页1377;束景南:《朱子大传》,页285—286。
⑤《朱文公文集》,卷73,页40下—41上,“胡子知言疑义”;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页374。
①《朱文公文集》,卷73,页47上下,“胡子知言疑义”。
②《朱文公文集》,卷73,页43上下,“胡子知言疑义”。
③《朱文公文集》,卷73,页41下—42上,“胡子知言疑义”。
①《朱文公文集》,卷73,页42下,“胡子知言疑义”;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台北:台湾中华书局再印,1969年),页214。
②《朱文公文集》,卷73,页42下—43上,“胡子知言疑义”。
③《朱文公文集》,卷73,页43上,“胡子知言疑义”。
①《朱文公文集》,卷73,页44下—45上,“胡子知言疑义”。
②《朱文公文集》,卷73,页43上下,“胡子知言疑义”;《二程集》,册1,页10。
③Wing-tsitChan(陈荣捷):ASourceBookinChinesePhilosop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3),p.529.
④钱穆:《朱子新学案》,册3,页209—215。
①《朱子新学案》,册3,页215—216。
②《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01,页4109—4110;(中华书局本),卷101,页2585—2586。
①《朱文公文集》,卷42,页4下,“答胡广仲第三书”。
②《朱文公文集》,卷46,页27下—28上;《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01,页4117,4119;(中华书局本),卷101,页2590,2591。
①《二程集》,册2,页366。
②《朱文公文集》,卷67,页20上下。
③《朱文公文集》,卷67,页20下。
①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百部丛书集成本),卷1,页7下,11下。
②佐藤仁:“朱子的仁说”,《史学评论》,第5期(1983年),页113。
③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页712。关于仁说,又参考钱穆:《朱子新学案》,册1,页55—60,73—81,345—366;册2,页39—81;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册3,页229—300;友枝龙太郎:《朱子の思想形成》,页102—122;刘述先:“朱子的仁说、太极观念与道统问题的再省察”,《史学评论》,第5期(1983年),页173—188;陈荣捷:“论朱子之仁说”,见其《朱子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页37—68,及《朱子新探索》,页371—381。
①刘述先:“朱子省察”,页177—181;刘先生根据陈淳的看法指出,朱熹在编辑张栻文集时,曾参考张栻的草稿而写完张栻的“仁说”。陈荣捷反对刘先生的意见,参见陈先生的《朱子新探索》,页376—381。
②《朱文公文集》,卷67,页20上。
③《朱文公文集》,卷33,页12上。
④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375—377;“论朱子之仁说”,页56。
⑤《朱文公文集》,卷33,页15上。
⑥《朱文公文集》,卷33,页15上。
⑦《朱文公文集》,卷33,页18下。“言仁录”是《洙泗言仁》的另一标题;序言部分在《南轩集》,卷14,页4上—5下。朱熹早一点提到它,见《朱文公文集》,卷31,页4下—5下,第十六书。又参考陈荣捷:“论仁说”,页56,58—59,及《朱子新探索》,页547。
①《朱文公文集》,卷31,页5上下。
①《南轩集》,卷21,页4上—5下。佐藤仁:“朱子的仁说”,页113—114。又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册3,页259—261。
②《朱文公文集》,卷42,页18上,“答吴晦叔第十书”;程颐的注解见其《易传》,卷2,在《二程集》,册3,页819。
①《南轩集》,卷21,页5上下。
②《朱文公文集》,卷32,页16下—18上,21上—24下;《南轩集》,卷21,页5上下;又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册2,页57—66;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册3,页259—261;佐藤仁:“朱子的仁说”,页125—129。
①《朱文公文集》,卷32,页18上下,19上下,21上下,23下—24下,33下—34下;《南轩集》,卷21,页5下,卷22,页5下—6上;又见陈荣捷:“论仁说”,页40—50;钱穆:《朱子新学案》,册1,页73—81,册2,页66—68;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册3,页267—272,285—296;佐藤仁:“朱子的仁说”,页127—129。
②《朱文公文集》,卷31,页6上;卷32,页17上—18上,20上下。又见钱穆:《朱子新学案》,册2,页70—7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册3,页273—284;佐藤仁:《朱子的仁说》,页128—129。
①《朱文公文集》,卷31,页5下—6上,卷67,页14上下,《观过说》;《南轩集》,卷21,页2下。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册3,页298;佐藤仁,页129—130;ChungTsai-chun(钟彩钧),TheDevelopmentoftheConceptsofHeavenandofMan,pp.146—148。
②《南轩集》,卷31,页5下—6上。
①《南轩集》,卷31,页6下。
②《宋元学案》,卷50,页1621。
③牟宗三:《心体与性体》,有关部分主要参考册3,页234—300。
①《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27,页1107;(中华书局本),卷27,689—690。
②《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37,页1570;(中华书局本),卷37,页985。
③《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20,页754;(中华书局本),卷20,页467。
④钱穆:《朱子新学案》,册1,页357—358,362—363;册2,页56。陈荣捷先生虽然回答牟宗三先生的部分问题,但是在“论仁说”(页44,49—51)中,陈先生只说这个看法是来自儒家另一个学派,没有展开详细的讨论。
⑤陈荣捷:“论仁说”,页55—58。他同意朱熹在此误解了张栻的看法。
⑥朱熹删除“无有不爱”与“不忍之心可包四德”。见陈荣捷:“论仁说”,页54—55。朱熹的“仁说图”见《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05,页4185;(中华书局本),卷105,页2633。
①佐藤仁,“朱子的仁说”,页122。
②《南轩集》,卷18,页1上—2上。关于他们观点差异,参见《朱文公文集》,卷32,页21上—33下,卷33,页15上,18上下,20上下;陈荣捷:“论仁说”,页56—58。
③陈荣捷:“论仁说”,页57。
④佐藤仁:“朱子的仁说”,页131。
①《朱文公文集》,卷47,页27上,在1185年写给吕祖俭的第25封信;又参见刘述先:《朱子哲学》,页145,189—90,及其“朱子省察”,页180。
②《朱文公文集》,卷47,页27上下。
①参见“年谱”,《东莱吕太史文集》(续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三编),册九;《宋史》,卷434,页12872—12874;《宋元学案》,卷51,页1652—1688;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邱汉生主编:《宋明理学史》,册1,页340—367;刘昭仁:《吕东莱之文学与史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页1—26;姚荣松:“吕祖谦”,收入王寿南总编辑:《中国历代思想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页1—17;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54—555。
①《宋元学业》,卷51,页1653。中原文献对吕学影响亦见于《宋史·吕祖谦传》,卷434,页12872。又参见孙克宽:《元代金华学述》(台中:东海大学,1975)。
①《宋元学业》,卷73,页2434;邱汉生主编:《宋明理学史》,册1,页341;刘昭仁:《吕东莱》,页215—262。
②对这些特点的讨论见于邱汉生主编:《宋明理学史》,册1,页341—344;《宋元学案》,卷36,页1234;步进智:“论吕祖谦的“婺学”特征”,《中国哲学史研究》,第2期(1983年),页89—98;刘昭仁:《吕东莱》,页113—121。
③《二程集》,册1,页338。
①张九成:《横浦文集》,卷20,页1上下;卷19,页9下—页10上;及其《横浦日新》(附于《横浦文集》),页17下。
②吕祖谦之师承,见刘昭仁:《吕东莱》,页84—93。
③《宋元学案》,卷32,页1127—1158。
④《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22,页4719;(中华书局本),卷122,页2949。
①《朱文公文集》,卷43,页21下。
②《吕东莱先生文集》(国学基本丛书本),卷14,页342—343,“易说·睽卦”;邱汉生主编:《宋明理学史》,册1,页343,认为这句话“很接近于禅说”。
③《朱文公文集》,卷47,页22上,第十九封给吕祖谦的信,写于约1177—1181年。
④《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24,页4762;(中华书局本),卷124,页2973。又参见束景南:“朱熹佛学思想渊源与逃禅归儒的三部曲”,朱瑞熙编,《朱熹教育和中国文化》,页3—35。
①钱穆:《宋明理学概述》,页198—199。又见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页41—47。
②《东莱吕太史文集·别集》,卷9,页8下,与刘衡州(名清之,字子澄)信;又见《吕东莱文集》,卷4,页90。
③《东莱吕太史文集.别集》,卷10,页1上,与陈傅良(君举)。
④《吕东莱文集》,卷20,页464,“杂说”。
⑤《宋元学案》,卷36,页1234。⑥《宋元学案》,卷19,页788。
①《宋元学案》,卷36,页1234。
②《宋史》,卷434,页12874。
①《吕东莱文集》,卷4,页84,又见页81,92。不但吕祖谦的症状,他三次丧妻也使人怀疑与肺结核病有关,因为历史上肺结核病对年轻妇女尤其有致命的危险。
②《朱文公文集》,卷82,页2上。
③《宋史》,卷434,页12874。
①《宋元学案》,卷51,页1654。
②《吕东莱文集》,卷4,页74。
③《东莱吕太史文集·别集》,卷9,页8上,与刘清之(子澄)书。
④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54。
①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页1—27。另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454—455。
②《宋元学案》,卷51,页1674。
③《宋元学案》,卷51,页1675。
①吕祖谦:《东莱先生左氏博议》,清人刘钟英注(宝山斋本;台北:世界书局重印,1984年),“东莱先生自序”。参见刘昭仁:《吕东莱》,页33—75。
②《宋元学案》,卷51,页1666。
③《宋元学案》,卷51,页1667。
④《宋元学案》,卷51,页1664。
⑤李心传:《道命录》,卷3,页6上,7上。又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页147—149;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80,页867—868。
①《吕东莱文集》,卷5,页127。
②《吕东莱文集》,卷20,页465,“杂说”。
③《宋元学案》,卷51,页1657。
④《宋元学案》,卷51,页1673。
①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9,页1上—7上。
②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页156—162。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担任地方官时执法很严; 参见 Conrad Schirokauer(谢康伦),“Chu Hsi as an Administrator, A Preliminary Studyin Francoise Aubin, ed., Etudes Song: Sung Studies in Memoriam Etienne Balazs.1st ser., no.3(1976), pp.228-232.除此以外,吕祖谦似乎比朱熹更肯定法律。
③《吕东莱文集》,卷20,页457,“杂说”;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思想初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39-47。
④《吕东莱文集》,卷19,页443,“史说”。
①吕祖谦:《东莱博议》,卷2,页138—139,“卫懿公好鹤”。
②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页285—302。
③吕祖谦:《东莱博议》,卷2,页139,“卫懿公好鹤”。
④《吕东莱文集》,卷19,页431,“史说”。
⑤《吕东莱文集》,卷20,页462,“杂说”。
①《吕东莱文集》,卷19,页431,“史说”。
②《吕东莱文集》,卷20,页453,“杂说”;又见卷12—14,“易说”。
③吕祖谦:《东莱博议》,卷3,页167—168。
④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四库全书本),卷9,页1上—7上。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思想初探》,页156—160。
①吕祖谦:《左氏传续说》(四库全书本),卷1,页1上,“纲领”。
②吕祖谦:《东莱吕太史文集·外集》,卷5,页26上。
③《吕东莱文集》,卷20,页462,“杂说”。《宋元学案》,卷51,页1663。
④刘昭仁:《吕东莱》,页178—190。
①见刘昭仁:《吕东莱》,页52—53,197。又参见吕祖谦:《大事记》(四库全书本);胡昌智:“吕祖谦与其史学”(硕士论文,台湾大学,1973年)。
②吕祖谦:《三国志详解》,卷1和12,见其《十七史详解》(1669—1670年山西刊本,普林斯顿大学善本书)。
③《吕东莱文集》,卷13,页309,“易说”。
④《吕东莱文集》,卷18,页415—416,“孟子说”。
⑤《吕东莱文集》,卷5,页121,“致潘叔度信”。
⑥《吕东莱文集》,卷20,页450,“杂说”。又见卷4,页96,“答潘叔昌”。
①《吕东莱文集》,卷3,页52,“致朱熹信”。
②《吕东莱文集》,卷20,页455,“杂说”。
③吕祖谦:《左氏传说》(百部丛书集成本),卷6,页12下—13上。
④参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9,页46下。
⑤《吕东莱文集》,卷18,页420,“孟子说”。
⑥《宋元学案》,卷51,页1657—1658;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思想初探》,页64—69。
①《吕东莱文集》,卷17,页391,“论语说”。
②《吕东莱文集》,卷17,页391,“论语说”。
③《吕东莱文集》,卷18,页417;又见“孟子说”,页420。
④《吕东莱文集》,卷17,页392,“论语说”。
⑤《吕东莱文集》,卷3,页60,“致朱熹信”。
①《吕东莱文集》,卷20,页461,“杂说”。
②《吕东莱文集》,卷20,页465,“杂说”。
①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55。
①《朱文公文集》,卷33,页12上,致吕祖谦第18封信;又见卷94,页27上,“亡嗣子圹志”;《续集》,卷8,页6上—8下;《东莱吕太史文集》,卷7,页16下—17上,致朱熹第20封信。
①《宋史》,卷362,页11332。
②《宋史》,卷362,页11329—11332;卷376,页11635—11637。
③《宋史》,卷434,页12872;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思想初探》,页52—60。
①《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33,页5135;(中华书局本),卷133,页3200。
②《朱文公文集》,卷77,页23下—24下;RichardvonGlahn,“CommunityandWelfare:ChuHsi'sCommunityGranaryinTheoryandPractice,”inRobertP.HymesandConradSchi-rokauer,eds.,OrderingtheWorld:ApproachestoStateandSocietyinSungDynasty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pp.223—236;梁庚尧:《南宋农村的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页279—293,及其“南宋的社仓”,《史学评论》,第4期(1982年),页1—33。
①梁庚尧:《南宋农村的经济》,页267—274;又参见王德毅:《宋代灾荒的救济政策》(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
②《南轩集》,卷12,页8下。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新校标点本,1959年),附1,页392—394;梁庚尧:《南宋的社仓》,页5—10。
③《朱文公文集》,卷79,页15下—17上。
①RichardvonGlahn,“CommunityandWelfare,”pp.236—238,242—246.
②《朱文公文集》,卷74,页23上—30上,特别23上下;卷99—100,特别卷99,页20下—21上。又见Monikaübelhor(余蓓荷),“TheCommunityCompact(Hsiangyueh)oftheSungandItsEducationalSignificance,”inWm.TheodoredeBaryandJohnW.Chaffee,eds.,Neo-ConfucianEducation:TheFormativeStage,(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pp.371—388;与ChuRon-Guey(朱荣贵),“ChuHsiandPublicInstruction,”Ibid.,pp.252—273;李晓东:“论吕大钧之《吕氏乡约》在理学史上的地位”,《西北大学学报》,第2期(1987年),页27—32。
①《宋元学案补遗》,卷49,页154上下;《宋元学案》,卷97,页3226。参见李弘祺:“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国立编译馆刊》,第19卷,第2期(台北,1990年)。
②《朱文公文集》,卷34,页11下,第69封信。
③杜甫:“赠左仆射正国公严公武”(赞严武诗),见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16,页1387。关于文翁事迹,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89,页5181—5183。
④关于书院历史以及朱熹的作用,特别参见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李科友:““意不在鱼”论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收入朱瑞熙编,《朱熹教育和中国文化》,页96—114;石之:“白鹿洞书院史事杂考”,收入朱瑞熙编,《朱熹教育和中国文化》,页346—350;李弘祺:“精舍与书院”,收入《汉学研究》,第10卷第2期(1992年),页307—332;陈荣捷:“朱子与书院”,万先法译,《史学评论》,第9期(1985年),页1—32;刘真:“宋代的学规和乡约”,收入《宋史研究集》,第1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58年),页367—391;朱汉民:“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中国哲学》,第16辑(1993年),页495—518;而且《白鹿洞书院通讯》从1189年开始。
①LindaWalton-Vargo(万安玲),“Education,SocialChangeandNeo-ConfucianisminSung-YüanChina:AcademiesandtheSocialEltieinMingPrefecture,”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Pennsylvania,1978,pp.243—247;该文总结现代中日学者对书院的解释。
②《朱文公文集》,书信见卷26,页3上—4下;卷50,页1上下;诗见卷7,页4下—6上;又见《别集》,卷7,页10上;致吕祖谦信见卷34,页9上下,13下,14下,24下,32上。周敦颐曾任南康知州,1071年在那里致仕。
①John Chaffee(贾志扬),“Chu Hsi in Nan-k'ang:Tao-hsueh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in Wm.Theodore de Bary and Chaffee,eds.,Neo-Confucian Education:The FormatiVeStag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416;贾志扬先生根据后来的矛盾发展看待这个时候的朱杨关系。
②《朱文公文集》,卷74,页17下。
①《朱文公文集》,卷82,页13上,朱熹为程端蒙学则作的跋文。
②《朱文公文集》,卷74,页16下—17上。
①《吕东莱文集》,卷10,页247;《东莱吕太史文集·别集》,卷5,页1上。
①《吕东莱文集》,卷10,页247—249;《东莱吕太史文集·别集》,卷5,页1上下。
②《吕东莱文集》,卷6,页138—139。
①邓广铭:“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收入季羡林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53—60。
①《南轩集》,卷10,页4下—5上,8上—13下,卷34,页4上下;胡宏:《五峰集》,卷3,页14下—16上。周敦颐:《周濂溪先生文集》(百部丛书集成本),卷13,收录很多宋人对他的颂文。另一出处见张栻的《南轩集》,卷9,页6下。
②《杨龟山文集》,卷5,页1下。
③《朱文公文集》,卷35,页7上—11上。
④《宋元学案》,卷12,页520。
①《二程集》,册2,页638,“明道先生行状”。又见朱熹:《伊洛渊源录》(百部丛书集成本),卷2,页11上。
②《朱文公文集》,卷76,页22下。
③关于传统上的哲学诠释,见陈荣捷:“朱子道统观之哲学性”,《东西文化》,第15期(1968年9月),页22—32。关于朱熹对周敦颐作用的看法,见《朱文公文集》,卷78,页12上—13下,15上—16上;卷79,页9上—11上;卷80,页11下—12下;《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93,页3741—3744;(中华书局本),卷93,页2356—2358。
④《朱文公文集》,卷80,页11下。
①在1190年左右,《诸儒鸣道集》成为北方道学在金人统治下复兴的主要依据;参见田浩:“金代儒教:道学在北部中国的印迹”,《中国哲学》,第14辑(1988年),页107—140。
①纪旳、永珞:《四库全书总目》(1782年四库全书本;北京:中华书局修订本,1965年),卷57, 页 519.
②Don J. Wyatt, “Chu Hsi's Critique of Shao Yung: One Instance of the Stand Against Fatalis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 2 (December 1985), pp. 649—666.陈荣捷:“朱子之《近思录》”,收入其《朱子论集》,页126。
③陈荣捷:“朱子之《近思录》”,页 132—136;及其(Wing-tsit Chan), trans. , Reflections on Things at Hand :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u Hsi and Lii Tsu-ch'ien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330—336;我根据书中的数字计算百 分比。
①Wing-tsitChan(陈荣捷),ReflectionsonThingsatHand,pp.324—325;钱穆:《朱子新学案》,册3,页156—157。
②《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19,页4592;(中华书局本),卷119,页2874—2875。
③邱汉生:“《伊川易传》的理学思想”,收入《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597—632。又参见KidderSmith,Jr.PeterK.Bol,JosephA.Adler,andDonJ.Wyatt,eds.,sungDynastyUsesoftheIChing,(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AnneD.Birdwhistell,TransitiontoNeo-Confucianism:ShaoYungonKnowledgeandSym-bolsofReality,(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pp.30—49.
①《朱文公文集》,卷38,页5下;卷66,页11下一27下;卷82,页20下;卷85,页6上 —8下;《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66,页2579;卷67,页2624—2632,2651;(中华书局本),卷66, 页1622;卷67,页1649-1654,1666.吕祖谦:《东莱吕氏古易》(百部丛书集成本)。又参见 钱穆:《朱子新学案》,册1,页501-522,册4,页1 —52;束景南:《朱子大传》,页594-606, 734-749i吾妻重二:“朱子の象数易思想とちの意义”,《フィロリフィア》,第68号(1980 年),页145-175;钟肇鹏:“朱熹的易学思想”,收入中国哲学史学会编:《论宋明理学》(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281—298;邹水贤:“朱熹解经的指导思想和他关于易学的几 个基本观点”,收入其主编:《朱熹思想丛论》(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页209-228; 曾春海:《朱子易学探微》(台北:辅仁大学,1983年)。Chang Li-wen (张立文),“Chu Hsi's System of Thought of I,” in Wing-tsit Chan, ed. , Chu Hsi and Neo-Confucianism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pp. 292—311.
②《朱文公文集》,卷33,页32下,第47封信。
①黄幹:《勉斋集》(四库全书本),卷36,页36上下;王懋竑:《朱子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重印本,1966年),卷4下,页216。又参见钱穆:《朱子新学案》,册2,页480—501。朱熹另外转求神谕的例子,见《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07,页4244—4245;(中华书局本),卷107,页2669—2670。
②吕祖谦:《东莱博议》,卷2,页109—110。
①吕祖谦:《增修东莱书说》(百部丛书集成本),卷3,页21上。
②《增修东莱书说》,卷7,页1下;卷9,页5下;卷10,页2下;卷14,页13下;卷15,页3下;卷19,页18上下;卷20,页4上;卷22,页8下;卷23,页4上;卷28,页12上。在卷10,页2下,吕祖谦引用《尚书》中“咸有一德”章。
③《增修东莱书说》,卷3,页17上下;邱汉生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页347。
④《吕东莱文集》,卷20,页451,“杂说”。
①《东莱博议》,卷1,页74。
②《东莱吕太史文集·别集》,卷16,页14上;卷16,页11上下。
③《东莱博议》,卷2,页164。
④《增修东莱书说》,卷8,页13下。
⑤《增修东莱书说》,卷8,页2下—3上;又见《东莱博议》,卷3,页196。
⑥《增修东莱书说》,卷12,页10上。
⑦《增修东莱书说》,卷3,页17下—18上。
①《吕东莱文集》,卷13,页301—303,“易说”。
②朱熹:《周易本义》(四库全书本),卷1,页44下—45上。
①《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95,页3887;(中华书局本),卷95,页2447。
②《荀子》(四部丛刊本),卷2,页4上下。
③朱熹:《朱子全书》(1713年渊鉴斋本;台北:广学社重印,1977年),卷45,页6上;又见《朱文公文集》,卷11,页8下,卷13,页6上—7上,卷57,页36下,卷95下,页22上下,以及《续集》,卷10,页14下。
④例如,ChanWing-tsit(陈荣捷):“EvolutionoftheConfucianConceptJen,”PhilosophyEastandWest,4.4(January1955),pp.295—319;以及其“TheNeo-ConfucianSolutiontotheProblemofEvil,”BulletinoftheInstituteofHistoryandPhilology,AcademiaSinica,28(1959),pp.773—791.
①Hoyt Tillman(田浩),Consciousness of T'ien in Chu Hsi's Thought,”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7.l(Jupe1987), pp.43—48.②胡宏:《五峰集》,卷2,页67上;《胡宏集》,页41。
①RobertHymes(韩明士),StatesmenandGentlemen:theEliteofFu-chou,Chiang-hsi,inNorthernandSouthernSung.(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6),pp.82—104,115—123.他强调婚姻形式的变化,但也说新迁入的家族可能是例外,见页211。
①《宋元学案》,卷51,页1670。
②《朱子语类》(正中书局本),卷122,页4719;(中华书局本),卷122,页2949;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59—561。
①《朱文公文集》,卷31,页4上;又见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59—561。
②《南轩集》,卷22,页3下。
③他的外祖父曾幾(1084—1166年)以及他的叔祖父吕本中都是有名的诗人。曾幾曾经受到江西诗人影响,但是他的好友吕本中却没有将他置于江西诗派的名单中。参见,刘昭仁:《吕东莱》,页147—153。
④刘昭仁:《吕东莱》,页129—159,特别是页132—133,141,144—145。
⑤《朱文公文集》,卷39,页45下。
⑥《吕东莱文集》,卷3,页78。
①《朱文公文集》,卷33,页6下,致吕祖谦第7封信。
②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本),卷17,页124—125;又参见刘子健:《论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3年)。
③《朱文公文集》,卷87,页12下;又见其《别集》,卷3,页12上。
①吕祖谦给张栻的一封信中提到他对朱熹的告诫,而张栻写信给朱熹,也曾经引用;见《南轩集》,卷22,页9下。朱熹给张栻的第27封信中承认这项缺点,见《朱文公文集》,卷31,页15下。又参陈荣捷:《朱子新探索》,页521—523。
②《南轩集》,卷20,页10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