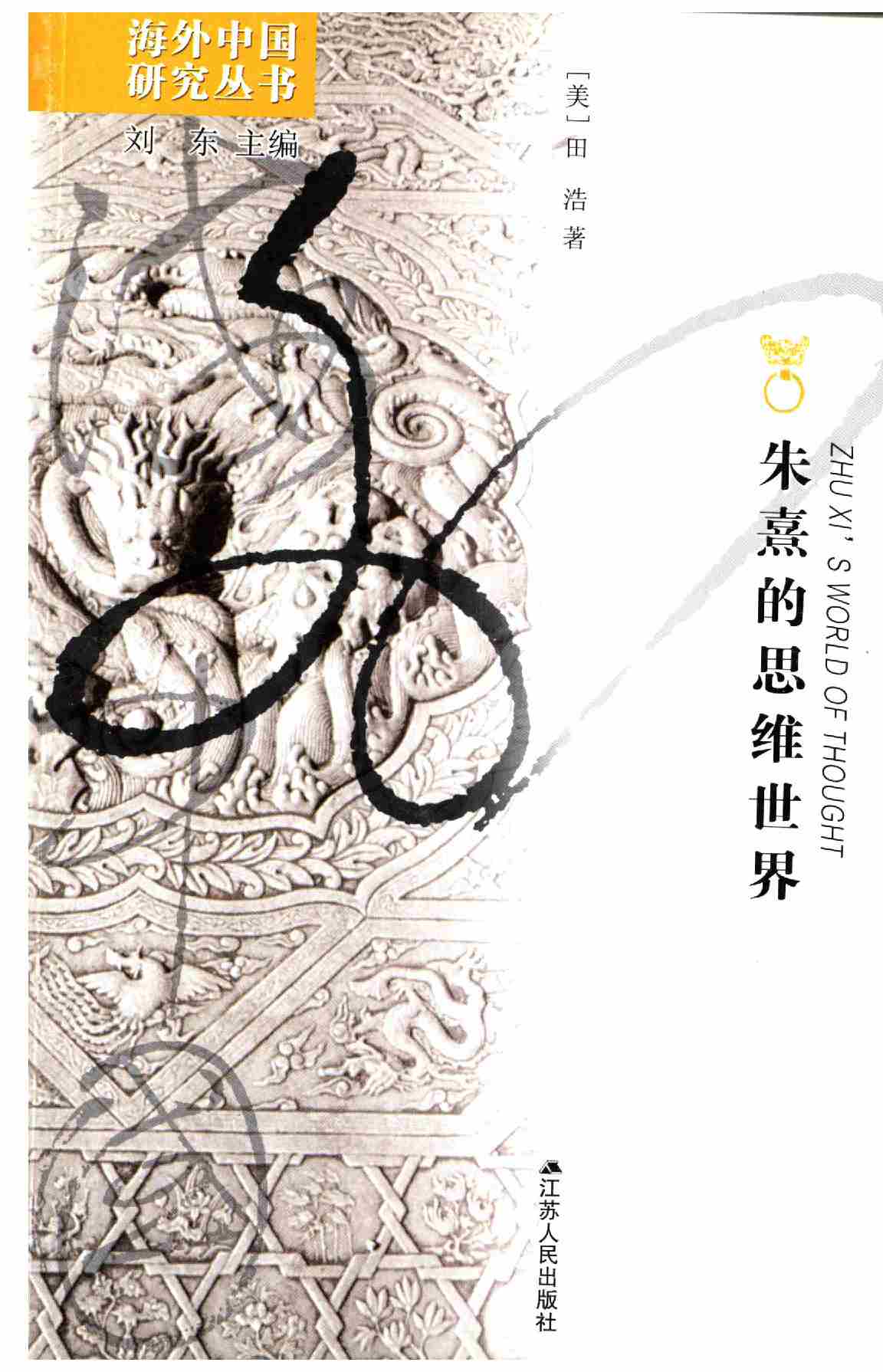内容
第一部
第一时期(1127—1162)女真人在1127年征服中国北方,导致中原文化的断裂,对宋代儒学的发展是一大灾难。南宋的朝廷在陪都临安(今杭州)致力重振朝纲,以巩固南方、抗拒女真金国政权(1115-1234年)的兼并,但南宋政权惨淡经营之余,不得不忍受耻辱,与金人和谈,因为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包括北宋的最后两个皇帝,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女真人公开蔑视汉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中原汉人接受女真人的发型和服饰。北宋的沦亡以及中原文化地区的丧失震撼知识分子和朝廷大臣,儒家知识分子为那些没有保持忠贞节操,甚至投靠“蛮夷”的士大夫感到特别的羞耻。①这些变化使人对儒家教育的效果提出质疑,同时也加深他们对儒家行为和价值观的忧虑。
很多儒生学者相信复兴文化和道德观可以使他们获得重建国家、驱逐外敌的力量;胡宏说:“中原无中原之道,然后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复行中原之道,则夷狄归其地矣。”②在此背景下,儒家学者之间展开一系列的辩论,探讨怎样的传统オ是对“道”正确的诠释,以及什么传统能成为儒教社会的价值标准。
南宋成立的头十年中,道学士人还是少数,但是有机会向年轻的高宗皇帝(1127—1162年在位)进言。高宗为求得政治军事的稳定,首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高宗对北宋最后30年控制朝政的改革派怀有敌意,不过,他也意识到即刻改变推行已久的新法并非易事,因此他不进行重大改变,而保留以前新法的政策。不过,高宗依然留恋保守的元祐时代,下令追封加谥司马光、苏轼和程颐等人。从1127年到1137年的十年中,重臣如吕好问(1064-1131年)和赵鼎(1085—1147年)等人对道学很有好感,道学人士在1132年和1135年的科举中名列榜首,甚至传闻说朱震(1072—1138年)要担任1138年的科举主考。朱震由于赵鼎的推荐而得到高宗的重用,担任皇子赞读,以后又升任中书舍人兼诩善;他是程颐的第二代门人,对《易经》颇有研究。①
由于道学迅速发展,朱震在1136年正式上书高宗,提出他对道统传承的看法。朱震所陈述的道学师承有如家族的世袭关系,这种师承关系虽然与佛教禅宗的说法相当类似,但是儒家的师承仍与佛教有不甚相同之处。禅宗大师往往要把象征权威和教化的衣钵交给他选定的继承人,而且这种师承关系历久不断;儒家发展的过程却有上千年的中断,所以师承的过程和内容也不同于佛教。在儒家体系中,每代学生中可以有一人以上接受师门传承,个人也可以自己得道,不需要老师的认可。而且,儒家不能像禅宗那样地“默传”,经典对儒家非常重要。二程虽然在儒学中断千年之后复兴道统,但不表示他们的传承不借助文字,因为经典(我们将在第五章加以讨论)是他们与圣人之心间不可或缺的联系。按照朱震的说法,儒家之道是由孔子经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子思(公元前492—前431年)到孟子的时期建立起来的,但以后道的传承中断达千年之久,直到北宋程氏兄弟出现为止,所以程子之学是儒学之道的真正传人,而程子的门人又将道传到南方。②这个看法虽然在道学群体之间广泛流行,但以前没有人在朝廷上公开讲过。
朱震发出垄断道统的大胆宣言,立刻引起异议。陈公辅和吕祉(1092—1137年)要求高宗禁止程颐的私学影响朝廷和科举,认为拥戴程氏兄弟的人受到北宋末年结党营私风气的影响而在堕落腐化;不论是程颐的私学,还是王安石的新法,都强迫大家同意他们的观点。陈公辅指出,禁止这种学说是复兴北宋王安石新法以前较自由讨论风气的唯一办法,并且用“狂言”、“怪语”、“淫说”和“鄙喻”形容程颐复兴孟子死后失传的道的说法,对程颐弟子的傲慢举止也大感不快,因为他们: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程〕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①南宋许多道学人士确实极力模仿古人,甚至学习古代的装束和举止作为。刘子健先生收集许多相关的材料,这样描述道学家:他们〔道学人士〕戴尖顶高帽,便装时又着圆帽,宽袍大袖,内衬白细薄纱。他们举止规范严格,直身正坐,度步直视,鞠躬深缓以示敬意,言语威严而少以手势相助。②这些看似矫饰的行为显示,这批力图恢复圣贤之道的儒士有极严格认真的生活方式和礼仪规定,但是这种过度矜持的做法惹恼了世儒和宿儒。
胡安国和尹淳(1071-1142年)挺身为二程之学辩护。胡安国在1137年所上的奏章中,极力排解这些责难,认为它们反映了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对程氏兄弟和司马光的攻击,他并且列举德高望重的学者,如谢良佐(1050-1120年)、杨时都是程氏兄弟的学生,并且刻意突显程颐与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1027-1097年)等元祐保守党人中资深政治家的关系。胡安国提到这些学者,目的是要缓和许多人对道学家行为举止的不满,但他对二程复兴道统的说法没有让步: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复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①程子之学是得道入门的途径,二程使宋代士人可以更确切了解先贤圣人的思想。胡安国认为这四个人以“道学德行”而闻名于世,大胆地要求为邵雍、张载和二程加封荣衔,不过高宗对他的建议并未理睬。
高宗认为应该限制这种正在发展的私学,以及它奇特的治学方法,所以态度倒向反道学的一边。他采纳吕祉的建议,发布敕令,张贴在太学中,要求学生研习古籍经典,而不是近世小人的文章。张淳(1096—1164年)虽然大力保荐胡安国出任官职,但他自己要求从征选任官的名单里除名。由于年长道学人士主动求退,赵鼎和张淳又遭罢免,秦桧(1090—1155年)的权力更形坐大。从1138年直到他去世为止,主和的秦桧使高宗的政权稳定下来,朝廷虽然明文规定官吏的铨选以及科举考试不会因考生的背景而有差别待遇,但其实高宗容许秦桧的主和派打压意见不同的人,尤其是排斥主战立场强硬的道学人士。秦桧当政期间与同党把持官吏的选用和科举考试,有时在朝廷上用“专门之学”这个巧妙的称谓贬抑赞成二程的学人官员,②暗示道学对儒学的理解相当狭隘,并且在1144年的科举排挤追随这种“专门之学”的学生。秦桧的专权和打压异己使思想文化窒息,③不过,比起北宋末几十年间压制元祐党人的做法,高宗还没让秦桧及其同党做得那么过分。
气氛即使压抑凝重,有些儒生学者还是致力保存道学的传统,甚至小有程度发展道学传统。年长的学者如杨时、尹淳与胡安国致力传授从程颐那里学习的道学学术。在女真人入侵前后,他们的学术活动为道学在南方打下基础,但是他们在南宋时期只过了8—15年时间,就相继去世。我们的讨论就从高宗时期道学人士的活动谈起,当时道学的根基已经足以支持几个枝干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第一章 南宋第一代学人:张九成与胡宏
程颐等人去世后,道学的幼苗仍然在一些重要地区顽强地发展。这个时期没有一个权威中心的人物,因此与世纪交际程颐领导道学的时期相比,此时的道学更具有多元的特性。12世纪60年代初以后,朱熹批判二程身后的两代门人,认为他们把二程之学引向歧途,尔后的儒家学者大多接受朱熹的看法。我们很难摆脱朱熹的影响,直接理解这些早期道学思想家,但是这些思想家对于我们了解12世纪道学的发展却至关重要。这一章将以两位很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来描述南宋初期道学群体内部的多元性。张九成和胡宏之间犹有分歧,但他们在论史、注疏经典以及传述道学传统时,有些共同关怀的课题,而他们对北宋道学名家的重要概念的评论,也能帮助了解12世纪道学成员所重视的思想要务。
一、张九成
张九成曾在北宋首都开封修习二程之学,主要师事杨时。他返回家乡杭州后,在1132年考中状元,得以进入礼部踏上仕途。张九成的著作中有1/4的篇幅是论史的文章,但是他曾三次婉拒高宗请他讲解《春秋》的要求。他在受命讲解《春秋》伦理内容时,推托说只能讲解《论语》和《孟子》。不过,高宗曾提到,就历史的学习而言,他从张九成那里所学到的知识,比从道学和史学名家胡安国那里所学到的要多。①除了曾抡取状元的荣衔外,他对《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的注解在当时也享有盛誉,不过,目前只有他对《孟子》和《中庸》的大部分注疏保留下来。他在一份上书中讲到:“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②由于如此直言不讳地抨击和金政策,于是触怒了权相秦桧。秦桧以其结党为借口,将他流放在外达14年。因为秦桧翦除异己,张九成认为“有道之士”可以谢绝入仕。③1155年秦桧死后,张九成才复出担任温州知州。
二程对天理、格物和个人修养的看法,在张九成的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张九成不仅继承程颢以理为万物自然之倾向的主张,而且也接受程颐理为天地万物的根源的观点。他与程颢都强调理为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而且理内在于人情,但更重于人情。他说:“理之至处,亦不离人情;但人舍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远。”④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也可以看到这种天理与人情的不同:“圣人以天理为人情,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⑤
张九成强调格物穷理为学问的首务。他建议说:
观六经者当先格物之学。格物则能穷天下之理,天下之理穷则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矣。⑥从心中的念头到外在的万事万物都遵守此理的规范,所以人应该开放心胸,关心万事万物,然后回归一理,如此则可与万事万物合而为一,所以,格物致知基本上是一种以修养达到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努力,而修养功夫必须集中在克除一己私欲,不懈地自律,以及在心性中存养天理。
张九成“心”、“仁”的概念主要来自程颢。他在论及程颢关于“医书以四肢痿癖为不仁”的看法时,把仁当做心的知觉;他解释说:“仁即是觉,觉即是心。因心生觉,因觉有仁。”①所谓“觉”不但意指感官知觉,也指对他人痛苦的感受,所以仁是一种与人合为一体的感觉。张九成用心能够感受他人的痛苦解释仁的意义,出自《孟子·告子上》的讨论。张九成诠释这段文字说:“仁之一理最是圣门亲切学问,唯孟子识得,故曰:‘仁,人心也’。”②仁体如天公正不私,又如道不可名物,张九成如此断言是因为仁就存在人心中,因此,实现仁的唯一方法就在于求仁于人心之中。
张九成认为心是通往仁的途径,也是万物的根源,所谓“心即理,理即心”。有时他对万物本体的论述似乎是一种哲学的唯心论,他说:“夫天下万事皆自心中来。”③张九成的观点还涉及到经典权威的问题,他认为大部分的经典在秦代已付之一炬,所以许多出于人心的道理已经无法在经书里寻得,唯有在后来贤士哲人的著作中才能找到人心中的道理。④
一旦此心悟出心中之理,那么他就会了解“《六经》皆吾心中物也”⑤,因为这些经典只是记载古代圣贤之心所发现的天理。张九成显然没有阐发哲学的唯心论,而是再三强调心在功夫修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谓的心一直是在修身养性的意义下谈的:“君子之心常厚,小人之心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乱、安危、得失、成败所自生也,不可不戒。”⑥
张九成对心中之物的看法多与文化道德修养有关,而他的论述基本属于这个范围层次。他最突出的观点是强调个人修养的实践、历史和经典的学习,而不是周敦颐曾为之冥思苦想的那种“无极而太极”。张九成告诫说:“道非虚无也,日用而已矣。以虚无为道,足以亡国。”①为避免走上这种异端,张九成教训说:“学问于平淡处得味,方可入道。”②也许我们现代人会觉得这些话平淡无奇,但是这种平凡正是宋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
张九成论及心的超越面向时,不仅认为它与新的哲学观念“天理”的意义相通,并且使用比较古老而不常使用的观念“天心”说明。例如,他至少两次将周文王的心视为“天心”,而心的意义更广泛时,他宣称:“秉此忠诚,上通天心,下通三王之心。”③张九成引用比较古老的“天心”观念,并且强调功夫修养,都反映他比较注重文化价值,介于实际政策与思辨哲学间的学术理论。
张九成维护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但不反对佛教。他与临济宗名僧大慧宗杲(1089—1163年)是挚友,他们被秦桧流放到同一地区渡过十年,因此相处甚为亲密。宗杲用佛教的语言解释《中庸》和格物的意义,力图糅合儒、佛、道三教为一家,并劝导张九成兼容三家学说,所以后来许多关于张九成的材料来自佛教的记载。张九成承认佛教有些正确的观点,并且把佛的“空”性哲学解释成去除人欲的道德修养,大慧宗杲无疑影响了张九成的儒学典籍讨论与注释;此外,张九成强调用格物的方法,以达到与万物合一的境界,与宗杲提倡的反省与觉悟,是他们最重要的相似之处。禅学的影响也促使张九成追随程颢提出的学说,将仁与心的知觉相提并论,并且认为心是理的根本。④这些综合的观念是他对道学重要概念发展的贡献。
这里谈到张九成在继承发展二程的理论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能平衡一般认为他是佛教徒的看法。张九成去世不久后,这种看法就开始流传。陈亮在12世纪60年代初曾经说:“家置其书,人习其法”,认为很多士人都受到迷惑,他对儒学的损害远甚于古代的杨朱和墨子。①根据张九成自己的看法,杨墨的异端很难排挤,因为他们同意儒学的某些伦理价值观念:“人多不识异端,所以难去。只如杨、墨,本学仁义,仁义岂是异端?惟孟子能辨之,故能去之也。”②
张九成虽然并不反佛,而且努力寻求儒佛学说的共同点,但仍然认为儒学比佛学优异。张九成批评佛学破坏儒家的基本三纲五常,导致伦理实践的缺失:
故君子谨其独也,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之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止于此而不进。
③从儒家的观点而论,佛学自满于参禅静坐,张九成则认为要达到道德的境界,需要不断修身养性,以建立更完善的自我与社会。他因为佛教的出世倾向而指责佛教执著于空的观念,而且始终自认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与佛教徒并不相同。张九成时代的许多程学门人对禅学颇感兴趣,所以他与佛学的关系密切,其实提高了他当时的声望。
张九成在南宋第一代学者中的声望,以及他很具代表性的儒佛合一论的观点,都在现存最早的道学文选《诸儒鸣道集》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部文选是一位或数位不知名的张九成弟子在12世纪60年代初期编辑的。①张九成与学生对谈的两卷记录“日新”,占全书最重要的地位,可见该书的编者认为张九成代表当时道学传统的高峰;但这个观点与朱熹的看法不同。
二、胡宏
胡宏是道学另外一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致朋友和学生的信中警告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②他的学生张栻说,胡宏的文章用心与“道学”一致。③这些材料整体显示胡宏的道学是他与学生、同道追随的一种思想、文化和道德的特殊传统。
胡宏来自经济发达的福建地区,但他选择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湖南地区,在当地任教20年。他年轻时曾经追随杨时,但大体师承父亲胡安国的家学,而这两位老师影响程学的传授甚巨。胡安国在朝廷担任官职,所以胡宏得以承荫受封荣衔,并且有几次出任官职的机会,但都因为反对朝廷的和金政策终身不入仕途。他爱国忧民,多次上书高宗皇帝,要求政府整饬纲常、强化军事以抗击金人。他认为高宗若能爱民,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国家就会强大,得以一雪金人入侵的仇恨,并且恢复中原。④秦桧曾询问胡宏是否愿意入仕,他表示不感兴趣,但谈到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却极表热心,⑤秦桧只好让他主持岳麓书院。秦桧死后,他仍在乡间致力教学,放弃入仕的机会。
胡宏笃信知先于行,一生致力于教授信仰的儒家史学和正统理论。他曾经根据程颐《易传》的要旨,为《易经》写作一卷注解。胡宏也曾编写《皇王大纪》,以80卷的篇幅叙述上古到周末的历史,承续父亲的《春秋》注释中的教化史学;胡寅(1095—1156年)史学的最主要特色也是以经典的褒贬治史。胡氏的家学不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为司马光的历史著作不足以适切运用儒家经典的道理与教训。道学发展的初期阶段,除胡氏一家人外,道学人士很少是历史学家,不过张九成本人与吕祖谦的几位家人写过历史著作。此外,胡氏一家对佛教有不容调解的敌意,在当时也有些反常。胡氏家人不但严厉拒斥儒佛调和,并且激烈抨击佛学,认为佛学将儒家的“心”等概念引入歧途。①胡宏殷切期望击退禅宗诱人的影响,并以经典与历史研究恢复古代的理想制度,这种心情促使他兼重儒学形而上学与社会政治制度层次的问题,与张九成专注两者间的文化价值层次的论题不同。
胡宏哲学思想的中心是以人性为天地的本体。《中庸》开宗明义地说:“天命之谓性”,胡宏解释道:“性,天下之大本也。”②他又赞扬人的内在本性:
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③
胡宏这里所谓的性无所不包,理则是万物各别涵具的理,理的层次比性低,而且比较偏颇。性无所不包,气自然也不能例外:“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①
内在的本性既然无所不包,圣人也对它不可名状,所以性有如“不可名”的道。性是理与气的基础,道也不能与实在的事物分离:“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②他还解释说,道家和一些儒生所谓“无”,只是道可见以前的状态;有形的事物可见,但道的“无”,其实只是人不能看见“道”而已;万物之理并不是“无”,老子等人把“无”当做万物的根源并不正确。胡宏并且坚持实先于名,名必须符实,③都显示胡宏的思想倾向是从实际的事物开始,而不是从抽象的领域出发。他虽然经常使用形而上学的字眼,但他没有从超越的优越立场谈论问题,他所使用的“体”和“形”概念,也不应该轻易以西方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的本质与形式的观念附会。
胡宏道不离事物的见解与性、心为一体两面的观点相通,他将万物一体与心性的关系演绎得十分清晰:
天地,圣人之父母;圣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则有子矣,有子则有父母矣。此万物之所以着见,道之所以名也。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圣人传心,教天下以仁也。④所以道的本体是性,心是道的作用功能,未发之前为性,已发之后是心;换言之,心是内在之性的体现。
心的作用十分重要,能够认识客观的事物之理,还有主导人性的作用:“气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纯,则性定而气正。”⑤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人心中的迷雾虽然难以去除,但如果能够消除心中的迷雾,那么就不会再有其他的迷雾。他在这里把心当做事物的主宰,然后把重点挪回到人性:“性定,则心宰。心宰,则物随。”①这个说法更能明确反映胡宏以人性为体、人心为用的思想。有一次学生问他经典里为什么强调“传心”,而不是强调“传性”?胡宏的回答又将重点放到心:“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②将心的作用归结于成性,然而他的基本主张是以性为万物的根源与心的本体,两项观点似乎互相抵触。有些学者将胡宏的矛盾解释成主观唯心论,但若不用如此简单的方式化解此矛盾,它或许可以作进一步考查胡宏的心性学说的支点。
胡宏认为心不以生死为转移,所以有超越的本质,也有性所具有的永恒与无边无际的特征:“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③而且“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不能推之尔;莫久于性,患在不能顺之尔。”④人虽然由于一己的私欲干扰,不易察见心的存在,但只要听从孟子的忠告,即可重新获致此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一旦明了自己的放心,就可以保存它、培养它、扩充它,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同矣”⑤。孔子到70岁时已经将此心扩大到极限,因此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也可以说孔子的心与天合一。⑥
唯有仁者可以尽心,而且人首先必须体认仁的本体。胡宏的基本主张是寓学问于读书与格物,但他认为知仁终究是一种直观的体验,在此体验的过程里,人与天的创化合一,因为天地之心蕴育万物,而仁是将人自己与天心、天地的造化合为一体的德行:⑦
诚天命、中天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惟仁者能之。委于命者,失天心。失天心者,兴用废。理其性者,天心存。天心存者,废用兴。达乎是,然后知大君之不可以不仁也。①
心与天所共有的本质是仁,所以人尽其心时,可以与天合而为一。胡宏的观点可以解释成:心所蕴育的仁与天就是心的本体,换句话说,就是性。但胡宏并不使用一般儒家的伦理道德特质描述性的性格,而用全然不同的概念解释性的意义。
性无所不包,连圣贤也对它不可名状,所以它超越一切既有的对立概念,甚至也超越善恶的观念。有人问胡宏性为什么是天地的根本,他回答说:“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②而且他回答学生的问难时解释说,孟子在“告子篇”对性善的论断只是赞美之辞,并不是肯定善与恶是相对的观念。他撇开孟子主张的性与“四端”的说法,强调圣人论述里的生理层面意义(“尽心下”):
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圣人因其性而导之,由于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③
胡宏还认为内在之性就是人内在的好恶,不过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显示,胡宏没有放弃孟子的主张,依然认为遵循人性的自然感情,是通往至善境界的道路。
胡宏认为生理感受内在于人的本性,所以比其他的道学家更能坦率承认男女“交而知有道焉”。④他认为人欲与道德原则都来自人的内在本性,所以他不像程颐那样严格区分人欲与天理的分别,而主张:“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①天理与人欲都以性为体,本质相同,因为没有善恶的分别。天理与人欲的“用”与心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天理与人欲的“用”不同:“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②所以好恶是本性的特征,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好恶不同。
将情与性视为相同的观念会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分别正确与错误的感情与行为?天理与人欲既然不可分别,天理仅指情、欲未发前的状态,亦就是性;情欲已发后,胡宏以是否“中节”衡量情欲的善恶。胡宏从儒者的立场,极力强调是否中节为标准:
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正,挟非而行则为邪。
正者为善,邪者为恶。③简单而言,内在之性的道就是“中”或“中庸”。就“中庸”的观点而论,性无所谓善恶的分别;但是人的行为可以与“中庸”一致而为善。这里似乎有明显的矛盾:“中庸”的性既然无善恶的分别,但是人的行为却可以合乎无善恶分别的“中庸”之性而行善。胡宏的根据是《中庸》的首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胡宏认为情欲未发前的“中”就是性;他显然结合“性”与“中”的观念解释《中庸》。
功夫修养是胡宏最为强调的重点之一,反映他对心性问题的看法。胡氏的家学认为静坐冥思以达到情欲未发前的状态,是一种无谓的精神浪费。他们认为情欲未发前的状态就是性,所以怎么可能以修养获致超越善恶、无所不包的性呢?修养功夫应该从日常生活中体会本心开始,心的活动是修养的关键,因此,功夫修养与最初的立志有绝大的关系:
是故明理居敬,然后诚道得。天理至诚,故无息;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地也。孔子自“志学”至乎“从心所欲不踰矩”,敬道之成也。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终身也。①
“敬”是对如何能变成善人的严肃态度,还有尊敬以及心灵平静的意思。修养功夫本身当然不是最终的目的,经过修养功夫②而改变的自我另有目标:“是故仁智合一,然后君子学成。”③成己然后能够成物。
胡宏认为功夫修养是平息不同见解争执的关键,因为各种不同的观点只是对于道各执一端的理解: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情。诸子百家亿之以意,饰之以辨。传闻袭见,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诸茫昧则已矣。悲夫!此邪说暴行所以盛行,而不为其所惑者鲜矣。然则奈何?曰在修吾身。④
功夫修养能够解决争执的问题,不但因为它培养道德情操,使人接近道,学者也必须向善,才可同心合力共事。胡宏使我们想见11和12世纪,士大夫为改革和战争而起的争论有何等的激烈,他悲观地说,批评别人的真正错误非常困难,而接受确实的批评又更加困难。如果大家能做到这两方面,就能了解友谊的真正意义,若没有这种友谊,就成为互相攻击陷害的小人。⑤这些都显示胡宏渴望儒生的友谊与合作,并且为实现这个愿望献身一生的精神,在偏远的湖南长沙地区任教,创建著名的湖湘学派。
胡宏的学派注重修身实践,而且极力强调性为天地万物的根本。但胡宏也说人性超越儒家一般的善恶区别等标准,而且性就是五官的好恶感觉。性的优越地位有时被心取代,心能够控制性、实现性或完成性。
胡宏从来没有清楚说明:心既然是性的“用”或表现,如何能够对自身的“体”有如此的宰制地位?他将心当做功夫修养的中心与实现性的枢纽,但是又认为心是被动的:“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象。”①胡宏的《知言》里简短不明的观点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它也没有严格分析日后道学体系不可或缺的观念。
然而,胡宏、张九成对道学概念的讨论,鼓励下一代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探讨,例如,第三章会谈到朱熹与同道如何广泛讨论《胡子知言》。秦桧当权期间,政治气氛虽然不友善,张九成与胡宏依然继续讨论佛教的学说,处理儒家的性、心、仁、学与修身等问题,不但保存道学的传统,并且使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政治环境改变后,下一代道学领袖拥有较大的空间和余裕发展宣扬更系统化的论点,也能更自由地加强同道的合作,并且为致力于道学的人士确立传统。
第一时期(1127—1162)女真人在1127年征服中国北方,导致中原文化的断裂,对宋代儒学的发展是一大灾难。南宋的朝廷在陪都临安(今杭州)致力重振朝纲,以巩固南方、抗拒女真金国政权(1115-1234年)的兼并,但南宋政权惨淡经营之余,不得不忍受耻辱,与金人和谈,因为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包括北宋的最后两个皇帝,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女真人公开蔑视汉人的生活方式,要求中原汉人接受女真人的发型和服饰。北宋的沦亡以及中原文化地区的丧失震撼知识分子和朝廷大臣,儒家知识分子为那些没有保持忠贞节操,甚至投靠“蛮夷”的士大夫感到特别的羞耻。①这些变化使人对儒家教育的效果提出质疑,同时也加深他们对儒家行为和价值观的忧虑。
很多儒生学者相信复兴文化和道德观可以使他们获得重建国家、驱逐外敌的力量;胡宏说:“中原无中原之道,然后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复行中原之道,则夷狄归其地矣。”②在此背景下,儒家学者之间展开一系列的辩论,探讨怎样的传统オ是对“道”正确的诠释,以及什么传统能成为儒教社会的价值标准。
南宋成立的头十年中,道学士人还是少数,但是有机会向年轻的高宗皇帝(1127—1162年在位)进言。高宗为求得政治军事的稳定,首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高宗对北宋最后30年控制朝政的改革派怀有敌意,不过,他也意识到即刻改变推行已久的新法并非易事,因此他不进行重大改变,而保留以前新法的政策。不过,高宗依然留恋保守的元祐时代,下令追封加谥司马光、苏轼和程颐等人。从1127年到1137年的十年中,重臣如吕好问(1064-1131年)和赵鼎(1085—1147年)等人对道学很有好感,道学人士在1132年和1135年的科举中名列榜首,甚至传闻说朱震(1072—1138年)要担任1138年的科举主考。朱震由于赵鼎的推荐而得到高宗的重用,担任皇子赞读,以后又升任中书舍人兼诩善;他是程颐的第二代门人,对《易经》颇有研究。①
由于道学迅速发展,朱震在1136年正式上书高宗,提出他对道统传承的看法。朱震所陈述的道学师承有如家族的世袭关系,这种师承关系虽然与佛教禅宗的说法相当类似,但是儒家的师承仍与佛教有不甚相同之处。禅宗大师往往要把象征权威和教化的衣钵交给他选定的继承人,而且这种师承关系历久不断;儒家发展的过程却有上千年的中断,所以师承的过程和内容也不同于佛教。在儒家体系中,每代学生中可以有一人以上接受师门传承,个人也可以自己得道,不需要老师的认可。而且,儒家不能像禅宗那样地“默传”,经典对儒家非常重要。二程虽然在儒学中断千年之后复兴道统,但不表示他们的传承不借助文字,因为经典(我们将在第五章加以讨论)是他们与圣人之心间不可或缺的联系。按照朱震的说法,儒家之道是由孔子经曾子(公元前505—前436年)、子思(公元前492—前431年)到孟子的时期建立起来的,但以后道的传承中断达千年之久,直到北宋程氏兄弟出现为止,所以程子之学是儒学之道的真正传人,而程子的门人又将道传到南方。②这个看法虽然在道学群体之间广泛流行,但以前没有人在朝廷上公开讲过。
朱震发出垄断道统的大胆宣言,立刻引起异议。陈公辅和吕祉(1092—1137年)要求高宗禁止程颐的私学影响朝廷和科举,认为拥戴程氏兄弟的人受到北宋末年结党营私风气的影响而在堕落腐化;不论是程颐的私学,还是王安石的新法,都强迫大家同意他们的观点。陈公辅指出,禁止这种学说是复兴北宋王安石新法以前较自由讨论风气的唯一办法,并且用“狂言”、“怪语”、“淫说”和“鄙喻”形容程颐复兴孟子死后失传的道的说法,对程颐弟子的傲慢举止也大感不快,因为他们: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程〕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①南宋许多道学人士确实极力模仿古人,甚至学习古代的装束和举止作为。刘子健先生收集许多相关的材料,这样描述道学家:他们〔道学人士〕戴尖顶高帽,便装时又着圆帽,宽袍大袖,内衬白细薄纱。他们举止规范严格,直身正坐,度步直视,鞠躬深缓以示敬意,言语威严而少以手势相助。②这些看似矫饰的行为显示,这批力图恢复圣贤之道的儒士有极严格认真的生活方式和礼仪规定,但是这种过度矜持的做法惹恼了世儒和宿儒。
胡安国和尹淳(1071-1142年)挺身为二程之学辩护。胡安国在1137年所上的奏章中,极力排解这些责难,认为它们反映了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对程氏兄弟和司马光的攻击,他并且列举德高望重的学者,如谢良佐(1050-1120年)、杨时都是程氏兄弟的学生,并且刻意突显程颐与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1027-1097年)等元祐保守党人中资深政治家的关系。胡安国提到这些学者,目的是要缓和许多人对道学家行为举止的不满,但他对二程复兴道统的说法没有让步:孔孟之道,不传久矣。自〔程〕颐兄弟始发明之,而复其道可学而至也。不然则或以《六经》、《语》、《孟》之书资口耳。取世资以干利禄,愈不得其门而入矣。今欲使学者蹈中庸、师孔孟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①程子之学是得道入门的途径,二程使宋代士人可以更确切了解先贤圣人的思想。胡安国认为这四个人以“道学德行”而闻名于世,大胆地要求为邵雍、张载和二程加封荣衔,不过高宗对他的建议并未理睬。
高宗认为应该限制这种正在发展的私学,以及它奇特的治学方法,所以态度倒向反道学的一边。他采纳吕祉的建议,发布敕令,张贴在太学中,要求学生研习古籍经典,而不是近世小人的文章。张淳(1096—1164年)虽然大力保荐胡安国出任官职,但他自己要求从征选任官的名单里除名。由于年长道学人士主动求退,赵鼎和张淳又遭罢免,秦桧(1090—1155年)的权力更形坐大。从1138年直到他去世为止,主和的秦桧使高宗的政权稳定下来,朝廷虽然明文规定官吏的铨选以及科举考试不会因考生的背景而有差别待遇,但其实高宗容许秦桧的主和派打压意见不同的人,尤其是排斥主战立场强硬的道学人士。秦桧当政期间与同党把持官吏的选用和科举考试,有时在朝廷上用“专门之学”这个巧妙的称谓贬抑赞成二程的学人官员,②暗示道学对儒学的理解相当狭隘,并且在1144年的科举排挤追随这种“专门之学”的学生。秦桧的专权和打压异己使思想文化窒息,③不过,比起北宋末几十年间压制元祐党人的做法,高宗还没让秦桧及其同党做得那么过分。
气氛即使压抑凝重,有些儒生学者还是致力保存道学的传统,甚至小有程度发展道学传统。年长的学者如杨时、尹淳与胡安国致力传授从程颐那里学习的道学学术。在女真人入侵前后,他们的学术活动为道学在南方打下基础,但是他们在南宋时期只过了8—15年时间,就相继去世。我们的讨论就从高宗时期道学人士的活动谈起,当时道学的根基已经足以支持几个枝干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第一章 南宋第一代学人:张九成与胡宏
程颐等人去世后,道学的幼苗仍然在一些重要地区顽强地发展。这个时期没有一个权威中心的人物,因此与世纪交际程颐领导道学的时期相比,此时的道学更具有多元的特性。12世纪60年代初以后,朱熹批判二程身后的两代门人,认为他们把二程之学引向歧途,尔后的儒家学者大多接受朱熹的看法。我们很难摆脱朱熹的影响,直接理解这些早期道学思想家,但是这些思想家对于我们了解12世纪道学的发展却至关重要。这一章将以两位很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来描述南宋初期道学群体内部的多元性。张九成和胡宏之间犹有分歧,但他们在论史、注疏经典以及传述道学传统时,有些共同关怀的课题,而他们对北宋道学名家的重要概念的评论,也能帮助了解12世纪道学成员所重视的思想要务。
一、张九成
张九成曾在北宋首都开封修习二程之学,主要师事杨时。他返回家乡杭州后,在1132年考中状元,得以进入礼部踏上仕途。张九成的著作中有1/4的篇幅是论史的文章,但是他曾三次婉拒高宗请他讲解《春秋》的要求。他在受命讲解《春秋》伦理内容时,推托说只能讲解《论语》和《孟子》。不过,高宗曾提到,就历史的学习而言,他从张九成那里所学到的知识,比从道学和史学名家胡安国那里所学到的要多。①除了曾抡取状元的荣衔外,他对《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的注解在当时也享有盛誉,不过,目前只有他对《孟子》和《中庸》的大部分注疏保留下来。他在一份上书中讲到:“金人有必亡之势,中国有必兴之理。”②由于如此直言不讳地抨击和金政策,于是触怒了权相秦桧。秦桧以其结党为借口,将他流放在外达14年。因为秦桧翦除异己,张九成认为“有道之士”可以谢绝入仕。③1155年秦桧死后,张九成才复出担任温州知州。
二程对天理、格物和个人修养的看法,在张九成的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张九成不仅继承程颢以理为万物自然之倾向的主张,而且也接受程颐理为天地万物的根源的观点。他与程颢都强调理为天地万物的自然法则,而且理内在于人情,但更重于人情。他说:“理之至处,亦不离人情;但人舍人情求至理,此所以相去甚远。”④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也可以看到这种天理与人情的不同:“圣人以天理为人情,常人往往徇人情而逆天理。”⑤
张九成强调格物穷理为学问的首务。他建议说:
观六经者当先格物之学。格物则能穷天下之理,天下之理穷则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矣。⑥从心中的念头到外在的万事万物都遵守此理的规范,所以人应该开放心胸,关心万事万物,然后回归一理,如此则可与万事万物合而为一,所以,格物致知基本上是一种以修养达到与天地万物合一的努力,而修养功夫必须集中在克除一己私欲,不懈地自律,以及在心性中存养天理。
张九成“心”、“仁”的概念主要来自程颢。他在论及程颢关于“医书以四肢痿癖为不仁”的看法时,把仁当做心的知觉;他解释说:“仁即是觉,觉即是心。因心生觉,因觉有仁。”①所谓“觉”不但意指感官知觉,也指对他人痛苦的感受,所以仁是一种与人合为一体的感觉。张九成用心能够感受他人的痛苦解释仁的意义,出自《孟子·告子上》的讨论。张九成诠释这段文字说:“仁之一理最是圣门亲切学问,唯孟子识得,故曰:‘仁,人心也’。”②仁体如天公正不私,又如道不可名物,张九成如此断言是因为仁就存在人心中,因此,实现仁的唯一方法就在于求仁于人心之中。
张九成认为心是通往仁的途径,也是万物的根源,所谓“心即理,理即心”。有时他对万物本体的论述似乎是一种哲学的唯心论,他说:“夫天下万事皆自心中来。”③张九成的观点还涉及到经典权威的问题,他认为大部分的经典在秦代已付之一炬,所以许多出于人心的道理已经无法在经书里寻得,唯有在后来贤士哲人的著作中才能找到人心中的道理。④
一旦此心悟出心中之理,那么他就会了解“《六经》皆吾心中物也”⑤,因为这些经典只是记载古代圣贤之心所发现的天理。张九成显然没有阐发哲学的唯心论,而是再三强调心在功夫修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所谓的心一直是在修身养性的意义下谈的:“君子之心常厚,小人之心多刻薄。心之所存,治乱、安危、得失、成败所自生也,不可不戒。”⑥
张九成对心中之物的看法多与文化道德修养有关,而他的论述基本属于这个范围层次。他最突出的观点是强调个人修养的实践、历史和经典的学习,而不是周敦颐曾为之冥思苦想的那种“无极而太极”。张九成告诫说:“道非虚无也,日用而已矣。以虚无为道,足以亡国。”①为避免走上这种异端,张九成教训说:“学问于平淡处得味,方可入道。”②也许我们现代人会觉得这些话平淡无奇,但是这种平凡正是宋代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
张九成论及心的超越面向时,不仅认为它与新的哲学观念“天理”的意义相通,并且使用比较古老而不常使用的观念“天心”说明。例如,他至少两次将周文王的心视为“天心”,而心的意义更广泛时,他宣称:“秉此忠诚,上通天心,下通三王之心。”③张九成引用比较古老的“天心”观念,并且强调功夫修养,都反映他比较注重文化价值,介于实际政策与思辨哲学间的学术理论。
张九成维护儒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但不反对佛教。他与临济宗名僧大慧宗杲(1089—1163年)是挚友,他们被秦桧流放到同一地区渡过十年,因此相处甚为亲密。宗杲用佛教的语言解释《中庸》和格物的意义,力图糅合儒、佛、道三教为一家,并劝导张九成兼容三家学说,所以后来许多关于张九成的材料来自佛教的记载。张九成承认佛教有些正确的观点,并且把佛的“空”性哲学解释成去除人欲的道德修养,大慧宗杲无疑影响了张九成的儒学典籍讨论与注释;此外,张九成强调用格物的方法,以达到与万物合一的境界,与宗杲提倡的反省与觉悟,是他们最重要的相似之处。禅学的影响也促使张九成追随程颢提出的学说,将仁与心的知觉相提并论,并且认为心是理的根本。④这些综合的观念是他对道学重要概念发展的贡献。
这里谈到张九成在继承发展二程的理论概念中所扮演的角色,希望能平衡一般认为他是佛教徒的看法。张九成去世不久后,这种看法就开始流传。陈亮在12世纪60年代初曾经说:“家置其书,人习其法”,认为很多士人都受到迷惑,他对儒学的损害远甚于古代的杨朱和墨子。①根据张九成自己的看法,杨墨的异端很难排挤,因为他们同意儒学的某些伦理价值观念:“人多不识异端,所以难去。只如杨、墨,本学仁义,仁义岂是异端?惟孟子能辨之,故能去之也。”②
张九成虽然并不反佛,而且努力寻求儒佛学说的共同点,但仍然认为儒学比佛学优异。张九成批评佛学破坏儒家的基本三纲五常,导致伦理实践的缺失:
故君子谨其独也,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之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止于此而不进。
③从儒家的观点而论,佛学自满于参禅静坐,张九成则认为要达到道德的境界,需要不断修身养性,以建立更完善的自我与社会。他因为佛教的出世倾向而指责佛教执著于空的观念,而且始终自认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与佛教徒并不相同。张九成时代的许多程学门人对禅学颇感兴趣,所以他与佛学的关系密切,其实提高了他当时的声望。
张九成在南宋第一代学者中的声望,以及他很具代表性的儒佛合一论的观点,都在现存最早的道学文选《诸儒鸣道集》里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部文选是一位或数位不知名的张九成弟子在12世纪60年代初期编辑的。①张九成与学生对谈的两卷记录“日新”,占全书最重要的地位,可见该书的编者认为张九成代表当时道学传统的高峰;但这个观点与朱熹的看法不同。
二、胡宏
胡宏是道学另外一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致朋友和学生的信中警告说:“道学衰微,风教大颓,吾徒当以死自担。”②他的学生张栻说,胡宏的文章用心与“道学”一致。③这些材料整体显示胡宏的道学是他与学生、同道追随的一种思想、文化和道德的特殊传统。
胡宏来自经济发达的福建地区,但他选择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湖南地区,在当地任教20年。他年轻时曾经追随杨时,但大体师承父亲胡安国的家学,而这两位老师影响程学的传授甚巨。胡安国在朝廷担任官职,所以胡宏得以承荫受封荣衔,并且有几次出任官职的机会,但都因为反对朝廷的和金政策终身不入仕途。他爱国忧民,多次上书高宗皇帝,要求政府整饬纲常、强化军事以抗击金人。他认为高宗若能爱民,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国家就会强大,得以一雪金人入侵的仇恨,并且恢复中原。④秦桧曾询问胡宏是否愿意入仕,他表示不感兴趣,但谈到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却极表热心,⑤秦桧只好让他主持岳麓书院。秦桧死后,他仍在乡间致力教学,放弃入仕的机会。
胡宏笃信知先于行,一生致力于教授信仰的儒家史学和正统理论。他曾经根据程颐《易传》的要旨,为《易经》写作一卷注解。胡宏也曾编写《皇王大纪》,以80卷的篇幅叙述上古到周末的历史,承续父亲的《春秋》注释中的教化史学;胡寅(1095—1156年)史学的最主要特色也是以经典的褒贬治史。胡氏的家学不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因为司马光的历史著作不足以适切运用儒家经典的道理与教训。道学发展的初期阶段,除胡氏一家人外,道学人士很少是历史学家,不过张九成本人与吕祖谦的几位家人写过历史著作。此外,胡氏一家对佛教有不容调解的敌意,在当时也有些反常。胡氏家人不但严厉拒斥儒佛调和,并且激烈抨击佛学,认为佛学将儒家的“心”等概念引入歧途。①胡宏殷切期望击退禅宗诱人的影响,并以经典与历史研究恢复古代的理想制度,这种心情促使他兼重儒学形而上学与社会政治制度层次的问题,与张九成专注两者间的文化价值层次的论题不同。
胡宏哲学思想的中心是以人性为天地的本体。《中庸》开宗明义地说:“天命之谓性”,胡宏解释道:“性,天下之大本也。”②他又赞扬人的内在本性:
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③
胡宏这里所谓的性无所不包,理则是万物各别涵具的理,理的层次比性低,而且比较偏颇。性无所不包,气自然也不能例外:“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①
内在的本性既然无所不包,圣人也对它不可名状,所以性有如“不可名”的道。性是理与气的基础,道也不能与实在的事物分离:“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闲之?故离物求道者,妄而已矣。”②他还解释说,道家和一些儒生所谓“无”,只是道可见以前的状态;有形的事物可见,但道的“无”,其实只是人不能看见“道”而已;万物之理并不是“无”,老子等人把“无”当做万物的根源并不正确。胡宏并且坚持实先于名,名必须符实,③都显示胡宏的思想倾向是从实际的事物开始,而不是从抽象的领域出发。他虽然经常使用形而上学的字眼,但他没有从超越的优越立场谈论问题,他所使用的“体”和“形”概念,也不应该轻易以西方的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的本质与形式的观念附会。
胡宏道不离事物的见解与性、心为一体两面的观点相通,他将万物一体与心性的关系演绎得十分清晰:
天地,圣人之父母;圣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则有子矣,有子则有父母矣。此万物之所以着见,道之所以名也。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圣人传心,教天下以仁也。④所以道的本体是性,心是道的作用功能,未发之前为性,已发之后是心;换言之,心是内在之性的体现。
心的作用十分重要,能够认识客观的事物之理,还有主导人性的作用:“气主乎性,性主乎心。心纯,则性定而气正。”⑤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他又说:人心中的迷雾虽然难以去除,但如果能够消除心中的迷雾,那么就不会再有其他的迷雾。他在这里把心当做事物的主宰,然后把重点挪回到人性:“性定,则心宰。心宰,则物随。”①这个说法更能明确反映胡宏以人性为体、人心为用的思想。有一次学生问他经典里为什么强调“传心”,而不是强调“传性”?胡宏的回答又将重点放到心:“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②将心的作用归结于成性,然而他的基本主张是以性为万物的根源与心的本体,两项观点似乎互相抵触。有些学者将胡宏的矛盾解释成主观唯心论,但若不用如此简单的方式化解此矛盾,它或许可以作进一步考查胡宏的心性学说的支点。
胡宏认为心不以生死为转移,所以有超越的本质,也有性所具有的永恒与无边无际的特征:“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为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③而且“天下莫大于心,患在不能推之尔;莫久于性,患在不能顺之尔。”④人虽然由于一己的私欲干扰,不易察见心的存在,但只要听从孟子的忠告,即可重新获致此心:“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一旦明了自己的放心,就可以保存它、培养它、扩充它,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同矣”⑤。孔子到70岁时已经将此心扩大到极限,因此可以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也可以说孔子的心与天合一。⑥
唯有仁者可以尽心,而且人首先必须体认仁的本体。胡宏的基本主张是寓学问于读书与格物,但他认为知仁终究是一种直观的体验,在此体验的过程里,人与天的创化合一,因为天地之心蕴育万物,而仁是将人自己与天心、天地的造化合为一体的德行:⑦
诚天命、中天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惟仁者能之。委于命者,失天心。失天心者,兴用废。理其性者,天心存。天心存者,废用兴。达乎是,然后知大君之不可以不仁也。①
心与天所共有的本质是仁,所以人尽其心时,可以与天合而为一。胡宏的观点可以解释成:心所蕴育的仁与天就是心的本体,换句话说,就是性。但胡宏并不使用一般儒家的伦理道德特质描述性的性格,而用全然不同的概念解释性的意义。
性无所不包,连圣贤也对它不可名状,所以它超越一切既有的对立概念,甚至也超越善恶的观念。有人问胡宏性为什么是天地的根本,他回答说:“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②而且他回答学生的问难时解释说,孟子在“告子篇”对性善的论断只是赞美之辞,并不是肯定善与恶是相对的观念。他撇开孟子主张的性与“四端”的说法,强调圣人论述里的生理层面意义(“尽心下”):
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圣人因其性而导之,由于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③
胡宏还认为内在之性就是人内在的好恶,不过这段话的后半部分显示,胡宏没有放弃孟子的主张,依然认为遵循人性的自然感情,是通往至善境界的道路。
胡宏认为生理感受内在于人的本性,所以比其他的道学家更能坦率承认男女“交而知有道焉”。④他认为人欲与道德原则都来自人的内在本性,所以他不像程颐那样严格区分人欲与天理的分别,而主张:“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①天理与人欲都以性为体,本质相同,因为没有善恶的分别。天理与人欲的“用”与心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天理与人欲的“用”不同:“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②所以好恶是本性的特征,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只是他们的好恶不同。
将情与性视为相同的观念会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分别正确与错误的感情与行为?天理与人欲既然不可分别,天理仅指情、欲未发前的状态,亦就是性;情欲已发后,胡宏以是否“中节”衡量情欲的善恶。胡宏从儒者的立场,极力强调是否中节为标准:
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正,挟非而行则为邪。
正者为善,邪者为恶。③简单而言,内在之性的道就是“中”或“中庸”。就“中庸”的观点而论,性无所谓善恶的分别;但是人的行为可以与“中庸”一致而为善。这里似乎有明显的矛盾:“中庸”的性既然无善恶的分别,但是人的行为却可以合乎无善恶分别的“中庸”之性而行善。胡宏的根据是《中庸》的首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胡宏认为情欲未发前的“中”就是性;他显然结合“性”与“中”的观念解释《中庸》。
功夫修养是胡宏最为强调的重点之一,反映他对心性问题的看法。胡氏的家学认为静坐冥思以达到情欲未发前的状态,是一种无谓的精神浪费。他们认为情欲未发前的状态就是性,所以怎么可能以修养获致超越善恶、无所不包的性呢?修养功夫应该从日常生活中体会本心开始,心的活动是修养的关键,因此,功夫修养与最初的立志有绝大的关系:
是故明理居敬,然后诚道得。天理至诚,故无息;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地也。孔子自“志学”至乎“从心所欲不踰矩”,敬道之成也。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终身也。①
“敬”是对如何能变成善人的严肃态度,还有尊敬以及心灵平静的意思。修养功夫本身当然不是最终的目的,经过修养功夫②而改变的自我另有目标:“是故仁智合一,然后君子学成。”③成己然后能够成物。
胡宏认为功夫修养是平息不同见解争执的关键,因为各种不同的观点只是对于道各执一端的理解:
道充乎身、塞乎天地,而拘于躯者不见其大。存乎饮食男女之事,而溺于流者不知其情。诸子百家亿之以意,饰之以辨。传闻袭见,蒙心之言。命之理、性之道置诸茫昧则已矣。悲夫!此邪说暴行所以盛行,而不为其所惑者鲜矣。然则奈何?曰在修吾身。④
功夫修养能够解决争执的问题,不但因为它培养道德情操,使人接近道,学者也必须向善,才可同心合力共事。胡宏使我们想见11和12世纪,士大夫为改革和战争而起的争论有何等的激烈,他悲观地说,批评别人的真正错误非常困难,而接受确实的批评又更加困难。如果大家能做到这两方面,就能了解友谊的真正意义,若没有这种友谊,就成为互相攻击陷害的小人。⑤这些都显示胡宏渴望儒生的友谊与合作,并且为实现这个愿望献身一生的精神,在偏远的湖南长沙地区任教,创建著名的湖湘学派。
胡宏的学派注重修身实践,而且极力强调性为天地万物的根本。但胡宏也说人性超越儒家一般的善恶区别等标准,而且性就是五官的好恶感觉。性的优越地位有时被心取代,心能够控制性、实现性或完成性。
胡宏从来没有清楚说明:心既然是性的“用”或表现,如何能够对自身的“体”有如此的宰制地位?他将心当做功夫修养的中心与实现性的枢纽,但是又认为心是被动的:“人心应万物,如水照万象。”①胡宏的《知言》里简短不明的观点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它也没有严格分析日后道学体系不可或缺的观念。
然而,胡宏、张九成对道学概念的讨论,鼓励下一代的学者进一步研究探讨,例如,第三章会谈到朱熹与同道如何广泛讨论《胡子知言》。秦桧当权期间,政治气氛虽然不友善,张九成与胡宏依然继续讨论佛教的学说,处理儒家的性、心、仁、学与修身等问题,不但保存道学的传统,并且使它的内容更加丰富,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政治环境改变后,下一代道学领袖拥有较大的空间和余裕发展宣扬更系统化的论点,也能更自由地加强同道的合作,并且为致力于道学的人士确立传统。
附注
①Hans van Ess, Van Ch 'eng I zu Chu Hsi: die Lehre vom rechten Weg in der Uberlieferung der Familie Hu (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3);与其“The Compilation of the Works of the Ch'eng Brothers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the Learning of the Right Way of the Southern Sung Period. n T'oung Pao 90.4—5 (2004) :264—298.
②Christian Soffel,Ein Universalgelehrter verarbeitet das Ende seiner Dynastic - Eine Analyse des Kunxue jiwen von Wang Yinglin(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2004).
③Kai Marchal, Die Ordnung des Politischen und die Ordnung des Herzens - Eine Studie zum politisch-philosophischen Denken des Lil Zuqian (1137—1181) in: Digitale Hochschulschriften ,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at Miinchen( University of Munich) July 2006.
④徐洪兴:《道学思潮》收入尹继佐、周山编:《中国学术思潮史》第五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6年)。
⑤小岛毅:《宋学の形成と展开》(东京:创文社,1999年)。
①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北京:三联书局,2004年)。
②HildedeWeerdt,"TheCompositionofExaminationStandards:DaoxueandSouthernSongDynastyExaminationCulture,”Ph.D.thesis,HarvardUniversity,1998;与其CompetitionOverContent:NegotiatingStandardsfortheCivilServiceExaminationsinImperialChina,1127—1279(Cambridge,MA:HarvardEastAsianMonographSerie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7).
① Hoyt Cleveland Tillman,“Zhu Xi’s Prayers to the Spirit of Confucius and Claim to the Transmission of the Way,”Philosophy Eastand West 54.4(October 2004):489—513.
②田浩:“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中国学术》2002年,第10辑,页167—192。
①冯友兰:“略论道学的特点、名称和形式”,收入中国哲学史学会编,《论宋明理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37—56。
②姜广辉:“宋代道学定名缘起”,《中国哲学》(1992年),第15辑,页240—246。
③关于此讨论及其哲学的意义,参见拙作“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Approaches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üeh,”Philosophy EastandWest,43.3(July 1992),pp.455—474;及“TheUsesofNeo-ConfucianismRevisited,”Ibid.,44.1(January 1994),pp.135—142.参中文本:“儒学研究一个新指向”,收入田浩编:《宋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77—97。
①李心传:《道命录》(百部丛书集成本)。又参见来可泓:《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王德毅:“李心传年谱”,收入《宋史研究集》第9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7年),页513—573。
①孙应时:《烛湖集》(四库全书本),卷6,页4下—5上。孙应时(1154—1206年)在浙江听到学人使用“道学”讽刺人,不过这个时候比“道学”一词初次出现已经晚了100年。周密(1232—1308年)在《癸辛杂识》(百部丛书集成本),册中,页4下—5下,也批评过13世纪末期的道学;参见石田肇:“周密道学”,《东洋史研究》,第49卷第2号(1990年9月),页25—47。
②例如,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48,页1252—1253。
①见JohnChaffee(贾志扬),TheThronyGatesofLearninginSungChina:ASocialHistoryofExaminat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5),p.104,这本书也被翻成中文:《宋代科举研究》(台北:三民书局,1995年);ThomasLee(李弘祺),GovernmentEduca-tionandExaminationinSungChina,(HongKong: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Press,1985),p.221.
②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东京:同朋社,1982年),页262—285。
①李心传:《道命录》,卷1,页1上—2上。
①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册1,页95(《遗书》卷六);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册1,页17。
②《二程集》,册2,页639;程颐的解说见册2,页638。
③《二程集》,册2,页643(《文集》卷11),“祭李端伯文”;程颐“祭刘质夫文”排在“祭李端伯文”前面,册2,页643。
④杨时:《杨龟山先生文集》(百部丛书集成本),卷2,页3下;卷2,页5上;卷2,页27上—28下;卷3,页2上;卷3,页12上;卷3,页25下;卷3,页29下;卷3,页31下;卷4,页14上。程颐在“明道先生行状”中论及道时,强调经典,而不是个人与天地或圣人之心的联系;参见《二程集》,册2,页638—639。
①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26,页305,“祭吕祖谦文”。
①刘子健先生的看法可以参见JamesT.C.Liu,ReforminSungChina:WangAn-shih(1021—1086)andHisNewPolicies,(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9).刘先生在ChinaTurningInward:Intellectual-PoliticalChangesintheEarlyTwelfthCentury,(Cambridge,Mass.: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HarvardUniversity,1988)一书中,有更详细的论述。在我们平时的讨论中,刘先生将这观点讲得更为明确。
①Wm.Theodore de Bary(狄培瑞),Neo-Confucian Orthodoxyand the Learning ofthe Mind-and-HHear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James Liu(刘子健):ChinaTurn-ingInward.
②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部备要本),卷72,页25上。
③朱熹:《朱子语类》,黎靖德编(台北:正中书局景印明成化九年江西藩司覆刊宋咸淳六年导江黎氏本,1962年),卷6,页159;我另外使用新校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6,页99。
① 参见James Liu(刘子健),China Turning Inward ,chapter4.关于南宋初年对金的战争,参见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上海:知识出版社,1988年),页35-52;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②胡宏:《胡子知言》(百部丛书集成本),卷6,页1上;及其《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页44。
①脱脱主编:《宋史》(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435,页12907。JamesLiu(刘子健),ChinaTurningInward,chapters4,5,6.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37,页1251—1261。
②李心传:《道命录》,卷3,页3上—5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国学基本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再版,1956年),卷101,页1660—1661。
①《道命录》,卷3,页5上一7上,特别是第6页。陈邦瞻、冯琦:《宋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卷80,页867。
②James Liu(刘子健),“How did a Neo-Confucian School Become the State Orthodoxy?” Philosophy East & West ,23.4 (October 1973),p. 497.
①《道命录》,卷3,页12下—13上。
②《道命录》,卷4,页3上—11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页2431—2432;卷
153,页2469;卷165,页2704;卷168,页2750;卷l73,页2847。
③黄宽重:“秦桧与文字狱”,收入其《南史丛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页41—72。刘子健:“秦桧的亲友”,《食货月刊复刊》,第14卷第7、8期(1984年),页34—47。又参见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时代”,收入《宋史研究集》(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第10辑,页245—302;TaoJingshen(陶晋生),“ThePersonalityofSungKao-tsung(r.1127—1162),”收入衣川强编:《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东京:同朋舍,1989年),页531—543。
①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1,页1960。我的统计资料主要根据张九成的《横浦文集》(1614年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再印,1925年)。经典与历史方面的材料,参见邓克铭:《张九成思想之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1990年),页47—55,60—63,143—146。
②《宋史》,卷374,页11577;张九成:《横浦文集》,卷12,页2上——9下。
③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8,页1754;《宋元学案》,卷40,页1315。
④《宋元学案》,卷40,页1309。关于张九成与程学的关系见邓克铭:《张九成思想之研究》,页119—131。
⑤张九成:《横浦心传》(附于《横浦文集》).上卷,页20下。
⑥张九成:《孟子传》(四库全书本),卷28,页5上。
①张九成:《横浦心传》,上卷,页31上。又见张九成:《孟子传》,卷14,页9上。
②张九成:《横浦心传》,上卷,页31上。又见张九成:《横浦文集》,卷5,页4上—9上。
③张九成:《孟子传》,卷27,页20下。
④《宋元学案》,卷40,页1305。
⑤张九成:《横浦文集》,卷18,页7上。
⑥《宋元学案》,卷40,页1310。
①《宋元学案》,卷40,页1312。
②《宋元学案》,卷40,页1303。
③张九成:《横浦文集》,卷9,页6上;卷8,页11上—12上。
④《宋元学案》,卷40,页1307。又见邓克铭:《张九成思想之研究》,页16—28。
①陈亮:《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新校标点本,1974年),卷9,页260;另用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卷27,页319。
②《宋元学案》,卷40,页1304—1305。
③张九成:《横浦文集》,卷5,页1上下;卷5,页8上;《横浦心传》,上卷,页16下—17上,40上下。
①张九成学生辑:《诸儒鸣道集》(约在12世纪60年代成书,1236年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陈来:“略论《诸儒鸣道集》”,《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1986年),页30—38。陈先生考订该文时间应不早于1159年,很可能早于1168年,但不晚于1179年。关于张九成在当时的声望以及对南宋的影响,见邓克铭:《张九成思想之研究》,页149—158。
②胡宏:《五峰集》(四库全书本),卷2,页86上;《胡宏集》,页147。又可见《五峰集》,卷2,页67上下;卷2,页84下;《胡宏集》,页133,146。
③张栻:《南轩集》(绵邑洗墨池刊本;台北:广学社重印,1975年),卷14,页7上。
④胡宏:《五峰集》,卷2,页4下—6上,17上下,25上—28下;《胡宏集》,页84—85,94,99—102。关于有关制度,见《五峰集》,卷2,页64下—65上;卷2,页75上下;卷3,页70下—71上;卷4,页53上—55上;胡宏:《胡子知言》,卷5,页13上;卷6,页3上—5上;《胡宏集》,页43,45—47,131,139—140,211,265—266。
⑤胡宏:《五峰集》,卷2,页32上—33上;《胡宏集》,页104—105。
①胡宏:《胡子知言》,卷1,页2上,3下,5上,10—11上;卷2,页1上,4上下;卷3,页6上;卷4,页10下;卷5,页10上。《五峰集》,卷2,页51下—55上。《胡宏集》,页2,3,4,9,10,13,22,34,41,120—123。
②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3,页40下,“胡子知言疑义”。
③胡宏:《胡子知言》,卷4,页2下;《胡宏集》,页28。
①《胡子知言》,卷3,页6上;《胡宏集》,页22;又见《胡子知言》,卷4,页1上—3下;《胡宏集》,页27—28。
②《胡子知言》,卷1,页4下;《胡宏集》,页4。
③邱汉生、侯外庐、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上册,页300—
302。
④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3,页47上,“胡子知言疑义”。
⑤胡宏:《胡子知言》,卷2,页7下;《胡宏集》,页16。
①《胡子知言》,卷4,页5上;《胡宏集》,页30。
②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3,页40下,“胡子知言疑义”。
③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3,页43上,“胡子知言疑义”。
④胡宏:《胡子知言》,卷3,页10上下;《胡宏集》,页25。
⑤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3,页45下,“胡子知言疑义”。又见页43上。
⑥胡宏:《胡子知言》,卷2,页1上;《胡宏集》,页10。又见《论语·为政》。
⑦《胡子知言》,卷1,页4上,7下;《五峰集》,卷3,页55下—56上;《胡宏集》,页4,6,196—197。又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正中书局,1968—1969年),册2,页484—501。
①胡宏:《胡子知言》,卷5,页9下。又见《五峰集》,卷2,页2上;卷2,页4下;卷4,页17上下23上下;《胡宏集》,页41,83,85,234,239。
②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3,页44上,“胡子知言疑义”。
③胡宏:《胡子知言》,卷1,页11上下;《胡宏集》,页9。
④胡宏:《胡子知言》,卷1,页8下;《胡宏集》,页7。又见《论语·八佾》。
①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3,页41下,“胡子知言疑义”。
②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3,页42下,“胡子知言疑义”。
③朱熹:《朱文公文集》,卷73,页44下—45上,“胡子知言疑义”。
①请见允晨本,p.66—67。
②胡宏:《胡子知言》,卷4,页3上下;《胡宏集》,页28。
③胡宏:《胡子知言》,卷1,页1上下;《胡宏集》,页1。
④胡宏:《胡子知言》,卷1,页3上下;《胡宏集》,页3。
⑤胡宏:《胡子知言》,卷3,页7上下;《胡宏集》,页23。
①胡宏:《胡子知言》,卷4,页10下;《胡宏集》,页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