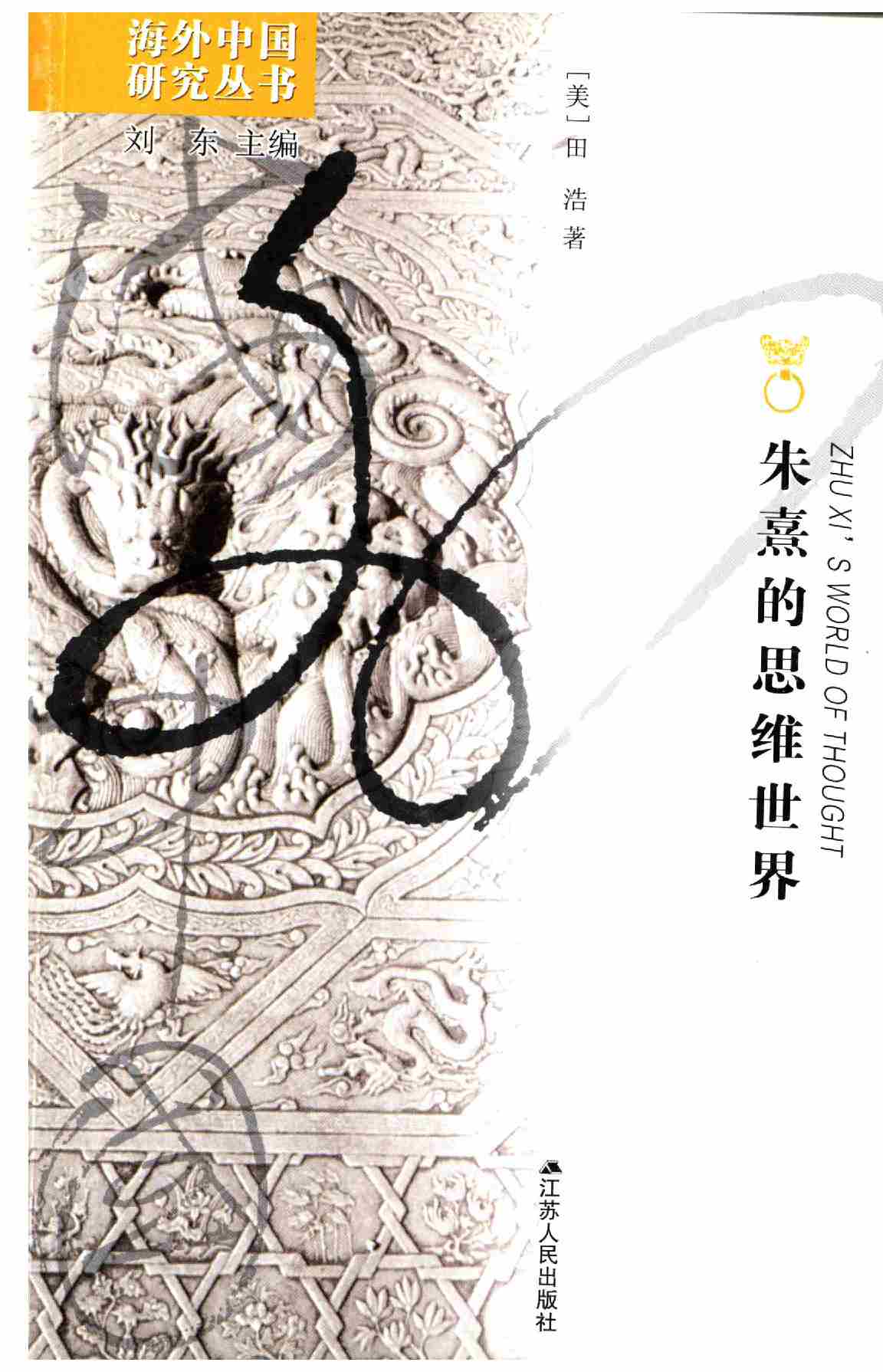内容
尽管在增订版中增加了新的内容(主要基于作者两篇学术期刊论文),本书的主旨仍然围绕两个主题展开:
第一,当将朱熹放置于同时代的儒家思想家的大框架中,我们对于朱熹及其思想是否能有新的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程朱理学有着过度的关注。如果将这种过于集中的视角转移一下,我们是否能更进一步地欣赏那些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这不仅是对他们自身思想的欣赏,更是对他们在朱熹就各种问题及政策提出的思想主张的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欣赏。
第二,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具有共同关注的一群儒家学者所组成的道学“团体”,是如何发展演变成自成一家的思想学派,乃至南宋末期正式成为政治思想上的正统学说的。尽管大多数近代学者将程朱理学的胜利归功于朱熹的门徒学生,那么其他儒家学者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更重要的是,在朱熹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自己的言行是怎样影响着道学团体的狭化的。比如说,朱熹对于经典的评价是否将自己推向一个解读经典的权威和道学传统的界定者的位置?
对于90年代出版的我的英文原版和扩充的中文版,几位学界同仁质疑我是否过分强调了朱熹成为道学领袖的企图。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界领袖倡导自己的学术主张,排斥异家学说,是很正常的,因此,朱熹在这一点上,与其他领袖并无显著不同。为阐述这一问题,我专门新增了“朱熹的祈祷文与道统观”一章,以证明朱熹超乎常理的言行与主张。比如说,在他献给孔子的祈祷文中,朱熹将自身作为其门徒和孔子灵魂的中介。在祠堂举行的祭祀先贤的仪式中,他让其门徒宣称在从古圣先贤到朱熹本人的道统传承过程中没有任何缺失;而且还让门徒们宣誓一定要原封不动地将自己的理论再传承下去。此章填补了1996年版《朱熹的思维世界》以及朱子学研究的一处空隙。
原版书中的另一个弱点就是结论过于集中于四个关键问题的讨论。这样一来,一些读者也许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忽略了书中原本设定的大框架中的其他重点议题。增订版在结论一章中新增了两个小节。第一个小节对于原书所设定的大框架中的重点议题进行了总结。新增的第三小节则用一个具体的范例阐释了通过对宋代儒家思想进行更为广阔的考查,我们能增强对当代有关儒家思想道德如何影响了东亚20世纪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解。我希望这一增补的总结,可以将我论文中关于我们对宋代儒家和一些当代问题的理解阐释清楚。
也许是在回应我在80和90年代的一系列著述,许多学者更多地采用“道学”作为一重要学术类别来讨论宋代儒家流派的发展演变。同时,他们普遍意识到“道学”在宋代发展成一个由朱熹及其主要门徒主导的排斥异说、唯我独尊思想学派的缓慢演变过程。在我获得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Prize(德国洪堡基金奖)的期间和之后,我有幸和Hans van Ess(叶翰)教授和他以前在慕尼黑大学的一些学生,以及很多其他德国学者,探讨了这一发展过程。实际上,叶翰教授①,Christian Soffel②(苏费翔)博士,Kai Marchal③(马恺之)博士的研究著述在深度和广度上增强了我对“道学”及其局限性的理解。2003年至2004年,我获得了 William Fulbright Foundation (富布莱特基金会)以及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科研资助,前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进行了16个月的研究。期间,我有幸和中心的同仁们,还有很多在别的单位的朋友们,包括陈来、姜广辉、梁涛、朱杰人、朱汉民等先生探讨了道学的有关问题。与台湾学者黄进兴、张寿安和夏长朴各位先生的讨论也使我受益匪浅。我很高兴地发现中国学者开始引用我对于道学发展历史的著述和观点;中国学者徐洪兴是其中一例。④日本东京大学的小岛毅先生及其宋代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特别值得一提。⑤尽管我们做的领域与方向不同,Benjamin Elman (爱 尔曼)教授和我对于“Neo-Confucianism”(新儒学)这个学术术语的看法却很相近,都认为这个术语的使用歪曲了儒家思想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发展进程。还有很多学术同仁和朋友的研究和讨论,丰富了我对宋代历史和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但在此我想特别感谢那些和 我同样致力于道学研究的学者们。
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当代的许多学者继续将广义的"新儒学”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意义等同于、但范围要广于传统"理学”的术语。但就像余英时老师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指出的那样,"道学”是宋代常用的术语,指的是一批人试图用政治影响来改良社会和政府;而"理学”则是宋代一个不太常用的范畴,而且它则更侧重于抽象和形而上的哲学概念。①然而,经过最近几个世纪的演变,"理学”逐步成为更常用的术语,并不但被用来指称狭义的程朱学派,而且被用来指称唐代(尤其是韩愈)以来所有的儒家思想学说,因此"理学”的范围很不清楚。一些学者(特别在美国)现在将"理学”、"道学”和"新儒学”作为同义词替换使用。我对这种宽泛的使用表示遗憾,因为它不仅混淆了不同的学派的区别,而且忽视了儒家思想在宋代及宋之后的发展变化过程。HildedeWeerdt(魏希德)博士最近将"道学”看成是朱熹在12世纪晚期将二程学说重新打造成的一个思想学派。而且她认为我所指的"道学”是所谓的"ecumenical”(各学派的大一统)。②她好像将我所提的"道学”观点过于简化了。另外,她看起来似乎太过囿于《宋史·道学传》中过分狭隘的"道学”理念。值得一提的是,魏希德教授引用了我于1992年发表在《东方与西方哲学》(PhilosophyEastandWest)的文章和199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而没有引用我后来发表的文章和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我希望这次带有更多补充章节和扩充结论的中文增订版可以将我的论据和观点表述清楚。
并入增订版中的两篇文章最初来源于两个国际著名的学术杂志。"朱熹的祈祷文与道统观”一章修改自我在2004年发表于《东方与西方哲学》杂志上的文章。①结论中新增补的两个章节修改自我在2002年发表于《中国学术》的文章。②对于两位杂志的主编,RogerAmes(安乐哲)先生和刘东先生同意我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修改并使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而且我也十分感激他们多年以来对我研究和出版工作的鼓励和帮助。还需提及的是,北大哲学系博士生高海坡翻译了我在《东方与西方哲学》杂志上的文章手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博士生姜长苏则翻译了我在《中国学术》杂志上的手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刘倩同仁和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张志惠与童永昌帮我进行了增订版二校的审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博士生阎琨帮助我翻译了这篇谢辞。
由于翻译撰写本书的原来中文稿,我那时候有机会扩充及修订英文原著对南宋道学的认识;那次重新阅读南宋思想的史料,使我能够提供一项比英文旧著更详尽、更精谨的论述,并且进一步发挥、澄清原来的论证。那时在亚利桑纳州立大学读书的牛朴、冀小斌先生为我翻译最初的草稿;黄进兴、池胜昌、黄明理、俞宗宪、程一凡及刘景修先生提供许多修改草稿的宝贵意见。池胜昌先生从新泽西(NewJersey)来到亚利桑纳,前后辛勤工作40余日,对草稿做最后的重新修订,不但润饰中文的写作风格,并使译文能够更忠实于我的本意。
我很感谢台湾大学教授夏长朴先生,特别为增订版写序。他在儒家哲学上的造诣和有关北宋的专著为本书对于南宋的探讨奠定了基石。我的原书已经绝版几年了,在此对于黄进兴先生推荐此书的再版和杨家兴先生细心的编辑修订工作表示感谢。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也已经绝版,在此对于刘东先生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增订本也表示感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余英时先生。他为原版中文书特别写序,并于此次再与新序。他的为人师表、学术建树始终是我努力的源泉。我谨将此增订版献给余英时老师,祝贺他获得克鲁格(Kluge)大奖。
我也必须感谢妻子宓联卿女士,以及子女田亮、田梅,他们在我觉得写作此书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时,仍然使我感到生活充满乐趣,并且使我的思想能够保持平衡,不致一去不返,迷失在遥远的南宋时代。
田浩
2008年1月20日写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第一,当将朱熹放置于同时代的儒家思想家的大框架中,我们对于朱熹及其思想是否能有新的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于程朱理学有着过度的关注。如果将这种过于集中的视角转移一下,我们是否能更进一步地欣赏那些与朱熹同时代的思想家?这不仅是对他们自身思想的欣赏,更是对他们在朱熹就各种问题及政策提出的思想主张的发展中所起作用的欣赏。
第二,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具有共同关注的一群儒家学者所组成的道学“团体”,是如何发展演变成自成一家的思想学派,乃至南宋末期正式成为政治思想上的正统学说的。尽管大多数近代学者将程朱理学的胜利归功于朱熹的门徒学生,那么其他儒家学者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更重要的是,在朱熹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他自己的言行是怎样影响着道学团体的狭化的。比如说,朱熹对于经典的评价是否将自己推向一个解读经典的权威和道学传统的界定者的位置?
对于90年代出版的我的英文原版和扩充的中文版,几位学界同仁质疑我是否过分强调了朱熹成为道学领袖的企图。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学界领袖倡导自己的学术主张,排斥异家学说,是很正常的,因此,朱熹在这一点上,与其他领袖并无显著不同。为阐述这一问题,我专门新增了“朱熹的祈祷文与道统观”一章,以证明朱熹超乎常理的言行与主张。比如说,在他献给孔子的祈祷文中,朱熹将自身作为其门徒和孔子灵魂的中介。在祠堂举行的祭祀先贤的仪式中,他让其门徒宣称在从古圣先贤到朱熹本人的道统传承过程中没有任何缺失;而且还让门徒们宣誓一定要原封不动地将自己的理论再传承下去。此章填补了1996年版《朱熹的思维世界》以及朱子学研究的一处空隙。
原版书中的另一个弱点就是结论过于集中于四个关键问题的讨论。这样一来,一些读者也许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忽略了书中原本设定的大框架中的其他重点议题。增订版在结论一章中新增了两个小节。第一个小节对于原书所设定的大框架中的重点议题进行了总结。新增的第三小节则用一个具体的范例阐释了通过对宋代儒家思想进行更为广阔的考查,我们能增强对当代有关儒家思想道德如何影响了东亚20世纪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解。我希望这一增补的总结,可以将我论文中关于我们对宋代儒家和一些当代问题的理解阐释清楚。
也许是在回应我在80和90年代的一系列著述,许多学者更多地采用“道学”作为一重要学术类别来讨论宋代儒家流派的发展演变。同时,他们普遍意识到“道学”在宋代发展成一个由朱熹及其主要门徒主导的排斥异说、唯我独尊思想学派的缓慢演变过程。在我获得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 Prize(德国洪堡基金奖)的期间和之后,我有幸和Hans van Ess(叶翰)教授和他以前在慕尼黑大学的一些学生,以及很多其他德国学者,探讨了这一发展过程。实际上,叶翰教授①,Christian Soffel②(苏费翔)博士,Kai Marchal③(马恺之)博士的研究著述在深度和广度上增强了我对“道学”及其局限性的理解。2003年至2004年,我获得了 William Fulbright Foundation (富布莱特基金会)以及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的科研资助,前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进行了16个月的研究。期间,我有幸和中心的同仁们,还有很多在别的单位的朋友们,包括陈来、姜广辉、梁涛、朱杰人、朱汉民等先生探讨了道学的有关问题。与台湾学者黄进兴、张寿安和夏长朴各位先生的讨论也使我受益匪浅。我很高兴地发现中国学者开始引用我对于道学发展历史的著述和观点;中国学者徐洪兴是其中一例。④日本东京大学的小岛毅先生及其宋代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也特别值得一提。⑤尽管我们做的领域与方向不同,Benjamin Elman (爱 尔曼)教授和我对于“Neo-Confucianism”(新儒学)这个学术术语的看法却很相近,都认为这个术语的使用歪曲了儒家思想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发展进程。还有很多学术同仁和朋友的研究和讨论,丰富了我对宋代历史和儒家思想的理解和认识,但在此我想特别感谢那些和 我同样致力于道学研究的学者们。
尽管如此,我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当代的许多学者继续将广义的"新儒学”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意义等同于、但范围要广于传统"理学”的术语。但就像余英时老师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指出的那样,"道学”是宋代常用的术语,指的是一批人试图用政治影响来改良社会和政府;而"理学”则是宋代一个不太常用的范畴,而且它则更侧重于抽象和形而上的哲学概念。①然而,经过最近几个世纪的演变,"理学”逐步成为更常用的术语,并不但被用来指称狭义的程朱学派,而且被用来指称唐代(尤其是韩愈)以来所有的儒家思想学说,因此"理学”的范围很不清楚。一些学者(特别在美国)现在将"理学”、"道学”和"新儒学”作为同义词替换使用。我对这种宽泛的使用表示遗憾,因为它不仅混淆了不同的学派的区别,而且忽视了儒家思想在宋代及宋之后的发展变化过程。HildedeWeerdt(魏希德)博士最近将"道学”看成是朱熹在12世纪晚期将二程学说重新打造成的一个思想学派。而且她认为我所指的"道学”是所谓的"ecumenical”(各学派的大一统)。②她好像将我所提的"道学”观点过于简化了。另外,她看起来似乎太过囿于《宋史·道学传》中过分狭隘的"道学”理念。值得一提的是,魏希德教授引用了我于1992年发表在《东方与西方哲学》(PhilosophyEastandWest)的文章和199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而没有引用我后来发表的文章和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我希望这次带有更多补充章节和扩充结论的中文增订版可以将我的论据和观点表述清楚。
并入增订版中的两篇文章最初来源于两个国际著名的学术杂志。"朱熹的祈祷文与道统观”一章修改自我在2004年发表于《东方与西方哲学》杂志上的文章。①结论中新增补的两个章节修改自我在2002年发表于《中国学术》的文章。②对于两位杂志的主编,RogerAmes(安乐哲)先生和刘东先生同意我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修改并使用,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而且我也十分感激他们多年以来对我研究和出版工作的鼓励和帮助。还需提及的是,北大哲学系博士生高海坡翻译了我在《东方与西方哲学》杂志上的文章手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博士生姜长苏则翻译了我在《中国学术》杂志上的手稿。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图书馆的刘倩同仁和台湾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张志惠与童永昌帮我进行了增订版二校的审定。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博士生阎琨帮助我翻译了这篇谢辞。
由于翻译撰写本书的原来中文稿,我那时候有机会扩充及修订英文原著对南宋道学的认识;那次重新阅读南宋思想的史料,使我能够提供一项比英文旧著更详尽、更精谨的论述,并且进一步发挥、澄清原来的论证。那时在亚利桑纳州立大学读书的牛朴、冀小斌先生为我翻译最初的草稿;黄进兴、池胜昌、黄明理、俞宗宪、程一凡及刘景修先生提供许多修改草稿的宝贵意见。池胜昌先生从新泽西(NewJersey)来到亚利桑纳,前后辛勤工作40余日,对草稿做最后的重新修订,不但润饰中文的写作风格,并使译文能够更忠实于我的本意。
我很感谢台湾大学教授夏长朴先生,特别为增订版写序。他在儒家哲学上的造诣和有关北宋的专著为本书对于南宋的探讨奠定了基石。我的原书已经绝版几年了,在此对于黄进兴先生推荐此书的再版和杨家兴先生细心的编辑修订工作表示感谢。2002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本也已经绝版,在此对于刘东先生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增订本也表示感谢。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余英时先生。他为原版中文书特别写序,并于此次再与新序。他的为人师表、学术建树始终是我努力的源泉。我谨将此增订版献给余英时老师,祝贺他获得克鲁格(Kluge)大奖。
我也必须感谢妻子宓联卿女士,以及子女田亮、田梅,他们在我觉得写作此书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时,仍然使我感到生活充满乐趣,并且使我的思想能够保持平衡,不致一去不返,迷失在遥远的南宋时代。
田浩
2008年1月20日写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相关人物
田浩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