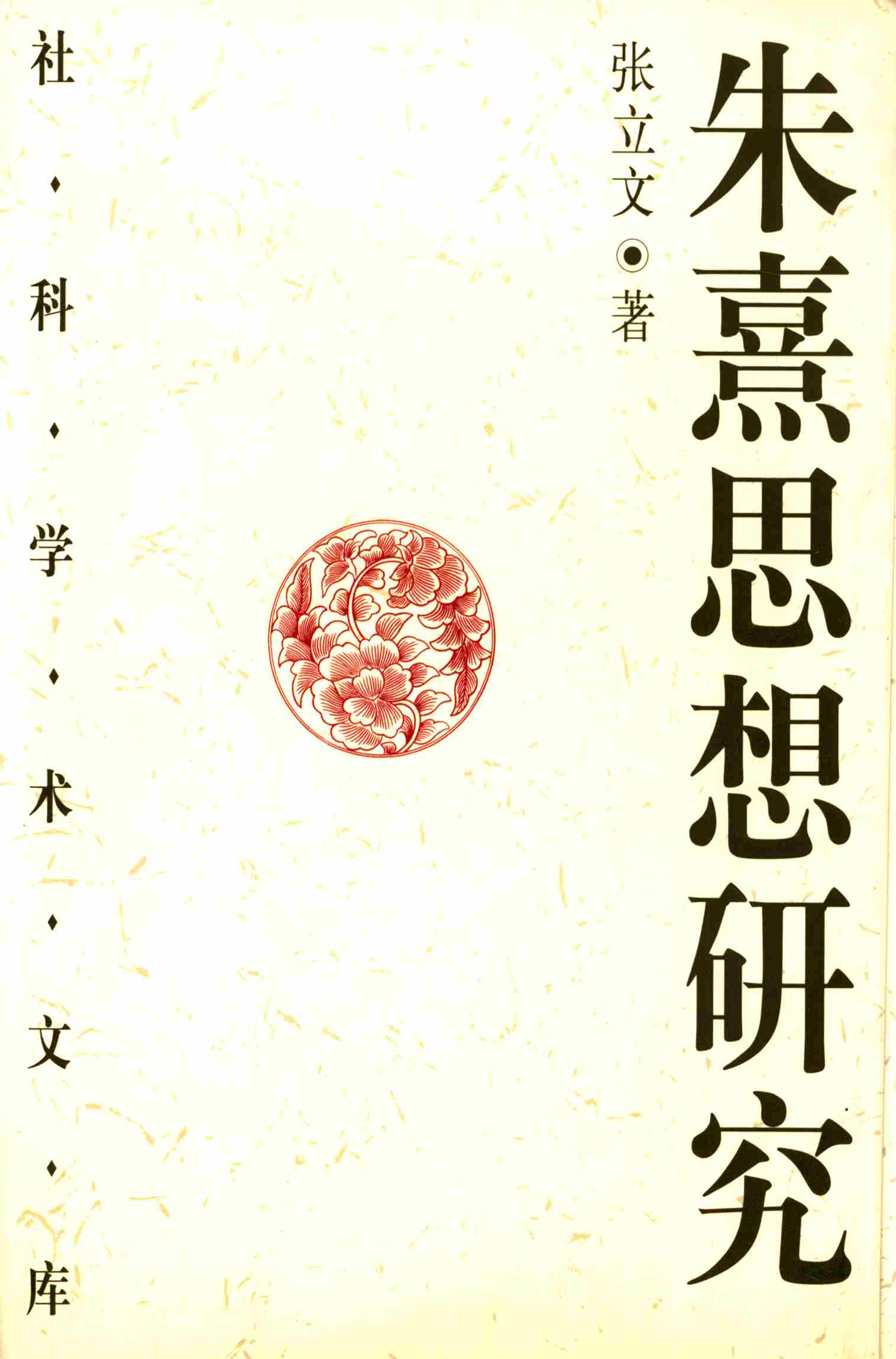内容
“理学”,作为一种历史的理论思维形态,多少年来,研究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理解,作了种种的诠释。
(一)问题的提出
有一种说法,“理学”就是“宋学”,即区别于汉唐以来训诂词章之学的宋代“性命义理”之学,而称之为“宋学”。
这种以朝代来命名学说,显然欠妥。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历史朝代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学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个不同的学派,而且也不能揭示“理学”所体现的特定的思想内容和特点。如果说宋代的“理学”为“宋学”,那么,明代的“理学”,只能称明学。退一步说,若以“性命义理”为“宋学”,虽然触及了问题的一些实质,但宋明时的哲学家几乎都谈“性命义理”,很难区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界限。作为非主流派的功利学派的陈亮、叶适也谈“性命义理”。叶适说:“余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①又说:“若孟子化血气从义理,其易如彼,而学者不察,方揠义理就血气,其难如此,盛衰顿异,勇怯绝殊,乃君子所甚畏也。”②又岂能说他们是主流派理学家!
另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之所以为“道学”,是因为《宋史》立有《道学传》。他们以《道学传》为准,凡列入《道学传》的为理学家,否则就不是理学家。
把《道学传》作为划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标准,而不是依据当时客观事实和各学术派别在理论论争中的态度为标准,显然没有道破问题的实质。《宋史》是元代宰相脱脱负责总编的。他们出于对程、朱的尊崇,只把濂、洛、关、闽四派人物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只有与程、朱关系极密的邵雍和张栻列入,其他都列入《儒林传》。这本之于朱熹《伊洛渊源录》的观点,明显的例子是对待司马光的问题。朱熹在作《六先生画像赞》时,曾将司马光和周、程、邵、张并提,但在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他作《伊洛渊源录》时,将司马光除去,而称“北宋五子”。因此《宋史》编撰者就没有将司马光列入《道学传》。如果放在当时政治和理论斗争中来考察,司马光应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的陆九龄和陆九渊等亦当入《道学传》而无疑。
尽管“道学”这一概念,北宋已有。张载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③程颐也说:“家兄(程颢)学术才行为时所重,……又其功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遂将泯没无闻,此尤深可哀也。”①此处“道学”,并非学派之称,而是指“道”与“学”。朱熹却称二程为“道学”:“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②“道学”是指继孔孟往圣之绝学的道统之学。朱熹晚年,政治上遭到排斥,“道学”也受攻击。淳熙十年,郑丙上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③陈贾也说:“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④因此,讲“道学”被视为罪状。朱熹上《封事》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⑤“道学”便是“守道循理”者的称呼。“道学”虽在理宗时被恢复名誉,但到明中叶李贽,抨诋为假道学。后来,道学家或道学先生就成为表面道貌岸然,内里欺世盗名的代名词。再者也容易与道家之学混淆,因此,“道学”之名被用滥了,超出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之名的特有范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断代哲学史的统称。
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样没有揭示“理学”的特定的思想实质和特点。如果说“理学”是断代哲学史的统称,那么,它就像清代李威所说的是一个大布袋,精粗巨细,无不纳入其中,各种学术思想和各种派别统统包容。这样的统称,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宋代“道学”是作为一个学派之名登上历史舞台的。据记载,当时“道学”与反“道学”的论争十分激烈。韩侂胄等以“道学”当名曰“伪学”,由是目“道学”为“伪学”。叶适说:“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①双方论争的阵线也很清楚。尽管当时道学家和反道学家不尽是哲学家,但亦无必要去否认这个历史事实。既有反“道学”的论争,便有“道学”在,也有非“道学”在。
上述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偏颇。笔者认为,“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学派的总称。
(二)所谓理学
“理学”是北宋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的元旨是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的转生,是对于笃守师说的批判,亦是对于以疑经为背道,以“破注”为非法的反动。宋代知识分子起来大破汉唐“传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实现了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埂。”②学术界萌发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思潮。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疑六经之首《周易》中的《易传》为非孔子之言;又撰《毛诗本义》,破毛享、郑玄传注。刘敞的《七经小传》,由疑经而改经。此外如司马光、李觏等之疑《孟子》,苏轼之讥《尚书》等,蔚然成风。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①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各个集团、阶层、学派的思想家,依据本集团、阶层、学派的利益及各自的思想,提出了各自救治社会的战略、方案以及主张、学说等。宋王朝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抑兼并,思想上的兼容并蓄和佑文政策,出现一种相对宽松的形势。这种形势为宋代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思潮提供一个较好的文化环境和生长的气候、土壤,很快形成了宋代各家异说,学派聚奎的可喜情境。
但是思想的解放思潮,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特别是“荆公新法”的失败,学术的论争被蒙上了政治的色彩,思想上的疑经改经思潮逐渐被无休止的政治党派斗争所冲淡。各派的学说随着政治的起伏而起伏,一时被颁之学官,一时又遭禁受诬,政治风云强烈制约各派学说的发展。原来思想界那种清新的、生气勃勃的空气减弱了;原旨意义上的理学社会思潮,便开始转向了,以至坠入了政治的漩涡。即使你主观上不愿意参与,客观上亦不可避免。
在庆历至熙宁的二三十年间,先后相继形成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可谓学派竞艳,相得益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主观条件的发展,原来“关学”、“洛学”、“新学”、“朔学”、“蜀学”并立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与熙宁新法的失败相联系,元祐初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上台,大贬新法派,“新学”便成为禁学。曾慥的《高斋漫录》说:“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公(王安石)问有何新事,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后来新法派虽又上台执政,但基本上属于政治上的党派斗争,于“新法”本身的发展已无太大关系,这样“新学”便式微了。“蜀学”的苏轼、苏辙,初亦主张改革,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由于方略、方法上的分歧而成为反新法派,在这点上“洛学”和“蜀学”结成了联盟。然而到新法废除后的元祐时期,洛、蜀两派又如同水火。此期间虽互有起伏,但二苏的“蜀学”总因其以三教合一为旨归①,释、道味道较浓而被目为禅。虽然后人有为其辩解的,但终宋之世,未改其“三家为一”的评论。人们虽认为其“三教合一”是“气习之弊”所致,非为邪心,不能像对待王安石“新学”那样贬斥“蜀学”。但又以为其不知“道”,问题也是够严重的了。因此,便将“蜀学”排之于“道学”之外。全祖望囿于宋明理学的正统观念,在《宋元学案》中,将“新学”和“蜀学”摈出正书,附之卷尾。
北宋惟“洛学”独盛,究其因:一是,二程初亦要求变法,后与吕公著、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新法和“新学”,元祐初,程颐得到他们的推荐,“太皇太后面谕将以为崇政殿说书”。②为哲宗皇帝讲“道学”。由于得太皇太后高氏和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巨公耆儒”的支持和宣扬,“洛学”便得以盛行;二是“洛学”在当时被视为醇儒,而无“蜀学”的那种禅味。程颐在程颢《墓表》中便说,程颢继孟子之后圣人不传之学,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①,因此,得到推崇;三是,门人弟子积极传道,张载死后其高足亦改换门庭,师事程颐。这样不仅“新学”和“蜀学”不能与“洛学”相抗衡,就连“关学”亦无“洛学”那样广泛流传。
南宋初年,朱熹和陆九渊、吕祖谦等鉴于北宋时政治斗争强烈左右学术论争之失,而企图从中摆脱出来,进行学术上的创新。他们冷静地总结、发展以往哲学理论思维,朱熹根据其出入佛、道的体会,认为儒学对稳定社会秩序较佛、道有效,绍承孔子、孟子《大学》、《中庸》,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之学之大成,即理学之大成。
所谓“理学”,从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辑的《近思录》中,可窥其梗概。此书章次的确定,材料的取舍,都体现了“理学”思想精神。共编十四卷:1.道体;2.为学大要;3.格物穷理;4.存养;5.改过迁善,克己复礼;6.齐家之道;7.出处进退辞受之义;8.治国、平天下之道;13.异端之害;14.圣贤气象。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中说:“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②作为登“理学”之堂奥,入“理学”之门的书,可谓上乘之作。
朱熹和吕祖谦所概括的这十四个问题,以“道体”和“性”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主静”、“居敬”的“存养”为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圣”为价值理想的目标。据此,宋明理学的性质和内容,试概括如下:
第一,宋明理学以探讨道体为核心,所谓道体就是指在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本性。这便是理学家所追求的所当然的所以然。所当然即是指自然、社会现象;所以然是指自然、社会现象背后的本体。如“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①。或自然、社会现象之上的本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②所当然与所以然的关系,即道体与自然、社会现象的关系。道体(天理)自身是“寂然不动”的,它“无造作”、“无计度”,然却具有“感而遂通”,或“感应之几”的功能,它是自然、社会现象的终极的根源,即“太极”。
第二,宋明理学以“穷理”为精髓。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后面“道体”(所以然之理)的体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对“理”(“道体”)的自省和回归,而且是“圣贤之象”之理想人格的自觉,即所谓“脱然有悟处”或“豁然有个觉处”。③“穷理”既是“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然者而已”,亦是“尽性至命”、“寻个是处”④,追求人性的根据。因此,“理有未穷”,知有未尽,“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性”⑤。不能穷得理,就不能尽心尽性。这就是说“穷理”是贯通“道体”、“理”、“性”、“命”、“心”的枢纽,是“明明德”⑥的工夫,所以,后来陆世仪概括说:“居敬穷理四字,是学者学圣人第一工夫,彻上彻下,彻首彻尾,总只此四字。”⑦抓住“穷理”这个精髓,便能联结“天人合一”,“己与天为一”。⑧万物与我同体,“物吾与也”,即“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①,达到其乐无穷的“道通为一”的理想境界。
第三,宋明理学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工夫。理学家认为在自然、社会、人生以至人类历史上,凡真的、善的、美的、正的、光明的,都是“天理”(“理”),是“天理之自然”,或“理之自然”;凡是假的、恶的、丑的、偏的、黑暗的,都是“人欲”,属于该去之列。无论主流派或非主流派都强调义理与大公,排斥功利与私欲。“存天理,去人欲”,便成为当时社会人人必遵而行之的原则。
如何“存天理,去人欲”,这就需“主静”、“居敬”的工夫,“涵养须用敬”,周敦颐“仁义中正而主静”,而达到“立人极”。二程“居敬集义”,其宗旨是为明“天理”,“敬”是主一,心不二用;敬是未发之中,发而合乎“中节”;敬是“直内”。如何“居敬”,程颐提出“操存闲邪”和“涵泳存养”两方面的修养方法。从而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目的。
第四,宋明理学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理学家都以此为己任。张载自谓其为学宗旨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程颐述程颢的为学宗旨是:“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③人与天地作为三才,人是天地的中心。天地由人而能立心,自然和社会由于人而有价值,人对天地具有特殊的义务。“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这便是“为生民立道”。即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然而,作为“尽性至命”与“孝弟”的融合,“穷神知化”与“礼乐”的融合,把“理”这个普遍的原则与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会通起来,把现实的制度理想化,便是“治国平天下”。
第五,宋明理学以为圣为价值理想的目标。辟佛、老,辨异端。宋明理学家既出佛、老,又融佛、老于儒,从而构筑了与佛、老不同的新的儒学哲学。尽管其间有些思想体系中佛、老的味道浓一些,但又既不等同于佛、老二教,亦不同于一般宗教。理学从根本上说是理性思维,是哲学的思辨。为往圣继绝学,以发扬孔孟学说为职志。通过为学、修德,建构了儒学精神家园,终极关怀,而达“圣贤气象”的境界。
(一)问题的提出
有一种说法,“理学”就是“宋学”,即区别于汉唐以来训诂词章之学的宋代“性命义理”之学,而称之为“宋学”。
这种以朝代来命名学说,显然欠妥。这不仅是因为在一个历史朝代内,有着各种不同的学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个不同的学派,而且也不能揭示“理学”所体现的特定的思想内容和特点。如果说宋代的“理学”为“宋学”,那么,明代的“理学”,只能称明学。退一步说,若以“性命义理”为“宋学”,虽然触及了问题的一些实质,但宋明时的哲学家几乎都谈“性命义理”,很难区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界限。作为非主流派的功利学派的陈亮、叶适也谈“性命义理”。叶适说:“余尝疑汤‘若有恒性’,伊尹‘习与性成’,孔子‘性近习远’,乃言性之正,非止善字所能弘通。”①又说:“若孟子化血气从义理,其易如彼,而学者不察,方揠义理就血气,其难如此,盛衰顿异,勇怯绝殊,乃君子所甚畏也。”②又岂能说他们是主流派理学家!
另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之所以为“道学”,是因为《宋史》立有《道学传》。他们以《道学传》为准,凡列入《道学传》的为理学家,否则就不是理学家。
把《道学传》作为划分“理学”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标准,而不是依据当时客观事实和各学术派别在理论论争中的态度为标准,显然没有道破问题的实质。《宋史》是元代宰相脱脱负责总编的。他们出于对程、朱的尊崇,只把濂、洛、关、闽四派人物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只有与程、朱关系极密的邵雍和张栻列入,其他都列入《儒林传》。这本之于朱熹《伊洛渊源录》的观点,明显的例子是对待司马光的问题。朱熹在作《六先生画像赞》时,曾将司马光和周、程、邵、张并提,但在宋孝宗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他作《伊洛渊源录》时,将司马光除去,而称“北宋五子”。因此《宋史》编撰者就没有将司马光列入《道学传》。如果放在当时政治和理论斗争中来考察,司马光应列入《道学传》。四派以外的陆九龄和陆九渊等亦当入《道学传》而无疑。
尽管“道学”这一概念,北宋已有。张载说:“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③程颐也说:“家兄(程颢)学术才行为时所重,……又其功业不得施于时,道学不及传之书,遂将泯没无闻,此尤深可哀也。”①此处“道学”,并非学派之称,而是指“道”与“学”。朱熹却称二程为“道学”:“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学于孔孟既没千载不传之后,可谓盛矣。”②“道学”是指继孔孟往圣之绝学的道统之学。朱熹晚年,政治上遭到排斥,“道学”也受攻击。淳熙十年,郑丙上疏:“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③陈贾也说:“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摈斥勿用。”④因此,讲“道学”被视为罪状。朱熹上《封事》说:“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之人,而加以矫激之罪,……盖自朝廷之上,以及闾里之间,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⑤“道学”便是“守道循理”者的称呼。“道学”虽在理宗时被恢复名誉,但到明中叶李贽,抨诋为假道学。后来,道学家或道学先生就成为表面道貌岸然,内里欺世盗名的代名词。再者也容易与道家之学混淆,因此,“道学”之名被用滥了,超出了作为一种学术思想之名的特有范围。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理学”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一家完整的哲学学说,它是我国特定时期(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的断代哲学史的统称。
这种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样没有揭示“理学”的特定的思想实质和特点。如果说“理学”是断代哲学史的统称,那么,它就像清代李威所说的是一个大布袋,精粗巨细,无不纳入其中,各种学术思想和各种派别统统包容。这样的统称,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事实上,宋代“道学”是作为一个学派之名登上历史舞台的。据记载,当时“道学”与反“道学”的论争十分激烈。韩侂胄等以“道学”当名曰“伪学”,由是目“道学”为“伪学”。叶适说:“盖自昔小人残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为好名,或以为立异,或以为植党。近创为‘道学’之目,郑丙倡之,陈贾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见士大夫有稍慕洁修,粗能操守,辄以道学之名归之。”①双方论争的阵线也很清楚。尽管当时道学家和反道学家不尽是哲学家,但亦无必要去否认这个历史事实。既有反“道学”的论争,便有“道学”在,也有非“道学”在。
上述三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偏颇。笔者认为,“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定的学术思想,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学派的总称。
(二)所谓理学
“理学”是北宋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的元旨是汉唐以来章句注疏之学的转生,是对于笃守师说的批判,亦是对于以疑经为背道,以“破注”为非法的反动。宋代知识分子起来大破汉唐“传注”,从“舍传求经”到“疑经改经”,松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实现了理论思维形态的转生。王应麟说:“自汉儒至于庆历间,谈经者,守训诂而不凿。《七经小传》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经[新]义》行,视汉儒之学若土埂。”②学术界萌发了一股新鲜的、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思潮。欧阳修的《易童子问》,疑六经之首《周易》中的《易传》为非孔子之言;又撰《毛诗本义》,破毛享、郑玄传注。刘敞的《七经小传》,由疑经而改经。此外如司马光、李觏等之疑《孟子》,苏轼之讥《尚书》等,蔚然成风。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①在这种风气的推动下,各个集团、阶层、学派的思想家,依据本集团、阶层、学派的利益及各自的思想,提出了各自救治社会的战略、方案以及主张、学说等。宋王朝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抑兼并,思想上的兼容并蓄和佑文政策,出现一种相对宽松的形势。这种形势为宋代疑经、改经的思想解放思潮提供一个较好的文化环境和生长的气候、土壤,很快形成了宋代各家异说,学派聚奎的可喜情境。
但是思想的解放思潮,并没有持续很久。随着“庆历新政”的失败,特别是“荆公新法”的失败,学术的论争被蒙上了政治的色彩,思想上的疑经改经思潮逐渐被无休止的政治党派斗争所冲淡。各派的学说随着政治的起伏而起伏,一时被颁之学官,一时又遭禁受诬,政治风云强烈制约各派学说的发展。原来思想界那种清新的、生气勃勃的空气减弱了;原旨意义上的理学社会思潮,便开始转向了,以至坠入了政治的漩涡。即使你主观上不愿意参与,客观上亦不可避免。
在庆历至熙宁的二三十年间,先后相继形成了以周敦颐为代表的“濂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可谓学派竞艳,相得益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主观条件的发展,原来“关学”、“洛学”、“新学”、“朔学”、“蜀学”并立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与熙宁新法的失败相联系,元祐初反对新法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上台,大贬新法派,“新学”便成为禁学。曾慥的《高斋漫录》说:“元祐初,温公(司马光)拜相,更易熙丰政事。……公(王安石)问有何新事,对曰:‘近有指挥不得看《字说》。’公曰:‘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后来新法派虽又上台执政,但基本上属于政治上的党派斗争,于“新法”本身的发展已无太大关系,这样“新学”便式微了。“蜀学”的苏轼、苏辙,初亦主张改革,但在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由于方略、方法上的分歧而成为反新法派,在这点上“洛学”和“蜀学”结成了联盟。然而到新法废除后的元祐时期,洛、蜀两派又如同水火。此期间虽互有起伏,但二苏的“蜀学”总因其以三教合一为旨归①,释、道味道较浓而被目为禅。虽然后人有为其辩解的,但终宋之世,未改其“三家为一”的评论。人们虽认为其“三教合一”是“气习之弊”所致,非为邪心,不能像对待王安石“新学”那样贬斥“蜀学”。但又以为其不知“道”,问题也是够严重的了。因此,便将“蜀学”排之于“道学”之外。全祖望囿于宋明理学的正统观念,在《宋元学案》中,将“新学”和“蜀学”摈出正书,附之卷尾。
北宋惟“洛学”独盛,究其因:一是,二程初亦要求变法,后与吕公著、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新法和“新学”,元祐初,程颐得到他们的推荐,“太皇太后面谕将以为崇政殿说书”。②为哲宗皇帝讲“道学”。由于得太皇太后高氏和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巨公耆儒”的支持和宣扬,“洛学”便得以盛行;二是“洛学”在当时被视为醇儒,而无“蜀学”的那种禅味。程颐在程颢《墓表》中便说,程颢继孟子之后圣人不传之学,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①,因此,得到推崇;三是,门人弟子积极传道,张载死后其高足亦改换门庭,师事程颐。这样不仅“新学”和“蜀学”不能与“洛学”相抗衡,就连“关学”亦无“洛学”那样广泛流传。
南宋初年,朱熹和陆九渊、吕祖谦等鉴于北宋时政治斗争强烈左右学术论争之失,而企图从中摆脱出来,进行学术上的创新。他们冷静地总结、发展以往哲学理论思维,朱熹根据其出入佛、道的体会,认为儒学对稳定社会秩序较佛、道有效,绍承孔子、孟子《大学》、《中庸》,集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之学之大成,即理学之大成。
所谓“理学”,从朱熹和吕祖谦共同编辑的《近思录》中,可窥其梗概。此书章次的确定,材料的取舍,都体现了“理学”思想精神。共编十四卷:1.道体;2.为学大要;3.格物穷理;4.存养;5.改过迁善,克己复礼;6.齐家之道;7.出处进退辞受之义;8.治国、平天下之道;13.异端之害;14.圣贤气象。朱熹在《书近思录后》中说:“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之要,与夫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②作为登“理学”之堂奥,入“理学”之门的书,可谓上乘之作。
朱熹和吕祖谦所概括的这十四个问题,以“道体”和“性”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以“主静”、“居敬”的“存养”为工夫,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以“为圣”为价值理想的目标。据此,宋明理学的性质和内容,试概括如下:
第一,宋明理学以探讨道体为核心,所谓道体就是指在自然现象、社会现象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本性。这便是理学家所追求的所当然的所以然。所当然即是指自然、社会现象;所以然是指自然、社会现象背后的本体。如“衣食,动作,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①。或自然、社会现象之上的本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②所当然与所以然的关系,即道体与自然、社会现象的关系。道体(天理)自身是“寂然不动”的,它“无造作”、“无计度”,然却具有“感而遂通”,或“感应之几”的功能,它是自然、社会现象的终极的根源,即“太极”。
第二,宋明理学以“穷理”为精髓。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后面“道体”(所以然之理)的体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对“理”(“道体”)的自省和回归,而且是“圣贤之象”之理想人格的自觉,即所谓“脱然有悟处”或“豁然有个觉处”。③“穷理”既是“欲知事物之所以然与其所然者而已”,亦是“尽性至命”、“寻个是处”④,追求人性的根据。因此,“理有未穷”,知有未尽,“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尽得性”⑤。不能穷得理,就不能尽心尽性。这就是说“穷理”是贯通“道体”、“理”、“性”、“命”、“心”的枢纽,是“明明德”⑥的工夫,所以,后来陆世仪概括说:“居敬穷理四字,是学者学圣人第一工夫,彻上彻下,彻首彻尾,总只此四字。”⑦抓住“穷理”这个精髓,便能联结“天人合一”,“己与天为一”。⑧万物与我同体,“物吾与也”,即“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①,达到其乐无穷的“道通为一”的理想境界。
第三,宋明理学以“存天理,去人欲”为“存养”工夫。理学家认为在自然、社会、人生以至人类历史上,凡真的、善的、美的、正的、光明的,都是“天理”(“理”),是“天理之自然”,或“理之自然”;凡是假的、恶的、丑的、偏的、黑暗的,都是“人欲”,属于该去之列。无论主流派或非主流派都强调义理与大公,排斥功利与私欲。“存天理,去人欲”,便成为当时社会人人必遵而行之的原则。
如何“存天理,去人欲”,这就需“主静”、“居敬”的工夫,“涵养须用敬”,周敦颐“仁义中正而主静”,而达到“立人极”。二程“居敬集义”,其宗旨是为明“天理”,“敬”是主一,心不二用;敬是未发之中,发而合乎“中节”;敬是“直内”。如何“居敬”,程颐提出“操存闲邪”和“涵泳存养”两方面的修养方法。从而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目的。
第四,宋明理学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实质。理学家都以此为己任。张载自谓其为学宗旨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②程颐述程颢的为学宗旨是:“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③人与天地作为三才,人是天地的中心。天地由人而能立心,自然和社会由于人而有价值,人对天地具有特殊的义务。“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④这便是“为生民立道”。即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价值。然而,作为“尽性至命”与“孝弟”的融合,“穷神知化”与“礼乐”的融合,把“理”这个普遍的原则与人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会通起来,把现实的制度理想化,便是“治国平天下”。
第五,宋明理学以为圣为价值理想的目标。辟佛、老,辨异端。宋明理学家既出佛、老,又融佛、老于儒,从而构筑了与佛、老不同的新的儒学哲学。尽管其间有些思想体系中佛、老的味道浓一些,但又既不等同于佛、老二教,亦不同于一般宗教。理学从根本上说是理性思维,是哲学的思辨。为往圣继绝学,以发扬孔孟学说为职志。通过为学、修德,建构了儒学精神家园,终极关怀,而达“圣贤气象”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