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代朱子学、理学的社会组织与礼仪设计及其经世致用
| 内容出处: |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910 |
| 颗粒名称: | (五)宋代朱子学、理学的社会组织与礼仪设计及其经世致用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3 |
| 页码: | 453-46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研究宋明时期的理学时,学者们过于注重理学家形上思维的辩论,导致忽视了基层社会的设计与管理。然而,宋代理学家们并不仅仅关注道德与政治,他们还致力于重新构建民间社会的行为礼仪和社会组织。 |
| 关键词: | 朱子学 理学 社会组织 |
内容
关于宋明“理学”研究的“哲学化”,学者们过分注重理学家们形上思维的“义理”之辩,恰恰又冷落甚至丢失了宋代“理学”另外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关于基层社会的设计与管理。事实上,宋代理学家们所倡导的“理学”,并不只是道德与政治的上层意识形态方面,他们还极力为民间社会的行为礼仪和社会组织进行重新的构建。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社会转型及其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平民化”或“市场化”程度的推进,汉唐及之前的诸侯门阀士族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宗法”世袭体制也分崩离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面对宋代以来这种新的社会重构组合历程,宋代许多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理学家们,根据这一新的时代特征,为宋代的社会重构和组合设计出了一系列的蓝图。这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莫过于民间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了。根据冯尔康等先生的研究,宋明时期的宗族、家族制度是从上古时期的“宗法制”演变而来的,汉晋时期则演变为门阀士族制度。这种深具统治特权的制度演化至宋代,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基本衰败。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成为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大批平民通过科举改变其社会地位。官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以官僚和士绅为主体建立起新的宗族制度。①
在唐宋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宋代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如张载、程颐、程颢、欧阳修、苏洵、范仲淹、司马光、陆九韶等,都积极参与其间,适时提倡建构具有平民色彩的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
北宋著名的学者张载在论证重建家族对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时说:“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①因此,重新建构家族组织,实行新的“宗法制”,是稳定社会秩序、重树良好社会风俗的必由之路,“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②。
宋代的社会现实,使家族制度的重建不可能与古代守法制度完全相同,因此,重建必须因地因时制宜地对古代礼制有所更新。朱熹以其对古代礼制的深入研究为基础,结合当时的民俗,为宋代社会礼仪特别是重建家族制度设计了新的规范。他在《朱子家礼》的开篇位置,就阐明了建立祠堂这一最具创造性的举措。朱熹说:“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③在倡导敬宗收族的同时,朱熹在《家礼》中对于民间社会的诸如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的习俗规范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以期社会有所遵行。
朱熹和宋代理学家们的努力,在宋代以及后世产生了重大与深远的影响。张载、程颐、朱熹等人极力倡导的重建民间家族制度和建立祠堂的主张,在宋以后的社会里已经成为推行家族制度的理论依据;欧阳修、苏洵等人创立了民间私家修撰族谱、家乘的样式,为后代所沿袭;《朱子家礼》的设计,至今还在不少地方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宋代所提倡的敬宗收族、义恤乡里以及“义仓”“义学”“义冢”等等,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在宋以后的许多民间族谱与相关文献的记载中,时时可见朱熹等宋儒们对于这些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影响,所谓“冠婚丧祭,一如文公《家礼》”,“四时祭飨,略如朱文公所著仪式”。①我曾经对闽台一带的民间族谱进行过统计分析,朱熹所撰写的族谱序言,至少在三十个不同姓氏的族谱中出现过。②这里摘录泉州刘氏家族族谱中的朱熹序言云:
余尝仰观天象,北辰为中天之枢,而三垣九曜旋绕归向,譬犹君之尊而无适不拱焉;俯察坤维,昆仑为华夏之镇,而五岳八表逶迤顾盼,譬犹祖之亲而无适不本焉。故君亲一理、忠孝一道,悖之者谓之逆,遗之者谓之弃,慢之者谓之亵。无将之戒,莫大于不忠;五刑之属,莫大于不孝。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而不可一毫或忽也。今阅刘氏谱牒,上溯姓源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者而能之乎?噫!世之去祖未远,问其自而懵然者,愧于刘氏多矣。
绍熙五年甲寅春三月
新安朱熹顿首拜撰③
我们现在固然无法确知现存的闽台民间族谱中这许多所谓的朱熹题序是否真的是朱熹的手笔,但是由此亦可以了解到朱熹构建家族理念对于闽台民间社会所产生的巨大而长远的影响力。
朱熹等理学家们对于宋代民间社会的建构,远不止于家族、宗族组织这一层面,而是涉及民风习尚等多方面的教化。例如,朱熹对于推行民间社会的孝道,除了在他著名的《朱子家礼》中有着重论述之外,在其他的著作中,也一再引导。朱子在《示俗》中阐述了对于民间基层施行孝道的看法:“《孝经》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谓依时及节耕种田土。谨身节用,谨身谓不作非违,不犯刑宪;节用谓省使俭用,不妄耗费。以养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则身安力足,有以奉养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稳快乐。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谓百姓也。’”①朱子所注的儒家经典《孝经》之一小段十分简单,即“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这种简易可行的尽孝之方,是庶民的孝养父母之道,其实就是在农耕文明中的农村生活世界中俭朴节约的孝道。朱子在民间社会中行政施教,很自然地会将儒家的庶民德教德化之传统予以推行。朱子继续注解曰:“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顺。虽是父母不存,亦须如此,方能保守父母产业,不至破坏,乃为孝顺。若父母生存不能奉养,父母亡殁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载,幽为鬼神所责,明为官法所诛,不可不深戒也。”②
朱子通过《孝经》在乡村家族中推行孝行,他强调奉养父母以及保守家业的重要性,能在世奉养死后保守,方是庶民孝道,同时,从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角度出发,朱子于此突出天地和鬼神,显示庶民社会的儒教着重宗教性的礼制,宣达儒家之道德理性主义的朱子在民间推行儒家德教时,却倾向儒家的宗教神圣之面向。朱子在此文最后说:“以上《孝经·庶人章》正文五句,系先圣‘至圣文宣王’所说。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①朱熹的这一结论很有意思,它表达了朱子心中亦有宗教化的孔子,一般而言,儒士均敬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如果以“至圣文宣王”来敬称孔子,即有圣王之意思,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是带有提升孔子为神圣的宗教崇拜的味道,而朱子劝庶民“逐日持诵”《孝经》,此《孝经》虽然大致已知是后儒撰写之文章,并非孔子亲述,亦非四书五经的正统儒家大典,但大儒朱子却视为孔子之创作,且要求或鼓励庶民百姓天天虔心一志地恭诵,就如同社会上一般佛教徒或善男信女天天诵读《阿弥陀佛经》《心经》或只持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朱子的想法就是以带有宗教信念的做法而以庶民孝道来教民化俗,使民间社会能够依靠儒家德教就成为文雅淳厚之乡土。
当然,朱子除了在民间社会推行移风易俗的行政之外,也十分注重儒学教育的建树。特别是对于那些较为偏远穷困的乡县,朱子甚重视其地的县学或是书院,也很留意表彰当地的故儒,其言行就是真切实践民间社会的儒家德教德化。这些关怀和践履,朱子之文本很丰富,振兴提倡县学方面,仅举一例明之:“予闻龙岩为县斗辟,介于两越之间,俗故穷陋。……今数百年,未闻有以道义功烈显于时者。岂其材之不足哉?殆为吏者未有以兴起之也。今二君相继贰令于此,乃能深以兴学化民为己任,其志既美矣。……夫所谓圣贤之学者,非有难知难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修其身,而求师取友,颂诗读书,以穷事物之理而已。……使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行日笃而身无不修也,求师取友,颂诗读书之趣日深而理无不得也,则自身而家,自家而国,以达于天下,将无所处而不当,固不必求道义功烈之显于时,而根深末茂,实大声闳,将有自然不可掩者矣。”①龙岩县即今福建省龙岩市地区,此县在南宋时代是山多田少而十分贫瘠的闽西穷乡,乡俗鄙陋粗俗。朱子为这里撰写的“学记”,实则十分平实素朴,他并没有高谈儒家形而上的哲理,或玄论天理心性等哲学之议题,他只是启发之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德目,是平日教化弟子和庶民、贵族、王者的平实话语,只需依照儒家道德伦常而为人,就能达到安乐祥和的乡土理想。
朱子对书院的贡献,我们不需再多赘言。倒是一般人刻板印象,认为朱子是一位宣讲天理性理的道德理性主义者,在乡土庶民的生活世界里,是不是毫无宗教神秘之密契?也就是毫无鬼神观。其实不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论及朱子宣扬民间社会孝道的方法一样,朱子正面肯定鬼神的话语甚多,在《朱子语类》卷三中就有朱子与弟子谈神说鬼的记载。其鬼神观基本上是以“气”之聚散伸缩而言,气聚是人,气散人死,死后其气伸展则为神,其气归返则为鬼。大体如此体会,但朱子很肯定生人与鬼神譬如祖先之间并非生死幽明隔绝,通过虔诚庄严的祭礼,人心是可以与鬼神之心有真切的“感格”的。②换言之,朱子并非无神论者,当他希望在民间社会实施教化时,他非常重视祭祀在德教德化中的感格作用。朱子在民间社会的礼治行事中有很多祭祀活动,限于篇幅,仅举两文以明之。《祈雨疏》中云:“丁壮在田,厉农功之既作;阴云布野,闵时雨之尚愆。由拙政之不修,顾疲民而何罪?肆陈丹悃,仰吁苍穹。伏愿鼓支以雷霆,亟霈为霖之施;泽及牛马,并销连死之忧。瞻仰归诚,吁嗟请命。”①《卧龙潭送水文》中说:“往分灵液,来即祠坛。诚未格于幽潜,泽尚愆于田亩。惟时淹久,惧弗吉蠲。敢奉冰壶,言归贝阙。别祷余润,用弭炎氛。尚神听之渊冲,鉴惟衷而响答。”②以上文章,一篇是祈祷降雨之疏文,一篇是祈祷陂潭送水之疏文。两者与农耕的田水息息相关,换言之,乃是由于当地久无甘霖,而陂潭之积水亦恐干涸而导致缺水灌田。自然灾害直接关系到南宋广大农民的生存大计,朱子的关怀完全在于农村百姓之生活和生命,从其撰述疏文向天地神明祈雨求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发乎真心诚意地想帮助百姓而非虚假的愚民手段。总之,具有宗教神圣韵味的庶民社会之儒学儒教,在朱子的社会伦常之实践中,充分呈现无余。他本人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民间社会的文化习俗体察至深,他对民间社会的道德教化,更多的是顺从了民间社会的文化精神需求。这也正是朱子学能够长期在民间社会得以继承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宋代朱熹等士大夫和理学家们所倡导的具有平民色彩的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比起他们的“义理”学说来,从宋代开始就显得幸运得多。在他们的设计、倡导以及亲自实践下,具有一定平民化色彩的新型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已经在宋代的许多地方出现。到了元代,平民化的家族制度又有新的进展,举祠堂之设为例,当时人说:“今也,下达于庶人,通享四代”③,“今夫中人之家,有十金之产者,亦莫不思为祖父享祀无穷之计”④。一些具有祭祀始祖及列祖十余世、二十余世以上的大宗祠也不断出现。①当然,从上层建筑的层面,对于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兴起,国家政府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延至明朝初期,政府对于民间出现的这种家庙祭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法律上的认可,规定贵族官僚可以建立家庙以祭祀四代祖先,士庶不可立家庙,只能在坟墓旁祭祀两代祖先。嘉靖年间大礼仪之争以后,明朝政府允许绅衿建立祠堂,纂修族谱以祭祀祖先。在大礼仪之争后,老百姓纷纷效仿,在家中修建祠堂,朝廷也因此修改律例,允许百姓修建祠堂祭祀祖先,这一变革逐步演变为一套有序的,足于维持基层社会稳定平衡的宗族模式。随着民间宗族祭祀制度的确立与扩散,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也日益向民间生活化和民俗化转变。宗族的首要任务是祭祀祖先,繁衍宗族子嗣,在此之外,族产的管理也是宗族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宗族通过集体控制财产来维持祭祀活动,同时也通过对族人招股集资进行商业活动,如进行借贷、扩张田产、经营店铺等,以此来为宗族创造经济利益。②可以说,到了明清时期,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成了中国民间最为重要和坚固的社会结构形式。
朱熹等人所倡导的家族建构与儒学对民间社会的教化,同样随着大陆移民的迁居而在台湾各地生根繁殖。到了清代后期,台湾地区的家族组织之完善,已经与其祖籍地福建等地鲜有差别。时至今日,台湾地区和福建两地,俨然就是全中国之内祠堂和寺庙最为发达的区域。至于对民间的教化与儒学基层化,我们从台湾地区的地方志中就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信息。如清代修纂的《苗栗县志》有如下叙述:“李纬烈,监生……素喜周急。道光六年,漳泉互斗,以粥赈难民,因而就食日多,舍无隙地,一时赖以活者数百人。行年七十三,预知寿尽,至期,正其衣冠端坐,以‘孝友’嘱子孙,言毕瞑目而逝。”这里记述监生李纬烈的一生行谊,即传统中国社会中乡治的“施善与教化”,然而他遗言说“孝友”,且必“正其衣冠端坐”,又有如朱子、曾子临终时道德性的身心姿态。可见清朝在台湾乡社的小知识分子之生命格调,已属糅合了儒家和佛教,而根本的伦常实践之核心,则属朱熹式的儒家伦常。再如:“李朝勋,字建初,纬烈子。性孝友,父母兄弟无间言,继母詹氏,养葬尽礼,称声载道。处世善善、恶恶,急公向义;为乡里排难解纷,抑强扶弱。……地方有事,率乡勇保卫,不吝赀财。生平好读书,尤精医术。晚筑家塾,设学田,延师训子孙。岁冬,命考家课,别优劣,赏赉有差。……”从这段记述李朝勋行谊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坚持的是彰善惩恶之德规以及教诲庶民行善避恶,他在宗祠中兴办家学,教族中子弟以儒行。①
再看《淡水厅志》中的记载。有郑崇和者,于竹堑办私家书院以教地方子弟:“晚益好宋儒书,如《性理精义》《朱子遗书》《近思录》诸书,沈潜反复,究极精微。尝示人曰:‘此数书具修齐治平之理,当令子弟于夙兴夜寐时,敬读数行,以洗心涤虑,久之可从此窥见圣贤学源流。’大抵先生之学原本六经,由事以知事;由宋儒书以析理,而其要则归于践履笃实且夫持身之严也;执事之敬也;治家之整肃也;与物之公而恕也;见义之勇于为也;执德信道之耄而不懈也。”①从这则记载中可以看出,郑氏是一位深信朱子儒学的道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依据之而实践者。他在竹堑教授儒子,根本目的是想造就圣贤,而不是用八股文教青年人只知道死盯着场屋僵死之试卷而求取利禄。《厅志》复云:“尝言:‘圣贤之学自主敬始,主敬之道,自克勤小物始。’居常见器物倾侧、几案错列,曰:‘此即不正之端。’必更为整顿,然后即安。……每日读书正襟危坐,如面质圣贤。……家庭肃穆,外言不入,内言不出,自写《朱氏家训》一篇,悬于中堂曰:‘正家之道,略尽此篇,朝夕晤对,开人心目,他佳图画,无以易此。’……次君用锡以名进士掌教书院,生徒林立,先生严诲之……谓:‘士君子砥行立名,必求居家无愧于乡,在官不负于国,庶几无忝所生。’”②郑崇和虽身为台湾边陲地区的佚名基层知识分子,但是他从朱子学的道德规范修身行事,并非拘泥僵硬的腐儒、朽儒、奴儒,其身心端正严毅与教化民间社会的理念,与我国大陆特别是福建地区的知识分子,没有本质的差别。
到了现当代,特别是1949年以后,有些学者从阶级演变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指摘了不少关于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负面因素,并且预示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衰落消亡。我却认为学者们的这种预测未免过于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两种倾向值得引起注意:一方面,不少地方的家族组织和乡族组织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甚至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在许多传统宗族制度和乡族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又一时未能寻找可以替代的社会组织的乡村里,普遍出现了一种道德混乱以及社会无序的现象。这两种倾向的出现,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宋明以来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长期存在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文化合理性。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宋明以来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这种文化合理性,基本上是在宋代理学家们的倡导下,由民间社会自行施行并得以发展兴盛起来的。国家政府不但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甚至在不少场合予以禁止和干扰。政府往往从强化专制统治的思维出发,认为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发展壮大,很有可能危及政府的社会治理,从而屡屡试图予以控制和限制。尽管如此,在强大的民间社会面前,这种不具有制度化的控制和限制,毕竟无法有效地影响明清时期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兴盛,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宋代“理学”所倡导设计的以宗族制度和乡族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正是由于较少受到专制政府的制度化约束,宋代“理学”的这一部分文化精神,比较正常地延续了下来,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基本认同。虽然到了现当代,有一部分学者从政治学术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但是它并没有像被制度化的“节孝”行为那样,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
宋代朱子学、理学演变到近现代,往往被人们讥讽为迂腐不堪、毫无实用的道德标榜,而注重实用的学人们,对于明清以来的所谓“经世致用”之学甚为欣赏。实际上,宋以来中国思想界所出现的“经世致用”之学,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形上思维,并没有真正实施的内涵与可能性。倒是宋代朱熹及其他理学家们所提倡的重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计与实践,在近千年的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全面的实施与推广,甚至延伸到海外的华人群体之中。因此,抛开学术与政治上的偏见,如果要在宋以后中国的思想家里寻找真正实施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那么,大概就只能是朱熹等宋儒们的这一主张了。
我们对宋代朱子学及理学的主要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历程做一简要叙述之后,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一)近现代以来偏重于“哲学”化的对于宋代“理学”的分析,往往把宋代以来的“理学”引向“形上思维”的文化精神的层面或意识形态的层面,忽视了宋代“理学”所倡导设计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二)宋代“理学”在宋代并没有得到较为广泛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政府的制度化的实践。经历元、明、清时期,以皇权为核心的政府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把宋代“理学”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制度化的实践与推广。在制度化的实践推广过程中,宋代“理学”所拥有的可贵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而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三)被明清时期政府制度化的宋代“理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被政府改造过的所谓“气节”观、“节孝”观等,不仅越来越偏离了宋代“理学”的本意,而且也越来越违背了人性的天真自然以及社会的进步,从而导致了近现代人们的诸多反感。与此相对照的是,宋代“理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反而在明清以来的民间社会得到了比较好的实践与传承,成为真正践行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对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四)从上面的三点认识延伸出来,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说:从中国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无论是孔子的儒学,还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以及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在其形成之初,都不乏各自优秀而积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特别是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在其倡导之时,其所包含的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监督意义,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极为宝贵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这种文化精神内涵一旦被社会当政者纳入其制度化的轨道,则必然逐渐沦为专制统治的附庸,从而日益显露出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性格。相反地,那些没有被专制统治者纳入到政治制度化当中的儒学传统,则有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其合理的本质,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显示出文化精神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唐宋时期社会转型及其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整个社会的“平民化”或“市场化”程度的推进,汉唐及之前的诸侯门阀士族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的“宗法”世袭体制也分崩离析,失去了其存在的社会基础。面对宋代以来这种新的社会重构组合历程,宋代许多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理学家们,根据这一新的时代特征,为宋代的社会重构和组合设计出了一系列的蓝图。这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莫过于民间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了。根据冯尔康等先生的研究,宋明时期的宗族、家族制度是从上古时期的“宗法制”演变而来的,汉晋时期则演变为门阀士族制度。这种深具统治特权的制度演化至宋代,已经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基本衰败。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成为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大批平民通过科举改变其社会地位。官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以官僚和士绅为主体建立起新的宗族制度。①
在唐宋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宋代许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如张载、程颐、程颢、欧阳修、苏洵、范仲淹、司马光、陆九韶等,都积极参与其间,适时提倡建构具有平民色彩的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
北宋著名的学者张载在论证重建家族对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意义时说:“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传。宗法若立,则人人各知来处。朝廷大有所益。或问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义岂有不立?忠义既立,朝廷之本岂有不固?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如此则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①因此,重新建构家族组织,实行新的“宗法制”,是稳定社会秩序、重树良好社会风俗的必由之路,“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②。
宋代的社会现实,使家族制度的重建不可能与古代守法制度完全相同,因此,重建必须因地因时制宜地对古代礼制有所更新。朱熹以其对古代礼制的深入研究为基础,结合当时的民俗,为宋代社会礼仪特别是重建家族制度设计了新的规范。他在《朱子家礼》的开篇位置,就阐明了建立祠堂这一最具创造性的举措。朱熹说:“今以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③在倡导敬宗收族的同时,朱熹在《家礼》中对于民间社会的诸如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的习俗规范都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以期社会有所遵行。
朱熹和宋代理学家们的努力,在宋代以及后世产生了重大与深远的影响。张载、程颐、朱熹等人极力倡导的重建民间家族制度和建立祠堂的主张,在宋以后的社会里已经成为推行家族制度的理论依据;欧阳修、苏洵等人创立了民间私家修撰族谱、家乘的样式,为后代所沿袭;《朱子家礼》的设计,至今还在不少地方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宋代所提倡的敬宗收族、义恤乡里以及“义仓”“义学”“义冢”等等,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在宋以后的许多民间族谱与相关文献的记载中,时时可见朱熹等宋儒们对于这些家族制度及其组织的影响,所谓“冠婚丧祭,一如文公《家礼》”,“四时祭飨,略如朱文公所著仪式”。①我曾经对闽台一带的民间族谱进行过统计分析,朱熹所撰写的族谱序言,至少在三十个不同姓氏的族谱中出现过。②这里摘录泉州刘氏家族族谱中的朱熹序言云:
余尝仰观天象,北辰为中天之枢,而三垣九曜旋绕归向,譬犹君之尊而无适不拱焉;俯察坤维,昆仑为华夏之镇,而五岳八表逶迤顾盼,譬犹祖之亲而无适不本焉。故君亲一理、忠孝一道,悖之者谓之逆,遗之者谓之弃,慢之者谓之亵。无将之戒,莫大于不忠;五刑之属,莫大于不孝。为人臣所当鞠躬尽瘁,而不可一毫或忽也。今阅刘氏谱牒,上溯姓源之始,下逮继世之宗,明昭穆以尚祖也,系所生以尚嫡也,序长幼以尚齿也,列像赞以尚思也,非大忠大孝者而能之乎?噫!世之去祖未远,问其自而懵然者,愧于刘氏多矣。
绍熙五年甲寅春三月
新安朱熹顿首拜撰③
我们现在固然无法确知现存的闽台民间族谱中这许多所谓的朱熹题序是否真的是朱熹的手笔,但是由此亦可以了解到朱熹构建家族理念对于闽台民间社会所产生的巨大而长远的影响力。
朱熹等理学家们对于宋代民间社会的建构,远不止于家族、宗族组织这一层面,而是涉及民风习尚等多方面的教化。例如,朱熹对于推行民间社会的孝道,除了在他著名的《朱子家礼》中有着重论述之外,在其他的著作中,也一再引导。朱子在《示俗》中阐述了对于民间基层施行孝道的看法:“《孝经》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谓依时及节耕种田土。谨身节用,谨身谓不作非违,不犯刑宪;节用谓省使俭用,不妄耗费。以养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则身安力足,有以奉养其父母,使其父母安稳快乐。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谓百姓也。’”①朱子所注的儒家经典《孝经》之一小段十分简单,即“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这种简易可行的尽孝之方,是庶民的孝养父母之道,其实就是在农耕文明中的农村生活世界中俭朴节约的孝道。朱子在民间社会中行政施教,很自然地会将儒家的庶民德教德化之传统予以推行。朱子继续注解曰:“能行此上四句之事,方是孝顺。虽是父母不存,亦须如此,方能保守父母产业,不至破坏,乃为孝顺。若父母生存不能奉养,父母亡殁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载,幽为鬼神所责,明为官法所诛,不可不深戒也。”②
朱子通过《孝经》在乡村家族中推行孝行,他强调奉养父母以及保守家业的重要性,能在世奉养死后保守,方是庶民孝道,同时,从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的角度出发,朱子于此突出天地和鬼神,显示庶民社会的儒教着重宗教性的礼制,宣达儒家之道德理性主义的朱子在民间推行儒家德教时,却倾向儒家的宗教神圣之面向。朱子在此文最后说:“以上《孝经·庶人章》正文五句,系先圣‘至圣文宣王’所说。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依此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不须更念佛号佛经,无益于身,枉费力也。”①朱熹的这一结论很有意思,它表达了朱子心中亦有宗教化的孔子,一般而言,儒士均敬称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如果以“至圣文宣王”来敬称孔子,即有圣王之意思,此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是带有提升孔子为神圣的宗教崇拜的味道,而朱子劝庶民“逐日持诵”《孝经》,此《孝经》虽然大致已知是后儒撰写之文章,并非孔子亲述,亦非四书五经的正统儒家大典,但大儒朱子却视为孔子之创作,且要求或鼓励庶民百姓天天虔心一志地恭诵,就如同社会上一般佛教徒或善男信女天天诵读《阿弥陀佛经》《心经》或只持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朱子的想法就是以带有宗教信念的做法而以庶民孝道来教民化俗,使民间社会能够依靠儒家德教就成为文雅淳厚之乡土。
当然,朱子除了在民间社会推行移风易俗的行政之外,也十分注重儒学教育的建树。特别是对于那些较为偏远穷困的乡县,朱子甚重视其地的县学或是书院,也很留意表彰当地的故儒,其言行就是真切实践民间社会的儒家德教德化。这些关怀和践履,朱子之文本很丰富,振兴提倡县学方面,仅举一例明之:“予闻龙岩为县斗辟,介于两越之间,俗故穷陋。……今数百年,未闻有以道义功烈显于时者。岂其材之不足哉?殆为吏者未有以兴起之也。今二君相继贰令于此,乃能深以兴学化民为己任,其志既美矣。……夫所谓圣贤之学者,非有难知难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修其身,而求师取友,颂诗读书,以穷事物之理而已。……使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行日笃而身无不修也,求师取友,颂诗读书之趣日深而理无不得也,则自身而家,自家而国,以达于天下,将无所处而不当,固不必求道义功烈之显于时,而根深末茂,实大声闳,将有自然不可掩者矣。”①龙岩县即今福建省龙岩市地区,此县在南宋时代是山多田少而十分贫瘠的闽西穷乡,乡俗鄙陋粗俗。朱子为这里撰写的“学记”,实则十分平实素朴,他并没有高谈儒家形而上的哲理,或玄论天理心性等哲学之议题,他只是启发之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德目,是平日教化弟子和庶民、贵族、王者的平实话语,只需依照儒家道德伦常而为人,就能达到安乐祥和的乡土理想。
朱子对书院的贡献,我们不需再多赘言。倒是一般人刻板印象,认为朱子是一位宣讲天理性理的道德理性主义者,在乡土庶民的生活世界里,是不是毫无宗教神秘之密契?也就是毫无鬼神观。其实不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论及朱子宣扬民间社会孝道的方法一样,朱子正面肯定鬼神的话语甚多,在《朱子语类》卷三中就有朱子与弟子谈神说鬼的记载。其鬼神观基本上是以“气”之聚散伸缩而言,气聚是人,气散人死,死后其气伸展则为神,其气归返则为鬼。大体如此体会,但朱子很肯定生人与鬼神譬如祖先之间并非生死幽明隔绝,通过虔诚庄严的祭礼,人心是可以与鬼神之心有真切的“感格”的。②换言之,朱子并非无神论者,当他希望在民间社会实施教化时,他非常重视祭祀在德教德化中的感格作用。朱子在民间社会的礼治行事中有很多祭祀活动,限于篇幅,仅举两文以明之。《祈雨疏》中云:“丁壮在田,厉农功之既作;阴云布野,闵时雨之尚愆。由拙政之不修,顾疲民而何罪?肆陈丹悃,仰吁苍穹。伏愿鼓支以雷霆,亟霈为霖之施;泽及牛马,并销连死之忧。瞻仰归诚,吁嗟请命。”①《卧龙潭送水文》中说:“往分灵液,来即祠坛。诚未格于幽潜,泽尚愆于田亩。惟时淹久,惧弗吉蠲。敢奉冰壶,言归贝阙。别祷余润,用弭炎氛。尚神听之渊冲,鉴惟衷而响答。”②以上文章,一篇是祈祷降雨之疏文,一篇是祈祷陂潭送水之疏文。两者与农耕的田水息息相关,换言之,乃是由于当地久无甘霖,而陂潭之积水亦恐干涸而导致缺水灌田。自然灾害直接关系到南宋广大农民的生存大计,朱子的关怀完全在于农村百姓之生活和生命,从其撰述疏文向天地神明祈雨求水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发乎真心诚意地想帮助百姓而非虚假的愚民手段。总之,具有宗教神圣韵味的庶民社会之儒学儒教,在朱子的社会伦常之实践中,充分呈现无余。他本人长期生活在农村,对于民间社会的文化习俗体察至深,他对民间社会的道德教化,更多的是顺从了民间社会的文化精神需求。这也正是朱子学能够长期在民间社会得以继承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宋代朱熹等士大夫和理学家们所倡导的具有平民色彩的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比起他们的“义理”学说来,从宋代开始就显得幸运得多。在他们的设计、倡导以及亲自实践下,具有一定平民化色彩的新型家族制度及其组织,已经在宋代的许多地方出现。到了元代,平民化的家族制度又有新的进展,举祠堂之设为例,当时人说:“今也,下达于庶人,通享四代”③,“今夫中人之家,有十金之产者,亦莫不思为祖父享祀无穷之计”④。一些具有祭祀始祖及列祖十余世、二十余世以上的大宗祠也不断出现。①当然,从上层建筑的层面,对于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兴起,国家政府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延至明朝初期,政府对于民间出现的这种家庙祭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法律上的认可,规定贵族官僚可以建立家庙以祭祀四代祖先,士庶不可立家庙,只能在坟墓旁祭祀两代祖先。嘉靖年间大礼仪之争以后,明朝政府允许绅衿建立祠堂,纂修族谱以祭祀祖先。在大礼仪之争后,老百姓纷纷效仿,在家中修建祠堂,朝廷也因此修改律例,允许百姓修建祠堂祭祀祖先,这一变革逐步演变为一套有序的,足于维持基层社会稳定平衡的宗族模式。随着民间宗族祭祀制度的确立与扩散,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也日益向民间生活化和民俗化转变。宗族的首要任务是祭祀祖先,繁衍宗族子嗣,在此之外,族产的管理也是宗族的重要任务。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地区,宗族通过集体控制财产来维持祭祀活动,同时也通过对族人招股集资进行商业活动,如进行借贷、扩张田产、经营店铺等,以此来为宗族创造经济利益。②可以说,到了明清时期,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成了中国民间最为重要和坚固的社会结构形式。
朱熹等人所倡导的家族建构与儒学对民间社会的教化,同样随着大陆移民的迁居而在台湾各地生根繁殖。到了清代后期,台湾地区的家族组织之完善,已经与其祖籍地福建等地鲜有差别。时至今日,台湾地区和福建两地,俨然就是全中国之内祠堂和寺庙最为发达的区域。至于对民间的教化与儒学基层化,我们从台湾地区的地方志中就可以看到不少这样的信息。如清代修纂的《苗栗县志》有如下叙述:“李纬烈,监生……素喜周急。道光六年,漳泉互斗,以粥赈难民,因而就食日多,舍无隙地,一时赖以活者数百人。行年七十三,预知寿尽,至期,正其衣冠端坐,以‘孝友’嘱子孙,言毕瞑目而逝。”这里记述监生李纬烈的一生行谊,即传统中国社会中乡治的“施善与教化”,然而他遗言说“孝友”,且必“正其衣冠端坐”,又有如朱子、曾子临终时道德性的身心姿态。可见清朝在台湾乡社的小知识分子之生命格调,已属糅合了儒家和佛教,而根本的伦常实践之核心,则属朱熹式的儒家伦常。再如:“李朝勋,字建初,纬烈子。性孝友,父母兄弟无间言,继母詹氏,养葬尽礼,称声载道。处世善善、恶恶,急公向义;为乡里排难解纷,抑强扶弱。……地方有事,率乡勇保卫,不吝赀财。生平好读书,尤精医术。晚筑家塾,设学田,延师训子孙。岁冬,命考家课,别优劣,赏赉有差。……”从这段记述李朝勋行谊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坚持的是彰善惩恶之德规以及教诲庶民行善避恶,他在宗祠中兴办家学,教族中子弟以儒行。①
再看《淡水厅志》中的记载。有郑崇和者,于竹堑办私家书院以教地方子弟:“晚益好宋儒书,如《性理精义》《朱子遗书》《近思录》诸书,沈潜反复,究极精微。尝示人曰:‘此数书具修齐治平之理,当令子弟于夙兴夜寐时,敬读数行,以洗心涤虑,久之可从此窥见圣贤学源流。’大抵先生之学原本六经,由事以知事;由宋儒书以析理,而其要则归于践履笃实且夫持身之严也;执事之敬也;治家之整肃也;与物之公而恕也;见义之勇于为也;执德信道之耄而不懈也。”①从这则记载中可以看出,郑氏是一位深信朱子儒学的道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依据之而实践者。他在竹堑教授儒子,根本目的是想造就圣贤,而不是用八股文教青年人只知道死盯着场屋僵死之试卷而求取利禄。《厅志》复云:“尝言:‘圣贤之学自主敬始,主敬之道,自克勤小物始。’居常见器物倾侧、几案错列,曰:‘此即不正之端。’必更为整顿,然后即安。……每日读书正襟危坐,如面质圣贤。……家庭肃穆,外言不入,内言不出,自写《朱氏家训》一篇,悬于中堂曰:‘正家之道,略尽此篇,朝夕晤对,开人心目,他佳图画,无以易此。’……次君用锡以名进士掌教书院,生徒林立,先生严诲之……谓:‘士君子砥行立名,必求居家无愧于乡,在官不负于国,庶几无忝所生。’”②郑崇和虽身为台湾边陲地区的佚名基层知识分子,但是他从朱子学的道德规范修身行事,并非拘泥僵硬的腐儒、朽儒、奴儒,其身心端正严毅与教化民间社会的理念,与我国大陆特别是福建地区的知识分子,没有本质的差别。
到了现当代,特别是1949年以后,有些学者从阶级演变与社会进化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指摘了不少关于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负面因素,并且预示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必将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逐渐衰落消亡。我却认为学者们的这种预测未免过于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当前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两种倾向值得引起注意:一方面,不少地方的家族组织和乡族组织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甚至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在许多传统宗族制度和乡族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又一时未能寻找可以替代的社会组织的乡村里,普遍出现了一种道德混乱以及社会无序的现象。这两种倾向的出现,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宋明以来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长期存在于民间基层社会的文化合理性。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宋明以来中国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这种文化合理性,基本上是在宋代理学家们的倡导下,由民间社会自行施行并得以发展兴盛起来的。国家政府不但始终处于一种被动应付的状态,甚至在不少场合予以禁止和干扰。政府往往从强化专制统治的思维出发,认为民间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发展壮大,很有可能危及政府的社会治理,从而屡屡试图予以控制和限制。尽管如此,在强大的民间社会面前,这种不具有制度化的控制和限制,毕竟无法有效地影响明清时期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发展,明清时期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的兴盛,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宋代“理学”所倡导设计的以宗族制度和乡族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正是由于较少受到专制政府的制度化约束,宋代“理学”的这一部分文化精神,比较正常地延续了下来,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基本认同。虽然到了现当代,有一部分学者从政治学术的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中国的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但是它并没有像被制度化的“节孝”行为那样,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
宋代朱子学、理学演变到近现代,往往被人们讥讽为迂腐不堪、毫无实用的道德标榜,而注重实用的学人们,对于明清以来的所谓“经世致用”之学甚为欣赏。实际上,宋以来中国思想界所出现的“经世致用”之学,说到底仍然是一种形上思维,并没有真正实施的内涵与可能性。倒是宋代朱熹及其他理学家们所提倡的重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计与实践,在近千年的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全面的实施与推广,甚至延伸到海外的华人群体之中。因此,抛开学术与政治上的偏见,如果要在宋以后中国的思想家里寻找真正实施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那么,大概就只能是朱熹等宋儒们的这一主张了。
我们对宋代朱子学及理学的主要内涵及其历史演变历程做一简要叙述之后,或许可以得出以下四点认识:(一)近现代以来偏重于“哲学”化的对于宋代“理学”的分析,往往把宋代以来的“理学”引向“形上思维”的文化精神的层面或意识形态的层面,忽视了宋代“理学”所倡导设计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理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二)宋代“理学”在宋代并没有得到较为广泛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政府的制度化的实践。经历元、明、清时期,以皇权为核心的政府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把宋代“理学”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制度化的实践与推广。在制度化的实践推广过程中,宋代“理学”所拥有的可贵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而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三)被明清时期政府制度化的宋代“理学”的部分内容,尤其是被政府改造过的所谓“气节”观、“节孝”观等,不仅越来越偏离了宋代“理学”的本意,而且也越来越违背了人性的天真自然以及社会的进步,从而导致了近现代人们的诸多反感。与此相对照的是,宋代“理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反而在明清以来的民间社会得到了比较好的实践与传承,成为真正践行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对宋代“理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等视而不见和全盘否定。(四)从上面的三点认识延伸出来,我们或许还可以这样说:从中国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来考察,无论是孔子的儒学,还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以及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在其形成之初,都不乏各自优秀而积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特别是从孔子到朱熹的儒家传统,在其倡导之时,其所包含的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监督意义,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注入了极为宝贵的文化精神内涵。但是,这种文化精神内涵一旦被社会当政者纳入其制度化的轨道,则必然逐渐沦为专制统治的附庸,从而日益显露出保守与阻碍社会进步的性格。相反地,那些没有被专制统治者纳入到政治制度化当中的儒学传统,则有可能长时间地保持其合理的本质,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显示出文化精神的生命力。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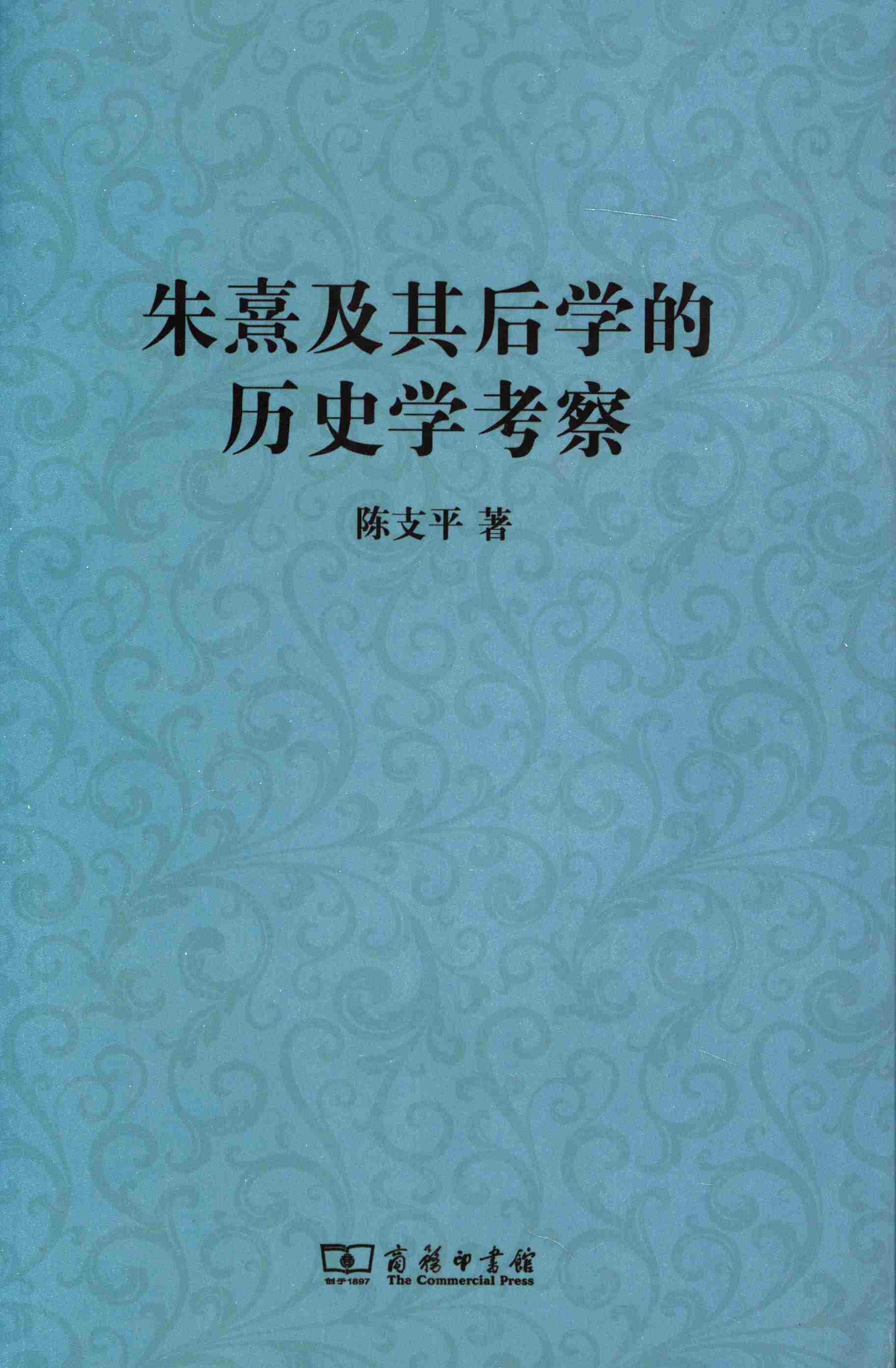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本书主要考察朱熹及其后学们究竟为当时的社会做了些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朱熹和他的学生们,有从政的经历,也有当平民的经历,他们在所谓的“行”的实践上,表现更多。鉴于此,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朱子学,突破了从哲学视角研究朱子学的传统。与从哲学视角注重“想什么”不同,历史学更注重“做什么”。作者以自己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对朱熹及其后学在这两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做出了尝试性的分析。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