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子对明清时期福建书院的影响及其变异
| 内容出处: |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898 |
| 颗粒名称: | 一、朱子对明清时期福建书院的影响及其变异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1 |
| 页码: | 406-41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对明清时期福建书院的影响及其变异的情况。其中包括朱熹对南安诗山书院的影响、朱子对福建书院的影响及其变异举例等。 |
| 关键词: | 朱子 书院 影响 |
内容
(一)朱熹对南安诗山书院的影响
明清时期福建各地成立的书院,几乎没有不受到朱子影响的。举创立于清代末期光绪十六年(1890),因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止科举制度,仅存世15年的福建南安县诗山书院为例。南安诗山书院虽然存世不久,但在其创办初期,首任书院总董、清举人戴凤仪就仿古志书的体例,网罗厘定,编辑刊印了《诗山书院志》十卷。书院志编辑完成之时,敦请时任福建督学使者南海戴鸿慈和泉州府知府番禺金学献撰写序文。戴、金二人在序文中均突出了朱子对书院的重大影响。戴鸿慈在序文中写道:
诗山居南安北隅,为唐欧阳博士生长之区,在宋,朱子尝过化焉。民务耕凿,士勤铅椠。曩者,里人拟成书院而未果。光绪庚寅之岁,戴敬斋中翰慨念前绪,力任其艰,与二三同志为之置学舍,购书田,筹廪膳,逾年而阙事成。由是丹青奂轮,巾卷匝序,岁科两试,游庠食饩者多出其间,盖彬彬乎有俎豆衣冠之盛矣。爰仿古志书之例,网罗厘定,自《形胜》迄《艺文》,都为十卷,以永其传。而《名训》一编,于朱子教人之法纂辑尤备。欲业其中者服膺至教,相期于明体达用,而无或偭规错矩以入于邪,其励学之意甚厚无穷也。……光绪庚子九月,福建督学使者南海戴鸿慈谨序,黄抟扶谨书。
金学献的序文云:
诗山为闽南胜区,在泉之南安十一都,乃唐博士欧阳四门发祥之地,亦朱子过化之乡也。戴敬斋中翰世居山麓,惩失泉俗骁悍,习于私斗,强渔弱,大陵小,鲜识礼让。而彼都人士去县治丰州书院道里窎远,莫与甄陶,乃倡捐巨资,就山头乡朱子祠拓为诗山书院,并为置书田,罗子史,缮规条。虑久而废弛侵蚀,复为搜志十卷,以谂来者。壬寅冬,余来守清源,中翰袖所辑《诗山书院志》索序,余受而读之。至《名训》一篇,乃知中翰拳拳于先贤先儒修身穷理之学,教人养士之方,志在易俗兴贤,非徒沾沾于科举荣名者。规制完美,体例精详,中翰诚有心世道人哉。特是方今功令岁科乡会,舍制艺而从事策论,兼试西国政教、工艺诸学矣。学问之道,原视风尚为转移,古人读书难,今人读书尤难。不博古无以通今,不达时亦无以应变。然不于修身穷理,端其本,终无以成远到之器,跻君子之林。尤愿主持文教者惩宿弊,励真修,正本澄源,时举《名训》一篇相诏勉。庶多士超然科举之累,乡学得媲三代之隆,士号通儒,民敦善俗,用副中辫绻绻初衷,毋徒以桂杏藻芹,矜育才之盛,夸志乘之光,是则余之所深望也,故乐为之序。光绪壬寅季冬之月,泉州府知府番禺金会学献顿首拜序,壬寅补科举人晋江黄鹤顿首拜书。
这两篇序文都强调了书院传承朱子的重要性。所谓志者史也,无论是地方志书,还是书院庙宇志书,一般而言,都是记录该地方或该书院庙宇的以往事迹。但是南安《诗山书院志》则有所不同,与其说它是记录书院的史迹,倒不如说是制定日后书院遵循的规制更为切合事实。而在这新制定的书院规制中,朱子理所当然地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如在卷首中,收入三幅哲人的画像,其中两幅是朱子的,即“朱子遗像附朱子自题铭语”和“朱子后像附诸贤赞语”,另外一幅画像是唐代泉州的名人欧阳詹。在卷二《列传》中,《朱子列传》同样放在首位,达15000余字,是全书字数的十分之一。在卷六的《祀典》中,一共有三祭文:祭朱子文、祭欧阳先生文、祭关帝暨开闽王后土神文。在卷八的《名训》中,共列有十五条名训,其中十三条是朱子的,其他两条是欧阳詹的《暗室箴》和《陶器铭》。在这十五条名训中,《朱子小学题辞》被置于首篇。《诗山书院志》戴凤仪在《朱子小学题辞》末尾写道:
仪按:朱子《小学》一书,示人以读书阶梯、做人模样,实与《鲁论·弟子章》相发明。学者非将此全书熟读体认,则无以收放心、养德性,而正一生之学术。是《小学》者,《大学》之基址,即正学之权舆也。……可知训蒙之法,必先从事于《小学》,以清其源,使浊流不得而混。然后《四书》《六经》《近思录》之精奥可渐次而通,善人、君子、圣人之堂室可渐次而入。许鲁斋所以终身敬之如神明也。但其书分内、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欲尽登诸志,每苦繁多。题辞则提纲挈领,体用兼该,叶以韵语,尤便诵读。爰录于《名训》之首,俾学者得因一端而究全书云。①
戴凤仪在引述了朱子十三条之后,再次强调朱子道德文章的重要性,所谓“考考亭著作浩多,如集注、或问、易本义、近思录、文集、语类诸书,均足开万古之群蒙。兹录十数篇,仅堂室之一隅耳。然学者奉是而讲明之,践履之,则升堂入室,无可以此为层阶矣。是所望于有志者”①。
从《诗山书院志》的一系列记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即使是到了清代末期,朱子在福建民间书院中的影响力,也是无可替代的。该书院的各种规制及课本,几乎都是源于朱子的教化理念。我们从清代末期福建南安县诗山书院的这一例子中,足以想象朱子对福建明清时期书院的深刻影响。
(二)朱子对福建书院的影响及其变异举例
福建各地书院之所以推崇朱子,以朱子为楷模榜样,当然是出于朱子的道德文章及其教化,以朱子道德的力量,培育后代,淳化社会。《诗山书院志》对此说得十分明确:
今日庠序之教微矣,圣贤之道熄矣。天地生人,岂无一二魁然特出之材,而科举溺人,自少迄壮,葄史枕经,父师只令其猎辞章,袭声调,以为弋取料名利禄计,无复有道德仁义之规。又际此海氛不靖,异教庞杂,濒海士习泯泯棼棼,罔归于正,使不亟诱以先师训语,则士习之愈趋愈下,伊胡底也。诗山文物虽蕃,而志道者鲜,且恐庞杂之教,或渐入而阴贼吾道,用是敬录考亭、四门之名训,以勖多士。由蒙养以至成德,次第犁然。想诸翘秀瓣香先哲,必能希踪先哲,不至囿于浅近,惑于异端,以自阻其极板登峰之路也。②
在前引的泉州府知府番禺金学献所撰写的序文中,同样也有类似批评科举的言论:“先贤先儒修身穷理之学,教人养士之方,志在易俗兴贤,非徒沾沾于科举荣名者。”《诗山书院志》特别提到科举制度对于德道教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因此希望通过朱子榜样的力量,对社会教化与世风有所矫正。然而社会的现实是,“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学子们进入书院,一方面学习先贤的道德文章,修身养性,充实自己的人格;另一方面,进入书院的一部分学子,最终是要走上科举之路的,对于功名仕途的追求同样是他们的最终追求。于是,在社会现实的刺激下,原本较为纯净的书院,也不能不逐渐有了功利的色彩。这体现在书院的设置上,许多书院在后续的建筑中,慢慢地增添了“文昌阁”“魁光阁”“奎光阁”一类祈拜司掌文章功名之神的场所。
位于福州郊区的“龙津书院”,亦称“朱(子)祠”,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由当地士绅董应举、郭心山等董其事。清代同治三年(1864)重修时,增设了“奎阁”,并且制定了奎阁祭典及经费筹集等条例。《龙津书院志》记云:
奎阁二诞定例各七千,取于各渡穙。如有歉数,系理事凑足,先期交当祭预备祭品,数列后。朱子诞,理事于祠租内拨出七千,预备祭品。数列后。……奎阁二诞,(文昌)帝君二月初三,魁星八月十五。朱子二祭仍旧春秋季丁,朱子诞九月十五。……朱祠主道学,奎阁主科名,一切求福禳灾等事,理事饬祠丁严行禁止。……一理事饬祠丁应用草柴安置边间,毋得擅置奎阁、朱祠等处,恐防火烛。一奎阁二诞当祭于酒,半席上每人颁寿桃三只。朱子二丁当祭于酒,半席上每人颁丁饼四只,理事之于朱子诞照奎阁之例。①
在这个“规例”里,书院明确提出了“朱祠主道学,奎阁主科名”的概念。为了保证朱祠和奎阁每年祭典的顺利进行,龙津书院还屡屡贴示谕告,督促应税的船户按期如数交纳祭银,该谕告云:
管理龙津书院事务,为严谕亭头道各船户知悉,吾里龙津书院崇祀先贤,历有年所。经前巡抚部院吕奏拨亭头道渡税银永为春秋祀典,例载先期交里之绅衿办理各祀典在案。本二月初三、八月十五系祠内奎阁神诞,各船户限于本口口日以前,照例于全年上季内应先交一半,交外更剩一半,如数交讫,毋得拖欠误公。如敢任意违延,致误公事,势必行单知会阖里绅衿,禀请地方官严追究治。事为大典攸关,决难从宽姑贷。先此谕知各船户,毋贻后悔。此谕。计开:马尾渡全年十六千,应先、再交八千。馆头渡全年五千,应先、再交二千五百。长乐渡全年一千四百,应先、再交七百。琅琦渡全年一千,应先、再交五百。潭头渡全年四百,应先、再交二百。②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清代后期朱子书院中的奎星崇拜,已经获得了与朱子同等的祭祀资格。或许在书院中读书的学子的潜意识中,奎光阁一类司掌功名利禄的神灵,对于自家的前途可能更为重要与实际。清后期同治十年至十一年间(1871~1872),福建巡抚王凯泰等人在福州原西湖书院旧址新建“致用”讲堂。西湖书院原先亦有“文昌阁”之设,文昌阁前楹联由清状元林枝春撰写,该楹联即道出了学子们的这种心思:“可知星象元司命,岂但文章始点头。”①
福州的鳌峰书院创建于清代前期康熙年间,由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倡导而立。鳌峰书院号称清代福建省的第一书院,其生员遍布闽台各地,科举辈出,许多著名人物如林则徐、梁章钜等,均出自该门下。书院开设之初,专祀朱子等道理先贤。但是到了清代中期的乾隆年间,在这里读书的学子们私下筹款建造了“文昌阁”。《鳌峰书院志》卷二有“文昌阁”条记云:
文昌阁,按阁初名奎光,建自乾隆十七年,尚为士子私祀。至嘉庆六年奉旨直省府州县各建祠崇祀春秋,列入祀典。春祭以二月初三日,秋祭部岁颁行云。②
《鳌峰书院志》的这则记载很值得注意,即清代中期,在书院之旁增设奎光阁、文昌阁一类的神灵,基本上属于学子们的“私祀”。但是到了嘉庆六年(1801)之后,文昌阁、奎光阁之类的祭祀,已经正式被政府列入祀典,成为书院中的“公祭”。这一演变过程,或许与文庙中附祀文昌帝君、魁星一类的规制形成过程,有相互类似与相互影响的因素吧!
终清代之世,朱子书院及其他福建书院中虽然有拜祭文昌帝君、奎星之神的,但是还没有发现把朱子本尊作为功名利禄之神来崇祀的。到了近年,在福建的少数地方,朱子本尊也有逐渐演化为司掌功名利禄之神者。我曾经在福建漳州南靖县从事田野调查时发现,在金山乡鹅髻山鹅仙洞附近有朱子读书处。金山鹅仙洞自然风景区位于国道319线126千米处(距厦门120千米),雨林、峭壁、云海、蝶群是它的四大特色,以奇险峻秀、空灵清幽闻名于世,是闽南著名的风景区之一。风景区里有一座青山,形如金字,奇峰突起千仞,石壁嶙峋险峻,山尖有巨石为鹅冠,因山顶像鹅髻,故名鹅髻仙峰,是南靖八景之首。南宋绍熙年间,朱子任职于漳州,曾经到鹅仙洞游览并讲学,后人为了纪念朱子过化之功,石刻其间,因而留有胜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高考竞争的激烈,有人又在石刻附近盖上小庙一座,里面供奉有三尊神像。居中的神像是朱子,左边比较清秀者,是文昌帝君,右边黝黑者,是奎星。在三尊神像之上,悬挂着一些酬谢的牌匾,酬谢朱子先生及文昌帝君、奎星等保佑某某子弟考上大学、研究生等等。
福建朱子书院及其他书院的这种变异,大概连朱子本人也一定始料不及吧!虽然说初创书院者大多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强调它的社会功能,而非专注于功利性的功名仕途。戴鸿慈在序文中说:“其自一郡一邑以至一乡,皆得踵其制而乐育之,非所以造就乎人材而不以广狭殊者耶!自功利中于人心,士之趋于获捷者众,所习非所用,所教非所求,疲精敝神以祈效乎帖括之一途,其余则竞声律、工楷法,沾沾自喜者皆是也。先王之教士之遗意渐淡焉!而忘所由来,而乘其敝者乃得挟其不经之说,以簧鼓天下,张其焰,足以畔道而离经;充其害,遂至伤风而败俗。议者谓名为储才,而实储不才。至欲举学校之制,荡涤而廓清之,毋亦言之过激而未得其方欤!然则居今日而实事求是,亦惟明其意俾勿漓,整其规俾勿堕而已。”①金学献在序文中也一再批评时风之敝:“学术之弊,莫盛于制科。……降及后世,改设制科取士,后器识而先文艺,忘实践而尚浮辞,利禄中于人心,上以是求,下即以是应,士风日陋,士趣日卑,遂不可问。昔朱文公慨学校之不修、正学之不明,俗士溺于利禄荣名之日深也,喟然曰:‘居今之世,虽宣尼复生,亦不免应举。非科举累人,人累科举耳。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书,据所见为文,得失置之度外,虽日应举而不累。’至哉言乎,可以针俗学之膏肓矣。……乃今者,直省郡县书院如林,选名区,构精舍,庋书籍,置租田,规模固犹是也。而拥皋比者,虚有主讲之名;怀铅椠者,曾无请益之实。惟官师月课竞投尘羹片帙而已。以视郡县诸学虚縻饩廪,师若弟漠不相识,相去几何?且问其所造就者,罔非俗学之士也。所训课者,则仍应举之文也。偶有翘然杰出之士,要不过工诗歌、精六法,旁涉泛鹜,标榜声誉以相高。返诸昔贤构院作人本旨大相刺谬矣!”①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无论是宋代的朱子,还是清代末期的戴鸿慈、金学献等人,对于学子为科举功名所吸引的弊端都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借助书院及前贤的力量和感召力,改变这一状况,使得书院的教育回归到道德教化的根本之上。但是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时至今日,科举制度已经改变为所谓的现代科学教育,但是进入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对于学生们日后的事业依然至关重要。这样一来,作为道德教化的典范朱子,就不能不在某种场合转化为司掌当代高考的命运之神了。这种历史的变异,也许正如朱子自己所说过的那样:“居今之世,虽宣尼复生,亦不免应举(试)。非科举(高考)累人,人累科举(高考)耳。”
在今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原属惠安县北部),有一座东岳庙,是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庙中也供奉有朱熹的神像。东岳庙位于峰尾古城南门外,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占地面积668平方米。该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及清光绪年间两次修缮扩建,“文革”期间遭破坏,1978年由乡贤民众共襄善举修葺一新。
峰尾镇东岳庙供奉朱熹神像,缘于朱熹的学生、当地人刘镜。刘镜又称刘叔光,早年受业于朱熹,由于师生关系,刘镜几度邀请朱熹到峰尾讲学,对峰尾一带的人文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镜的好友张巽字“子文”,又字“深道”,早期从学于湖南岳麓书院山长、城南书院创办人张栻。张巽学归惠邑后,恳求好友刘镜引荐并同往武夷书院拜望,师从朱熹。同期还有晋江文人扬至、扬履正和永春人陈易等也由刘镜举荐师从朱熹,颇得朱子理学真传。尤其是刘镜、张巽两位好友又于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一起在惠安城西山中的“龙津陂之原”——刘镜的“鉴湖别墅”研讨、讲习朱熹之“闽学”,教授生徒,接续儒学道统,吸引了远近不少士子和坊巷士绅。刘镜和张巽二人为传播朱熹理学近乎忘我,当时刘镜不辞劳苦地经常往返于惠邑城西其“鉴湖别墅”和峰尾“尾山埕”故居,在家乡的各祠堂、家塾中点燃炬光,倾尽心力传教“朱子读法”。明清时期,惠安县衙明伦堂后的朱子祠主祀朱熹,配祀刘镜和张巽,每年春、秋仲月丁日享祭。峰尾钟德堂内也一直沿袭敬奉朱熹、刘镜大幅画像,将刘镜列为本宗祠之先贤楷模以崇德报功,显亲荣祖,并激励后昆奋志勉力为家族争光,以此凝聚人心、敦宗睦族。
清代峰尾镇重修东岳庙时,乡民鉴于朱熹在当地的影响力,遂把朱熹和元代峰尾的著名诗人卢琦塑成神像,与文昌帝君等,一并作为该庙的配祀供奉于庙中。从此以后,朱熹逐渐也就演变成为专司功名的神祗。从清代延续至今,在古代科举和如今高考时节,总有许多信众来东岳庙进香祈求朱文公(朱熹)和文昌爷(文昌帝君),望能佑子孙读书上进,一路连科,金榜题名。从古至今已相沿成俗的朱子崇拜,或许就是东岳庙东侧殿奉祀朱熹的价值取向和“邹鲁遗风”文化意蕴的大众化转变的一种趋向吧!民俗化以及朱子崇拜的功利化,同样也是我们今天探讨朱子学历史影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①
明清时期福建各地成立的书院,几乎没有不受到朱子影响的。举创立于清代末期光绪十六年(1890),因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废止科举制度,仅存世15年的福建南安县诗山书院为例。南安诗山书院虽然存世不久,但在其创办初期,首任书院总董、清举人戴凤仪就仿古志书的体例,网罗厘定,编辑刊印了《诗山书院志》十卷。书院志编辑完成之时,敦请时任福建督学使者南海戴鸿慈和泉州府知府番禺金学献撰写序文。戴、金二人在序文中均突出了朱子对书院的重大影响。戴鸿慈在序文中写道:
诗山居南安北隅,为唐欧阳博士生长之区,在宋,朱子尝过化焉。民务耕凿,士勤铅椠。曩者,里人拟成书院而未果。光绪庚寅之岁,戴敬斋中翰慨念前绪,力任其艰,与二三同志为之置学舍,购书田,筹廪膳,逾年而阙事成。由是丹青奂轮,巾卷匝序,岁科两试,游庠食饩者多出其间,盖彬彬乎有俎豆衣冠之盛矣。爰仿古志书之例,网罗厘定,自《形胜》迄《艺文》,都为十卷,以永其传。而《名训》一编,于朱子教人之法纂辑尤备。欲业其中者服膺至教,相期于明体达用,而无或偭规错矩以入于邪,其励学之意甚厚无穷也。……光绪庚子九月,福建督学使者南海戴鸿慈谨序,黄抟扶谨书。
金学献的序文云:
诗山为闽南胜区,在泉之南安十一都,乃唐博士欧阳四门发祥之地,亦朱子过化之乡也。戴敬斋中翰世居山麓,惩失泉俗骁悍,习于私斗,强渔弱,大陵小,鲜识礼让。而彼都人士去县治丰州书院道里窎远,莫与甄陶,乃倡捐巨资,就山头乡朱子祠拓为诗山书院,并为置书田,罗子史,缮规条。虑久而废弛侵蚀,复为搜志十卷,以谂来者。壬寅冬,余来守清源,中翰袖所辑《诗山书院志》索序,余受而读之。至《名训》一篇,乃知中翰拳拳于先贤先儒修身穷理之学,教人养士之方,志在易俗兴贤,非徒沾沾于科举荣名者。规制完美,体例精详,中翰诚有心世道人哉。特是方今功令岁科乡会,舍制艺而从事策论,兼试西国政教、工艺诸学矣。学问之道,原视风尚为转移,古人读书难,今人读书尤难。不博古无以通今,不达时亦无以应变。然不于修身穷理,端其本,终无以成远到之器,跻君子之林。尤愿主持文教者惩宿弊,励真修,正本澄源,时举《名训》一篇相诏勉。庶多士超然科举之累,乡学得媲三代之隆,士号通儒,民敦善俗,用副中辫绻绻初衷,毋徒以桂杏藻芹,矜育才之盛,夸志乘之光,是则余之所深望也,故乐为之序。光绪壬寅季冬之月,泉州府知府番禺金会学献顿首拜序,壬寅补科举人晋江黄鹤顿首拜书。
这两篇序文都强调了书院传承朱子的重要性。所谓志者史也,无论是地方志书,还是书院庙宇志书,一般而言,都是记录该地方或该书院庙宇的以往事迹。但是南安《诗山书院志》则有所不同,与其说它是记录书院的史迹,倒不如说是制定日后书院遵循的规制更为切合事实。而在这新制定的书院规制中,朱子理所当然地被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如在卷首中,收入三幅哲人的画像,其中两幅是朱子的,即“朱子遗像附朱子自题铭语”和“朱子后像附诸贤赞语”,另外一幅画像是唐代泉州的名人欧阳詹。在卷二《列传》中,《朱子列传》同样放在首位,达15000余字,是全书字数的十分之一。在卷六的《祀典》中,一共有三祭文:祭朱子文、祭欧阳先生文、祭关帝暨开闽王后土神文。在卷八的《名训》中,共列有十五条名训,其中十三条是朱子的,其他两条是欧阳詹的《暗室箴》和《陶器铭》。在这十五条名训中,《朱子小学题辞》被置于首篇。《诗山书院志》戴凤仪在《朱子小学题辞》末尾写道:
仪按:朱子《小学》一书,示人以读书阶梯、做人模样,实与《鲁论·弟子章》相发明。学者非将此全书熟读体认,则无以收放心、养德性,而正一生之学术。是《小学》者,《大学》之基址,即正学之权舆也。……可知训蒙之法,必先从事于《小学》,以清其源,使浊流不得而混。然后《四书》《六经》《近思录》之精奥可渐次而通,善人、君子、圣人之堂室可渐次而入。许鲁斋所以终身敬之如神明也。但其书分内、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欲尽登诸志,每苦繁多。题辞则提纲挈领,体用兼该,叶以韵语,尤便诵读。爰录于《名训》之首,俾学者得因一端而究全书云。①
戴凤仪在引述了朱子十三条之后,再次强调朱子道德文章的重要性,所谓“考考亭著作浩多,如集注、或问、易本义、近思录、文集、语类诸书,均足开万古之群蒙。兹录十数篇,仅堂室之一隅耳。然学者奉是而讲明之,践履之,则升堂入室,无可以此为层阶矣。是所望于有志者”①。
从《诗山书院志》的一系列记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即使是到了清代末期,朱子在福建民间书院中的影响力,也是无可替代的。该书院的各种规制及课本,几乎都是源于朱子的教化理念。我们从清代末期福建南安县诗山书院的这一例子中,足以想象朱子对福建明清时期书院的深刻影响。
(二)朱子对福建书院的影响及其变异举例
福建各地书院之所以推崇朱子,以朱子为楷模榜样,当然是出于朱子的道德文章及其教化,以朱子道德的力量,培育后代,淳化社会。《诗山书院志》对此说得十分明确:
今日庠序之教微矣,圣贤之道熄矣。天地生人,岂无一二魁然特出之材,而科举溺人,自少迄壮,葄史枕经,父师只令其猎辞章,袭声调,以为弋取料名利禄计,无复有道德仁义之规。又际此海氛不靖,异教庞杂,濒海士习泯泯棼棼,罔归于正,使不亟诱以先师训语,则士习之愈趋愈下,伊胡底也。诗山文物虽蕃,而志道者鲜,且恐庞杂之教,或渐入而阴贼吾道,用是敬录考亭、四门之名训,以勖多士。由蒙养以至成德,次第犁然。想诸翘秀瓣香先哲,必能希踪先哲,不至囿于浅近,惑于异端,以自阻其极板登峰之路也。②
在前引的泉州府知府番禺金学献所撰写的序文中,同样也有类似批评科举的言论:“先贤先儒修身穷理之学,教人养士之方,志在易俗兴贤,非徒沾沾于科举荣名者。”《诗山书院志》特别提到科举制度对于德道教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因此希望通过朱子榜样的力量,对社会教化与世风有所矫正。然而社会的现实是,“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根深蒂固,学子们进入书院,一方面学习先贤的道德文章,修身养性,充实自己的人格;另一方面,进入书院的一部分学子,最终是要走上科举之路的,对于功名仕途的追求同样是他们的最终追求。于是,在社会现实的刺激下,原本较为纯净的书院,也不能不逐渐有了功利的色彩。这体现在书院的设置上,许多书院在后续的建筑中,慢慢地增添了“文昌阁”“魁光阁”“奎光阁”一类祈拜司掌文章功名之神的场所。
位于福州郊区的“龙津书院”,亦称“朱(子)祠”,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由当地士绅董应举、郭心山等董其事。清代同治三年(1864)重修时,增设了“奎阁”,并且制定了奎阁祭典及经费筹集等条例。《龙津书院志》记云:
奎阁二诞定例各七千,取于各渡穙。如有歉数,系理事凑足,先期交当祭预备祭品,数列后。朱子诞,理事于祠租内拨出七千,预备祭品。数列后。……奎阁二诞,(文昌)帝君二月初三,魁星八月十五。朱子二祭仍旧春秋季丁,朱子诞九月十五。……朱祠主道学,奎阁主科名,一切求福禳灾等事,理事饬祠丁严行禁止。……一理事饬祠丁应用草柴安置边间,毋得擅置奎阁、朱祠等处,恐防火烛。一奎阁二诞当祭于酒,半席上每人颁寿桃三只。朱子二丁当祭于酒,半席上每人颁丁饼四只,理事之于朱子诞照奎阁之例。①
在这个“规例”里,书院明确提出了“朱祠主道学,奎阁主科名”的概念。为了保证朱祠和奎阁每年祭典的顺利进行,龙津书院还屡屡贴示谕告,督促应税的船户按期如数交纳祭银,该谕告云:
管理龙津书院事务,为严谕亭头道各船户知悉,吾里龙津书院崇祀先贤,历有年所。经前巡抚部院吕奏拨亭头道渡税银永为春秋祀典,例载先期交里之绅衿办理各祀典在案。本二月初三、八月十五系祠内奎阁神诞,各船户限于本口口日以前,照例于全年上季内应先交一半,交外更剩一半,如数交讫,毋得拖欠误公。如敢任意违延,致误公事,势必行单知会阖里绅衿,禀请地方官严追究治。事为大典攸关,决难从宽姑贷。先此谕知各船户,毋贻后悔。此谕。计开:马尾渡全年十六千,应先、再交八千。馆头渡全年五千,应先、再交二千五百。长乐渡全年一千四百,应先、再交七百。琅琦渡全年一千,应先、再交五百。潭头渡全年四百,应先、再交二百。②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清代后期朱子书院中的奎星崇拜,已经获得了与朱子同等的祭祀资格。或许在书院中读书的学子的潜意识中,奎光阁一类司掌功名利禄的神灵,对于自家的前途可能更为重要与实际。清后期同治十年至十一年间(1871~1872),福建巡抚王凯泰等人在福州原西湖书院旧址新建“致用”讲堂。西湖书院原先亦有“文昌阁”之设,文昌阁前楹联由清状元林枝春撰写,该楹联即道出了学子们的这种心思:“可知星象元司命,岂但文章始点头。”①
福州的鳌峰书院创建于清代前期康熙年间,由时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倡导而立。鳌峰书院号称清代福建省的第一书院,其生员遍布闽台各地,科举辈出,许多著名人物如林则徐、梁章钜等,均出自该门下。书院开设之初,专祀朱子等道理先贤。但是到了清代中期的乾隆年间,在这里读书的学子们私下筹款建造了“文昌阁”。《鳌峰书院志》卷二有“文昌阁”条记云:
文昌阁,按阁初名奎光,建自乾隆十七年,尚为士子私祀。至嘉庆六年奉旨直省府州县各建祠崇祀春秋,列入祀典。春祭以二月初三日,秋祭部岁颁行云。②
《鳌峰书院志》的这则记载很值得注意,即清代中期,在书院之旁增设奎光阁、文昌阁一类的神灵,基本上属于学子们的“私祀”。但是到了嘉庆六年(1801)之后,文昌阁、奎光阁之类的祭祀,已经正式被政府列入祀典,成为书院中的“公祭”。这一演变过程,或许与文庙中附祀文昌帝君、魁星一类的规制形成过程,有相互类似与相互影响的因素吧!
终清代之世,朱子书院及其他福建书院中虽然有拜祭文昌帝君、奎星之神的,但是还没有发现把朱子本尊作为功名利禄之神来崇祀的。到了近年,在福建的少数地方,朱子本尊也有逐渐演化为司掌功名利禄之神者。我曾经在福建漳州南靖县从事田野调查时发现,在金山乡鹅髻山鹅仙洞附近有朱子读书处。金山鹅仙洞自然风景区位于国道319线126千米处(距厦门120千米),雨林、峭壁、云海、蝶群是它的四大特色,以奇险峻秀、空灵清幽闻名于世,是闽南著名的风景区之一。风景区里有一座青山,形如金字,奇峰突起千仞,石壁嶙峋险峻,山尖有巨石为鹅冠,因山顶像鹅髻,故名鹅髻仙峰,是南靖八景之首。南宋绍熙年间,朱子任职于漳州,曾经到鹅仙洞游览并讲学,后人为了纪念朱子过化之功,石刻其间,因而留有胜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高考竞争的激烈,有人又在石刻附近盖上小庙一座,里面供奉有三尊神像。居中的神像是朱子,左边比较清秀者,是文昌帝君,右边黝黑者,是奎星。在三尊神像之上,悬挂着一些酬谢的牌匾,酬谢朱子先生及文昌帝君、奎星等保佑某某子弟考上大学、研究生等等。
福建朱子书院及其他书院的这种变异,大概连朱子本人也一定始料不及吧!虽然说初创书院者大多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强调它的社会功能,而非专注于功利性的功名仕途。戴鸿慈在序文中说:“其自一郡一邑以至一乡,皆得踵其制而乐育之,非所以造就乎人材而不以广狭殊者耶!自功利中于人心,士之趋于获捷者众,所习非所用,所教非所求,疲精敝神以祈效乎帖括之一途,其余则竞声律、工楷法,沾沾自喜者皆是也。先王之教士之遗意渐淡焉!而忘所由来,而乘其敝者乃得挟其不经之说,以簧鼓天下,张其焰,足以畔道而离经;充其害,遂至伤风而败俗。议者谓名为储才,而实储不才。至欲举学校之制,荡涤而廓清之,毋亦言之过激而未得其方欤!然则居今日而实事求是,亦惟明其意俾勿漓,整其规俾勿堕而已。”①金学献在序文中也一再批评时风之敝:“学术之弊,莫盛于制科。……降及后世,改设制科取士,后器识而先文艺,忘实践而尚浮辞,利禄中于人心,上以是求,下即以是应,士风日陋,士趣日卑,遂不可问。昔朱文公慨学校之不修、正学之不明,俗士溺于利禄荣名之日深也,喟然曰:‘居今之世,虽宣尼复生,亦不免应举。非科举累人,人累科举耳。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书,据所见为文,得失置之度外,虽日应举而不累。’至哉言乎,可以针俗学之膏肓矣。……乃今者,直省郡县书院如林,选名区,构精舍,庋书籍,置租田,规模固犹是也。而拥皋比者,虚有主讲之名;怀铅椠者,曾无请益之实。惟官师月课竞投尘羹片帙而已。以视郡县诸学虚縻饩廪,师若弟漠不相识,相去几何?且问其所造就者,罔非俗学之士也。所训课者,则仍应举之文也。偶有翘然杰出之士,要不过工诗歌、精六法,旁涉泛鹜,标榜声誉以相高。返诸昔贤构院作人本旨大相刺谬矣!”①
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无论是宋代的朱子,还是清代末期的戴鸿慈、金学献等人,对于学子为科举功名所吸引的弊端都是十分清楚的,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借助书院及前贤的力量和感召力,改变这一状况,使得书院的教育回归到道德教化的根本之上。但是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时至今日,科举制度已经改变为所谓的现代科学教育,但是进入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对于学生们日后的事业依然至关重要。这样一来,作为道德教化的典范朱子,就不能不在某种场合转化为司掌当代高考的命运之神了。这种历史的变异,也许正如朱子自己所说过的那样:“居今之世,虽宣尼复生,亦不免应举(试)。非科举(高考)累人,人累科举(高考)耳。”
在今泉州市泉港区峰尾镇(原属惠安县北部),有一座东岳庙,是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庙中也供奉有朱熹的神像。东岳庙位于峰尾古城南门外,坐北朝南,主体建筑占地面积668平方米。该庙始建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及清光绪年间两次修缮扩建,“文革”期间遭破坏,1978年由乡贤民众共襄善举修葺一新。
峰尾镇东岳庙供奉朱熹神像,缘于朱熹的学生、当地人刘镜。刘镜又称刘叔光,早年受业于朱熹,由于师生关系,刘镜几度邀请朱熹到峰尾讲学,对峰尾一带的人文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刘镜的好友张巽字“子文”,又字“深道”,早期从学于湖南岳麓书院山长、城南书院创办人张栻。张巽学归惠邑后,恳求好友刘镜引荐并同往武夷书院拜望,师从朱熹。同期还有晋江文人扬至、扬履正和永春人陈易等也由刘镜举荐师从朱熹,颇得朱子理学真传。尤其是刘镜、张巽两位好友又于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一起在惠安城西山中的“龙津陂之原”——刘镜的“鉴湖别墅”研讨、讲习朱熹之“闽学”,教授生徒,接续儒学道统,吸引了远近不少士子和坊巷士绅。刘镜和张巽二人为传播朱熹理学近乎忘我,当时刘镜不辞劳苦地经常往返于惠邑城西其“鉴湖别墅”和峰尾“尾山埕”故居,在家乡的各祠堂、家塾中点燃炬光,倾尽心力传教“朱子读法”。明清时期,惠安县衙明伦堂后的朱子祠主祀朱熹,配祀刘镜和张巽,每年春、秋仲月丁日享祭。峰尾钟德堂内也一直沿袭敬奉朱熹、刘镜大幅画像,将刘镜列为本宗祠之先贤楷模以崇德报功,显亲荣祖,并激励后昆奋志勉力为家族争光,以此凝聚人心、敦宗睦族。
清代峰尾镇重修东岳庙时,乡民鉴于朱熹在当地的影响力,遂把朱熹和元代峰尾的著名诗人卢琦塑成神像,与文昌帝君等,一并作为该庙的配祀供奉于庙中。从此以后,朱熹逐渐也就演变成为专司功名的神祗。从清代延续至今,在古代科举和如今高考时节,总有许多信众来东岳庙进香祈求朱文公(朱熹)和文昌爷(文昌帝君),望能佑子孙读书上进,一路连科,金榜题名。从古至今已相沿成俗的朱子崇拜,或许就是东岳庙东侧殿奉祀朱熹的价值取向和“邹鲁遗风”文化意蕴的大众化转变的一种趋向吧!民俗化以及朱子崇拜的功利化,同样也是我们今天探讨朱子学历史影响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①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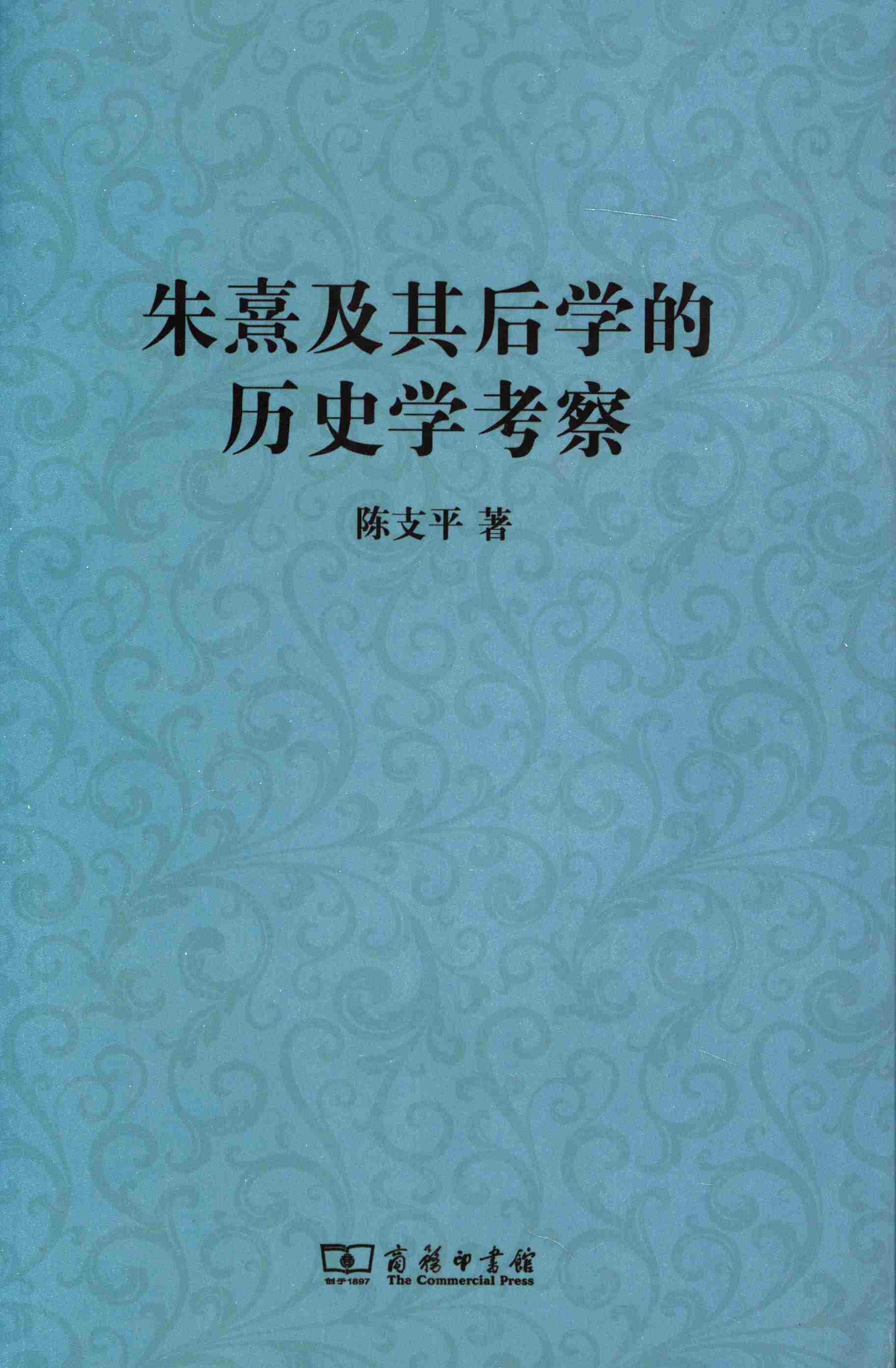
《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
本书主要考察朱熹及其后学们究竟为当时的社会做了些什么,以及这些事情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朱熹和他的学生们,有从政的经历,也有当平民的经历,他们在所谓的“行”的实践上,表现更多。鉴于此,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考察朱子学,突破了从哲学视角研究朱子学的传统。与从哲学视角注重“想什么”不同,历史学更注重“做什么”。作者以自己所擅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对朱熹及其后学在这两个领域的所作所为,做出了尝试性的分析。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