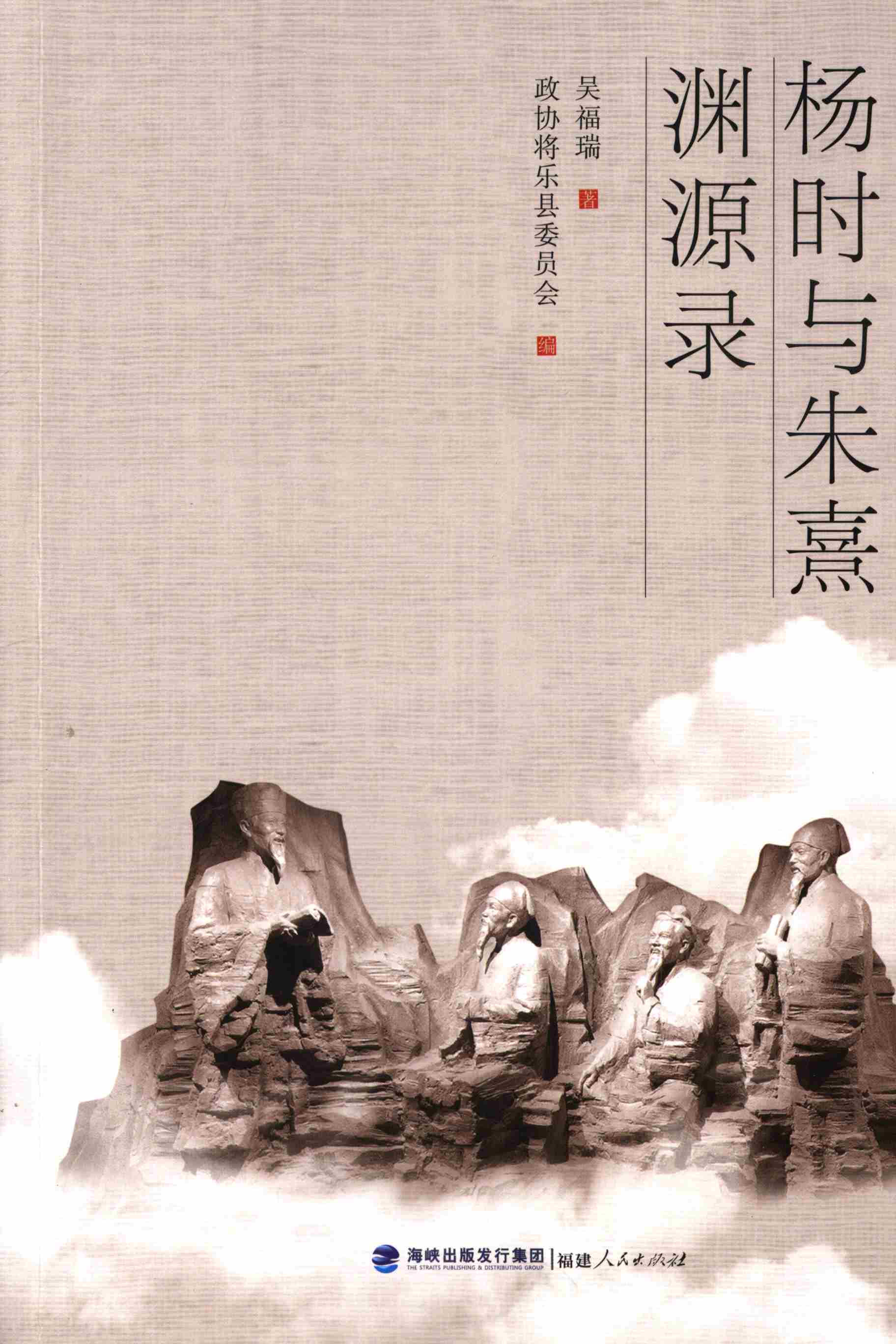(六)朱熹有关杨时的其他评论
| 内容出处: | 《杨时与朱熹渊源录》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710 |
| 颗粒名称: | (六)朱熹有关杨时的其他评论 |
| 分类号: | B244. 75 |
| 页数: | 13 |
| 页码: | 094-10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在其学术研究中吸收了杨时的成果,但并非全盘照搬,他在继承和发展杨时的道学观点时展示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朱熹通过评论、赞扬、肯定和质疑等方式对杨时的观点进行了综合评价。在《朱子语类》中的各篇章,朱熹赞赏了杨时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
| 关键词: | 朱熹 杨时 评论 |
内容
朱熹吸收了杨时的学术研究成果,并集诸儒之大成,创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但却没有因杨时是“道南”祖师、“程氏正宗”而全盘照搬,在继承和发展杨时所倡导的道学过程中,朱熹对杨时的观点是该赞扬的赞扬,该肯定的肯定,该质疑的质疑,该批评的批评,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如《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学而篇》:
问《道千乘之国》章。曰:“龟山说此处,极好看。今若治国不本此五者,则君臣上下漠然无干涉,何以为国!”又问:“须是先有此五者,方可议及礼乐刑政。”曰:“且要就此五者,反复推寻,看古人治国之势要。此五者极好看,若每章翻来复去,看得分明,若看十章,敢道便有长进!”
又《论语·学而篇》:
文振说“道千乘之国”,曰:“龟山最说得好,须看此五者是要紧。古圣王所以必如此者,盖有是五者,而后上之意接于下,下之情高始得亲于上。上下相关,方可以为治。若无此五者,则君抗然于上,而民盖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朱子语类》卷三十八《论语·乡党篇》:
问:“‘康子馈药,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见圣人应接之间,义理发见,极其周密。”曰:“这般所在,却是龟山看得子细,云:‘大夫有赐,拜而受之,礼也;未达不敢尝,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礼,故其直不绞。’龟山为人粘泥,故说之较密。”
《朱子语类》卷四十二:
问:“杨氏谓:‘欲民之不为盗,在不欲而已。’横渠谓:‘欲生于不足,则民盗。能使无欲,则民自不为盗。假设以子不欲之物,赏子使窃,子必不窃。故为政在乎足民,使无所欲而已。’如横渠说,则是当面以季康子比盗矣。孔子于季康子虽不纯于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圣人气象,恐不若是。如杨氏之说,只是责季康子之贪,然气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厉。今欲且从杨说,如何?”曰:“善。”
《朱子语类》卷五十三《孟子·公孙丑上》:
龟山答人问赤子入井,令求所以然一段,好。
《朱子语类》卷六十四《易一》:
龟山过黄亭詹季鲁家。季鲁问《易》。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圆圈,用墨涂其中,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
用龟山《易》参看《易传》数段,见其大小得失。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程子门人·总论》:
伊川之门,谢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着。张思叔最后进,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门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杨龟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程子门人·杨中立》:
龟山天资高,朴实简易;然所见一定,更不须穷究。某尝谓这般人,皆是天资出人,非假学力。如龟山极是简易,衣服也只据见定。终日坐在门垠上,人犯之亦不较。其简率皆如此。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程子门人·杨中立》:
龟山与范济美言:“学者须当以求仁为要。求仁,则‘刚、毅、木、讷近仁’,一言为要。”先生曰:“今之学者,亦不消专以求仁为念;相将只去看说仁处,他处尽遗了。须要将一部《论语》,粗粗细细,一齐理会去,自然有贯通处,却会得仁,方好。又,今人说曾子只是以鲁得之,盖曾子是资质省力易学。设使如今人之鲁,也不济事。范济美博学高才,俊甚,故龟山只引‘刚、毅、木、讷’告之,非定理也。”
《朱子语类》卷一〇二《杨氏门人·廖用中》:
龟山与廖尚书说以义利事。廖云:“义利即是天理人欲。”龟山曰:“只怕贤错认,以利为义也。”后来被召主和议,果如龟山说。……因言廖用中议和事,云:“廖用中固非诡随者,但见道理不曾分晓。”当时龟山已尝有语云“恐子以利为义”者,政为是也。
尤其是在当时许多人对杨时晚年由蔡京之子荐于朝和批判王安石之事不理解时,朱熹能站在公正的立场,极力为杨时辩护,并充分肯定他的道德品质和在朝中所发挥的作用。
如《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程子门人·杨中立》:
蔡京在政府,问人材于其族子蔡子应,(端明之孙)以张柔直对。张时在部注拟,京令子应招之,授之门馆。张至,以师礼自尊,京之弟子怪之。一日,张教京家弟子习走。其子弟云:“从来先生教某们慢行,今令行走,何也?”张云:“乃公作相久,败坏天下。相次盗起,先杀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脱,何得不习!”家人以为心风,白京。京愀然曰:“此人非病风。”召与语,问所以扶救今日之道及人材可用者。张公遂言龟山杨公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始知有杨先生。
问:“龟山晚岁一出,为士子诟骂,果有之否?”曰:“他当时一出,追夺荆公王爵,罢配享夫子,且欲毁劈《三经》板。士子不乐,遂相与聚问《三经》有何不可,辄欲毁之?当时龟山亦谨避之。”问:“或者疑龟山此出为无补于事,徒尔纷纷。或以为大贤出处不可以此议,如何?”曰:“龟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梦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极好。”
龟山之出,人多议之。惟胡文定之言曰:“当时若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此语最公,盖龟山当此时虽负重名,亦无杀活手段。若谓其怀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谨勿击居安”之语,则诬矣。幸而此言出于孙觌,人自不信。
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笼出来底人才,伯纪(李纲)亦所不免,如李泰发(李光)是甚次硬底人,亦为京所罗致,他可知矣。
坐客问龟山立朝事。曰:“故文定论得好:‘朝廷若委吴元忠辈推行其说,决须救得一半,不至如后来狼狈。’然当时国势已如此,虏初退后,便须急急理会,如救焚拯溺。诸公今日论蔡京,明日论王黼,当时奸党各已行遣了,只管理会不休,担搁了日子。如吴元忠、李伯纪向来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吃人议论。龟山亦被孙觌辈窘扰。”
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龟山墓志》,主张龟山似柳下惠,看来是如此。
孙觌见龟山撰《曾内翰行状》,曰:“杨中立却会做文字。”先生(朱熹)曰:“龟山曾理会文字来。”李先生(李侗)尝云:“人见龟山似不管事,然其晓事也。”
李先生(李侗)言:“龟山对刘器之言,为贫。文定代云竿木云云,不若龟山之逊避也。”
先生(黄干)问:“寻常《精义》,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诸说恐不相上下。”又问蜚卿。答曰:“自二程外,唯龟山胜。”(《朱子语类》卷十九)
又问:“读书宜以何为法?”曰:“须少看。凡读书须子细研读讲究,不可放过。……昔五峰于京师问龟山读书法,龟山云:‘先读《论语》。’五峰问:‘《论语》二十篇,以何为紧要?’龟山曰:‘事事紧要。’看此可见。”(《朱子语类》卷一一八)
在肯定龟山的同时,朱熹对其不足之处,也能大胆指出。如对于杨时讲格物在于“反身而诚”,朱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朱子语类》卷十八中,他明确指出:“龟山说‘反身而诚’,却大段好。须是反身,乃见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须见得孝弟,我元有在这里。若能反身,争多少事。”而对于杨时所认为的“万物皆备于我,不须外面求”,朱熹则指出“此却错了”,“若果如此,则圣贤都易做了”。因为不是所有事物的原理在人身上都可找到,还必须到外面去探求。他说:“近世如龟山之论,便是如此,以为反身而诚,则天下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如何会反身而诚了,天下万物之理便自然备于我?成个什么?”(《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他还说:“反身而诚,乃为物格知至以后之事,言其穷理之至,无所不尽,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诸身,皆有以见,其如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之毕具于此,而无毫发之不实耳。固非以是方为格物之事,亦不谓但务反求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无不诚也。”“杨氏反身之说为未安耳,盖反身而诚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未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如前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无内外、隐显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真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四书或问》“龟山于天下事极明得,如言治道与官府政事,至纤至细处,亦晓得,到这里却恁说,次第他把来做两截看了。”(《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
对于杨时的“于静中体认大本”的为学与养心之方,朱熹既肯定了他读书的一面,也认为这是“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对其门人有深远的影响。当朱熹门人问:“龟山之学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侗)学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朱熹则答曰:“龟山只是要闲散,然却读书,尹和靖便不读书。”他还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并发出“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之叹。但朱熹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后,对杨时这种“默坐澄心”的“体验未发”之法大胆地进行了质疑。他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天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许有什么物事。某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他还说:“龟山所谓‘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已发之际能得所谓和’,此语为近之,然未免有病。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遂成嗟过,孤负此翁耳。”
《朱子语类》中还有不少朱子对龟山先生的评价:
杨氏以义利为君子、小人之别,其说皆通。而于深浅之间,似不可不别。窃谓小人之得名有三,而为人,为利,徇外务末,其过亦有浅深。
问:“《横浦语录》载张子韶戒杀,不食蟹。高抑崇相对,故食之。龟山云:‘子韶不杀,抑崇故杀,不可。’抑崇退,龟山问子韶:‘周公何如人?’对曰:‘仁人。’曰:‘周公驱猛兽,兼夷狄,灭国者五十,何尝不杀?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见其非不杀耳,犹有未尽。须知上古圣人制为罔罟佃渔,食禽兽之肉。但‘君子远庖厨’,不暴殄天物。须如此说,方切事物。”
李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亦尝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
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如谢上蔡之说如彼,杨龟山之说如此,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所以为得者是如何?所以为失者是如何?
《龟山集》中有《政日录》数段,却好。盖龟山长于攻王氏。然《三经义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当辨而不曾辨者。
杨时的“中庸”说是朱熹诠释《中庸》的重要思想渊源。如龟山称《中庸》首章为“一篇之体要”,被朱熹引入《中庸章句》中;朱熹还称“龟山杨子‘天命之谓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语直截”。“龟山‘人欲非性’之说自好”。对《中庸》首章“修道之谓教”的解释,朱熹也认为“游、杨说好,谓修者只是品节之也”。对第六章“执其两端”的解释,朱熹则认为“两端之说,吕、杨为优”。对第二十六章“至诚无息”的解释,朱熹也认为“杨氏动以天,故无息之语,甚善!”
但是,朱熹对杨时的《中庸》说总体评价却不甚高。在弟子问及程门游酢、杨时、吕(大临)、侯(师圣)四家的《中庸》说孰优时,朱熹回答说:
此非后学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论之,则于吕称其深潜缜密;于游称其颖悟温厚;谓杨不及游,而亦每称其颖悟;谓侯氏之言,但可隔壁听。今且熟复其言,究核其意,而以此语证之,则其高下浅深亦可见矣。过此以往,则非后学所敢言也。(《四书或问》)
朱熹在此虽然说“此非后学所敢言也”,但是,他还是借“程子之言论”,给诸子排定了座次,即吕、游、杨、侯。此外,朱熹在其他场合和文章中,也多次对杨时的《中庸》说提出了批评,如:
李先生说:“陈几叟辈皆以杨氏《中庸》不如吕氏。”先生曰:“吕氏饱满充实。”
龟山的人自言龟山《中庸》枯燥,不如与叔(吕大临)浃洽。先生曰:“与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远。”
游、杨诸公解《中庸》,引书语皆失本意。
又曰:“《大学》所以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以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所以只说格物。‘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所谓道者是如此,何尝说物便是则。龟山便指那物做则,只是就这物上分精粗为物则。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视乃则也;耳物也,耳之听乃则也。殊不知目视而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龟山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乐在是’(以上皆出自《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如此,则世间伊尹多矣!龟山说话,大概有此病。”
龟山《中庸》有可疑处,如论“《中庸》不可能”“不可以为道”,“鬼神之为德等章,实有病”。
朱熹对程门诸子在注解《中庸》的过程中“颇详尽而多所发明”有所赞扬,但对他们“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尖锐的批评,其中也包含龟山在内。如《朱子语类》所载:
伊川之门,谢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着。张思叔最后进,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门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杨龟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见一截,少下面着实工夫,故流弊至此。
一日,论伊川门人,云:“多流入于释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龟山辈不如此。”曰:“只《论语序》,便可见。”
程门诸子,在当时亲见二程,至于释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晓。观《中庸说》可见。如龟山云:“吾儒与释氏,其差只在眇忽之间。”其谓何止眇忽?直是从源头便不同。
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龟山云:“儒、释之辩,其差眇忽。以某观之,真似冰炭。”
龟山张皇佛氏之势,亦如李邺张皇金虏也。
此外,对于杨时的一些其他不足之处,朱熹也坦率地提出了批评:
龟山解文字著述,无纲要。
龟山文字议论,如手捉一物正紧,忽坠地,此由其气弱。
龟山言:“天命之谓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无人欲,不必如此立说。《知言》云:“天理人欲,同体而异同,同行而异情。”自是它全看错了。
尽管朱熹对杨时的某些理学思想曾提出过一些批评,但无妨于他在编注《四书章句集注》《论孟精义》过程中汲取和采纳许多杨时的观点,无妨于他对杨时的高度赞扬,无妨于他对自己是龟山“门下生”的认定。他曾在龟山先生遗像上题曰:“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门下生朱熹拜赠。”
朱熹还为杨时画像题赞曰:
大学失绪,病在人心。昔子与子,闲卫圣真。
推彼厥功,以“亚圣”称。适至我翁,继统而兴。
理阐“性命”,学悟“执中”。天开长夜,人坐春风。
值彼荆国,籍倡《新经》。诋非先哲,聋聩蒸民。
士趋蹊径,性散本真。“精一”之旨,眩惑弥深。
惟微脉绝,时事孔殷。翁独毅然,距闢诐淫。
力黜其配,理毁其经。人心斯正,吾道日星。
功符孟氏,德续先声。
宋隆兴元年(1163)李侗逝世,次年朱熹返回福建,写了《祭李延平先生文》:
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
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
唯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
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惟道是资。
精义造约,穷深极微。冻解冰释,发于天机。
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风霆之变,日月之光。
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伦之正,王道之中。
一以贯之,其外无馀。缕析毫差,其分则殊。
体用混元,隐显昭融。万变并酬,浮云太空。
仁孝友弟,洒落诚明。清通和乐,展也大成。
婆娑坵林,世莫我知。优哉游哉,卒岁以嬉。
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来抠衣,发其蔽昏。
侯伯闻风,拥彗以迎。大本大经,是度是程。
税驾云初,讲义有端。疾病乘之,医穷技殚。
呜呼先生,而止于斯。命之不融,谁实尸之。
合散屈伸,消息满虚。廓然大公,与化为徒。
古今一息,曷计短长。物我一身,孰为穷通。
嗟嗟圣学,不绝如线。先生得之,既厚以全。
进未获施,退未及传。殉身以歿,孰云非天。
熹也小生,卯角趋拜。恭惟先生,实共源派。
訚訚侃侃,敛衽推先。冰壶秋月,谓公则然。
施及后人,敢渝斯志。从游十年,诱掖谆至。
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瑾,无幽不穷。
相期日深,见励弥切。蹇步方休,鞭绳已掣。
安车署行,过我衡门。返饰相遭,凉秋已分。
熹于此时,适有命召。问所宜言,反覆教诏。
最后有言,吾子勉之。凡兹众理,子所自知。
奉以周旋,幸不失坠。归装朝严,讣音夕至。
失声长号,泪落悬泉。何意斯言,而诀终天。
病不举扶,没不饭含。奔走后人,死有馀憾。
仪形永隔,卒业无期。坠绪茫茫,孰知我悲。
伏哭柩前,奉奠以贽。不亡者存,鉴此诚意。
又山颓梁坏,岁月不留。即远有期,亲宾毕会。
柳车既饬,薤露怀悲。生荣死哀,孰不推慕。
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学未传心,言徒在耳。
载瞻穗綍,弥切悲伤。筑室三年,莫酬夙志。
举觞一恸,永诀终天。呜呼哀哉!
这篇祭文说自孟子之后,儒学道统已经失传了千年以上,直到二程出现才得以延续。杨时立雪程门,师事二程,尽得二程不传之秘,倡道东南,将道统传给了罗从彦,罗从彦又传给了李侗。而自己有幸师事李侗,成为千古以来道统的正宗传承者,并以此为自豪。文中提到“实共源派”,指的就是朱熹与其师李侗共出于杨时所传的伊洛正宗。
《宋史·道学列传》称:“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朱熹的门人及孙婿赵师夏也在《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答问跋》中称:“延平李先生之学,得之仲素罗先生;罗先生之学,得之龟山杨先生。龟山盖伊洛之高弟也……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仕,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今文公先生之言布满天下,光明俊伟”,是“实延平先生一言之绪也”。
关于杨时与朱熹的渊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蔡尚思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蔡尚思先生在《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杨时是理学南传与闽学的祖师》一文中说道:
无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学术史上、思想史上、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都居于主要位置的是宋代理学,宋代理学中最重要的是闽学一派,闽学一派中最重要的是朱熹。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杨时是中国理学由北传南的关键人物,所以被称为闽学创始人。闽学的祖师是杨时而不是朱熹,朱熹是闽派,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没有杨时把理学传入闽北,也不可能造就朱熹。
为此,他赋诗赞曰:
鲁南有孔孟,闽北出杨朱。
古代人文上,均成为楷模。
如《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学而篇》:
问《道千乘之国》章。曰:“龟山说此处,极好看。今若治国不本此五者,则君臣上下漠然无干涉,何以为国!”又问:“须是先有此五者,方可议及礼乐刑政。”曰:“且要就此五者,反复推寻,看古人治国之势要。此五者极好看,若每章翻来复去,看得分明,若看十章,敢道便有长进!”
又《论语·学而篇》:
文振说“道千乘之国”,曰:“龟山最说得好,须看此五者是要紧。古圣王所以必如此者,盖有是五者,而后上之意接于下,下之情高始得亲于上。上下相关,方可以为治。若无此五者,则君抗然于上,而民盖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朱子语类》卷三十八《论语·乡党篇》:
问:“‘康子馈药,拜而受之’,看此一事,见圣人应接之间,义理发见,极其周密。”曰:“这般所在,却是龟山看得子细,云:‘大夫有赐,拜而受之,礼也;未达不敢尝,所以慎疾;必告之,直也。直而有礼,故其直不绞。’龟山为人粘泥,故说之较密。”
《朱子语类》卷四十二:
问:“杨氏谓:‘欲民之不为盗,在不欲而已。’横渠谓:‘欲生于不足,则民盗。能使无欲,则民自不为盗。假设以子不欲之物,赏子使窃,子必不窃。故为政在乎足民,使无所欲而已。’如横渠说,则是当面以季康子比盗矣。孔子于季康子虽不纯于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圣人气象,恐不若是。如杨氏之说,只是责季康子之贪,然气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厉。今欲且从杨说,如何?”曰:“善。”
《朱子语类》卷五十三《孟子·公孙丑上》:
龟山答人问赤子入井,令求所以然一段,好。
《朱子语类》卷六十四《易一》:
龟山过黄亭詹季鲁家。季鲁问《易》。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圆圈,用墨涂其中,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
《朱子语类》卷六十七《易三》:
用龟山《易》参看《易传》数段,见其大小得失。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程子门人·总论》:
伊川之门,谢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着。张思叔最后进,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门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杨龟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程子门人·杨中立》:
龟山天资高,朴实简易;然所见一定,更不须穷究。某尝谓这般人,皆是天资出人,非假学力。如龟山极是简易,衣服也只据见定。终日坐在门垠上,人犯之亦不较。其简率皆如此。
《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程子门人·杨中立》:
龟山与范济美言:“学者须当以求仁为要。求仁,则‘刚、毅、木、讷近仁’,一言为要。”先生曰:“今之学者,亦不消专以求仁为念;相将只去看说仁处,他处尽遗了。须要将一部《论语》,粗粗细细,一齐理会去,自然有贯通处,却会得仁,方好。又,今人说曾子只是以鲁得之,盖曾子是资质省力易学。设使如今人之鲁,也不济事。范济美博学高才,俊甚,故龟山只引‘刚、毅、木、讷’告之,非定理也。”
《朱子语类》卷一〇二《杨氏门人·廖用中》:
龟山与廖尚书说以义利事。廖云:“义利即是天理人欲。”龟山曰:“只怕贤错认,以利为义也。”后来被召主和议,果如龟山说。……因言廖用中议和事,云:“廖用中固非诡随者,但见道理不曾分晓。”当时龟山已尝有语云“恐子以利为义”者,政为是也。
尤其是在当时许多人对杨时晚年由蔡京之子荐于朝和批判王安石之事不理解时,朱熹能站在公正的立场,极力为杨时辩护,并充分肯定他的道德品质和在朝中所发挥的作用。
如《朱子语类》卷一〇一《程子门人·杨中立》:
蔡京在政府,问人材于其族子蔡子应,(端明之孙)以张柔直对。张时在部注拟,京令子应招之,授之门馆。张至,以师礼自尊,京之弟子怪之。一日,张教京家弟子习走。其子弟云:“从来先生教某们慢行,今令行走,何也?”张云:“乃公作相久,败坏天下。相次盗起,先杀汝家人,惟善走者可脱,何得不习!”家人以为心风,白京。京愀然曰:“此人非病风。”召与语,问所以扶救今日之道及人材可用者。张公遂言龟山杨公诸人姓名,自是京父子始知有杨先生。
问:“龟山晚岁一出,为士子诟骂,果有之否?”曰:“他当时一出,追夺荆公王爵,罢配享夫子,且欲毁劈《三经》板。士子不乐,遂相与聚问《三经》有何不可,辄欲毁之?当时龟山亦谨避之。”问:“或者疑龟山此出为无补于事,徒尔纷纷。或以为大贤出处不可以此议,如何?”曰:“龟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后人又何曾梦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极好。”
龟山之出,人多议之。惟胡文定之言曰:“当时若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此语最公,盖龟山当此时虽负重名,亦无杀活手段。若谓其怀蔡氏汲引之恩,力庇其子,至有“谨勿击居安”之语,则诬矣。幸而此言出于孙觌,人自不信。
靖康名流,多是蔡京晚年牢笼出来底人才,伯纪(李纲)亦所不免,如李泰发(李光)是甚次硬底人,亦为京所罗致,他可知矣。
坐客问龟山立朝事。曰:“故文定论得好:‘朝廷若委吴元忠辈推行其说,决须救得一半,不至如后来狼狈。’然当时国势已如此,虏初退后,便须急急理会,如救焚拯溺。诸公今日论蔡京,明日论王黼,当时奸党各已行遣了,只管理会不休,担搁了日子。如吴元忠、李伯纪向来亦是蔡京引用,免不得略遮庇,只管吃人议论。龟山亦被孙觌辈窘扰。”
伯夷微似老子。胡文定作《龟山墓志》,主张龟山似柳下惠,看来是如此。
孙觌见龟山撰《曾内翰行状》,曰:“杨中立却会做文字。”先生(朱熹)曰:“龟山曾理会文字来。”李先生(李侗)尝云:“人见龟山似不管事,然其晓事也。”
李先生(李侗)言:“龟山对刘器之言,为贫。文定代云竿木云云,不若龟山之逊避也。”
先生(黄干)问:“寻常《精义》,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诸说恐不相上下。”又问蜚卿。答曰:“自二程外,唯龟山胜。”(《朱子语类》卷十九)
又问:“读书宜以何为法?”曰:“须少看。凡读书须子细研读讲究,不可放过。……昔五峰于京师问龟山读书法,龟山云:‘先读《论语》。’五峰问:‘《论语》二十篇,以何为紧要?’龟山曰:‘事事紧要。’看此可见。”(《朱子语类》卷一一八)
在肯定龟山的同时,朱熹对其不足之处,也能大胆指出。如对于杨时讲格物在于“反身而诚”,朱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朱子语类》卷十八中,他明确指出:“龟山说‘反身而诚’,却大段好。须是反身,乃见得道理分明。如孝如弟,须见得孝弟,我元有在这里。若能反身,争多少事。”而对于杨时所认为的“万物皆备于我,不须外面求”,朱熹则指出“此却错了”,“若果如此,则圣贤都易做了”。因为不是所有事物的原理在人身上都可找到,还必须到外面去探求。他说:“近世如龟山之论,便是如此,以为反身而诚,则天下万物之理皆备于我,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如何会反身而诚了,天下万物之理便自然备于我?成个什么?”(《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他还说:“反身而诚,乃为物格知至以后之事,言其穷理之至,无所不尽,故凡天下之理,反求诸身,皆有以见,其如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之毕具于此,而无毫发之不实耳。固非以是方为格物之事,亦不谓但务反求诸身,而天下之理,自然无不诚也。”“杨氏反身之说为未安耳,盖反身而诚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未身,则所明之善无不实有。如前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无内外、隐显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则反之而不诚者多矣。安得真谓但能反求诸身则不待求之于外,而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而无不诚哉?况格物之功,正在即事即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离去事物而专务求之于身,尤非《大学》之本意矣。”《四书或问》“龟山于天下事极明得,如言治道与官府政事,至纤至细处,亦晓得,到这里却恁说,次第他把来做两截看了。”(《朱子语类》卷十八《大学》)
对于杨时的“于静中体认大本”的为学与养心之方,朱熹既肯定了他读书的一面,也认为这是“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对其门人有深远的影响。当朱熹门人问:“龟山之学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燕闲静一之中。’李先生(侗)学于龟山,其源流是如此。”朱熹则答曰:“龟山只是要闲散,然却读书,尹和靖便不读书。”他还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并发出“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之叹。但朱熹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后,对杨时这种“默坐澄心”的“体验未发”之法大胆地进行了质疑。他说:“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物事?见人说四方天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许有什么物事。某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是何物。”他还说:“龟山所谓‘未发之际能体所谓中,已发之际能得所谓和’,此语为近之,然未免有病。旧闻李先生论此最详,后来所见不同,遂不复致思……当时既不领略,后来又不深思,遂成嗟过,孤负此翁耳。”
《朱子语类》中还有不少朱子对龟山先生的评价:
杨氏以义利为君子、小人之别,其说皆通。而于深浅之间,似不可不别。窃谓小人之得名有三,而为人,为利,徇外务末,其过亦有浅深。
问:“《横浦语录》载张子韶戒杀,不食蟹。高抑崇相对,故食之。龟山云:‘子韶不杀,抑崇故杀,不可。’抑崇退,龟山问子韶:‘周公何如人?’对曰:‘仁人。’曰:‘周公驱猛兽,兼夷狄,灭国者五十,何尝不杀?亦去不仁以行其仁耳。’”先生曰:“此特见其非不杀耳,犹有未尽。须知上古圣人制为罔罟佃渔,食禽兽之肉。但‘君子远庖厨’,不暴殄天物。须如此说,方切事物。”
李先生居处有常,不作费力事。……亦尝为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居常无甚异同,颓如也。真得龟山法门,亦尝议龟山之失。
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如谢上蔡之说如彼,杨龟山之说如此,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所以为得者是如何?所以为失者是如何?
《龟山集》中有《政日录》数段,却好。盖龟山长于攻王氏。然《三经义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当辨而不曾辨者。
杨时的“中庸”说是朱熹诠释《中庸》的重要思想渊源。如龟山称《中庸》首章为“一篇之体要”,被朱熹引入《中庸章句》中;朱熹还称“龟山杨子‘天命之谓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语直截”。“龟山‘人欲非性’之说自好”。对《中庸》首章“修道之谓教”的解释,朱熹也认为“游、杨说好,谓修者只是品节之也”。对第六章“执其两端”的解释,朱熹则认为“两端之说,吕、杨为优”。对第二十六章“至诚无息”的解释,朱熹也认为“杨氏动以天,故无息之语,甚善!”
但是,朱熹对杨时的《中庸》说总体评价却不甚高。在弟子问及程门游酢、杨时、吕(大临)、侯(师圣)四家的《中庸》说孰优时,朱熹回答说:
此非后学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论之,则于吕称其深潜缜密;于游称其颖悟温厚;谓杨不及游,而亦每称其颖悟;谓侯氏之言,但可隔壁听。今且熟复其言,究核其意,而以此语证之,则其高下浅深亦可见矣。过此以往,则非后学所敢言也。(《四书或问》)
朱熹在此虽然说“此非后学所敢言也”,但是,他还是借“程子之言论”,给诸子排定了座次,即吕、游、杨、侯。此外,朱熹在其他场合和文章中,也多次对杨时的《中庸》说提出了批评,如:
李先生说:“陈几叟辈皆以杨氏《中庸》不如吕氏。”先生曰:“吕氏饱满充实。”
龟山的人自言龟山《中庸》枯燥,不如与叔(吕大临)浃洽。先生曰:“与叔却似行到,他人如登高望远。”
游、杨诸公解《中庸》,引书语皆失本意。
又曰:“《大学》所以说格物,却不说穷理。盖说穷理,则以悬空无捉摸处。只说格物,则只就那形而下之器上,便寻那形而上之道,便见得这个元不相离,所以只说格物。‘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所谓道者是如此,何尝说物便是则。龟山便指那物做则,只是就这物上分精粗为物则。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视乃则也;耳物也,耳之听乃则也。殊不知目视而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龟山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乐在是’(以上皆出自《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如此,则世间伊尹多矣!龟山说话,大概有此病。”
龟山《中庸》有可疑处,如论“《中庸》不可能”“不可以为道”,“鬼神之为德等章,实有病”。
朱熹对程门诸子在注解《中庸》的过程中“颇详尽而多所发明”有所赞扬,但对他们“倍其师说而淫于老佛者”,亦有尖锐的批评,其中也包含龟山在内。如《朱子语类》所载:
伊川之门,谢上蔡自禅门来,其说亦有着。张思叔最后进,然深惜其早世,使天予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门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杨龟山最老,其所得亦深。
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龟山辈,下梢皆入禅学去,必是程先生当初说得高了,他们只见一截,少下面着实工夫,故流弊至此。
一日,论伊川门人,云:“多流入于释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龟山辈不如此。”曰:“只《论语序》,便可见。”
程门诸子,在当时亲见二程,至于释氏,却多看不破,是不可晓。观《中庸说》可见。如龟山云:“吾儒与释氏,其差只在眇忽之间。”其谓何止眇忽?直是从源头便不同。
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氏以神识为不生不灭。龟山云:“儒、释之辩,其差眇忽。以某观之,真似冰炭。”
龟山张皇佛氏之势,亦如李邺张皇金虏也。
此外,对于杨时的一些其他不足之处,朱熹也坦率地提出了批评:
龟山解文字著述,无纲要。
龟山文字议论,如手捉一物正紧,忽坠地,此由其气弱。
龟山言:“天命之谓性,人欲非性也。”天命之善,本是无人欲,不必如此立说。《知言》云:“天理人欲,同体而异同,同行而异情。”自是它全看错了。
尽管朱熹对杨时的某些理学思想曾提出过一些批评,但无妨于他在编注《四书章句集注》《论孟精义》过程中汲取和采纳许多杨时的观点,无妨于他对杨时的高度赞扬,无妨于他对自己是龟山“门下生”的认定。他曾在龟山先生遗像上题曰:“孔颜道脉,程子箴规。先生之德,百世所师。门下生朱熹拜赠。”
朱熹还为杨时画像题赞曰:
大学失绪,病在人心。昔子与子,闲卫圣真。
推彼厥功,以“亚圣”称。适至我翁,继统而兴。
理阐“性命”,学悟“执中”。天开长夜,人坐春风。
值彼荆国,籍倡《新经》。诋非先哲,聋聩蒸民。
士趋蹊径,性散本真。“精一”之旨,眩惑弥深。
惟微脉绝,时事孔殷。翁独毅然,距闢诐淫。
力黜其配,理毁其经。人心斯正,吾道日星。
功符孟氏,德续先声。
宋隆兴元年(1163)李侗逝世,次年朱熹返回福建,写了《祭李延平先生文》:
道丧千载,两程勃兴。有的其绪,龟山是承。
龟山之南,道则与俱。有觉其徒,望门以趋。
唯时豫章,传得其宗。一箪一瓢,凛然高风。
猗欤先生,果自得师。身世两忘,惟道是资。
精义造约,穷深极微。冻解冰释,发于天机。
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风霆之变,日月之光。
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伦之正,王道之中。
一以贯之,其外无馀。缕析毫差,其分则殊。
体用混元,隐显昭融。万变并酬,浮云太空。
仁孝友弟,洒落诚明。清通和乐,展也大成。
婆娑坵林,世莫我知。优哉游哉,卒岁以嬉。
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来抠衣,发其蔽昏。
侯伯闻风,拥彗以迎。大本大经,是度是程。
税驾云初,讲义有端。疾病乘之,医穷技殚。
呜呼先生,而止于斯。命之不融,谁实尸之。
合散屈伸,消息满虚。廓然大公,与化为徒。
古今一息,曷计短长。物我一身,孰为穷通。
嗟嗟圣学,不绝如线。先生得之,既厚以全。
进未获施,退未及传。殉身以歿,孰云非天。
熹也小生,卯角趋拜。恭惟先生,实共源派。
訚訚侃侃,敛衽推先。冰壶秋月,谓公则然。
施及后人,敢渝斯志。从游十年,诱掖谆至。
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瑾,无幽不穷。
相期日深,见励弥切。蹇步方休,鞭绳已掣。
安车署行,过我衡门。返饰相遭,凉秋已分。
熹于此时,适有命召。问所宜言,反覆教诏。
最后有言,吾子勉之。凡兹众理,子所自知。
奉以周旋,幸不失坠。归装朝严,讣音夕至。
失声长号,泪落悬泉。何意斯言,而诀终天。
病不举扶,没不饭含。奔走后人,死有馀憾。
仪形永隔,卒业无期。坠绪茫茫,孰知我悲。
伏哭柩前,奉奠以贽。不亡者存,鉴此诚意。
又山颓梁坏,岁月不留。即远有期,亲宾毕会。
柳车既饬,薤露怀悲。生荣死哀,孰不推慕。
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学未传心,言徒在耳。
载瞻穗綍,弥切悲伤。筑室三年,莫酬夙志。
举觞一恸,永诀终天。呜呼哀哉!
这篇祭文说自孟子之后,儒学道统已经失传了千年以上,直到二程出现才得以延续。杨时立雪程门,师事二程,尽得二程不传之秘,倡道东南,将道统传给了罗从彦,罗从彦又传给了李侗。而自己有幸师事李侗,成为千古以来道统的正宗传承者,并以此为自豪。文中提到“实共源派”,指的就是朱熹与其师李侗共出于杨时所传的伊洛正宗。
《宋史·道学列传》称:“凡绍兴初崇尚元祐学术,而朱熹、张栻之学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络皆出于时。”朱熹的门人及孙婿赵师夏也在《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答问跋》中称:“延平李先生之学,得之仲素罗先生;罗先生之学,得之龟山杨先生。龟山盖伊洛之高弟也……文公幼孤,从屏山刘公学问。及仕,以父执事延平而已,至于论学,盖未之契,而文公每诵其闻,延平亦莫之许也。文公领簿同安,反复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于是尽弃所学而师事焉。”“今文公先生之言布满天下,光明俊伟”,是“实延平先生一言之绪也”。
关于杨时与朱熹的渊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蔡尚思先生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蔡尚思先生在《杨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杨时是理学南传与闽学的祖师》一文中说道:
无论在中国文化史上、学术史上、思想史上、哲学史上、伦理学史上都居于主要位置的是宋代理学,宋代理学中最重要的是闽学一派,闽学一派中最重要的是朱熹。朱熹之学来自二程与杨时。杨时是中国理学由北传南的关键人物,所以被称为闽学创始人。闽学的祖师是杨时而不是朱熹,朱熹是闽派,也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但是,如果没有杨时把理学传入闽北,也不可能造就朱熹。
为此,他赋诗赞曰:
鲁南有孔孟,闽北出杨朱。
古代人文上,均成为楷模。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