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儒“曾点气象论”的演变及其精神
| 内容出处: |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344 |
| 颗粒名称: | 第三节 宋儒“曾点气象论”的演变及其精神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44 |
| 页码: | 47-90 |
| 摘要: | 本节介绍了宋儒“曾点气象论”的演变及其精神。文章指出,在唐之前,虽然也有人零星谈论曾点,但这些文字多属于文学性质,也多无深意。自宋代开始,才出现了士大夫竞相谈论“曾点气象”的盛况,而其所谈论的内容,也才有了一定的思想内涵。宋儒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朱熹之前。在此期间,人们主要关注曾点的高尚品德和非凡才智,以及他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气象。朱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曾点气象”的研究,认为曾点的气象体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境界,可以为个人修养和道德修养提供帮助。总之,宋儒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体现出了儒家思想中重视人格修养和道德修养的精神。 |
| 关键词: | 朱熹 曾点气象 哲学思想 研究 |
内容
一 朱子前“曾点气象论”的演变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对“曾点气象”的基本概况与时人关注此问题的原因略有叙述。为了加深大家对此问题的了解,这里有必要对在朱子之前理学中讨论“曾点气象”的整体面貌做出分疏。需要指出的是:自宋初到朱子之前,人们对曾点及“曾点气象”的讨论很散,本文也只是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材料略作介绍,其目的只在于揭示理学中讨论该问题的大致演变,揭示他们在讨论该话题背后体现出的深层问题,实不以穷尽材料为目的。
总的来说,在唐之前,虽然也有人零星做诗来吟咏曾点,但这些文字多属于文学性质,也多无深意。自宋代开始,才出现了士大夫竞相谈论“曾点气象”的盛况,而其所谈论的内容,也才有了一定的思想内涵。当然,在宋代之后,提到“曾点气象”的文学作品仍然很多,这些作品也始终缺乏思想意蕴,这一点不必细说。不过,在唐宋之际的文学领域,对曾点“疏狂”一面的渲染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所包含的,是佛老之学对世人的深刻影响。当时人们对曾点的理解,也多流于疏狂和玄远洒落一路①。这和理学兴起后人们对“曾点气象”的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宋明之际,尤其是在理学系统内部,讨论“曾点气象”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在当时,自周敦颐以发其端,此后探讨“与点之乐”者蔚然成风,这种状况一直到了明末清初才渐趋式微。在此过程中,儒者们凭借对“曾点气象”的各自诠释,纷纷表达了他们对儒学之所应然的不同认识。他们对“曾点气象”的诠释在许多方面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当然,有些儒者对“曾点气象”的理解摇荡在似禅非禅之间,“遂复非名敎之所能羁络”;也有些儒者把“曾点气象”作为其发泄自己感性情识的借口,或者是当作其独善其身的借口。这也使得“曾点气象”的内容变得异常丰富。而在此过程中占居主导地位的,还是对人们对“曾点气象”的儒学化诠释与理解。其中,朱子以“天理浑然”阳明以“良知呈现”来诠释“曾点气象”最为典型。
与此同时,儒学内部也始终存在另一种声音①,呼吁人们要警惕“曾点气象”的多义性,要人们警惕过分渲染“曾点之乐”可能带来的弊端。这一呼声自小程子开始,中间经过朱子的大力宣扬而始终绵延不绝。正是在这一呼声的有效影响下,“曾点气象”的大多数鼓吹者们才会时时注意强调“与点之乐”的儒学特质,没有把乐作为为学的惟一目的来追求。这两种声音在理学发展史上交映争辉,共同推动着儒学在一个大本前提下的多元发展。它们之间的互动可以被概括为敬畏与洒落之争,也可以被概括为有无之辩,还可以被归结为围绕究竟应该是从心的角度,还是从理的角度来理解“曾点气象”问题的争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曾点气象”就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出人们对儒学之根本精神的不同理解,可以照出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1017—1073)一向被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因为他比宋初三先生(胡瑗,字翼之,993—1059;孙复,字明复,992—1057,人称泰山先生;石介,字守道,1005—1045,时人尊称为徂徕先生)更为集中和明确地提出理学的几个核心问题。也正是他,使得儒学的心性概念首次具有了本体化的意义,从而启动了儒学发展的根本转向——转向内在化、转向心性本体化。这也促使儒学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实现了天与人的贯通②。周濂溪还是理学中讨论“孔颜乐处”和“与点之乐”问题的始作俑者,其对儒学境界论的形成有奠基之功。
濂溪论学,还以在理学史上首次提出“希圣希贤”、“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①等口号而著称。仅就此而论,孔颜才是濂溪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而如曾点者,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濂溪本人的文集中。但是,在后人纪念濂溪的文字里,濂溪与曾点尤其是“曾点气象”被紧密地连在了一起②,这绝非偶然:就“气象”论,濂溪给人的最大印象是“洒落”,是极高的天资如后人心目中的曾点者,而程明道也曾说过: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③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④
可见,濂溪与“曾点气象”确实有难以割舍的联系。
在濂溪的思想中,乐是一大关键词。但他所说的乐,不是指个人的一己之乐与富贵之乐,而是指“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⑤——对于其所乐者,濂溪明言“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⑥此道此德此乐,其主流是儒学精神,毕竟不同于庄子、禅学之乐。当然,濂溪较后人来说,缺乏对于严辨儒学与佛老界限的自觉,其思想不脱受佛老道家(教)的影响,这也是事实。就是濂溪本人之“气象”,也很难说是纯而又纯的儒者。正像有些学者所说,濂溪在理学中能有今天的地位,更多是和朱子对其形象的重新塑造是分不开的。
于濂溪,还较早的从工夫论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无欲”与主静、礼乐教化这双方面的努力来获得“乐”与天的合一,此即“至诚”之境。此“乐”既有“生生不息”之意,又有“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成人”、“成物”之志。由此,濂溪的“吟风弄月”,既包含着洒落与自由的精神,又不失“正”、“义”的德性成分,也还使得传统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增添了浓厚的境界论成分。完全可以说,新儒学之有新气象,是自濂溪开始的。另外需要指出,今人在提到濂溪“气象”时,往往只会留心黄庭坚论濂溪“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①的一面,却很少注意朱子认为濂溪“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②的一面。我们说,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把握濂溪在与点之乐、寻孔颜乐处上的真意所在。
邵雍(字尧夫,号康节,1011—1077),在宋儒中,只有邵康节把“安乐逍遥”标明为自己的为学宗旨,公然宣称“学不至于乐,不可以谓之学”③,可谓开泰州学派之先。康节还曾作“《清风长吟》、《垂柳长吟》、《落花长吟》、《芳草长吟》、《春水长吟》、《花月长吟》、《落花短吟》、《芳草短吟》、《垂柳短吟》、《春水短吟》、《清风短吟》形成了一个吟风弄月的咏物系列。这些咏物诗不属于物以明德、物以彰德或物以比德的模式,更没有多少托物以言志、借物以写心的内容。诗人只是在肯定自然美价值的前提下,把自然事物当作自在之物进行赏玩,展露了自己精神生活的另一侧面”①。康节的这些作品,极力渲染了宇宙的生命意识,有着“莺飞鱼跃”的活泼气象,也非常类似于儒家所强调的“仁”之境界。但是,其一,康节强调自身安乐逍遥有余,却认为“治人应物”只是余事;其二,康节没有像其他理学家们那样,刻意点出此乐中所包含的德性因素。这些都使他的思想多少带有些“异端”色彩,如《宋元学案》在论康节时,就引了熊禾(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为辅广弟子,1247—1312年)的观点认为:
……但其(康节)制行不免近于高旷,若使进之圣门,则曾皙非不高明,子贡非不颖悟,终不可谓与颜(回)曾(参)同得其传,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②
熊氏的观点也基本符合程伊川和朱子对康节的大致定位。康节之乐,还常被认为有刻意求乐之嫌,因此受到过小程子等人的批评。但是,理学中对康节的正面评价也不少:
魏鹤山曰:若邵子者,使犹得从游于舞雩之下,浴沂咏归,毋宁使曾皙独见称于圣人也欤?洙泗已矣,秦汉以来无此气象,读者当自得之。③
这是说康节之气象真正能体现出宋儒之超越秦汉儒之处,也真正能和“曾点气象”相通,表现为自得之境界。
虽然康节所留下的文献里并没有直接提到过曾点,但是在后人的理解中,他二人还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朱子更对康节一味渲染乐的言辞心存芥蒂。他多次将庄子之乐、康节之乐和曾点之乐相提并论,并对其展开了细致地比较与评述(详见后文论述)。
在论“曾点气象”时,不能不提到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张载(字子厚,1026—1077,因出生于横渠镇,被称为横渠先生)。横渠之学,注重诚明两进,既包括以“穷神知化”为内容的逻辑思考;又包括“体天下之物”的直觉体会。如他强调“大心”,提倡“民胞物与”,提倡直心而发的“四为”精神,这些说法的立意都非常高,也有浓重的境界论色彩。但是,人们对横渠之“气象”的总体印象却是:他没有很好地把这两方面融合在一起,显得“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①。这就是说,横渠之学总的精神是提倡刚恪严毅,苦心力索,基本上不讲从容自在与和乐之情。其气象正和“曾点气象”相反。例如,他的弟子就记录到:
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②
这是对横渠之为学精神的最好概括。朱子对于横渠的这一点曾赞不绝口,指出:“横渠最亲切,程氏规模广大,其后学者少有能如横渠辈用工者。近看得横渠用工最亲切,直是可畏,学者用工须是如此亲切。”①基于个人的特殊“气象”,张横渠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下功夫”类型的曾参和颜回,而非曾点者。因此,张横渠对于那些虚谈“曾点气象”者来说,不啻是一针强有力的清醒剂。对于这一点,王船山更是有着非常真切的体认:
张子之学所为壁立万仞,而不假人以游佚之便,先儒或病其已迫,乃诚伪之分,善恶之介,必如此谨严而后可与立。彼托于春风沂水之狂而陶然自遂者,未足以开来学,立人道也。②
船山本人对于“曾点气象”评价颇高(详见后文),他在这里所批评的,也只是那些“托于”曾点之狂的“陶然自遂”者,指已近于“鱼馁肉烂”的阳明后学。船山明确地反对“托于春风沂水”的狂者气象,而坚持严肃主义的道德修养③。这是他和朱子在此问题上的相通之处,而其更早的思想源头,正是张横渠。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朱子既推崇曾点之“气象”,更推崇横渠之“气象”,他认为后者有给前者奠基的意义。从他一贯注重下学上达,一贯反对虚说“气象”的立场来看,强调苦与乐贯通,敬畏与洒落的贯通,是朱子思想复杂性与立体性的具体体现。在朱子来说,只有通过强调张载这一类型的“气象”来约束和限定时人对“曾点气象”的过分迷恋,才能使之不走作,不流于佛老的一边。
程颢(字伯淳,后人称为明道先生,1032—1085)。明道论学,强调生意、强调和气、强调仁心和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强调活泼自在的精神。他也被后人视为是理学中洒落派的重要代表。因此,我们能在他的文字中找到大量宣扬自得、宣扬和乐之境甚至“优游”、“闲”、“无事”的内容:
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死生有命人何与,消长随时我不悲。直到希夷无事处,先生非是爱吟诗。①
“心闲”、“无事”、“从容”、“淡云微雨”、“云淡风轻”,这些很容易被认为会冲淡儒学的基本价值观的词汇,却经常出现在明道的诗文中。他还提到:
太(泰?下同)山为高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②
若论气象,明道此论可谓高矣。在他看来,即使是如尧舜一般的“事业”、“事功”,也终归是“太山”而已,都不可滞留于心,都只能是“如一点浮云过目”。这一“气象”,我们已经在他早年的大作《定性书》里见到过了。但是,以上所述只是明道思想的一个方面。在另一非常重要的方面,明道也同样强调诚与敬,强调格物穷理的下学工夫,表现出淳儒的气象。以上两方面的结合才能揭示一个完整的明道形象: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魂。①
在这里,明道意谓“无心”与“与必有事焉”是一体之两面,注意二者的有机结合就会活泼泼地,否则就会出现差错,流于佛家的弄精魂。注意二者的结合也足以保证明道思想的儒学本质。那种认为程颢心中既没有“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的悲天悯人之情,也没有程颐那样的“纯粹天理”的道德厚重感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
具体到本文,明道对“曾点气象”的看法颇为典型,对朱子之论“曾点气象”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谓狂矣。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理道理,所以为夫子笑,若知为国以理之道,便却是这气象也。①
子路,冉有,公西华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又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圣人与之。”②
自程明道开始,曾点之志和漆雕开之见就变成了理学中的重要话题,他们也被圣学化了。甚至明道还把曾点之志等同于尧舜之志,其对“曾点气象”之推崇可见一斑。事实上,“曾点气象”之所以能在后来鼓动一时学人的心,明道对其的特殊推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明道的“曾点说”也对朱子的“曾点气象论”有着直接的影响。大程子认为曾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和“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这两句,后来每每成为弟子们向朱熹提出质疑的重要内容,而后一句又是朱熹借以讨论工夫与本体之辨的大话题。
我们说,明道的“曾点论”,也正是他个人“气象”的具体注脚。如谢良佐就曾提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有见明道先生在鄠县作簿时有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看他胸怀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船①
可见,明道胸怀之开阔,气象之和乐,都与“曾点气象”不谋而合,其核心都可谓之“洒落”。
程颐(字正叔,后人称为伊川先生,1033—1107),伊川是明道之弟。众所周知,伊川的为学工夫与“气象”都与明道显有不同。具体而言,就是小程子更强调庄敬严肃,更强调格物致知,因而更具有理性的特色。他在论“曾点气象”上,也颇与明道不同:
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之序,近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为。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如子路、冉求、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与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②
伊川此论,抛开曾点不论,却大谈时人的好高无实,其核心是虚实之辨。应该说,小程子对“曾点气象”不感兴趣,但也没有贬词。而他反复强调为学的先后之序、强调崇实事为却对朱熹有着极大影响,这也成为朱熹后来诠释“曾点气象”问题的一贯观点。
二程兄弟气象的不同,以及其对“曾点气象”的不同态度,是后人热烈讨论的大题目。他们的“曾点说”也都对朱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协调二人“曾点说”的异同,进而在吸取二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就成了朱子后来长期考虑的问题。
二程弟子们几乎人人讨论过“曾点气象”,朱子也在编辑《论孟精义》时收入了范(祖禹?字淳夫,一作纯父、纯甫,一字梦得,1041—1098)、吕大临(字与叔,1044—1091)、谢良佐(字显道,后人称为上蔡先生,1050—1103)、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先生,1053—1135)、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人称尹和靖,1071—1142)论“曾点气象”的内容。但是,其中只有谢上蔡的“曾点说”对朱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谢上蔡是程门高足,被乃师誉为是不为佛所夺的少数弟子之一,黄宗羲更认为:“程门弟子,予窃以上蔡为第一。”①全祖望(字绍衣,亦作裔,小字补,亦作阿补、补儿,号谢山,亦自署鲒琦亭长、双韭氏、双韭山民、孤山社小泉翁、勾曲山人、子全子,学者称谢山先生,1705—1755②)也认为“洛学之魁,皆推上蔡”③。但是,在朱子及后人眼中,谢上蔡同样带有明显的佛老气息④,这又突出体现在他的“曾点说”上: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若指鸢鱼为言,则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
曾本(按,指曾恬所录的版本)此下云: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怀此意在胸中,在曾点看着正可笑尔。学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才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吴本作贤)近于忘。①
谢曰:吾曾历举佛说与吾儒同处问伊川。(伊川)先生曰: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余问本领何故不是?谢曰:为他不循天理,只将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当做大小事,任意纵横,将来作用,便是差处,便是私处。余(曾恬)问:作用何故是私?(谢)曰:把来作用做弄,便是做两般看当了,是将此时横在肚里,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点冷眼看,他只管独对春风吟咏,肚里浑没些能解,岂不快活!①针对谢上蔡的这段话,陈来先生曾指出:
“谢良佐十分推崇曾点的境界,他认为曾点的境界就是‘不著一事’的境界,这个解释显然受到来自禅宗的影响”、“谢良佐明确地用佛教‘无著’的思想解释曾点气象是有意识地吸收了佛教提倡的‘无执无著’的人生境界”、“谢显道了解的尧舜气象既是不著一事在胸中的勿忘勿助、活泼泼底精神境界。”②
陈先生的观点也是朱子在中年以后对谢良佐的基本印象。不过,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谢所说的“不著一事”也就是为程明道所宣扬的“无事”。当然,若单论“不著一事”的来源,则其肯定有比禅宗更早的渊源,比如王弼、老庄之学等。因此,仅靠这一则材料尚不足以表明谢上蔡与佛学有多大的渊源。
谢上蔡是朱子早年的主要思想引路人,而谢的“曾点说”,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对朱子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事实上,朱子后来曾花了很长的时间认真反思谢的“曾点论”,着力清算其中的“禅学”因素①。朱子与张栻之间围绕曾点问题的讨论,其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如何消化谢的思想的问题。当然,就谢本人的思想而论,谢并不只是一味强调洒落,他论求仁、论穷理、论常惺惺,都包含有强调敬畏的内容,而朱子所忧虑的,是谢的思想的立意颇高,会引导人不顾下学,务求上达,会促使人在不自觉中转向佛老。此外,谢与朱子在曾点问题上不解的渊源,还体现在朱子与弟子们围绕谢的一些具体观点如说曾点“虽禹稷之事固可优为”等的反复辩难中。伴随着弟子们的纷纷质疑,朱子后来屡有对谢良佐极为严厉的批评②。
朱子曾数次提到,从谢上蔡到张九成(字子韶,号横浦居士,又号无垢居士,1092—1159),从张九成到陆九渊,其言论越来越放荡而近禅③。张横浦更是交游于宗门人士宗杲,被朱子认为是“阳儒而阴释”的代表。④朱子甚至把张的作品比为洪水猛兽,并对其《中庸解》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判。此后,黄震(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1213—1281)因袭了朱子的说法,认为横浦“于孔门正学,未必无似是之非”⑤。但是,黄梨洲和全谢山都在《宋元学案》中对张横浦有所回护,如谢山就认为:“然横浦之羽翼圣门者,正未可泯也。”①而今人王伟民先生更是认为:
这里,我们看不出他(指张横浦)的“驳”,也看不出有什么“禅”,更看不出是“务在愚一世之耳目”。②
王先生似乎对朱子所说的“驳”和“禅”的特殊含义并不十分了解(后有详述)。但其强调张氏也曾激烈的批判过佛学,这确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张氏所著的《少仪论》来窥见他对佛学以及“曾点气象”的态度:
圣人之道,本无小大,于其中有辨之不精者,此予所以不得无说。大矣哉,圣人之论礼也。其曰:“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故“君子谨其独”也。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止于此而不进,以其乍脱人欲之营营,而入天理之大,其乐无涯,遂认廓然无物者为极致,是故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功业为尘垢,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为赘疣,以天地日月春夏秋冬为梦幻,离天人,绝本末,决内外,茕茕无偶,其视臣弑君,子弑父,兵革扰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气象也乎?殆将灭五常,绝三纲,有孤高之绝体,无敷荣之大用,此其所以得罪于圣人也。礼之以多为贵者,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得不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礼在于是,则感而遂通之时也,发而中节之时也,易所谓“义以方外”也,孟子所谓“存其心,养其性”也。自内心之贵进而得于此,则为尧舜禹汤文武之功业,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为天地日月春夏秋冬之照用,兼天人,通本末,合内外,循环往复,无有不可。譬之于木,从元生本,从本立根,从根立干,从干发枝,从枝敷条,从条出叶,以枝叶而观本元,相去远矣!然枝枝叶叶皆元气也。有元气而无枝叶,不足以见元气之功;有内心无外心,则无以见礼之大用。由是而推一叶之黄,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一拜之不酬,一言之不中,皆内心之不充也。昔尧舜性之,则不勉不思,内外兼得矣;汤武反之,则触人欲而知反矣。然而其反也,有力量之浅深焉。昔颜子三月不违,其余日月至焉,犹未如汤武之一反而不复起也。盖汤武之反,反于礼而已,以礼为反,则动容周旋皆中于礼矣。皆中于礼,则一唯一诺,一起一止,一进一退,一取一舍,无不合于礼者,此其所以为圣人也……且夫释氏之学,以归根反本为至极。岂知恻隱之心为仁之端,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辞逊之心为礼之端,是非之心为智之端乎……昔子思明此道矣,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明内心之理矣。
又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此又明内心而进于外心之礼矣,此少仪之意也。诸君诚有意于斯道,当自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其所谓内心傥有得焉,勿止也;当求夫发而中节之用,使进退起居,饮食寝处,不学而入于乡党之篇,则合内外之道,可与论圣人矣……①
之所以详引张的这篇长文,是想从中找出朱子对于佛老之辨的态度。
张氏的这篇大文,在学理上堪称是辨析儒学与佛学之辨的力作。总的来看,张氏的这篇文章目的就在于辨析儒学与佛学的异同,而他也做得很成功。在他看来,如果只是注意向内心寻求“寂然不动”的一面,“遂认廓然无物者为极致”,进而蔑视外在的尧舜汤武功业、人伦物理、“离天人,绝本末,决内外”,有体无用,就会流向禅学。这种人也无法真正地领略到“曾点气象”强调内外贯通的真意。在张横浦看来,君子的为学之道,既要能“谨其独”,又要能“乐其发”,要贯通天人、本末、大小、内外和体用。由体发用,因用以见体,循环往复,这样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儒学精神。显然,张横浦心中的“曾点气象”,绝非那种务内遗外,独善其身的形象,而是为明道所宣扬的那种“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精神,这是真正的儒学精神。
张横浦据此批判了佛学,认为后者“以归根反本为至极”,而根本不知“四端”为何物,无法让人“承其庇覆”。我们可以从张横浦的这篇文章中读出他对辨析儒释之别的自觉,其辨析的内容也基本上同于二程等人的论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说张横浦在总体上还是坚持了一个儒者的基本立场。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尽管张横浦也曾提到,君子既要能“谨其独”,又要能“乐其发”,在为学上强调一种“未可已也”的精神,但是他的观点总给人一种只是强调“应当如何”,却缺乏“具体如何”去做的感觉。试问,张所说的“‘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明内心之理矣。又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此又明内心而进于外心之礼矣”,所有这些仅仅靠“反之”就能实现吗?说“反于礼而已”,那礼又从何而来?儒学中还没有人会认为礼是先验的。我们也能从朱子对张氏乃师杨时“返身而诚”的批判中读出这一点:“外心之礼”是需要格而后能知,知而后才能行的,离开了为朱子所强调的落实到物上的格物致知工夫,仅仅说“有内心还不够,还需要有外心”云云,就等于空说而已。这在朱子的理解中,无疑就等同于禅学。
再者,我们也能感觉到张横浦强调心(又分为内心和外心)有余,而强调理不足之处。而其强调礼的时候,又主张通过“反”来求礼,这给人一种以心法起灭天地的感觉①。总之,张横浦的这篇文章从学理的角度上看未尝不是,但如果从工夫论的角度来考虑,则有点似是而非。在这方面,其被朱子指为“阳儒而阴释”,符合朱子自己的逻辑和判断标准。
张横浦强于论心、略于论工夫的特点在他其论“曾点言志”的另一材料中更有所体现,其文曰:
识此心则万里犹一堂也,千岁犹一昔也,岂问地之远近,时之先后哉?夫尧舜禹汤文武,皆圣人也……孔子又身入舜文王之所入,故艺则执御,能则鄙,事则吾岂敢,未之有得,皆舜与文王之心也。异时问二三子之志,而曾点有暮春浴沂童冠舞雩之乐,乃入舜与文王道路中,此夫子所以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岂不以圣人之道,此路最高乎?夫子倡此心于洙泗,诸弟子虽于圣人阃奥浅深不同,而自此路入者,亦何其多也?①
这里,张横浦更是直接把曾点和古人心目中的圣人相提并论的味道。其对理想人格状态之期许可见一斑。上文已经提到,在横浦心中,“曾点气象”是纯儒的典型,因此在这段文字中也没有禅学的味道。但是,此文仅仅提到“识此心”则会如何如何,但具体到要如何才能“识此心”,张横浦依然言之未详。
《宋元学案》认为,张横浦上承谢上蔡,下启陆象山。我们也从这段话中读出一点“古圣相传只此心”的味道来。张横浦并没有认为曾点之乐是圣人之道中的最高,但却认为千古一揆的心是“最高”。而传心之说,在此前的儒学传统中绝无先例,毫无疑问是来自于禅学。朱子紧承二程的观点,认为“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②。考其实,则“天”实而“心”正虚。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横浦此说是刊落工夫、虚说心体、直求顿悟的代表,一句话,也是禅学的代表。
在许多人们的印象中,陆九渊(字子静,后人称为象山先生,1139—1193),应该是洒落一派的代表①。因此,他们多认为象山应该与“曾点气象”相似,且都与禅学相通。这一印象,又往往被以下材料所强化了:
祖道(曾祖道,字择之,生卒不详,江西永丰人,1197年始从学于朱子)又曰:顷年亦尝见陆象山。先生笑日: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祖道)曰:象山之学,祖道晓不得,更是不敢学。(朱子)曰:如何不敢学?(祖道)曰:象山与祖道言,“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硬要将一物去治一物,须要如此做甚?咏归舞雩,自是吾子家风!”祖道曰:是则是有此理,恐非初学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铄以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见处,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缠绕旧习,如落陷井,卒除不得。先生曰:陆子静所学,分明是禅(黄卓录)。②
于朱子,“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就是以知觉言性、言仁,这尚且不能体现出儒家之为儒的基本精神,而是典型的禅家语。受这则材料的影响,同时也是受朱学一系的长期渲染①,甚至我们也在潜意识里把陆学和阳明学混为一谈的影响,凡此种种,使我们很容易认为陆九渊只是一味地在宣扬“咏归舞雩”的家风。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更容易加深我们的这一印象,那就是朱子晚年对时人论“曾点气象”之流弊的批判中,其矛头所指向的,往往是曾经向象山处问过学的弟子,而就此问题向朱子多次提问的,也往往是这些人②。所以,在《语类》中,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
近日陆子静门人寄得数篇诗来,只将颜渊曾点数件事重迭说,其它诗书礼乐都不说,如吾友下学也只是拣那尖利底说,粗钝底都掉了,今日下学,明日日便要上达……如论语二十篇,只拣那曾点底意思来涵泳,都要盖了,单单说个风乎舞雩,咏而归,只做个四时景致,论语何用说许多事(陈淳录)?③
问:说漆雕开章云云,先生不应,又说与点章云云,先生又不应。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会那漆雕开与曾点,而今且莫要理会。所谓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会言忠信,行笃敬,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须是步步理会,坐如尸,便要常常如尸,立如齐,便须要常常如齐,而今却只管去理会那流行底,不知是个甚么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随科随坎皆是(黄义刚录)。①
据此,钱穆先生亦认为:“象山陆学好言与点、颜乐而不求实下工夫处”②。其实,钱先生实是误会象山了,至少是在陆子对待曾点气象的态度上,现实情况与此恰好相反——象山的文集和语录中提到曾点的次数非常少,这或许是与陆子不善著述有关。但是我们也没有在他的语类中发现大段讨论“曾点气象”的内容。这反而和朱子的大量讨论曾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象山论及“曾点气象”处往往寥寥数字极见精神③。他在提及曾点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处处将当时普遍被认为是重工夫的颜回和曾点并列,强调二者之间不相悖违;他在提到咏归之乐时,也一定会同时提到“戒谨恐惧”或是“履冰”的诚敬状态。
论及工夫,在许多人看来,陆学是一味求乐,大讲简易,刊落工夫的典型,也几乎就是禅学的翻版,这同样是对陆子的误解。陆子反复强调:自下升高,积小之大,纵令不跌不止,犹当次第而进,
便欲无过,夫岂易有?以夫子之天纵,犹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后,颜子之粹而犹若是。如有所立卓尔之地,竭其才而未能进,此岂可遽言乎?①
这与朱子的态度如出一辙,而这样的话在陆子的著作中举不胜举。其实,就是提到“简易”二字,陆子所说的“简易”和许多人理解中的“简易”并不相同:
然开端发足不可不谨,养正渉邪则当早辨。学之正而得所养,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谁得而御之?今之学者气不至甚塞,质不至甚薄,向善之志号为笃切,鞭勉巳至,循省已熟,乃日困于茫然之地而无所至止,是岂非其志有所陷,学有所蔽而然耶?②
可见,陆子所说的“简易”,是指由于“学之正而得所养”,因而由本之末、无所窒碍的顺畅,是指不支离,而不是指刊落工夫,一步登天的简易,更不是指容易。在陆子看来:
临深履冰,此古人实处,浴沂之咏,曲肱陋巷之乐,与此不相悖违。岂今之学失其正,无所至止,谬生疑惧,浪为艰难者,所可同日道哉?③
陆子认为,为学与乐两不相悖违,但为学工夫一定要谨于开端,次第而进,实下工夫,不能轻言容易。“浴沂之志”和“中庸之戒谨恐惧”乃至于舜、文王、夫子、孟子的工夫都是一致的,失去了任何一方面都会有所偏失。在这方面,象山与明道可谓心有灵犀。但在象山看来,“浴沂之志”是人用力的“所主者”,也是人应当用力不已之地:
改过迁善,固应无难,为仁由己,圣人不我欺也。直使存养至于无间,亦分内事耳。然懈怠纵弛,人之通患,旧习乘机之,捷于影响,慢游是好,傲雪是作,游逸淫乐之戒,大禹伯益犹进于舜;盘盂几杖之铭,成汤犹赖之;夫子七十而从心。吾曹学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尝用力而旧习释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于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养性以事天,岂无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谨恐惧,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乐,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应不劳,若茫然而无主,泛然而无归,则将有颠顿狼狈之患,圣贤乐地,尚安得而至乎?①
可见,陆子认为改过迁善从应然的层面上讲是不难,但在实然的层面上讲,则一定要强调省察之功的不能已,而“浴沂之志”也必须从属于此。陆子还在《与潘文叔》一文中提到:“盖所谓儆戒抑畏,戒谨恐惧者,粹然一出于正,与曲肱陋巷之乐,舞雩咏归之志不相悖违。”
上述资料足以表明,强调必须兼顾“曾点气象”与“儆戒抑畏,戒谨恐惧”,强调二者不相悖违,这是陆子对于“曾点气象”的基本看法,其中也体现出了他的基本为学精神。这一点,也能从朱子对陆子的评价中得到印证:朱子多次指出,陆子力行持守迥然超出常人,而其只重践履,不重穷理却有一条腿走路的嫌疑。我们说,陆子在对“曾点气象”的理解上,与为朱子反复批评的陆子后学实不可同日而语。
陆子还曾指出,其实为学过程是极其苦涩的,绝非一个乐字所能概括:
作事业固当随分有程准,若着实下手处,未易泛言……盖此事论到着实处,极是苦涩。除是实有终身之大念,近到此间,却尽有坚实朋友与之切磋,皆辄望风畏怯,不肯近前。①
莫厌辛苦,此学脉也。②
强调苦与乐不相悖违、简易与苦涩不相悖违,这是陆子思想的辩证法,也是他思想丰富性、深刻性的具体体现。当然,陆子也在行动上切实地贯彻了这一点,如杨简就在《行状》中提到陆子:“读书不苟简,外视虽若闲暇,而实勤于考索。伯兄总家务,常夜分起,必见先生秉烛检书”①。我们常常能见到朱子认为为学必须见苦涩处的语录。实际上,陆子应该是先于朱子提到这一点的②。当然,基于为学宗旨上的显著差异,朱陆二人对如何做工夫肯定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陆子对苦涩的强调与晚明心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陆子到阳明,他们在对“曾点气象”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也是时代的差异使然。
在与朱子的交流中,吕祖谦也提出过对“曾点气象”的看法:
所谓狂者,是心到力不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不是言不副行,其志甚大,但不能无病耳。……曾皙当二三子言志时,欲风乎舞雩咏而归,则是颜子陋巷亦不过此,观此一段气象,则是春秋衰周之时,直有唐虞三代之气味,曾点岂不难得?至季武子死则倚其门而歌,直是容一个武子不得,亦是心到力不到,此之谓狂,狂者度量甚高,止是力有未到处耳。③吕伯恭此论的中心,是强调曾点“其志甚大”,“度量甚高”,乃至于有唐虞三代气味。他不同意程明道认为曾点“言不副行”的定性,而是认为曾点是心到力不到,因此只欠“宽以居之”,待其自然用力而实现其志。可见吕祖谦对曾点的推崇,比程明道更甚。对此,朱子评论到:
问:“东莱说‘曾点只欠宽以居之’,这是如何?”曰:“他是太宽了,却是工夫欠细密。”因举明道说康节云:“尧夫豪杰之士,根本不贴贴地。”又曰:“今人却怕做庄老,却不怕做管商,可笑”(叶贺孙录)!①
朱子显然认为曾点颇有些放荡,空疏。因此对他来说只能严加约束使之归于朴实。于朱子,若对曾点宽以居之,更会使其流于佛老。但反过来说,若完全不讲“曾点气象”,不讲心性修养,又会使人有流于管商的危险,这也是他特别忧虑的。
在当时,游离于理学正统之外的人物也在讨论“曾点气象”,其典型者则是叶适(字正则,后人称为水心先生,1150—1223)。水心论学,以“放言砭古(全谢山语)”、“漂剥古人(陈钟凡语)”为最大特色,其批判的锋芒所及,“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②,而其论说的核心则在虚实之辨。正是基于这一精神,水心针对理学诸子好言尧舜气象的“儒释”③特色,抨击尤为激烈。其辨“黄叔度为后世颜子”之说,更被吕思勉先生指为能切中宋儒好言“圣贤气象”之失①。所有这些,似乎都显示水心应该对“曾点气象”不感兴趣,但其实情却又不尽然。
对于“曾点气象”,叶水心的态度有些复杂,却更符合辩证的精神。他曾大量撰文正面地吟咏过“曾点气象”:除在一些诗文中吟咏曾点外②,他还写了《风雩堂记》来具体说明自己的思想:
……若夫曾皙异于三子,则其乐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乎沂,风乎舞雩,鲁之褉事也,陈宛丘、郑溱洧皆是也。方其士女和会,众粲交发,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者,固以淫情荡志为讥矣,而内有所操,不与众俱靡者,岂不以闭关绝物为病哉?欣时和美备服,即名川之易狎,同鲁人之愿游,咏歌而还,容顺体适,此义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显晦,用舍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终不能毕用而无遗。孔子尝一用于鲁,流离困厄,遂至终老,况三子区区邦邑之间,自许以求用,何其陋也?点之甘服闾里,而自安于不用,亦岂忘世也欤?浴沂舞雩,近时语道之大端也,学者未知洁己以并(即摒字)俗,远利以寡怨,悬料浮想,庶几圣贤,而出处得丧之争,能全其乐鲜矣……虽然,犹有待于物,点之乐也;无待于物,颜氏之乐也。③
本文作于嘉定七年,即1211年,颇能代表水心的晚年观点。他在论及曾点时,语气极为平实,没有高妙之论,更没有涉及心性性命的内容,这是他和正统理学一系在论此问题上的最大不同。于他来说,搬弄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其实无异于“阳儒阴释”。水心强调,曾点之乐“可以名言”、“可勉而至”,没有丝毫的神秘气息,而是当时的一种普通现象。这种乐既未流于“淫情荡志”的一面,又没有走向“闭关绝物”的另一个极端,更不是要“忘世”,而是体现出了“义理之中,物我之平”,是“洁己以并(摒)俗”的代表。这一点在水心看来正是儒学的真实一面。水心的这一说法诚如黄震的评论:
风雩今为圣门一大议论,善形容者往往极于高明,水心谓舞雩鲁之禊事,点不敢必放用,甘服闾里耳。说极平实而文采灿然可读也。①
在对“曾点言志”一节的态度上,黄震与水心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甚至黄震还走得更远,要从根本上取消“曾点气象”的正面价值(见后)。也正因此,他才能够发现水心论“曾点言志”一节的价值所在。我们说,水心的这一观点,大大扫除了时人关于“曾点气象”的种种玄虚不实之论,而这正能体现出水心为学之道的基本精神。同时,水心还结合自己的感受,给予了曾点以“同情之理解”,指出自安与不用,绝不能和忘世直接划等号。可以说,与其入世而不为所用,不能一展报复,还不如高尚其志,这在宋代士人中几成共识①。这也是水心为自己言行的一种辩解。
我们说,水心一方面肯定“曾点气象”,认为它只是一种毫无神秘色彩的平实活动,另一方面,他也对时人过于渲染“曾点气象”、使曾点玄虚化的弊端有所警觉,在极力批判时人一味虚说曾点之乐的危害:
曾皙虽未闻道,而其心庶几焉,故孔子喟然与之。且浴沂风雩,咏歌而归,通国皆然,但不狎邪,所以至道。而后世之论纷纷不已,无实而妄意,可哀也。②
水心认为:“曾皙虽未闻道,而其心庶几焉”,其赞许之情和正面肯定的意味非常明显。在水心的心中,曾点的“庶己”、“至道”和后人的“无实而妄意”,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他对这两者的评价也显然不同:可哀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他还指出了后者的危害:
然近世学者以浴沂舞雩为知道一大节目,意料浮想,遂为师传,执虚承误,无与进德,则其陋有甚于昔之传注者,不可不知也。③
君子言忧不言乐,然而乐在其中也。小人知乐不知忧,故忧常及之。若夫《蟋蟀》之诗,知忧不知乐,则其患亦大矣。①
许多人都曾指出,汉唐之儒只重文字训诂,其弊端丛生。理学的兴起转而强调心性之学,大讲与点,颜乐,这颇有因病施药的价值,这是其长。但是,这样新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却又导致了虚说“气象”的弊端,可谓有得亦有失。这里,水心就是在抨击时人只凭玄想,虚说曾点。他认为这种风气比两汉时期拘泥传注文字的学风为害更大。当然,在水心看来,若是走向另一面,单纯“知忧而不知乐”,也是片面的。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绝对地排斥“曾点气象”的原因所在。在水心看来,儒学中因为过度渲染乐而走向更大偏颇的代表是邵康节,乃至于程明道:
邵雍诗以玩物为道,非是。孔氏之门,惟曾皙直云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与之。若言偃观蜡,樊迟从游,仲由揖观射者,皆因物以讲德,指意不在物也。此亦山人隠士所以自乐,而儒者信之,故有云淡风轻、傍花随柳之趣,其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何以较重轻,而谓道在此不在彼乎?②
这是他在抨击邵雍的“玩物为道”,乃至最终丧道,沦为山人隐士。水心在讨论曾点问题上的态度,与他所一贯坚持的黜虚
崇实的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出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水心的这一批评,当与朱子对此问题的基本态度齐观。
上文主要是从第二个层面,即哲学的角度介绍了人们对“曾点气象”的看法。其实,在整个唐宋之际,在文学领域即本文所说的第一个层面上,同样有大量吟咏曾点的作品。在宋代,如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1021—1086)①、司马光(字君实,1019—1083)②、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③、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1039—1112)④、陆游(字务观,号放翁,1125—1210)⑤、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1127—1206)⑥者,都有吟咏“曾点气象”的诗作与文字。上述这些人所吟咏或是评论曾点的内容,既没有太深的思辨内容,也没有涉及到道德心性性命的内容。仅就此题目而言,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哲学的论域之内,故本文不再展开介绍。
二 宋儒论“曾点气象”的精神
那么,宋儒尤其是朱子会想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来表达什么
思想?他们的讨论又体现出了什么样的精神?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对当时特定的时代以及曾点问题的特殊性的分析,而是从整个哲学史发展的大背景、大视野来看待该问题,那么可以说,朱子等人对该问题的特殊关注,也体现着他对哲学发展史上某些永恒问题的关注。由于本文会在后面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详细讨论,这里只是对上文中的一些内容略做归纳和提示。
第一点,关涉工夫与本体之关系。
工夫与本体关系从来都是理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也包含异常丰富的内容,宋儒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也直接与此相关。需要指出,虽然宋儒对本体的理解颇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虚实之辨,都反对脱离工夫虚说本体,反对单单说本体,反对把本体玄虚化、佛老化。在宋儒中也很少有人把本体作为独立的概念使用的实例。他们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们所说的“大本”、“源头”云云,也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本体。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们都非常审慎地强调,曾点所见是“大本”,是“源头”,是道体的流行发用。此“体”与佛老的“体”的区别就在于,它绝非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别有一物光辉闪烁,动荡流转”,更不是一个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个“体”有着非常具体的规定:理,以及由此层层展开的人伦物理……宋儒都坚信,由此,这个“体”是最实的。就这个“体”与人的关系而言,这个“体”本身不与人隔绝。但就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受气质之蔽的限定,我们是自绝于“体”的。因此,若非经过下学工夫来格物穷理从而突破这一限定,我们就不能对这个“体”有真实、切实的体认,不能做到实有诸己。就我们所见的“体”来说,同是这个“体”,在不同的人心中,会有不同的显现,会有虚实之别。这不是因为“体”不同,而是因为“我”不同,此即“理一分殊”。从这个角度来说,工夫对于我们所能见到何种的“体”,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后来黄宗羲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既是本体”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子每谈及本体时必会提到工夫。强调这个“体”需要你反身去实际地体认,需要你循着下学上达的为学之序实有所见,实有所知。朱子还反复强调说,由于没有扎实下学工夫的支撑,曾点的所见只是一个虚的大轮廓,他的“气象”很虚。这是其与圣贤气象的真正差别,但却是质的差别。因此,应该循着颜回、曾参的工夫型为学之方,走向真实的圣贤气象,真正地超越“曾点气象”。朱子的这一观点,具有浓厚的现实批判色彩。
第二点,关涉内外之辨。
我们说,《论语》中的这一节确实很容易引起后人对“内圣外王”问题的思考。“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简言之,这一思想体现了儒家既要涵养个人境界,又希望实现治国安天下之抱负的人生理想。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强调“内圣”对于“外王”的优先地位,主张由“内圣”而开“外王”是这一思想的基调。其原因本文前面已经有所说明:儒学的政治模式以圣人之治为核心,而其从来都认为人成德的根据和可能性源自其内在的本性,也就是其善性。因此内重于外是儒学的根本特色,至少是自孟子以后的特色。不过,在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内圣与外王问题是分开讨论的。大家都很清楚,有了内圣不一定就会有外王,实现外王是需要机缘或是机遇的——乃至于孔孟诸贤都无法集内圣外王于一身。他们提出的“八条目”,只是强调一种由近到远的、推己及人的为学“顺序”,最终实现兼有内圣和外王。显然,内圣与外王之间是有联系,却不是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更不是“由内圣开外王”的关系。
在理学中,为了回应佛学提出儒学治世、佛学治心的口号,希望把自己上升为本,而把儒学定位为末的企图,理学不得不强调自身就已经实现了治世与治心之间内在的贯通,不得不强调“内圣外王”的内外、本末关系。同时,针对当时“管商之学”横行的现实,他们又不得不提出由内圣来开外王的口号,从而使得“内圣外王”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
一者,他们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建立在了理欲之辨这一心性论的范围,使之具有了内向化、本体化的意味。李景林师认为:言心性义理,本非宋明儒学所独有,其强调“性与天道”的内在贯通,亦本为先秦儒学的固有精神。但只有到了宋明理学这里,其言心言性,才真正具有了本体化的意味。故宋明理学所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对于先秦儒学的“性与天道”思想,既是继承,亦是一种新的理论创造①。李老师的意思是说,于先秦,是性命与天道两分;于宋儒,则实现了二者的内在结合与真正贯通。我们说,宋儒的这种运思方式,也使得他们对内圣外王之辨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反映在“曾点气象”的问题上,宋儒大都强调曾点之志的价值,并认为这是曾点超越三子的所在,也是为什么三子都强调事为,都要志在为国,却得不到夫子赞许的原因。
二者,他们首次运用了体用、本末的思维模式来处理这一问题。给予了“内圣”之学更为基础、奠基性的地位。宋儒空前地强调理欲之辨,强调本末之辨,论及“曾点气象”,朱子突出强调“曾点气象”代表着了无私欲、天理浑然的方面,强调是它才使得我们的“事为之末”的活动不至于迷失方向。他甚至长期认为有“曾点气象”作为源头,“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表明宋明理学是只讲内圣不讲外王,乃至迷失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基本宗旨,大家在这方面有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说,儒学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会导致用哲学化的思维来处理治理国家的复杂问题,会把它简化为一个道德的、教化的问题,或是人性批判的问题。对此,余英时先生和张汝伦先生都有所强调,如张先生认为:“试图以哲学主导政治,其结果一定是无视政治的独立意义,造成哲学和政治的脱节。”①这一点,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前,另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于宋儒,我们不能单讲他们的道德性命之学,而是更应该注重其与儒学大传统的关联。我们说,对此也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宋儒之学的新,就在于其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道德性命之学,那么我们在讨论他们的学术思想时,是该把重心放在他们继承前人的东西上呢?还是应该放在他们的新突破上呢,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吗?片面渲染宋儒的道德性命之学,乃至于忽视了他们的士大夫形象固然不好,但把宋代学术思想刻意描述为政治思想史,却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第三点,关涉“敬畏”派与“洒落”派的学术分野。
当时学界对“曾点气象”的热烈讨论,还关涉到理学中“敬畏”与“洒落”派的学术分野。概括而言,陈来先生曾多次指出:
儒家的境界本来是包含有不同的向度或不同层面的,孔子既提倡“克己复礼”的严肃修养,又赞赏“吾与点也”的活泼境界……从宏观上看儒家,受佛造影响较大的周邵的“洒落”境界与近于康德意义的“敬畏”境界的程朱派构成了一种互补的平衡。①
周濂溪的光风霁月,邵康节的逍遥安乐,程明道的吟风弄月,正如黄庭坚评价濂溪时用的一个词汇,都属于“洒落”的境界。后来朱子的老师李侗也用过这个词汇,成为宋儒浪漫主义境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由程颐到朱熹,更多地提倡庄整齐肃的“主敬”修养,动容貌、修辞气,培养一种“敬畏”的境界。这两种境界在儒学中一直有一种紧张.过度的洒落,会游离了道德的规范性与淡化了社会的责任感;过度的敬良,使心灵不能摆脱束缚感而以自由活泼的心境发挥主体的潜能。这个紧张也就是有心与无心的紧张的一种表现。②
“敬畏”和“洒落”,被认为是两种相对的气象。“敬畏”的涵义相对集中,而“洒落”的涵义就很复杂,既可以指儒学中
“活泼泼地”等正面至少是中性的气象,也可以指“旷荡放逸,纵情肆意”等越出儒学价值观约束的气象。因此,在理学中反对提倡“洒落”者多,而认为完全不要“敬畏”者就很少。当然,此二者的分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儒学中强调“敬畏”者未必不谈“洒落”,强调“洒落”者也未必不谈“敬畏”,这在两宋之际尤其是如此。这是因为,“敬畏”与“洒落”不只是表现为对立和矛盾,它们也有相统一的一面。如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1472—1529)就曾指出:
夫谓“敬畏之增,不能不为洒落之累”,又谓“敬畏为有心,如何可以无心而出于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谓欲速助长之为病也。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之累耶?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岐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动多拂戾,而流于欲速助长。①
我们知道,宋儒中早有既强调必有事焉,又强调勿忘勿助,如程明道者。于他们,“敬畏”和“洒落”就不是对立的。因为“敬畏”不是株守,“洒落”更不是放倒,而阳明更把二者水乳交融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确了。
在阳明看来,“洒落”是心之体,是头脑,而戒慎恐惧却是具体工夫。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之两面,合之两美,析之两伤。如果把“敬畏”与“洒落”截然划为不相关联乃至相互排斥的领域,就会使二者都失去生命力。由此,阳明并不像大多数宋儒和明代早期儒者那样单讲“敬畏”不讲“洒落”,而是给两者以适当的限定,使两者互相肯定、互相补充。他强调,一方面“洒落”产生于常存天理,天理常存则来自戒惶恐惧之无间。因此戒慎恐惧的功夫愈详密,愈有助于“洒落”境界的实现;另一方面,“敬畏”也要有明确的“所敬畏者”以为头脑,若失去了“所敬畏者”这个本,“敬畏”也不会是纯粹的儒家工夫。从这个立场看,认为一讲“洒落”就会导致刊落工夫的说法,是错会了“洒落”,把“洒落”等同于了放荡;同样,那种把“敬畏”当成“洒落”的障碍的说法,表明其工夫还未能真正落到实处。这都是片面的②。
在这一点上,朱子和阳明的态度完全一致。朱子反复指出,一方面,曾点的“快活”需要“克念”的工夫使之趋于“实”,因而“洒落”需要“敬畏”来限制和充实;另一方面,“敬畏”之情同样需要以曾点式的“洒落”来引导使之开阔,来提升,来指点出“敬畏”后面的“所敬畏者”,并消解其不自然的一面。在他与弟子们热议的“放与守的话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朱子也曾长期用“洒落”一词来诠释“曾点气象”,并把这理解为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不“规规为事为之末”的典型。他也对横渠为学之方的过于拘束多有微词。对朱子来说,割裂二者的联系,只讲“敬畏”,或是只讲“洒落”,都不符合儒学以中行为最高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他发现时人竞言“洒落”之流弊日深,他终于下决心把对“曾点气象”的评价改为更为平实,更为具体的内容。在他的天平上,二者之间的地位也逐渐在向“敬畏”偏斜。
应该说,朱子也没有因为时人的流弊而不言“洒落”。反之,他终其晚年,一直在寻求一种较为妥帖的文字重新诠释“洒落”,以达到扬其之长,抑其之短的目的,使之与敬畏形成良性的互补。我们说《论语》“曾点言志”一节的定稿,就很能体现朱子的这一心态。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中详细讨论。再者,正像是大家所看到的,出于对人们一味宣扬“洒落”之流弊的警觉,朱子突出强调了通向真“洒落”之境的艰难,同时也突出强调“敬畏”在儒学中居于更为基本的地位。总之,朱子虽然突出强调“敬畏”,但并不是不讲“洒落”,这是朱子学具有包容性和多侧面性的体现。这也是陈来先生所说的“儒家的境界本来是包含有不同的向度或不同层面的”具体反映。
当然,理学家们在讨论“气象”时,因为其偏重点的不同,大体也可以分为突出“庄敬严毅”的一脉和以“活泼洒落”为理想的一脉。论及“气象”,前者更多注重在“有”上做文章,极力渲染该“气象”的理性义、道德义、责任义的一面,而后者则更多强调心灵的空灵自由或是“浑然与物同体”的“无”的一面;论及实现“气象”的工夫,前者更多的显现出以致知、穷理为宗旨的“智性”色彩,而后者则更强调以内向的逆觉体证或简易直接的明心工夫为主。尤其是在明代,这一紧张关系更有明朗化的趋势。“曾点气象”这一本身就存在不同解释可能性的问题,自然也成了他们借以批判对方并表达自己思想最佳载体。事实上,究竟是从“有”的一面还是从“无”的一面来诠释“曾点气象”就构成了整个理学中的一个讨论极为热烈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理学中对此问题的讨论也显示出了独特的一面。在当时“希圣、希贤”热潮的鼓舞下,评点“气象”也自然就成了指示圣人的所应然和所必然的重要手段。正如崔大华先生所指出,时人之所以如此热烈的投入对“气象”问题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弄清圣人境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而树立一种有别于佛老之超脱境界、真正属于理学自身特色的理想人格与基本为学精神①,而“曾点言志”这一具有较大发挥空间的素材,就成了他们寄言出意的绝佳工具。考其实,正是通过对“曾点气象,妙在那里”的不断追问,理学家们紧紧围绕着什么是“曾点气象”、如何实现“曾点气象”、“曾点气象”与“圣贤气象”的异同这一核心,系统地讨论儒释之辨、心性之论、理欲之辨、义利之辨、工夫与本体之辨等诸问题②。应该说,这些话题都是在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而人们从“曾点气象”出发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则具有鲜明的个性。这正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比如围绕儒释之辨,他们意在强调“曾点气象”与佛老气象的异同;围绕心性之辨,他们重在辨析究竟应该是从理的一面、还是从心的一面来诠释“曾点气象”;围绕理欲之辨,他们强调了天理浑然、毫无私欲作为治国平天下之“大本”的重要性;围绕义利之辨,他们重在强调“有意的为国之心”和“规归于事为之末”的不可取,反之,若能一循天理,就会“虽尧舜事业固尤为之”;围绕工夫与本体之辨,他们重点讨论了“曾点气象”的虚实问题,讨论了格物穷理的工夫对于培养“气象”的重要性等内容。当然,时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每每会有重叠,也常常会表现为一而
二、二而一的复杂关系。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善于把握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体现出的总的精神,同时还要圆融领会他们在讨论每个具体问题时所体现出的独特性。这样才能够超越文字的局限,领会其在讨论“曾点气象”中所包含的独特价值所在。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对“曾点气象”的基本概况与时人关注此问题的原因略有叙述。为了加深大家对此问题的了解,这里有必要对在朱子之前理学中讨论“曾点气象”的整体面貌做出分疏。需要指出的是:自宋初到朱子之前,人们对曾点及“曾点气象”的讨论很散,本文也只是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材料略作介绍,其目的只在于揭示理学中讨论该问题的大致演变,揭示他们在讨论该话题背后体现出的深层问题,实不以穷尽材料为目的。
总的来说,在唐之前,虽然也有人零星做诗来吟咏曾点,但这些文字多属于文学性质,也多无深意。自宋代开始,才出现了士大夫竞相谈论“曾点气象”的盛况,而其所谈论的内容,也才有了一定的思想内涵。当然,在宋代之后,提到“曾点气象”的文学作品仍然很多,这些作品也始终缺乏思想意蕴,这一点不必细说。不过,在唐宋之际的文学领域,对曾点“疏狂”一面的渲染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这一现象背后所包含的,是佛老之学对世人的深刻影响。当时人们对曾点的理解,也多流于疏狂和玄远洒落一路①。这和理学兴起后人们对“曾点气象”的认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宋明之际,尤其是在理学系统内部,讨论“曾点气象”似乎成为一种时尚。在当时,自周敦颐以发其端,此后探讨“与点之乐”者蔚然成风,这种状况一直到了明末清初才渐趋式微。在此过程中,儒者们凭借对“曾点气象”的各自诠释,纷纷表达了他们对儒学之所应然的不同认识。他们对“曾点气象”的诠释在许多方面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当然,有些儒者对“曾点气象”的理解摇荡在似禅非禅之间,“遂复非名敎之所能羁络”;也有些儒者把“曾点气象”作为其发泄自己感性情识的借口,或者是当作其独善其身的借口。这也使得“曾点气象”的内容变得异常丰富。而在此过程中占居主导地位的,还是对人们对“曾点气象”的儒学化诠释与理解。其中,朱子以“天理浑然”阳明以“良知呈现”来诠释“曾点气象”最为典型。
与此同时,儒学内部也始终存在另一种声音①,呼吁人们要警惕“曾点气象”的多义性,要人们警惕过分渲染“曾点之乐”可能带来的弊端。这一呼声自小程子开始,中间经过朱子的大力宣扬而始终绵延不绝。正是在这一呼声的有效影响下,“曾点气象”的大多数鼓吹者们才会时时注意强调“与点之乐”的儒学特质,没有把乐作为为学的惟一目的来追求。这两种声音在理学发展史上交映争辉,共同推动着儒学在一个大本前提下的多元发展。它们之间的互动可以被概括为敬畏与洒落之争,也可以被概括为有无之辩,还可以被归结为围绕究竟应该是从心的角度,还是从理的角度来理解“曾点气象”问题的争论。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曾点气象”就像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出人们对儒学之根本精神的不同理解,可以照出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1017—1073)一向被奉为理学的开山祖,因为他比宋初三先生(胡瑗,字翼之,993—1059;孙复,字明复,992—1057,人称泰山先生;石介,字守道,1005—1045,时人尊称为徂徕先生)更为集中和明确地提出理学的几个核心问题。也正是他,使得儒学的心性概念首次具有了本体化的意义,从而启动了儒学发展的根本转向——转向内在化、转向心性本体化。这也促使儒学从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实现了天与人的贯通②。周濂溪还是理学中讨论“孔颜乐处”和“与点之乐”问题的始作俑者,其对儒学境界论的形成有奠基之功。
濂溪论学,还以在理学史上首次提出“希圣希贤”、“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①等口号而著称。仅就此而论,孔颜才是濂溪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而如曾点者,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濂溪本人的文集中。但是,在后人纪念濂溪的文字里,濂溪与曾点尤其是“曾点气象”被紧密地连在了一起②,这绝非偶然:就“气象”论,濂溪给人的最大印象是“洒落”,是极高的天资如后人心目中的曾点者,而程明道也曾说过:某自再见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③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④
可见,濂溪与“曾点气象”确实有难以割舍的联系。
在濂溪的思想中,乐是一大关键词。但他所说的乐,不是指个人的一己之乐与富贵之乐,而是指“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⑤——对于其所乐者,濂溪明言“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⑥此道此德此乐,其主流是儒学精神,毕竟不同于庄子、禅学之乐。当然,濂溪较后人来说,缺乏对于严辨儒学与佛老界限的自觉,其思想不脱受佛老道家(教)的影响,这也是事实。就是濂溪本人之“气象”,也很难说是纯而又纯的儒者。正像有些学者所说,濂溪在理学中能有今天的地位,更多是和朱子对其形象的重新塑造是分不开的。
于濂溪,还较早的从工夫论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无欲”与主静、礼乐教化这双方面的努力来获得“乐”与天的合一,此即“至诚”之境。此“乐”既有“生生不息”之意,又有“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的“成人”、“成物”之志。由此,濂溪的“吟风弄月”,既包含着洒落与自由的精神,又不失“正”、“义”的德性成分,也还使得传统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增添了浓厚的境界论成分。完全可以说,新儒学之有新气象,是自濂溪开始的。另外需要指出,今人在提到濂溪“气象”时,往往只会留心黄庭坚论濂溪“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①的一面,却很少注意朱子认为濂溪“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②的一面。我们说,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充分把握濂溪在与点之乐、寻孔颜乐处上的真意所在。
邵雍(字尧夫,号康节,1011—1077),在宋儒中,只有邵康节把“安乐逍遥”标明为自己的为学宗旨,公然宣称“学不至于乐,不可以谓之学”③,可谓开泰州学派之先。康节还曾作“《清风长吟》、《垂柳长吟》、《落花长吟》、《芳草长吟》、《春水长吟》、《花月长吟》、《落花短吟》、《芳草短吟》、《垂柳短吟》、《春水短吟》、《清风短吟》形成了一个吟风弄月的咏物系列。这些咏物诗不属于物以明德、物以彰德或物以比德的模式,更没有多少托物以言志、借物以写心的内容。诗人只是在肯定自然美价值的前提下,把自然事物当作自在之物进行赏玩,展露了自己精神生活的另一侧面”①。康节的这些作品,极力渲染了宇宙的生命意识,有着“莺飞鱼跃”的活泼气象,也非常类似于儒家所强调的“仁”之境界。但是,其一,康节强调自身安乐逍遥有余,却认为“治人应物”只是余事;其二,康节没有像其他理学家们那样,刻意点出此乐中所包含的德性因素。这些都使他的思想多少带有些“异端”色彩,如《宋元学案》在论康节时,就引了熊禾(字去非,号勿轩,又号退斋,为辅广弟子,1247—1312年)的观点认为:
……但其(康节)制行不免近于高旷,若使进之圣门,则曾皙非不高明,子贡非不颖悟,终不可谓与颜(回)曾(参)同得其传,百世以俟,不易吾言矣。②
熊氏的观点也基本符合程伊川和朱子对康节的大致定位。康节之乐,还常被认为有刻意求乐之嫌,因此受到过小程子等人的批评。但是,理学中对康节的正面评价也不少:
魏鹤山曰:若邵子者,使犹得从游于舞雩之下,浴沂咏归,毋宁使曾皙独见称于圣人也欤?洙泗已矣,秦汉以来无此气象,读者当自得之。③
这是说康节之气象真正能体现出宋儒之超越秦汉儒之处,也真正能和“曾点气象”相通,表现为自得之境界。
虽然康节所留下的文献里并没有直接提到过曾点,但是在后人的理解中,他二人还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朱子更对康节一味渲染乐的言辞心存芥蒂。他多次将庄子之乐、康节之乐和曾点之乐相提并论,并对其展开了细致地比较与评述(详见后文论述)。
在论“曾点气象”时,不能不提到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张载(字子厚,1026—1077,因出生于横渠镇,被称为横渠先生)。横渠之学,注重诚明两进,既包括以“穷神知化”为内容的逻辑思考;又包括“体天下之物”的直觉体会。如他强调“大心”,提倡“民胞物与”,提倡直心而发的“四为”精神,这些说法的立意都非常高,也有浓重的境界论色彩。但是,人们对横渠之“气象”的总体印象却是:他没有很好地把这两方面融合在一起,显得“有苦心极力之象,而无宽裕温和之气,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屡偏而言多窒”①。这就是说,横渠之学总的精神是提倡刚恪严毅,苦心力索,基本上不讲从容自在与和乐之情。其气象正和“曾点气象”相反。例如,他的弟子就记录到:
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②
这是对横渠之为学精神的最好概括。朱子对于横渠的这一点曾赞不绝口,指出:“横渠最亲切,程氏规模广大,其后学者少有能如横渠辈用工者。近看得横渠用工最亲切,直是可畏,学者用工须是如此亲切。”①基于个人的特殊“气象”,张横渠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下功夫”类型的曾参和颜回,而非曾点者。因此,张横渠对于那些虚谈“曾点气象”者来说,不啻是一针强有力的清醒剂。对于这一点,王船山更是有着非常真切的体认:
张子之学所为壁立万仞,而不假人以游佚之便,先儒或病其已迫,乃诚伪之分,善恶之介,必如此谨严而后可与立。彼托于春风沂水之狂而陶然自遂者,未足以开来学,立人道也。②
船山本人对于“曾点气象”评价颇高(详见后文),他在这里所批评的,也只是那些“托于”曾点之狂的“陶然自遂”者,指已近于“鱼馁肉烂”的阳明后学。船山明确地反对“托于春风沂水”的狂者气象,而坚持严肃主义的道德修养③。这是他和朱子在此问题上的相通之处,而其更早的思想源头,正是张横渠。就本文的主题而言,朱子既推崇曾点之“气象”,更推崇横渠之“气象”,他认为后者有给前者奠基的意义。从他一贯注重下学上达,一贯反对虚说“气象”的立场来看,强调苦与乐贯通,敬畏与洒落的贯通,是朱子思想复杂性与立体性的具体体现。在朱子来说,只有通过强调张载这一类型的“气象”来约束和限定时人对“曾点气象”的过分迷恋,才能使之不走作,不流于佛老的一边。
程颢(字伯淳,后人称为明道先生,1032—1085)。明道论学,强调生意、强调和气、强调仁心和浑然与物同体的境界、强调活泼自在的精神。他也被后人视为是理学中洒落派的重要代表。因此,我们能在他的文字中找到大量宣扬自得、宣扬和乐之境甚至“优游”、“闲”、“无事”的内容:
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死生有命人何与,消长随时我不悲。直到希夷无事处,先生非是爱吟诗。①
“心闲”、“无事”、“从容”、“淡云微雨”、“云淡风轻”,这些很容易被认为会冲淡儒学的基本价值观的词汇,却经常出现在明道的诗文中。他还提到:
太(泰?下同)山为高矣,然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虽尧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虚中一点浮云过目。②
若论气象,明道此论可谓高矣。在他看来,即使是如尧舜一般的“事业”、“事功”,也终归是“太山”而已,都不可滞留于心,都只能是“如一点浮云过目”。这一“气象”,我们已经在他早年的大作《定性书》里见到过了。但是,以上所述只是明道思想的一个方面。在另一非常重要的方面,明道也同样强调诚与敬,强调格物穷理的下学工夫,表现出淳儒的气象。以上两方面的结合才能揭示一个完整的明道形象: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魂。①
在这里,明道意谓“无心”与“与必有事焉”是一体之两面,注意二者的有机结合就会活泼泼地,否则就会出现差错,流于佛家的弄精魂。注意二者的结合也足以保证明道思想的儒学本质。那种认为程颢心中既没有“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的悲天悯人之情,也没有程颐那样的“纯粹天理”的道德厚重感的说法,显然是片面的。
具体到本文,明道对“曾点气象”的看法颇为典型,对朱子之论“曾点气象”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者,真所谓狂矣。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理道理,所以为夫子笑,若知为国以理之道,便却是这气象也。①
子路,冉有,公西华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孔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又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圣人与之。”②
自程明道开始,曾点之志和漆雕开之见就变成了理学中的重要话题,他们也被圣学化了。甚至明道还把曾点之志等同于尧舜之志,其对“曾点气象”之推崇可见一斑。事实上,“曾点气象”之所以能在后来鼓动一时学人的心,明道对其的特殊推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明道的“曾点说”也对朱子的“曾点气象论”有着直接的影响。大程子认为曾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和“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这两句,后来每每成为弟子们向朱熹提出质疑的重要内容,而后一句又是朱熹借以讨论工夫与本体之辨的大话题。
我们说,明道的“曾点论”,也正是他个人“气象”的具体注脚。如谢良佐就曾提到: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有见明道先生在鄠县作簿时有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看他胸怀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船①
可见,明道胸怀之开阔,气象之和乐,都与“曾点气象”不谋而合,其核心都可谓之“洒落”。
程颐(字正叔,后人称为伊川先生,1033—1107),伊川是明道之弟。众所周知,伊川的为学工夫与“气象”都与明道显有不同。具体而言,就是小程子更强调庄敬严肃,更强调格物致知,因而更具有理性的特色。他在论“曾点气象”上,也颇与明道不同:
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之序,近之学者,却只做一场话说,务高而已……今之学者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为。然游、夏一言一事却总是实,如子路、冉求、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与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②
伊川此论,抛开曾点不论,却大谈时人的好高无实,其核心是虚实之辨。应该说,小程子对“曾点气象”不感兴趣,但也没有贬词。而他反复强调为学的先后之序、强调崇实事为却对朱熹有着极大影响,这也成为朱熹后来诠释“曾点气象”问题的一贯观点。
二程兄弟气象的不同,以及其对“曾点气象”的不同态度,是后人热烈讨论的大题目。他们的“曾点说”也都对朱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如何协调二人“曾点说”的异同,进而在吸取二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就成了朱子后来长期考虑的问题。
二程弟子们几乎人人讨论过“曾点气象”,朱子也在编辑《论孟精义》时收入了范(祖禹?字淳夫,一作纯父、纯甫,一字梦得,1041—1098)、吕大临(字与叔,1044—1091)、谢良佐(字显道,后人称为上蔡先生,1050—1103)、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先生,1053—1135)、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人称尹和靖,1071—1142)论“曾点气象”的内容。但是,其中只有谢上蔡的“曾点说”对朱子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谢上蔡是程门高足,被乃师誉为是不为佛所夺的少数弟子之一,黄宗羲更认为:“程门弟子,予窃以上蔡为第一。”①全祖望(字绍衣,亦作裔,小字补,亦作阿补、补儿,号谢山,亦自署鲒琦亭长、双韭氏、双韭山民、孤山社小泉翁、勾曲山人、子全子,学者称谢山先生,1705—1755②)也认为“洛学之魁,皆推上蔡”③。但是,在朱子及后人眼中,谢上蔡同样带有明显的佛老气息④,这又突出体现在他的“曾点说”上: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无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体无所不在,非指鸢鱼而言也。若指鸢鱼为言,则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长则知此,知此则知夫子与点之意。
曾本(按,指曾恬所录的版本)此下云:季路冉求言志之事,非大才做不得,然常怀此意在胸中,在曾点看着正可笑尔。学者不可着一事在胸中,才着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然易做,只是无心(吴本作贤)近于忘。①
谢曰:吾曾历举佛说与吾儒同处问伊川。(伊川)先生曰: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余问本领何故不是?谢曰:为他不循天理,只将拈匙把筯日用底便承当做大小事,任意纵横,将来作用,便是差处,便是私处。余(曾恬)问:作用何故是私?(谢)曰:把来作用做弄,便是做两般看当了,是将此时横在肚里,一如子路、冉子相似,便被他曾点冷眼看,他只管独对春风吟咏,肚里浑没些能解,岂不快活!①针对谢上蔡的这段话,陈来先生曾指出:
“谢良佐十分推崇曾点的境界,他认为曾点的境界就是‘不著一事’的境界,这个解释显然受到来自禅宗的影响”、“谢良佐明确地用佛教‘无著’的思想解释曾点气象是有意识地吸收了佛教提倡的‘无执无著’的人生境界”、“谢显道了解的尧舜气象既是不著一事在胸中的勿忘勿助、活泼泼底精神境界。”②
陈先生的观点也是朱子在中年以后对谢良佐的基本印象。不过,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谢所说的“不著一事”也就是为程明道所宣扬的“无事”。当然,若单论“不著一事”的来源,则其肯定有比禅宗更早的渊源,比如王弼、老庄之学等。因此,仅靠这一则材料尚不足以表明谢上蔡与佛学有多大的渊源。
谢上蔡是朱子早年的主要思想引路人,而谢的“曾点说”,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对朱子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事实上,朱子后来曾花了很长的时间认真反思谢的“曾点论”,着力清算其中的“禅学”因素①。朱子与张栻之间围绕曾点问题的讨论,其背后也隐藏着一个如何消化谢的思想的问题。当然,就谢本人的思想而论,谢并不只是一味强调洒落,他论求仁、论穷理、论常惺惺,都包含有强调敬畏的内容,而朱子所忧虑的,是谢的思想的立意颇高,会引导人不顾下学,务求上达,会促使人在不自觉中转向佛老。此外,谢与朱子在曾点问题上不解的渊源,还体现在朱子与弟子们围绕谢的一些具体观点如说曾点“虽禹稷之事固可优为”等的反复辩难中。伴随着弟子们的纷纷质疑,朱子后来屡有对谢良佐极为严厉的批评②。
朱子曾数次提到,从谢上蔡到张九成(字子韶,号横浦居士,又号无垢居士,1092—1159),从张九成到陆九渊,其言论越来越放荡而近禅③。张横浦更是交游于宗门人士宗杲,被朱子认为是“阳儒而阴释”的代表。④朱子甚至把张的作品比为洪水猛兽,并对其《中庸解》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判。此后,黄震(字东发,学者称于越先生,1213—1281)因袭了朱子的说法,认为横浦“于孔门正学,未必无似是之非”⑤。但是,黄梨洲和全谢山都在《宋元学案》中对张横浦有所回护,如谢山就认为:“然横浦之羽翼圣门者,正未可泯也。”①而今人王伟民先生更是认为:
这里,我们看不出他(指张横浦)的“驳”,也看不出有什么“禅”,更看不出是“务在愚一世之耳目”。②
王先生似乎对朱子所说的“驳”和“禅”的特殊含义并不十分了解(后有详述)。但其强调张氏也曾激烈的批判过佛学,这确属事实。我们可以通过张氏所著的《少仪论》来窥见他对佛学以及“曾点气象”的态度:
圣人之道,本无小大,于其中有辨之不精者,此予所以不得无说。大矣哉,圣人之论礼也。其曰:“礼之以少为贵者,以其内心也。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故“君子谨其独”也。礼在于是,则寂然不动之时也,喜怒哀乐未发之时也,《易》所谓“敬以直内”也,《孟子》所谓“尽其心,知其性”也。有得于此,未可已也,释氏疑近之矣。然止于此而不进,以其乍脱人欲之营营,而入天理之大,其乐无涯,遂认廓然无物者为极致,是故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功业为尘垢,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为赘疣,以天地日月春夏秋冬为梦幻,离天人,绝本末,决内外,茕茕无偶,其视臣弑君,子弑父,兵革扰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之气象也乎?殆将灭五常,绝三纲,有孤高之绝体,无敷荣之大用,此其所以得罪于圣人也。礼之以多为贵者,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得不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礼在于是,则感而遂通之时也,发而中节之时也,易所谓“义以方外”也,孟子所谓“存其心,养其性”也。自内心之贵进而得于此,则为尧舜禹汤文武之功业,为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为天地日月春夏秋冬之照用,兼天人,通本末,合内外,循环往复,无有不可。譬之于木,从元生本,从本立根,从根立干,从干发枝,从枝敷条,从条出叶,以枝叶而观本元,相去远矣!然枝枝叶叶皆元气也。有元气而无枝叶,不足以见元气之功;有内心无外心,则无以见礼之大用。由是而推一叶之黄,一枝之瘁,皆本根之病也。一拜之不酬,一言之不中,皆内心之不充也。昔尧舜性之,则不勉不思,内外兼得矣;汤武反之,则触人欲而知反矣。然而其反也,有力量之浅深焉。昔颜子三月不违,其余日月至焉,犹未如汤武之一反而不复起也。盖汤武之反,反于礼而已,以礼为反,则动容周旋皆中于礼矣。皆中于礼,则一唯一诺,一起一止,一进一退,一取一舍,无不合于礼者,此其所以为圣人也……且夫释氏之学,以归根反本为至极。岂知恻隱之心为仁之端,羞恶之心为义之端,辞逊之心为礼之端,是非之心为智之端乎……昔子思明此道矣,曰:“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明内心之理矣。
又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此又明内心而进于外心之礼矣,此少仪之意也。诸君诚有意于斯道,当自喜怒哀乐未发之前,求其所谓内心傥有得焉,勿止也;当求夫发而中节之用,使进退起居,饮食寝处,不学而入于乡党之篇,则合内外之道,可与论圣人矣……①
之所以详引张的这篇长文,是想从中找出朱子对于佛老之辨的态度。
张氏的这篇大文,在学理上堪称是辨析儒学与佛学之辨的力作。总的来看,张氏的这篇文章目的就在于辨析儒学与佛学的异同,而他也做得很成功。在他看来,如果只是注意向内心寻求“寂然不动”的一面,“遂认廓然无物者为极致”,进而蔑视外在的尧舜汤武功业、人伦物理、“离天人,绝本末,决内外”,有体无用,就会流向禅学。这种人也无法真正地领略到“曾点气象”强调内外贯通的真意。在张横浦看来,君子的为学之道,既要能“谨其独”,又要能“乐其发”,要贯通天人、本末、大小、内外和体用。由体发用,因用以见体,循环往复,这样才能体现出真正的儒学精神。显然,张横浦心中的“曾点气象”,绝非那种务内遗外,独善其身的形象,而是为明道所宣扬的那种“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的精神,这是真正的儒学精神。
张横浦据此批判了佛学,认为后者“以归根反本为至极”,而根本不知“四端”为何物,无法让人“承其庇覆”。我们可以从张横浦的这篇文章中读出他对辨析儒释之别的自觉,其辨析的内容也基本上同于二程等人的论述。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可以说张横浦在总体上还是坚持了一个儒者的基本立场。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尽管张横浦也曾提到,君子既要能“谨其独”,又要能“乐其发”,在为学上强调一种“未可已也”的精神,但是他的观点总给人一种只是强调“应当如何”,却缺乏“具体如何”去做的感觉。试问,张所说的“‘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此明内心之理矣。又曰:‘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此又明内心而进于外心之礼矣”,所有这些仅仅靠“反之”就能实现吗?说“反于礼而已”,那礼又从何而来?儒学中还没有人会认为礼是先验的。我们也能从朱子对张氏乃师杨时“返身而诚”的批判中读出这一点:“外心之礼”是需要格而后能知,知而后才能行的,离开了为朱子所强调的落实到物上的格物致知工夫,仅仅说“有内心还不够,还需要有外心”云云,就等于空说而已。这在朱子的理解中,无疑就等同于禅学。
再者,我们也能感觉到张横浦强调心(又分为内心和外心)有余,而强调理不足之处。而其强调礼的时候,又主张通过“反”来求礼,这给人一种以心法起灭天地的感觉①。总之,张横浦的这篇文章从学理的角度上看未尝不是,但如果从工夫论的角度来考虑,则有点似是而非。在这方面,其被朱子指为“阳儒而阴释”,符合朱子自己的逻辑和判断标准。
张横浦强于论心、略于论工夫的特点在他其论“曾点言志”的另一材料中更有所体现,其文曰:
识此心则万里犹一堂也,千岁犹一昔也,岂问地之远近,时之先后哉?夫尧舜禹汤文武,皆圣人也……孔子又身入舜文王之所入,故艺则执御,能则鄙,事则吾岂敢,未之有得,皆舜与文王之心也。异时问二三子之志,而曾点有暮春浴沂童冠舞雩之乐,乃入舜与文王道路中,此夫子所以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岂不以圣人之道,此路最高乎?夫子倡此心于洙泗,诸弟子虽于圣人阃奥浅深不同,而自此路入者,亦何其多也?①
这里,张横浦更是直接把曾点和古人心目中的圣人相提并论的味道。其对理想人格状态之期许可见一斑。上文已经提到,在横浦心中,“曾点气象”是纯儒的典型,因此在这段文字中也没有禅学的味道。但是,此文仅仅提到“识此心”则会如何如何,但具体到要如何才能“识此心”,张横浦依然言之未详。
《宋元学案》认为,张横浦上承谢上蔡,下启陆象山。我们也从这段话中读出一点“古圣相传只此心”的味道来。张横浦并没有认为曾点之乐是圣人之道中的最高,但却认为千古一揆的心是“最高”。而传心之说,在此前的儒学传统中绝无先例,毫无疑问是来自于禅学。朱子紧承二程的观点,认为“圣人本天,释氏本心”②。考其实,则“天”实而“心”正虚。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横浦此说是刊落工夫、虚说心体、直求顿悟的代表,一句话,也是禅学的代表。
在许多人们的印象中,陆九渊(字子静,后人称为象山先生,1139—1193),应该是洒落一派的代表①。因此,他们多认为象山应该与“曾点气象”相似,且都与禅学相通。这一印象,又往往被以下材料所强化了:
祖道(曾祖道,字择之,生卒不详,江西永丰人,1197年始从学于朱子)又曰:顷年亦尝见陆象山。先生笑日:这却好商量,公且道象山如何?(祖道)曰:象山之学,祖道晓不得,更是不敢学。(朱子)曰:如何不敢学?(祖道)曰:象山与祖道言,“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硬要将一物去治一物,须要如此做甚?咏归舞雩,自是吾子家风!”祖道曰:是则是有此理,恐非初学者所到地位。象山曰:吾子有之,而必欲外铄以为本,可惜也。祖道曰:此恐只是先生见处,今使祖道便要如此,恐成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者矣。象山曰:缠绕旧习,如落陷井,卒除不得。先生曰:陆子静所学,分明是禅(黄卓录)。②
于朱子,“目能视,耳能听,鼻能知香臭,口能知味,心能思,手足能运动,如何更要甚存诚持敬”,就是以知觉言性、言仁,这尚且不能体现出儒家之为儒的基本精神,而是典型的禅家语。受这则材料的影响,同时也是受朱学一系的长期渲染①,甚至我们也在潜意识里把陆学和阳明学混为一谈的影响,凡此种种,使我们很容易认为陆九渊只是一味地在宣扬“咏归舞雩”的家风。
另外,还有一个情况更容易加深我们的这一印象,那就是朱子晚年对时人论“曾点气象”之流弊的批判中,其矛头所指向的,往往是曾经向象山处问过学的弟子,而就此问题向朱子多次提问的,也往往是这些人②。所以,在《语类》中,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
近日陆子静门人寄得数篇诗来,只将颜渊曾点数件事重迭说,其它诗书礼乐都不说,如吾友下学也只是拣那尖利底说,粗钝底都掉了,今日下学,明日日便要上达……如论语二十篇,只拣那曾点底意思来涵泳,都要盖了,单单说个风乎舞雩,咏而归,只做个四时景致,论语何用说许多事(陈淳录)?③
问:说漆雕开章云云,先生不应,又说与点章云云,先生又不应。久之却云:“公那江西人,只管要理会那漆雕开与曾点,而今且莫要理会。所谓道者,只是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便是。而今只去理会言忠信,行笃敬,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须是步步理会,坐如尸,便要常常如尸,立如齐,便须要常常如齐,而今却只管去理会那流行底,不知是个甚么物事,又不是打破一桶水,随科随坎皆是(黄义刚录)。①
据此,钱穆先生亦认为:“象山陆学好言与点、颜乐而不求实下工夫处”②。其实,钱先生实是误会象山了,至少是在陆子对待曾点气象的态度上,现实情况与此恰好相反——象山的文集和语录中提到曾点的次数非常少,这或许是与陆子不善著述有关。但是我们也没有在他的语类中发现大段讨论“曾点气象”的内容。这反而和朱子的大量讨论曾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且,象山论及“曾点气象”处往往寥寥数字极见精神③。他在提及曾点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处处将当时普遍被认为是重工夫的颜回和曾点并列,强调二者之间不相悖违;他在提到咏归之乐时,也一定会同时提到“戒谨恐惧”或是“履冰”的诚敬状态。
论及工夫,在许多人看来,陆学是一味求乐,大讲简易,刊落工夫的典型,也几乎就是禅学的翻版,这同样是对陆子的误解。陆子反复强调:自下升高,积小之大,纵令不跌不止,犹当次第而进,
便欲无过,夫岂易有?以夫子之天纵,犹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后,颜子之粹而犹若是。如有所立卓尔之地,竭其才而未能进,此岂可遽言乎?①
这与朱子的态度如出一辙,而这样的话在陆子的著作中举不胜举。其实,就是提到“简易”二字,陆子所说的“简易”和许多人理解中的“简易”并不相同:
然开端发足不可不谨,养正渉邪则当早辨。学之正而得所养,如木日茂,如泉日流,谁得而御之?今之学者气不至甚塞,质不至甚薄,向善之志号为笃切,鞭勉巳至,循省已熟,乃日困于茫然之地而无所至止,是岂非其志有所陷,学有所蔽而然耶?②
可见,陆子所说的“简易”,是指由于“学之正而得所养”,因而由本之末、无所窒碍的顺畅,是指不支离,而不是指刊落工夫,一步登天的简易,更不是指容易。在陆子看来:
临深履冰,此古人实处,浴沂之咏,曲肱陋巷之乐,与此不相悖违。岂今之学失其正,无所至止,谬生疑惧,浪为艰难者,所可同日道哉?③
陆子认为,为学与乐两不相悖违,但为学工夫一定要谨于开端,次第而进,实下工夫,不能轻言容易。“浴沂之志”和“中庸之戒谨恐惧”乃至于舜、文王、夫子、孟子的工夫都是一致的,失去了任何一方面都会有所偏失。在这方面,象山与明道可谓心有灵犀。但在象山看来,“浴沂之志”是人用力的“所主者”,也是人应当用力不已之地:
改过迁善,固应无难,为仁由己,圣人不我欺也。直使存养至于无间,亦分内事耳。然懈怠纵弛,人之通患,旧习乘机之,捷于影响,慢游是好,傲雪是作,游逸淫乐之戒,大禹伯益犹进于舜;盘盂几杖之铭,成汤犹赖之;夫子七十而从心。吾曹学者省察之功,其可已乎?承喻未尝用力而旧习释然,此真善用力者也。舜之孳孳,文王之翼翼,夫子言主忠信,又言仁能守之,又言用其力于仁,孟子言必有事焉,又言勿忘,又言存心养性以事天,岂无所用其力哉?此中庸之戒谨恐惧,而浴沂之志,曲肱陋巷之乐,不外是矣。此其用力,自应不劳,若茫然而无主,泛然而无归,则将有颠顿狼狈之患,圣贤乐地,尚安得而至乎?①
可见,陆子认为改过迁善从应然的层面上讲是不难,但在实然的层面上讲,则一定要强调省察之功的不能已,而“浴沂之志”也必须从属于此。陆子还在《与潘文叔》一文中提到:“盖所谓儆戒抑畏,戒谨恐惧者,粹然一出于正,与曲肱陋巷之乐,舞雩咏归之志不相悖违。”
上述资料足以表明,强调必须兼顾“曾点气象”与“儆戒抑畏,戒谨恐惧”,强调二者不相悖违,这是陆子对于“曾点气象”的基本看法,其中也体现出了他的基本为学精神。这一点,也能从朱子对陆子的评价中得到印证:朱子多次指出,陆子力行持守迥然超出常人,而其只重践履,不重穷理却有一条腿走路的嫌疑。我们说,陆子在对“曾点气象”的理解上,与为朱子反复批评的陆子后学实不可同日而语。
陆子还曾指出,其实为学过程是极其苦涩的,绝非一个乐字所能概括:
作事业固当随分有程准,若着实下手处,未易泛言……盖此事论到着实处,极是苦涩。除是实有终身之大念,近到此间,却尽有坚实朋友与之切磋,皆辄望风畏怯,不肯近前。①
莫厌辛苦,此学脉也。②
强调苦与乐不相悖违、简易与苦涩不相悖违,这是陆子思想的辩证法,也是他思想丰富性、深刻性的具体体现。当然,陆子也在行动上切实地贯彻了这一点,如杨简就在《行状》中提到陆子:“读书不苟简,外视虽若闲暇,而实勤于考索。伯兄总家务,常夜分起,必见先生秉烛检书”①。我们常常能见到朱子认为为学必须见苦涩处的语录。实际上,陆子应该是先于朱子提到这一点的②。当然,基于为学宗旨上的显著差异,朱陆二人对如何做工夫肯定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陆子对苦涩的强调与晚明心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陆子到阳明,他们在对“曾点气象”的态度上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也是时代的差异使然。
在与朱子的交流中,吕祖谦也提出过对“曾点气象”的看法:
所谓狂者,是心到力不到。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不是言不副行,其志甚大,但不能无病耳。……曾皙当二三子言志时,欲风乎舞雩咏而归,则是颜子陋巷亦不过此,观此一段气象,则是春秋衰周之时,直有唐虞三代之气味,曾点岂不难得?至季武子死则倚其门而歌,直是容一个武子不得,亦是心到力不到,此之谓狂,狂者度量甚高,止是力有未到处耳。③吕伯恭此论的中心,是强调曾点“其志甚大”,“度量甚高”,乃至于有唐虞三代气味。他不同意程明道认为曾点“言不副行”的定性,而是认为曾点是心到力不到,因此只欠“宽以居之”,待其自然用力而实现其志。可见吕祖谦对曾点的推崇,比程明道更甚。对此,朱子评论到:
问:“东莱说‘曾点只欠宽以居之’,这是如何?”曰:“他是太宽了,却是工夫欠细密。”因举明道说康节云:“尧夫豪杰之士,根本不贴贴地。”又曰:“今人却怕做庄老,却不怕做管商,可笑”(叶贺孙录)!①
朱子显然认为曾点颇有些放荡,空疏。因此对他来说只能严加约束使之归于朴实。于朱子,若对曾点宽以居之,更会使其流于佛老。但反过来说,若完全不讲“曾点气象”,不讲心性修养,又会使人有流于管商的危险,这也是他特别忧虑的。
在当时,游离于理学正统之外的人物也在讨论“曾点气象”,其典型者则是叶适(字正则,后人称为水心先生,1150—1223)。水心论学,以“放言砭古(全谢山语)”、“漂剥古人(陈钟凡语)”为最大特色,其批判的锋芒所及,“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②,而其论说的核心则在虚实之辨。正是基于这一精神,水心针对理学诸子好言尧舜气象的“儒释”③特色,抨击尤为激烈。其辨“黄叔度为后世颜子”之说,更被吕思勉先生指为能切中宋儒好言“圣贤气象”之失①。所有这些,似乎都显示水心应该对“曾点气象”不感兴趣,但其实情却又不尽然。
对于“曾点气象”,叶水心的态度有些复杂,却更符合辩证的精神。他曾大量撰文正面地吟咏过“曾点气象”:除在一些诗文中吟咏曾点外②,他还写了《风雩堂记》来具体说明自己的思想:
……若夫曾皙异于三子,则其乐可以名言,而知德者可勉而至也。浴乎沂,风乎舞雩,鲁之褉事也,陈宛丘、郑溱洧皆是也。方其士女和会,众粲交发,彼外有所逐徇,一世而狂者,固以淫情荡志为讥矣,而内有所操,不与众俱靡者,岂不以闭关绝物为病哉?欣时和美备服,即名川之易狎,同鲁人之愿游,咏歌而还,容顺体适,此义理之中,物我之平也。身之显晦,用舍而已,以舜、文王之急士,终不能毕用而无遗。孔子尝一用于鲁,流离困厄,遂至终老,况三子区区邦邑之间,自许以求用,何其陋也?点之甘服闾里,而自安于不用,亦岂忘世也欤?浴沂舞雩,近时语道之大端也,学者未知洁己以并(即摒字)俗,远利以寡怨,悬料浮想,庶几圣贤,而出处得丧之争,能全其乐鲜矣……虽然,犹有待于物,点之乐也;无待于物,颜氏之乐也。③
本文作于嘉定七年,即1211年,颇能代表水心的晚年观点。他在论及曾点时,语气极为平实,没有高妙之论,更没有涉及心性性命的内容,这是他和正统理学一系在论此问题上的最大不同。于他来说,搬弄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其实无异于“阳儒阴释”。水心强调,曾点之乐“可以名言”、“可勉而至”,没有丝毫的神秘气息,而是当时的一种普通现象。这种乐既未流于“淫情荡志”的一面,又没有走向“闭关绝物”的另一个极端,更不是要“忘世”,而是体现出了“义理之中,物我之平”,是“洁己以并(摒)俗”的代表。这一点在水心看来正是儒学的真实一面。水心的这一说法诚如黄震的评论:
风雩今为圣门一大议论,善形容者往往极于高明,水心谓舞雩鲁之禊事,点不敢必放用,甘服闾里耳。说极平实而文采灿然可读也。①
在对“曾点言志”一节的态度上,黄震与水心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甚至黄震还走得更远,要从根本上取消“曾点气象”的正面价值(见后)。也正因此,他才能够发现水心论“曾点言志”一节的价值所在。我们说,水心的这一观点,大大扫除了时人关于“曾点气象”的种种玄虚不实之论,而这正能体现出水心为学之道的基本精神。同时,水心还结合自己的感受,给予了曾点以“同情之理解”,指出自安与不用,绝不能和忘世直接划等号。可以说,与其入世而不为所用,不能一展报复,还不如高尚其志,这在宋代士人中几成共识①。这也是水心为自己言行的一种辩解。
我们说,水心一方面肯定“曾点气象”,认为它只是一种毫无神秘色彩的平实活动,另一方面,他也对时人过于渲染“曾点气象”、使曾点玄虚化的弊端有所警觉,在极力批判时人一味虚说曾点之乐的危害:
曾皙虽未闻道,而其心庶几焉,故孔子喟然与之。且浴沂风雩,咏歌而归,通国皆然,但不狎邪,所以至道。而后世之论纷纷不已,无实而妄意,可哀也。②
水心认为:“曾皙虽未闻道,而其心庶几焉”,其赞许之情和正面肯定的意味非常明显。在水心的心中,曾点的“庶己”、“至道”和后人的“无实而妄意”,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他对这两者的评价也显然不同:可哀的是后者,而非前者。他还指出了后者的危害:
然近世学者以浴沂舞雩为知道一大节目,意料浮想,遂为师传,执虚承误,无与进德,则其陋有甚于昔之传注者,不可不知也。③
君子言忧不言乐,然而乐在其中也。小人知乐不知忧,故忧常及之。若夫《蟋蟀》之诗,知忧不知乐,则其患亦大矣。①
许多人都曾指出,汉唐之儒只重文字训诂,其弊端丛生。理学的兴起转而强调心性之学,大讲与点,颜乐,这颇有因病施药的价值,这是其长。但是,这样新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却又导致了虚说“气象”的弊端,可谓有得亦有失。这里,水心就是在抨击时人只凭玄想,虚说曾点。他认为这种风气比两汉时期拘泥传注文字的学风为害更大。当然,在水心看来,若是走向另一面,单纯“知忧而不知乐”,也是片面的。这也是他为什么没有绝对地排斥“曾点气象”的原因所在。在水心看来,儒学中因为过度渲染乐而走向更大偏颇的代表是邵康节,乃至于程明道:
邵雍诗以玩物为道,非是。孔氏之门,惟曾皙直云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与之。若言偃观蜡,樊迟从游,仲由揖观射者,皆因物以讲德,指意不在物也。此亦山人隠士所以自乐,而儒者信之,故有云淡风轻、傍花随柳之趣,其与穿花蛱蝶,点水蜻蜓何以较重轻,而谓道在此不在彼乎?②
这是他在抨击邵雍的“玩物为道”,乃至最终丧道,沦为山人隐士。水心在讨论曾点问题上的态度,与他所一贯坚持的黜虚
崇实的精神是一致的,都体现出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怀和强烈的批判精神。水心的这一批评,当与朱子对此问题的基本态度齐观。
上文主要是从第二个层面,即哲学的角度介绍了人们对“曾点气象”的看法。其实,在整个唐宋之际,在文学领域即本文所说的第一个层面上,同样有大量吟咏曾点的作品。在宋代,如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1021—1086)①、司马光(字君实,1019—1083)②、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③、苏辙(字子由,号颍滨遗老,1039—1112)④、陆游(字务观,号放翁,1125—1210)⑤、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1127—1206)⑥者,都有吟咏“曾点气象”的诗作与文字。上述这些人所吟咏或是评论曾点的内容,既没有太深的思辨内容,也没有涉及到道德心性性命的内容。仅就此题目而言,甚至都没有进入到哲学的论域之内,故本文不再展开介绍。
二 宋儒论“曾点气象”的精神
那么,宋儒尤其是朱子会想借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来表达什么
思想?他们的讨论又体现出了什么样的精神?如果我们不再局限于对当时特定的时代以及曾点问题的特殊性的分析,而是从整个哲学史发展的大背景、大视野来看待该问题,那么可以说,朱子等人对该问题的特殊关注,也体现着他对哲学发展史上某些永恒问题的关注。由于本文会在后面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详细讨论,这里只是对上文中的一些内容略做归纳和提示。
第一点,关涉工夫与本体之关系。
工夫与本体关系从来都是理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也包含异常丰富的内容,宋儒对“曾点气象”的讨论也直接与此相关。需要指出,虽然宋儒对本体的理解颇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强调虚实之辨,都反对脱离工夫虚说本体,反对单单说本体,反对把本体玄虚化、佛老化。在宋儒中也很少有人把本体作为独立的概念使用的实例。他们对“曾点气象”的讨论,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们所说的“大本”、“源头”云云,也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本体。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儒们都非常审慎地强调,曾点所见是“大本”,是“源头”,是道体的流行发用。此“体”与佛老的“体”的区别就在于,它绝非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别有一物光辉闪烁,动荡流转”,更不是一个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个“体”有着非常具体的规定:理,以及由此层层展开的人伦物理……宋儒都坚信,由此,这个“体”是最实的。就这个“体”与人的关系而言,这个“体”本身不与人隔绝。但就每个具体的人来说,受气质之蔽的限定,我们是自绝于“体”的。因此,若非经过下学工夫来格物穷理从而突破这一限定,我们就不能对这个“体”有真实、切实的体认,不能做到实有诸己。就我们所见的“体”来说,同是这个“体”,在不同的人心中,会有不同的显现,会有虚实之别。这不是因为“体”不同,而是因为“我”不同,此即“理一分殊”。从这个角度来说,工夫对于我们所能见到何种的“体”,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后来黄宗羲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既是本体”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子每谈及本体时必会提到工夫。强调这个“体”需要你反身去实际地体认,需要你循着下学上达的为学之序实有所见,实有所知。朱子还反复强调说,由于没有扎实下学工夫的支撑,曾点的所见只是一个虚的大轮廓,他的“气象”很虚。这是其与圣贤气象的真正差别,但却是质的差别。因此,应该循着颜回、曾参的工夫型为学之方,走向真实的圣贤气象,真正地超越“曾点气象”。朱子的这一观点,具有浓厚的现实批判色彩。
第二点,关涉内外之辨。
我们说,《论语》中的这一节确实很容易引起后人对“内圣外王”问题的思考。“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简言之,这一思想体现了儒家既要涵养个人境界,又希望实现治国安天下之抱负的人生理想。在整个儒学发展史上,强调“内圣”对于“外王”的优先地位,主张由“内圣”而开“外王”是这一思想的基调。其原因本文前面已经有所说明:儒学的政治模式以圣人之治为核心,而其从来都认为人成德的根据和可能性源自其内在的本性,也就是其善性。因此内重于外是儒学的根本特色,至少是自孟子以后的特色。不过,在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内圣与外王问题是分开讨论的。大家都很清楚,有了内圣不一定就会有外王,实现外王是需要机缘或是机遇的——乃至于孔孟诸贤都无法集内圣外王于一身。他们提出的“八条目”,只是强调一种由近到远的、推己及人的为学“顺序”,最终实现兼有内圣和外王。显然,内圣与外王之间是有联系,却不是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更不是“由内圣开外王”的关系。
在理学中,为了回应佛学提出儒学治世、佛学治心的口号,希望把自己上升为本,而把儒学定位为末的企图,理学不得不强调自身就已经实现了治世与治心之间内在的贯通,不得不强调“内圣外王”的内外、本末关系。同时,针对当时“管商之学”横行的现实,他们又不得不提出由内圣来开外王的口号,从而使得“内圣外王”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意义。
一者,他们把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建立在了理欲之辨这一心性论的范围,使之具有了内向化、本体化的意味。李景林师认为:言心性义理,本非宋明儒学所独有,其强调“性与天道”的内在贯通,亦本为先秦儒学的固有精神。但只有到了宋明理学这里,其言心言性,才真正具有了本体化的意味。故宋明理学所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对于先秦儒学的“性与天道”思想,既是继承,亦是一种新的理论创造①。李老师的意思是说,于先秦,是性命与天道两分;于宋儒,则实现了二者的内在结合与真正贯通。我们说,宋儒的这种运思方式,也使得他们对内圣外王之辨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反映在“曾点气象”的问题上,宋儒大都强调曾点之志的价值,并认为这是曾点超越三子的所在,也是为什么三子都强调事为,都要志在为国,却得不到夫子赞许的原因。
二者,他们首次运用了体用、本末的思维模式来处理这一问题。给予了“内圣”之学更为基础、奠基性的地位。宋儒空前地强调理欲之辨,强调本末之辨,论及“曾点气象”,朱子突出强调“曾点气象”代表着了无私欲、天理浑然的方面,强调是它才使得我们的“事为之末”的活动不至于迷失方向。他甚至长期认为有“曾点气象”作为源头,“是虽尧舜事业固优为之”。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表明宋明理学是只讲内圣不讲外王,乃至迷失了儒学经世致用的基本宗旨,大家在这方面有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说,儒学这样做的一个后果,就是会导致用哲学化的思维来处理治理国家的复杂问题,会把它简化为一个道德的、教化的问题,或是人性批判的问题。对此,余英时先生和张汝伦先生都有所强调,如张先生认为:“试图以哲学主导政治,其结果一定是无视政治的独立意义,造成哲学和政治的脱节。”①这一点,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前,另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于宋儒,我们不能单讲他们的道德性命之学,而是更应该注重其与儒学大传统的关联。我们说,对此也要有一个全面的理解。宋儒之学的新,就在于其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道德性命之学,那么我们在讨论他们的学术思想时,是该把重心放在他们继承前人的东西上呢?还是应该放在他们的新突破上呢,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吗?片面渲染宋儒的道德性命之学,乃至于忽视了他们的士大夫形象固然不好,但把宋代学术思想刻意描述为政治思想史,却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第三点,关涉“敬畏”派与“洒落”派的学术分野。
当时学界对“曾点气象”的热烈讨论,还关涉到理学中“敬畏”与“洒落”派的学术分野。概括而言,陈来先生曾多次指出:
儒家的境界本来是包含有不同的向度或不同层面的,孔子既提倡“克己复礼”的严肃修养,又赞赏“吾与点也”的活泼境界……从宏观上看儒家,受佛造影响较大的周邵的“洒落”境界与近于康德意义的“敬畏”境界的程朱派构成了一种互补的平衡。①
周濂溪的光风霁月,邵康节的逍遥安乐,程明道的吟风弄月,正如黄庭坚评价濂溪时用的一个词汇,都属于“洒落”的境界。后来朱子的老师李侗也用过这个词汇,成为宋儒浪漫主义境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同时,由程颐到朱熹,更多地提倡庄整齐肃的“主敬”修养,动容貌、修辞气,培养一种“敬畏”的境界。这两种境界在儒学中一直有一种紧张.过度的洒落,会游离了道德的规范性与淡化了社会的责任感;过度的敬良,使心灵不能摆脱束缚感而以自由活泼的心境发挥主体的潜能。这个紧张也就是有心与无心的紧张的一种表现。②
“敬畏”和“洒落”,被认为是两种相对的气象。“敬畏”的涵义相对集中,而“洒落”的涵义就很复杂,既可以指儒学中
“活泼泼地”等正面至少是中性的气象,也可以指“旷荡放逸,纵情肆意”等越出儒学价值观约束的气象。因此,在理学中反对提倡“洒落”者多,而认为完全不要“敬畏”者就很少。当然,此二者的分野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儒学中强调“敬畏”者未必不谈“洒落”,强调“洒落”者也未必不谈“敬畏”,这在两宋之际尤其是如此。这是因为,“敬畏”与“洒落”不只是表现为对立和矛盾,它们也有相统一的一面。如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1472—1529)就曾指出:
夫谓“敬畏之增,不能不为洒落之累”,又谓“敬畏为有心,如何可以无心而出于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谓欲速助长之为病也。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之累耶?惟夫不知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岐为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动多拂戾,而流于欲速助长。①
我们知道,宋儒中早有既强调必有事焉,又强调勿忘勿助,如程明道者。于他们,“敬畏”和“洒落”就不是对立的。因为“敬畏”不是株守,“洒落”更不是放倒,而阳明更把二者水乳交融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确了。
在阳明看来,“洒落”是心之体,是头脑,而戒慎恐惧却是具体工夫。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之两面,合之两美,析之两伤。如果把“敬畏”与“洒落”截然划为不相关联乃至相互排斥的领域,就会使二者都失去生命力。由此,阳明并不像大多数宋儒和明代早期儒者那样单讲“敬畏”不讲“洒落”,而是给两者以适当的限定,使两者互相肯定、互相补充。他强调,一方面“洒落”产生于常存天理,天理常存则来自戒惶恐惧之无间。因此戒慎恐惧的功夫愈详密,愈有助于“洒落”境界的实现;另一方面,“敬畏”也要有明确的“所敬畏者”以为头脑,若失去了“所敬畏者”这个本,“敬畏”也不会是纯粹的儒家工夫。从这个立场看,认为一讲“洒落”就会导致刊落工夫的说法,是错会了“洒落”,把“洒落”等同于了放荡;同样,那种把“敬畏”当成“洒落”的障碍的说法,表明其工夫还未能真正落到实处。这都是片面的②。
在这一点上,朱子和阳明的态度完全一致。朱子反复指出,一方面,曾点的“快活”需要“克念”的工夫使之趋于“实”,因而“洒落”需要“敬畏”来限制和充实;另一方面,“敬畏”之情同样需要以曾点式的“洒落”来引导使之开阔,来提升,来指点出“敬畏”后面的“所敬畏者”,并消解其不自然的一面。在他与弟子们热议的“放与守的话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朱子也曾长期用“洒落”一词来诠释“曾点气象”,并把这理解为胸次悠然,上下与天地同流,不“规规为事为之末”的典型。他也对横渠为学之方的过于拘束多有微词。对朱子来说,割裂二者的联系,只讲“敬畏”,或是只讲“洒落”,都不符合儒学以中行为最高的基本原则。但是,随着他发现时人竞言“洒落”之流弊日深,他终于下决心把对“曾点气象”的评价改为更为平实,更为具体的内容。在他的天平上,二者之间的地位也逐渐在向“敬畏”偏斜。
应该说,朱子也没有因为时人的流弊而不言“洒落”。反之,他终其晚年,一直在寻求一种较为妥帖的文字重新诠释“洒落”,以达到扬其之长,抑其之短的目的,使之与敬畏形成良性的互补。我们说《论语》“曾点言志”一节的定稿,就很能体现朱子的这一心态。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中详细讨论。再者,正像是大家所看到的,出于对人们一味宣扬“洒落”之流弊的警觉,朱子突出强调了通向真“洒落”之境的艰难,同时也突出强调“敬畏”在儒学中居于更为基本的地位。总之,朱子虽然突出强调“敬畏”,但并不是不讲“洒落”,这是朱子学具有包容性和多侧面性的体现。这也是陈来先生所说的“儒家的境界本来是包含有不同的向度或不同层面的”具体反映。
当然,理学家们在讨论“气象”时,因为其偏重点的不同,大体也可以分为突出“庄敬严毅”的一脉和以“活泼洒落”为理想的一脉。论及“气象”,前者更多注重在“有”上做文章,极力渲染该“气象”的理性义、道德义、责任义的一面,而后者则更多强调心灵的空灵自由或是“浑然与物同体”的“无”的一面;论及实现“气象”的工夫,前者更多的显现出以致知、穷理为宗旨的“智性”色彩,而后者则更强调以内向的逆觉体证或简易直接的明心工夫为主。尤其是在明代,这一紧张关系更有明朗化的趋势。“曾点气象”这一本身就存在不同解释可能性的问题,自然也成了他们借以批判对方并表达自己思想最佳载体。事实上,究竟是从“有”的一面还是从“无”的一面来诠释“曾点气象”就构成了整个理学中的一个讨论极为热烈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理学中对此问题的讨论也显示出了独特的一面。在当时“希圣、希贤”热潮的鼓舞下,评点“气象”也自然就成了指示圣人的所应然和所必然的重要手段。正如崔大华先生所指出,时人之所以如此热烈的投入对“气象”问题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弄清圣人境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而树立一种有别于佛老之超脱境界、真正属于理学自身特色的理想人格与基本为学精神①,而“曾点言志”这一具有较大发挥空间的素材,就成了他们寄言出意的绝佳工具。考其实,正是通过对“曾点气象,妙在那里”的不断追问,理学家们紧紧围绕着什么是“曾点气象”、如何实现“曾点气象”、“曾点气象”与“圣贤气象”的异同这一核心,系统地讨论儒释之辨、心性之论、理欲之辨、义利之辨、工夫与本体之辨等诸问题②。应该说,这些话题都是在理学中最基本的问题。而人们从“曾点气象”出发对此问题展开的讨论,则具有鲜明的个性。这正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内容:比如围绕儒释之辨,他们意在强调“曾点气象”与佛老气象的异同;围绕心性之辨,他们重在辨析究竟应该是从理的一面、还是从心的一面来诠释“曾点气象”;围绕理欲之辨,他们强调了天理浑然、毫无私欲作为治国平天下之“大本”的重要性;围绕义利之辨,他们重在强调“有意的为国之心”和“规归于事为之末”的不可取,反之,若能一循天理,就会“虽尧舜事业固尤为之”;围绕工夫与本体之辨,他们重点讨论了“曾点气象”的虚实问题,讨论了格物穷理的工夫对于培养“气象”的重要性等内容。当然,时人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每每会有重叠,也常常会表现为一而
二、二而一的复杂关系。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善于把握他们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所体现出的总的精神,同时还要圆融领会他们在讨论每个具体问题时所体现出的独特性。这样才能够超越文字的局限,领会其在讨论“曾点气象”中所包含的独特价值所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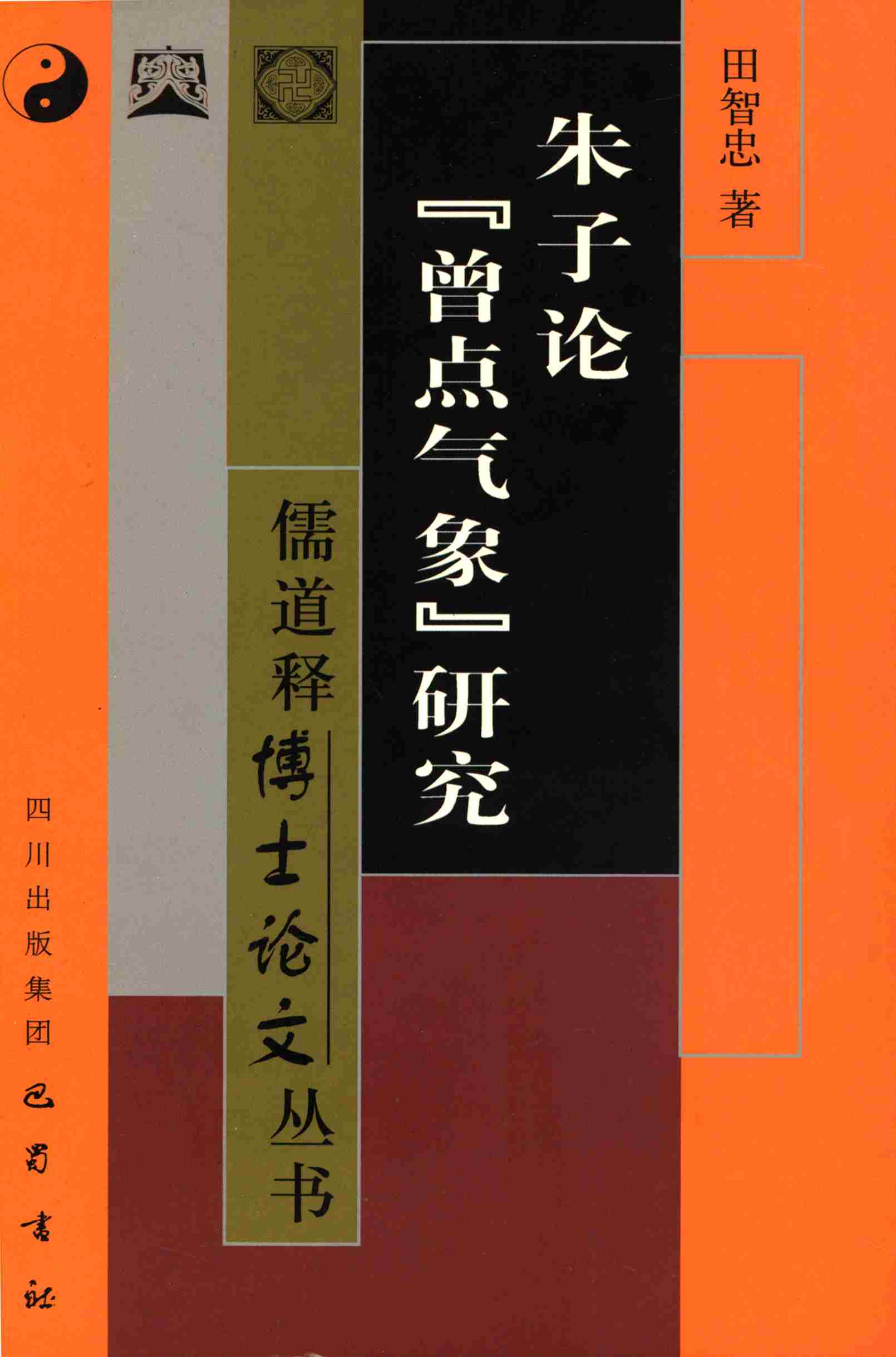
《朱子论“曾点气象”研究》
出版者:四川出版集团
本书从朱熹关于“曾点气象”话题的讨论契入,直探朱子思想中的有无虚实之辨和儒学与佛老之辨等关键问题,旁及历史上相关“曾点气象”的评论,进而引出中国哲学中关于精神境界、本体与功夫的讨论。
阅读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