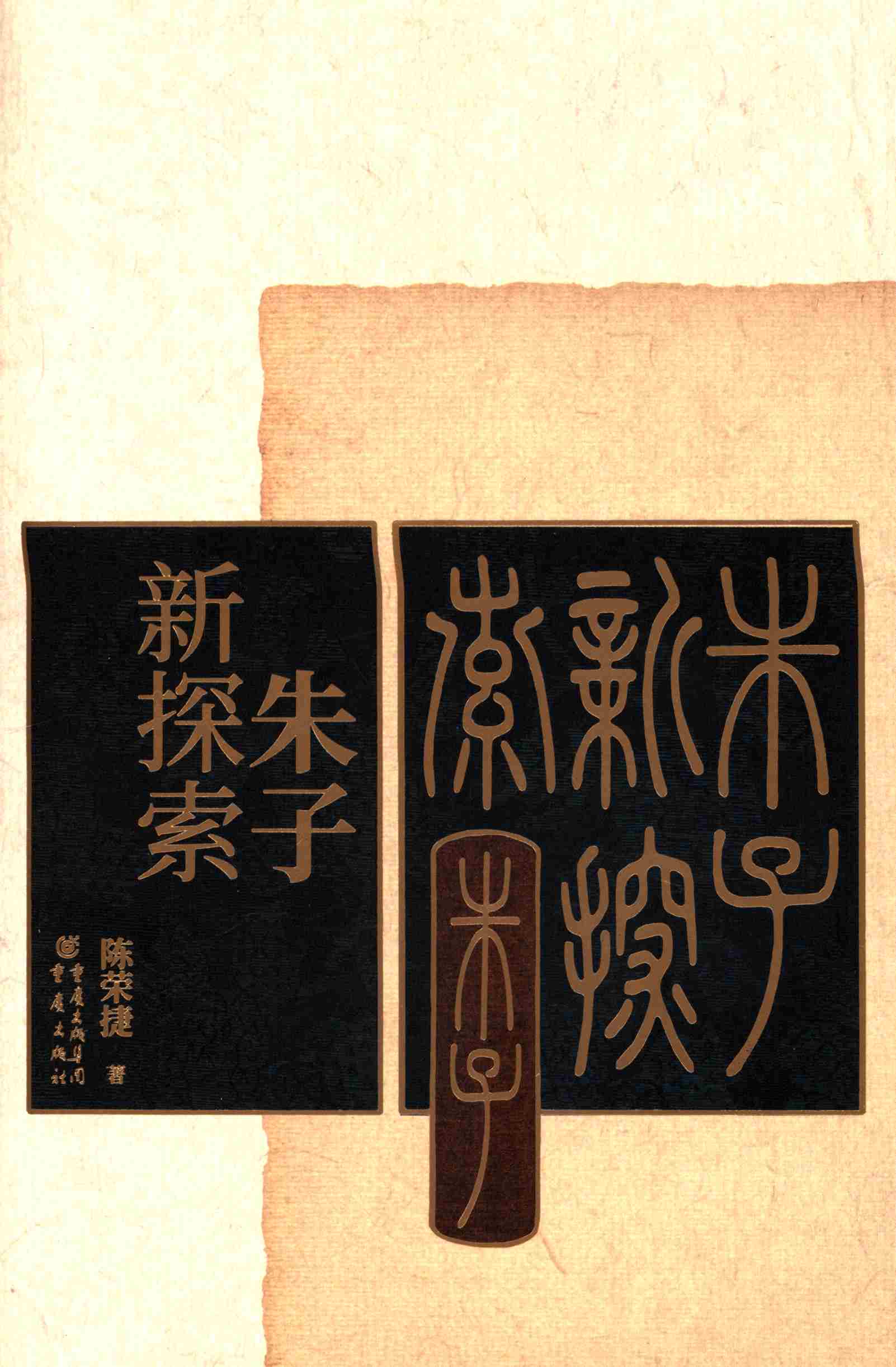【八二】 朱子与张南轩
| 内容出处: | 《朱子新探索》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153 |
| 颗粒名称: | 【八二】 朱子与张南轩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24 |
| 页码: | 527-55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南轩(张栻)和朱子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学术交流。南轩对朱子的修养和言行提出规劝,并与他进行了多次的书信往来。他们还一起游览过南岳衡山,合作创作《南岳唱酬集》。南轩关心朱子的决策和行为,朱子也非常重视南轩的意见。他们共同努力在地方设立了社仓,帮助受灾的人们。南轩对朱子的一些言行表示担忧,但这可能是基于传闻产生的误解。朱子对此作了解释,并表示考虑了利益和害处。朱子的门人们也在其他地方效仿了社仓的建立。总的来说,南轩对朱子的影响对他的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
| 关键词: | 张栻 朱子 学术交 |
内容
(1)两贤之关系
张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字敬夫,又称钦夫,自号南轩。朱子之莫逆交也。两人首次相会,是在隆兴元年癸未(一一六三)冬季。是年有旨召赴行在(杭州)。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据《语类》:“上初召魏公。1先召南轩来。某亦赴召至行在,语南轩云……”2是年朱子三十四岁,南轩三十一岁。翌年魏公没,“九月廿日至豫章3及魏公之舟而哭之。……自豫章送之丰城。4舟中与钦夫得三日之款。”5三年后(一一六七),携门人范念德访南轩于潭州(长沙),九月八日抵达。6留长沙两月,十一月六日与南轩暨门人林择之(名用中)游南岳衡山。十三日登山。中间胡实与范念德来会。十六日下山。十九日离南岳。二十三日至槠州。7次日话别。由十日至十六日朱张与林三人唱咏凡一百四十九首,辑为《南岳唱酬集》。8南轩当时讲学长沙岳麓书院。或云彼官于衡湘间,未知是否。
南轩之于朱子,的是切磋琢磨之益友。书札规劝者屡屡。不止对朱子禀气而言。他如辞受、社仓、刊书、酒气,均有所规谏。南轩与东莱(吕祖谦,一一三七—一一八一)有同情之感,均谓朱子犹有伤急不容耐处。9尝致书云:“又虑元晦学行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是他人不是,觉己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辩论之劲,排辟之严。纵有所疑,不敢以请。深恐谀言多而拂论少。万有一于所偏处,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间相知,孰逾于元晦。切磋之义,其敢后于他人?”10又一书云:“观所与广仲(胡实)书,析理固是精明,亦可谓极力救拔之矣。然言语未免有少和平处。谓当循前人样辙,言约而意该。于紧要处下针。若听者肯思量,当自有入处。不然,我虽愈极力,彼恐愈不近也。”11答胡广仲之书,不知何指。《文集》存答胡广仲六书,或指讨论涵养致知所疑有七之第五书,或已不存。六书并无刚厉之气。然伤急不容耐之病,朱子亦自知其然。12南轩之书续云:“两日从共父(刘珙,一一二二—一一七八)详问日用间事,使人叹服者固多。但以鄙意观之,其间有于气禀偏处,似未能尽变于旧。……愿以平常时以为细故者,作大病医疗。异时相见,当观变化气质之功。”13朱子有与刘共父书,讨论“侄”应否改为“犹子”,有谓共父自主张太过,自处太重。14南轩云:“读所与共父书,辞似逆诈亿不信,而少含弘感悟之意,殆有怒发冲冠之象。”故“却望兄平心易气,以审其是非焉”15。
朱子出处甚严,辞者再三。南轩“向来有疑于兄辞受之间”,与东莱均劝其一出,承当朝廷美意。16乾道四年戊子(一一六八),建宁大饥。朱子与耆老建立社仓于五夫里。是为地方救济之新纪元,于我国历史上有特殊之意义。南轩闻之,去书曰:“闻兄在乡里因岁之歉,请于官得米而储之。春散秋偿。所取之息,不过以备耗失而已。一乡之人赖焉。此固未害也。然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讥。兄闻之作,而曰王介甫(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所行独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奋然欲作社仓记以述此意。某以为此则过矣。夫介甫窃《周官》泉府17之说,强贷而规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其与元晦今日社会之意,义利相异者,固亦晓然。”18南轩所闻,恐是传言之误。朱子《五夫里社仓记》(一一七四)明谓:“常平义仓……皆藏于州县。……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频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19何利何害,朱子固已了然,固不特义利之分而已也。十一年后(一一八五),东莱门人潘景宪白其父出谷以设金华社仓。朱子为之记曰:“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之青苗为说耳。……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20此记似因南轩来书而作,然南轩非不知朱子者也,朱子亦非不知南轩者也。传闻之误耳。
又一传闻之误,乃朱子酒酣气张,悲歌慷慨之报道。21酒兴而歌,事诚有之,然非如谣传之甚耳。(参看页一六一“朱子之酒兴”条)朱子因穷而刊书出售,却是事实。南轩以为未安,然亦无别法也。(参看一五八“朱子之印务”条)
凡此箴规,均出于至诚,朱子亦以至诚接受。尝以书告南轩云:“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已者,皆准止酒例戒而绝之,似觉省事。……常苦求之太过,措词烦猥。近日乃觉其非。”22南轩死后有书寄东莱云:“今日请祠,便是奉行敬夫遗戒第一义。”23及东莱死,则告刘子澄(刘清之,一一三九—一一九五)曰:“前时犹得敬夫伯恭(吕东莱)时惠规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绝不闻此等语。……今乃深有望于吾子澄。”24尝有书敬夫,谓:“大率观书,但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25此乃以自勉,亦所以勉南轩也。
规劝以外,书札往复关及私事,刊书、友朋过往者亦有之,然以之比较东莱,少而又少。盖长沙比金华较远,而浙江又为首都所在,士人往来者多。然南轩亦讲及其止酒决意26,建筑书楼27,与其谢遣生徒28之事,而于其子肺病29,朱子与伯恭之丧偶30,尤致意焉。《文集》所载朱子书札,几全是学术讨论。只顾及或疑学徒日众,非中都官守所宜。朱子则不以为虑31,并劝其时祭应用俗礼而已32。《语类》则有数事可记者。朱子书阁上只匾南轩所书“藏书”二字。33南轩废俗节之祭。朱子问其:“于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阳能不饮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于汝安乎?”34南轩曾谓朱子之命官多禄少。朱子云:“平日辞官文字甚多。35南轩自魏公有事后在家。凡出入人事之类,必以两轿同其弟出入。36”凡此均是以见两者之亲密处。
(2)论南轩
南轩既是朱子之知己,则其对于其友有赞有评,是意中事。兹从《文集》与《语类》观朱子对于南轩之评价。《语类》所载多是南轩死后朱子答门人之问。可谓盖棺定论矣。
朱子谓南轩文字极易成。尝见其就腿上起草,顷刻便就。37劝其改一文,则曰:“改亦只如是。不解更好了。”38故其文字“不甚改。改后往往反不好”39。然在朱子商议之下,其《论语说》则已改许多。《孟子说》则不曾商量。40因其聪明过人,决断太快,故看文字甚疏,以《麻衣易》为真道者之书。41又以“端庄”二字题伪书东坡(苏轼,一〇三七—一一〇一)之字。42又因其太聪敏,讲理太快,说过便了。43更不问人晓会与否。是以其门人之敏悟者,理会其说。其资质不逮者,则无着摸。44朱子云:“敬夫为人明快。每与学者说话,一切倾倒说出。此非不可。但学者未到这里,见他如此说,便不复致思,亦甚害事。”45且因其聪明,每看道理不子细。如说心之昭昭为已发,亦是太过。盖昭昭乃心之体。心有指体而言,亦有指用而言,不可便以昭昭为已发也。46又如说无极而太极,言莫之为而为之,则是说差道理,以初见为定论。盖太极只言极至,无所作为也。47故朱子谓:“其说有太快处。”48又谓:“敬夫议论,出得太早,多有差舛。”49其“未发之”云,乃初年议论。后觉其误,即已改之。独惜旧说已传,学者或未之察耳。50朱子谓:“南轩见处高,如架屋相似。大间架已就,只中间少装折。”51谓其少日常工夫也。尝有书致敬夫,可算是总评。其言曰:“窃所存,大抵庄重。沉密气象,有所未足。以故所发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养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虑事,故恐视听之不能审,而思虑之不能详也。近年见所为文,多无节奏条理。又多语学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52
朱子又以南轩与象山(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三)相比,谓“子静(象山)却杂些禅,又有术数。或说或不说。南轩却平直恁地说,却逢人便说”53。以张、吕相提并论更多。“金溪(象山)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54又谓二者皆令学者专读程颐(一〇三三—一一〇七)《易传》,往往皆无所得55。两者比较,则“钦夫见识极高,却不耐事。伯恭学耐事,却有病”56。又云:“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南轩疏略,从高处去。伯恭疏略,从卑处去。”57虽是如许批评,然卒谓“伯恭、敬夫二人,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58。
以上多点批判,均是小怨。大段光明,才是大德。于本人则谓:“敬夫爱予甚笃。”59于敬夫则谓“钦夫之学,所以超脱自在,见得分明,不为言句所桎梏。只为合下入处亲切。今日说话,虽未能绝无渗漏,终是本领。是当非吾辈所及”60。与诸生说,则曰:“南轩见义勇为。他便是没安排周遮。要做便做。人说道他勇,便是勇。这便是不可及。”说罢叹息数声。61此是叶贺孙〔叶味道,嘉定十三年庚辰(一二二〇)进士〕辛亥(一一九一)以后所闻。盖南轩已去世十余年矣。
南轩死,讣至,罢宴哭之。为祭文者二。其一叹曰:“呜呼,敬夫遽弃予而死也?”62其一曰:“兄之明……我之愚。……兄乔木……我衡茅。……兄高明……我狷狭。……我尝谓兄……兄亦谓我……”63屡言尔我,可若生前对话,情义绸缪。朱子祭文未有如是之动人者。数月后致书伯恭云:“钦夫之逝,忽忽半载。每一念之,未尝不酸噎。同志书来,亦无不相吊者,益使人慨叹。盖不唯吾道之衰,于当世亦大利害也。”64既而为之象赞,谓:“扩仁义之端,至于可以弥六合。谨善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65此非可以应酬文章视之也。五六年后,更撰神道碑。南轩之弟杓移书朱子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于是朱子铭其碑曰:“盖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既精,信道又笃。其乐于闻过而
勇于徙义,则又奋厉明决,无毫发滞吝意。……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义利之间,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其剖析开明,倾倒切至,必竭两端而后已。”66友朋之中,朱子为之撰两祭文,撰赞撰碑铭者,南轩一人而已。
(3)朱子与南轩思想之同异
朱子《又祭张敬夫殿撰文》曰:“唯我之与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乡,而终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缴纷往反者几十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67缴纷往反,皆备于《文集》。所然所议,则详于《语类》。《语类》所言,多关“四书”文句。诸生有疑方问,故异超于同。《文集》所论,乃在基本概念缴纷而卒也同归。以下举其异同之处。总而观之,足以窥见两者之始异终同。南轩《论语解》不取胡寅(字明仲,一〇九八—一一五六)说。朱子不以为然,曰:“若是说得是者岂可废?”68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69,南轩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朱子与之说,若如此说,则虽终身不改可也。70“子不语怪力乱神”71,南轩以为无,朱子以为有,特不语耳72。南轩解“天下归仁”73为无一物之不体。朱子初与之同。后以文义不然,改作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74南轩解“无适”“无莫”75为“适”是有所必,而“莫”是无所主。朱子则谓无所定亦无所不定尔。76孔子谓犁牛之子亦可用,77南轩作孔子教仲弓用人。以朱子观之,南轩牵合,只要回互,不欲说仲弓之父不肖耳。78南轩以颜回之不改其乐79与孔子之乐在其中80不同。朱子则谓只在深浅之间而已。81南轩分“观过”“知仁”82为二说,朱子以为未甚安帖83。南轩以曾子三省其身84为曾子之所以为仁,在朱子则学者莫非为仁,不必专指此事。85南轩解“仁者能好人”86为仁者为能克己,朱子以克己乃仁87。南轩解“不逆诈”、“不亿不信”88以先觉人情者是能为贤,朱子不以为然。盖知人之诈与不信,谓之先觉,但不先臆度其诈与不信也。89南轩以“知者利仁”90为有所为而为,朱子谓只顺道理而已,不待安排也。91南轩误认《孟子》勿忘勿助长92之意,遂作不当忘,不当助长。不知所谓勿忘勿助者,非立此做的防检,而乃俱无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93南轩重视“知皆扩而充之”94之知,朱子谓文势未有此意。“知”字带“广充”而言也。95南轩说“故者以利为本”96以“故”为本然。朱子曰:“如是则善外别有本然。”在朱子,“故”是已然之迹。97
以上均是对南轩之《论语解》与《孟子解》而言。不同之处,当然不止此数。此乃要点而已。其他经书,亦有异议《中庸》云鸢飞鱼跃。98南轩只说能跃之意,故与上文不贯。99南轩说《易》,谓只依孔子《系辞》说便了。朱子则以《系辞》乃所明卦爻之义,故必亦看卦爻而后能理会《系辞》之意。100南轩坚守五峰(胡宏,一一〇六—一一六一)之说,以喜怒哀乐之中101,言众人之常性,而以“寂然不动”102言圣人之道心。朱子则以“寂然不动”,众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103,唯圣人能之104。“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105,两者所解亦异106,南轩谓周子(周敦颐,一〇一七—一〇七三)《太极图说》“无极之真,二(气)五(行)之精”107,不可混说,而“无极之真”,应属上句。朱子报书曰:“若如此则无极之真,自为一物,不与二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万物,又无与乎太极也。”108朱子编《程氏遗书》改若干字。南轩以为有不必改者,亦有不当改者。109南轩以冠礼难行。朱子则以为易。110朱子以南轩说东汉诛宦官事,只是翻誊好看。其实不曾说着当时事体。111
解经之异虽多,唯关于中心问题者甚少。以下则从重要思想,看两者之意见相背者为何。南轩以文章中有性与天道。朱子评之曰:“他太聪敏,便说过了。”112南轩说仁与智都无分别,朱子以之为病。113门人问:明道论生之谓性,既云性善,又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114,却言气质之性,与上文不相接。朱子答曰:“不是言气禀之性。正如水为泥沙所混,不成不唤做水。”门人曰:“适所问乃南轩之论。”朱子曰:“敬夫议论出得太早,多有差舛。”115南轩谓心体昭昭为已发,朱子不以为然,已如上述。116南轩之发,是心体无时而不发。及其既发,则当事而存之而为之宰。朱子曰:“心岂待发而为之宰?”117南轩以心无时不虚。既识此心,则用无不利。朱子以为失之太快,流于异学。心固无时不虚,而人欲己私,汨浸久矣。118南轩谓动中见静,方识此心。朱子则谓复119是静中见动,乃见天地之心。南轩却倒说了。120南轩言圣人虽教人以仁,而未尝不本性命以发之。朱子则谓如此是以仁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121南轩以克己在乎致知格物122,朱子则以克己为胜己之私,而谓南轩:“恐只是一时信笔写将去,殊欠商量。”123南轩不信鬼神,而朱子以鬼神为造化之迹。124
综上所述,可见异处无数。唯其有异,故门人疑问,而书札往复,有讨论之必要。恐相同之点而不见于记载者,为数更大,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有记载其相同者。南轩解子路、子贡问管仲,疑其未仁非仁125,故举其功以告之。朱子曰:“此说却当。”126南轩谓汉后当以蜀汉年号继之。朱子赞同。127南轩言胡明仲(胡寅,一〇九八—一一五六)有三大功。朱子谓南轩见得好,128南轩以孔子之出处为“守身之常法,体道之大权”。又云,“欲往者爱物之仁,终不往者,知人之智”。朱子谓其说得分明。129问南轩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诚而已。此语如何?朱子曰:“诚是实然之理,鬼神亦是实理。”130或曰忠恕,南轩解此云:“圣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朱子曰:“此亦说得好。”131此外尚有朱子加以补充而实相同者。南轩言孔明(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其体正大,问学未至。朱子以之为本不知学,全是驳杂,然却有儒者气象。132朱子云:“南轩尝谓太极所以明动静之蕴,盖得之矣。”133门人问南轩云太极之体至静,朱子以为不是134,而其本人亦谓“静即太极之体,动即太极之用”135。盖以门人以南轩只言体而不言用耳。南轩谓为己者,无所为而然也。朱子曰:“此其语意之深切,盖有前贤所未发者。学者以是而自省焉,则有以察于义利之间,而无一毫厘之差矣。”136南轩以《太极图说》之中正仁义137皆有动静。朱子初以为剩语。然细思之,谓:“盖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贞四字。元亨利贞,一通一复,岂得为无动静乎?”138《答友人书》云:“钦夫未发之论,诚若分别太深。然其所谓无者,非谓本无此理,但谓物欲交引,无复澄静之时耳。”139南轩云敬字通贯动静而以静为本,朱子虽主实践,然亦谓闲时静坐些,小也不妨。140南轩云:“行之至则知益明,知既明则行益至。”朱子以为是,但谓工夫当并进。141如是有同有异,此必然之势。
欲知两者之小异而大同,亦即始异而终同,莫善于窥探其讨论握要之处。此处有三:中和之参究、《知言疑义》之附议,与《仁说》之讨论是也。
甲 中和之参究
朱子从延平(李侗,一〇九三—一一六三)得默坐澄心之教,观未发以前气象。唯于心未安。南轩独得五峰之传,为湖湘学派领袖,主先在已发处察识然后存养。朱子特不远千里而访之,以求究竟。据《年谱》,范念德谓“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王懋竑(一六六八—一七四一)以“此语绝无所据”142。然念德当时在场,非道听途说也。考最古之《朱子年谱》,为叶公回所校订(一四三一),“访长沙”条下称:“往复而深相契者,太极之旨也。”但又述念德之言。王懋竑未见叶本而根据洪去芜改订本(一七〇〇),亦谓:“洪本所云深契太极之旨,此以赠行诗与答诗臆度之耳。”143王氏主意在强调二者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之意见相同,此诚是矣。然《中庸》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何以致之?应先察识抑先涵养?则三日讨论,未能归一也。在长沙亦论仁。《语类》云:“问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辩此。’”144至主张如何,则已不可考矣。
朱子在长沙有书致曹晋叔云:“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论)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方向。往往骋空言而远实理。告语之责,敬夫不可辞也。”145此可为南轩讲学岳麓书院之一证。随后又答石子重〔石〓,绍兴十五年乙丑(一一四五)进士〕云:“熹自去秋之中走长沙,阅月而后至。
留两月而后归。在道缭绕,又五十余日。还家幸老人康健,诸况粗适。他无足言。钦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但其天姿明敏。从初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遂一例学为虚谈。其流弊亦将有害。比来颇觉此病矣。别后当有以救之。然从游之士,亦自绝难得朴实头理会者。可见此道之难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门人,亦有语此者。然皆无实得。拈槌竖拂,几如说禅矣。与文定(胡安国,一〇七四—一一三八)合下门庭,大段相反,更无商量处。惟钦夫见得表里通彻。旧来习见微有所偏。今此相见,尽觉释去,尽好商量也。”146可谓赞美南轩之至。
朱子归后曾与南轩四书,所谓“中和旧说四书”,讨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47之问题。此四书,王懋竑定在访长沙之前,即乾道二年丙戌(一一六六),朱子三十七岁。148钱穆则定在乾道四年。149钱氏理由似较充足。第一书云:“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良心萌蘗,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150此书显示朱子略受湖南影响,渐离延平之默坐求中而趋于湖湘学派之因事省察矣。然究非朱子所寻之答案,故日后自注云:“此书非是。”第二书曰:“兹辱诲喻,乃知尚有认为两物之蔽。……自今观之,只一念间已具此体用。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了无间断隔截处。”151张书不存,大抵以朱子分未发已发为两截。故朱子强调体用一源。如是更近于胡五峰之心性如一矣。及后思之,益为不安。故自注云:“此书所论尤乖戾。”第三书曰:“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52者,乃在于此。而前此方往方来之说,正是手忙足乱,无着身处。”153此书比前书前进一步。盖方往方来,乃随逐气化。而今始有主宰也。第四书云:“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从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顿着处。今觉得如水到船浮,解维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适矣。”154今心为主宰,纯粹自然。存养之功,乃从容自得。
南轩对此四书之反应,除尚有两物之蔽外,已无可考。《南轩文集》则有两书简单商量。一书云:“中字之说甚密。但在中之义作中外之中未安。……若只说作在里面底道理,然则已发之后,中何尝不在里面乎?”155另一书云:“中者性之体,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状性之体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体。若曰性之体中而其用则和,斯可矣。”156
彼此交换意见,当然互有影响。然亦有坚持己见者。朱子《答程允夫(程洵)》云:“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是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157言下似有批评湘湖学者向内省察之意。《答林择之》曰:“近得南轩书,诸说皆相然诺。但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未发已发,条理亦甚明。盖乍易旧说,犹待就所安耳。”158又一书云:“近看南轩文字,大抵皆无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故工夫亦通有无,该动静,方无透漏。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其发处自然中节者多,不中节者少。体察之际,亦甚明审,易为着力。与异时无本可据之说,大不同矣。”159择之在长沙必曾参加此等问题之讨论,故朱子告之如此。
数年之后,朱子四十岁,有《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曰:“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无不中节矣。……故程子(程颐)……以敬为言……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160”此书161将前四书优点,加以敬字为言,而组成有统系之中和论。于是涵养察识,用敬致知,遂为朱子之两轮两翼,三十年丝毫不变。此书虽仍是早年未定之论,然敬义夹持之人生哲学,已于此完成矣。因此有千余言之长书与南轩申明涵养察识,同时并进之旨。“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又指出仁字,“盖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心也。仁则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此彻上彻下之道,圣学之本统。明乎此,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又如所谓学者先须察识端倪之发,然后可加存养之功,则熹于此不能无疑。盖发处固当察识。但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合存养。岂可必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耶?且从初不曾存养,便欲随事察识,窃恐浩浩茫茫,无下手处。”于是结语云:“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敬义夹持,不容间断。”162
乾道八年壬辰(一一七二),朱子撰《中和旧说序》,叙述参究中和之经过。其言曰:“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予以所闻,余亦未之见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乾道(五年)己丑(一一六九)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蔡元定,一一三五—一一九八)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163。此指上面与湖南诸公书。钦夫深以为然,独仍主先察识而后存养耳。论者或谓南轩常随朱子脚跟转,恐是过言。
乙《知言疑义》之附议
南轩学于五峰,独得其传。五峰著《知言》。朱子撰《胡子知言疑义》,逐段反驳,与吕祖谦与南轩讨论。164《知言》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此是朱子所谓“《知言》疑义大端有八”中之“心以用尽”165,恐胡氏混心性为一。故欲改其“以成性”为“统性情”。南轩云:“‘统’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此说朱子未即接纳。《知言》曰:“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朱子评之曰:“此章即性无善恶之意。若果如此,则性但有好恶而无善恶之则矣。”南轩谓:“好恶性也,此一语无害。……今欲作好恶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循其性者也,小人则以人欲乱之而失其则矣。”朱子驳之曰:“直谓之性则不可。盖好恶,物也。好善而恶恶,物之则也。……今欲语性,乃举物而遗则,恐未得为无害也。”《知言》曰:“人之为道,至大也,至善也。”朱子疑之曰:“若性果无善恶,则何以能若是耶?”南轩释其误会颇详,谓:“专善而无恶者,性也。而其动则为情。……于是而有恶焉。是岂性之本哉?其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166者,盖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尝不在也。”朱子指出明道此语乃说气禀之性而非性之本然。其下数处,南轩或同意朱子,或谓《知言》本语应删去,无甚重要。通篇南轩较东莱议论为多。据《语类》,南轩坚持其师“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不与恶对”167之说。168
丙《仁说》之讨论
朱子祭南轩文“缴纷往反者几十年”之语,虽是泛说,然或针对《仁说》169之讨论而言。朱子与友辈商量《仁说》时期最长,而与南轩错商最多。今《朱子文集》所存讨论《仁说》之书四通,《南轩文集》所存二通。朱子释仁为“心之德,爱之理”170。南轩《论语解》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71为“孝弟而始,为仁之道,生而不穷”。朱子评之曰:“此章仁字正指爱之理而言。”172日本学者山崎美成(一七九六—一八五六)据《龙龛手鉴》解仁,谓“心之德,爱之理”原为佛语。173经山口察常(一八八二—一九四八)指出其误。然山口又谓“爱之理”来自南轩。以其《论语解》云:“原人之性,其爱之理,乃仁也。”174山口盖未审《论语解》成于乾道九年癸巳(一一七三)。其时《仁说》已定稿矣。175
朱张往来六书讨论《仁说》,甚为详尽。致钦夫第一书逐句解答。176南轩原书不存,朱子引之。朱子《仁说》首谓:“天地以生物为心。”南轩以此语为未安。朱子坚辨天地只以生物为事。此语未有病也。其后南轩复书云:“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平看虽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为人之心’似完全。”177《仁说》未之改也。南轩谓:“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朱子则谓:“不忍之心包四端,犹仁之可以包四德也。”其后南轩云:“不忍之心虽可以包四者,然据文势对乾元坤元言,恐须只统言之则曰仁而可也。”178南轩以“仁者则其体无不善”,朱子以此为“不知其为善之长”。南轩以“对义礼智而言,其发见则为不忍之心”,朱子以此为未安,盖仁义礼智“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南轩以“仁之为道,无一物之不体”,朱子以此为“不知仁之所以无所不体”。南轩以“程子之所诃,正谓以爱名仁者”,此乃评《仁说》“程子之所诃,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之语。朱子答之曰:“程子曰:‘仁,性也。爱,情也。岂可便以爱为仁?’此正谓不可认情为性耳。非谓仁之性不发于爱之情,而爱之仁不本于仁之性也。”南轩以元之义不专于生。朱子则以此语恐有大病。盖元为义理根源也。南轩有书复云:“前日所谓元之义不专主于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说生生之义不尽。今详所谓生物者,亦无不尽矣。”179南轩以仁者无所不爱,但有差等。朱子以差等乃义之事:“仁义虽不相离,然其用则各有所主而不可乱也。”
第二论仁之书180乃朱子复南轩接朱子第一书后所来之书181。南轩之书以公为仁之体。公天下而无物我之私,故爱无不溥。朱子则谓:“仁乃性之德而爱之本。……若以公天下而无物我之私便为仁体,则恐所谓公者,漠然无情,但如虚空木石。”第三书专论知觉为仁。182南轩曾有书说知觉为仁。此书不存。朱子复之云:“仁本吾心之德,又将谁使知而觉之耶?……然此亦只是智之发用处。但惟仁者为能兼之。故谓仁者必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第四书与第二书意同,即谓公与物我一体皆非仁体183。
以上辩论,南轩每为朱子所折服。辩论结果,《仁说》亦有所更改。今以答南轩书与《仁说》比较,可知经南轩诘难而改正者。不忍之心可包四者之语已不见《仁说》。《仁说》亦无讨论孟子仁无不爱之文,必是因南轩之批评而删。然于天地生物之心一点,则始终坚持。朱子自谓:“《仁说》只说前一截好。”184谅因下截评物我一体与知觉为仁两说未曾释明其所以非仁之故。朱子为《仁说图》185,特标未发已发与体用,且“公”字两见。或亦与南轩讨论之效也。(参看页三八七“《仁说图》”条)
南轩亦作《仁说》186(参看页三九一“南轩《仁说》”条),曾与朱子《仁说》相混。朱子《仁说》题下附注云:“淅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实则人各一篇。两者《仁说》大意相同。唯克己、去蔽、知存,则南轩《仁说》比朱子《仁说》为详而有力。朱子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仁之两面,南轩则只言“爱之理”而不言“心之德”。朱子有《答钦夫<仁说>》187,对南轩《仁说》初稿,多所批评。予曾论之颇详,兹不复述矣。188(参看页三九一“南轩《仁说》”条)南轩又类聚圣贤言仁处,而以程子等人之意释之,名曰《洙泗言仁》。此书已佚,只存其序。朱子于南轩此举,极不赞同,盖谓圣人不言仁处亦有用,而将使学者欲速好径,而陷于不仁也。189然两者均以仁为道德之高峰,教人汲汲求仁。此其两者末乃同归而一致欤。
张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字敬夫,又称钦夫,自号南轩。朱子之莫逆交也。两人首次相会,是在隆兴元年癸未(一一六三)冬季。是年有旨召赴行在(杭州)。十一月六日奏事垂拱殿。据《语类》:“上初召魏公。1先召南轩来。某亦赴召至行在,语南轩云……”2是年朱子三十四岁,南轩三十一岁。翌年魏公没,“九月廿日至豫章3及魏公之舟而哭之。……自豫章送之丰城。4舟中与钦夫得三日之款。”5三年后(一一六七),携门人范念德访南轩于潭州(长沙),九月八日抵达。6留长沙两月,十一月六日与南轩暨门人林择之(名用中)游南岳衡山。十三日登山。中间胡实与范念德来会。十六日下山。十九日离南岳。二十三日至槠州。7次日话别。由十日至十六日朱张与林三人唱咏凡一百四十九首,辑为《南岳唱酬集》。8南轩当时讲学长沙岳麓书院。或云彼官于衡湘间,未知是否。
南轩之于朱子,的是切磋琢磨之益友。书札规劝者屡屡。不止对朱子禀气而言。他如辞受、社仓、刊书、酒气,均有所规谏。南轩与东莱(吕祖谦,一一三七—一一八一)有同情之感,均谓朱子犹有伤急不容耐处。9尝致书云:“又虑元晦学行为人所尊敬。眼前多出己下。平时只是箴规他人。是他人不是,觉己是处多。他人亦惮元晦辩论之劲,排辟之严。纵有所疑,不敢以请。深恐谀言多而拂论少。万有一于所偏处,不加省察,则异日流弊,恐不可免。念世间相知,孰逾于元晦。切磋之义,其敢后于他人?”10又一书云:“观所与广仲(胡实)书,析理固是精明,亦可谓极力救拔之矣。然言语未免有少和平处。谓当循前人样辙,言约而意该。于紧要处下针。若听者肯思量,当自有入处。不然,我虽愈极力,彼恐愈不近也。”11答胡广仲之书,不知何指。《文集》存答胡广仲六书,或指讨论涵养致知所疑有七之第五书,或已不存。六书并无刚厉之气。然伤急不容耐之病,朱子亦自知其然。12南轩之书续云:“两日从共父(刘珙,一一二二—一一七八)详问日用间事,使人叹服者固多。但以鄙意观之,其间有于气禀偏处,似未能尽变于旧。……愿以平常时以为细故者,作大病医疗。异时相见,当观变化气质之功。”13朱子有与刘共父书,讨论“侄”应否改为“犹子”,有谓共父自主张太过,自处太重。14南轩云:“读所与共父书,辞似逆诈亿不信,而少含弘感悟之意,殆有怒发冲冠之象。”故“却望兄平心易气,以审其是非焉”15。
朱子出处甚严,辞者再三。南轩“向来有疑于兄辞受之间”,与东莱均劝其一出,承当朝廷美意。16乾道四年戊子(一一六八),建宁大饥。朱子与耆老建立社仓于五夫里。是为地方救济之新纪元,于我国历史上有特殊之意义。南轩闻之,去书曰:“闻兄在乡里因岁之歉,请于官得米而储之。春散秋偿。所取之息,不过以备耗失而已。一乡之人赖焉。此固未害也。然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讥。兄闻之作,而曰王介甫(王安石,一〇二一—一〇八六)所行独有散青苗一事是耳。奋然欲作社仓记以述此意。某以为此则过矣。夫介甫窃《周官》泉府17之说,强贷而规取其利,逆天下之公理。……其与元晦今日社会之意,义利相异者,固亦晓然。”18南轩所闻,恐是传言之误。朱子《五夫里社仓记》(一一七四)明谓:“常平义仓……皆藏于州县。……深山长谷,力穑远输之民,则虽饥饿频死,而不能及也。又其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视民之殍而不肯发。”19何利何害,朱子固已了然,固不特义利之分而已也。十一年后(一一八五),东莱门人潘景宪白其父出谷以设金华社仓。朱子为之记曰:“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过以王氏之青苗为说耳。……则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其行之以聚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20此记似因南轩来书而作,然南轩非不知朱子者也,朱子亦非不知南轩者也。传闻之误耳。
又一传闻之误,乃朱子酒酣气张,悲歌慷慨之报道。21酒兴而歌,事诚有之,然非如谣传之甚耳。(参看页一六一“朱子之酒兴”条)朱子因穷而刊书出售,却是事实。南轩以为未安,然亦无别法也。(参看一五八“朱子之印务”条)
凡此箴规,均出于至诚,朱子亦以至诚接受。尝以书告南轩云:“近日一种向外走作,心悦之而不能自已者,皆准止酒例戒而绝之,似觉省事。……常苦求之太过,措词烦猥。近日乃觉其非。”22南轩死后有书寄东莱云:“今日请祠,便是奉行敬夫遗戒第一义。”23及东莱死,则告刘子澄(刘清之,一一三九—一一九五)曰:“前时犹得敬夫伯恭(吕东莱)时惠规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绝不闻此等语。……今乃深有望于吾子澄。”24尝有书敬夫,谓:“大率观书,但当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所在。”25此乃以自勉,亦所以勉南轩也。
规劝以外,书札往复关及私事,刊书、友朋过往者亦有之,然以之比较东莱,少而又少。盖长沙比金华较远,而浙江又为首都所在,士人往来者多。然南轩亦讲及其止酒决意26,建筑书楼27,与其谢遣生徒28之事,而于其子肺病29,朱子与伯恭之丧偶30,尤致意焉。《文集》所载朱子书札,几全是学术讨论。只顾及或疑学徒日众,非中都官守所宜。朱子则不以为虑31,并劝其时祭应用俗礼而已32。《语类》则有数事可记者。朱子书阁上只匾南轩所书“藏书”二字。33南轩废俗节之祭。朱子问其:“于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阳能不饮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于汝安乎?”34南轩曾谓朱子之命官多禄少。朱子云:“平日辞官文字甚多。35南轩自魏公有事后在家。凡出入人事之类,必以两轿同其弟出入。36”凡此均是以见两者之亲密处。
(2)论南轩
南轩既是朱子之知己,则其对于其友有赞有评,是意中事。兹从《文集》与《语类》观朱子对于南轩之评价。《语类》所载多是南轩死后朱子答门人之问。可谓盖棺定论矣。
朱子谓南轩文字极易成。尝见其就腿上起草,顷刻便就。37劝其改一文,则曰:“改亦只如是。不解更好了。”38故其文字“不甚改。改后往往反不好”39。然在朱子商议之下,其《论语说》则已改许多。《孟子说》则不曾商量。40因其聪明过人,决断太快,故看文字甚疏,以《麻衣易》为真道者之书。41又以“端庄”二字题伪书东坡(苏轼,一〇三七—一一〇一)之字。42又因其太聪敏,讲理太快,说过便了。43更不问人晓会与否。是以其门人之敏悟者,理会其说。其资质不逮者,则无着摸。44朱子云:“敬夫为人明快。每与学者说话,一切倾倒说出。此非不可。但学者未到这里,见他如此说,便不复致思,亦甚害事。”45且因其聪明,每看道理不子细。如说心之昭昭为已发,亦是太过。盖昭昭乃心之体。心有指体而言,亦有指用而言,不可便以昭昭为已发也。46又如说无极而太极,言莫之为而为之,则是说差道理,以初见为定论。盖太极只言极至,无所作为也。47故朱子谓:“其说有太快处。”48又谓:“敬夫议论,出得太早,多有差舛。”49其“未发之”云,乃初年议论。后觉其误,即已改之。独惜旧说已传,学者或未之察耳。50朱子谓:“南轩见处高,如架屋相似。大间架已就,只中间少装折。”51谓其少日常工夫也。尝有书致敬夫,可算是总评。其言曰:“窃所存,大抵庄重。沉密气象,有所未足。以故所发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养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虑事,故恐视听之不能审,而思虑之不能详也。近年见所为文,多无节奏条理。又多语学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52
朱子又以南轩与象山(陆九渊,一一三九—一一九三)相比,谓“子静(象山)却杂些禅,又有术数。或说或不说。南轩却平直恁地说,却逢人便说”53。以张、吕相提并论更多。“金溪(象山)学问真正是禅。钦夫、伯恭缘不曾看佛书,所以看他不破。只某便识得他。”54又谓二者皆令学者专读程颐(一〇三三—一一〇七)《易传》,往往皆无所得55。两者比较,则“钦夫见识极高,却不耐事。伯恭学耐事,却有病”56。又云:“南轩、伯恭之学皆疏略。南轩疏略,从高处去。伯恭疏略,从卑处去。”57虽是如许批评,然卒谓“伯恭、敬夫二人,使至今不死,大段光明”58。
以上多点批判,均是小怨。大段光明,才是大德。于本人则谓:“敬夫爱予甚笃。”59于敬夫则谓“钦夫之学,所以超脱自在,见得分明,不为言句所桎梏。只为合下入处亲切。今日说话,虽未能绝无渗漏,终是本领。是当非吾辈所及”60。与诸生说,则曰:“南轩见义勇为。他便是没安排周遮。要做便做。人说道他勇,便是勇。这便是不可及。”说罢叹息数声。61此是叶贺孙〔叶味道,嘉定十三年庚辰(一二二〇)进士〕辛亥(一一九一)以后所闻。盖南轩已去世十余年矣。
南轩死,讣至,罢宴哭之。为祭文者二。其一叹曰:“呜呼,敬夫遽弃予而死也?”62其一曰:“兄之明……我之愚。……兄乔木……我衡茅。……兄高明……我狷狭。……我尝谓兄……兄亦谓我……”63屡言尔我,可若生前对话,情义绸缪。朱子祭文未有如是之动人者。数月后致书伯恭云:“钦夫之逝,忽忽半载。每一念之,未尝不酸噎。同志书来,亦无不相吊者,益使人慨叹。盖不唯吾道之衰,于当世亦大利害也。”64既而为之象赞,谓:“扩仁义之端,至于可以弥六合。谨善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65此非可以应酬文章视之也。五六年后,更撰神道碑。南轩之弟杓移书朱子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于是朱子铭其碑曰:“盖公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既精,信道又笃。其乐于闻过而
勇于徙义,则又奋厉明决,无毫发滞吝意。……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义利之间,而后明理居敬以造其极。其剖析开明,倾倒切至,必竭两端而后已。”66友朋之中,朱子为之撰两祭文,撰赞撰碑铭者,南轩一人而已。
(3)朱子与南轩思想之同异
朱子《又祭张敬夫殿撰文》曰:“唯我之与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穷,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是,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乡,而终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挤,而晚得其味。盖缴纷往反者几十余年,末乃同归而一致。”67缴纷往反,皆备于《文集》。所然所议,则详于《语类》。《语类》所言,多关“四书”文句。诸生有疑方问,故异超于同。《文集》所论,乃在基本概念缴纷而卒也同归。以下举其异同之处。总而观之,足以窥见两者之始异终同。南轩《论语解》不取胡寅(字明仲,一〇九八—一一五六)说。朱子不以为然,曰:“若是说得是者岂可废?”68于“三年无改于父之道”69,南轩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朱子与之说,若如此说,则虽终身不改可也。70“子不语怪力乱神”71,南轩以为无,朱子以为有,特不语耳72。南轩解“天下归仁”73为无一物之不体。朱子初与之同。后以文义不然,改作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74南轩解“无适”“无莫”75为“适”是有所必,而“莫”是无所主。朱子则谓无所定亦无所不定尔。76孔子谓犁牛之子亦可用,77南轩作孔子教仲弓用人。以朱子观之,南轩牵合,只要回互,不欲说仲弓之父不肖耳。78南轩以颜回之不改其乐79与孔子之乐在其中80不同。朱子则谓只在深浅之间而已。81南轩分“观过”“知仁”82为二说,朱子以为未甚安帖83。南轩以曾子三省其身84为曾子之所以为仁,在朱子则学者莫非为仁,不必专指此事。85南轩解“仁者能好人”86为仁者为能克己,朱子以克己乃仁87。南轩解“不逆诈”、“不亿不信”88以先觉人情者是能为贤,朱子不以为然。盖知人之诈与不信,谓之先觉,但不先臆度其诈与不信也。89南轩以“知者利仁”90为有所为而为,朱子谓只顺道理而已,不待安排也。91南轩误认《孟子》勿忘勿助长92之意,遂作不当忘,不当助长。不知所谓勿忘勿助者,非立此做的防检,而乃俱无此而皆天理之流行耳。93南轩重视“知皆扩而充之”94之知,朱子谓文势未有此意。“知”字带“广充”而言也。95南轩说“故者以利为本”96以“故”为本然。朱子曰:“如是则善外别有本然。”在朱子,“故”是已然之迹。97
以上均是对南轩之《论语解》与《孟子解》而言。不同之处,当然不止此数。此乃要点而已。其他经书,亦有异议《中庸》云鸢飞鱼跃。98南轩只说能跃之意,故与上文不贯。99南轩说《易》,谓只依孔子《系辞》说便了。朱子则以《系辞》乃所明卦爻之义,故必亦看卦爻而后能理会《系辞》之意。100南轩坚守五峰(胡宏,一一〇六—一一六一)之说,以喜怒哀乐之中101,言众人之常性,而以“寂然不动”102言圣人之道心。朱子则以“寂然不动”,众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103,唯圣人能之104。“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105,两者所解亦异106,南轩谓周子(周敦颐,一〇一七—一〇七三)《太极图说》“无极之真,二(气)五(行)之精”107,不可混说,而“无极之真”,应属上句。朱子报书曰:“若如此则无极之真,自为一物,不与二五相合,而二五之凝,化生万物,又无与乎太极也。”108朱子编《程氏遗书》改若干字。南轩以为有不必改者,亦有不当改者。109南轩以冠礼难行。朱子则以为易。110朱子以南轩说东汉诛宦官事,只是翻誊好看。其实不曾说着当时事体。111
解经之异虽多,唯关于中心问题者甚少。以下则从重要思想,看两者之意见相背者为何。南轩以文章中有性与天道。朱子评之曰:“他太聪敏,便说过了。”112南轩说仁与智都无分别,朱子以之为病。113门人问:明道论生之谓性,既云性善,又谓“恶亦不可不谓之性”114,却言气质之性,与上文不相接。朱子答曰:“不是言气禀之性。正如水为泥沙所混,不成不唤做水。”门人曰:“适所问乃南轩之论。”朱子曰:“敬夫议论出得太早,多有差舛。”115南轩谓心体昭昭为已发,朱子不以为然,已如上述。116南轩之发,是心体无时而不发。及其既发,则当事而存之而为之宰。朱子曰:“心岂待发而为之宰?”117南轩以心无时不虚。既识此心,则用无不利。朱子以为失之太快,流于异学。心固无时不虚,而人欲己私,汨浸久矣。118南轩谓动中见静,方识此心。朱子则谓复119是静中见动,乃见天地之心。南轩却倒说了。120南轩言圣人虽教人以仁,而未尝不本性命以发之。朱子则谓如此是以仁为未足,而又假性命之云以助之也。121南轩以克己在乎致知格物122,朱子则以克己为胜己之私,而谓南轩:“恐只是一时信笔写将去,殊欠商量。”123南轩不信鬼神,而朱子以鬼神为造化之迹。124
综上所述,可见异处无数。唯其有异,故门人疑问,而书札往复,有讨论之必要。恐相同之点而不见于记载者,为数更大,此自然之理也。然亦有记载其相同者。南轩解子路、子贡问管仲,疑其未仁非仁125,故举其功以告之。朱子曰:“此说却当。”126南轩谓汉后当以蜀汉年号继之。朱子赞同。127南轩言胡明仲(胡寅,一〇九八—一一五六)有三大功。朱子谓南轩见得好,128南轩以孔子之出处为“守身之常法,体道之大权”。又云,“欲往者爱物之仁,终不往者,知人之智”。朱子谓其说得分明。129问南轩鬼神一言以蔽之,曰诚而已。此语如何?朱子曰:“诚是实然之理,鬼神亦是实理。”130或曰忠恕,南轩解此云:“圣人全乎此,天之道也”,朱子曰:“此亦说得好。”131此外尚有朱子加以补充而实相同者。南轩言孔明(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其体正大,问学未至。朱子以之为本不知学,全是驳杂,然却有儒者气象。132朱子云:“南轩尝谓太极所以明动静之蕴,盖得之矣。”133门人问南轩云太极之体至静,朱子以为不是134,而其本人亦谓“静即太极之体,动即太极之用”135。盖以门人以南轩只言体而不言用耳。南轩谓为己者,无所为而然也。朱子曰:“此其语意之深切,盖有前贤所未发者。学者以是而自省焉,则有以察于义利之间,而无一毫厘之差矣。”136南轩以《太极图说》之中正仁义137皆有动静。朱子初以为剩语。然细思之,谓:“盖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贞四字。元亨利贞,一通一复,岂得为无动静乎?”138《答友人书》云:“钦夫未发之论,诚若分别太深。然其所谓无者,非谓本无此理,但谓物欲交引,无复澄静之时耳。”139南轩云敬字通贯动静而以静为本,朱子虽主实践,然亦谓闲时静坐些,小也不妨。140南轩云:“行之至则知益明,知既明则行益至。”朱子以为是,但谓工夫当并进。141如是有同有异,此必然之势。
欲知两者之小异而大同,亦即始异而终同,莫善于窥探其讨论握要之处。此处有三:中和之参究、《知言疑义》之附议,与《仁说》之讨论是也。
甲 中和之参究
朱子从延平(李侗,一〇九三—一一六三)得默坐澄心之教,观未发以前气象。唯于心未安。南轩独得五峰之传,为湖湘学派领袖,主先在已发处察识然后存养。朱子特不远千里而访之,以求究竟。据《年谱》,范念德谓“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王懋竑(一六六八—一七四一)以“此语绝无所据”142。然念德当时在场,非道听途说也。考最古之《朱子年谱》,为叶公回所校订(一四三一),“访长沙”条下称:“往复而深相契者,太极之旨也。”但又述念德之言。王懋竑未见叶本而根据洪去芜改订本(一七〇〇),亦谓:“洪本所云深契太极之旨,此以赠行诗与答诗臆度之耳。”143王氏主意在强调二者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之意见相同,此诚是矣。然《中庸》未发之中与已发之和,何以致之?应先察识抑先涵养?则三日讨论,未能归一也。在长沙亦论仁。《语类》云:“问先生旧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否?曰:‘亦有一二处未合。敬夫说本胡氏。胡氏之说,惟敬夫独得之。其余门人皆不晓,但云当守师之说。向来往长沙,正与敬夫辩此。’”144至主张如何,则已不可考矣。
朱子在长沙有书致曹晋叔云:“熹此月八日抵长沙,今半月矣。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论)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岳麓学者渐多。其间亦有气质醇粹,志趣确实者。只是未知方向。往往骋空言而远实理。告语之责,敬夫不可辞也。”145此可为南轩讲学岳麓书院之一证。随后又答石子重〔石〓,绍兴十五年乙丑(一一四五)进士〕云:“熹自去秋之中走长沙,阅月而后至。
留两月而后归。在道缭绕,又五十余日。还家幸老人康健,诸况粗适。他无足言。钦夫见处,卓然不可及。从游之久,反复开益为多。但其天姿明敏。从初不历阶级而得之。故今日语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学子从之游者,遂一例学为虚谈。其流弊亦将有害。比来颇觉此病矣。别后当有以救之。然从游之士,亦自绝难得朴实头理会者。可见此道之难明也。胡氏子弟及他门人,亦有语此者。然皆无实得。拈槌竖拂,几如说禅矣。与文定(胡安国,一〇七四—一一三八)合下门庭,大段相反,更无商量处。惟钦夫见得表里通彻。旧来习见微有所偏。今此相见,尽觉释去,尽好商量也。”146可谓赞美南轩之至。
朱子归后曾与南轩四书,所谓“中和旧说四书”,讨论《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47之问题。此四书,王懋竑定在访长沙之前,即乾道二年丙戌(一一六六),朱子三十七岁。148钱穆则定在乾道四年。149钱氏理由似较充足。第一书云:“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机。虽一日之间,万起万灭。而其寂然之本体,则未尝不寂然也。所谓未发,如是而已。……良心萌蘗,亦未尝不因事而发见。学者于是致察而操存之,则庶乎可以贯乎大本达道之全体而复其初矣。”150此书显示朱子略受湖南影响,渐离延平之默坐求中而趋于湖湘学派之因事省察矣。然究非朱子所寻之答案,故日后自注云:“此书非是。”第二书曰:“兹辱诲喻,乃知尚有认为两物之蔽。……自今观之,只一念间已具此体用。发者方往,而未发者方来,了无间断隔截处。”151张书不存,大抵以朱子分未发已发为两截。故朱子强调体用一源。如是更近于胡五峰之心性如一矣。及后思之,益为不安。故自注云:“此书所论尤乖戾。”第三书曰:“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有一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152者,乃在于此。而前此方往方来之说,正是手忙足乱,无着身处。”153此书比前书前进一步。盖方往方来,乃随逐气化。而今始有主宰也。第四书云:“盖通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物,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者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即夫日用之间,浑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运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动静本末,洞然无一毫之间,而鸢飞鱼跃,触处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养者养此而已。……从前是做多少安排,没顿着处。今觉得如水到船浮,解维正柂,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适矣。”154今心为主宰,纯粹自然。存养之功,乃从容自得。
南轩对此四书之反应,除尚有两物之蔽外,已无可考。《南轩文集》则有两书简单商量。一书云:“中字之说甚密。但在中之义作中外之中未安。……若只说作在里面底道理,然则已发之后,中何尝不在里面乎?”155另一书云:“中者性之体,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状性之体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体。若曰性之体中而其用则和,斯可矣。”156
彼此交换意见,当然互有影响。然亦有坚持己见者。朱子《答程允夫(程洵)》云:“去冬走湖湘,讲论之益不少。然此事须是自做工夫,于日用间行住坐卧处,方自有见处。然后从此操存,以至于极,方为己物尔。敬夫所见,超诣卓然,非所可及。”157言下似有批评湘湖学者向内省察之意。《答林择之》曰:“近得南轩书,诸说皆相然诺。但先察识后涵养之论,执之尚坚。未发已发,条理亦甚明。盖乍易旧说,犹待就所安耳。”158又一书云:“近看南轩文字,大抵皆无前面一截工夫也。大抵心体通有无,该动静。故工夫亦通有无,该动静,方无透漏。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其发处自然中节者多,不中节者少。体察之际,亦甚明审,易为着力。与异时无本可据之说,大不同矣。”159择之在长沙必曾参加此等问题之讨论,故朱子告之如此。
数年之后,朱子四十岁,有《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曰:“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觉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无不中节矣。……故程子(程颐)……以敬为言……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160”此书161将前四书优点,加以敬字为言,而组成有统系之中和论。于是涵养察识,用敬致知,遂为朱子之两轮两翼,三十年丝毫不变。此书虽仍是早年未定之论,然敬义夹持之人生哲学,已于此完成矣。因此有千余言之长书与南轩申明涵养察识,同时并进之旨。“未发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养之实。已发之际是敬也,又常行于省察之间。”又指出仁字,“盖主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者,心也。仁则心之道,而敬则心之贞也。此彻上彻下之道,圣学之本统。明乎此,则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又如所谓学者先须察识端倪之发,然后可加存养之功,则熹于此不能无疑。盖发处固当察识。但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合存养。岂可必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耶?且从初不曾存养,便欲随事察识,窃恐浩浩茫茫,无下手处。”于是结语云:“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敬义夹持,不容间断。”162
乾道八年壬辰(一一七二),朱子撰《中和旧说序》,叙述参究中和之经过。其言曰:“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旨。未达而先生没。余窃自悼其不敏,若穷人之无归。闻张钦夫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焉。钦夫告予以所闻,余亦未之见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寝食。一日,喟然叹曰:人自婴儿以至老死,虽语默动静之不同,然其大体,莫非已发,特其未发者为未尝发尔。……乾道(五年)己丑(一一六九)之春,为友人蔡季通(蔡元定,一一三五—一一九八)言之。问辨之际,予忽自疑。……则复取程氏书虚心平气而徐读之。未及数行,冻解冰释。……亟以书报钦夫及尝同为此论者。惟钦夫复书深以为然。其余则或信或疑,或至于今累年而未定也”163。此指上面与湖南诸公书。钦夫深以为然,独仍主先察识而后存养耳。论者或谓南轩常随朱子脚跟转,恐是过言。
乙《知言疑义》之附议
南轩学于五峰,独得其传。五峰著《知言》。朱子撰《胡子知言疑义》,逐段反驳,与吕祖谦与南轩讨论。164《知言》曰:“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此是朱子所谓“《知言》疑义大端有八”中之“心以用尽”165,恐胡氏混心性为一。故欲改其“以成性”为“统性情”。南轩云:“‘统’字亦恐未安。欲作‘而主性情’,如何?”此说朱子未即接纳。《知言》曰:“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朱子评之曰:“此章即性无善恶之意。若果如此,则性但有好恶而无善恶之则矣。”南轩谓:“好恶性也,此一语无害。……今欲作好恶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循其性者也,小人则以人欲乱之而失其则矣。”朱子驳之曰:“直谓之性则不可。盖好恶,物也。好善而恶恶,物之则也。……今欲语性,乃举物而遗则,恐未得为无害也。”《知言》曰:“人之为道,至大也,至善也。”朱子疑之曰:“若性果无善恶,则何以能若是耶?”南轩释其误会颇详,谓:“专善而无恶者,性也。而其动则为情。……于是而有恶焉。是岂性之本哉?其曰‘恶亦不可不谓之性’166者,盖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尝不在也。”朱子指出明道此语乃说气禀之性而非性之本然。其下数处,南轩或同意朱子,或谓《知言》本语应删去,无甚重要。通篇南轩较东莱议论为多。据《语类》,南轩坚持其师“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不与恶对”167之说。168
丙《仁说》之讨论
朱子祭南轩文“缴纷往反者几十年”之语,虽是泛说,然或针对《仁说》169之讨论而言。朱子与友辈商量《仁说》时期最长,而与南轩错商最多。今《朱子文集》所存讨论《仁说》之书四通,《南轩文集》所存二通。朱子释仁为“心之德,爱之理”170。南轩《论语解》释“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171为“孝弟而始,为仁之道,生而不穷”。朱子评之曰:“此章仁字正指爱之理而言。”172日本学者山崎美成(一七九六—一八五六)据《龙龛手鉴》解仁,谓“心之德,爱之理”原为佛语。173经山口察常(一八八二—一九四八)指出其误。然山口又谓“爱之理”来自南轩。以其《论语解》云:“原人之性,其爱之理,乃仁也。”174山口盖未审《论语解》成于乾道九年癸巳(一一七三)。其时《仁说》已定稿矣。175
朱张往来六书讨论《仁说》,甚为详尽。致钦夫第一书逐句解答。176南轩原书不存,朱子引之。朱子《仁说》首谓:“天地以生物为心。”南轩以此语为未安。朱子坚辨天地只以生物为事。此语未有病也。其后南轩复书云:“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平看虽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为人之心’似完全。”177《仁说》未之改也。南轩谓:“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朱子则谓:“不忍之心包四端,犹仁之可以包四德也。”其后南轩云:“不忍之心虽可以包四者,然据文势对乾元坤元言,恐须只统言之则曰仁而可也。”178南轩以“仁者则其体无不善”,朱子以此为“不知其为善之长”。南轩以“对义礼智而言,其发见则为不忍之心”,朱子以此为未安,盖仁义礼智“根于心,而未发所谓理也”。南轩以“仁之为道,无一物之不体”,朱子以此为“不知仁之所以无所不体”。南轩以“程子之所诃,正谓以爱名仁者”,此乃评《仁说》“程子之所诃,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之语。朱子答之曰:“程子曰:‘仁,性也。爱,情也。岂可便以爱为仁?’此正谓不可认情为性耳。非谓仁之性不发于爱之情,而爱之仁不本于仁之性也。”南轩以元之义不专于生。朱子则以此语恐有大病。盖元为义理根源也。南轩有书复云:“前日所谓元之义不专主于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说生生之义不尽。今详所谓生物者,亦无不尽矣。”179南轩以仁者无所不爱,但有差等。朱子以差等乃义之事:“仁义虽不相离,然其用则各有所主而不可乱也。”
第二论仁之书180乃朱子复南轩接朱子第一书后所来之书181。南轩之书以公为仁之体。公天下而无物我之私,故爱无不溥。朱子则谓:“仁乃性之德而爱之本。……若以公天下而无物我之私便为仁体,则恐所谓公者,漠然无情,但如虚空木石。”第三书专论知觉为仁。182南轩曾有书说知觉为仁。此书不存。朱子复之云:“仁本吾心之德,又将谁使知而觉之耶?……然此亦只是智之发用处。但惟仁者为能兼之。故谓仁者必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第四书与第二书意同,即谓公与物我一体皆非仁体183。
以上辩论,南轩每为朱子所折服。辩论结果,《仁说》亦有所更改。今以答南轩书与《仁说》比较,可知经南轩诘难而改正者。不忍之心可包四者之语已不见《仁说》。《仁说》亦无讨论孟子仁无不爱之文,必是因南轩之批评而删。然于天地生物之心一点,则始终坚持。朱子自谓:“《仁说》只说前一截好。”184谅因下截评物我一体与知觉为仁两说未曾释明其所以非仁之故。朱子为《仁说图》185,特标未发已发与体用,且“公”字两见。或亦与南轩讨论之效也。(参看页三八七“《仁说图》”条)
南轩亦作《仁说》186(参看页三九一“南轩《仁说》”条),曾与朱子《仁说》相混。朱子《仁说》题下附注云:“淅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实则人各一篇。两者《仁说》大意相同。唯克己、去蔽、知存,则南轩《仁说》比朱子《仁说》为详而有力。朱子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仁之两面,南轩则只言“爱之理”而不言“心之德”。朱子有《答钦夫<仁说>》187,对南轩《仁说》初稿,多所批评。予曾论之颇详,兹不复述矣。188(参看页三九一“南轩《仁说》”条)南轩又类聚圣贤言仁处,而以程子等人之意释之,名曰《洙泗言仁》。此书已佚,只存其序。朱子于南轩此举,极不赞同,盖谓圣人不言仁处亦有用,而将使学者欲速好径,而陷于不仁也。189然两者均以仁为道德之高峰,教人汲汲求仁。此其两者末乃同归而一致欤。
附注
1 张浚(一〇九六-一一六四),张栻之父。
2 《语类》卷一〇三,第五十条,页四一四六。
3 江西南昌。
4 南昌之西南。
5 《文集》续集卷五《答罗参议》,页十一下。
6 同上,正集卷二十四《与曹晋叔》,页十四下。
7 即湖南株洲市,或作精州。
8 南轩有《南岳唱酬序》,载《南轩先生文集》(《近世汉籍丛刊》本)卷十五,页一上至三下,总页
五〇五至五一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二》(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页四,总页
四一四八,谓五十七题皆三人同赋,不当云一百四十九。
9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答朱元晦秘书(第四十三书)》,页十上,总页七〇九。
10 同上,卷二十第十一书,页十一上下,总页六五九至六六〇。
11 同上,第十书,页八下,总页六五四。
12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二十七书)》,页十五下。
13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二《答朱元晦秘书(第十书)》,页八下。
14 《文集》卷三十七《与刘共父(第一书)》,页十四上。
15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第十五书)》,页二下至三上,总页六六八至六六九。“逆诈”
出《论语·宪问》第三十三章。“怒发”出《史记》(《四部丛刊》本)卷八十一《蔺相如传》,页一下。
16 同上,卷二十,第二书,页二上,总页六四一;卷二十一,第二十五书,页八上,总页六七九。
17 《周礼·地官·司徒·泉府》。
18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第十一书,页九下,总页六五六。
19 《文集》卷七十七《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页二十四下至二十五上。
20 同上,卷七十九《婺州金华县社仓记》,页十六下。
21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第十一书,页十一上,总页六五九。
22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二十七书)》,页十四下至十五上。
23 同上,卷三十四《答吕伯恭(第八十四书)》,页二十八下。
24 同上,卷三十五《答刘子澄(第七书)》,页十七上。
25 同上,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二十书)》,页九下。
26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第二十书)》,页四下,总页六七二。
27 同上,第二十四书,页八上,总页六七九。
28 同上,第三十一书,页十二上,总页六八八。
29 同上,卷二十三,第五十三书,页八上,总页七二八。
30 同上,第五十六书,页十二上,总页七三五;卷二十四,第七十一书,页十一上,总页七五七。
31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十五书)》,页四下。
32 同上,卷三十《答张钦父(第八书)》,页二十七下。
33 《语类》卷一〇七,第六十一一条,页四二五四。
34 同上,卷九十,第一三二条,页三六八四。
35 同上,卷一〇七,第七十条,页四二五七。
36 同上,卷一〇三,第五十条,页四一四九。
37 同上,卷一四〇,第五十四条,页五三五〇。
38 同上,第九十四条,页五三五八。
39 同上,卷一三九,第五十条,页五三一三。
40 同上,卷一〇三,第四十五条,页四一四三。
41 同上,卷一二五,第六十二条,页四八一一。
42 同上,卷一四〇,第九十五条,页五三五九。
43 同上,卷四十四,第九十七条,页一八一一。
44 同上,卷一〇三,第三十五条,页四一四〇。
45 同上,第三十六条,页四一四一。
46 同上,卷六十二,第一三三条,页二四〇一。
47 同上,卷九十四,第十八条,页三七六二。
48 《文集》卷三十八《答詹体仁》,页三十八下。
49 《语类》卷九十五,第三十九条,页三八五一。
50 《文集》卷五十六《答方宾王(第五书)》,页十五上。
51 《语类》卷九十三,第六十条,页三七四四。
52 《文集》卷二十五《答张敬夫(第一书)》,页二下。
53 《语类》卷一二四,第五十四条,页四七七七。
54 同上,第二十五条,页四七六二。
55 《文集》卷五十《答郑仲礼(第一书)》,页二十三下。
56 《语类》卷一〇三,第三十三条,页四一四〇。
57 同上。
58 《语类》卷三十一,第六十六条,页一二七九。
59 《文集》卷二十四《与曹晋叔》,页十四下。
60 同上,卷四十《答何叔京(第十一书)》,页二十四上。
61 《语类》卷一〇八,第四十四条,页四二七一至四二七二。
62 《文集》卷八十七《祭张敬夫殿撰文》,页八下。
63 同上,《又祭张敬夫殿撰文》,页九下。
64 同上,卷三十四《答吕伯恭(第八十三书)》,页二十五上。
65 同上,卷八十五《张敬夫画像赞》,页十上。
66 同上,卷八十九《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页八下。
67 《文集》卷八十七《又祭张敬夫殿撰文》页九下。
68 《语类》卷十九,第六十七条,页七〇五。
69 《论语·学而》,第十一章。
70 《语类》卷二十二,第二十九条,页八二五;第三十条,页八二七。
71 《论语·述而》,第二十章。
72 《语类》卷八十三,第九十九条,页三四三八。
73 《论语·颜渊》,第一章。
74 《语类》卷四十一,第九十条,页一七〇二。
75 《论语·里仁》,第十章。
76 《语类》卷二十六,第九十七条,页一〇六六;卷一一三,第三十二条,页四三七八。
77 《论语·雍也》,第四章。
78 《语类》卷三十一,第七条,页一二五一。
79 《论语·雍也》,第九章。
80 《论语·述而》,第十五章。
81 《语类》卷三十一,第六十五条,页一二七八。
82 《论语·里仁》,第七章。
83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十六书)》,页五下。
84 《论语·学而》,第四章。
85 《文集》卷三十一,第二十一书,页十下。
86 《论语·里仁》,第三章。
87 《文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页二十四下。
88 《论语.宪问》,第三十三章。
89 《语类》卷四十四,第七十六条,页一八〇二。
90 《论语·里仁》,第二章。
91 《语类》卷二十六,第九条,页一〇三二。
92 《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
93 《语类》卷六十三,第七十五条,页二四三七。
94 《孟子·公孙丑》上,第六章。
95 《语类》卷五十三,第六十三条,页二〇五一。
96 《孟子·离娄》下,第二十六章。
97 《语类》卷五十七,第五十九条,页二一四五。
98 《中庸》,第十二章。
99 《语类》卷六十三,第八十条,页二四三九。
100 同上,卷六十七,第七十三条,页二六四六。参看卷七十二,第八十条,页二九一七;卷七十,第一三三条,页二八〇九;卷六十,第七条,页二五七八。《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三《答朱元晦秘书(第四十四书)》,页二下,总页七一六。
101 《中庸》,第一章。
102 《易经·系辞上传》,第十章。
103 同上。
104 《语类》卷九十五,第二条,页三八三三至三八三四。
105 《易经·系辞上传》,第四章。
106 《语类》卷九十四,第一〇六条,页三七八九。
107 《周子全书》(《国学基本丛书》本)卷一《太极图说》,页十四。
108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十二书)》,页二下至三上。
109 同上,卷三十《与张钦夫论程集改字》,页二十三上;《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第十五书)》,页二上,总页六六七。
110 《语类》卷八十九,第三条,页三六〇三。
111 同上,卷一三五,第六十九条,页五一八六。
112 同上,卷四十四,第九十七条,页一八一一。
113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十七书)》,页六上。
114 《遗书》(《四部备要·二程全书》本)卷一,页七下。
115 《语类》卷九十五,第三十九条,页三八五一。
116 《语类》卷六十二,第一三三条,页二四〇一。参看《语类》卷九十七,第一二二条,页三九八〇。
117 《文集》卷三十《答张钦夫(第二书)》,页十八上下。
118 《语类》卷一〇〇,第四十六条,页四〇五四。
119 《易经》,第二十四卦。
120 《语类》卷一〇三,第四十三条,页四一四二。
121 《文集》卷三十《答张钦夫(第九书)》,页二十八下。
122 《南轩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克斋铭》,页二上,总页一〇五五。
123 《语类》卷四十一,第十七条,页一六六五。
124 同上,卷三,第十九条,页五十八。
125 《论语·宪问》,第十七、十八章。
126 《语类》卷四十四,第五十四条,页一七九三。
127 同上,卷一〇五,第五十五条,页四一九〇。
128 同上,卷一〇一,第一四四条,页四一〇三。
129 同上,卷四十七,第二十三条,页一八八一。
130 同上,卷六十三,第一三〇条,页二四六二。
131 同上,卷二十七,第八十三条,页四。
132 同上,卷一三六,第六条,页五一九二。
133 《文集》卷四十五《答吴德夫》,页十一上。
134 《语类》卷九十四,第四十三条,页三七七一。
135 同上,第二十九条,页三七六六。
136 《大学或问》(《近世汉籍丛刊》本),页九上下,总页十七至十八。参看《语类》卷十七,第四十五条,页六一六。
137 《周子全书》卷二《太极图说》,页二十三。
138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十六书)》,页五下至六上。
139 同上,卷四十二《答胡广仲(第一书)》,页一上。
140 《语类》卷二十六,第六十三条,页一〇五四。
141 同上,卷一〇三,第三十九条,页四一四一;卷九,第五条,页二三五至二三六。
142 《朱子年谱·考异》(《丛书集成》本)卷一,页二五八。
143 同上,页二五七。
144 《语类》卷一〇三,第四十一条,页四一四二。
145 《文集》卷二十四《与曹晋叔》,页十四下至十五上。
146 《文集》卷四十二《答石子重(第五书)》,页二十二下至二十三上。
147 《中庸》,第一章。
148 《朱子年谱》卷一上,页二十三至二十五。
149 《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一九七一)第二册,页一三四、一四〇、一六〇。
150 《文集》卷三十《与张钦夫(第三书)》,页十九上下。
151 同上,第四书,页二十上。
152 程颐《易传序》。
153 《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第三十三书)》,页四上下。
154 《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第三十四书)》,页五上下。
155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秘书(第五书)》,页四上下,总页六四五至六四六。
156 同上,第六书,页五下,总页六四八。
157 《文集》卷四十一《答程允夫(第五书)》,页十七上下。
158 同上,卷四十三《答林择之(第三书)》,页十八上。
159 同上,第二十二书,页三十下。
160 《遗书》卷十八,页五下。
161 《文集》卷六十四,页二十八下至二十九上。卷六十七,页十上。其“已发未发记”文句相同,是其初稿。予已将此书译英,载拙著A SourceBooKin Chinese PhilosoPhy(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63),页六〇〇至六〇二。
162 同上,卷三十二《答张钦夫(第四十七书)》,页二十五下至下二十六上。“互为其根”,引周子《太极图说》。“夹持”引《遗书》,卷五,页二下。
163 同上,卷七十五,页二十二下至二十三下。
164 《文集》卷七十三,页四十上至四十七下。《疑义》所述五峰之语,皆不复出《胡子知言》六卷。东莱南轩所言,亦不见其两人文集。
165 《语类》卷一〇一,第一五四条,页四一〇四。
166 《遗书》卷一页七下《明道论性》。
167 《文集》卷七十三《胡子知言疑义》,页四十四上。
168 《语类》卷一〇三,第四十二条,页四一四二。
169 《文集》卷六十七,页二十上至二十一下。
170 《论语集注·学而》,第二章;《孟子集注·梁惠王》上,第一章。
171 《论语·学而》,第二章。
172 《文集》卷三十一《与张敬夫论癸巳论语说》,页二十一下。
173 详见拙著《朱学论集·论朱子之<仁说>》(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二),页四十二至四十八。
174 同上。南轩注《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第二十二章。参看山口察常《仁之研究》(东京岩波书店,一九三六),页三七〇至三七三。
175 《详朱学论集》,页四十三。
176 《文集》卷三十二《答张敬夫论<仁说>》,页十六上至十八下。
177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第二十一书)》页五下,总页六七四。
178 同上,卷二十,第九书,页七下。
179 同上。
180 《文集》卷三十二《又论<仁说>》,页十九上下。
181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第二十一书)》,页五下至六上,总页六七四至六七五。
182 《文集》卷三十二《又论<仁说>》,页二十上下。
183 同上,《又论<仁说>》,页二十一上下。《朱学论集》,页五十一至五十四,讨论“四书”较详。
184 《语类》卷一〇五,第四十二条,页四一八二。
185 同上,第四十三条,页四一八五。
186 《南轩先生文集》卷十八,页一上至二上,总页五九一至五九二。
187 《文集》卷三十二《答钦夫<仁说>》,页二十三下至二十四F。
188 《朱学论集》,页五十七至五十八。
189 《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第十八书)》,页七下。《语类》卷一〇三,第四十八条,页四一四二;卷一一八,第四十七条,页四五五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