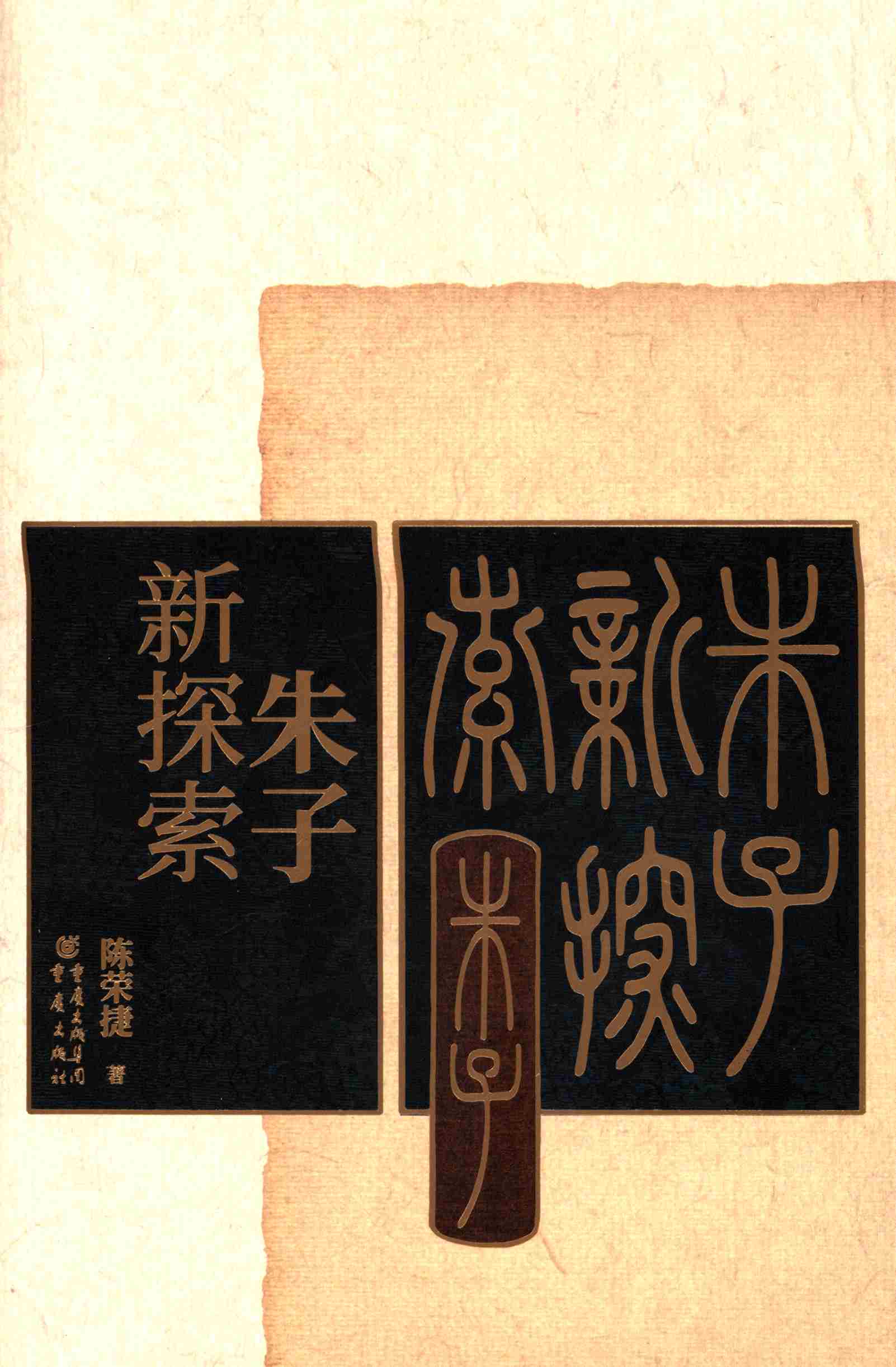【五九】 南轩《仁说》
| 内容出处: | 《朱子新探索》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130 |
| 颗粒名称: | 【五九】 南轩《仁说》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7 |
| 页码: | 391-39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张栻在《仁说》中探讨了人性中的仁、义、礼、智四德,认为它们是人性的根源,并指出仁是其中最重要的德行。他认为人性中只有这四德,而仁作为其中的核心可以兼容其他三者。仁的实现需要克己,只有克己才能达到大公无私的境界,并使爱之理不被蒙蔽,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爱之理即仁,公是能够实现仁的基础。仁同时包含了恭让有节的礼和知觉不昧的智。张栻认为学者应该把追求仁作为最重要的目标,并通过克己来实现仁。 |
| 关键词: | 张栻 仁说 人性 |
内容
张栻(一一三三—一一八〇)尝著《仁说》,载《南轩先生文集》。兹录全文如下:
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理,则智也。是四者,虽未形见,而其理固根于此,则体实具于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谓爱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发见于情,则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而所谓恻隐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为不仁,甚至于为忮为忍。岂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爱之理无所蔽,则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其用亦无不周矣。故指爱以名仁,则迷其体。(程子所谓“爱是情,仁是性”1,谓此。)而爱之理,则仁也。指公以为仁,则失其真。(程子所谓“仁道难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为仁”2,谓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静而仁义礼智之体具,动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达。其名义位置,固不容相夺伦,然而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恭让而有节,是礼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知觉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见其兼能而贯通者矣。是以孟子于仁,统言之曰:“仁,人心也。”3亦犹存《易》乾坤四德,而总言“乾元”“坤元”也。4然则学者其可不以求仁为要,而为仁其可不以克己为道乎?5
此文尝与朱子《仁说》相混。《朱子文集·仁说》题下注云:“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6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夏威夷举行国际朱熹会议,日本佐藤仁教授在其提供论文《朱子之<仁说>》中指出陈淳(一一五九—一二二三)谓:“文公有《仁说》二篇……一篇误在《南轩文集》中。”朱子门人熊节〔庆元五年己未(一一九九)进士〕编《性理群书句解》,亦采录此篇以为朱子自著。7可知朱门亦有误以南轩《仁说》为朱子所作者云云。愚亦以南轩《仁说》非朱子所撰。尝著《论朱子之<仁说>》,第九节专论南轩《仁说》,指出两《仁说》相同之点甚多,唯克己、去私、知存,则南轩比朱子为详而有力。最不同者,则朱子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仁之两面,而南轩则只言爱之理而不言心之德。愚又根据朱子《答伯恭(吕祖谦,称东莱先生)》,指出南轩《仁说》成于朱子《伊洛渊源录》之后8,而朱子《仁说》在《渊源录》成书之前9。故以朱子《仁说》在前,南轩《仁说》在后,并解释何以在朱子《仁说》之后,另著《仁说》。10今尚有一重要之点,不容忽略者,即朱子《仁说》开始即谓“天地以生物为心”11,而南轩《仁说》则文内只云“天地生物之心”。此为两人争论焦点之一。南轩尝批评朱子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云:“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平看虽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为人之心似完全。”12此其《仁说》所以不言“天地以生物为心”而言“天地生物之心”也。
国际朱熹会议以时间短迫,未及详细讨论佐藤教授所宣读之《朱子之<仁说>》。拙著《论朱子之<仁说>》虽然一年以前发表,与会学者曾见之者,究属少数,而《朱学论集》新在台北出版,尚未寄到会所。年初刘述先博士之《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已由台北学生书局刊行。内有专章讨论朱子《仁说》。惜以邮误,亦未寄到会场。吾等三人俱于朱子《仁说》,相当努力。苟能从容切磋,陶养新知,则其乐也何似!惜时间无多。予亦因主理会务,绝无宁暇。目视良机之失,今日思之,犹叹息不置也。
会后刘博士撰《朱子的仁说、太极观念与道统问题的再省察——参加国际朱子会议归来纪感》,载于《史学评论》。13关于《仁说》,刘博士集中于朱子《仁说》之著作时期与南轩《仁说》两点。刘先生坚持其朱子《仁说》定稿于乾道九年癸巳(一一七三),比愚以其定稿在乾道七年辛卯(一一七一)较后。刘先生在其新著内之《朱子对于仁的理解与有关<仁说>的论辨》章有详细讨论。14此问题牵涉太大,非另行为文探索,恐难言尽其意。今只论关于南轩之《仁说》。
刘先生提出惊人之论,谓南轩《仁说》乃朱子所作,加上南轩之名,编入《南轩文集》以纪念亡友。刘先生云:
指出《南轩文集》全部由朱子编次。朱子把《南轩文集》中凡不合于他自己思路的书信文章,当作南轩少年时代不成熟的东西看待,全部加以删削。是否有可能南轩撰《仁说》初稿受到朱子批评之后,一直未定稿。他死后朱子乃把自己与南轩共同商订以后另写的一篇《仁说》,编在《南轩文集》之中,当作南轩的作品而刻出。所以有的门人如陈淳、熊节还把这篇《仁说》认定为朱子的作品。就我的了解来说,要不是这样的情形,在朱子的及门弟子就产生了这样的混淆,根本是不可以想象的事。当然,佐藤先生大概由于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根本没有对我提出的问题给予任何答复。陈(荣捷)先生代为答复,乃谓陈淳当时不在朱子跟前,熊节的理解甚差,所以才会产生了这样的混淆。但这样的答复对我来说,是不能满足的。陈淳为朱子最得意的晚年弟子,“卫师甚力”(全祖望语)。他既然斩钉截铁地说朱子著有两篇《仁说》,应有所据。大概朱子写了另一篇《仁说》,接受了南轩的批评,把克己的观念写入文章之中,又采用了南轩的“天地万物血脉贯通”一类的话头。为了纪念亡友,就把这篇东西当作南轩的定见,编入《南轩文集》之内。这种情形,绝不是不可以想象的。15
如此云云,诚是大胆假设。苟能找出证据,则不愧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发现。刘博士并不武断,彼云:“我生平不擅考据。对于哲学思想一贯性的把握则略有一点心得。此处暂姑备一说,以待来贤校正。”16愚不敢以贤自待,加以校正。今只提出四点,以供研究。
(1)熊节之《性理群书句解》列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为七贤之一。朱子于竹林精舍落成,行释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司马光等七贤从祀。熊氏继承此意,可谓无后来门户之见矣。然其书究为训课童蒙而设,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浅近之甚,殊无可采”17。陈淳诚为朱门高弟。其所著《北溪字义》,实足以代表朱子纯正思想。然彼庚戌(绍熙元年,一一九〇)十一月乃师事朱子。距《仁说》之著已二十年。《仁说》讨论,早已沉寂。当时著者多次易稿。各家著作,抄写传递之间,名称或有混乱。陈淳以其师有两《仁说》,殊不足怪。陈淳答陈伯澡书有云:“文公有《仁说》二篇。莫须已曾见否?一篇误在《南轩文集》中。一篇近方得温陵18卓丈传来。”19可知彼对于朱子《仁说》及其讨论经过,素未详悉。是则南轩《仁说》之不能出于朱子之手,陈淳无从而辨也。
(2)陈淳发觉《仁说》两篇并存之时间,与《朱子文集》编辑之时间,当相隔不远。《朱子文集》为朱子之子朱在(一一六九年生)等所编,与陈淳见《仁说》之时期相去不远。彼等谓“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是则当时有人以南轩《仁说》为朱子所作,亦有人以南轩《仁说》为非朱子所作。编《文集》者不以南轩《仁说》出于朱子。彼等必代表多数而比较可靠。吾人生在数百年之后,苟任信其一,则非《文集》编者莫属。
(3)若谓朱子既自著《仁说》,又以南轩本人之意替之另撰《仁说》,故此《仁说》特重南轩之克己。又接受南轩之批评,不用自己
开章明义之“天地以生物为心”,而用南轩认为“似安全”之“天地生物之心”,更不用数十年所考虑周详之“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而只用“爱之理”以之纪念亡友。然则所谓纪念者何在?南轩讨论《仁说》,已详其与朱子来往书简。20其克己之说,详与朱子书21《克斋铭》22。
与《主一斋铭》23。朱子何必越俎代庖,徒作赘语?至于南轩本人何以又于朱子已著《仁说》之后,自著《仁说》,亦有可解。拙文《论朱子之<仁说>》尝云:盖南轩认仁乃是天地之心所由生,但不认天地以生物为心,故不言心之德。朱子《仁说》侧重理论。虽言学者应汲汲于求仁,究于求仁之方,未有畅言。南轩则并言仁者之能推以至存义、存礼、存智。尤重要者,南轩以为仁莫要于克己,学者当以克己为道。朱子《仁说》虽引《论语》克己一次,顺及而已,非要义也。朱子谓南轩以其《仁说》不如《克斋记》24,即谓朱子忽略克己为仁之方,或亦为其自作《仁说》之一因,以补朱子之不足耳。且当《仁说》讨论热烈之际,学者如林熙之、周叔瑾、杨仲思、“契丈”等,均著《仁说》25,各扬其说。南轩其中之一耳。
(4)最重要者,乃此等间接手段,是否与朱子性格相符?朱子性素忠直,其感化士子者以此,其开罪权贵者亦以此。生平有如程子明道(程颢),最恨自私用智。今以另著《仁说》插入《南轩文集》之内作为南轩自作,可谓绝非自私,然不得不谓之用智也。此则朱子决不肯为而亦南轩所决不肯受也。
人之性,仁、义、礼、智四德具焉。其爱之理,则仁也;宜之理,则义也;让之理,则礼也;知之理,则智也。是四者,虽未形见,而其理固根于此,则体实具于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万善皆管乎是焉。而所谓爱之理者,是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为四德之长,而又可以兼包焉。惟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发见于情,则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之端,而所谓恻隐者,亦未尝不贯通焉。此性情之所以为体用,而心之道则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之,以失其性之理,而为不仁,甚至于为忮为忍。岂人之情也哉?其陷溺者深矣。是以为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则廓然大公,而其爱之理,素具于性者,无所蔽矣。爱之理无所蔽,则与天地万物血脉贯通,而其用亦无不周矣。故指爱以名仁,则迷其体。(程子所谓“爱是情,仁是性”1,谓此。)而爱之理,则仁也。指公以为仁,则失其真。(程子所谓“仁道难名,惟公近之。不可便指公为仁”2,谓此。)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夫静而仁义礼智之体具,动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端达。其名义位置,固不容相夺伦,然而惟仁者,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义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恭让而有节,是礼之所存者也。惟仁者为能知觉而不昧,是智之所存者也。此可见其兼能而贯通者矣。是以孟子于仁,统言之曰:“仁,人心也。”3亦犹存《易》乾坤四德,而总言“乾元”“坤元”也。4然则学者其可不以求仁为要,而为仁其可不以克己为道乎?5
此文尝与朱子《仁说》相混。《朱子文集·仁说》题下注云:“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而以先生《仁说》为序。”6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夏威夷举行国际朱熹会议,日本佐藤仁教授在其提供论文《朱子之<仁说>》中指出陈淳(一一五九—一二二三)谓:“文公有《仁说》二篇……一篇误在《南轩文集》中。”朱子门人熊节〔庆元五年己未(一一九九)进士〕编《性理群书句解》,亦采录此篇以为朱子自著。7可知朱门亦有误以南轩《仁说》为朱子所作者云云。愚亦以南轩《仁说》非朱子所撰。尝著《论朱子之<仁说>》,第九节专论南轩《仁说》,指出两《仁说》相同之点甚多,唯克己、去私、知存,则南轩比朱子为详而有力。最不同者,则朱子以心之德爱之理为仁之两面,而南轩则只言爱之理而不言心之德。愚又根据朱子《答伯恭(吕祖谦,称东莱先生)》,指出南轩《仁说》成于朱子《伊洛渊源录》之后8,而朱子《仁说》在《渊源录》成书之前9。故以朱子《仁说》在前,南轩《仁说》在后,并解释何以在朱子《仁说》之后,另著《仁说》。10今尚有一重要之点,不容忽略者,即朱子《仁说》开始即谓“天地以生物为心”11,而南轩《仁说》则文内只云“天地生物之心”。此为两人争论焦点之一。南轩尝批评朱子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云:“天地以生物为心之语,平看虽不妨。然恐不若只云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为人之心似完全。”12此其《仁说》所以不言“天地以生物为心”而言“天地生物之心”也。
国际朱熹会议以时间短迫,未及详细讨论佐藤教授所宣读之《朱子之<仁说>》。拙著《论朱子之<仁说>》虽然一年以前发表,与会学者曾见之者,究属少数,而《朱学论集》新在台北出版,尚未寄到会所。年初刘述先博士之《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已由台北学生书局刊行。内有专章讨论朱子《仁说》。惜以邮误,亦未寄到会场。吾等三人俱于朱子《仁说》,相当努力。苟能从容切磋,陶养新知,则其乐也何似!惜时间无多。予亦因主理会务,绝无宁暇。目视良机之失,今日思之,犹叹息不置也。
会后刘博士撰《朱子的仁说、太极观念与道统问题的再省察——参加国际朱子会议归来纪感》,载于《史学评论》。13关于《仁说》,刘博士集中于朱子《仁说》之著作时期与南轩《仁说》两点。刘先生坚持其朱子《仁说》定稿于乾道九年癸巳(一一七三),比愚以其定稿在乾道七年辛卯(一一七一)较后。刘先生在其新著内之《朱子对于仁的理解与有关<仁说>的论辨》章有详细讨论。14此问题牵涉太大,非另行为文探索,恐难言尽其意。今只论关于南轩之《仁说》。
刘先生提出惊人之论,谓南轩《仁说》乃朱子所作,加上南轩之名,编入《南轩文集》以纪念亡友。刘先生云:
指出《南轩文集》全部由朱子编次。朱子把《南轩文集》中凡不合于他自己思路的书信文章,当作南轩少年时代不成熟的东西看待,全部加以删削。是否有可能南轩撰《仁说》初稿受到朱子批评之后,一直未定稿。他死后朱子乃把自己与南轩共同商订以后另写的一篇《仁说》,编在《南轩文集》之中,当作南轩的作品而刻出。所以有的门人如陈淳、熊节还把这篇《仁说》认定为朱子的作品。就我的了解来说,要不是这样的情形,在朱子的及门弟子就产生了这样的混淆,根本是不可以想象的事。当然,佐藤先生大概由于语言表达能力的限制,根本没有对我提出的问题给予任何答复。陈(荣捷)先生代为答复,乃谓陈淳当时不在朱子跟前,熊节的理解甚差,所以才会产生了这样的混淆。但这样的答复对我来说,是不能满足的。陈淳为朱子最得意的晚年弟子,“卫师甚力”(全祖望语)。他既然斩钉截铁地说朱子著有两篇《仁说》,应有所据。大概朱子写了另一篇《仁说》,接受了南轩的批评,把克己的观念写入文章之中,又采用了南轩的“天地万物血脉贯通”一类的话头。为了纪念亡友,就把这篇东西当作南轩的定见,编入《南轩文集》之内。这种情形,绝不是不可以想象的。15
如此云云,诚是大胆假设。苟能找出证据,则不愧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发现。刘博士并不武断,彼云:“我生平不擅考据。对于哲学思想一贯性的把握则略有一点心得。此处暂姑备一说,以待来贤校正。”16愚不敢以贤自待,加以校正。今只提出四点,以供研究。
(1)熊节之《性理群书句解》列司马光(一〇一九—一〇八六)为七贤之一。朱子于竹林精舍落成,行释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司马光等七贤从祀。熊氏继承此意,可谓无后来门户之见矣。然其书究为训课童蒙而设,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浅近之甚,殊无可采”17。陈淳诚为朱门高弟。其所著《北溪字义》,实足以代表朱子纯正思想。然彼庚戌(绍熙元年,一一九〇)十一月乃师事朱子。距《仁说》之著已二十年。《仁说》讨论,早已沉寂。当时著者多次易稿。各家著作,抄写传递之间,名称或有混乱。陈淳以其师有两《仁说》,殊不足怪。陈淳答陈伯澡书有云:“文公有《仁说》二篇。莫须已曾见否?一篇误在《南轩文集》中。一篇近方得温陵18卓丈传来。”19可知彼对于朱子《仁说》及其讨论经过,素未详悉。是则南轩《仁说》之不能出于朱子之手,陈淳无从而辨也。
(2)陈淳发觉《仁说》两篇并存之时间,与《朱子文集》编辑之时间,当相隔不远。《朱子文集》为朱子之子朱在(一一六九年生)等所编,与陈淳见《仁说》之时期相去不远。彼等谓“浙本误以南轩先生《仁说》为先生《仁说》”。是则当时有人以南轩《仁说》为朱子所作,亦有人以南轩《仁说》为非朱子所作。编《文集》者不以南轩《仁说》出于朱子。彼等必代表多数而比较可靠。吾人生在数百年之后,苟任信其一,则非《文集》编者莫属。
(3)若谓朱子既自著《仁说》,又以南轩本人之意替之另撰《仁说》,故此《仁说》特重南轩之克己。又接受南轩之批评,不用自己
开章明义之“天地以生物为心”,而用南轩认为“似安全”之“天地生物之心”,更不用数十年所考虑周详之“仁者,心之德、爱之理”,而只用“爱之理”以之纪念亡友。然则所谓纪念者何在?南轩讨论《仁说》,已详其与朱子来往书简。20其克己之说,详与朱子书21《克斋铭》22。
与《主一斋铭》23。朱子何必越俎代庖,徒作赘语?至于南轩本人何以又于朱子已著《仁说》之后,自著《仁说》,亦有可解。拙文《论朱子之<仁说>》尝云:盖南轩认仁乃是天地之心所由生,但不认天地以生物为心,故不言心之德。朱子《仁说》侧重理论。虽言学者应汲汲于求仁,究于求仁之方,未有畅言。南轩则并言仁者之能推以至存义、存礼、存智。尤重要者,南轩以为仁莫要于克己,学者当以克己为道。朱子《仁说》虽引《论语》克己一次,顺及而已,非要义也。朱子谓南轩以其《仁说》不如《克斋记》24,即谓朱子忽略克己为仁之方,或亦为其自作《仁说》之一因,以补朱子之不足耳。且当《仁说》讨论热烈之际,学者如林熙之、周叔瑾、杨仲思、“契丈”等,均著《仁说》25,各扬其说。南轩其中之一耳。
(4)最重要者,乃此等间接手段,是否与朱子性格相符?朱子性素忠直,其感化士子者以此,其开罪权贵者亦以此。生平有如程子明道(程颢),最恨自私用智。今以另著《仁说》插入《南轩文集》之内作为南轩自作,可谓绝非自私,然不得不谓之用智也。此则朱子决不肯为而亦南轩所决不肯受也。
附注
1 《遗书》(《四部备要·二程全书》本)卷十八,页一上。
2 同上,卷三,页三下。
3 《孟子·告子》上,第十一章。
4 《易经·乾卦·彖辞》云:“乾,元亨利贞。”《彖传》日:“大哉乾元。”《坤卦·彖辞》日:“至哉坤元。”
5 《南轩先生文集》(《近世汉籍丛刊》本)卷十八,页一上至三上,总页五九一至五九五。
6 《文集》卷六十七,页二十上。
7 《性理群书句解》(《近世汉籍丛刊》本)卷八,页八上全十下,总页三六七至三七二。
8 此文先刊于《哲学与文化》第八期(一九八一年六月),旋采入拙著《朱学论集》(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二),页二十七至六十八。关于以上各点,参看页五十六。
9 同上,页四十。
10 同上,页五十七。
11 程颐语。《外书》(《二程全书》本)卷三,页一上。明沈桂《明道全书》以此为程颢语。
12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第二十一书)》,页五下,总页六七四。
13 《史学评论》第五期(一九八三年一月),页一七三至一八八。
14 《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一九八〇),第四章。
15 《史学评论》(第五期,一九八三年一月),页一七九至一八〇。
16 《史学评论》(第五期,一九八三年一月),页一八一。
1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儒家类二》(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总页一九一九。
18 福建泉州。
19 《北溪大全集》(《四书全书》本)卷二十六《答陈伯澡(第五书)》,页五下。
20 《南轩先生文集》卷二十《答朱元晦秘书(第七书)》,页七上下,总页六五一至六五二;卷二十一《答朱元晦秘书(第十九书)》,页五下,拙著《朱学论集》,页五十一至五十三,讨论颇详。
21 同上,卷二十《答朱元晦秘书(第十一书)》,页十二上下。
22 同上,卷三十六;页一下至二上,总页一〇五四至一〇五五。
23 《元晦秘书(第十九书)》,页六上下,总页一〇六三至一〇六四。
24 《文集》卷七十七,页十五上至十六上。
25 《朱学论集》,页三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