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007 |
| 颗粒名称: | 博士论文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9 |
| 页码: | 244-25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子学研究博士论文的情况。其中包括“心法”即“心学”、理学的发生、中日韩《孟子》学研究等。 |
| 关键词: | 朱子学 博士论文 研究 |
内容
“心法”即“心学”
赵玫(山东大学2020年,导师:沈顺福教授)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划分,已成为学界共识。以“心学”称朱子学,似犯下指鹿为马的错误。然而,从文献依据与义理依据两方面看,朱子心学的提法是公允且必要的。
从文献依据上看,自朱子之后以至于明弘治(1488—1505),不以“心学”与“理学”之称法作派系划分,朱学也被称为“心学”。嘉靖年(1522—1566),出现“心学”独指阳明学之论。万历年(1573—1620),邓元锡作《皇明书》,视阳明学为儒家正宗,称心学。清黄梨洲父子编订《宋元学案》,更彰明“心学”、“理学”二分,以“心学”独指陆王学之见。由此可见,“心学”与“理学”的划分,最初是带有门户之见的,沿用这一划分,会陷入门户争论之窠臼。
学者历来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判分朱学为“理学”,陆王为“心学”,从义理上反思这一判分显得非常重要。反思的前提是对“心即理”与“性即理”的定位,这两个命题不仅是本体论问题,亦为工夫论问题。就此,朱陆之学有同异。将太极与理视作理论基础与目标指向,是二人学问之同。从实然心的定位与功能来看,陆王直接以心为性体,属形而上者,则相应的工夫路径简易径直,朱子严判性、心为形而上、下,同时又看到心的超越性与有限性两个面向,则心能自明、自觉、自立,并落实为细密严缜的心地工夫,此为二人之异。总之,朱子强调终极本体为性而非心,此即“性即理”,故为“性本论”。但他同时强调在本然与境界中,有限之心具超越性,实现心理无间与心体流行,此即“心即理”,故朱子之“性即理”涵摄了“心即理”。因此,不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严判朱、陆为“理学”与“心学”。
朱子学为传道之学,亦为传心之学,此即“道学”,亦为“心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与“心学”,乃至于“理学”、“性学”不是对立存在,而是共同包含在任何派别的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当中。
传心之学即传心法之学,它包括言心之学、修心之法,因此,心法即心学。朱子心学有内在结构,这反映在朱子对《中庸》首章的训释中。这一结构包括了宇宙本体论(从“本原”到“实体”)、基于心性论的工夫论(“存养省察之要”)、境界论(“圣神功化之极”)三大部分。朱子对《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的诠释,是心学的总论。
在天而言,“天命”作为“本原”;在人而言,“人性”作为“实体”。天人一贯,是作为形而上之理的“天命”与“人性”的一贯,这一过程必须在理气共同作用下完成,含理之气则为心,或称为“天地之心”,这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阐释心学。
一方面,朱子论“天地之心”有别于汉唐儒视“天地之心”为经验化、人格化的存在,又不同于王弼由“动息地中”见得静与默,从而复归本体的解释。朱子光大了自唐宋以来儒家宇宙本体论自觉的星火,回归了儒家经典的原意,同时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诠释系统。朱子对程颐、邵雍、程颢“天地之心”说的诠释,呈现了“天地之心”是理气圆融无间、生生流行这一特点。天地之心统天地之性、天地之情,这与人生论中“心统性情”架构相吻合。
另一方面,理气关系与天地之心可以互释。理的四种训义与“天地无心”与“天地有心”对应:理之能然、必然说明理决定气之主宰与运作,而见得天地生物造物的能力,可知天地有心;理之当然、自然说明天地之心的生生不已,万物生化自然有序,可知天地无心。可见,从天地之心入手,可以诠释朱子的理气观,并突出理气圆融的生生之意。
再一方面,朱子言仁,有指体、指用、统摄体用三种情况。统体之仁包体用,贯天人。在天而言,统体之仁即天地之心,其包天地之“性”与“情”,它不但指元、亨、利、贞四天德,也包含春、夏、秋、冬四季。在人而言,统体之仁即人心,其体为仁、义、礼、智四人德,发用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四端。因此,仁是贯通天人的关窍,天地之心亦然。由此获得两点结论:一则,天地之心与仁一样,是一元之气的流行生化不已,其具备内在自足的善性而表现出生物不已、温然爱人利物的特点。二则,“心学”与“仁学”、“气学”在朱子思想中具有了同等地位,朱子的“仁学”即“心学”。
朱子中和新旧说的转变即旧的心学转向新的心学,这是朱子“心学”的人生论说明,它包括心性本体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部分,三部分相互交融。
从中和旧说形成过程上来看,大致分为四个小阶段。朱子师从李延平期间,他对延平默坐澄心之旨不能契合,此时中和旧说初具雏形;隆兴二年甲申,朱子赴豫章哭祭张浚并见张栻,他极认可张栻涵养察识于已发的工夫,更加固了旧说的认识;乾道二年丙戌,朱子与张栻书信讨论中和问题,标志中和旧说成形;乾道三年丁亥春,朱子思想中出现了“识仁”与“持敬”工夫的认识转向,这标志着中和新说思想已经开始酝酿。
朱子在中和旧说中,持性体心用的心性观及涵养察识于已发的工夫论,这说明了心的重要性:心作为可知、可感者,是性的直接呈露;作用于已发之心的工夫可以直接通达本体。但此种旧的心学存在问题:一方面,将心体视作纯粹的形而上者,称中即性,此为命名不当;另一方面,直接导致缺却了对未发心体的涵养,从而陷入工夫论困境。这两点是朱子中和旧说转向新说的重要原因。
中和新说即朱子成熟的心学理论。随着朱子中和新说的形成,在心性关系上,朱子保留了“心具性”之旨,强调因心之寄寓方有性之得名,由性为根本方才有心之运作。这说明:从概念分析角度来看,性、心形而上、下性质有别;从实存的角度来看,性和心不是分离而在的两物,彼此互作规定与说明。在“心具性”的总旨下,朱子又接续孟子、张载的思想资源,形成了“心统性情”的成熟之见。心是主宰者,又虚灵不寐,性、情并非是心中存在的事物,而是对心之体、用的分别表达。这不仅进一步避免视心性、性情分别为二物,又因心贯穿未发已发,更突显了心的地位。相应的工夫论中,涵养、察识分别作用于心之体、用,此非对象性的作用。察识是已发处心的自我明鉴,以去除物欲之蔽。涵养是未有思虑萌动时的主宰严肃专一,诚敬一旦生起,本体自立。因此,已发之察识并非以心识心,未发之涵养并非寻求一个心体。基于此,朱子批评了湖湘学的工夫论传统,并反思延平教授的求中于未发之旨,对“静坐”说又作了补充。涵养与察识作用各别,但又体用一源,则涵养与察识可以互救。因工夫修养中的具体效验,个体差异与议论角度不同,涵养察识之先后不执死。敬作为工夫总脑,统合二者,从而形成由体而达用、由用而达体的体用一源的心学工夫。
朱子对“十六字”心诀的阐释是“心法”总论。道心人心说是言心之学,“惟精”与“惟一”是修心之法,这是朱子心学的总体概括。“十六字”未必假说的提出,是阐发朱子“心学”与“心法”的文献前提。从朱子道心人心说的形成过程来看,甲午的“心说之辩”到丁未朱子与蔡季通、郑可学的论辩,直至己酉的《中庸章句序》的写定,都有一贯之旨:朱子将道心人心视作已发;并认为道心纯然善,人心危殆;道心人心并非二心。
由此可见,心呈现出两个面向:它既具虚灵明觉的特性,是心体的自然流行发见,是纯善无伪之超越实体,如道心;它又具有形而下之气的属性,当被气质物欲所拘蔽,而成为可善可恶的经验物,如人心。两个面向,前者说明人之心具有内在自发的道德自觉,后者指出其形下特征会干扰道德本心的呈现。进而可以说,朱子言心,既重视其内在超越性,又承认其经验的局限性,心能实现从经验性向超越性的飞跃,便是其自觉能动性的表现。
“惟精”与“惟一”作为修心之法,是工夫总脑。这是复明心之全体的“明明德”工夫,它强调心的自发、自觉、自醒与自立,又是克制人欲,复全天理的有效途径。“惟精”即由用而见体的工夫,包括格物致知;“惟一”即由体而达用的工夫,包括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是同一工夫的两种面相,是在心之用上复明本心的工夫。格物包括格“心”与格“事物”。
朱子心物并举,阳明重心而轻物。究其根源,阳明视心为形上之性理,朱子视心为超越的形而下者。阳明对人心有十足的自信,朱子则对心之知、见、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格心”是朱子格物说中的一端,但却是阳明格物说的全部,因此朱子格物说囊括了阳明格物说。
总之,朱子心学即“传心之学”、“修心之法”,属广义心学。朱子拥有以“理本论”为基础的“心学”,此“心学”与“理学”、“性学”、“仁学”不冲突违背,且相互照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朱子学。
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
张恒(山东大学2020年,导师:沈顺福教授)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在中国哲学这条大河之中,宋明理学总可算作湍急壮丽之一处。然而明清以降,理学的命运却往往因政治、社会等因素而颠簸不定,一度遭到彻底否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理学重又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热点,但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多集中于朱熹、王阳明等“大人物”,掀起了“朱子热”“阳明热”等研究热潮。当然,从思想的成熟性、深刻性而言,“大人物”自有其研究价值,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出现都是其哲学使命驱动的结果,要想准确理解某一思潮、学派、学者,不仅要认识其巅峰形态,还应不断返回其原初形态,因其思想密码早已蕴含在发生之时。由此,要想准确理解理学思潮、反理学思潮并实现理学现代化,必须对“理学的发生”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鉴于以往学界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研究的经验教训,从“范式转换”的动态视角切入理学发生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一视角下,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魏晋玄学、佛道宗教、隋唐儒学)之间的关联,确认它们各自所属的哲学范式,并揭示范式转换背后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内部及其与巅峰理学之间的关联,承认它们之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比较级”——逻辑发展意义上的“比较级”,以揭示理学范式形成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早期理学以“北宋五子”为代表,通过对他们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各自哲学的特点。其中,邵雍在“象数”上用力颇多,创建了精致繁复的象数体系,但这并不构成其在哲学史上的真正贡献。邵雍的贡献恰在于对“象数”终极性的否定以及对“象数”背后之“理”的探赜求索。邵雍所谓“理”主要指物理、数理,其中最为核心的“至理”是体现于“坤复之变”的阴极阳动、动静之变,邵雍又谓之“天地之心”或“太极”。“天地之心”作为神妙万物的几微之理,有经验的一面但也有试图超越经验的倾向。可见邵雍之学并非“数术”而是“心学”,它构成了对佛教“心学”的解构,也启发了程朱、陆王两大学派。对于周敦颐哲学的形态,学界历来有宇宙生成论与思辨存在论之争,而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判定周敦颐的本原概念“太极”究竟属“气”还是属“理”。历史地看,“太极元气说”诠释进路在周敦颐那里是行得通的;哲学地看,周敦颐又赋予“太极”以超越意涵,这集中体现在“神”的超越性上;再一方面,“太极”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它是人伦的终极本原。总之,从历史话语、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综合考察,周敦颐哲学与邵雍哲学一样展现出了从宇宙生成论跃向思辨存在论的努力,尽管两种范式的共存说明它们的形态尚不成熟,但这种努力已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理学开拓者。张载以“太虚”为核心范畴,一方面他有将“太虚”还原为“气”的倾向,亦即沿革传统“气论”;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太虚”之“神”的揭示,使“太虚”具有了一定超越性,具有了成为超越本原之可能,这是张载哲学的创新之处。基于后一重向度,“太虚”不等同于“气”,二者是体用关系,即太虚之体借助气实现了万物的化生,其关系展现为“太虚→气→万物”架构。与此同时,太虚还是价值之体,借助“仁”实现人间的伦理秩序,其关系展现为“太虚→仁→礼义”架构。张载试图辨析“太虚”与“气”,并试图将“太虚”提升为超越本原,这比邵雍、周敦颐以“太极”熔铸一切的做法有所进步。中国哲学对“道”的追问至程颢、程颐兄弟转变为对“理”的追问,“理”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话语与思想系统“金字塔”的塔尖。“由道而理”的话语转换是中国哲学逻辑发展或范式转换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这是中国本土哲学思维方式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即“本末”思维亟待向“体用”思维转变;另一方面,这又是时代价值观念重建的迫切要求,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强调“理”的实在性、道德性,以重建儒家价值观念的哲理基础。二程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是通过对理与气、理与性、理与欲等范畴的辨析建立起来的,“理”相较于“气”具有了更加自足与超越的品格,比邵雍、周敦颐、张载等人的观念都更为成熟。
通过对“北宋五子”进行分别研究、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作为学术共同体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上的范式特点。就哲学使命而言,从天人学视角来看,理学家普遍推重的“天人合一”观念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以“天人合一于气”为主要形态,而隋唐时期兴盛的佛教则主张“万法唯心”亦即“天人合一于心”,二者产生了张力。有鉴于此,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家针对佛教的“心学”体系,试图赋予“心”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以使之既区别于佛教的虚空性,又区别于中国本土哲学的经验性。对“天地之心”的追问成为理学的哲学使命及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就思维方式而言,中国本土哲学以“道”为本原追问之鹄的,以“本末论”为本原追问之方法,这种思维在追问“经验的存在之先”时简洁有效,但有不可消解的理论困境,即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多元论、本末分离。为解决上述困境,玄学与佛教作了许多探索,逐渐建立起“体相用”思维,但这种思维具有否弃现实与伦理的倾向,走上了宗教超越之路。为了走向哲学超越,早期理学家扬弃上述两种思维方式,发展出“体用”思维,既实现了对“超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又不舍弃现实与伦理。思维方式之变是理学发生的核心机制。就价值观念而言,理学对“天地之心”的追问不单是形式逻辑问题,更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重建构成了理学范式转换的重要一环。儒学自初唐开始复兴,强调道德,尊崇孟子,抬升“四书”,注重义理。在这些准备工作基础上,“北宋五子”直入“心性”问题,赋予“性”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使之既区别于佛教思辨性的“空”,又区别于传统儒家经验性的“有”。二程“性即理”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上述工作的基本完成,理学实现了儒家价值形上化,儒家价值在哲理上获得了重建。此外,“北宋五子”关于“太极”“太虚”“天理”等的言说也集中体现了早期理学家较之以往的话语体系之变。
总而言之,从哲学发生学视角来看,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佛学、玄学等相比,其哲学范式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四个向度上发生了显著转换,或者说,理学就发生于这四个向度的范式转换之中。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王 岩(山西大学2020年,导师:刘毓庆教授)
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
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
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
《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
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
《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
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
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赵玫(山东大学2020年,导师:沈顺福教授)
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划分,已成为学界共识。以“心学”称朱子学,似犯下指鹿为马的错误。然而,从文献依据与义理依据两方面看,朱子心学的提法是公允且必要的。
从文献依据上看,自朱子之后以至于明弘治(1488—1505),不以“心学”与“理学”之称法作派系划分,朱学也被称为“心学”。嘉靖年(1522—1566),出现“心学”独指阳明学之论。万历年(1573—1620),邓元锡作《皇明书》,视阳明学为儒家正宗,称心学。清黄梨洲父子编订《宋元学案》,更彰明“心学”、“理学”二分,以“心学”独指陆王学之见。由此可见,“心学”与“理学”的划分,最初是带有门户之见的,沿用这一划分,会陷入门户争论之窠臼。
学者历来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判分朱学为“理学”,陆王为“心学”,从义理上反思这一判分显得非常重要。反思的前提是对“心即理”与“性即理”的定位,这两个命题不仅是本体论问题,亦为工夫论问题。就此,朱陆之学有同异。将太极与理视作理论基础与目标指向,是二人学问之同。从实然心的定位与功能来看,陆王直接以心为性体,属形而上者,则相应的工夫路径简易径直,朱子严判性、心为形而上、下,同时又看到心的超越性与有限性两个面向,则心能自明、自觉、自立,并落实为细密严缜的心地工夫,此为二人之异。总之,朱子强调终极本体为性而非心,此即“性即理”,故为“性本论”。但他同时强调在本然与境界中,有限之心具超越性,实现心理无间与心体流行,此即“心即理”,故朱子之“性即理”涵摄了“心即理”。因此,不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严判朱、陆为“理学”与“心学”。
朱子学为传道之学,亦为传心之学,此即“道学”,亦为“心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学”与“心学”,乃至于“理学”、“性学”不是对立存在,而是共同包含在任何派别的宋明理学家的思想当中。
传心之学即传心法之学,它包括言心之学、修心之法,因此,心法即心学。朱子心学有内在结构,这反映在朱子对《中庸》首章的训释中。这一结构包括了宇宙本体论(从“本原”到“实体”)、基于心性论的工夫论(“存养省察之要”)、境界论(“圣神功化之极”)三大部分。朱子对《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的诠释,是心学的总论。
在天而言,“天命”作为“本原”;在人而言,“人性”作为“实体”。天人一贯,是作为形而上之理的“天命”与“人性”的一贯,这一过程必须在理气共同作用下完成,含理之气则为心,或称为“天地之心”,这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阐释心学。
一方面,朱子论“天地之心”有别于汉唐儒视“天地之心”为经验化、人格化的存在,又不同于王弼由“动息地中”见得静与默,从而复归本体的解释。朱子光大了自唐宋以来儒家宇宙本体论自觉的星火,回归了儒家经典的原意,同时重建了儒家形上学的诠释系统。朱子对程颐、邵雍、程颢“天地之心”说的诠释,呈现了“天地之心”是理气圆融无间、生生流行这一特点。天地之心统天地之性、天地之情,这与人生论中“心统性情”架构相吻合。
另一方面,理气关系与天地之心可以互释。理的四种训义与“天地无心”与“天地有心”对应:理之能然、必然说明理决定气之主宰与运作,而见得天地生物造物的能力,可知天地有心;理之当然、自然说明天地之心的生生不已,万物生化自然有序,可知天地无心。可见,从天地之心入手,可以诠释朱子的理气观,并突出理气圆融的生生之意。
再一方面,朱子言仁,有指体、指用、统摄体用三种情况。统体之仁包体用,贯天人。在天而言,统体之仁即天地之心,其包天地之“性”与“情”,它不但指元、亨、利、贞四天德,也包含春、夏、秋、冬四季。在人而言,统体之仁即人心,其体为仁、义、礼、智四人德,发用为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四端。因此,仁是贯通天人的关窍,天地之心亦然。由此获得两点结论:一则,天地之心与仁一样,是一元之气的流行生化不已,其具备内在自足的善性而表现出生物不已、温然爱人利物的特点。二则,“心学”与“仁学”、“气学”在朱子思想中具有了同等地位,朱子的“仁学”即“心学”。
朱子中和新旧说的转变即旧的心学转向新的心学,这是朱子“心学”的人生论说明,它包括心性本体论、工夫论与境界论三部分,三部分相互交融。
从中和旧说形成过程上来看,大致分为四个小阶段。朱子师从李延平期间,他对延平默坐澄心之旨不能契合,此时中和旧说初具雏形;隆兴二年甲申,朱子赴豫章哭祭张浚并见张栻,他极认可张栻涵养察识于已发的工夫,更加固了旧说的认识;乾道二年丙戌,朱子与张栻书信讨论中和问题,标志中和旧说成形;乾道三年丁亥春,朱子思想中出现了“识仁”与“持敬”工夫的认识转向,这标志着中和新说思想已经开始酝酿。
朱子在中和旧说中,持性体心用的心性观及涵养察识于已发的工夫论,这说明了心的重要性:心作为可知、可感者,是性的直接呈露;作用于已发之心的工夫可以直接通达本体。但此种旧的心学存在问题:一方面,将心体视作纯粹的形而上者,称中即性,此为命名不当;另一方面,直接导致缺却了对未发心体的涵养,从而陷入工夫论困境。这两点是朱子中和旧说转向新说的重要原因。
中和新说即朱子成熟的心学理论。随着朱子中和新说的形成,在心性关系上,朱子保留了“心具性”之旨,强调因心之寄寓方有性之得名,由性为根本方才有心之运作。这说明:从概念分析角度来看,性、心形而上、下性质有别;从实存的角度来看,性和心不是分离而在的两物,彼此互作规定与说明。在“心具性”的总旨下,朱子又接续孟子、张载的思想资源,形成了“心统性情”的成熟之见。心是主宰者,又虚灵不寐,性、情并非是心中存在的事物,而是对心之体、用的分别表达。这不仅进一步避免视心性、性情分别为二物,又因心贯穿未发已发,更突显了心的地位。相应的工夫论中,涵养、察识分别作用于心之体、用,此非对象性的作用。察识是已发处心的自我明鉴,以去除物欲之蔽。涵养是未有思虑萌动时的主宰严肃专一,诚敬一旦生起,本体自立。因此,已发之察识并非以心识心,未发之涵养并非寻求一个心体。基于此,朱子批评了湖湘学的工夫论传统,并反思延平教授的求中于未发之旨,对“静坐”说又作了补充。涵养与察识作用各别,但又体用一源,则涵养与察识可以互救。因工夫修养中的具体效验,个体差异与议论角度不同,涵养察识之先后不执死。敬作为工夫总脑,统合二者,从而形成由体而达用、由用而达体的体用一源的心学工夫。
朱子对“十六字”心诀的阐释是“心法”总论。道心人心说是言心之学,“惟精”与“惟一”是修心之法,这是朱子心学的总体概括。“十六字”未必假说的提出,是阐发朱子“心学”与“心法”的文献前提。从朱子道心人心说的形成过程来看,甲午的“心说之辩”到丁未朱子与蔡季通、郑可学的论辩,直至己酉的《中庸章句序》的写定,都有一贯之旨:朱子将道心人心视作已发;并认为道心纯然善,人心危殆;道心人心并非二心。
由此可见,心呈现出两个面向:它既具虚灵明觉的特性,是心体的自然流行发见,是纯善无伪之超越实体,如道心;它又具有形而下之气的属性,当被气质物欲所拘蔽,而成为可善可恶的经验物,如人心。两个面向,前者说明人之心具有内在自发的道德自觉,后者指出其形下特征会干扰道德本心的呈现。进而可以说,朱子言心,既重视其内在超越性,又承认其经验的局限性,心能实现从经验性向超越性的飞跃,便是其自觉能动性的表现。
“惟精”与“惟一”作为修心之法,是工夫总脑。这是复明心之全体的“明明德”工夫,它强调心的自发、自觉、自醒与自立,又是克制人欲,复全天理的有效途径。“惟精”即由用而见体的工夫,包括格物致知;“惟一”即由体而达用的工夫,包括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是同一工夫的两种面相,是在心之用上复明本心的工夫。格物包括格“心”与格“事物”。
朱子心物并举,阳明重心而轻物。究其根源,阳明视心为形上之性理,朱子视心为超越的形而下者。阳明对人心有十足的自信,朱子则对心之知、见、行时刻保持警惕。因此,“格心”是朱子格物说中的一端,但却是阳明格物说的全部,因此朱子格物说囊括了阳明格物说。
总之,朱子心学即“传心之学”、“修心之法”,属广义心学。朱子拥有以“理本论”为基础的“心学”,此“心学”与“理学”、“性学”、“仁学”不冲突违背,且相互照应、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朱子学。
理学的发生
——基于范式转换的视角
张恒(山东大学2020年,导师:沈顺福教授)
孟子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在中国哲学这条大河之中,宋明理学总可算作湍急壮丽之一处。然而明清以降,理学的命运却往往因政治、社会等因素而颠簸不定,一度遭到彻底否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理学重又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点、热点,但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多集中于朱熹、王阳明等“大人物”,掀起了“朱子热”“阳明热”等研究热潮。当然,从思想的成熟性、深刻性而言,“大人物”自有其研究价值,但任何一种哲学形态的出现都是其哲学使命驱动的结果,要想准确理解某一思潮、学派、学者,不仅要认识其巅峰形态,还应不断返回其原初形态,因其思想密码早已蕴含在发生之时。由此,要想准确理解理学思潮、反理学思潮并实现理学现代化,必须对“理学的发生”问题给予足够重视。
鉴于以往学界关于“理学的发生”问题研究的经验教训,从“范式转换”的动态视角切入理学发生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一视角下,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魏晋玄学、佛道宗教、隋唐儒学)之间的关联,确认它们各自所属的哲学范式,并揭示范式转换背后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须正视早期理学内部及其与巅峰理学之间的关联,承认它们之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比较级”——逻辑发展意义上的“比较级”,以揭示理学范式形成过程及其经验教训。
早期理学以“北宋五子”为代表,通过对他们进行个案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各自哲学的特点。其中,邵雍在“象数”上用力颇多,创建了精致繁复的象数体系,但这并不构成其在哲学史上的真正贡献。邵雍的贡献恰在于对“象数”终极性的否定以及对“象数”背后之“理”的探赜求索。邵雍所谓“理”主要指物理、数理,其中最为核心的“至理”是体现于“坤复之变”的阴极阳动、动静之变,邵雍又谓之“天地之心”或“太极”。“天地之心”作为神妙万物的几微之理,有经验的一面但也有试图超越经验的倾向。可见邵雍之学并非“数术”而是“心学”,它构成了对佛教“心学”的解构,也启发了程朱、陆王两大学派。对于周敦颐哲学的形态,学界历来有宇宙生成论与思辨存在论之争,而解决这一争论的关键在于判定周敦颐的本原概念“太极”究竟属“气”还是属“理”。历史地看,“太极元气说”诠释进路在周敦颐那里是行得通的;哲学地看,周敦颐又赋予“太极”以超越意涵,这集中体现在“神”的超越性上;再一方面,“太极”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它是人伦的终极本原。总之,从历史话语、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综合考察,周敦颐哲学与邵雍哲学一样展现出了从宇宙生成论跃向思辨存在论的努力,尽管两种范式的共存说明它们的形态尚不成熟,但这种努力已使他们成为事实上的理学开拓者。张载以“太虚”为核心范畴,一方面他有将“太虚”还原为“气”的倾向,亦即沿革传统“气论”;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太虚”之“神”的揭示,使“太虚”具有了一定超越性,具有了成为超越本原之可能,这是张载哲学的创新之处。基于后一重向度,“太虚”不等同于“气”,二者是体用关系,即太虚之体借助气实现了万物的化生,其关系展现为“太虚→气→万物”架构。与此同时,太虚还是价值之体,借助“仁”实现人间的伦理秩序,其关系展现为“太虚→仁→礼义”架构。张载试图辨析“太虚”与“气”,并试图将“太虚”提升为超越本原,这比邵雍、周敦颐以“太极”熔铸一切的做法有所进步。中国哲学对“道”的追问至程颢、程颐兄弟转变为对“理”的追问,“理”从此走上了中国哲学话语与思想系统“金字塔”的塔尖。“由道而理”的话语转换是中国哲学逻辑发展或范式转换的必然结果:一方面,这是中国本土哲学思维方式走向成熟的内在要求,即“本末”思维亟待向“体用”思维转变;另一方面,这又是时代价值观念重建的迫切要求,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强调“理”的实在性、道德性,以重建儒家价值观念的哲理基础。二程以“理”为中心范畴的哲学体系是通过对理与气、理与性、理与欲等范畴的辨析建立起来的,“理”相较于“气”具有了更加自足与超越的品格,比邵雍、周敦颐、张载等人的观念都更为成熟。
通过对“北宋五子”进行分别研究、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他们作为学术共同体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上的范式特点。就哲学使命而言,从天人学视角来看,理学家普遍推重的“天人合一”观念初步形成于魏晋时期,以“天人合一于气”为主要形态,而隋唐时期兴盛的佛教则主张“万法唯心”亦即“天人合一于心”,二者产生了张力。有鉴于此,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家针对佛教的“心学”体系,试图赋予“心”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以使之既区别于佛教的虚空性,又区别于中国本土哲学的经验性。对“天地之心”的追问成为理学的哲学使命及其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就思维方式而言,中国本土哲学以“道”为本原追问之鹄的,以“本末论”为本原追问之方法,这种思维在追问“经验的存在之先”时简洁有效,但有不可消解的理论困境,即容易导向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多元论、本末分离。为解决上述困境,玄学与佛教作了许多探索,逐渐建立起“体相用”思维,但这种思维具有否弃现实与伦理的倾向,走上了宗教超越之路。为了走向哲学超越,早期理学家扬弃上述两种思维方式,发展出“体用”思维,既实现了对“超验的存在之先”的追问,又不舍弃现实与伦理。思维方式之变是理学发生的核心机制。就价值观念而言,理学对“天地之心”的追问不单是形式逻辑问题,更是价值观念问题,价值重建构成了理学范式转换的重要一环。儒学自初唐开始复兴,强调道德,尊崇孟子,抬升“四书”,注重义理。在这些准备工作基础上,“北宋五子”直入“心性”问题,赋予“性”以超越性、实在性与道德性,使之既区别于佛教思辨性的“空”,又区别于传统儒家经验性的“有”。二程“性即理”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上述工作的基本完成,理学实现了儒家价值形上化,儒家价值在哲理上获得了重建。此外,“北宋五子”关于“太极”“太虚”“天理”等的言说也集中体现了早期理学家较之以往的话语体系之变。
总而言之,从哲学发生学视角来看,以“北宋五子”为代表的早期理学与“前理学”时期诸哲学形态如佛学、玄学等相比,其哲学范式在哲学使命、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四个向度上发生了显著转换,或者说,理学就发生于这四个向度的范式转换之中。
中日韩《孟子》学研究
王 岩(山西大学2020年,导师:刘毓庆教授)
作为“四书”之一,儒学经典《孟子》在中国宋朝、日本江户时代、韩国朝鲜朝都具有重要影响,其仁说、性善说、“不动心”说、仁政说等深刻影响着中日韩三国的社会思潮走向、社会制度建设乃至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中日韩三国大儒均带着经世致用的济世情怀和历史使命感进入了注释《孟子》的领域,以注释儒学经典的方式表达着对天道、人性和社会等问题的看法,引领着时代思潮的走向。其中,尤以朱熹(1130—1200)、伊藤仁斋(1627—1705)和丁若镛(1762——1836)的注释最具代表性。
中国宋朝,在汉学向宋学转移的大势下,朱熹《孟子集注》以赵岐注为底本,上承韩愈、周敦颐、程颐、张载,下采张栻、杨时、范祖禹、吕希哲、尹焞、吕大临、游酢、谢良佐、侯仲良、周孚先等人,荟萃条疏,辨同别异,将经学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对心性之微的探索、宇宙之理的追索,建立起以理学精神为主的新孟子学,影响元明清七百余年的中国历史。并且,伴随着朱子学在汉文化圈的流播,《孟子》在日本及朝鲜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末期即已出现汉学与宋学的分野。进入江户时代后,朱子学在幕府支持下获得了官学地位。十八世纪,反朱子学的力量壮大了起来,古学派开创者伊藤仁斋建立起以《论语》《孟子》为核心的古学思想体系,恢复人伦日用的古学之道,开启了儒学日本化进程。作为仁斋思想成熟时期的著作,《孟子古义》既是仁斋古学思想的代表,又是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试图摆脱朱子学影响、实现本土化的反映,鲜明体现了儒学在异域文化背景下的变化形态。儒学传入韩国的最早记载是公元640年唐太宗设立崇文馆,新罗、高句丽、百济将子弟送到唐朝学习,关于《孟子》可查证的最早记载是罗末丽初(约为公元十世纪)崔致远(857—?)在《无染和尚碑铭》中的六处征引。而《孟子》的正式接受是在朝鲜朝时期。作为实学派集大成者,茶山丁若镛认为《孟子》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积极践行的实践精神,最能体现洙泗之学的真谛。茶山倾浸心血注释的《孟子要义》,既继承了朝鲜朝前期儒学的成果,又吸取了西学的内容,成为能够体现性理学、阳明学、北学和西学的思想载体,体现了十九世纪韩国儒学界尝试以儒学世界观来理解西方思想体系的努力。
然而,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的《孟子》诠释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建立在其对“道”不同角度的理解之上。朱熹将宇宙起源、万物化生、飞禽动植、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融入对“道”的理解,进而为传统儒学中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联结起来的“天人一体”思想提供了形而上的宇宙论根据。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反对从形而上的“天理”来理解“道”的视角,转而将“道”的视角拉回到人伦日用之间,强调了自然秩序与人伦道德之间的分离,构成了其《孟子》阐释的思想基础。如果说对“道”的理解体现了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理解,那么,对“理”的不同阐释则凸显出朱子学东传日韩之后所引起的种种反映。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条理、腠理、文理之义来重新理解“理”,从而完成了对朱熹“天理”之义的解构。故对“道”、“理”的不同理解构成三家对《孟子》阐释不同的深层原因,但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又并非决然相同,而是存在着若干具体差异。具体来说,朱熹以理气一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心性之学为核心,视《孟子》为阐释仁义礼智本然之性的儒学经典,进而使儒家在心性之说上超越佛家,巩固了社会价值观引领的地位。仁斋提出一元之气为天道之全体,反对朱熹以“心性”解《孟子》的作法,将《孟子》视为体现仁义之德、王道之要的儒学经典,最终以“仁义之德”表达了对君臣、父子人伦秩序的尊崇。与仁斋相似,丁若镛亦在反对理气一体宇宙观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以“孝弟慈”为核心的人伦之道。然而,丁若镛更为强调“心”的实践意义,认为“天命之性”的贵重当体现于“行事”之间尽己之心的意愿之上。但是,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主旨的不同把握并非临空蹈虚,而是在对《孟子》具体学说的阐释之中充分展开。
《孟子》开篇即提出“仁”字,对“仁”一字之阐释凸显出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对《孟子》的不同把握。《孟子集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实际上分宇宙界与人生界两个层次来说仁。仁之理为天地生物之心,仁之气是天地温和之气,一“仁”字实际上绾合了理与气,接通了宇宙界与人生界。朱熹以天地之理、阴阳之气来说仁,既继承了孔孟儒学,又将仁字上升至宇宙界,使“仁”具有贯通天人的特色,真正体现了中国儒学特有的精神传统和认识世界的方式。伊藤仁斋从人伦之道的古学观点出发,认为仁只是爱,不是“爱之理”;仁是忠信之爱,是实德,是实实在在的人伦情感;仁不是个人的私情、私爱,而是遍施于他人的公共之爱。而其思想基础则是天道与人道分立、道德法则与自然秩序分离的天人分立思想。可见,对中国儒学中对于天人关系的舍弃,透露出仁斋及德川儒学在吸收中国儒学时所持有的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指导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的实用性为标尺。这种以实用性选择文化的态度,不仅在江户时代迅速将儒学转化为推动社会兴盛的工具,也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能够迅速从传统中转型,吸取西方文化中的有用部分,从而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转型的文化心理基础。茶山将“仁”看作现实社会中孝弟慈等人伦关系,尤其注意分辨心与仁义礼智之间的差别。茶山认为,仁义礼智与心并非是一段,仁义礼智只是在外之德行,能够真正地实现这一德行的根本在于“心”的权衡抉择,从而突出了“心”自主抉择的重要性,体现了韩国儒学注重实践性的特征。进而,茶山接受利玛窦西学的影响,将“天”理解为人格神意义的上帝,从而在天人关系的把握上区别于朱熹,形成了韩国儒学的特质。
经由朱熹之解,性善说既成为《孟子》的核心思想,又成为日韩儒者绕不开的话题。朱熹“性即理”继承了汉儒以“天人宇宙图式”论性的传统,其“理一分殊”性学体系解决了儒家悬而未决的“性与天道”形而上根据的问题;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不离不即的关系,又最终将性善说挽回到人生义上来。仁斋“性好恶说”分离了“性”与仁义礼智大德之间的关系,认为气质之性天然有好仁义的倾向,顺性则可行仁义,顺人情可知性善,甚至将情提高到了“道”的位置,体现了德川儒者重“情”的普遍特点,为教化说、王道说打下了基础。丁若镛“性嗜好说”沿袭先秦儒学“以心见性”的模式,注重从心的好恶判断等直观感受上来认识性,既为心的自主之权留下广阔的空间,又使性善说能从朱熹天理的框架中脱离开来,具有指导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的实际意义。要言之,对“性善”的不同理解实根源于三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把握。
《孟子·公孙丑上·不动心》章因提出了“不动心”、“知言”、“善养吾浩然之气”、“集义”等重要论断历来备受关注,是理解三家《孟子》阐释异同的绝佳样本。朱熹重视“未尝必其不动而自然不动”的圣贤心态以及俯仰无愧怍的浩然之气,集中阐述了“集义”的日用功夫,表现了理学沟通天地正气与人之精神气魄、推崇以“义”为核心的日常践履功夫的品格。仁斋以朱子学为继承和批评的对象,批驳朱熹对“不动心”和“浩然之气”的重视,集中阐发了以“仁义”为核心的思想,表现了古学派不谈性与天道、注重人伦日用之道的实学特色。丁若镛集中阐发了对“心”为神形妙合之主的推崇,“不动心”只是志士仁人在伦理世界的世俗心态,完成了对朱熹所言“天理”与“不动心”关系的分离。
仁政是孟子提出的治世理想,为中日韩儒者描摹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朱熹认为仁政之大要在于人君一心之间的天理人欲之别,君子尽本性之善,由一心上溯至天理;圣人笃恭而天下平,修一己之德而天下从之。仁斋认为王道说是《孟子》乃至“四书”的主旨,其“生生之德”既继承了朱熹天地生生之意发畅不已的生命观,又将之限定在人世间的范围之内,具有了瞩目于人伦日用之道的古学特色。仁斋认为,仁政之本在于人君能与民偕乐,与天下同情,将“好货”、“好色”等合理情感欲望推己及人,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与民偕乐”(“同民之好恶”)之说。丁若镛认为,治国当以用人、理财为要务,合理的田制是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基础,经界之法、井田之制为礼乐兵刑等制度的根本,并重视以天命启迪道心的教化说,尝试为朝鲜朝的变革描绘出现实路径。
结言之,朱熹、伊藤仁斋与丁若镛都以儒学经典《孟子》的重新诠释来表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这种经典的学问生产方法奠定了以经书为核心的东亚精神传统、思想传统,维护了儒家精神在东亚文化圈内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三国对以“天人关系”为主的儒学核心价值理解不同,形成了三国儒学的不同特色,影响到三国的近代化进程。然而,中日韩同属汉文化圈,整体上存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传统:即都不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根基和目标,而是注重群体合作、人际和谐。这既是儒学带给中日韩文化共同的基本要义,也是三国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心理,是三国面临西方文化之时所共同拥有的思想底色,对我们今日理解人与社会的关系亦具有深刻影响。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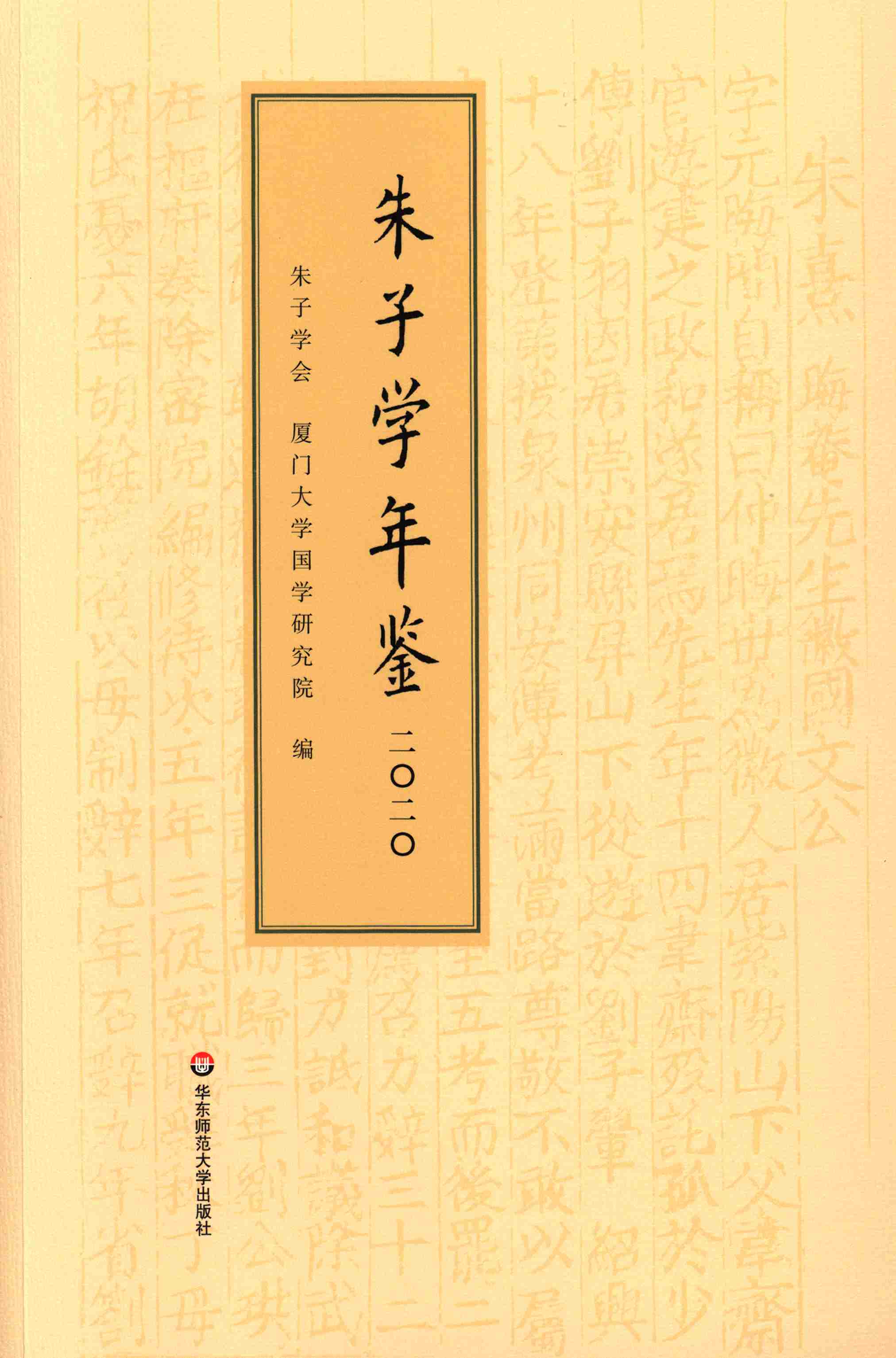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