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王夫之评嵇绍仕晋合说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809 |
| 颗粒名称: | 朱熹、王夫之评嵇绍仕晋合说 |
| 分类号: | B244.75;G127 |
| 页数: | 15 |
| 页码: | 205-219 |
| 摘要: |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了嵇康和嵇绍的命运以及历代儒者对其评价的不同。嵇康被司马昭诛杀后,历代史臣和儒者都给予高度评价;而嵇绍仕晋和后为晋惠帝死难,则褒贬不一,朱熹认为嵇绍应该选择复仇而不是效忠于敌人,支持大复仇理论。王夫之对此有更深入的评价。宋代因儒学重振,对嵇绍评价更为重视,且有新的评价视角。 |
| 关键词: | 嵇康 嵇绍 晋朝 |
内容
魏景元四年,竹林七贤首要人物嵇康被已把持朝政的司马昭诛于洛阳东市。晋泰始九年,因山涛向司马昭推荐和对嵇康之子嵇绍劝说,嵇绍入仕晋朝,任秘书丞。后随惠帝北伐,在荡阴为晋室死难身亡。对嵇康从容就义、拒不仕晋的高风气节,历代史臣和儒者都普遍给予高度评价、嘉褒有加;而对嵇绍仕晋和后为晋惠帝死难,则褒贬不一,讥讽居多。宋代因儒学重振,倡导名节,对嵇绍评价更为重视,且有新的评价视角,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说:“臣光曰:昔舜诛鲧而禹事舜,不敢废至公也。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嵇绍使无荡阴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②这是宋儒对嵇绍仕晋最早的较系统评价,注目于嵇绍应不应仕晋,涉及父子之伦和君臣之伦的关系,影响大。其后,南宋大儒朱熹首次对司马光评价提出质疑,对嵇绍仕晋及由此涉及的孝道和臣道关系有许多论述,朱说同样也影响大,在明儒中多有继承者,继承者认同和承接朱熹基本观点,对嵇绍仕晋又有不同层面的深化评价,其中以王夫之为最。
一
朱熹评价始终是围绕嵇绍应不应仕晋展开的。朱熹明确主张嵇绍不可仕晋,“绍不当仕晋明矣”①,嵇绍仕晋是背父不孝的行为,即使以后为晋惠帝死难也不抵此咎。原因为其父嵇康无罪被司马昭诛杀,嵇康是魏臣,作为其子,嵇绍应该复仇,即使因时势难以为之,也至少应该避世隐居,而尤不可仕仇君之朝。朱熹反对子仕仇君之朝,他答门人子升问:“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时说:“不可。”此无可选择。当然,随着时世变迁,到了孙曾时代,情况可有变化,“世数渐远,终是渐轻,亦有可仕之理”,有出仕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亦须知“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权也”②,不仕的原则立场和权的变通之宜分野区别仍然是必须明白的。
嵇绍最有价值的行为选择是向司马氏复仇。对儒家尤其是公羊春秋所主张的大复仇理论,朱熹基本上是赞同的。他评价伍子胥为其父复仇楚平王时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③赞成伍子胥复仇于楚平王的行为,当然若受诛者本有罪则不在此类。复仇不仅是适应于臣为君报仇,也适应于子为父报仇,即使仇者是君主,它是适应于父子和君臣两伦的。“然则其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则有为臣子者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报其仇者,其志岂有穷哉!故记礼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有天下也”,所不同的只是庶人,百姓报父仇“未及五世之外”,而“有天下”的君主,“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非若庶民五世”,“自高祖以至玄孙,亲尽服穷而遂已”①,是没有世代时期限制的。这里“记礼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一段是孔子回答子夏问,载《礼记·檀弓上》。朱熹通过引据典籍和转述孔子之言阐述了儒家的大复仇思想。
比较嵇绍仕晋行为与历史上相似行为是评价嵇绍重要的参考标准。朱熹首先进行的是嵇绍与同时代的王裒比较,王裒是晋武帝谋臣王仪之子,王仪也被晋武帝无罪诛杀。后晋室招王裒进朝入仕,王裒拒招隐居,朱熹赞许之。“而裒不仕,乃过于于厚者”②,王裒不仕是忠于孝道的表现,尽了职责,值得提倡。况且王仪是司马昭的军师,是晋臣,而嵇康是魏臣,拒绝入仕被诛杀,两者很有区别。“王仪为司马昭军师,昭杀之虽无辜,裒仕晋犹有可说”,司马昭与王裒非异朝之君,若仕也有可说之理,本无事异朝之君这层障碍,王裒拒仕是孝道高于君道的一个榜样典范。嵇绍与其相去甚远。
嵇绍仕晋也不能与管仲不死公子子纠而后仕于齐桓公、魏徵先仕李建成而后仕于李世民相比较,他们的情况不同。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和魏徵不为李建成死节且后皆仕杀故主的仇人,衷心辅佐,屡建奇功是有原因的,主要为尊周室、攘夷狄、存华夏和一统天下。“管仲不死子纠,圣人无说,见得不当死”,后又有奇功伟业,“郑魏公则是前仕建成矣,不当更仕太宗,后却有功”,此二人不死节都是事出有因。所以可说魏公“功可以补过犹可”,“管仲则前无过而后有功”①,情况不同于嵇绍。朱熹此项比较评价的取向标准是出仕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管仲和魏徵都只是故主被杀,还都不是其父无罪被杀,他们都没有涉及孝道,没有涉及父子一伦。
在阐述对嵇绍仕晋行为的评价后,朱熹对司马光关于嵇绍荡阴死难可补偿仕晋之咎的观点提出质疑。司马光也认为嵇绍不应仕晋,但后在荡阴为晋惠帝死难可补不当仕之咎,“使无荡阴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讥”②。朱熹说:“荡阴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赎”③,虽然嵇绍确有其忠,也不能赎入仕之咎。因为“既策名委质,只得死也,不可以后功掩前过”④,一旦入仕为臣,则当尽臣之道,尽忠死节是正常的,此只是尽了臣道,是君臣关系,与以前违背父子之道是两回事,后臣道之忠不能掩盖和弥补前孝道之失,不能相混为一。“事仇之过,自不相掩”,温公之言有误。对嵇绍的讥讽批评,是从入朝仕晋而不是从仕晋后是否尽君臣之道开始的,因此也不是尽忠君所能抵偿和弥补的,为其不能和无法“免也”,故“不知君子之讥,初不可免也”⑤。嵇绍仕晋伊始讥讽就随之而起,就批评此是不尽孝道,非孝子之举。因为父子之道是一个独立的人伦范畴和理念,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意义,并不依君臣之道和随君臣之道而起的。实际上,其价值意义高于君臣之道、重于君臣之道,因此即使嵇绍后来有忠君表现也无法抵偿以前不孝之咎。应该看到,对嵇绍仕晋评价朱熹与司马光是有重要区别的。司马光曰:“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也认为因嵇康无罪受诛嵇绍可以不仕晋室,但没有做绝对性的要求,不明确断言不可仕,只说不仕“可也”,“可也”是有或然性的评断,可不仕,也可仕。司马光没有完全否定和批评仕,同时还没有绝对要求不仕,只是指出了不仕有合理性,可以谅解。所以,司马光对嵇康仕晋的批评是温和的,对于其仕和不仕的要求是有伸缩性的。而且,从举禹父鲧因治水不力被舜诛后仍事舜的例证,认为父子是私,臣君是公,赞扬舜不敢以其私而“废至公”观点看,他还是主张嵇绍可以而且应该仕晋的。①司马温公更没有嵇绍应该复仇的观点。
而且,司马光以舜杀鲧做司马昭杀嵇康而后嵇绍仕晋的例证,有逻辑背悖,容易引起误评。一方面承认嵇康死“不以其罪”,另一方面又用舜杀鲧有理为例证,颇不类不伦。有罪受诛者是不能与无罪受诛者视为同类的。这有意无意把嵇康受诛也视为有罪受诛之例,客观上影响到对嵇绍仕晋性质的评价。实际上,朱熹其前的一些史论正是按照这一路向运作的,北宋胡致堂著名的《资治通鉴》评读即是如此。“昔舜殛死崇伯而禹事舜为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书曰:诛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尔。何以见其服乎,以禹观之,子尚不能以殛其父为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谓天下咸服。如绍者终身不仕晋室,如王裒可也。”但嵇绍却“忘父之怨,而从於禄仕之利”②,仕晋是错误的。胡氏先说禹不念其父被杀而事舜的合理性,后又批评嵇绍忘父仇仕晋的过咎,颇有些不伦不类、不着边际。清儒郭蒿焘说:“崇安胡氏《读史管见》”,“或因古人之事,传以己意;或是一己之辨,求胜前人,多失其平”。①看来,郭氏评胡氏是有道理的,但胡氏此评的路向思路是循从司马光的,两评大体相同。朱熹不赞同司马光评价,首先着力区别舜杀鲧与司马昭杀嵇康的性质有异,是有道理的。
朱熹的嵇绍仕晋说在朱熹在世时就有接受者和同调。户部右曹郎官王回做《嵇绍赞》,否定嵇绍之死是尽忠“死得其所”,是“行于乱世不汙,而能卒以忠为烈,非其积累,明于仁义,孰能自信如此耶”的观点。嵇绍不是素积仁义、临难自信的,也不值得后人效法赞颂。其父非“犯有司”,是为晋篡魏重要障碍而无罪受诛,“特晋方谋篡魏,忌其贤而见图”。嵇绍实是“兼父与君之仇者也”,嵇绍若“力不能报,犹且避之天下,”但他却“为仇人子孙死而为之,”“岂不谬哉!”②嵇绍是不值得“颂”的。显然,王回的评价是遵循嵇康无罪被诛和嵇绍不应仕晋这两个要点的。
明儒吴廷翰明确批评嵇绍仕晋是有君道而无父道。“嵇绍荡阴之节,君子多与之。然父为人杀,非其罪,力不能仇,忍复仕乎”,嵇康无罪被诛,嵇绍不能复仇,尚有可原,但岂能复仕其朝。“父仇不报,委身以事,而复为之死,是有君臣而无父子也,宁免君子之议乎?”嵇绍委身仕晋,更为之死难,不报父死,这种违背父子之道行为,受到后人讥议是难免的。讥议之要是在违背父子一伦,而不在忠君一伦,违背父子之道即使是遵从君臣之道,同样也要受到批评和讥议。司马光“或以绍之仕晋,苟无荡险之节,几不免君子之议”①的观点是错误的。顾炎武则说:“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②指出,嵇绍仕晋三十余年,忘父久矣定能以荡阴死难而赎其罪,况且所事又非君。
王夫之对嵇绍仕晋而死难行为的评价更苛刻、尖锐。他首先明确指出“嵇绍不可仕晋”,而一旦仕晋按照臣道要求则必然要为其死,“仕而恶可弗死也”,这就决定了死不得其所,“仕则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不仕是决定不死于非所的前提。“父不受诛,子弗仇焉,非心也”③,嵇康死于无罪,绍不报父仇是无良心,无父子人伦的。
如果说朱熹还承认嵇绍荡阴死难是忠的性质,还是在承认忠臣行为的基础上进行与仕晋之咎的功过比较的话,王夫之则完全否定了荡阴之死是忠的行为,倒是不仁和愚昧之举。“绍盖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烂而殉怨不共天之乱贼,愚哉其不仁也”,绍仕不当仕之朝,又以父母所予之身为有父仇的昏庸之君死难是不仁且愚昧之举,无忠义可言。而是“逆先人之志节以殉仇贼之子孙”的不仁不智行为,是“妄人之妄,自毙而已矣”。嵇绍死不得其所,而死不得其所者乃是刑戮之民,“死而不得其所者,谓之刑戮之民。而谁邪?”嵇绍应为刑戮之民。王夫之痛愤地设问,嵇绍的荡阴之血,为何“不洒于魏社为屋之日”,为何“不洒于叔夜赴市之琴”,反倒“洒于司马氏之衣呢?”①王夫之指出,“嵇绍忘怨而忠其君”,“几于悖”也,忘父仇而效忠惠帝是忠孝相悖,“绍能死而不能不仕也”,他能够为惠帝死难以尽所谓臣道,却不能不仕而尽孝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忠义之举。因此,对嵇绍“许之孝而不得,则许之忠而亦不得已”②,嵇绍不可许之为孝是自然,许之为忠也是很牵强,很悖理。完全否定嵇绍有忠君行为是王夫之评价的重要特点,这是有针对性的。或许朱熹承认嵇绍死难是忠君行为,明儒中从朱说者程潜说,晋惠帝时朝政昏暗、士风颓败,“独嵇绍一死,遣芳万古,凛乎其可敬也”③。赞扬了嵇绍死难是其时难得之举,流芳于古的。所以,王夫之此说对嵇绍评价有深化作用。
二
有明一代,王夫之批评嵇绍仕晋最为严厉和尖锐,相关论述也最多。更重要的是,与朱熹一样,对评价嵇绍仕晋过咎的立论基础和指导理念也揭示得最为深刻、阐述得最为集中。由于朱熹和王夫之的同调合力,使评价嵇绍仕晋终成为一个具规模、持运作、影响大的儒家思想史上问题意识,这就是我们所以把朱熹、王夫之并立合说,一起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因。
嵇绍仕晋评价作为一种史论,既有明确的是非功过的具体评断,又有或显或隐的作出评断的立论基础和指导理念,任何史论都是有相应的立论基础和指导理念,前者实际上是在后者引导和规范下运行的。所以,后者的研究是史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它是史论研究的前理解或理论视域研究,即是理论框架的研究。
评价嵇绍仕晋的理论框架是什么?是父子之论和君臣之论的比较关系,是孝道和臣道的比较关系。王夫之说:“出处者,君子之大节也。”①出处即是士的仕或不仕问题。嵇绍是否应该仕晋属于儒家历来关注的士之仕和不仕问题意识,但“出处”的具体内涵指向是不同的。由于其父嵇康是无罪受诛,若仕晋则不孝其父,不仕则孝其父,若仕晋又必忠其君,但其君是杀父仇人,故忠君则是忠杀父仇人,违于孝道,这里孝和忠处于矛盾相悖关系中,这就是嵇绍仕晋问题的具体内涵指向。朱熹和王夫之等主张嵇绍不应仕,而司马氏所以不能为嵇绍所仕之君,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杀父仇人,而不是篡魏权臣。应该看到,在朱熹正统论中,晋是一统天下的正统朝代,非“僭伪”。在宋以前,朱熹只认定周、秦、汉、晋、隋、唐六朝是正统,余者皆不是正统。正统判定标准只是天下为一,诸侯归属,“只天下为一、诸侯乾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不是对政权取得和朝廷施政状况做历史或道德的评价,所谓正统说关键是在“统”而不在“正”。晋之为正统是在司马炎兵吞蜀、吴后,“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②朱熹认为,嵇绍所以不能仕晋就只在于司马氏是嵇绍杀父仇人,仕则违背孝道,不仕自然不能尽臣道,不能为其忠。因此,所谓嵇绍是否应仕晋,实际上已经表现为嵇绍是应尽孝道还是尽臣道的问题,转化为嵇绍如何认识和处理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关系问题。
朱熹和王夫之评价嵇绍仕晋问题是紧紧围绕着怎样认识和处理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关系问题展开的。因此,他们自己是怎样认识和理解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关系则自然成为评价的前理解。实际上,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的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的理论框架,就有怎样的嵇绍仕晋具体评价。朱熹和王夫之评价嵇绍仕晋确实也涉及许多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关系,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被儒家认为是五种基本人伦关系,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又是五伦之大,“并大于域”中者。①忠君主与孝父母是一致的统一的,都是仁义礼智信五德的表现形式,但由于嵇绍仕晋面临着尽孝道则不应仕和尽臣道则可仕的矛盾选择,渗透和体现的是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既一体又差异的一面。因此,朱熹和王夫之论述两类伦理,需要着重揭示和凸现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的区别差异性。
朱熹对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是既论其同,也识其别。他认为两类伦理最重要的区别是父子关系是自然天属关系,是先天的,人不可以选择;而君臣关系是非自然天属关系,是后天的,人可以选择。在五伦中,“唯父子、兄弟为天属,而以人合者居三焉”,天属者只有父子和兄弟二伦,人合者有君臣、夫妻、朋友三伦。朱熹对前贤五伦皆“天之所叙”的属性关系观点提出质疑,虽然他以前也曾如此认为。“人之大伦,其别有五,自昔圣贤皆认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但现在“考之”,乃“若有可疑者”。五伦中只有父子、兄弟二伦才是真正的“天之所叙”关系。所谓“天之所叙”者是血缘关系,是先天的“不得不合”者,无可选择和逃避;而君臣、夫妻、朋友三伦是后天性的“以人而合”者,所谓“以人而合”者是非血缘关系,是后天的“义合”,可以选择和逃避。“义合”是有人为的选择性和契合性的,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但可以选择自己的君臣和朋友。当然,“义合”也是体现和符合天理的,“虽或人而合,其实皆天理之自然”①。朱熹特别强调了父子关系的无可逃脱性和君臣关系的可以选择性,如庄子说“子之于父,无适而非命也”,父子是命的关系;“臣之于君,无适而非义也”,君臣是义的关系。“义合”总可选择,而父子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②
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的形成起源和本质属性的重要区别,导致出两类伦理的情感状况的区别。朱熹解析了君臣情感的后天人为特征,他回答门人问“君臣父子,同是天伦,爱君之心,终不如爱父,何也”时说,这是一般庶民的心理状况,承认这种心理状况的存在普遍性,同时指出,贤人君子是爱君如同爱父的。接着剖析了这种情感状况的产生原因。因为君臣是后天的“义合”关系,有选择可能性,所以“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义合的人为感情可能会被看得轻又苟且待之。君臣关系“自是有不得已的意思”,总是难免有强制性和权宜性,不能等同于先天纯自然的血缘感情。“父子兄弟夫妇,总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而君臣感情难达于此。
朱熹揭示和阐述的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的重要区别及其情感状况特点为评价嵇绍仕晋提供了重要的立论根据。君臣伦理不同于父子伦理的非自然天属的后天“义合”性质的,是士的仕或不仕的取舍选择有合理性的内在原因,士不一定必须仕和只能仕,同样也可以不仕,仕或不仕取决于是否符合“义合”的要求。非自然属性关系总是有去留自由的,这不同于无可逃避的自然天属关系。自然天属性质还决定和导致出对非自然天属性质关系的本位性和制约性,儒家本是移孝入忠,而不是移忠入孝的。朱熹赞同“以孝弟推说君臣等事”,他们“皆天然合当如此底道理”①。儒家主张忠君,忠诚事朝,忠君的感情应该如同孝父感情一样淳厚,但对孝敬父的感情大于和重于对忠君的感情,仍然是儒家最推崇和赞扬的理想感情。孟子说,舜“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人之所祈求的好色、富、贵皆有之,但仍“不足以解忧”,而“唯顺于父母,可以解忧”,明确地把舜视为孝道重于和大于君道的人格典范。朱熹很赞同孟子的解说和评价,说舜“极天下之欲不足以解忧,则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真知舜之心哉!”②。舜是士认识和处理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时应该效法的榜样,以舜为榜样,嵇绍完全是可以不仕更不应仕的。
王夫之也是从辨析父子伦理与君臣伦理的差异区别去寻求评价立论基础的,他对《孝经》一段论述的解读,窥识出父子一伦和君臣一伦的差异,展示了臣对待君的感情特点。《孝经·士章第五》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此是“士之孝”的重要内容。邢邴注曰:“资,取也”,取父爱而事母,取父敬而事君,士应爱母敬君,事母是爱,事君是敬,而唯有事父兼有爱和敬。王夫之诠释说:“君之与父,不得合敬而同爱矣,”君臣关系不可能像父子那样是敬爱同兼的。臣子对君主的行为原则主要是“敬”。何谓“敬”?“若论敬,则陈善闭邪之说也”,臣下对君主要进善杜邪,对君主不是为非之处应该劝谏,若无效,则“即以去言之”,行臣之道是“道合则从,不合则法,美则将顺,恶则匡救”,这是与行子之道大不相同的,对父亲之非不是,“谏而不从”也“终无去道也”。王夫之指出:“故汤、武、伊、霍之事,概与父子之事父天地悬隔”,大不区别。因此,对于两类人伦关系不可以随意“套著说”。李延平说:“天下无不是底父母”,这是“全从天性之爱上发出”,有道理,此是就爱言,“却与(对君主)敬处不相干涉”,潜室说:“天下无不是底君”、则是错误,是套李说,成为庸臣佞才“逢君之恶”的根据,根本有违于儒家父子君臣之道的真谛。同样,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①论点也错误。王夫之此解说是有价值的。儒家移孝入忠,从父子关系推论君臣关系,因此,认识理解父子关系感情形态也就成为把握和处理君臣关系的一个应备前提,正如邢邴曰:“兼取爱敬者其惟父乎,既说爱敬取舍之理,逐明出身入仕之行。”②明白待父感情与待君感情的异同,对于出身入仕是很重要的。王夫之以《孝经》为经典文本去阐述处理君臣关系的感情原则也是有匠心的,《孝经》是能够完整体现和忠实展现孔子原始儒家孝忠思想真谛的一个经典文本。明儒吕维祺说:孔子作“孝经为万世帝王法”,如果把东汉马融《忠经》与《孝经》“并称”,则大“不可”,是错误的。《忠经》说“众善咸起于忠”,以忠而非孝为众善之本源,甚至主张“君子行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这“有悖于”儒家“事君之旨”,若按马融所言,则不仕的“隐居之士终不得言孝”,不仕者已本无忠君可言。把《忠经》比拟《孝经》实“何异井之窥天,蠡之测海也”①。
王夫之正是从《孝经》经典中撷取和凸现儒家的尽忠须行孝,不行孝难言尽忠的孝本位思想,并且以此为立论根据,严厉批评了嵇绍仕晋行为。他说:“有夫妻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②指出父子关系对君臣关系的本位性和起源性,因此,嵇绍仕晋后为晋惠帝死难实为“不知有父者,恶知有君”③,嵇绍丧失父子之伦,岂能尽君臣之道?他强调:“孝,道之大者也,非至德者其孰能凝之?”孝道是大道之美德,不是依附忠道的派生物,唯至德者才能真正体验和践行。王夫之立足于孝本位立场对嵇绍的严厉批评,尤其是“孝道之大能统忠,而无与相悖之理”的观点。④清儒中是有回应的,清儒毛先舒说:按照儒家经典,“君尊于父,父统于君”,君的尊严自然大于父,而父却统率于君。因此,“忠之大者不背孝”,即使是大忠也不能违背于孝,嵇绍仕晋后的死难不能称为忠,“忘父所君而事其仇,其得谓之忠也?”忠已与嵇绍无缘了。《晋书》列嵇绍入《忠义传》是不妥的。⑤
因与尽孝道矛盾相悖而嵇绍不应仕晋,不可仕晋,这说明尽孝道对尽臣道的限制和制约,即父子一伦对君臣一伦的限制和制约,说明士之入仕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士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可以仕,都可尽君臣之道。在这里,尽孝道而不可仕与尽臣道而可以仕两者处在一种矛盾对立关系,有矛盾对立则必有取舍选择,朱熹、王夫之都主张选择结果应是尽父子之孝道的不仕,而不是违背父子之伦去履行君臣之伦的仕,这体现和显示儒家的孝道高于臣道、父子人伦优于君臣人伦的价值取向,即使不尽君臣之道也应该尽父子之道的选择取舍,体现和显示在两类人伦矛盾相悖情况下,父子一伦对君臣一伦的首位性和主导性。
一
朱熹评价始终是围绕嵇绍应不应仕晋展开的。朱熹明确主张嵇绍不可仕晋,“绍不当仕晋明矣”①,嵇绍仕晋是背父不孝的行为,即使以后为晋惠帝死难也不抵此咎。原因为其父嵇康无罪被司马昭诛杀,嵇康是魏臣,作为其子,嵇绍应该复仇,即使因时势难以为之,也至少应该避世隐居,而尤不可仕仇君之朝。朱熹反对子仕仇君之朝,他答门人子升问:“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时说:“不可。”此无可选择。当然,随着时世变迁,到了孙曾时代,情况可有变化,“世数渐远,终是渐轻,亦有可仕之理”,有出仕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亦须知“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权也”②,不仕的原则立场和权的变通之宜分野区别仍然是必须明白的。
嵇绍最有价值的行为选择是向司马氏复仇。对儒家尤其是公羊春秋所主张的大复仇理论,朱熹基本上是赞同的。他评价伍子胥为其父复仇楚平王时说:“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③赞成伍子胥复仇于楚平王的行为,当然若受诛者本有罪则不在此类。复仇不仅是适应于臣为君报仇,也适应于子为父报仇,即使仇者是君主,它是适应于父子和君臣两伦的。“然则其君父不幸而罹于横逆之故,则有为臣子者所以痛愤怨疾而求为之必报其仇者,其志岂有穷哉!故记礼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干,不与共有天下也”,所不同的只是庶人,百姓报父仇“未及五世之外”,而“有天下”的君主,“承万世无疆之统,则亦有万世必报之仇,非若庶民五世”,“自高祖以至玄孙,亲尽服穷而遂已”①,是没有世代时期限制的。这里“记礼者曰”“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一段是孔子回答子夏问,载《礼记·檀弓上》。朱熹通过引据典籍和转述孔子之言阐述了儒家的大复仇思想。
比较嵇绍仕晋行为与历史上相似行为是评价嵇绍重要的参考标准。朱熹首先进行的是嵇绍与同时代的王裒比较,王裒是晋武帝谋臣王仪之子,王仪也被晋武帝无罪诛杀。后晋室招王裒进朝入仕,王裒拒招隐居,朱熹赞许之。“而裒不仕,乃过于于厚者”②,王裒不仕是忠于孝道的表现,尽了职责,值得提倡。况且王仪是司马昭的军师,是晋臣,而嵇康是魏臣,拒绝入仕被诛杀,两者很有区别。“王仪为司马昭军师,昭杀之虽无辜,裒仕晋犹有可说”,司马昭与王裒非异朝之君,若仕也有可说之理,本无事异朝之君这层障碍,王裒拒仕是孝道高于君道的一个榜样典范。嵇绍与其相去甚远。
嵇绍仕晋也不能与管仲不死公子子纠而后仕于齐桓公、魏徵先仕李建成而后仕于李世民相比较,他们的情况不同。管仲不为公子纠死节和魏徵不为李建成死节且后皆仕杀故主的仇人,衷心辅佐,屡建奇功是有原因的,主要为尊周室、攘夷狄、存华夏和一统天下。“管仲不死子纠,圣人无说,见得不当死”,后又有奇功伟业,“郑魏公则是前仕建成矣,不当更仕太宗,后却有功”,此二人不死节都是事出有因。所以可说魏公“功可以补过犹可”,“管仲则前无过而后有功”①,情况不同于嵇绍。朱熹此项比较评价的取向标准是出仕的目的,更重要的是,管仲和魏徵都只是故主被杀,还都不是其父无罪被杀,他们都没有涉及孝道,没有涉及父子一伦。
在阐述对嵇绍仕晋行为的评价后,朱熹对司马光关于嵇绍荡阴死难可补偿仕晋之咎的观点提出质疑。司马光也认为嵇绍不应仕晋,但后在荡阴为晋惠帝死难可补不当仕之咎,“使无荡阴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讥”②。朱熹说:“荡阴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赎”③,虽然嵇绍确有其忠,也不能赎入仕之咎。因为“既策名委质,只得死也,不可以后功掩前过”④,一旦入仕为臣,则当尽臣之道,尽忠死节是正常的,此只是尽了臣道,是君臣关系,与以前违背父子之道是两回事,后臣道之忠不能掩盖和弥补前孝道之失,不能相混为一。“事仇之过,自不相掩”,温公之言有误。对嵇绍的讥讽批评,是从入朝仕晋而不是从仕晋后是否尽君臣之道开始的,因此也不是尽忠君所能抵偿和弥补的,为其不能和无法“免也”,故“不知君子之讥,初不可免也”⑤。嵇绍仕晋伊始讥讽就随之而起,就批评此是不尽孝道,非孝子之举。因为父子之道是一个独立的人伦范畴和理念,有其自身独立的价值意义,并不依君臣之道和随君臣之道而起的。实际上,其价值意义高于君臣之道、重于君臣之道,因此即使嵇绍后来有忠君表现也无法抵偿以前不孝之咎。应该看到,对嵇绍仕晋评价朱熹与司马光是有重要区别的。司马光曰:“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也认为因嵇康无罪受诛嵇绍可以不仕晋室,但没有做绝对性的要求,不明确断言不可仕,只说不仕“可也”,“可也”是有或然性的评断,可不仕,也可仕。司马光没有完全否定和批评仕,同时还没有绝对要求不仕,只是指出了不仕有合理性,可以谅解。所以,司马光对嵇康仕晋的批评是温和的,对于其仕和不仕的要求是有伸缩性的。而且,从举禹父鲧因治水不力被舜诛后仍事舜的例证,认为父子是私,臣君是公,赞扬舜不敢以其私而“废至公”观点看,他还是主张嵇绍可以而且应该仕晋的。①司马温公更没有嵇绍应该复仇的观点。
而且,司马光以舜杀鲧做司马昭杀嵇康而后嵇绍仕晋的例证,有逻辑背悖,容易引起误评。一方面承认嵇康死“不以其罪”,另一方面又用舜杀鲧有理为例证,颇不类不伦。有罪受诛者是不能与无罪受诛者视为同类的。这有意无意把嵇康受诛也视为有罪受诛之例,客观上影响到对嵇绍仕晋性质的评价。实际上,朱熹其前的一些史论正是按照这一路向运作的,北宋胡致堂著名的《资治通鉴》评读即是如此。“昔舜殛死崇伯而禹事舜为司空,又受其天下,何哉?至公故也,书曰:诛四罪而天下咸服言之云尔。何以见其服乎,以禹观之,子尚不能以殛其父为憾,他人可知矣,此之谓天下咸服。如绍者终身不仕晋室,如王裒可也。”但嵇绍却“忘父之怨,而从於禄仕之利”②,仕晋是错误的。胡氏先说禹不念其父被杀而事舜的合理性,后又批评嵇绍忘父仇仕晋的过咎,颇有些不伦不类、不着边际。清儒郭蒿焘说:“崇安胡氏《读史管见》”,“或因古人之事,传以己意;或是一己之辨,求胜前人,多失其平”。①看来,郭氏评胡氏是有道理的,但胡氏此评的路向思路是循从司马光的,两评大体相同。朱熹不赞同司马光评价,首先着力区别舜杀鲧与司马昭杀嵇康的性质有异,是有道理的。
朱熹的嵇绍仕晋说在朱熹在世时就有接受者和同调。户部右曹郎官王回做《嵇绍赞》,否定嵇绍之死是尽忠“死得其所”,是“行于乱世不汙,而能卒以忠为烈,非其积累,明于仁义,孰能自信如此耶”的观点。嵇绍不是素积仁义、临难自信的,也不值得后人效法赞颂。其父非“犯有司”,是为晋篡魏重要障碍而无罪受诛,“特晋方谋篡魏,忌其贤而见图”。嵇绍实是“兼父与君之仇者也”,嵇绍若“力不能报,犹且避之天下,”但他却“为仇人子孙死而为之,”“岂不谬哉!”②嵇绍是不值得“颂”的。显然,王回的评价是遵循嵇康无罪被诛和嵇绍不应仕晋这两个要点的。
明儒吴廷翰明确批评嵇绍仕晋是有君道而无父道。“嵇绍荡阴之节,君子多与之。然父为人杀,非其罪,力不能仇,忍复仕乎”,嵇康无罪被诛,嵇绍不能复仇,尚有可原,但岂能复仕其朝。“父仇不报,委身以事,而复为之死,是有君臣而无父子也,宁免君子之议乎?”嵇绍委身仕晋,更为之死难,不报父死,这种违背父子之道行为,受到后人讥议是难免的。讥议之要是在违背父子一伦,而不在忠君一伦,违背父子之道即使是遵从君臣之道,同样也要受到批评和讥议。司马光“或以绍之仕晋,苟无荡险之节,几不免君子之议”①的观点是错误的。顾炎武则说:“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余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②指出,嵇绍仕晋三十余年,忘父久矣定能以荡阴死难而赎其罪,况且所事又非君。
王夫之对嵇绍仕晋而死难行为的评价更苛刻、尖锐。他首先明确指出“嵇绍不可仕晋”,而一旦仕晋按照臣道要求则必然要为其死,“仕而恶可弗死也”,这就决定了死不得其所,“仕则必死之,故必不可仕也”,不仕是决定不死于非所的前提。“父不受诛,子弗仇焉,非心也”③,嵇康死于无罪,绍不报父仇是无良心,无父子人伦的。
如果说朱熹还承认嵇绍荡阴死难是忠的性质,还是在承认忠臣行为的基础上进行与仕晋之咎的功过比较的话,王夫之则完全否定了荡阴之死是忠的行为,倒是不仁和愚昧之举。“绍盖前人之美,而以父母之身,糜烂而殉怨不共天之乱贼,愚哉其不仁也”,绍仕不当仕之朝,又以父母所予之身为有父仇的昏庸之君死难是不仁且愚昧之举,无忠义可言。而是“逆先人之志节以殉仇贼之子孙”的不仁不智行为,是“妄人之妄,自毙而已矣”。嵇绍死不得其所,而死不得其所者乃是刑戮之民,“死而不得其所者,谓之刑戮之民。而谁邪?”嵇绍应为刑戮之民。王夫之痛愤地设问,嵇绍的荡阴之血,为何“不洒于魏社为屋之日”,为何“不洒于叔夜赴市之琴”,反倒“洒于司马氏之衣呢?”①王夫之指出,“嵇绍忘怨而忠其君”,“几于悖”也,忘父仇而效忠惠帝是忠孝相悖,“绍能死而不能不仕也”,他能够为惠帝死难以尽所谓臣道,却不能不仕而尽孝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忠义之举。因此,对嵇绍“许之孝而不得,则许之忠而亦不得已”②,嵇绍不可许之为孝是自然,许之为忠也是很牵强,很悖理。完全否定嵇绍有忠君行为是王夫之评价的重要特点,这是有针对性的。或许朱熹承认嵇绍死难是忠君行为,明儒中从朱说者程潜说,晋惠帝时朝政昏暗、士风颓败,“独嵇绍一死,遣芳万古,凛乎其可敬也”③。赞扬了嵇绍死难是其时难得之举,流芳于古的。所以,王夫之此说对嵇绍评价有深化作用。
二
有明一代,王夫之批评嵇绍仕晋最为严厉和尖锐,相关论述也最多。更重要的是,与朱熹一样,对评价嵇绍仕晋过咎的立论基础和指导理念也揭示得最为深刻、阐述得最为集中。由于朱熹和王夫之的同调合力,使评价嵇绍仕晋终成为一个具规模、持运作、影响大的儒家思想史上问题意识,这就是我们所以把朱熹、王夫之并立合说,一起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因。
嵇绍仕晋评价作为一种史论,既有明确的是非功过的具体评断,又有或显或隐的作出评断的立论基础和指导理念,任何史论都是有相应的立论基础和指导理念,前者实际上是在后者引导和规范下运行的。所以,后者的研究是史论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可或缺。它是史论研究的前理解或理论视域研究,即是理论框架的研究。
评价嵇绍仕晋的理论框架是什么?是父子之论和君臣之论的比较关系,是孝道和臣道的比较关系。王夫之说:“出处者,君子之大节也。”①出处即是士的仕或不仕问题。嵇绍是否应该仕晋属于儒家历来关注的士之仕和不仕问题意识,但“出处”的具体内涵指向是不同的。由于其父嵇康是无罪受诛,若仕晋则不孝其父,不仕则孝其父,若仕晋又必忠其君,但其君是杀父仇人,故忠君则是忠杀父仇人,违于孝道,这里孝和忠处于矛盾相悖关系中,这就是嵇绍仕晋问题的具体内涵指向。朱熹和王夫之等主张嵇绍不应仕,而司马氏所以不能为嵇绍所仕之君,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杀父仇人,而不是篡魏权臣。应该看到,在朱熹正统论中,晋是一统天下的正统朝代,非“僭伪”。在宋以前,朱熹只认定周、秦、汉、晋、隋、唐六朝是正统,余者皆不是正统。正统判定标准只是天下为一,诸侯归属,“只天下为一、诸侯乾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不是对政权取得和朝廷施政状况做历史或道德的评价,所谓正统说关键是在“统”而不在“正”。晋之为正统是在司马炎兵吞蜀、吴后,“晋初亦未得正统”,“自泰康以后,方始得正统”。②朱熹认为,嵇绍所以不能仕晋就只在于司马氏是嵇绍杀父仇人,仕则违背孝道,不仕自然不能尽臣道,不能为其忠。因此,所谓嵇绍是否应仕晋,实际上已经表现为嵇绍是应尽孝道还是尽臣道的问题,转化为嵇绍如何认识和处理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关系问题。
朱熹和王夫之评价嵇绍仕晋问题是紧紧围绕着怎样认识和处理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关系问题展开的。因此,他们自己是怎样认识和理解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关系则自然成为评价的前理解。实际上,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的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的理论框架,就有怎样的嵇绍仕晋具体评价。朱熹和王夫之评价嵇绍仕晋确实也涉及许多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关系,有许多这方面的论述。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被儒家认为是五种基本人伦关系,君臣关系和父子关系又是五伦之大,“并大于域”中者。①忠君主与孝父母是一致的统一的,都是仁义礼智信五德的表现形式,但由于嵇绍仕晋面临着尽孝道则不应仕和尽臣道则可仕的矛盾选择,渗透和体现的是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既一体又差异的一面。因此,朱熹和王夫之论述两类伦理,需要着重揭示和凸现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的区别差异性。
朱熹对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是既论其同,也识其别。他认为两类伦理最重要的区别是父子关系是自然天属关系,是先天的,人不可以选择;而君臣关系是非自然天属关系,是后天的,人可以选择。在五伦中,“唯父子、兄弟为天属,而以人合者居三焉”,天属者只有父子和兄弟二伦,人合者有君臣、夫妻、朋友三伦。朱熹对前贤五伦皆“天之所叙”的属性关系观点提出质疑,虽然他以前也曾如此认为。“人之大伦,其别有五,自昔圣贤皆认为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为也”,但现在“考之”,乃“若有可疑者”。五伦中只有父子、兄弟二伦才是真正的“天之所叙”关系。所谓“天之所叙”者是血缘关系,是先天的“不得不合”者,无可选择和逃避;而君臣、夫妻、朋友三伦是后天性的“以人而合”者,所谓“以人而合”者是非血缘关系,是后天的“义合”,可以选择和逃避。“义合”是有人为的选择性和契合性的,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兄弟,但可以选择自己的君臣和朋友。当然,“义合”也是体现和符合天理的,“虽或人而合,其实皆天理之自然”①。朱熹特别强调了父子关系的无可逃脱性和君臣关系的可以选择性,如庄子说“子之于父,无适而非命也”,父子是命的关系;“臣之于君,无适而非义也”,君臣是义的关系。“义合”总可选择,而父子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②
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的形成起源和本质属性的重要区别,导致出两类伦理的情感状况的区别。朱熹解析了君臣情感的后天人为特征,他回答门人问“君臣父子,同是天伦,爱君之心,终不如爱父,何也”时说,这是一般庶民的心理状况,承认这种心理状况的存在普遍性,同时指出,贤人君子是爱君如同爱父的。接着剖析了这种情感状况的产生原因。因为君臣是后天的“义合”关系,有选择可能性,所以“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义合的人为感情可能会被看得轻又苟且待之。君臣关系“自是有不得已的意思”,总是难免有强制性和权宜性,不能等同于先天纯自然的血缘感情。“父子兄弟夫妇,总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而君臣感情难达于此。
朱熹揭示和阐述的父子伦理和君臣伦理的重要区别及其情感状况特点为评价嵇绍仕晋提供了重要的立论根据。君臣伦理不同于父子伦理的非自然天属的后天“义合”性质的,是士的仕或不仕的取舍选择有合理性的内在原因,士不一定必须仕和只能仕,同样也可以不仕,仕或不仕取决于是否符合“义合”的要求。非自然属性关系总是有去留自由的,这不同于无可逃避的自然天属关系。自然天属性质还决定和导致出对非自然天属性质关系的本位性和制约性,儒家本是移孝入忠,而不是移忠入孝的。朱熹赞同“以孝弟推说君臣等事”,他们“皆天然合当如此底道理”①。儒家主张忠君,忠诚事朝,忠君的感情应该如同孝父感情一样淳厚,但对孝敬父的感情大于和重于对忠君的感情,仍然是儒家最推崇和赞扬的理想感情。孟子说,舜“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人之所祈求的好色、富、贵皆有之,但仍“不足以解忧”,而“唯顺于父母,可以解忧”,明确地把舜视为孝道重于和大于君道的人格典范。朱熹很赞同孟子的解说和评价,说舜“极天下之欲不足以解忧,则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孟子真知舜之心哉!”②。舜是士认识和处理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时应该效法的榜样,以舜为榜样,嵇绍完全是可以不仕更不应仕的。
王夫之也是从辨析父子伦理与君臣伦理的差异区别去寻求评价立论基础的,他对《孝经》一段论述的解读,窥识出父子一伦和君臣一伦的差异,展示了臣对待君的感情特点。《孝经·士章第五》说:“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此是“士之孝”的重要内容。邢邴注曰:“资,取也”,取父爱而事母,取父敬而事君,士应爱母敬君,事母是爱,事君是敬,而唯有事父兼有爱和敬。王夫之诠释说:“君之与父,不得合敬而同爱矣,”君臣关系不可能像父子那样是敬爱同兼的。臣子对君主的行为原则主要是“敬”。何谓“敬”?“若论敬,则陈善闭邪之说也”,臣下对君主要进善杜邪,对君主不是为非之处应该劝谏,若无效,则“即以去言之”,行臣之道是“道合则从,不合则法,美则将顺,恶则匡救”,这是与行子之道大不相同的,对父亲之非不是,“谏而不从”也“终无去道也”。王夫之指出:“故汤、武、伊、霍之事,概与父子之事父天地悬隔”,大不区别。因此,对于两类人伦关系不可以随意“套著说”。李延平说:“天下无不是底父母”,这是“全从天性之爱上发出”,有道理,此是就爱言,“却与(对君主)敬处不相干涉”,潜室说:“天下无不是底君”、则是错误,是套李说,成为庸臣佞才“逢君之恶”的根据,根本有违于儒家父子君臣之道的真谛。同样,韩愈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①论点也错误。王夫之此解说是有价值的。儒家移孝入忠,从父子关系推论君臣关系,因此,认识理解父子关系感情形态也就成为把握和处理君臣关系的一个应备前提,正如邢邴曰:“兼取爱敬者其惟父乎,既说爱敬取舍之理,逐明出身入仕之行。”②明白待父感情与待君感情的异同,对于出身入仕是很重要的。王夫之以《孝经》为经典文本去阐述处理君臣关系的感情原则也是有匠心的,《孝经》是能够完整体现和忠实展现孔子原始儒家孝忠思想真谛的一个经典文本。明儒吕维祺说:孔子作“孝经为万世帝王法”,如果把东汉马融《忠经》与《孝经》“并称”,则大“不可”,是错误的。《忠经》说“众善咸起于忠”,以忠而非孝为众善之本源,甚至主张“君子行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这“有悖于”儒家“事君之旨”,若按马融所言,则不仕的“隐居之士终不得言孝”,不仕者已本无忠君可言。把《忠经》比拟《孝经》实“何异井之窥天,蠡之测海也”①。
王夫之正是从《孝经》经典中撷取和凸现儒家的尽忠须行孝,不行孝难言尽忠的孝本位思想,并且以此为立论根据,严厉批评了嵇绍仕晋行为。他说:“有夫妻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②指出父子关系对君臣关系的本位性和起源性,因此,嵇绍仕晋后为晋惠帝死难实为“不知有父者,恶知有君”③,嵇绍丧失父子之伦,岂能尽君臣之道?他强调:“孝,道之大者也,非至德者其孰能凝之?”孝道是大道之美德,不是依附忠道的派生物,唯至德者才能真正体验和践行。王夫之立足于孝本位立场对嵇绍的严厉批评,尤其是“孝道之大能统忠,而无与相悖之理”的观点。④清儒中是有回应的,清儒毛先舒说:按照儒家经典,“君尊于父,父统于君”,君的尊严自然大于父,而父却统率于君。因此,“忠之大者不背孝”,即使是大忠也不能违背于孝,嵇绍仕晋后的死难不能称为忠,“忘父所君而事其仇,其得谓之忠也?”忠已与嵇绍无缘了。《晋书》列嵇绍入《忠义传》是不妥的。⑤
因与尽孝道矛盾相悖而嵇绍不应仕晋,不可仕晋,这说明尽孝道对尽臣道的限制和制约,即父子一伦对君臣一伦的限制和制约,说明士之入仕是有条件,有限制的,士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可以仕,都可尽君臣之道。在这里,尽孝道而不可仕与尽臣道而可以仕两者处在一种矛盾对立关系,有矛盾对立则必有取舍选择,朱熹、王夫之都主张选择结果应是尽父子之孝道的不仕,而不是违背父子之伦去履行君臣之伦的仕,这体现和显示儒家的孝道高于臣道、父子人伦优于君臣人伦的价值取向,即使不尽君臣之道也应该尽父子之道的选择取舍,体现和显示在两类人伦矛盾相悖情况下,父子一伦对君臣一伦的首位性和主导性。
附注
①肖美丰,芜湖市委党校教师。
②《资治通鉴》卷八〇《晋纪二》。
①《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1页。
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1页。
③《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11页。
①《朱熹集》卷七五《戊午谠议序》,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11页。
①《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9页。
②《资治通鉴》卷八〇《晋纪二》。
③《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1页。
④《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9页。
⑤《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41页。
①《资治通鉴》卷八〇《晋纪二》。
②《致堂读史笔见》第六《晋纪·武帝上》,载阮元辑《宛委别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①《彭笙陔明史论略序》,载《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
②《嵇绍赞》,载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七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①《吴廷翰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8页。
②《日知录》,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471页。
③《船山全书》第10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23页。
①《船山全书》第10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43页。
②《船山全书》第5册《续春秋左传氏博议卷下》,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92页。
③程潜:《明断编》,《丛书集成》初编本。
①《船山全书》第8册《四书训义》(下),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651页。
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36页。
①顾大韶:《放言一》(《清文汇》上册),北京出版社1955年版,第53页。
①《朱熹集》卷八一《跋黄仲友朋友说》,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3页。
①《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4页。
②《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3页。
①《船山全书》第6册《读四书大全说》,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012页。
②《孝经注疏》,《十三经注疏》本。
①吕维祺:《孝经或问》,《丛书集成》初编本,第92页。
②《船山全书》第5册《春秋家说》,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127页。
③《船山全书》第10册《读通鉴论》,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24页。
④《船山全书》第5册,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92页。
⑤毛先舒:《出处论》(《清文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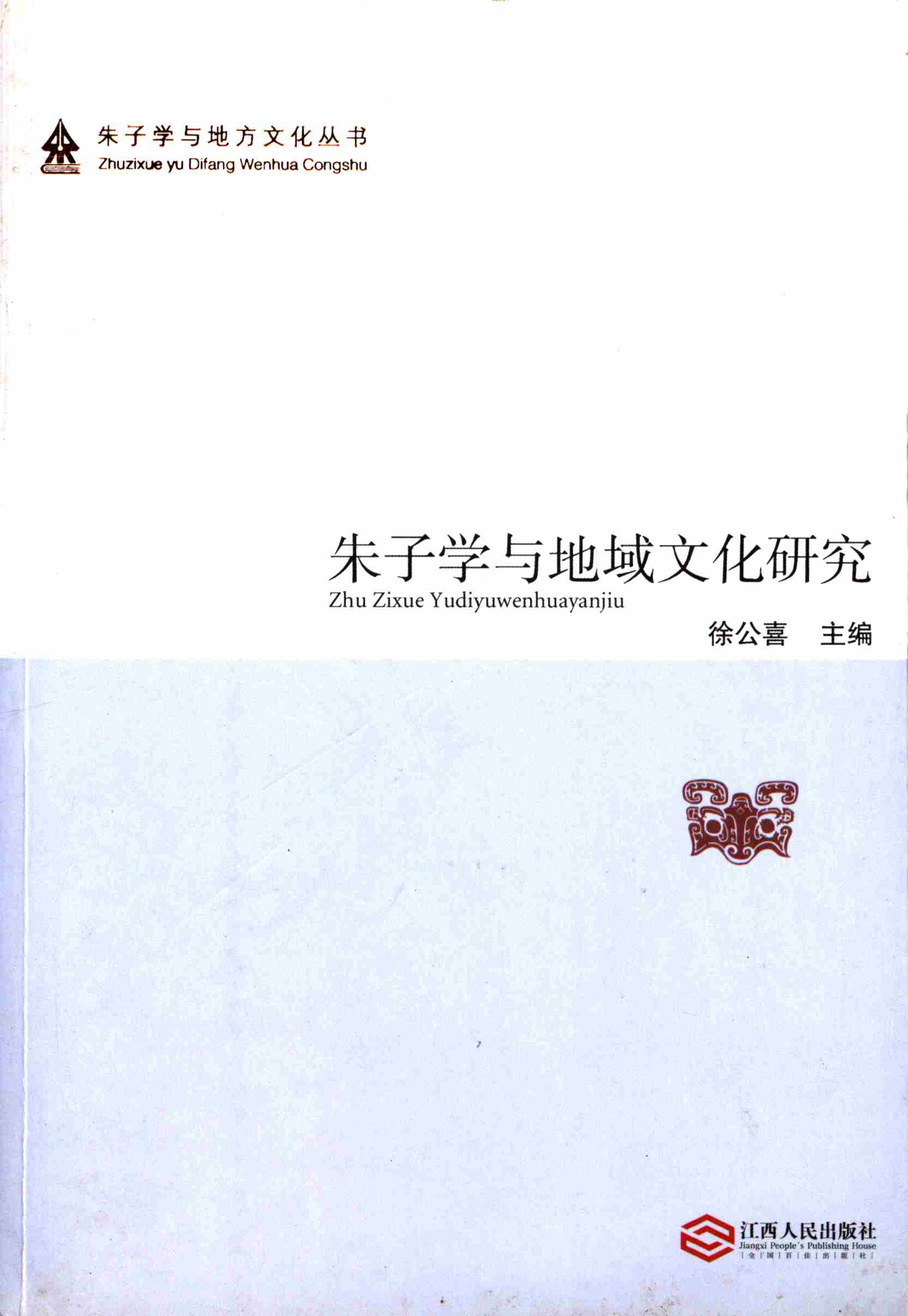
《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2013年“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研讨会的成果汇编,收录《新安理学特质》、《试论饶鲁的学术思想与心学化的双峰学派》、《朱子理学与关帝信仰》、《韩国九曲园林雏形阶段》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肖美丰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