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期闽中理学的理论特征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765 |
| 颗粒名称: | 二、早期闽中理学的理论特征 |
| 分类号: | B244.75;G127 |
| 页数: | 10 |
| 页码: | 58-67 |
| 摘要: | 这篇文章讲述了早期闽中理学的理论特征,早期闽中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早期闽中理学的理论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强调太极是至理之源;注重“格物致知”;重视“知行合一”;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强调“诚意正心”。 |
| 关键词: | 朱熹 理学 哲学史 |
内容
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除了与北方中原理学有思想渊源关系,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外,还受到闽中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应该说,早期闽中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这一理论特征可以从早期闽中理学的代表者思想中得到体现。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特征,早期闽中理学才能成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学派的理学流派。早期闽中理学的理论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理阐释太极,强调太极是至理之源
太极一词始见于《易·系辞上》:“易有太极。”理学家讲“太极”,肇始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自无极而为太极。”“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周氏把“无极”作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本源,而以太极为阴阳混沌未分之气。张载以“气”为本体,同时用太极一词来说明“气”。他说:“一物两体,气也。”①“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②二程以“理”为本体,他说:“万物皆是一理。”③二程讲理本,“太极”未提到基本范畴。邵雍主象数学,是最早把“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他说:“生天地之始,太极也。”“能造万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极也。”④邵雍以“太极”为本体,而“理”则只是物的自然属性的表现而已。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对北宋五子的理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闽中学者杨时作为二程的门人,也是以“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他说,“盖天下只是一理”⑤这个理是宇宙的最高原则,无论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还是社会的伦理纲常,都“本于一理”。杨时认为,理贯穿于一切事物,“有物必有则也,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性”。⑥每个事物都是天理的体现。但是,与北宋五子所不同的是,杨时以理为太极,他说:“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⑦太极就是自然之理,它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杨时的这一思想到再传弟子李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李侗发挥了二程“天下只有一个理”的理本论,以其“理”的一元论来诠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太极动而生阳,“此只是理”,“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①在这里,李侗提出了太极是“至理之源”,是最高的理。这一思想是对周敦颐、二程本体论思想的一个很好发挥。应该说,以太极为至理之源,是早期闽中理学的重要特征,也是它区别其他学派的标志之一。
(二)阐发理一分殊,强调以殊求一
“理一分殊”思想是程颐在回答杨时关于张载《西铭》的疑问时提出来的。绍圣三年(1096),杨时去信给程颐请教:“《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②认为《西铭》虽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讲“仁之用”,如此就可能导致墨子之兼爱说。程颐在复信中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③。程颐认为理一与分殊均不可偏废,就如仁与义。杨时正是通过对“理一分殊”概念的阐发,既继承了二程之学的立场,又说出了张载《西铭》之中的未尽之意,并且将“理一分殊”赋予普遍意义,使之成为早期闽中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杨时认为“理一分殊”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进而以仁与义诠释理一与分殊。他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①这就将本体的“理”和现实的伦理紧密地联系起来,丰富了其伦理道德的意蕴。杨时还用体用关系来阐述“理一分殊”,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他说:“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其用处,则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也。”②体用就如人的身体与百骸,从人的全身来看,这是理一之体;从四体的百骸来看,这是分殊之用。故用不离体,分在理中。杨时从体用处说“理一分殊”,把“理一分殊”之说应用到道德修养上,知如何去实现仁的品德修养,知所谓“分殊”,使二程超越时空绝对的“理”,与现实沟通更密切了。
杨时的门人罗从彦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亦用体用关系阐发“理一分殊”思想。他说:“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之谓也。”③这就使其师杨时的观点更加明确。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他在杨时“体用兼备”思想的基础上,更重视分殊,强调阐明“理之用”的重要性。他认为:“理不患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④又说,“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万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⑤可见,李侗特别重视“分殊”,而且对分殊的认识强调要很细致,做到毫发不可失。同时,李侗还认为,知其理一要在“知”字上用力。他说:“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①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着眼于“知”字,强调对分殊的认识,因而也就具有“穷理”的认识论意义。早期闽中理学的格物穷理方法,正是注重从具体的分殊的事物入手,认为经过对分殊的积累,自然会上升到对理的认识。这种注重对“理一分殊”思想的阐发,强调以“殊”求“一”的理论,亦是早期闽中理学的明显理论特征。
(三)既注重格物穷理,又强调反身而诚
格物致知说是早期闽中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二程格物致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程的诸多弟子中,闽中杨时是比较注重对格物致知说进行阐发的。就杨时“格物致知”的路向而言,明显地存在着把外求的格物功夫与内省的明心涵养相结合的倾向。杨时说:“为是道着,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②又说,“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③这就是说,要“明善”就必须致知,格物是致知的有效途径。杨时又认为:“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心之知。”④“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鼻之于臭味,接乎外而不得循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物与吾一也。”⑤杨时主张通过主体接触客体,以获得关于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认识,其格物之道就是要求通过多种途径遍格众物,以“极尽物理”。但是,天下万物,如何穷尽?要格尽天下万物,杨时提出了“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①的办法。可见,杨时的格物致知论既强调向外求索,又要求“反身而诚”,并且认为,只有在向外求索中,又“反身而诚”,才能“举天下之物在我矣”。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杨时讲“反身而诚”是作为“格物”过程中为了格尽天下万物而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讨论“格物”与“反身而诚”的先后次序关系。
李侗在主张静坐体认天理的同时,又强调要“于日用处着力”,“须就事体用下功夫”。他说:“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处着力,可见端绪,在勉之尔。”②李侗还提出了“融释”说。他说:“为学之初,且常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穷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所及也。”③这里所说的“常存此心”,就是要时时保持持敬之心,排除不符合天理,即排除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干扰,做到“心与理一”。遇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实际上也就是格物穷理。“融释”就是程颐所谓的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然有贯通处。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学者是采取外向探索和内省工夫,渐次积累和豁然贯通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格物致知论。(四)默坐澄心,静中体认未发
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十分注重对《中庸》之中道思想的阐发,从《中庸》中寻找所谓未发之旨。杨时作《中庸义》曰:“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①杨时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亦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②杨时这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之法,在于他认为通过默而识之的内心体验工夫,最终能够超然自得。但这所得既然来源于言意之表,也就无法言说传诵。由此可知,杨时由《中庸》而来的这种涵养心性,体验喜怒哀乐未发的功夫,不是如禅门的“悟无所得”,而是有确定的内容,即“至道”的。道出于书言意象之外,所以忘言忘象才能体道,而非口耳诵数所得识。杨时提出“以身体之,心验之”默识中道的存养工夫,后来成为闽中道南学派的重要课题。
罗从彦对其师杨时“默识中道”的存养功夫,认真予以践履。他曾入罗浮山筑室静坐三年,“以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他作诗云:“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周诚程敬应初会,奥理休从此外寻。”③罗从彦“观心”所追求的“奥理”,他认为可以从周敦颐的“诚”和二程的“敬”中去寻求。心中一尘不染,闲中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便可进入一种“彩笔书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无痕。人心但得如空水,与物自然无怨恩”④的境界。如何体验“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罗从彦明确提出了“静中体验未发”之说。故后人多说罗从彦为学是“以主静为宗”①,理由有:一是罗从彦曾筑室于罗浮山,静坐穷理,即通过内心的体悟把握天理;二是罗从彦主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这种“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阐发,构成了早期闽中理学学者追求“静养”的境界的特征。
李侗对“静中体认未发”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②李侗的学生亦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旨诀。”③未发之“中”作何“气象”,实际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但毕竟包含“进学”和“养心”的双重内容,二者之间是一体互发的关系。李侗认为,进学与养心的目的都在于“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如此的“气象”,既是指圣贤洒落超脱的境界,又同时意味着哲学的本体,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中”。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学者体验未发之中的心性锻炼,是一种追寻哲学本体和提升道德境界的综合进程。
(五)重视对“四书”的诠释
宋代以后,中国正宗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书”之中。《宋史·列传·道学一》说: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从这段文字可见,“四书”并行,最初是出于二程的提倡。闽中学者游酢师承二程,对“四书”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为学重在发挥经书中的义理,“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①。游酢所撰写的《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都是对“四书”诠释的重要著作。在他的这些著作中,“足资深发者固已多矣”②。清人方宗诚说:“自二程夫子起,始独得于章句笺疏之外,而见圣贤立言之本心。先生(指游酢)及同门诸子,互有以发明之,于是经之大体大用始著。”③杨时亦非常重视“四书”。他认为:“《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④“《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⑤“《孟子》以睿知刚明之材,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为知言也。今其书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⑥“《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⑦杨时对门人说:“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⑧罗从彦于政和元年(1111),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后写成《语孟师说》、《中庸说》和《议论要语》等名著,对“四书”亦进行了阐发。李侗拜师罗从彦后,“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①。李侗在《延平答问》中,诸多条是回答学生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中的疑问的。闽中武夷学派的胡宪对“四书”中的《论语》有极深的研究。他广泛收集数十家《论语》解说,后来以二程说为本,抄摘各家精要,并附以己意而写成《论语会义》。该书为后来朱熹以《论语》为核心的“四书”学奠定了根基。宋代以后,儒家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这个转变始自二程,而由朱熹所完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早期闽中理学家们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料。据美国著名朱子学家陈荣捷教授统计,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用了32位学者的731条语录,其中引述闽中学者杨时之论73条,李侗之论13条。此外,还有引用游酢等闽中学者的语录。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家推崇“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诠释“四书”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上述可见,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理学文化现象,它是整个理学思潮的一部分。它同中原理学的发展,闽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理学渊源关系而言,它是中原理学南移后的一个发展。就理论特征而言,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应该说,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为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来源和有益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一)以理阐释太极,强调太极是至理之源
太极一词始见于《易·系辞上》:“易有太极。”理学家讲“太极”,肇始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自无极而为太极。”“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周氏把“无极”作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本源,而以太极为阴阳混沌未分之气。张载以“气”为本体,同时用太极一词来说明“气”。他说:“一物两体,气也。”①“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②二程以“理”为本体,他说:“万物皆是一理。”③二程讲理本,“太极”未提到基本范畴。邵雍主象数学,是最早把“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他说:“生天地之始,太极也。”“能造万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极也。”④邵雍以“太极”为本体,而“理”则只是物的自然属性的表现而已。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对北宋五子的理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闽中学者杨时作为二程的门人,也是以“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他说,“盖天下只是一理”⑤这个理是宇宙的最高原则,无论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还是社会的伦理纲常,都“本于一理”。杨时认为,理贯穿于一切事物,“有物必有则也,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性”。⑥每个事物都是天理的体现。但是,与北宋五子所不同的是,杨时以理为太极,他说:“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⑦太极就是自然之理,它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杨时的这一思想到再传弟子李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李侗发挥了二程“天下只有一个理”的理本论,以其“理”的一元论来诠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太极动而生阳,“此只是理”,“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①在这里,李侗提出了太极是“至理之源”,是最高的理。这一思想是对周敦颐、二程本体论思想的一个很好发挥。应该说,以太极为至理之源,是早期闽中理学的重要特征,也是它区别其他学派的标志之一。
(二)阐发理一分殊,强调以殊求一
“理一分殊”思想是程颐在回答杨时关于张载《西铭》的疑问时提出来的。绍圣三年(1096),杨时去信给程颐请教:“《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②认为《西铭》虽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讲“仁之用”,如此就可能导致墨子之兼爱说。程颐在复信中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③。程颐认为理一与分殊均不可偏废,就如仁与义。杨时正是通过对“理一分殊”概念的阐发,既继承了二程之学的立场,又说出了张载《西铭》之中的未尽之意,并且将“理一分殊”赋予普遍意义,使之成为早期闽中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杨时认为“理一分殊”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进而以仁与义诠释理一与分殊。他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①这就将本体的“理”和现实的伦理紧密地联系起来,丰富了其伦理道德的意蕴。杨时还用体用关系来阐述“理一分殊”,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他说:“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其用处,则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也。”②体用就如人的身体与百骸,从人的全身来看,这是理一之体;从四体的百骸来看,这是分殊之用。故用不离体,分在理中。杨时从体用处说“理一分殊”,把“理一分殊”之说应用到道德修养上,知如何去实现仁的品德修养,知所谓“分殊”,使二程超越时空绝对的“理”,与现实沟通更密切了。
杨时的门人罗从彦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亦用体用关系阐发“理一分殊”思想。他说:“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之谓也。”③这就使其师杨时的观点更加明确。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他在杨时“体用兼备”思想的基础上,更重视分殊,强调阐明“理之用”的重要性。他认为:“理不患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④又说,“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万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⑤可见,李侗特别重视“分殊”,而且对分殊的认识强调要很细致,做到毫发不可失。同时,李侗还认为,知其理一要在“知”字上用力。他说:“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①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着眼于“知”字,强调对分殊的认识,因而也就具有“穷理”的认识论意义。早期闽中理学的格物穷理方法,正是注重从具体的分殊的事物入手,认为经过对分殊的积累,自然会上升到对理的认识。这种注重对“理一分殊”思想的阐发,强调以“殊”求“一”的理论,亦是早期闽中理学的明显理论特征。
(三)既注重格物穷理,又强调反身而诚
格物致知说是早期闽中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二程格物致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程的诸多弟子中,闽中杨时是比较注重对格物致知说进行阐发的。就杨时“格物致知”的路向而言,明显地存在着把外求的格物功夫与内省的明心涵养相结合的倾向。杨时说:“为是道着,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②又说,“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③这就是说,要“明善”就必须致知,格物是致知的有效途径。杨时又认为:“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心之知。”④“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鼻之于臭味,接乎外而不得循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物与吾一也。”⑤杨时主张通过主体接触客体,以获得关于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认识,其格物之道就是要求通过多种途径遍格众物,以“极尽物理”。但是,天下万物,如何穷尽?要格尽天下万物,杨时提出了“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①的办法。可见,杨时的格物致知论既强调向外求索,又要求“反身而诚”,并且认为,只有在向外求索中,又“反身而诚”,才能“举天下之物在我矣”。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杨时讲“反身而诚”是作为“格物”过程中为了格尽天下万物而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讨论“格物”与“反身而诚”的先后次序关系。
李侗在主张静坐体认天理的同时,又强调要“于日用处着力”,“须就事体用下功夫”。他说:“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处着力,可见端绪,在勉之尔。”②李侗还提出了“融释”说。他说:“为学之初,且常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穷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所及也。”③这里所说的“常存此心”,就是要时时保持持敬之心,排除不符合天理,即排除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干扰,做到“心与理一”。遇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实际上也就是格物穷理。“融释”就是程颐所谓的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然有贯通处。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学者是采取外向探索和内省工夫,渐次积累和豁然贯通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格物致知论。(四)默坐澄心,静中体认未发
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十分注重对《中庸》之中道思想的阐发,从《中庸》中寻找所谓未发之旨。杨时作《中庸义》曰:“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①杨时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亦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②杨时这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之法,在于他认为通过默而识之的内心体验工夫,最终能够超然自得。但这所得既然来源于言意之表,也就无法言说传诵。由此可知,杨时由《中庸》而来的这种涵养心性,体验喜怒哀乐未发的功夫,不是如禅门的“悟无所得”,而是有确定的内容,即“至道”的。道出于书言意象之外,所以忘言忘象才能体道,而非口耳诵数所得识。杨时提出“以身体之,心验之”默识中道的存养工夫,后来成为闽中道南学派的重要课题。
罗从彦对其师杨时“默识中道”的存养功夫,认真予以践履。他曾入罗浮山筑室静坐三年,“以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他作诗云:“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周诚程敬应初会,奥理休从此外寻。”③罗从彦“观心”所追求的“奥理”,他认为可以从周敦颐的“诚”和二程的“敬”中去寻求。心中一尘不染,闲中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便可进入一种“彩笔书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无痕。人心但得如空水,与物自然无怨恩”④的境界。如何体验“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罗从彦明确提出了“静中体验未发”之说。故后人多说罗从彦为学是“以主静为宗”①,理由有:一是罗从彦曾筑室于罗浮山,静坐穷理,即通过内心的体悟把握天理;二是罗从彦主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这种“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阐发,构成了早期闽中理学学者追求“静养”的境界的特征。
李侗对“静中体认未发”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②李侗的学生亦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旨诀。”③未发之“中”作何“气象”,实际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但毕竟包含“进学”和“养心”的双重内容,二者之间是一体互发的关系。李侗认为,进学与养心的目的都在于“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如此的“气象”,既是指圣贤洒落超脱的境界,又同时意味着哲学的本体,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中”。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学者体验未发之中的心性锻炼,是一种追寻哲学本体和提升道德境界的综合进程。
(五)重视对“四书”的诠释
宋代以后,中国正宗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书”之中。《宋史·列传·道学一》说: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从这段文字可见,“四书”并行,最初是出于二程的提倡。闽中学者游酢师承二程,对“四书”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为学重在发挥经书中的义理,“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①。游酢所撰写的《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都是对“四书”诠释的重要著作。在他的这些著作中,“足资深发者固已多矣”②。清人方宗诚说:“自二程夫子起,始独得于章句笺疏之外,而见圣贤立言之本心。先生(指游酢)及同门诸子,互有以发明之,于是经之大体大用始著。”③杨时亦非常重视“四书”。他认为:“《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④“《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⑤“《孟子》以睿知刚明之材,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为知言也。今其书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⑥“《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⑦杨时对门人说:“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⑧罗从彦于政和元年(1111),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后写成《语孟师说》、《中庸说》和《议论要语》等名著,对“四书”亦进行了阐发。李侗拜师罗从彦后,“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①。李侗在《延平答问》中,诸多条是回答学生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中的疑问的。闽中武夷学派的胡宪对“四书”中的《论语》有极深的研究。他广泛收集数十家《论语》解说,后来以二程说为本,抄摘各家精要,并附以己意而写成《论语会义》。该书为后来朱熹以《论语》为核心的“四书”学奠定了根基。宋代以后,儒家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这个转变始自二程,而由朱熹所完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早期闽中理学家们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料。据美国著名朱子学家陈荣捷教授统计,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用了32位学者的731条语录,其中引述闽中学者杨时之论73条,李侗之论13条。此外,还有引用游酢等闽中学者的语录。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家推崇“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诠释“四书”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上述可见,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理学文化现象,它是整个理学思潮的一部分。它同中原理学的发展,闽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理学渊源关系而言,它是中原理学南移后的一个发展。就理论特征而言,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应该说,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为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来源和有益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附注
①《正蒙·参两》。
②《正蒙·大易》。
③《伊川先生语》,《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
④《邵子全书·无名公传》。
⑤《余杭所闻》,《龟山集》卷一三。
⑥《南都所闻》,《龟山集》卷一三。
⑦《南都所闻》,《龟山集》卷一三。
①《延平答问》。
②《寄伊川先生书》,《龟山集》卷一六。
③《答杨时论西铭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九。
①《龟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五。
②《京师所闻》,《龟山集》卷一一。
③《遵尧录二》,《豫章文集》卷二。
④《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答问跋》,《延平答问·附录》。
⑤《延平答问》。
①《延平答问》。
②《答李杭》,《龟山集》卷一八。
③《答李杭》,《龟山集》卷一八。
④《答胡康侯其一》,《龟山集》卷二〇。
⑤《题萧欲仁大学篇后》,《龟山集》卷二六。
①《龟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五。
②《延平答问》。
③《豫章学案》,《宋元学案》卷三九。
①《龟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五。
②《龟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五。
③《观书有感》,《豫章文集》卷一三。
④《勉李愿中五首》,《豫章文集》卷一三。
①罗天广:《重刻豫章先生集序》,《罗豫章集》卷首。
②《延平答问》。
③《答何叔京》书二,《朱文公文集》卷四〇。
①《游定夫先生集·序》。
②《诸儒论述》,《游定夫先生集》卷首。
③《诸儒论述》,《游定夫先生集》卷首。
④《题萧欲仁大学篇后》,《龟山集》卷二六。
⑤《论语义序》,《龟山集》卷二五。
⑥《孟子义序》,《龟山集》卷二五。
⑦《中庸义序》,《龟山集》二五。
⑧《题中庸后示陈知默》,《龟山集》卷二六。
㊽《李侗传》,《宋史》卷四。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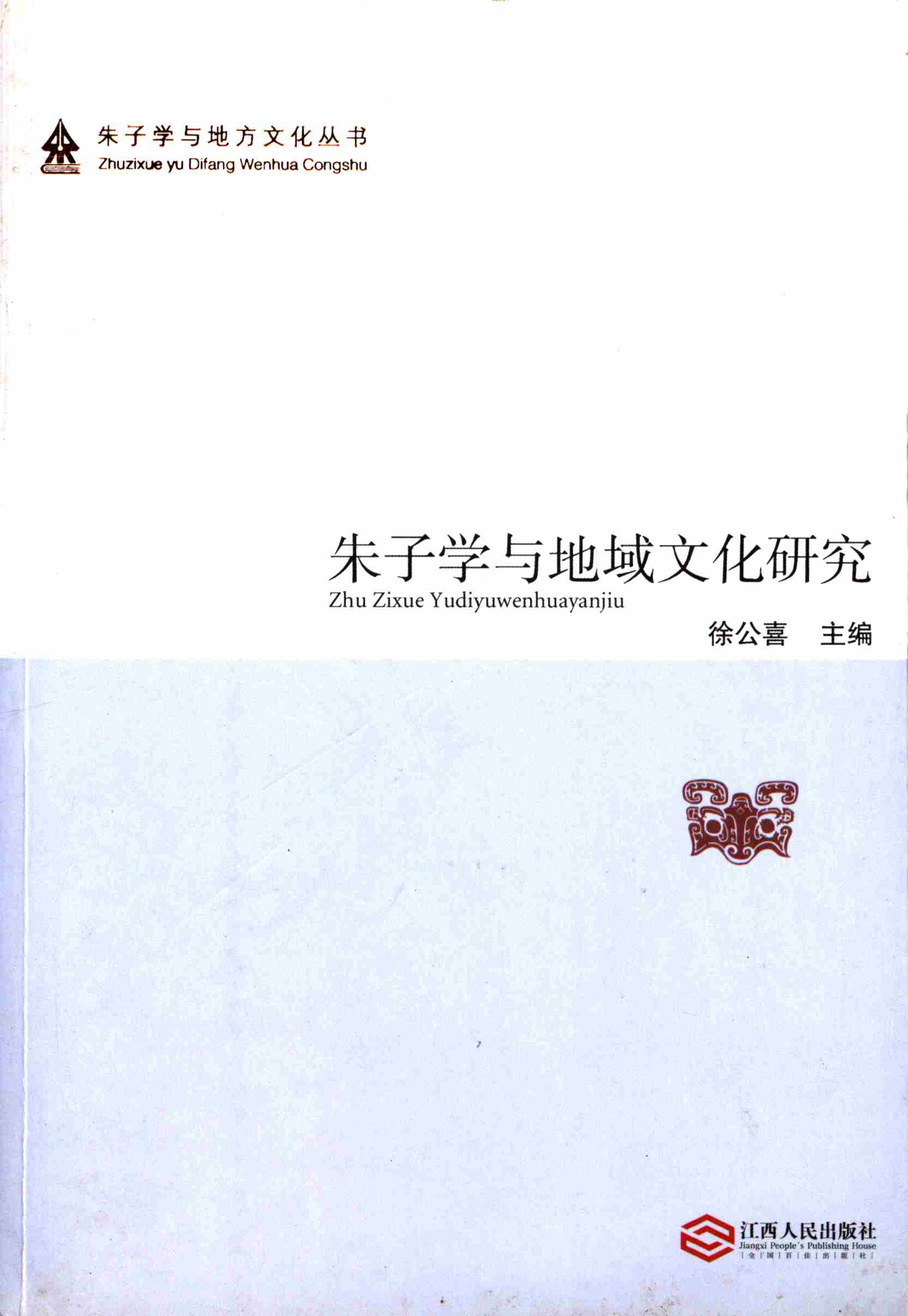
《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2013年“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研讨会的成果汇编,收录《新安理学特质》、《试论饶鲁的学术思想与心学化的双峰学派》、《朱子理学与关帝信仰》、《韩国九曲园林雏形阶段》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张品端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