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禅皆误,杜鹃声里初归儒
| 内容出处: | 《大儒世泽——朱子传》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703 |
| 颗粒名称: | 道禅皆误,杜鹃声里初归儒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5 |
| 页码: | 58-62 |
| 摘要: | 这段文章描述了朱子与李侗的对话和朱子的思考。朱子试图向李侗展示自己的理解和领悟,但李侗似乎并不以为然。朱子开始怀疑李侗是否真正理解圣人之道。他继续探讨禅理,并受到高士轩和武夷山仰上人的启发。朱子并没有逃避,而是选择追寻圣人大道的另一条道路。 |
| 关键词: | 朱子 实际问题 地方防务 |
内容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五月,朱子赴任同安经过延平的时候,曾去拜见李侗——那位“冰壶秋月,莹彻无瑕”的先生。彼时榴花怒放,红艳似火。朱子体悟大道的方法,依然不离道谦的教诲,勇猛直前地参话头禅,悟“狗子佛性”。
道谦所说的是参禅之道,而不是体悟圣人之法。看着平静安坐的李侗,朱子急于要把李侗超凡入圣的方法给套出来。朱子语锋尖锐,言语犀利,似提刀而入,一再叩询,多方质问,但朱子刀锋所向,都被李侗淡淡的话语轻轻撇开,化为无形,朱子的振振有词也全然没有得到李侗的颔首。李侗也没说为什么不行,只说不是!朱子再问为何不是时,李侗只说去看圣人言语。对于这个少言寡语的李侗,朱子起了疑心——可能李侗自己都没有理会到圣人之道。于是,朱子又大谈禅理。李侗听了半天,回应一句:“圣人之道也没有什么玄妙,只是不能像你这样去悬空理会,对面前之事却视而不见。你为何不转向关注日用之间实实在在地去做工夫?关注日用,就自然会悟见大道。”
朱子心存疑惑,也不服气。不日,拜别李侗,来到同安。
初到同安,主簿的官廨老屋破败,明显不可居住。朱子转头,却见西北角地势高亢处伫立一座轩阁。公务之暇,朱子就登上轩阁,好地方,真真令人欣喜,好像是前人特意为朱子所建。于是,朱子稍加修葺,题名悬匾——高士轩。
高士轩的高士追求使朱子写诗的灵感勃发,夏秋之间,不到3个月,作诗47首,这是在同安写诗最多的时段了,写的都是高士之诗。也结交了许多修道的山中高士。一位叫一维那的上人,听说朱子的母亲祝夫人得了重听之症,听力越来越差,就配了一服药来。母亲服了一维那的药后,耳疾竟然好了。上人说:“贫道想讨要主簿的一首诗。”朱子一点也不吝啬,立刻写《与一维那》相赠。
朱子学禅修道,实在是想在追寻圣人大道上另辟蹊径。追随道谦,于道未得;问道李侗,不知所云;如今,又杂以武夷山仰上人传授的步虚焚修的方法来体悟……
遁入禅、道中的朱子并不是逃离,他的本质是儒,而且这位儒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到同安的第一年七月,长子朱塾出生;第二年七月,次子朱埜出生;年长的母亲得了重听。妻子在家服侍老人,照顾幼小。虽然家事杂多,但尚有妻子的苦苦支撑。朱子任同安主簿之职又兼管县学之事,一边是民政,一边是学政,税收、簿记、经界、吏治、民生、教育、策试、礼俗等经济要务与教化兴学的问题一并落到了这位20多岁后生的肩上。
道谦禅师的话头禅、高士轩中的步虚词在现实面前越来越变得空泛而缺乏实际意义,朱子的修炼受到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一地之官的责任冲击。谈空说性的禅师和道士,“待其出寺下山,见了天地之大,民物之繁,自会讨头不着”。到了同安的广阔天地,对着同安的士民工商,朱子越发觉得参禅问道的一无所用。难道真是如愿中先生李侗所说的“关注日用,就自然会悟见大道”吗?朱子开始反思李侗所说的“关注日用之间”的话了,此时,同安的“日用之间”也真出大事了。盗贼来犯同安,民政、学政之外,朱子介入了地方军务防务。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夏,盗贼逼近同安,县令及县丞以下的官员分区负责地方防务,监盐税曹沆和主簿朱子守卫同安的西北角。以往同安遭受盗贼攻击的时候,西北角总是首当其冲。曹沆和朱子的防戍任
务艰巨。一天,朱子和曹沆登城四处巡看,慷慨激扬,指点江山,互相谈论。他们临风站立,西北角防范的弱点暴露在他们的视界里。“日用之间”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楔入朱子的脑中。朱子迎着西北角的夏风大声地对曹沆说:“西北角守不住,我等就死无葬身之地,就算我辈力量卑微,也须尽力而为。”朱子与曹沆到他们所辖的部属处劝勉鼓励,激励士人与属吏的士气。曹沆又说:“兵法有云,‘曲道险厄,则剑楯利;仰高临下,则弓矢便’,我们守卫的西北角正是仰高临下的所在,而射手是环城固守的利器,优秀的射击技能,非一日之功可成,一定要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多加练习,一旦险情出现,即可派上用场。”朱子与曹沆找到县城一处平坦的角落,开辟出射圃。射手每天在射圃习射。不久,盗贼散去,险情解除。但选拔射手到射圃练习射击成了一项常规训练,不再断辍。
警报一解除,朱子就重新投入到经史阁的建设,朱子从福建经略安抚司弄来的书要有去处。经史阁建在县学的大成殿后。明伦堂的左侧还建了一幢教思堂。教思堂建好后,朱子写了一首诗,《教思堂作示诸同志》:
吏局了无事,横舍终日闲。
庭树秋风至,凉气满窗间。
高阁富文史,诸生时往还。
纵谈忽忘倦,时观非云悭。
咏归同与点,坐忘庶希颜。
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
朱子说“吏局了无事”那全是忙里偷闲的话,而“何必栖空山”则是有了某种隐约的回归。作为一地之官,毕竟要从“空山”回到“红尘”。秋天到了,朱子将之前禅道气味浓烈的诗作一并收起,编成《牧斋净稿》,把“栖空山”念想抛下,开始“关注日用”,转回儒学,从道与禅的空寂转回到眼前的点点滴滴中。官守虽卑,年纪虽轻,但他是丈夫、是儿子、是父亲、是管文书的主簿、是管县学的教谕、是管城防的
戍官……朱子参禅问道,修为再高又有何用?面对经界法、经总制钱、盗贼进犯、学风日下的同安诸生……参禅问道真能普渡苍生?禅、道是出世法,大济苍生需儒的入世法。先生刘子翚以三字诀——“不远复”传授,是不是自己走参禅学道的路走太远了,是不是真该回头了?冰壶秋月的李侗,对咄咄逼人的朱子只说“不是”,朱子当时怀疑李侗水平差、不懂禅,如今,想到李侗所说“且将圣人书来读”时,朱子有了幡然悔悟之感。
一边思索大道,一边为王事而四处奔波。朱子常常奉檄往其他州县公干。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春末,朱子奉檄前往德化。三月春寒锁不住万物葱茏,为王事而四处奔走的朱子从同安往北,过永春,经龟龙桥、通德桥,黄昏莅临,朱子来到了剧头铺,前方是虎豹关,过虎豹关就到德化了。
剧头铺的晚餐后,朱子望着天上半轮清亮的月亮,微寒的风拂面而来。李侗让朱子看圣人书,让朱子关注日用。与日用相关最紧密的圣人之书就是《论语》《孟子》了,那是圣人日常言谈论辩的话语。此次奉檄一路向北,行程孤独,行走中,朱子的思路时时落到《论语·子张》中的“子夏之门人章”: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
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
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
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
这是孔子两个学生——子游和子夏对门人求道方法的争论。
子游讥笑子夏本末倒置,说他教育门人只求细枝末节,对于道的根本却没有传授,执着于小学的洒扫应对、趋走进退了。
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观点,他认为君子之道的核心是“先传后倦”。
什么是“先传后倦”,朱子翻看了二程弟子的解读,但他们解读来解读去,反而把朱子给丢入云里雾里,越来越疑惑了。
愿中先生说读圣人之书关键在领悟,道理要在白天的各项事务中理会,夜里要去静处坐着慢慢思量,细心领悟、着力思量才会有所收获。朱子将道谦所说的勇猛精进移入儒家的求圣之道,将李侗说的静坐思量落到剧头铺的夜色中。剧头铺的夜渐深,五更寒凉,朱子没有感觉到寒意,只一心一意咬定“先传后倦”四字认真思考。
一连几个晚上的体悟,朱子终于明白,子夏的“先传后倦”是要让学者循序渐进。事情有本末精粗,道理却只是一个。学者不能以追求根本大道为托词而放弃细节与基础。如果不论学人的深浅,不论事务的生熟,就一概教之以高远的大道理,那与欺骗就没两样了。事的大小有别,理的大小却都是理啊!
伴随着剧头铺声声的杜鹃啼叫,清晨的寒气依然逼人,朱子忘了疲倦,他下床披好衣裳写道:
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
道理不可以悬空去体悟,要脚踏实地,关注身边,关注眼前,循序渐进,做实在工夫,体悟圣人之理。
夜间,荒山穷岭,寒裘不耐春寒,子规声哀啼;晨起,却又春光大放,韶光如许,朱子在剧头铺题下《之德化宿剧头铺,夜闻杜宇》:
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
如何独宿荒山夜,更拥寒裘听子规。
后来,朱子和门人提及此事时说:“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
一夜杜鹃,唤出圣人“先传后倦”的低语,这不正与愿中先生李侗“关注日用”的说法相吻合?耽于道禅的朱子猛醒过来,对儒家的圣人有了重新的认识。
道谦所说的是参禅之道,而不是体悟圣人之法。看着平静安坐的李侗,朱子急于要把李侗超凡入圣的方法给套出来。朱子语锋尖锐,言语犀利,似提刀而入,一再叩询,多方质问,但朱子刀锋所向,都被李侗淡淡的话语轻轻撇开,化为无形,朱子的振振有词也全然没有得到李侗的颔首。李侗也没说为什么不行,只说不是!朱子再问为何不是时,李侗只说去看圣人言语。对于这个少言寡语的李侗,朱子起了疑心——可能李侗自己都没有理会到圣人之道。于是,朱子又大谈禅理。李侗听了半天,回应一句:“圣人之道也没有什么玄妙,只是不能像你这样去悬空理会,对面前之事却视而不见。你为何不转向关注日用之间实实在在地去做工夫?关注日用,就自然会悟见大道。”
朱子心存疑惑,也不服气。不日,拜别李侗,来到同安。
初到同安,主簿的官廨老屋破败,明显不可居住。朱子转头,却见西北角地势高亢处伫立一座轩阁。公务之暇,朱子就登上轩阁,好地方,真真令人欣喜,好像是前人特意为朱子所建。于是,朱子稍加修葺,题名悬匾——高士轩。
高士轩的高士追求使朱子写诗的灵感勃发,夏秋之间,不到3个月,作诗47首,这是在同安写诗最多的时段了,写的都是高士之诗。也结交了许多修道的山中高士。一位叫一维那的上人,听说朱子的母亲祝夫人得了重听之症,听力越来越差,就配了一服药来。母亲服了一维那的药后,耳疾竟然好了。上人说:“贫道想讨要主簿的一首诗。”朱子一点也不吝啬,立刻写《与一维那》相赠。
朱子学禅修道,实在是想在追寻圣人大道上另辟蹊径。追随道谦,于道未得;问道李侗,不知所云;如今,又杂以武夷山仰上人传授的步虚焚修的方法来体悟……
遁入禅、道中的朱子并不是逃离,他的本质是儒,而且这位儒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实际问题。到同安的第一年七月,长子朱塾出生;第二年七月,次子朱埜出生;年长的母亲得了重听。妻子在家服侍老人,照顾幼小。虽然家事杂多,但尚有妻子的苦苦支撑。朱子任同安主簿之职又兼管县学之事,一边是民政,一边是学政,税收、簿记、经界、吏治、民生、教育、策试、礼俗等经济要务与教化兴学的问题一并落到了这位20多岁后生的肩上。
道谦禅师的话头禅、高士轩中的步虚词在现实面前越来越变得空泛而缺乏实际意义,朱子的修炼受到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为一地之官的责任冲击。谈空说性的禅师和道士,“待其出寺下山,见了天地之大,民物之繁,自会讨头不着”。到了同安的广阔天地,对着同安的士民工商,朱子越发觉得参禅问道的一无所用。难道真是如愿中先生李侗所说的“关注日用,就自然会悟见大道”吗?朱子开始反思李侗所说的“关注日用之间”的话了,此时,同安的“日用之间”也真出大事了。盗贼来犯同安,民政、学政之外,朱子介入了地方军务防务。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夏,盗贼逼近同安,县令及县丞以下的官员分区负责地方防务,监盐税曹沆和主簿朱子守卫同安的西北角。以往同安遭受盗贼攻击的时候,西北角总是首当其冲。曹沆和朱子的防戍任
务艰巨。一天,朱子和曹沆登城四处巡看,慷慨激扬,指点江山,互相谈论。他们临风站立,西北角防范的弱点暴露在他们的视界里。“日用之间”的问题实实在在地楔入朱子的脑中。朱子迎着西北角的夏风大声地对曹沆说:“西北角守不住,我等就死无葬身之地,就算我辈力量卑微,也须尽力而为。”朱子与曹沆到他们所辖的部属处劝勉鼓励,激励士人与属吏的士气。曹沆又说:“兵法有云,‘曲道险厄,则剑楯利;仰高临下,则弓矢便’,我们守卫的西北角正是仰高临下的所在,而射手是环城固守的利器,优秀的射击技能,非一日之功可成,一定要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多加练习,一旦险情出现,即可派上用场。”朱子与曹沆找到县城一处平坦的角落,开辟出射圃。射手每天在射圃习射。不久,盗贼散去,险情解除。但选拔射手到射圃练习射击成了一项常规训练,不再断辍。
警报一解除,朱子就重新投入到经史阁的建设,朱子从福建经略安抚司弄来的书要有去处。经史阁建在县学的大成殿后。明伦堂的左侧还建了一幢教思堂。教思堂建好后,朱子写了一首诗,《教思堂作示诸同志》:
吏局了无事,横舍终日闲。
庭树秋风至,凉气满窗间。
高阁富文史,诸生时往还。
纵谈忽忘倦,时观非云悭。
咏归同与点,坐忘庶希颜。
尘累日以销,何必栖空山?
朱子说“吏局了无事”那全是忙里偷闲的话,而“何必栖空山”则是有了某种隐约的回归。作为一地之官,毕竟要从“空山”回到“红尘”。秋天到了,朱子将之前禅道气味浓烈的诗作一并收起,编成《牧斋净稿》,把“栖空山”念想抛下,开始“关注日用”,转回儒学,从道与禅的空寂转回到眼前的点点滴滴中。官守虽卑,年纪虽轻,但他是丈夫、是儿子、是父亲、是管文书的主簿、是管县学的教谕、是管城防的
戍官……朱子参禅问道,修为再高又有何用?面对经界法、经总制钱、盗贼进犯、学风日下的同安诸生……参禅问道真能普渡苍生?禅、道是出世法,大济苍生需儒的入世法。先生刘子翚以三字诀——“不远复”传授,是不是自己走参禅学道的路走太远了,是不是真该回头了?冰壶秋月的李侗,对咄咄逼人的朱子只说“不是”,朱子当时怀疑李侗水平差、不懂禅,如今,想到李侗所说“且将圣人书来读”时,朱子有了幡然悔悟之感。
一边思索大道,一边为王事而四处奔波。朱子常常奉檄往其他州县公干。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春末,朱子奉檄前往德化。三月春寒锁不住万物葱茏,为王事而四处奔走的朱子从同安往北,过永春,经龟龙桥、通德桥,黄昏莅临,朱子来到了剧头铺,前方是虎豹关,过虎豹关就到德化了。
剧头铺的晚餐后,朱子望着天上半轮清亮的月亮,微寒的风拂面而来。李侗让朱子看圣人书,让朱子关注日用。与日用相关最紧密的圣人之书就是《论语》《孟子》了,那是圣人日常言谈论辩的话语。此次奉檄一路向北,行程孤独,行走中,朱子的思路时时落到《论语·子张》中的“子夏之门人章”:
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
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
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
也。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
这是孔子两个学生——子游和子夏对门人求道方法的争论。
子游讥笑子夏本末倒置,说他教育门人只求细枝末节,对于道的根本却没有传授,执着于小学的洒扫应对、趋走进退了。
子夏不同意子游的观点,他认为君子之道的核心是“先传后倦”。
什么是“先传后倦”,朱子翻看了二程弟子的解读,但他们解读来解读去,反而把朱子给丢入云里雾里,越来越疑惑了。
愿中先生说读圣人之书关键在领悟,道理要在白天的各项事务中理会,夜里要去静处坐着慢慢思量,细心领悟、着力思量才会有所收获。朱子将道谦所说的勇猛精进移入儒家的求圣之道,将李侗说的静坐思量落到剧头铺的夜色中。剧头铺的夜渐深,五更寒凉,朱子没有感觉到寒意,只一心一意咬定“先传后倦”四字认真思考。
一连几个晚上的体悟,朱子终于明白,子夏的“先传后倦”是要让学者循序渐进。事情有本末精粗,道理却只是一个。学者不能以追求根本大道为托词而放弃细节与基础。如果不论学人的深浅,不论事务的生熟,就一概教之以高远的大道理,那与欺骗就没两样了。事的大小有别,理的大小却都是理啊!
伴随着剧头铺声声的杜鹃啼叫,清晨的寒气依然逼人,朱子忘了疲倦,他下床披好衣裳写道:
理无小大,无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从头做去,不可拣择。
道理不可以悬空去体悟,要脚踏实地,关注身边,关注眼前,循序渐进,做实在工夫,体悟圣人之理。
夜间,荒山穷岭,寒裘不耐春寒,子规声哀啼;晨起,却又春光大放,韶光如许,朱子在剧头铺题下《之德化宿剧头铺,夜闻杜宇》:
王事贤劳只自嗤,一官今是五年期。
如何独宿荒山夜,更拥寒裘听子规。
后来,朱子和门人提及此事时说:“某旧年思量义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传后倦’一章,凡三四夜,穷究到明,彻夜闻杜鹃声。”
一夜杜鹃,唤出圣人“先传后倦”的低语,这不正与愿中先生李侗“关注日用”的说法相吻合?耽于道禅的朱子猛醒过来,对儒家的圣人有了重新的认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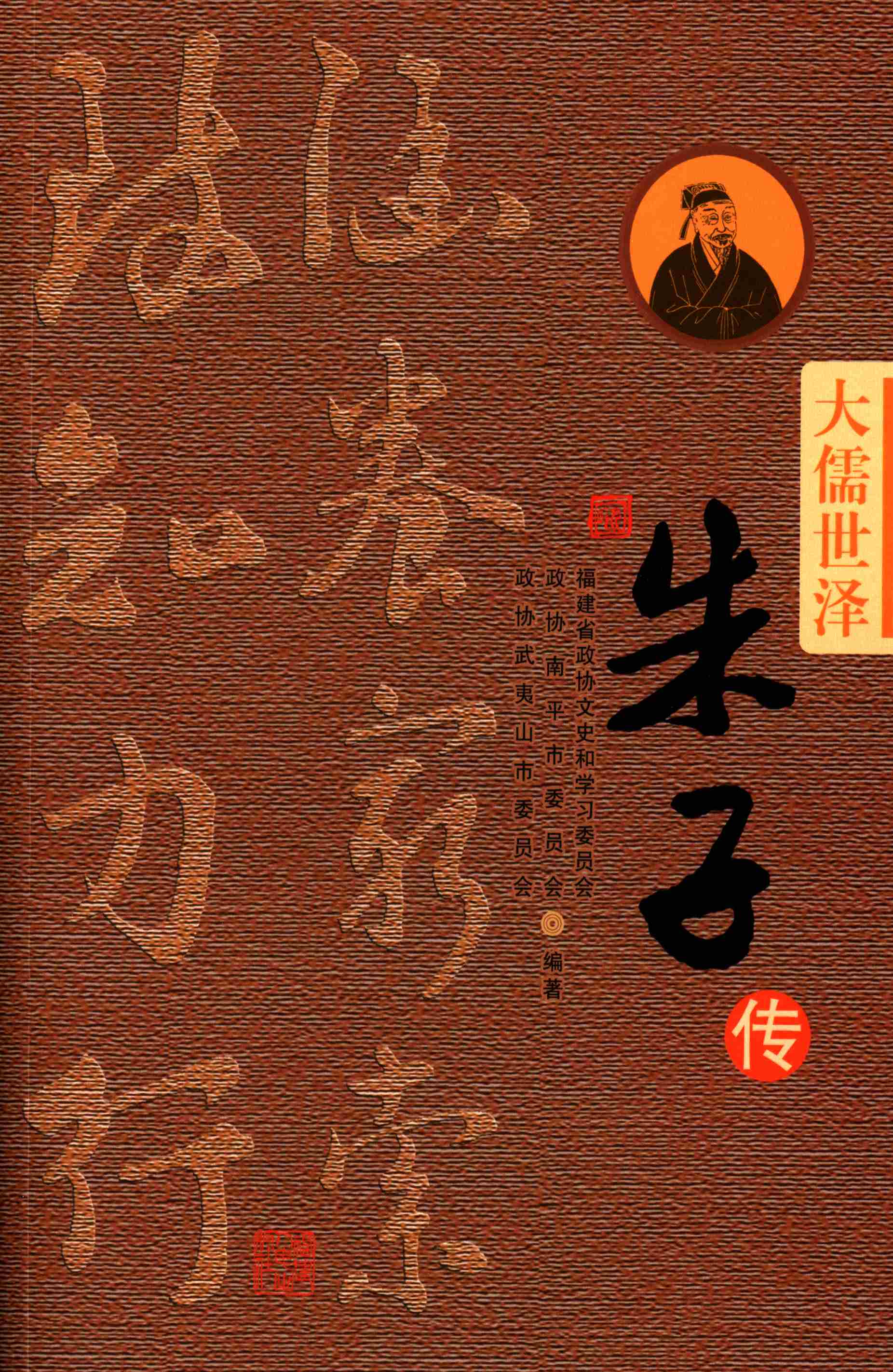
《大儒世泽——朱子传》
出版者:福建人民出版社
本书介绍了朱熹的生平、思想和贡献,并强调了朱子文化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性。本书将朱子理学作了通俗化的阐述、时代性的评说,是朱子文化宣传普及上的进一步。同时,本书也表达了要在文化自信中继续前进的信念,认为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常常是以文化的复兴和精神的崛起为先导。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