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5》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520 |
| 颗粒名称: | 2015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6 |
| 页码: | 128-13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2015年日本朱子学研究综述包括向“方法论”的挑战、两个思想史讲座、“训读”的思想史情况。 |
| 关键词: | 日本 朱子学研究 综述 |
内容
一、向“方法论”的挑战
在当今日本学术界,日本朱子学尽管在“东洋哲学”“政治思想史”“伦理思想史”等各专门领域内开展研究,但在质量与数量上都构成该研究之核心的是名为“日本思想史”的学科。日本思想史学会现拥有730名个人会员与来自31个机构的团体会员[1],每年出版学会期刊《日本思想史学》。业已发行了47期的《日本思想史学》是一部刊登日本国内特别是有关日本近世儒教研究方面一主要原因之一是不存在如古代、中世思想中的与佛教研究、 国文学研究相竞争之状况——具有最高水准的论文的杂志,这一点是众口ー词的。
该日本思想史学会,于今年(2015)围绕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展开了针锋对麦芒的争论。首先是2015年9月12日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东京都文京区)举办了题为“思想史之对话”的研究会。在会上,学会现任会长前田勉(爱知教育大学教授)在对率领战后的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ーー实质上其大半为儒教研究——的丸山真男、安丸良夫、子安宣邦等人各自描绘的近世思想史 的“全体像”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今后思想史应如何描绘“全体像”提出了建议,笔者(板东)也做了若干应答。接着,在10月17日、18日接连两日于早稻田大学户山校区(东京都新宿区)举办的日本思想史学会大会上,首日下午举办了以“思想史学的设问方式ー一基于两个日本思想史讲座”的整体研讨会。这ー研讨会不限于近世思想史、儒教研究,与前田勉同样毕业于东北大学的日本儒教研究核心人物之一田尻祐一郎(东洋大学教授)做了题为“回顾战 后近世思想史研究”的报告,泽井启ー(惠泉女学园大学名誉教授)与高山大毅(驹泽大学讲师)各自对此加以了细致的点评。[2]
为何当今日本的研究者们要对其研究对象,即以引入朱子学而开其端绪的日本儒教提出诸如“全体像”“设问方式”“方法论”等大问题呢?这大概是源于东亚其他各地域的儒教研究中少见的日本特有的情况。说到底,是因为与其他地域不同,在日本不存在将儒教——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与之交锋——视为“我们的传统”的这一想法。当然,在日本也存在跨越19世纪的近代化,融入基层民俗活动与行为方式中,宛如潜流的思想传统。可是大半都被视为“佛教”与“神道”,而绝不是“儒教”。因此,日本研究者不得不长期意识“为何要探究儒教?”这一问题来开展研究。如果研究者们对这个单纯的设问提不出简明的回答,在日本人文学面临崩溃的状况中,近世创造出的无数的朱子学、新儒学的文本群就只能一直藏在各地书库中,不见天日。
在此意义上,在上述两次会议中,前田勉与田尻祐一郎两人都重点选择丸山真男与子安宣邦的近世思想史研究为题是耐人寻味的。通过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发现了近世的朱子学向徂徕学、国学的展开过程中的日本内发性近代化之萌芽(及其限界)的丸山真男之论述于战后日本与日本思想史学重新起步之际,吸引了众人瞩目。直至当今日本思想史学“偏重于”近世思想是深受丸山真男影响的。另外,1990年代将法国、美国的最新批评理论用于近世思想研究的子安宣邦的研究,一方面运用高度抽象的分析概念,另一方面也带有彻底批判近、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这一极其明了且兼具现代性的意义。[3]尽管两者都容易受到来自实证性文献研究视点的批评,但通过添加重要的辅助线,提出“故事”,在不具有将儒教视为“传统”之共识的日本,明确了当地揭示出将日本儒教作为主题来探讨的当下意义,激起众多日本人关心这一贡献是巨大的。今日重提他们的工作,恰是由于将日本儒教再次变为对众多日本人具有切实意义的对象来把握这一点已是燃眉之急的课题。
尽管对现状拥有上述共同的认识,但前田勉与田尻祐一郎的建议是对照性的。力图构筑超越丸山真男的近世儒教研究之“大理论”的前田勉不断提出基于其膨大知识素养的崭新的“全体像”,如认为近世日本的基底思想不是朱子学,而是作为武家政权之基本教养的“兵学”,朱子学只不过是作为外来思想占据着局部性地位而已[4],以及提出近世后期的儒教经典“会读”之场所与近代以后的自由的言论空间直接相关的“会读”论[5]等,直至今日强有力地带动着日本儒教研究。与他相对,以扎实的山崎暗斋与徂徕学派研究而闻名的田尻祐一郎[6]则指出:“与伟大的思想家不断踏实对话这一态度(方法),在当今的思想史研究中是否淡化了”(据上述大会发表资料)。田尻祐一郎所提倡的该“态度”或“方法”是认真研读《论语》或《书经》,通过与圣贤开展内在性对话来获得真理,甚至尝试磨炼人格修养,这倒是儒教中传统的“态度”与“方法”。当今的日本人文学越来越趋于不容忍那种做法,但儒教是以“读书”“学文”为其基础行为的思想这一点有必要不断被想起。
二、两个思想史讲座
田尻祐一郎、泽井启ー、高山大毅等人参加的学会研讨会之副题中写道:“基于两个日本思想史讲座”,正如那样,2015年的特色在于,这是日本思想史学相关书籍的主要出版社ーー岩波书店与ぺりかん社两公司分别出版的新的日本思想史讲座完成之年。前ー节中提及的围绕思想史之“方法论”的活跃论争同时也具有总体概括两个讲座的意义。
岩波书店邀请莉部直、黑住真、佐藤弘夫、末木文美士担任编集委员而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の思想(日本的思想)》共八卷,按主题分卷。各卷探讨的主题分别是“‘日本’与日本思想”“场与器”“内与外”“自然与人为”“身与心”“秩序与规范”“礼仪与创造”“走向神圣”(按卷数顺序),令人想起当下颇受关注的问题群之分布。[7]而由ぺりかん社在上述学者之外并邀请田尻祐一郎共五人担任编辑委员而出版的《日本思想史讲座》共五卷,在“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各时代分卷之后,第五卷还探讨了“方法”。这ー讲座按时代顺序编排,因此更加便于使用,特别是“近世”卷(2012年刊行)是把握日本国内开展的日本儒教研究目前状况之梗概的最佳著作。
不同于2014年编辑完成的岩波讲座,ぺりかん社版讲座的最终卷之完成遇到了困难,最终于本年12月出版,两个讲座系列オ大功告成。在此将ぺりかん社版讲座第五卷(《日本思想史讲座5——方法》,ペり力、んネ士,2015年12月)作为日本思想史研究的今年代表性著作,仅就与日本朱子学相关的内容做ー简洁的介绍。
内容大体上分为四部分。首先,在“研究的课题与方法”中,黑住真(东京大学教授)与片冈龙(东北大学教授)提出了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与课题”。其次,在“方法的诸方面”中,针对“拟古”“论争”“训读”“书物”“性与性别”“环境”等具体的研究视角,由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分别做了概括。并且在“世界中的日本思想史——来自海外的研究”中,介绍了中国(包括台湾)、韩国、欧美等的研究。其中,卞崇道与吴光辉、蓝弘岳介绍的中国研究状况都以日本儒教为核心主题。最后,在“走进日本思想史ーー概括介绍”中,对“神道”“佛教”“儒教”“基督教”等各种思想分别做了简明的“概括介绍”。“儒教”ー节的执笔者是前年的本系列综述中也曾介绍的土田健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并且在卷末附有“日本思想史学相关文献一览表”与最新的“日本思想史年表”,相当有助于学习者。特别是在文献一览表的“近世、ー般”栏中,恰当地刊登了至今仍受重视的日本儒教研究文献,非常便于海外研究。
三、“训读”的思想史
当今日本儒教研究中广为议论,与日本朱子学也关系颇深的一个主题是ペりかん社版讲座中也提及的“训读”。该主题的国内领军人物正是在讲座相关处执笔的中村春作(广岛大学教授)。中村春作关于“训读”的论述,此外还有岩波书店版讲座第二卷所收的《训读と翻译ーー原典との间をつなぐ(训读与翻 译ーー联结与原典之间的距离)》,另外在总结了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特定地域研究“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形成”(2005〜2009,代表:小岛毅)中由他主持的“日中儒学班”之研究成果的内容浩瀚的《“训读”论ーー东アジア汉文世界と日本语(“训读”论——东亚汉文世界与日语)》(勉诚出版,2008 )、《续“训读”论ーー东アジア汉文世界と日本语の形成(续“训读”论ーー东亚汉文世界与日语之形成》(勉诚出版,2010)之中,与各位专家所著专论ー起,刊登了他思路清晰的概论。下文将根据其中被视为阐述得最精当的收入岩波讲座的《训读与翻译》来介绍该研究主题所及范围与有趣之处。[8]
据文献记载,自6世纪儒教经典传至日本以来,日本人长期地不是将《书经》《论语》等经典类书籍作为中文,按中文发音来读,而是在原文上加入独特的符号,将它“翻译”成日语来读。其中当然需要对汉语与日语语序不同的词语进行调整其顺序,增补中文中不存在的(在日语话者看来需要的)助词,用与之相当的日语词汇来对汉语单词进行更换解读等的工作。这就是“训读”。虽经种种周折,该技法至今仍保留在中等、高等的语文教育中,正因如此,当现代的日本人见到古典汉语文字列时,脑中不会浮现出中文语音之连续,浮现的是被“训读”的特殊的日语文言文。“训读”是因日本处于汉文文化圈周边这ー位置而形成的巧妙的翻译技法。
然而,这ー持续了千年多的“训读”传统曾遇到一大转折。那正是因导入朱子学而发生的。时值15世纪,当时,因贵族社会之颓废,“训读”技法为世袭的博士之家所垄断。在其中“秘传的、匠人气的汉文读书法”(第36页)成为主流,充斥着极其封闭的气息。可是在其中出现了号称“儒学不依晦庵无以为学”(《桂庵和尚家法训点》),尊信朱子学的禅僧桂庵玄树(1427〜1508),开创出了更为一般的公开的训读技法。从桂庵玄树继承到南浦文之(1555〜1620),并通过近世的林罗山、山崎暗斋、佐藤一斋等醇儒而一般化的该新训读法与博士家的“古法”相对,被称为“近世训点”。17世纪以后日本的经典类书籍之大半是以属于该近世训点的林罗山的“道春点”来训 读的。
该训读之转换“不单是技法上的转换”(同上),也是“与接受朱子学相呼应的ー种思想性转换”(同上)。中村春作得出的结论是,桂庵点,乃至近世训点一般的特征在于仔细地读“而”“矣”等“助字”,“桂庵的这一’置字‘必须一字一字训读,将原文的每一字都改为日文的姿态是与对经书上的每一字都逻辑性地、抽象地进行概念规定,做完全解释的朱熹的注释方法相呼应的”(第37页)。一方面以“理一分殊”为理论前提,一方面作为对格物致知的实践,而细致地注释经书的朱熹的姿态在日本的对应物正是向所有人公开的简明平易的近世训点。
其后,正是否定朱子学“理”之思想的荻生徂彿提倡废除训读,并且,近世末期的读书人习以为常的训读文体变为文明开化时期书写规范文体的母体,乃至当今日本的书面语仍处于其决定性的影响之下,这些有关“训读”与朱子学的问题群正构成了日本儒教史、日语史、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化史等中最关键的结点,这样说也绝不为过。当今日本人阅读、书写的语言本身正处于朱子学遥远的遗留下的影响之中。对于“训读”的这ー重要性,除了哲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者之外,文学研究者也当然相当关注[9],目前在“训读”研究领域,自然地呈现出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之面貌。令人期待进ー步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
在当今日本学术界,日本朱子学尽管在“东洋哲学”“政治思想史”“伦理思想史”等各专门领域内开展研究,但在质量与数量上都构成该研究之核心的是名为“日本思想史”的学科。日本思想史学会现拥有730名个人会员与来自31个机构的团体会员[1],每年出版学会期刊《日本思想史学》。业已发行了47期的《日本思想史学》是一部刊登日本国内特别是有关日本近世儒教研究方面一主要原因之一是不存在如古代、中世思想中的与佛教研究、 国文学研究相竞争之状况——具有最高水准的论文的杂志,这一点是众口ー词的。
该日本思想史学会,于今年(2015)围绕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展开了针锋对麦芒的争论。首先是2015年9月12日在东京大学本乡校区(东京都文京区)举办了题为“思想史之对话”的研究会。在会上,学会现任会长前田勉(爱知教育大学教授)在对率领战后的日本近世思想史研究ーー实质上其大半为儒教研究——的丸山真男、安丸良夫、子安宣邦等人各自描绘的近世思想史 的“全体像”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对今后思想史应如何描绘“全体像”提出了建议,笔者(板东)也做了若干应答。接着,在10月17日、18日接连两日于早稻田大学户山校区(东京都新宿区)举办的日本思想史学会大会上,首日下午举办了以“思想史学的设问方式ー一基于两个日本思想史讲座”的整体研讨会。这ー研讨会不限于近世思想史、儒教研究,与前田勉同样毕业于东北大学的日本儒教研究核心人物之一田尻祐一郎(东洋大学教授)做了题为“回顾战 后近世思想史研究”的报告,泽井启ー(惠泉女学园大学名誉教授)与高山大毅(驹泽大学讲师)各自对此加以了细致的点评。[2]
为何当今日本的研究者们要对其研究对象,即以引入朱子学而开其端绪的日本儒教提出诸如“全体像”“设问方式”“方法论”等大问题呢?这大概是源于东亚其他各地域的儒教研究中少见的日本特有的情况。说到底,是因为与其他地域不同,在日本不存在将儒教——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与之交锋——视为“我们的传统”的这一想法。当然,在日本也存在跨越19世纪的近代化,融入基层民俗活动与行为方式中,宛如潜流的思想传统。可是大半都被视为“佛教”与“神道”,而绝不是“儒教”。因此,日本研究者不得不长期意识“为何要探究儒教?”这一问题来开展研究。如果研究者们对这个单纯的设问提不出简明的回答,在日本人文学面临崩溃的状况中,近世创造出的无数的朱子学、新儒学的文本群就只能一直藏在各地书库中,不见天日。
在此意义上,在上述两次会议中,前田勉与田尻祐一郎两人都重点选择丸山真男与子安宣邦的近世思想史研究为题是耐人寻味的。通过名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发现了近世的朱子学向徂徕学、国学的展开过程中的日本内发性近代化之萌芽(及其限界)的丸山真男之论述于战后日本与日本思想史学重新起步之际,吸引了众人瞩目。直至当今日本思想史学“偏重于”近世思想是深受丸山真男影响的。另外,1990年代将法国、美国的最新批评理论用于近世思想研究的子安宣邦的研究,一方面运用高度抽象的分析概念,另一方面也带有彻底批判近、现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这一极其明了且兼具现代性的意义。[3]尽管两者都容易受到来自实证性文献研究视点的批评,但通过添加重要的辅助线,提出“故事”,在不具有将儒教视为“传统”之共识的日本,明确了当地揭示出将日本儒教作为主题来探讨的当下意义,激起众多日本人关心这一贡献是巨大的。今日重提他们的工作,恰是由于将日本儒教再次变为对众多日本人具有切实意义的对象来把握这一点已是燃眉之急的课题。
尽管对现状拥有上述共同的认识,但前田勉与田尻祐一郎的建议是对照性的。力图构筑超越丸山真男的近世儒教研究之“大理论”的前田勉不断提出基于其膨大知识素养的崭新的“全体像”,如认为近世日本的基底思想不是朱子学,而是作为武家政权之基本教养的“兵学”,朱子学只不过是作为外来思想占据着局部性地位而已[4],以及提出近世后期的儒教经典“会读”之场所与近代以后的自由的言论空间直接相关的“会读”论[5]等,直至今日强有力地带动着日本儒教研究。与他相对,以扎实的山崎暗斋与徂徕学派研究而闻名的田尻祐一郎[6]则指出:“与伟大的思想家不断踏实对话这一态度(方法),在当今的思想史研究中是否淡化了”(据上述大会发表资料)。田尻祐一郎所提倡的该“态度”或“方法”是认真研读《论语》或《书经》,通过与圣贤开展内在性对话来获得真理,甚至尝试磨炼人格修养,这倒是儒教中传统的“态度”与“方法”。当今的日本人文学越来越趋于不容忍那种做法,但儒教是以“读书”“学文”为其基础行为的思想这一点有必要不断被想起。
二、两个思想史讲座
田尻祐一郎、泽井启ー、高山大毅等人参加的学会研讨会之副题中写道:“基于两个日本思想史讲座”,正如那样,2015年的特色在于,这是日本思想史学相关书籍的主要出版社ーー岩波书店与ぺりかん社两公司分别出版的新的日本思想史讲座完成之年。前ー节中提及的围绕思想史之“方法论”的活跃论争同时也具有总体概括两个讲座的意义。
岩波书店邀请莉部直、黑住真、佐藤弘夫、末木文美士担任编集委员而出版的《岩波讲座日本の思想(日本的思想)》共八卷,按主题分卷。各卷探讨的主题分别是“‘日本’与日本思想”“场与器”“内与外”“自然与人为”“身与心”“秩序与规范”“礼仪与创造”“走向神圣”(按卷数顺序),令人想起当下颇受关注的问题群之分布。[7]而由ぺりかん社在上述学者之外并邀请田尻祐一郎共五人担任编辑委员而出版的《日本思想史讲座》共五卷,在“古代”“中世”“近世”“近代”各时代分卷之后,第五卷还探讨了“方法”。这ー讲座按时代顺序编排,因此更加便于使用,特别是“近世”卷(2012年刊行)是把握日本国内开展的日本儒教研究目前状况之梗概的最佳著作。
不同于2014年编辑完成的岩波讲座,ぺりかん社版讲座的最终卷之完成遇到了困难,最终于本年12月出版,两个讲座系列オ大功告成。在此将ぺりかん社版讲座第五卷(《日本思想史讲座5——方法》,ペり力、んネ士,2015年12月)作为日本思想史研究的今年代表性著作,仅就与日本朱子学相关的内容做ー简洁的介绍。
内容大体上分为四部分。首先,在“研究的课题与方法”中,黑住真(东京大学教授)与片冈龙(东北大学教授)提出了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与课题”。其次,在“方法的诸方面”中,针对“拟古”“论争”“训读”“书物”“性与性别”“环境”等具体的研究视角,由各领域的领军人物分别做了概括。并且在“世界中的日本思想史——来自海外的研究”中,介绍了中国(包括台湾)、韩国、欧美等的研究。其中,卞崇道与吴光辉、蓝弘岳介绍的中国研究状况都以日本儒教为核心主题。最后,在“走进日本思想史ーー概括介绍”中,对“神道”“佛教”“儒教”“基督教”等各种思想分别做了简明的“概括介绍”。“儒教”ー节的执笔者是前年的本系列综述中也曾介绍的土田健次郎(早稻田大学教授)。并且在卷末附有“日本思想史学相关文献一览表”与最新的“日本思想史年表”,相当有助于学习者。特别是在文献一览表的“近世、ー般”栏中,恰当地刊登了至今仍受重视的日本儒教研究文献,非常便于海外研究。
三、“训读”的思想史
当今日本儒教研究中广为议论,与日本朱子学也关系颇深的一个主题是ペりかん社版讲座中也提及的“训读”。该主题的国内领军人物正是在讲座相关处执笔的中村春作(广岛大学教授)。中村春作关于“训读”的论述,此外还有岩波书店版讲座第二卷所收的《训读と翻译ーー原典との间をつなぐ(训读与翻 译ーー联结与原典之间的距离)》,另外在总结了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特定地域研究“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形成”(2005〜2009,代表:小岛毅)中由他主持的“日中儒学班”之研究成果的内容浩瀚的《“训读”论ーー东アジア汉文世界と日本语(“训读”论——东亚汉文世界与日语)》(勉诚出版,2008 )、《续“训读”论ーー东アジア汉文世界と日本语の形成(续“训读”论ーー东亚汉文世界与日语之形成》(勉诚出版,2010)之中,与各位专家所著专论ー起,刊登了他思路清晰的概论。下文将根据其中被视为阐述得最精当的收入岩波讲座的《训读与翻译》来介绍该研究主题所及范围与有趣之处。[8]
据文献记载,自6世纪儒教经典传至日本以来,日本人长期地不是将《书经》《论语》等经典类书籍作为中文,按中文发音来读,而是在原文上加入独特的符号,将它“翻译”成日语来读。其中当然需要对汉语与日语语序不同的词语进行调整其顺序,增补中文中不存在的(在日语话者看来需要的)助词,用与之相当的日语词汇来对汉语单词进行更换解读等的工作。这就是“训读”。虽经种种周折,该技法至今仍保留在中等、高等的语文教育中,正因如此,当现代的日本人见到古典汉语文字列时,脑中不会浮现出中文语音之连续,浮现的是被“训读”的特殊的日语文言文。“训读”是因日本处于汉文文化圈周边这ー位置而形成的巧妙的翻译技法。
然而,这ー持续了千年多的“训读”传统曾遇到一大转折。那正是因导入朱子学而发生的。时值15世纪,当时,因贵族社会之颓废,“训读”技法为世袭的博士之家所垄断。在其中“秘传的、匠人气的汉文读书法”(第36页)成为主流,充斥着极其封闭的气息。可是在其中出现了号称“儒学不依晦庵无以为学”(《桂庵和尚家法训点》),尊信朱子学的禅僧桂庵玄树(1427〜1508),开创出了更为一般的公开的训读技法。从桂庵玄树继承到南浦文之(1555〜1620),并通过近世的林罗山、山崎暗斋、佐藤一斋等醇儒而一般化的该新训读法与博士家的“古法”相对,被称为“近世训点”。17世纪以后日本的经典类书籍之大半是以属于该近世训点的林罗山的“道春点”来训 读的。
该训读之转换“不单是技法上的转换”(同上),也是“与接受朱子学相呼应的ー种思想性转换”(同上)。中村春作得出的结论是,桂庵点,乃至近世训点一般的特征在于仔细地读“而”“矣”等“助字”,“桂庵的这一’置字‘必须一字一字训读,将原文的每一字都改为日文的姿态是与对经书上的每一字都逻辑性地、抽象地进行概念规定,做完全解释的朱熹的注释方法相呼应的”(第37页)。一方面以“理一分殊”为理论前提,一方面作为对格物致知的实践,而细致地注释经书的朱熹的姿态在日本的对应物正是向所有人公开的简明平易的近世训点。
其后,正是否定朱子学“理”之思想的荻生徂彿提倡废除训读,并且,近世末期的读书人习以为常的训读文体变为文明开化时期书写规范文体的母体,乃至当今日本的书面语仍处于其决定性的影响之下,这些有关“训读”与朱子学的问题群正构成了日本儒教史、日语史、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化史等中最关键的结点,这样说也绝不为过。当今日本人阅读、书写的语言本身正处于朱子学遥远的遗留下的影响之中。对于“训读”的这ー重要性,除了哲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者之外,文学研究者也当然相当关注[9],目前在“训读”研究领域,自然地呈现出充满活力的跨学科研究之面貌。令人期待进ー步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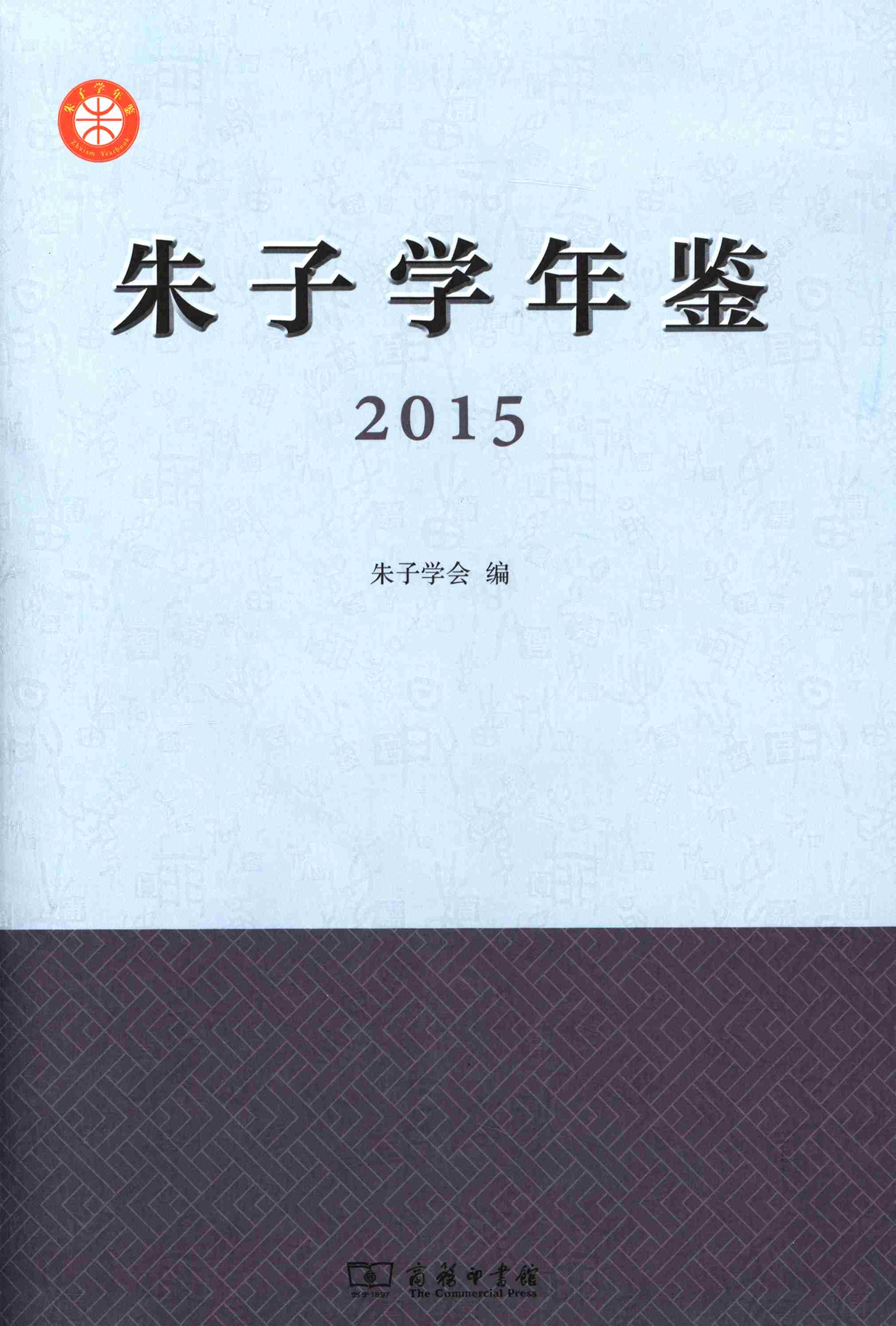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5》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主要内容有“特稿”栏目选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陈来教授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的文章,前者以李退溪与李栗谷的理发气发说为中心来探讨韩国朱子学,后者分析了韩国朱子学的心说论争研究现况。“朱子学研究新视野”栏目推介了杨祖汉教授的《论朱子所说的“诚意”与“致知”关系的问题》、杨立华教授的《朱子理气动静思想再探讨》、方旭东教授的《无思有觉、圣凡体别——朝鲜儒者李珥的“未发”说》、朱人求教授的《朱子“全体大用”观及其发展演变》、许家星教授的《朱子学的羽翼、辨正与“内转”——以勉斋<论语>学为中心》、方笑一副教授的《<近思录专辑>简介》、吾妻重二教授的《周惇颐墓——其历史与现状》等。“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栏目比较详细地梳理了2015年中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朱子学的研究现状,介绍了目前全球朱子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朱子学书评”栏目选刊了对《朱熹大辞典》《朱熹文学思想研究》《宋明理学十五讲》等著作的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学者简介”“朱子学研究机构”“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朱子学学术动态”“资料辑要”等栏目尽可能全面地展示2015年全球朱子学界的最新成果和学术动态。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