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思想与实践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3》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961 |
| 颗粒名称: | 文献、思想与实践 |
| 其他题名: | 评吾妻重二《朱熹〈家礼〉实证研究》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196-20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家礼〉实证研究》是吾妻重二教授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一本关于朱子学研究的专著。吾妻教授是关西大学的教授,曾在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毕业,并于早稻田大学期间作为访华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选择朱子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于2003年在早稻田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的思想史地平》。 |
| 关键词: | 朱子学 思想 实践 |
内容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是日本关西大学吾妻重二教授新近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一部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专著。[1]吾妻教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求学期间曾作为日本第一批访华留学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早大阶段,虽师从著名道教学者楠山春树先生,但吾妻教授选择了朱子学作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他在2003年向早大提交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朱子学的新研究——近世士大夫的思想史地平》(东京:创文社,2004年)。《朱子学的新研究》中,吾妻教授的研究即已体现了既注重对朱熹文献、哲学思想的细致分析,又重视朱熹思想在历史、实践层面展开的特点。在这部以朱熹《家礼》为中心的新作中,吾妻教授不仅延续了先前研究的特色,而且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东亚近世,进一步对朱子思想在实践与制度层面的展开做了更为深详周密的考察。
一
吾妻教授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朱子学的理解与认知偏重于朱熹哲学思想与身心修养的一面,这固然是朱子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无论从朱子学整体所包含的丰富性,还是从朱子学对后世多层面的影响来说,都应当认识到朱子学作为一种综合“文化”的面貌。具体地说,朱子学是包含哲学、自然、历史、经济、文学、道德、政治理论、教育、祭祀、礼仪等多层丰富内容的有机整体,其影响亦渗透到近世中国及东亚世界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正是从对朱子学作为一种综合“文化”的认识出发,近年来,吾妻教授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朱熹的礼学上。“礼”作为“仁”的外在形式或“天理之节文”,是儒家思想在历史实践中最重要的承载者。同样,朱熹的礼学也是朱熹哲学思想在实践与制度层面最忠实的呈现。而在朱熹诸多礼学著作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后世最深的无疑便是《家礼》。
吾妻教授将《家礼》称作“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本”[3],他认为:“《家礼》的问世,可谓是中国近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力之大,并不亚于《四书集注》。”[4]理由有三:第一,与以《仪礼》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礼文献相比,《家礼》是中国近世(宋元明清)礼文献的新古典;第二,《家礼》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篇上》)的传统界限,从而让儒家之礼真正走向庶民的生活,使“士”、“庶”各个阶层都能践履。这正反映了“人人皆可为圣人”这一朱子学“平等主义”的人类观;第三,伴随着朱子学作为一种“普遍思想”在东亚近世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影响,《家礼》的影响范围也超越了中国的地域范围,扩展到日本、韩国等东亚世界。而在近世的东亚,礼实际上成为区分“华夷”的中心指标。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以下简称《实证研究》)便是吾妻教授有关《家礼》研究成果的一次结集。《实证研究》一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篇”,第二部分是“文献篇”。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实际包含了三方面:一是对与《家礼》有关的先行研究的系统梳理。第一章内容即属于这一部分;二是对《家礼》从文献角度展开的考察。其中包括第三章对《家礼》刊刻与版本的讨论以及第二部分“文献篇”即第八章中对《家礼》文本的勘定;三是有关《家礼》的专题性研究。包括第二章中从文献学入手对日本江户时代礼学整体样貌的说明,以及对《家礼》中一些核心要素如第四章中对“家庙(或祠堂)”,第五、六章中对“木主”,第七章中对“深衣”的细致探讨。与从经学或礼学史角度进行的《家礼》研究不同,吾妻教授的《家礼》研究始终是在朱子学的视野中展开的。因此,以下在对各章内容特点进行介绍的同时,亦将试图指出其对当下朱子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二
《实证研究》的第一章是《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家礼〉为中心》。“儒教”一词是日本中国学界对儒学的惯称。“教”之一字更多的是指儒学是包含思想与制度在内的“教化”的整体。这章中,作者不仅讨论了中国古代仪礼与儒教的关系,儒教仪礼所包含的意义,同时也详细地检讨了迄今为止围绕中国儒教礼仪研究的一些中心课题,尤其是与《家礼》相关的研究焦点所在,如“《家礼》的作者问题”,“《家礼》与《书仪》(司马光)的关系问题”,“《家礼》在东亚的传播与展开”,“丧祭(葬祭)仪礼以及祖先祭祀、家族的问题”等。值得一提的是文末所附《〈家礼〉研究文献目录》。该目录几乎涵盖了所有近代以来各国学者有关《家礼》的研究成果,并做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其搜集之广、用功之勤令人叹服。可以说,对先行研究成果的充分重视是作者研究的入门途径。这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史的全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作者自觉地将自身的研究纳入研究史的脉络中,从而建立起与先行研究间的对话关系。通过对话,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与新的领域,从而将研究不断推进。研究篇中其余各章内容的成立及创获之处,都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一个结果。
三
《〈家礼〉的刊刻与版本——到〈性理大全〉为止》与第八章《宋版〈家礼〉校勘》是对《家礼》从文献角度展开的考察。正如本书题名所揭示的,“实证”是作者在研究方式上的另一大特色。在作者看来,不管是思想,还是制度,与之历史有关的实证研究最重要的依据都是文献。因此,《家礼》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家礼》文本的考订。在这一部分,作者的贡献有三点:
第一,彻底厘清了《家礼》在历史流传中的版本系统,并在此基础上以南宋周复本为底本,在尽可能掌握各种参校本的基础上,对宋版《家礼》进行了巨细靡遗的严密校勘。其最终成果即本书第八章《宋版(家礼)校勘》,可谓向学界提供了一部足可信赖的《家礼》定本。
第二,解决了长期以来围绕《家礼》作者问题的争议,将《家礼》视作朱熹尚未定稿的稿本之结论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最为稳妥的定说。朱熹《家礼》自清代王懋竑提出“伪作说”,经四库馆臣的蹈袭,几成定论。近代以来,钱穆、上山春平、陈来等诸多学者皆对“伪作说”有所质疑。作者在继承先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家礼》流传各版本及周边资料特别是序、跋的研究,为推翻“伪作说”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如作者所指出的:朱熹逝后不久,相继出现了五羊本、余杭本以及严洲本等数种不同版本的《家礼》。而与这些刊本密切相关的陈淳、黄榦、廖明德以及杨复等都是直接师从朱熹的门人,在他们留下的序跋资料中,无一例外地将《家礼》视作朱熹的著作并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对《家礼》的敬意。如果《家礼》真的是一部出自别人的伪作,那绝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王懋竑认为《家礼》的序文也是伪作,现存宋版《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卷首所载朱熹亲笔序的翻刻本便直接证明了王说之谬;至于王懋竑所言《家礼》记述内容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作者亦正确地指出:这是因为《家礼》流传于世的时候并非完本,而是未完的稿本,即陈淳所说“未成之缺典”(《代陈宪跋家礼》),黄榦所言的“未暇更定”(《朱子行状》),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判定《家礼》为伪作的证据。
第三,作者对《家礼》版本流传历史的梳理,其目的并不止步于对版本系统的清楚认识,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家礼》在中国近世社会中如何得以普及而又产生影响这一问题。由此亦可窥见作者实证姿态背后真正的关切所在。如在元代刊刻本中,作者列举了元代姚枢的《家礼》刻本。元太宗七年(1235),元军攻克德安(湖北省)之际,江汉先生赵复被随军的姚枢救出,于是向姚枢“尽出程朱二子性理之书”。这是标志朱子学开始在北方得以传播的著名故事。而姚枢在退居辉州苏门山(河南省)后,刊刻道学书籍内便有《小学书》、《论孟或问》与《家礼》。这说明赵复献给姚枢的书籍中,《家礼》应包含其中。由此可以推知:自朱子学北传之初,《家礼》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说明了《家礼》在士人和民间所引起的关注,还根据《元典章》中有关“婚姻礼制”的相关记载即朝廷于至元八年(1264)颁布敕令,明确规定婚礼必须以《朱文公家礼》为准,点明了《家礼》自元代起就已进入国家礼制的层面。这无疑为我们探讨“朱子学如何进入国家法典”这一问题在通常所熟知的自元仁宗朝起《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取士标准的史实之外提供了极为有益的补充。与此问题相关,则是对明代《性理大全》本的考察。如果从版本史的角度来看,朝鲜与日本出版的诸多《家礼》注释书基本上都是以《性理大全》本为底本。因此,在作者看来,《性理大全》本堪称是《家礼》的“普及决定版”。但《性理大全》本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作者指出:明永乐十三年(1415)胡广等奉旨编纂的《性理大全》70卷,将《家礼》收入其中,这意味着《家礼》作为官方认定的文本正式登场。又据《明史·礼制》,永乐年间,《家礼》由朝廷正式向全国颁行。作者认为,被颁行的应该就是新撰的《性理大全》本《家礼》。这代表着出现于朱子学团体这一民间学派的《家礼》,最终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自此反过来由国家向民间进行推广。
四
从以上特别是第三点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作者以实证姿态指向的对文献的关照并未止步于文献,在对文献广泛搜集与精密考证的背后所包含的是对研究史、思想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关切。换言之,作者以文献入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始终具备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一点在有关《家礼》专题研究的各部分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证研究》第二章《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以文献学考察为中心》便是通过文献对江户时代《三礼》以及《家礼》接受情况的考察。向来,在日本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礼学在近世日本的影响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作为思想而被学习和讲习,并没有进入到人们实际生活的实践中。但作者在梳理江户时代礼学著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17世纪后半期日本曾掀起一股《家礼》风潮,这不仅表现在各派学者尤其是朱子学系与阳明学系学者所留下的有关《家礼》的著作上,而且体现在很多著名学者、政治人物如林罗山、德川光圀、池田光政等依据《家礼》举行丧、祭仪式的实例中。对《家礼》在丧、祭场合的广泛运用这一历史事实的揭示,不仅有效地纠正了流行的习见,而且与《家礼》冠婚丧祭各种仪礼都得到广泛普及的中国和朝鲜相比,点明了日本儒教仪礼接受的特色。
第四章至第七章是对《家礼》中与礼制有关的一些核心要素的考察。以下仅以第四章有关“家庙”的讨论为例来说明作者上述的研究特点。
第四章《宋代的家庙与祖先祭祀》中的“家庙”乃是一种总称,有时也被称为影堂、祭堂或祠堂,是祭祀一族之祖先灵魂的设施。换言之,家庙(或祠堂)是实行祭礼的场所。《家礼卷第一通礼》便首论“祠堂”,其下有小字自注曰:“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首。”可见,在朱熹对《家礼》的构想中,祠堂被置于首要的位置。显然,作者对“家庙(或祠堂)”的专题研究也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此章研究的特点在于揭示宋代家庙制度的历史脉络,通过对朱熹前后家庙制度历史流变的考察,朱熹有关家庙设想的“损益”之处及其历史意义便适时地凸显出来。作者指出:以《礼记》等中国古代礼文献为依据的家庙制度的特征在于根据身份、官品来确定能否建立家庙,而家庙的设立是高级官僚的特权。在这种制度下,子孙一旦失去祖先所拥有的官品便有可能失去建立家庙的资格。随着门阀贵族制的崩坏,唐代以前曾发挥过有效功能的家庙制度到了官品只限于一代的宋代,便成为不合时宜、徒具形式的东西。这是造成宋代家庙制度在国家礼制层面进程缓慢的原因。与之相应的,则是士人们的积极探索。北宋的韩琦及司马光或张载、程颐、吕大防等道学家们的努力便是典型案例。在这当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程颐的主张,其意义表现为:第一,所有士人都应当拥有家庙;第二,可以使用此前只有高官才被允许使用的神主;第三,援用《仪礼》的丧服规定,将在家庙中常祭的对象规定在高祖以下四代即小宗的范围内。朱熹《家礼》的祭祖部分就是继承了程颐的这一构想而制定的。这样一来,程朱的努力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重建礼乐”,而家庙也通过这一重建终于从贵族的独享物转变为士人的日常设置。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发掘了以往研究“程朱思想关联”时所未注意的层面,即朱熹在家庙制度上对程颐思想的继承,而且在对家庙制度历史性的重构中指明了其背后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的动因。如果将“士必有庙”这一《家礼》继承自程颐的特点视作程朱思想中平等主义原则的延伸,那么,作者对于《家礼》形成历史背景中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这一客观变化的揭示同样也不容忽视。至此,可以进一步提问的是:既然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变迁已导致国家礼制层面家庙制度难以推进,那为何道学家们仍然会汲汲于家庙的重建呢?除上引朱熹自注中所说明的理由外,作者还不失时机地指出,家庙的建立实际上使得祭祖的场所由墓祠移至家庙。墓祠是宋代流行的设置在坟墓之侧的祠堂。当时,也有将坟墓的管理委托佛寺的情况,一般称为坟寺或坟庵。这些都可纳入墓祠的范畴内。此外,还可以看到道教宫观作为坟墓看守以及在道观内建立祠堂的事例,这也就是说,无论从设施方面还是从仪礼方面来看,佛道二教在民间祭祀祖先方面承担着相当大的作用。因此,将祭祖由墓祠移至家庙,实际上意味着将祭祀这一重要环节的仪礼方式由佛教或道教的形式扭转为儒教的形式。
此外,作者还在本书的第五、六章中讨论了家庙中最重要的祭器——“木主”的问题,以及在第七章中探讨了《家礼》中的儒服——“深衣”问题。这两项专题研究同样在细密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精彩创见,本文在此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从有关“木主”、“深衣”这两项《家礼》核心要素的专题研究中,还可看到的一点是,作者的研究始终是在东亚文化交涉的视野中展开的。如“木主”部分,除中国外,作者还检讨了对于日本、韩国的影响;“深衣”部分同样也讨论了在朝鲜王朝时期与德川日本的施行情況。毋宁说,从东亚文化交涉的角度看朱子学,这也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一
吾妻教授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朱子学的理解与认知偏重于朱熹哲学思想与身心修养的一面,这固然是朱子学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无论从朱子学整体所包含的丰富性,还是从朱子学对后世多层面的影响来说,都应当认识到朱子学作为一种综合“文化”的面貌。具体地说,朱子学是包含哲学、自然、历史、经济、文学、道德、政治理论、教育、祭祀、礼仪等多层丰富内容的有机整体,其影响亦渗透到近世中国及东亚世界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正是从对朱子学作为一种综合“文化”的认识出发,近年来,吾妻教授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朱熹的礼学上。“礼”作为“仁”的外在形式或“天理之节文”,是儒家思想在历史实践中最重要的承载者。同样,朱熹的礼学也是朱熹哲学思想在实践与制度层面最忠实的呈现。而在朱熹诸多礼学著作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后世最深的无疑便是《家礼》。
吾妻教授将《家礼》称作“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本”[3],他认为:“《家礼》的问世,可谓是中国近世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其影响力之大,并不亚于《四书集注》。”[4]理由有三:第一,与以《仪礼》为代表的中国古典礼文献相比,《家礼》是中国近世(宋元明清)礼文献的新古典;第二,《家礼》突破了“礼不下庶人”(《礼记·曲礼篇上》)的传统界限,从而让儒家之礼真正走向庶民的生活,使“士”、“庶”各个阶层都能践履。这正反映了“人人皆可为圣人”这一朱子学“平等主义”的人类观;第三,伴随着朱子学作为一种“普遍思想”在东亚近世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影响,《家礼》的影响范围也超越了中国的地域范围,扩展到日本、韩国等东亚世界。而在近世的东亚,礼实际上成为区分“华夷”的中心指标。
《朱熹〈家礼〉实证研究》(以下简称《实证研究》)便是吾妻教授有关《家礼》研究成果的一次结集。《实证研究》一书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篇”,第二部分是“文献篇”。但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实际包含了三方面:一是对与《家礼》有关的先行研究的系统梳理。第一章内容即属于这一部分;二是对《家礼》从文献角度展开的考察。其中包括第三章对《家礼》刊刻与版本的讨论以及第二部分“文献篇”即第八章中对《家礼》文本的勘定;三是有关《家礼》的专题性研究。包括第二章中从文献学入手对日本江户时代礼学整体样貌的说明,以及对《家礼》中一些核心要素如第四章中对“家庙(或祠堂)”,第五、六章中对“木主”,第七章中对“深衣”的细致探讨。与从经学或礼学史角度进行的《家礼》研究不同,吾妻教授的《家礼》研究始终是在朱子学的视野中展开的。因此,以下在对各章内容特点进行介绍的同时,亦将试图指出其对当下朱子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二
《实证研究》的第一章是《儒教仪礼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以〈家礼〉为中心》。“儒教”一词是日本中国学界对儒学的惯称。“教”之一字更多的是指儒学是包含思想与制度在内的“教化”的整体。这章中,作者不仅讨论了中国古代仪礼与儒教的关系,儒教仪礼所包含的意义,同时也详细地检讨了迄今为止围绕中国儒教礼仪研究的一些中心课题,尤其是与《家礼》相关的研究焦点所在,如“《家礼》的作者问题”,“《家礼》与《书仪》(司马光)的关系问题”,“《家礼》在东亚的传播与展开”,“丧祭(葬祭)仪礼以及祖先祭祀、家族的问题”等。值得一提的是文末所附《〈家礼〉研究文献目录》。该目录几乎涵盖了所有近代以来各国学者有关《家礼》的研究成果,并做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其搜集之广、用功之勤令人叹服。可以说,对先行研究成果的充分重视是作者研究的入门途径。这不仅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研究史的全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作者自觉地将自身的研究纳入研究史的脉络中,从而建立起与先行研究间的对话关系。通过对话,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与新的领域,从而将研究不断推进。研究篇中其余各章内容的成立及创获之处,都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一个结果。
三
《〈家礼〉的刊刻与版本——到〈性理大全〉为止》与第八章《宋版〈家礼〉校勘》是对《家礼》从文献角度展开的考察。正如本书题名所揭示的,“实证”是作者在研究方式上的另一大特色。在作者看来,不管是思想,还是制度,与之历史有关的实证研究最重要的依据都是文献。因此,《家礼》研究的首要任务便是对《家礼》文本的考订。在这一部分,作者的贡献有三点:
第一,彻底厘清了《家礼》在历史流传中的版本系统,并在此基础上以南宋周复本为底本,在尽可能掌握各种参校本的基础上,对宋版《家礼》进行了巨细靡遗的严密校勘。其最终成果即本书第八章《宋版(家礼)校勘》,可谓向学界提供了一部足可信赖的《家礼》定本。
第二,解决了长期以来围绕《家礼》作者问题的争议,将《家礼》视作朱熹尚未定稿的稿本之结论为学界提供了一个最为稳妥的定说。朱熹《家礼》自清代王懋竑提出“伪作说”,经四库馆臣的蹈袭,几成定论。近代以来,钱穆、上山春平、陈来等诸多学者皆对“伪作说”有所质疑。作者在继承先前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家礼》流传各版本及周边资料特别是序、跋的研究,为推翻“伪作说”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如作者所指出的:朱熹逝后不久,相继出现了五羊本、余杭本以及严洲本等数种不同版本的《家礼》。而与这些刊本密切相关的陈淳、黄榦、廖明德以及杨复等都是直接师从朱熹的门人,在他们留下的序跋资料中,无一例外地将《家礼》视作朱熹的著作并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对《家礼》的敬意。如果《家礼》真的是一部出自别人的伪作,那绝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王懋竑认为《家礼》的序文也是伪作,现存宋版《纂图集注文公家礼》卷首所载朱熹亲笔序的翻刻本便直接证明了王说之谬;至于王懋竑所言《家礼》记述内容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作者亦正确地指出:这是因为《家礼》流传于世的时候并非完本,而是未完的稿本,即陈淳所说“未成之缺典”(《代陈宪跋家礼》),黄榦所言的“未暇更定”(《朱子行状》),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判定《家礼》为伪作的证据。
第三,作者对《家礼》版本流传历史的梳理,其目的并不止步于对版本系统的清楚认识,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家礼》在中国近世社会中如何得以普及而又产生影响这一问题。由此亦可窥见作者实证姿态背后真正的关切所在。如在元代刊刻本中,作者列举了元代姚枢的《家礼》刻本。元太宗七年(1235),元军攻克德安(湖北省)之际,江汉先生赵复被随军的姚枢救出,于是向姚枢“尽出程朱二子性理之书”。这是标志朱子学开始在北方得以传播的著名故事。而姚枢在退居辉州苏门山(河南省)后,刊刻道学书籍内便有《小学书》、《论孟或问》与《家礼》。这说明赵复献给姚枢的书籍中,《家礼》应包含其中。由此可以推知:自朱子学北传之初,《家礼》便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说明了《家礼》在士人和民间所引起的关注,还根据《元典章》中有关“婚姻礼制”的相关记载即朝廷于至元八年(1264)颁布敕令,明确规定婚礼必须以《朱文公家礼》为准,点明了《家礼》自元代起就已进入国家礼制的层面。这无疑为我们探讨“朱子学如何进入国家法典”这一问题在通常所熟知的自元仁宗朝起《四书集注》被钦定为科举取士标准的史实之外提供了极为有益的补充。与此问题相关,则是对明代《性理大全》本的考察。如果从版本史的角度来看,朝鲜与日本出版的诸多《家礼》注释书基本上都是以《性理大全》本为底本。因此,在作者看来,《性理大全》本堪称是《家礼》的“普及决定版”。但《性理大全》本的意义还不仅于此。作者指出:明永乐十三年(1415)胡广等奉旨编纂的《性理大全》70卷,将《家礼》收入其中,这意味着《家礼》作为官方认定的文本正式登场。又据《明史·礼制》,永乐年间,《家礼》由朝廷正式向全国颁行。作者认为,被颁行的应该就是新撰的《性理大全》本《家礼》。这代表着出现于朱子学团体这一民间学派的《家礼》,最终引起了国家的重视,自此反过来由国家向民间进行推广。
四
从以上特别是第三点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作者以实证姿态指向的对文献的关照并未止步于文献,在对文献广泛搜集与精密考证的背后所包含的是对研究史、思想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关切。换言之,作者以文献入手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始终具备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这一点在有关《家礼》专题研究的各部分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实证研究》第二章《江户时代儒教仪礼研究——以文献学考察为中心》便是通过文献对江户时代《三礼》以及《家礼》接受情况的考察。向来,在日本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礼学在近世日本的影响只是作为书本上的知识、作为思想而被学习和讲习,并没有进入到人们实际生活的实践中。但作者在梳理江户时代礼学著作的基础上明确指出,17世纪后半期日本曾掀起一股《家礼》风潮,这不仅表现在各派学者尤其是朱子学系与阳明学系学者所留下的有关《家礼》的著作上,而且体现在很多著名学者、政治人物如林罗山、德川光圀、池田光政等依据《家礼》举行丧、祭仪式的实例中。对《家礼》在丧、祭场合的广泛运用这一历史事实的揭示,不仅有效地纠正了流行的习见,而且与《家礼》冠婚丧祭各种仪礼都得到广泛普及的中国和朝鲜相比,点明了日本儒教仪礼接受的特色。
第四章至第七章是对《家礼》中与礼制有关的一些核心要素的考察。以下仅以第四章有关“家庙”的讨论为例来说明作者上述的研究特点。
第四章《宋代的家庙与祖先祭祀》中的“家庙”乃是一种总称,有时也被称为影堂、祭堂或祠堂,是祭祀一族之祖先灵魂的设施。换言之,家庙(或祠堂)是实行祭礼的场所。《家礼卷第一通礼》便首论“祠堂”,其下有小字自注曰:“此章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首。”可见,在朱熹对《家礼》的构想中,祠堂被置于首要的位置。显然,作者对“家庙(或祠堂)”的专题研究也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认识。此章研究的特点在于揭示宋代家庙制度的历史脉络,通过对朱熹前后家庙制度历史流变的考察,朱熹有关家庙设想的“损益”之处及其历史意义便适时地凸显出来。作者指出:以《礼记》等中国古代礼文献为依据的家庙制度的特征在于根据身份、官品来确定能否建立家庙,而家庙的设立是高级官僚的特权。在这种制度下,子孙一旦失去祖先所拥有的官品便有可能失去建立家庙的资格。随着门阀贵族制的崩坏,唐代以前曾发挥过有效功能的家庙制度到了官品只限于一代的宋代,便成为不合时宜、徒具形式的东西。这是造成宋代家庙制度在国家礼制层面进程缓慢的原因。与之相应的,则是士人们的积极探索。北宋的韩琦及司马光或张载、程颐、吕大防等道学家们的努力便是典型案例。在这当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程颐的主张,其意义表现为:第一,所有士人都应当拥有家庙;第二,可以使用此前只有高官才被允许使用的神主;第三,援用《仪礼》的丧服规定,将在家庙中常祭的对象规定在高祖以下四代即小宗的范围内。朱熹《家礼》的祭祖部分就是继承了程颐的这一构想而制定的。这样一来,程朱的努力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重建礼乐”,而家庙也通过这一重建终于从贵族的独享物转变为士人的日常设置。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作者不仅发掘了以往研究“程朱思想关联”时所未注意的层面,即朱熹在家庙制度上对程颐思想的继承,而且在对家庙制度历史性的重构中指明了其背后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的动因。如果将“士必有庙”这一《家礼》继承自程颐的特点视作程朱思想中平等主义原则的延伸,那么,作者对于《家礼》形成历史背景中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变迁这一客观变化的揭示同样也不容忽视。至此,可以进一步提问的是:既然政治制度与社会阶层的变迁已导致国家礼制层面家庙制度难以推进,那为何道学家们仍然会汲汲于家庙的重建呢?除上引朱熹自注中所说明的理由外,作者还不失时机地指出,家庙的建立实际上使得祭祖的场所由墓祠移至家庙。墓祠是宋代流行的设置在坟墓之侧的祠堂。当时,也有将坟墓的管理委托佛寺的情况,一般称为坟寺或坟庵。这些都可纳入墓祠的范畴内。此外,还可以看到道教宫观作为坟墓看守以及在道观内建立祠堂的事例,这也就是说,无论从设施方面还是从仪礼方面来看,佛道二教在民间祭祀祖先方面承担着相当大的作用。因此,将祭祖由墓祠移至家庙,实际上意味着将祭祀这一重要环节的仪礼方式由佛教或道教的形式扭转为儒教的形式。
此外,作者还在本书的第五、六章中讨论了家庙中最重要的祭器——“木主”的问题,以及在第七章中探讨了《家礼》中的儒服——“深衣”问题。这两项专题研究同样在细密的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精彩创见,本文在此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从有关“木主”、“深衣”这两项《家礼》核心要素的专题研究中,还可看到的一点是,作者的研究始终是在东亚文化交涉的视野中展开的。如“木主”部分,除中国外,作者还检讨了对于日本、韩国的影响;“深衣”部分同样也讨论了在朝鲜王朝时期与德川日本的施行情況。毋宁说,从东亚文化交涉的角度看朱子学,这也是作者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立场。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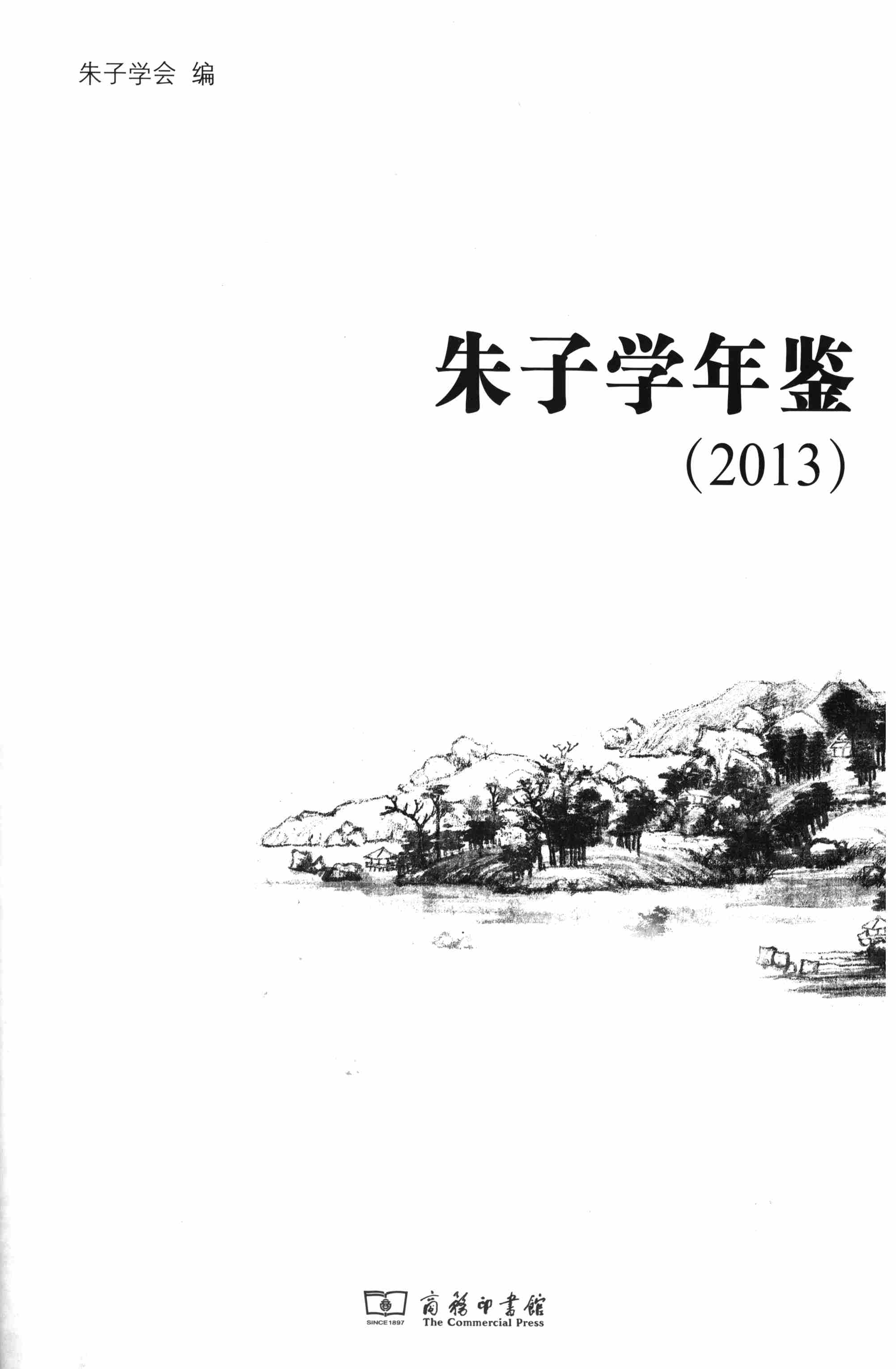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3》
本书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动态、资料辑要(介绍朱子学新书目录、期刊论文索引、全球朱子学研究资料目录等)9个栏目。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