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日本学者朱子学研究现状述评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3》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952 |
| 颗粒名称: | 2013年日本学者朱子学研究现状述评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8 |
| 页码: | 160-177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日本朱子学研究的现状。与中国内地不断兴盛的朱子学研究相比,日本的研究队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后继乏力的情况。虽然有人可能认为可以忽略日本的相关研究,但这可能是得不偿失的。日本有着近百年的汉学研究传统,注重严谨扎实,在研究某个课题时会广泛搜集相关研究成果,并以实证主义精神为基础进行论证。这种学风和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尽管2013年日本学者在朱子学研究方面的成果非常有限,但本文将扩大范围,包括单篇论文的介绍,补充介绍去年遗漏的重要研究,并对一些相关主题进行简要回溯性介绍,重点介绍朱熹的鬼神观以及与真德秀相关的研究。 |
| 关键词: | 朱子 经学思想 研究现状 日本 |
内容
与中国内地近几年来方兴未艾的朱子学研究相比,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呈现出研究队伍后继乏力的局面,对这一点,石立善在2006年撰写的研究综述中已指出,笔者在去年为年鉴所撰写的《2011—2012年日本学者朱子学研究现状述评》[1]一文中也有论及,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之,在此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如果仅因近期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青黄不接,就以为可以绕过日本的相关研究,那可能是得不偿失的。笔者在去年的述评中曾指出,日本有近百年的汉学研究之传统,在学风上大多务求严谨扎实,在对某课题进行研究时,一方面会尽可能搜集相关先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论证时基本都以材料为依据,不喜浮夸之谈,这就是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实证主义精神,这当中有相当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借鉴。
由于从数量来说,2013年日本学者的朱子学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因此本文在介绍的范围上与去年的述评相比又有所扩大:其一,与去年一样,笔者会将单篇论文列入介绍范围;其二,对去年述评中遗漏的重要研究进行补充介绍;其三,在介绍中,对若干相关主题进行简要的回溯性介绍(此次述评中重点介绍朱熹的鬼神观以及与真德秀相关的研究)。
据笔者所知,2013年在日本出版的朱子学专著只有木下铁矢的《朱子学》(讲谈社,2013年)一本,因此本文不再区分论著和论文。此书属于讲谈社出版的一系列古典普及型研究,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在定位上略有不同。该书可以说是木下对近十多年来自己研究之汇总,但因为要顾及一般读者,无论是论证还是引用材料上都会受到限制,因此在这里,笔者想向国内同仁介绍一下木下先前的研究成果。木下原来研究清朝考据学,后转为专攻朱子学,1999年出版的《朱熹再読——朱子学理解への一序說》(研文出版),可以说是其力作,木下在书中提出了诸多崭新而敏锐的观点,很值得仔细研究。对此,石立善在述评中也有介绍,就不再重复了。之后,木下继续从事朱熹思想研究,并将2000年至2007年的九篇相关论文汇集成新著《朱熹哲学の視軸——続朱熹再読》[2]。
在这里仅以《续朱熹再读》的第一章《朱熹の思索、その面差しと可能性》(《朱熹之思索,其面相及其可能性》)为例进行介绍。通常人们都把朱熹理解为所谓“二元论者”,即理气、阴阳、已发未发等二项对立之思维,然而在木下看来,朱熹本人毋宁说是力图打破这些二元之对立的,这体现在朱熹对“心”的理解上:
“心则通贯已发、未发之间,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心是与性相独立、性之具在的‘场所’,并且是时时变换的独特之‘场’”,与此同时,“心”和“太极”都是“无对”之存在,朱熹将其特征描述为“妙”字(“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木下通过对“神”、“妙”以及“机”之分析,指出“使阴阳之相互转换得以进行的运转之机关(switching),此转换运转之作用便是太极”(第17页),所谓“作用”,木下用“事件存在”来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物件存在”。何谓“事件存在”?例如朱熹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解释是:“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不说“仁者之心,以己及人”,正是排除日常思维的先有某物件、然后对此物件进行描述的方式,而倒转过来是以事件性的“以己及人”为先,此事件才能与“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相联系。同样的,通常我们理解宋明儒学之“万物一体”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式的“人物均受天地之气(理)而生”的基础上,但是朱熹曾明确否认此说法:“不须问他从初时,只今便是一体……他那物事自是爱,这个是说那无所不爱了,方能得同体。若爱,则是自然爱,不是同体了方爱。”[3]对他者乃至万物之爱是自然生起的“事件”,先在于“彼此是否同体”的理论性思维。木下在这篇文章中反复强调的是什么?是朱熹在努力克服所谓常识性的思维(实体化,二元对立等等),或者毋宁说,木下所看到的朱熹的形象,在很大意义上是木下自己的思索之深刻性的折射——对于先有某物后有某事的(主语与述语的语言之惯性与主语先在性的捏造,这至少可以上溯到尼采对康德的批判)思维惰性的批判,以及对“事件”、“此时此刻”之强调,不难让我们联想到诸如Whitehead等西方哲学家破除实体化思维的努力。
另外,木下还有一篇论文《“仁義礼智信”力か“仁義礼智”か——現在の朱子学理解を問う》(《“仁义礼智信”还是“仁义礼智”?——对当今朱子学理解之疑问》),收录在《吉田公平教授退休纪念论集》(研文出版,2013年)一书中。事实上,在去年日本有好几个并非研究朱子学的老师以及同学都问笔者是否看过此文,何以该文会受到如此关注?木下近几年来一贯地批判岛田虔次[4]的朱子学理解,在木下看来,由于岛田式解读的重大偏差,时至今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对朱熹都普遍存在严重的误读。就朱子学而言,最核心的概念无疑是“性”与“理”,朱熹继承二程之观点,主张“性即理”,而对于“理”,在后文还会提到,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存在很多种解释,但就“性即理”这一命题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偏向于从“本质”(essence)上去进行理解,木下在第一节就举了日本朱子研究的代表人物吾妻重二的说法:“就人而言,人存在之理是‘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仁与动物或者植物相区别开的本质(存在规定)。”[5]这个说明比较简略,接下来木下以日本思想史研究者渡边浩(渡边是丸山真男的直系弟子)为例,依照渡边之理解,“理”能判定某个体究竟属于“人”还是“桃子”或者“椅子”等类别,并且是此各个类别之特定的“应有之存在方式”(在るべき在り方),这显然与吾妻所说的“本质(存在规定)”同出一辙——桃子是桃子,是因为桃子所应有的存在方式、亦即是“理”之内在性。木下认为,这种“本质”论属于经院哲学所讨论的“本质存在”(essentia)与“事实存在”(exsistentia)之范畴中的“本质存在”:本质存在是“某物是什么”、亦即是说面前某物究竟是桌子还是椅子,而事实存在说的是某物是否实际存在,例如面前是否有一张桌子。那么,朱熹所说的“理”就成为区分“人”与其他类别的“本质”所在。但是,木下仅举了一例,就动摇了上述看似理所当然的解释:在《孟子·离娄下》中,朱熹如此解释孟子的“人之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无少异耳。[6]
朱熹明确指出:人与物同得“天地之理”,理无所谓完全不完全,区别就在于人与物得到“天地之气”是不同的,人能得“形气之正”,故能“全其性”而已。接下来木下还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与分析岛田等先行研究的问题所在,而在笔者看来,关于“理”是否是人之本质规定这一点,在朱熹本身的文脉中,其实就是“理同气异”论,而二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云:“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71朱熹的“气有偏正”说显然源于二程。用“气”来解释人与其他生物之不同固然可行,但朱熹仍然需要解释:同样作为“人”,人与人之间何以存在着先天或者后天的巨大差距?木下引用了岛田的说法,岛田认为:“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五常”(仁义礼智信),既然万物之基本组成都是“五行”,那么五行之间的比例差异就决定了即便同样是“人”,如果“木气”盛则性格偏于“仁”,“火气”盛则偏向“礼”。由此,木下认为,岛田依然是在主张“理”之本质主义论。但公允地说,在原文中岛田并没有说此处之“仁”即是“理”,而毋宁可能是说:“仁”等“五常”之德在现实世界中所展现出来的程度,是由“气”,亦即“五行”所决定的,因此这依然可以说是“理同气异”论。包括朱熹有时候说“理有偏全”,这依然是在后天“理”被“气”遮蔽而产生的差异,从“理一分殊”的角度来说,人与其他万物之间的“理”不可能是“异”。岛田将“理”解释为“仁义礼智信”,并不妨碍他以及学界主流的“本质=存在规定”之理解。在之后,木下还针对岛田之说法,提出“性=理”的内容究竟是“五常=仁义礼智信”还是“仁义礼智”的问题,并依据朱熹文献的检索结果以及理论分析,论证了晚年朱熹是站在“仁义礼智”一边理解“性=理”的立场。但如果岛田并不是以“理异”来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话,那么“是四德还是五常”的讨论相对于“存在规定”说之批判而言,可能并不那么重要。
事实上,不管是吾妻、渡边,还是被木下视为此理解之发端者的岛田,都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所主张的所谓“本质”、“存在规定”之说法源于经院哲学(在笔者看来更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习焉而不察的词汇,不管是“本质”、
“内在”,还是“形而上学”,尽管在这个时代,“形而上学”已经偏于贬义,而大多数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也对西方哲学以及理论不感冒,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汇时能够避免其背后长达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背景。木下是当今日本极少数中国思想史研究出身而又具有一定西哲素养的学者,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一再发现诸如上述之问题所在。
同样收录在《吉田公平教授退休纪念论集》中的朱子学研究还有一篇:牛尾弘孝《朱熹の鬼神論の構造——生者と死者をつなぐ領域》(以下简称《构造》)。关于牛尾,去年的年鉴中有介绍,请读者参看之。牛尾在《中国哲学论集》第36号的《書評吾妻重二著『朱子学の新研究』》[8]一文中,曾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日本学者对朱熹的鬼神观研究,而《构造》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书评之延续,因此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鬼神观问题在日本方面的先行研究状况。朱熹上承张载与二程之思想,以气之屈伸往来为鬼神,而市川安司早在《朱子哲学论考》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张载持“气之循环”论,气虽然有消长,但总量不变,而程颐主张“气”是“生生”,产生新“气”的根源为“真元”,朱熹则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之后的土田健次郎以及三浦国雄的观点也基本相同。市来津由彦则进一步指出:朱熹“在继承程颐之气说的同时,新之气生生不息,补充了减少的成分,因而从总量上看天地间之气没有增减,如此便对张载的气化宇宙论和程颐的气说之间进行了调停”[9]。牛尾还提到,关于程颐的“真元之气”说,友枝龙太郎解释为“生命体之根源”,而山田庆儿以及土田健次郎则认为应当与道教有关,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具体的说明,因此还有进一步检讨的余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朱熹认为气并非循环而是会趋向消亡,那么在祭祀鬼神尤其是自己的祖先时,所谓“祖考来格”便不可理解,这一点后藤俊瑞早在1937年就已经指出[10],战后居于学术统治地位的岛田也认为这是朱子学理论的自我矛盾[11]。但在此后,又有不少学者站出来为朱熹辩护,因而有所谓“破绽说”之争论。在这里不可能一一罗列,仅举两人为例。柴田笃在《陰陽の霊としての鬼神——朱子鬼神魂魄論への序章》(《作为阴阳之灵的鬼神——朱子鬼神魂魄论序章》)一文中,并不像某些学者那样以存在论、工夫论等区分来为朱熹辩护,而是以关键词“灵”出发,他指出:“灵这个字是对如下之事实的表达——作为存在原理之天理而内在于万物生成要素的气当中。”就人而言,就是“心”:“心本体因为保有理,换句话说与理合一,因而具有能够认识与知觉事物之理的机能。这被称为心之虚灵。”那么鬼神魂魄也同样具备“理气妙合”之性质,因而祭祀时候的“感格”正体现出魂魄理气妙合之灵妙性[12]。市来津由彦则指出,光从“气”是“聚散”还是“消亡”的角度来思考是不够的,他建议从“理”的角度进行理解:从存在论上看,气之生成与聚散说到底都依据“理”,人之存在本身就是理气一体,这一点和柴田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实践的角度看,如果应当祭祀,就应当去祭祀,特别是在祭祀之时,通过尽自己之诚敬而达到心灵之纯化,“就祭祀本身而言,由祈祷而使得鬼神来格,所追求的是祭祀者引发此感格……这种由祈祷而来的心灵之纯化,就在朱熹以及其门人的主观之中得到保存”。
在介绍完上述研究成果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牛尾的《构造》一文。朱熹以气之屈伸往来解释鬼神,但事实上此处说的鬼神是泛指意义,即天地间周流不息之气,就人而言则是魂魄。如果“昼”为“神”,“夜”为“鬼”,那么生者就是“神”,死者就是“鬼”,但是生者也有“鬼”,其屈伸消长是渐变的,因此可以画出一幅类似于物理学上的沙漏轨迹图。其次,牛尾以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第二书为例:
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但有是理,则有是气……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皆非性之谓也。故祭祀之礼,以类而感,以类而应。若性则又岂有类之可言哉。然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下划线为笔者所加)。故上蔡谓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盖谓此也。[13]
对于“其根于理而日生者”一句,牛尾问道:此“理”是何“理”?“生”又是何意?一般作为中国人,既然是自己的母语,尤其对像“生”这样的词,不会有太大的警觉,但是作为日本汉学的传统,采用江户训读法进行训读是基本功课,而在训读之时,对于一个字应该怎样训读,其实就直接牵涉对此字乃至整个句子的理解。就“生”而言,牛尾列举了几种先行研究的训读法:荒木见悟的翻译是“以理为依据,每天都(继续)活着(日々生き(続け)てい、るもの)”,这种解读应该是考虑到了后文“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的说法。而市来津由彦则直接训读为“根于理而日日生者(生じる者)”,其分析是“像生生之气那样,连续不断被生出的东西,这从天地运作之普遍性视角来看,果然还是归结为理”。比较有趣的是,近几年来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的部分学者开始强调通过“东亚儒学”之视角来重新探讨儒学以及儒学思想史,即便不直接接受此主张,不少学者也陆续把目光转向日本或者韩国的儒学,期待从中发掘出新的东西。无独有偶,牛尾在文章中提到了日本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山崎暗斋(1618—1682)的晚年弟子三宅尚斋(1662—1741)所撰写的《祭祀来格说》,该书只有短短的八页,但内容上正好是关于祭祀之礼的鬼神来格与三宅自己的个人体验:
不灭之理,藏于不绝之气。以不灭之理,求之于不绝之气,则不绝之气,根于所藏之理,模写于所求之理而出来。洋洋仿佛,见前日事,见前年祖考。气之根于理而生,随感而见者,如此矣。[14]
事实上,土田健次郎早在1996年就已经注意到了该文,并评论道:“祖先之精神(灵妙之作用)根于天地之精神而生生不穷,这里的强调点与其说是气,不如说是理。”[15]笔者对三宅尚斋没有研究,但就此段文字而言,如果能点明“不绝之气”之所以“不绝”或者“生生”,正是因为“天地生生之大德=理”的话会更好。牛尾很欣赏三宅的上述理解,并指出,三宅并不是想暗示“理”真的能生“气”。由于“理”能乘于“气”,因此“气”之生生不穷,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也能说是“理”之流行。
刚从东洋大学退休的阳明学研究者吉田公平教授在2012年出版了《中国近世の心学思想》(研文出版),当中有若干篇论文与朱熹相关,但因为时间关系,笔者未能在去年的年鉴截稿日期前看到此书,因此在本次论文中进行简要的补充介绍:此书是吉田公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的论文合集,在内容上自然以阳明学以及相关研究为主。东洋大学是日本唯一一所以哲学为主要学科的大学(其创始人为日本著名思想家井上圆了)[16],以吉田公平为首的中国哲学教研室均秉承大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哲学与思想,另一方面有很强的现实关怀,这两点在日本其他中国思想研究基地以及学者身上是很难看到的。吉田公平此书以“心学”为题,但此“心学”不是泛泛之意义的心学,而是建立在两大前提上。其一,依照其老师荒木见悟在《仏教と儒教》中提出的著名理念、即“本来性”与“现实性”:人之为人的本性是“性”或者佛教说的“佛性”,此是“本来具有”而完全自足;其二,虽然人的现实状态会有所欠缺,但是不需要通过外力,而通过自己之努力“悟”得本来完全之性。在吉田公平看来,既然近代是“上帝已死”的世俗化社会,则宋明儒学的“自立本愿”之精神恰恰能发挥作用。由于各篇论文主题不一,在此无法一一介绍,但是例如《告子について》一文,对于宋明儒学中历来被作为“异端”的告子,非常冷静地剖析了其与孟子的论辩,指出孟子的诘难均存在逻辑上的跳跃,并不足以驳倒告子,而朱熹则先入为主地以孟子之见为“正统”,完全无视告子之人性论的意义所在。另外,例如对于《大学》的“新民”与“亲民”之辨,朱熹注重圣贤对民众之教化而取“新民”之意,但是如此一来,“占绝对多数的民众必须通过他者之救济,如此不免使得性善说与自力主义有所褪色……民众结果只是教化之对象,而无法成为人伦上的自觉之创造者”,而王阳明使用“亲民”,则强调“他者虽是助缘,从究竟上来说还是需要人之自力,而此力量本来就是人人本来固有的”[1刀。对以上之评判是否公允,在此不赘,但是很显然,对于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抱着客观实证之态度,而积极反思其思想与实践之意义以及问题所在,吉田公平的上述学问之姿态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
接下来介绍单篇论文。辻井义辉《朱熹哲学における感応と理》(《朱熹哲学中的“感应”与“理”》)(东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纪要第21号,2013年,第219—244页),去年的年鉴中对辻井及其论文有简单介绍,请读者参看之,在此不赘。该文研究的对象是老生常谈的朱子学之“理”,在简单介绍了日本学界的若干种解释(楠本正继:“生成世界的主宰之根本因”;安田二郎:“意味”;岛田虔次:“宇宙、万物之根据,宇宙之应有的原理,就个体而言是个体之所以成此个体的原理”)之后,辻井特别推崇木下铁矢的看法,木下将“理”理解为“元→亨→利→贞”之顺次展开旋律(Rhythm)、将“性”理解为“活动程式(Program)”,辻井此文即以“阴阳”为线索来证成木下之理解。首先,朱熹认为,天下之物都是“有阴有阳”、“有动有静”,阴阳之间既相互转化,也相互抗争,是极具动态的。那么,何以阴阳会如此运作?那自然是因为有“阴阳之理”。但是,辻井引用了两则材料,试图证明“阴阳之运作是由于理是主体”(第227页),却颇有问题。两则都出自《朱子语类》:
动则此理行,此动中之太极也。静则此理存,此静中之太极也。[18]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19]
我们知道,中文“则”字有多重含义,而“动则此理行”的“A则B”结构,显然属于承接关系,像《论语·为政篇》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如此。A与B未必就是因果关系,但A在时间上不可能晚于B。如果“理”是“主体”,何以作为“客体”(既然辻井认为理是主体,那么动静当然就被认定为是客体)的“动静”会先行或者至少不在“理”之后?要确切理解这两句话,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看。“理”是否是某种实体性的存在?回答显然是“否”,朱熹明确否定“理”或者“太极”是“一物”。如果不是,那么说“理”是“主体”是什么意思?辻井在同文第232页上以“动静者,所承之机”为例,认为如同人骑在马上一样,“理”乘于“气”,那么“动作之主便是理”、“绝非没有意义地单纯搭乘在上面,而毋宁说是操纵”。问题在于,朱熹此比喻虽然有名,但本身却存在问题:“理”与“气”并不处在同一层面上,本不能以“人”、“马”这样两种相对待之物来进行理解。如果说“理”是“操纵”气,那么何以朱熹不说“人欲一出一入,马亦与之一出一入”,而要倒过来说“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理”本身不可言“动静”,更不可言“主体”,否则朱熹就不会为“气”偏离“理”之问题而苦恼了。
既然理不是“一物”,那么“动则此理行”,意思就是说“动”则此“理”寓于“动”之中,此即“不相离”之意,而“动”之所以能“动”以及此“动”之运作方式,则依据“理”。
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20]
作为前半部分的结论,辻井认为,阴阳之理,便是使得气能够规律性地自动运转、依据一定之节奏而发生阴阳之运作,是此自动装置的“内在动力因”,这其实是重复了木下的结论,而“动力因”的说法与“主体”是相差很远的。
论文后半部分以“感应”为研究对象,衔接非常紧密。何以见得?盖朱熹曰:“凡在天地间,无非感应之理,造化与人事皆是。且如雨旸,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个旸出来。旸不成只管旸,旸已是应处,又感得雨来。”21]辻井注意到,朱熹强调感格之重要性,以至于像豚鱼这样的无知之物,只要人“至信”,便能“感豚鱼,涉险难,而不可以失其正”[22],并指出:“此‘感’并不只是从外部进行作用,而是能深入到对方的内部而作用,换句话说,是‘唤起’、‘引起’之意味”(第238页),当然,这一点在实践上更重要,儒家主张父慈子孝,父之“慈”能够“感”化子女,而子女由此而唤起自身本有之孝心,与此同时,“‘应’在作为‘应’而作用时,同时也在‘感’对方”(第239页)。诚然如此。用符号标记来看会更清楚一些:
(A应)A感→B应(B感)→A应(A感)→……
但是,木下早在《朱熹再读》一书中就已指出,上述“感应论”模式均以A、B为不同主体为前提,但事实上程颐就提到“‘寂然不动’,万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则只是自内感。不是外面将一件物来感于此也”[23],朱熹在回答弟子对此的提问时说:“物固有自内感者,然亦不专是内感,固有自外感者。所谓‘内感’,如一动一静,一往一来,此只是一物先后自相感。”[241亦即是说,所谓“感应”,有“外感”和“内感”两种。但辻井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其基本原理都是相互唤起、相互抗争、同时相互转换,此自动装置之所以可能,当然是因为“理”之存在(第243页)。
福谷彬《孔孟一致論の展開と朱子の位置——人性論を中心として》(《孔孟一致论之展开与朱子的地位——以人性论为中心》)(《日本中国学会报》第65集,2013年,第103—118页,以下简称《孔孟》)。福谷彬是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硕士时期就开始研究朱熹,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儒学者动辄称“孔孟之道”,但孔子与孟子之一致性并非理所当然,从汉代开始,出现认为孔子与孟子在根本思想上一致的观点,而福谷认为,此“孔孟一致论”的最终完成是程朱理学。福谷在该文中以“人性论”为切入点,对思想史上的“孔孟一致论”进行了梳理。关键句其实就两句,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而孟子主张“性善”,“人皆可为尧舜”,就字面意思来看,孔子持阶层式人性论,而孟子主张人性向善之普遍性。福谷首先梳理了扬雄、王充、韩愈的孔孟一致论观点,指出他们都以《论语》的阶层式人性论为基础,调停《论语》与《孟子》。到了汉代,董仲舒以爱敬父母之德为“孟子之善”,以遵从三纲五纪为“圣人之善”。而作为唯一现存古注的作者赵岐,对孟子的圣凡一致论则理解为:“圣人亦人也,其相觉者,以心知耳。故体类与人同,故举相似也。”于是圣人与凡人只有形体意义上的相似。这依然是延续了阶层式人性论的观点。到了北宋,王安石推崇孟子,但认为孟子所说之“性”其实是表现在外面的“情”,赞同孔子的性相近论,但是,王安石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下愚”并非“不可移”,而是不愿意努力去“移”,因此从理论上说,“下愚”也存在向上之可能性。到了朱熹的时代,福谷首先整理了道学的谱系,指出张载所提出的“气质之性”与“本然之性”的区分至为关键,由此,孔子所说的“性相近”就是“气质之性”,孟子所言“性善”则是“本然之性”,而“下愚”也只是自己不愿意“移”而已。“同样是孔孟一致论,朱熹认为,既然孟子正确地继承了孔子之思想,那么由孟子之思想完全可以逆推出其由来、亦即孔子之思想,这毋宁是以《孟子》为基准而理解《论语》”(第113页)。当然,福谷也指出,朱熹并没有因此而抬高孟子的地位,他始终强调,孟子之思想来源于孔子,不可言《孟子》胜过《孔子》,与此同时,朱熹还认为,《论语》的记载多切实具体,而《孟子》则多从理论方面着眼,两书各有特色。
在介绍完该文之后,笔者想提出两点疑问。首先,福谷认为“孔孟一致论从汉代开始到宋代逐渐形成,但其内容之变化到目前为止则没有受到关注”(第115页)。但是,孔子与孟子之异同,不知古今有多少大家曾经论及,而人性论上的“性相近,习相远”与“人皆可以为尧舜”命题,几乎是基本中的基本,以思想史(尤其是孟子学)的角度进行整理的先行研究也是不胜枚举。即便其他先行研究没有用“孔孟一致论”的题目进行讨论,但在内容上也多有重复之处。不管是汉代的人性论,还是道学的人性论,福谷所言很难说有超越前人之处。如果将该文界定为总结与梳理之文章(在日本的话,此类文章应当划分为“研究笔记(研究ノ一ト)”,而非“论文”),那么列举相关的先行研究就非常必要,但该文所列参考资料又非常有限。其次,福谷在开篇就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为阶层式人性论,并以陈述句式说“两书(笔者按,指《论语》和《孟子》)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撇开宋明儒学的“气质之性”、“本然之性”的理解,《论语》和《孟子》的人性论真的有很大差异吗?特别像《论语》那样,经常缺乏前后文语脉的情况下,要断定孔子之原意,在笔者看来几乎不可能。在孔子的时代,对于“性”之讨论还没有展开,他说“性相近”,此“性”究竟是何义?“相近”又是何义?此皆不可晓。但孔子说“相近”,那与主张人性普遍论的孟子就未必有“很大的差异”,并且对孟子的“性善论”的理解,我们也需要注意,孟子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都已经是“善”或者是“圣人”了,否则孟子还需要说什么“扩充”的工夫呢?孟子竭力主张的只是人人都有先天向善之可能性,并且在后天之干扰被排除后,就如同水流之就下那样,自然会向善。当然,上述理解只是笔者肤浅的个人见解而已,但至少从行文上来说,如果“孔孟一致”并非理所当然,那么“孔孟并非一致”也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另外,该文以思想史的角度进行人性论的探讨,得出宋代之前“孔孟一致论”的儒家持阶层性人性论的观点,而宋代以后则倾向于普遍性人性论,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向深层挖掘而追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这种变化是否只限于道学的谱系,还是说是儒家整体乃至社会层面对人性论的理解之改观?要回答上述问题,就不是狭隘的思想史研究所能解决了。
福谷彬《r資治通鑑綱目』と朱子の春秋学について——義例説と直書の筆法を中心として》(《〈资治通鉴纲目〉与朱子的春秋学——以“义例说”和“直笔”书法为中心》)(东方学第127辑,2014年2月,第66—82页)。众所周知,朱熹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是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之体例与笔法为准,从大义名分论之立场进行修改的作品,其体例模仿《左传》,“纲”之笔法也多采用“春秋笔法”。但是,朱熹本人一直反对“一字之褒贬”那样的穿凿附会,认为孔子是依据鲁史而“直笔”写成,否定“义例说”,而另一方面,在《纲目》中事实上却存在着大量褒贬的书法,因而例如大名鼎鼎的内藤湖南早就指出其中存在的矛盾,福谷为了解决此矛盾,重新探讨了朱熹的春秋学观点。首先,福谷认为朱熹春秋学的独创性即是“义例说之否定”与“直笔说之提倡”(第67页),但事实上这两点在朱熹之前都早已有人提出,例如唐人啖助就提出“美恶在于事迹,见其文足以知其褒贬”,北宋蜀学的崔子方更明确批判《公羊传》、《穀梁传》的所谓“日月为例”说,此皆为治春秋之常识,不多赘述。福谷指出,朱熹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对“义例说”抱有怀疑,在晚年的《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依然如此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话: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
何谓“鲁史旧文”?
如晋史书赵盾弑君,齐史书崔杼弑君,鲁却不然,盖恐是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
福谷指出,此说依据的是杜预的“义例说”。在杜预看来,在孔子笔削之前就存在的春秋书法之规定是“凡例”,与之相异的是“变例”,所谓“变例”就是孔子“一字褒贬”之新意。由此可见,朱熹否定的“义例说”是指“变例”,而非“凡例”(第70页)。但问题在于,福谷可能过于夸大了杜预与朱熹之间的差异。杜预虽然看似像今文经学家那样主张孔子通过“不书”、“故书”等解经语来“微显阐幽”,但“正例”与“变例”之外还存在着无例可言的情况:“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因而在今文经学家看来是“例”的很多东西杜预都不承认。
但是,如果一味否认圣人褒贬之义,那么孔子修春秋的意义究竟何在就成了问题。因此朱熹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朱熹所指的是隐公元年之记事。经文所记录之事件在朱熹看来,都是与人伦相关的教训,因此即便孔子不加一字之褒贬,其内容也已经有所谓“大义”在了。福谷还引用了另一条相关的材料:
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词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
福谷指出“朱子一方面否定《春秋》有一字褒贬,主张直书说,另一方面认为其中有‘言外之意’”,并认为这并不矛盾(第72页)。例如《朱子语类》卷五十八中有如下记录:
孔子已自直书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会齐候于某,公与夫人姜氏会齐候于某……此等显然在目,虽无传亦可晓。
这里牵涉的是鲁桓公与夫人文姜在访问齐国时,齐襄公与文姜奸通,桓公知情却反而被杀,文姜也没有返回鲁国。虽然《左传》有详细记载,但朱熹认为光看经文中反复提及“姜氏”的记载就能够明白事情之缘由。由此,福谷总结道:“通过记录事实,使得毁誉褒贬自见,与此同时,为了明此毁誉褒贬,而通过直书史实的记录者之作为,以上两点即是朱子所认为的‘直笔之笔法’。”(第73页)
在分析完朱熹的春秋观之后,福谷进一步考察了《纲目》之编纂与朱熹春秋学的关联。在初稿完成阶段(1172),朱熹在序文中点题:“因两公四书(笔者按,即司马光的《通鉴》、《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的《通鉴举要补遗》),别为义例,增损隐括,以就此编。”但是,在淳熙六年(1179)《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的《答李滨老书》中,朱熹却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
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隐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此“别为一书”当为《纲目》之“凡例”。对于“凡例”之修订,福谷引用了文集卷三十七《答尤延之书》来证明其与春秋学的关系。按照司马光《通鉴》之旧例(现不可考),事王莽之臣者去世时皆书“死”字,但对于同样侍奉王莽的扬雄,记录却是“是岁,扬雄卒”。对此,朱熹在书信中说:“正以其(笔者按,指扬雄)与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虽异,而其为事莽者则同……所以著万世臣子之戒明。虽无臣贼之心,但畏死贪生,而有其迹,则亦不免于诛绝之罪。此正春秋谨严之法。若温公之变例,则不知何所据依。”在朱熹看来,司马光对王莽之臣书“死”是“直笔”,那么对于同样是王莽之臣属的扬雄就没有理由网开一面。
朱熹还从其他史书中吸收“直笔”之写法。例如《后汉书》中对于曹操而书“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朱熹就很称许,他对于《通鉴》中的“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的“封”字很不以为然,并在《纲目》凡例之“篡贼”条目中写道:“至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得其政,迁官,建国,皆依范史,直以自为自立书之。”福谷对此评论道:“《纲目》中的‘曹操自立’之记述,与其说是朱熹以自己的意图对《通鉴》进行笔削,不如说是《通鉴》对《后汉书》的记述进行了不恰当的修改,而朱熹又重新还原到范晔《后汉书》原先的记述中去。从先前所述的朱子春秋学的立场来讲,不是通过一字之褒贬来进行笔削,而是以尊重旧史之记述与旧例的立场出发,直书事实。”(第77页)同样,《纲目》中有名的“蜀汉正统论”等等也都出现在“凡例”中,福谷认为,这并不是朱熹本人下褒贬之意,而只是参取“史法之善者”。
由于《纲目》的题材性质,加之非朱熹本人所作之说由来已久,《纲目》很少受到思想史研究者的关注,因此笔者花了很大篇幅介绍此文。一方面,福谷对于先行研究之整理以及分梳都很清晰,值得参看;另一方面,朱熹所称许的“直笔”与“朱熹所否定之义例是指变例”这两点也得到初步澄清。但是,笔者依然想指出:在朱熹看来,孔子直书史实,是有“言外之意”和“毁誉褒贬”的,只是不像后世今文经学那样认定个别字眼之变动或者“不书”都有圣人之“微言大义”(在朱熹看来如果真是那样圣人就有“私意”)。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朱熹这样说是建立在其天理人伦观千古不变的普遍性框架下的,换句话说,孔子当时以父子君臣之人伦为“正”,而千百年之后的人们依然会认为父子君臣为天经地义,因此朱熹才有信心说圣人是“付诸后世公论”,因为“公论”千百年不变。其次,朱熹自己编订《纲目》之“凡例”,但此“凡例”中却充满了种种朱子学的价值判断,不管是君臣之义还是蜀汉正统论。如果“凡例”不包含价值判断,朱熹何以能判断过去的史书之书法中何为“善”何为“不善”?正是因为朱熹自认为自己的价值理念是万世不变的前提下,他才能批评《纲目》对扬雄(不书“死”而书“卒”)以及曹操(不书“自立”而书“封”)之姑息,这背后所隐藏的是非常强烈的君臣名分论。我们可以说,从朱熹自身的立场来看,“直笔”之书法与“凡例”之建立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在朱熹的世界观中,“事实”与“价值”永远是不可分割且永恒不变的,所以直书“事实”即可以说“无私意”,又可以说是蕴含着自明之“褒贬”。但如果并非朱子学的信徒,那么“直笔”与“义例说”之矛盾就无法消解,或者更准确地说,朱熹所说的“直笔”只对接受朱子学理念的人而言才成立。对此问题,福谷其实是有所意识的,因此他才在文章最后写道:“在今人看来,《纲目》之‘凡例’,在内容上是以伦理之观点对史实进行笔法上的区分而作,在史实中掺入伦理评价的倾向非常明显……这样的‘凡例’之恣意性,反而让我们想起了微言大义。”(第78—79页)
中纯夫[251《本末格物说考》(《日本中国学会报》第62集,2010年)。从朱熹作《大学》补传开始,对于《大学》的“格物”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就一直是聚讼不止的话题,以至于在明代出现了黄宗羲所谓七十二家“格物”说的程度。中纯夫在该文中对宋明时期的“格物”说进行了系统的整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对于《礼记·大学篇》的“格物”应该如何解释,历来是众说纷纭。代表性的无疑是朱熹的训“格”为“至”,训“物”为“事”,而王阳明则以“格”为“正”,“物”为“意之所在”,除此之外,王心斋以大学本文的“物有本末”训“物”的所谓“淮南格物说”非常有名(但事实上在王心斋之前就有人如此解释,朝鲜儒学也是),中纯夫即对明末的“本末格物说”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并分出“以格物为本”(王柏),“以致知为本”(冯从吾),“以诚意为本”(黎立武、袁俊翁、罗汝芳、刘宗周、毛奇龄、汤斌、朱鹤龄),“以修身为本”(王艮、蒋信、王栋、耿定向、章潢、姚舜牧、李颙)四大类。中纯夫指出,本末格物说之意义首先就在于将“八条目”视为本末终始之次序,在此情形下,将“格物”视为“本”并不符合逻辑,“致知”的情形也是一样,因此只有王柏和冯从吾分别以“格物”和“致知”为本,是毫不奇怪的,而“诚意为本”和“修身为本”在逻辑上都能说通。另外,《大学》之文本在明代的主流至少有:①《大学章句》,②《大学》古本,③(伪)石经《大学》三种。从理论上说三种版本都能得出本末格物说之结论,但在依据《大学章句》的情况下,与朱熹的传第五章之格物解释必然会产生冲突,而事实表明也是如此,不过,对于即物穷理之说,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即便否定朱熹的经书解释,也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工夫论;相对而言,阳明学出现之后的十四例中,十一例对良知说采取肯定之立场。
关于朱熹本人的思想史研究就介绍到这里。事实上,就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内地朱子学研究这几年已经开始逐渐拓宽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于朱子后学的几个重要门人弟子的相关研究——黄榦、陈淳、真德秀,已经获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反观日本方面,由于一方面中国思想史研究队伍后继乏力,而一线研究者则纷纷将目光转向日本或者韩国朱子学,而在大环境下,近几年中日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对立日趋激化,导致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抱有负面印象,中国的古典就更很少有人问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江户时代,尤其是中后期,由于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需要,朱子学在日本有逐渐普及化的趋势,因此无论对朱子学抱有多么负面的评价,对朱子学本身的界定几乎都可以说是理解日本“近代化”的一个关键点。正因为如此,对于朱熹本人,事实上一般的人文学者还可能会有一定的关注,但是朱熹之后的朱子后学,与日本的“近代化”问题几乎没有关系,那么朱子后学之研究被冷落,从以上笔者归纳的三点来看,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以上论述只是一个宏观性的把握。姑且不论质量,单从论文的数量来看,对黄榦的研究远远少于陈淳和真德秀。何以如此?以笔者之管见,陈淳对朱子学的基本概念进行整理与解释而作的《北溪字义》,很早就传到江户时代的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朱子学的理解,从江户时代直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此书。原因很简单,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固然是经典,但毕竟是朱熹对传统儒学之诠释,要理解与把握朱熹本人思想,那就必须阅读数量庞大的《文集》书信以及《朱子语类》,这对于江户时代的人而言几乎不可能,而在今天,能够不借助江户训读法直接阅读朱熹原著的日本学者,尤其是日本思想史研究者越来越少,相对而言,陈淳的《北溪字义》简直就是一本“朱子学入门字典”,姑且不论陈淳本人的思想与晚年朱熹是否存在偏差(至少笔者认为是存在的),陈淳本人在朱熹门下之地位以及其实力,都确实使得《北溪字义》成为朱子学入门的基本参考书目,因此不难理解,尤其是日本近世思想史学者对于《北溪字义》的熟悉程度很可能要高于朱熹本人。那么,真德秀又何以相对受到关注?事实上,检索真德秀的相关研究就会发现,有好几位研究者撰写过与真德秀宗教思想以及政策相关的论文。因为笔者去年也曾撰写过真德秀的论文,在此即以真德秀为例进行介绍。
就思想史而言,从明代开始的儒学内部对真德秀的评价不高,此不需多说。但值得注意的是,真德秀一方面留下了总计400余篇“青词”、“疏语”、“祝文”[26]。事实上,小岛毅早在1991年发表的《牧民管之祈祷——真德秀的场合》[27]一文中,就针对通常不为“思想研究”所重视的卷四十八至五十四所收录的“青词”、“疏语”、“祝文”进行了分析与整理。该文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真德秀“为民祈祷”的理念以及祠庙拜谒、祷告所牵涉的正统性问题,对于卷四十八、四十九的道教“青词”并没有详细地展开。在此之后,松本浩一对真德秀的祝文、青词等进行了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小岛毅论文的补充[28]。但该文仍然延续了“儒家正统与道教思想、民间信仰”的视角。松本浩一还列举了同时代的魏了翁、黄震以及陈淳等儒家对于民间道教的看法,由此指出:在当时已经无法完全扭转民间对佛教、道教信仰的情况下,像真德秀那样对于佛道进行统摄与吸收的做法可能是明智之举。
另外,前川亨[29]《真徳秀の政治思想——史弥遠政権期における朱子学の一動向》(《真德秀的政治思想——史弥远政权期的朱子学之动向》)(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第5号,1994年,第65—84页)一文,结合南宋政治来探讨真德秀的宗教政策,很具有参考价值。众所周知,朱熹在死前被韩侂胄政权打为“伪学”,但随后打倒韩氏而掌权的史弥远(1164—1233),却积极为朱子学平反并争取拉拢朱子学士人,在短短30年间,朱子学完成了“反体制”到“体制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在此期间出入政坛的朱子学者,正是私淑朱熹的真德秀。但是,真德秀本人无论在思想以及为人方面都颇受后儒之诟病,不管是全祖望还是四库馆臣都认为真德秀沉溺于佛老之学而“不纯”。前川并没有直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真德秀学问之“不纯”,而是从朝廷宗教政策出发,得出了史弥远与真德秀在立场上极其相近的惊人结论。何以说“惊人”?大凡治宋史者都知道,史弥远在史书上被刻画为玩弄权术的权相,并且宝庆元年(1225)真德秀与魏了翁之落官也是史氏党徒之所为,但就此认为史弥远是反朱子学者,则未免过于轻信偏袒朱子学的史官之记载。前川列举了史弥远与朱子学之间存在某种政治协调关系的理由:其一,史弥远推翻反朱子学的韩侂胄政权,那么反过来说史氏与朱子学在反韩氏这点上就有亲和性;其二,史弥远拥立宋理宗上台,其中的核心人物是郑清之,郑氏与朱子学之亲和关系能为史氏搭桥;其三,史弥远上台正值南宋败于金朝、人心惶惶不安之时,在以政权稳定和维持秩序为紧要课题的情况下,不管是朱子学还是其他宗教,凡是能够加以利用的史弥远都必须利用。反过来就朱子学的立场来看,朱子学派急需摆脱“伪学”的帽子而站稳脚跟,因而前川认为,史弥远政权与朱子学虽然表面对立,实则两者政治利益存在一致性,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朱子学能够很快返回政治舞台而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
前川以宗教政策为例试图证明其观点:佛教政策方面,嘉定年间(1208—1224)史弥远确立了五山制度,例如禅宗寺院之住持等任命权均操纵在史弥远的手上,国家对佛教之干涉达到顶峰,也同时标志着世俗权力对宗教的全面压制。而在五山制度确立后不久,真德秀就为径山之住持撰写文章:“师,名妙崧……道价为当世第一”[30],真德秀之用意可见一斑。真德秀本人的佛教观如何?在文集卷二十九的《送高上人序》中,真德秀开篇即自问:“道一而已,乃有儒释氏之不同,何哉?”并答以佛教离弃人伦,故不可取。但接下来笔锋一转,当真德秀听到高上人(未详)年幼时家贫而不得葬双亲,去年回到三山后行葬礼、甚至还在墓地之附近建“思亲”之精舍,便大加赞赏。前川分析道:“不犯破坏世俗人伦秩序之谬误,反而拥护此秩序,这是认可佛教的必要条件。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在具备此条件的情况下,佛教也因此而能在体制内确保自己的地位。”(第71页)在此情形下,就不存在佛教与儒教之不同,正所谓“道一而已”,而这样的话,不管是二程还是朱熹都绝不会说,我们只要想起《中庸章句序》中著名的“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就可以了。如果说上述对佛教的认可尚属于消极层面,那么例如文集卷三十五的《敕封慧应大师后记》中,真德秀提及嘉定十五年(1122)、很多地方出现疫情,净空禅师现身做祷告,“风雨旋至,瑞雪继之”,并评论道:“昔者,帝王受命,显穹为神人主……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对此,前川认为,施行仁政而安民,是世俗世界之官僚的职责,但这毕竟是“人治”,例如疫情以及自然灾害等等,则超出了“人治”之范围,而宗教领域的佛教之神力正能够辅佐人治之不足,所以真德秀才说“幽明虽殊,其为劝奖,一也”,“人治=儒教=明”与“人治所弗及=佛教=幽”,如此而形成政治支配之稳定性。那么,真德秀对于佛教的立场,显然与史弥远相近,即“利用(着重号为前川所加)佛教的咒术之力,以巩固政治支配”(第73页)。道教方面,真德秀自己更积极地设醮祷告,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学者论及,就不再重复了,其着眼点也同样在于利用道教仪式来补充世俗政权之不足。在文章末尾,前川预想了两种对其观点的反驳,在这里仅介绍第二点,即对于朱熹去世之后的朱子学之发展,前川是否过高评价了真德秀的作用?事实上,真德秀在中央政权并没有多大作为,其功绩如下文要介绍的小林义广所说,更多地体现在作为“父母官”的地方行政上。因此,真德秀与之后取得国教地位的元代朱子学很难说有直接关联。但前川认为,真德秀作为朱子学之范式,其意义重大。在元代,以“咒术之园”的喇嘛教为代表,很多宗教都被蒙古统治者“宽容”地接受,在之后日益明显的“超越三教之别的中国式万神殿”、“宗教界的中国式正统”之过程,与作为政治支配护航的意识形态而确立自身地位的朱子学,恰恰可以看作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一点从史弥远时期的宗教动向以及真德秀的政治思想探讨中就能够看出端倪(第80页)。
前川的上述论证颇具冲击力,尤其是其一方面关注宗教政策与政治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又紧密结合朱子学的发展状况与定位,其视野之广阔与敏锐很值得借鉴。不过,笔者在这里有两点小小的疑问,仅供参考:其一,朱熹本人是否如前川所说,是“反体制”的?这个问题与前些年争议很大的朱熹皇权论有类似之处——朱熹究竟是主张伸张“士权”、抑制皇权,使皇权仅具备象征意义(就像日本近代史著名的美农部达吉“天皇机关说”),还是作为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支持皇权?其二,笔者在《从“上帝”到“万神殿”——以真德秀之青词祷告为例》一文中曾指出,不管是小岛毅还是松本浩一,均强调真德秀是站在“牧民官”之立场而“为民祈祷”,这种理解的潜在前提可能是“神道设教”。事实上,前川亨在分析与比较真德秀与权相史弥远的宗教政策之相似性的论文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理解。但是,即便不参照《文集》、《大学衍义》等其他文本,就卷四十八、四十九两卷而言,真德秀留下了十篇“生日设醮青词”以及九篇为母亲祷告的青词,这些青词显然不属于“为民祷告”之范畴,如果真德秀本人并不相信道教之诸神以及斋醮祷告之有效性,他为什么还通过这种形式来为自己以及家人祈祷,便完全成为不可解[31]。
小林义广《宋代地方官と民衆——真徳秀を中心として》(《宋代地方官与民众——以真德秀为中心》)(《研究论集》第10集,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12年12月,第89—106页)。小林是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历史学博士,现任东海大学文学部教授,他是日本正统的东洋史研究专家,主要方向是宋代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族、地域研究[32]。所谓“谕俗文”,众所周知就是与民众直接接触机会较多的地方官员为了教化民众而撰写并公开布告的文章,就现有文献而言,宋代的“谕俗文”只有20余篇,但如果不拘泥于形式而关注内容的话,例如振兴农业的“劝农文”在宋代很常见,而地方官为了排除农业生产活动的负面因素,大多还会关注民众的生活方式,这当中就包含了教化的成分,其他例如“劝学文”、“劝孝文”、“晓谕词讼文”、“劝谕救荒文”等多种形式,其实都可以看作是“谕俗文”的变体。其次,在宋代,谕俗文最初的撰写者是北宋的陈襄(1017—1080),他在皇祐年间(1049—1053)作为台州仙居县知事而作了“劝谕文”,此举得到了朱熹的赏识。而私淑朱熹的真德秀,也在自己的谕告文中提道:“昔密学陈公襄为仙居宰,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其次来看谕俗文的内容,既然是教化民众,前提当然是民风与儒家道德不相合。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地方官大多在布告中提到民间诉讼相争的问题。在宋代,即便是同一族内部,贫富差距也急剧扩大,围绕财产等事情,骨肉之亲都会不惜对簿公堂。再来看真德秀,在《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中,共收录了“潭州谕俗文”、“再守泉州劝孝文”、“福州谕俗文”三篇,从内容上看,基本方向都是教导民众团结和睦、孝敬亲长,其中两篇都提到了“健讼”的问题,宋代社会之风气由此可见。其次,从谕俗文中能看出当地的一些特色,例如二度上任泉州的“泉州劝孝文”中,提到追荐供养之不必要性,其背景就是泉州当时佛教盛行,因此布施僧尼以及供养很流行,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庶榜”等文中得到佐证。再次,真德秀作为地方官,其谕告文中的两篇都被收录在明刻本《明公书判清明集》的卷首,可见其模范效应,那么真德秀的施政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在小林看来,主要还在于作为朱子学者,真德秀身体力行朱熹的“诚”说,自己在上任时以身作则,并且相信一旦地方官员有诚意,那么民众也必定会受到感化,遵从官员之教化。小林认为,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明真德秀相信“民众并非单方面的是被统治者,而是具有主体之自觉来看待地方官之行政”(第102页)。对此,笔者认为可能需要更全面地考察真德秀的思想,尤其是尊王论来进行综合判断,在此就不细说了。最后,小林提到,在传统社会,一般民众的识字率很低,因此官员要传达自己的教化,光靠到处张贴布告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无论是从各种历史文献,还是真德秀的谕俗文中,我们都能看到“父老”、亦即有教养与学识的士人以及年长者的身影,有了“父老”之配合,儒家所主张的“风教”才可能顺利传达到一般民众中去。通观全文,小林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东洋史研究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在论述中紧密结合真德秀的事例来进行分析,并准确地把握真德秀与其他宋代地方官之“同”与“异”,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以上就日本2013年的朱子学研究做了简单介绍与评价,并对于若干主题进行了回溯性的介绍与分析。由于笔者之学识限制,难免挂一漏万,敬请谅解为感。
(作者单位: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
但是,如果仅因近期日本朱子学研究的青黄不接,就以为可以绕过日本的相关研究,那可能是得不偿失的。笔者在去年的述评中曾指出,日本有近百年的汉学研究之传统,在学风上大多务求严谨扎实,在对某课题进行研究时,一方面会尽可能搜集相关先行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论证时基本都以材料为依据,不喜浮夸之谈,这就是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实证主义精神,这当中有相当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学习与借鉴。
由于从数量来说,2013年日本学者的朱子学研究成果非常有限,因此本文在介绍的范围上与去年的述评相比又有所扩大:其一,与去年一样,笔者会将单篇论文列入介绍范围;其二,对去年述评中遗漏的重要研究进行补充介绍;其三,在介绍中,对若干相关主题进行简要的回溯性介绍(此次述评中重点介绍朱熹的鬼神观以及与真德秀相关的研究)。
据笔者所知,2013年在日本出版的朱子学专著只有木下铁矢的《朱子学》(讲谈社,2013年)一本,因此本文不再区分论著和论文。此书属于讲谈社出版的一系列古典普及型研究,因此与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著作在定位上略有不同。该书可以说是木下对近十多年来自己研究之汇总,但因为要顾及一般读者,无论是论证还是引用材料上都会受到限制,因此在这里,笔者想向国内同仁介绍一下木下先前的研究成果。木下原来研究清朝考据学,后转为专攻朱子学,1999年出版的《朱熹再読——朱子学理解への一序說》(研文出版),可以说是其力作,木下在书中提出了诸多崭新而敏锐的观点,很值得仔细研究。对此,石立善在述评中也有介绍,就不再重复了。之后,木下继续从事朱熹思想研究,并将2000年至2007年的九篇相关论文汇集成新著《朱熹哲学の視軸——続朱熹再読》[2]。
在这里仅以《续朱熹再读》的第一章《朱熹の思索、その面差しと可能性》(《朱熹之思索,其面相及其可能性》)为例进行介绍。通常人们都把朱熹理解为所谓“二元论者”,即理气、阴阳、已发未发等二项对立之思维,然而在木下看来,朱熹本人毋宁说是力图打破这些二元之对立的,这体现在朱熹对“心”的理解上:
“心则通贯已发、未发之间,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动一静之全体也”(《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心是与性相独立、性之具在的‘场所’,并且是时时变换的独特之‘场’”,与此同时,“心”和“太极”都是“无对”之存在,朱熹将其特征描述为“妙”字(“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木下通过对“神”、“妙”以及“机”之分析,指出“使阴阳之相互转换得以进行的运转之机关(switching),此转换运转之作用便是太极”(第17页),所谓“作用”,木下用“事件存在”来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物件存在”。何谓“事件存在”?例如朱熹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解释是:“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矣。”不说“仁者之心,以己及人”,正是排除日常思维的先有某物件、然后对此物件进行描述的方式,而倒转过来是以事件性的“以己及人”为先,此事件才能与“天理之周流而无间”相联系。同样的,通常我们理解宋明儒学之“万物一体”论是建立在形而上学式的“人物均受天地之气(理)而生”的基础上,但是朱熹曾明确否认此说法:“不须问他从初时,只今便是一体……他那物事自是爱,这个是说那无所不爱了,方能得同体。若爱,则是自然爱,不是同体了方爱。”[3]对他者乃至万物之爱是自然生起的“事件”,先在于“彼此是否同体”的理论性思维。木下在这篇文章中反复强调的是什么?是朱熹在努力克服所谓常识性的思维(实体化,二元对立等等),或者毋宁说,木下所看到的朱熹的形象,在很大意义上是木下自己的思索之深刻性的折射——对于先有某物后有某事的(主语与述语的语言之惯性与主语先在性的捏造,这至少可以上溯到尼采对康德的批判)思维惰性的批判,以及对“事件”、“此时此刻”之强调,不难让我们联想到诸如Whitehead等西方哲学家破除实体化思维的努力。
另外,木下还有一篇论文《“仁義礼智信”力か“仁義礼智”か——現在の朱子学理解を問う》(《“仁义礼智信”还是“仁义礼智”?——对当今朱子学理解之疑问》),收录在《吉田公平教授退休纪念论集》(研文出版,2013年)一书中。事实上,在去年日本有好几个并非研究朱子学的老师以及同学都问笔者是否看过此文,何以该文会受到如此关注?木下近几年来一贯地批判岛田虔次[4]的朱子学理解,在木下看来,由于岛田式解读的重大偏差,时至今日,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对朱熹都普遍存在严重的误读。就朱子学而言,最核心的概念无疑是“性”与“理”,朱熹继承二程之观点,主张“性即理”,而对于“理”,在后文还会提到,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存在很多种解释,但就“性即理”这一命题而言,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偏向于从“本质”(essence)上去进行理解,木下在第一节就举了日本朱子研究的代表人物吾妻重二的说法:“就人而言,人存在之理是‘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据,是仁与动物或者植物相区别开的本质(存在规定)。”[5]这个说明比较简略,接下来木下以日本思想史研究者渡边浩(渡边是丸山真男的直系弟子)为例,依照渡边之理解,“理”能判定某个体究竟属于“人”还是“桃子”或者“椅子”等类别,并且是此各个类别之特定的“应有之存在方式”(在るべき在り方),这显然与吾妻所说的“本质(存在规定)”同出一辙——桃子是桃子,是因为桃子所应有的存在方式、亦即是“理”之内在性。木下认为,这种“本质”论属于经院哲学所讨论的“本质存在”(essentia)与“事实存在”(exsistentia)之范畴中的“本质存在”:本质存在是“某物是什么”、亦即是说面前某物究竟是桌子还是椅子,而事实存在说的是某物是否实际存在,例如面前是否有一张桌子。那么,朱熹所说的“理”就成为区分“人”与其他类别的“本质”所在。但是,木下仅举了一例,就动摇了上述看似理所当然的解释:在《孟子·离娄下》中,朱熹如此解释孟子的“人之所以异乎禽兽者几希”: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无少异耳。[6]
朱熹明确指出:人与物同得“天地之理”,理无所谓完全不完全,区别就在于人与物得到“天地之气”是不同的,人能得“形气之正”,故能“全其性”而已。接下来木下还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与分析岛田等先行研究的问题所在,而在笔者看来,关于“理”是否是人之本质规定这一点,在朱熹本身的文脉中,其实就是“理同气异”论,而二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云:“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人与物,但气有偏正耳。”[71朱熹的“气有偏正”说显然源于二程。用“气”来解释人与其他生物之不同固然可行,但朱熹仍然需要解释:同样作为“人”,人与人之间何以存在着先天或者后天的巨大差距?木下引用了岛田的说法,岛田认为:“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五常”(仁义礼智信),既然万物之基本组成都是“五行”,那么五行之间的比例差异就决定了即便同样是“人”,如果“木气”盛则性格偏于“仁”,“火气”盛则偏向“礼”。由此,木下认为,岛田依然是在主张“理”之本质主义论。但公允地说,在原文中岛田并没有说此处之“仁”即是“理”,而毋宁可能是说:“仁”等“五常”之德在现实世界中所展现出来的程度,是由“气”,亦即“五行”所决定的,因此这依然可以说是“理同气异”论。包括朱熹有时候说“理有偏全”,这依然是在后天“理”被“气”遮蔽而产生的差异,从“理一分殊”的角度来说,人与其他万物之间的“理”不可能是“异”。岛田将“理”解释为“仁义礼智信”,并不妨碍他以及学界主流的“本质=存在规定”之理解。在之后,木下还针对岛田之说法,提出“性=理”的内容究竟是“五常=仁义礼智信”还是“仁义礼智”的问题,并依据朱熹文献的检索结果以及理论分析,论证了晚年朱熹是站在“仁义礼智”一边理解“性=理”的立场。但如果岛田并不是以“理异”来把握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话,那么“是四德还是五常”的讨论相对于“存在规定”说之批判而言,可能并不那么重要。
事实上,不管是吾妻、渡边,还是被木下视为此理解之发端者的岛田,都没有明确表示自己所主张的所谓“本质”、“存在规定”之说法源于经院哲学(在笔者看来更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我们在生活中有太多习焉而不察的词汇,不管是“本质”、
“内在”,还是“形而上学”,尽管在这个时代,“形而上学”已经偏于贬义,而大多数日本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也对西方哲学以及理论不感冒,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汇时能够避免其背后长达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背景。木下是当今日本极少数中国思想史研究出身而又具有一定西哲素养的学者,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一再发现诸如上述之问题所在。
同样收录在《吉田公平教授退休纪念论集》中的朱子学研究还有一篇:牛尾弘孝《朱熹の鬼神論の構造——生者と死者をつなぐ領域》(以下简称《构造》)。关于牛尾,去年的年鉴中有介绍,请读者参看之。牛尾在《中国哲学论集》第36号的《書評吾妻重二著『朱子学の新研究』》[8]一文中,曾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绍日本学者对朱熹的鬼神观研究,而《构造》一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书评之延续,因此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鬼神观问题在日本方面的先行研究状况。朱熹上承张载与二程之思想,以气之屈伸往来为鬼神,而市川安司早在《朱子哲学论考》一书中就已经指出:张载持“气之循环”论,气虽然有消长,但总量不变,而程颐主张“气”是“生生”,产生新“气”的根源为“真元”,朱熹则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之后的土田健次郎以及三浦国雄的观点也基本相同。市来津由彦则进一步指出:朱熹“在继承程颐之气说的同时,新之气生生不息,补充了减少的成分,因而从总量上看天地间之气没有增减,如此便对张载的气化宇宙论和程颐的气说之间进行了调停”[9]。牛尾还提到,关于程颐的“真元之气”说,友枝龙太郎解释为“生命体之根源”,而山田庆儿以及土田健次郎则认为应当与道教有关,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具体的说明,因此还有进一步检讨的余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朱熹认为气并非循环而是会趋向消亡,那么在祭祀鬼神尤其是自己的祖先时,所谓“祖考来格”便不可理解,这一点后藤俊瑞早在1937年就已经指出[10],战后居于学术统治地位的岛田也认为这是朱子学理论的自我矛盾[11]。但在此后,又有不少学者站出来为朱熹辩护,因而有所谓“破绽说”之争论。在这里不可能一一罗列,仅举两人为例。柴田笃在《陰陽の霊としての鬼神——朱子鬼神魂魄論への序章》(《作为阴阳之灵的鬼神——朱子鬼神魂魄论序章》)一文中,并不像某些学者那样以存在论、工夫论等区分来为朱熹辩护,而是以关键词“灵”出发,他指出:“灵这个字是对如下之事实的表达——作为存在原理之天理而内在于万物生成要素的气当中。”就人而言,就是“心”:“心本体因为保有理,换句话说与理合一,因而具有能够认识与知觉事物之理的机能。这被称为心之虚灵。”那么鬼神魂魄也同样具备“理气妙合”之性质,因而祭祀时候的“感格”正体现出魂魄理气妙合之灵妙性[12]。市来津由彦则指出,光从“气”是“聚散”还是“消亡”的角度来思考是不够的,他建议从“理”的角度进行理解:从存在论上看,气之生成与聚散说到底都依据“理”,人之存在本身就是理气一体,这一点和柴田的观点不谋而合;从实践的角度看,如果应当祭祀,就应当去祭祀,特别是在祭祀之时,通过尽自己之诚敬而达到心灵之纯化,“就祭祀本身而言,由祈祷而使得鬼神来格,所追求的是祭祀者引发此感格……这种由祈祷而来的心灵之纯化,就在朱熹以及其门人的主观之中得到保存”。
在介绍完上述研究成果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牛尾的《构造》一文。朱熹以气之屈伸往来解释鬼神,但事实上此处说的鬼神是泛指意义,即天地间周流不息之气,就人而言则是魂魄。如果“昼”为“神”,“夜”为“鬼”,那么生者就是“神”,死者就是“鬼”,但是生者也有“鬼”,其屈伸消长是渐变的,因此可以画出一幅类似于物理学上的沙漏轨迹图。其次,牛尾以文集卷四十五《答廖子晦》第二书为例:
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气而已矣……但有是理,则有是气……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皆非性之谓也。故祭祀之礼,以类而感,以类而应。若性则又岂有类之可言哉。然气之已散者,既化而无有,其根于理而日生者,则固浩然而无穷(下划线为笔者所加)。故上蔡谓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盖谓此也。[13]
对于“其根于理而日生者”一句,牛尾问道:此“理”是何“理”?“生”又是何意?一般作为中国人,既然是自己的母语,尤其对像“生”这样的词,不会有太大的警觉,但是作为日本汉学的传统,采用江户训读法进行训读是基本功课,而在训读之时,对于一个字应该怎样训读,其实就直接牵涉对此字乃至整个句子的理解。就“生”而言,牛尾列举了几种先行研究的训读法:荒木见悟的翻译是“以理为依据,每天都(继续)活着(日々生き(続け)てい、るもの)”,这种解读应该是考虑到了后文“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的说法。而市来津由彦则直接训读为“根于理而日日生者(生じる者)”,其分析是“像生生之气那样,连续不断被生出的东西,这从天地运作之普遍性视角来看,果然还是归结为理”。比较有趣的是,近几年来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的部分学者开始强调通过“东亚儒学”之视角来重新探讨儒学以及儒学思想史,即便不直接接受此主张,不少学者也陆续把目光转向日本或者韩国的儒学,期待从中发掘出新的东西。无独有偶,牛尾在文章中提到了日本朱子学派的代表人物山崎暗斋(1618—1682)的晚年弟子三宅尚斋(1662—1741)所撰写的《祭祀来格说》,该书只有短短的八页,但内容上正好是关于祭祀之礼的鬼神来格与三宅自己的个人体验:
不灭之理,藏于不绝之气。以不灭之理,求之于不绝之气,则不绝之气,根于所藏之理,模写于所求之理而出来。洋洋仿佛,见前日事,见前年祖考。气之根于理而生,随感而见者,如此矣。[14]
事实上,土田健次郎早在1996年就已经注意到了该文,并评论道:“祖先之精神(灵妙之作用)根于天地之精神而生生不穷,这里的强调点与其说是气,不如说是理。”[15]笔者对三宅尚斋没有研究,但就此段文字而言,如果能点明“不绝之气”之所以“不绝”或者“生生”,正是因为“天地生生之大德=理”的话会更好。牛尾很欣赏三宅的上述理解,并指出,三宅并不是想暗示“理”真的能生“气”。由于“理”能乘于“气”,因此“气”之生生不穷,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也能说是“理”之流行。
刚从东洋大学退休的阳明学研究者吉田公平教授在2012年出版了《中国近世の心学思想》(研文出版),当中有若干篇论文与朱熹相关,但因为时间关系,笔者未能在去年的年鉴截稿日期前看到此书,因此在本次论文中进行简要的补充介绍:此书是吉田公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到最近的论文合集,在内容上自然以阳明学以及相关研究为主。东洋大学是日本唯一一所以哲学为主要学科的大学(其创始人为日本著名思想家井上圆了)[16],以吉田公平为首的中国哲学教研室均秉承大学的优良传统,一方面积极学习和吸收西方哲学与思想,另一方面有很强的现实关怀,这两点在日本其他中国思想研究基地以及学者身上是很难看到的。吉田公平此书以“心学”为题,但此“心学”不是泛泛之意义的心学,而是建立在两大前提上。其一,依照其老师荒木见悟在《仏教と儒教》中提出的著名理念、即“本来性”与“现实性”:人之为人的本性是“性”或者佛教说的“佛性”,此是“本来具有”而完全自足;其二,虽然人的现实状态会有所欠缺,但是不需要通过外力,而通过自己之努力“悟”得本来完全之性。在吉田公平看来,既然近代是“上帝已死”的世俗化社会,则宋明儒学的“自立本愿”之精神恰恰能发挥作用。由于各篇论文主题不一,在此无法一一介绍,但是例如《告子について》一文,对于宋明儒学中历来被作为“异端”的告子,非常冷静地剖析了其与孟子的论辩,指出孟子的诘难均存在逻辑上的跳跃,并不足以驳倒告子,而朱熹则先入为主地以孟子之见为“正统”,完全无视告子之人性论的意义所在。另外,例如对于《大学》的“新民”与“亲民”之辨,朱熹注重圣贤对民众之教化而取“新民”之意,但是如此一来,“占绝对多数的民众必须通过他者之救济,如此不免使得性善说与自力主义有所褪色……民众结果只是教化之对象,而无法成为人伦上的自觉之创造者”,而王阳明使用“亲民”,则强调“他者虽是助缘,从究竟上来说还是需要人之自力,而此力量本来就是人人本来固有的”[1刀。对以上之评判是否公允,在此不赘,但是很显然,对于研究对象并不仅仅抱着客观实证之态度,而积极反思其思想与实践之意义以及问题所在,吉田公平的上述学问之姿态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的。
接下来介绍单篇论文。辻井义辉《朱熹哲学における感応と理》(《朱熹哲学中的“感应”与“理”》)(东洋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纪要第21号,2013年,第219—244页),去年的年鉴中对辻井及其论文有简单介绍,请读者参看之,在此不赘。该文研究的对象是老生常谈的朱子学之“理”,在简单介绍了日本学界的若干种解释(楠本正继:“生成世界的主宰之根本因”;安田二郎:“意味”;岛田虔次:“宇宙、万物之根据,宇宙之应有的原理,就个体而言是个体之所以成此个体的原理”)之后,辻井特别推崇木下铁矢的看法,木下将“理”理解为“元→亨→利→贞”之顺次展开旋律(Rhythm)、将“性”理解为“活动程式(Program)”,辻井此文即以“阴阳”为线索来证成木下之理解。首先,朱熹认为,天下之物都是“有阴有阳”、“有动有静”,阴阳之间既相互转化,也相互抗争,是极具动态的。那么,何以阴阳会如此运作?那自然是因为有“阴阳之理”。但是,辻井引用了两则材料,试图证明“阴阳之运作是由于理是主体”(第227页),却颇有问题。两则都出自《朱子语类》:
动则此理行,此动中之太极也。静则此理存,此静中之太极也。[18]
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19]
我们知道,中文“则”字有多重含义,而“动则此理行”的“A则B”结构,显然属于承接关系,像《论语·为政篇》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如此。A与B未必就是因果关系,但A在时间上不可能晚于B。如果“理”是“主体”,何以作为“客体”(既然辻井认为理是主体,那么动静当然就被认定为是客体)的“动静”会先行或者至少不在“理”之后?要确切理解这两句话,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看。“理”是否是某种实体性的存在?回答显然是“否”,朱熹明确否定“理”或者“太极”是“一物”。如果不是,那么说“理”是“主体”是什么意思?辻井在同文第232页上以“动静者,所承之机”为例,认为如同人骑在马上一样,“理”乘于“气”,那么“动作之主便是理”、“绝非没有意义地单纯搭乘在上面,而毋宁说是操纵”。问题在于,朱熹此比喻虽然有名,但本身却存在问题:“理”与“气”并不处在同一层面上,本不能以“人”、“马”这样两种相对待之物来进行理解。如果说“理”是“操纵”气,那么何以朱熹不说“人欲一出一入,马亦与之一出一入”,而要倒过来说“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理”本身不可言“动静”,更不可言“主体”,否则朱熹就不会为“气”偏离“理”之问题而苦恼了。
既然理不是“一物”,那么“动则此理行”,意思就是说“动”则此“理”寓于“动”之中,此即“不相离”之意,而“动”之所以能“动”以及此“动”之运作方式,则依据“理”。
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20]
作为前半部分的结论,辻井认为,阴阳之理,便是使得气能够规律性地自动运转、依据一定之节奏而发生阴阳之运作,是此自动装置的“内在动力因”,这其实是重复了木下的结论,而“动力因”的说法与“主体”是相差很远的。
论文后半部分以“感应”为研究对象,衔接非常紧密。何以见得?盖朱熹曰:“凡在天地间,无非感应之理,造化与人事皆是。且如雨旸,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个旸出来。旸不成只管旸,旸已是应处,又感得雨来。”21]辻井注意到,朱熹强调感格之重要性,以至于像豚鱼这样的无知之物,只要人“至信”,便能“感豚鱼,涉险难,而不可以失其正”[22],并指出:“此‘感’并不只是从外部进行作用,而是能深入到对方的内部而作用,换句话说,是‘唤起’、‘引起’之意味”(第238页),当然,这一点在实践上更重要,儒家主张父慈子孝,父之“慈”能够“感”化子女,而子女由此而唤起自身本有之孝心,与此同时,“‘应’在作为‘应’而作用时,同时也在‘感’对方”(第239页)。诚然如此。用符号标记来看会更清楚一些:
(A应)A感→B应(B感)→A应(A感)→……
但是,木下早在《朱熹再读》一书中就已指出,上述“感应论”模式均以A、B为不同主体为前提,但事实上程颐就提到“‘寂然不动’,万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则只是自内感。不是外面将一件物来感于此也”[23],朱熹在回答弟子对此的提问时说:“物固有自内感者,然亦不专是内感,固有自外感者。所谓‘内感’,如一动一静,一往一来,此只是一物先后自相感。”[241亦即是说,所谓“感应”,有“外感”和“内感”两种。但辻井认为,无论是哪一种,其基本原理都是相互唤起、相互抗争、同时相互转换,此自动装置之所以可能,当然是因为“理”之存在(第243页)。
福谷彬《孔孟一致論の展開と朱子の位置——人性論を中心として》(《孔孟一致论之展开与朱子的地位——以人性论为中心》)(《日本中国学会报》第65集,2013年,第103—118页,以下简称《孔孟》)。福谷彬是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博士,硕士时期就开始研究朱熹,取得了一定成果。研究儒学者动辄称“孔孟之道”,但孔子与孟子之一致性并非理所当然,从汉代开始,出现认为孔子与孟子在根本思想上一致的观点,而福谷认为,此“孔孟一致论”的最终完成是程朱理学。福谷在该文中以“人性论”为切入点,对思想史上的“孔孟一致论”进行了梳理。关键句其实就两句,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而孟子主张“性善”,“人皆可为尧舜”,就字面意思来看,孔子持阶层式人性论,而孟子主张人性向善之普遍性。福谷首先梳理了扬雄、王充、韩愈的孔孟一致论观点,指出他们都以《论语》的阶层式人性论为基础,调停《论语》与《孟子》。到了汉代,董仲舒以爱敬父母之德为“孟子之善”,以遵从三纲五纪为“圣人之善”。而作为唯一现存古注的作者赵岐,对孟子的圣凡一致论则理解为:“圣人亦人也,其相觉者,以心知耳。故体类与人同,故举相似也。”于是圣人与凡人只有形体意义上的相似。这依然是延续了阶层式人性论的观点。到了北宋,王安石推崇孟子,但认为孟子所说之“性”其实是表现在外面的“情”,赞同孔子的性相近论,但是,王安石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下愚”并非“不可移”,而是不愿意努力去“移”,因此从理论上说,“下愚”也存在向上之可能性。到了朱熹的时代,福谷首先整理了道学的谱系,指出张载所提出的“气质之性”与“本然之性”的区分至为关键,由此,孔子所说的“性相近”就是“气质之性”,孟子所言“性善”则是“本然之性”,而“下愚”也只是自己不愿意“移”而已。“同样是孔孟一致论,朱熹认为,既然孟子正确地继承了孔子之思想,那么由孟子之思想完全可以逆推出其由来、亦即孔子之思想,这毋宁是以《孟子》为基准而理解《论语》”(第113页)。当然,福谷也指出,朱熹并没有因此而抬高孟子的地位,他始终强调,孟子之思想来源于孔子,不可言《孟子》胜过《孔子》,与此同时,朱熹还认为,《论语》的记载多切实具体,而《孟子》则多从理论方面着眼,两书各有特色。
在介绍完该文之后,笔者想提出两点疑问。首先,福谷认为“孔孟一致论从汉代开始到宋代逐渐形成,但其内容之变化到目前为止则没有受到关注”(第115页)。但是,孔子与孟子之异同,不知古今有多少大家曾经论及,而人性论上的“性相近,习相远”与“人皆可以为尧舜”命题,几乎是基本中的基本,以思想史(尤其是孟子学)的角度进行整理的先行研究也是不胜枚举。即便其他先行研究没有用“孔孟一致论”的题目进行讨论,但在内容上也多有重复之处。不管是汉代的人性论,还是道学的人性论,福谷所言很难说有超越前人之处。如果将该文界定为总结与梳理之文章(在日本的话,此类文章应当划分为“研究笔记(研究ノ一ト)”,而非“论文”),那么列举相关的先行研究就非常必要,但该文所列参考资料又非常有限。其次,福谷在开篇就以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为阶层式人性论,并以陈述句式说“两书(笔者按,指《论语》和《孟子》)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撇开宋明儒学的“气质之性”、“本然之性”的理解,《论语》和《孟子》的人性论真的有很大差异吗?特别像《论语》那样,经常缺乏前后文语脉的情况下,要断定孔子之原意,在笔者看来几乎不可能。在孔子的时代,对于“性”之讨论还没有展开,他说“性相近”,此“性”究竟是何义?“相近”又是何义?此皆不可晓。但孔子说“相近”,那与主张人性普遍论的孟子就未必有“很大的差异”,并且对孟子的“性善论”的理解,我们也需要注意,孟子并没有天真到认为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都已经是“善”或者是“圣人”了,否则孟子还需要说什么“扩充”的工夫呢?孟子竭力主张的只是人人都有先天向善之可能性,并且在后天之干扰被排除后,就如同水流之就下那样,自然会向善。当然,上述理解只是笔者肤浅的个人见解而已,但至少从行文上来说,如果“孔孟一致”并非理所当然,那么“孔孟并非一致”也不是不言自明的前提。另外,该文以思想史的角度进行人性论的探讨,得出宋代之前“孔孟一致论”的儒家持阶层性人性论的观点,而宋代以后则倾向于普遍性人性论,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向深层挖掘而追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这种变化是否只限于道学的谱系,还是说是儒家整体乃至社会层面对人性论的理解之改观?要回答上述问题,就不是狭隘的思想史研究所能解决了。
福谷彬《r資治通鑑綱目』と朱子の春秋学について——義例説と直書の筆法を中心として》(《〈资治通鉴纲目〉与朱子的春秋学——以“义例说”和“直笔”书法为中心》)(东方学第127辑,2014年2月,第66—82页)。众所周知,朱熹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是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之体例与笔法为准,从大义名分论之立场进行修改的作品,其体例模仿《左传》,“纲”之笔法也多采用“春秋笔法”。但是,朱熹本人一直反对“一字之褒贬”那样的穿凿附会,认为孔子是依据鲁史而“直笔”写成,否定“义例说”,而另一方面,在《纲目》中事实上却存在着大量褒贬的书法,因而例如大名鼎鼎的内藤湖南早就指出其中存在的矛盾,福谷为了解决此矛盾,重新探讨了朱熹的春秋学观点。首先,福谷认为朱熹春秋学的独创性即是“义例说之否定”与“直笔说之提倡”(第67页),但事实上这两点在朱熹之前都早已有人提出,例如唐人啖助就提出“美恶在于事迹,见其文足以知其褒贬”,北宋蜀学的崔子方更明确批判《公羊传》、《穀梁传》的所谓“日月为例”说,此皆为治春秋之常识,不多赘述。福谷指出,朱熹从年轻时候就开始对“义例说”抱有怀疑,在晚年的《书临漳所刊四经后》依然如此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朱子语类》中的一段话: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
何谓“鲁史旧文”?
如晋史书赵盾弑君,齐史书崔杼弑君,鲁却不然,盖恐是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
福谷指出,此说依据的是杜预的“义例说”。在杜预看来,在孔子笔削之前就存在的春秋书法之规定是“凡例”,与之相异的是“变例”,所谓“变例”就是孔子“一字褒贬”之新意。由此可见,朱熹否定的“义例说”是指“变例”,而非“凡例”(第70页)。但问题在于,福谷可能过于夸大了杜预与朱熹之间的差异。杜预虽然看似像今文经学家那样主张孔子通过“不书”、“故书”等解经语来“微显阐幽”,但“正例”与“变例”之外还存在着无例可言的情况:“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因而在今文经学家看来是“例”的很多东西杜预都不承认。
但是,如果一味否认圣人褒贬之义,那么孔子修春秋的意义究竟何在就成了问题。因此朱熹说:“春秋一发首不书即位,即君臣之事也。书仲子嫡庶之分,即夫妇之事也……一开首,人伦便尽在。”朱熹所指的是隐公元年之记事。经文所记录之事件在朱熹看来,都是与人伦相关的教训,因此即便孔子不加一字之褒贬,其内容也已经有所谓“大义”在了。福谷还引用了另一条相关的材料:
当时天下大乱,圣人且据实而书之,其是非得失,付诸后世公论。盖有言外之意。若必于一字一词之间,求褒贬所在,窃恐不然。
福谷指出“朱子一方面否定《春秋》有一字褒贬,主张直书说,另一方面认为其中有‘言外之意’”,并认为这并不矛盾(第72页)。例如《朱子语类》卷五十八中有如下记录:
孔子已自直书在其中。如云:夫人姜氏会齐候于某,公与夫人姜氏会齐候于某……此等显然在目,虽无传亦可晓。
这里牵涉的是鲁桓公与夫人文姜在访问齐国时,齐襄公与文姜奸通,桓公知情却反而被杀,文姜也没有返回鲁国。虽然《左传》有详细记载,但朱熹认为光看经文中反复提及“姜氏”的记载就能够明白事情之缘由。由此,福谷总结道:“通过记录事实,使得毁誉褒贬自见,与此同时,为了明此毁誉褒贬,而通过直书史实的记录者之作为,以上两点即是朱子所认为的‘直笔之笔法’。”(第73页)
在分析完朱熹的春秋观之后,福谷进一步考察了《纲目》之编纂与朱熹春秋学的关联。在初稿完成阶段(1172),朱熹在序文中点题:“因两公四书(笔者按,即司马光的《通鉴》、《通鉴目录》、《通鉴举要历》和胡安国的《通鉴举要补遗》),别为义例,增损隐括,以就此编。”但是,在淳熙六年(1179)《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的《答李滨老书》中,朱熹却说:“通鉴之书,顷尝观考,病其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
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稍加隐括,别为一书而未及就。”此“别为一书”当为《纲目》之“凡例”。对于“凡例”之修订,福谷引用了文集卷三十七《答尤延之书》来证明其与春秋学的关系。按照司马光《通鉴》之旧例(现不可考),事王莽之臣者去世时皆书“死”字,但对于同样侍奉王莽的扬雄,记录却是“是岁,扬雄卒”。对此,朱熹在书信中说:“正以其(笔者按,指扬雄)与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虽异,而其为事莽者则同……所以著万世臣子之戒明。虽无臣贼之心,但畏死贪生,而有其迹,则亦不免于诛绝之罪。此正春秋谨严之法。若温公之变例,则不知何所据依。”在朱熹看来,司马光对王莽之臣书“死”是“直笔”,那么对于同样是王莽之臣属的扬雄就没有理由网开一面。
朱熹还从其他史书中吸收“直笔”之写法。例如《后汉书》中对于曹操而书“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朱熹就很称许,他对于《通鉴》中的“夏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为魏公”的“封”字很不以为然,并在《纲目》凡例之“篡贼”条目中写道:“至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得其政,迁官,建国,皆依范史,直以自为自立书之。”福谷对此评论道:“《纲目》中的‘曹操自立’之记述,与其说是朱熹以自己的意图对《通鉴》进行笔削,不如说是《通鉴》对《后汉书》的记述进行了不恰当的修改,而朱熹又重新还原到范晔《后汉书》原先的记述中去。从先前所述的朱子春秋学的立场来讲,不是通过一字之褒贬来进行笔削,而是以尊重旧史之记述与旧例的立场出发,直书事实。”(第77页)同样,《纲目》中有名的“蜀汉正统论”等等也都出现在“凡例”中,福谷认为,这并不是朱熹本人下褒贬之意,而只是参取“史法之善者”。
由于《纲目》的题材性质,加之非朱熹本人所作之说由来已久,《纲目》很少受到思想史研究者的关注,因此笔者花了很大篇幅介绍此文。一方面,福谷对于先行研究之整理以及分梳都很清晰,值得参看;另一方面,朱熹所称许的“直笔”与“朱熹所否定之义例是指变例”这两点也得到初步澄清。但是,笔者依然想指出:在朱熹看来,孔子直书史实,是有“言外之意”和“毁誉褒贬”的,只是不像后世今文经学那样认定个别字眼之变动或者“不书”都有圣人之“微言大义”(在朱熹看来如果真是那样圣人就有“私意”)。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朱熹这样说是建立在其天理人伦观千古不变的普遍性框架下的,换句话说,孔子当时以父子君臣之人伦为“正”,而千百年之后的人们依然会认为父子君臣为天经地义,因此朱熹才有信心说圣人是“付诸后世公论”,因为“公论”千百年不变。其次,朱熹自己编订《纲目》之“凡例”,但此“凡例”中却充满了种种朱子学的价值判断,不管是君臣之义还是蜀汉正统论。如果“凡例”不包含价值判断,朱熹何以能判断过去的史书之书法中何为“善”何为“不善”?正是因为朱熹自认为自己的价值理念是万世不变的前提下,他才能批评《纲目》对扬雄(不书“死”而书“卒”)以及曹操(不书“自立”而书“封”)之姑息,这背后所隐藏的是非常强烈的君臣名分论。我们可以说,从朱熹自身的立场来看,“直笔”之书法与“凡例”之建立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在朱熹的世界观中,“事实”与“价值”永远是不可分割且永恒不变的,所以直书“事实”即可以说“无私意”,又可以说是蕴含着自明之“褒贬”。但如果并非朱子学的信徒,那么“直笔”与“义例说”之矛盾就无法消解,或者更准确地说,朱熹所说的“直笔”只对接受朱子学理念的人而言才成立。对此问题,福谷其实是有所意识的,因此他才在文章最后写道:“在今人看来,《纲目》之‘凡例’,在内容上是以伦理之观点对史实进行笔法上的区分而作,在史实中掺入伦理评价的倾向非常明显……这样的‘凡例’之恣意性,反而让我们想起了微言大义。”(第78—79页)
中纯夫[251《本末格物说考》(《日本中国学会报》第62集,2010年)。从朱熹作《大学》补传开始,对于《大学》的“格物”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就一直是聚讼不止的话题,以至于在明代出现了黄宗羲所谓七十二家“格物”说的程度。中纯夫在该文中对宋明时期的“格物”说进行了系统的整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对于《礼记·大学篇》的“格物”应该如何解释,历来是众说纷纭。代表性的无疑是朱熹的训“格”为“至”,训“物”为“事”,而王阳明则以“格”为“正”,“物”为“意之所在”,除此之外,王心斋以大学本文的“物有本末”训“物”的所谓“淮南格物说”非常有名(但事实上在王心斋之前就有人如此解释,朝鲜儒学也是),中纯夫即对明末的“本末格物说”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并分出“以格物为本”(王柏),“以致知为本”(冯从吾),“以诚意为本”(黎立武、袁俊翁、罗汝芳、刘宗周、毛奇龄、汤斌、朱鹤龄),“以修身为本”(王艮、蒋信、王栋、耿定向、章潢、姚舜牧、李颙)四大类。中纯夫指出,本末格物说之意义首先就在于将“八条目”视为本末终始之次序,在此情形下,将“格物”视为“本”并不符合逻辑,“致知”的情形也是一样,因此只有王柏和冯从吾分别以“格物”和“致知”为本,是毫不奇怪的,而“诚意为本”和“修身为本”在逻辑上都能说通。另外,《大学》之文本在明代的主流至少有:①《大学章句》,②《大学》古本,③(伪)石经《大学》三种。从理论上说三种版本都能得出本末格物说之结论,但在依据《大学章句》的情况下,与朱熹的传第五章之格物解释必然会产生冲突,而事实表明也是如此,不过,对于即物穷理之说,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并不少,由此可见,即便否定朱熹的经书解释,也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工夫论;相对而言,阳明学出现之后的十四例中,十一例对良知说采取肯定之立场。
关于朱熹本人的思想史研究就介绍到这里。事实上,就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内地朱子学研究这几年已经开始逐渐拓宽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于朱子后学的几个重要门人弟子的相关研究——黄榦、陈淳、真德秀,已经获得了不少阶段性成果。反观日本方面,由于一方面中国思想史研究队伍后继乏力,而一线研究者则纷纷将目光转向日本或者韩国朱子学,而在大环境下,近几年中日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对立日趋激化,导致很多日本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抱有负面印象,中国的古典就更很少有人问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江户时代,尤其是中后期,由于幕府的官方意识形态需要,朱子学在日本有逐渐普及化的趋势,因此无论对朱子学抱有多么负面的评价,对朱子学本身的界定几乎都可以说是理解日本“近代化”的一个关键点。正因为如此,对于朱熹本人,事实上一般的人文学者还可能会有一定的关注,但是朱熹之后的朱子后学,与日本的“近代化”问题几乎没有关系,那么朱子后学之研究被冷落,从以上笔者归纳的三点来看,就不难理解了。当然,以上论述只是一个宏观性的把握。姑且不论质量,单从论文的数量来看,对黄榦的研究远远少于陈淳和真德秀。何以如此?以笔者之管见,陈淳对朱子学的基本概念进行整理与解释而作的《北溪字义》,很早就传到江户时代的日本,日本对于中国朱子学的理解,从江户时代直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此书。原因很简单,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固然是经典,但毕竟是朱熹对传统儒学之诠释,要理解与把握朱熹本人思想,那就必须阅读数量庞大的《文集》书信以及《朱子语类》,这对于江户时代的人而言几乎不可能,而在今天,能够不借助江户训读法直接阅读朱熹原著的日本学者,尤其是日本思想史研究者越来越少,相对而言,陈淳的《北溪字义》简直就是一本“朱子学入门字典”,姑且不论陈淳本人的思想与晚年朱熹是否存在偏差(至少笔者认为是存在的),陈淳本人在朱熹门下之地位以及其实力,都确实使得《北溪字义》成为朱子学入门的基本参考书目,因此不难理解,尤其是日本近世思想史学者对于《北溪字义》的熟悉程度很可能要高于朱熹本人。那么,真德秀又何以相对受到关注?事实上,检索真德秀的相关研究就会发现,有好几位研究者撰写过与真德秀宗教思想以及政策相关的论文。因为笔者去年也曾撰写过真德秀的论文,在此即以真德秀为例进行介绍。
就思想史而言,从明代开始的儒学内部对真德秀的评价不高,此不需多说。但值得注意的是,真德秀一方面留下了总计400余篇“青词”、“疏语”、“祝文”[26]。事实上,小岛毅早在1991年发表的《牧民管之祈祷——真德秀的场合》[27]一文中,就针对通常不为“思想研究”所重视的卷四十八至五十四所收录的“青词”、“疏语”、“祝文”进行了分析与整理。该文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真德秀“为民祈祷”的理念以及祠庙拜谒、祷告所牵涉的正统性问题,对于卷四十八、四十九的道教“青词”并没有详细地展开。在此之后,松本浩一对真德秀的祝文、青词等进行了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小岛毅论文的补充[28]。但该文仍然延续了“儒家正统与道教思想、民间信仰”的视角。松本浩一还列举了同时代的魏了翁、黄震以及陈淳等儒家对于民间道教的看法,由此指出:在当时已经无法完全扭转民间对佛教、道教信仰的情况下,像真德秀那样对于佛道进行统摄与吸收的做法可能是明智之举。
另外,前川亨[29]《真徳秀の政治思想——史弥遠政権期における朱子学の一動向》(《真德秀的政治思想——史弥远政权期的朱子学之动向》)(驹泽大学禅研究所年报第5号,1994年,第65—84页)一文,结合南宋政治来探讨真德秀的宗教政策,很具有参考价值。众所周知,朱熹在死前被韩侂胄政权打为“伪学”,但随后打倒韩氏而掌权的史弥远(1164—1233),却积极为朱子学平反并争取拉拢朱子学士人,在短短30年间,朱子学完成了“反体制”到“体制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在此期间出入政坛的朱子学者,正是私淑朱熹的真德秀。但是,真德秀本人无论在思想以及为人方面都颇受后儒之诟病,不管是全祖望还是四库馆臣都认为真德秀沉溺于佛老之学而“不纯”。前川并没有直接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理解真德秀学问之“不纯”,而是从朝廷宗教政策出发,得出了史弥远与真德秀在立场上极其相近的惊人结论。何以说“惊人”?大凡治宋史者都知道,史弥远在史书上被刻画为玩弄权术的权相,并且宝庆元年(1225)真德秀与魏了翁之落官也是史氏党徒之所为,但就此认为史弥远是反朱子学者,则未免过于轻信偏袒朱子学的史官之记载。前川列举了史弥远与朱子学之间存在某种政治协调关系的理由:其一,史弥远推翻反朱子学的韩侂胄政权,那么反过来说史氏与朱子学在反韩氏这点上就有亲和性;其二,史弥远拥立宋理宗上台,其中的核心人物是郑清之,郑氏与朱子学之亲和关系能为史氏搭桥;其三,史弥远上台正值南宋败于金朝、人心惶惶不安之时,在以政权稳定和维持秩序为紧要课题的情况下,不管是朱子学还是其他宗教,凡是能够加以利用的史弥远都必须利用。反过来就朱子学的立场来看,朱子学派急需摆脱“伪学”的帽子而站稳脚跟,因而前川认为,史弥远政权与朱子学虽然表面对立,实则两者政治利益存在一致性,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朱子学能够很快返回政治舞台而成为官方正统意识形态。
前川以宗教政策为例试图证明其观点:佛教政策方面,嘉定年间(1208—1224)史弥远确立了五山制度,例如禅宗寺院之住持等任命权均操纵在史弥远的手上,国家对佛教之干涉达到顶峰,也同时标志着世俗权力对宗教的全面压制。而在五山制度确立后不久,真德秀就为径山之住持撰写文章:“师,名妙崧……道价为当世第一”[30],真德秀之用意可见一斑。真德秀本人的佛教观如何?在文集卷二十九的《送高上人序》中,真德秀开篇即自问:“道一而已,乃有儒释氏之不同,何哉?”并答以佛教离弃人伦,故不可取。但接下来笔锋一转,当真德秀听到高上人(未详)年幼时家贫而不得葬双亲,去年回到三山后行葬礼、甚至还在墓地之附近建“思亲”之精舍,便大加赞赏。前川分析道:“不犯破坏世俗人伦秩序之谬误,反而拥护此秩序,这是认可佛教的必要条件。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在具备此条件的情况下,佛教也因此而能在体制内确保自己的地位。”(第71页)在此情形下,就不存在佛教与儒教之不同,正所谓“道一而已”,而这样的话,不管是二程还是朱熹都绝不会说,我们只要想起《中庸章句序》中著名的“以至于老佛之徒出,则弥近理而大乱真矣”就可以了。如果说上述对佛教的认可尚属于消极层面,那么例如文集卷三十五的《敕封慧应大师后记》中,真德秀提及嘉定十五年(1122)、很多地方出现疫情,净空禅师现身做祷告,“风雨旋至,瑞雪继之”,并评论道:“昔者,帝王受命,显穹为神人主……而又秩百神崇明祀,以佐人治所弗及。”对此,前川认为,施行仁政而安民,是世俗世界之官僚的职责,但这毕竟是“人治”,例如疫情以及自然灾害等等,则超出了“人治”之范围,而宗教领域的佛教之神力正能够辅佐人治之不足,所以真德秀才说“幽明虽殊,其为劝奖,一也”,“人治=儒教=明”与“人治所弗及=佛教=幽”,如此而形成政治支配之稳定性。那么,真德秀对于佛教的立场,显然与史弥远相近,即“利用(着重号为前川所加)佛教的咒术之力,以巩固政治支配”(第73页)。道教方面,真德秀自己更积极地设醮祷告,这一点已经有很多学者论及,就不再重复了,其着眼点也同样在于利用道教仪式来补充世俗政权之不足。在文章末尾,前川预想了两种对其观点的反驳,在这里仅介绍第二点,即对于朱熹去世之后的朱子学之发展,前川是否过高评价了真德秀的作用?事实上,真德秀在中央政权并没有多大作为,其功绩如下文要介绍的小林义广所说,更多地体现在作为“父母官”的地方行政上。因此,真德秀与之后取得国教地位的元代朱子学很难说有直接关联。但前川认为,真德秀作为朱子学之范式,其意义重大。在元代,以“咒术之园”的喇嘛教为代表,很多宗教都被蒙古统治者“宽容”地接受,在之后日益明显的“超越三教之别的中国式万神殿”、“宗教界的中国式正统”之过程,与作为政治支配护航的意识形态而确立自身地位的朱子学,恰恰可以看作是同一硬币的正反两面,这一点从史弥远时期的宗教动向以及真德秀的政治思想探讨中就能够看出端倪(第80页)。
前川的上述论证颇具冲击力,尤其是其一方面关注宗教政策与政治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又紧密结合朱子学的发展状况与定位,其视野之广阔与敏锐很值得借鉴。不过,笔者在这里有两点小小的疑问,仅供参考:其一,朱熹本人是否如前川所说,是“反体制”的?这个问题与前些年争议很大的朱熹皇权论有类似之处——朱熹究竟是主张伸张“士权”、抑制皇权,使皇权仅具备象征意义(就像日本近代史著名的美农部达吉“天皇机关说”),还是作为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支持皇权?其二,笔者在《从“上帝”到“万神殿”——以真德秀之青词祷告为例》一文中曾指出,不管是小岛毅还是松本浩一,均强调真德秀是站在“牧民官”之立场而“为民祈祷”,这种理解的潜在前提可能是“神道设教”。事实上,前川亨在分析与比较真德秀与权相史弥远的宗教政策之相似性的论文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理解。但是,即便不参照《文集》、《大学衍义》等其他文本,就卷四十八、四十九两卷而言,真德秀留下了十篇“生日设醮青词”以及九篇为母亲祷告的青词,这些青词显然不属于“为民祷告”之范畴,如果真德秀本人并不相信道教之诸神以及斋醮祷告之有效性,他为什么还通过这种形式来为自己以及家人祈祷,便完全成为不可解[31]。
小林义广《宋代地方官と民衆——真徳秀を中心として》(《宋代地方官与民众——以真德秀为中心》)(《研究论集》第10集,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2012年12月,第89—106页)。小林是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历史学博士,现任东海大学文学部教授,他是日本正统的东洋史研究专家,主要方向是宋代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族、地域研究[32]。所谓“谕俗文”,众所周知就是与民众直接接触机会较多的地方官员为了教化民众而撰写并公开布告的文章,就现有文献而言,宋代的“谕俗文”只有20余篇,但如果不拘泥于形式而关注内容的话,例如振兴农业的“劝农文”在宋代很常见,而地方官为了排除农业生产活动的负面因素,大多还会关注民众的生活方式,这当中就包含了教化的成分,其他例如“劝学文”、“劝孝文”、“晓谕词讼文”、“劝谕救荒文”等多种形式,其实都可以看作是“谕俗文”的变体。其次,在宋代,谕俗文最初的撰写者是北宋的陈襄(1017—1080),他在皇祐年间(1049—1053)作为台州仙居县知事而作了“劝谕文”,此举得到了朱熹的赏识。而私淑朱熹的真德秀,也在自己的谕告文中提道:“昔密学陈公襄为仙居宰,教民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其次来看谕俗文的内容,既然是教化民众,前提当然是民风与儒家道德不相合。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地方官大多在布告中提到民间诉讼相争的问题。在宋代,即便是同一族内部,贫富差距也急剧扩大,围绕财产等事情,骨肉之亲都会不惜对簿公堂。再来看真德秀,在《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中,共收录了“潭州谕俗文”、“再守泉州劝孝文”、“福州谕俗文”三篇,从内容上看,基本方向都是教导民众团结和睦、孝敬亲长,其中两篇都提到了“健讼”的问题,宋代社会之风气由此可见。其次,从谕俗文中能看出当地的一些特色,例如二度上任泉州的“泉州劝孝文”中,提到追荐供养之不必要性,其背景就是泉州当时佛教盛行,因此布施僧尼以及供养很流行,这一点也可以从李元弼的《作邑自箴》卷六“劝谕民庶榜”等文中得到佐证。再次,真德秀作为地方官,其谕告文中的两篇都被收录在明刻本《明公书判清明集》的卷首,可见其模范效应,那么真德秀的施政何以能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在小林看来,主要还在于作为朱子学者,真德秀身体力行朱熹的“诚”说,自己在上任时以身作则,并且相信一旦地方官员有诚意,那么民众也必定会受到感化,遵从官员之教化。小林认为,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明真德秀相信“民众并非单方面的是被统治者,而是具有主体之自觉来看待地方官之行政”(第102页)。对此,笔者认为可能需要更全面地考察真德秀的思想,尤其是尊王论来进行综合判断,在此就不细说了。最后,小林提到,在传统社会,一般民众的识字率很低,因此官员要传达自己的教化,光靠到处张贴布告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无论是从各种历史文献,还是真德秀的谕俗文中,我们都能看到“父老”、亦即有教养与学识的士人以及年长者的身影,有了“父老”之配合,儒家所主张的“风教”才可能顺利传达到一般民众中去。通观全文,小林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东洋史研究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另一方面,在论述中紧密结合真德秀的事例来进行分析,并准确地把握真德秀与其他宋代地方官之“同”与“异”,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以上就日本2013年的朱子学研究做了简单介绍与评价,并对于若干主题进行了回溯性的介绍与分析。由于笔者之学识限制,难免挂一漏万,敬请谅解为感。
(作者单位:日本关西大学亚洲文化研究中心)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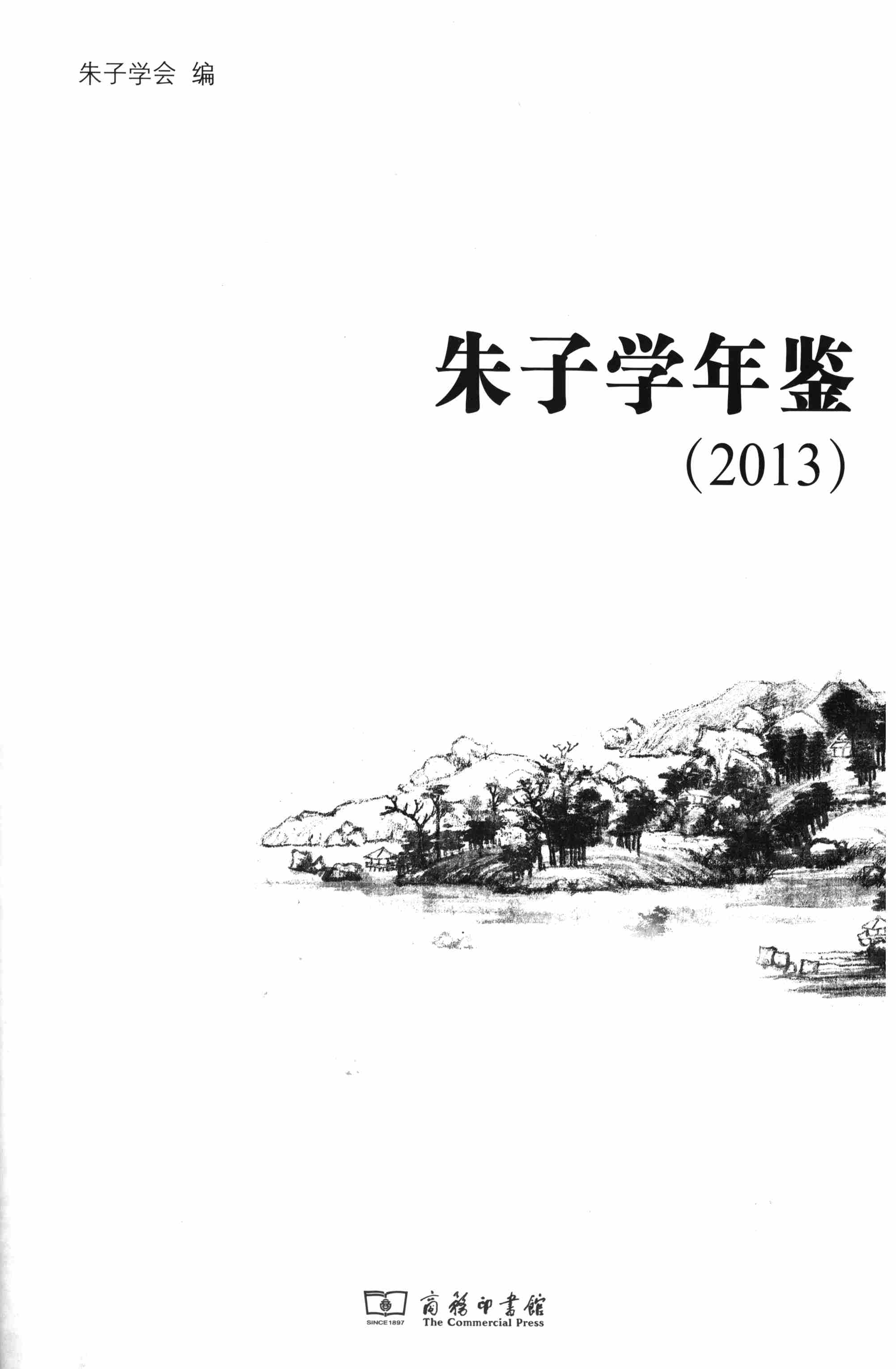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3》
本书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动态、资料辑要(介绍朱子学新书目录、期刊论文索引、全球朱子学研究资料目录等)9个栏目。
阅读
相关人物
陈晓杰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