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朱子学研究成果提要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3》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941 |
| 颗粒名称: | 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朱子学研究成果提要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1 |
| 页码: | 139-149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朱子学的研究状况。中国台湾学界的朱子学研究非常多元化,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朱熹或朱子学的思想。同时,中国台湾学界也非常注重“东亚”这一视野,从东亚的脉络来重新检视儒学相关问题。在中国台湾学界,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思想对宋明理学研究的影响很大。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的朱子思想或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有专书3本、期刊论文41篇、专书论文4篇、学位论文6篇。以下简单介绍其中主要研究成果。 |
| 关键词: | 朱子 经学思想 研究现状 台湾 |
内容
综观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朱子学研究的状况,朱熹思想或朱子学相关的研究仍然相当丰富,有从经学、义理、历史、文学、道德修养等各种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朱子或朱子学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中国台湾学界的朱子学研究相当多元化。提到多元化,近年来中国台湾学界非常注重“东亚”这一视野、观点,从“东亚”的脉络来重新检视儒学相关问题的研讨会、演讲以及课程相当盛行,其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硕,在中国台湾学界“东亚儒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受到认可。关于朱子学研究,在中国台湾学界,除了中国大陆朱子学之外,探讨朝鲜朱子学、越南朱子学、日本朱子学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
另外,中国台湾宋明理学研究历来深受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台湾宋明理学研究的影响相当凸显。牟先生对朱子思想的分析非常细致,且具有哲学性,其研究成果、观点,在朱子学研究上确实不能忽略。因此,在中国台湾学界,无论继承或批判牟先生的观点,许多朱子学研究仍以牟先生的观点为前提或出发点进行分析、探讨。关于这一点,看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便知。
据初步调查,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的朱子思想或朱子学相关研究的成果,专书有3本,期刊论文有41篇,专书论文有4篇,学位论文有6篇。以下简单介绍其中主要研究成果(参考2013年台湾朱子学研究相关资料)。
一、专书
关于朱子学相关研究的专书,有以下三本。陈逢源《“镕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台北:政大出版社),林庆彰、姜广辉、蒋秋华主编《文革时期评朱熹(上、下)》(台北:万卷楼),林莉娜、何炎泉、陈建志编《故宫法书新编十七:宋朱熹墨迹》(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法书新编十七:宋朱熹墨迹》属于书法艺术领域的著作,并不是朱子学研究的学术性成果,故在此不谈,以下介绍前两本专著。
首先,《“镕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是由在台湾地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研究相当著名的陈逢源教授所作。陈教授2006年撰写《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里仁书局),从“历史价值、撰作历程、思想体系、注解体例、援据来源、义理内涵等”不同角度来探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价值”。[1]《“镕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是收集陈教授这几年发表的朱子学研究的成果编辑而成的。全书由以下六章以及附录两篇构成:
第一章“颖悟”与“笃实”——朱熹论孔门弟子
第二章“治统”与“道统”——朱熹到道统之渊源考察
第三章“政治”与“心性”——朱熹注《孟子》的历史脉络
第四章“纵贯”与“横摄”——朱熹征引二程语录之分析
第五章“道南”与“湖湘”——朱熹义理进程之检讨
第六章“详味”与“潜玩”——朱熹叮咛语之梳理与检讨
附录一思想史重构——诠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进路的思索与反省
附录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引书目辑考
本书在每一章最后“结论”部分,条列式地归纳出本文获得的结论,相当简要明白,对理解本书所开展的朱子学研究的重点以及成果非常有益。因此,以下根据本书的结论部分,简单介绍其内容。
第一章:“颖悟”与“笃实”——朱熹论孔门弟子
本章考察、分析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如何征引论列孔门弟子,如何评论孔孟弟子等问题,作者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1.圣人气象,孔、颜乐处,原是北宋儒者思索的重要课题,更是“道学”成立的关键,朱熹征引前贤之见,从中及于孔门弟子高下之分析,以及儒学脉络的厘清,《论语》遂有不同以往的诠释角度。
2.朱熹以孔门弟子“颖悟”与“笃实”两分,取代以往“四科十哲”的分类概念,颜渊与曾子代表孔门正宗,而曾子更关乎“道统”之传,自此孔子门人层次井然,儒学传续,遂有清楚的线索。
3.为求凸显圣人形象,表彰颜渊、曾子之学,朱熹更留意孔子弟子质性不同,以及孔子“因材施教”的内容,孔门弟子以道相向,笃实为学,让人风慕向往。只是“药病”之说,诠释一偏,过于强调弟子缺失,形成《四书章句集注》十分特殊的现象。[2]
第二章:“治统”与“道统”——朱熹到道统之渊源考察
本章透过分析《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重新检视朱熹建构道统的进程及其目的。作者提供以下结论:
1.孔子之下,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五贤相继,从表彰韩愈而及于孟子,成为北宋庆历、熙宁间儒者政治实践的重要思考方向。
2.回归于心性,终于确定孟子独特孔子之传,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系谱遂取代五贤相继的说法,儒学内涵更为清楚明白。
3.标举孔、曾、思、孟,推崇二程,以心性为依归,全然为朱熹所接受,北宋以来儒学实践与反思,成为“四书”义理核心。[3]
第三章:“政治”与“心性”——朱熹注《孟子》的历史脉络
本章透过朱熹《孟子集注》所征引的材料,探讨朱熹建构《孟子》经典地位的思考过程。作者提供以下结论:
1.宋儒表彰韩愈,进而发现《孟子》价值,历经庆历时期的思考,到新旧党争,在尊孟与反孟之间,意见分歧,然而从二程及诸儒意见中,朱熹剔除疑义,终于确立《孟子》地位。
2.朱熹以“天命”消解“不尊周”的质疑;以儒者应有之出处态度,分判君臣分际,然而回归根本,得见“性善”为儒学思想的核心,于此皆是响应诸儒质疑的结果。[4]
3.朱熹进一步绾合圣圣相承意象,揭出“道统”概念,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传中,深化儒学历史情怀,确立得孔子之传的线索,《孟子》经典地位终于完成。
第四章:“纵贯”与“横摄”——朱熹征引二程语录之分析
本章整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征引二程之材料,阐明朱熹联结、综合明道的“纵贯”系统与伊川的“横摄”系统的情形。作者获得的结论主要如下:
1.朱熹原本分别二程,清楚明白,但《四书章句集注》并二程为一家,由分而合,乃是熔铸之后的结果。
2.朱熹寻求二程与圣人旨趣,从穷究于字句间,进而兼取并用,最后熔铸一体,乃是朱熹得见明道与伊川义理的传承与互补作用。
3.朱熹征引二程,从文字之“迹”,达致其“意”,注解形态的跃升,为“四书”建立义理核心,终于完成经典重构工作。[5]
第五章:“道南”与“湖湘”——朱熹义理进程之检讨
本章检核《四书章句集注》征引内容,探讨杨时的“道南”系统与谢良佐的“湖湘”系统,分析两派系统的思想在朱熹完成《四书章句集注》而建构“四书”体系时扮演的角色以及影响。
本文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1.朱熹继承道南一系,检核《四书章句集注》,关注所在,集中于李侗与杨时,对于“四书”体要之处,多以杨时说法为宗。
2.朱熹从湖湘一系所得,检核《四书章句集注》,征引内容以谢良佐、胡寅、张栻为主,重点集中于圣人气象的掌握,以及《论语》章句语脉的辨析,已由义理讲论,进于经旨阐发,于此可见朱熹学术进程。
3.朱熹以中和新说,汇整道南与湖湘两系,以心统性情的架构,融通体用,贯通动静,镕铸二程所传“静”、“敬”法门,不仅确立了二程学术地位,也终于形构了儒学
之宏大规模。[6]
第六章:“详味”与“潜玩”——朱熹叮咛语之梳理与检讨
本章关注《四书章句集注》的注释、论述方式,阐明朱熹突破一般经注的体例局限,站在读者的立场,采用反复叮咛、提示重点的论述方式的情形。作者归纳出以下结论: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据之余,往往镕铸体会,一抒个人心得,文字之间,深致叮咛,遂使诠释有感人的力量。
2.朱熹化解歧义,对于工夫与境界、圣与凡之间,建立观察,形塑儒学之传的线索,提醒后人继承,道统论述于此得见。
3.从经注工作而及于圣人事业,《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衔接,体系已具,朱熹遂以读者的心情,寄语于叮咛,祈求千载知音,详味思考,期许也有同样丰盈的感动。[7]
总之,作者脱离“门户之见”,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文本,实证性地阐明朱熹学术思想的正面貌。其分析方法、论述脉络非常理性、客观,本书所提供的各种观点、分析结果非常有说服力,一定对朱子学研究有贡献。
林庆彰、姜广辉、蒋秋华主编的《文革时期评朱熹(上、下)》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执行的“新中国六十年经学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根据“编辑说明”,本书“收集文化大革命末期批判朱熹及相关人物之论文九十余篇,论文集三本,专书一本。论文均采自全国各地之报纸、期刊和学报”。本书分为“单篇论文”与“专书”两部分,“单篇论文”部分进一步分类为朱熹总评、评朱熹理学、评朱子著作、评朱子生平行事、评朱子与陈亮、评朱子与林彪、评朱子科学等七类内容而收入相关文章共85篇。“专书”部分收入《朱熹的丑恶面目》(上饶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婺源县革命委员会政治宣传部)、《略评朱熹》(江西人民出版社编)、《可恶的朱熹》(赣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编)、《批判朱熹文集》(福建省图书馆编)等四种。
如主编林庆彰教授所指出,本书所收入的“文革”时期的朱子评论“有太多情绪的语言,有些几近谩骂,甚至是污蔑”,完全称不上客观理性的纯学术性朱子学研究。因此若从朱子学研究的成果这一角度来说,其学术意义确实有局限,但从“文革”研究或历史上的朱子学评价这一角度来说,这些朱子评论以及研究肯定具有参考价值、学术意义。总之,透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在“文革”时期如何评价朱子,如何批判朱子学等实际状况,本书提供了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各种研究课题。
二、期刊论文
论文方面,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的朱熹思想及朱子学的相关研究论文殆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朱熹思想与观念问题
有关朱熹思想的问题,本年度的研究以沈享民的《朱熹批判“观过知仁”与“知觉为仁”之探讨——对比于程明道与谢上蔡的诠释进路》和陈佳铭的《朱子格物思想中“心与理”的属性与关系新探》为佳。
朱熹与湖湘学派的渊源,可以上溯自朱子早年深受谢良佐的思想影响,大抵是朱子由“习禅”到之后从学李延平“由禅返儒”的这段时间,等到朱子思想臻至成熟,便开始对上蔡有较为严厉的批判,其中“以觉训仁”便是一个争论点。沈享民《朱熹批判“观过知仁”与“知觉为仁”之探讨——对比于程明道与谢上蔡的诠释进路》旨在阐述朱熹对湖湘学派以“知觉”训“仁”的批判问题,沈氏认为,朱熹对湖湘学者有关于“仁”的认识,并不完全是牟宗三先生所言的“误解”,反倒是湖湘学者对于“仁”说的认识主要是继承谢上蔡,沈氏把程明道与《上蔡语录》中的诸条数据做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明道解仁一词多是使用近于譬喻的方式;但上蔡则否,上蔡在“心有所觉谓之仁”与“四肢偏痹谓之不仁”两语表述中的“谓之”有近于“定义”语,就朱熹而言,“仁”作为体,为“心之德”,并不能等同于“知觉”,故沈氏认为朱熹对于湖湘学派所谓“误解”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来自谢上蔡粗略、大而化之的义理疏解方式。[8]
朱子的理气论问题,是处理朱子思想核心的重要定位,牟宗三对于朱子思想的判定深深影响着中国台湾学界,其认为朱子的“理”不能活动,故理的道德意义及力量便被减杀。陈佳铭的《朱子格物思想中“心与理”的属性与关系新探》一文,旨在修正牟宗三对于朱子规定的“理不活动”说。陈氏一文认为,在朱熹理气论的架构下,心属于气,但做工夫的心是属于心气与理浑然为一的状态。陈氏认为“朱子的工夫至某种程度时,则此理即可对心有某种动力,故不当视朱子的理的道德动力不足”,意即朱子的理并非只具有静态、不活动的面向,理尚能表现出“生生不已、天理流行”的一面,其关键在于是否臻至“心静理明”、“豁然贯通”之境。陈氏以为所谓的“豁然贯通”之境可自“心与理为二”及“心与理为一”的两种背景为前提下来探得,“心与理为二”概是强调理为“所以然之理”,理不活动;但在“心与理为一”下的理解,通过“豁然贯通”以致尽心的程度,心与理可彼此相合,这种“心理相融”的状态则可以展现出宇宙间生生不已的创生动力,是以,就“心理相融”来看,朱子亦是体认到理的活动性。[9]
(二)“四书”与经学相关研究
本年度有关“四书”及经学的相关研究,有王志玮《论明初〈四书大全〉的纂修意义》,姜龙翔《朱子〈五经〉阅读次序及其义理定位》和周欣婷《朱子〈易学〉的动静观:从经学与理学的交涉谈起》等三篇文章。
《四书大全》为明代胡广等人奉成祖之诏修撰,成祖修撰此书意在以圣人之道治天下,王志玮《论明初〈四书大全〉的纂修意义》一文,主要考察《四书大全》纂修所代表的历史意义。王氏认为历来先行研究多推尊《五经正义》而贬低《四书大全》,其实是受到清儒“汉宋之争”的关系。而《四书大全》的形成当从纂修的目的以及朱门后学对于朱注的疏解而论,王氏认为,就政治层面来看,明成祖纂修《四书大全》的目的乃是在强调自己“行道”的正当性;但就奉命纂修的儒臣而论,《四书大全》当是具道统代表的辑成,因此,《四书大全》的修纂便以朱门后学倪士毅的《四书辑释》为蓝本,企图彰显朱熹的宗主性及其道统地位。王氏认为《四书大全》纂修的过程,是明成祖欲以治统收纳儒林的道统,这一点自儒臣的《进书表》与明成祖的《御制序》便不难看出两股势力的角力,《四书大全》的纂成其实是这两股势力之间激荡与妥协下的成果。[10]
历来的先行研究多只探讨朱子对于阅读“四书”的次序及义理问题,却忽略了朱子如何透过阅读“五经”来建构他的思维,姜龙翔《朱子〈五经〉阅读次序及其义理定位》一文意在阐述朱子阅读“五经”的次序及义理问题,并以此来补足朱子读书法的全貌,姜氏指出朱子的读书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阅读“四书”为基础,作为探求义理的“精粹之法”,再者是必须回归“五经”,“五经”的阅读顺序为《诗》、《书》、《礼》、《易》、《春秋》,《春秋》之后则是由经典入史籍,透过读史来对史事义理进行判断的“应用阶段”。另外,姜氏认为,朱子的读书法乃是透过“四书”先确定义理的探求之法,之后再透过阅读“五经”形成两次的“义理建构循环”,探求义理的方法以及对于圣人之意皆为该备后,便能以此作为衡定史事的得失,故阅读史籍成为朱子读书中的第三阶段,同时也是将“义理建构循环”运用于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通过这种读书次序作为取径的建构,方可作为朱子理想的义理阐释进程。[11]
在朱子建构理学体系之前,当有其援用的思想资源,其中对于经典的注疏和诠释,便是他思维的展现,周欣婷的《朱子(易学)的动静观:从经学与理学的交涉谈起》一文即尝试从朱子的《易》学出发,并扣紧《易》中的“动静”问题,周氏认为以“动静”为切入点来思考《易》被放在“经学”与“理学”两种不同的脉络交涉下,有它一定的意义,因为它涉及朱子以“以静为本”的主静说来奠基“以理为本”的新儒学,同时又从太极与阴阳的关系来探讨太极之理,朱子的太极同时包含着形上、形下两种层次的“动静”。此外,朱子更以《坤》、《复》、《艮》等卦来说明理学所谓“静”的内涵,并以此检别儒释之间的不同,这一点成为“儒释之辨”课题中重要的依据,尤其反映在工夫论上。周氏认为,朱子对于“动静”之义的看重主要牵涉经学的“经旨”与理学的“道体”,这一点放在对《易》学的观察上,最得以显见。[12]
(三)朱子后学的研究
关于朱子后学的研究,本年度共有两篇论文,分别是王奕然的《探析朱子与门人对“理学字义”的论述——以〈性理字训〉、〈北溪字义〉为讨论文本》,以及孙淑芳的《存心之学——〈心经附注〉的圣学论述》。
朱子后学对于朱子学说的推衍,可有助于进一步掌握朱子思想,王奕然的《探析朱子与门人对“理学字义”的论述——以〈性理字训〉、〈北溪字义〉为讨论文本》一文在对比分析程端蒙的《性理字训》及陈淳《北溪字义》中对于朱子理学概念的疏解,以朱子的“小学”为切入点,最重要的是,《性理字训》和《北溪字义》两书撰成的旨要皆在于“训蒙”之用,以此作为童子入道之径,字义浅显易懂是作为“训蒙”之书的首要条件,但这同时也招致疏解过“粗”及“浅陋”的批评。王氏一文旨在对比两书,透过全书的次序编排及理学概念,来析论同为朱门后学对于师说继承,及其说与朱子师说原旨的差异性。[13]
朱子后学除小学范畴的“训蒙”之说外,当以发扬师说的大学之道为己任,偏重在对性理学的阐发,孙淑芳的《存心之学——〈心经附注〉的圣学论述》试图透过真德秀撰、程敏政附注的《心经附注》来阐释圣学论述中的本体与工夫论,《心经附注》中所论的圣人心法以“诚”与“敬”为修养的根源,通过“诚敬兼修”的“存心”之学进而达成天命之实践。孙氏此文除了针对《心经附注》中所蕴含的心法做分析外,亦关注到《心经附注》在东亚世界的传衍,尤其是它在朝鲜时期传入韩国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心经附注》广为朝鲜士林所重视的原因,乃在于朱子“存心”之学中的“诚”与“敬”成为朝鲜儒者(如李滉、李珥、曹植等人)建构“圣学”的重要依据,朝鲜的“圣学”旨要不但是“修己之学”,同时亦是“修己治人”的王道理想。[14]
(四)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开展
近年来儒学于域外的传播成为汉学研究讨论的焦点之一,而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开展,更是不可忽略的重点,本年度的朱子学相关论文,日本儒学方面有张文朝的《〈朱熹诗集传〉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的流传》、田世民的《从媒体史的观点看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朱子家礼)实践》,以及藤井伦明的《神儒妙契——山崎暗斋垂加神道中的“心”概念》、《从格物到觉知——德川日本崎门朱子学者三宅尚斋“格物致知”论探析》等四篇文章;韩国儒学有张雅评的《李栗谷、成牛溪“四端七情”论辩》,越南儒学方面则有林维杰的《黎贵惇的朱子学及其仙佛思想》一文。
近年来,域外汉籍的传播成为汉学(域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朱子学的研究而论,汉籍的传播更是不能忽略的观察点。张文朝的《朱熹〈诗集传〉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的流传》一文持续深化他关注的《诗经》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等议题。张氏一文主要是针对朱子《诗集传》在江户时代的传播问题,共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江户前期(1603—1692)的《诗经》相关书籍的流布多以朱子学新注系统为主,但等到中期开始(1693),古注系统的开始增加,概是因为古义学与古文辞学等古学抬头的影响,等到“宽政异学之禁”(1790)后,朱子学由德川幕府颁定为“正学”,朱子学以外的学问遂遭到压抑。张氏亦透过对于藩校教育的观察来申阐《诗经》的影响,其认为不管就藩校出版、刊行的教材,还是就学风而论,朱子学新注影响所及仍较古学为广、为多,可见朱子《诗集传》在日本《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性。[15]
汉籍的传播与接受成为研究东亚朱子学的前提条件,朱子的著作是如何为东亚世界的儒者所接受,且他们如何使朱子的学说适应当地?如何实践?这都是问题意识的形成。田世民的《从媒体史的观点看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朱子家礼〉实践》尝试用“媒体史”的方法来考察《家礼》在近世日本的传衍,就媒体史的论点来看朱子学的传播,可以发现明代官修的《性理大全》以及丘浚的《家礼仪节》在对外流传时,同时也使《家礼》得以广为流布于东亚世界。《家礼》传入日本,为日本儒者接受当有其时代脉络,《家礼》实践的原则主要落在“不做佛事”上,抗击佛家的祭祀礼仪,并以此奉为圭臬。由是观之,田氏认为以神主或位牌而论,更可当成是一种传播的“媒体”(media),这当中或有各家学说之间的彼此倾轧,如朱子学派讲求位牌一语为儒家本有,认为即便佛家有所谓位牌的形制,主要还是借自儒家;同时,古学派为了对抗朱子学的礼制,亦讲求恢复汉唐的神主形式。《家礼》作为媒体的传播,不再是一种只针对版本的考察,反而是必须将其放在历史脉络中,方可知儒者在实践过程中所代表的时代意义。[16]
儒学于日本的脉络化(Contextualize)最具代表性的学派莫过于山崎暗斋的崎门(きもん)学派,山崎暗斋学习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对于朱子学说严格遵守,此外暗斋亦在晚年学习神道,透过神儒兼习的方式来完善对于朱子学的认识,可以说,暗斋是最具“日本思维”的朱子学者。藤井伦明《神儒妙契——山崎暗斋垂加神道中的“心”概念》一文旨在阐明暗斋是如何通过神道作为思想资源,并以此来与朱子学对应,借以臻至所谓“神儒妙契”的情形。文中认为高岛元洋对于暗斋的研究值得商榷,高岛认为暗斋对于朱子学认知逸出朱子本身,两者基本上是属于“异质”的观点,暗斋对于朱子的理解并不相同,主要在于暗斋将他所认识的“神”理解为朱子学中的“理”。但藤井氏认为这种说法有其矛盾存在,依照暗斋自身的理解,他所认知的“神”应该等同于朱子学中的“心”,暗斋认识的“心”属于一具感应功能的活物,显然并未逸出朱子学的范畴,故藤井氏认为暗斋所理解的朱子学并不如高岛所言般相差得那么遥远。且若把暗斋这种“心”、“神”说法读入神道系谱中来理解,则可发现以“神”对应于朱子学中的“心”,概为中世以来神道学者所认识的共相,暗斋的神儒妙契之说,当是系在“心”与“神”对应而成的妙合为前提之下,在这个意义上,暗斋的所倡行理学与神道可以产生对应,且不相冲突。[17]
藤井伦明的第二篇文章《从格物到觉知——德川日本崎门朱子学者三宅尚斋“格物致知”论探析》,同样以崎门朱子学为中心,他以“崎门三杰”之一三宅尚斋的“格物致知”论为探讨的重点,相较于崎门朱子学中的“居敬”工夫,即物穷理的工夫反倒为尚斋所重视,尚斋认为“气”便是“理”的具体化,因此这世界的万事万物皆可视为“一理”的具现,故尚斋的理气论往往被定义为“理一元论”,但藤井氏一反历来学界的推断,认为尚斋的理气论应如内田周平所阐明的“理气二元一体论”,因为在尚斋的理解中,理、气关系不过是同一存在的体、用两种不同面向,对于“理”的预设排斥了行上与抽象的世界,反而注重在现象世界中的“即物性”,深具日本式的思维。由尚斋的理气关系推导到他的义理结构,藤井氏认为,尚斋的“理”当是“心具万理”(呈浑然貌),必须透过“格物”来确认内在之“理”,即通过对外在事物进行“格物”的方式,来认识心中潜在具有的“条理区别”,由此亦可证成“格物→觉知”,使心的全貌得以朗现,就尚斋而言,“心体之明”同时也是“明德”的工夫,是为一种“心法”。[18]
相较于前述日本儒者抗拒对于形而上学、抽象思考的思维特色,韩国朝鲜时期儒者则侧重对性理学的阐发,张雅评的《李栗谷、成牛溪“四端七情”论辩》一文,便关注到作为朱子学者的李栗谷和成牛溪及两者对于“四端七情”的论辩问题,事实上,“四端七情”的论辩早在栗谷和牛溪之前,李退溪及其门生奇高峰即已展开,大抵而言,牛溪继承退溪立场,认为“四端七情”及“人心道心”可分别言之,但栗谷的立场基本上与高峰相同,同样持“七情包四端”的看法,认为两者并不能分开言说。牛溪的立场在于可将道心与人心的关系分别统属于理气关系,即道心为理(四端),人心为气(七情),四端在七情之外;栗谷则反对牛溪的观点,认为四端虽为纯善,但仍是属于“情”的范畴,因为四端是性(纯善)直接的表现,若“善情”为气所掩,则同样有沦于恶的可能,故栗谷认为,七情是情的“总会”,它必然包含四端。张氏认为,由牛溪、栗谷开启的“四端七情”之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不出退溪及高峰的认识,但其实牛溪的立场亦不是完全立足于退溪的认识,反而是滑转在栗谷与退溪之间。[19]
有别于东北亚的朱子学,东南亚的朱子学则有其不同特色的展现,如越南朱子学的发展深受当地的“风气”所影响。林维杰的《黎贵惇的朱子学及其仙佛思想》一文,旨在阐述越南后黎朝时期的儒者黎贵惇和其对于中国儒学的吸纳、融摄,黎贵惇为学宗于朱熹,故他对于世界的认识便系在朱子学中的“理气”思维上,本篇文章主要探析黎贵惇是如何运用“理气”关系来了解鬼神,但这其中必须包含越南的风土影响,如他在解释自然界所生成的现象时,便将之“串接”理气关系,如“以气论风”、以气贯穿万事万物存在的生灭节奏等,黎贵惇重视“气”的作用概与安南的自身的宗教习俗(儒、释、道三教)相关,“理”所扮演的伦常角色则被弱化。“气化”强调通过祭祀活动来进行“感应”,如黎贵惇以“卜筮”来说明人心可与鬼神相感,人心与鬼神的感应,属于气的“同质相感”,但他所强调气的感应仅注重在祭祀活动的“功利性”,对于鬼神必须保持敬意且不可诋毁,即是纯就宗教层面而论,并未深化进入到如朱子般所强调的“宗教人文化”,以“德化”作为对伦常的护持。故此,林氏认为,黎贵惇的朱子学并未像朱熹本人般严谨,他喜谈鬼神,讲求业报轮回,反而使越南的朱子学特色走向了“简明化”、“世俗化”甚至于“修正化”。[20]
另外,本年度关于朱子学研究的学位论文共计为六篇,硕士论文有赖妤宜的《探讨朱熹的思维模式——以〈朱熹的思维世界〉为蓝本》,以及苏昊《从朱熹的心性论论其“中和”理论》等两篇文章;博士论文则有王家泠的《从玄学到理学——魏晋、唐宋之间(论语)诠释史研究》,王奕然《朱熹门人考述及其思想研究——以黄榦、陈淳及蔡氏父子为论述核心》,曾瀚仪《理气之争?——朱熹与戴震对孟子重要观念解法之比较》,以及郭芳如的《从鬼神观论朱熹哲学及其宗教向度》,共四篇文章。具体论文介绍详见后文的“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
综而论之,本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的研究议题除了对朱子本身学术思想观念重新做了探讨与诠释,以及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外,亦关注到朱子学说于域外的传衍,这方面可举朱子的著作为要,如《诗集传》与《朱子家礼》,尤其是它们在德川日本的流布。对于朱子学说的内在阐发,韩国朝鲜时期的儒者则侧重于对性理学的发掘,甚至于适应越南宗教、风土而生成的东南亚朱子学,都在阐发朱子学的多义性及多元性,从中我们亦可以窥知的是,自明清以降,朱子学的思想活力主要是在域外存续,尤其是比邻中国的日本与朝鲜,甚至越南等地。对于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开发是当前中国台湾学界的重要发展领域,除本文所介绍的专书、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外,2012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其后会议论文亦由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钟彩钧教授编辑成论文集于2013年出版[21],《“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东亚视域中的儒学》的内容便特别强调以“东亚儒学”为名,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亦有多篇围绕在对“东亚朱子学”议题的建构上(参考后文的“2013年台湾地区朱子学研究相关资料”),显而易见的是,朱子学的研究并不仅是聚焦于中国域内,域外“汉学”(Sinology)性质的朱子学,甚至于儒学的多元性还尚待我们开发。
(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
另外,中国台湾宋明理学研究历来深受牟宗三、唐君毅等新儒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牟宗三先生对中国台湾宋明理学研究的影响相当凸显。牟先生对朱子思想的分析非常细致,且具有哲学性,其研究成果、观点,在朱子学研究上确实不能忽略。因此,在中国台湾学界,无论继承或批判牟先生的观点,许多朱子学研究仍以牟先生的观点为前提或出发点进行分析、探讨。关于这一点,看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朱子学相关研究成果便知。
据初步调查,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的朱子思想或朱子学相关研究的成果,专书有3本,期刊论文有41篇,专书论文有4篇,学位论文有6篇。以下简单介绍其中主要研究成果(参考2013年台湾朱子学研究相关资料)。
一、专书
关于朱子学相关研究的专书,有以下三本。陈逢源《“镕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台北:政大出版社),林庆彰、姜广辉、蒋秋华主编《文革时期评朱熹(上、下)》(台北:万卷楼),林莉娜、何炎泉、陈建志编《故宫法书新编十七:宋朱熹墨迹》(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法书新编十七:宋朱熹墨迹》属于书法艺术领域的著作,并不是朱子学研究的学术性成果,故在此不谈,以下介绍前两本专著。
首先,《“镕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是由在台湾地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研究相当著名的陈逢源教授所作。陈教授2006年撰写《朱熹与四书章句集注》(台北:里仁书局),从“历史价值、撰作历程、思想体系、注解体例、援据来源、义理内涵等”不同角度来探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价值”。[1]《“镕铸”与“进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历史思维》是收集陈教授这几年发表的朱子学研究的成果编辑而成的。全书由以下六章以及附录两篇构成:
第一章“颖悟”与“笃实”——朱熹论孔门弟子
第二章“治统”与“道统”——朱熹到道统之渊源考察
第三章“政治”与“心性”——朱熹注《孟子》的历史脉络
第四章“纵贯”与“横摄”——朱熹征引二程语录之分析
第五章“道南”与“湖湘”——朱熹义理进程之检讨
第六章“详味”与“潜玩”——朱熹叮咛语之梳理与检讨
附录一思想史重构——诠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进路的思索与反省
附录二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征引书目辑考
本书在每一章最后“结论”部分,条列式地归纳出本文获得的结论,相当简要明白,对理解本书所开展的朱子学研究的重点以及成果非常有益。因此,以下根据本书的结论部分,简单介绍其内容。
第一章:“颖悟”与“笃实”——朱熹论孔门弟子
本章考察、分析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如何征引论列孔门弟子,如何评论孔孟弟子等问题,作者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1.圣人气象,孔、颜乐处,原是北宋儒者思索的重要课题,更是“道学”成立的关键,朱熹征引前贤之见,从中及于孔门弟子高下之分析,以及儒学脉络的厘清,《论语》遂有不同以往的诠释角度。
2.朱熹以孔门弟子“颖悟”与“笃实”两分,取代以往“四科十哲”的分类概念,颜渊与曾子代表孔门正宗,而曾子更关乎“道统”之传,自此孔子门人层次井然,儒学传续,遂有清楚的线索。
3.为求凸显圣人形象,表彰颜渊、曾子之学,朱熹更留意孔子弟子质性不同,以及孔子“因材施教”的内容,孔门弟子以道相向,笃实为学,让人风慕向往。只是“药病”之说,诠释一偏,过于强调弟子缺失,形成《四书章句集注》十分特殊的现象。[2]
第二章:“治统”与“道统”——朱熹到道统之渊源考察
本章透过分析《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重新检视朱熹建构道统的进程及其目的。作者提供以下结论:
1.孔子之下,孟子、荀子、扬雄、王通、韩愈五贤相继,从表彰韩愈而及于孟子,成为北宋庆历、熙宁间儒者政治实践的重要思考方向。
2.回归于心性,终于确定孟子独特孔子之传,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系谱遂取代五贤相继的说法,儒学内涵更为清楚明白。
3.标举孔、曾、思、孟,推崇二程,以心性为依归,全然为朱熹所接受,北宋以来儒学实践与反思,成为“四书”义理核心。[3]
第三章:“政治”与“心性”——朱熹注《孟子》的历史脉络
本章透过朱熹《孟子集注》所征引的材料,探讨朱熹建构《孟子》经典地位的思考过程。作者提供以下结论:
1.宋儒表彰韩愈,进而发现《孟子》价值,历经庆历时期的思考,到新旧党争,在尊孟与反孟之间,意见分歧,然而从二程及诸儒意见中,朱熹剔除疑义,终于确立《孟子》地位。
2.朱熹以“天命”消解“不尊周”的质疑;以儒者应有之出处态度,分判君臣分际,然而回归根本,得见“性善”为儒学思想的核心,于此皆是响应诸儒质疑的结果。[4]
3.朱熹进一步绾合圣圣相承意象,揭出“道统”概念,从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传中,深化儒学历史情怀,确立得孔子之传的线索,《孟子》经典地位终于完成。
第四章:“纵贯”与“横摄”——朱熹征引二程语录之分析
本章整理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征引二程之材料,阐明朱熹联结、综合明道的“纵贯”系统与伊川的“横摄”系统的情形。作者获得的结论主要如下:
1.朱熹原本分别二程,清楚明白,但《四书章句集注》并二程为一家,由分而合,乃是熔铸之后的结果。
2.朱熹寻求二程与圣人旨趣,从穷究于字句间,进而兼取并用,最后熔铸一体,乃是朱熹得见明道与伊川义理的传承与互补作用。
3.朱熹征引二程,从文字之“迹”,达致其“意”,注解形态的跃升,为“四书”建立义理核心,终于完成经典重构工作。[5]
第五章:“道南”与“湖湘”——朱熹义理进程之检讨
本章检核《四书章句集注》征引内容,探讨杨时的“道南”系统与谢良佐的“湖湘”系统,分析两派系统的思想在朱熹完成《四书章句集注》而建构“四书”体系时扮演的角色以及影响。
本文主要获得以下结论:
1.朱熹继承道南一系,检核《四书章句集注》,关注所在,集中于李侗与杨时,对于“四书”体要之处,多以杨时说法为宗。
2.朱熹从湖湘一系所得,检核《四书章句集注》,征引内容以谢良佐、胡寅、张栻为主,重点集中于圣人气象的掌握,以及《论语》章句语脉的辨析,已由义理讲论,进于经旨阐发,于此可见朱熹学术进程。
3.朱熹以中和新说,汇整道南与湖湘两系,以心统性情的架构,融通体用,贯通动静,镕铸二程所传“静”、“敬”法门,不仅确立了二程学术地位,也终于形构了儒学
之宏大规模。[6]
第六章:“详味”与“潜玩”——朱熹叮咛语之梳理与检讨
本章关注《四书章句集注》的注释、论述方式,阐明朱熹突破一般经注的体例局限,站在读者的立场,采用反复叮咛、提示重点的论述方式的情形。作者归纳出以下结论: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据之余,往往镕铸体会,一抒个人心得,文字之间,深致叮咛,遂使诠释有感人的力量。
2.朱熹化解歧义,对于工夫与境界、圣与凡之间,建立观察,形塑儒学之传的线索,提醒后人继承,道统论述于此得见。
3.从经注工作而及于圣人事业,《四书章句集注》义理衔接,体系已具,朱熹遂以读者的心情,寄语于叮咛,祈求千载知音,详味思考,期许也有同样丰盈的感动。[7]
总之,作者脱离“门户之见”,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文本,实证性地阐明朱熹学术思想的正面貌。其分析方法、论述脉络非常理性、客观,本书所提供的各种观点、分析结果非常有说服力,一定对朱子学研究有贡献。
林庆彰、姜广辉、蒋秋华主编的《文革时期评朱熹(上、下)》是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执行的“新中国六十年经学研究计划”的研究成果。根据“编辑说明”,本书“收集文化大革命末期批判朱熹及相关人物之论文九十余篇,论文集三本,专书一本。论文均采自全国各地之报纸、期刊和学报”。本书分为“单篇论文”与“专书”两部分,“单篇论文”部分进一步分类为朱熹总评、评朱熹理学、评朱子著作、评朱子生平行事、评朱子与陈亮、评朱子与林彪、评朱子科学等七类内容而收入相关文章共85篇。“专书”部分收入《朱熹的丑恶面目》(上饶地区革命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组婺源县革命委员会政治宣传部)、《略评朱熹》(江西人民出版社编)、《可恶的朱熹》(赣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编)、《批判朱熹文集》(福建省图书馆编)等四种。
如主编林庆彰教授所指出,本书所收入的“文革”时期的朱子评论“有太多情绪的语言,有些几近谩骂,甚至是污蔑”,完全称不上客观理性的纯学术性朱子学研究。因此若从朱子学研究的成果这一角度来说,其学术意义确实有局限,但从“文革”研究或历史上的朱子学评价这一角度来说,这些朱子评论以及研究肯定具有参考价值、学术意义。总之,透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在“文革”时期如何评价朱子,如何批判朱子学等实际状况,本书提供了研究现代中国史的各种研究课题。
二、期刊论文
论文方面,2013年中国台湾学界的朱熹思想及朱子学的相关研究论文殆可分为以下四类。
(一)朱熹思想与观念问题
有关朱熹思想的问题,本年度的研究以沈享民的《朱熹批判“观过知仁”与“知觉为仁”之探讨——对比于程明道与谢上蔡的诠释进路》和陈佳铭的《朱子格物思想中“心与理”的属性与关系新探》为佳。
朱熹与湖湘学派的渊源,可以上溯自朱子早年深受谢良佐的思想影响,大抵是朱子由“习禅”到之后从学李延平“由禅返儒”的这段时间,等到朱子思想臻至成熟,便开始对上蔡有较为严厉的批判,其中“以觉训仁”便是一个争论点。沈享民《朱熹批判“观过知仁”与“知觉为仁”之探讨——对比于程明道与谢上蔡的诠释进路》旨在阐述朱熹对湖湘学派以“知觉”训“仁”的批判问题,沈氏认为,朱熹对湖湘学者有关于“仁”的认识,并不完全是牟宗三先生所言的“误解”,反倒是湖湘学者对于“仁”说的认识主要是继承谢上蔡,沈氏把程明道与《上蔡语录》中的诸条数据做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出,明道解仁一词多是使用近于譬喻的方式;但上蔡则否,上蔡在“心有所觉谓之仁”与“四肢偏痹谓之不仁”两语表述中的“谓之”有近于“定义”语,就朱熹而言,“仁”作为体,为“心之德”,并不能等同于“知觉”,故沈氏认为朱熹对于湖湘学派所谓“误解”的原因,其根本原因来自谢上蔡粗略、大而化之的义理疏解方式。[8]
朱子的理气论问题,是处理朱子思想核心的重要定位,牟宗三对于朱子思想的判定深深影响着中国台湾学界,其认为朱子的“理”不能活动,故理的道德意义及力量便被减杀。陈佳铭的《朱子格物思想中“心与理”的属性与关系新探》一文,旨在修正牟宗三对于朱子规定的“理不活动”说。陈氏一文认为,在朱熹理气论的架构下,心属于气,但做工夫的心是属于心气与理浑然为一的状态。陈氏认为“朱子的工夫至某种程度时,则此理即可对心有某种动力,故不当视朱子的理的道德动力不足”,意即朱子的理并非只具有静态、不活动的面向,理尚能表现出“生生不已、天理流行”的一面,其关键在于是否臻至“心静理明”、“豁然贯通”之境。陈氏以为所谓的“豁然贯通”之境可自“心与理为二”及“心与理为一”的两种背景为前提下来探得,“心与理为二”概是强调理为“所以然之理”,理不活动;但在“心与理为一”下的理解,通过“豁然贯通”以致尽心的程度,心与理可彼此相合,这种“心理相融”的状态则可以展现出宇宙间生生不已的创生动力,是以,就“心理相融”来看,朱子亦是体认到理的活动性。[9]
(二)“四书”与经学相关研究
本年度有关“四书”及经学的相关研究,有王志玮《论明初〈四书大全〉的纂修意义》,姜龙翔《朱子〈五经〉阅读次序及其义理定位》和周欣婷《朱子〈易学〉的动静观:从经学与理学的交涉谈起》等三篇文章。
《四书大全》为明代胡广等人奉成祖之诏修撰,成祖修撰此书意在以圣人之道治天下,王志玮《论明初〈四书大全〉的纂修意义》一文,主要考察《四书大全》纂修所代表的历史意义。王氏认为历来先行研究多推尊《五经正义》而贬低《四书大全》,其实是受到清儒“汉宋之争”的关系。而《四书大全》的形成当从纂修的目的以及朱门后学对于朱注的疏解而论,王氏认为,就政治层面来看,明成祖纂修《四书大全》的目的乃是在强调自己“行道”的正当性;但就奉命纂修的儒臣而论,《四书大全》当是具道统代表的辑成,因此,《四书大全》的修纂便以朱门后学倪士毅的《四书辑释》为蓝本,企图彰显朱熹的宗主性及其道统地位。王氏认为《四书大全》纂修的过程,是明成祖欲以治统收纳儒林的道统,这一点自儒臣的《进书表》与明成祖的《御制序》便不难看出两股势力的角力,《四书大全》的纂成其实是这两股势力之间激荡与妥协下的成果。[10]
历来的先行研究多只探讨朱子对于阅读“四书”的次序及义理问题,却忽略了朱子如何透过阅读“五经”来建构他的思维,姜龙翔《朱子〈五经〉阅读次序及其义理定位》一文意在阐述朱子阅读“五经”的次序及义理问题,并以此来补足朱子读书法的全貌,姜氏指出朱子的读书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阅读“四书”为基础,作为探求义理的“精粹之法”,再者是必须回归“五经”,“五经”的阅读顺序为《诗》、《书》、《礼》、《易》、《春秋》,《春秋》之后则是由经典入史籍,透过读史来对史事义理进行判断的“应用阶段”。另外,姜氏认为,朱子的读书法乃是透过“四书”先确定义理的探求之法,之后再透过阅读“五经”形成两次的“义理建构循环”,探求义理的方法以及对于圣人之意皆为该备后,便能以此作为衡定史事的得失,故阅读史籍成为朱子读书中的第三阶段,同时也是将“义理建构循环”运用于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上,通过这种读书次序作为取径的建构,方可作为朱子理想的义理阐释进程。[11]
在朱子建构理学体系之前,当有其援用的思想资源,其中对于经典的注疏和诠释,便是他思维的展现,周欣婷的《朱子(易学)的动静观:从经学与理学的交涉谈起》一文即尝试从朱子的《易》学出发,并扣紧《易》中的“动静”问题,周氏认为以“动静”为切入点来思考《易》被放在“经学”与“理学”两种不同的脉络交涉下,有它一定的意义,因为它涉及朱子以“以静为本”的主静说来奠基“以理为本”的新儒学,同时又从太极与阴阳的关系来探讨太极之理,朱子的太极同时包含着形上、形下两种层次的“动静”。此外,朱子更以《坤》、《复》、《艮》等卦来说明理学所谓“静”的内涵,并以此检别儒释之间的不同,这一点成为“儒释之辨”课题中重要的依据,尤其反映在工夫论上。周氏认为,朱子对于“动静”之义的看重主要牵涉经学的“经旨”与理学的“道体”,这一点放在对《易》学的观察上,最得以显见。[12]
(三)朱子后学的研究
关于朱子后学的研究,本年度共有两篇论文,分别是王奕然的《探析朱子与门人对“理学字义”的论述——以〈性理字训〉、〈北溪字义〉为讨论文本》,以及孙淑芳的《存心之学——〈心经附注〉的圣学论述》。
朱子后学对于朱子学说的推衍,可有助于进一步掌握朱子思想,王奕然的《探析朱子与门人对“理学字义”的论述——以〈性理字训〉、〈北溪字义〉为讨论文本》一文在对比分析程端蒙的《性理字训》及陈淳《北溪字义》中对于朱子理学概念的疏解,以朱子的“小学”为切入点,最重要的是,《性理字训》和《北溪字义》两书撰成的旨要皆在于“训蒙”之用,以此作为童子入道之径,字义浅显易懂是作为“训蒙”之书的首要条件,但这同时也招致疏解过“粗”及“浅陋”的批评。王氏一文旨在对比两书,透过全书的次序编排及理学概念,来析论同为朱门后学对于师说继承,及其说与朱子师说原旨的差异性。[13]
朱子后学除小学范畴的“训蒙”之说外,当以发扬师说的大学之道为己任,偏重在对性理学的阐发,孙淑芳的《存心之学——〈心经附注〉的圣学论述》试图透过真德秀撰、程敏政附注的《心经附注》来阐释圣学论述中的本体与工夫论,《心经附注》中所论的圣人心法以“诚”与“敬”为修养的根源,通过“诚敬兼修”的“存心”之学进而达成天命之实践。孙氏此文除了针对《心经附注》中所蕴含的心法做分析外,亦关注到《心经附注》在东亚世界的传衍,尤其是它在朝鲜时期传入韩国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心经附注》广为朝鲜士林所重视的原因,乃在于朱子“存心”之学中的“诚”与“敬”成为朝鲜儒者(如李滉、李珥、曹植等人)建构“圣学”的重要依据,朝鲜的“圣学”旨要不但是“修己之学”,同时亦是“修己治人”的王道理想。[14]
(四)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开展
近年来儒学于域外的传播成为汉学研究讨论的焦点之一,而朱子学在东亚世界的开展,更是不可忽略的重点,本年度的朱子学相关论文,日本儒学方面有张文朝的《〈朱熹诗集传〉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的流传》、田世民的《从媒体史的观点看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朱子家礼)实践》,以及藤井伦明的《神儒妙契——山崎暗斋垂加神道中的“心”概念》、《从格物到觉知——德川日本崎门朱子学者三宅尚斋“格物致知”论探析》等四篇文章;韩国儒学有张雅评的《李栗谷、成牛溪“四端七情”论辩》,越南儒学方面则有林维杰的《黎贵惇的朱子学及其仙佛思想》一文。
近年来,域外汉籍的传播成为汉学(域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朱子学的研究而论,汉籍的传播更是不能忽略的观察点。张文朝的《朱熹〈诗集传〉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8)的流传》一文持续深化他关注的《诗经》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等议题。张氏一文主要是针对朱子《诗集传》在江户时代的传播问题,共分为三个阶段,其中江户前期(1603—1692)的《诗经》相关书籍的流布多以朱子学新注系统为主,但等到中期开始(1693),古注系统的开始增加,概是因为古义学与古文辞学等古学抬头的影响,等到“宽政异学之禁”(1790)后,朱子学由德川幕府颁定为“正学”,朱子学以外的学问遂遭到压抑。张氏亦透过对于藩校教育的观察来申阐《诗经》的影响,其认为不管就藩校出版、刊行的教材,还是就学风而论,朱子学新注影响所及仍较古学为广、为多,可见朱子《诗集传》在日本《诗经》学史上的重要性。[15]
汉籍的传播与接受成为研究东亚朱子学的前提条件,朱子的著作是如何为东亚世界的儒者所接受,且他们如何使朱子的学说适应当地?如何实践?这都是问题意识的形成。田世民的《从媒体史的观点看近世日本知识人的〈朱子家礼〉实践》尝试用“媒体史”的方法来考察《家礼》在近世日本的传衍,就媒体史的论点来看朱子学的传播,可以发现明代官修的《性理大全》以及丘浚的《家礼仪节》在对外流传时,同时也使《家礼》得以广为流布于东亚世界。《家礼》传入日本,为日本儒者接受当有其时代脉络,《家礼》实践的原则主要落在“不做佛事”上,抗击佛家的祭祀礼仪,并以此奉为圭臬。由是观之,田氏认为以神主或位牌而论,更可当成是一种传播的“媒体”(media),这当中或有各家学说之间的彼此倾轧,如朱子学派讲求位牌一语为儒家本有,认为即便佛家有所谓位牌的形制,主要还是借自儒家;同时,古学派为了对抗朱子学的礼制,亦讲求恢复汉唐的神主形式。《家礼》作为媒体的传播,不再是一种只针对版本的考察,反而是必须将其放在历史脉络中,方可知儒者在实践过程中所代表的时代意义。[16]
儒学于日本的脉络化(Contextualize)最具代表性的学派莫过于山崎暗斋的崎门(きもん)学派,山崎暗斋学习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对于朱子学说严格遵守,此外暗斋亦在晚年学习神道,透过神儒兼习的方式来完善对于朱子学的认识,可以说,暗斋是最具“日本思维”的朱子学者。藤井伦明《神儒妙契——山崎暗斋垂加神道中的“心”概念》一文旨在阐明暗斋是如何通过神道作为思想资源,并以此来与朱子学对应,借以臻至所谓“神儒妙契”的情形。文中认为高岛元洋对于暗斋的研究值得商榷,高岛认为暗斋对于朱子学认知逸出朱子本身,两者基本上是属于“异质”的观点,暗斋对于朱子的理解并不相同,主要在于暗斋将他所认识的“神”理解为朱子学中的“理”。但藤井氏认为这种说法有其矛盾存在,依照暗斋自身的理解,他所认知的“神”应该等同于朱子学中的“心”,暗斋认识的“心”属于一具感应功能的活物,显然并未逸出朱子学的范畴,故藤井氏认为暗斋所理解的朱子学并不如高岛所言般相差得那么遥远。且若把暗斋这种“心”、“神”说法读入神道系谱中来理解,则可发现以“神”对应于朱子学中的“心”,概为中世以来神道学者所认识的共相,暗斋的神儒妙契之说,当是系在“心”与“神”对应而成的妙合为前提之下,在这个意义上,暗斋的所倡行理学与神道可以产生对应,且不相冲突。[17]
藤井伦明的第二篇文章《从格物到觉知——德川日本崎门朱子学者三宅尚斋“格物致知”论探析》,同样以崎门朱子学为中心,他以“崎门三杰”之一三宅尚斋的“格物致知”论为探讨的重点,相较于崎门朱子学中的“居敬”工夫,即物穷理的工夫反倒为尚斋所重视,尚斋认为“气”便是“理”的具体化,因此这世界的万事万物皆可视为“一理”的具现,故尚斋的理气论往往被定义为“理一元论”,但藤井氏一反历来学界的推断,认为尚斋的理气论应如内田周平所阐明的“理气二元一体论”,因为在尚斋的理解中,理、气关系不过是同一存在的体、用两种不同面向,对于“理”的预设排斥了行上与抽象的世界,反而注重在现象世界中的“即物性”,深具日本式的思维。由尚斋的理气关系推导到他的义理结构,藤井氏认为,尚斋的“理”当是“心具万理”(呈浑然貌),必须透过“格物”来确认内在之“理”,即通过对外在事物进行“格物”的方式,来认识心中潜在具有的“条理区别”,由此亦可证成“格物→觉知”,使心的全貌得以朗现,就尚斋而言,“心体之明”同时也是“明德”的工夫,是为一种“心法”。[18]
相较于前述日本儒者抗拒对于形而上学、抽象思考的思维特色,韩国朝鲜时期儒者则侧重对性理学的阐发,张雅评的《李栗谷、成牛溪“四端七情”论辩》一文,便关注到作为朱子学者的李栗谷和成牛溪及两者对于“四端七情”的论辩问题,事实上,“四端七情”的论辩早在栗谷和牛溪之前,李退溪及其门生奇高峰即已展开,大抵而言,牛溪继承退溪立场,认为“四端七情”及“人心道心”可分别言之,但栗谷的立场基本上与高峰相同,同样持“七情包四端”的看法,认为两者并不能分开言说。牛溪的立场在于可将道心与人心的关系分别统属于理气关系,即道心为理(四端),人心为气(七情),四端在七情之外;栗谷则反对牛溪的观点,认为四端虽为纯善,但仍是属于“情”的范畴,因为四端是性(纯善)直接的表现,若“善情”为气所掩,则同样有沦于恶的可能,故栗谷认为,七情是情的“总会”,它必然包含四端。张氏认为,由牛溪、栗谷开启的“四端七情”之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不出退溪及高峰的认识,但其实牛溪的立场亦不是完全立足于退溪的认识,反而是滑转在栗谷与退溪之间。[19]
有别于东北亚的朱子学,东南亚的朱子学则有其不同特色的展现,如越南朱子学的发展深受当地的“风气”所影响。林维杰的《黎贵惇的朱子学及其仙佛思想》一文,旨在阐述越南后黎朝时期的儒者黎贵惇和其对于中国儒学的吸纳、融摄,黎贵惇为学宗于朱熹,故他对于世界的认识便系在朱子学中的“理气”思维上,本篇文章主要探析黎贵惇是如何运用“理气”关系来了解鬼神,但这其中必须包含越南的风土影响,如他在解释自然界所生成的现象时,便将之“串接”理气关系,如“以气论风”、以气贯穿万事万物存在的生灭节奏等,黎贵惇重视“气”的作用概与安南的自身的宗教习俗(儒、释、道三教)相关,“理”所扮演的伦常角色则被弱化。“气化”强调通过祭祀活动来进行“感应”,如黎贵惇以“卜筮”来说明人心可与鬼神相感,人心与鬼神的感应,属于气的“同质相感”,但他所强调气的感应仅注重在祭祀活动的“功利性”,对于鬼神必须保持敬意且不可诋毁,即是纯就宗教层面而论,并未深化进入到如朱子般所强调的“宗教人文化”,以“德化”作为对伦常的护持。故此,林氏认为,黎贵惇的朱子学并未像朱熹本人般严谨,他喜谈鬼神,讲求业报轮回,反而使越南的朱子学特色走向了“简明化”、“世俗化”甚至于“修正化”。[20]
另外,本年度关于朱子学研究的学位论文共计为六篇,硕士论文有赖妤宜的《探讨朱熹的思维模式——以〈朱熹的思维世界〉为蓝本》,以及苏昊《从朱熹的心性论论其“中和”理论》等两篇文章;博士论文则有王家泠的《从玄学到理学——魏晋、唐宋之间(论语)诠释史研究》,王奕然《朱熹门人考述及其思想研究——以黄榦、陈淳及蔡氏父子为论述核心》,曾瀚仪《理气之争?——朱熹与戴震对孟子重要观念解法之比较》,以及郭芳如的《从鬼神观论朱熹哲学及其宗教向度》,共四篇文章。具体论文介绍详见后文的“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
综而论之,本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的研究议题除了对朱子本身学术思想观念重新做了探讨与诠释,以及朱子后学的相关研究外,亦关注到朱子学说于域外的传衍,这方面可举朱子的著作为要,如《诗集传》与《朱子家礼》,尤其是它们在德川日本的流布。对于朱子学说的内在阐发,韩国朝鲜时期的儒者则侧重于对性理学的发掘,甚至于适应越南宗教、风土而生成的东南亚朱子学,都在阐发朱子学的多义性及多元性,从中我们亦可以窥知的是,自明清以降,朱子学的思想活力主要是在域外存续,尤其是比邻中国的日本与朝鲜,甚至越南等地。对于东亚朱子学研究的开发是当前中国台湾学界的重要发展领域,除本文所介绍的专书、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外,2012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其后会议论文亦由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钟彩钧教授编辑成论文集于2013年出版[21],《“中央研究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东亚视域中的儒学》的内容便特别强调以“东亚儒学”为名,论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亦有多篇围绕在对“东亚朱子学”议题的建构上(参考后文的“2013年台湾地区朱子学研究相关资料”),显而易见的是,朱子学的研究并不仅是聚焦于中国域内,域外“汉学”(Sinology)性质的朱子学,甚至于儒学的多元性还尚待我们开发。
(作者单位: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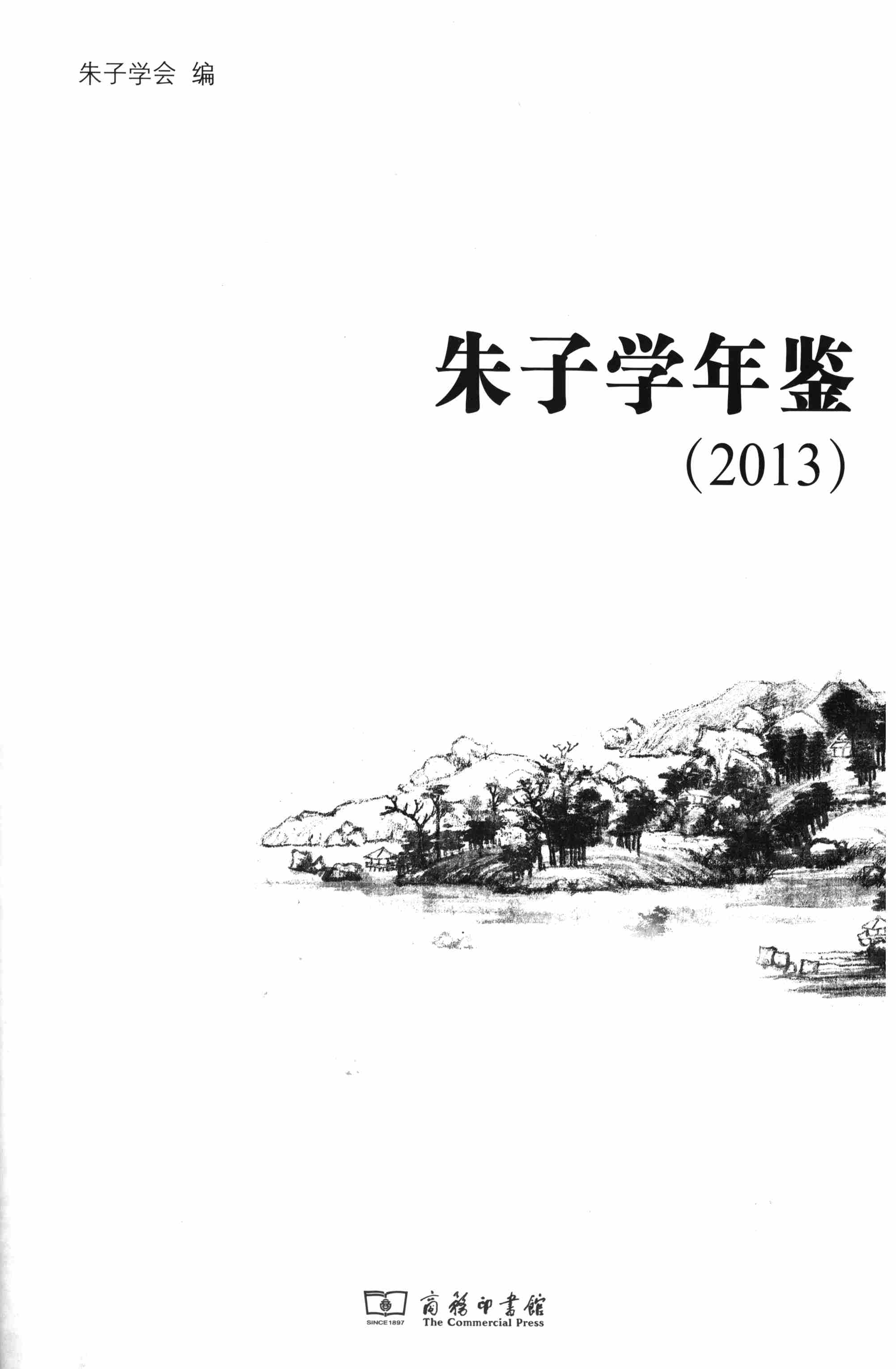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3》
本书设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朱子学动态、资料辑要(介绍朱子学新书目录、期刊论文索引、全球朱子学研究资料目录等)9个栏目。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