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朱子心性之学发展的本体诠释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4》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672 |
| 颗粒名称: | 四、对朱子心性之学发展的本体诠释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6 |
| 页码: | 017-022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孟子结合了孔子、曾子和子思的理解与体验,提出了心性的理念。他认为人性本善,心是情感和知觉的共同体,既是感觉又是知觉。他将心称为四端之心,认为心中根植着仁、义、礼、智这四种德行。他强调心与性的相通,通过心的拣择和知觉,性中的善能够发展成为不同的德行,从而实现亲仁民爱物。 |
| 关键词: | 心性之学 朱子文化 |
内容
孟子对心性的理解是集先秦学之大成者。他结合了孔子、曾子与子思的理解与体验,提出了性善而发为心的四端说。此说的创意历史上并未能完全彰显,因其所说之心是情与知觉的共同体,既是feeling又是知觉,故我早年英译为heart-mind。虽至今为人所通用,但用者往往无见其意旨。此一“感知”之认识可以张载语证之:“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35]孟子并有心之官则思的观察,思则能明觉。
此心正是孟子四端之心。但孟子更有新意:性中有四德,乃根植于心,所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36],由此可见心、性是相通的:性之原善因心的拣择与知觉发为不同相应的德,乃能“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再者,心是可以用养气充实的,以致仁、义不可胜用。孟子又有不动心之说,且不同于告子。他主张:“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37]此处显示发于言的道理可以应征于心,可见心的备万物与天理,有了心的理解乃能发而为生气之行了。此处看出了心的本体通贯性,是联系性与行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是意志。心能“尚志”,“志”为“气之帅”,因而能成为意志。因之我最后提出“heart-mind-will”一词对孟子之心进行诠释。由此可以说明心的主体性与包含性以及发展性,形成了大丈夫的担当精神。
孟子的心的概念所包含的主体性与意志性事实上来自于孔子。孔子《论语》六次用“心”字,其中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8],又说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39]。可见心之自律性。其实孔子对心的理解非常深刻,不举心之名而实显心的主体意志,如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其所谓己实乃意志之心也。未明言心之主体意志,而实示之,在《中庸》则有“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能率者能修者何?显然非心莫属。乃至孟子之《尽心》者,《中庸》之“诚则明,明则诚”者,《大学》之“诚意而正心”者,皆以心为主体而不显。由此可见心之自立性与彰显性。故可说尽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天。
孟子提出性与命之分别,《告子上》即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40]由此以见性之具有创发与自然开拓性,何以如此则必以心的创发性与自主性说明之。性是自然的、不自觉的,而心则为创造的、知觉的,乃至自觉的。
二程的心性之说是在孟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建立的源泉来自于义理的肯认与心灵的体验及体悟。但二程也把《易传》中的天道流行阴阳互动的考察引入,体现了心有天理与作为万物生机之源的一面。得出“心即性,性即生”[41 ]的观点,而又实感受之。
我认为二程的心性之说基本上是孟子心性之说的一种发展,在四处深化了孟子:(1)心能感通于道而知万物之理。道是整体的,理是分别的,心能兼通道和理,最后得到理一分殊的结论。这是心的本体性。(2)因心的无形迹,故心能通道与太虚,成为虚灵之心,可能受到了张载《正蒙》“大其心”思想的影响。(3)由于对天理的体会,理成为心的潜在的内涵,“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42],说明心之理一分殊的显现。既显之后则不可后天的等同,而必须分别开来。可说为心的本体性的现象化。在现象化的层次乃可以说性发为情,又可说心之具有持善而行的能力与意志,但也有陷溺于私欲与蒙蔽的可能,因之本体全善之本体心成为现象心之后,或持善为道心,或陷于恶成人心。这是程颐“心有善恶”的说明。(4)孟子有心之修养之说,“心勿忘,勿助长也”[43]。人要靠修持以持善并反其本心,二程的“治心”更从理上说,治心在求与理一。理则为天地之理。
程颢倾向于就本体的心性一体来面对差别,而程颐则逐渐强调了落实于气的人的实体现象来说心性的差异,发展了性气、性情、性心的差别,以性理为体、为本,而以气情为用。心乃有体性的一面又有性用之一面。在未发与已发的辨别上以未发之性为体而以已发之心或情为用显然不妥,因心性同本。善恶的问题也必须从本体性与现象性的分别来说才有意义。程颐之异于程颢于此可见。本体上只有善,但事实上的善恶即使不离本体言,也因现象被说成本体的性也有善恶了。这是程颢的推理,但程颐却更能重视心之为人经验上的判断力与选择了。朱子之重“性无不善”而“心有善恶”也正是程颐分别性的本体性与心的现象性的结果。
胡宏从天地之大体论述“万物生于性”“万事贯于理”[44],所谓“生于性”指的是万物因生而有性而各为物。这是物性个体化原则的提出,借以说明生→性→心→善恶的发生过程。依于此,他看不出理的作用,以为理是性的内涵而非根基。此一与二程的差异来之于易学的生命哲学,以理为心的格致的学问,而非性存的本体,有回归孟子的气概。为何胡宏主张“性无善恶”[45]呢?我的解释是:他认为心生于性,心成立后方能分辨善恶,因选择而有善恶。性无心之辨别则无善恶,其所谓性无善恶可说明为性是绝对的自然,不受心的判断左右而超越于心。这是过分还原于本,而无视心性是循环的一体以及心之现象性,可能是受了道家与告子的影响。
胡宏又有心性二元论的倾向,以心无不仁,除了认知能力外,心有感通能力而能与天一。但心源于性,即成为心,则其功能异于性而为性之用。“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46]未发为体而已发为中。至于何以心宰万物以成性,这里说明了心的功能,是体现及实现性的潜力的唯一或重要途径与手段,也就是显性以成行的所指。我认为胡宏仍能自成其说的圆融,只是不能彰显心的其他功能而已。
显然,胡宏虽然影响了张栻,使其学有同于己处,却也促使张栻就自身的体验来发展其心性之学。
南轩的心说是基于孟子心性学的另一种陈述:以心为宇宙主体来说性之谓性。他仍接受了胡宏物生成为性的观点,但却用心来贯穿性的创发性与道德之善性,是另一种以心明性的本体论证:心为本,性故善。所谓心则是天地之心的创发与创化之动能与创造力也。心扮演了朱熹哲学中理生气的理的角色。心显然也是认识的能力,能够觉知天地万物之动。心有仁的内涵,“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谓仁也”。[47]心与理一,故是心即理。与陆象山何异?其异在较能以性为心的载体体现本体上一心性众的生命原理。他的心本气末的思想与孟子也有雷同之处: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以心为主宰,以天地之本体为心之本体,体现了孟子的天人一体。另一方面,性对南轩来说为发生之本,而心则为主宰之本。完全继承了孟子与中庸的性说:性为本根,为全善,性是正理,涉及气则有偏,由于气化之故,有二元论的调和问题。
夫心性关系者,从原始儒学乃至宋明理学,似乎均有二元的冲突:性之著见为心,以心发表于性,但性又赖心来发挥。两者应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较圆融与动态的理论。可以说心体性用,也可以说性体心用。应该发为心性互为体用的说法。
以上的认识前提,并不妨碍朱子将之化为一种新的结构,在此传化中,他借助了《中庸》里传统的中和之说。中之所指显然是一个活动的性,此性中已有心的发动。因为必须考虑到知觉的重要性,往往因知觉而有情发。总言之,性、情与心(甚至心智与心志)均有内在的联系。若以性为体,则情与心均可说为用。但就心的自主与独立言之,则情更为用,心为主、为体也是可以说得通的。这与孟子之说实际上亦可以契合。
朱子对心性问题之分析存在疑难。经过1167年与张南轩的沟通,他被暂时地说服了,认同“性体心用”。其后他重新以之为非,盖是遥受二程的影响。此外,他回想到李延平的静坐默思之法。朱熹向来觉得心有独立的作用,而在张南轩之“性体心用”中没看到情之独立表达。最终他的思想发生转向,发挥程颐所论的存养之说,认为“心”无时不在,不管“性”是否已发为“情”,“心”的运行都在其中。他也特别强调“心”在情感作用之外的认知作用,并强调心具有虚灵明觉的作用。心能发挥变动不居之力量,应能独立于性地法天理以成道心,亦可落入欲念而成人心。人应尽可能使之成为道心,进而于行为上通于仁者之心。朱熹综合心知,对人的心灵有所体悟,乃写成了《仁说》之文。朱熹的心同时具有本体创化性、知觉性与反思性,经格物而知万物,因其本具万物之理。但心却有气的虚灵知觉,可以落入欲念,必须法天理以成道心,也必须发挥其道德的修持能力方可。朱熹认为仁者之心是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48]人心包四德而贯四端。
朱熹此心究竟如何与性相接?朱熹理气相生的概念说明了性为生命之体,兼气质与天理。情则为性之用,彰显了气质的面,故是有善有恶,但心的地位是如何成为朱熹思想中的根本问题的。这个难题困扰着他,在程颐与苏季明的对话中并未能确定一个答案,因而在他37岁秋月访张南轩以解心中之惑。他所感受的困惑是什么?乃是心性在义理上都有本体性,但不知何者更为根本?他大可以性为本、以心为体、以情为用而形成一个动力的心性体系。但他当时看不到此,以后的发展则需要进一步整合讨论。对于之后的朱子而言,“心”事实上是一种反思、知觉、存养的意向,“心”存养于未发之际、已发之前。所谓存养者,即要参与其中。“心”一方面参与,一方面又能超越,乃成为一种可以克己复礼、规范其“性”的力量。这样一来,朱熹当然不能再继续接受“性体心用”,而是把“情”当作“用”、把“心”当作能统之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朱子忘掉了“心”的根源性,及“心”“性”的相互发挥之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朱子是以“性”为本、以“心”为体、以“情”为用,而不可只说是以“性”为体、以“心”为用。这样一来,“心”的地位得到了彰显,但“性”的来源之问题就被掩盖了。关于此论,可参考我发表在2006年《朱子学刊》上的论文:《朱熹四书次第与其整合问题:兼论朱熹中和新旧说的内容与含义》一文。这是我对朱熹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朱子、胡宏、张南轩的心性一体说之思想背景与思维方式,和张载、程颐均有关系。朱子主张“性本心体情用”与张南轩主张“性体心用”,在学术上到底有没有可以调和的地方?需要强调的是,从双方学理的分析上看,张南轩固然启发了朱子走向三分结构之学说;他对朱子的影响,应不止于启发作用,应该还有补充作用。张南轩的“性体心用”说,更清楚地说明了“性”的根源地位,并彰明了“性”有感思“心”的能力,而非把“心”突出为一些分别的作用而已,以致与情、与义失去内在的关联。事实上,心之为性之用在心为一知觉、情感与意志(所谓知情意)的统合体,更能发挥与实现性之为性的创造与实践的能力。显然,朱子也不是没感受到此一灼见,故用“心统性情”来进行对心性关系的表达,只是此一“统”字却未能反映出心之本体性的地位,心源于性而为性之用。从此一角度看,南轩是有助于朱子的观点,而不可为朱子之中和新说遽废也。
蔡方鹿《宋明理学心性论》一书中论及张栻与朱熹的中和之辩,至为清楚。其要点为指出张栻从胡宏主张性体心用,有其学统的背景。在1 167年张朱会晤论学中说服了朱熹,认定了性体心用。未发之性未发之前无法体认,只有已发之时察识。这是朱熹的丙戌之悟。返回或随即反思而生疑。何以有此一生疑,朱熹已有43岁时的说明(中和旧说序)。导致他自性体情用以致“心统性情”之中和新说,是为他的己丑之悟。此处突出了朱子之转化仍在从用以见体的了悟,而不必把心性视为二橛。因之我指出朱子的中和新说不必非否认中和旧说的本体内涵,而必须要以中和旧说中的性体心用为基源引导出心与性或与性情之间的多种关系。心之统合性情或心之统帅性情只是此等多种关系之一二端而已。
我谓南轩有助于朱子,并非指朱子必然超越或扬弃了南轩。南轩有助于朱熹的地方是:使朱熹对心之作用有了新的思想与经验整合,提升了一个层次,直觉到心的统合性以及主宰性。但于此亦不必否认性的本源性与基础性,而心实为性的创发性的提升,事实上更应借助张栻“性体心用”以表达“心”的直接呈现之意义,而不止于广延的包含与独立的主宰之意义而已。就张栻而言,他虽同意朱熹的两个见解,但究其自身与胡宏的心性贯通的认识,并非不可与朱熹之说并列同行而互补,显示心之为用的呈现义,以及心之为体的包含义(情)与主宰义(意)。也就是说,“性”“心”“情”的功能,涉及了本与体、体与用之关系,性情更属于本体性之问题,“心体”之说则更属于认识论之问题。
此心正是孟子四端之心。但孟子更有新意:性中有四德,乃根植于心,所谓“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36],由此可见心、性是相通的:性之原善因心的拣择与知觉发为不同相应的德,乃能“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再者,心是可以用养气充实的,以致仁、义不可胜用。孟子又有不动心之说,且不同于告子。他主张:“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37]此处显示发于言的道理可以应征于心,可见心的备万物与天理,有了心的理解乃能发而为生气之行了。此处看出了心的本体通贯性,是联系性与行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是意志。心能“尚志”,“志”为“气之帅”,因而能成为意志。因之我最后提出“heart-mind-will”一词对孟子之心进行诠释。由此可以说明心的主体性与包含性以及发展性,形成了大丈夫的担当精神。
孟子的心的概念所包含的主体性与意志性事实上来自于孔子。孔子《论语》六次用“心”字,其中自谓“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38],又说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39]。可见心之自律性。其实孔子对心的理解非常深刻,不举心之名而实显心的主体意志,如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其所谓己实乃意志之心也。未明言心之主体意志,而实示之,在《中庸》则有“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能率者能修者何?显然非心莫属。乃至孟子之《尽心》者,《中庸》之“诚则明,明则诚”者,《大学》之“诚意而正心”者,皆以心为主体而不显。由此可见心之自立性与彰显性。故可说尽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天。
孟子提出性与命之分别,《告子上》即谓:“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40]由此以见性之具有创发与自然开拓性,何以如此则必以心的创发性与自主性说明之。性是自然的、不自觉的,而心则为创造的、知觉的,乃至自觉的。
二程的心性之说是在孟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建立的源泉来自于义理的肯认与心灵的体验及体悟。但二程也把《易传》中的天道流行阴阳互动的考察引入,体现了心有天理与作为万物生机之源的一面。得出“心即性,性即生”[41 ]的观点,而又实感受之。
我认为二程的心性之说基本上是孟子心性之说的一种发展,在四处深化了孟子:(1)心能感通于道而知万物之理。道是整体的,理是分别的,心能兼通道和理,最后得到理一分殊的结论。这是心的本体性。(2)因心的无形迹,故心能通道与太虚,成为虚灵之心,可能受到了张载《正蒙》“大其心”思想的影响。(3)由于对天理的体会,理成为心的潜在的内涵,“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42],说明心之理一分殊的显现。既显之后则不可后天的等同,而必须分别开来。可说为心的本体性的现象化。在现象化的层次乃可以说性发为情,又可说心之具有持善而行的能力与意志,但也有陷溺于私欲与蒙蔽的可能,因之本体全善之本体心成为现象心之后,或持善为道心,或陷于恶成人心。这是程颐“心有善恶”的说明。(4)孟子有心之修养之说,“心勿忘,勿助长也”[43]。人要靠修持以持善并反其本心,二程的“治心”更从理上说,治心在求与理一。理则为天地之理。
程颢倾向于就本体的心性一体来面对差别,而程颐则逐渐强调了落实于气的人的实体现象来说心性的差异,发展了性气、性情、性心的差别,以性理为体、为本,而以气情为用。心乃有体性的一面又有性用之一面。在未发与已发的辨别上以未发之性为体而以已发之心或情为用显然不妥,因心性同本。善恶的问题也必须从本体性与现象性的分别来说才有意义。程颐之异于程颢于此可见。本体上只有善,但事实上的善恶即使不离本体言,也因现象被说成本体的性也有善恶了。这是程颢的推理,但程颐却更能重视心之为人经验上的判断力与选择了。朱子之重“性无不善”而“心有善恶”也正是程颐分别性的本体性与心的现象性的结果。
胡宏从天地之大体论述“万物生于性”“万事贯于理”[44],所谓“生于性”指的是万物因生而有性而各为物。这是物性个体化原则的提出,借以说明生→性→心→善恶的发生过程。依于此,他看不出理的作用,以为理是性的内涵而非根基。此一与二程的差异来之于易学的生命哲学,以理为心的格致的学问,而非性存的本体,有回归孟子的气概。为何胡宏主张“性无善恶”[45]呢?我的解释是:他认为心生于性,心成立后方能分辨善恶,因选择而有善恶。性无心之辨别则无善恶,其所谓性无善恶可说明为性是绝对的自然,不受心的判断左右而超越于心。这是过分还原于本,而无视心性是循环的一体以及心之现象性,可能是受了道家与告子的影响。
胡宏又有心性二元论的倾向,以心无不仁,除了认知能力外,心有感通能力而能与天一。但心源于性,即成为心,则其功能异于性而为性之用。“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46]未发为体而已发为中。至于何以心宰万物以成性,这里说明了心的功能,是体现及实现性的潜力的唯一或重要途径与手段,也就是显性以成行的所指。我认为胡宏仍能自成其说的圆融,只是不能彰显心的其他功能而已。
显然,胡宏虽然影响了张栻,使其学有同于己处,却也促使张栻就自身的体验来发展其心性之学。
南轩的心说是基于孟子心性学的另一种陈述:以心为宇宙主体来说性之谓性。他仍接受了胡宏物生成为性的观点,但却用心来贯穿性的创发性与道德之善性,是另一种以心明性的本体论证:心为本,性故善。所谓心则是天地之心的创发与创化之动能与创造力也。心扮演了朱熹哲学中理生气的理的角色。心显然也是认识的能力,能够觉知天地万物之动。心有仁的内涵,“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谓仁也”。[47]心与理一,故是心即理。与陆象山何异?其异在较能以性为心的载体体现本体上一心性众的生命原理。他的心本气末的思想与孟子也有雷同之处: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以心为主宰,以天地之本体为心之本体,体现了孟子的天人一体。另一方面,性对南轩来说为发生之本,而心则为主宰之本。完全继承了孟子与中庸的性说:性为本根,为全善,性是正理,涉及气则有偏,由于气化之故,有二元论的调和问题。
夫心性关系者,从原始儒学乃至宋明理学,似乎均有二元的冲突:性之著见为心,以心发表于性,但性又赖心来发挥。两者应联合起来,形成一个较圆融与动态的理论。可以说心体性用,也可以说性体心用。应该发为心性互为体用的说法。
以上的认识前提,并不妨碍朱子将之化为一种新的结构,在此传化中,他借助了《中庸》里传统的中和之说。中之所指显然是一个活动的性,此性中已有心的发动。因为必须考虑到知觉的重要性,往往因知觉而有情发。总言之,性、情与心(甚至心智与心志)均有内在的联系。若以性为体,则情与心均可说为用。但就心的自主与独立言之,则情更为用,心为主、为体也是可以说得通的。这与孟子之说实际上亦可以契合。
朱子对心性问题之分析存在疑难。经过1167年与张南轩的沟通,他被暂时地说服了,认同“性体心用”。其后他重新以之为非,盖是遥受二程的影响。此外,他回想到李延平的静坐默思之法。朱熹向来觉得心有独立的作用,而在张南轩之“性体心用”中没看到情之独立表达。最终他的思想发生转向,发挥程颐所论的存养之说,认为“心”无时不在,不管“性”是否已发为“情”,“心”的运行都在其中。他也特别强调“心”在情感作用之外的认知作用,并强调心具有虚灵明觉的作用。心能发挥变动不居之力量,应能独立于性地法天理以成道心,亦可落入欲念而成人心。人应尽可能使之成为道心,进而于行为上通于仁者之心。朱熹综合心知,对人的心灵有所体悟,乃写成了《仁说》之文。朱熹的心同时具有本体创化性、知觉性与反思性,经格物而知万物,因其本具万物之理。但心却有气的虚灵知觉,可以落入欲念,必须法天理以成道心,也必须发挥其道德的修持能力方可。朱熹认为仁者之心是以天地生物之心为心,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48]人心包四德而贯四端。
朱熹此心究竟如何与性相接?朱熹理气相生的概念说明了性为生命之体,兼气质与天理。情则为性之用,彰显了气质的面,故是有善有恶,但心的地位是如何成为朱熹思想中的根本问题的。这个难题困扰着他,在程颐与苏季明的对话中并未能确定一个答案,因而在他37岁秋月访张南轩以解心中之惑。他所感受的困惑是什么?乃是心性在义理上都有本体性,但不知何者更为根本?他大可以性为本、以心为体、以情为用而形成一个动力的心性体系。但他当时看不到此,以后的发展则需要进一步整合讨论。对于之后的朱子而言,“心”事实上是一种反思、知觉、存养的意向,“心”存养于未发之际、已发之前。所谓存养者,即要参与其中。“心”一方面参与,一方面又能超越,乃成为一种可以克己复礼、规范其“性”的力量。这样一来,朱熹当然不能再继续接受“性体心用”,而是把“情”当作“用”、把“心”当作能统之主。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朱子忘掉了“心”的根源性,及“心”“性”的相互发挥之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朱子是以“性”为本、以“心”为体、以“情”为用,而不可只说是以“性”为体、以“心”为用。这样一来,“心”的地位得到了彰显,但“性”的来源之问题就被掩盖了。关于此论,可参考我发表在2006年《朱子学刊》上的论文:《朱熹四书次第与其整合问题:兼论朱熹中和新旧说的内容与含义》一文。这是我对朱熹体系发展的一个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朱子、胡宏、张南轩的心性一体说之思想背景与思维方式,和张载、程颐均有关系。朱子主张“性本心体情用”与张南轩主张“性体心用”,在学术上到底有没有可以调和的地方?需要强调的是,从双方学理的分析上看,张南轩固然启发了朱子走向三分结构之学说;他对朱子的影响,应不止于启发作用,应该还有补充作用。张南轩的“性体心用”说,更清楚地说明了“性”的根源地位,并彰明了“性”有感思“心”的能力,而非把“心”突出为一些分别的作用而已,以致与情、与义失去内在的关联。事实上,心之为性之用在心为一知觉、情感与意志(所谓知情意)的统合体,更能发挥与实现性之为性的创造与实践的能力。显然,朱子也不是没感受到此一灼见,故用“心统性情”来进行对心性关系的表达,只是此一“统”字却未能反映出心之本体性的地位,心源于性而为性之用。从此一角度看,南轩是有助于朱子的观点,而不可为朱子之中和新说遽废也。
蔡方鹿《宋明理学心性论》一书中论及张栻与朱熹的中和之辩,至为清楚。其要点为指出张栻从胡宏主张性体心用,有其学统的背景。在1 167年张朱会晤论学中说服了朱熹,认定了性体心用。未发之性未发之前无法体认,只有已发之时察识。这是朱熹的丙戌之悟。返回或随即反思而生疑。何以有此一生疑,朱熹已有43岁时的说明(中和旧说序)。导致他自性体情用以致“心统性情”之中和新说,是为他的己丑之悟。此处突出了朱子之转化仍在从用以见体的了悟,而不必把心性视为二橛。因之我指出朱子的中和新说不必非否认中和旧说的本体内涵,而必须要以中和旧说中的性体心用为基源引导出心与性或与性情之间的多种关系。心之统合性情或心之统帅性情只是此等多种关系之一二端而已。
我谓南轩有助于朱子,并非指朱子必然超越或扬弃了南轩。南轩有助于朱熹的地方是:使朱熹对心之作用有了新的思想与经验整合,提升了一个层次,直觉到心的统合性以及主宰性。但于此亦不必否认性的本源性与基础性,而心实为性的创发性的提升,事实上更应借助张栻“性体心用”以表达“心”的直接呈现之意义,而不止于广延的包含与独立的主宰之意义而已。就张栻而言,他虽同意朱熹的两个见解,但究其自身与胡宏的心性贯通的认识,并非不可与朱熹之说并列同行而互补,显示心之为用的呈现义,以及心之为体的包含义(情)与主宰义(意)。也就是说,“性”“心”“情”的功能,涉及了本与体、体与用之关系,性情更属于本体性之问题,“心体”之说则更属于认识论之问题。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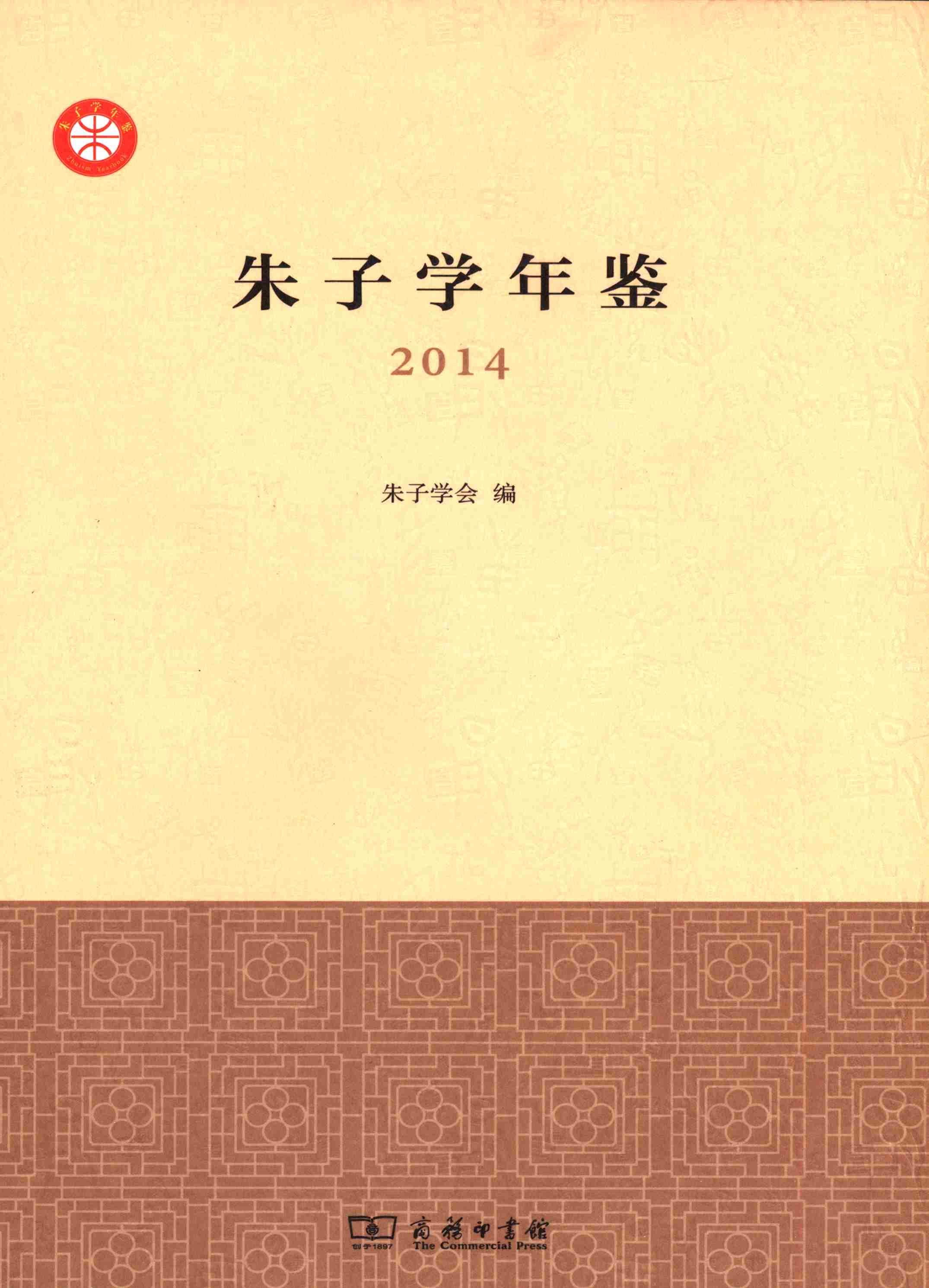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4》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本书分为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朱子学研究论著、朱子学研究硕博士论文荟萃、朱子学界概况等九个栏目,收录了《朱熹人性论与儒家道德哲学》、《对方东美朱熹诠释的反思》、《2014年韩国朱子学的研究概况》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成中英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