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辨饮食天理人欲之正
| 内容出处: | 《朱子与南剑州建州》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237 |
| 颗粒名称: | 一、辨饮食天理人欲之正 |
| 分类号: | R155 |
| 页数: | 4 |
| 页码: | 93-96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朱熹在饮食方面的天理人欲之辨,以及他对于饮食的态度和主张。朱熹认为饮食是人的天理,但要求饮食一定要适度,不能过度追求美味,否则就会陷于物欲而不能自拔。他主张饮食宁俭勿奢,提倡简朴节药,并教导人们要随遇而安,不要过份强求。同时,他也非常重视饮食天理人欲之辨,饮其所当饮,食其所当食,避免陷于物欲而不能自拔。 |
| 关键词: | 饮食 天理人欲 简朴节药 随遇而安 |
内容
朱子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人身上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论,同时又继承程颐“性即理”的基本思想。朱子认为,理表现在人身上就叫做性。天地之性为天所命,所以又叫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就是天理,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受气所累而有不善。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人修养的目的就是要变化气质,克服“气质之性”带来的不善因素,恢复天命之性的至善。朱子说:“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3]性是善的,情则有善有不善;流于不善,即受物欲的引诱与蒙蔽。在朱子的语境里,本体的心,是天理的显现,叫做道心;人心可善可不善,流于不善,即是人欲。人的目的,从心方面说,就是要使人心服从道心,存天理而灭人欲。
朱子重视饮食中天理人欲的辨别。他说:“一饮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无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时也食,不正也食,失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吃得许多物事,如不当吃,才去贪吃不住,都是逆天理。”[3]又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3]。饮食是一个人生存的前提条件,是天理,但是要求饮食一定要山珍海味,就属人欲了。又说:“须是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而道心亡矣!”[3];又说:“饥食渴饮,人心也;如是而饮食,如是而不饮食,道心也”[3];“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但为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于孔悝之类,此不可食者”[3];“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3]又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3]又说:“使饮食之人,真个无所失,则口腹之养本无害。然人屑屑理会口腹,则必有所失无疑。是以当知养其大体,而口腹底他自会去讨吃,不到得饿了也。”[3]譬如饮食之有五谷,惟其平常,故不可易。朱子说:“若是珍羞异味不常得之物,则暂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3],所以广因举释子偈有云:“世间万事不如常,又不惊人又久长。”[3]从以上这些言论,反映了朱子非常重视饮食天理人欲之辨,饮其所当饮,食其所当食,避免陷于物欲而不能自拔。
端正饮食态度很重要。朱子说:“中重于正,正不必中。”[3]又说:“一件物事自以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饥渴饮食是正;若过些子,便非中节。中节处乃中也。”[3]“饮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义,万钟不取,道心也。人心、道心,如饮食男女之欲,出于其正,即道心矣。”[3]又说:“‘割不正不食’,与‘席不正不坐’,此是圣人之心纯正,故日用间才有不正处,便与心不相合,心亦不安。”[3]且如‘不得其酱不食’,这一物合用酱而不得其酱,圣人宁可不吃,盖皆欲得其当然之则故也。”[3]《礼记》中有数般酱,随所用而不同,鱼脍芥酱之类。朱子说:“今人不是不理会道理,只是不肯仔细,只守着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没分别。”[3]
朱子教导小孩们说:“凡饮食,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但粥饭充饥不可缺”[4]。也就是饮食要随遇而安之,不要过份的强求。他主张饮食宁俭勿奢,提倡简朴节药。他说:“譬如人之饮食,有珍馐异馔,须是吃得尽方好。若吃不透,亦徒然”。“珍馐”是指珍奇名贵的食物,“异馔”是指特别的饭食。吃了这些山珍海味却没吃完,或者却弄不清楚到底吃了啥,也是徒然劳神费力做这些美食了。很多人就未能明辨天理人欲。就以胡紘为例,《宋史·胡紘》记载,胡紘曾到武夷山拜朱熹为师:“胡紘,处州遂昌人。淳熙中,举进士。绍熙五年,以京镗荐,监都进奏院,迁司农寺主簿、秘书郎。韩侂胄用事,逐朱熹、赵汝愚,意犹未快,遂擢紘监察御史。紘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紘不能异也。紘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赵汝愚,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汝愚遂谪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国,缙绅大夫与夫学校之士,皆愤悒不平,疏论甚众。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门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于已,欲尽去之,谓不可一一诬以罪,则设为伪学之目以摈之[5]。《素隐》中对“脱粟”是这样解释的:“脱粟,方脱壳而已,言不精凿也。故“脱粟饭”即指“糙米饭”。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期间,生活比较艰难,师生每天的主食就是“脱粟饭”,一种去壳而不加精舂的粗粮,粗涩难以下咽,以此实践其“咬得茶根,方能做得学问”的主张,学生辅广负笈前来,友人赠诗说:“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道命录》卷七也记载:“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6]。朱子与许多学生虽生活却十分清苦,但精神愉悦。可是朱熹却因招待胡紘以脱粟饭而惹祸,胡紘不告而别后,于庆元党禁中,他罗织朱熹六大罪状,堕落成权奸韩侂胄的爪牙和打手。后来监察御史沈继祖奏劾朱熹六大罪状之一:“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今熹欲餐精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6]胡紘为一己之私,不顾朱子当年已辞官生活的艰难,仅因没有鸡酒款待就罗织朱子罪名,进行大肆毁谤诬蔑,逆理悖德无过于此。
朱子重视饮食中天理人欲的辨别。他说:“一饮一食,都有是非。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人欲。如孔子‘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多食’,无非天理。如口腹之人,不时也食,不正也食,失饪也食,便都是人欲,便都是逆天理。如只吃得许多物事,如不当吃,才去贪吃不住,都是逆天理。”[3]又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3]。饮食是一个人生存的前提条件,是天理,但是要求饮食一定要山珍海味,就属人欲了。又说:“须是食其所当食,饮其所当饮,乃不失所谓‘道心’。若饮盗泉之水,食嗟来之食,则人心胜而道心亡矣!”[3];又说:“饥食渴饮,人心也;如是而饮食,如是而不饮食,道心也”[3];“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但为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以食。如子路食于孔悝之类,此不可食者”[3];“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3]又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3]又说:“使饮食之人,真个无所失,则口腹之养本无害。然人屑屑理会口腹,则必有所失无疑。是以当知养其大体,而口腹底他自会去讨吃,不到得饿了也。”[3]譬如饮食之有五谷,惟其平常,故不可易。朱子说:“若是珍羞异味不常得之物,则暂一食之可也,焉能久乎!”[3],所以广因举释子偈有云:“世间万事不如常,又不惊人又久长。”[3]从以上这些言论,反映了朱子非常重视饮食天理人欲之辨,饮其所当饮,食其所当食,避免陷于物欲而不能自拔。
端正饮食态度很重要。朱子说:“中重于正,正不必中。”[3]又说:“一件物事自以为正,却有不中在。且如饥渴饮食是正;若过些子,便非中节。中节处乃中也。”[3]“饮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义,万钟不取,道心也。人心、道心,如饮食男女之欲,出于其正,即道心矣。”[3]又说:“‘割不正不食’,与‘席不正不坐’,此是圣人之心纯正,故日用间才有不正处,便与心不相合,心亦不安。”[3]且如‘不得其酱不食’,这一物合用酱而不得其酱,圣人宁可不吃,盖皆欲得其当然之则故也。”[3]《礼记》中有数般酱,随所用而不同,鱼脍芥酱之类。朱子说:“今人不是不理会道理,只是不肯仔细,只守着自底便了,是是非非,一向都没分别。”[3]
朱子教导小孩们说:“凡饮食,有则食之,无则不可思索,但粥饭充饥不可缺”[4]。也就是饮食要随遇而安之,不要过份的强求。他主张饮食宁俭勿奢,提倡简朴节药。他说:“譬如人之饮食,有珍馐异馔,须是吃得尽方好。若吃不透,亦徒然”。“珍馐”是指珍奇名贵的食物,“异馔”是指特别的饭食。吃了这些山珍海味却没吃完,或者却弄不清楚到底吃了啥,也是徒然劳神费力做这些美食了。很多人就未能明辨天理人欲。就以胡紘为例,《宋史·胡紘》记载,胡紘曾到武夷山拜朱熹为师:“胡紘,处州遂昌人。淳熙中,举进士。绍熙五年,以京镗荐,监都进奏院,迁司农寺主簿、秘书郎。韩侂胄用事,逐朱熹、赵汝愚,意犹未快,遂擢紘监察御史。紘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紘不能异也。紘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樽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赵汝愚,且诋其引用朱熹为伪学罪首,汝愚遂谪永州。”汝愚初抵罪去国,缙绅大夫与夫学校之士,皆愤悒不平,疏论甚众。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门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于已,欲尽去之,谓不可一一诬以罪,则设为伪学之目以摈之[5]。《素隐》中对“脱粟”是这样解释的:“脱粟,方脱壳而已,言不精凿也。故“脱粟饭”即指“糙米饭”。朱熹在武夷精舍讲学期间,生活比较艰难,师生每天的主食就是“脱粟饭”,一种去壳而不加精舂的粗粮,粗涩难以下咽,以此实践其“咬得茶根,方能做得学问”的主张,学生辅广负笈前来,友人赠诗说:“闻说平生辅汉卿,武夷山下啜残羹”,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道命录》卷七也记载:“先生待学子惟脱粟饭,至茄熟,则用姜醯浸三四枚共食”[6]。朱子与许多学生虽生活却十分清苦,但精神愉悦。可是朱熹却因招待胡紘以脱粟饭而惹祸,胡紘不告而别后,于庆元党禁中,他罗织朱熹六大罪状,堕落成权奸韩侂胄的爪牙和打手。后来监察御史沈继祖奏劾朱熹六大罪状之一:“人子之于亲,当极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宁米白,甲于闽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籴仓米以食之,其母不堪食,每以语人。尝赴乡邻之招,归谓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饭。’闻者怜之。……今熹欲餐精钓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无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亲,大罪一也。”[6]胡紘为一己之私,不顾朱子当年已辞官生活的艰难,仅因没有鸡酒款待就罗织朱子罪名,进行大肆毁谤诬蔑,逆理悖德无过于此。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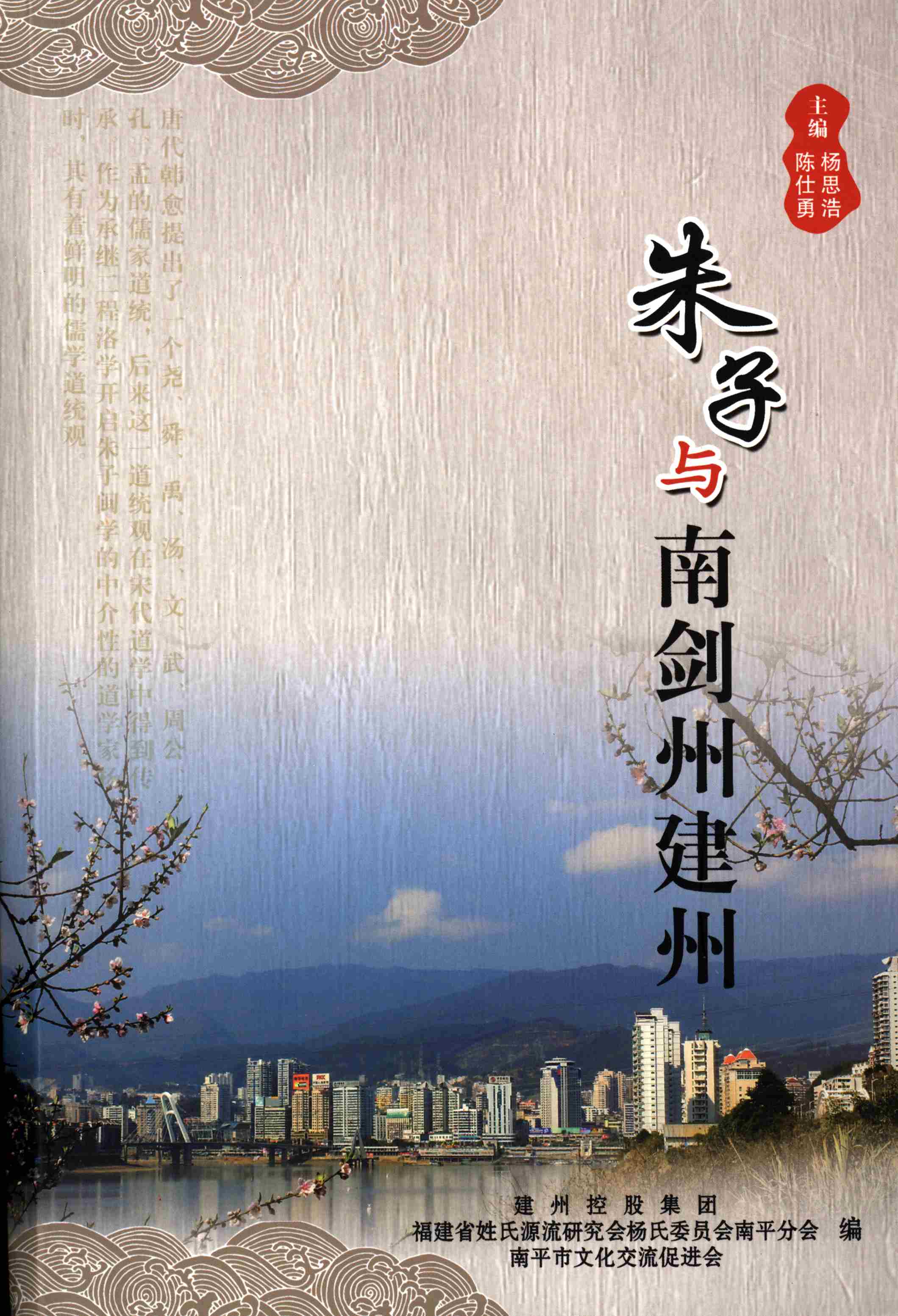
《朱子与南剑州建州》
本书围绕朱子与南剑州建州展开讨论,涉及朱熹的生平、思想、政治实践以及他在南剑州建州的文化影响等方面。同时,还探讨了杨时、李侗等儒家学者与朱熹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南剑州建州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在深入理解朱熹及其时代背景,同时探讨南剑州建州在闽学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