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辞章之学
| 内容出处: | 《朱子与南剑州建州》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205 |
| 颗粒名称: | 二、辞章之学 |
| 分类号: | K928.5 |
| 页数: | 6 |
| 页码: | 10-15 |
| 摘要: | 本文讨论了杨时对汉唐儒者的批评观点。他认为汉唐儒者过于注重辞章之学,虽然文章技巧高超,但并未真正揭示儒家圣人思想的真髓。杨时对杨雄持较高评价,但认为其仍未完全达到道学的境界。对于韩愈,尽管他看到了韩愈立志做圣人和排佛的努力,但仍认为他只是追求名誉的辞章之学,智慧还不足以理解先王之道和传承孔孟之学。因此,杨时主张超越辞章之学的局限,致力于研究和传承道学。 |
| 关键词: | 道学 传承 评价 局限 |
内容
在杨时看来,汉唐之儒往往多致力于辞章之学。自秦以下,汉唐儒者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韩愈、柳宗元以文赋驰骋古今,但从义理上考察他们则终究并不能真正倡道阐明道学,窥探到儒家圣人思想的内在精髓所在,故杨时认为汉唐之士以多著文章而自我满足,着力精雕辞句篇章以惊世骇俗,他说“自秦焚诗书、坑术士,六艺残缺。汉儒收拾补缀,至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若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相如、杨雄之徒继武而出,雄文大笔,驰骋古今,……积至于唐,文籍之备,盖十百前古。元和之间,韩柳辈出……自汉迄唐千余岁,而士之名能文者无过是数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学,窥圣人阃奥如古人者。”“区区于汉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务为辞章以惊眩末俗,非善学也。”[5]杨时认为,为汉唐辞章的儒者学习之勤奋,所涉猎的书籍之广博,文章内容之宏大精妙,并非今天一般儒者后学所能达到的水平,不过从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承看,则终究不被笃守儒家圣人之道的学者所称许,杨时甚至贬斥“区区汉儒不足学”,他说“汉之诸儒若贾谊、相如、司马迁辈,用力亦勤矣自书契以来,简册所存,下至阴阳星历、山经地志、虫鱼草木,殊名诡号,该洽无一或遗者,其文宏妙,殆非后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学渊源,论笃者终莫之与也。……区区汉儒不足学也。”[10]
杨时对于汉唐儒者,以杨雄和韩愈的论述最多。他对杨雄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汉唐名扬于世的大儒,只有杨雄而已,但杨雄对正道本分还没有完全尽到,仅接近道而没有做到尽道,他说“孟子没千有余岁,更汉历唐,士之名世,杨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择所处,于义命犹有未尽。”[11]“惟杨雄庶几于道,然尚恨其有未尽者。”[5]就其著述和学说之评价也与此类似,杨时认为杨雄学识超过其他汉唐儒者,但并没有把握儒家性命论(不知《易》,也就是不知性命之理),未能窥圣学门墙,他说“性命之说,虽杨雄犹未能造其藩篱,况他人乎?”[12]“杨雄作《太玄》,准《易》。此最为诳后学。……其实雄未尝知《易》。”[8]他还有具体的理论评述,语录载他批杨雄博约之说云“杨雄云:‘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其言终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为无病。盖博学详说,所以趋约;至于约,则其道得矣。谓之守以‘约’、‘卓’于多闻多见之中,将何守?”[13]杨时认为杨雄强调在多闻多见中守卓、守约不妥,不如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之说,其强调通过博学详说的手段和途径而反求简约、趋向简约,这样才得道而可以守,而杨雄在手段和途径上多闻多见方法与守约、守卓并举,问题在多闻多见学无所定则怎能有所守。他批杨雄性论说:“杨雄云:‘学所以修性。’夫物有变坏,然后可修;性无变坏,岂可修乎?唯不假修。”[13]杨雄主张性善恶混,修其善者为善,修其恶者为恶,有“学者,所以修性也”[14]的说法,杨时就此作批驳,认为,只有物坏掉才可以说修,性没有变坏,不可说修,所性不要借助于修,杨时将性作全善无恶并无变坏看,与杨雄性善恶混不同。对于韩愈,杨时虽看到其立志做孔子这样的圣人和极力排佛的功绩,但认为韩愈仍然不过是雕章镂句的辞章之学,获取当世名誉而已,其智慧还不足以明先王之道、传孔孟之学,所以其所操守不违背圣人之道的不多,他说“岂当时之士,卒无志于圣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韩愈,盖尝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则亦不可谓无其志也。及观其所学,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誉而止耳。”[5]“若唐之韩退之,今之孙明复、石守道、欧阳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数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传孔孟之学,其所守不叛于道盖寡矣”[2]杨时有诗评价到“吏部文章世所珍,终惭无补费精神。”[15]即韩愈辞章之学虽为世间所珍爱,但终究未能得圣人之道补益世教,徒费人工夫而已。这个评价从杨时对韩愈《原道》“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16]的批判可以看出,他说“韩子曰:‘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仁义,性所有也,则舍仁义而言道者,故非也;道固有仁义,而仁义不足以尽道,则以道德为虚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则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尽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顺道德而理于义’,又引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某谓若以道德为虚位,则士依于仁足矣,又奚必志于道、据于德?理与义足矣,又奚曰和顺道德?有可以和顺,有可以志据,则道德固非虚位也。”[17]韩愈认为道与德为虚位,道与德以仁义为实,杨时就此从两个角度作了批判:第一,依《中庸》“率性之谓道”和《易》“形上之道”“继善成性”来疏解,性有仁、义、礼、智等多般善,“率性”为道,离开仁义言道固然不可取,而仁义不足以尽道(性还有礼、智等多般善),显然以道与德离开仁义为虚位也不可取,即道德除仁义之外还有别的并非虚位。第二,从“和顺道德而理于义”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来看,如果认为道与德为虚位,则只要理于义就够了,不需要和顺于道与德,只要依于仁就够了,就不需要志于道、据于德,既然有可以和顺,有可以志和据,则道与德就不是虚位了。杨时因此强调道和德(仁、义、礼、智等多般善充足己)不是虚位,是一个实在。
杨时认为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即是此文章之学。他赞赏苏轼文章之成就,为当时之儒宗,学人士子得其一言足以名扬天下,他说“余窃谓东坡文妙天下,为时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5]然而又批评苏轼作诗多讥玩,无恻隐爱君情怀和温柔敦厚之气,故多得罪人,他说“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7]并在学说上,就苏辙的道论、性论作了批判。苏辙曾说“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圣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禅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之欲以道相诏者,至于一与中,尽矣。……及孔子既没,曾子传之子思。子思因其说而广之。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之说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与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为性善之论。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始枝矣。”[18]杨时则批判到“则‘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谓道者果何物耶?”“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谓‘一’者安在哉!”“夫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说也。学者更深考之,则孟子、苏氏之学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诬者矣。”[19]杨时的评述认为,“一”是姑且指称道不可用名辞概念言说的(道体),而“中”本身不是(道体),只是道之所寄在(形容道体之所在的),不是道本身,不可以中称道,道本身是什么呢?子思说为“中和”,此则是道可以用来言说的(“中和”兼体用,则道体显用则可以言说),所谓“一”又何在,即道之体用不二,哪有“一”(道体)在“中和”之中,实质即“一”就是“中和”本身;孟子说“性善”则是将天道通于人性,并未使“中”与“一”由此发生支离。可见杨时认可从三圣一直到孟子这样一脉而来对道的言说。苏辙有言“孟子学于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然而性之有习,习之有善恶,譬如火之能熟与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谓善,则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孙卿之所谓恶,则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孙卿之失则远矣。”[20]杨时批判了苏辙关于性善恶问题的探讨,他说“世儒之论曰:‘性之有习,习之有善恶,譬如火之能热与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谓善,得火之能热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谓恶,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间,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克之而火生焉。木与火未尝相离,盖子母之道也。火无形丽木而有焉,非焚之,则火之用息矣,何热之有哉?而谓热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盖亦不审矣。夫子思之学,惟孟子之传得其宗。异哉,世儒之论也,以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说而渐失之,而轻为之议,其亦不思之过欤!”[19]杨时此处从对木与火母子相生之道、焚与热的一体不二关系批驳苏辙的比喻,以论证性不是如火之能热与能焚一样的生命活动之作用,而是如火无形丽木而有的子母之道的这种生命本体本身,故焚与热并非是得性与失性、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的差异,实质孟子言性是就生命本体本身,性只是一个全善无恶的性,现实的善恶则关键在后天这个善性能否尽得还尽不得,所以孟子说性善,并未偏离子思“天命之谓性”的说法。
而在杨时看来,为何辞章之学去道远,不能明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学?原因在于这些儒家学者虽能以道自任,有志于圣人,然其为学方法往往为深探博取、支离蔓衍,而不知慎择约守,所以用力越勤、志向越坚定则离道越远,使的学者们茫然不知学习方向去路,他说“日夜惫精劳思,深探博取,可为勤矣。然其支离蔓衍,不知慎择而约守之,故其用志益劳而去道弥远,使天下学者靡然趋之”[11]辞章之儒往往以通古今博学为文,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不义之事,然而不知闻道为根本,而在杨时看来,问道则为问学之根本,强调“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他说“今时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所学,以博通古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已,而不知须是闻道故应如此。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13]而在杨时看来,圣学和圣人之道,不是儒者笔舌、辞章所言、所书能穷尽的,圣学和圣道旨归以“身体之,心验之”的亲身体验和实践而得,超越语言文字的表层的形式和表达,而重在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义理,不这样为学,则皆是辞章口耳诵数之学,背离道学,不得圣道之传,他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17]
杨时对于汉唐儒者,以杨雄和韩愈的论述最多。他对杨雄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汉唐名扬于世的大儒,只有杨雄而已,但杨雄对正道本分还没有完全尽到,仅接近道而没有做到尽道,他说“孟子没千有余岁,更汉历唐,士之名世,杨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择所处,于义命犹有未尽。”[11]“惟杨雄庶几于道,然尚恨其有未尽者。”[5]就其著述和学说之评价也与此类似,杨时认为杨雄学识超过其他汉唐儒者,但并没有把握儒家性命论(不知《易》,也就是不知性命之理),未能窥圣学门墙,他说“性命之说,虽杨雄犹未能造其藩篱,况他人乎?”[12]“杨雄作《太玄》,准《易》。此最为诳后学。……其实雄未尝知《易》。”[8]他还有具体的理论评述,语录载他批杨雄博约之说云“杨雄云:‘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其言终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为无病。盖博学详说,所以趋约;至于约,则其道得矣。谓之守以‘约’、‘卓’于多闻多见之中,将何守?”[13]杨时认为杨雄强调在多闻多见中守卓、守约不妥,不如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之说,其强调通过博学详说的手段和途径而反求简约、趋向简约,这样才得道而可以守,而杨雄在手段和途径上多闻多见方法与守约、守卓并举,问题在多闻多见学无所定则怎能有所守。他批杨雄性论说:“杨雄云:‘学所以修性。’夫物有变坏,然后可修;性无变坏,岂可修乎?唯不假修。”[13]杨雄主张性善恶混,修其善者为善,修其恶者为恶,有“学者,所以修性也”[14]的说法,杨时就此作批驳,认为,只有物坏掉才可以说修,性没有变坏,不可说修,所性不要借助于修,杨时将性作全善无恶并无变坏看,与杨雄性善恶混不同。对于韩愈,杨时虽看到其立志做孔子这样的圣人和极力排佛的功绩,但认为韩愈仍然不过是雕章镂句的辞章之学,获取当世名誉而已,其智慧还不足以明先王之道、传孔孟之学,所以其所操守不违背圣人之道的不多,他说“岂当时之士,卒无志于圣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韩愈,盖尝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则亦不可谓无其志也。及观其所学,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誉而止耳。”[5]“若唐之韩退之,今之孙明复、石守道、欧阳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数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传孔孟之学,其所守不叛于道盖寡矣”[2]杨时有诗评价到“吏部文章世所珍,终惭无补费精神。”[15]即韩愈辞章之学虽为世间所珍爱,但终究未能得圣人之道补益世教,徒费人工夫而已。这个评价从杨时对韩愈《原道》“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16]的批判可以看出,他说“韩子曰:‘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仁义,性所有也,则舍仁义而言道者,故非也;道固有仁义,而仁义不足以尽道,则以道德为虚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则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尽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顺道德而理于义’,又引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某谓若以道德为虚位,则士依于仁足矣,又奚必志于道、据于德?理与义足矣,又奚曰和顺道德?有可以和顺,有可以志据,则道德固非虚位也。”[17]韩愈认为道与德为虚位,道与德以仁义为实,杨时就此从两个角度作了批判:第一,依《中庸》“率性之谓道”和《易》“形上之道”“继善成性”来疏解,性有仁、义、礼、智等多般善,“率性”为道,离开仁义言道固然不可取,而仁义不足以尽道(性还有礼、智等多般善),显然以道与德离开仁义为虚位也不可取,即道德除仁义之外还有别的并非虚位。第二,从“和顺道德而理于义”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来看,如果认为道与德为虚位,则只要理于义就够了,不需要和顺于道与德,只要依于仁就够了,就不需要志于道、据于德,既然有可以和顺,有可以志和据,则道与德就不是虚位了。杨时因此强调道和德(仁、义、礼、智等多般善充足己)不是虚位,是一个实在。
杨时认为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即是此文章之学。他赞赏苏轼文章之成就,为当时之儒宗,学人士子得其一言足以名扬天下,他说“余窃谓东坡文妙天下,为时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5]然而又批评苏轼作诗多讥玩,无恻隐爱君情怀和温柔敦厚之气,故多得罪人,他说“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7]并在学说上,就苏辙的道论、性论作了批判。苏辙曾说“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圣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禅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之欲以道相诏者,至于一与中,尽矣。……及孔子既没,曾子传之子思。子思因其说而广之。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之说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与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为性善之论。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始枝矣。”[18]杨时则批判到“则‘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谓道者果何物耶?”“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谓‘一’者安在哉!”“夫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说也。学者更深考之,则孟子、苏氏之学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诬者矣。”[19]杨时的评述认为,“一”是姑且指称道不可用名辞概念言说的(道体),而“中”本身不是(道体),只是道之所寄在(形容道体之所在的),不是道本身,不可以中称道,道本身是什么呢?子思说为“中和”,此则是道可以用来言说的(“中和”兼体用,则道体显用则可以言说),所谓“一”又何在,即道之体用不二,哪有“一”(道体)在“中和”之中,实质即“一”就是“中和”本身;孟子说“性善”则是将天道通于人性,并未使“中”与“一”由此发生支离。可见杨时认可从三圣一直到孟子这样一脉而来对道的言说。苏辙有言“孟子学于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然而性之有习,习之有善恶,譬如火之能熟与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谓善,则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孙卿之所谓恶,则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孙卿之失则远矣。”[20]杨时批判了苏辙关于性善恶问题的探讨,他说“世儒之论曰:‘性之有习,习之有善恶,譬如火之能热与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谓善,得火之能热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谓恶,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间,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克之而火生焉。木与火未尝相离,盖子母之道也。火无形丽木而有焉,非焚之,则火之用息矣,何热之有哉?而谓热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盖亦不审矣。夫子思之学,惟孟子之传得其宗。异哉,世儒之论也,以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说而渐失之,而轻为之议,其亦不思之过欤!”[19]杨时此处从对木与火母子相生之道、焚与热的一体不二关系批驳苏辙的比喻,以论证性不是如火之能热与能焚一样的生命活动之作用,而是如火无形丽木而有的子母之道的这种生命本体本身,故焚与热并非是得性与失性、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的差异,实质孟子言性是就生命本体本身,性只是一个全善无恶的性,现实的善恶则关键在后天这个善性能否尽得还尽不得,所以孟子说性善,并未偏离子思“天命之谓性”的说法。
而在杨时看来,为何辞章之学去道远,不能明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学?原因在于这些儒家学者虽能以道自任,有志于圣人,然其为学方法往往为深探博取、支离蔓衍,而不知慎择约守,所以用力越勤、志向越坚定则离道越远,使的学者们茫然不知学习方向去路,他说“日夜惫精劳思,深探博取,可为勤矣。然其支离蔓衍,不知慎择而约守之,故其用志益劳而去道弥远,使天下学者靡然趋之”[11]辞章之儒往往以通古今博学为文,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不义之事,然而不知闻道为根本,而在杨时看来,问道则为问学之根本,强调“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他说“今时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所学,以博通古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已,而不知须是闻道故应如此。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13]而在杨时看来,圣学和圣人之道,不是儒者笔舌、辞章所言、所书能穷尽的,圣学和圣道旨归以“身体之,心验之”的亲身体验和实践而得,超越语言文字的表层的形式和表达,而重在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义理,不这样为学,则皆是辞章口耳诵数之学,背离道学,不得圣道之传,他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17]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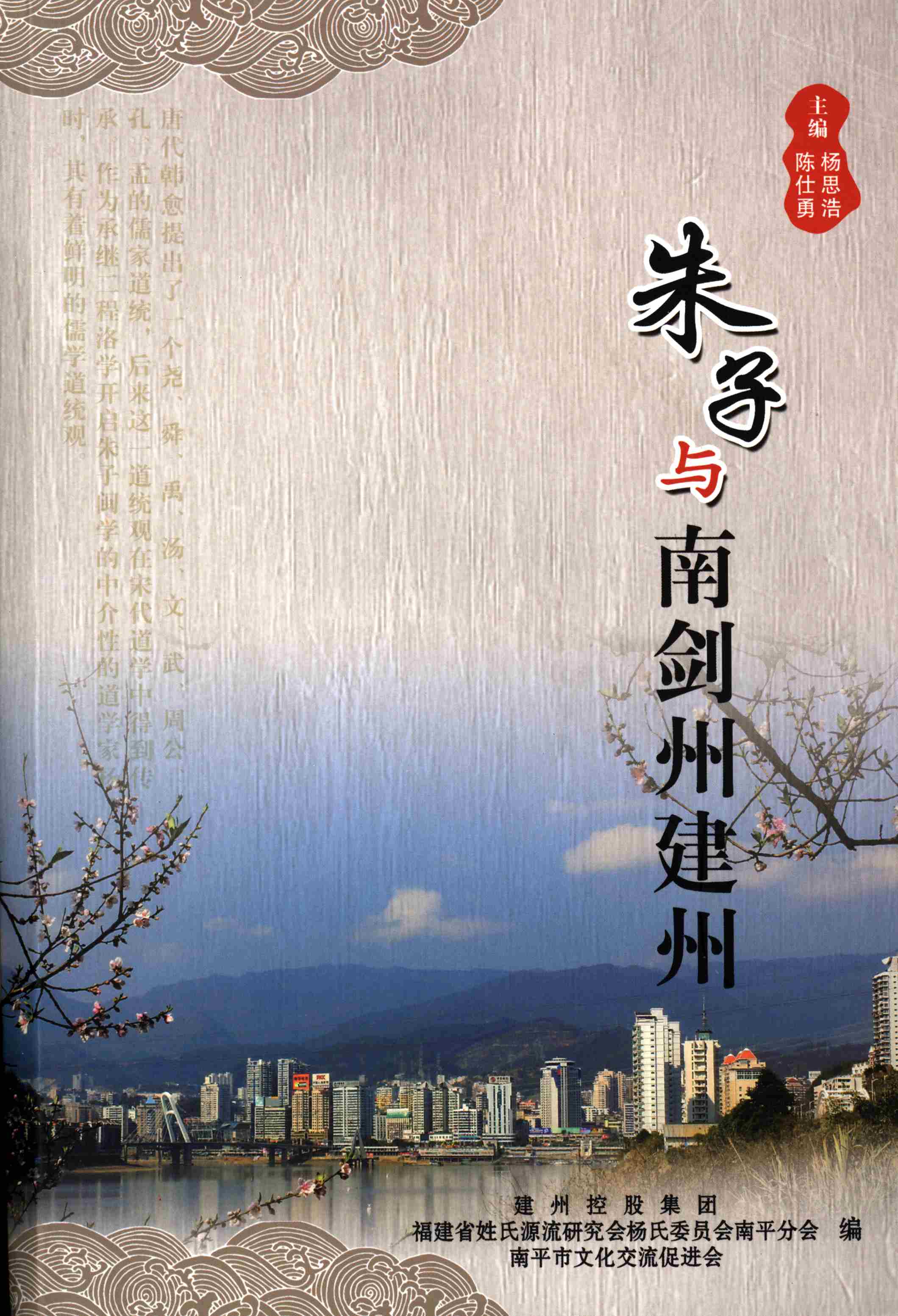
《朱子与南剑州建州》
本书围绕朱子与南剑州建州展开讨论,涉及朱熹的生平、思想、政治实践以及他在南剑州建州的文化影响等方面。同时,还探讨了杨时、李侗等儒家学者与朱熹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南剑州建州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在深入理解朱熹及其时代背景,同时探讨南剑州建州在闽学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