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道学视阈中的儒家末学及其文化意涵
内容
唐代韩愈提出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儒家道统,后来这一道统观在宋代道学中得到传承。作为承继二程洛学开启朱子闽学的中介性的道学家杨时,其有着鲜明的儒学道统观。杨时自29岁问道程颢接受道学熏陶,领悟到先前所学(荆公新学)之非,陈渊说“杨时始宗安石,后得程颢师之,乃悟其非。”[1]自此杨时终生笃守二程学说,他曾自述“某自抵京师,与定夫从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粗闻其绪言,虽未能窥圣学门墙,然亦不为异端(佛教)迁惑矣。”[2]而且在杨时的道学视域中,笃守己学来排斥其他异端学术,并非是政治党派性的意气之争,而是作为知道的道学学者可贵之处——能择别是非、审辨正邪,他说“自守所学以排异端即谓之立党尚气相攻,是必无择是非”“夫所贵乎知道者,谓其能别是非、审邪正也。”[3]显然,杨时将自己所学(二程所传学说)加以笃守的同时,一面以此为标尺将先秦以来的学说作了是非、正邪的判别和衡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言,在狭义上,杨时的道统观当指极力推重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的宗传;在广义上,还包括大力鞑伐儒门之外的异端之学——杨、墨、管、商等诸子之学、佛老之说、荆公新学(杨时视荆公新学非儒学,而为兼管、商、佛、老于一身的异端之学),以及批判儒门之内的儒家歧出之学(庄子之说、辞章之学、训诂之学)。他有诗句说“(儒家)末流学多岐,倚门诵韩庄(注意此处韩指韩愈、庄指庄子,此正是北宋熙宁以来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出入方寸间,雕镌事辞章。”[4]即将庄子之说和韩愈精于文辞雕镌的辞章之学认作儒家的末流歧出之学。正因北宋文化大发展时期的兼容并蓄,诸学“杂出而并传”,“异端”并逐、末流学说多歧出,使得亘千年之久的儒家圣人之道隐没不传,离圣贤之世愈来愈远。他曾称“宋兴百年,士稍知师古,诸子百氏之籍,与夫佛老荒唐谬悠之书,下迨战国纵横之论,幽人逸士浮夸诡异可喜之文章,皆杂出而并传。”“驾异端而并逐兮,骈交毂乎多岐。亘千岁其泯泯兮,去圣远而遗真。”[5]可见,在杨时道学的视域中,正是儒门之外的异端之学和儒门内部的儒家末流歧出内外两面的影响而隐没了道学的真传。
杨时从其所笃守的道学出发,对先秦以来儒门内部的儒家末流歧出,作了是非、正邪的分判和辨别。大体分而言之,在杨时那儿,儒学末流歧出有三:一是庄子之说(杨时不将庄子认作老氏道教之学,而是认作儒家末流歧出)、二是辞章之学;三是章句之学。
一、庄子之说
在杨时看来,儒家圣道之传、圣人之学到了孔子之后,春秋战国之际,因孔门弟子分处各诸侯国,其皆以他们各自所闻见到的孔子学说,传授于弟子,致使孔门儒学流衍分化,而这一分化早在战国时韩非就已经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韩非子·显学》)。而在这些分化的末流支派中,真正得孔子儒学真传者很少,比如孔子→子夏→田子方→庄子之传便是如此。这些儒学末流支派去圣道也远,未能得圣道之传,实际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宗传之外的歧出,他说“孔子殁,群弟子离散,分处诸侯之国,虽各以其所闻授弟子,然得其传者盖寡。故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为庄周,则其去本浸远矣。独曾子之后,子思、孟子之传得其宗。”[5]杨时将庄子之说看作孔子之末流后学,有孔子→子夏→田子方→庄子之歧出之传。
杨时不仅从师承谱系来论庄子为孔子之后学歧出,而且还在学说上揭示了庄子之说和孔门学说之间的相通性。他说“余顷自京师得《元道》之书阅之,喜其言无益生之祥,窃谓行之,其几于道也。及来毗陵,闻道士严奉先得卫生之经,夜卧无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问焉,听其言,殆将有意乎庄生所谓‘息以踵者也’。”[6]指出严奉先养生的方法差不多接近道教《元道》的“兀然自止者矣”的境界(此是一种自然养生观,而非延年益寿的炼养观),这种方法接近儒家圣人之道,严奉先修养生命大概追求庄子所谓“息以踵者”(真气可以遍布全身的真人的境界)的自然澄明之境,肯定了庄子“息以踵者”之说接近儒家圣人之道。而且杨时还认为庄子之说和儒学宗传的子思、孟子之说义理相通,只是与儒家圣人之说在言说方式上不同:儒家圣人所认为的寻常事,而庄子则夸大其辞,曲譬广喻,张大其说。他说“圣人以为寻常事者,庄周则夸言之。庄周之博,乃禅家呵佛骂祖之类是也。如《逍遥游》、《养生主》,曲譬广喻,张大其说。论其要,则《逍遥游》一篇,乃子思所谓‘无入而不自得’,《养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谓‘行其所无事’而已。”[7]在杨时道学看来,庄子的《逍遥游》在境界旨要上和子思《中庸》“无入而不自得”的从容中道的境界一致,《养生主》在工夫的旨要上和孟子“行其所无事”顺性而行的方法是一致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子学说在思想上有和孔孟宗传有一脉相似处,然其学说仍于孔孟宗传有不同处。这个从杨时关于颜回“屡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杨时认为,儒家所说的空是心胸中不留存外在一物、心不为外物所诱一而不杂的境界,是忘物之境,而颜回“屡空”的状态还没有达到空的境界,《答胡德辉问》载“问:‘回也其庶乎,屡空。’说者谓若庄周所谓忘仁义礼乐与夫坐忘之谓也。然下文言‘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则所谓‘空’者,非忘仁义之类也。然空必谓之‘屡’者何如?答:‘其心三月不违仁’,则盖有时而违也。然而其复不远,则其空也屡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贡货殖,未能无物也。孔门所谓货殖者,岂若世之营营者耶?特于物未能忘焉耳。”[3]言下之意,儒家所说的空不是庄子超脱人事社会活动的的忘弃“仁义礼乐”和“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境界,而是在应事接物中物不留于胸次的状态;而且颜回只是“屡空”,并未达到空的状态。杨时曾强调“学至于圣人,则一物不留于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屡空’而已。谓之‘屡空’,则有时乎不空。”[8]“屡空”是有时还不空,是颜回差不多接近空的状态,而学至于圣人则自然会有一物不留于胸中而常空的境界,而颜回则没有达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杨时道学视域中,达至见体、得道的圣人境界自然有空的境界,但学至于一物不留于胸次的常空的境界来还仍未达至见体、得道的境界,他说“‘屡空’,有时乎不空,‘三月不违仁’,则有时乎违是也。以空为学之始,而仁之体未见;至于不违仁,则仁之体见矣。未知仁以何为体?不可谓有一‘仁’字便谓仁之体见,则《论语》之言仁处多矣。以空为学之始……”[9]在杨时看来,空之境界只是使得心不为外物所诱一而不杂,这仅是为学之始,而未达到圣人之境界,圣人之境界则是见仁之体,即见仁体、得道,事事皆由自我本心仁性而行,无时无处都不违背人的本心仁性。这见仁体、得道实质就是体悟到道我一体、物我为一,正如语录所载“曰:‘安得自然如此。若体究此理,知其所从来,则仁之道不远矣。’二人退,余从容问曰:‘万物与我为一,其仁之体乎?’曰:‘然。’”[8]见仁体、得道实质即体究到万物与己一体,这也就是从容中道,从心不逾矩的状态,杨时曾言“道固与我为一也,非至于‘从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与此。”[9]只有心达到这样的状态,才也可能实现道与我为一,这不是一物不留于胸次的空所能达到的。可见,在杨时看来,庄子所说的超脱人事社会活动的的忘弃“仁义礼乐”和“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和儒家境界有着相当的差异,儒家并不超脱人事活动而是在人事活动之中作内在超越。
在杨时看来,秦以下,至汉唐,圣道不明、圣学失传,儒者往往“务为辞章”而有辞章之学,“区区于章句之末”而为训诂之学,以应对科举考试,博取功名。
二、辞章之学
在杨时看来,汉唐之儒往往多致力于辞章之学。自秦以下,汉唐儒者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韩愈、柳宗元以文赋驰骋古今,但从义理上考察他们则终究并不能真正倡道阐明道学,窥探到儒家圣人思想的内在精髓所在,故杨时认为汉唐之士以多著文章而自我满足,着力精雕辞句篇章以惊世骇俗,他说“自秦焚诗书、坑术士,六艺残缺。汉儒收拾补缀,至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若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相如、杨雄之徒继武而出,雄文大笔,驰骋古今,……积至于唐,文籍之备,盖十百前古。元和之间,韩柳辈出……自汉迄唐千余岁,而士之名能文者无过是数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学,窥圣人阃奥如古人者。”“区区于汉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务为辞章以惊眩末俗,非善学也。”[5]杨时认为,为汉唐辞章的儒者学习之勤奋,所涉猎的书籍之广博,文章内容之宏大精妙,并非今天一般儒者后学所能达到的水平,不过从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承看,则终究不被笃守儒家圣人之道的学者所称许,杨时甚至贬斥“区区汉儒不足学”,他说“汉之诸儒若贾谊、相如、司马迁辈,用力亦勤矣自书契以来,简册所存,下至阴阳星历、山经地志、虫鱼草木,殊名诡号,该洽无一或遗者,其文宏妙,殆非后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学渊源,论笃者终莫之与也。……区区汉儒不足学也。”[10]
杨时对于汉唐儒者,以杨雄和韩愈的论述最多。他对杨雄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汉唐名扬于世的大儒,只有杨雄而已,但杨雄对正道本分还没有完全尽到,仅接近道而没有做到尽道,他说“孟子没千有余岁,更汉历唐,士之名世,杨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择所处,于义命犹有未尽。”[11]“惟杨雄庶几于道,然尚恨其有未尽者。”[5]就其著述和学说之评价也与此类似,杨时认为杨雄学识超过其他汉唐儒者,但并没有把握儒家性命论(不知《易》,也就是不知性命之理),未能窥圣学门墙,他说“性命之说,虽杨雄犹未能造其藩篱,况他人乎?”[12]“杨雄作《太玄》,准《易》。此最为诳后学。……其实雄未尝知《易》。”[8]他还有具体的理论评述,语录载他批杨雄博约之说云“杨雄云:‘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其言终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为无病。盖博学详说,所以趋约;至于约,则其道得矣。谓之守以‘约’、‘卓’于多闻多见之中,将何守?”[13]杨时认为杨雄强调在多闻多见中守卓、守约不妥,不如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之说,其强调通过博学详说的手段和途径而反求简约、趋向简约,这样才得道而可以守,而杨雄在手段和途径上多闻多见方法与守约、守卓并举,问题在多闻多见学无所定则怎能有所守。他批杨雄性论说:“杨雄云:‘学所以修性。’夫物有变坏,然后可修;性无变坏,岂可修乎?唯不假修。”[13]杨雄主张性善恶混,修其善者为善,修其恶者为恶,有“学者,所以修性也”[14]的说法,杨时就此作批驳,认为,只有物坏掉才可以说修,性没有变坏,不可说修,所性不要借助于修,杨时将性作全善无恶并无变坏看,与杨雄性善恶混不同。对于韩愈,杨时虽看到其立志做孔子这样的圣人和极力排佛的功绩,但认为韩愈仍然不过是雕章镂句的辞章之学,获取当世名誉而已,其智慧还不足以明先王之道、传孔孟之学,所以其所操守不违背圣人之道的不多,他说“岂当时之士,卒无志于圣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韩愈,盖尝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则亦不可谓无其志也。及观其所学,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誉而止耳。”[5]“若唐之韩退之,今之孙明复、石守道、欧阳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数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传孔孟之学,其所守不叛于道盖寡矣”[2]杨时有诗评价到“吏部文章世所珍,终惭无补费精神。”[15]即韩愈辞章之学虽为世间所珍爱,但终究未能得圣人之道补益世教,徒费人工夫而已。这个评价从杨时对韩愈《原道》“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16]的批判可以看出,他说“韩子曰:‘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仁义,性所有也,则舍仁义而言道者,故非也;道固有仁义,而仁义不足以尽道,则以道德为虚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则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尽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顺道德而理于义’,又引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某谓若以道德为虚位,则士依于仁足矣,又奚必志于道、据于德?理与义足矣,又奚曰和顺道德?有可以和顺,有可以志据,则道德固非虚位也。”[17]韩愈认为道与德为虚位,道与德以仁义为实,杨时就此从两个角度作了批判:第一,依《中庸》“率性之谓道”和《易》“形上之道”“继善成性”来疏解,性有仁、义、礼、智等多般善,“率性”为道,离开仁义言道固然不可取,而仁义不足以尽道(性还有礼、智等多般善),显然以道与德离开仁义为虚位也不可取,即道德除仁义之外还有别的并非虚位。第二,从“和顺道德而理于义”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来看,如果认为道与德为虚位,则只要理于义就够了,不需要和顺于道与德,只要依于仁就够了,就不需要志于道、据于德,既然有可以和顺,有可以志和据,则道与德就不是虚位了。杨时因此强调道和德(仁、义、礼、智等多般善充足己)不是虚位,是一个实在。
杨时认为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即是此文章之学。他赞赏苏轼文章之成就,为当时之儒宗,学人士子得其一言足以名扬天下,他说“余窃谓东坡文妙天下,为时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5]然而又批评苏轼作诗多讥玩,无恻隐爱君情怀和温柔敦厚之气,故多得罪人,他说“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7]并在学说上,就苏辙的道论、性论作了批判。苏辙曾说“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圣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禅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之欲以道相诏者,至于一与中,尽矣。……及孔子既没,曾子传之子思。子思因其说而广之。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之说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与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为性善之论。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始枝矣。”[18]杨时则批判到“则‘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谓道者果何物耶?”“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谓‘一’者安在哉!”“夫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说也。学者更深考之,则孟子、苏氏之学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诬者矣。”[19]杨时的评述认为,“一”是姑且指称道不可用名辞概念言说的(道体),而“中”本身不是(道体),只是道之所寄在(形容道体之所在的),不是道本身,不可以中称道,道本身是什么呢?子思说为“中和”,此则是道可以用来言说的(“中和”兼体用,则道体显用则可以言说),所谓“一”又何在,即道之体用不二,哪有“一”(道体)在“中和”之中,实质即“一”就是“中和”本身;孟子说“性善”则是将天道通于人性,并未使“中”与“一”由此发生支离。可见杨时认可从三圣一直到孟子这样一脉而来对道的言说。苏辙有言“孟子学于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然而性之有习,习之有善恶,譬如火之能熟与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谓善,则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孙卿之所谓恶,则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孙卿之失则远矣。”[20]杨时批判了苏辙关于性善恶问题的探讨,他说“世儒之论曰:‘性之有习,习之有善恶,譬如火之能热与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谓善,得火之能热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谓恶,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间,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克之而火生焉。木与火未尝相离,盖子母之道也。火无形丽木而有焉,非焚之,则火之用息矣,何热之有哉?而谓热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盖亦不审矣。夫子思之学,惟孟子之传得其宗。异哉,世儒之论也,以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说而渐失之,而轻为之议,其亦不思之过欤!”[19]杨时此处从对木与火母子相生之道、焚与热的一体不二关系批驳苏辙的比喻,以论证性不是如火之能热与能焚一样的生命活动之作用,而是如火无形丽木而有的子母之道的这种生命本体本身,故焚与热并非是得性与失性、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的差异,实质孟子言性是就生命本体本身,性只是一个全善无恶的性,现实的善恶则关键在后天这个善性能否尽得还尽不得,所以孟子说性善,并未偏离子思“天命之谓性”的说法。
而在杨时看来,为何辞章之学去道远,不能明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学?原因在于这些儒家学者虽能以道自任,有志于圣人,然其为学方法往往为深探博取、支离蔓衍,而不知慎择约守,所以用力越勤、志向越坚定则离道越远,使的学者们茫然不知学习方向去路,他说“日夜惫精劳思,深探博取,可为勤矣。然其支离蔓衍,不知慎择而约守之,故其用志益劳而去道弥远,使天下学者靡然趋之”[11]辞章之儒往往以通古今博学为文,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不义之事,然而不知闻道为根本,而在杨时看来,问道则为问学之根本,强调“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他说“今时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所学,以博通古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已,而不知须是闻道故应如此。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13]而在杨时看来,圣学和圣人之道,不是儒者笔舌、辞章所言、所书能穷尽的,圣学和圣道旨归以“身体之,心验之”的亲身体验和实践而得,超越语言文字的表层的形式和表达,而重在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义理,不这样为学,则皆是辞章口耳诵数之学,背离道学,不得圣道之传,他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17]
三、章句之末
再者,在杨时看来,汉唐之儒往往“区区于章句之末”,为训诂之学。汉唐以来经传注疏盛行,无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往往各守专经研治、各有擅长,而他们往往注疏各异、相互诟病指责,他说“汉兴,诸儒守专门之学,互相疵病,至父子有异同之论”[5]如此为经传注疏的儒者,他们的著述合乎道者不超过一半,然这样不能概略地称他们为“知道者”,因为他们不符合道、不符合理的更多,他说“由汉而来,为传注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过半,然不可㮣谓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3]如此经传注疏,执着于文字分析与训诂,琐屑地辨析文章之字句,他说“类皆分文析字,屑屑于章句之末。”[5]杨时就《易》和《诗经》的研习,批评了这种“区区于章句之末”的训诂之学。在杨时看来,之所以汉魏以来,以研究《易》而闻名的将近几十上百人,不过他们的书不为士大夫批评讪笑,成为废纸用作覆盖酱瓿的没有几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区区于章句之末”,为经传注疏之学,他说“夫《易》于六经尤难知,自汉魏以来,以《易》名家者殆数十百人,观其用力之勤,盖自谓能窥天人之奥,著为成书,足以师后世。然其书具在,不为士大夫议评讪笑用覆酱瓿者无几矣。”“区区于章句之末,又安能免于讥评讪笑乎?”[2]当今学者非但作文章之学因文害辞,更大的问题是,通过分析字之偏傍以取义理(训诂方法)为训诂之学,这样怎能还会真正理解《诗》,能得《诗》之义理而传于世呢?他说“大抵今之说《诗》者,多以文害辞。非徒以文害辞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傍以取义理,如此岂复有《诗》?”[7]
这些“区区于章句之末”的训诂之学,不曾精思力究经典之义理,常常以粗浅意见和臆测,通过琐屑地文字分析与训诂,以求得圣人所言之隐微之义理,自谓有得,实质离圣人之道本真更远,他说“未尝精思力究,妄以肤见臆度,求尽圣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铢较,自谓得之,而不知去本益远。”[17]这样的章句之儒,只是琐屑地专注文字辨析与训诂,以这种方式去求圣人之道,怎能不为大方之家所耻笑,怎能求得圣人之道?他说“章句之儒,辨析声病,为科举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几何不见笑于大方之家?”[17]在杨时看来,圣人之道不仅仅依赖语言而传的,士人学者如想窥探圣学奥秘,如果执着于章句文字,就如同以千里马的外在形貌筋骨特征而求千里一样,终不可得,故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不要执着于章句之末,他说“余于是得为学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传也审矣。士欲窥圣学渊源,而区区于章句之末,是犹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马也,其可得乎?余于是书也,于牝牡有不知者盖多矣,学者能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则于余言其庶矣乎。”[5]研习经典核心要把握经典的义理、精髓,而不在其外在形式,当得意而忘言,经籍文字如同糟糠,所谓“微言窥圣域,妙应期得髓。默坐筌蹄忘,斯文亦糠粃。”[4]
四、文化意涵
综前所论,杨时不但在道统人物谱系上,明确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的宗传,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庄子之说)、辞章之学、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也在道学天道、心性、工夫方法的理论阐释中体现着贬斥汉唐以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在天道的阐释上,他批判了韩愈“道与德为虚位”和苏辙“寄之曰中”、“一和中之在是”、“孟子性善论出,一与中始枝”的说法;在心性论上,他批驳了杨雄“修性”说法和苏辙以热与焚、“得其性”和“失其性”说法论孟子性善、荀子性恶;在工夫方法论上,他批判杨雄“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之说和韩愈雕饰辞章的做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上对汉唐以来辞章、章句之学的贬斥是与其对二程传承的孔孟儒学正统(道学)的凸显是一体的。综合学界研究成果看,大体认为,杨时道学凸显了一个二程所传承的三代授受、孔孟宗传的天道、心性、工夫和境界一体的一贯之道,在天道上,杨时将《易》“形上之道”“继善成性”、《论语》道和仁、子思《中庸》“中和”“率性之道”、孟子“性善”加以阐释凸显;在心性论上,杨时将《易》“继善成性”、子思《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性善”相贯通;在工夫论上,杨时注意到曾子《大学》“格物致知”、尧舜禹“执中”、子思《中庸》“已发”“未发”、孟子“博学反约”“反身而诚”的工夫。足见,从道统人物谱系和理论阐释上,杨时道学内在地体现着贬斥辞章之学、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而凸显二程传承的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的文化意涵。甚至杨时将汉唐以来的辞章之学、章句之学贬斥为徒增闻见知识、应付科举的功名利禄之学,而远非孔孟宗传的为己之学,他说“尝窃念圣人没,逮今千数百年,学士大夫皆外诱势利,鲜克为己者。”[2]“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7]在杨时看来,这些学术之蔽非但在文化的中心和上层士人、大学者那儿,这种状况也深深影响了地方士人学子,他们也往往“诵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为章句训诂之学、科举之文,应科举博功名,杨时曾言“吾邑距中州数千里之远……故后生晚学,无所窥观,游谈戏论,不闻箴规切磨之益。……亦不过诵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为章句之儒,钓声利而已。”[6]总之,杨时在道学视域下将辞章之学、章句之学认定为儒家内部末学歧出,内在地体现了杨时道学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汉唐以来的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为末学歧出的文化意涵。而杨时的这种认定及其内在体现的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汉唐以来的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为末学歧出的文化意涵,也是二程及其其他门人的整体文化倾向。二程(主要是程颐)一面凸显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传道的统绪,程颐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21]“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22]强调二程传承的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同时二程还指出,除了儒者之学(实质即孔孟之学)的正统外,还有文章之学(辞章之学)、训诂之学(此二者相当于儒家末流歧出),乃至异端之学,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23]“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詀,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23]二程认为汉代经学事工于章句训诂,而不知经籍旨要,二程说“汉之经术安用?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且如解《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东汉则又不足道也。”[23]二程还就汉唐辞章之学的代表人物杨雄和韩愈的理论作了批判,二程认为杨雄性论有错,二程说“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杨雄,规模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24]也认为韩愈“道与德为虚位”说法不正确,二程说“(韩退之)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25]显然,作为笃守二程学说的杨时,其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的文化倾向当源自二程。与杨时一样,同事二程的程门弟子游酢、谢良佐、胡寅等也承继着其师相似的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的文化倾向。游酢在人性论上,赞赏子思“天命之谓性”和孟子的“性善”论,而贬斥杨雄的“性善恶混”和韩愈“性三品”说,他说“知天命之谓性,则孟子性善之说可见矣。或曰性恶,或曰善恶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26]“杨雄言人之性善恶混,韩愈言性有三品,盖皆蔽于末流,而不知其本也。”[26]而谢良佐指出秦汉以下,道学未能得以阐明(言下之意,包括辞章和章句之学在内的汉唐学术未得孔孟真传),尽管秦汉以下志于道、求道而为善的人并不缺乏,他说“然秦汉以来,学(道学)虽不明,而为善者不絶于天下,天下若能志于大者远者,不为目前移夺,虽是非小有失中,大体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27]而胡寅也指出,孟子以下,汉唐即便是韩愈这样的大儒也未能得邹鲁孔孟之学的精髓,最多也只是佛教戒律讲论的宗派和佛家传心直超佛地之宗的关系,他说“自韩退之而后,皆以爱命仁。则恐失之。子思传之曰:‘仁者,人也。’孟子传之曰:‘仁,人心也。’此心何处不备。独指以为爱可乎?汉、唐以来,名世儒学,往往工于训诂度数刑名,而未必知此。故曰轲之死不得其传。”[28]“惟邹、鲁之学,由秦、汉、隋、唐,莫有传授。其间名世大儒,仅如佛家者流,所谓戒律讲论之宗而已。至于言外传心,直超佛地,则未见其人。”[29]一言以蔽之,杨时与二程及游酢、谢良佐、胡寅等二程其他弟子有着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的共同的文化倾向。
杨时从其所笃守的道学出发,对先秦以来儒门内部的儒家末流歧出,作了是非、正邪的分判和辨别。大体分而言之,在杨时那儿,儒学末流歧出有三:一是庄子之说(杨时不将庄子认作老氏道教之学,而是认作儒家末流歧出)、二是辞章之学;三是章句之学。
一、庄子之说
在杨时看来,儒家圣道之传、圣人之学到了孔子之后,春秋战国之际,因孔门弟子分处各诸侯国,其皆以他们各自所闻见到的孔子学说,传授于弟子,致使孔门儒学流衍分化,而这一分化早在战国时韩非就已经指出“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韩非子·显学》)。而在这些分化的末流支派中,真正得孔子儒学真传者很少,比如孔子→子夏→田子方→庄子之传便是如此。这些儒学末流支派去圣道也远,未能得圣道之传,实际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宗传之外的歧出,他说“孔子殁,群弟子离散,分处诸侯之国,虽各以其所闻授弟子,然得其传者盖寡。故子夏之后有田子方,子方之后为庄周,则其去本浸远矣。独曾子之后,子思、孟子之传得其宗。”[5]杨时将庄子之说看作孔子之末流后学,有孔子→子夏→田子方→庄子之歧出之传。
杨时不仅从师承谱系来论庄子为孔子之后学歧出,而且还在学说上揭示了庄子之说和孔门学说之间的相通性。他说“余顷自京师得《元道》之书阅之,喜其言无益生之祥,窃谓行之,其几于道也。及来毗陵,闻道士严奉先得卫生之经,夜卧无出入息,其庶乎《元道》‘兀然自止者矣。’造其室而问焉,听其言,殆将有意乎庄生所谓‘息以踵者也’。”[6]指出严奉先养生的方法差不多接近道教《元道》的“兀然自止者矣”的境界(此是一种自然养生观,而非延年益寿的炼养观),这种方法接近儒家圣人之道,严奉先修养生命大概追求庄子所谓“息以踵者”(真气可以遍布全身的真人的境界)的自然澄明之境,肯定了庄子“息以踵者”之说接近儒家圣人之道。而且杨时还认为庄子之说和儒学宗传的子思、孟子之说义理相通,只是与儒家圣人之说在言说方式上不同:儒家圣人所认为的寻常事,而庄子则夸大其辞,曲譬广喻,张大其说。他说“圣人以为寻常事者,庄周则夸言之。庄周之博,乃禅家呵佛骂祖之类是也。如《逍遥游》、《养生主》,曲譬广喻,张大其说。论其要,则《逍遥游》一篇,乃子思所谓‘无入而不自得’,《养生主》一篇乃孟子所谓‘行其所无事’而已。”[7]在杨时道学看来,庄子的《逍遥游》在境界旨要上和子思《中庸》“无入而不自得”的从容中道的境界一致,《养生主》在工夫的旨要上和孟子“行其所无事”顺性而行的方法是一致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子学说在思想上有和孔孟宗传有一脉相似处,然其学说仍于孔孟宗传有不同处。这个从杨时关于颜回“屡空”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杨时认为,儒家所说的空是心胸中不留存外在一物、心不为外物所诱一而不杂的境界,是忘物之境,而颜回“屡空”的状态还没有达到空的境界,《答胡德辉问》载“问:‘回也其庶乎,屡空。’说者谓若庄周所谓忘仁义礼乐与夫坐忘之谓也。然下文言‘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则所谓‘空’者,非忘仁义之类也。然空必谓之‘屡’者何如?答:‘其心三月不违仁’,则盖有时而违也。然而其复不远,则其空也屡矣。空也者,不以一物置其胸中也。子贡货殖,未能无物也。孔门所谓货殖者,岂若世之营营者耶?特于物未能忘焉耳。”[3]言下之意,儒家所说的空不是庄子超脱人事社会活动的的忘弃“仁义礼乐”和“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境界,而是在应事接物中物不留于胸次的状态;而且颜回只是“屡空”,并未达到空的状态。杨时曾强调“学至于圣人,则一物不留于次,乃其常也。回未至此,‘屡空’而已。谓之‘屡空’,则有时乎不空。”[8]“屡空”是有时还不空,是颜回差不多接近空的状态,而学至于圣人则自然会有一物不留于胸中而常空的境界,而颜回则没有达到。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杨时道学视域中,达至见体、得道的圣人境界自然有空的境界,但学至于一物不留于胸次的常空的境界来还仍未达至见体、得道的境界,他说“‘屡空’,有时乎不空,‘三月不违仁’,则有时乎违是也。以空为学之始,而仁之体未见;至于不违仁,则仁之体见矣。未知仁以何为体?不可谓有一‘仁’字便谓仁之体见,则《论语》之言仁处多矣。以空为学之始……”[9]在杨时看来,空之境界只是使得心不为外物所诱一而不杂,这仅是为学之始,而未达到圣人之境界,圣人之境界则是见仁之体,即见仁体、得道,事事皆由自我本心仁性而行,无时无处都不违背人的本心仁性。这见仁体、得道实质就是体悟到道我一体、物我为一,正如语录所载“曰:‘安得自然如此。若体究此理,知其所从来,则仁之道不远矣。’二人退,余从容问曰:‘万物与我为一,其仁之体乎?’曰:‘然。’”[8]见仁体、得道实质即体究到万物与己一体,这也就是从容中道,从心不逾矩的状态,杨时曾言“道固与我为一也,非至于‘从心所欲不踰矩’者,不足以与此。”[9]只有心达到这样的状态,才也可能实现道与我为一,这不是一物不留于胸次的空所能达到的。可见,在杨时看来,庄子所说的超脱人事社会活动的的忘弃“仁义礼乐”和“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和儒家境界有着相当的差异,儒家并不超脱人事活动而是在人事活动之中作内在超越。
在杨时看来,秦以下,至汉唐,圣道不明、圣学失传,儒者往往“务为辞章”而有辞章之学,“区区于章句之末”而为训诂之学,以应对科举考试,博取功名。
二、辞章之学
在杨时看来,汉唐之儒往往多致力于辞章之学。自秦以下,汉唐儒者贾谊、董仲舒、司马迁、司马相如、杨雄、韩愈、柳宗元以文赋驰骋古今,但从义理上考察他们则终究并不能真正倡道阐明道学,窥探到儒家圣人思想的内在精髓所在,故杨时认为汉唐之士以多著文章而自我满足,着力精雕辞句篇章以惊世骇俗,他说“自秦焚诗书、坑术士,六艺残缺。汉儒收拾补缀,至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若贾谊、董仲舒、司马迁、相如、杨雄之徒继武而出,雄文大笔,驰骋古今,……积至于唐,文籍之备,盖十百前古。元和之间,韩柳辈出……自汉迄唐千余岁,而士之名能文者无过是数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学,窥圣人阃奥如古人者。”“区区于汉唐之士以多文自富,务为辞章以惊眩末俗,非善学也。”[5]杨时认为,为汉唐辞章的儒者学习之勤奋,所涉猎的书籍之广博,文章内容之宏大精妙,并非今天一般儒者后学所能达到的水平,不过从儒家圣人之道的传承看,则终究不被笃守儒家圣人之道的学者所称许,杨时甚至贬斥“区区汉儒不足学”,他说“汉之诸儒若贾谊、相如、司马迁辈,用力亦勤矣自书契以来,简册所存,下至阴阳星历、山经地志、虫鱼草木,殊名诡号,该洽无一或遗者,其文宏妙,殆非后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学渊源,论笃者终莫之与也。……区区汉儒不足学也。”[10]
杨时对于汉唐儒者,以杨雄和韩愈的论述最多。他对杨雄有很高的评价,认为汉唐名扬于世的大儒,只有杨雄而已,但杨雄对正道本分还没有完全尽到,仅接近道而没有做到尽道,他说“孟子没千有余岁,更汉历唐,士之名世,杨雄氏而止耳。雄之自择所处,于义命犹有未尽。”[11]“惟杨雄庶几于道,然尚恨其有未尽者。”[5]就其著述和学说之评价也与此类似,杨时认为杨雄学识超过其他汉唐儒者,但并没有把握儒家性命论(不知《易》,也就是不知性命之理),未能窥圣学门墙,他说“性命之说,虽杨雄犹未能造其藩篱,况他人乎?”[12]“杨雄作《太玄》,准《易》。此最为诳后学。……其实雄未尝知《易》。”[8]他还有具体的理论评述,语录载他批杨雄博约之说云“杨雄云:‘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其言终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为无病。盖博学详说,所以趋约;至于约,则其道得矣。谓之守以‘约’、‘卓’于多闻多见之中,将何守?”[13]杨时认为杨雄强调在多闻多见中守卓、守约不妥,不如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之说,其强调通过博学详说的手段和途径而反求简约、趋向简约,这样才得道而可以守,而杨雄在手段和途径上多闻多见方法与守约、守卓并举,问题在多闻多见学无所定则怎能有所守。他批杨雄性论说:“杨雄云:‘学所以修性。’夫物有变坏,然后可修;性无变坏,岂可修乎?唯不假修。”[13]杨雄主张性善恶混,修其善者为善,修其恶者为恶,有“学者,所以修性也”[14]的说法,杨时就此作批驳,认为,只有物坏掉才可以说修,性没有变坏,不可说修,所性不要借助于修,杨时将性作全善无恶并无变坏看,与杨雄性善恶混不同。对于韩愈,杨时虽看到其立志做孔子这样的圣人和极力排佛的功绩,但认为韩愈仍然不过是雕章镂句的辞章之学,获取当世名誉而已,其智慧还不足以明先王之道、传孔孟之学,所以其所操守不违背圣人之道的不多,他说“岂当时之士,卒无志于圣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韩愈,盖尝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则亦不可谓无其志也。及观其所学,则不过乎欲雕章镂句,取名誉而止耳。”[5]“若唐之韩退之,今之孙明复、石守道、欧阳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数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传孔孟之学,其所守不叛于道盖寡矣”[2]杨时有诗评价到“吏部文章世所珍,终惭无补费精神。”[15]即韩愈辞章之学虽为世间所珍爱,但终究未能得圣人之道补益世教,徒费人工夫而已。这个评价从杨时对韩愈《原道》“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16]的批判可以看出,他说“韩子曰:‘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仁义,性所有也,则舍仁义而言道者,故非也;道固有仁义,而仁义不足以尽道,则以道德为虚位者,亦非也。孔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则仁知者,乃道之一隅,果不足以尽道也。如仲敢所引‘和顺道德而理于义’,又引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某谓若以道德为虚位,则士依于仁足矣,又奚必志于道、据于德?理与义足矣,又奚曰和顺道德?有可以和顺,有可以志据,则道德固非虚位也。”[17]韩愈认为道与德为虚位,道与德以仁义为实,杨时就此从两个角度作了批判:第一,依《中庸》“率性之谓道”和《易》“形上之道”“继善成性”来疏解,性有仁、义、礼、智等多般善,“率性”为道,离开仁义言道固然不可取,而仁义不足以尽道(性还有礼、智等多般善),显然以道与德离开仁义为虚位也不可取,即道德除仁义之外还有别的并非虚位。第二,从“和顺道德而理于义”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来看,如果认为道与德为虚位,则只要理于义就够了,不需要和顺于道与德,只要依于仁就够了,就不需要志于道、据于德,既然有可以和顺,有可以志和据,则道与德就不是虚位了。杨时因此强调道和德(仁、义、礼、智等多般善充足己)不是虚位,是一个实在。
杨时认为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即是此文章之学。他赞赏苏轼文章之成就,为当时之儒宗,学人士子得其一言足以名扬天下,他说“余窃谓东坡文妙天下,为时儒宗,士有得其一言者皆足以名世,况知之之深乎?”[5]然而又批评苏轼作诗多讥玩,无恻隐爱君情怀和温柔敦厚之气,故多得罪人,他说“如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7]并在学说上,就苏辙的道论、性论作了批判。苏辙曾说“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圣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禅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之欲以道相诏者,至于一与中,尽矣。……及孔子既没,曾子传之子思。子思因其说而广之。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之说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与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为性善之论。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始枝矣。”[18]杨时则批判到“则‘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谓道者果何物耶?”“夫子思之言,‘中和’而已,此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谓‘一’者安在哉!”“夫性善之论出,而‘一’与‘中’何自而枝耶?是必有说也。学者更深考之,则孟子、苏氏之学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诬者矣。”[19]杨时的评述认为,“一”是姑且指称道不可用名辞概念言说的(道体),而“中”本身不是(道体),只是道之所寄在(形容道体之所在的),不是道本身,不可以中称道,道本身是什么呢?子思说为“中和”,此则是道可以用来言说的(“中和”兼体用,则道体显用则可以言说),所谓“一”又何在,即道之体用不二,哪有“一”(道体)在“中和”之中,实质即“一”就是“中和”本身;孟子说“性善”则是将天道通于人性,并未使“中”与“一”由此发生支离。可见杨时认可从三圣一直到孟子这样一脉而来对道的言说。苏辙有言“孟子学于子思,得其说而渐失之,……然而性之有习,习之有善恶,譬如火之能熟与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谓善,则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孙卿之所谓恶,则火之能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孙卿之失则远矣。”[20]杨时批判了苏辙关于性善恶问题的探讨,他说“世儒之论曰:‘性之有习,习之有善恶,譬如火之能热与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谓善,得火之能热者也,是火之得其性也;荀子之所谓恶,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间,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故木以金克之而火生焉。木与火未尝相离,盖子母之道也。火无形丽木而有焉,非焚之,则火之用息矣,何热之有哉?而谓热者火之得其性,焚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盖亦不审矣。夫子思之学,惟孟子之传得其宗。异哉,世儒之论也,以为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说而渐失之,而轻为之议,其亦不思之过欤!”[19]杨时此处从对木与火母子相生之道、焚与热的一体不二关系批驳苏辙的比喻,以论证性不是如火之能热与能焚一样的生命活动之作用,而是如火无形丽木而有的子母之道的这种生命本体本身,故焚与热并非是得性与失性、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的差异,实质孟子言性是就生命本体本身,性只是一个全善无恶的性,现实的善恶则关键在后天这个善性能否尽得还尽不得,所以孟子说性善,并未偏离子思“天命之谓性”的说法。
而在杨时看来,为何辞章之学去道远,不能明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学?原因在于这些儒家学者虽能以道自任,有志于圣人,然其为学方法往往为深探博取、支离蔓衍,而不知慎择约守,所以用力越勤、志向越坚定则离道越远,使的学者们茫然不知学习方向去路,他说“日夜惫精劳思,深探博取,可为勤矣。然其支离蔓衍,不知慎择而约守之,故其用志益劳而去道弥远,使天下学者靡然趋之”[11]辞章之儒往往以通古今博学为文,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不义之事,然而不知闻道为根本,而在杨时看来,问道则为问学之根本,强调“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他说“今时学者,平居则曰:‘吾当为古人之所为。’才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盖其所学,以博通古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愿悫,不为非义而已,而不知须是闻道故应如此。由是观之,学而不闻道,犹不学也。”[13]而在杨时看来,圣学和圣人之道,不是儒者笔舌、辞章所言、所书能穷尽的,圣学和圣道旨归以“身体之,心验之”的亲身体验和实践而得,超越语言文字的表层的形式和表达,而重在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义理,不这样为学,则皆是辞章口耳诵数之学,背离道学,不得圣道之传,他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于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17]
三、章句之末
再者,在杨时看来,汉唐之儒往往“区区于章句之末”,为训诂之学。汉唐以来经传注疏盛行,无论是今文经学家,还是古文经学家,往往各守专经研治、各有擅长,而他们往往注疏各异、相互诟病指责,他说“汉兴,诸儒守专门之学,互相疵病,至父子有异同之论”[5]如此为经传注疏的儒者,他们的著述合乎道者不超过一半,然这样不能概略地称他们为“知道者”,因为他们不符合道、不符合理的更多,他说“由汉而来,为传注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过半,然不可㮣谓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3]如此经传注疏,执着于文字分析与训诂,琐屑地辨析文章之字句,他说“类皆分文析字,屑屑于章句之末。”[5]杨时就《易》和《诗经》的研习,批评了这种“区区于章句之末”的训诂之学。在杨时看来,之所以汉魏以来,以研究《易》而闻名的将近几十上百人,不过他们的书不为士大夫批评讪笑,成为废纸用作覆盖酱瓿的没有几个,原因就在于他们“区区于章句之末”,为经传注疏之学,他说“夫《易》于六经尤难知,自汉魏以来,以《易》名家者殆数十百人,观其用力之勤,盖自谓能窥天人之奥,著为成书,足以师后世。然其书具在,不为士大夫议评讪笑用覆酱瓿者无几矣。”“区区于章句之末,又安能免于讥评讪笑乎?”[2]当今学者非但作文章之学因文害辞,更大的问题是,通过分析字之偏傍以取义理(训诂方法)为训诂之学,这样怎能还会真正理解《诗》,能得《诗》之义理而传于世呢?他说“大抵今之说《诗》者,多以文害辞。非徒以文害辞也,又有甚者,分析字之偏傍以取义理,如此岂复有《诗》?”[7]
这些“区区于章句之末”的训诂之学,不曾精思力究经典之义理,常常以粗浅意见和臆测,通过琐屑地文字分析与训诂,以求得圣人所言之隐微之义理,自谓有得,实质离圣人之道本真更远,他说“未尝精思力究,妄以肤见臆度,求尽圣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铢较,自谓得之,而不知去本益远。”[17]这样的章句之儒,只是琐屑地专注文字辨析与训诂,以这种方式去求圣人之道,怎能不为大方之家所耻笑,怎能求得圣人之道?他说“章句之儒,辨析声病,为科举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几何不见笑于大方之家?”[17]在杨时看来,圣人之道不仅仅依赖语言而传的,士人学者如想窥探圣学奥秘,如果执着于章句文字,就如同以千里马的外在形貌筋骨特征而求千里一样,终不可得,故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不要执着于章句之末,他说“余于是得为学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传也审矣。士欲窥圣学渊源,而区区于章句之末,是犹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马也,其可得乎?余于是书也,于牝牡有不知者盖多矣,学者能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则于余言其庶矣乎。”[5]研习经典核心要把握经典的义理、精髓,而不在其外在形式,当得意而忘言,经籍文字如同糟糠,所谓“微言窥圣域,妙应期得髓。默坐筌蹄忘,斯文亦糠粃。”[4]
四、文化意涵
综前所论,杨时不但在道统人物谱系上,明确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的宗传,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庄子之说)、辞章之学、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也在道学天道、心性、工夫方法的理论阐释中体现着贬斥汉唐以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在天道的阐释上,他批判了韩愈“道与德为虚位”和苏辙“寄之曰中”、“一和中之在是”、“孟子性善论出,一与中始枝”的说法;在心性论上,他批驳了杨雄“修性”说法和苏辙以热与焚、“得其性”和“失其性”说法论孟子性善、荀子性恶;在工夫方法论上,他批判杨雄“多闻,守之以约;多见,守之以卓。”之说和韩愈雕饰辞章的做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理论上对汉唐以来辞章、章句之学的贬斥是与其对二程传承的孔孟儒学正统(道学)的凸显是一体的。综合学界研究成果看,大体认为,杨时道学凸显了一个二程所传承的三代授受、孔孟宗传的天道、心性、工夫和境界一体的一贯之道,在天道上,杨时将《易》“形上之道”“继善成性”、《论语》道和仁、子思《中庸》“中和”“率性之道”、孟子“性善”加以阐释凸显;在心性论上,杨时将《易》“继善成性”、子思《中庸》“天命之性”、孟子“性善”相贯通;在工夫论上,杨时注意到曾子《大学》“格物致知”、尧舜禹“执中”、子思《中庸》“已发”“未发”、孟子“博学反约”“反身而诚”的工夫。足见,从道统人物谱系和理论阐释上,杨时道学内在地体现着贬斥辞章之学、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而凸显二程传承的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的文化意涵。甚至杨时将汉唐以来的辞章之学、章句之学贬斥为徒增闻见知识、应付科举的功名利禄之学,而远非孔孟宗传的为己之学,他说“尝窃念圣人没,逮今千数百年,学士大夫皆外诱势利,鲜克为己者。”[2]“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7]在杨时看来,这些学术之蔽非但在文化的中心和上层士人、大学者那儿,这种状况也深深影响了地方士人学子,他们也往往“诵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为章句训诂之学、科举之文,应科举博功名,杨时曾言“吾邑距中州数千里之远……故后生晚学,无所窥观,游谈戏论,不闻箴规切磨之益。……亦不过诵六艺之文、百家之编,为章句之儒,钓声利而已。”[6]总之,杨时在道学视域下将辞章之学、章句之学认定为儒家内部末学歧出,内在地体现了杨时道学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汉唐以来的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为末学歧出的文化意涵。而杨时的这种认定及其内在体现的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汉唐以来的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为末学歧出的文化意涵,也是二程及其其他门人的整体文化倾向。二程(主要是程颐)一面凸显了一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颢(程颐)传道的统绪,程颐说“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21]“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先生(程颢)生千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22]强调二程传承的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同时二程还指出,除了儒者之学(实质即孔孟之学)的正统外,还有文章之学(辞章之学)、训诂之学(此二者相当于儒家末流歧出),乃至异端之学,他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23]“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詀,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23]二程认为汉代经学事工于章句训诂,而不知经籍旨要,二程说“汉之经术安用?只是以章句训诂为事。且如解《尧典》二字,至三万余言,是不知要也。东汉则又不足道也。”[23]二程还就汉唐辞章之学的代表人物杨雄和韩愈的理论作了批判,二程认为杨雄性论有错,二程说“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杨雄,规模窄狭。道即性也。言性已错,更何所得?”[24]也认为韩愈“道与德为虚位”说法不正确,二程说“(韩退之)只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便乱说。”[25]显然,作为笃守二程学说的杨时,其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的文化倾向当源自二程。与杨时一样,同事二程的程门弟子游酢、谢良佐、胡寅等也承继着其师相似的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的文化倾向。游酢在人性论上,赞赏子思“天命之谓性”和孟子的“性善”论,而贬斥杨雄的“性善恶混”和韩愈“性三品”说,他说“知天命之谓性,则孟子性善之说可见矣。或曰性恶,或曰善恶混,或曰有三品,皆非知天命者也。”[26]“杨雄言人之性善恶混,韩愈言性有三品,盖皆蔽于末流,而不知其本也。”[26]而谢良佐指出秦汉以下,道学未能得以阐明(言下之意,包括辞章和章句之学在内的汉唐学术未得孔孟真传),尽管秦汉以下志于道、求道而为善的人并不缺乏,他说“然秦汉以来,学(道学)虽不明,而为善者不絶于天下,天下若能志于大者远者,不为目前移夺,虽是非小有失中,大体固已立矣。不失此心可也。”[27]而胡寅也指出,孟子以下,汉唐即便是韩愈这样的大儒也未能得邹鲁孔孟之学的精髓,最多也只是佛教戒律讲论的宗派和佛家传心直超佛地之宗的关系,他说“自韩退之而后,皆以爱命仁。则恐失之。子思传之曰:‘仁者,人也。’孟子传之曰:‘仁,人心也。’此心何处不备。独指以为爱可乎?汉、唐以来,名世儒学,往往工于训诂度数刑名,而未必知此。故曰轲之死不得其传。”[28]“惟邹、鲁之学,由秦、汉、隋、唐,莫有传授。其间名世大儒,仅如佛家者流,所谓戒律讲论之宗而已。至于言外传心,直超佛地,则未见其人。”[29]一言以蔽之,杨时与二程及游酢、谢良佐、胡寅等二程其他弟子有着凸显孔孟之学为儒学正统、贬斥辞章、章句之学为儒家末学歧出的共同的文化倾向。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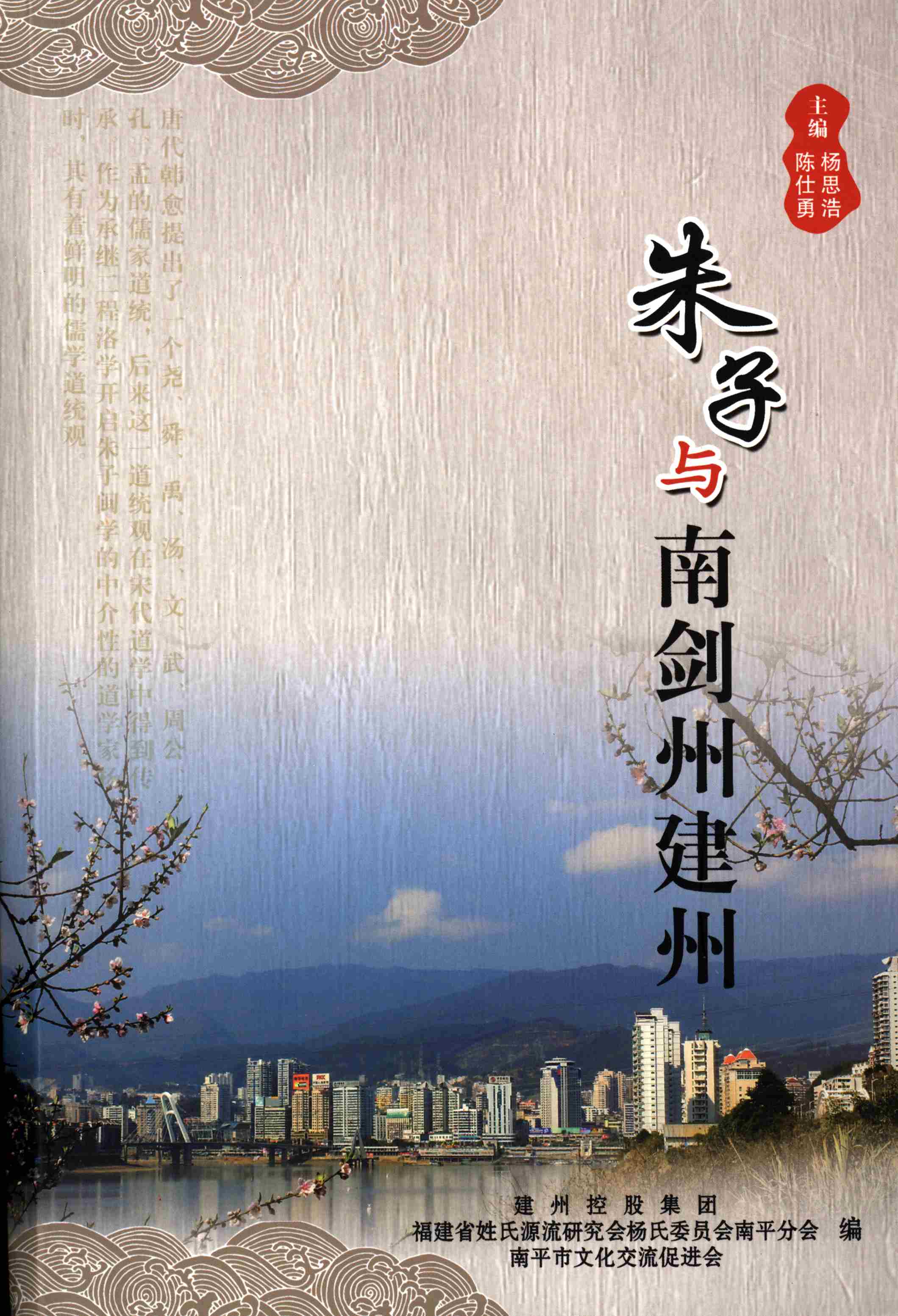
《朱子与南剑州建州》
本书围绕朱子与南剑州建州展开讨论,涉及朱熹的生平、思想、政治实践以及他在南剑州建州的文化影响等方面。同时,还探讨了杨时、李侗等儒家学者与朱熹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南剑州建州的文化传承和发展。在深入理解朱熹及其时代背景,同时探讨南剑州建州在闽学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阅读
相关人物
包佳道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