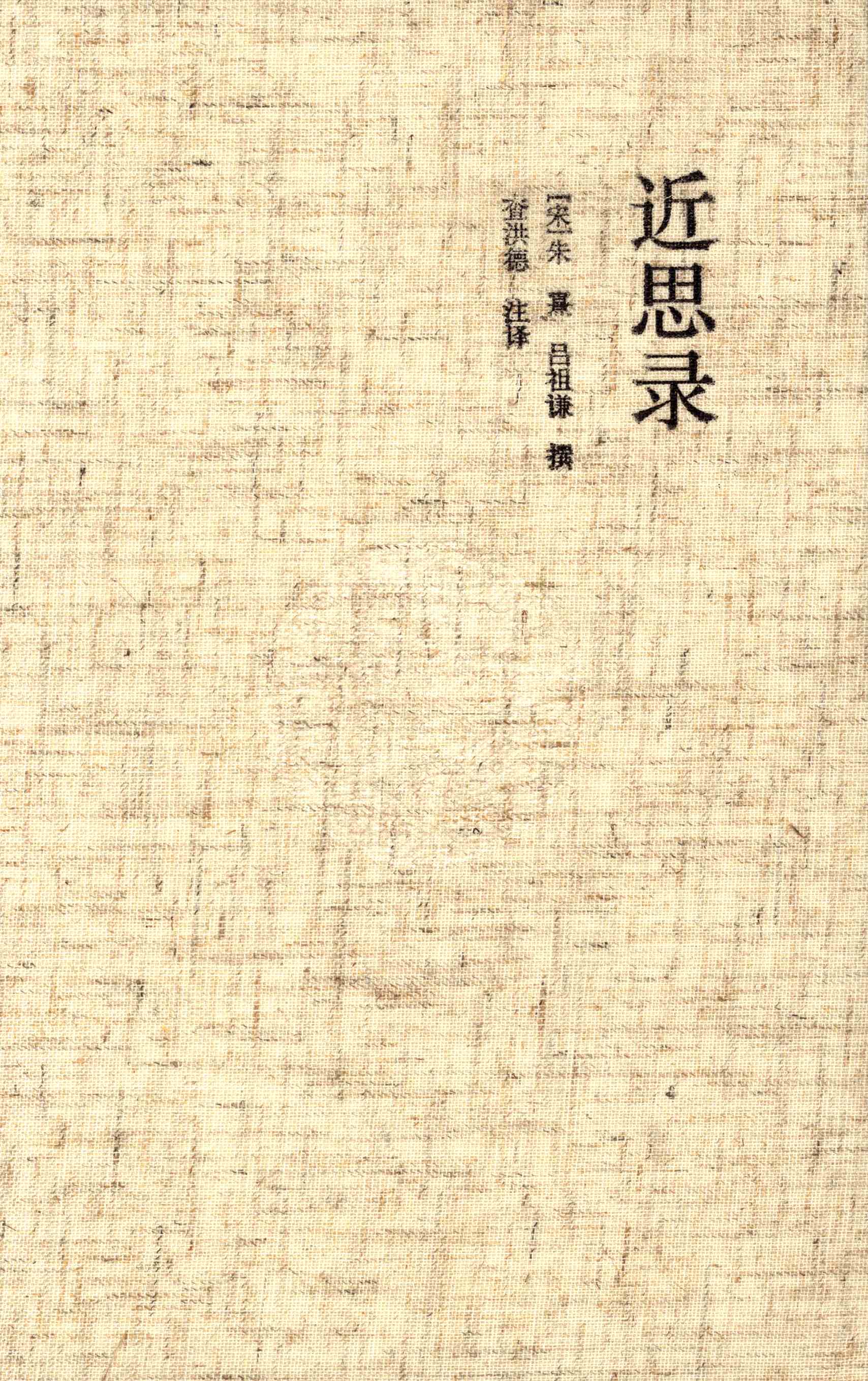内容
一 序跋
朱熹原序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谨识。
吕祖谦原序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陵节,流于空疏,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东莱吕祖谦谨书。
叶采《近思录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圣传德,跨唐越汉,上接三代统纪。而天僖、明道间,仁深泽厚,儒术兴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关发蒙,启千载无传之学。既而洛二程子,关中张子,缵承羽翼,阐而大之。圣学淹而复明,道统绝而复续,猗欤盛哉!中兴再造,崇儒务学,遹遵祖武,是以巨儒辈出,沿溯大原,考合诸论。时则朱子与吕成公,采四先生之书,条分类别,凡十四卷,名曰《近思录》,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备,本末殚举。至于辟邪说,明正宗,罔不精核洞尽,是则我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也。尝闻朱子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盖时有远近,言有详约不同,学者必自近而详者,推求远且约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学,受读是书,字求其训,句探其旨,研思积久,因成《集解》。其诸纲要,悉本朱子旧注,参以升堂纪闻,乃诸儒辩论,择其精纯,刊除繁复,以次编入。有阙略者,乃出臆说。朝删暮辑,逾三十年,义稍明备,以授家庭训习。或者谓寒乡晚出,有志苦学,而旁无师友,苟得是集观之,亦可创通大义,然后以类而推,以观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长至日,建安叶采谨序。
江永《朱子原订近思录集注序》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后,一线弗坠。有宋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与吕东莱先生,晤于寒泉精舍,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闳博无涯,恐始学不得其门,因公掇其关于大体、切于日用者,为《近思录》十四卷,凡义理根原,圣学体用,皆在此编。其于学者身心疵病,应接乖违,言之尤详,箴之极切。概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朱子尝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又谓:“《近思录》所言,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则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岂寻常之编录哉!其间义旨渊微,非注不显。考朱子朝夕与门人讲论,多及此书。或解析文义,或阐发奥理,或辨别同异,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与此相发,散见《文集》、《或问》、《语类》诸书,前人未有为之荟萃者。宋淳祐间,平岩叶氏采,进《近思录集解》,采朱子语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叶氏注,以己意别立条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细校原文,或增或复,且复脱漏讹舛,大非寒泉纂集之旧。后来刻本相仍,几不可读。永自早岁,先人授以朱子遗书原本,沉潜反复有年。今已垂暮,所学无成,日置是书案头,默自省察,以当严师。窃病近本既行,原书破碎。朱子精言,复多刊落。因仍旧本次第,裒辑朱子之言有关此录者,悉采入注。朱子说未备,乃采平岩及他氏说补之,间亦窃附鄙说,尽其余蕴。盖欲昭晰,不厌详备。由是寻绎本文,弥觉义旨深远。研之愈出,味之无穷。窃谓此录既为四子之阶梯,则此注又当为此录之牡钥,开扃发鐍,祛疑释蔽,于读者不无小补。晚学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儒先之志。既以自勖,且公诸同好,共相与砥砺焉。乾隆壬戌九月丁巳朔,婺源后学江永序。
先福《重刻近思录序》卜子云:“切问而近思。”近思云者,将以收其放心也。操之则存其固有之良,舍之则亡其本来之善。圣狂殊途,只争克念与否耳。朱子《近思录》一编,为学者切要之橐钥,所当朝夕循诵以发深省也。省厓使者视学江西,顷语余云:“江右为人文之薮,代有英贤。〓轩所及,课士命题,类多博通淹雅,斐然可观。若再勖以先儒心性经术之精,修己治人之要,其所进当不止是。”因嘱刊《近思录》,遍布学宫,俾知证向。爰与方伯、廉使、观察诸公,共商剞劂。梓成,因弁其端,并敬告以勖多士。嘉庆十九年岁在甲戌春二月初吉,长白先福谨序。
王鼎《朱子原订近思录序》
学术与治术,一以贯之者也。古之圣贤,戒慎恐惧,主敬存诚,默察乎天命民彝之本,体验于躬行实践之余,而天地之所以裁成,民物之所以发育,经曲之所以灿陈,与夫一切制度文为之淆列,而与时损益以各适其宜者,悉于是乎出。推之人心而同,放之天下而准。故学为有本之学,而治为可久之治。况夫学术醇则风尚端,胶庠稽古之士,范身名教,而乡里薰其德而善良者,效可立睹。又为裨益政教之急务乎!欧阳子曰:“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迁革,使趋于善。至于礼让兴行,而风俗醇美,然后为学之成。”诚哉是言也!国家以经义育才,自太学以迄郡、州、县,莫不立之学而设之官。教之之法,则使人日诵习五经四子书,以讲求义理之精,为升选登进之阶。海内之士,争自濯磨,学术画然一出于正,以应朝廷之选者,盖百七十余年矣。窃尝思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治以协天地之大同。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秦火以后,汉之江都,隋之河汾,唐之昌黎,皆能阐发道义,力任正学。然或见其本而倚于偏,或窥其广大而未及乎精微。其他纷纭舛错,解经而不得圣人之用心者,指不胜屈。于异端害道,又何责焉?宋周、程、张、朱诸大贤出,剖晰于理欲之微,并进乎知行之功,密动静之交养,见内外之合一,由小学以及大学,由治己而推之治世,巨细精粗,本末始终,莫不同条而共贯,体立而用行,然后千古之道统治法,灿然以明,而后世得有所取法。今科场功令命题,一本五经四子书。其援引传说,必以朱子为断。诚以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夫圣人之道,高矣美矣。而朱子引之以近圣人,尽其性推而行之,以尽人物之情,极于赞化育,参天地。而朱子则教学者慎之于思。昔吕东莱先生过于寒泉精舍,朱子留与阅周、程、张四家之书,择其切实粹精,裨于性情心术之正,人生日用之恒,经世宰物之宜者,得六百二十二条,分为十四卷,名曰《近思录》,其后往复商榷,久而始定,以此为下学切要工夫,且曰:“《近思录》,四子书之阶梯;四子书,五经之阶梯也。”然则士生圣教昌明之会,诵圣贤之书,志圣贤之志,学圣贤之学,以仰体圣人之化育者,舍是书其何以为阶哉!嘉庆壬申冬,余奉命视学江右。抵任后,循例按试各郡。恭绎先皇“饬士习,厚风俗,正人心”之喻,兢兢与士子相勖以实学,爰取《近思录》为入德门户。士之颖异者,翕然知所尊尚,而潜心研究之子,亦时能陈其意蕴。顾其所读本,率皆近世汪氏、施氏之编,且坊刻歧误甚多,非复朱子之旧矣。忆予廿年前,得婺源江氏慎修集注,极为完善,十年前又得大兴朱文正公与徽人之宦京师者新刻江氏本,合而校之,藏诸箧中。因出以商诸中丞芝圃先公,重为刊刻,遍示学宫弟子。公曰:“善。”遂与方伯柏田袁公、廉访孟岩盛公暨僚属等输赀发刊,起癸酉冬十一月,越次年夏五月告成,按学分大小而周布之,盖人人得善本焉。夫是书自朱子手订后,淳祐中,叶氏采《集解》,一遵原本。其后周公恕分标细目,移动本文,破碎纠纷,不免漏落妄增之讥。新安朱氏本,或节去本文,或以本文讹入分注,又或讹叶注为本文,谬伪滋甚,大率沿周氏本而益误也。汪氏、施氏,又取朱子语附益其中,复引后儒之说发明之,均失原编之义。兹刻江氏集注,标名曰《朱子原订近思录》,从其朔也。
余惟古昔教育人才之法,莫重于学。而学宫之制,我朝更详备于古。学所以求道也,道成己而成物者也。士君子穷经致用,思圣天子振兴文治,广励师儒之意,原欲使经正民兴,俾乡有善俗,国有真才也。其服习必于仁义,而所学必求衷诸正,不矜博览章句之能,尽捐富贵利达之见。一志虑之专,以戒夫浮薄之失;殚切磋之益,而致力夫道德之精。以之持己,则诚而明;以之式俗,则顺而祥;以之处家国天下之事,无所施而不当。则必于《近思录》基之。体认既熟,于以读四子书,始恍然于义理之悦我心。由四子书而研穷诸经,益恍然于唐虞三代之学与治。运用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亘万古而不易,然后博稽史传,考制作之得失,验人心之邪正,自釐然以辨,而不蔽以偏私。由是取以公卿大夫百职事之选,才皆预定,而设施亦皆素所习闻。即偶处乡曲,而训俗型方,亦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事也,岂不休哉!若夫拘守是书而不复旁通,徒事口耳而不求心得,甚或摭拾腐说,支离傅会,而一毫无裨于实用,反使记诵之学嗤其陋,词章之学哂其拙,此则蹈嘉定以来末学谈理之流弊,非今日刊刻之意矣。读者幸鉴余之苦心也夫。嘉庆十有九年岁次甲戌夏五月,关中王鼎序并书。
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序》
子朱子纂辑周、程、张四先生之书以为《近思录》,盖古圣贤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实具于此,而与《大学》一书相发明者也。故其书篇目,要不外三纲领、八条目之间,而子朱子亦往往以《小学》并称,意可见矣。先君子默存先生尝手录是书,俾不肖星来受而卒业,谓曰:“此圣道阶梯也。”星来反复寻绎,久而稍觉有得,颇思博求注解以资参讨,顾今坊间所行者,惟建安叶氏《集解》而已,杨氏泳斋《衍注》,则藏书家仅有存者,星来尝取读之,粗率肤浅,于是书了无发明,又都解所不必解,其有稍费拟议处则阙焉。至于中间彼此错乱,字句舛讹。以二子亲承朱子绪论,而其为书乃如此,其他又何论乎?然则彼穷乡晚进,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虽使有志于学,得是书而玩心焉,亦恐终无以得其门而入矣。星来用是,不揣固陋,辄购取四先生全书及宋元来《近思录》本,为之校正其异同得失,其先后次第,悉仍其旧。旧本舛错,仿朱氏《论》、《孟》重出错简之例,注明其下,不敢擅自更易也。本既定,然后乃敢会萃众说,参以愚见,支分节解,不留疑窦。其名物训诂,虽非是书所重,亦必详其本末,庶几为学者多识之一助。又仿朱氏《论》、《孟》附《史记》世家、列传例,取《伊洛渊源录》中四先生事状,删其繁复,为之注释,以附简端。盖是二书相为表里,且以见录中所言,实可见诸施行,四先生固已小用之而小效也。其与朱子未尽合处,亦以愚见斟酌从违,使会归于一也。盖星来悉心探讨,随得随记,亦已有年。期于是书粗有所补,弆之箧衍,以为后之有志于学者取焉。康熙辛丑七月七日,归安茅星来序。
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后序》
《近思录集注》既成,或疑名物训诂非是书所重,胡考订援据之不惮烦为?曰:此正愚注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而后之言程朱之学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间,而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于是彼稍稍知究心古学者,辄用是为诟病,以谓道学之说兴而经学寝微。噫!何言之甚欤?夫道者所以为儒之具也,而学也者,所以治其具也。故人不学则不知道,不知道则不可以为儒,而不通知古今则不可以言学。夫经,其本也。不通经,则虽欲博观今古,亦泛滥而无所归也。《宋史》离而二之,过矣。伊川分学者为三,曰文章,曰训诂,曰儒者。夫六经皆文章也,其异同疑似,为之博考而详辨之,即训诂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非儒者之训诂乎?然则文章也,训诂也,而儒者之所以为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间。然而伊川且必欲别儒于文章、训诂之外者,何也?盖欲求儒者之道于文章、训诂中则可,而欲以文章、训诂尽儒者之道则不可。其本末先后之间,固有辨也。奈之何进训诂、章句之学于儒林,而反别道学于儒之外?其无识可谓甚也。夫道学与政术判为二事,横渠犹病之,况离道学与儒而二之耶?甚矣其蔽也!盖尝窃论之: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长短轻重也。微权度则货之长短轻重不见,而非百货所聚,则虽有权度亦无所用之矣。故愚尝以谓:欲求程、朱之学者,其必自马、郑诸传疏始。愚故于是编,备著汉唐诸家之说,以见程朱诸先生之有本,俾彼空疏寡学者,无得以藉口焉。乾隆元年正月之望,归安后学茅星来谨识。
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序》
集群圣之成者,孔子也。删定往训,垂为六经,而道统治法备焉。集诸儒之成者,朱子也。采摭遗书,作《近思录》,而性功王事该焉。夫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圣,使不得孔子继起而绍述之,则《诗》、《书》、《礼》、《乐》,虽识大识小之有人,而残缺裂灭之余,谁为阐圣言于来祀?以周子、程子、张子诸儒之贤,使不得朱子会萃而表章之,微文大义,所与及门授受而讲贯者,即未尽泯没于庐山之阜,伊洛之滨,关中之所传贻,然而斯人徒与,寥落几何?一脉绵延,安恃不堕?况其时又有介甫之坚僻,杨、刘之纤巧,佛老之寂灭虚无,浸淫渐染,卒难铲除,其势皆足为吾道敌。惟子朱子承先启后,崇正辟邪,振寰宇之心思,开一时之聋聩,亟取周子、二程子、张子各书,采其关于大体、切于日用者,辑为是录,俾学者寻绎玩味,心解力行,庶几自近及远,自卑升高,而诐、淫、邪、遁不能淆,训诂、词章不得而汩没焉。此则许鲁斋所称入圣之基,而朱子亦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者也。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圣,得孔子而益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虽贤,不亦得朱子而益著哉!我皇上德迈唐虞,学配孔孟,性功与王猷并懋,道统偕治法兼隆。故六经四子而外,每于濂洛关闽四氏之书,加意振兴,以宏教育。近复特颁盛典,俎豆宫墙,跻朱子于十哲之次,诚以集群圣之成者孔子,用是师表于万世;集诸儒之成者朱子,故能启佑乎后人也。伯行束发受书,垂五十余年,兢兢焉以周程张朱为标准,而于朱子是录,尤服膺弗失。间尝纂集诸说,谬为疏解,极知浅陋无当,然藉是以与天下之有志者,端厥趋向,淬厉濯磨,毋厌卑近而骛高远,毋觊凌躐而遁虚无,然后优柔厌饫,有先后次序,所谓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以不负先儒谆复诲诱之心也,于是乎士希贤而贤希圣,其以维持道脉,光辅圣朝,斯文之盛未艾矣。爰命李生丹桂、史生大范校梓,而书此以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夏谷旦,仪封后学张伯行题于姑苏之正谊堂。
尹会一《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序》
子朱子有言:“修身大法,《小学》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诚以二书固圣道之阶梯,学者所宜亟尽心也。自人骛词章,此二书或罕寓目。欲以入道,难矣。余备官淮海,以商士请,因安定故祠辟书院,延余同年友王罕皆太史为师。既进诸生,屡申《小学》,尤欲以《近思录》与讲明而切究焉。仪封张先生《集解》,致为晓畅,惜版已漫灭,乃与太史商重锓之。盖太史故尝讲学于先生之门,而余亦获交嗣君西铭宪副,窃闻庭训,得藉手兹编,广先生教泽,余二人实厚幸焉。按《集解》旧节四十余条,先生当自有意,顾念后出晚进,未睹朱子原编,兹悉为增列。采宋叶平岩先生辑注参补之,欲学者得尽见此书之全也。谨序。乾隆元年丙辰夏五,博陵后学尹会一书于维扬使院。
赵氏《近思录跋》
朱子、吕子相与讲明伊洛之学,取其言之简而要者,集为是书,要使学者知所趣向,譬如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涂路,则千里虽远,行无不至矣。然其间亦有平居师友相问答之际,尽意倾吐,义已切至,而语不暇择者,学者得其意、玩其辞可也,不然,徒高远其言,诡异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学云云者。”则甚非朱、吕所以为书之意也(《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十七)。
李承端《近思录集注跋》
前秋谒相国石君师,出《近思录集注》抄本语端曰:“江先生辑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至为精切。虽非时儒所好,然使是书得行,必将有读之而兴起者。用裨益于世道人心不浅。夫人必能体程朱之心,然后能为程朱之学。躬行实践,岂在多言?以江先生之发挥汉学,著述等身,考据家莫不宗仰。至其深入奥窔,研悦而羽翼之,则知者鲜矣。”端受书退,因与锐斋汪君互相校雠,订其讹舛,请正于师,醵资授梓。今校成,不幸师不及见,未得一序言为可惜也。然其表章正学以迪后进之盛心,于兹刻盖三致意云。
嘉庆十二年丁卯春正月,婺源后学李承端谨识。
二 江永集注本辑朱熹论《近思录》
朱子答吕伯恭曰:《近思录》向时嫌其太高,去却数段,如太极及明道论性之类者。今看得似不可无。如以颜子论为首,却非专论道体,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三段。又事亲居家,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缓,今欲别作一卷,令在“出处”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数段,不知于尊意如何?此书若欲行之,须更得老兄数字,附于目录之后,致丁宁之意为佳。千万勿吝也。
又曰:《近思录》数段已补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见教。所欲移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
答汪易直曰:《近思录》,此间书坊别刊得一本,卷尾有所增,已附入卷中矣。
答宋泽之曰:《近思录》比旧本增多数条,如“买椟还珠”之论,尤可以警今日学者用心之谬。家仪乡仪,亦有补于风教。幸勿以为空言而轻读之也。
答宋深之曰:熹自十四五时得河南程先生、横渠张先生两家之书读之,至今四十余年,但觉其义之深,指之远。而近世纷纷所谓文章议论者,殆不足复过眼,信乎孟氏以来,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无以信其必然也。旧尝择其言之近者,别为一书,名曰《近思录》,幸细读之。
答李子能曰:程先生说“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若只于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众理自著,日用应接,各有条理矣。《近思录》前三四卷,专说此事。
答窦文卿曰:知日诵四书,时时省察,此意甚善。《近思录》说得近世学问规模病痛亲切,更能兼看亦佳。
答或人曰:《近思录》本为学者不能遍观诸先生之书,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渐。若已看得浃洽通晓,自当推类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数卷之书,尚不能晓会,何暇尽案头边所载之书,而悉观之乎?
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
《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
《近思录》大率所录杂,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处事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一段在。
《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或言《近思录》中语,甚有切身处。曰:圣贤说得语言平,如《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皆平易。《近思录》是近来人语,便较切。
且熟看《大学》了,即读《语》、《孟》,《近思录》又难看。
《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为此也。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却不如《语》《孟》只是平铺说去,可以游心。
看《近思录》若于第一卷未晓得,且从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后看第一卷,则渐晓得。
问:蜚卿《近思录》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这文字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子细看来看去,却自中间有个路陌。推寻通得四五十条后,却又只是一个道理。伊川云:“穷理岂是一日穷得尽。”穷得多后,道理自然通彻。
因论《近思录》,曰:“不当编《易传》所载。”问:“如何?”曰:“公须自见。”意谓《易传》已自成书。
东见录中明道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云云,极好,当添入《近思录》。
《遗书·晁氏客语》卷中,张思叔记程先生语云:“思欲格物,则已近道”一段甚好,当收入《近思录》。
横渠语录,用关陕方言,甚者皆不可晓。《近思录》所载皆易晓者。因论《近思续录》,曰:如今书已尽多了,更有,却看不辩。
三 叶采集解本各卷小序
卷一道体: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
卷二为学:此卷总论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斯可究为学之大凡矣。
卷三致知:此卷论致知。知之至而后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总论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于读书,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总论读书之法,三十四段以后,乃分论读书之法,而以书之先后为序。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化,故继之以《易》;理之明,义之精,而达乎造化之蕴,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则可推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横渠易说》以下,则仍语录之序,而《周官》之义,因以具焉。
卷四存养:此卷论存养。盖穷格之虽至,而涵养之不足,则其知将日昏,而亦何以为力行之地哉!故存养之功,实贯乎知行,而此卷之编,列乎二者之间也。
卷五克治:此卷论力行。盖穷理既明,涵养既厚,及推于行己之间,尤当尽其克治之功也。
卷六家道:此卷论齐家。盖克己之功既至,则施之家而家可齐矣。
卷七出处:此卷论出处。盖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义之从,所当审处也。
卷八治体:此卷论治道。盖明乎出处之义,则于治道之纲领,不可不求讲明之。一旦得时行道,则举而措之矣。
卷九治法:此卷论治法。盖治本虽立,而治具不容缺,礼乐刑政有一之未备,未足以成极治之功也。
卷十政事:此卷论临政处事。盖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则施于有政矣。凡居官任职,事上抚下,待同列,选贤才,处世之道具焉。
卷十一教学:此卷论教人之道。盖君子进则推斯道以觉天下,退则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谓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卷十二警戒:此卷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常存警省之意。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恶日积矣。
卷十三辨异端:此卷辨异端。盖君子之学虽已至,然异端之辨,尤不可不明。苟于此有毫厘之未辨,则贻害于人心者甚矣。
卷十四观圣贤:此卷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断自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楚有荀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
四 茅星来《附说》辑评
朱子曰: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则《近思录》详之。
又曰:《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又曰:圣贤说得语言平。如《大学》、《中庸》、《语》、《孟》皆平易。《近思录》是近人说话,便较切。
又曰:《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又曰:《近思录》比旧本增多数条,如“买椟还珠”之论,尤可以警今日学者用心之谬。
又曰:《近思录》文字,猝乍看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仔细看来看去,却自中间有个路脉。推寻通得四五十条,又却只是一个道理。
又曰:向编《近思录》,欲入数段说科举坏人心术处,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个病根从彼时已栽种培养得在心田里了,令人痛恨。
又曰:《易传》自是成书,伯恭都摭来作阃范,今亦载在《近思录》。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细点检来,段段皆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缺者,于学者甚有益。
又曰:程子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薛氏曰:《近思录》宜熟读,其间有与朱子不同者须参考。
胡氏曰:学者当就《小学》、《近思录》熟读体验,有所得方可博观今古。
张氏曰:学者能读《近思录》,方可以治经。
又曰:予年二十五六时,求《近思录》不可得,适贾人持至,因得读之,然后稍知为学之门。
姚氏曰:予丁卯馆锦村,有出《近思录》宋刻相示,录中凡先圣贤与诸先生必空一字,想朱子原本式也。五卷末较他本多一条。后于友人处得杨泳斋《衍注》阅之,注甚约而精要亦少。其书实宋刻,但嫌其中多载章句、集注语。盖此时章句、集注未行世,而门人只以师说示学者故也。但与前所见本又有不尽同者。杨名伯岩,字彦瞻,朱子门人。
五 《四库全书总目》各本《近思录》提要
叶采集解本提要:按《年谱》,是书成于淳熙二年,朱子年四十六矣。书前有朱子题词,曰:“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云云。是其书与吕祖谦同定,朱子固自著之,且并载祖谦题词。又《晦庵集》中有乙未八月与祖谦一书,又有丙申与祖谦一书,戊戌与祖谦一书,皆商榷改定《近思录》,灼然可证。《宋史·艺文志》尚并题朱熹、吕祖谦类编。后来讲学家力争门户,务黜众说而定一尊,遂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非其实也。书凡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门,实为后来性理诸书之祖。然朱子之学,大旨主于格物穷理,由博反约,根株六经,而参观百氏,原未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故题词有曰:“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止,则非纂集此书之意。”然则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为限,亦岂教人株守是编,而一切圣经贤传束之高阁哉?又吕祖谦题词,论首列阴阳性命之故曰:“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往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自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凌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药连篇累牍,动谈未有天地之前者矣。其《集解》则朱子没后叶采所补作。淳熙十二年,采官朝奉郎,监登闻鼓院,兼景献府教授,时尝赍进于朝,前有进表及自序。采字仲圭,号平岩,建安人。其自序谓悉本朱子旧注,参以升堂纪闻及诸儒辨论,有阙略者,乃出臆说。又举其大旨,著于各卷之下,凡阅三十年而后成云。
又:《近思录》十四卷,宋朱子与吕祖谦所共辑。盖周张二程之书,宏深奥衍。承学之士,莫由得其涯涘。朱子虑其不知所择,因与祖谦分类缉纂,以成是书。独取《太极图说》、《易通》、《西铭》、《正蒙》、《经学理窟》、《二程遗书》、《易传》,而于邵子之书则从姑舍,盖其慎也。书以《近思》名,盖取“切问近思”之义,俾学者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骛于高远。论者谓为五经之阶梯,信不诬欤!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其后因有续而广之者,亦堪辅翼,而权舆之精,无过是编云(前为载于《总目》者,此为载于《四库全书》中《近思录》卷首者)。
茅星来集注本提要:星来字岂宿,乌程人,康熙间诸生。按朱子《近思录》,宋以来注者数家,惟叶采《集解》至今盛行,星来病其粗率肤浅,解所不必解,而稍费拟议者则阙。又多彼此错乱,字句讹舛。因取周张二程全书,及宋元《近思录》刊本,参校同异。凡近刻舛错者,悉从朱子考正错简之例,各注本条之下。又荟萃众说,参以己见,为之支分节解。于名物训诂,考证尤详。更以《伊洛渊源录》所载四子事迹,具为笺释,冠于简端,谓之《附说》。书成于康熙辛丑,有星来自序。又有后序一篇,作于乾隆丙辰,去书成时十五年,盖殚一生之精力为之也。其后序有曰:“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而言程朱之学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间,不复通经学古为事。盖尝窃论之: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轻重长短者也。微权度,则货之轻重长短不见;而非百货所聚,则虽有权度亦无所用之。故欲求程朱之学者,其必自马、郑诸传疏始。愚于是编,备著汉唐诸家之说,以见程、朱诸先生学之有本,俾彼空疏寡学者无得以藉口”云云。其持论光明洞达,无党同伐异,争名求胜之私,可谓能正其心术矣。
江永集注本提要:案《朱子年谱》,《近思录》成于淳熙二年,其后又数经删补。然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书为先后,而不及标立篇名。至淳祐间,叶采纂为《集解》,表进于朝。虽阐发不免少略,尚无所窜乱于其间。明代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立细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注语,谬误几不可读。永以其贻误后学,因仍原本次第为之集注。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说有未备,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洽。盖永邃于经学,究心古义,穿穴于典籍者深,虽以余力为此书,亦具有实征,与讲学之家空谈尊朱者异也。
李文炤集解本提要:是编取朱子之说散见各书者,附于《近思录》各条之下。其未备者,则益以诸家之说,间亦附己意。前有纲领数条,末附《感应诗》解一卷,《训子诗》解一卷。《感应诗》见《朱子大全集》,《训子诗》称传自黄幹,而无可证据,其诗浅俗,决非朱子所为也。
朱熹原序
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盖凡学者所以求端用力、处己治人,与夫所以辨异端、观圣贤之大略,皆粗见其梗概,以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如此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沉潜反复,优柔厌饫,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则其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则非今日所以纂集此书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谨识。
吕祖谦原序
《近思录》既成,或疑首卷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祖谦窃尝与闻次缉之意,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具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几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陵节,流于空疏,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览者宜详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东莱吕祖谦谨书。
叶采《近思录集解序》
皇宋受命,列圣传德,跨唐越汉,上接三代统纪。而天僖、明道间,仁深泽厚,儒术兴行。天相斯文,是生濂溪周子,抽关发蒙,启千载无传之学。既而洛二程子,关中张子,缵承羽翼,阐而大之。圣学淹而复明,道统绝而复续,猗欤盛哉!中兴再造,崇儒务学,遹遵祖武,是以巨儒辈出,沿溯大原,考合诸论。时则朱子与吕成公,采四先生之书,条分类别,凡十四卷,名曰《近思录》,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备,本末殚举。至于辟邪说,明正宗,罔不精核洞尽,是则我宋之一经,将与四子并列,诏后学而垂无穷也。尝闻朱子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盖时有远近,言有详约不同,学者必自近而详者,推求远且约者,斯可矣。采年在志学,受读是书,字求其训,句探其旨,研思积久,因成《集解》。其诸纲要,悉本朱子旧注,参以升堂纪闻,乃诸儒辩论,择其精纯,刊除繁复,以次编入。有阙略者,乃出臆说。朝删暮辑,逾三十年,义稍明备,以授家庭训习。或者谓寒乡晚出,有志苦学,而旁无师友,苟得是集观之,亦可创通大义,然后以类而推,以观四先生之大全,亦“近思”之意云。淳祐戊申长至日,建安叶采谨序。
江永《朱子原订近思录集注序》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后,一线弗坠。有宋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与吕东莱先生,晤于寒泉精舍,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闳博无涯,恐始学不得其门,因公掇其关于大体、切于日用者,为《近思录》十四卷,凡义理根原,圣学体用,皆在此编。其于学者身心疵病,应接乖违,言之尤详,箴之极切。概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朱子尝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又谓:“《近思录》所言,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则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岂寻常之编录哉!其间义旨渊微,非注不显。考朱子朝夕与门人讲论,多及此书。或解析文义,或阐发奥理,或辨别同异,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与此相发,散见《文集》、《或问》、《语类》诸书,前人未有为之荟萃者。宋淳祐间,平岩叶氏采,进《近思录集解》,采朱子语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叶氏注,以己意别立条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细校原文,或增或复,且复脱漏讹舛,大非寒泉纂集之旧。后来刻本相仍,几不可读。永自早岁,先人授以朱子遗书原本,沉潜反复有年。今已垂暮,所学无成,日置是书案头,默自省察,以当严师。窃病近本既行,原书破碎。朱子精言,复多刊落。因仍旧本次第,裒辑朱子之言有关此录者,悉采入注。朱子说未备,乃采平岩及他氏说补之,间亦窃附鄙说,尽其余蕴。盖欲昭晰,不厌详备。由是寻绎本文,弥觉义旨深远。研之愈出,味之无穷。窃谓此录既为四子之阶梯,则此注又当为此录之牡钥,开扃发鐍,祛疑释蔽,于读者不无小补。晚学幸生朱子之乡,取其遗编,辑而释之,或亦儒先之志。既以自勖,且公诸同好,共相与砥砺焉。乾隆壬戌九月丁巳朔,婺源后学江永序。
先福《重刻近思录序》卜子云:“切问而近思。”近思云者,将以收其放心也。操之则存其固有之良,舍之则亡其本来之善。圣狂殊途,只争克念与否耳。朱子《近思录》一编,为学者切要之橐钥,所当朝夕循诵以发深省也。省厓使者视学江西,顷语余云:“江右为人文之薮,代有英贤。〓轩所及,课士命题,类多博通淹雅,斐然可观。若再勖以先儒心性经术之精,修己治人之要,其所进当不止是。”因嘱刊《近思录》,遍布学宫,俾知证向。爰与方伯、廉使、观察诸公,共商剞劂。梓成,因弁其端,并敬告以勖多士。嘉庆十九年岁在甲戌春二月初吉,长白先福谨序。
王鼎《朱子原订近思录序》
学术与治术,一以贯之者也。古之圣贤,戒慎恐惧,主敬存诚,默察乎天命民彝之本,体验于躬行实践之余,而天地之所以裁成,民物之所以发育,经曲之所以灿陈,与夫一切制度文为之淆列,而与时损益以各适其宜者,悉于是乎出。推之人心而同,放之天下而准。故学为有本之学,而治为可久之治。况夫学术醇则风尚端,胶庠稽古之士,范身名教,而乡里薰其德而善良者,效可立睹。又为裨益政教之急务乎!欧阳子曰:“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迁革,使趋于善。至于礼让兴行,而风俗醇美,然后为学之成。”诚哉是言也!国家以经义育才,自太学以迄郡、州、县,莫不立之学而设之官。教之之法,则使人日诵习五经四子书,以讲求义理之精,为升选登进之阶。海内之士,争自濯磨,学术画然一出于正,以应朝廷之选者,盖百七十余年矣。窃尝思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治以协天地之大同。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秦火以后,汉之江都,隋之河汾,唐之昌黎,皆能阐发道义,力任正学。然或见其本而倚于偏,或窥其广大而未及乎精微。其他纷纭舛错,解经而不得圣人之用心者,指不胜屈。于异端害道,又何责焉?宋周、程、张、朱诸大贤出,剖晰于理欲之微,并进乎知行之功,密动静之交养,见内外之合一,由小学以及大学,由治己而推之治世,巨细精粗,本末始终,莫不同条而共贯,体立而用行,然后千古之道统治法,灿然以明,而后世得有所取法。今科场功令命题,一本五经四子书。其援引传说,必以朱子为断。诚以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夫圣人之道,高矣美矣。而朱子引之以近圣人,尽其性推而行之,以尽人物之情,极于赞化育,参天地。而朱子则教学者慎之于思。昔吕东莱先生过于寒泉精舍,朱子留与阅周、程、张四家之书,择其切实粹精,裨于性情心术之正,人生日用之恒,经世宰物之宜者,得六百二十二条,分为十四卷,名曰《近思录》,其后往复商榷,久而始定,以此为下学切要工夫,且曰:“《近思录》,四子书之阶梯;四子书,五经之阶梯也。”然则士生圣教昌明之会,诵圣贤之书,志圣贤之志,学圣贤之学,以仰体圣人之化育者,舍是书其何以为阶哉!嘉庆壬申冬,余奉命视学江右。抵任后,循例按试各郡。恭绎先皇“饬士习,厚风俗,正人心”之喻,兢兢与士子相勖以实学,爰取《近思录》为入德门户。士之颖异者,翕然知所尊尚,而潜心研究之子,亦时能陈其意蕴。顾其所读本,率皆近世汪氏、施氏之编,且坊刻歧误甚多,非复朱子之旧矣。忆予廿年前,得婺源江氏慎修集注,极为完善,十年前又得大兴朱文正公与徽人之宦京师者新刻江氏本,合而校之,藏诸箧中。因出以商诸中丞芝圃先公,重为刊刻,遍示学宫弟子。公曰:“善。”遂与方伯柏田袁公、廉访孟岩盛公暨僚属等输赀发刊,起癸酉冬十一月,越次年夏五月告成,按学分大小而周布之,盖人人得善本焉。夫是书自朱子手订后,淳祐中,叶氏采《集解》,一遵原本。其后周公恕分标细目,移动本文,破碎纠纷,不免漏落妄增之讥。新安朱氏本,或节去本文,或以本文讹入分注,又或讹叶注为本文,谬伪滋甚,大率沿周氏本而益误也。汪氏、施氏,又取朱子语附益其中,复引后儒之说发明之,均失原编之义。兹刻江氏集注,标名曰《朱子原订近思录》,从其朔也。
余惟古昔教育人才之法,莫重于学。而学宫之制,我朝更详备于古。学所以求道也,道成己而成物者也。士君子穷经致用,思圣天子振兴文治,广励师儒之意,原欲使经正民兴,俾乡有善俗,国有真才也。其服习必于仁义,而所学必求衷诸正,不矜博览章句之能,尽捐富贵利达之见。一志虑之专,以戒夫浮薄之失;殚切磋之益,而致力夫道德之精。以之持己,则诚而明;以之式俗,则顺而祥;以之处家国天下之事,无所施而不当。则必于《近思录》基之。体认既熟,于以读四子书,始恍然于义理之悦我心。由四子书而研穷诸经,益恍然于唐虞三代之学与治。运用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亘万古而不易,然后博稽史传,考制作之得失,验人心之邪正,自釐然以辨,而不蔽以偏私。由是取以公卿大夫百职事之选,才皆预定,而设施亦皆素所习闻。即偶处乡曲,而训俗型方,亦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事也,岂不休哉!若夫拘守是书而不复旁通,徒事口耳而不求心得,甚或摭拾腐说,支离傅会,而一毫无裨于实用,反使记诵之学嗤其陋,词章之学哂其拙,此则蹈嘉定以来末学谈理之流弊,非今日刊刻之意矣。读者幸鉴余之苦心也夫。嘉庆十有九年岁次甲戌夏五月,关中王鼎序并书。
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序》
子朱子纂辑周、程、张四先生之书以为《近思录》,盖古圣贤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实具于此,而与《大学》一书相发明者也。故其书篇目,要不外三纲领、八条目之间,而子朱子亦往往以《小学》并称,意可见矣。先君子默存先生尝手录是书,俾不肖星来受而卒业,谓曰:“此圣道阶梯也。”星来反复寻绎,久而稍觉有得,颇思博求注解以资参讨,顾今坊间所行者,惟建安叶氏《集解》而已,杨氏泳斋《衍注》,则藏书家仅有存者,星来尝取读之,粗率肤浅,于是书了无发明,又都解所不必解,其有稍费拟议处则阙焉。至于中间彼此错乱,字句舛讹。以二子亲承朱子绪论,而其为书乃如此,其他又何论乎?然则彼穷乡晚进,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虽使有志于学,得是书而玩心焉,亦恐终无以得其门而入矣。星来用是,不揣固陋,辄购取四先生全书及宋元来《近思录》本,为之校正其异同得失,其先后次第,悉仍其旧。旧本舛错,仿朱氏《论》、《孟》重出错简之例,注明其下,不敢擅自更易也。本既定,然后乃敢会萃众说,参以愚见,支分节解,不留疑窦。其名物训诂,虽非是书所重,亦必详其本末,庶几为学者多识之一助。又仿朱氏《论》、《孟》附《史记》世家、列传例,取《伊洛渊源录》中四先生事状,删其繁复,为之注释,以附简端。盖是二书相为表里,且以见录中所言,实可见诸施行,四先生固已小用之而小效也。其与朱子未尽合处,亦以愚见斟酌从违,使会归于一也。盖星来悉心探讨,随得随记,亦已有年。期于是书粗有所补,弆之箧衍,以为后之有志于学者取焉。康熙辛丑七月七日,归安茅星来序。
茅星来《近思录集注后序》
《近思录集注》既成,或疑名物训诂非是书所重,胡考订援据之不惮烦为?曰:此正愚注之所以作也。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而后之言程朱之学者,往往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间,而不复以通经学古为事,于是彼稍稍知究心古学者,辄用是为诟病,以谓道学之说兴而经学寝微。噫!何言之甚欤?夫道者所以为儒之具也,而学也者,所以治其具也。故人不学则不知道,不知道则不可以为儒,而不通知古今则不可以言学。夫经,其本也。不通经,则虽欲博观今古,亦泛滥而无所归也。《宋史》离而二之,过矣。伊川分学者为三,曰文章,曰训诂,曰儒者。夫六经皆文章也,其异同疑似,为之博考而详辨之,即训诂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儒者之文章乎?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非儒者之训诂乎?然则文章也,训诂也,而儒者之所以为儒者,要未始不存乎其间。然而伊川且必欲别儒于文章、训诂之外者,何也?盖欲求儒者之道于文章、训诂中则可,而欲以文章、训诂尽儒者之道则不可。其本末先后之间,固有辨也。奈之何进训诂、章句之学于儒林,而反别道学于儒之外?其无识可谓甚也。夫道学与政术判为二事,横渠犹病之,况离道学与儒而二之耶?甚矣其蔽也!盖尝窃论之: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长短轻重也。微权度则货之长短轻重不见,而非百货所聚,则虽有权度亦无所用之矣。故愚尝以谓:欲求程、朱之学者,其必自马、郑诸传疏始。愚故于是编,备著汉唐诸家之说,以见程朱诸先生之有本,俾彼空疏寡学者,无得以藉口焉。乾隆元年正月之望,归安后学茅星来谨识。
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序》
集群圣之成者,孔子也。删定往训,垂为六经,而道统治法备焉。集诸儒之成者,朱子也。采摭遗书,作《近思录》,而性功王事该焉。夫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圣,使不得孔子继起而绍述之,则《诗》、《书》、《礼》、《乐》,虽识大识小之有人,而残缺裂灭之余,谁为阐圣言于来祀?以周子、程子、张子诸儒之贤,使不得朱子会萃而表章之,微文大义,所与及门授受而讲贯者,即未尽泯没于庐山之阜,伊洛之滨,关中之所传贻,然而斯人徒与,寥落几何?一脉绵延,安恃不堕?况其时又有介甫之坚僻,杨、刘之纤巧,佛老之寂灭虚无,浸淫渐染,卒难铲除,其势皆足为吾道敌。惟子朱子承先启后,崇正辟邪,振寰宇之心思,开一时之聋聩,亟取周子、二程子、张子各书,采其关于大体、切于日用者,辑为是录,俾学者寻绎玩味,心解力行,庶几自近及远,自卑升高,而诐、淫、邪、遁不能淆,训诂、词章不得而汩没焉。此则许鲁斋所称入圣之基,而朱子亦谓“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者也。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圣,得孔子而益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虽贤,不亦得朱子而益著哉!我皇上德迈唐虞,学配孔孟,性功与王猷并懋,道统偕治法兼隆。故六经四子而外,每于濂洛关闽四氏之书,加意振兴,以宏教育。近复特颁盛典,俎豆宫墙,跻朱子于十哲之次,诚以集群圣之成者孔子,用是师表于万世;集诸儒之成者朱子,故能启佑乎后人也。伯行束发受书,垂五十余年,兢兢焉以周程张朱为标准,而于朱子是录,尤服膺弗失。间尝纂集诸说,谬为疏解,极知浅陋无当,然藉是以与天下之有志者,端厥趋向,淬厉濯磨,毋厌卑近而骛高远,毋觊凌躐而遁虚无,然后优柔厌饫,有先后次序,所谓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以不负先儒谆复诲诱之心也,于是乎士希贤而贤希圣,其以维持道脉,光辅圣朝,斯文之盛未艾矣。爰命李生丹桂、史生大范校梓,而书此以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夏谷旦,仪封后学张伯行题于姑苏之正谊堂。
尹会一《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序》
子朱子有言:“修身大法,《小学》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诚以二书固圣道之阶梯,学者所宜亟尽心也。自人骛词章,此二书或罕寓目。欲以入道,难矣。余备官淮海,以商士请,因安定故祠辟书院,延余同年友王罕皆太史为师。既进诸生,屡申《小学》,尤欲以《近思录》与讲明而切究焉。仪封张先生《集解》,致为晓畅,惜版已漫灭,乃与太史商重锓之。盖太史故尝讲学于先生之门,而余亦获交嗣君西铭宪副,窃闻庭训,得藉手兹编,广先生教泽,余二人实厚幸焉。按《集解》旧节四十余条,先生当自有意,顾念后出晚进,未睹朱子原编,兹悉为增列。采宋叶平岩先生辑注参补之,欲学者得尽见此书之全也。谨序。乾隆元年丙辰夏五,博陵后学尹会一书于维扬使院。
赵氏《近思录跋》
朱子、吕子相与讲明伊洛之学,取其言之简而要者,集为是书,要使学者知所趣向,譬如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涂路,则千里虽远,行无不至矣。然其间亦有平居师友相问答之际,尽意倾吐,义已切至,而语不暇择者,学者得其意、玩其辞可也,不然,徒高远其言,诡异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学云云者。”则甚非朱、吕所以为书之意也(《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十七)。
李承端《近思录集注跋》
前秋谒相国石君师,出《近思录集注》抄本语端曰:“江先生辑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至为精切。虽非时儒所好,然使是书得行,必将有读之而兴起者。用裨益于世道人心不浅。夫人必能体程朱之心,然后能为程朱之学。躬行实践,岂在多言?以江先生之发挥汉学,著述等身,考据家莫不宗仰。至其深入奥窔,研悦而羽翼之,则知者鲜矣。”端受书退,因与锐斋汪君互相校雠,订其讹舛,请正于师,醵资授梓。今校成,不幸师不及见,未得一序言为可惜也。然其表章正学以迪后进之盛心,于兹刻盖三致意云。
嘉庆十二年丁卯春正月,婺源后学李承端谨识。
二 江永集注本辑朱熹论《近思录》
朱子答吕伯恭曰:《近思录》向时嫌其太高,去却数段,如太极及明道论性之类者。今看得似不可无。如以颜子论为首,却非专论道体,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三段。又事亲居家,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缓,今欲别作一卷,令在“出处”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数段,不知于尊意如何?此书若欲行之,须更得老兄数字,附于目录之后,致丁宁之意为佳。千万勿吝也。
又曰:《近思录》数段已补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见教。所欲移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
答汪易直曰:《近思录》,此间书坊别刊得一本,卷尾有所增,已附入卷中矣。
答宋泽之曰:《近思录》比旧本增多数条,如“买椟还珠”之论,尤可以警今日学者用心之谬。家仪乡仪,亦有补于风教。幸勿以为空言而轻读之也。
答宋深之曰:熹自十四五时得河南程先生、横渠张先生两家之书读之,至今四十余年,但觉其义之深,指之远。而近世纷纷所谓文章议论者,殆不足复过眼,信乎孟氏以来,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无以信其必然也。旧尝择其言之近者,别为一书,名曰《近思录》,幸细读之。
答李子能曰:程先生说“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若只于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众理自著,日用应接,各有条理矣。《近思录》前三四卷,专说此事。
答窦文卿曰:知日诵四书,时时省察,此意甚善。《近思录》说得近世学问规模病痛亲切,更能兼看亦佳。
答或人曰:《近思录》本为学者不能遍观诸先生之书,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渐。若已看得浃洽通晓,自当推类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数卷之书,尚不能晓会,何暇尽案头边所载之书,而悉观之乎?
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
《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近思录》逐篇纲目:一道体;二为学大要;三格物穷理;四存养;五改过迁善,克己复礼;六齐家之道;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八治国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处事之方;十一教学之道;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十三异端之学;十四圣贤气象。
《近思录》大率所录杂,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处事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一段在。
《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或言《近思录》中语,甚有切身处。曰:圣贤说得语言平,如《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皆平易。《近思录》是近来人语,便较切。
且熟看《大学》了,即读《语》、《孟》,《近思录》又难看。
《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为此也。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却不如《语》《孟》只是平铺说去,可以游心。
看《近思录》若于第一卷未晓得,且从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后看第一卷,则渐晓得。
问:蜚卿《近思录》看得如何?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这文字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子细看来看去,却自中间有个路陌。推寻通得四五十条后,却又只是一个道理。伊川云:“穷理岂是一日穷得尽。”穷得多后,道理自然通彻。
因论《近思录》,曰:“不当编《易传》所载。”问:“如何?”曰:“公须自见。”意谓《易传》已自成书。
东见录中明道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云云,极好,当添入《近思录》。
《遗书·晁氏客语》卷中,张思叔记程先生语云:“思欲格物,则已近道”一段甚好,当收入《近思录》。
横渠语录,用关陕方言,甚者皆不可晓。《近思录》所载皆易晓者。因论《近思续录》,曰:如今书已尽多了,更有,却看不辩。
三 叶采集解本各卷小序
卷一道体: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
卷二为学:此卷总论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斯可究为学之大凡矣。
卷三致知:此卷论致知。知之至而后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总论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于读书,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总论读书之法,三十四段以后,乃分论读书之法,而以书之先后为序。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化,故继之以《易》;理之明,义之精,而达乎造化之蕴,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则可推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横渠易说》以下,则仍语录之序,而《周官》之义,因以具焉。
卷四存养:此卷论存养。盖穷格之虽至,而涵养之不足,则其知将日昏,而亦何以为力行之地哉!故存养之功,实贯乎知行,而此卷之编,列乎二者之间也。
卷五克治:此卷论力行。盖穷理既明,涵养既厚,及推于行己之间,尤当尽其克治之功也。
卷六家道:此卷论齐家。盖克己之功既至,则施之家而家可齐矣。
卷七出处:此卷论出处。盖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义之从,所当审处也。
卷八治体:此卷论治道。盖明乎出处之义,则于治道之纲领,不可不求讲明之。一旦得时行道,则举而措之矣。
卷九治法:此卷论治法。盖治本虽立,而治具不容缺,礼乐刑政有一之未备,未足以成极治之功也。
卷十政事:此卷论临政处事。盖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则施于有政矣。凡居官任职,事上抚下,待同列,选贤才,处世之道具焉。
卷十一教学:此卷论教人之道。盖君子进则推斯道以觉天下,退则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谓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卷十二警戒:此卷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常存警省之意。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恶日积矣。
卷十三辨异端:此卷辨异端。盖君子之学虽已至,然异端之辨,尤不可不明。苟于此有毫厘之未辨,则贻害于人心者甚矣。
卷十四观圣贤:此卷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断自唐尧虞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楚有荀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
四 茅星来《附说》辑评
朱子曰: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则《近思录》详之。
又曰:《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
又曰:圣贤说得语言平。如《大学》、《中庸》、《语》、《孟》皆平易。《近思录》是近人说话,便较切。
又曰:《近思录》一书,无不切人身、救人病者。
又曰:《近思录》比旧本增多数条,如“买椟还珠”之论,尤可以警今日学者用心之谬。
又曰:《近思录》文字,猝乍看也是难,有时前面恁地说,后面又不是恁地。这里说得如此,那里又却不如此。仔细看来看去,却自中间有个路脉。推寻通得四五十条,又却只是一个道理。
又曰:向编《近思录》,欲入数段说科举坏人心术处,而伯恭不肯。今日乃知此个病根从彼时已栽种培养得在心田里了,令人痛恨。
又曰:《易传》自是成书,伯恭都摭来作阃范,今亦载在《近思录》。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细点检来,段段皆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缺者,于学者甚有益。
又曰:程子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薛氏曰:《近思录》宜熟读,其间有与朱子不同者须参考。
胡氏曰:学者当就《小学》、《近思录》熟读体验,有所得方可博观今古。
张氏曰:学者能读《近思录》,方可以治经。
又曰:予年二十五六时,求《近思录》不可得,适贾人持至,因得读之,然后稍知为学之门。
姚氏曰:予丁卯馆锦村,有出《近思录》宋刻相示,录中凡先圣贤与诸先生必空一字,想朱子原本式也。五卷末较他本多一条。后于友人处得杨泳斋《衍注》阅之,注甚约而精要亦少。其书实宋刻,但嫌其中多载章句、集注语。盖此时章句、集注未行世,而门人只以师说示学者故也。但与前所见本又有不尽同者。杨名伯岩,字彦瞻,朱子门人。
五 《四库全书总目》各本《近思录》提要
叶采集解本提要:按《年谱》,是书成于淳熙二年,朱子年四十六矣。书前有朱子题词,曰:“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云云。是其书与吕祖谦同定,朱子固自著之,且并载祖谦题词。又《晦庵集》中有乙未八月与祖谦一书,又有丙申与祖谦一书,戊戌与祖谦一书,皆商榷改定《近思录》,灼然可证。《宋史·艺文志》尚并题朱熹、吕祖谦类编。后来讲学家力争门户,务黜众说而定一尊,遂没祖谦之名,但称朱子《近思录》,非其实也。书凡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门,实为后来性理诸书之祖。然朱子之学,大旨主于格物穷理,由博反约,根株六经,而参观百氏,原未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故题词有曰:“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诚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矣。然后求诸四君子之全书,以致其博而反诸约焉,庶乎其有以尽得之。若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止,则非纂集此书之意。”然则四子之言,且不以此十四卷为限,亦岂教人株守是编,而一切圣经贤传束之高阁哉?又吕祖谦题词,论首列阴阳性命之故曰:“后出晚进,于义理之本原,虽未容骤语,苟茫然不识其梗概,则亦何所底?列之篇端,特使知其名义,有所向往而已。至于余卷所载讲学之方,日用躬行之实,自有科级。循是而进,自卑升高,自近及远,庶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厌卑近而骛高远,躐等凌节,流于空虚,迄无所依据,则岂所谓‘近思’者耶?”其言著明深切,尤足药连篇累牍,动谈未有天地之前者矣。其《集解》则朱子没后叶采所补作。淳熙十二年,采官朝奉郎,监登闻鼓院,兼景献府教授,时尝赍进于朝,前有进表及自序。采字仲圭,号平岩,建安人。其自序谓悉本朱子旧注,参以升堂纪闻及诸儒辨论,有阙略者,乃出臆说。又举其大旨,著于各卷之下,凡阅三十年而后成云。
又:《近思录》十四卷,宋朱子与吕祖谦所共辑。盖周张二程之书,宏深奥衍。承学之士,莫由得其涯涘。朱子虑其不知所择,因与祖谦分类缉纂,以成是书。独取《太极图说》、《易通》、《西铭》、《正蒙》、《经学理窟》、《二程遗书》、《易传》,而于邵子之书则从姑舍,盖其慎也。书以《近思》名,盖取“切问近思”之义,俾学者致力于日用之实,而不使骛于高远。论者谓为五经之阶梯,信不诬欤!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其后因有续而广之者,亦堪辅翼,而权舆之精,无过是编云(前为载于《总目》者,此为载于《四库全书》中《近思录》卷首者)。
茅星来集注本提要:星来字岂宿,乌程人,康熙间诸生。按朱子《近思录》,宋以来注者数家,惟叶采《集解》至今盛行,星来病其粗率肤浅,解所不必解,而稍费拟议者则阙。又多彼此错乱,字句讹舛。因取周张二程全书,及宋元《近思录》刊本,参校同异。凡近刻舛错者,悉从朱子考正错简之例,各注本条之下。又荟萃众说,参以己见,为之支分节解。于名物训诂,考证尤详。更以《伊洛渊源录》所载四子事迹,具为笺释,冠于简端,谓之《附说》。书成于康熙辛丑,有星来自序。又有后序一篇,作于乾隆丙辰,去书成时十五年,盖殚一生之精力为之也。其后序有曰:“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二,而言程朱之学者,但求之身心性命之间,不复通经学古为事。盖尝窃论之:马、郑、贾、孔之说经,譬则百货之所聚也。程朱诸先生之说经,譬则操权度以平百货之轻重长短者也。微权度,则货之轻重长短不见;而非百货所聚,则虽有权度亦无所用之。故欲求程朱之学者,其必自马、郑诸传疏始。愚于是编,备著汉唐诸家之说,以见程、朱诸先生学之有本,俾彼空疏寡学者无得以藉口”云云。其持论光明洞达,无党同伐异,争名求胜之私,可谓能正其心术矣。
江永集注本提要:案《朱子年谱》,《近思录》成于淳熙二年,其后又数经删补。然各卷之中,惟以所引之书为先后,而不及标立篇名。至淳祐间,叶采纂为《集解》,表进于朝。虽阐发不免少略,尚无所窜乱于其间。明代有周公恕者,始妄加分析,各立细目,移置篇章。或漏落正文,或淆混注语,谬误几不可读。永以其贻误后学,因仍原本次第为之集注。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说有未备,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洽。盖永邃于经学,究心古义,穿穴于典籍者深,虽以余力为此书,亦具有实征,与讲学之家空谈尊朱者异也。
李文炤集解本提要:是编取朱子之说散见各书者,附于《近思录》各条之下。其未备者,则益以诸家之说,间亦附己意。前有纲领数条,末附《感应诗》解一卷,《训子诗》解一卷。《感应诗》见《朱子大全集》,《训子诗》称传自黄幹,而无可证据,其诗浅俗,决非朱子所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