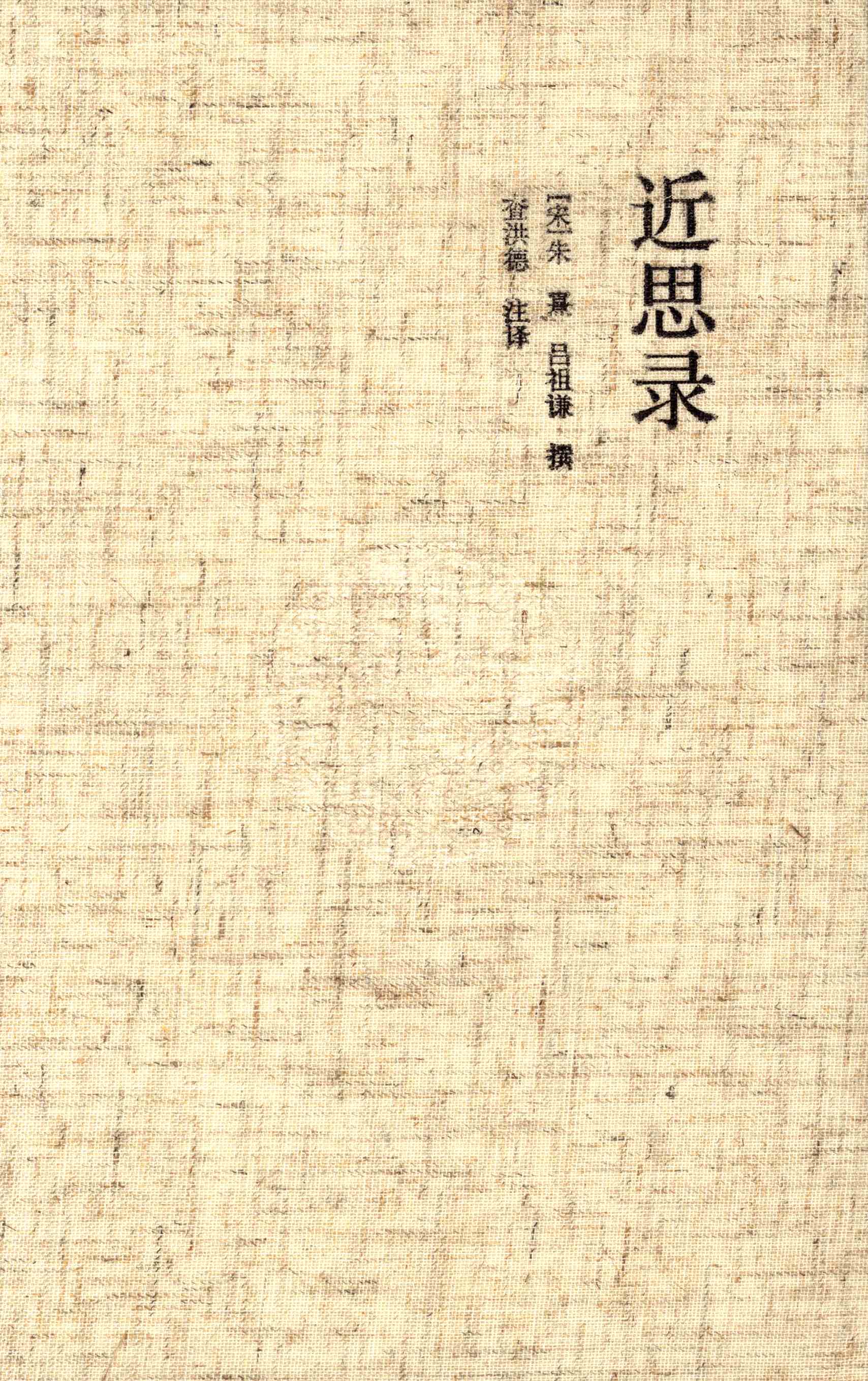内容
14.1 明道先生曰:尧、舜更无优劣,及至汤、武便别。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无人如此说,只孟子分别出来,便知得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文王之德则似尧、舜,禹之德则似汤、武。①要之皆是圣人。
——《二程遗书》卷二上
[注释]
①《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又《尽心下》:“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之,是说出于本性之自然,不习而得,不勉而中。反之,是说通过修习恢复其本善之性。
[译文]
程颢说:尧和舜再分不得优劣,及至商汤和周武王,就有了区别。孟子说:“尧、舜的仁德是出于自然的本性”,“汤、武的仁德是恢复了其本然的善性”,自古没有人这么说,只有孟子分别出来,便可知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周文王之德则近似于尧、舜,大禹之德则近似于汤、武。总之都是圣人。
14.2 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①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焉而已。②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③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④ ——《二程遗书》卷五
[注释]
①此条反复形容孔子(仲尼)、颜回(颜子)、孟子气象之不同。张伯行解:“夫子阴阳合德,不刚不柔,太和充满,众理渊涵,如一元之气,浑沦溥博,自然而然,无二无间,此圣不可知者也。颜子则亚圣之资,盎若春阳,蔼若春风,万物发荣滋润,到处皆有生意。”“孟子亦亚圣之才,而有刚明果毅整齐严肃之意”,“所谓并秋杀尽见者。”元气:古人所谓天地未分前的混沌之气。春生:春天生物气象。秋杀:指秋天萧飒之气。孟子批杨、墨,好辩,厉声色。②《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张伯行解:“元气贯通四时,则无所不包,此仲尼之道全德备,非一善可名者也。春意发生,则有自然之和气,此颜子之‘不违,如愚’,与圣人合德,令后世可以想见,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秋爽气清,高旷轩朗,此孟子之英气发越,为露其才,盖亦战国之时,异端滋炽,又无夫子主盟其上,故其卫道之严,距邪之力,不得不然者也。”③气象:指人的气度,气局,风神,景象。宋龚昱《乐庵语录》卷五:“如舜孳孳为善,想其气象必是个温良恭顺底人。”近人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之《近思录随劄》有对于气象的解说,可参考。张伯行解:“天地无心而成化,虽日发育万物,人莫得窥其迹者也。仲尼一理浑然,泛应曲当,如是焉已。风云变化,虽不知其所以然,而微有迹可见,如颜子为仁之问,喟然之叹,庶乎可以窥测其微也。泰山岩岩,壁立万仞,其中景物,昭布森列,如《孟子》一书,发挥透露,不留余蕴,其迹著明也。”④张伯行解:“明者,心无渣滓,人欲尽而天理见也。快者,心无系累,万物一体而因物付物也,所谓气质清明、义理昭著,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是也。”“岂,和乐也。弟,谦逊也。”岂弟:即恺悌,也作恺弟,和乐平易。《左传》僖公十二年:“《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杜预注:“恺,乐也;悌,易也。”
[译文]
孔子含蓄博大,圣不可知,就如天地一元之气;颜回之祥和就如春风春雨之发育生长万物之意;孟子抨击异端邪说之严厉就表现出秋天肃杀之气。孔子道全德备,一切之善无不包含,颜回以“不违背孔子的话,像是迟钝”的学习精神展示给后世,有一种自然和气,使后世之人不言而自化。孟子则显露出自己的才气,那也是时势使他如此的呀。孔子的无不覆无不载,高明博厚就如天地;颜回就如和风庆云一样有一种和气祥光;孟子的刚强峻拔直如泰山壁立的山岩气象。观察他们语言的不同风格就可以明白了。孔子之道与天地浑然一体,无迹可寻,颜回则微露些迹象,孟子则是心迹昭著,发挥透彻。孔子全然是一个明快人,颜回全是谦和,孟子全是雄辩。
14.3 曾子传圣人学,①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如言“吾得正而毙”②,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后人虽有好言语,只被气象卑,终不类道。
——《二程遗书》卷十五
[注释]
①《论语》一书,记载孔子弟子一般称字,独曾参、有若二人称“子”,故前人多认为《论语》由他们特别是曾参的学生纂述。又据前人考证,曾子为孔子正传并开以后的思孟学派。《孟子外书》记:“曼丘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何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曾子:曾参。②《礼记·檀弓上》载,曾参病将死,而所铺为大夫才能用的席子,曾参一定要换掉,说:“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正而毙:规规矩矩合乎礼地死去。
[译文]
曾参传授圣人之学,其德行后来日益上进到不可测量的地步,怎么知道他没有达到圣人的高度呢?如他说“我只求规规矩矩合礼地死去”,且不要推敲文字,只看他气度极好,他所看到的是大处。后人虽然也有些好的言语,只因为气度卑下,到底也不像个有道的人。
14.4 传经为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已差。①圣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则几乎息矣。道何尝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厉不由也。”② ——《二程遗书》卷十七
[注释]
①孔子之后,至战国时期,儒家分为八派,按《韩非子·显学》之说,“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二程所继承的,是子思、孟子递相传授的思孟学派,此派以外的,在程氏看来,均为“有差”。子思,名孔伋,孔子之孙,相传为曾参的学生,而孟子又学于子思门人。②见董仲舒《对贤良策》。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周代无道之君。
[译文]
传授圣人的典籍学说是很困难的,如孔子死后才百十年,传授就已经有了偏差。孔子的学说,如果不是子思、孟子的发扬,则几乎要熄灭了。圣人之道何曾熄灭过,只是人们不实行。就如董仲舒说的:“周文王、武王的思想并没有消亡,只是幽王、厉王不实行。”
14.5 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①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荀卿:即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思想家。扬雄:又作杨雄,西汉思想家、文学家。叶采解:“荀卿才高,敢为异论,如以人性为恶,以子思、孟子为非,其过多;扬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拟《易》,《法言》以拟《论语》,皆模仿前圣之遗言,其过少。”
[译文]
荀子才识高远,敢为异说,故其过错也较多;扬雄才识短浅,刻意模仿圣贤,故其过错也较少。
14.6 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已自不识性,更说甚道?① ——《二程遗书》卷十九
[注释]
①荀子人性论与孟子对立,主性恶,《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扬雄则主人性善恶混,《法言·修身》:“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二程继承孟子的性善论,故批荀、扬之说。
[译文]
荀子的学说极其偏失驳杂,只一句“性恶”,根本就错了;扬雄虽然少有过错,但他既然不懂得性,还谈论什么道?
14.7 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① ——《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注释]
①见《汉书·董仲舒传》。朱熹说,此语是“不论利害,只论是非”。谊:同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本仁祖谊,褒有德,禄贤能。”谊,即义。度越:超越。诸子:指孟子之后汉唐诸儒。
[译文]
董仲舒说:“搞正确什么是义与不义,而不去谋求利益;讲明圣人之道而不计较功效。”这就是董仲舒超过诸子的原因所在。
14.8 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人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①下此至于扬雄,规模又窄狭矣。② ——《二程遗书》卷一
[注释]
①毛苌:或作毛长,汉时人,传《诗经》,为河间献王博士。所谓得圣人之意,张伯行以为:“毛以修身齐家为论治之要,董以正谊明道为格君之本是也。”见道不分明,朱熹以为:“如董云性者生之质”,“似不识本然之性”。“毛公诗传,紧要有数处”,“要之亦不多见,只是气象大概好耳”。②扬雄规模窄狭,朱熹解:“学老氏将取固与之术,卒为莽大夫,非儒者规模,其窄狭又甚矣。”莽指王莽。王莽篡汉,扬雄校书天禄阁,官至大夫。
[译文]
汉代的儒者如毛苌、董仲舒,最能理解圣人之意,但对圣人之道认识得不够分明。他们之下就挨到了扬雄,其规模就更窄狭了。
14.9 林希①谓扬雄为禄隐。扬雄,后人只为见他著书,便须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②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林希:宋人,字子中,长乐人。《宋元学案》入《荆公新学案》(卷九十八),王安石婿。又《宋元学案》卷九十六《元祐学案》列入所附“攻元祐之学者”。②张伯行解:“扬子云失身事莽,大节已亏,而人犹以为禄隐。禄隐者,道不行而浮沉下位也。子云固如是哉?人但见其所著书奥衍深僻,诧其有才,便要说他是。”其书“亦不知道而作,徒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怎有是处?”做他是:肯定他。
[译文]
林希说扬雄是食禄的隐士。扬雄这人,后人只看到他写了书,便要肯定他,怎么能够肯定呢?
14.10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若刘表子琮,将为曹公所并,取而兴刘氏,可也。① ——《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注释]
①孔明:诸葛亮,字孔明,佐刘备创立蜀汉。《孟子·公孙丑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刘璋:字季,益州牧刘焉子,时居蜀。刘备入蜀,围成都,刘璋出降。刘表:字景升,为荆州牧,刘表死,其子刘琮以荆州降曹操。程颢以刘氏为正统,以复兴刘汉天下为王者事,凡不合此,即以为不义。
[译文]
诸葛亮有王佐之心,但对于圣人之道却未完全把握。以仁政治天下的王者,哪怕让他做一件不义的事就能得到天下,他也不做。诸葛亮执著于追求成功而攻取刘璋。圣人宁可不求成功,这种事做不得呀。像刘表之子刘琮,将要被曹操吞并,夺取之而兴刘氏,是可以的。
14.11 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①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朱熹解:“孔明虽尝学申、韩,然资质好,却有正大气象。”诸葛亮封武乡侯。
[译文]
诸葛亮有儒者的气度景象。
14.12 孔明庶几礼乐。① ——《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注释]
①王通《中说·王道》:“使孔明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此条缘此而发。
[译文]
诸葛亮也许可以兴起礼乐。
14.13 文中子本是一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议论,附会成书,其间极有格言,荀、扬道不到处。① ——《二程遗书》卷十九
[注释]
①文中子:隋代哲学家王通,门人私谥文中子,隐居不仕,居河汾之间讲学,门人记其言行,为《中说》(又名《文中子》)十卷。附会:这里义近拼凑。其《中说》为弟子汇集其语录编纂而成。
[译文]
王通本是一位隐居君子,世人往往记下他的议论,附会而成书,其中很有些精辟的话,为荀子、扬雄所达不到的地方。
14.14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①至如断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②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
——《二程遗书》卷一
[注释]
①韩愈:字退之,见(1.35)注。《原道》:韩愈所著,其中提出了与佛、老之道对立的道,及儒家之道由尧而下传承的“统绪”。许大见识:指《原道》中所阐述的一些重要认识,按张伯行所举,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相传之正统”,有“仁义道德之必合而言之”,有“人性有五而情有七”,有“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有“排诋佛氏”。②引文分别见韩愈《读荀子》、《原道》。
[译文]
韩愈也是近代的豪杰之士,如《原道》一文中言语虽有些毛病,但自孟子以后,能将这么大的见识探寻出来,仅有他一人。至于判定说:“孟子是醇而又醇的儒者。”又说“荀子与扬雄,其学术选择得不够精审,阐释得又不够详明”。如果不是他确有真见,怎能在孟子既死千年之后,判断得如此分明?
14.15 学者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①退之却倒学了②,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③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④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论语·宪问》:“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②韩愈字退之。朱熹解:“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才是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在程氏看来,学应该是学道,韩愈却是因学文而学道,所以说他学倒了。③韩愈《原道》:“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以为孟轲死,圣道坠溺。此说为宋理学家称道。④凿空:凭空无据。撰:杜撰。
[译文]
学道原本是修德,有了德行然后就有好的言语表达。韩愈却倒过来学了,他是由于要学写文章,每天追求自己未能达到的东西,于是就于圣人之道有了收获。如他说:“孟轲死后圣人之道没有能继续向下传。”像这样的言语,不是蹈袭前人,也不是凭空杜撰得出的,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如果不是自有见地,就不明白他自己说的圣贤所传的是什么东西。
14.16 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①其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②
——《宋史·周敦颐传》、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
[注释]
①黄庭坚《山谷集》卷一《濂溪诗并序》:“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语又载《宋史·周敦颐传》及吴子良《林下偶谈》。光风霁月:雨过天晴时的明净景象,比喻人的胸怀光明磊落。②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一《濂溪先生事状》:“先生博学力行,闻道甚早。遇事刚果,有古人风。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张伯行解:“精详者难于缜密,严毅者不能宽恕,周子则兼而有之。”
[译文]
周敦颐胸中洒落,就像光风霁月一样晶莹明净。他处理政务精详又缜密,严毅又宽恕,务在穷尽道理。
14.17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状》曰: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①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苍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②,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见善若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③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④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⑤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⑥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⑦辩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辩。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⑧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⑨。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⑩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⑪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兢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⑫,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先生进将觉斯人,退将明之书。不幸早世,皆未及也。⑬其辨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耳。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⑭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⑮先生接物,辨而不间⑩,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从,怒人而人不怨。贤愚善恶,咸得其心。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⑰闻风者诚服,睹德者心醉。⑱虽小人以趋向之异,顾于利害,时见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为君子也。⑲先生为政,治恶以宽,处烦而裕。当法令繁密之际,未尝从众为应文逃责之事。④人皆病于拘碍,而先生处之绰然。㉑众忧以为甚难,而先生为之沛然。虽当仓卒,不动声色。方监司㉒兢为严急之时,其待先生率皆宽厚。设施㉓之际,有所赖焉。先生所为纲条法度,人可效而为也。至其导之而从,动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则人不可及也。㉔
——《二程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
[注释]
①《尚书·周书·君陈》:“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大而不失去约束。和而不流:见《礼记·中庸》,和顺而不至随物流迁。叶采云:“以上一节言资禀之粹、充养之厚也。”②行己:处身行事。张伯行解:“敬以持身,无妄思妄动;恕以及物,推心如心。”③《后汉书·孔融传》:“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以上一节言行己之本末也。⑤几:将近。《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明达事物之情,详察人伦之序。庶物,普通事物。物,同事。见(13.14)注。⑥《周易·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见(6.11)注。⑦《周易·系辞下》:“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孔颖达疏:“穷极微妙之神,晓知变化之道,乃是圣人德之极盛。”《礼记·乐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通乎礼则知万化散殊之迹,通乎乐则穷万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实本乎人也。”⑧《二程遗书》卷十八载:“问: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学释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谓‘知者过之’也。”知者过之,见《礼记·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过与不及均失于中庸。叶采曰:“昔之害,杨墨申韩是也。今之害,佛老是也。浅近故迷暗者为所惑,深远故高明者反陷其中。”⑨开物成务:见《周易·系辞上》,孔颖达疏:“言能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见(3.49)注。叶采言佛教“自谓通达玄妙,实则不可以有为于天下”。⑩周遍:周全。张伯行解:“自认为性周法界,一黍之中呈现三千大千,其言无不周遍,而废三纲五常,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灭尽了,是外于伦理也。”⑪张伯行解:“又以为穷深极微,超出阴阳之外,为不生不灭之说,而不知无浅非深,无微非显,尧舜以来相传之道,大中至正,其以教易明而事易行也。索隐行怪,便不可入尧舜之道。”⑫蓁芜:杂乱丛生的草木。⑩斯人:即斯民,民众,百姓。张伯行解:“先生为一时人心计,则将以斯道觉斯民;为万世之人心计,则将明之书以示来世。乃进既不大用于时,退而著书未就,不幸享年仅五十四,力皆未及。”世,即没世,逝世。⑩《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谓“知止”,即“知其所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又“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茅星来引陈醇言:“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按“致知”到“知止”,是学以求知的开头与终结,是学习知。“诚意”至“平天下”,是学为治民的开头与终结,是学习行。都是从最初步到最高言。洒扫应对,为学之始;穷理尽性,为学之终。张伯行解此三句:“如教人以求知也,则自学问思辨,实尽致知之事,以至于真知所当止之地,中间理一分殊,不希顿悟。其教人以力行也,则自好恶慎独,实尽诚意之事,以至于举而措之平天下之大,中间功效次第,知所先后。凡以约之于下学之中,使人从洒扫应对工夫做起,自然渐渐向上去,至于穷理尽性而止。”穷理,穷究事物之理。尽性,充分发挥人的本善之性。参考(1.28)、(6.11)。⑮叶采云:“此一节言教人之道,本末备具,而循序渐进,惟恐学者厌卑近而务高远,轻自肆而无实得也。”⑯辨而不间:明辨其恶但不拒绝人。⑰狡伪:狡诈奸伪。暴慢:凶暴傲慢。⑩心醉:佩服,倾倒。《庄子·应帝王》:“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叶采解:“教人各因其资而平易明白,故易从。怒所当怒,心平气和,故不怨。爱而公,故咸得其心。待人尽其诚,而人不忍欺之。待人尽其礼,而人不忍以非礼加之。”⑲叶采云:“以上一节,言接物之道。”⑳法令繁密之际:指王安石推行新法之时。参见(10.3)及注。应文逃责:应付着法令条文行事以免于责备。㉑拘碍:束缚阻碍难行。绰然:即绰有余裕。《孟子·公孙丑下》:“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后以“绰有余裕”形容态度从容、不慌不忙。绰然义同。㉒监司:指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提点常平等官,有监察各州县官吏之责。见(10.41)及注。程颢曾知扶沟县。㉓设施:措置,筹划。《淮南子·兵略训》:“昼则多旌,夜则多火,暝冥多鼓,此善为设施者也。”此处指处置行政事务。㉔叶采解:“以上一节言为政之道。”
[译文]
程颐为程颢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说:先生他天资禀赋既已不同常人,而他扩充善性持养身心又得法。他的品行,纯粹得就如精金,温润又如美玉。他的性情,宽大而有节制,和顺但不随波逐流。他忠诚之志可贯透金石,敬父爱兄之意可上达于神明。看他的容颜,其待人接物就像春天的太阳那样温和;听他的言语,其深入人心就如时雨一样滋润万物。心胸光明如重门洞开,透彻而无间隔隐蔽;而要测其学识的蕴蓄,则又浩浩然如沧海之无边无际;想说清楚他的美德,他却众善皆备再好的言语也不足以形容。他推行自己的思想,首先自身主于谨敬,然后再推广自我之心以及人。见到别人有善行就像自己的善行一样珍视和赞扬,自己所不想接受的决不施加于人。心胸之宽就如住在广大的居室中,行为端方正大就如走在正直的大路上,发言必定切实不作空言,行动必有常规而不肆意。他的学习,从十五六时听到周敦颐谈论圣人之道,于是就厌倦世人争相追逐的科举之业,慨然有探求圣道的志向。起初不得要领,漫无边际地杂学各家,出入于老庄佛释将近十年,又回到六经上才得其真谛。他明达事物之情,详察人伦之序。他懂得,尽性知命的高深必本于孝亲敬长之实。又明白,穷神知化的认识天道原与明礼知乐的人事相通。辨析异端之学的似是而非,揭明千万年未能弄明的迷惑。自秦汉以后,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些道理。他认为孟子死后圣学没有往下传,他以重兴礼乐教化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说:大道之所以不能明于天下,是由于异端之学妨害了它。过去危害圣学的杨墨申韩之类学说粗浅而容易看出其荒谬,今日害道的佛老之学深远而难以明辨。过去的异端之学迷惑人是利用人的迷暗,今天的异说侵入人心却是利用人的高明。佛家自称能通达天地的玄妙,而其实不能有为于天下。佛家称他们的学说包括一切无不周详,其实他们是丢弃了人类伦常之理。佛家自认为其穷尽深奥之理、探极幽微之处,而玄怪深僻恰恰不能达于尧舜坦荡平易的大道。天下的学问,若不是浅陋而不通达,就必然跑到佛教那里去。自从圣人之道不得明于天下,邪诞妖异之说竞相兴起,堵塞了人民的耳目,把天下沉陷在污泥浊水之中。即使有高明才智之士,局限于耳目的见闻,生如沉醉,死如梦寐,而不自觉其不明理的迷惑。这些都是正路上的荒草秽木,堵塞圣学之门的障碍,必须开辟出路径才能进入大道。先生他进身为官是为要唤醒今世的人民,退身隐居要著书明理以垂后世。不幸早逝,进退之事都未及做成。他辨析精微之论,多少有一些为世人所见到的,是他的学生们传播的呀。先生他的门下,学生多了。他的言语,平易易知,不论贤明的愚笨的,听了都能受益,就像一群人在大河里喝水,虽然各自所需不同,但各自都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他的教人,从寻求明识开始一直到知其所止,从内心诚意开始一直学到平治天下,从童子初学的洒扫应对开始直到入圣人之域的穷理尽性,整个过程都循循而有序。他批评世俗的学者舍弃浅近的而务求高远,身处于下却窥望高处,导致自己的轻浮自大而到底也学无所得。先生他对待人,明辨其恶但也不拒绝他,以意感人人必能应,教导人人能轻松地听从,怒责人人也不会怨恨。不论贤愚善恶,各种各样的人,他都能得其心。狡猾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奉献真诚,暴戾傲慢的人在他面前也表现出谦恭。听说他的风范的人就诚服,看到他的德行的人佩服得心醉神迷。纵然是小人与他追求不同,考虑利害相妨,时时加以排斥,但他们退处而自我思考时,没有不认为先生他是正人君子的。先生的治理政事,用宽大去治理恶人导其向善,处于烦琐的事务中却宽闲优裕。当朝廷法令繁苛峻密之时,他也从未学着众人去做虚应形式逃避职责的事。人人都认为法令不当束缚妨碍着没法做事,而他却能在这种法令下处理得绰有余地。众人担心很难做的事,而他做得却很兴盛。即使在仓促遇变之时,也不动声色。当监司们竞相严密紧急地伺察州县官时,他们对待做州县官的程颢先生全都很宽厚。处置事务时,还有依赖先生处。先生他制定的纲纪条文法度,人们可以效法着去做。至于他引导人民,人民就会跟从,以诚动人而人自然和顺,不求外物应己而外物自应之,未曾以自己的诚信施于人时人民已先相信了,这些则是人们没法赶得上的。
14.18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①(本注:子厚观驴鸣,亦谓如此。②)
——《二程遗书》卷三
[注释]
①茅星来解:“指生意周流无间而言。”②茅星来解:“盖取其有自得之意也。”
[译文]
程颢说:周敦颐窗前的草不除去,问他,他说:“草上表现出的生意与我的心意一样。”(本注:张载看驴叫,也是这么说。)
14.19 张子厚闻皇子生,喜甚;见饿莩者,食便不美。①
——《二程遗书》卷三
[注释]
①饿莩:即饿殍,饿死的人或饿得快死的人。《后汉书·仲长统传》:“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此为已饿死的人。白居易《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策》:“凶歉之年,则贱粜以活饿殍。”此为饿得将死的人。
[译文]
张载听说皇子出生了,就非常高兴;见到有饿死的和饿得奄奄一息的人,吃饭就不香甜。
14.20 伯淳尝与子厚在兴国寺讲论终日,而曰: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①
——《二程遗书》卷一
[注释]
①伯淳:程颢。子厚:张载。兴国寺:即开封相国寺。张伯行解:“千载上下,皆此心此理,则旧日合有如此人,讲论亦合有如此事。”
[译文]
程颢曾和张载在相国寺谈论了一整天,又说:不知道过去曾经有什么人在此处谈论这样的事。
14.21 谢显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 。——《二程外书》卷十二
[译文]
谢良佐说:程颢先生坐着安详稳静就像一个泥塑的人,与人相处则全然是一团和气。
14.22 侯师圣云: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①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俟立。②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③ ——《二程外书》卷十二
[注释]
①侯仲良,字师圣;朱光庭,字公掞。均程颢门人。汝:即汝州,时程颢监汝州酒税。成语“如坐春风”即出此。②游为游酢,杨为杨时,为程门四弟子中二人。程颢死,两人复从程颐学,初见非初次相见,是初次从师。③叶采曰:“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师道尊严,皆盛德所形,但气质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颜子,伊川似孟子。”此即“程门立雪”故事成语出处。
[译文]
侯师圣说:朱光庭到汝州去见程颢,回来后告诉人说:“我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酢、杨时初次去见程颐拜师,程颐瞑目而坐,两人站着等候。程颐醒后,看着他俩说:“你们还在这里呀?天已经晚了,算了吧。”及至出门,门外积雪深一尺。
14.23 刘安礼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①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 ——《二程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
[注释]
①刘立之,字宗礼,二程门人。此作安礼,误,见(10.58)注。粹和之气,盎于面背:《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乐易:和乐平易,《荀子·荣辱》:“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
[译文]
刘立之说:程颢先生德性充实完美,粹和之气,漾溢前前后后,和乐平易宽大,一天到晚都是喜悦的。我跟从先生三十年,从未见过他有忿愤严厉的脸色。
14.24 吕与叔撰《明道先生哀词》云①:先生负特立之才,知大学之要;博文强识,躬行力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②其造于约也,虽事变之感不一,知应以是心而不穷;虽天下之理至众,知反之吾身而自足。③其致于一也,异端并立而不能移,圣人复起而不与易。④其养之成也,和气充浃,见于声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优为,从容不迫,然诚心恳恻,弗之措也。⑤其自任之重也,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⑥成名;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其自信之笃也,吾志可行,不苟洁其去就;吾义所安,虽小官有所不屑。⑦ ——《二程遗书》附录
[注释]
①吕与叔:吕大临,二程弟子。《明道先生哀词》,此文又载《伊洛渊源录》卷三。②特立:独出于众人之上,无人可及之意。大学之要:理学家认为,洒扫应对是小学事,尽性至命,成就天德是大学事。《大学》所论也即大学之事。大学之要,在理学家看来,不是治国平天下,而是正心诚意。明王守仁《大学古本序》所论符合程颢之意:“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博文强识:博览古代文献而又有很强的记忆。《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后以“博文”指通晓古代文献。察伦明物:即察于人伦,明于物理。见(13.14)注⑧、(14.17)注⑤。道体:道的本体,道的主旨。《淮南子·人间训》:“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或解构妄言而反当。”③此一节言其学虽博而能达于约。《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约,简要,要领。达于约即返于约,掌握要领统领其博。达于约,其心即能应万事无穷之感,以物付物而各得其当;天下之理无穷,而万理归于一理,此一理则可返求之吾身而得之,不假外求而自足。叶采解:“应感无穷,而实本乎吾心;物理散殊,而皆备乎吾身。言其学虽博而有要也。”④叶采解:“致一者,见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说不能移,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⑤充浃:充盈浃洽。崇深:高藏深隐,崇高而又渊深。慢:轻慢,轻视。恳恻:诚恳痛切。汉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又元和故事,复申先典,前后制书,推心恳恻。”弗之措:不弃置,不放弃。《礼记·中庸》:“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孔颖达疏:“措,置也。言学不至于能,不措置休废,必待能之乃已也。”这一节说他做事从容不迫,但从不懈怠,从不放弃。⑥一善:一种善行,一种美德。《礼记·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⑦这一节言其出处去就,都以能否行其志、安于义为准的。
[译文]
吕大临作《明道先生哀词》说:先生他负有特立独出之才能,明于高深学问的要领;博学于文献而强记之,亲身践行努力探讨;详察人伦明知事理,透彻地掌握了人之所当止;心中如涣然冰释,透彻理解了大道的本体。他的学问由博而返于约,掌握的要领就在自己一心一身。虽然外事作用于我者变化不一,他明白心是应物之主,以一心随感而应也没有穷尽;天下之理虽然众多,他明白万理皆备于我身,反求于我身则一切理都可自足。他的修养达到了精诚致一的地步,异端之学并兴也不能改变他的自信之心,圣人再生也不会修改他的学说。他的德行养成了,太和之气充盈透彻,表现于声音容貌,使人望见其崇高渊深,无法轻慢;遇事当为而为,从容不迫,然而其至诚之心诚恳深切,做不好决不放弃。他对自己的希望和要求远大,宁可学圣人而未能达到,也不凭借一种善行美德成就名声;宁可把天下有一物不受圣人恩泽看做自己的过错,追求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一样的圣君,不把一时的有利于人作为追求的事功。他自信笃厚,只要我的志向能够推行,就不故作高洁而去其位;只要是依义而行我心得安,虽有小官也有所不屑于做。
14.25 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康定用兵时,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①公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②,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嘉祐初,见程伯淳、正叔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本注:尹彦明云: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③晚自崇文移疾,西归横渠,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④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⑤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尝谓门人:“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⑥者,豫而已矣。”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喻,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张子全书》卷十五
[注释]
①此条摘录吕大临撰张载行状而成。宋仁宗康定元年,西夏攻宋。时范仲淹为陕西招讨副使。张载上书谒见。②名教:指儒家进行教化的名分、名目、名节、功名,此处泛指儒家学说。③尹彦明:即尹焞。此说极不可信。《二程外书》卷十一载程颐就吕大临所作行状中“尽弃其所学而学焉”(此本作“尽弃异学”,较当)一语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张载与二程关系,就年岁说长程颢十二岁,长程颐十三岁,就辈分说为二程表叔,与二程关系密切,学术上互相影响。④宋神宗熙宁二年,张载被召入对,除崇文院校书,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次年移病西归,居横渠镇。崇文院为藏书馆名。简编:指书籍。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是张载学术的突出特点。⑤知礼成性:出张载《经学理窟》,懂得了礼并用以守持形成本性。参见本书(2.86)及注。变化气质:改变其气质之性而恢复其天然本善之性。参见本书(2.101)及注。⑥精义入神:出《周易·系辞下》,参见本书(2.79)及注。
[译文]
吕大临作《横渠先生行状》说:仁宗康定年间同西夏打仗时,张载先生十八岁,当时慨然以立功边疆自许,上书拜见范仲淹。范仲淹看出他是远大之器,想要成就他,就责备他说:“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学问,干什么要从事于军事?”于是劝他读《中庸》。张载先生读《中庸》,虽然喜欢,但仍感到不满足,于是又访求佛教、道家之书,读了多年,透彻地了解了佛、道的学问,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又回过头来读六经。嘉祐初年,与程颢、程颐兄弟相见于京师,一同探讨道学之大要。先生他胸中的疑问涣然消释,自信地说:“我们儒学的理论自身十分充足,干什么要寻求别家之说?”于是尽弃异端之学,成为淳正的儒者。(本注:尹焞说:张载过去在京师,坐虎皮,讲《周易》,听的人很多。一天晚上,二程到来,谈论《周易》。第二天,张载撤去虎皮,对学生们说:我平日给诸位所讲的,都是乱说。有二程近日来到,深明《周易》的学问,是我所赶不上的,你们可以去向他们学习。)晚年从崇文院因病去职西归回到横渠镇,一天到晚恭恭敬敬坐在一间房子里,左右放的都是书,俯首而读,仰首而思,有所得就记下来。有时半夜坐起来,点上灯烛去写。他对圣人之道的追求与精深思考,从未有片刻停息,也从未有一刻的忘记。学生有所问,多告诉他们学礼并用礼去持养本性,和学问变化气质的方法,要求学生学习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地步才可以。听到他这些话的人无不触动于心而有所进步。他曾经对门人说:“我治学心中有所领悟时,就选取恰当的言辞把它表述出来;表述得没有差失,然后用来判断事务;判断事务没有差失,我就感到胸中充盛了。精熟义理,达到神妙的境界,就要在事情没有出现时,先要熟知有关这事的道理,如此而已。”先生他气质刚毅,德性充盛,容貌严肃。但和人相处,时间久了就一天天亲近。他的治家与在外接交,大致说是正己以感人。人未能信从他,他就回过头来修养自身,而不告诉给人。虽然有的人始终也不明白他的用心,他照样安心而行并不后悔。所以认识他的与不认识他的人,闻其风而畏服,不合义的事,不敢以一丝一毫加到他身上。
14.26 横渠先生曰:二程从十四五时,便锐然欲学圣人。①
——张载《横渠语录》
[注释]
①《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学者不可谓年少,自缓便是四十五十。二程从十四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今尽及四十未能及颜、闵之徒。小程可如颜子,然恐未如颜子无我。”《论语·先进》载,孔子评价其主要弟子们各自长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译文]
张载说:程颢、程颐兄弟二人,从十四五岁时,就立志锐意要学圣人。
——《二程遗书》卷二上
[注释]
①《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又《尽心下》:“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之,是说出于本性之自然,不习而得,不勉而中。反之,是说通过修习恢复其本善之性。
[译文]
程颢说:尧和舜再分不得优劣,及至商汤和周武王,就有了区别。孟子说:“尧、舜的仁德是出于自然的本性”,“汤、武的仁德是恢复了其本然的善性”,自古没有人这么说,只有孟子分别出来,便可知尧、舜是生而知之,汤、武是学而能之。周文王之德则近似于尧、舜,大禹之德则近似于汤、武。总之都是圣人。
14.2 仲尼,元气也;颜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杀尽见。①仲尼无所不包,颜子示“不违,如愚”之学于后世,有自然之和气,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则露其才,盖亦时焉而已。②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观其言皆可见之矣。仲尼无迹,颜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③孔子尽是明快人,颜子尽岂弟,孟子尽雄辩。④ ——《二程遗书》卷五
[注释]
①此条反复形容孔子(仲尼)、颜回(颜子)、孟子气象之不同。张伯行解:“夫子阴阳合德,不刚不柔,太和充满,众理渊涵,如一元之气,浑沦溥博,自然而然,无二无间,此圣不可知者也。颜子则亚圣之资,盎若春阳,蔼若春风,万物发荣滋润,到处皆有生意。”“孟子亦亚圣之才,而有刚明果毅整齐严肃之意”,“所谓并秋杀尽见者。”元气:古人所谓天地未分前的混沌之气。春生:春天生物气象。秋杀:指秋天萧飒之气。孟子批杨、墨,好辩,厉声色。②《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张伯行解:“元气贯通四时,则无所不包,此仲尼之道全德备,非一善可名者也。春意发生,则有自然之和气,此颜子之‘不违,如愚’,与圣人合德,令后世可以想见,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秋爽气清,高旷轩朗,此孟子之英气发越,为露其才,盖亦战国之时,异端滋炽,又无夫子主盟其上,故其卫道之严,距邪之力,不得不然者也。”③气象:指人的气度,气局,风神,景象。宋龚昱《乐庵语录》卷五:“如舜孳孳为善,想其气象必是个温良恭顺底人。”近人钱穆《宋代理学三书随劄》之《近思录随劄》有对于气象的解说,可参考。张伯行解:“天地无心而成化,虽日发育万物,人莫得窥其迹者也。仲尼一理浑然,泛应曲当,如是焉已。风云变化,虽不知其所以然,而微有迹可见,如颜子为仁之问,喟然之叹,庶乎可以窥测其微也。泰山岩岩,壁立万仞,其中景物,昭布森列,如《孟子》一书,发挥透露,不留余蕴,其迹著明也。”④张伯行解:“明者,心无渣滓,人欲尽而天理见也。快者,心无系累,万物一体而因物付物也,所谓气质清明、义理昭著,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是也。”“岂,和乐也。弟,谦逊也。”岂弟:即恺悌,也作恺弟,和乐平易。《左传》僖公十二年:“《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杜预注:“恺,乐也;悌,易也。”
[译文]
孔子含蓄博大,圣不可知,就如天地一元之气;颜回之祥和就如春风春雨之发育生长万物之意;孟子抨击异端邪说之严厉就表现出秋天肃杀之气。孔子道全德备,一切之善无不包含,颜回以“不违背孔子的话,像是迟钝”的学习精神展示给后世,有一种自然和气,使后世之人不言而自化。孟子则显露出自己的才气,那也是时势使他如此的呀。孔子的无不覆无不载,高明博厚就如天地;颜回就如和风庆云一样有一种和气祥光;孟子的刚强峻拔直如泰山壁立的山岩气象。观察他们语言的不同风格就可以明白了。孔子之道与天地浑然一体,无迹可寻,颜回则微露些迹象,孟子则是心迹昭著,发挥透彻。孔子全然是一个明快人,颜回全是谦和,孟子全是雄辩。
14.3 曾子传圣人学,①其德后来不可测,安知其不至圣人?如言“吾得正而毙”②,且休理会文字,只看他气象极好,被他所见处大。后人虽有好言语,只被气象卑,终不类道。
——《二程遗书》卷十五
[注释]
①《论语》一书,记载孔子弟子一般称字,独曾参、有若二人称“子”,故前人多认为《论语》由他们特别是曾参的学生纂述。又据前人考证,曾子为孔子正传并开以后的思孟学派。《孟子外书》记:“曼丘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何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曾子:曾参。②《礼记·檀弓上》载,曾参病将死,而所铺为大夫才能用的席子,曾参一定要换掉,说:“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正而毙:规规矩矩合乎礼地死去。
[译文]
曾参传授圣人之学,其德行后来日益上进到不可测量的地步,怎么知道他没有达到圣人的高度呢?如他说“我只求规规矩矩合礼地死去”,且不要推敲文字,只看他气度极好,他所看到的是大处。后人虽然也有些好的言语,只因为气度卑下,到底也不像个有道的人。
14.4 传经为难,如圣人之后才百年,传之已差。①圣人之学,若非子思、孟子,则几乎息矣。道何尝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厉不由也。”② ——《二程遗书》卷十七
[注释]
①孔子之后,至战国时期,儒家分为八派,按《韩非子·显学》之说,“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子)之儒,有乐正氏之儒”。二程所继承的,是子思、孟子递相传授的思孟学派,此派以外的,在程氏看来,均为“有差”。子思,名孔伋,孔子之孙,相传为曾参的学生,而孟子又学于子思门人。②见董仲舒《对贤良策》。幽、厉:指周幽王、周厉王,周代无道之君。
[译文]
传授圣人的典籍学说是很困难的,如孔子死后才百十年,传授就已经有了偏差。孔子的学说,如果不是子思、孟子的发扬,则几乎要熄灭了。圣人之道何曾熄灭过,只是人们不实行。就如董仲舒说的:“周文王、武王的思想并没有消亡,只是幽王、厉王不实行。”
14.5 荀卿才高,其过多;扬雄才短,其过少。①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荀卿:即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思想家。扬雄:又作杨雄,西汉思想家、文学家。叶采解:“荀卿才高,敢为异论,如以人性为恶,以子思、孟子为非,其过多;扬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拟《易》,《法言》以拟《论语》,皆模仿前圣之遗言,其过少。”
[译文]
荀子才识高远,敢为异说,故其过错也较多;扬雄才识短浅,刻意模仿圣贤,故其过错也较少。
14.6 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扬子虽少过,然已自不识性,更说甚道?① ——《二程遗书》卷十九
[注释]
①荀子人性论与孟子对立,主性恶,《荀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扬雄则主人性善恶混,《法言·修身》:“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二程继承孟子的性善论,故批荀、扬之说。
[译文]
荀子的学说极其偏失驳杂,只一句“性恶”,根本就错了;扬雄虽然少有过错,但他既然不懂得性,还谈论什么道?
14.7 董仲舒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诸子。① ——《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注释]
①见《汉书·董仲舒传》。朱熹说,此语是“不论利害,只论是非”。谊:同义,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本仁祖谊,褒有德,禄贤能。”谊,即义。度越:超越。诸子:指孟子之后汉唐诸儒。
[译文]
董仲舒说:“搞正确什么是义与不义,而不去谋求利益;讲明圣人之道而不计较功效。”这就是董仲舒超过诸子的原因所在。
14.8 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人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①下此至于扬雄,规模又窄狭矣。② ——《二程遗书》卷一
[注释]
①毛苌:或作毛长,汉时人,传《诗经》,为河间献王博士。所谓得圣人之意,张伯行以为:“毛以修身齐家为论治之要,董以正谊明道为格君之本是也。”见道不分明,朱熹以为:“如董云性者生之质”,“似不识本然之性”。“毛公诗传,紧要有数处”,“要之亦不多见,只是气象大概好耳”。②扬雄规模窄狭,朱熹解:“学老氏将取固与之术,卒为莽大夫,非儒者规模,其窄狭又甚矣。”莽指王莽。王莽篡汉,扬雄校书天禄阁,官至大夫。
[译文]
汉代的儒者如毛苌、董仲舒,最能理解圣人之意,但对圣人之道认识得不够分明。他们之下就挨到了扬雄,其规模就更窄狭了。
14.9 林希①谓扬雄为禄隐。扬雄,后人只为见他著书,便须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②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林希:宋人,字子中,长乐人。《宋元学案》入《荆公新学案》(卷九十八),王安石婿。又《宋元学案》卷九十六《元祐学案》列入所附“攻元祐之学者”。②张伯行解:“扬子云失身事莽,大节已亏,而人犹以为禄隐。禄隐者,道不行而浮沉下位也。子云固如是哉?人但见其所著书奥衍深僻,诧其有才,便要说他是。”其书“亦不知道而作,徒以艰深之词,文浅易之说,怎有是处?”做他是:肯定他。
[译文]
林希说扬雄是食禄的隐士。扬雄这人,后人只看到他写了书,便要肯定他,怎么能够肯定呢?
14.10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若刘表子琮,将为曹公所并,取而兴刘氏,可也。① ——《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注释]
①孔明:诸葛亮,字孔明,佐刘备创立蜀汉。《孟子·公孙丑上》:“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刘璋:字季,益州牧刘焉子,时居蜀。刘备入蜀,围成都,刘璋出降。刘表:字景升,为荆州牧,刘表死,其子刘琮以荆州降曹操。程颢以刘氏为正统,以复兴刘汉天下为王者事,凡不合此,即以为不义。
[译文]
诸葛亮有王佐之心,但对于圣人之道却未完全把握。以仁政治天下的王者,哪怕让他做一件不义的事就能得到天下,他也不做。诸葛亮执著于追求成功而攻取刘璋。圣人宁可不求成功,这种事做不得呀。像刘表之子刘琮,将要被曹操吞并,夺取之而兴刘氏,是可以的。
14.11 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①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朱熹解:“孔明虽尝学申、韩,然资质好,却有正大气象。”诸葛亮封武乡侯。
[译文]
诸葛亮有儒者的气度景象。
14.12 孔明庶几礼乐。① ——《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注释]
①王通《中说·王道》:“使孔明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此条缘此而发。
[译文]
诸葛亮也许可以兴起礼乐。
14.13 文中子本是一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议论,附会成书,其间极有格言,荀、扬道不到处。① ——《二程遗书》卷十九
[注释]
①文中子:隋代哲学家王通,门人私谥文中子,隐居不仕,居河汾之间讲学,门人记其言行,为《中说》(又名《文中子》)十卷。附会:这里义近拼凑。其《中说》为弟子汇集其语录编纂而成。
[译文]
王通本是一位隐居君子,世人往往记下他的议论,附会而成书,其中很有些精辟的话,为荀子、扬雄所达不到的地方。
14.14 韩愈亦近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语虽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将许大见识寻求者,才见此人。①至如断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与扬,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②若不是他见得,岂千余年后,便能断得如此分明?
——《二程遗书》卷一
[注释]
①韩愈:字退之,见(1.35)注。《原道》:韩愈所著,其中提出了与佛、老之道对立的道,及儒家之道由尧而下传承的“统绪”。许大见识:指《原道》中所阐述的一些重要认识,按张伯行所举,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为相传之正统”,有“仁义道德之必合而言之”,有“人性有五而情有七”,有“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有“排诋佛氏”。②引文分别见韩愈《读荀子》、《原道》。
[译文]
韩愈也是近代的豪杰之士,如《原道》一文中言语虽有些毛病,但自孟子以后,能将这么大的见识探寻出来,仅有他一人。至于判定说:“孟子是醇而又醇的儒者。”又说“荀子与扬雄,其学术选择得不够精审,阐释得又不够详明”。如果不是他确有真见,怎能在孟子既死千年之后,判断得如此分明?
14.15 学者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①退之却倒学了②,因学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轲之死不得其传。”③似此言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凿空撰得出,④必有所见。若无所见,不知言所传者何事。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论语·宪问》:“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②韩愈字退之。朱熹解:“韩文公第一义是去学文字,第二义才是去穷究道理,所以看得不亲切。”在程氏看来,学应该是学道,韩愈却是因学文而学道,所以说他学倒了。③韩愈《原道》:“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以为孟轲死,圣道坠溺。此说为宋理学家称道。④凿空:凭空无据。撰:杜撰。
[译文]
学道原本是修德,有了德行然后就有好的言语表达。韩愈却倒过来学了,他是由于要学写文章,每天追求自己未能达到的东西,于是就于圣人之道有了收获。如他说:“孟轲死后圣人之道没有能继续向下传。”像这样的言语,不是蹈袭前人,也不是凭空杜撰得出的,一定要自己有所认识。如果不是自有见地,就不明白他自己说的圣贤所传的是什么东西。
14.16 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①其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②
——《宋史·周敦颐传》、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
[注释]
①黄庭坚《山谷集》卷一《濂溪诗并序》:“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此语又载《宋史·周敦颐传》及吴子良《林下偶谈》。光风霁月:雨过天晴时的明净景象,比喻人的胸怀光明磊落。②朱熹《伊洛渊源录》卷一《濂溪先生事状》:“先生博学力行,闻道甚早。遇事刚果,有古人风。为政精密严恕,务尽道理。”张伯行解:“精详者难于缜密,严毅者不能宽恕,周子则兼而有之。”
[译文]
周敦颐胸中洒落,就像光风霁月一样晶莹明净。他处理政务精详又缜密,严毅又宽恕,务在穷尽道理。
14.17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状》曰: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①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苍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先生行己②,内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见善若出诸己,不欲弗施于人。③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④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⑤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⑥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⑦辩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异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难辩。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⑧自谓之穷神知化,而不足以开物成务⑨。言为无不周遍,实则外于伦理。⑩穷深极微,而不可以入尧舜之道。⑪天下之学,非浅陋固滞,则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诞妖异之说兢起,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虽高才明智,胶于见闻,醉生梦死,不自觉也。是皆正路之蓁芜⑫,圣门之蔽塞,辟之而后可以入道。先生进将觉斯人,退将明之书。不幸早世,皆未及也。⑬其辨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耳。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⑭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⑮先生接物,辨而不间⑩,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从,怒人而人不怨。贤愚善恶,咸得其心。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⑰闻风者诚服,睹德者心醉。⑱虽小人以趋向之异,顾于利害,时见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为君子也。⑲先生为政,治恶以宽,处烦而裕。当法令繁密之际,未尝从众为应文逃责之事。④人皆病于拘碍,而先生处之绰然。㉑众忧以为甚难,而先生为之沛然。虽当仓卒,不动声色。方监司㉒兢为严急之时,其待先生率皆宽厚。设施㉓之际,有所赖焉。先生所为纲条法度,人可效而为也。至其导之而从,动之而和,不求物而物应,未施信而民信,则人不可及也。㉔
——《二程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
[注释]
①《尚书·周书·君陈》:“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大而不失去约束。和而不流:见《礼记·中庸》,和顺而不至随物流迁。叶采云:“以上一节言资禀之粹、充养之厚也。”②行己:处身行事。张伯行解:“敬以持身,无妄思妄动;恕以及物,推心如心。”③《后汉书·孔融传》:“融闻人之善,若出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④《孟子·滕文公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以上一节言行己之本末也。⑤几:将近。《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明达事物之情,详察人伦之序。庶物,普通事物。物,同事。见(13.14)注。⑥《周易·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见(6.11)注。⑦《周易·系辞下》:“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孔颖达疏:“穷极微妙之神,晓知变化之道,乃是圣人德之极盛。”《礼记·乐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通乎礼则知万化散殊之迹,通乎乐则穷万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实本乎人也。”⑧《二程遗书》卷十八载:“问:明道先生云:‘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学释氏者,往往皆高明之人。所谓‘知者过之’也。”知者过之,见《礼记·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过与不及均失于中庸。叶采曰:“昔之害,杨墨申韩是也。今之害,佛老是也。浅近故迷暗者为所惑,深远故高明者反陷其中。”⑨开物成务:见《周易·系辞上》,孔颖达疏:“言能开通万物之志,成就天下之务。”见(3.49)注。叶采言佛教“自谓通达玄妙,实则不可以有为于天下”。⑩周遍:周全。张伯行解:“自认为性周法界,一黍之中呈现三千大千,其言无不周遍,而废三纲五常,把父子君臣天地上下之理殄灭尽了,是外于伦理也。”⑪张伯行解:“又以为穷深极微,超出阴阳之外,为不生不灭之说,而不知无浅非深,无微非显,尧舜以来相传之道,大中至正,其以教易明而事易行也。索隐行怪,便不可入尧舜之道。”⑫蓁芜:杂乱丛生的草木。⑩斯人:即斯民,民众,百姓。张伯行解:“先生为一时人心计,则将以斯道觉斯民;为万世之人心计,则将明之书以示来世。乃进既不大用于时,退而著书未就,不幸享年仅五十四,力皆未及。”世,即没世,逝世。⑩《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所谓“知止”,即“知其所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又“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茅星来引陈醇言:“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按“致知”到“知止”,是学以求知的开头与终结,是学习知。“诚意”至“平天下”,是学为治民的开头与终结,是学习行。都是从最初步到最高言。洒扫应对,为学之始;穷理尽性,为学之终。张伯行解此三句:“如教人以求知也,则自学问思辨,实尽致知之事,以至于真知所当止之地,中间理一分殊,不希顿悟。其教人以力行也,则自好恶慎独,实尽诚意之事,以至于举而措之平天下之大,中间功效次第,知所先后。凡以约之于下学之中,使人从洒扫应对工夫做起,自然渐渐向上去,至于穷理尽性而止。”穷理,穷究事物之理。尽性,充分发挥人的本善之性。参考(1.28)、(6.11)。⑮叶采云:“此一节言教人之道,本末备具,而循序渐进,惟恐学者厌卑近而务高远,轻自肆而无实得也。”⑯辨而不间:明辨其恶但不拒绝人。⑰狡伪:狡诈奸伪。暴慢:凶暴傲慢。⑩心醉:佩服,倾倒。《庄子·应帝王》:“列子见之而心醉,归以告壶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则又有至焉者矣。'”叶采解:“教人各因其资而平易明白,故易从。怒所当怒,心平气和,故不怨。爱而公,故咸得其心。待人尽其诚,而人不忍欺之。待人尽其礼,而人不忍以非礼加之。”⑲叶采云:“以上一节,言接物之道。”⑳法令繁密之际:指王安石推行新法之时。参见(10.3)及注。应文逃责:应付着法令条文行事以免于责备。㉑拘碍:束缚阻碍难行。绰然:即绰有余裕。《孟子·公孙丑下》:“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后以“绰有余裕”形容态度从容、不慌不忙。绰然义同。㉒监司:指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提点常平等官,有监察各州县官吏之责。见(10.41)及注。程颢曾知扶沟县。㉓设施:措置,筹划。《淮南子·兵略训》:“昼则多旌,夜则多火,暝冥多鼓,此善为设施者也。”此处指处置行政事务。㉔叶采解:“以上一节言为政之道。”
[译文]
程颐为程颢所作《明道先生行状》说:先生他天资禀赋既已不同常人,而他扩充善性持养身心又得法。他的品行,纯粹得就如精金,温润又如美玉。他的性情,宽大而有节制,和顺但不随波逐流。他忠诚之志可贯透金石,敬父爱兄之意可上达于神明。看他的容颜,其待人接物就像春天的太阳那样温和;听他的言语,其深入人心就如时雨一样滋润万物。心胸光明如重门洞开,透彻而无间隔隐蔽;而要测其学识的蕴蓄,则又浩浩然如沧海之无边无际;想说清楚他的美德,他却众善皆备再好的言语也不足以形容。他推行自己的思想,首先自身主于谨敬,然后再推广自我之心以及人。见到别人有善行就像自己的善行一样珍视和赞扬,自己所不想接受的决不施加于人。心胸之宽就如住在广大的居室中,行为端方正大就如走在正直的大路上,发言必定切实不作空言,行动必有常规而不肆意。他的学习,从十五六时听到周敦颐谈论圣人之道,于是就厌倦世人争相追逐的科举之业,慨然有探求圣道的志向。起初不得要领,漫无边际地杂学各家,出入于老庄佛释将近十年,又回到六经上才得其真谛。他明达事物之情,详察人伦之序。他懂得,尽性知命的高深必本于孝亲敬长之实。又明白,穷神知化的认识天道原与明礼知乐的人事相通。辨析异端之学的似是而非,揭明千万年未能弄明的迷惑。自秦汉以后,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些道理。他认为孟子死后圣学没有往下传,他以重兴礼乐教化作为自己的责任。他曾说:大道之所以不能明于天下,是由于异端之学妨害了它。过去危害圣学的杨墨申韩之类学说粗浅而容易看出其荒谬,今日害道的佛老之学深远而难以明辨。过去的异端之学迷惑人是利用人的迷暗,今天的异说侵入人心却是利用人的高明。佛家自称能通达天地的玄妙,而其实不能有为于天下。佛家称他们的学说包括一切无不周详,其实他们是丢弃了人类伦常之理。佛家自认为其穷尽深奥之理、探极幽微之处,而玄怪深僻恰恰不能达于尧舜坦荡平易的大道。天下的学问,若不是浅陋而不通达,就必然跑到佛教那里去。自从圣人之道不得明于天下,邪诞妖异之说竞相兴起,堵塞了人民的耳目,把天下沉陷在污泥浊水之中。即使有高明才智之士,局限于耳目的见闻,生如沉醉,死如梦寐,而不自觉其不明理的迷惑。这些都是正路上的荒草秽木,堵塞圣学之门的障碍,必须开辟出路径才能进入大道。先生他进身为官是为要唤醒今世的人民,退身隐居要著书明理以垂后世。不幸早逝,进退之事都未及做成。他辨析精微之论,多少有一些为世人所见到的,是他的学生们传播的呀。先生他的门下,学生多了。他的言语,平易易知,不论贤明的愚笨的,听了都能受益,就像一群人在大河里喝水,虽然各自所需不同,但各自都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他的教人,从寻求明识开始一直到知其所止,从内心诚意开始一直学到平治天下,从童子初学的洒扫应对开始直到入圣人之域的穷理尽性,整个过程都循循而有序。他批评世俗的学者舍弃浅近的而务求高远,身处于下却窥望高处,导致自己的轻浮自大而到底也学无所得。先生他对待人,明辨其恶但也不拒绝他,以意感人人必能应,教导人人能轻松地听从,怒责人人也不会怨恨。不论贤愚善恶,各种各样的人,他都能得其心。狡猾的人在他面前也会奉献真诚,暴戾傲慢的人在他面前也表现出谦恭。听说他的风范的人就诚服,看到他的德行的人佩服得心醉神迷。纵然是小人与他追求不同,考虑利害相妨,时时加以排斥,但他们退处而自我思考时,没有不认为先生他是正人君子的。先生的治理政事,用宽大去治理恶人导其向善,处于烦琐的事务中却宽闲优裕。当朝廷法令繁苛峻密之时,他也从未学着众人去做虚应形式逃避职责的事。人人都认为法令不当束缚妨碍着没法做事,而他却能在这种法令下处理得绰有余地。众人担心很难做的事,而他做得却很兴盛。即使在仓促遇变之时,也不动声色。当监司们竞相严密紧急地伺察州县官时,他们对待做州县官的程颢先生全都很宽厚。处置事务时,还有依赖先生处。先生他制定的纲纪条文法度,人们可以效法着去做。至于他引导人民,人民就会跟从,以诚动人而人自然和顺,不求外物应己而外物自应之,未曾以自己的诚信施于人时人民已先相信了,这些则是人们没法赶得上的。
14.18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般。”①(本注:子厚观驴鸣,亦谓如此。②)
——《二程遗书》卷三
[注释]
①茅星来解:“指生意周流无间而言。”②茅星来解:“盖取其有自得之意也。”
[译文]
程颢说:周敦颐窗前的草不除去,问他,他说:“草上表现出的生意与我的心意一样。”(本注:张载看驴叫,也是这么说。)
14.19 张子厚闻皇子生,喜甚;见饿莩者,食便不美。①
——《二程遗书》卷三
[注释]
①饿莩:即饿殍,饿死的人或饿得快死的人。《后汉书·仲长统传》:“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短,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殍之满道。”此为已饿死的人。白居易《辨水旱之灾明存救之术策》:“凶歉之年,则贱粜以活饿殍。”此为饿得将死的人。
[译文]
张载听说皇子出生了,就非常高兴;见到有饿死的和饿得奄奄一息的人,吃饭就不香甜。
14.20 伯淳尝与子厚在兴国寺讲论终日,而曰:不知旧日曾有甚人于此处讲此事。①
——《二程遗书》卷一
[注释]
①伯淳:程颢。子厚:张载。兴国寺:即开封相国寺。张伯行解:“千载上下,皆此心此理,则旧日合有如此人,讲论亦合有如此事。”
[译文]
程颢曾和张载在相国寺谈论了一整天,又说:不知道过去曾经有什么人在此处谈论这样的事。
14.21 谢显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则浑是一团和气 。——《二程外书》卷十二
[译文]
谢良佐说:程颢先生坐着安详稳静就像一个泥塑的人,与人相处则全然是一团和气。
14.22 侯师圣云:朱公掞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①游、杨初见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俟立。②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之雪深一尺。③ ——《二程外书》卷十二
[注释]
①侯仲良,字师圣;朱光庭,字公掞。均程颢门人。汝:即汝州,时程颢监汝州酒税。成语“如坐春风”即出此。②游为游酢,杨为杨时,为程门四弟子中二人。程颢死,两人复从程颐学,初见非初次相见,是初次从师。③叶采曰:“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师道尊严,皆盛德所形,但气质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颜子,伊川似孟子。”此即“程门立雪”故事成语出处。
[译文]
侯师圣说:朱光庭到汝州去见程颢,回来后告诉人说:“我朱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游酢、杨时初次去见程颐拜师,程颐瞑目而坐,两人站着等候。程颐醒后,看着他俩说:“你们还在这里呀?天已经晚了,算了吧。”及至出门,门外积雪深一尺。
14.23 刘安礼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气,盎于面背,乐易多恕,终日怡悦。①立之从先生三十年,未尝见其忿厉之容。 ——《二程遗书》附录《门人朋友叙述》
[注释]
①刘立之,字宗礼,二程门人。此作安礼,误,见(10.58)注。粹和之气,盎于面背:《孟子·尽心上》:“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乐易:和乐平易,《荀子·荣辱》:“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
[译文]
刘立之说:程颢先生德性充实完美,粹和之气,漾溢前前后后,和乐平易宽大,一天到晚都是喜悦的。我跟从先生三十年,从未见过他有忿愤严厉的脸色。
14.24 吕与叔撰《明道先生哀词》云①:先生负特立之才,知大学之要;博文强识,躬行力究;察伦明物,极其所止;涣然心释,洞见道体。②其造于约也,虽事变之感不一,知应以是心而不穷;虽天下之理至众,知反之吾身而自足。③其致于一也,异端并立而不能移,圣人复起而不与易。④其养之成也,和气充浃,见于声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优为,从容不迫,然诚心恳恻,弗之措也。⑤其自任之重也,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⑥成名;宁以一物不被泽为己病,不欲以一时之利为己功。其自信之笃也,吾志可行,不苟洁其去就;吾义所安,虽小官有所不屑。⑦ ——《二程遗书》附录
[注释]
①吕与叔:吕大临,二程弟子。《明道先生哀词》,此文又载《伊洛渊源录》卷三。②特立:独出于众人之上,无人可及之意。大学之要:理学家认为,洒扫应对是小学事,尽性至命,成就天德是大学事。《大学》所论也即大学之事。大学之要,在理学家看来,不是治国平天下,而是正心诚意。明王守仁《大学古本序》所论符合程颢之意:“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博文强识:博览古代文献而又有很强的记忆。《论语·雍也》:“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后以“博文”指通晓古代文献。察伦明物:即察于人伦,明于物理。见(13.14)注⑧、(14.17)注⑤。道体:道的本体,道的主旨。《淮南子·人间训》:“或明礼义、推道体而不行,或解构妄言而反当。”③此一节言其学虽博而能达于约。《孟子·离娄下》:“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约,简要,要领。达于约即返于约,掌握要领统领其博。达于约,其心即能应万事无穷之感,以物付物而各得其当;天下之理无穷,而万理归于一理,此一理则可返求之吾身而得之,不假外求而自足。叶采解:“应感无穷,而实本乎吾心;物理散殊,而皆备乎吾身。言其学虽博而有要也。”④叶采解:“致一者,见之明而守之定。故邪说不能移,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也。”⑤充浃:充盈浃洽。崇深:高藏深隐,崇高而又渊深。慢:轻慢,轻视。恳恻:诚恳痛切。汉蔡邕《上封事陈政要七事》:“又元和故事,复申先典,前后制书,推心恳恻。”弗之措:不弃置,不放弃。《礼记·中庸》:“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孔颖达疏:“措,置也。言学不至于能,不措置休废,必待能之乃已也。”这一节说他做事从容不迫,但从不懈怠,从不放弃。⑥一善:一种善行,一种美德。《礼记·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⑦这一节言其出处去就,都以能否行其志、安于义为准的。
[译文]
吕大临作《明道先生哀词》说:先生他负有特立独出之才能,明于高深学问的要领;博学于文献而强记之,亲身践行努力探讨;详察人伦明知事理,透彻地掌握了人之所当止;心中如涣然冰释,透彻理解了大道的本体。他的学问由博而返于约,掌握的要领就在自己一心一身。虽然外事作用于我者变化不一,他明白心是应物之主,以一心随感而应也没有穷尽;天下之理虽然众多,他明白万理皆备于我身,反求于我身则一切理都可自足。他的修养达到了精诚致一的地步,异端之学并兴也不能改变他的自信之心,圣人再生也不会修改他的学说。他的德行养成了,太和之气充盈透彻,表现于声音容貌,使人望见其崇高渊深,无法轻慢;遇事当为而为,从容不迫,然而其至诚之心诚恳深切,做不好决不放弃。他对自己的希望和要求远大,宁可学圣人而未能达到,也不凭借一种善行美德成就名声;宁可把天下有一物不受圣人恩泽看做自己的过错,追求使自己的君主成为尧舜一样的圣君,不把一时的有利于人作为追求的事功。他自信笃厚,只要我的志向能够推行,就不故作高洁而去其位;只要是依义而行我心得安,虽有小官也有所不屑于做。
14.25 吕与叔撰《横渠先生行状》云:康定用兵时,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许,上书谒范文正公。①公知其远器,欲成就之,乃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②,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先生读其书,虽爱之,犹以为未足,于是又访诸释老之书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嘉祐初,见程伯淳、正叔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先生涣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尽弃异学,淳如也。(本注:尹彦明云: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③晚自崇文移疾,西归横渠,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④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学者有问,多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⑤闻者莫不动心有进。尝谓门人:“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命辞无差,然后断事;断事无失,吾乃沛然。精义入神⑥者,豫而已矣。”先生气质刚毅,德盛貌严。然与人居,久而日亲。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语人。虽有未喻,安行而无悔。故识与不识,闻风而畏,非其义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张子全书》卷十五
[注释]
①此条摘录吕大临撰张载行状而成。宋仁宗康定元年,西夏攻宋。时范仲淹为陕西招讨副使。张载上书谒见。②名教:指儒家进行教化的名分、名目、名节、功名,此处泛指儒家学说。③尹彦明:即尹焞。此说极不可信。《二程外书》卷十一载程颐就吕大临所作行状中“尽弃其所学而学焉”(此本作“尽弃异学”,较当)一语说:“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顷年属与叔删去,不谓尚存斯言,几于无忌惮。”张载与二程关系,就年岁说长程颢十二岁,长程颐十三岁,就辈分说为二程表叔,与二程关系密切,学术上互相影响。④宋神宗熙宁二年,张载被召入对,除崇文院校书,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次年移病西归,居横渠镇。崇文院为藏书馆名。简编:指书籍。知礼成性和变化气质是张载学术的突出特点。⑤知礼成性:出张载《经学理窟》,懂得了礼并用以守持形成本性。参见本书(2.86)及注。变化气质:改变其气质之性而恢复其天然本善之性。参见本书(2.101)及注。⑥精义入神:出《周易·系辞下》,参见本书(2.79)及注。
[译文]
吕大临作《横渠先生行状》说:仁宗康定年间同西夏打仗时,张载先生十八岁,当时慨然以立功边疆自许,上书拜见范仲淹。范仲淹看出他是远大之器,想要成就他,就责备他说:“读书人自有读书人的学问,干什么要从事于军事?”于是劝他读《中庸》。张载先生读《中庸》,虽然喜欢,但仍感到不满足,于是又访求佛教、道家之书,读了多年,透彻地了解了佛、道的学问,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又回过头来读六经。嘉祐初年,与程颢、程颐兄弟相见于京师,一同探讨道学之大要。先生他胸中的疑问涣然消释,自信地说:“我们儒学的理论自身十分充足,干什么要寻求别家之说?”于是尽弃异端之学,成为淳正的儒者。(本注:尹焞说:张载过去在京师,坐虎皮,讲《周易》,听的人很多。一天晚上,二程到来,谈论《周易》。第二天,张载撤去虎皮,对学生们说:我平日给诸位所讲的,都是乱说。有二程近日来到,深明《周易》的学问,是我所赶不上的,你们可以去向他们学习。)晚年从崇文院因病去职西归回到横渠镇,一天到晚恭恭敬敬坐在一间房子里,左右放的都是书,俯首而读,仰首而思,有所得就记下来。有时半夜坐起来,点上灯烛去写。他对圣人之道的追求与精深思考,从未有片刻停息,也从未有一刻的忘记。学生有所问,多告诉他们学礼并用礼去持养本性,和学问变化气质的方法,要求学生学习一定要达到圣人的地步才可以。听到他这些话的人无不触动于心而有所进步。他曾经对门人说:“我治学心中有所领悟时,就选取恰当的言辞把它表述出来;表述得没有差失,然后用来判断事务;判断事务没有差失,我就感到胸中充盛了。精熟义理,达到神妙的境界,就要在事情没有出现时,先要熟知有关这事的道理,如此而已。”先生他气质刚毅,德性充盛,容貌严肃。但和人相处,时间久了就一天天亲近。他的治家与在外接交,大致说是正己以感人。人未能信从他,他就回过头来修养自身,而不告诉给人。虽然有的人始终也不明白他的用心,他照样安心而行并不后悔。所以认识他的与不认识他的人,闻其风而畏服,不合义的事,不敢以一丝一毫加到他身上。
14.26 横渠先生曰:二程从十四五时,便锐然欲学圣人。①
——张载《横渠语录》
[注释]
①《经学理窟·学大原上》:“学者不可谓年少,自缓便是四十五十。二程从十四岁时便锐然欲学圣人,今尽及四十未能及颜、闵之徒。小程可如颜子,然恐未如颜子无我。”《论语·先进》载,孔子评价其主要弟子们各自长处:“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译文]
张载说:程颢、程颐兄弟二人,从十四五岁时,就立志锐意要学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