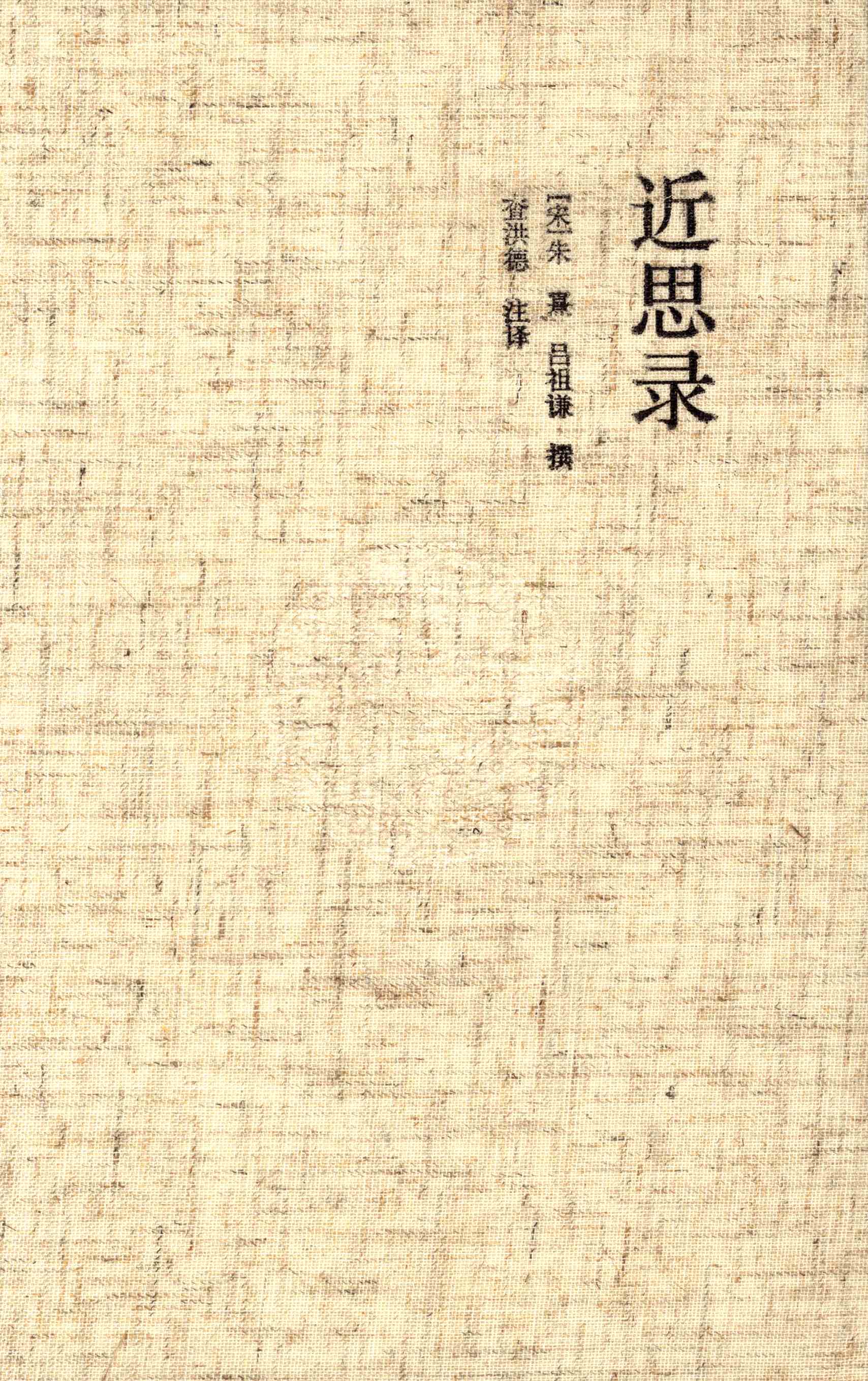内容
13.1 明道先生曰: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①杨氏为我疑②于义;墨氏兼爱疑于仁。申、韩则浅陋易见。故孟子只辟③杨、墨,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杨、墨之比,此所以其惑尤甚。④杨、墨之害,亦经孟子辟之,所以廓如也。 ——《二程遗书》卷十三
[注释]
①杨、墨:即杨朱和墨翟,战国时两位思想家,各自代表一个学派。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互相对立,而又同是儒家的反对派。申、韩:申不害、韩非,两人都是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主张刑名法术,主张君主以权术御下。佛、老:佛教和道家。韩愈排佛,即以佛老为异端,《进学解》:“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②疑:疑似,近似。杨、墨之论,接近与仁义,容易惑众,故要力抵。③辟:驳斥。《孟子·滕文公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也。”因而要“距杨墨,放淫辞”。④叶采解:“佛氏言心性,老氏谈道德,皆近于理,又非杨墨之比,故其为人心之害尤甚。”
[译文]
程颢说:杨、墨学说的危害,比申、韩严重;而佛、老的危害,又比杨、墨严重。杨氏主张为我,与义接近;墨氏主张兼爱,又与仁相似。申、韩的学说则浅陋,容易看出其错处。所以孟子只驳斥杨、墨,因为他们迷惑世人严重。佛、老的言论接近于理,又不是杨、墨的学说所可比的,因此就更为严重地迷惑世人。杨、墨的危害,经过孟子的批驳,所以廓然大明于天下了。
13.2 伊川先生曰: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①,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②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③ ——《二程遗书》卷十七
[注释]
①《论语·先进》:“师也过,商也不及。”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又《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②旧说杨子之学源于子夏,墨子之学出于子张。此说不确,前人已辨其非。叶采解:“子张才高意广,泛爱兼容,故常过乎中。子夏笃信自守,规模谨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于道,亦未远也。然师之过,其流必至于墨氏之兼爱;子夏之不及,其后传……是杨氏为我之学也。”③《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译文]
程颐说:儒者潜心于正道,不允许有所偏差。一有偏差,开始看来偏差极其微小,最终则发展到不可救药。比如说,“子张有些过头,子夏有点不及。”对于圣人的中正之道而言,子张只是过于厚了一点点,子夏只是差一点点还不够。但是厚这一点点就渐渐发展成为兼爱,差那一点点便发展到了为我。其过和不及同是出于儒者,其末流就发展成为杨朱之为我和墨翟之兼爱。进一步说,至于杨、墨,也还不到无父无君的程度,孟子加以推理便到了这地步,那是因为偏差发展下去必然会到这一步。
13.3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①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外于道也远矣。②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若有适有莫,则于道为有间,非天地之全也。③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④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此佛教之所以为隘也。⑤吾道则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圣人于《易》备言之。(本注:又云:佛有一个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⑥ ——《二程遗书》卷四
[注释]
①道之外无物:是说天地万物,一切都依道的法则生成,概莫能外。物之外无道:是说所有的物都体现着道,“率性之谓道”,顺应事物的本性便是道,故物之外无道。②即父子:体现在父子关系上。这几句说:释氏之说离道很远。佛家以地、水、风、火为四大,人身也由四大幻化而成,主张寂灭幻根,断除一切。如此一来,不知身由何处而来,是不知有父母,所以说是毁人伦。断除四大,则不知有身,更不知心存何处。所谓道,即存其本心。不知心之所存,所以离道当然太远了。③见《论语·里仁》。佛教认定寂灭为可,是“适”,而处事应物为不可,是“莫”。有适有莫:就不是顺应天地之性,破坏了天地完整自然之性,是“非天地之全”。④《周易·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张伯行解:“就释氏之学论之,习定此心,收敛虚静,亦若吾儒常惺惺之法,与所云‘敬以直内’者相合。然天下事理,各有当然之义。一切扫灭,不求精察,则有体无用,吾儒所云‘义以方外’者,未之有也。既无方外之义,则敬之云者,亦只是一个灵觉”,“其直内之本,亦不是矣”。⑤张伯行解:“一味拘滞固执不化者,则劳筋苦骨,屠肤乞钵,入于枯槁而无人道;其疏旷自恣,矫语通达者,则浮沤世故,超豁顿悟,归于恣肆而侮天地。是皆外物以为道之病。”⑥觉:即觉悟,通过虚静的内心修持,而超越迷惑的世界,超越生死的烦恼,而悟解佛的妙境。与儒家“敬以直内”有某些相通处。朱熹言,此条“游定夫所编,恐有差误”。
[译文]
程颢说:道之外没有物,物之外也没有道,如此则天地之间,无处不体现着道。就父子说,父子之道在则父子亲,就君臣说,君臣之道在则君臣之分严,以至于为夫妇之道、长幼之道、朋友之道,没有任何一事而不遵循着道的,这就是道一刻也离不了的原因。那么佛教的毁灭人伦、断除四大,就离道远了。所以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既不执著于一定要怎么做,也不坚持不怎么做,怎么做合乎义便怎么做。”如果一定要怎样或一定不怎样,那么和道之间就有了差距,破坏了天地之性的自然。他们佛家的学说,在“敬以直内”方面有一些,而“义以方外”则没有。所以那些偏执固守的人就走向苦修行,那些疏旷放达的人就流于恣意放肆,这些都是佛教偏狭的地方。我们儒家之道则没有这些弊病,顺着天地万物的本性做去就是了,这就是理。圣人在《周易》中说得很周详了。(本注:又说:佛教有一个觉悟之理,可用作“敬以直内”了,但是没有“义以方外”,那么其使内心正直的,从根本上说也不对了。)
13.4 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①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②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谓识心见性是也。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③彼固曰:“出家独善”,便于道体自不足。④或曰: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人设此怖,令为善。先生曰:至诚贯天地,人尚有不化,岂有立伪教而人可化乎?
——《二程遗书》卷十三
[注释]
①叶采解:“释氏谓有生必有灭,故有轮回。今求不生不灭之理,可免轮回之苦,此本出于利己之私意也。”②《论语·宪问》:“下学而上达。”下学,指就人事上学习普通的知识。上达,透悟高深的道理,或上达天命。叶采曰:“绝学而求顿悟,故无下学工夫。”茅星来解:“务上达者,求了悟也。无下学者,屏弃事物也。人之所以事事物物穷究其理者,惟求其有是无非则已。今既扫除一切,而惟求此心之了悟,故曰:‘岂有是也?’”不相连属、有间断,均指下学与上达之间不连属、有间断。张伯行解:“道本是彻上彻下,周流连属。若离下求上,则元不连属,有间断而非道矣,尚可谓上达乎?”③引文见《孟子·尽心上》。茅星来解:“识心即离念,见性即解脱。”朱熹曰:“此恐纪录者有误。盖释氏于心性之间,固不可谓之无所见,但只略见得些心性影子,初未尝仔细向里面体会。其理亦不可谓之不能存养,但只存养得所见影子,非心性之真耳。”④出家独善:是说佛教的出家为僧,如儒家所提倡的独善其身。叶采解:“道本人伦,今日出家,则于道体亏欠大矣。”
[译文]
佛教原本害怕生死轮回,学佛以求免除生死轮回之苦,那是出于利己,哪里是公道?只求悟彻玄深之理而没有就事物上下实学工夫,那么他们要了悟的,哪有正确的道理呢?实学工夫与悟彻事理不能连起来,中间只要有间断,就不是道。孟子说:“充分发扬善的本心,这就显示明白了人的本性。”佛教说的认识本心发展本性说的就是这道理。至于存心养性方面的事,则没有。他们当然会说,“出家独善其身”,只是出家就损伤道体。有人说:佛教地狱之类的说法,都是为根基智质低下的人所设的一种恫吓,使他们因惧怕而为善。程颢说:天下惟有诚心能感化人,圣人至诚之心贯彻天地,人尚且有不为所化者,难道设立一个本无诚心的伪教,人倒可以被感化吗?
13.5 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其中矣。颜渊问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复戒以“放郑声,远佞人”。曰:“郑声淫,佞人殆。”①彼佞人者,是他一边佞耳,然而于己则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于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②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须著如此戒惧,犹恐不免。释氏之学,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后,便不能乱得。 ——《二程遗书》卷二上
[注释]
①《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殆,危险。②见《尚书·皋陶谟》。参见(12.13)。
[译文]
学者对于佛教的学说,只应像对待淫声美色一样远远地离开,否则,就会急急忙忙地跑到里边去。颜回问如何治国,孔子告诉了他二帝三王之事以后,又告诫他“抛弃郑地的音乐,远离巧牙利舌的小人”,说:“郑国的音乐淫荡,奸佞的小人危险。”那些奸佞的小人,就他本身说是能说会道,但对于你来说则是危险。只因为他能使人为之改变,所以危险。至于大禹说的“何畏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只需要畏惧。只是必须做到如此戒惧谨慎,尚且恐怕不免为之所动。佛教的学说,更不用说是要常常戒备的了,直到自己有了自信以后,它就不能扰乱你了。
13.6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①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②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③快活。释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得去尽根尘④。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释氏其实是爱身,放不得,故说许多。譬如负版之虫,已载不起,犹自更取物在身。⑤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终不道放下石头,惟嫌重也。
——《二程遗书》卷二上
[注释]
①此理:如说“是道”,理学家所谓先天地而生又禀赋于万物的理。《周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孳生不绝,繁衍不已。孔颖达疏:“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②人则能推:《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推即推而行之,通即会通适变。程颢又说:“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则推有推广、推行、实行、验证等义。又说:“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如此,“推”之义可明。物不能推,不能说物不有此理。③大小大:宋时俗语,何等、多么之意。江永按:“大小大快活,犹云许多快活也。”④根尘:六根六尘。佛家以耳、目、口、鼻、身、意为六根,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眼入色、耳入声、鼻入臭、舌入味、身入触、意入法,为六入,认为幻尘灭故幻根亦灭,幻根灭故幻心亦灭。所以要去尽根尘。⑤柳宗元《蝜蝂传》:“蝜蝂者,善负之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印其首负之,负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率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译文]
所以说万物一体的原因,是万物都具备这同一天理,只因为都从这天理中来。《周易》说:“生生不已就是易。”虽然就道说是生生不已变易无穷,物之生则是一时所生,所有的人和物,自其生成,理就完备无缺。人禀气清,则能推扩此理,物则禀气昏而不能推而扩之,但不可说物不与人一样具有此理。只因为人自私,只在自己身体上去思考,所以把这广大无边无处不在的理看得小了。要把这身体放在万物之中,与万物一样看待,大小一切事,都得极大快活。佛教不懂得万物一体、身与万物为一的道理,只就他身上去思考,又拿这身体无可奈何,所以就厌恶躯体,想要去尽六根六尘,而后归于清净。又因为心源不定,所以要使这心如枯木死灰无息无动。然而既有身有心,就决无静定如枯木死灰的道理,要得有此道理,除非是人死去。佛教其实是爱怜自己的身体,放不下,不能忘却物我之别将此身同于万物,所以才说了许多舍弃身躯的话。就像一只蝜蝂,背负的东西已经使它跌倒起不来了,它仍然要再取物放在身上。佛教以躯体的负累,已经压得他受不了了,还是要背负着不肯放下(能理会得万物一体,身与万物为一,忘却物我之分,即忘我就是放下)。又像抱着石头投河,因为石头重就越加向下沉,只嫌这石头太重,却到底也想不到把这石头放下,只嫌躯体为负累(却不懂得要忘我以解除这负累)。
13.7 人有语导气①者,问先生曰:君亦有术乎?曰:吾尝夏葛而冬裘②,饥食而渴饮,节嗜欲,定心气,如斯而已。
——《二程遗书》卷四
[注释]
①导气:即导引,又作道引,是一种呼吸与动作配合的功法。《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是一种养生术。②夏葛而冬裘: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意谓顺天理之自然。
[译文]
有一个谈论导气之术的人,问程颢:您也有养生之术吗?程颢回答说:我常常是夏天穿单葛衣冬天穿皮衣,饥了就吃饭渴了就饮水,节制自己的嗜欲,静定自己的心气,如此而已。
13.8 佛氏不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安得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乎?① ——《二程遗书》卷十四
[注释]
①叶采解:“形而上者,性命也。阴阳、昼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气之屈伸。释氏指为轮回、为幻妄,则其所谈性命,亦异乎圣人矣。”《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指尚未形成物的形质而又超乎形质之上的东西,或称道,或称命,或称性。儒家所谈的形而上者,是性、命。佛教讲见性成佛,似乎与儒家形而上者同,程颢加以辩驳,说:既然佛教把儒家认为的是天命流行、二气屈伸所形成的阴阳、昼夜、死生、古今解释成轮回,以为是幻妄,那么他们说的性、命也就不同于儒家所说的性、命。
[译文]
佛家不懂得阴阳、昼夜、死生、古今是怎样形成的,那怎么能说他们说的形而上者与圣人所说的形而上者相同呢?
13.9 释氏之说,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而为佛矣。只且于迹上考之。①其设教如是,则其心果如何?②固难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则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乱说。③故不若且于迹上断定不与圣人合,其言有合处,则吾道固已有。有不合处,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甚省易。
——《二程遗书》卷十五
[注释]
①迹:形迹,心的表现,现象性的东西。宋李觏《易论》:“事以时变者其迹也,统而论之者其心也。”此指其表现在外的行为、行事等。②江永按:“毁弃人伦是其迹之大异者,然则其心皆无父无君也,尚何取于彼哉?”③《中说·问易篇》载,魏征问:“圣人有忧乎?”王通答:“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问疑,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魏征不同意,对董常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王通说:“汝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
[译文]
程颐说:佛教的学说,如果想透彻研究而后加以选择吸收,那么你还没能研究透它,自身就已经化为佛徒了。只且就它的行事上考察。他们设教如此(弃人伦,无君臣父子),那么他们的存心到底怎么样呢?固然难以只吸取他的存心而不取他的行事,有这样的存心,就会有这样的行事。王通言心和迹的分别,就是乱说。所以不如先从行事上断定它与圣人不合,那些言论有相合的地方,那么我儒家学说中本来已有。有不相合的地方,固然是不吸取的。这样立定脚跟,却很容易。
13.10 问:神仙之说有诸?曰:若说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言居山林间保形炼气①以延年益寿则有之。譬如一炉火,置之风中则易过②,置之密室则难过,有此理也。又问:扬子曰:“圣人不师仙,厥术异也。”圣人能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间一贼,若非窃造化之机,安能延年?使圣人肯为,周、孔为之久③矣。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保形:保养形体。炼气:道家之说,指通过吐纳导引等术以求长生的方法。见扬雄《法言·君子篇》。②过:宋元俗语,火熄灭。③底本无“久”字,据《二程遗书》补。
[译文]
有人问:人们说的修炼成仙这种事有没有呢?程颐说:如果说白日飞升之类的事是没有的,如果说居住山林之中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则是有的。人的生命就像一炉火,把它放在风中就容易熄灭,放在密室之中就难以熄灭,就是这个道理。又问:扬雄说:“圣人不学神仙之事,因为所操之术不同。”圣人不肯做这类事,那么圣人能不能做呢?程颐说:求延年益寿的人是天地间一贼,人之寿夭由造物者司掌,他若不是窃取了造物者的权柄,怎么能延年?假如圣人肯做这种盗贼的事,周公、孔子决不是不能做,该是已经做了好久了。
13.11 谢显道历举佛说与吾儒同处问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①
——《二程外书》卷十二
[注释]
①谢显道:谢良佐字显道,程门四大弟子之一,见(2.77)注。本领:本源,根本,主旨,要领。《朱子语类》卷二十七:“本领若是,事事发出来皆是;本领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
[译文]
谢良佐历举佛教之说与儒家相同之处问程颐,程颐说:如此相同的地方虽然多,只是根本与要领不对,一齐全都差了。
13.12 横渠先生曰: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虚空之大,此所以语大语小,流遁失中。①其过于大也,尘芥六合;其蔽于小也,梦幻人世。②谓之穷理可乎?不知穷理而谓之尽性可乎?谓之无不知可乎?尘芥六合,谓天地为有穷也;梦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从也。
——张载《正蒙·大心》
[注释]
①佛教认为,心的真如是绝对不变的实体,是真实,而尘世的一切都非真实,而是人心的幻象,因而都是虚妄的。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产生色、声、香、味、触、法六识,由此形成天地世界,即天地是由人心的因缘发生的。《周易·系辞上》:“范围天地之化。”范围之意,是如果将天地造化比作熔炉中的铁汁,则易理就是铸造的模型,造物千变万化,不出其范围。今人或译作包括,或解为裁成。以上一段,是讲天地生成本体论上理学与佛教的矛盾:理学认为天地由先于天地之理生成,佛教认为天地是人心的幻象。流遁:放逸而失于正道。为一身之小所蔽,而不能认识天地功用的广大无边,这是说佛教只从人身六根去认识天地。人的志趣本应以笃实为贵,佛教却沉迷于对虚空之大的追求。所以佛教所说的小和大,都不切于中正。②佛教认为,一微尘芥子中有无限大千世界。六合即天地四方。佛教又认为人世不是真实的,就如梦幻泡影。
[译文]
张载说:佛家不懂天性而臆断胡说,不懂得天理裁成天地万物的功用,反而以小小的人的感官为生成天地的因缘,他们的聪明不能透彻了解天地日月的来处,就谎说天地日月是幻妄,由一身之小蔽塞着而不知天地功用之大,志趣又沉溺于对虚空之大的追求,因此他们谈论大谈论小,全都流于荒诞而不得其中。其关于大的说法的错误,认为一微尘芥子中有天地四方;其为小所蒙蔽处,认为人世全是心的梦幻。说他们穷究事理行吗?不能穷尽事理却说他们能充分扩充其本善之性行吗?说他们无所不知行吗?说尘芥之中有六合,是认为天地是有穷尽的;以人世为梦幻,说明他们不能推究人世的来处。
13.13 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①
——张载《正蒙·大易》
[注释]
①茅星来解:“《系辞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夫形而上、下者皆谓之形,则其不得以道与器分有形无形明矣。而孔氏正义乃以道为无,以器为有,且曰:‘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唯在于有。’盖自王弼祖述老庄而以有无论易,而孔氏专主王注,故其说云然。张子之言,盖为此而发。”孔氏,指唐经学家孔颖达,有《五经正义》。王弼,三国魏玄学家,有《周易注》。张载所以批有无之论,是因言有无就入于老、庄。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道为无,以器为有,正同此说。按此语又见《横渠易说·系辞上》。《周易·系辞上》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张载之解,针对“幽明之故”。此条上文有:“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张载此语乃针对老庄将“无”“皆归之空虚”而发。
[译文]
大《易》不谈论有无。谈论有无,是诸子的浅陋。
13.14浮图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①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②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③大学当先知天德,④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图剧论要归,必谓死生流转,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本注: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通阴阳,体之无二。)⑤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⑥乃其俗达之天下,致善恶、知愚、男女、臧获,人人著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⑦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⑧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⑨自古诐、淫、邪、遁之辞,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⑩向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哉?——张载《正蒙·乾称》
[注释]
①浮图:又作浮屠,即佛陀。佛,此指佛教。见(9.17)注。明鬼:《墨子》有《明鬼》篇,说明鬼的存在。这里说,佛教相信鬼的存在。受生循环:指佛家所谓的六道轮回,即认为人死后为鬼,鬼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中循环转变,最为痛苦可怕,只有得道成佛到极乐世界,才能免除这种痛苦。张载认为人由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气散则归于太虚,以其归也,故名为鬼。厌苦:厌烦以为苦事,此指厌烦轮回之苦。妄见:佛教语,佛教认为一切皆非实有,肯定存在都是妄见,和“真如”相对。《楞严经》卷四:“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儒家认为天人本为一体,人死自然归天,而佛家却认为只有成佛才能升天,是妄生取舍。②儒家认为,天指太虚,气化流行谓道。道存在于天。而佛教直以天为道。③《周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韩康伯注:“精气缊,聚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游魂,言其游散也。”游魂,指的是游散之气。信佛者则认为游魂是人死后的鬼魂,而“变”就是六道轮回。④大学:大的学问。茅星来解:“指儒者之学。”天德:茅星来解:“即天道之本然者,如下文所谓死生、天人、昼夜、阳阴之类皆是。”注见(2.34)。⑤剧论:激切论辩,极力要论证的。要归:要旨与归趣,立论之关键。叶采解:“当生而生,当死而死,是则有义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厌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昼夜,通阴阳,则知生死之说,何所谓轮回?”按《孟子·告子上》:“舍生而取义。”人的死生都服从于义,义当死则不求生。《论语·颜渊》:“死生有命。”此即有义有命。⑥门墙:师门。《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沦胥:沦陷、沦丧,陷溺。沦胥其间,指为大道:沉溺其中,认为其教为高明的学说。按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经梁武帝,到唐宪宗时大盛。⑦英才间气:如说英雄豪杰。耳目恬习:看得习惯,听得习惯,不以为怪,而可以安。世儒:俗儒。《史记·律书》:“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遂执不移等哉!”⑧《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赵岐注:“舜明庶物之情,察人事之序。”庶物,即普通的事物。忽:政治之混乱。《尚书·益稷》:“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蔡沈集传:“在,察也。忽,治之反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忽,乱也。⑨茅星来解:“上无礼则法度不立,故无以防其伪;下无学则不知是非,故无以稽其弊。”上指执政者,下指士。⑩《孟子·公孙丑上》:“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诐(bì)辞是偏颇不全面的话,淫辞是过分的话,邪辞是不合正道的话,遁辞是躲躲闪闪的话。翕然:兴盛、盛行的样子。
[译文]
佛教谈论鬼,说那些有见识的鬼,在要他投生轮回时,就厌倦轮回之苦,宁可不投生以求免于轮回之苦。能说佛徒们懂得什么是鬼吗?佛教认为人生是幻妄不实的,这能说他们了解人吗?天与人原本是一物,佛教却弃人事而追求升天成佛,这能说他们懂得什么是天吗?孔孟所说的天,他们却称为道。被佛教迷惑的人又把“游魂为变”当做六道轮回,这真是不加思考的乱说。学儒学的人应该先了解天道运行的本然,了解了天道运行的本然,也就懂得了圣人的学说,也就明白了什么是鬼神。现在佛家理论的关键,一定要讲到死生轮回,说除非得道成佛的人不能免于轮回之苦,说他们悟解了道可以吗?(本注:如果悟道,就会懂得死生有义有命决定,同等地看待生和死,把天人看做一体,明白了昼夜、阴阳之理,用昼夜、阴阳之理去体验死生、天人之理,其理原本无二。)自从佛家学说盛传于中国,读书人尚未来得及窥见儒家圣学的师门,已经被佛学引诱而去,沉陷其间,指佛教为高明的学说。佛教之俗风行天下,以至于不论善恶、智愚、男女、奴婢,人人信仰。即使有英雄豪杰,生下来耳濡目染看惯了佛家之事,长大后又学习了无学无识的俗儒崇尚佛教的言论,于是糊里糊涂地被驱赶到佛教那里去了,为佛教顿悟及识心成佛之说(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迷惑,于是就认为不用修养就可成为圣人,不用学习就可悟彻大道。所以还不了解圣人之存心,就说不必推求圣人的行事;还不理解君子的志趣,就说不必去阅读他们的文字。因此而不能体察人事之序,不能明了事物之情,政事因此被忽视,德行因此被搞乱。异端之说灌满耳朵,在上者没有一个法度以防其伪诈,在下的人没有学问不能考出其弊病。自古以来一切诐辞、淫辞、邪辞、遁辞,一下子全都兴盛起来,全都是出于佛教之门,已达一千五百年之久。如果不是能独立不惧,精诚专一坚定自信,有远远超过一般人才识的人,怎么能卓然正身立于其间,而与之较量、辨析是非得失呢?
[注释]
①杨、墨:即杨朱和墨翟,战国时两位思想家,各自代表一个学派。杨朱主张为我,墨子主张兼爱,互相对立,而又同是儒家的反对派。申、韩:申不害、韩非,两人都是战国时法家代表人物,主张刑名法术,主张君主以权术御下。佛、老:佛教和道家。韩愈排佛,即以佛老为异端,《进学解》:“先生之业可谓勤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②疑:疑似,近似。杨、墨之论,接近与仁义,容易惑众,故要力抵。③辟:驳斥。《孟子·滕文公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者也。”因而要“距杨墨,放淫辞”。④叶采解:“佛氏言心性,老氏谈道德,皆近于理,又非杨墨之比,故其为人心之害尤甚。”
[译文]
程颢说:杨、墨学说的危害,比申、韩严重;而佛、老的危害,又比杨、墨严重。杨氏主张为我,与义接近;墨氏主张兼爱,又与仁相似。申、韩的学说则浅陋,容易看出其错处。所以孟子只驳斥杨、墨,因为他们迷惑世人严重。佛、老的言论接近于理,又不是杨、墨的学说所可比的,因此就更为严重地迷惑世人。杨、墨的危害,经过孟子的批驳,所以廓然大明于天下了。
13.2 伊川先生曰:儒者潜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终则不可救。如“师也过,商也不及”①,于圣人中道,师只是过于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则渐至于兼爱,不及则便至于为我。其过、不及,同出于儒者,其末遂至杨、墨。②至如杨、墨,亦未至于无父无君,孟子推之便至于此,盖其差必至于是也。③ ——《二程遗书》卷十七
[注释]
①《论语·先进》:“师也过,商也不及。”师,颛孙师,即子张。商,卜商,即子夏。又《礼记·仲尼燕居》:“子曰:师尔过,而商也不及。”②旧说杨子之学源于子夏,墨子之学出于子张。此说不确,前人已辨其非。叶采解:“子张才高意广,泛爱兼容,故常过乎中。子夏笃信自守,规模谨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于道,亦未远也。然师之过,其流必至于墨氏之兼爱;子夏之不及,其后传……是杨氏为我之学也。”③《孟子·滕文公下》:“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译文]
程颐说:儒者潜心于正道,不允许有所偏差。一有偏差,开始看来偏差极其微小,最终则发展到不可救药。比如说,“子张有些过头,子夏有点不及。”对于圣人的中正之道而言,子张只是过于厚了一点点,子夏只是差一点点还不够。但是厚这一点点就渐渐发展成为兼爱,差那一点点便发展到了为我。其过和不及同是出于儒者,其末流就发展成为杨朱之为我和墨翟之兼爱。进一步说,至于杨、墨,也还不到无父无君的程度,孟子加以推理便到了这地步,那是因为偏差发展下去必然会到这一步。
13.3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无物,物之外无道,是天地之间,无适而非道也。①即父子而父子在所亲,即君臣而君臣在所严,以至为夫妇、为长幼、为朋友,无所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须臾离也。然则毁人伦、去四大者,其外于道也远矣。②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若有适有莫,则于道为有间,非天地之全也。③彼释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④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此佛教之所以为隘也。⑤吾道则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圣人于《易》备言之。(本注:又云:佛有一个觉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无“义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⑥ ——《二程遗书》卷四
[注释]
①道之外无物:是说天地万物,一切都依道的法则生成,概莫能外。物之外无道:是说所有的物都体现着道,“率性之谓道”,顺应事物的本性便是道,故物之外无道。②即父子:体现在父子关系上。这几句说:释氏之说离道很远。佛家以地、水、风、火为四大,人身也由四大幻化而成,主张寂灭幻根,断除一切。如此一来,不知身由何处而来,是不知有父母,所以说是毁人伦。断除四大,则不知有身,更不知心存何处。所谓道,即存其本心。不知心之所存,所以离道当然太远了。③见《论语·里仁》。佛教认定寂灭为可,是“适”,而处事应物为不可,是“莫”。有适有莫:就不是顺应天地之性,破坏了天地完整自然之性,是“非天地之全”。④《周易·坤·文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张伯行解:“就释氏之学论之,习定此心,收敛虚静,亦若吾儒常惺惺之法,与所云‘敬以直内’者相合。然天下事理,各有当然之义。一切扫灭,不求精察,则有体无用,吾儒所云‘义以方外’者,未之有也。既无方外之义,则敬之云者,亦只是一个灵觉”,“其直内之本,亦不是矣”。⑤张伯行解:“一味拘滞固执不化者,则劳筋苦骨,屠肤乞钵,入于枯槁而无人道;其疏旷自恣,矫语通达者,则浮沤世故,超豁顿悟,归于恣肆而侮天地。是皆外物以为道之病。”⑥觉:即觉悟,通过虚静的内心修持,而超越迷惑的世界,超越生死的烦恼,而悟解佛的妙境。与儒家“敬以直内”有某些相通处。朱熹言,此条“游定夫所编,恐有差误”。
[译文]
程颢说:道之外没有物,物之外也没有道,如此则天地之间,无处不体现着道。就父子说,父子之道在则父子亲,就君臣说,君臣之道在则君臣之分严,以至于为夫妇之道、长幼之道、朋友之道,没有任何一事而不遵循着道的,这就是道一刻也离不了的原因。那么佛教的毁灭人伦、断除四大,就离道远了。所以孔子说:“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既不执著于一定要怎么做,也不坚持不怎么做,怎么做合乎义便怎么做。”如果一定要怎样或一定不怎样,那么和道之间就有了差距,破坏了天地之性的自然。他们佛家的学说,在“敬以直内”方面有一些,而“义以方外”则没有。所以那些偏执固守的人就走向苦修行,那些疏旷放达的人就流于恣意放肆,这些都是佛教偏狭的地方。我们儒家之道则没有这些弊病,顺着天地万物的本性做去就是了,这就是理。圣人在《周易》中说得很周详了。(本注:又说:佛教有一个觉悟之理,可用作“敬以直内”了,但是没有“义以方外”,那么其使内心正直的,从根本上说也不对了。)
13.4 释氏本怖死生,为利,岂是公道?①唯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②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谓识心见性是也。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③彼固曰:“出家独善”,便于道体自不足。④或曰:释氏地狱之类,皆是为下根之人设此怖,令为善。先生曰:至诚贯天地,人尚有不化,岂有立伪教而人可化乎?
——《二程遗书》卷十三
[注释]
①叶采解:“释氏谓有生必有灭,故有轮回。今求不生不灭之理,可免轮回之苦,此本出于利己之私意也。”②《论语·宪问》:“下学而上达。”下学,指就人事上学习普通的知识。上达,透悟高深的道理,或上达天命。叶采曰:“绝学而求顿悟,故无下学工夫。”茅星来解:“务上达者,求了悟也。无下学者,屏弃事物也。人之所以事事物物穷究其理者,惟求其有是无非则已。今既扫除一切,而惟求此心之了悟,故曰:‘岂有是也?’”不相连属、有间断,均指下学与上达之间不连属、有间断。张伯行解:“道本是彻上彻下,周流连属。若离下求上,则元不连属,有间断而非道矣,尚可谓上达乎?”③引文见《孟子·尽心上》。茅星来解:“识心即离念,见性即解脱。”朱熹曰:“此恐纪录者有误。盖释氏于心性之间,固不可谓之无所见,但只略见得些心性影子,初未尝仔细向里面体会。其理亦不可谓之不能存养,但只存养得所见影子,非心性之真耳。”④出家独善:是说佛教的出家为僧,如儒家所提倡的独善其身。叶采解:“道本人伦,今日出家,则于道体亏欠大矣。”
[译文]
佛教原本害怕生死轮回,学佛以求免除生死轮回之苦,那是出于利己,哪里是公道?只求悟彻玄深之理而没有就事物上下实学工夫,那么他们要了悟的,哪有正确的道理呢?实学工夫与悟彻事理不能连起来,中间只要有间断,就不是道。孟子说:“充分发扬善的本心,这就显示明白了人的本性。”佛教说的认识本心发展本性说的就是这道理。至于存心养性方面的事,则没有。他们当然会说,“出家独善其身”,只是出家就损伤道体。有人说:佛教地狱之类的说法,都是为根基智质低下的人所设的一种恫吓,使他们因惧怕而为善。程颢说:天下惟有诚心能感化人,圣人至诚之心贯彻天地,人尚且有不为所化者,难道设立一个本无诚心的伪教,人倒可以被感化吗?
13.5 学者于释氏之说,直须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其中矣。颜渊问为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复戒以“放郑声,远佞人”。曰:“郑声淫,佞人殆。”①彼佞人者,是他一边佞耳,然而于己则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于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②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须著如此戒惧,犹恐不免。释氏之学,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后,便不能乱得。 ——《二程遗书》卷二上
[注释]
①《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殆,危险。②见《尚书·皋陶谟》。参见(12.13)。
[译文]
学者对于佛教的学说,只应像对待淫声美色一样远远地离开,否则,就会急急忙忙地跑到里边去。颜回问如何治国,孔子告诉了他二帝三王之事以后,又告诫他“抛弃郑地的音乐,远离巧牙利舌的小人”,说:“郑国的音乐淫荡,奸佞的小人危险。”那些奸佞的小人,就他本身说是能说会道,但对于你来说则是危险。只因为他能使人为之改变,所以危险。至于大禹说的“何畏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只需要畏惧。只是必须做到如此戒惧谨慎,尚且恐怕不免为之所动。佛教的学说,更不用说是要常常戒备的了,直到自己有了自信以后,它就不能扰乱你了。
13.6 所以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①人则能推,物则气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与有也。②人只为自私,将自家躯壳上头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③快活。释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得去尽根尘④。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释氏其实是爱身,放不得,故说许多。譬如负版之虫,已载不起,犹自更取物在身。⑤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终不道放下石头,惟嫌重也。
——《二程遗书》卷二上
[注释]
①此理:如说“是道”,理学家所谓先天地而生又禀赋于万物的理。《周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孳生不绝,繁衍不已。孔颖达疏:“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②人则能推:《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推即推而行之,通即会通适变。程颢又说:“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则推有推广、推行、实行、验证等义。又说:“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虽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如此,“推”之义可明。物不能推,不能说物不有此理。③大小大:宋时俗语,何等、多么之意。江永按:“大小大快活,犹云许多快活也。”④根尘:六根六尘。佛家以耳、目、口、鼻、身、意为六根,以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眼入色、耳入声、鼻入臭、舌入味、身入触、意入法,为六入,认为幻尘灭故幻根亦灭,幻根灭故幻心亦灭。所以要去尽根尘。⑤柳宗元《蝜蝂传》:“蝜蝂者,善负之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印其首负之,负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率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
[译文]
所以说万物一体的原因,是万物都具备这同一天理,只因为都从这天理中来。《周易》说:“生生不已就是易。”虽然就道说是生生不已变易无穷,物之生则是一时所生,所有的人和物,自其生成,理就完备无缺。人禀气清,则能推扩此理,物则禀气昏而不能推而扩之,但不可说物不与人一样具有此理。只因为人自私,只在自己身体上去思考,所以把这广大无边无处不在的理看得小了。要把这身体放在万物之中,与万物一样看待,大小一切事,都得极大快活。佛教不懂得万物一体、身与万物为一的道理,只就他身上去思考,又拿这身体无可奈何,所以就厌恶躯体,想要去尽六根六尘,而后归于清净。又因为心源不定,所以要使这心如枯木死灰无息无动。然而既有身有心,就决无静定如枯木死灰的道理,要得有此道理,除非是人死去。佛教其实是爱怜自己的身体,放不下,不能忘却物我之别将此身同于万物,所以才说了许多舍弃身躯的话。就像一只蝜蝂,背负的东西已经使它跌倒起不来了,它仍然要再取物放在身上。佛教以躯体的负累,已经压得他受不了了,还是要背负着不肯放下(能理会得万物一体,身与万物为一,忘却物我之分,即忘我就是放下)。又像抱着石头投河,因为石头重就越加向下沉,只嫌这石头太重,却到底也想不到把这石头放下,只嫌躯体为负累(却不懂得要忘我以解除这负累)。
13.7 人有语导气①者,问先生曰:君亦有术乎?曰:吾尝夏葛而冬裘②,饥食而渴饮,节嗜欲,定心气,如斯而已。
——《二程遗书》卷四
[注释]
①导气:即导引,又作道引,是一种呼吸与动作配合的功法。《庄子·刻意》:“吹呴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是一种养生术。②夏葛而冬裘: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意谓顺天理之自然。
[译文]
有一个谈论导气之术的人,问程颢:您也有养生之术吗?程颢回答说:我常常是夏天穿单葛衣冬天穿皮衣,饥了就吃饭渴了就饮水,节制自己的嗜欲,静定自己的心气,如此而已。
13.8 佛氏不识阴阳、昼夜、死生、古今,安得谓形而上者与圣人同乎?① ——《二程遗书》卷十四
[注释]
①叶采解:“形而上者,性命也。阴阳、昼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气之屈伸。释氏指为轮回、为幻妄,则其所谈性命,亦异乎圣人矣。”《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上指尚未形成物的形质而又超乎形质之上的东西,或称道,或称命,或称性。儒家所谈的形而上者,是性、命。佛教讲见性成佛,似乎与儒家形而上者同,程颢加以辩驳,说:既然佛教把儒家认为的是天命流行、二气屈伸所形成的阴阳、昼夜、死生、古今解释成轮回,以为是幻妄,那么他们说的性、命也就不同于儒家所说的性、命。
[译文]
佛家不懂得阴阳、昼夜、死生、古今是怎样形成的,那怎么能说他们说的形而上者与圣人所说的形而上者相同呢?
13.9 释氏之说,若欲穷其说而去取之,则其说未能穷,固已化而为佛矣。只且于迹上考之。①其设教如是,则其心果如何?②固难为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则有是迹。王通言心迹之判,便是乱说。③故不若且于迹上断定不与圣人合,其言有合处,则吾道固已有。有不合处,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甚省易。
——《二程遗书》卷十五
[注释]
①迹:形迹,心的表现,现象性的东西。宋李觏《易论》:“事以时变者其迹也,统而论之者其心也。”此指其表现在外的行为、行事等。②江永按:“毁弃人伦是其迹之大异者,然则其心皆无父无君也,尚何取于彼哉?”③《中说·问易篇》载,魏征问:“圣人有忧乎?”王通答:“天下皆忧,吾独得不忧?”问疑,曰:“天下皆疑,吾独得不疑?”魏征不同意,对董常说:“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王通说:“汝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
[译文]
程颐说:佛教的学说,如果想透彻研究而后加以选择吸收,那么你还没能研究透它,自身就已经化为佛徒了。只且就它的行事上考察。他们设教如此(弃人伦,无君臣父子),那么他们的存心到底怎么样呢?固然难以只吸取他的存心而不取他的行事,有这样的存心,就会有这样的行事。王通言心和迹的分别,就是乱说。所以不如先从行事上断定它与圣人不合,那些言论有相合的地方,那么我儒家学说中本来已有。有不相合的地方,固然是不吸取的。这样立定脚跟,却很容易。
13.10 问:神仙之说有诸?曰:若说白日飞升之类则无,若言居山林间保形炼气①以延年益寿则有之。譬如一炉火,置之风中则易过②,置之密室则难过,有此理也。又问:扬子曰:“圣人不师仙,厥术异也。”圣人能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间一贼,若非窃造化之机,安能延年?使圣人肯为,周、孔为之久③矣。 ——《二程遗书》卷十八
[注释]
①保形:保养形体。炼气:道家之说,指通过吐纳导引等术以求长生的方法。见扬雄《法言·君子篇》。②过:宋元俗语,火熄灭。③底本无“久”字,据《二程遗书》补。
[译文]
有人问:人们说的修炼成仙这种事有没有呢?程颐说:如果说白日飞升之类的事是没有的,如果说居住山林之中保形炼气以延年益寿则是有的。人的生命就像一炉火,把它放在风中就容易熄灭,放在密室之中就难以熄灭,就是这个道理。又问:扬雄说:“圣人不学神仙之事,因为所操之术不同。”圣人不肯做这类事,那么圣人能不能做呢?程颐说:求延年益寿的人是天地间一贼,人之寿夭由造物者司掌,他若不是窃取了造物者的权柄,怎么能延年?假如圣人肯做这种盗贼的事,周公、孔子决不是不能做,该是已经做了好久了。
13.11 谢显道历举佛说与吾儒同处问伊川先生,先生曰:恁地同处虽多,只是本领不是,一齐差却。①
——《二程外书》卷十二
[注释]
①谢显道:谢良佐字显道,程门四大弟子之一,见(2.77)注。本领:本源,根本,主旨,要领。《朱子语类》卷二十七:“本领若是,事事发出来皆是;本领若不是,事事皆不是也。”
[译文]
谢良佐历举佛教之说与儒家相同之处问程颐,程颐说:如此相同的地方虽然多,只是根本与要领不对,一齐全都差了。
13.12 横渠先生曰:释氏妄意天性,而不知范围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缘天地,明不能尽,则诬天地日月为幻妄,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溺其志于虚空之大,此所以语大语小,流遁失中。①其过于大也,尘芥六合;其蔽于小也,梦幻人世。②谓之穷理可乎?不知穷理而谓之尽性可乎?谓之无不知可乎?尘芥六合,谓天地为有穷也;梦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从也。
——张载《正蒙·大心》
[注释]
①佛教认为,心的真如是绝对不变的实体,是真实,而尘世的一切都非真实,而是人心的幻象,因而都是虚妄的。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产生色、声、香、味、触、法六识,由此形成天地世界,即天地是由人心的因缘发生的。《周易·系辞上》:“范围天地之化。”范围之意,是如果将天地造化比作熔炉中的铁汁,则易理就是铸造的模型,造物千变万化,不出其范围。今人或译作包括,或解为裁成。以上一段,是讲天地生成本体论上理学与佛教的矛盾:理学认为天地由先于天地之理生成,佛教认为天地是人心的幻象。流遁:放逸而失于正道。为一身之小所蔽,而不能认识天地功用的广大无边,这是说佛教只从人身六根去认识天地。人的志趣本应以笃实为贵,佛教却沉迷于对虚空之大的追求。所以佛教所说的小和大,都不切于中正。②佛教认为,一微尘芥子中有无限大千世界。六合即天地四方。佛教又认为人世不是真实的,就如梦幻泡影。
[译文]
张载说:佛家不懂天性而臆断胡说,不懂得天理裁成天地万物的功用,反而以小小的人的感官为生成天地的因缘,他们的聪明不能透彻了解天地日月的来处,就谎说天地日月是幻妄,由一身之小蔽塞着而不知天地功用之大,志趣又沉溺于对虚空之大的追求,因此他们谈论大谈论小,全都流于荒诞而不得其中。其关于大的说法的错误,认为一微尘芥子中有天地四方;其为小所蒙蔽处,认为人世全是心的梦幻。说他们穷究事理行吗?不能穷尽事理却说他们能充分扩充其本善之性行吗?说他们无所不知行吗?说尘芥之中有六合,是认为天地是有穷尽的;以人世为梦幻,说明他们不能推究人世的来处。
13.13 大《易》不言有无。言有无,诸子之陋也。①
——张载《正蒙·大易》
[注释]
①茅星来解:“《系辞传》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夫形而上、下者皆谓之形,则其不得以道与器分有形无形明矣。而孔氏正义乃以道为无,以器为有,且曰:‘易理备包有无,而易象唯在于有。’盖自王弼祖述老庄而以有无论易,而孔氏专主王注,故其说云然。张子之言,盖为此而发。”孔氏,指唐经学家孔颖达,有《五经正义》。王弼,三国魏玄学家,有《周易注》。张载所以批有无之论,是因言有无就入于老、庄。老子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以道为无,以器为有,正同此说。按此语又见《横渠易说·系辞上》。《周易·系辞上》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张载之解,针对“幽明之故”。此条上文有:“气聚则离明得施而有形,气不聚则离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谓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谓之无?故圣人仰观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张载此语乃针对老庄将“无”“皆归之空虚”而发。
[译文]
大《易》不谈论有无。谈论有无,是诸子的浅陋。
13.14浮图明鬼,谓有识之死,受生循环,遂厌苦求免,可谓知鬼乎?以人生为妄见,可谓知人乎?天人一物,辄生取舍,可谓知天乎?①孔孟所谓天,彼所谓道。②惑者指“游魂为变”为轮回,未之思也。③大学当先知天德,④知天德,则知圣人、知鬼神。今浮图剧论要归,必谓死生流转,非得道不免,谓之悟道可乎?(本注:悟则有义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昼夜,通阴阳,体之无二。)⑤自其说炽传中国,儒者未容窥圣学门墙,已为引取,沦胥其间,指为大道。⑥乃其俗达之天下,致善恶、知愚、男女、臧获,人人著信。使英才间气,生则溺耳目恬习之事,长则师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驱,因谓圣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学而知。⑦故未识圣人心,已谓不必求其迹;未见君子志,已谓不必事其文。此人伦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乱。⑧异言满耳,上无礼以防其伪,下无学以稽其弊。⑨自古诐、淫、邪、遁之辞,翕然并兴,一出于佛氏之门者,千五百年。⑩向非独立不惧,精一自信,有大过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间,与之较是非、计得失哉?——张载《正蒙·乾称》
[注释]
①浮图:又作浮屠,即佛陀。佛,此指佛教。见(9.17)注。明鬼:《墨子》有《明鬼》篇,说明鬼的存在。这里说,佛教相信鬼的存在。受生循环:指佛家所谓的六道轮回,即认为人死后为鬼,鬼在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中循环转变,最为痛苦可怕,只有得道成佛到极乐世界,才能免除这种痛苦。张载认为人由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气散则归于太虚,以其归也,故名为鬼。厌苦:厌烦以为苦事,此指厌烦轮回之苦。妄见:佛教语,佛教认为一切皆非实有,肯定存在都是妄见,和“真如”相对。《楞严经》卷四:“如是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儒家认为天人本为一体,人死自然归天,而佛家却认为只有成佛才能升天,是妄生取舍。②儒家认为,天指太虚,气化流行谓道。道存在于天。而佛教直以天为道。③《周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韩康伯注:“精气缊,聚而成物,聚极则散,而游魂为变也。游魂,言其游散也。”游魂,指的是游散之气。信佛者则认为游魂是人死后的鬼魂,而“变”就是六道轮回。④大学:大的学问。茅星来解:“指儒者之学。”天德:茅星来解:“即天道之本然者,如下文所谓死生、天人、昼夜、阳阴之类皆是。”注见(2.34)。⑤剧论:激切论辩,极力要论证的。要归:要旨与归趣,立论之关键。叶采解:“当生而生,当死而死,是则有义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厌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昼夜,通阴阳,则知生死之说,何所谓轮回?”按《孟子·告子上》:“舍生而取义。”人的死生都服从于义,义当死则不求生。《论语·颜渊》:“死生有命。”此即有义有命。⑥门墙:师门。《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沦胥:沦陷、沦丧,陷溺。沦胥其间,指为大道:沉溺其中,认为其教为高明的学说。按佛教自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经梁武帝,到唐宪宗时大盛。⑦英才间气:如说英雄豪杰。耳目恬习:看得习惯,听得习惯,不以为怪,而可以安。世儒:俗儒。《史记·律书》:“岂与世儒暗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遂执不移等哉!”⑧《孟子·离娄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赵岐注:“舜明庶物之情,察人事之序。”庶物,即普通的事物。忽:政治之混乱。《尚书·益稷》:“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蔡沈集传:“在,察也。忽,治之反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忽,乱也。⑨茅星来解:“上无礼则法度不立,故无以防其伪;下无学则不知是非,故无以稽其弊。”上指执政者,下指士。⑩《孟子·公孙丑上》:“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诐(bì)辞是偏颇不全面的话,淫辞是过分的话,邪辞是不合正道的话,遁辞是躲躲闪闪的话。翕然:兴盛、盛行的样子。
[译文]
佛教谈论鬼,说那些有见识的鬼,在要他投生轮回时,就厌倦轮回之苦,宁可不投生以求免于轮回之苦。能说佛徒们懂得什么是鬼吗?佛教认为人生是幻妄不实的,这能说他们了解人吗?天与人原本是一物,佛教却弃人事而追求升天成佛,这能说他们懂得什么是天吗?孔孟所说的天,他们却称为道。被佛教迷惑的人又把“游魂为变”当做六道轮回,这真是不加思考的乱说。学儒学的人应该先了解天道运行的本然,了解了天道运行的本然,也就懂得了圣人的学说,也就明白了什么是鬼神。现在佛家理论的关键,一定要讲到死生轮回,说除非得道成佛的人不能免于轮回之苦,说他们悟解了道可以吗?(本注:如果悟道,就会懂得死生有义有命决定,同等地看待生和死,把天人看做一体,明白了昼夜、阴阳之理,用昼夜、阴阳之理去体验死生、天人之理,其理原本无二。)自从佛家学说盛传于中国,读书人尚未来得及窥见儒家圣学的师门,已经被佛学引诱而去,沉陷其间,指佛教为高明的学说。佛教之俗风行天下,以至于不论善恶、智愚、男女、奴婢,人人信仰。即使有英雄豪杰,生下来耳濡目染看惯了佛家之事,长大后又学习了无学无识的俗儒崇尚佛教的言论,于是糊里糊涂地被驱赶到佛教那里去了,为佛教顿悟及识心成佛之说(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迷惑,于是就认为不用修养就可成为圣人,不用学习就可悟彻大道。所以还不了解圣人之存心,就说不必推求圣人的行事;还不理解君子的志趣,就说不必去阅读他们的文字。因此而不能体察人事之序,不能明了事物之情,政事因此被忽视,德行因此被搞乱。异端之说灌满耳朵,在上者没有一个法度以防其伪诈,在下的人没有学问不能考出其弊病。自古以来一切诐辞、淫辞、邪辞、遁辞,一下子全都兴盛起来,全都是出于佛教之门,已达一千五百年之久。如果不是能独立不惧,精诚专一坚定自信,有远远超过一般人才识的人,怎么能卓然正身立于其间,而与之较量、辨析是非得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