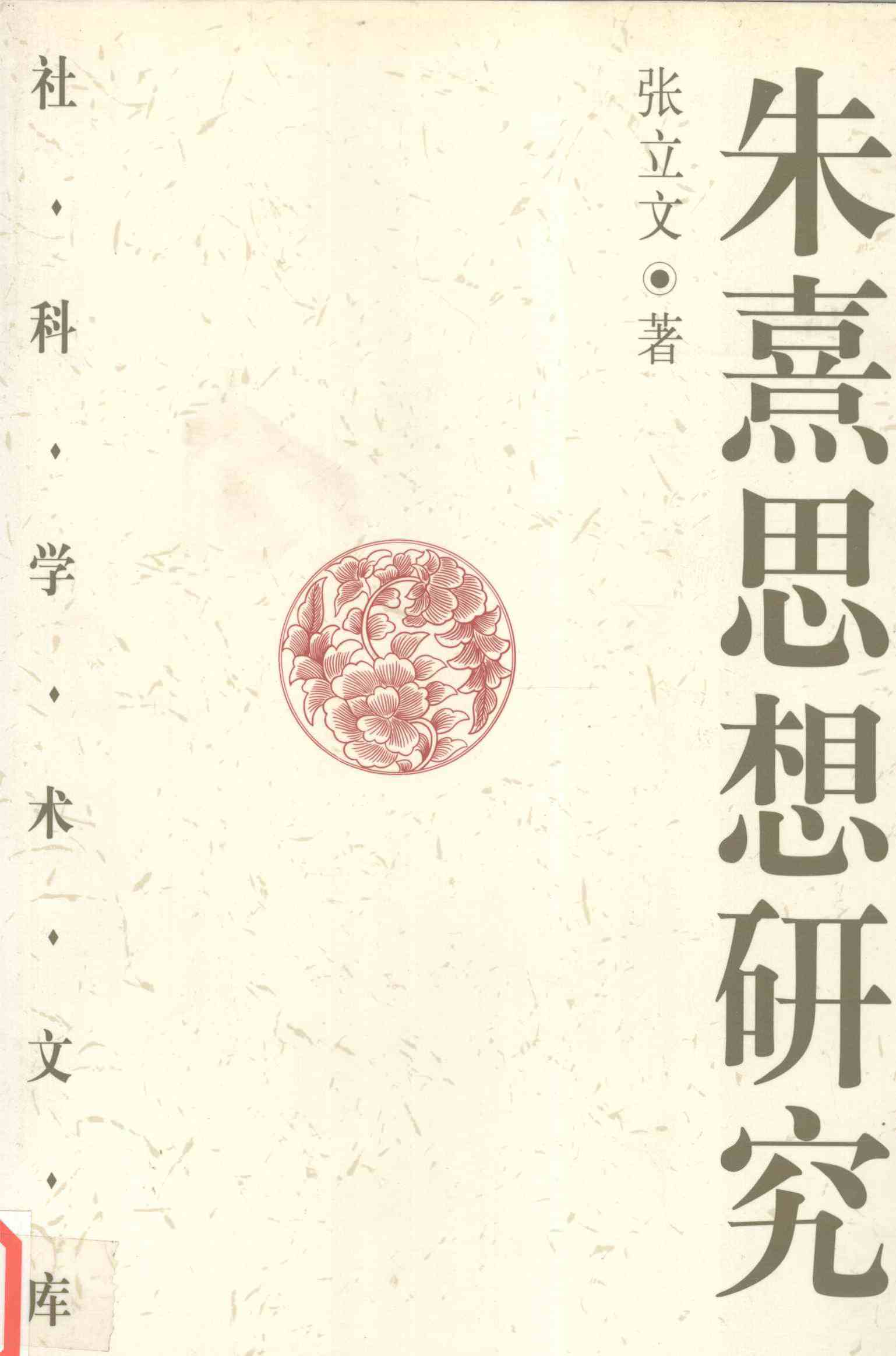内容
美善合一的贯彻与展开,便是文道合一①。善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内容,便与自然之道与社会之道(包括伦理道德规范)相符合,这就是道;美是作为善这种内容的形式,它与道的外在形式文,具有相似的意义。善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融合,便要求道的内容与文的形式相统一。
文道统一,是朱熹美学理论的要旨,亦是他与中唐以来古文家的根本分歧所在。《语类》记载:“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说:‘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②思辨地说明了道与文的关系也是中唐以来文与道论争的总结。
在朱熹看来,古文家各派其理论失足的要害,就在于把内在的道与外在的文分离,即文自文,道自道,分文与道为二。被苏轼称赞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主张文以明道或修辞以明道。此道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以此为文的内容;辞是指文辞,要讲究文辞,即文章的形式美。虽然韩愈没有明确讲“文以明道”,但古文运动的代表柳宗元,便明确指出“文者以明道”①的口号,柳宗元所谓道,包括儒家仁义道德,这是两人之同,其异就在于柳宗元的道,又指自然与社会的规范、准则,“物者,道之准也”。②后来,韩愈的学生、女婿李汉提出“文以贯道”,是对于韩、柳“文以明道”的说明。
“文以贯道”,是在文与道相分的前提下论述其关系的。假如文可以贯道,意思是说作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文,可以贯到作为内容的道中去,而不是外在形式的文是内在道的体现,那就颠倒文与道,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了。朱熹认为,道与文的关系,是一种本与末的关系,形而上的本体道是文这种现象的决定者,文这种现象只能是道的体现。无道便无所谓表现,即表现必须有所表现者的存在;所表现者支配表现。如以文贯道,就意味着依文而存在,道由文定了,便是本末颠倒。朱熹批评韩愈说:“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小。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董、贾;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狙圣伏之叹。至于其徒之论,亦但以剽掠僭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受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③这段文字直指出韩愈等古文家两个弊病:
其一,韩愈所说的道,由其没有探讨如何才能实行,不具有践行的效果,而仅是空言而已。这样,虽然韩愈倡导恢复儒家仁义道德,但这个道是空虚的。“世之业儒者既大为利禄所决溃于其前,而文辞组丽之习,见闻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渗泄之于其后,使其心不复自知道之在是,是以虽欲慕其名而勉为之,然其所安,终在彼而不在此也。”①这里业儒包括韩愈后继者在内,他们为功名利禄所引诱,为文辞华丽所蒙蔽,只追求外学,不知道诚意修身,勉力践行心性之内学。这样,虽在外观上以明道自高,但却徒有其名,而实为空虚。于是,所谓文以明道、贯道,亦无所本、所据。朱熹从揭露道为空虚,而否定文以明道、贯道,实犹火底抽薪,既然文丧失了道的充实内容,与时文亦无什么区别了,“所喻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论其极,则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②古文家起家的本钱是反对时文和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到朱熹手里,这两方面看家宝都被否定了。
其二,分裂道与文为两物,把本来是文轻道重,文缓道急,道本文末,道主文宾的关系,倒悬逆置过来。韩、柳的古文运动,出发点和着眼点是文。因此复兴儒学之道就要靠文,而去做贯道之文。这在朱熹看来,古文家是把文当作本,道当作末了。他批评韩愈“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虽然说“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实际上文仍是文,道仍是道,文道分二。
宋初曾袭五代文风,柳开有鉴于“属对精切”而“不达体要”以骈文陋习,首倡革新。他一面复古(复唐代之古),一面革新。复古与革新往往冲突融合在一起,两种面貌同时存在一件事上或一人之身。王禹偁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③,是在复韩、柳、李(白)、杜(甫)之古。柳开给古文有一界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①古文与时文的不同:在内容方面是“古其理”,即宣扬圣人之道,而非徒说无实;在形式方面,非求淫巧侈丽,浮华纂组,而可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华采并不能传“圣人之道”。主张“文道相兼”,“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②。内在最高的道德品质与外在华丽的形式美是兼而有之的。
宋代复古革新至欧阳修有综合之势。他认为,“充于中”的道德仁义之道与“发于外”的文华辞丽之文,应是道胜文至。文之所以辉煌光彩,是因为心中充满着纯粹的道。他曾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③的话,似有文附于道的意思。果如此,便与朱熹等观点相近,但欧阳修并未否定文的相对独立性,既然事业与文章两难相兼,隐含着对于柳开“文道相兼”的微辞,但亦并非文与道的联系。苏轼在《欧阳修墓志铭》中引用了欧阳修“吾之为文,必与道俱”的话。“文与道俱”,即既讲文与道相对待,又讲文不离道。
尽管宋代的古文运动与唐代韩、柳有异,但基本路线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朱熹是把欧阳修与韩愈捆在一起批评的。“欧阳子出,其文之妙,盖已不愧于韩氏。……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④虽然韩愈、柳宗元等提倡“文以明道”,欧阳修等主张“文与道俱”,意思不同,但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一是,以文贯道,颠倒本末;以文与道俱,两者并列,不分本末主宾。两者之失,都是文自文,道自道。朱熹说:“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放入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①“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是苏轼引欧阳修的话。朱熹并非不知道②,他之所以当作苏轼的话,是认为“文与道俱”与苏轼思想更切合。韩愈、欧阳修虽有倒置或不分轻重、本末之病,但仍不失为“扶持正学,不杂释老者也”③。苏轼便“杂以佛老,到急处便添入佛老,相和倾瞒人”④,离道更远。文本是文,只是在作文时,讨个道放入里面,道与文是分离的。不是先理会了道理去作文,而是在作文中不自觉地说些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欧阳修在文与道关系上只是有病,而不像苏轼“大本都差”了,有害正道。
二是,无论是韩、柳,还是欧、苏,朱熹都把他们视为古文家,而不看作道学家。然而在道学家内部,文与道的关系,意见亦异。被朱熹《伊洛渊源录》列为卷首的周敦颐,他在《通书》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⑤文指文字,文字必须修饰,犹如车有轮辕等装饰之美。以文与车相喻,文便含有美饰车马,雕琢刻镂之类与生活美有关的感性文饰和文采,亦蕴涵着美的创造的成就或物质精神之美的成就等内涵。朱熹解释说:“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其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之而人不用,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哉!”①道为文词之实,文词为道之华。文与车、道与物均不可无。无车,物不能载,无文,道不能载;车为载物之车,文为载道之文。车美其饰而不用,犹为虚饰虚车;文美其饰而人必爱之,就会传之久远。如果有道德而无文章之美,人们不爱好它,即引不起人们精神或感性的愉快,人就不传;更不能久远。依朱熹对“文以载道”的理解,实是道与文合一之意。由于朱熹的这个解释,后来的道学家都以周敦颐的“文以载道”为正统。
如果说周敦颐并不否定载道之文需要美其饰,以引起人们喜爱而传之久远的话,那么,程颐便有否定文的意思。作文害道,因作文会迁移人们的志趣,迷恋文辞而不喜求道,犹如玩物丧志。这样,便把文与道对待起来。程颐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②把文章作为学之三弊之一,只有去三弊,才能趋于道。如何才能趋向道,便是学儒者之学。这是因为儒者之学,就是明道之学,学文不能明道。程颐“作文害道”,从思维模式来说,可以说是文自文、道自道模式的沿袭。
朱熹有分析地批评了唐代古文家韩、柳及宋初古文革新运动的柳开、欧阳修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和“文与道俱”等观点和失足之处,对道学家周敦颐和程颐的“文以载道”、“作文害道”,亦作了修正和阐发,由此,朱熹综罗各家得失利弊,而开创出“文道合一”论。他说:“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①彼是指欧阳修。朱熹认为,欧阳修讲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以后,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欧阳修只知道政事与礼乐的合一,却不讲道德与文章的合一,其实文与道尤其不能分二。虽道充实于内,是体,表现于外为文采,两者相互融合,不可分割。“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②文与道分二的结果,必然是道外有文,文外有道。这样,道不足为道,文不足为文。若道自道,文自文,实乃道不道,文不文。因此,朱熹提倡“即文讲道”、“文道一贯”。
朱熹强调文道融合、相即、一贯,这并不妨碍文与道自身的地位、作用的相异。“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③道与文犹如根本与枝叶,尽管有根本与枝叶之分,但本为一体。有根本而无枝叶,无从成树,根本亦会腐烂;有枝叶而无根本,丧失依据,枝叶亦会枯槁。两者相依而生,两得一贯,否则便两失无存。
朱熹文道合一的精彩处,便是“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皆从此心写出”。这里便涉及源与流、真与写这两对概念范畴的关系。在朱熹哲学逻辑结构中,道(理、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柢、根据,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根据和根柢的表现或化生;文从心写出,是指圣贤以道为心,圣贤之文就是这道心的写真。既然流是源的延伸,写是真的摄影,那么,文也就是发之于语言文字的道,或自然流露出来的道心。流不能离源、写不能离真,离源无流,离真无写,两者相依不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流与源都是水,写照与真实的人或事,都是一个模样,这就是说,“文便是道”。但是本性与本性的表现,毕竟是差分的,这就是说,两者是相分不杂的。文与道既相依不离,又相分不杂,不离不杂,思辨地解决了以往古文家与从周敦颐以来道学家的种种论调,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文从道中流出”的不离不杂,既是他的审美标准,亦是其美学价值观。他在评品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时,既注重道德思想内涵,即道和善,亦不忽视文艺形式的美饰和感性的愉快,即文和美。他在强调道德、思想标准(道)的前提下,实现道德、思想内容与文艺形式的融合,即在善本美末,道体文用的不杂下,要求善与美、道与文的合一。从道和善来说,不载道的文和不载物的车,虽有装饰之美,文辞之丽,朱熹认为,“此犹车不载物,而徒美其饰也”①。这是道和善的价值观。从文和美来说,“为文者,必善其词说”②,只有讲求文学、艺术的形式美,才能使“人之爱而用之”,若不美其饰,人不喜爱,即使道德、思想内容至高无上,也无用而落空。基于这样的体认,尽管他批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把道与文相颠倒、相分离,但对于他们的文亦多有所肯定和称赞:“韩文公诗文冠当时,后世未易及”。“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不似韩文规模阔”。“柳子厚文有所模仿者极精”。“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欧公文学敷腴湿润”。“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①“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②虽对他们的文字亦有所批评,但总的态度是“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③。文学和道理到了欧阳修、曾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和二程,才理顺通畅,这是文和美的价值观。因此,朱熹认为,道与文、善与美的融合,是最完善完美的价值观。
文道统一,是朱熹美学理论的要旨,亦是他与中唐以来古文家的根本分歧所在。《语类》记载:“才卿问:‘韩文《李汉序》头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来有病。’陈曰:‘文者,贯道之器。且如《六经》是文,其中所道皆是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其后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说:‘苏文害正道,甚于老佛,……’”②思辨地说明了道与文的关系也是中唐以来文与道论争的总结。
在朱熹看来,古文家各派其理论失足的要害,就在于把内在的道与外在的文分离,即文自文,道自道,分文与道为二。被苏轼称赞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主张文以明道或修辞以明道。此道是指儒家的仁义道德,以此为文的内容;辞是指文辞,要讲究文辞,即文章的形式美。虽然韩愈没有明确讲“文以明道”,但古文运动的代表柳宗元,便明确指出“文者以明道”①的口号,柳宗元所谓道,包括儒家仁义道德,这是两人之同,其异就在于柳宗元的道,又指自然与社会的规范、准则,“物者,道之准也”。②后来,韩愈的学生、女婿李汉提出“文以贯道”,是对于韩、柳“文以明道”的说明。
“文以贯道”,是在文与道相分的前提下论述其关系的。假如文可以贯道,意思是说作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文,可以贯到作为内容的道中去,而不是外在形式的文是内在道的体现,那就颠倒文与道,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了。朱熹认为,道与文的关系,是一种本与末的关系,形而上的本体道是文这种现象的决定者,文这种现象只能是道的体现。无道便无所谓表现,即表现必须有所表现者的存在;所表现者支配表现。如以文贯道,就意味着依文而存在,道由文定了,便是本末颠倒。朱熹批评韩愈说:“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小。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论古人,则又直以屈原、孟轲、马迁、相如、扬雄为一等,而犹不及于董、贾;其论当世之弊,则但以词不己出而遂有神狙圣伏之叹。至于其徒之论,亦但以剽掠僭窃为文之病,大振颓风,教人自为为韩之功,则其师生之间,传受之际,盖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③这段文字直指出韩愈等古文家两个弊病:
其一,韩愈所说的道,由其没有探讨如何才能实行,不具有践行的效果,而仅是空言而已。这样,虽然韩愈倡导恢复儒家仁义道德,但这个道是空虚的。“世之业儒者既大为利禄所决溃于其前,而文辞组丽之习,见闻掇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渗泄之于其后,使其心不复自知道之在是,是以虽欲慕其名而勉为之,然其所安,终在彼而不在此也。”①这里业儒包括韩愈后继者在内,他们为功名利禄所引诱,为文辞华丽所蒙蔽,只追求外学,不知道诚意修身,勉力践行心性之内学。这样,虽在外观上以明道自高,但却徒有其名,而实为空虚。于是,所谓文以明道、贯道,亦无所本、所据。朱熹从揭露道为空虚,而否定文以明道、贯道,实犹火底抽薪,既然文丧失了道的充实内容,与时文亦无什么区别了,“所喻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论其极,则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②古文家起家的本钱是反对时文和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到朱熹手里,这两方面看家宝都被否定了。
其二,分裂道与文为两物,把本来是文轻道重,文缓道急,道本文末,道主文宾的关系,倒悬逆置过来。韩、柳的古文运动,出发点和着眼点是文。因此复兴儒学之道就要靠文,而去做贯道之文。这在朱熹看来,古文家是把文当作本,道当作末了。他批评韩愈“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于经纶实务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虽然说“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实际上文仍是文,道仍是道,文道分二。
宋初曾袭五代文风,柳开有鉴于“属对精切”而“不达体要”以骈文陋习,首倡革新。他一面复古(复唐代之古),一面革新。复古与革新往往冲突融合在一起,两种面貌同时存在一件事上或一人之身。王禹偁说:“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③,是在复韩、柳、李(白)、杜(甫)之古。柳开给古文有一界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①古文与时文的不同:在内容方面是“古其理”,即宣扬圣人之道,而非徒说无实;在形式方面,非求淫巧侈丽,浮华纂组,而可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华采并不能传“圣人之道”。主张“文道相兼”,“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②。内在最高的道德品质与外在华丽的形式美是兼而有之的。
宋代复古革新至欧阳修有综合之势。他认为,“充于中”的道德仁义之道与“发于外”的文华辞丽之文,应是道胜文至。文之所以辉煌光彩,是因为心中充满着纯粹的道。他曾说过“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③的话,似有文附于道的意思。果如此,便与朱熹等观点相近,但欧阳修并未否定文的相对独立性,既然事业与文章两难相兼,隐含着对于柳开“文道相兼”的微辞,但亦并非文与道的联系。苏轼在《欧阳修墓志铭》中引用了欧阳修“吾之为文,必与道俱”的话。“文与道俱”,即既讲文与道相对待,又讲文不离道。
尽管宋代的古文运动与唐代韩、柳有异,但基本路线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朱熹是把欧阳修与韩愈捆在一起批评的。“欧阳子出,其文之妙,盖已不愧于韩氏。……然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④虽然韩愈、柳宗元等提倡“文以明道”,欧阳修等主张“文与道俱”,意思不同,但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一是,以文贯道,颠倒本末;以文与道俱,两者并列,不分本末主宾。两者之失,都是文自文,道自道。朱熹说:“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放入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①“吾所谓文,必与道俱”是苏轼引欧阳修的话。朱熹并非不知道②,他之所以当作苏轼的话,是认为“文与道俱”与苏轼思想更切合。韩愈、欧阳修虽有倒置或不分轻重、本末之病,但仍不失为“扶持正学,不杂释老者也”③。苏轼便“杂以佛老,到急处便添入佛老,相和倾瞒人”④,离道更远。文本是文,只是在作文时,讨个道放入里面,道与文是分离的。不是先理会了道理去作文,而是在作文中不自觉地说些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欧阳修在文与道关系上只是有病,而不像苏轼“大本都差”了,有害正道。
二是,无论是韩、柳,还是欧、苏,朱熹都把他们视为古文家,而不看作道学家。然而在道学家内部,文与道的关系,意见亦异。被朱熹《伊洛渊源录》列为卷首的周敦颐,他在《通书》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文辞,艺也;道德,实也。笃其实而艺者书之,美则爱,爱则传焉。贤者得以学而至之,是为教。”⑤文指文字,文字必须修饰,犹如车有轮辕等装饰之美。以文与车相喻,文便含有美饰车马,雕琢刻镂之类与生活美有关的感性文饰和文采,亦蕴涵着美的创造的成就或物质精神之美的成就等内涵。朱熹解释说:“文所以载道,犹车所以载物。故为车者,必饰其轮辕;为文者,必善其词说,皆欲人之爱而用之,然我饰之而人不用,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况不载物之车,不载道之文,虽美其饰,亦何为哉!”①道为文词之实,文词为道之华。文与车、道与物均不可无。无车,物不能载,无文,道不能载;车为载物之车,文为载道之文。车美其饰而不用,犹为虚饰虚车;文美其饰而人必爱之,就会传之久远。如果有道德而无文章之美,人们不爱好它,即引不起人们精神或感性的愉快,人就不传;更不能久远。依朱熹对“文以载道”的理解,实是道与文合一之意。由于朱熹的这个解释,后来的道学家都以周敦颐的“文以载道”为正统。
如果说周敦颐并不否定载道之文需要美其饰,以引起人们喜爱而传之久远的话,那么,程颐便有否定文的意思。作文害道,因作文会迁移人们的志趣,迷恋文辞而不喜求道,犹如玩物丧志。这样,便把文与道对待起来。程颐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②把文章作为学之三弊之一,只有去三弊,才能趋于道。如何才能趋向道,便是学儒者之学。这是因为儒者之学,就是明道之学,学文不能明道。程颐“作文害道”,从思维模式来说,可以说是文自文、道自道模式的沿袭。
朱熹有分析地批评了唐代古文家韩、柳及宋初古文革新运动的柳开、欧阳修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和“文与道俱”等观点和失足之处,对道学家周敦颐和程颐的“文以载道”、“作文害道”,亦作了修正和阐发,由此,朱熹综罗各家得失利弊,而开创出“文道合一”论。他说:“然彼知政事礼乐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夫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然初岂有意学为如是之文哉!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①彼是指欧阳修。朱熹认为,欧阳修讲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以后,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欧阳修只知道政事与礼乐的合一,却不讲道德与文章的合一,其实文与道尤其不能分二。虽道充实于内,是体,表现于外为文采,两者相互融合,不可分割。“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②文与道分二的结果,必然是道外有文,文外有道。这样,道不足为道,文不足为文。若道自道,文自文,实乃道不道,文不文。因此,朱熹提倡“即文讲道”、“文道一贯”。
朱熹强调文道融合、相即、一贯,这并不妨碍文与道自身的地位、作用的相异。“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③道与文犹如根本与枝叶,尽管有根本与枝叶之分,但本为一体。有根本而无枝叶,无从成树,根本亦会腐烂;有枝叶而无根本,丧失依据,枝叶亦会枯槁。两者相依而生,两得一贯,否则便两失无存。
朱熹文道合一的精彩处,便是“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文皆从此心写出”。这里便涉及源与流、真与写这两对概念范畴的关系。在朱熹哲学逻辑结构中,道(理、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柢、根据,万事万物都是这个根据和根柢的表现或化生;文从心写出,是指圣贤以道为心,圣贤之文就是这道心的写真。既然流是源的延伸,写是真的摄影,那么,文也就是发之于语言文字的道,或自然流露出来的道心。流不能离源、写不能离真,离源无流,离真无写,两者相依不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流与源都是水,写照与真实的人或事,都是一个模样,这就是说,“文便是道”。但是本性与本性的表现,毕竟是差分的,这就是说,两者是相分不杂的。文与道既相依不离,又相分不杂,不离不杂,思辨地解决了以往古文家与从周敦颐以来道学家的种种论调,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文从道中流出”的不离不杂,既是他的审美标准,亦是其美学价值观。他在评品艺术创作和文学创作时,既注重道德思想内涵,即道和善,亦不忽视文艺形式的美饰和感性的愉快,即文和美。他在强调道德、思想标准(道)的前提下,实现道德、思想内容与文艺形式的融合,即在善本美末,道体文用的不杂下,要求善与美、道与文的合一。从道和善来说,不载道的文和不载物的车,虽有装饰之美,文辞之丽,朱熹认为,“此犹车不载物,而徒美其饰也”①。这是道和善的价值观。从文和美来说,“为文者,必善其词说”②,只有讲求文学、艺术的形式美,才能使“人之爱而用之”,若不美其饰,人不喜爱,即使道德、思想内容至高无上,也无用而落空。基于这样的体认,尽管他批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把道与文相颠倒、相分离,但对于他们的文亦多有所肯定和称赞:“韩文公诗文冠当时,后世未易及”。“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柳文是较古,但却易学,……不似韩文规模阔”。“柳子厚文有所模仿者极精”。“韩文高,欧阳文可学”。“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议论亦好”。“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欧公文学敷腴湿润”。“东坡文字明快。老苏文雄浑,尽有好处。”①“苏氏文辞伟丽,近世无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范。”②虽对他们的文字亦有所批评,但总的态度是“文字到欧、曾、苏,道理到二程,方是畅”③。文学和道理到了欧阳修、曾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和二程,才理顺通畅,这是文和美的价值观。因此,朱熹认为,道与文、善与美的融合,是最完善完美的价值观。
附注
①“文”这个范畴,有其演变和发展。先秦时,文、史、哲、社不分,以日、月、星、辰为文(天文),礼乐刑政亦是文(人文),文是一个很普遍的范畴。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文(章)与学(术)分开,文章专指文学作品,又有“文笔之辩”。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五经六艺;狭义文是指诗、赋、铭、颂等。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文,指文体机制而言,宋代沿袭了这个意思。
②《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①《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卷三十四。
②《守道论》,《柳宗元集》卷三。
③《读唐志》,《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①《答杨子顺》,《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九。
②《答徐载叔》,《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
③《小畜集》卷十,四部丛刊本。
①《应责》,《河东集》卷一。
②同上。
③《答吴充秀才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七。
④《读唐志》,《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①《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②朱熹在《读唐志》中曾引过欧阳修“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这句话。(见《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③《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④同上。
⑤《文辞注》第二十八,《周子全书》卷十
①《文辞注》第二十八,《周子全书》卷十。
②《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①《读唐志》,《朱文公文集》卷七十。
②《与汪尚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
③《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①《文辞注》第二十八,《周子全书》卷十。
②同上。
①以上均见《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②《答程允夫》,《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一。
③《朱子语类》卷一三九。
相关地名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