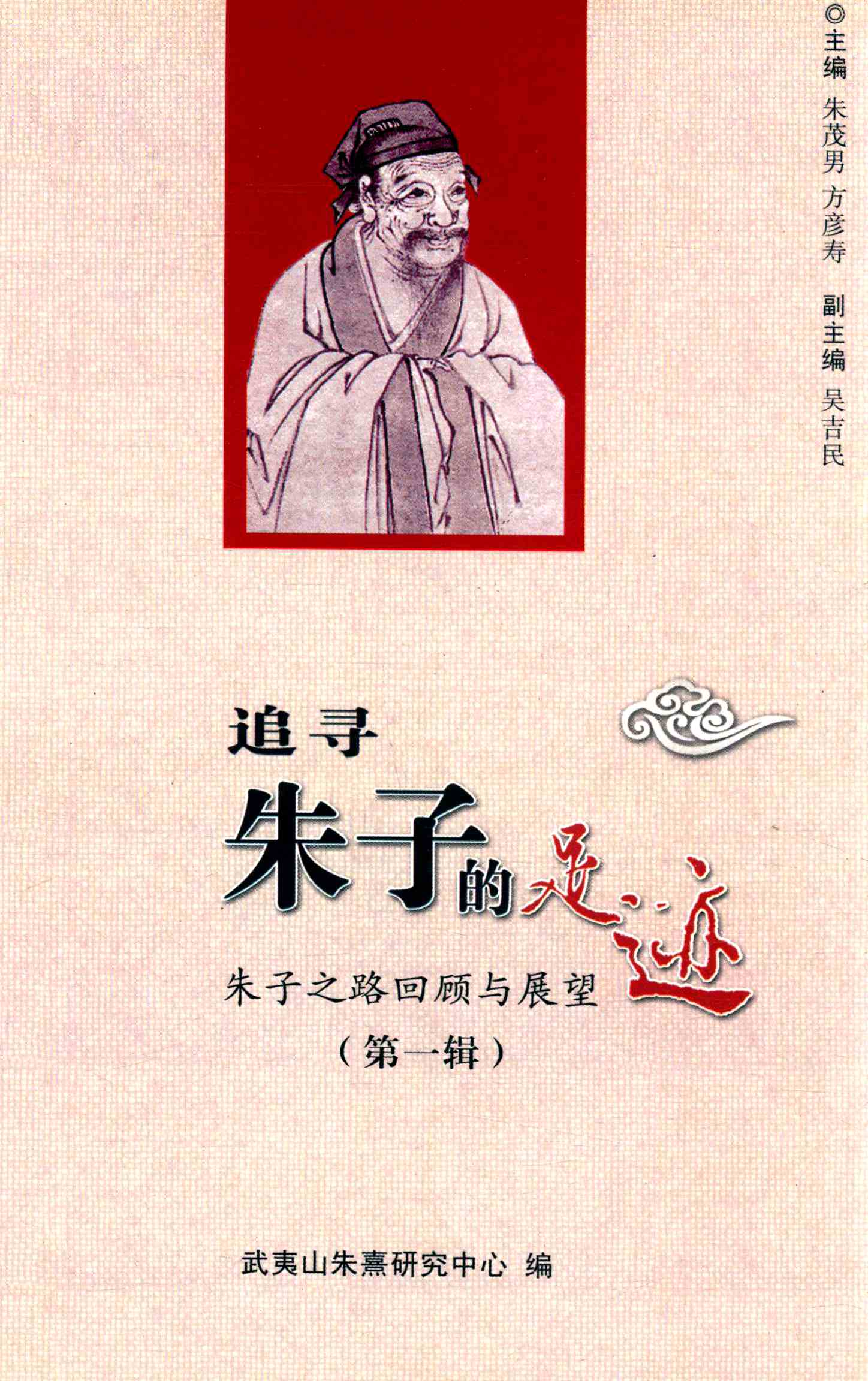朱子之路的一点省思
内容
这趟由台湾朱氏宗亲文教基金会赞助,由朱茂男会长与清华大学杨儒宾教授共同发起的“武夷山五夫里朱子之路知性之旅”,成员主要由教授与研究生组成,希望能透过实地走访朱熹故里,而有助于学子对朱子一生有更切身的体会。朱子之路的行程以金门为起点,再到闽北朱熹生平活动之地,范围涵盖了朱熹童年所在的尤溪、大半生定居的五夫里、曾任职的武夷、生命最后几年所在的考亭、以及身后安居的黄坑陵墓等。五天的行程造访了相当多的古迹景点,包括金门浯江书院朱子祠、武夷精舍、祝夫人墓、朱子陵墓、考亭书院、紫阳楼、朱子巷、兴贤书院、五夫仓社、建瓯孔庙、博士府、艮泉井、沈郎樟公园、南溪书院、开山书院等,行程相当充实紧凑。
笔者有幸能参加这趟行程。走完朱子之路,增加了不少对朱熹的认识,收获颇丰。然而结束旅程后,与此行收获同样鲜明的,却是心中不断升起的疑问:到底什么才是贴近朱熹最好的方式?到底什么样条件的建筑可称得上“古迹”?而这些“古迹”究竟与朱熹本身有多少关连?我们透过“古迹”究竟想寻求什么?它们的存在是否真能象征一条穿越时间的钮带?在这些日子的沉淀中,这些疑惑成了心中的主旋律。因此,本文将不会是一篇记录这些天的游记,也不会是一篇朱子之路的旅游报导。本文将会是一篇与这些疑问对话的反省书写。
一个地方,是否一定要有“古迹”才能引发思古幽情?另一方面,“古迹”或“历史建筑物”的存在,是否就能担负起保存文化的功能?这些疑问既因这些天走访的行程而来,底下将选择金门、紫阳楼、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祝夫人墓等几个关键行程作为反省的焦点。
金门,是我们此行的首站,也是最让我们惊艳的地方。金门流传着不少朱熹到过金门的传说。朱熹曾任同安主簿,很可能到过当时作为辖区之一的翔风里(即今之金门),可惜朱熹著作中并无相关记载,因此这些传说也无从证明真伪。然而在这一天半的短暂停留中,却深深感受到金门人对朱子的景仰,以及鼎盛的文风。从宋代开始,金门代代有进士,历史上数百位之多的进士,足以说明金门书香传家的悠远传统。而即使现代,从错落有致的传统闽式建筑,到淳朴敦厚的民风与浓厚的人文气息,整个金门仍旧散发一股典雅的儒家风范。首晚于浯江书院朱子祠举行“朱子、金门与传统文化”座谈会,听当地的老师与文史工作者讨论朱子与金门的关系,从他们热切而诚恳的言谈中,更深深感受到金门人对朱子的孺慕之情。而这种发自内心的景仰,丝毫不受缺乏历史佐证影响。朱子是否到过金门,这问题有待历史学家考证。但事隔八百年,即使朱子曾到过金门,其遗迹亦杳眇难寻,然而文化传承却可百代如新。朱子不仅活在当地人心中,金门也体现了一种可作为现代儒家社会典范的文雅风貌。这里虽然没有朱子留下的遗迹,但我们在这里体会到的朱子却更深刻而鲜明。
朱子一生70岁的生命,有40多年即在武夷山五夫里紫阳楼度过。现今所见的紫阳楼已是1999年重新修建,依照朱子《名堂室记》所载以恢复当年格局。访客来到紫阳楼,可透过正厅两旁的韦斋、礼斋、后进的祝夫人敬斋、朱熹的义斋、以及子女住的梅、兰、桂、芙、蓉、菱等斋,试着想象朱子当年的居家生活。然而屋内时而出现不甚协调的现代摆设,却容易打断这类的联想。因此,当试着透过这空间遥想当年朱子生活时,不禁感到有点落寞。唯一与朱熹精神相关的摆设,该属墙上挂的朱熹书法——“静我神”、“不远复”、“涵养天机”,以及正厅双柱上题着的“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这些蕴涵朱熹哲学与精神境界的书法,是唯一令人感到贴近朱子之处。然而走出紫阳楼,蓝天艳阳下,还有朱熹手植的古樟伫立在天地间。繁茂的枝叶至今仍庇荫着树下乘凉的老妪。古樟傍着一弯清澈的小溪,溪外更有稻田与青山。忆起当初朱熹义父刘子翚为朱熹母子筑室紫阳楼,正是精心选在山(屏山)环水(潭溪)绕之地。原始的紫阳楼早已湮没尘土间,而美丽的山水仍在。望着这片青山绿水,终于找到可与朱熹对话的时空桥梁。
朱熹一生曾建立三座精舍: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后宋理宗赐名为考亭书院)。寒泉精舍今已不在。武夷精舍近年则重新修建,颇具规模。朱熹当初选在大隐屏峰下,九曲溪畔建立武夷精舍,原也是相当清幽之所。原来的武夷精舍只剩左右两道断壁残垣,而今只能隔着玻璃缅怀。这座重建的新古迹,以建筑型制与规模来说,颇见筹建者的用心。然而,遗址重建所要延续的,也许不只是让这块地方不被后世遗忘,更重要的,是能否在里面重新注入原来的精神。访客来来去去,其带走的印象可能只是来过这么一个地方,至于武夷精舍为何重要?有何特别?为何近代还要重建?则可能无法体会。南宋张栻曾谓:“当今道在武夷。”指的就是朱熹当时在武夷精舍进行的学术活动之重要性。因此,如何让重建的武夷精舍更能体现朱熹思想并发扬人文精神,而不只是一栋“新古迹”,也许是个值得思索的课题。
考亭书院,古迹部份只剩明嘉靖年间所设之牌坊,经过历史积淀的牌坊相当具有古味,它的存在仿佛见证了沧桑的历史。书院本身则已荡然无存,书院原址成了一片葡萄园,于是当局选择在附近新盖了一座朱子祠。这当然也是一种纪念朱子的方式,只是朱子祠太过普遍,而里面的陈设也相当制式、一般化,显不出考亭书院独特的意义。陈荣捷教授曾指出:“在这三所精舍中,以竹林精舍最为重要,这因为朱子的许多有名弟子都在此处从游于朱门,而且许多语录都是在竹林记载出来。”(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8),页483) 如今实地走访考亭书院“遗址”,不能说没有一丝遗憾之情。因为并不是有了一座“新古迹”,书院的意义便能被保存了下来。如何在一个地方重塑朱子精神,保留朱子文化,所需要的远比建造一座朱子祠之类的建筑物要来的更多。
最后,在闽北这些天的行程中,笔者最欣赏的是祝夫人墓。后人在重新整理上,并无太多的外在修饰,而是尽量恢复其原貌,这使得祝夫人墓具有一种古朴的气象。而望着前方一潭寒泉(天湖),以及泉边的翁郁翠竹,整体透显出一股绝伦的清幽。而寒泉精舍正因朱熹当年在此守丧而创立。寒泉精舍虽已不在,然因着既有之景,遥想当时情境,更多了份时空交错之美。尤其这潭寒泉,听当地人说,它终年水量不变,干旱如此,大水来也只是如此。不由得由衷佩服朱熹择地的眼光。从南宋至今,世间几多变化,而寒泉依旧与祝夫人墓遥相对望,宁静而悠远。朱子陵墓前方的一池活泉也是至今仍在。
古迹的意义,不在于华丽雕琢,也不在于建筑宏伟,而在于它的存在是否传达出其象征的历史蕴意。古迹的重新修建,若少了人文精神的充实,也只能沦为观光客歇脚之地,而无法兴起缅怀朱子之思古幽情。然另一方面,这些天所行经的自然风光,却让笔者意外地切身体会到朱子一生与山水对话的深情,以及他选择每一块墓地、建筑每一座精舍背后的眼光。虽然三座精舍命运各不相同,或已随历史灰飞湮灭,或经后人重新修建而保存,但不变的是周围美丽的自然景致。在这片青山绿水间,似乎仍可瞥见朱熹带着门人吟咏而过。朱熹的精神,或许正遥寄于闽北的山水之间。
我们该如何穿越八百年的时光以贴近朱熹的一生?拜访与朱熹相关的古迹,是最普遍的方法。然而此行,笔者却有不同的感受。朱熹的精神并不存在于古迹本身,它毋宁体现于一个景仰朱熹而温柔敦厚的社会,如金门。同样地,原址重建的“新古迹”,若少了人文精神的灌注,也只是水泥建筑。反而是闽北的大好山水,却是缅怀朱熹不可或缺的一环,毕竟正是这里的风土,培育了一代大哲。朱熹更曾写过多首歌咏武夷山水的清丽诗篇。笔者有幸,能在自然环境未受破坏之前,亲身体会朱熹对这片山水的热爱。维护朱子故里,应不仅限于历史建筑物,若能在将来开发的洪流中,维持住闽北的好山好水,后人才有机会继续体会到朱子与这块土地的深厚关联——而这也是贴近朱子最自然的一种方式。(林淑娟: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笔者有幸能参加这趟行程。走完朱子之路,增加了不少对朱熹的认识,收获颇丰。然而结束旅程后,与此行收获同样鲜明的,却是心中不断升起的疑问:到底什么才是贴近朱熹最好的方式?到底什么样条件的建筑可称得上“古迹”?而这些“古迹”究竟与朱熹本身有多少关连?我们透过“古迹”究竟想寻求什么?它们的存在是否真能象征一条穿越时间的钮带?在这些日子的沉淀中,这些疑惑成了心中的主旋律。因此,本文将不会是一篇记录这些天的游记,也不会是一篇朱子之路的旅游报导。本文将会是一篇与这些疑问对话的反省书写。
一个地方,是否一定要有“古迹”才能引发思古幽情?另一方面,“古迹”或“历史建筑物”的存在,是否就能担负起保存文化的功能?这些疑问既因这些天走访的行程而来,底下将选择金门、紫阳楼、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祝夫人墓等几个关键行程作为反省的焦点。
金门,是我们此行的首站,也是最让我们惊艳的地方。金门流传着不少朱熹到过金门的传说。朱熹曾任同安主簿,很可能到过当时作为辖区之一的翔风里(即今之金门),可惜朱熹著作中并无相关记载,因此这些传说也无从证明真伪。然而在这一天半的短暂停留中,却深深感受到金门人对朱子的景仰,以及鼎盛的文风。从宋代开始,金门代代有进士,历史上数百位之多的进士,足以说明金门书香传家的悠远传统。而即使现代,从错落有致的传统闽式建筑,到淳朴敦厚的民风与浓厚的人文气息,整个金门仍旧散发一股典雅的儒家风范。首晚于浯江书院朱子祠举行“朱子、金门与传统文化”座谈会,听当地的老师与文史工作者讨论朱子与金门的关系,从他们热切而诚恳的言谈中,更深深感受到金门人对朱子的孺慕之情。而这种发自内心的景仰,丝毫不受缺乏历史佐证影响。朱子是否到过金门,这问题有待历史学家考证。但事隔八百年,即使朱子曾到过金门,其遗迹亦杳眇难寻,然而文化传承却可百代如新。朱子不仅活在当地人心中,金门也体现了一种可作为现代儒家社会典范的文雅风貌。这里虽然没有朱子留下的遗迹,但我们在这里体会到的朱子却更深刻而鲜明。
朱子一生70岁的生命,有40多年即在武夷山五夫里紫阳楼度过。现今所见的紫阳楼已是1999年重新修建,依照朱子《名堂室记》所载以恢复当年格局。访客来到紫阳楼,可透过正厅两旁的韦斋、礼斋、后进的祝夫人敬斋、朱熹的义斋、以及子女住的梅、兰、桂、芙、蓉、菱等斋,试着想象朱子当年的居家生活。然而屋内时而出现不甚协调的现代摆设,却容易打断这类的联想。因此,当试着透过这空间遥想当年朱子生活时,不禁感到有点落寞。唯一与朱熹精神相关的摆设,该属墙上挂的朱熹书法——“静我神”、“不远复”、“涵养天机”,以及正厅双柱上题着的“鸢飞月窟地”、“鱼跃海中天”,这些蕴涵朱熹哲学与精神境界的书法,是唯一令人感到贴近朱子之处。然而走出紫阳楼,蓝天艳阳下,还有朱熹手植的古樟伫立在天地间。繁茂的枝叶至今仍庇荫着树下乘凉的老妪。古樟傍着一弯清澈的小溪,溪外更有稻田与青山。忆起当初朱熹义父刘子翚为朱熹母子筑室紫阳楼,正是精心选在山(屏山)环水(潭溪)绕之地。原始的紫阳楼早已湮没尘土间,而美丽的山水仍在。望着这片青山绿水,终于找到可与朱熹对话的时空桥梁。
朱熹一生曾建立三座精舍: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后宋理宗赐名为考亭书院)。寒泉精舍今已不在。武夷精舍近年则重新修建,颇具规模。朱熹当初选在大隐屏峰下,九曲溪畔建立武夷精舍,原也是相当清幽之所。原来的武夷精舍只剩左右两道断壁残垣,而今只能隔着玻璃缅怀。这座重建的新古迹,以建筑型制与规模来说,颇见筹建者的用心。然而,遗址重建所要延续的,也许不只是让这块地方不被后世遗忘,更重要的,是能否在里面重新注入原来的精神。访客来来去去,其带走的印象可能只是来过这么一个地方,至于武夷精舍为何重要?有何特别?为何近代还要重建?则可能无法体会。南宋张栻曾谓:“当今道在武夷。”指的就是朱熹当时在武夷精舍进行的学术活动之重要性。因此,如何让重建的武夷精舍更能体现朱熹思想并发扬人文精神,而不只是一栋“新古迹”,也许是个值得思索的课题。
考亭书院,古迹部份只剩明嘉靖年间所设之牌坊,经过历史积淀的牌坊相当具有古味,它的存在仿佛见证了沧桑的历史。书院本身则已荡然无存,书院原址成了一片葡萄园,于是当局选择在附近新盖了一座朱子祠。这当然也是一种纪念朱子的方式,只是朱子祠太过普遍,而里面的陈设也相当制式、一般化,显不出考亭书院独特的意义。陈荣捷教授曾指出:“在这三所精舍中,以竹林精舍最为重要,这因为朱子的许多有名弟子都在此处从游于朱门,而且许多语录都是在竹林记载出来。”(陈荣捷,《朱子新探索》(台北:学生书局,1988),页483) 如今实地走访考亭书院“遗址”,不能说没有一丝遗憾之情。因为并不是有了一座“新古迹”,书院的意义便能被保存了下来。如何在一个地方重塑朱子精神,保留朱子文化,所需要的远比建造一座朱子祠之类的建筑物要来的更多。
最后,在闽北这些天的行程中,笔者最欣赏的是祝夫人墓。后人在重新整理上,并无太多的外在修饰,而是尽量恢复其原貌,这使得祝夫人墓具有一种古朴的气象。而望着前方一潭寒泉(天湖),以及泉边的翁郁翠竹,整体透显出一股绝伦的清幽。而寒泉精舍正因朱熹当年在此守丧而创立。寒泉精舍虽已不在,然因着既有之景,遥想当时情境,更多了份时空交错之美。尤其这潭寒泉,听当地人说,它终年水量不变,干旱如此,大水来也只是如此。不由得由衷佩服朱熹择地的眼光。从南宋至今,世间几多变化,而寒泉依旧与祝夫人墓遥相对望,宁静而悠远。朱子陵墓前方的一池活泉也是至今仍在。
古迹的意义,不在于华丽雕琢,也不在于建筑宏伟,而在于它的存在是否传达出其象征的历史蕴意。古迹的重新修建,若少了人文精神的充实,也只能沦为观光客歇脚之地,而无法兴起缅怀朱子之思古幽情。然另一方面,这些天所行经的自然风光,却让笔者意外地切身体会到朱子一生与山水对话的深情,以及他选择每一块墓地、建筑每一座精舍背后的眼光。虽然三座精舍命运各不相同,或已随历史灰飞湮灭,或经后人重新修建而保存,但不变的是周围美丽的自然景致。在这片青山绿水间,似乎仍可瞥见朱熹带着门人吟咏而过。朱熹的精神,或许正遥寄于闽北的山水之间。
我们该如何穿越八百年的时光以贴近朱熹的一生?拜访与朱熹相关的古迹,是最普遍的方法。然而此行,笔者却有不同的感受。朱熹的精神并不存在于古迹本身,它毋宁体现于一个景仰朱熹而温柔敦厚的社会,如金门。同样地,原址重建的“新古迹”,若少了人文精神的灌注,也只是水泥建筑。反而是闽北的大好山水,却是缅怀朱熹不可或缺的一环,毕竟正是这里的风土,培育了一代大哲。朱熹更曾写过多首歌咏武夷山水的清丽诗篇。笔者有幸,能在自然环境未受破坏之前,亲身体会朱熹对这片山水的热爱。维护朱子故里,应不仅限于历史建筑物,若能在将来开发的洪流中,维持住闽北的好山好水,后人才有机会继续体会到朱子与这块土地的深厚关联——而这也是贴近朱子最自然的一种方式。(林淑娟: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相关人物
林淑娟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