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象数论
| 内容出处: |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1034 |
| 颗粒名称: | 2.象数论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5 |
| 页码: | 92-96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刘因对朱子学术观点象数论,表明他对宋代理学的了解和吸收已经达到比较高的程度。刘因文集中有好几篇谈到象数问题。 |
| 关键词: | 刘因 象数论 朱子文化 |
内容
刘因文集中有好几篇谈到象数问题。《椟蓍记》一文用邵雍之说论蓍数、象卦之理,自称“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说而得之”,并能运用此说分析有关观点:“知此,则知夫误推一行三爻八卦之象谓阴阳老少不在乎过揲者为昧乎体用之相,因而误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谓七八九六不在乎卦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④他还解释了朱子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然而朱子犹以大衍为不自然。于河图而变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画之不可以形上者。又以为短于龟其三索之说,则一行有成。说既取之《本义》后,复以为不必然。而卦之阴阳之奇偶,画与位合,则《大传》有明文,既著之筮说,而不明言于《启蒙》,是又恐后人求之过巧而每遗恨,不能致古人之详也。”①《太极图后记》一文则详辨周敦颐的太极图为其自作而非有所授受,基本观点大体承自朱子,但也有他自己的发挥,主要是认为周敦颐与邵雍之学原理相通:“周子、邵子之学,先天、太极之图,虽不敢必其所传之出于一,而其理则未尝不一;而其理之出于河图者,则又未尝不一也。夫河图之中宫,则先天图之所谓无极,所谓太极,所谓道与心者也。先天图之所谓无极,所谓太极,所谓道与心者,即太极图之所谓无极而太极,所谓太极本无极,所谓人之所以最灵者也。”②《河图辨》一文更历数河图之数与先天图之相对应者:“夫河图之中宫,则先天图之所谓无极。所谓太极,所谓道与心者,即太极图之所谓无极而太极,所谓太极本无极,所谓人之所以最灵者也。河图之东北阳之二生数统夫阴之二成数,则先天之左方阳动者也。其兑离之为阳中之阴,即阳动中之为阴静之根也。河图之西南阴之二生数统夫阳之为二成数,则先天图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也。先天图之右方巽四坎艮五坤六者,即太极图右方阴静者也。其坎艮之为阴中之阳者,则阴静中之为阳动之根者也。河图之奇偶,即先天太极图之所谓阴阳。而凡阳皆乾,凡阴皆坤也。河图、先天太极图之左方皆离之象也,右方皆坎之象也。是以河图水火居南北之极,先天图离列左右之门。太极图阳变阴合而即生水火也,而《易》之为书,所以首乾坤终坎离,终既济未济。而先天之为图,中孚、颐、小过、大过,各以其类而居于正也。如是,则周子、邵子其学虽异,先天太极其源虽殊,而其理未尝不一,而其所以出于河图者,则又未尝不一也。”③河图、先天图、太极图,本是三种不同来源的图,它们之间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刘因的看法是,三者可以整合为一。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以理观之。他的数学因此呈现出浓重的理学色彩。
《河图辨》还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河图的有关争议,刘因力主朱子之说,谓“河图之说,朱子尽之矣。后人虽欲议之,不可得而议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于己而后是,是以致疑于其间者尚纷纷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为之者,有指先天图而为之者,亦有主刘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误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画一图为之者”①。一一辨其不合,最后总结说:“夫前之所论,皆托言出于希夷而不合乎邵学者也。若朱子发、张文饶又求之邵学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则极邵子之大,尽周子之精,而贯之以程子之正也,后人恶得而议之?”②刘因对朱子学术观点的捍卫与继承,表明他对宋代理学的了解和吸收已经达到比较高的程度。天假以年,他在比较全面地继承宋代理学的基础上也许会做出一个更大的综合。
刘因与许衡并称元北方两大儒,被认为是“元之所藉以立国者”③。虽然享年不永,所及不远,时人对刘因还是有很高评价,欧阳玄为其作像赞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④赞词指出,刘因虽然连元世祖也不能招致,但其本意却并非要做遗世独立的高人,从刘因积极从事经史研究这个情况来看,他是有着周公、孔子那样崇高的文化理想的。刘因在世时弟子不多,在他死后,安熙以私淑弟子自居,安熙又传苏天爵,刘因之学得以接续。
安熙(1270—1311年),字敬仲,号默庵。幼承家学,后闻刘因之学而欲从之,未及造门而刘因已卒,遂从刘因门人乌冲(字叔备)“问其绪说”,录其遗书而还,潜心钻研,终身服膺,著作多佚,今存有《安默庵先生文集》。安熙治学,“一以(刘)因为宗”,像刘因一样,他在经学上也推崇朱子。他曾校订过刘因的《四书集义精要》,而有《四书精要考异》。当有人攻击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时,他起而捍卫:“朱夫子以为道之不明,由说经者不足以得圣贤之意。于是竭其精力,作为传注以著明之。至于一字未安、一词未备,必沉潜反复,以求至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于数千载之上。其间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可谓极深研几,发其旨趣而无所疑矣。”①他还仿《四书集义精要》体例撰集了《诗传精要》,自述写作缘起说:“近因看《诗传》(即朱子《诗集传》——编者注),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语录之言,凡涉论《诗》,有与《集传》相发明者,依《精要》例写出,以便初学,亦似有益。”②此外,他还打算仿朱子《通鉴纲目》写一部《春秋》学著作,节取《左传》和秦汉以来诸家《春秋》说,“以类相从,各附本句”,“其大旨一以朱子为本,而达于张、程,以求圣人之意”,以使治《春秋》者“有以考传”,治《左传》者“亦知有经”。③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后人称滋溪先生。少从安熙游,后入国子学,累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文集为《滋溪文稿》。因年轻时跟安熙学习过,苏天爵终生以师礼待之,在安熙死后,为其作《行状》《墓志铭》,并编辑《默庵文集》,“拳拳于其师之遗书”④。因安熙之故,对刘因也很敬仰,盛赞后者“以高明之资,躬圣贤之学,道德风采,耸动四方”⑤。苏天爵长于史学,曾三居史职,预修武宗、文宗《实录》,又自撰《元朝名臣事略》,辑《元文类》,被称为“身任一代文献之寄”。元末灾异屡现,他根据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向元廷发出警告:“盖闻应天以实,不以文;动人以行,不以言。此自昔国家消弭天变,感格人心之至计也。……迩者,日月薄食,星文示变。河北、山东旱蝗为灾,辽阳、江淮黎民乏食。方此春夏之始,农人播植之时,灾异若此,岁事何望?夫天之变异,盖不虚生,将恐人事有乖和气。当是之时,国家正宜访求直言,指切时政。”①苏天爵还有较强的疑经精神,如他在读朱子《诗集传》和吕祖谦《读诗记》时就产生了对《诗经》的一些疑问,他对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说法加以质疑:“由今观之,所正者独《豳》以下诗也,而《雅》《颂》何尝不得其所乎?若曰左氏后出,而作传者何独《豳》之下《雅》之上不得其次欤?”②他进而对孔子删《诗》的说法也表示怀疑:“当季札之聘鲁,请观周乐,于时夫子未删《诗》也,自《雅》《颂》之外,其十五国风尽歌之。
考之今三百篇及鲁人所存,无加损也。其谓夫子删《诗》者,果可信乎?”③
《河图辨》还用大量篇幅讨论了河图的有关争议,刘因力主朱子之说,谓“河图之说,朱子尽之矣。后人虽欲议之,不可得而议之也。然其自私者必出于己而后是,是以致疑于其间者尚纷纷然也。有指伏羲八卦次序为之者,有指先天图而为之者,亦有主刘牧而疑朱子取舍之误者。近世大儒又有自画一图为之者”①。一一辨其不合,最后总结说:“夫前之所论,皆托言出于希夷而不合乎邵学者也。若朱子发、张文饶又求之邵学而失之者也。若夫朱子,则极邵子之大,尽周子之精,而贯之以程子之正也,后人恶得而议之?”②刘因对朱子学术观点的捍卫与继承,表明他对宋代理学的了解和吸收已经达到比较高的程度。天假以年,他在比较全面地继承宋代理学的基础上也许会做出一个更大的综合。
刘因与许衡并称元北方两大儒,被认为是“元之所藉以立国者”③。虽然享年不永,所及不远,时人对刘因还是有很高评价,欧阳玄为其作像赞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乌乎!麒麟凤凰,固宇内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鸣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④赞词指出,刘因虽然连元世祖也不能招致,但其本意却并非要做遗世独立的高人,从刘因积极从事经史研究这个情况来看,他是有着周公、孔子那样崇高的文化理想的。刘因在世时弟子不多,在他死后,安熙以私淑弟子自居,安熙又传苏天爵,刘因之学得以接续。
安熙(1270—1311年),字敬仲,号默庵。幼承家学,后闻刘因之学而欲从之,未及造门而刘因已卒,遂从刘因门人乌冲(字叔备)“问其绪说”,录其遗书而还,潜心钻研,终身服膺,著作多佚,今存有《安默庵先生文集》。安熙治学,“一以(刘)因为宗”,像刘因一样,他在经学上也推崇朱子。他曾校订过刘因的《四书集义精要》,而有《四书精要考异》。当有人攻击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时,他起而捍卫:“朱夫子以为道之不明,由说经者不足以得圣贤之意。于是竭其精力,作为传注以著明之。至于一字未安、一词未备,必沉潜反复,以求至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莫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所以妙得古人本旨于数千载之上。其间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可谓极深研几,发其旨趣而无所疑矣。”①他还仿《四书集义精要》体例撰集了《诗传精要》,自述写作缘起说:“近因看《诗传》(即朱子《诗集传》——编者注),亦欲取《朱子文集》及语录之言,凡涉论《诗》,有与《集传》相发明者,依《精要》例写出,以便初学,亦似有益。”②此外,他还打算仿朱子《通鉴纲目》写一部《春秋》学著作,节取《左传》和秦汉以来诸家《春秋》说,“以类相从,各附本句”,“其大旨一以朱子为本,而达于张、程,以求圣人之意”,以使治《春秋》者“有以考传”,治《左传》者“亦知有经”。③苏天爵(1294—1352),字伯修,后人称滋溪先生。少从安熙游,后入国子学,累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文集为《滋溪文稿》。因年轻时跟安熙学习过,苏天爵终生以师礼待之,在安熙死后,为其作《行状》《墓志铭》,并编辑《默庵文集》,“拳拳于其师之遗书”④。因安熙之故,对刘因也很敬仰,盛赞后者“以高明之资,躬圣贤之学,道德风采,耸动四方”⑤。苏天爵长于史学,曾三居史职,预修武宗、文宗《实录》,又自撰《元朝名臣事略》,辑《元文类》,被称为“身任一代文献之寄”。元末灾异屡现,他根据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向元廷发出警告:“盖闻应天以实,不以文;动人以行,不以言。此自昔国家消弭天变,感格人心之至计也。……迩者,日月薄食,星文示变。河北、山东旱蝗为灾,辽阳、江淮黎民乏食。方此春夏之始,农人播植之时,灾异若此,岁事何望?夫天之变异,盖不虚生,将恐人事有乖和气。当是之时,国家正宜访求直言,指切时政。”①苏天爵还有较强的疑经精神,如他在读朱子《诗集传》和吕祖谦《读诗记》时就产生了对《诗经》的一些疑问,他对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的说法加以质疑:“由今观之,所正者独《豳》以下诗也,而《雅》《颂》何尝不得其所乎?若曰左氏后出,而作传者何独《豳》之下《雅》之上不得其次欤?”②他进而对孔子删《诗》的说法也表示怀疑:“当季札之聘鲁,请观周乐,于时夫子未删《诗》也,自《雅》《颂》之外,其十五国风尽歌之。
考之今三百篇及鲁人所存,无加损也。其谓夫子删《诗》者,果可信乎?”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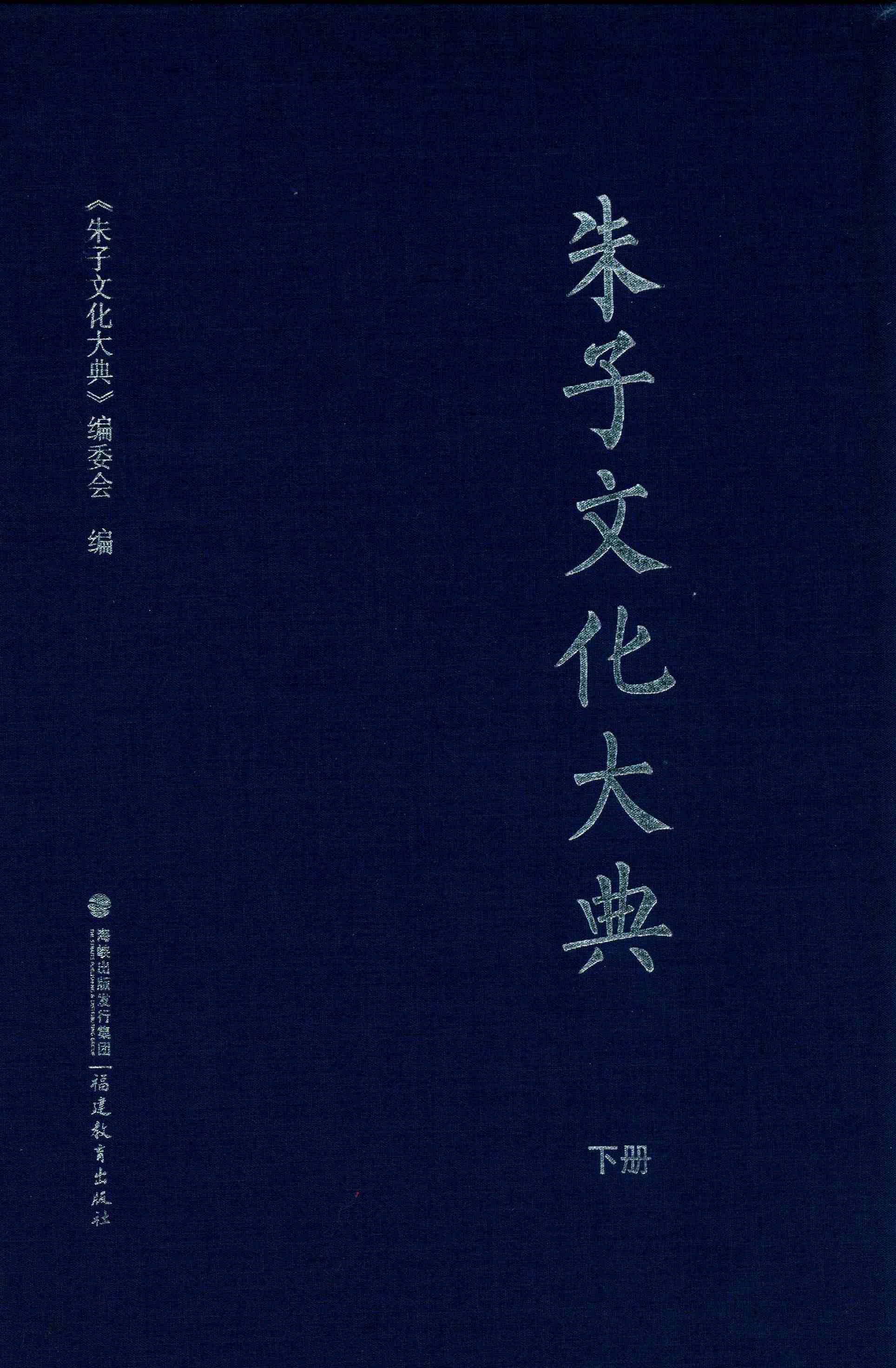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介绍朱子生平,包括家世、从学、讲学、论道、政绩等内容。中册阐述朱子文化源流,包括朱子理学形成的历史背景、朱子的理学思想、朱子的经学思想、朱子的教育思想等内容。下册着重介绍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