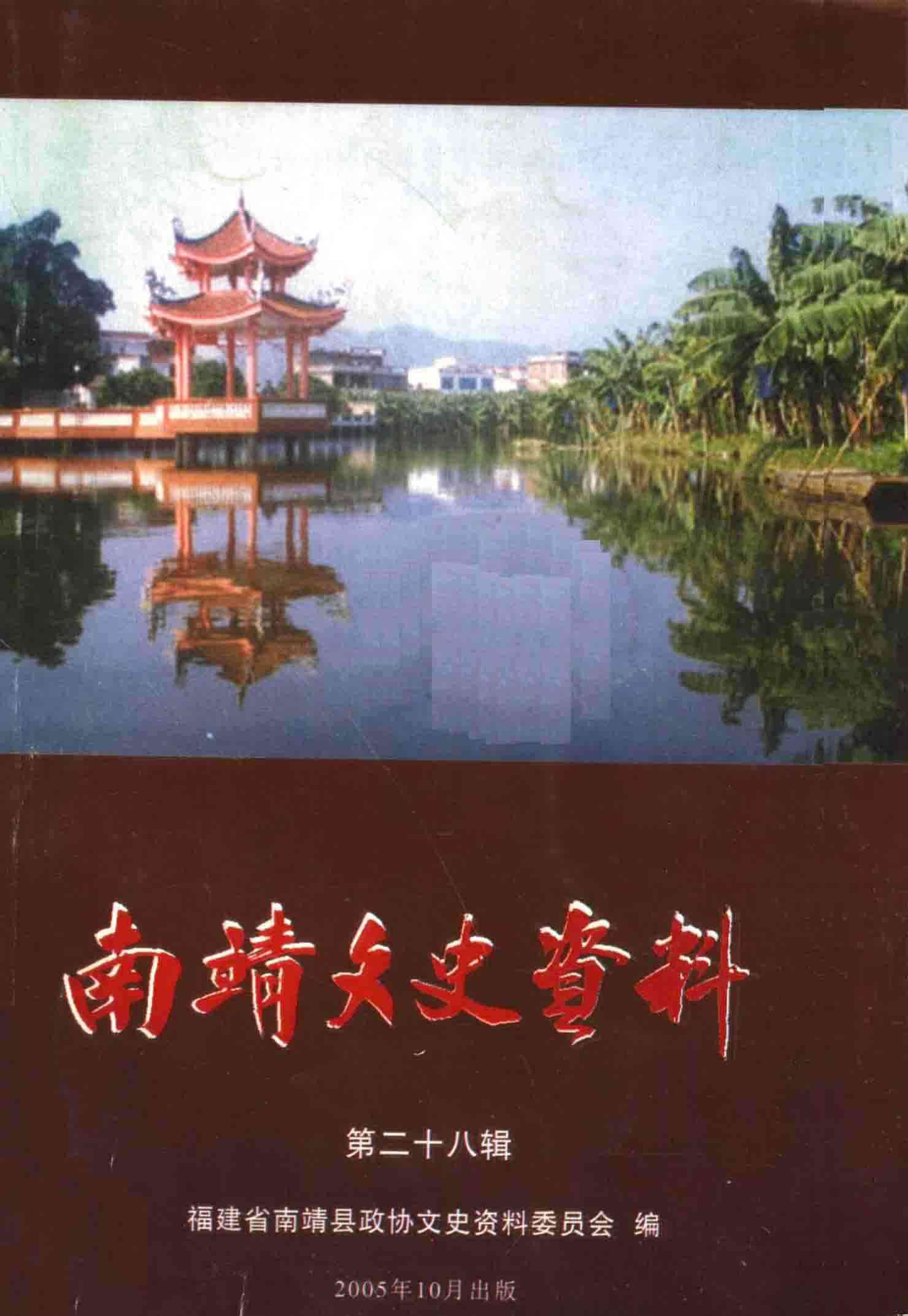人物春秋
| 内容出处: | 《南靖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2514 |
| 颗粒名称: | 人物春秋 |
| 分类号: | K250.657 |
| 页数: | 15 |
| 页码: | 177-191 |
| 摘要: | 本章人物春秋收录了垦荒修圳赖镏公和老红军李锦洲的相关内容。 |
| 关键词: | 南靖县 文史资料 人物春秋 |
内容
垦荒修圳赖镏公
——记清代水利专家郭锡镏
郭凯歌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暮秋的一天傍晚,十几条南靖县移民台湾的大帆船在茫茫海峡中飘荡。
5岁的郭锡镏,与父亲站在最后一条船的甲板上,身披万朵红霞,迎着浩浩海风,奶声奶气地朗诵起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回望渐去渐远的家乡,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问道:“天赐(郭锡镏的乳名),你还记得咱们的故乡和祖先吗?”
小锡镏昂起头,答道:“我们的故乡在漳州府南靖县涌口保庙兜社。我们是唐朝‘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阿爸,这个问题您考我多次了,怎么还问呀?您说,我们这次搬家要搬到什么地方?”
父亲抚摸着儿子的头,深情依依地说:“搬到台湾彰化县的半线,那里有我们早些年迁去的乡亲。”
“搬到那里做生意吗?”
“不,开荒。那里有大片大片的荒埔,我们要把那里变成大粮仓。”
船到彰化,乡亲们都到海边来迎接。
从此,小锡镏就在这里侨居,开始了少年的私塾学习生活。他的聪慧早熟,特别是伶俐的口才,不知博得多少人的赞誉,大家都把他看作神童。
岁月如梭,光阴流逝,郭锡镏长大了。他没有去异邦继续求学,而是与父亲一起披荆斩棘,发展垦殖业。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郭氏家族开拓了大片大片的田地,拥有了相当雄厚的资产。
随着大陆移民的不断涌入,郭氏田产的四邻都有人开发,继续发展的余地没有了。郭锡镏毅然决定,留下一部分人在彰化守业,其余的人向北迁移。
乾隆初年,郭锡镏带领郭氏家族迁移至大加纳(今属台北市)兴雅庄一带开发大荒埔。新一轮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又开始了。
当时台湾的农田灌溉大部分依靠池塘洼窟,这种简陋的灌溉设施根本无法满足日愈拓展的农田用水,若遇干旱,则只能仰天长叹盼云霓了。郭锡镏决心兴修水利,改变落后的农田灌溉现状。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郭锡镏变卖了彰.化的所有田产,得银二万余两,招募二百余名民工,用三年时间在新店溪支流的青潭溪上围堰截水,开凿了大坪林合兴寮石空顶的水圳。
工程建设期间,郭锡镏和工人农友们一起同吃同睡同劳动,一点儿也没有庄园主的架子。他们在深山密林里与毒蛇猛兽斗,与狂风暴雨斗,与严寒酷暑斗,还要与“番害”斗。
提起“番害”,许多人都会不寒而栗。当时的高山族番民,对大陆移民开发台湾很不理解,认为是霸占他们土地,便经常向移民们发动突然袭击,不少移民在他们的明枪暗箭下成了冤魂野鬼。郭锡镏在采取建造公馆、设立鼓亭和派人守望、击鼓报警的防范措施的同时,还采取番汉联婚,化仇为亲的办法,鼓励移民们与高山族人喜结良缘。他自己则带头和番,娶当地姑娘为妻。
“番害”平息后,为彻底根治干旱,郭锡镏于石空顶水利工程竣工的第二年,又决定直接从新店溪开辟渠道,引水汇合石空顶圳水。
引水工程所经过的路线绝大部分是荒谷深涧,中间一段还要跨越一条名叫“景美溪”的大河。郭锡镏他们以修筑渡槽连接两岸水渠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工程难点。没想到当地老百姓却嫌摆渡过河麻烦而把渡槽当作桥梁使用,结果不到一年,渡槽就坍塌了。郭锡镏只好改从暗渠引渡,将水缸去底,一一衔接后埋进河下。
暗渠引渡的成功,终于使这条长达数十里,前后修筑21年的金石川圳全线贯通,灌溉面积扩大到1.5万亩,实现了旱涝保收,大大降低了农业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为大陆移民开垦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3年),台北地区暴雨成灾,金石川水圳多处被山洪冲毁。面对洪魔遗下的水毁工程,郭锡镏欲哭无泪。此时的他,为兴修水利已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和钱财。他终于积劳成疾,于当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在台北逝世,享年60岁,安葬在锡口山北的下塔悠(今台北市松山区),私谥为“宽和先生”。
郭锡镏逝世后,他的儿子郭克汾继承父志,募捐钱银,组织群众修复水毁工程,并雇员巡检看护,年年维修,使得这一条水圳能永续使用。
后人为纪念郭锡镏的治水业绩,把金石川水圳命名为“镏公圳”。如今,镏公圳的渠水还在灌溉着台北的万亩良田,还在悄然诉说着郭锡镏垦荒修圳的不朽功德。
老红军李锦洲
李鑫
这是一部与“命运”相抗衡的人生交响曲,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李锦洲历经“农民——红军——新四军——‘叛徒’——农民——老红军”,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报名当红军
1913年9月,李锦洲出生在南靖县溪边村的车前坂自然村。9岁那年,辛勤劳作了一生的父亲去逝了,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两年后,他慈祥的母亲也离开了人间。从此,他就成了孤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被卖到山城镇。过了两年,他的伯父才把他赎回,带回故乡坂寮坑口李自然村,以造纸为生。
李锦洲的家乡,四周都是山。由于交通闭塞,外界的消息很难及时传到这里。第一次红军来到版寮的时候,因为乡亲们对红军游击队不了解,认为自古以来“官匪是一家”,因此,一听到红军要进入版寮的消息,都纷纷跑进崇山密林中去躲避“风头”。但红军的模范行为很快就消除了乡亲们的疑虑,大家又从山上纷纷回家。
1934年4月8日,这是李锦洲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红军到他家里来,动员他去参加红军游击队,那年,他21岁了,长得身强力壮,尽管脸色蜡黄,但上山砍柴已挑得动180多斤了,他非常想去,但伯父不肯,说他是个孤儿,若有个三长两短,怎对得起他那死去的爹娘呢?他很焦急,便苦苦恳求伯父:
“伯父,让我去参加吧,红军游击队里头都是好人,再说,一直呆在家里也没什么出路。”
他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伯父还是不答应,后来,见到其他穷人的孩子也参加了,才勉强答应。伯父同意了,他高兴得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报名。村子里的李长绵、李天妹和邻村的刘传芳、刘永清等很多有志的穷苦青年都应征入伍了。红军给每个参军的家里送了3块银元,聊补安家费用。因为当时红军游击队很穷,不可能拿更多的钱。
参军后,他被分配到刘永生同志率领的金丰游击队(四支队三大队)。从永定的乌叶出发,到达金丰大山后,刘永生同志接见他们这些新兵。刘永生说:“同志们,大家都是有志气的年轻人,我代表红军游击队,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穷人的队伍。我们都是受苦人,为了今后能过上好日子,就得拿起枪杆子,跟国民党反动派干……”讲到最后,刘永生同志还幽默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好好干吧!等到革命成功后,我帮大家都娶个好老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刘永生同志讲完话后,就叫战士们发给新兵每人一套军装和一支枪,但子弹非常少,老战士们就教他们用黄麻杆折成一小节一小节,把小竹子剁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分别装进子弹袋,远远望去,谁也认不清是真子弹还是假子弹,但遇上打仗,就得以拼刺刀为主了,假子弹只能吓唬敌人。
因为李锦洲在家时曾跟人家学过拳术,又长得虎彪彪的,刘永生同志就把他分配到特务连去。
第一次战斗
李锦洲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攻打下版寮。当时下版寮有敌民团200多人,200多支长、短枪,土楼的围墙很厚,并都设有枪眼。红军围了五、六天,敌人都不开门投降,还凭借坚硬的“乌龟壳”向红军疯狂扫射。
为了迅速结束战斗,红军采取了强攻的办法,利用晚上,用自制的长竹梯靠近大土楼的后窗口。当红军战士爬上竹梯,接近窗口时,敌人突然用滚烫的米糠浆,倒在战士们的头上。大家都知道,米糠浆比开水还厉害,谁被烫着也受不了。许多战士就这样被米糠浆烫伤而掉下来的。
敌人仗着子弹多,盲目地向红军扫射,白天很难接近大土楼。战士们就想出一个好办法,向老乡们借来几张八仙桌,桌上铺着三、四层厚厚的湿棉被,人躲在八仙桌下,背驮着这“新式武器”,冒着枪林弹雨前进。但由于楼高墙厚,一时也难于攻破。
后来,大家又想了一条妙计,把地道挖到大土楼底下,用土硝300多斤和炸药装进棺材,然后沿着地道把棺材抬到土楼底下。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轰隆”一声闷响,大土楼被炸开了一角。战士们在一片喊杀声中冲进了大土楼。
这次战斗,红军缴获了200多支枪,杀了5个民愤极大的民团头目。
当时,因为李锦州他们是新兵,打仗没有经验,领导上就把他们新兵的一个班安排在离土楼约半里路的地方,准备伏击逃出楼的敌人。他们埋伏了5天,连饭都由炊事员们天天送来。大土楼攻破后,有两个狡猾的民团丁趁乱仓惶出逃,没想到就当了他们新兵的俘虏。
四面楚歌声
1935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李锦洲他们100多人攻打南靖书洋长教的一个大圆楼。
当红军队伍包围了这座大圆楼后,战士们就一齐大声喊话:“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还组织“拉拉队”唱歌:
白军弟兄们,
快快来当红军。
国民党军阀,
真个不是人,
压迫你们弟兄们,
你们当了兵,
东扣西扣扣得干干净。
你们官长好享福,
吃酒又吃肉,
可怜你们士兵们,
天天吃稀粥,
你们快快来当红军,
我们官长士兵都平等。
敌人在四面楚歌声中,早已动摇了军心。那些士兵们,听到歌声,想起了平日里受到国民党长官的欺侮压迫,很多人明白了,替反动派卖命是没有好下场的,于是,有的借故离开岗哨,有的朝天盲目地开枪,有的借酒浇愁。总之,早已无心恋战。战斗很快结束了,红军打死了几个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的顽固分子。敌人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早已脚底抹油——溜了。
红军把俘虏教育后全部释放。接着,他们就把大土楼里的大米、银元、床单、棉被、蚊帐等东西挑走,把毛猪扛走,把水牛牵走。李锦洲负责牵一头水牛,趁着黑夜,迅速地离开了长教。
在这次战斗中,支队长刘永生肩膀上挂了花,卫生员给包扎完伤口后,他又带领战士们撤出了长教。
这时,敌人大概是听到了长教方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立即派兵来增援,但红军早已隐进了茫茫林海之中,敌人只好“望山兴叹”,鞭长莫及了。
突围金丰山
1935年春天,李锦洲他们驻在金丰大山,有一次,侦察员老李因麻痹大意,没有认真侦察地形,结果被敌人偷偷地包围了。那天早晨,雾很大,漫山遍野,白茫茫的一片,敌人到了面前才发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再也不能犹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紧急突围开始了。但因敌众我寡,牺牲了很多同志,刘永生同志的爱人尤大嫂(当时是搞宣传的)也被敌人捉去了,敌人以她为人质,妄图迫使刘永生投降。但敌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真正的革命战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敌人捞不到半根稻草,恼羞成怒,凶残地割下了尤大嫂的两个乳头,用刺刀在她脸上划了许多横七竖八的道道。直到1936年底国共合作时,尤大嫂才被释放,脸上横竖都是伤疤。大家知道后,都伤心地哭了。
这次突围,红军损失很大,12入中,只有5个人突围出来,那个麻痹大意的侦察员老李也牺牲了。
为烈士送葬
1937年3月,李锦洲的战友李细登在永定县黄泥塘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获悉李细登是金丰游击队的连长时,便把他杀害了。敌人残忍地割下烈士的头颅,挂在永定县城示众,还扬言说待示众3天后要将烈士的遗体剁成4段,来个“五马分尸”。
消息传到金丰游击队,李锦洲和战友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请示刘永生率部袭击县城,夺回战友的遗体。
刘永生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仔细分析了敌情后毅然决定出兵。于是,在李细登头颅示众的第一天夜里,刘永生率领的金丰游击队,就像猛虎下山般地攻破了永定县城,活捉了伪县长。
伪县长吓破了胆,战战兢兢地被李锦州押到刘永生面前跪下。
刘永生喝问道:“李细登是你下令砍头的吗?”
伪县长点点头,结结巴巴地说:“是,是,我有罪,我有罪!”
“还要五马分尸吗?”刘永生拍了一下桌子。
“不敢,不敢!”伪县长磕头如捣蒜。
“那好,你回去后马上下令,将我红军游击队李连长的头颅解下,与遗体缝合完整,用上好棺材入殓,尔后隆重厚葬,否则,用你的脑袋来换!”刘永生板着脸,一字一顿地说。
“是,是,是!一切照办!一切照办!”伪县长抖腿如筛糠。
第二天上午,伪县长一时找不到上好棺材,只好叫人将为他父亲准备的寿棺扛来,给缝好遗体的李细登人殓。随后,伪县长亲率县衙里的文武官员及保安队100余人,与游击队指战员们一起,披麻带孝,为李细登烈士送葬上山。
这件事,轰动了永和靖边区。老百姓们都说:“李细登死得最惨,埋得最光荣。”
沙场肉搏战
1938年春,李锦州随整编后的红九团北上抗日,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三营三连第二班班长。不久,上级领导调他到军部教导队学习社会发展史、军事知识等。半年毕业后,他就到七连当指导员,两个月后又调到军部任特务连连长。
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勇敢机智,深受好评。有一次,日本鬼子包围了李锦州他们驻守的山头。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他只好带领战士们在阵地上与日寇展开了肉搏战。
正当他与一个日本鬼子拼刺刀的时候,没提防身后刺来一刀,刺中胸部,淋漓的鲜血很快就把棉衣染红了。他刺死前面的那个日本鬼子后,转身一看,捅他刺刀的原来是一个矮个子的日本鬼子。他忍着伤痛,怒目喷火,大吼一声,猛然扑向敌兵,双手掐住敌兵的脖子在草地上打滚。他牛高马大,尽管伤口流血,但还是把那个日本鬼子压倒在地,掐脖的双手越掐越紧,终于把那个日本鬼子活活掐死了。
李锦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顾不上擦干脸上的血汗,就连忙撕下绑带,包扎起自己的伤口,幸亏有棉衣挡着,刺刀进肉不深,血很快就止住了。
奇怪,阵地上怎么这么静呀?刚才的喊杀声、铿锵声哪里去了?他放眼四望,但见阵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战友的遗体和敌人的尸体。部队突围出去了,整个战场,死一般的静寂。
突然,山脚下隐隐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呜哩哇啦”的说话声。糟啦!敌人正在打扫战场,怎么办呢?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难道要成为敌人的俘虏吗?不,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入魔掌!革命还未成功,日寇还未赶出国门,怎么能轻易死去呢?李锦洲想到这里,顿时来了精神,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于是,他迅速地把20多位战友的遗体拖到一个战壕边,杂七杂八地叠放在一起,然后手抹战友的鲜血涂在脸上,在遗体中躲藏着,用沙包袋遮住。警惕的双眼时刻注视着战场上的动静。
这时,一大群日本鬼子开始打扫战场,搜索新四军伤员了。他们的刺刀在战友的遗体堆里乱戮乱刺,突然刺伤李锦洲的手臂,鲜血立即流出。他强忍伤痛,闭上眼睛一动也不动,待敌人离去后才从战友的遗体堆里爬出来,等到太阳下山才摸黑返回部队。
“皖南事变”中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9000余人奉命北移,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血战了七天七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
当时,李锦洲任第三团代理侦察参谋,带领第三团第三营的全体同志突围。在这次突围中,他头部负伤,加上又饥又渴,四肢无力,连路都走不动了,只能靠屁股磨蹭着挪动。
在敌人重兵压到军部时,他想:“革命到底”(牺牲的意思)算了,免得半死不活的,拖累其他同志,影响同志们的突围。于是,他掏出手枪……。
叶挺军长发现了,一下子夺过他的手枪,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锦洲,不能死!我们要活着出去!人民是拥护我们的。”
一路上照顾他的小战士也哭了起来:“李参谋,你不能死!我就是背,也要背着你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啊!”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友谊呢?
这时候,叶挺军长已经觉察到,要想突出敌兵重围,是没有多大希望了,就对李锦洲说:“文件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赶快全部烧掉。”他点了点头,叫小战士把文件全部烧掉了。
敌人又涌上来了。他们把枪支的零件也卸掉,扔进荆刺丛中……。
李锦洲与叶挺军长、王若飞特派员他们一道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死里逃生后
在上饶集中营里,李锦洲整整度过了1年零4个月的铁窗生活。在敌人把他们押送到福建的途中——江西铅山的石堂时,天已黑了,他和瑞金籍的二连长袁正金,趁押送的敌兵不注意,解开绑在他们身上的麻绳,突然跳到路边的河里。敌人发觉后,只打冷枪,不敢来追捕,大概生怕逃掉更多的人吧?
死里逃生,慌不择路,到处都是黑漆漆的一片。天亮后,李锦洲昏倒在山坡上,被当地一位大嫂救回家。
从此,李锦洲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到过福建的武夷山、崇安一带,寻找部队未果,又想到安徽去找,结果因日本重兵驻扎,未能去成,只好在上饶一带谋生。
敌人到处在搜捕逃散的新四军。李锦洲眼看就要混不下去了,便回来与那位大嫂商量对策。大嫂说:“我是个寡妇,你如果不嫌我丑,我就招你为夫。你若入赘我家,就有了合法的身份。等有机会,你再找部队抗日去!先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李锦洲想起她用祖传的中草药为自己疗伤治病、半夜熬鸡汤为他滋补身子……不禁热泪盈眶,为她的善良和深明大义而感动,就点头答应了。从此,他就在上饶的应家乡安家落户了。
1949年,上级委任李锦洲当乡队长,负责搞地方武装工作。在剿匪反霸时,他被土匪打断了两支胸骨,走路都直不起腰,不能继续工作了。后经医生的精心治疗,到了1956年才渐渐能直起腰来走路。
因李锦洲是从敌人的魔爪下逃出来的,组织上对他“老红军”问题迟疑不决。就这样,他开始了漫长的农村生活,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农”。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无官,二无钱的李锦洲突然被红卫兵造反派“确认”为“叛徒”,残遭批斗迫害,“文革”后他虽然被撤消了“叛徒”罪名,但直到1994年才给他恢复老红军的名誉。
1998年农历三月初三,李锦洲因病在上饶县应家乡去世,亨年85岁。
——记清代水利专家郭锡镏
郭凯歌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暮秋的一天傍晚,十几条南靖县移民台湾的大帆船在茫茫海峡中飘荡。
5岁的郭锡镏,与父亲站在最后一条船的甲板上,身披万朵红霞,迎着浩浩海风,奶声奶气地朗诵起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回望渐去渐远的家乡,父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问道:“天赐(郭锡镏的乳名),你还记得咱们的故乡和祖先吗?”
小锡镏昂起头,答道:“我们的故乡在漳州府南靖县涌口保庙兜社。我们是唐朝‘汾阳王’郭子仪的后代。阿爸,这个问题您考我多次了,怎么还问呀?您说,我们这次搬家要搬到什么地方?”
父亲抚摸着儿子的头,深情依依地说:“搬到台湾彰化县的半线,那里有我们早些年迁去的乡亲。”
“搬到那里做生意吗?”
“不,开荒。那里有大片大片的荒埔,我们要把那里变成大粮仓。”
船到彰化,乡亲们都到海边来迎接。
从此,小锡镏就在这里侨居,开始了少年的私塾学习生活。他的聪慧早熟,特别是伶俐的口才,不知博得多少人的赞誉,大家都把他看作神童。
岁月如梭,光阴流逝,郭锡镏长大了。他没有去异邦继续求学,而是与父亲一起披荆斩棘,发展垦殖业。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奋斗,郭氏家族开拓了大片大片的田地,拥有了相当雄厚的资产。
随着大陆移民的不断涌入,郭氏田产的四邻都有人开发,继续发展的余地没有了。郭锡镏毅然决定,留下一部分人在彰化守业,其余的人向北迁移。
乾隆初年,郭锡镏带领郭氏家族迁移至大加纳(今属台北市)兴雅庄一带开发大荒埔。新一轮筚路蓝缕的艰苦创业又开始了。
当时台湾的农田灌溉大部分依靠池塘洼窟,这种简陋的灌溉设施根本无法满足日愈拓展的农田用水,若遇干旱,则只能仰天长叹盼云霓了。郭锡镏决心兴修水利,改变落后的农田灌溉现状。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郭锡镏变卖了彰.化的所有田产,得银二万余两,招募二百余名民工,用三年时间在新店溪支流的青潭溪上围堰截水,开凿了大坪林合兴寮石空顶的水圳。
工程建设期间,郭锡镏和工人农友们一起同吃同睡同劳动,一点儿也没有庄园主的架子。他们在深山密林里与毒蛇猛兽斗,与狂风暴雨斗,与严寒酷暑斗,还要与“番害”斗。
提起“番害”,许多人都会不寒而栗。当时的高山族番民,对大陆移民开发台湾很不理解,认为是霸占他们土地,便经常向移民们发动突然袭击,不少移民在他们的明枪暗箭下成了冤魂野鬼。郭锡镏在采取建造公馆、设立鼓亭和派人守望、击鼓报警的防范措施的同时,还采取番汉联婚,化仇为亲的办法,鼓励移民们与高山族人喜结良缘。他自己则带头和番,娶当地姑娘为妻。
“番害”平息后,为彻底根治干旱,郭锡镏于石空顶水利工程竣工的第二年,又决定直接从新店溪开辟渠道,引水汇合石空顶圳水。
引水工程所经过的路线绝大部分是荒谷深涧,中间一段还要跨越一条名叫“景美溪”的大河。郭锡镏他们以修筑渡槽连接两岸水渠的方式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工程难点。没想到当地老百姓却嫌摆渡过河麻烦而把渡槽当作桥梁使用,结果不到一年,渡槽就坍塌了。郭锡镏只好改从暗渠引渡,将水缸去底,一一衔接后埋进河下。
暗渠引渡的成功,终于使这条长达数十里,前后修筑21年的金石川圳全线贯通,灌溉面积扩大到1.5万亩,实现了旱涝保收,大大降低了农业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为大陆移民开垦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
乾隆三十年(公元1763年),台北地区暴雨成灾,金石川水圳多处被山洪冲毁。面对洪魔遗下的水毁工程,郭锡镏欲哭无泪。此时的他,为兴修水利已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和钱财。他终于积劳成疾,于当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在台北逝世,享年60岁,安葬在锡口山北的下塔悠(今台北市松山区),私谥为“宽和先生”。
郭锡镏逝世后,他的儿子郭克汾继承父志,募捐钱银,组织群众修复水毁工程,并雇员巡检看护,年年维修,使得这一条水圳能永续使用。
后人为纪念郭锡镏的治水业绩,把金石川水圳命名为“镏公圳”。如今,镏公圳的渠水还在灌溉着台北的万亩良田,还在悄然诉说着郭锡镏垦荒修圳的不朽功德。
老红军李锦洲
李鑫
这是一部与“命运”相抗衡的人生交响曲,这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李锦洲历经“农民——红军——新四军——‘叛徒’——农民——老红军”,命运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报名当红军
1913年9月,李锦洲出生在南靖县溪边村的车前坂自然村。9岁那年,辛勤劳作了一生的父亲去逝了,家里的生活更加困难。两年后,他慈祥的母亲也离开了人间。从此,他就成了孤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被卖到山城镇。过了两年,他的伯父才把他赎回,带回故乡坂寮坑口李自然村,以造纸为生。
李锦洲的家乡,四周都是山。由于交通闭塞,外界的消息很难及时传到这里。第一次红军来到版寮的时候,因为乡亲们对红军游击队不了解,认为自古以来“官匪是一家”,因此,一听到红军要进入版寮的消息,都纷纷跑进崇山密林中去躲避“风头”。但红军的模范行为很快就消除了乡亲们的疑虑,大家又从山上纷纷回家。
1934年4月8日,这是李锦洲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红军到他家里来,动员他去参加红军游击队,那年,他21岁了,长得身强力壮,尽管脸色蜡黄,但上山砍柴已挑得动180多斤了,他非常想去,但伯父不肯,说他是个孤儿,若有个三长两短,怎对得起他那死去的爹娘呢?他很焦急,便苦苦恳求伯父:
“伯父,让我去参加吧,红军游击队里头都是好人,再说,一直呆在家里也没什么出路。”
他好说歹说,磨破了嘴皮,伯父还是不答应,后来,见到其他穷人的孩子也参加了,才勉强答应。伯父同意了,他高兴得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一早,他就去报名。村子里的李长绵、李天妹和邻村的刘传芳、刘永清等很多有志的穷苦青年都应征入伍了。红军给每个参军的家里送了3块银元,聊补安家费用。因为当时红军游击队很穷,不可能拿更多的钱。
参军后,他被分配到刘永生同志率领的金丰游击队(四支队三大队)。从永定的乌叶出发,到达金丰大山后,刘永生同志接见他们这些新兵。刘永生说:“同志们,大家都是有志气的年轻人,我代表红军游击队,欢迎你们参加我们穷人的队伍。我们都是受苦人,为了今后能过上好日子,就得拿起枪杆子,跟国民党反动派干……”讲到最后,刘永生同志还幽默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好好干吧!等到革命成功后,我帮大家都娶个好老婆……”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刘永生同志讲完话后,就叫战士们发给新兵每人一套军装和一支枪,但子弹非常少,老战士们就教他们用黄麻杆折成一小节一小节,把小竹子剁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分别装进子弹袋,远远望去,谁也认不清是真子弹还是假子弹,但遇上打仗,就得以拼刺刀为主了,假子弹只能吓唬敌人。
因为李锦洲在家时曾跟人家学过拳术,又长得虎彪彪的,刘永生同志就把他分配到特务连去。
第一次战斗
李锦洲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攻打下版寮。当时下版寮有敌民团200多人,200多支长、短枪,土楼的围墙很厚,并都设有枪眼。红军围了五、六天,敌人都不开门投降,还凭借坚硬的“乌龟壳”向红军疯狂扫射。
为了迅速结束战斗,红军采取了强攻的办法,利用晚上,用自制的长竹梯靠近大土楼的后窗口。当红军战士爬上竹梯,接近窗口时,敌人突然用滚烫的米糠浆,倒在战士们的头上。大家都知道,米糠浆比开水还厉害,谁被烫着也受不了。许多战士就这样被米糠浆烫伤而掉下来的。
敌人仗着子弹多,盲目地向红军扫射,白天很难接近大土楼。战士们就想出一个好办法,向老乡们借来几张八仙桌,桌上铺着三、四层厚厚的湿棉被,人躲在八仙桌下,背驮着这“新式武器”,冒着枪林弹雨前进。但由于楼高墙厚,一时也难于攻破。
后来,大家又想了一条妙计,把地道挖到大土楼底下,用土硝300多斤和炸药装进棺材,然后沿着地道把棺材抬到土楼底下。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轰隆”一声闷响,大土楼被炸开了一角。战士们在一片喊杀声中冲进了大土楼。
这次战斗,红军缴获了200多支枪,杀了5个民愤极大的民团头目。
当时,因为李锦州他们是新兵,打仗没有经验,领导上就把他们新兵的一个班安排在离土楼约半里路的地方,准备伏击逃出楼的敌人。他们埋伏了5天,连饭都由炊事员们天天送来。大土楼攻破后,有两个狡猾的民团丁趁乱仓惶出逃,没想到就当了他们新兵的俘虏。
四面楚歌声
1935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李锦洲他们100多人攻打南靖书洋长教的一个大圆楼。
当红军队伍包围了这座大圆楼后,战士们就一齐大声喊话:“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快投降吧!”还组织“拉拉队”唱歌:
白军弟兄们,
快快来当红军。
国民党军阀,
真个不是人,
压迫你们弟兄们,
你们当了兵,
东扣西扣扣得干干净。
你们官长好享福,
吃酒又吃肉,
可怜你们士兵们,
天天吃稀粥,
你们快快来当红军,
我们官长士兵都平等。
敌人在四面楚歌声中,早已动摇了军心。那些士兵们,听到歌声,想起了平日里受到国民党长官的欺侮压迫,很多人明白了,替反动派卖命是没有好下场的,于是,有的借故离开岗哨,有的朝天盲目地开枪,有的借酒浇愁。总之,早已无心恋战。战斗很快结束了,红军打死了几个死心塌地为蒋家王朝卖命的顽固分子。敌人有的当了俘虏,有的早已脚底抹油——溜了。
红军把俘虏教育后全部释放。接着,他们就把大土楼里的大米、银元、床单、棉被、蚊帐等东西挑走,把毛猪扛走,把水牛牵走。李锦洲负责牵一头水牛,趁着黑夜,迅速地离开了长教。
在这次战斗中,支队长刘永生肩膀上挂了花,卫生员给包扎完伤口后,他又带领战士们撤出了长教。
这时,敌人大概是听到了长教方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立即派兵来增援,但红军早已隐进了茫茫林海之中,敌人只好“望山兴叹”,鞭长莫及了。
突围金丰山
1935年春天,李锦洲他们驻在金丰大山,有一次,侦察员老李因麻痹大意,没有认真侦察地形,结果被敌人偷偷地包围了。那天早晨,雾很大,漫山遍野,白茫茫的一片,敌人到了面前才发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再也不能犹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紧急突围开始了。但因敌众我寡,牺牲了很多同志,刘永生同志的爱人尤大嫂(当时是搞宣传的)也被敌人捉去了,敌人以她为人质,妄图迫使刘永生投降。但敌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真正的革命战士,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敌人捞不到半根稻草,恼羞成怒,凶残地割下了尤大嫂的两个乳头,用刺刀在她脸上划了许多横七竖八的道道。直到1936年底国共合作时,尤大嫂才被释放,脸上横竖都是伤疤。大家知道后,都伤心地哭了。
这次突围,红军损失很大,12入中,只有5个人突围出来,那个麻痹大意的侦察员老李也牺牲了。
为烈士送葬
1937年3月,李锦洲的战友李细登在永定县黄泥塘的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获悉李细登是金丰游击队的连长时,便把他杀害了。敌人残忍地割下烈士的头颅,挂在永定县城示众,还扬言说待示众3天后要将烈士的遗体剁成4段,来个“五马分尸”。
消息传到金丰游击队,李锦洲和战友们个个义愤填膺,纷纷请示刘永生率部袭击县城,夺回战友的遗体。
刘永生根据侦察员的报告,仔细分析了敌情后毅然决定出兵。于是,在李细登头颅示众的第一天夜里,刘永生率领的金丰游击队,就像猛虎下山般地攻破了永定县城,活捉了伪县长。
伪县长吓破了胆,战战兢兢地被李锦州押到刘永生面前跪下。
刘永生喝问道:“李细登是你下令砍头的吗?”
伪县长点点头,结结巴巴地说:“是,是,我有罪,我有罪!”
“还要五马分尸吗?”刘永生拍了一下桌子。
“不敢,不敢!”伪县长磕头如捣蒜。
“那好,你回去后马上下令,将我红军游击队李连长的头颅解下,与遗体缝合完整,用上好棺材入殓,尔后隆重厚葬,否则,用你的脑袋来换!”刘永生板着脸,一字一顿地说。
“是,是,是!一切照办!一切照办!”伪县长抖腿如筛糠。
第二天上午,伪县长一时找不到上好棺材,只好叫人将为他父亲准备的寿棺扛来,给缝好遗体的李细登人殓。随后,伪县长亲率县衙里的文武官员及保安队100余人,与游击队指战员们一起,披麻带孝,为李细登烈士送葬上山。
这件事,轰动了永和靖边区。老百姓们都说:“李细登死得最惨,埋得最光荣。”
沙场肉搏战
1938年春,李锦州随整编后的红九团北上抗日,任新四军二支队三团三营三连第二班班长。不久,上级领导调他到军部教导队学习社会发展史、军事知识等。半年毕业后,他就到七连当指导员,两个月后又调到军部任特务连连长。
在战场上,他身先士卒,勇敢机智,深受好评。有一次,日本鬼子包围了李锦州他们驻守的山头。子弹打光了,手榴弹扔完了,他只好带领战士们在阵地上与日寇展开了肉搏战。
正当他与一个日本鬼子拼刺刀的时候,没提防身后刺来一刀,刺中胸部,淋漓的鲜血很快就把棉衣染红了。他刺死前面的那个日本鬼子后,转身一看,捅他刺刀的原来是一个矮个子的日本鬼子。他忍着伤痛,怒目喷火,大吼一声,猛然扑向敌兵,双手掐住敌兵的脖子在草地上打滚。他牛高马大,尽管伤口流血,但还是把那个日本鬼子压倒在地,掐脖的双手越掐越紧,终于把那个日本鬼子活活掐死了。
李锦洲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顾不上擦干脸上的血汗,就连忙撕下绑带,包扎起自己的伤口,幸亏有棉衣挡着,刺刀进肉不深,血很快就止住了。
奇怪,阵地上怎么这么静呀?刚才的喊杀声、铿锵声哪里去了?他放眼四望,但见阵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战友的遗体和敌人的尸体。部队突围出去了,整个战场,死一般的静寂。
突然,山脚下隐隐传来杂乱的脚步声和“呜哩哇啦”的说话声。糟啦!敌人正在打扫战场,怎么办呢?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之下,难道要成为敌人的俘虏吗?不,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入魔掌!革命还未成功,日寇还未赶出国门,怎么能轻易死去呢?李锦洲想到这里,顿时来了精神,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心。于是,他迅速地把20多位战友的遗体拖到一个战壕边,杂七杂八地叠放在一起,然后手抹战友的鲜血涂在脸上,在遗体中躲藏着,用沙包袋遮住。警惕的双眼时刻注视着战场上的动静。
这时,一大群日本鬼子开始打扫战场,搜索新四军伤员了。他们的刺刀在战友的遗体堆里乱戮乱刺,突然刺伤李锦洲的手臂,鲜血立即流出。他强忍伤痛,闭上眼睛一动也不动,待敌人离去后才从战友的遗体堆里爬出来,等到太阳下山才摸黑返回部队。
“皖南事变”中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9000余人奉命北移,6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还击,血战了七天七夜,终因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皖南事变”。
当时,李锦洲任第三团代理侦察参谋,带领第三团第三营的全体同志突围。在这次突围中,他头部负伤,加上又饥又渴,四肢无力,连路都走不动了,只能靠屁股磨蹭着挪动。
在敌人重兵压到军部时,他想:“革命到底”(牺牲的意思)算了,免得半死不活的,拖累其他同志,影响同志们的突围。于是,他掏出手枪……。
叶挺军长发现了,一下子夺过他的手枪,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锦洲,不能死!我们要活着出去!人民是拥护我们的。”
一路上照顾他的小战士也哭了起来:“李参谋,你不能死!我就是背,也要背着你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啊!”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友谊呢?
这时候,叶挺军长已经觉察到,要想突出敌兵重围,是没有多大希望了,就对李锦洲说:“文件不能落到敌人手里,赶快全部烧掉。”他点了点头,叫小战士把文件全部烧掉了。
敌人又涌上来了。他们把枪支的零件也卸掉,扔进荆刺丛中……。
李锦洲与叶挺军长、王若飞特派员他们一道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死里逃生后
在上饶集中营里,李锦洲整整度过了1年零4个月的铁窗生活。在敌人把他们押送到福建的途中——江西铅山的石堂时,天已黑了,他和瑞金籍的二连长袁正金,趁押送的敌兵不注意,解开绑在他们身上的麻绳,突然跳到路边的河里。敌人发觉后,只打冷枪,不敢来追捕,大概生怕逃掉更多的人吧?
死里逃生,慌不择路,到处都是黑漆漆的一片。天亮后,李锦洲昏倒在山坡上,被当地一位大嫂救回家。
从此,李锦洲与组织上失去了联系。后来,他到过福建的武夷山、崇安一带,寻找部队未果,又想到安徽去找,结果因日本重兵驻扎,未能去成,只好在上饶一带谋生。
敌人到处在搜捕逃散的新四军。李锦洲眼看就要混不下去了,便回来与那位大嫂商量对策。大嫂说:“我是个寡妇,你如果不嫌我丑,我就招你为夫。你若入赘我家,就有了合法的身份。等有机会,你再找部队抗日去!先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李锦洲想起她用祖传的中草药为自己疗伤治病、半夜熬鸡汤为他滋补身子……不禁热泪盈眶,为她的善良和深明大义而感动,就点头答应了。从此,他就在上饶的应家乡安家落户了。
1949年,上级委任李锦洲当乡队长,负责搞地方武装工作。在剿匪反霸时,他被土匪打断了两支胸骨,走路都直不起腰,不能继续工作了。后经医生的精心治疗,到了1956年才渐渐能直起腰来走路。
因李锦洲是从敌人的魔爪下逃出来的,组织上对他“老红军”问题迟疑不决。就这样,他开始了漫长的农村生活,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农”。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无官,二无钱的李锦洲突然被红卫兵造反派“确认”为“叛徒”,残遭批斗迫害,“文革”后他虽然被撤消了“叛徒”罪名,但直到1994年才给他恢复老红军的名誉。
1998年农历三月初三,李锦洲因病在上饶县应家乡去世,亨年85岁。
知识出处